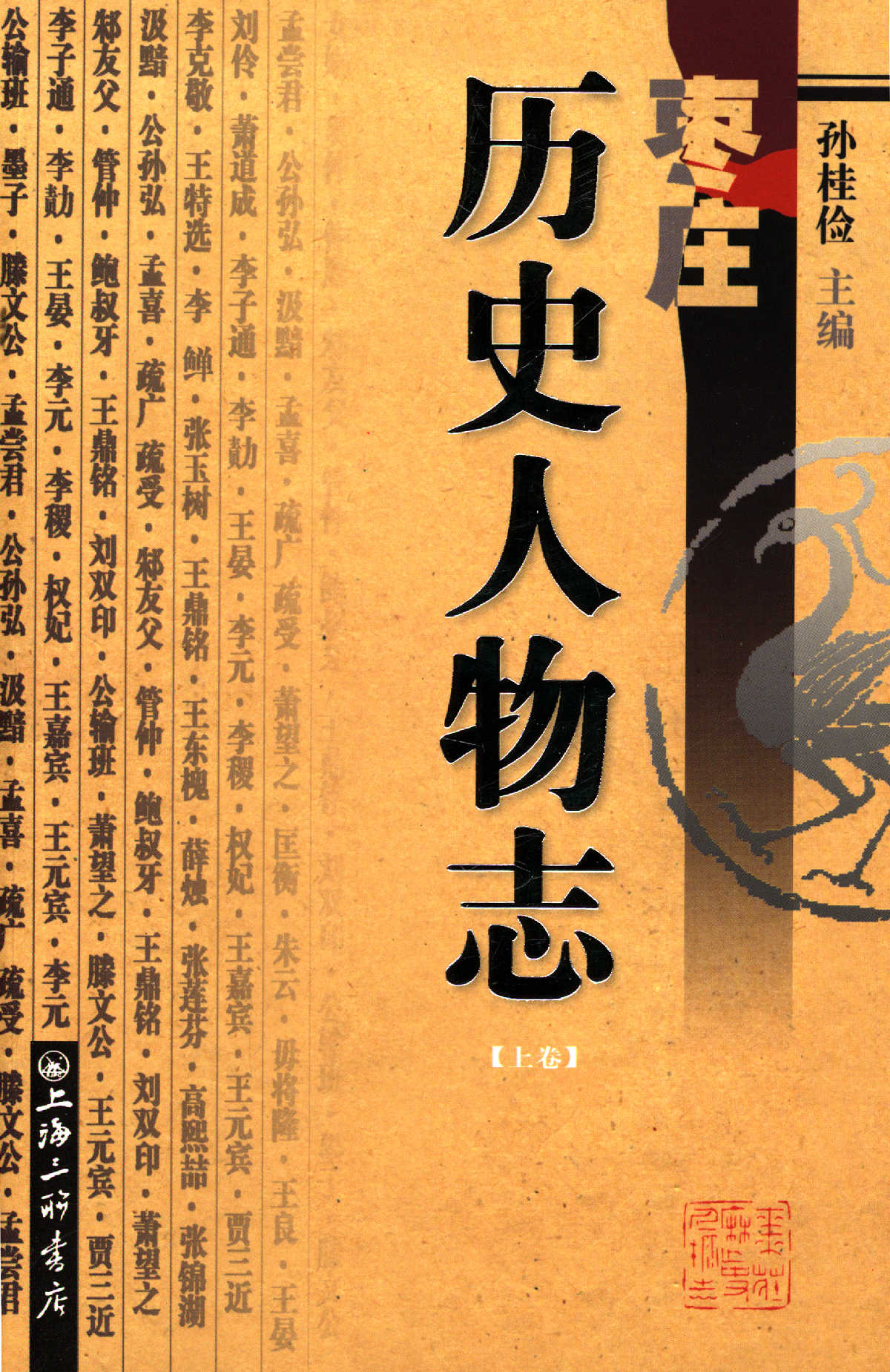内容
薛烛,生卒年月不详,春秋时期薛国(今山东省枣庄市官桥一带)人。以善于铸剑、相剑闻名。越王勾践二十年(公元前476年)专赴越国为越王相剑。民间流传故事青出于蓝春秋末年,诸侯连年征战,随着铜、铁等金属的广泛使用,作战兵器不断更新,作战方式不断改进,车战改成了步战。兵士们近距离搏斗需要随身携带方便而又锋利的兵器。剑轻巧、灵便,自然为人青睐。
古代的薛国,西接韩秦,北临魏赵,东临齐鲁,南临楚越,为 “三国五邑”之地,是中原的战略中心。战争的需要,使薛国冶炼业十分发达,铸铁、铸铜的铺子鳞次柿比,分工十分精细,仅冶铜的工匠就分筑、冶、鬼、栗、段、桃等,桃即专指铸剑。薛烛就出生在那时的薛国。薛烛的先祖也算是名门望族,可到了爷爷一辈就已经家道中落,到了薛烛这一代就仅剩一间容身的房子。他家的门口就是一排排的冶金铺子。可以说,少年薛烛就是在叮叮当当的敲打声陪伴下长大的。
每天天不亮,铸剑铺的下工就捅开了炉子,大师傅用过早点,便开始了一天“叮当叮当”地敲击。薛烛在家就能听到“叮当”的敲击声,家里人嫌聒噪,把门重重地关上,骂铸剑人一天到晚都不让人清静。薛烛却非常喜欢这声音。“叮当叮当”的敲击声在他的耳朵里如同天籁声一般动人。他经常趁人不注意猫到铸剑铺子里,看着师傅们在那里忙活。炉子里的火在皮风囊的鼓吹下热烈地燃烧着,照在薛烛的脸上,如同五月的石榴花一样鲜艳。那些坚硬无比的铁块、铜块搬进坩埚里,不用多长时间,就柔软得如同水一般。如同水一般的铜铁汁,倒进“制范”里,初具了剑模,再稍加打磨装饰,砥砺开刃,一柄锐利的剑就出来了。薛烛常常躲在一边呆呆地看着,连饭也忘了吃。他幻想着自己什么时候也能亲手铸造一把削金断铁的宝剑。如是,那该是多么快乐的事啊!薛烛常看着那些当兵的腰里挎着的长剑发呆。那些兵士们张口唱到:“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口里一边唱着一边用手拍着剑鞘。薛烛感觉到自己的眼睛再也离不开那些有着金色的剑箍、配着鲜艳的漆制剑鞘、剑颈上缠着细丝的绳子、刻着铭文的宝剑。这时候,薛烛的心随着宝剑飞了。
一转眼,薛烛十八岁了,他跟随铸剑师傅学习铸剑已经有一年多。师傅觉着薛烛的技术差不多了,让薛烛出师。薛烛很高兴,他庆幸自己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铸剑师了。
师傅看着他高兴的样子,提醒他学无止境,说:“你应该出去走走,外面的世界很大哩! ”薛烛恍然大悟。是啊,自己怎么就没想到去各处转转、寻找名师指点技艺呢?薛烛猛敲了一下自己的头,这才离开家,周游各地,寻找出名的铸剑师拜师学艺。
青胜于蓝清冷的风迎面扑来,薛烛不由地打了个寒战。虽然是早春二月,薛烛还是早早地换上了单布衣裤,这样干起活来更加利索。哪里想到这二月的风吹在身上像刀子割的锐利,浸入骨髓,薛烛不由地就加快了脚步。今天师傅说开大炉,要下功夫铸最好的剑呢。风继续吹着。薛烛隐隐约约听到“当当”的敲击声和此起彼伏的呼喝声。举目望去,一人多高的大剑炉昂然地直立在还是薄雾冥冥的山脚下,大火在炉中烧得轰轰烈烈,火舌还趁机钻出炉口,映得半边天都亮了。火炉旁边竖着几架木梯,几个剑工正匆匆忙忙、上下来回地跑着。
“薛师哥,快来看看! ”一个身穿夹衣的小伙子看见薛烛,脸上露出喜色,高声地嚷嚷着。
“怎么了? ”薛烛赶紧加快脚步。喊他的是年纪最小的师弟小伍子。
“温度上不去,‘料’化不开。”小伍子皱着眉头说。
應二...东周•青铜壶“师傅呢?” 薛烛接过捅条。
“师傅不知道到哪儿去了。一会儿就该配 ‘料,了。”小伍子说得飞快,一看就是个急性子人,“要是配料再找不到师傅就坏事了。”薛烛根本没听见他说的话。火舌几乎燎着了他的头发。他把头伸到炉子底下,清着炉壁上的结垢。所有的剑工都停了下来,抹着额上的汗,看着薛烛在那里咬牙清炉。
好一会儿,薛烛直起身,把烧红的捅条扔到地上,吁了口气说:“烧的时间长了,炉垢积得太厚,所以影响温度上升。现在行了,添柴,加大火候!”薛烛健步飞上木梯,凝望着坩埚里一平如初的炉水,脸上显现前所未有的凝重。这批“料”是上好的青铜料,因此沸点也高。师傅计划着要铸造出一批最好的宝剑来。这从“制范”就可以看出师傅的决心,以往“制范”师傅派两个仔细点的弟子也就算细心了,现在却是他领着薛烛亲自做,精心不放过任何一个小的细节。如今铜汁就要熬好,应该再往里添“料”了,怎么他老人家就不露面了呢?“师傅找到了没有? ”薛烛大声问下面的剑工。
“没有! ”剑工大声回答。
“再去找,要快!”薛烛望了望天,师傅到底是上哪里去了呢?平常师傅办事稳健,不是那心里没数的人呀。
薛烛看着热气在坩埚的上方氤氲着,心里忽然一动。这几次师傅铸的剑并不是很成功,总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有时剑的硬度和强度够了,剑身却非常的脆弱,容易折断。这是为什么呢?薛烛琢磨了很长时间。应该和“制范”没有多大关系。“制范”是以铜剑的器形设计为依据,铜剑器形是否能够达到设计要求,规范而协调,匀称而美观,取决于“制范”是否精细。但这与剑是否脆弱没有关系。那么是否与“调剂”配料有关系?薛烛眉毛结成一个疙瘩,但是到底是哪些“料”的问题呢?师傅说过,“调剂”是铸剑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宝剑是否锋利、坚硬,都取决于“调剂”如何。师傅对薛烛应该是知无不言,每一次“调剂”时都把薛烛带在身边,让他细细看他是怎么配料的。师傅说:“改天我不在的时候,你就大胆地配一次。”师傅说这话的时候非常认真。
想到这儿薛烛的心也亮了一下,身上热乎乎的。师傅早就对他说过,铸剑最好的材料是青铜,青铜非常昂贵。青铜是铜、锡或者是铜、锡、铅的合金,剂量是青铜合金中各成份占的比例。熔炼青铜之前要根据配比规律,对铜、锡或者铜、锡、铅等原料进行调配。师傅说过很多次,在一定范围内,青铜中含铅量的提高是能够相应地提高合金的硬度和强度,但含铅量超过合金量的界限,就会使青铜合金变得非常脆弱,易于折断;但是在青铜合金中加入少量的锡,可以调节金属的铸造性能。
想到这儿,薛烛眉间的大疙瘩松开了。师傅说锡是按照定量加的,可没说铅是按照什么加的呀!薛烛清楚地记得铸剑工艺书上说过,如果合金中铅的含量过高,也会降低合金的硬度和强度。薛烛把手一拍,连连说:“是了是了,就是这样了!什么东西不都有个界么,只有合金中各成分的比例调节配对了,才能得到既坚且韧的青铜宝剑的剑材呀!”薛烛兴冲冲几步跃下木梯。薛烛伸手抓起筐里最小的铅块, 掂了掂,放进坩埚。
薛烛跑到炉口看了看火候,火烧得正好,火旺而不散。薛烛看看坩埚的上方,黑浊的气体已经渐渐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黄白的气体。薛烛心里一动,那黑色的浊气是原料上附着的木炭、树枝燃烧产生的,这黄白色的气体却是沸点较低的锡铅了。
“薛师哥,你给我们讲讲怎么根据气体颜色看熔炼的火候吧! ”小伍子拉着几个年幼的师弟跑了过来。
“好。”薛烛让他们靠拢过来,注意看那熔炉上的气体。“你们看,现在炉中上方是黄白气体。刚才炉口上方还是黑色稍稍混浊的气体,那些黑色的浊气是原料上附着的木炭、树枝燃烧产生的,这黄白色的气体呢却是沸点较低的锡铅溶化产生的。原料中含有的不同东西挥发出来形成的烟气颜色也就不同,过不了多长时间那些黄白气体就该变成青色的气体了。”薛烛又往炉膛里扔了两块木炭,接着说:“温度继续升高后,铜熔化的青白颜色就呈现了出来,等到青白气体全部挥发完了,温度继续升高,铜就全部熔化好了。因为铜的比例远远要比锡、铅的大,所以这个时候只有青气,而且颜色也非常的纯净,这说明,原料中的杂质大都随气体跑掉了。”薛烛继续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浇铸了……”小伍子他们都大眼瞪小眼地望着薛烛,满眼里都是敬佩。
薛烛接着说:“这剑又分剑身与剑茎,每一部位都有名称。” 薛烛抓起一把长剑,指给师弟们看:“剑身前端称‘锋’,剑体中线凸起称‘脊’,‘脊’两侧成坡状称‘从’,‘从’外的刃称 ‘锷’,合‘脊’与两‘从’为‘腊’,剑把称‘茎’。茎主要有圆型和扁型,茎和身之间有护手的格又称‘卫’,茎的末端常有圆型的称‘首’,短剑又称4匕’。”这时候,炉里的黄白气体已绝,缓缓升起的正是纯净的青气。
不能再等了,薛烛沉思了一下,把腰带紧了一下,果断地说: “开炉! ”随着薛烛一声吆喝,熔化好的青铜液体缓缓地流入事先准备好的剑范。一、二、三、四、五,薛烛看着五个剑范灌满了青铜液,揩了一把脸上的汗。只需等它们冷却、凝固就行了。
薛烛蹲下身子,开始斟酌着如何给铸后的青铜剑加工。因为刚刚浇铸出的宝剑表面粗糙,卸去剑范后,还得仔细刮削琢磨,让它们表面平整光滑。
一阵刮削打磨后,薛烛手中的铜剑已经有些模样了。薛烛用手试了试,嗯,轻重力度都很称手,应当是一把好剑。薛烛在铸成的花纹沟槽中镶上琉璃,嵌错铜丝、金银丝。“嵌错”手艺是薛烛最拿手的。虽然这道工序在剑工们眼里是个再琐碎不过的活计, 而薛烛做起来却津津有味。因为在薛烛眼里一切和宝剑有关的事都是那么有趣。
薛烛刚刚直起腰来,有人就喊了起来:“师傅来了。”所有的人“呼啦”都围了过去,七嘴八舌地问:“师傅,你到哪去了?是薛师兄领我们铸的剑。”师傅径直向薛烛走了过来,问:“干得怎么样?”小伍子嘴快,早三言两语地把铸剑过程向师傅说了一遍。师傅笑着对薛烛说:“这不干得挺好吗!”薛烛全都明白了,师傅是故意藏起来的,想看看自己的真本领。薛烛几乎要流出泪来。
“走走走,咱们看看你薛师兄铸的剑去!”薛烛师徒来到“削砥工”旁。宝剑还未开刃,只是刚刚打磨光洁。师傅用手掂起宝剑,对着阳光照了几照,面露喜色,连声道,“好!好剑!”又眯缝上眼睛,把剑斜对着阳光再瞧,那太阳光映出七色光辉从剑身流过,如同彩虹一般瑰丽。师傅细细地把玩着剑的“嵌错”,整齐划一的七颗绿松石如同星星一样耀眼。最后师傅缓声对薛烛道:“薛烛,这实在是一把好剑呀!”“师傅,徒儿还有一事想向你汇报。”薛烛忐忑不安地说。“我把您的配料改了,铅少放了五分。”“为什么?”师傅挑起一条眉毛。
“因为如果合金中铅的含量较高,也会降低合金的硬度和强度。”薛烛小声说,“这几次我们铸的剑虽然都很锋利但是硬度和强度却都不够,太脆弱,而且容易折断。”“唔。”师傅又用手掂了掂手里的剑,用手指握成一个圆弧,然后猛一松手,剑身“嗡”地一声迅速弹了回来,铮铮作响。师傅高兴地说:“薛烛,这是你铸的第一把宝剑,你人师门虽然只有一年多,但你的资质与天赋很高。师傅这次铸剑躲了出去,就是想让你放开手脚地干,显一显你的真本领。师傅现在看到了,薛烛啊,你可以出师了。”薛烛以为师傅生气了,“扑通”跪倒,惶恐地说:“师傅,弟子知错了,但求你不要把薛烛逐出师门。”师傅“哈哈”笑了,一手搀起薛烛,说:“你想到哪里去了?” 师傅顿了顿,继续说道:“薛烛啊,从你敢改师傅的料单,师傅就知道以你的聪颖,必成大器。师傅老了,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教你,楚国、吴国都是铸剑的大国,那里有铸剑的大师欧冶子、干将,师傅也希望你能铸出龙渊、湛庐那样的好剑。你应该到那里去,一来开阔眼界,二来也磨炼一下自己,闯出点名气来。”师傅拍了拍薛烛的肩膀,鼓励道:“青胜于蓝啊,师傅相信,你将来会成为一代相剑名家。”越国相剑天刚刚亮,滋润了一夜的木槿花愈发得丰腴肥厚。越王勾践早早地命令掌管宝剑的人把宝剑收拾好。
日上三竿,宫门大开。越王府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他就是薛烛。越王知道,薛烛虽然年纪轻轻,却名噪列国,被人称为天下第一相剑大师。今日一见,虎背熊腰,剑眉星目,果然不同于一般人。
宾主自然少不了一番客套寒暄。随后,越王勾践就带着薛烛来到室外宽阔的露台上。越王勾践酷爱刀剑,这个露台高达数丈,气势宏伟,光线充沛,专门用来相剑赏刀。落座之后,薛烛道: “请大王端上宝剑吧。”越王叹道:“果然是个剑痴呀!”掌管剑的人把剑端出。越王知道薛烛虽然年轻,却已是阅剑无数,一般的剑根本就没打算让薛烛过目。最先端出的是名剑豪曹。薛烛只看了看,就轻轻地放下了。
越王把身子探了出来,问道:“如何?”“豪曹不是宝剑。”薛烛肯定地回答,“所谓宝剑,要求青红黄白黑五种光芒同时出现,哪一种光芒都不许胜过其他的光芒,豪曹在这一方面还很不足,不能算是宝剑。”“噢? ”越王的身子往前探了探,感到很新鲜,“那你再看看这把。”越王又挥了挥手。
掌剑人这回端上来的是巨阙。薛烛拿过来看了看又放下了,说:“这也不能算是上品的宝剑。”薛烛指着巨阙说:“好的宝剑要求铅锡与铜调和均勻。现在巨阙的铅锡都游离于铜之外,因此不能算是宝剑。”越王勾践叹息着说:“我可一直把它当作宝啊!巨阙炼成的时候,我拿着它坐在露坛上,有四个宫人驾着四匹快马拉的车从鹿的身边飞驰而过,马车跑得快,把鹿吓得乱跑,我抽出这把剑向马车一挥,马车飞上了半空。后来我用它刺向铜鼎,铜鼎被刺开了一个缺口,砍向铁锅,铁锅齐茬而开。所以我就叫它巨阙了。”薛烛听了越王勾践解释,只是微笑不语。
“拿纯钩来。”“什么?”薛烛仿佛没听清楚,紧赶着又问了一句。
“拿纯钩呀! ”越王赌气一般。
“纯钩? ”薛烛又重复了一遍:“真是纯钩吗?”“当然。”越王看着薛烛魂不守舍的样子开始洋洋自得起来,“就是纯钩宝剑。”薛烛听到“纯钩”这个名字,惊得呆在了那里,过了好一会才回过神。他走下台阶,恭敬地整理好衣帽,然后重新坐了下来。掌剑人用金托盘垫着红色的绸缎把“纯钩”端了上来,放在薛烛的面前。
薛烛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看了好半天,然后双手擎起宝剑,先是用力一震,接着轻轻地用手朝宝剑拂去,最后拿起剑猛然向上空挥去,只见空中一片凛然,宝剑光华四处,就像新开的荷花一样妩媚。看那剑身的花纹布满菱格,灿烂的光辉就像天上的星星在缓缓地运行。看那剑的光彩,就像初春池塘溢出的水,波波相连。看被它砍开的地方,如同高耸的悬崖一般整齐。看它的质地,光泽晶莹,如同刚开始消融的坚冰或是陈年的古玉……薛烛认真地鉴赏了好半天,才喃喃地说:“这才是宝剑啊!”“是呀!这当然是宝剑。”越王看着薛烛失态的样子得意地说:“前些日子有个北方的客人估算它的价值,说它抵得过两个带有集市的繁华乡,加上一千匹骏马和两座一千户的城池。你说它有那么大的价值吗?”薛烛站起身朗声问道:“您怀疑它的价值吗?”“那倒不是。”越王赶紧辩白。
“让我来说给您听听吧。”薛烛坐了下来,认真地说:“如果拿那些城池来换这把宝剑,未免太不划算了。当年欧冶子先生铸这把宝剑的时候,赤堇山崩裂采到锡矿;若耶溪干涸,才采到铜矿;天上的雨神飘洒着除尘的细雨,雷神雷电交加如同拉着助威的风箱,龙王小心翼翼地捧着炼剑的洪炉,天帝前来往炉里加炭,太上老君下凡观看。为铸这一口宝剑,天上的神仙都下来帮忙了。”薛烛稍稍喘了一口气,接着说道:“欧冶子正是借助了众位天神的力量,拿出他全部的智慧,才铸造出三把大型宝剑和二把小型宝剑。一个叫湛庐,一个叫纯钩。纯钩就是大王拥有的这把。另外三把,一个是胜邪,一个是鱼肠,一个是巨阙。吴王阖闾时得到了其中的三把,就是胜邪、鱼肠和湛庐。”“吴王阖闾残暴不仁,他女儿死了,他杀了很多的人来陪葬。湛庐剑是君子剑,湛庐剑憎恨吴王阖闾暴虐无道,离开了吴宫,沿着水路过楚国到秦国。恰巧楚昭王睡觉醒来,在他的床上发现了吴王的湛庐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召来大臣风胡子问道:‘这是一把什么样的剑?’风胡子说:‘这就是越王献给吴王的湛庐宝剑,它是欧冶子采五金之英、太阳之精所铸造的神器。谁拥有它,出之有神,服之有威,所向披靡。如今吴王阖闾暴虐无道,湛庐剑离开无道之君,归依有道之主,所以来到楚国。’ 楚昭王听了非常高兴,把湛庐剑当作了宝贝。秦王得到消息,向楚王来索取湛庐剑,没有到手,就兴兵攻打楚国,还扬言说: ‘只有把湛庐剑给我,我才收兵。’但是楚王还是不肯将湛庐剑交出来。”“鱼肠剑纹理细腻,是死士绝勇之剑。阖闾就是派刺客专诸用鱼肠剑刺杀了吴王僚。”薛烛说着闭上眼睛,仿佛看到了那把锐利的短剑和刺客专诸。
“彼时黑铁一般的大鹰向大殿疾飞的时候,专诸也正端着亲手烹制的梅花凤鲂炙走上殿来。天空里阳光猎猎,大鹰疾飞如故。大殿间甲士陈列,专诸稳步向前。云朵被飞鹰的气势惊得纷纷游走。吴王僚被专诸手里的菜香所吸引,他只看到菜没有看到专诸。那道菜叫梅花凤鲚炙,梅花是严冬的寒梅,凤鲚是太湖里只在酷暑出现的凤尾鲚鱼,炙,是用严冬寒梅的枝杆来烤炙盛夏太湖里的凤尾鲚鱼。飞鹰已经看到大殿的轮廓,天色突然暗了下来。专诸已经来到吴王僚的面前,把菜放在案上,殿内灯火依旧。
乌云在天空翻滚,大鹰已经收翅。
吴王僚吞着口水,看着面前的美味。专诸稳稳地用手掰鱼。伴随着一声响雷,飞鹰向大殿凌空击下。吴王僚突然感到一股凛冽的杀气从鱼腹中射出,他被惊呆了。鱼肠剑已经出鞘(鱼腹),它稳稳地落在专诸的手中,疾速向前。两把训练有素的铁戈从面前交叉拦住,鱼肠剑从缝隙中穿过,依然疾进。面前有三层狻猊铠甲。第一层穿透,第二层穿透,穿透第三层时,鱼肠剑变成了断剑。剑断,杀气未断,鱼肠剑依旧向前。飞鹰拍击大殿的时候,鱼肠剑也挺进了吴王僚的心脏。飞鹰在受伤下坠的时候满足地打了一声呼哨。断成一半的鱼肠剑在吴王僚渐渐减弱的心跳中砰然落下。被刀锋剑雨扑倒的专诸,也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向着脸下的土地,绽出了一个寂寞的、只有他自己才能懂得的微笑。”薛烛停止了叙说。
露台上一片死寂。
越王听得很专注,脸上神情悲戚。薛烛又深深地望了他一眼,接着往下说:“这些宝剑还都是在吴王僚身上小试锋芒而已,还没有人真把它大用于天下。现在赤堇山的缺口已经闭合,若耶溪的水流深不可测,天上的诸位神仙们也都没有下凡,欧冶子也已经年老力衰无法开炉铸剑了。所以现在即使是用黄金把城装满,用珠玉堆得河水断流,也得不到这样的宝物了。两个乡,加上一千匹骏马和两座一千户的城池,又算得上什么呢?”薛烛相剑令越王折服,遂拜为上宾,陪越王谈剑论酒。薛烛声名从此远播。
泰阿归真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带兵灭了吴王阖闾后,乘胜率军北渡淮水,在徐州会盟齐、晋、宋、鲁、滕、薛等国诸侯,如愿以偿争得了中原霸主之位,越国也成为一个时期最为强大的国家。
霸业的成功,勾践忘乎所以,凶相毕露,狡兔死走狗烹,开始谋害帮他成就霸业的大臣。先后逼得良相范蠡逃跑,大将文种自杀。薛烛对此极为震惊,他不明白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怎么这样多疑、残忍?跟随他多年的老臣居然说杀就杀,当真是人不如物,物有情而人却无情。
薛烛叹息自己相剑无数却不能相人,只怕再呆下去,对自己也无益处。于是萌生了离开越国的念头。
越王对薛烛始终热情有加,经常派自己的马车接薛烛到宫里喝酒谈剑。又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越王宫内菊花盛开。勾践邀了一帮老臣来宫内赏菊论剑,薛烛仍被奉为上宾。
越王问薛烛道:“又是一年了,薛卿来此有几年了吧?”薛烛趁机说道:“大王,薛烛到越已有五载了,北雁南飞,旅人也应该回返了。”“噢? ”越王放下酒杯。“听薛卿之意是想家喽!”薛烛点点头,回答道:“是。薛烛四处游荡,离家多年,家中杳无音讯,这几日常常做梦,甚为想念家乡。还请大王开恩,允薛烛返乡,以慰思念之情。”“那好吧!”勾践想了想说:“既然如此,孤家就不留你了,可惜从此孤身边就没有陪着谈剑喝酒的人了。来人啊!把前几日楚国献的宝剑呈上来。”听到“宝剑”二字,薛烛的眼睛一亮,又坐了下来。
掌剑人用金漆盘端上一个长布包裹。薛烛打开包裹,看到一柄带着褐色剑鞘的宝剑。
“薛卿看看这是什么剑? ”勾践笑眯眯地说。
薛烛神情庄重并不答话。他把剑从剑鞘中抽出,神色大变,脱口道:“好剑!此乃泰阿矣!”“泰阿如何好? ”勾践紧逼一句。
“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籾也,黄白杂则坚且韧,良剑也。”“泰阿有何典故?”“泰阿宝剑乃是一把正义之剑。”薛烛正色说道:“当初楚王对风胡子说:‘我听说吴国有位干将,楚国有位欧冶子,这两人才艺盖世,是天下少有的铸剑名师。我想以楚国的稀世珍宝,请你向吴王礼聘这两人来帮我铸剑好吗? ’于是风胡子到吴国求见欧冶子和干将,请他们铸造铁剑。欧冶子和干将铸成三把铁剑,一把叫龙渊,一把叫泰阿,一把叫工布。大王这把泰阿剑就是欧冶子所铸的泰阿剑。”薛烛瞄了一眼越王,绘声绘色地继续讲道:“昔日楚国的都城被晋国的兵马围困三年,就是想得到楚国的镇国之宝泰阿剑。世人都说,泰阿剑是欧冶子和干将两大剑师联手所铸。但是两位大师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说泰阿剑是一把威道之剑早已存在,只是无形无迹,但是剑气早已存于天地之间,只等待时机凝聚起来,天时地利人和三道归一,此剑即成。晋国东周•青铜剑当时最为强大,晋王当然认为自己最有资格得到这把宝剑,但事与愿违,此剑却在弱楚铸成。出剑之时,剑身果然天然镌刻篆体 ‘泰阿’二字,可见欧冶子、干将所言不虚。晋王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向楚王索剑,楚王拒绝,于是晋王出兵伐楚。楚国被困三年。城里粮草告罄,兵革无存,危在旦夕。晋国派来使者发出最后通牒:如再不交剑,明天将攻陷此城,到时玉石倶焚!楚王不屈,吩咐左右明天随自己上城头杀敌,如果城破,自己将用此剑自刎,然后左右要拾得此剑,骑快马奔到大湖,将此剑沉入湖底,让泰阿剑永留楚国。第二天拂晓,楚王登上城头,只见城外晋国兵马遮天蔽日,自己的都城宛如汪洋之中的一叶扁舟,随时有倾灭的危险。晋国兵马开始攻城,呐喊声如同山呼海啸,城破在即。楚王双手捧剑,长叹一声:泰阿啊,泰阿,我今天将用自己的鲜血来祭你!于是,拔剑出鞘,引剑直指敌军。匪夷所思的奇迹出现了:只见一团磅礴剑气射出,城外霎时飞砂走石,遮天蔽日,似有猛兽咆哮。晋国兵马大乱,旌旗仆地,流血千里,全军覆没……事情过后,楚王召来国中智者风胡子问道:‘泰阿剑为何会有如此之威?’风胡子对道:‘泰阿剑是一把威道之剑,而内心之威才是真威。大王身处逆境威武不屈,正是大王的内心之威激发出泰阿剑的剑气之威啊! ’ ”薛烛一口气说完,竟然有些气喘吁吁。
薛烛话音落了好久,竟然没有一人答话,似乎都沉醉于薛烛讲述描绘的场景里。勾践最后回味过来,不由得击掌赞叹:“先生不愧是相剑高手,宝剑入你手,便是遇得知音。”勾践边说边操起案上的泰阿剑,恋恋不舍地看了又看,说:“泰阿啊,泰阿,跟你的知音去吧。”薛烛愣了。薛烛好半晌才抬起头,“真的给我了?”“趁着我还没改变主意以前,赶紧拿走! ”勾践把脸背过去,不忍再看宝剑。
“是! ”薛烛伸手接过宝剑,双膝跪下磕了一个响头,说: “谢大王知遇之恩。”说完,离开了越王府。
手下的侍者问越王:“如此宝剑,怎么就便宜薛烛了?” 勾践把酒一饮而尽道:“自古宝剑识英雄。跟随薛烛,也算没有辜负这把宝剑。”薛烛辞谢了越王,背上心爱的泰阿向暮色苍茫的远方走去。
古代的薛国,西接韩秦,北临魏赵,东临齐鲁,南临楚越,为 “三国五邑”之地,是中原的战略中心。战争的需要,使薛国冶炼业十分发达,铸铁、铸铜的铺子鳞次柿比,分工十分精细,仅冶铜的工匠就分筑、冶、鬼、栗、段、桃等,桃即专指铸剑。薛烛就出生在那时的薛国。薛烛的先祖也算是名门望族,可到了爷爷一辈就已经家道中落,到了薛烛这一代就仅剩一间容身的房子。他家的门口就是一排排的冶金铺子。可以说,少年薛烛就是在叮叮当当的敲打声陪伴下长大的。
每天天不亮,铸剑铺的下工就捅开了炉子,大师傅用过早点,便开始了一天“叮当叮当”地敲击。薛烛在家就能听到“叮当”的敲击声,家里人嫌聒噪,把门重重地关上,骂铸剑人一天到晚都不让人清静。薛烛却非常喜欢这声音。“叮当叮当”的敲击声在他的耳朵里如同天籁声一般动人。他经常趁人不注意猫到铸剑铺子里,看着师傅们在那里忙活。炉子里的火在皮风囊的鼓吹下热烈地燃烧着,照在薛烛的脸上,如同五月的石榴花一样鲜艳。那些坚硬无比的铁块、铜块搬进坩埚里,不用多长时间,就柔软得如同水一般。如同水一般的铜铁汁,倒进“制范”里,初具了剑模,再稍加打磨装饰,砥砺开刃,一柄锐利的剑就出来了。薛烛常常躲在一边呆呆地看着,连饭也忘了吃。他幻想着自己什么时候也能亲手铸造一把削金断铁的宝剑。如是,那该是多么快乐的事啊!薛烛常看着那些当兵的腰里挎着的长剑发呆。那些兵士们张口唱到:“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口里一边唱着一边用手拍着剑鞘。薛烛感觉到自己的眼睛再也离不开那些有着金色的剑箍、配着鲜艳的漆制剑鞘、剑颈上缠着细丝的绳子、刻着铭文的宝剑。这时候,薛烛的心随着宝剑飞了。
一转眼,薛烛十八岁了,他跟随铸剑师傅学习铸剑已经有一年多。师傅觉着薛烛的技术差不多了,让薛烛出师。薛烛很高兴,他庆幸自己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铸剑师了。
师傅看着他高兴的样子,提醒他学无止境,说:“你应该出去走走,外面的世界很大哩! ”薛烛恍然大悟。是啊,自己怎么就没想到去各处转转、寻找名师指点技艺呢?薛烛猛敲了一下自己的头,这才离开家,周游各地,寻找出名的铸剑师拜师学艺。
青胜于蓝清冷的风迎面扑来,薛烛不由地打了个寒战。虽然是早春二月,薛烛还是早早地换上了单布衣裤,这样干起活来更加利索。哪里想到这二月的风吹在身上像刀子割的锐利,浸入骨髓,薛烛不由地就加快了脚步。今天师傅说开大炉,要下功夫铸最好的剑呢。风继续吹着。薛烛隐隐约约听到“当当”的敲击声和此起彼伏的呼喝声。举目望去,一人多高的大剑炉昂然地直立在还是薄雾冥冥的山脚下,大火在炉中烧得轰轰烈烈,火舌还趁机钻出炉口,映得半边天都亮了。火炉旁边竖着几架木梯,几个剑工正匆匆忙忙、上下来回地跑着。
“薛师哥,快来看看! ”一个身穿夹衣的小伙子看见薛烛,脸上露出喜色,高声地嚷嚷着。
“怎么了? ”薛烛赶紧加快脚步。喊他的是年纪最小的师弟小伍子。
“温度上不去,‘料’化不开。”小伍子皱着眉头说。
應二...东周•青铜壶“师傅呢?” 薛烛接过捅条。
“师傅不知道到哪儿去了。一会儿就该配 ‘料,了。”小伍子说得飞快,一看就是个急性子人,“要是配料再找不到师傅就坏事了。”薛烛根本没听见他说的话。火舌几乎燎着了他的头发。他把头伸到炉子底下,清着炉壁上的结垢。所有的剑工都停了下来,抹着额上的汗,看着薛烛在那里咬牙清炉。
好一会儿,薛烛直起身,把烧红的捅条扔到地上,吁了口气说:“烧的时间长了,炉垢积得太厚,所以影响温度上升。现在行了,添柴,加大火候!”薛烛健步飞上木梯,凝望着坩埚里一平如初的炉水,脸上显现前所未有的凝重。这批“料”是上好的青铜料,因此沸点也高。师傅计划着要铸造出一批最好的宝剑来。这从“制范”就可以看出师傅的决心,以往“制范”师傅派两个仔细点的弟子也就算细心了,现在却是他领着薛烛亲自做,精心不放过任何一个小的细节。如今铜汁就要熬好,应该再往里添“料”了,怎么他老人家就不露面了呢?“师傅找到了没有? ”薛烛大声问下面的剑工。
“没有! ”剑工大声回答。
“再去找,要快!”薛烛望了望天,师傅到底是上哪里去了呢?平常师傅办事稳健,不是那心里没数的人呀。
薛烛看着热气在坩埚的上方氤氲着,心里忽然一动。这几次师傅铸的剑并不是很成功,总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有时剑的硬度和强度够了,剑身却非常的脆弱,容易折断。这是为什么呢?薛烛琢磨了很长时间。应该和“制范”没有多大关系。“制范”是以铜剑的器形设计为依据,铜剑器形是否能够达到设计要求,规范而协调,匀称而美观,取决于“制范”是否精细。但这与剑是否脆弱没有关系。那么是否与“调剂”配料有关系?薛烛眉毛结成一个疙瘩,但是到底是哪些“料”的问题呢?师傅说过,“调剂”是铸剑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宝剑是否锋利、坚硬,都取决于“调剂”如何。师傅对薛烛应该是知无不言,每一次“调剂”时都把薛烛带在身边,让他细细看他是怎么配料的。师傅说:“改天我不在的时候,你就大胆地配一次。”师傅说这话的时候非常认真。
想到这儿薛烛的心也亮了一下,身上热乎乎的。师傅早就对他说过,铸剑最好的材料是青铜,青铜非常昂贵。青铜是铜、锡或者是铜、锡、铅的合金,剂量是青铜合金中各成份占的比例。熔炼青铜之前要根据配比规律,对铜、锡或者铜、锡、铅等原料进行调配。师傅说过很多次,在一定范围内,青铜中含铅量的提高是能够相应地提高合金的硬度和强度,但含铅量超过合金量的界限,就会使青铜合金变得非常脆弱,易于折断;但是在青铜合金中加入少量的锡,可以调节金属的铸造性能。
想到这儿,薛烛眉间的大疙瘩松开了。师傅说锡是按照定量加的,可没说铅是按照什么加的呀!薛烛清楚地记得铸剑工艺书上说过,如果合金中铅的含量过高,也会降低合金的硬度和强度。薛烛把手一拍,连连说:“是了是了,就是这样了!什么东西不都有个界么,只有合金中各成分的比例调节配对了,才能得到既坚且韧的青铜宝剑的剑材呀!”薛烛兴冲冲几步跃下木梯。薛烛伸手抓起筐里最小的铅块, 掂了掂,放进坩埚。
薛烛跑到炉口看了看火候,火烧得正好,火旺而不散。薛烛看看坩埚的上方,黑浊的气体已经渐渐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黄白的气体。薛烛心里一动,那黑色的浊气是原料上附着的木炭、树枝燃烧产生的,这黄白色的气体却是沸点较低的锡铅了。
“薛师哥,你给我们讲讲怎么根据气体颜色看熔炼的火候吧! ”小伍子拉着几个年幼的师弟跑了过来。
“好。”薛烛让他们靠拢过来,注意看那熔炉上的气体。“你们看,现在炉中上方是黄白气体。刚才炉口上方还是黑色稍稍混浊的气体,那些黑色的浊气是原料上附着的木炭、树枝燃烧产生的,这黄白色的气体呢却是沸点较低的锡铅溶化产生的。原料中含有的不同东西挥发出来形成的烟气颜色也就不同,过不了多长时间那些黄白气体就该变成青色的气体了。”薛烛又往炉膛里扔了两块木炭,接着说:“温度继续升高后,铜熔化的青白颜色就呈现了出来,等到青白气体全部挥发完了,温度继续升高,铜就全部熔化好了。因为铜的比例远远要比锡、铅的大,所以这个时候只有青气,而且颜色也非常的纯净,这说明,原料中的杂质大都随气体跑掉了。”薛烛继续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浇铸了……”小伍子他们都大眼瞪小眼地望着薛烛,满眼里都是敬佩。
薛烛接着说:“这剑又分剑身与剑茎,每一部位都有名称。” 薛烛抓起一把长剑,指给师弟们看:“剑身前端称‘锋’,剑体中线凸起称‘脊’,‘脊’两侧成坡状称‘从’,‘从’外的刃称 ‘锷’,合‘脊’与两‘从’为‘腊’,剑把称‘茎’。茎主要有圆型和扁型,茎和身之间有护手的格又称‘卫’,茎的末端常有圆型的称‘首’,短剑又称4匕’。”这时候,炉里的黄白气体已绝,缓缓升起的正是纯净的青气。
不能再等了,薛烛沉思了一下,把腰带紧了一下,果断地说: “开炉! ”随着薛烛一声吆喝,熔化好的青铜液体缓缓地流入事先准备好的剑范。一、二、三、四、五,薛烛看着五个剑范灌满了青铜液,揩了一把脸上的汗。只需等它们冷却、凝固就行了。
薛烛蹲下身子,开始斟酌着如何给铸后的青铜剑加工。因为刚刚浇铸出的宝剑表面粗糙,卸去剑范后,还得仔细刮削琢磨,让它们表面平整光滑。
一阵刮削打磨后,薛烛手中的铜剑已经有些模样了。薛烛用手试了试,嗯,轻重力度都很称手,应当是一把好剑。薛烛在铸成的花纹沟槽中镶上琉璃,嵌错铜丝、金银丝。“嵌错”手艺是薛烛最拿手的。虽然这道工序在剑工们眼里是个再琐碎不过的活计, 而薛烛做起来却津津有味。因为在薛烛眼里一切和宝剑有关的事都是那么有趣。
薛烛刚刚直起腰来,有人就喊了起来:“师傅来了。”所有的人“呼啦”都围了过去,七嘴八舌地问:“师傅,你到哪去了?是薛师兄领我们铸的剑。”师傅径直向薛烛走了过来,问:“干得怎么样?”小伍子嘴快,早三言两语地把铸剑过程向师傅说了一遍。师傅笑着对薛烛说:“这不干得挺好吗!”薛烛全都明白了,师傅是故意藏起来的,想看看自己的真本领。薛烛几乎要流出泪来。
“走走走,咱们看看你薛师兄铸的剑去!”薛烛师徒来到“削砥工”旁。宝剑还未开刃,只是刚刚打磨光洁。师傅用手掂起宝剑,对着阳光照了几照,面露喜色,连声道,“好!好剑!”又眯缝上眼睛,把剑斜对着阳光再瞧,那太阳光映出七色光辉从剑身流过,如同彩虹一般瑰丽。师傅细细地把玩着剑的“嵌错”,整齐划一的七颗绿松石如同星星一样耀眼。最后师傅缓声对薛烛道:“薛烛,这实在是一把好剑呀!”“师傅,徒儿还有一事想向你汇报。”薛烛忐忑不安地说。“我把您的配料改了,铅少放了五分。”“为什么?”师傅挑起一条眉毛。
“因为如果合金中铅的含量较高,也会降低合金的硬度和强度。”薛烛小声说,“这几次我们铸的剑虽然都很锋利但是硬度和强度却都不够,太脆弱,而且容易折断。”“唔。”师傅又用手掂了掂手里的剑,用手指握成一个圆弧,然后猛一松手,剑身“嗡”地一声迅速弹了回来,铮铮作响。师傅高兴地说:“薛烛,这是你铸的第一把宝剑,你人师门虽然只有一年多,但你的资质与天赋很高。师傅这次铸剑躲了出去,就是想让你放开手脚地干,显一显你的真本领。师傅现在看到了,薛烛啊,你可以出师了。”薛烛以为师傅生气了,“扑通”跪倒,惶恐地说:“师傅,弟子知错了,但求你不要把薛烛逐出师门。”师傅“哈哈”笑了,一手搀起薛烛,说:“你想到哪里去了?” 师傅顿了顿,继续说道:“薛烛啊,从你敢改师傅的料单,师傅就知道以你的聪颖,必成大器。师傅老了,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教你,楚国、吴国都是铸剑的大国,那里有铸剑的大师欧冶子、干将,师傅也希望你能铸出龙渊、湛庐那样的好剑。你应该到那里去,一来开阔眼界,二来也磨炼一下自己,闯出点名气来。”师傅拍了拍薛烛的肩膀,鼓励道:“青胜于蓝啊,师傅相信,你将来会成为一代相剑名家。”越国相剑天刚刚亮,滋润了一夜的木槿花愈发得丰腴肥厚。越王勾践早早地命令掌管宝剑的人把宝剑收拾好。
日上三竿,宫门大开。越王府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他就是薛烛。越王知道,薛烛虽然年纪轻轻,却名噪列国,被人称为天下第一相剑大师。今日一见,虎背熊腰,剑眉星目,果然不同于一般人。
宾主自然少不了一番客套寒暄。随后,越王勾践就带着薛烛来到室外宽阔的露台上。越王勾践酷爱刀剑,这个露台高达数丈,气势宏伟,光线充沛,专门用来相剑赏刀。落座之后,薛烛道: “请大王端上宝剑吧。”越王叹道:“果然是个剑痴呀!”掌管剑的人把剑端出。越王知道薛烛虽然年轻,却已是阅剑无数,一般的剑根本就没打算让薛烛过目。最先端出的是名剑豪曹。薛烛只看了看,就轻轻地放下了。
越王把身子探了出来,问道:“如何?”“豪曹不是宝剑。”薛烛肯定地回答,“所谓宝剑,要求青红黄白黑五种光芒同时出现,哪一种光芒都不许胜过其他的光芒,豪曹在这一方面还很不足,不能算是宝剑。”“噢? ”越王的身子往前探了探,感到很新鲜,“那你再看看这把。”越王又挥了挥手。
掌剑人这回端上来的是巨阙。薛烛拿过来看了看又放下了,说:“这也不能算是上品的宝剑。”薛烛指着巨阙说:“好的宝剑要求铅锡与铜调和均勻。现在巨阙的铅锡都游离于铜之外,因此不能算是宝剑。”越王勾践叹息着说:“我可一直把它当作宝啊!巨阙炼成的时候,我拿着它坐在露坛上,有四个宫人驾着四匹快马拉的车从鹿的身边飞驰而过,马车跑得快,把鹿吓得乱跑,我抽出这把剑向马车一挥,马车飞上了半空。后来我用它刺向铜鼎,铜鼎被刺开了一个缺口,砍向铁锅,铁锅齐茬而开。所以我就叫它巨阙了。”薛烛听了越王勾践解释,只是微笑不语。
“拿纯钩来。”“什么?”薛烛仿佛没听清楚,紧赶着又问了一句。
“拿纯钩呀! ”越王赌气一般。
“纯钩? ”薛烛又重复了一遍:“真是纯钩吗?”“当然。”越王看着薛烛魂不守舍的样子开始洋洋自得起来,“就是纯钩宝剑。”薛烛听到“纯钩”这个名字,惊得呆在了那里,过了好一会才回过神。他走下台阶,恭敬地整理好衣帽,然后重新坐了下来。掌剑人用金托盘垫着红色的绸缎把“纯钩”端了上来,放在薛烛的面前。
薛烛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看了好半天,然后双手擎起宝剑,先是用力一震,接着轻轻地用手朝宝剑拂去,最后拿起剑猛然向上空挥去,只见空中一片凛然,宝剑光华四处,就像新开的荷花一样妩媚。看那剑身的花纹布满菱格,灿烂的光辉就像天上的星星在缓缓地运行。看那剑的光彩,就像初春池塘溢出的水,波波相连。看被它砍开的地方,如同高耸的悬崖一般整齐。看它的质地,光泽晶莹,如同刚开始消融的坚冰或是陈年的古玉……薛烛认真地鉴赏了好半天,才喃喃地说:“这才是宝剑啊!”“是呀!这当然是宝剑。”越王看着薛烛失态的样子得意地说:“前些日子有个北方的客人估算它的价值,说它抵得过两个带有集市的繁华乡,加上一千匹骏马和两座一千户的城池。你说它有那么大的价值吗?”薛烛站起身朗声问道:“您怀疑它的价值吗?”“那倒不是。”越王赶紧辩白。
“让我来说给您听听吧。”薛烛坐了下来,认真地说:“如果拿那些城池来换这把宝剑,未免太不划算了。当年欧冶子先生铸这把宝剑的时候,赤堇山崩裂采到锡矿;若耶溪干涸,才采到铜矿;天上的雨神飘洒着除尘的细雨,雷神雷电交加如同拉着助威的风箱,龙王小心翼翼地捧着炼剑的洪炉,天帝前来往炉里加炭,太上老君下凡观看。为铸这一口宝剑,天上的神仙都下来帮忙了。”薛烛稍稍喘了一口气,接着说道:“欧冶子正是借助了众位天神的力量,拿出他全部的智慧,才铸造出三把大型宝剑和二把小型宝剑。一个叫湛庐,一个叫纯钩。纯钩就是大王拥有的这把。另外三把,一个是胜邪,一个是鱼肠,一个是巨阙。吴王阖闾时得到了其中的三把,就是胜邪、鱼肠和湛庐。”“吴王阖闾残暴不仁,他女儿死了,他杀了很多的人来陪葬。湛庐剑是君子剑,湛庐剑憎恨吴王阖闾暴虐无道,离开了吴宫,沿着水路过楚国到秦国。恰巧楚昭王睡觉醒来,在他的床上发现了吴王的湛庐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召来大臣风胡子问道:‘这是一把什么样的剑?’风胡子说:‘这就是越王献给吴王的湛庐宝剑,它是欧冶子采五金之英、太阳之精所铸造的神器。谁拥有它,出之有神,服之有威,所向披靡。如今吴王阖闾暴虐无道,湛庐剑离开无道之君,归依有道之主,所以来到楚国。’ 楚昭王听了非常高兴,把湛庐剑当作了宝贝。秦王得到消息,向楚王来索取湛庐剑,没有到手,就兴兵攻打楚国,还扬言说: ‘只有把湛庐剑给我,我才收兵。’但是楚王还是不肯将湛庐剑交出来。”“鱼肠剑纹理细腻,是死士绝勇之剑。阖闾就是派刺客专诸用鱼肠剑刺杀了吴王僚。”薛烛说着闭上眼睛,仿佛看到了那把锐利的短剑和刺客专诸。
“彼时黑铁一般的大鹰向大殿疾飞的时候,专诸也正端着亲手烹制的梅花凤鲂炙走上殿来。天空里阳光猎猎,大鹰疾飞如故。大殿间甲士陈列,专诸稳步向前。云朵被飞鹰的气势惊得纷纷游走。吴王僚被专诸手里的菜香所吸引,他只看到菜没有看到专诸。那道菜叫梅花凤鲚炙,梅花是严冬的寒梅,凤鲚是太湖里只在酷暑出现的凤尾鲚鱼,炙,是用严冬寒梅的枝杆来烤炙盛夏太湖里的凤尾鲚鱼。飞鹰已经看到大殿的轮廓,天色突然暗了下来。专诸已经来到吴王僚的面前,把菜放在案上,殿内灯火依旧。
乌云在天空翻滚,大鹰已经收翅。
吴王僚吞着口水,看着面前的美味。专诸稳稳地用手掰鱼。伴随着一声响雷,飞鹰向大殿凌空击下。吴王僚突然感到一股凛冽的杀气从鱼腹中射出,他被惊呆了。鱼肠剑已经出鞘(鱼腹),它稳稳地落在专诸的手中,疾速向前。两把训练有素的铁戈从面前交叉拦住,鱼肠剑从缝隙中穿过,依然疾进。面前有三层狻猊铠甲。第一层穿透,第二层穿透,穿透第三层时,鱼肠剑变成了断剑。剑断,杀气未断,鱼肠剑依旧向前。飞鹰拍击大殿的时候,鱼肠剑也挺进了吴王僚的心脏。飞鹰在受伤下坠的时候满足地打了一声呼哨。断成一半的鱼肠剑在吴王僚渐渐减弱的心跳中砰然落下。被刀锋剑雨扑倒的专诸,也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向着脸下的土地,绽出了一个寂寞的、只有他自己才能懂得的微笑。”薛烛停止了叙说。
露台上一片死寂。
越王听得很专注,脸上神情悲戚。薛烛又深深地望了他一眼,接着往下说:“这些宝剑还都是在吴王僚身上小试锋芒而已,还没有人真把它大用于天下。现在赤堇山的缺口已经闭合,若耶溪的水流深不可测,天上的诸位神仙们也都没有下凡,欧冶子也已经年老力衰无法开炉铸剑了。所以现在即使是用黄金把城装满,用珠玉堆得河水断流,也得不到这样的宝物了。两个乡,加上一千匹骏马和两座一千户的城池,又算得上什么呢?”薛烛相剑令越王折服,遂拜为上宾,陪越王谈剑论酒。薛烛声名从此远播。
泰阿归真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带兵灭了吴王阖闾后,乘胜率军北渡淮水,在徐州会盟齐、晋、宋、鲁、滕、薛等国诸侯,如愿以偿争得了中原霸主之位,越国也成为一个时期最为强大的国家。
霸业的成功,勾践忘乎所以,凶相毕露,狡兔死走狗烹,开始谋害帮他成就霸业的大臣。先后逼得良相范蠡逃跑,大将文种自杀。薛烛对此极为震惊,他不明白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怎么这样多疑、残忍?跟随他多年的老臣居然说杀就杀,当真是人不如物,物有情而人却无情。
薛烛叹息自己相剑无数却不能相人,只怕再呆下去,对自己也无益处。于是萌生了离开越国的念头。
越王对薛烛始终热情有加,经常派自己的马车接薛烛到宫里喝酒谈剑。又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越王宫内菊花盛开。勾践邀了一帮老臣来宫内赏菊论剑,薛烛仍被奉为上宾。
越王问薛烛道:“又是一年了,薛卿来此有几年了吧?”薛烛趁机说道:“大王,薛烛到越已有五载了,北雁南飞,旅人也应该回返了。”“噢? ”越王放下酒杯。“听薛卿之意是想家喽!”薛烛点点头,回答道:“是。薛烛四处游荡,离家多年,家中杳无音讯,这几日常常做梦,甚为想念家乡。还请大王开恩,允薛烛返乡,以慰思念之情。”“那好吧!”勾践想了想说:“既然如此,孤家就不留你了,可惜从此孤身边就没有陪着谈剑喝酒的人了。来人啊!把前几日楚国献的宝剑呈上来。”听到“宝剑”二字,薛烛的眼睛一亮,又坐了下来。
掌剑人用金漆盘端上一个长布包裹。薛烛打开包裹,看到一柄带着褐色剑鞘的宝剑。
“薛卿看看这是什么剑? ”勾践笑眯眯地说。
薛烛神情庄重并不答话。他把剑从剑鞘中抽出,神色大变,脱口道:“好剑!此乃泰阿矣!”“泰阿如何好? ”勾践紧逼一句。
“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籾也,黄白杂则坚且韧,良剑也。”“泰阿有何典故?”“泰阿宝剑乃是一把正义之剑。”薛烛正色说道:“当初楚王对风胡子说:‘我听说吴国有位干将,楚国有位欧冶子,这两人才艺盖世,是天下少有的铸剑名师。我想以楚国的稀世珍宝,请你向吴王礼聘这两人来帮我铸剑好吗? ’于是风胡子到吴国求见欧冶子和干将,请他们铸造铁剑。欧冶子和干将铸成三把铁剑,一把叫龙渊,一把叫泰阿,一把叫工布。大王这把泰阿剑就是欧冶子所铸的泰阿剑。”薛烛瞄了一眼越王,绘声绘色地继续讲道:“昔日楚国的都城被晋国的兵马围困三年,就是想得到楚国的镇国之宝泰阿剑。世人都说,泰阿剑是欧冶子和干将两大剑师联手所铸。但是两位大师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说泰阿剑是一把威道之剑早已存在,只是无形无迹,但是剑气早已存于天地之间,只等待时机凝聚起来,天时地利人和三道归一,此剑即成。晋国东周•青铜剑当时最为强大,晋王当然认为自己最有资格得到这把宝剑,但事与愿违,此剑却在弱楚铸成。出剑之时,剑身果然天然镌刻篆体 ‘泰阿’二字,可见欧冶子、干将所言不虚。晋王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向楚王索剑,楚王拒绝,于是晋王出兵伐楚。楚国被困三年。城里粮草告罄,兵革无存,危在旦夕。晋国派来使者发出最后通牒:如再不交剑,明天将攻陷此城,到时玉石倶焚!楚王不屈,吩咐左右明天随自己上城头杀敌,如果城破,自己将用此剑自刎,然后左右要拾得此剑,骑快马奔到大湖,将此剑沉入湖底,让泰阿剑永留楚国。第二天拂晓,楚王登上城头,只见城外晋国兵马遮天蔽日,自己的都城宛如汪洋之中的一叶扁舟,随时有倾灭的危险。晋国兵马开始攻城,呐喊声如同山呼海啸,城破在即。楚王双手捧剑,长叹一声:泰阿啊,泰阿,我今天将用自己的鲜血来祭你!于是,拔剑出鞘,引剑直指敌军。匪夷所思的奇迹出现了:只见一团磅礴剑气射出,城外霎时飞砂走石,遮天蔽日,似有猛兽咆哮。晋国兵马大乱,旌旗仆地,流血千里,全军覆没……事情过后,楚王召来国中智者风胡子问道:‘泰阿剑为何会有如此之威?’风胡子对道:‘泰阿剑是一把威道之剑,而内心之威才是真威。大王身处逆境威武不屈,正是大王的内心之威激发出泰阿剑的剑气之威啊! ’ ”薛烛一口气说完,竟然有些气喘吁吁。
薛烛话音落了好久,竟然没有一人答话,似乎都沉醉于薛烛讲述描绘的场景里。勾践最后回味过来,不由得击掌赞叹:“先生不愧是相剑高手,宝剑入你手,便是遇得知音。”勾践边说边操起案上的泰阿剑,恋恋不舍地看了又看,说:“泰阿啊,泰阿,跟你的知音去吧。”薛烛愣了。薛烛好半晌才抬起头,“真的给我了?”“趁着我还没改变主意以前,赶紧拿走! ”勾践把脸背过去,不忍再看宝剑。
“是! ”薛烛伸手接过宝剑,双膝跪下磕了一个响头,说: “谢大王知遇之恩。”说完,离开了越王府。
手下的侍者问越王:“如此宝剑,怎么就便宜薛烛了?” 勾践把酒一饮而尽道:“自古宝剑识英雄。跟随薛烛,也算没有辜负这把宝剑。”薛烛辞谢了越王,背上心爱的泰阿向暮色苍茫的远方走去。
相关人物
薛烛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