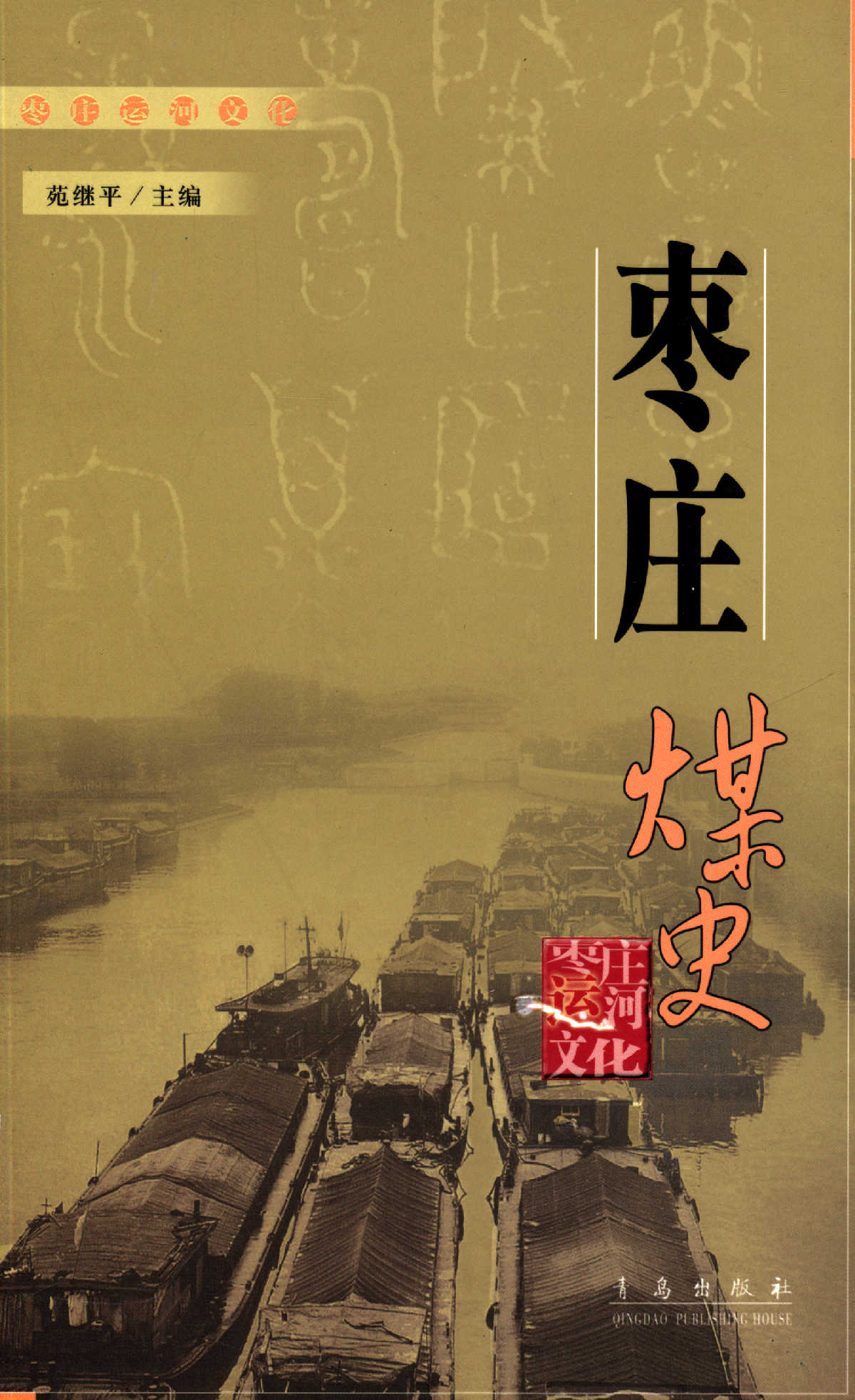内容
清代“任其采取,输税于官”的政策促进了煤矿事业的发展,峄县境内煤窑大增,煤炭运输出现了繁荣景象。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陆续产生了一批近代工业。各种近代工业的兴办,需要更多的煤炭来做燃料。当时各口岸虽然都有“洋煤”进口,但供不应求;由于煤炭缺乏,进口洋煤往往故意囤积居奇,造成煤价上涨。因此,山东及其他地方的一些官僚和富商,对储量丰富、煤质优良的枣庄煤田便格外关注。当时,峄县地主所开办的小煤窑,一部分人乐于和握有政治、经济大权的官僚和商人合作。于是就出现了以戴华藻为总办,由官僚、商人和地主集资合办的峄县中兴矿局。发起筹办中兴矿局的,是峄县人金铭和李朝相。他们都是当地的绅士,与崔、宋、黄、梁、田、王等家统称“峄县八大家族”。他们“以枣庄煤矿质佳,而自咸丰初年大乱后,本地财力困乏,无人开采,大窑弃之可惜,因与济宁州人直隶东明知县米协麟筹议兴办。米协麟与直隶候补知县戴华藻协商议妥”,招股集资筹划办理。
戴华藻,号心斋,安徽寿县人,系直隶候补知县,其堂弟戴宗骞是淮军的统领,因而与李鸿章有些关系。为了寻求靠山,他们便把筹备峄县中兴炭矿的情况稟告了当时任直隶总督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而李鸿章此时正在各地兴建军火工业,对煤炭非常需要,所以一拍即合,当即奏派米协麟和戴华藻来枣庄设立中兴矿局,用土法开办煤窑。
戴华藻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遂于光绪五年(1879年)春,正式立官窑总局。由于“事属创始,一切炭局章程,皆手自厘订”。后来,戴华藻补授了直隶望都知县,矿局总办便改为他的堂弟、从九品戴睿藻。筹划开办峄县矿局的除戴华藻外,还有地方官员王筱云(道员)、黄佩兰(道员)、朱采(知府)以及当地的绅士李伟、王曰智等数十家。他们被呈准开办后,虽然名义上也是“官督商办”,但声明“不领官本”,全部由私人投资。.初创时,仅集资白银2.5万两,这个数目在当时新兴办的采煤业中算是少的。而和它差不多同时创办的开平矿局最初资金却有80万两,比它创办稍晚的徐州利国驿煤矿,其资本有1〇万两。由于资金不足,因而中兴煤矿无力采用先进机器设备,不得不依旧沿用简陋的土法开采。而枣庄矿区经过数百年的连续开采,离地面较近的煤层已被挖掘殆尽,要大量生产煤炭,中兴矿局就必须开掘三四十丈乃至五六十丈的深井。可是,矿井加深,井内积水也就大量增加,再用滑车、牛皮包那样落后的工具戽水,是很难奏效的,因而必须添购动力较大的新式排水设备,也就必须扩大资本。光绪七年至光绪八年间(1881〜1882年),戴华藻为了进一步筹集资金,便通过他的堂弟戴宗骞先后函请湖南提督周盛波、通永镇总兵贾起胜、直隶候补道张莲芬以及江苏补用同知陈德浚等一批清政府官僚帮助集股。贾、张、戴等“共招寅友集凑股本白银5万余两;江苏同知陈丞(德浚)先后亦集有款(万金),俾资接济”。从此,矿局遂有南、北股之分。南股的代表人物陈德浚并被委任为矿局的转运委员,掌握了煤炭运销、器材采购等方面的实权。
有了资本之后,又因李鸿章的关系,中兴矿局得到了天津制造局道员王德均的协助,陆续订购汲水机器4架,并从广东、上海等地雇请技师和技术工人从事操作,局面逐渐好转。
中兴矿局先后共开了12个小窑,因为没能排干矿井积水,《峄县志》记载:枣庄煤质“质色尤佳”。在其创办的前3年间(1878〜1880年),始终未能产煤。有了新式排水设备以后,因为“法捷费省”,“一日而得数十日之功,一人而兼数十人之用”,工程进度大大加快,使得“一县长老皆惊以为自有炭窑所未闻也”。矿井积水排干后,于1882年2月开始见煤,到9月间,已能日产120余吨。由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非常需要煤炭,再加上峄煤“质色并佳,远近争先购用,运到天津、金陵制造局烧试,较日本上等煤尤佳,与英国松白相仿”,故而中兴矿局所产的煤销路很好。光绪九年(1883年)7月13日,李鸿章又向清政府奏准,峄县中兴矿局所产煤炭,仿照“台湾、开平、湖北等处开煤奏准成案,每吨交出口正税银一钱。各省兵商轮船机器制造局用煤,准其一律免税。完税之后,经过常关,应准呈验税单放行,运煤船只完纳船钞,免征船料。如此,则与各处矿局既免分歧,亦可收畅运之效”(《李文忠公奏稿》卷47,第11页)。清政府这一措施,使中兴矿局所产煤炭更加畅销。当时峄县境内,专门为它推销产品的商贩即有30余家。煤炭出井之后,商贩争相抢购。矿局恐怕酿成事端,就与他们订立合同,先期付款、排号,按号供煤,这些商贩从矿局得到煤炭后,便“择利而趋,到处行销”,其中很大一部分经过运河远销于长江沿岸,“售与轮船和机局”。1887年9月17日的《捷报》报道说:“山东峄县的煤矿甚为活跃,很多的大沙船装载上等的煤炭运往清江浦。”可见当时其声势之盛。
光绪九年(1883年),中兴矿局计划扩大规模,在上海公开招股,拟募集股本凑足10万两。不料恰逢上海金融恐慌,扩充股本、添购机器的计划未能实现。中兴矿局在生产组织和经营管理方面,基本上仍是沿袭地主小窑的制度,即所谓“用民窑之制,而以官法行之”。如设立班头、筐头,强拉农民下井等等。矿局最初只有工人数百人,以后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工人数目陆续增加。中兴矿局把这些工人分为“正掘班”和“公令班”两类。“正掘班”即长工,每两人为一组,先预支给工资制钱20吊至30吊不等,每人每日伙食制钱1〇〇文,挖出之煤按量计算,每斛(150斤)给制钱45文。“公令班”是按日计工,每日轮班替换。他们不仅在工作上没有 “正掘班”那样稳定,而且在待遇上和“正掘班”也有差别。他们没有预付工资,只是每人每日给制钱2〇〇文,挖掘一斛也给制钱45文。此外,矿局还有一部分抬筐与拉滑车的杂工,他们也属于按日计工,每人每日给制钱140文。
中兴矿局之所以要把工人分为上述两类,这是因为:一,可以根据不同时斯的生产需要(如季节的旺、淡),毫无顾忌地把一部分“公令班”工人招之来、挥之去。即使在工人来源缺乏时,他们仍然牢牢地控制着“正掘班”工人,使生产不致陷于停顿。二,这样做可以在工人中划分界限,长短工中自然产生了隔阂,不能团结一心,以便于他们控制工人。同时,对“公令班” 工人的报酬采用零开碎付的办法,使工人日进日销、身无余钱, 这样矿局更便于把工人掌握在自己手中,牢牢地拴在自己的井架上(据朱采:光绪八年《禀丁宫保论峄县煤矿地方官禀陈失实》)。后来,矿局把工人划分为“里工”和“外工”,但实际上还是这种“正掘班”和“公令班”制度的延续。
由于中兴矿局的主持者还不懂得“专利”的有关条款,所以不像后来中兴煤矿公司那样明确划定矿界。正如《峄县志》 .中所说“虽以官名,而邑旧采煤者争相慕效,远近分立,皆任其自为”。所以官局和地主小窑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和纠纷,其中突出的表现就是互相诱骗对方的工人。双方斗争相当激烈,有时官司一直打到山东巡抚部院。
峄县中兴矿局虽然是一座小型的商办煤矿,但仍受着封建官僚势力的干扰。起初,李鸿章企图通过山东巡抚处理,稍后,山东巡抚又在经济上要求“抽厘”报效。对此,矿局主持者只好尽力应付。表面上不能不答应官方指派会办的到来,但将其职权尽可能限制在“弹压事宜”上,即管理煤矿工人和应付地方事务,而不允许过问矿务。同时又请求以“助饷”代替“抽厘”。因为,从矿局主持者看来,“盖抽厘以见煤之日为始,而助饷则必须成本已敷,然后斟酌捐助”。他们在力求避免官府的干扰,设法减轻自己的负担。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陆续产生了一批近代工业。各种近代工业的兴办,需要更多的煤炭来做燃料。当时各口岸虽然都有“洋煤”进口,但供不应求;由于煤炭缺乏,进口洋煤往往故意囤积居奇,造成煤价上涨。因此,山东及其他地方的一些官僚和富商,对储量丰富、煤质优良的枣庄煤田便格外关注。当时,峄县地主所开办的小煤窑,一部分人乐于和握有政治、经济大权的官僚和商人合作。于是就出现了以戴华藻为总办,由官僚、商人和地主集资合办的峄县中兴矿局。发起筹办中兴矿局的,是峄县人金铭和李朝相。他们都是当地的绅士,与崔、宋、黄、梁、田、王等家统称“峄县八大家族”。他们“以枣庄煤矿质佳,而自咸丰初年大乱后,本地财力困乏,无人开采,大窑弃之可惜,因与济宁州人直隶东明知县米协麟筹议兴办。米协麟与直隶候补知县戴华藻协商议妥”,招股集资筹划办理。
戴华藻,号心斋,安徽寿县人,系直隶候补知县,其堂弟戴宗骞是淮军的统领,因而与李鸿章有些关系。为了寻求靠山,他们便把筹备峄县中兴炭矿的情况稟告了当时任直隶总督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而李鸿章此时正在各地兴建军火工业,对煤炭非常需要,所以一拍即合,当即奏派米协麟和戴华藻来枣庄设立中兴矿局,用土法开办煤窑。
戴华藻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遂于光绪五年(1879年)春,正式立官窑总局。由于“事属创始,一切炭局章程,皆手自厘订”。后来,戴华藻补授了直隶望都知县,矿局总办便改为他的堂弟、从九品戴睿藻。筹划开办峄县矿局的除戴华藻外,还有地方官员王筱云(道员)、黄佩兰(道员)、朱采(知府)以及当地的绅士李伟、王曰智等数十家。他们被呈准开办后,虽然名义上也是“官督商办”,但声明“不领官本”,全部由私人投资。.初创时,仅集资白银2.5万两,这个数目在当时新兴办的采煤业中算是少的。而和它差不多同时创办的开平矿局最初资金却有80万两,比它创办稍晚的徐州利国驿煤矿,其资本有1〇万两。由于资金不足,因而中兴煤矿无力采用先进机器设备,不得不依旧沿用简陋的土法开采。而枣庄矿区经过数百年的连续开采,离地面较近的煤层已被挖掘殆尽,要大量生产煤炭,中兴矿局就必须开掘三四十丈乃至五六十丈的深井。可是,矿井加深,井内积水也就大量增加,再用滑车、牛皮包那样落后的工具戽水,是很难奏效的,因而必须添购动力较大的新式排水设备,也就必须扩大资本。光绪七年至光绪八年间(1881〜1882年),戴华藻为了进一步筹集资金,便通过他的堂弟戴宗骞先后函请湖南提督周盛波、通永镇总兵贾起胜、直隶候补道张莲芬以及江苏补用同知陈德浚等一批清政府官僚帮助集股。贾、张、戴等“共招寅友集凑股本白银5万余两;江苏同知陈丞(德浚)先后亦集有款(万金),俾资接济”。从此,矿局遂有南、北股之分。南股的代表人物陈德浚并被委任为矿局的转运委员,掌握了煤炭运销、器材采购等方面的实权。
有了资本之后,又因李鸿章的关系,中兴矿局得到了天津制造局道员王德均的协助,陆续订购汲水机器4架,并从广东、上海等地雇请技师和技术工人从事操作,局面逐渐好转。
中兴矿局先后共开了12个小窑,因为没能排干矿井积水,《峄县志》记载:枣庄煤质“质色尤佳”。在其创办的前3年间(1878〜1880年),始终未能产煤。有了新式排水设备以后,因为“法捷费省”,“一日而得数十日之功,一人而兼数十人之用”,工程进度大大加快,使得“一县长老皆惊以为自有炭窑所未闻也”。矿井积水排干后,于1882年2月开始见煤,到9月间,已能日产120余吨。由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非常需要煤炭,再加上峄煤“质色并佳,远近争先购用,运到天津、金陵制造局烧试,较日本上等煤尤佳,与英国松白相仿”,故而中兴矿局所产的煤销路很好。光绪九年(1883年)7月13日,李鸿章又向清政府奏准,峄县中兴矿局所产煤炭,仿照“台湾、开平、湖北等处开煤奏准成案,每吨交出口正税银一钱。各省兵商轮船机器制造局用煤,准其一律免税。完税之后,经过常关,应准呈验税单放行,运煤船只完纳船钞,免征船料。如此,则与各处矿局既免分歧,亦可收畅运之效”(《李文忠公奏稿》卷47,第11页)。清政府这一措施,使中兴矿局所产煤炭更加畅销。当时峄县境内,专门为它推销产品的商贩即有30余家。煤炭出井之后,商贩争相抢购。矿局恐怕酿成事端,就与他们订立合同,先期付款、排号,按号供煤,这些商贩从矿局得到煤炭后,便“择利而趋,到处行销”,其中很大一部分经过运河远销于长江沿岸,“售与轮船和机局”。1887年9月17日的《捷报》报道说:“山东峄县的煤矿甚为活跃,很多的大沙船装载上等的煤炭运往清江浦。”可见当时其声势之盛。
光绪九年(1883年),中兴矿局计划扩大规模,在上海公开招股,拟募集股本凑足10万两。不料恰逢上海金融恐慌,扩充股本、添购机器的计划未能实现。中兴矿局在生产组织和经营管理方面,基本上仍是沿袭地主小窑的制度,即所谓“用民窑之制,而以官法行之”。如设立班头、筐头,强拉农民下井等等。矿局最初只有工人数百人,以后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工人数目陆续增加。中兴矿局把这些工人分为“正掘班”和“公令班”两类。“正掘班”即长工,每两人为一组,先预支给工资制钱20吊至30吊不等,每人每日伙食制钱1〇〇文,挖出之煤按量计算,每斛(150斤)给制钱45文。“公令班”是按日计工,每日轮班替换。他们不仅在工作上没有 “正掘班”那样稳定,而且在待遇上和“正掘班”也有差别。他们没有预付工资,只是每人每日给制钱2〇〇文,挖掘一斛也给制钱45文。此外,矿局还有一部分抬筐与拉滑车的杂工,他们也属于按日计工,每人每日给制钱140文。
中兴矿局之所以要把工人分为上述两类,这是因为:一,可以根据不同时斯的生产需要(如季节的旺、淡),毫无顾忌地把一部分“公令班”工人招之来、挥之去。即使在工人来源缺乏时,他们仍然牢牢地控制着“正掘班”工人,使生产不致陷于停顿。二,这样做可以在工人中划分界限,长短工中自然产生了隔阂,不能团结一心,以便于他们控制工人。同时,对“公令班” 工人的报酬采用零开碎付的办法,使工人日进日销、身无余钱, 这样矿局更便于把工人掌握在自己手中,牢牢地拴在自己的井架上(据朱采:光绪八年《禀丁宫保论峄县煤矿地方官禀陈失实》)。后来,矿局把工人划分为“里工”和“外工”,但实际上还是这种“正掘班”和“公令班”制度的延续。
由于中兴矿局的主持者还不懂得“专利”的有关条款,所以不像后来中兴煤矿公司那样明确划定矿界。正如《峄县志》 .中所说“虽以官名,而邑旧采煤者争相慕效,远近分立,皆任其自为”。所以官局和地主小窑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和纠纷,其中突出的表现就是互相诱骗对方的工人。双方斗争相当激烈,有时官司一直打到山东巡抚部院。
峄县中兴矿局虽然是一座小型的商办煤矿,但仍受着封建官僚势力的干扰。起初,李鸿章企图通过山东巡抚处理,稍后,山东巡抚又在经济上要求“抽厘”报效。对此,矿局主持者只好尽力应付。表面上不能不答应官方指派会办的到来,但将其职权尽可能限制在“弹压事宜”上,即管理煤矿工人和应付地方事务,而不允许过问矿务。同时又请求以“助饷”代替“抽厘”。因为,从矿局主持者看来,“盖抽厘以见煤之日为始,而助饷则必须成本已敷,然后斟酌捐助”。他们在力求避免官府的干扰,设法减轻自己的负担。
相关机构
枣庄市中兴矿局
相关机构
相关地名
枣庄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