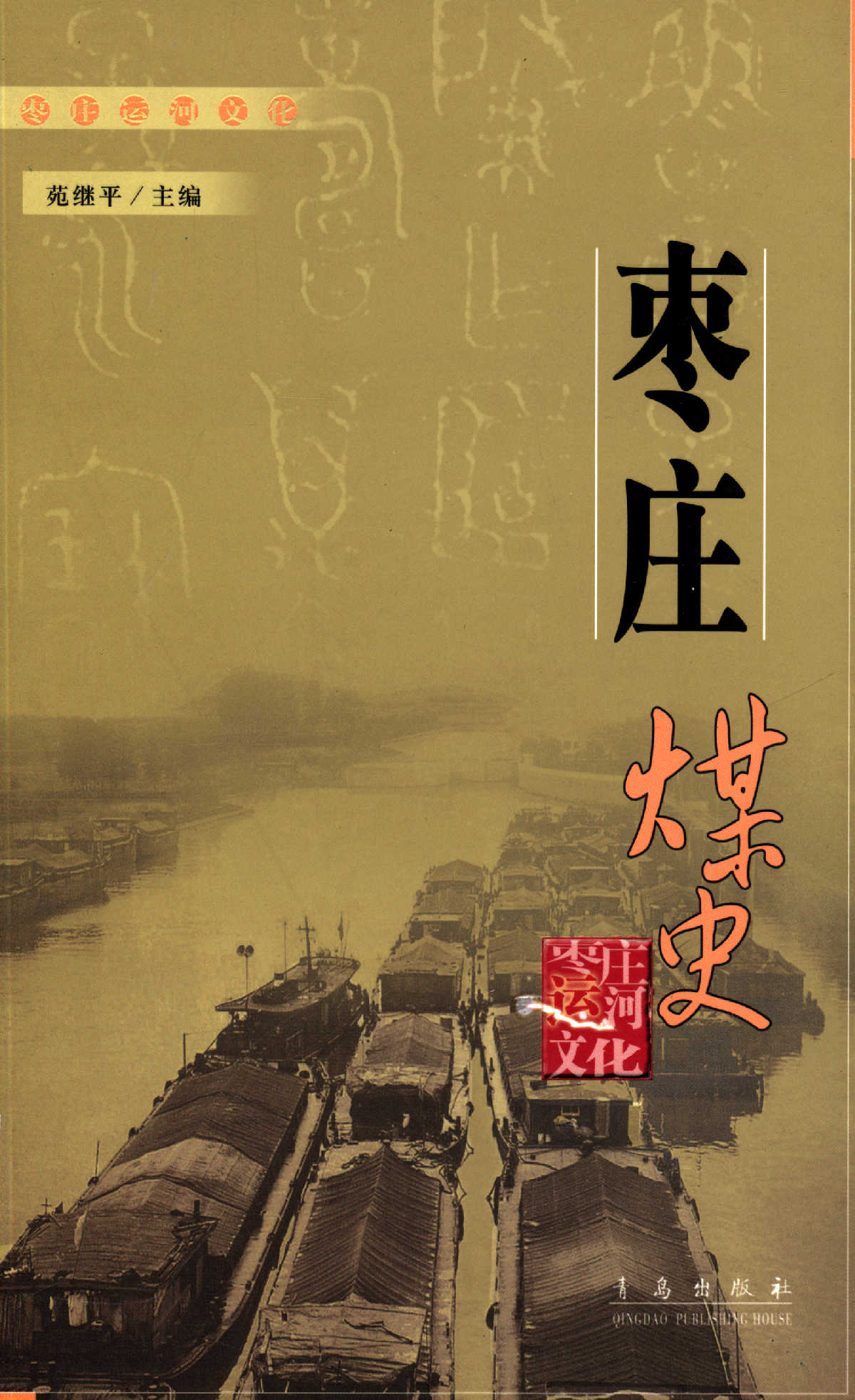内容
清代“任其采取,输税于官”的政策促进了煤矿事业的发展,峄县境内煤窑大增,煤炭运输出现了繁荣景象。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陆续产生了一批近代工业。各种近代工业的兴办,需要更多的煤炭来做燃料。当时各口岸虽然都有“洋煤”进口,但供不应求;由于煤炭缺乏,进口洋煤往往故意囤积居奇,造成煤价上涨。因此,山东及其他地方的一些官僚和富商,对储量丰富、煤质优良的枣庄煤田便格外关注。当时,峄县地主所开办的小煤窑,一部分人乐于和握有政治、经济大权的官僚和商人合作。于是就出现了以戴华藻为总办,由官僚、商人和地主集资合办的峄县中兴矿局。发起筹办中兴矿局的,是峄县人金铭和李朝相。他们都是当地的绅士,与崔、宋、黄、梁、田、王等家统称“峄县八大家族”。他们“以枣庄煤矿质佳,而自咸丰初年大乱后,本地财力困乏,无人开采,大窑弃之可惜,因与济宁州人直隶东明知县米协麟筹议兴办。米协麟与直隶候补知县戴华藻协商议妥”,招股集资筹划办理。
戴华藻,号心斋,安徽寿县人,系直隶候补知县,其堂弟戴宗骞是淮军的统领,因而与李鸿章有些关系。为了寻求靠山,他们便把筹备峄县中兴炭矿的情况稟告了当时任直隶总督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而李鸿章此时正在各地兴建军火工业,对煤炭非常需要,所以一拍即合,当即奏派米协麟和戴华藻来枣庄设立中兴矿局,用土法开办煤窑。
戴华藻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遂于光绪五年(1879年)春,正式立官窑总局。由于“事属创始,一切炭局章程,皆手自厘订”。后来,戴华藻补授了直隶望都知县,矿局总办便改为他的堂弟、从九品戴睿藻。筹划开办峄县矿局的除戴华藻外,还有地方官员王筱云(道员)、黄佩兰(道员)、朱采(知府)以及当地的绅士李伟、王曰智等数十家。他们被呈准开办后,虽然名义上也是“官督商办”,但声明“不领官本”,全部由私人投资。.初创时,仅集资白银2.5万两,这个数目在当时新兴办的采煤业中算是少的。而和它差不多同时创办的开平矿局最初资金却有80万两,比它创办稍晚的徐州利国驿煤矿,其资本有1〇万两。由于资金不足,因而中兴煤矿无力采用先进机器设备,不得不依旧沿用简陋的土法开采。而枣庄矿区经过数百年的连续开采,离地面较近的煤层已被挖掘殆尽,要大量生产煤炭,中兴矿局就必须开掘三四十丈乃至五六十丈的深井。可是,矿井加深,井内积水也就大量增加,再用滑车、牛皮包那样落后的工具戽水,是很难奏效的,因而必须添购动力较大的新式排水设备,也就必须扩大资本。光绪七年至光绪八年间(1881〜1882年),戴华藻为了进一步筹集资金,便通过他的堂弟戴宗骞先后函请湖南提督周盛波、通永镇总兵贾起胜、直隶候补道张莲芬以及江苏补用同知陈德浚等一批清政府官僚帮助集股。贾、张、戴等“共招寅友集凑股本白银5万余两;江苏同知陈丞(德浚)先后亦集有款(万金),俾资接济”。从此,矿局遂有南、北股之分。南股的代表人物陈德浚并被委任为矿局的转运委员,掌握了煤炭运销、器材采购等方面的实权。
有了资本之后,又因李鸿章的关系,中兴矿局得到了天津制造局道员王德均的协助,陆续订购汲水机器4架,并从广东、上海等地雇请技师和技术工人从事操作,局面逐渐好转。
中兴矿局先后共开了12个小窑,因为没能排干矿井积水,《峄县志》记载:枣庄煤质“质色尤佳”。在其创办的前3年间(1878〜1880年),始终未能产煤。有了新式排水设备以后,因为“法捷费省”,“一日而得数十日之功,一人而兼数十人之用”,工程进度大大加快,使得“一县长老皆惊以为自有炭窑所未闻也”。矿井积水排干后,于1882年2月开始见煤,到9月间,已能日产120余吨。由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非常需要煤炭,再加上峄煤“质色并佳,远近争先购用,运到天津、金陵制造局烧试,较日本上等煤尤佳,与英国松白相仿”,故而中兴矿局所产的煤销路很好。光绪九年(1883年)7月13日,李鸿章又向清政府奏准,峄县中兴矿局所产煤炭,仿照“台湾、开平、湖北等处开煤奏准成案,每吨交出口正税银一钱。各省兵商轮船机器制造局用煤,准其一律免税。完税之后,经过常关,应准呈验税单放行,运煤船只完纳船钞,免征船料。如此,则与各处矿局既免分歧,亦可收畅运之效”(《李文忠公奏稿》卷47,第11页)。清政府这一措施,使中兴矿局所产煤炭更加畅销。当时峄县境内,专门为它推销产品的商贩即有30余家。煤炭出井之后,商贩争相抢购。矿局恐怕酿成事端,就与他们订立合同,先期付款、排号,按号供煤,这些商贩从矿局得到煤炭后,便“择利而趋,到处行销”,其中很大一部分经过运河远销于长江沿岸,“售与轮船和机局”。1887年9月17日的《捷报》报道说:“山东峄县的煤矿甚为活跃,很多的大沙船装载上等的煤炭运往清江浦。”可见当时其声势之盛。
光绪九年(1883年),中兴矿局计划扩大规模,在上海公开招股,拟募集股本凑足10万两。不料恰逢上海金融恐慌,扩充股本、添购机器的计划未能实现。中兴矿局在生产组织和经营管理方面,基本上仍是沿袭地主小窑的制度,即所谓“用民窑之制,而以官法行之”。如设立班头、筐头,强拉农民下井等等。矿局最初只有工人数百人,以后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工人数目陆续增加。中兴矿局把这些工人分为“正掘班”和“公令班”两类。“正掘班”即长工,每两人为一组,先预支给工资制钱20吊至30吊不等,每人每日伙食制钱1〇〇文,挖出之煤按量计算,每斛(150斤)给制钱45文。“公令班”是按日计工,每日轮班替换。他们不仅在工作上没有 “正掘班”那样稳定,而且在待遇上和“正掘班”也有差别。他们没有预付工资,只是每人每日给制钱2〇〇文,挖掘一斛也给制钱45文。此外,矿局还有一部分抬筐与拉滑车的杂工,他们也属于按日计工,每人每日给制钱140文。
中兴矿局之所以要把工人分为上述两类,这是因为:一,可以根据不同时斯的生产需要(如季节的旺、淡),毫无顾忌地把一部分“公令班”工人招之来、挥之去。即使在工人来源缺乏时,他们仍然牢牢地控制着“正掘班”工人,使生产不致陷于停顿。二,这样做可以在工人中划分界限,长短工中自然产生了隔阂,不能团结一心,以便于他们控制工人。同时,对“公令班” 工人的报酬采用零开碎付的办法,使工人日进日销、身无余钱, 这样矿局更便于把工人掌握在自己手中,牢牢地拴在自己的井架上(据朱采:光绪八年《禀丁宫保论峄县煤矿地方官禀陈失实》)。后来,矿局把工人划分为“里工”和“外工”,但实际上还是这种“正掘班”和“公令班”制度的延续。
由于中兴矿局的主持者还不懂得“专利”的有关条款,所以不像后来中兴煤矿公司那样明确划定矿界。正如《峄县志》 .中所说“虽以官名,而邑旧采煤者争相慕效,远近分立,皆任其自为”。所以官局和地主小窑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和纠纷,其中突出的表现就是互相诱骗对方的工人。双方斗争相当激烈,有时官司一直打到山东巡抚部院。
峄县中兴矿局虽然是一座小型的商办煤矿,但仍受着封建官僚势力的干扰。起初,李鸿章企图通过山东巡抚处理,稍后,山东巡抚又在经济上要求“抽厘”报效。对此,矿局主持者只好尽力应付。表面上不能不答应官方指派会办的到来,但将其职权尽可能限制在“弹压事宜”上,即管理煤矿工人和应付地方事务,而不允许过问矿务。同时又请求以“助饷”代替“抽厘”。因为,从矿局主持者看来,“盖抽厘以见煤之日为始,而助饷则必须成本已敷,然后斟酌捐助”。他们在力求避免官府的干扰,设法减轻自己的负担。
枣庄矿工与山东工人阶级的形成山东是我国近代工业比较集中、工人运动开展比较早的地区之一。特别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山东工人运动,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鸦片战争之后,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相继侵人中国,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从19世纪60年代起,开展了以兴办军火工业为主的洋务运动。1858年,中英签订《天津条约》,登州(烟台)被列为 •通商口岸之一;1872年,德在烟台设立了蛋粉厂,又成立了烟台缫丝局,德M家大银行组成“德华银行”,在山东修铁路、建码头、开金矿等。这是山东工人阶级形成的第一个基点(《山东工运史资料》1982年第5期)。
此间,清政府推行洋务运动,在山东济南泺口创立了 “山东机器局”,兴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开办了铅矿和金矿,工人过千人,这是山东工人阶级形成的第二个基点。
山东民族资本家随之兴办了近代工业,在当时中国最大的私营采煤企业枣庄中兴矿局,工人已达4000余人;爱国华侨张弼士创办了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雇佣工人1000余人。这是山东工人阶级形成的第三个基点,也是工人人数最多的企业 (《山东工运史资料》1982年第5期第2页)。
1875年(光绪元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奏请批准,在济南泺口创设了山东机器局(即新城兵工厂),先后从美国、德国购进新式机器,生产枪支弹药(《山东工运史资料》1982年第5期第2页)。1878年,李鸿章奏派东明知县米协麟和候补知县戴华藻等,在枣庄创办了中兴矿局(《枣庄煤矿史》第6页)。随着工业的发展,矿工人数增至3000人,已成为山东工人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不完全统计,到1910年辛亥革命前夕,山东有大、中型企业88家,产业工人约30000余人,山东工人阶级队伍迅速扩大。特别是近代工业中的产业工人是革命最彻底、最有组织、纪律性最强的阶级队伍,是社会大生产的承担者和体现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山东特殊的地理、政治、经济因素,加之马列主义的传入,使枣庄工人真正成为一支稳定的工人阶级队伍。
中兴矿局的生产规模和用工峄县中兴矿局由于资金不足,开创之初,挖了12座小井,由于未能排干矿井积水,在前三年(1879〜1881年)内未能产煤,有了新式水设备之后,工程进度也大大加快,很快排干了矿井积水,1882年2月就开始产煤,到9月间,已能日产120余吨,以后逐年有所增加。当时,峄县境内专门为它推销产品的商贩争相抢购,订立合同,运销于长江沿岸,“售于轮船和机局” (光绪八年,朱采《峄县地方官禀陈失实》)。中兴矿局所用工人,没有固定数字,完全视生产的兴衰而定。最初只有夫工数百人,后来逐渐增多。在其全盛时期,用工当在4000人左右。
光绪八年(1882年)春间,知府朱采在《禀丁宫保论峄县煤矿地方宫禀陈失实》一文中,对矿局的用工情况,有这样一段记载:“卑职初到峄境察访时,有崔姓煤窑一座,所用夫工上下仅2〇〇余人,其用工亦不过千人。”“现卑局机器只能抽出深水,其他工作皆用土人(按:指峄县枣庄一带当地居民)。比起来矿井较多,施力较大,核之土窑所用人夫,不翅倍蓰。……(由于)官窑佣值重而程课宽,民夫多乐就者,土窑夫工日形不足。假令官窑停止,此等寻常土窑能筹巨款接办税收,不但窑户不能,即豪民亦不能。”如此,则“无业穷民”,又当“立即拷腹”了。
另外,李鸿章在光绪九年(1883年)7月13日的《峄县开矿片》一文中也说:“该处地瘠民贫,自矿局日有起色,赖以生活者数千家。”光绪八至九年间,中兴矿局刚刚投产不久,用工人数即如此之多,故推断其在“煤斤旺出”之际,矿局工人总数均为三四千人,恐怕也不能算是夸大了。
至于这些矿工的来源,上面几段文字基本上作了交待,除了操纵机器的所谓“技师”和“机匠”等,是由上海、广东等地雇用的以外,其余井下采煤、运搬等工种所用工人(即所谓“煤夫”),绝大多数都来自附近农村。后来,也有少数来自莱芜和新泰两县。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中兴煤矿公司接办初期,基本上也没有多大变化。
大运河与枣庄煤炭运销枣庄地处山东南部,距运河40公里,漕运可达江苏、安徽等长江沿岸诸省,正如《峄县志》所述,“北跨琅琊,南控江淮”,交通方便。台枣铁路未修前,枣庄到运河码头——台儿庄,每天皆以牛车踯躅其间,多达一、二百辆,颇极一时之盛。但是,仅“资民车拉运,车少费重,常年载运无多,……虽煤质优佳,销运不广”。1882年,枣庄共有小煤井10多座,最高日产120余筐,除部分当地散销外,大部分通过运河民船运销于上下游。济宁是当时煤炭集中销售地,经营商铺近70家。在枣庄境内推销煤炭舍商家也有30余户。
19世纪末,上海月耗煤量1300多吨,主要来至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只有很少数量是中国土窑生产的煤炭。由于外煤的送输远涉重洋,煤价十分高昂,当时英国煤每吨售价银11两,澳大利亚吨煤价8两,日本煤质低劣,每吨5.5两。当时,用京西煤价每吨2.5两,但需牛车辗转天津,再到上海,煤价增到12两(张国辉著《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煤炭一时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特需燃料。李鸿章向清朝政府奏准,中兴矿局生产的煤炭,每吨只交出口正税一钱银子,就可运销各地,不再交纳其他税金。而售予各省兵商轮船和机械制造局的用煤,一律免税。这给枣庄地区的售煤创造了极好的发展机会。此间,中兴矿局煤炭产量已达8.5万筐,在运河沿岸建立了销煤机构和码头,使煤炭由船运到各地, 枣庄境内呈现出人拉骡驮,连樯北上,船运南下的繁荣景象,给枣庄煤炭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为煤炭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半截筒子小窑发生矿难由于在生产技术上,中兴矿局除了购置几架抽水机器外,其他方面仍然墨守成规、率由旧章,再加上矿井大大延伸,因而劳动条件更加恶劣,井下的伤亡事故日益增多。尤其是矿区经过数百年的自由开采,废弃古井到处都是,里面积水很多,一旦打透,就会造成惨重的水灾。光绪十九年(1893年)6月14日早班,半截筒子小窑发生了一次极为惨重的特大水灾。当时窑内水势很汹,在井下工作的人们乱成一团,都拥挤到窑口,紧紧抓住拉煤的绳子向上攀爬,因人太多,把绳子都拉断了。而矿局资方代表没有采取积极营救措施,结果全窑100多名矿工都被淹死在井下。
灾难的发生,激起了广大矿工和当地人民群众的愤怒。枣庄、齐村、郭里集一带的群众,聚集了1000多人,抬着土炮之类的武器来围攻矿局。后来,由于峄县知县派兵镇压,人们被迫散去。同时,矿局又给予死难工人的家属抚恤金(每人200吊钱)。在威逼利诱下,群众忍气吞声,负屈了事。
大坟子中兴矿局遭封禁半截筒子小窑矿难发生后,直隶总督以戴睿藻等办理不善将其撤差,另外饬派峄矿转运委员江苏补用同知陈德浚为经理。陈德浚又因有淞沪厘局差务,不容分身,便禀请派委候补道陈宝荣接办。于是,矿局的经营管理大权便由北股转移到了南股手里。陈德凌、陈宝荣等经营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矿局营业情况有了一些好转,获利甚厚,结果引起了南北股之间矛盾的激化,连《峄县志》也为之说法有异:“洎戴君以事归里,陈司马德渙继之,萧规曹随,不烦丝粟之力,而炭矿大出,遂致资百余万。前之人劳而不蒙其福,后之人安而得食其报,岂天道果有如是者耶?”实际上,自半截筒子小窑发生矿难以后,中兴矿局的营业便逐渐衰落下来。其衰落的主要原因一是资金不足,无力进一步扩充生产和运销设备以降低成本,因此,很难和当时进口的洋煤以及资金较大的开平等煤矿竞销,更经不住这次特大矿难的打击;二是矿局内部南北股之间矛盾日益尖锐,而掌管经营大权的官僚又腐败无能,贪污私吞,最后竟除了4架抽水机器和局房外,所有股本亏耗净尽。就在这四面楚歌的困境中,恰好碰上山东巡抚李k衡在全省封禁矿井。
李秉衡于光绪二H年11月11日(1896年1月4日)上了一个奏折,内称:“山东历办矿务并无成效……开矿所用,率多扩焊无赖之人。方其开也,藏亡纳叛,奸宄日滋,及其停也,大慝巨凶,无业无家,尤虑铤而走险。方今威海所驻倭兵已七八千人,深恐此种不逞之徒,散无可归,因而起衅,为患不堪设想。”清廷批示:“著照所请,户部知道。”于是,山东沿海矿业便悉遭封禁了。此事虽与峄县中兴矿局本无直接关系,但陈德浚等看到矿局营业不振,原就打算早日抽出资金,此时也不和北股贾起胜等商量,便趁机请求撤局,连账目都未清理,就急忙宣布停办了。而所有抽水机器均未运走,悉数封存于枣庄的机房内〇中兴矿局关闭后,南北股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更加尖锐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6月间,陈德浚又私自将机器大小4件租与济宁州绅士米汝厚等在枣庄附近开挖民窑使用,这一来更使南北双方的冲突表面化。北股股东通永镇总兵贾起胜致函峄县知县说,机器系伊等购置,现已出租,令伊戚戴幼珍 (即戴绪盛)去峄经营。峄县知县只好两不开罪,便以未咨明 “宪台”为由,双方均不准动用。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7月,陈德後又派江苏候补知县虞廷翰来峄,强行启封,将机器交付米汝厚等收用。而贾起胜派来的戴绪盛又力请禁止,双方越闹越僵。虞廷翰不问米汝厚能否开窑,只管交付机器,戴绪盛也不问其交收后能用与否,只管阻挠。双方气势汹汹。峄县知县赓勋左右为难,采取了两个措施:一、他以机器系北洋之物,地方宫不便过问为由,不公开禁止虞廷翰出租机器,却派人在枣庄附近张贴告示,严禁绅民开窑。这样既然不准开窑,机器将焉用之?自然也就出租不成了。二、禀请山东巡抚转咨北洋大臣,提出“官窑既已停歇,机器即应随时移去,不当仍留峄境……深恐滋生事故”;且“机器件数颇多,价亦甚贵”,地方保管甚难,同时局房地基从前按年给租,但“自上年撤局后,至今分文不给,业主讵肯甘心?目前虽暂隐忍,日后终必与争”,因此请求北洋大臣命令矿局移去机器,拆毁局房,将地基归还原主。
直隶总督兼王文韶接此禀帖后,便札委通永镇总兵贾起胜,会同办理津榆铁轨公司直隶候补道张莲芬前往查办。最后账目未及清理,所有汲水机器和笨重器材,封存于枣庄局机房。轰动一时的峄县中兴矿局(官窑矿局),就此结束。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陆续产生了一批近代工业。各种近代工业的兴办,需要更多的煤炭来做燃料。当时各口岸虽然都有“洋煤”进口,但供不应求;由于煤炭缺乏,进口洋煤往往故意囤积居奇,造成煤价上涨。因此,山东及其他地方的一些官僚和富商,对储量丰富、煤质优良的枣庄煤田便格外关注。当时,峄县地主所开办的小煤窑,一部分人乐于和握有政治、经济大权的官僚和商人合作。于是就出现了以戴华藻为总办,由官僚、商人和地主集资合办的峄县中兴矿局。发起筹办中兴矿局的,是峄县人金铭和李朝相。他们都是当地的绅士,与崔、宋、黄、梁、田、王等家统称“峄县八大家族”。他们“以枣庄煤矿质佳,而自咸丰初年大乱后,本地财力困乏,无人开采,大窑弃之可惜,因与济宁州人直隶东明知县米协麟筹议兴办。米协麟与直隶候补知县戴华藻协商议妥”,招股集资筹划办理。
戴华藻,号心斋,安徽寿县人,系直隶候补知县,其堂弟戴宗骞是淮军的统领,因而与李鸿章有些关系。为了寻求靠山,他们便把筹备峄县中兴炭矿的情况稟告了当时任直隶总督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而李鸿章此时正在各地兴建军火工业,对煤炭非常需要,所以一拍即合,当即奏派米协麟和戴华藻来枣庄设立中兴矿局,用土法开办煤窑。
戴华藻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遂于光绪五年(1879年)春,正式立官窑总局。由于“事属创始,一切炭局章程,皆手自厘订”。后来,戴华藻补授了直隶望都知县,矿局总办便改为他的堂弟、从九品戴睿藻。筹划开办峄县矿局的除戴华藻外,还有地方官员王筱云(道员)、黄佩兰(道员)、朱采(知府)以及当地的绅士李伟、王曰智等数十家。他们被呈准开办后,虽然名义上也是“官督商办”,但声明“不领官本”,全部由私人投资。.初创时,仅集资白银2.5万两,这个数目在当时新兴办的采煤业中算是少的。而和它差不多同时创办的开平矿局最初资金却有80万两,比它创办稍晚的徐州利国驿煤矿,其资本有1〇万两。由于资金不足,因而中兴煤矿无力采用先进机器设备,不得不依旧沿用简陋的土法开采。而枣庄矿区经过数百年的连续开采,离地面较近的煤层已被挖掘殆尽,要大量生产煤炭,中兴矿局就必须开掘三四十丈乃至五六十丈的深井。可是,矿井加深,井内积水也就大量增加,再用滑车、牛皮包那样落后的工具戽水,是很难奏效的,因而必须添购动力较大的新式排水设备,也就必须扩大资本。光绪七年至光绪八年间(1881〜1882年),戴华藻为了进一步筹集资金,便通过他的堂弟戴宗骞先后函请湖南提督周盛波、通永镇总兵贾起胜、直隶候补道张莲芬以及江苏补用同知陈德浚等一批清政府官僚帮助集股。贾、张、戴等“共招寅友集凑股本白银5万余两;江苏同知陈丞(德浚)先后亦集有款(万金),俾资接济”。从此,矿局遂有南、北股之分。南股的代表人物陈德浚并被委任为矿局的转运委员,掌握了煤炭运销、器材采购等方面的实权。
有了资本之后,又因李鸿章的关系,中兴矿局得到了天津制造局道员王德均的协助,陆续订购汲水机器4架,并从广东、上海等地雇请技师和技术工人从事操作,局面逐渐好转。
中兴矿局先后共开了12个小窑,因为没能排干矿井积水,《峄县志》记载:枣庄煤质“质色尤佳”。在其创办的前3年间(1878〜1880年),始终未能产煤。有了新式排水设备以后,因为“法捷费省”,“一日而得数十日之功,一人而兼数十人之用”,工程进度大大加快,使得“一县长老皆惊以为自有炭窑所未闻也”。矿井积水排干后,于1882年2月开始见煤,到9月间,已能日产120余吨。由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非常需要煤炭,再加上峄煤“质色并佳,远近争先购用,运到天津、金陵制造局烧试,较日本上等煤尤佳,与英国松白相仿”,故而中兴矿局所产的煤销路很好。光绪九年(1883年)7月13日,李鸿章又向清政府奏准,峄县中兴矿局所产煤炭,仿照“台湾、开平、湖北等处开煤奏准成案,每吨交出口正税银一钱。各省兵商轮船机器制造局用煤,准其一律免税。完税之后,经过常关,应准呈验税单放行,运煤船只完纳船钞,免征船料。如此,则与各处矿局既免分歧,亦可收畅运之效”(《李文忠公奏稿》卷47,第11页)。清政府这一措施,使中兴矿局所产煤炭更加畅销。当时峄县境内,专门为它推销产品的商贩即有30余家。煤炭出井之后,商贩争相抢购。矿局恐怕酿成事端,就与他们订立合同,先期付款、排号,按号供煤,这些商贩从矿局得到煤炭后,便“择利而趋,到处行销”,其中很大一部分经过运河远销于长江沿岸,“售与轮船和机局”。1887年9月17日的《捷报》报道说:“山东峄县的煤矿甚为活跃,很多的大沙船装载上等的煤炭运往清江浦。”可见当时其声势之盛。
光绪九年(1883年),中兴矿局计划扩大规模,在上海公开招股,拟募集股本凑足10万两。不料恰逢上海金融恐慌,扩充股本、添购机器的计划未能实现。中兴矿局在生产组织和经营管理方面,基本上仍是沿袭地主小窑的制度,即所谓“用民窑之制,而以官法行之”。如设立班头、筐头,强拉农民下井等等。矿局最初只有工人数百人,以后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工人数目陆续增加。中兴矿局把这些工人分为“正掘班”和“公令班”两类。“正掘班”即长工,每两人为一组,先预支给工资制钱20吊至30吊不等,每人每日伙食制钱1〇〇文,挖出之煤按量计算,每斛(150斤)给制钱45文。“公令班”是按日计工,每日轮班替换。他们不仅在工作上没有 “正掘班”那样稳定,而且在待遇上和“正掘班”也有差别。他们没有预付工资,只是每人每日给制钱2〇〇文,挖掘一斛也给制钱45文。此外,矿局还有一部分抬筐与拉滑车的杂工,他们也属于按日计工,每人每日给制钱140文。
中兴矿局之所以要把工人分为上述两类,这是因为:一,可以根据不同时斯的生产需要(如季节的旺、淡),毫无顾忌地把一部分“公令班”工人招之来、挥之去。即使在工人来源缺乏时,他们仍然牢牢地控制着“正掘班”工人,使生产不致陷于停顿。二,这样做可以在工人中划分界限,长短工中自然产生了隔阂,不能团结一心,以便于他们控制工人。同时,对“公令班” 工人的报酬采用零开碎付的办法,使工人日进日销、身无余钱, 这样矿局更便于把工人掌握在自己手中,牢牢地拴在自己的井架上(据朱采:光绪八年《禀丁宫保论峄县煤矿地方官禀陈失实》)。后来,矿局把工人划分为“里工”和“外工”,但实际上还是这种“正掘班”和“公令班”制度的延续。
由于中兴矿局的主持者还不懂得“专利”的有关条款,所以不像后来中兴煤矿公司那样明确划定矿界。正如《峄县志》 .中所说“虽以官名,而邑旧采煤者争相慕效,远近分立,皆任其自为”。所以官局和地主小窑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和纠纷,其中突出的表现就是互相诱骗对方的工人。双方斗争相当激烈,有时官司一直打到山东巡抚部院。
峄县中兴矿局虽然是一座小型的商办煤矿,但仍受着封建官僚势力的干扰。起初,李鸿章企图通过山东巡抚处理,稍后,山东巡抚又在经济上要求“抽厘”报效。对此,矿局主持者只好尽力应付。表面上不能不答应官方指派会办的到来,但将其职权尽可能限制在“弹压事宜”上,即管理煤矿工人和应付地方事务,而不允许过问矿务。同时又请求以“助饷”代替“抽厘”。因为,从矿局主持者看来,“盖抽厘以见煤之日为始,而助饷则必须成本已敷,然后斟酌捐助”。他们在力求避免官府的干扰,设法减轻自己的负担。
枣庄矿工与山东工人阶级的形成山东是我国近代工业比较集中、工人运动开展比较早的地区之一。特别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山东工人运动,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鸦片战争之后,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相继侵人中国,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从19世纪60年代起,开展了以兴办军火工业为主的洋务运动。1858年,中英签订《天津条约》,登州(烟台)被列为 •通商口岸之一;1872年,德在烟台设立了蛋粉厂,又成立了烟台缫丝局,德M家大银行组成“德华银行”,在山东修铁路、建码头、开金矿等。这是山东工人阶级形成的第一个基点(《山东工运史资料》1982年第5期)。
此间,清政府推行洋务运动,在山东济南泺口创立了 “山东机器局”,兴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开办了铅矿和金矿,工人过千人,这是山东工人阶级形成的第二个基点。
山东民族资本家随之兴办了近代工业,在当时中国最大的私营采煤企业枣庄中兴矿局,工人已达4000余人;爱国华侨张弼士创办了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雇佣工人1000余人。这是山东工人阶级形成的第三个基点,也是工人人数最多的企业 (《山东工运史资料》1982年第5期第2页)。
1875年(光绪元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奏请批准,在济南泺口创设了山东机器局(即新城兵工厂),先后从美国、德国购进新式机器,生产枪支弹药(《山东工运史资料》1982年第5期第2页)。1878年,李鸿章奏派东明知县米协麟和候补知县戴华藻等,在枣庄创办了中兴矿局(《枣庄煤矿史》第6页)。随着工业的发展,矿工人数增至3000人,已成为山东工人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不完全统计,到1910年辛亥革命前夕,山东有大、中型企业88家,产业工人约30000余人,山东工人阶级队伍迅速扩大。特别是近代工业中的产业工人是革命最彻底、最有组织、纪律性最强的阶级队伍,是社会大生产的承担者和体现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山东特殊的地理、政治、经济因素,加之马列主义的传入,使枣庄工人真正成为一支稳定的工人阶级队伍。
中兴矿局的生产规模和用工峄县中兴矿局由于资金不足,开创之初,挖了12座小井,由于未能排干矿井积水,在前三年(1879〜1881年)内未能产煤,有了新式水设备之后,工程进度也大大加快,很快排干了矿井积水,1882年2月就开始产煤,到9月间,已能日产120余吨,以后逐年有所增加。当时,峄县境内专门为它推销产品的商贩争相抢购,订立合同,运销于长江沿岸,“售于轮船和机局” (光绪八年,朱采《峄县地方官禀陈失实》)。中兴矿局所用工人,没有固定数字,完全视生产的兴衰而定。最初只有夫工数百人,后来逐渐增多。在其全盛时期,用工当在4000人左右。
光绪八年(1882年)春间,知府朱采在《禀丁宫保论峄县煤矿地方宫禀陈失实》一文中,对矿局的用工情况,有这样一段记载:“卑职初到峄境察访时,有崔姓煤窑一座,所用夫工上下仅2〇〇余人,其用工亦不过千人。”“现卑局机器只能抽出深水,其他工作皆用土人(按:指峄县枣庄一带当地居民)。比起来矿井较多,施力较大,核之土窑所用人夫,不翅倍蓰。……(由于)官窑佣值重而程课宽,民夫多乐就者,土窑夫工日形不足。假令官窑停止,此等寻常土窑能筹巨款接办税收,不但窑户不能,即豪民亦不能。”如此,则“无业穷民”,又当“立即拷腹”了。
另外,李鸿章在光绪九年(1883年)7月13日的《峄县开矿片》一文中也说:“该处地瘠民贫,自矿局日有起色,赖以生活者数千家。”光绪八至九年间,中兴矿局刚刚投产不久,用工人数即如此之多,故推断其在“煤斤旺出”之际,矿局工人总数均为三四千人,恐怕也不能算是夸大了。
至于这些矿工的来源,上面几段文字基本上作了交待,除了操纵机器的所谓“技师”和“机匠”等,是由上海、广东等地雇用的以外,其余井下采煤、运搬等工种所用工人(即所谓“煤夫”),绝大多数都来自附近农村。后来,也有少数来自莱芜和新泰两县。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中兴煤矿公司接办初期,基本上也没有多大变化。
大运河与枣庄煤炭运销枣庄地处山东南部,距运河40公里,漕运可达江苏、安徽等长江沿岸诸省,正如《峄县志》所述,“北跨琅琊,南控江淮”,交通方便。台枣铁路未修前,枣庄到运河码头——台儿庄,每天皆以牛车踯躅其间,多达一、二百辆,颇极一时之盛。但是,仅“资民车拉运,车少费重,常年载运无多,……虽煤质优佳,销运不广”。1882年,枣庄共有小煤井10多座,最高日产120余筐,除部分当地散销外,大部分通过运河民船运销于上下游。济宁是当时煤炭集中销售地,经营商铺近70家。在枣庄境内推销煤炭舍商家也有30余户。
19世纪末,上海月耗煤量1300多吨,主要来至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只有很少数量是中国土窑生产的煤炭。由于外煤的送输远涉重洋,煤价十分高昂,当时英国煤每吨售价银11两,澳大利亚吨煤价8两,日本煤质低劣,每吨5.5两。当时,用京西煤价每吨2.5两,但需牛车辗转天津,再到上海,煤价增到12两(张国辉著《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煤炭一时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特需燃料。李鸿章向清朝政府奏准,中兴矿局生产的煤炭,每吨只交出口正税一钱银子,就可运销各地,不再交纳其他税金。而售予各省兵商轮船和机械制造局的用煤,一律免税。这给枣庄地区的售煤创造了极好的发展机会。此间,中兴矿局煤炭产量已达8.5万筐,在运河沿岸建立了销煤机构和码头,使煤炭由船运到各地, 枣庄境内呈现出人拉骡驮,连樯北上,船运南下的繁荣景象,给枣庄煤炭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为煤炭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半截筒子小窑发生矿难由于在生产技术上,中兴矿局除了购置几架抽水机器外,其他方面仍然墨守成规、率由旧章,再加上矿井大大延伸,因而劳动条件更加恶劣,井下的伤亡事故日益增多。尤其是矿区经过数百年的自由开采,废弃古井到处都是,里面积水很多,一旦打透,就会造成惨重的水灾。光绪十九年(1893年)6月14日早班,半截筒子小窑发生了一次极为惨重的特大水灾。当时窑内水势很汹,在井下工作的人们乱成一团,都拥挤到窑口,紧紧抓住拉煤的绳子向上攀爬,因人太多,把绳子都拉断了。而矿局资方代表没有采取积极营救措施,结果全窑100多名矿工都被淹死在井下。
灾难的发生,激起了广大矿工和当地人民群众的愤怒。枣庄、齐村、郭里集一带的群众,聚集了1000多人,抬着土炮之类的武器来围攻矿局。后来,由于峄县知县派兵镇压,人们被迫散去。同时,矿局又给予死难工人的家属抚恤金(每人200吊钱)。在威逼利诱下,群众忍气吞声,负屈了事。
大坟子中兴矿局遭封禁半截筒子小窑矿难发生后,直隶总督以戴睿藻等办理不善将其撤差,另外饬派峄矿转运委员江苏补用同知陈德浚为经理。陈德浚又因有淞沪厘局差务,不容分身,便禀请派委候补道陈宝荣接办。于是,矿局的经营管理大权便由北股转移到了南股手里。陈德凌、陈宝荣等经营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矿局营业情况有了一些好转,获利甚厚,结果引起了南北股之间矛盾的激化,连《峄县志》也为之说法有异:“洎戴君以事归里,陈司马德渙继之,萧规曹随,不烦丝粟之力,而炭矿大出,遂致资百余万。前之人劳而不蒙其福,后之人安而得食其报,岂天道果有如是者耶?”实际上,自半截筒子小窑发生矿难以后,中兴矿局的营业便逐渐衰落下来。其衰落的主要原因一是资金不足,无力进一步扩充生产和运销设备以降低成本,因此,很难和当时进口的洋煤以及资金较大的开平等煤矿竞销,更经不住这次特大矿难的打击;二是矿局内部南北股之间矛盾日益尖锐,而掌管经营大权的官僚又腐败无能,贪污私吞,最后竟除了4架抽水机器和局房外,所有股本亏耗净尽。就在这四面楚歌的困境中,恰好碰上山东巡抚李k衡在全省封禁矿井。
李秉衡于光绪二H年11月11日(1896年1月4日)上了一个奏折,内称:“山东历办矿务并无成效……开矿所用,率多扩焊无赖之人。方其开也,藏亡纳叛,奸宄日滋,及其停也,大慝巨凶,无业无家,尤虑铤而走险。方今威海所驻倭兵已七八千人,深恐此种不逞之徒,散无可归,因而起衅,为患不堪设想。”清廷批示:“著照所请,户部知道。”于是,山东沿海矿业便悉遭封禁了。此事虽与峄县中兴矿局本无直接关系,但陈德浚等看到矿局营业不振,原就打算早日抽出资金,此时也不和北股贾起胜等商量,便趁机请求撤局,连账目都未清理,就急忙宣布停办了。而所有抽水机器均未运走,悉数封存于枣庄的机房内〇中兴矿局关闭后,南北股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更加尖锐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6月间,陈德浚又私自将机器大小4件租与济宁州绅士米汝厚等在枣庄附近开挖民窑使用,这一来更使南北双方的冲突表面化。北股股东通永镇总兵贾起胜致函峄县知县说,机器系伊等购置,现已出租,令伊戚戴幼珍 (即戴绪盛)去峄经营。峄县知县只好两不开罪,便以未咨明 “宪台”为由,双方均不准动用。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7月,陈德後又派江苏候补知县虞廷翰来峄,强行启封,将机器交付米汝厚等收用。而贾起胜派来的戴绪盛又力请禁止,双方越闹越僵。虞廷翰不问米汝厚能否开窑,只管交付机器,戴绪盛也不问其交收后能用与否,只管阻挠。双方气势汹汹。峄县知县赓勋左右为难,采取了两个措施:一、他以机器系北洋之物,地方宫不便过问为由,不公开禁止虞廷翰出租机器,却派人在枣庄附近张贴告示,严禁绅民开窑。这样既然不准开窑,机器将焉用之?自然也就出租不成了。二、禀请山东巡抚转咨北洋大臣,提出“官窑既已停歇,机器即应随时移去,不当仍留峄境……深恐滋生事故”;且“机器件数颇多,价亦甚贵”,地方保管甚难,同时局房地基从前按年给租,但“自上年撤局后,至今分文不给,业主讵肯甘心?目前虽暂隐忍,日后终必与争”,因此请求北洋大臣命令矿局移去机器,拆毁局房,将地基归还原主。
直隶总督兼王文韶接此禀帖后,便札委通永镇总兵贾起胜,会同办理津榆铁轨公司直隶候补道张莲芬前往查办。最后账目未及清理,所有汲水机器和笨重器材,封存于枣庄局机房。轰动一时的峄县中兴矿局(官窑矿局),就此结束。
相关地名
枣庄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