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七后裔在胶州
| 内容出处: | 《胶州文史资料 第十六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50020020220012349 |
| 颗粒名称: | 于七后裔在胶州 |
| 分类号: | K248.301 |
| 页数: | 10 |
| 页码: | 186-195 |
| 摘要: | 清顺治五年(1648)在山东大地上以锯齿山为根据地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抗清起义运动,这就是于七领导的农民抗清起义军。于七(1609-1702)名孟禧,字乐吾,山东栖霞唐家泊村人。3年后,这场起义在清廷的软硬兼施和拉拢之下瓦解了,转成了若干小股的起义武装,又过了13年即顺治十八年(1661),于七复率旧部重上锯齿山反清,清军三路围攻锯齿山,激战于次年春,后于七突围而出,不知所终(一说他逃到了青岛,在崂山出家做了华严寺的第三代住持)。在于七再次起义之前,他便让长儿媳带着3个孩子(于七的长孙,长孙女、次孙)逃亡到胶州。 |
| 关键词: | 于七 后裔 胶州 |
内容
清顺治五年(1648)在山东大地上以锯齿山为根据地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抗清起义运动,这就是于七领导的农民抗清起义军。于七(1609-1702)名孟禧,字乐吾,山东栖霞唐家泊村人。3年后,这场起义在清廷的软硬兼施和拉拢之下瓦解了,转成了若干小股的起义武装,又过了13年即顺治十八年(1661),于七复率旧部重上锯齿山反清,清军三路围攻锯齿山,激战于次年春,后于七突围而出,不知所终(一说他逃到了青岛,在崂山出家做了华严寺的第三代住持)。在于七再次起义之前,他便让长儿媳带着3个孩子(于七的长孙,长孙女、次孙)逃亡到胶州。现把当时逃亡胶州的历程及于七后裔在胶州的发展情况整理成文,以现当年于七家人出逃之谜,希望能为专家们研究于七起义及当时的历史提供一定帮助。
于七后裔逃往胶州
清顺治十八年(1661)四月十五日是莱阳宝泉山庙会,十乡八里的莱阳、海阳和栖霞的百姓,都趁春暖花开的宜人之时,纷纷赶山逛市,赏花拜佛。于七之弟于九,也陪妻子衣氏去赶庙会,为衣氏之母所患的眼病上山求神烧香。于九之妻衣氏,是名门闺秀,光彩照人,当即被莱阳土豪、人称“恶太岁”的宋彝秉看见了,便对衣氏动手动脚纠缠不休。于九知道此事后,将宋彝秉打了个鼻青脸肿。从此,为于七家惹下了灭顶之祸。
宋彝秉被于九打伤之后,四处寻机报复。他弄清了打他的人是栖霞唐家泊村于七之弟时,便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于七。宋彝秉依仗他的父亲在清廷兵部为官的权势(其父宋璜已死,明降清),直接进京找其父的故交,诬告说:“于七在栖霞盖金鸾殿、绣龙袍、准备反清复明当皇帝。”清廷下旨令登州府查抄,登州府急派镇将带兵役300多人,于七月二十日中午来到唐家泊村,将村和于七家团团包围,说是奉旨查抄。见人就打,见物就抢,抢不走的就砸。当时于七不在家,于九和于十正睡午觉。于七之妻李俊梅急忙叫醒于九和于十,兄弟两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与村民一起将登州兵役打了个丢盔弃甲,狼狈逃回了登州城(蓬莱)。为此,清廷决定发兵“征剿”于七。
于七回家之后,知道灭顶大祸从天降下了,被清廷满门抄斩迫在眉捷,遂布置家小,能逃走的赶快逃走,不能在家等死。
七月二十二日晚上,趁残月未升漆黑一片之时,于七之长子护送其妻与子女(于七的长孙、长孙女、次孙),人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唐家泊村的于姓大门。于七长子一行,走了20多华里,灰蒙蒙的残月才爬上了山顶,便借着月光继续赶路。经桃村、海阳、莱阳、即墨.在似火的骄阳暴晒之下,马不停蹄,人不歇息,经过一夜一天的奔走,傍晚来到了蓝村镇。喂过马,吃过饭,略加歇息,趁天黑快马加鞭,通过了店口桥,过了大沽河,来到了店口村西头大庙前的土地庙旁,就这样离开了栖霞这是非地,到达了胶州这个保险区。于七的长子吩咐下人卸了马,到车马店 (旅店)歇息去了。
在店口村西头大庙前的土地庙旁,借着惨淡灰暗的月光,于七的长子与妻子、儿女厮守了人生的最后一个夜晚。相拥着哭得死去活来,他们清楚,只有狠心分别,才能给于家留下条根,才有死里逃生的一线希望。
于七的长子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妻子儿女,快马加鞭赶回了唐家泊村,协助父亲在锯齿牙山上拼死作战,终因寡不敌众,惨死在清兵的屠刀之下。
于七之长儿媳,一个大户人家的少妇.年仅27岁的小脚女人,为了于家后代的逃生,从此沦为吃苦受难之人。
于七的长儿媳在店口村西头与丈夫分手之后,雇了2辆独轮车,抱上2个小一点的孩子和从家中带出的物品,自己领着大一点的孩子跟在车后,从店口村沿着军粮道,往西步行20多里路,来到胶州城北的周家庄,借了1间小房子住了下来,从此开始了她们娘儿3个漫长的要饭生涯。
一个月之后,于七的儿媳看到从军粮道上浩浩荡荡地往东过清兵,听说是到胶东抄于七家的。为了安全起见,于七的长儿媳又带上3个孩子,到胶州东偏僻的一个小村南临胶州湾海滩的李家河村定居下来。
艰难的百年岁月
于七的长儿媳,带3个孩子逃到了胶州之后便隐于姓张,有名也不敢叫,说是没有名字,这样于七的长孙就成了张没名,也就是我们胶州于姓家谱上的于一世(没名)。
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小脚女人,要维持一家4口人的生计,真是难于上青天。那些年正逢山东大旱灾,人人吃不饱,家家缺衣穿。拖儿带女四处要饭的人很多。所以,于七的长儿媳带上3个孩子要饭并不显眼,但仅靠要饭想吃饱肚子很困难的。所以,一家4口经常处在忍饥挨饿中。于七的后代,在极度的险恶情况下,匿迹在紧靠胶东是非地的胶州东乡,在清兵眼皮子底下,能安然无恙地不被清兵发现,是胶州人对于姓的大恩大德。
于七的长儿媳听传说于七家被清廷斩草除根了,她连续多日为于家老少悲痛伤心,暗地恸哭,还不敢让孩子知道。她庆幸为于家保住了3条命根子,除了穷困之外,又加上提心吊胆,每一天都像走在高空钢丝上,睡在锋利的刀刃上,怕被清兵发现,苦不堪言,真是度日如年。
2年之后,大孩子可以领着妹妹单独讨饭了,于七的长儿媳也略松了一口气。又过了2年,大孩子可以找小活了,家中少了一张嘴。女儿也可以领着5岁的弟弟四处讨饭了,于七的长儿媳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4年下来,虽然才30出头的人,已经苍老地象40多岁的人了。后来女儿进城给富人家当了丫环,小儿子也能给人扛小活了,于七的长儿媳给富人家当了厨娘,逐渐地摆脱了忍饥挨饿、缺衣受冻的凄惨日子。小儿子在小麻湾村董财主家当长工。董财主的女儿婆家是李哥庄,韩姓独门户,年轻时守寡,她有2个女儿,大女儿已出嫁,小女儿待嫁,董财主与女儿商量给小外孙女儿招个养老女婿。17岁的于七之次孙,已经是英俊的棒小伙了,就这样小儿子就到了李哥庄给韩姓当了养老女婿。于七的长儿媳,巴不得能有这天上掉下来的好事。这就是胶州于姓分两支的由来。
于七的长孙,一直与母亲在李家河村居住,穷得娶不上媳妇,40多岁时才在弟弟的帮助下,娶了个穷家女子为妻。三辈单传,几乎到了绝苗断根的境地,这也是“穷大辈”之说的原因。
胶州东乡大富户
于姓逃到胶州105年后(1766)的春天,于没名(于一世)之孙于茂(于三世)夫妇挑一担、抱一子、领一女,由李家河村东迁,来到当时不足10户的石家庄村居住下来。
35岁的于茂(于三世)来到石家庄之时,正是乾隆年间,他在石家庄仅仅过了30多年,就已经置买土地860多亩。晚年又给3个孙子(于五世)盖起了青砖青瓦的3座独立大宅院,这就是胶州东乡直到解放以后仍很有知名度的 “于家三大门”。石家庄于姓,当时成了胶州有名的大富户之一。当时,总财产价值约7万钢洋。当时在石家庄小河(大沽河支流)的北岸,除了并排的3大宅院之外,自东向西并排的还有于家俑房、于家祠堂、于家讲武堂和练武场、于家大菜园、于家大场园及车马棚和于家大草园、于家花木果园、大粮仓、磨房、碾房、鞭炮作坊、大戏台等等,东西长约半华里。目前石家庄全村各姓共200多户,房宅主要建在这半华里的于姓地皮上。现在石家庄可耕地也基本上与当年于家860亩相差无几。于家当时骡马拴在大街上,胶州东乡称之为“胶州骡马市”。
于茂(于三世)为什么由李家河村东迁来到离大沽河不远、离店口村只有5华里的石家庄村呢?原来,于七的长子当年送妻子儿女过大沽河,来到店口村西头大庙前的土地庙旁,艰难地熬过了生死离别的一夜。在夜深人静之时,夫妇两人将离家时于七给的2个小木箱子埋在了土地庙后边,如果人能幸存下来,待机会再挖出来,置些家产以养家糊口。于七的长儿媳曾多次将于家藏宝地讲给儿子(于一世)和孙子(于二世)听,于二世也曾带领儿子于茂(于三世)利用所谓赶店口集的机会,到店口村土地庙旁多次实地看过地形。当时所谓的乾隆盛世,就是民心比较安顿。于茂认为时机成熟了,便遵照祖父(于一世)和父亲(于二世)的嘱咐,将埋在地下百多年的藏宝连夜挖回了家。2个小木箱打开了,里边是整整齐齐的80个金元宝,每个20两,于茂就是靠这1600两金元宝致了富,发了家,使石家庄于姓从此进入了鼎盛时期。
于茂有2个儿子(于四世),3个孙子(于五世),4个曾孙子(于六世)和11个玄孙(于七世,我的曾祖父)。于七世,当时人称于家三大院里的11只小老虎,可谓人财两旺。
于家第二大院(中大院),直到20世纪末仍保存完好,可惜在全村统一规划时被拆除了。
于姓逃到胶州至解放前290年间,一直是低着头走路,夹着尾巴做人,生怕惹岀是非来,又要遭满门抄斩。至今340年以来,石家庄于姓不偷、不盗、不抢、不赌、不骗,没出过坏人。虽然于姓也有过鼎盛时期,但富而不显,富而不恶,济贫是老当家的主要责任。我祖父的祖父(六世祖),老年时的任务就是每天坐在大门口打发讨饭的。
因为于姓忠厚老实,守法济贫,团结乡里,所以在清朝晚期的咸丰元年(1851),胶州知州给我家老祖于镐(于五世)赠送了一方巨匾(166厘米X65厘米)曰“礼隆尚齿”,此匾一直悬挂在三大门楼的中大门门楼上,直到“文革”时才摘了下来,现在仍保存在石家庄我兄长家中。因为历史原因,当时于姓的家训是:只学武,为防身,不习文,不给满清干事情。
于家鼎盛时期,有偌大的讲武堂和练武场,唯独没有私塾和学堂。11只小老虎个个武艺高强,枪、刀、剑、戟十八般练艺样样会,骑马、射箭百步穿杨,武秀才好几名。于家不习文,我的曾祖母是书香门第之女,富家闺秀。她的4个儿子(于八世,我的祖父)和10来个孙子(于九世,我的父辈),同样没有一个上学识字的。直到全国解放,石家庄于姓没有出过一个文化人。清同治七年(1868),于家被清廷欺骗,11只虎中有五六名被强征拉去当州兵,说是去“打土匪.保家园”。在胶州东滩与“土匪”大混战中,几乎人人挂彩受伤。东、西两大院遭火烧,并且殃及中大院。东大院2兄弟老大致残,家产耗尽;中大院5兄弟,老大(我的大曾祖父)战死,年方26岁;西大院4兄弟,老大、老二的孩子被绑票,家产耗过多半。实际上这次与“土匪”混战,是清胶州乡兵与捻军(太平军)在山东最后的一战。于家受骗,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精神和财产都受到了严重摧残。从此,于家也不再练武了。
于家的大练武场,直到解放前仍大门紧锁,荒芜了近百年。阴森森的大院里杂草高过人,大树参天人不抱,草丛中到处皆是练武的器具,练武的第二方鼎巨石(60厘米X33厘米X33厘米,重200斤),现在仍在我家的院子中。
于姓盼到了天亮
清廷将于七冠以“贼”名,于七的后代怕杀头,胶东于姓抬不起头,胶州于姓更不敢承认我们家是于七的后代。
共产党胶东区委书记林浩,早在抗日战争时期(1941),就在《大众报》上撰文和赋诗赞颂于七为“牙山英雄”。在解放区,相继出版了各种版本的“牙山英雄于七”剧本。各种文艺形式和各种剧种的“牙山英雄于七”唱红了胶东解放区。于七是胶东农民抗清起义的英雄,胶东抗清起义的农民都是英雄,共产党推翻了压在于姓头上的“贼”山,胶东于姓得到了彻底解放,于姓被侮辱、压迫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于姓要好好地感谢共产党,要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早在解放前,我于姓“桂”辈的两位兄长就参加了解放军,有3位兄长参加了抗美援朝,有立功的,有受伤的,也有长眠在朝鲜国土上的。
解放初期,石家庄于姓40多户,我“桂”辈兄弟正是青少年时期。到目前为止,有自解放初就当村干部、一直干到退休的兄长,有转业和退伍的一批当年的军人,更有不少的退休干部和退休工人,这些人,在我“桂”辈兄弟中占了很大的数量。年轻的下一代人中,有在政府部门任职的领导和其他机关任职的干部,也有在部队服役的营、团级军官和土兵,更有教师、工程师、医生、护士等各类技术人员和已经毕业的和正在上学的一批大学生。
于七后裔近况
于七逃亡到胶州的后代,分为“大沽河西于”和“大沽河东于”。“大沽河西于”即胶州市胶东镇石家庄于,是于七的长孙后代。“大沽河东于”即胶州市李哥庄镇李哥庄于,是于七的次孙的后代。目前,两个村的于姓户数相差不大,合计约有300户。两村一河之隔却如同相距千里。几百年以来,一直没有来往。
石家庄于姓有很多于七的传说,这是因为于七的长孙在逃离栖霞时已经是7岁的大孩子了,对唐家泊村的一切都记忆犹新,于家大院的情况都历历在目。再加上一直陪伴在母亲身边,经常听到母亲的述说,后来,于茂搬到石家庄发了财之后,便将祖父(于一世)和父亲(于二世)所见所闻的传说,亲口传到孙子(于五世)和曾孙(于六世,我祖父的祖父),就这样,于七的传说一代一代相传至今。
李哥庄于姓,对于七的传说几乎一无所知,这是因为于七的次孙逃离栖霞时还是一个吃奶的孩子,又加上不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所以所知无几。大沽河两岸于姓是一家,石家庄于姓人人皆知。李哥庄于姓就不知道这段历史。
石家庄于姓目前约150户,其中三分之一居住在青岛、济南、胶州、大连等城市。
于七后裔逃往胶州
清顺治十八年(1661)四月十五日是莱阳宝泉山庙会,十乡八里的莱阳、海阳和栖霞的百姓,都趁春暖花开的宜人之时,纷纷赶山逛市,赏花拜佛。于七之弟于九,也陪妻子衣氏去赶庙会,为衣氏之母所患的眼病上山求神烧香。于九之妻衣氏,是名门闺秀,光彩照人,当即被莱阳土豪、人称“恶太岁”的宋彝秉看见了,便对衣氏动手动脚纠缠不休。于九知道此事后,将宋彝秉打了个鼻青脸肿。从此,为于七家惹下了灭顶之祸。
宋彝秉被于九打伤之后,四处寻机报复。他弄清了打他的人是栖霞唐家泊村于七之弟时,便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于七。宋彝秉依仗他的父亲在清廷兵部为官的权势(其父宋璜已死,明降清),直接进京找其父的故交,诬告说:“于七在栖霞盖金鸾殿、绣龙袍、准备反清复明当皇帝。”清廷下旨令登州府查抄,登州府急派镇将带兵役300多人,于七月二十日中午来到唐家泊村,将村和于七家团团包围,说是奉旨查抄。见人就打,见物就抢,抢不走的就砸。当时于七不在家,于九和于十正睡午觉。于七之妻李俊梅急忙叫醒于九和于十,兄弟两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与村民一起将登州兵役打了个丢盔弃甲,狼狈逃回了登州城(蓬莱)。为此,清廷决定发兵“征剿”于七。
于七回家之后,知道灭顶大祸从天降下了,被清廷满门抄斩迫在眉捷,遂布置家小,能逃走的赶快逃走,不能在家等死。
七月二十二日晚上,趁残月未升漆黑一片之时,于七之长子护送其妻与子女(于七的长孙、长孙女、次孙),人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唐家泊村的于姓大门。于七长子一行,走了20多华里,灰蒙蒙的残月才爬上了山顶,便借着月光继续赶路。经桃村、海阳、莱阳、即墨.在似火的骄阳暴晒之下,马不停蹄,人不歇息,经过一夜一天的奔走,傍晚来到了蓝村镇。喂过马,吃过饭,略加歇息,趁天黑快马加鞭,通过了店口桥,过了大沽河,来到了店口村西头大庙前的土地庙旁,就这样离开了栖霞这是非地,到达了胶州这个保险区。于七的长子吩咐下人卸了马,到车马店 (旅店)歇息去了。
在店口村西头大庙前的土地庙旁,借着惨淡灰暗的月光,于七的长子与妻子、儿女厮守了人生的最后一个夜晚。相拥着哭得死去活来,他们清楚,只有狠心分别,才能给于家留下条根,才有死里逃生的一线希望。
于七的长子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妻子儿女,快马加鞭赶回了唐家泊村,协助父亲在锯齿牙山上拼死作战,终因寡不敌众,惨死在清兵的屠刀之下。
于七之长儿媳,一个大户人家的少妇.年仅27岁的小脚女人,为了于家后代的逃生,从此沦为吃苦受难之人。
于七的长儿媳在店口村西头与丈夫分手之后,雇了2辆独轮车,抱上2个小一点的孩子和从家中带出的物品,自己领着大一点的孩子跟在车后,从店口村沿着军粮道,往西步行20多里路,来到胶州城北的周家庄,借了1间小房子住了下来,从此开始了她们娘儿3个漫长的要饭生涯。
一个月之后,于七的儿媳看到从军粮道上浩浩荡荡地往东过清兵,听说是到胶东抄于七家的。为了安全起见,于七的长儿媳又带上3个孩子,到胶州东偏僻的一个小村南临胶州湾海滩的李家河村定居下来。
艰难的百年岁月
于七的长儿媳,带3个孩子逃到了胶州之后便隐于姓张,有名也不敢叫,说是没有名字,这样于七的长孙就成了张没名,也就是我们胶州于姓家谱上的于一世(没名)。
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小脚女人,要维持一家4口人的生计,真是难于上青天。那些年正逢山东大旱灾,人人吃不饱,家家缺衣穿。拖儿带女四处要饭的人很多。所以,于七的长儿媳带上3个孩子要饭并不显眼,但仅靠要饭想吃饱肚子很困难的。所以,一家4口经常处在忍饥挨饿中。于七的后代,在极度的险恶情况下,匿迹在紧靠胶东是非地的胶州东乡,在清兵眼皮子底下,能安然无恙地不被清兵发现,是胶州人对于姓的大恩大德。
于七的长儿媳听传说于七家被清廷斩草除根了,她连续多日为于家老少悲痛伤心,暗地恸哭,还不敢让孩子知道。她庆幸为于家保住了3条命根子,除了穷困之外,又加上提心吊胆,每一天都像走在高空钢丝上,睡在锋利的刀刃上,怕被清兵发现,苦不堪言,真是度日如年。
2年之后,大孩子可以领着妹妹单独讨饭了,于七的长儿媳也略松了一口气。又过了2年,大孩子可以找小活了,家中少了一张嘴。女儿也可以领着5岁的弟弟四处讨饭了,于七的长儿媳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4年下来,虽然才30出头的人,已经苍老地象40多岁的人了。后来女儿进城给富人家当了丫环,小儿子也能给人扛小活了,于七的长儿媳给富人家当了厨娘,逐渐地摆脱了忍饥挨饿、缺衣受冻的凄惨日子。小儿子在小麻湾村董财主家当长工。董财主的女儿婆家是李哥庄,韩姓独门户,年轻时守寡,她有2个女儿,大女儿已出嫁,小女儿待嫁,董财主与女儿商量给小外孙女儿招个养老女婿。17岁的于七之次孙,已经是英俊的棒小伙了,就这样小儿子就到了李哥庄给韩姓当了养老女婿。于七的长儿媳,巴不得能有这天上掉下来的好事。这就是胶州于姓分两支的由来。
于七的长孙,一直与母亲在李家河村居住,穷得娶不上媳妇,40多岁时才在弟弟的帮助下,娶了个穷家女子为妻。三辈单传,几乎到了绝苗断根的境地,这也是“穷大辈”之说的原因。
胶州东乡大富户
于姓逃到胶州105年后(1766)的春天,于没名(于一世)之孙于茂(于三世)夫妇挑一担、抱一子、领一女,由李家河村东迁,来到当时不足10户的石家庄村居住下来。
35岁的于茂(于三世)来到石家庄之时,正是乾隆年间,他在石家庄仅仅过了30多年,就已经置买土地860多亩。晚年又给3个孙子(于五世)盖起了青砖青瓦的3座独立大宅院,这就是胶州东乡直到解放以后仍很有知名度的 “于家三大门”。石家庄于姓,当时成了胶州有名的大富户之一。当时,总财产价值约7万钢洋。当时在石家庄小河(大沽河支流)的北岸,除了并排的3大宅院之外,自东向西并排的还有于家俑房、于家祠堂、于家讲武堂和练武场、于家大菜园、于家大场园及车马棚和于家大草园、于家花木果园、大粮仓、磨房、碾房、鞭炮作坊、大戏台等等,东西长约半华里。目前石家庄全村各姓共200多户,房宅主要建在这半华里的于姓地皮上。现在石家庄可耕地也基本上与当年于家860亩相差无几。于家当时骡马拴在大街上,胶州东乡称之为“胶州骡马市”。
于茂(于三世)为什么由李家河村东迁来到离大沽河不远、离店口村只有5华里的石家庄村呢?原来,于七的长子当年送妻子儿女过大沽河,来到店口村西头大庙前的土地庙旁,艰难地熬过了生死离别的一夜。在夜深人静之时,夫妇两人将离家时于七给的2个小木箱子埋在了土地庙后边,如果人能幸存下来,待机会再挖出来,置些家产以养家糊口。于七的长儿媳曾多次将于家藏宝地讲给儿子(于一世)和孙子(于二世)听,于二世也曾带领儿子于茂(于三世)利用所谓赶店口集的机会,到店口村土地庙旁多次实地看过地形。当时所谓的乾隆盛世,就是民心比较安顿。于茂认为时机成熟了,便遵照祖父(于一世)和父亲(于二世)的嘱咐,将埋在地下百多年的藏宝连夜挖回了家。2个小木箱打开了,里边是整整齐齐的80个金元宝,每个20两,于茂就是靠这1600两金元宝致了富,发了家,使石家庄于姓从此进入了鼎盛时期。
于茂有2个儿子(于四世),3个孙子(于五世),4个曾孙子(于六世)和11个玄孙(于七世,我的曾祖父)。于七世,当时人称于家三大院里的11只小老虎,可谓人财两旺。
于家第二大院(中大院),直到20世纪末仍保存完好,可惜在全村统一规划时被拆除了。
于姓逃到胶州至解放前290年间,一直是低着头走路,夹着尾巴做人,生怕惹岀是非来,又要遭满门抄斩。至今340年以来,石家庄于姓不偷、不盗、不抢、不赌、不骗,没出过坏人。虽然于姓也有过鼎盛时期,但富而不显,富而不恶,济贫是老当家的主要责任。我祖父的祖父(六世祖),老年时的任务就是每天坐在大门口打发讨饭的。
因为于姓忠厚老实,守法济贫,团结乡里,所以在清朝晚期的咸丰元年(1851),胶州知州给我家老祖于镐(于五世)赠送了一方巨匾(166厘米X65厘米)曰“礼隆尚齿”,此匾一直悬挂在三大门楼的中大门门楼上,直到“文革”时才摘了下来,现在仍保存在石家庄我兄长家中。因为历史原因,当时于姓的家训是:只学武,为防身,不习文,不给满清干事情。
于家鼎盛时期,有偌大的讲武堂和练武场,唯独没有私塾和学堂。11只小老虎个个武艺高强,枪、刀、剑、戟十八般练艺样样会,骑马、射箭百步穿杨,武秀才好几名。于家不习文,我的曾祖母是书香门第之女,富家闺秀。她的4个儿子(于八世,我的祖父)和10来个孙子(于九世,我的父辈),同样没有一个上学识字的。直到全国解放,石家庄于姓没有出过一个文化人。清同治七年(1868),于家被清廷欺骗,11只虎中有五六名被强征拉去当州兵,说是去“打土匪.保家园”。在胶州东滩与“土匪”大混战中,几乎人人挂彩受伤。东、西两大院遭火烧,并且殃及中大院。东大院2兄弟老大致残,家产耗尽;中大院5兄弟,老大(我的大曾祖父)战死,年方26岁;西大院4兄弟,老大、老二的孩子被绑票,家产耗过多半。实际上这次与“土匪”混战,是清胶州乡兵与捻军(太平军)在山东最后的一战。于家受骗,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精神和财产都受到了严重摧残。从此,于家也不再练武了。
于家的大练武场,直到解放前仍大门紧锁,荒芜了近百年。阴森森的大院里杂草高过人,大树参天人不抱,草丛中到处皆是练武的器具,练武的第二方鼎巨石(60厘米X33厘米X33厘米,重200斤),现在仍在我家的院子中。
于姓盼到了天亮
清廷将于七冠以“贼”名,于七的后代怕杀头,胶东于姓抬不起头,胶州于姓更不敢承认我们家是于七的后代。
共产党胶东区委书记林浩,早在抗日战争时期(1941),就在《大众报》上撰文和赋诗赞颂于七为“牙山英雄”。在解放区,相继出版了各种版本的“牙山英雄于七”剧本。各种文艺形式和各种剧种的“牙山英雄于七”唱红了胶东解放区。于七是胶东农民抗清起义的英雄,胶东抗清起义的农民都是英雄,共产党推翻了压在于姓头上的“贼”山,胶东于姓得到了彻底解放,于姓被侮辱、压迫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于姓要好好地感谢共产党,要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早在解放前,我于姓“桂”辈的两位兄长就参加了解放军,有3位兄长参加了抗美援朝,有立功的,有受伤的,也有长眠在朝鲜国土上的。
解放初期,石家庄于姓40多户,我“桂”辈兄弟正是青少年时期。到目前为止,有自解放初就当村干部、一直干到退休的兄长,有转业和退伍的一批当年的军人,更有不少的退休干部和退休工人,这些人,在我“桂”辈兄弟中占了很大的数量。年轻的下一代人中,有在政府部门任职的领导和其他机关任职的干部,也有在部队服役的营、团级军官和土兵,更有教师、工程师、医生、护士等各类技术人员和已经毕业的和正在上学的一批大学生。
于七后裔近况
于七逃亡到胶州的后代,分为“大沽河西于”和“大沽河东于”。“大沽河西于”即胶州市胶东镇石家庄于,是于七的长孙后代。“大沽河东于”即胶州市李哥庄镇李哥庄于,是于七的次孙的后代。目前,两个村的于姓户数相差不大,合计约有300户。两村一河之隔却如同相距千里。几百年以来,一直没有来往。
石家庄于姓有很多于七的传说,这是因为于七的长孙在逃离栖霞时已经是7岁的大孩子了,对唐家泊村的一切都记忆犹新,于家大院的情况都历历在目。再加上一直陪伴在母亲身边,经常听到母亲的述说,后来,于茂搬到石家庄发了财之后,便将祖父(于一世)和父亲(于二世)所见所闻的传说,亲口传到孙子(于五世)和曾孙(于六世,我祖父的祖父),就这样,于七的传说一代一代相传至今。
李哥庄于姓,对于七的传说几乎一无所知,这是因为于七的次孙逃离栖霞时还是一个吃奶的孩子,又加上不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所以所知无几。大沽河两岸于姓是一家,石家庄于姓人人皆知。李哥庄于姓就不知道这段历史。
石家庄于姓目前约150户,其中三分之一居住在青岛、济南、胶州、大连等城市。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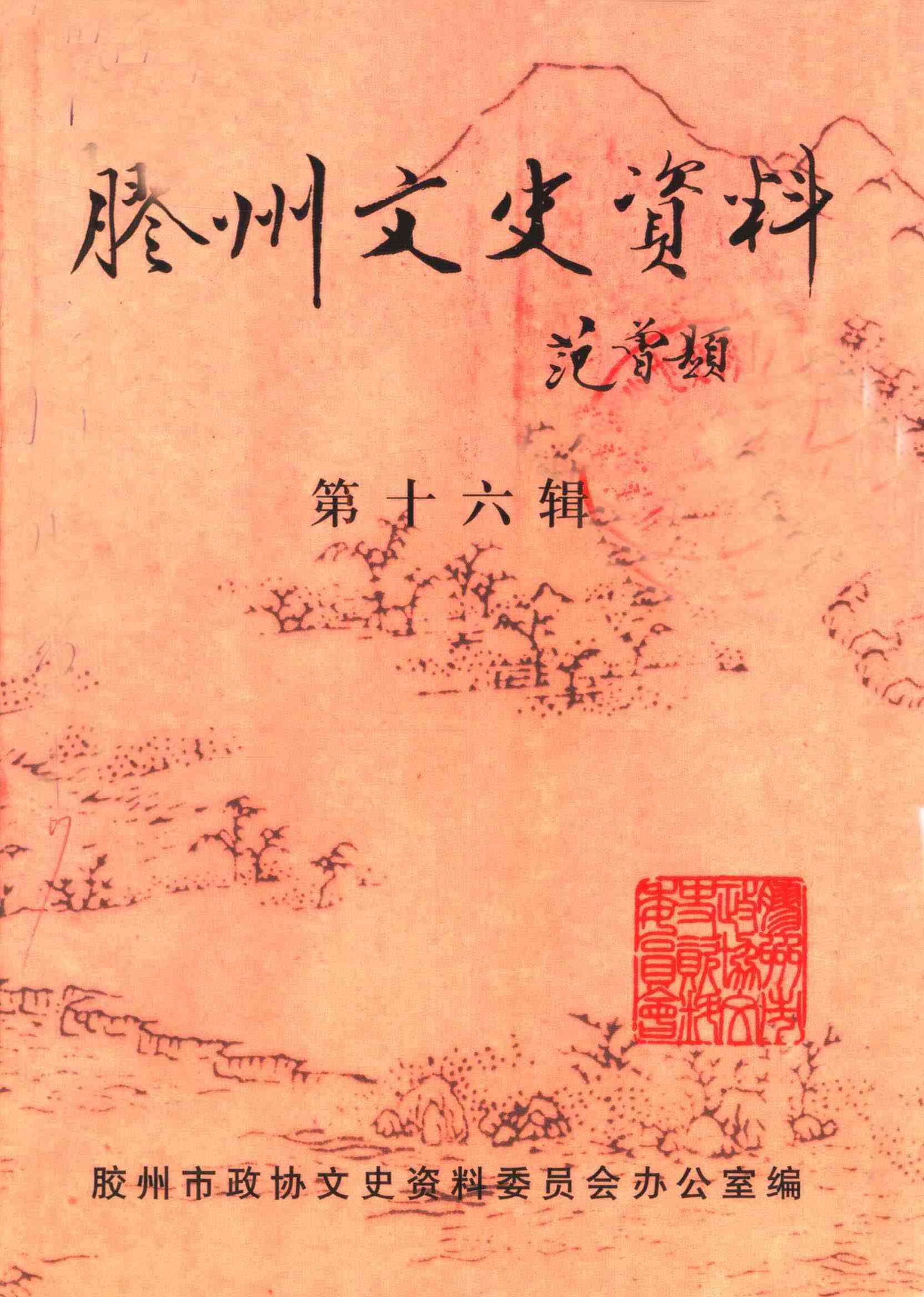
相关人物
于桂明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