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 内容出处: | 《罗庄区文史资料第一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50020020220010119 |
| 颗粒名称: | 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
| 分类号: | I251 |
| 页数: | 9 |
| 页码: | 65-73 |
| 摘要: |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过去三十个年头了,许多的往事已不再记忆,但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段生活却总是难以忘怀,在自己的脑海里怎么也抹不去。一石激起千层浪,上山下乡的热浪席卷了济南的各个中学。同学们热血沸腾,争相报名,自愿结合,组成了一个个“上山下乡知青小组”。当时贴出的最响亮的标语口号是“有志青年到沂蒙山区老革命根据地去,接受锻炼和考验! ”。 |
| 关键词: | 回忆录 革命回忆录 |
内容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过去三十个年头了,许多的往事已不再记忆,但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段生活却总是难以忘怀,在自己的脑海里怎么也抹不去。
1968年,文化大革命正处在“轰轰烈烈”之际,66、67、68届(统称老三届)的高、初中毕业生在城市里再也待不下去了,一部分同学自发地组织起来,要求上山下乡到农村去锻炼和改造自己。一石激起千层浪,上山下乡的热浪席卷了济南的各个中学。同学们热血沸腾,争相报名,自愿结合,组成了一个个“上山下乡知青小组”。当时贴出的最响亮的标语口号是“有志青年到沂蒙山区老革命根据地去,接受锻炼和考验! ”。
来沂蒙山区的济南知青分五批进行了安置:第一批在1968年2月份,第二批在5月份,第三批先是7月份后改在9月份,第四批11月份,第五批在翌年的3月份。大部分安置在莒南县、日照县、莒县、临沂县,少部分去了苍山县、费县、平邑县、沂水县。来临沂县的知青重点去了册山、俄庄(现枣沟头)、太平公社。1969年册山又分为册山、塘崖两个公社。来册山、塘崖的知青被安置在了东高都、西高都、沈牌子、前后坦、后后坦、大塘崖、小李庄、薛庄、肖庄、车網、南头、破石桥(现新桥)等村庄1968年9月19日,我们来到了册山公社的西高都大队(现属西高都镇),全村的老百姓敲锣打鼓地出来欢迎我们。我们知青小组有五名男生、七名女生,分别来自济南一中、五中、八中和山师附中,年龄最大的18岁,最小的还不足16岁,我任小组长。
艰辛的生活
三个月的粮库供应结束了(按规定知青保留三个月的国库粮),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们渐渐学会了蒸地瓜、摊煎饼、擀面条,学会了推磨、簸米。大队里分给我们三分菜园地(即自留地),我们学着社员的样子种上了白菜、韭菜、茄子、豆角、辣椒、南瓜。在生产队长的帮助下,我们买了两头小猪,同学们待宝贝似的照顾、喂养它们。每天劳动收工回来,男同学打扫厕所、挑水,上菜园捡菜、施肥,女同学喂猪、垫圈、推磨、扫院。小组的同学轮流做饭,每人半个月,半年轮一次。同学做饭都有过做夹生饭的历史,推磨也都尝过天旋地转、头晕恶心的滋味。不论谁做饭,半个月只配给半斤油,40斤小麦,90斤稻(约70斤大米),叁元钱,瓜干和菜园的菜不限量。所以,半个月的伙头军,谁干谁头疼,都想调节好生活,可情况不允许。每天,天不亮起床,浇水、做饭、切菜、拌猪食、备柴草;白天,洗瓜干、泡瓜干、嗑稻、磨面、簸米、挑水;晚上,推磨、摊煎饼。推一个小时的磨,摊三个小时的煎饼,仅够十二个人一天的饭。又是烧火又是摊煎饼,灰头灰脸汗淋淋,一天下来精疲力尽。下地干活,我们和社员一样地出工、出力、挣工分,一年下来,各小队的分值不一样,分得的现金有多有少。这些现金都做为小组的收人,然后根据在小组的出工情况做第二次分配。这样劳动一年,平均每人能分30元钱。
1969年的冬天,大雪封地,北风凛冽,天特别的冷。一夜下雪,从窗缝、门缝往屋里飘满了雪花,屋里没有取暖的炉子,老式窗户上仅贴了一层纸,所以,屋里屋外一个温度。我们住着一排五间房,男同学二间女同学三间,天冷,我们男生将五张单人床排在一起,床上铺上厚厚的一层麦草,上面再铺上席子,来了一个大合铺,还真暖和。女同学见了也效仿。几年的冬天,都是这样度过的。
好不容易公社批给我们小组一吨煤,同学们好高兴。一大早,女同学给备好干粮,男同学拉着排车上路了。从西高都到汤庄45里路,走罗庄、付庄,到汤庄煤矿已是十点钟了,一遍遍的手续,一次次的等,待装好煤,已是下午两点多了。回到知青点天已经很黑了,女同学在家做好饭,等我们回来一起才吃。社员见我们有煤烧,不知有多么的羡慕。
知青生活,有苦有乐。时间一长,劳动累了,想家啊,真是想啊!每个同学都流过泪。晚上,躺在床上,蒙上被子,起初是偷偷地落泪,过一会哭出了声,有的同学就过去安慰,就这样你流泪时我劝你,我流泪时你劝我。几年来,同学们就是这样相互激励、相互鼓舞着走过来的。说乐也真是乐的开怀,当时,哪个村有知青,哪个村的文化生活就“红火”,知青点成了“文化大院”、“文化活动中心”。那时的文化生活少的可怜,村里没有收音机、录音机,更谈不上电视机,家家墙上挂着小喇叭,听支歌就是最大的享受。知青来了,爱说爱唱,老百姓一到晚上就来知青点拉呱儿、说笑话、唱小曲,知青也教他们唱歌、跳舞、拉二胡、吹笛子。村里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村里演,到公社演,还有一支基本的观众队伍,你走到哪里演,他就跟到哪里看,台上台下一家人,演的高兴,看的开心。那是什么样的表演啊,伸伸手,弯弯腰,蹦两蹦,喊两声,可老百姓看得津津有味,他是把我们看成自家的孩儿了。那真诚,朴实的感情,深深的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骨子里。
老百姓有病人,病得不轻,可硬是不上医院看大夫,一是舍不得花钱,二是大老远的不想去,苦苦的熬,我们见了,心里真不是滋味。于是同学发誓要学医、学针灸。五名同学进城买了医书,买了针,对照书本面对面,你给我扎,我给你扎,乡亲们看了心疼啊!半年的自学,对一般的病,如头痛、胃痛、关节痛、扭伤等,还真能见效。后来又到了临沂军分区304独立营医疗队学了新针疗法,打水针(即在穴位上注射葡萄糖),埋羊肠线(专治气管炎),还到了地区医院(今市人民医院)针灸室实习。以后,每天收工回来,小组里就有老百姓早早的等在那里,知青的床也就成了老百姓的“病床”,每次都是先给“病人”下好针,然后再吃饭。时间长了,乡亲们就拿你当亲人待:家里来客人啦,做点好吃的啦,忘不了你;新麦下来了,摊回全麦的煎饼,大娘、大婶特意的抹上猪大油,放上葱花盐,卷起来,热乎乎的送到你手里;你有病了她更是放心不下,拿出过年的面,擀上碗面条、打两个荷包蛋,端到你床前;衣服破了,大娘、大婶争着拿去给你补。乡亲们的那份情,那份爱,今生今世也难忘怀。
文化大革命,村上的老百姓也受了罪、遭了殃,也分了两派闹“革命”,整天地你批我,我整你。我们知青通过一段时间和老百姓接触,觉得都是好人,都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应该团结起来。于是我们找了大队革委会的头头谈,谈团结,谈一碗水端平……,这下可惹恼了这个头头,说我们知青阶级立场有问题,派人在我们大门口站了岗,晚上出门跟哨。他喝上酒,还在喇叭里发酒疯:“你们是知识青年吗?我看是吃屎青年!你们懂什么?你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就得老老实实听我的。”有天半夜,他带一伙人,头戴柳条帽,手拿红缨枪,敲开我们的门,冲进我们的屋,硬说我们有藏的什么东西,一阵乱翻,同学们紧张地缩在了一起。那一夜好冷好冷,谁也没再睡觉,想了许多许多……这一年,他不准我们回家过年,这个年我们过得好孤单,好冷清,家家都在放鞭炮,我们好想家…
难忘的劳动我们12名同学,分到了五个生产小队。乡亲们高髙兴兴地接纳了我们,手把手地教我们插秧、割稻、推小车、耕地、切地瓜干等农活。时间长了,知青和社员也能并肩干活了,插一天秧,也能插上一亩二分田;推小车往地里送粪,一天十二趟,趟趟也能装满篓子。社员们都点头齐叫好。
割了麦子栽稻子,节气不等人,水也不等人。放水、灌田、耙地、插秧,环环相扣不能误。等水灌田是第一件大事,不论是白天晚上都得有人等。有一次我们第五生产小队分在晚上灌稻田,吃过晚饭,我与队长身披蓑衣,手提马灯,肩扛铁锨,来到地里。在地里不停地走,撅埂、放水、灌田,一个稻方一个稻方的灌,一个稻方一个稻方的看。夜深人静,劳动了一天又接着干,真是有点累。我撅开了二个田埂,铺开蓑衣,就躺在了地上,看着晴朗的夜空,数着天上的星星,不知不觉睡着了。一陈凉风吹来,我一个冷颤,醒来一看,已是一身水,一身泥
夏天,生产队种的西瓜、甜瓜下来了,和社员一起拉着排车赶大集。头带一顶草帽,脚穿“沂蒙凉鞋”(用旧推车轮胎自制的鞋),赶罗庄、付庄集,赶册山、塘崖集,赶临沂城里的大集,一车瓜最多卖上十元八元钱。中午太阳偏西了,找个小饭店俩人花去伍角钱,要块大锅饼, 二碗油渣子粉条杂烩菜,这就是外出的最高待遇了。
秋天到了,该秋收了。满场的稻谷和地瓜,又是一个丰收年,老百姓一年就盼着这一季。三夏不折一秋忙,真是黑白昼夜地忙:忙割稻、打稻、刨地瓜,忙耕地、耙地、种小麦,忙切瓜干、晒瓜干、收瓜干。我们知青小组这时歌声少了,笑声少了,互相之间谈天说地少了,饭也吃不到一起了,接连几天白天你不见我,我不见你,晚上回来倒头就睡,真是太累了。早上,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晚饭后,还要到生产队的场上去打稻。满天的星星满场的人,满场的打稻机轰鸣着,一干就是大半夜,天上的“三星”偏过了正中才收工。就这样,一个半月过去了,晚上该穿棉袄了,可场上的稻谷还是没有打完。
春节就要来临,生产队也得给社员忙年。组织一伙壮劳力,推上大米去东海、连云港换大豆。那时,粮食不准流通,不准卖,路上查得紧,只好白天住店晚上走。我们几个男知青也都参加了换大豆的行列。吃饱了饭,攒足了劲,两夜的急行军,赶到东海县。挨门挨户换,一斤二两大米换一斤大豆。回来之后按人分到社员家,家家磨豆子,做豆腐,忙忙活活过大年。
一年过去了,生产队又该选生产队长、会计、保管员、计工员了。知青有文化,办事公道,有的选上小队会计,有的选上保管员、计工员。那个年代,其实干什么也不容易,小队会计就是当家人,“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可那时任你怎么算计也是穷。当保管员,你一大早就得起床,称上饲料,看着磨好,拌到牲口槽里,这才放心,怕得是饲养员和牲口争粮食。当记工员更是不能马虎,“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我干过生产小队的保管员、记工员。记得当记工员时,半年下来,一公布帐,张三找,李四找,这个找,那个找,都说少记了,弄得不可开交。后来在记分的时候,我就用英文字母来替代,早上A,中午B,下午C,干什么活,赶什么集,也用字母来代替,如:推小车是X,赶册山集是W,上午干了一半活去赶册山集,我就记:BXW。年终兑帐,社员拿着我记的帐本,左看右看不明白,我却说得头头是道,社员高兴啦,都说:“知识青年就是有知识,记帐也和咱不一样,可记得一点不错。”
1970年年底,济南来招工,大部分知青招工返回济南了,我招工没有走,留在了临沂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为临沂县吕剧团,现兰山区歌舞团)。临走那几天,大娘大爷都来看我们,流着眼泪送了一程又一程,都说:“这些孩子来俺这里可吃了大苦了。”1973年小组又有二名知青上了临沂师范、临沂卫校,1974年最后一名知青也上了学。至此,从济南来到临沂西高都村的知识青年全部离开了知青点,其他点上的知青也都陆续的走了,走向了工厂,走向了学校,走向了各自的工作岗位,遍布全国各地。
知青这段生活,有苦有乐,有酸有甜,平平凡凡,朴朴实实。多年来对这段历史,许多的人写书撰文,有褒有贬。我从来不去议论它,不管怎么说,经历过上山下乡那段生活的人,在今天的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是能咬咬牙挺过去的。
(吉敦洁撰文)
1968年,文化大革命正处在“轰轰烈烈”之际,66、67、68届(统称老三届)的高、初中毕业生在城市里再也待不下去了,一部分同学自发地组织起来,要求上山下乡到农村去锻炼和改造自己。一石激起千层浪,上山下乡的热浪席卷了济南的各个中学。同学们热血沸腾,争相报名,自愿结合,组成了一个个“上山下乡知青小组”。当时贴出的最响亮的标语口号是“有志青年到沂蒙山区老革命根据地去,接受锻炼和考验! ”。
来沂蒙山区的济南知青分五批进行了安置:第一批在1968年2月份,第二批在5月份,第三批先是7月份后改在9月份,第四批11月份,第五批在翌年的3月份。大部分安置在莒南县、日照县、莒县、临沂县,少部分去了苍山县、费县、平邑县、沂水县。来临沂县的知青重点去了册山、俄庄(现枣沟头)、太平公社。1969年册山又分为册山、塘崖两个公社。来册山、塘崖的知青被安置在了东高都、西高都、沈牌子、前后坦、后后坦、大塘崖、小李庄、薛庄、肖庄、车網、南头、破石桥(现新桥)等村庄1968年9月19日,我们来到了册山公社的西高都大队(现属西高都镇),全村的老百姓敲锣打鼓地出来欢迎我们。我们知青小组有五名男生、七名女生,分别来自济南一中、五中、八中和山师附中,年龄最大的18岁,最小的还不足16岁,我任小组长。
艰辛的生活
三个月的粮库供应结束了(按规定知青保留三个月的国库粮),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们渐渐学会了蒸地瓜、摊煎饼、擀面条,学会了推磨、簸米。大队里分给我们三分菜园地(即自留地),我们学着社员的样子种上了白菜、韭菜、茄子、豆角、辣椒、南瓜。在生产队长的帮助下,我们买了两头小猪,同学们待宝贝似的照顾、喂养它们。每天劳动收工回来,男同学打扫厕所、挑水,上菜园捡菜、施肥,女同学喂猪、垫圈、推磨、扫院。小组的同学轮流做饭,每人半个月,半年轮一次。同学做饭都有过做夹生饭的历史,推磨也都尝过天旋地转、头晕恶心的滋味。不论谁做饭,半个月只配给半斤油,40斤小麦,90斤稻(约70斤大米),叁元钱,瓜干和菜园的菜不限量。所以,半个月的伙头军,谁干谁头疼,都想调节好生活,可情况不允许。每天,天不亮起床,浇水、做饭、切菜、拌猪食、备柴草;白天,洗瓜干、泡瓜干、嗑稻、磨面、簸米、挑水;晚上,推磨、摊煎饼。推一个小时的磨,摊三个小时的煎饼,仅够十二个人一天的饭。又是烧火又是摊煎饼,灰头灰脸汗淋淋,一天下来精疲力尽。下地干活,我们和社员一样地出工、出力、挣工分,一年下来,各小队的分值不一样,分得的现金有多有少。这些现金都做为小组的收人,然后根据在小组的出工情况做第二次分配。这样劳动一年,平均每人能分30元钱。
1969年的冬天,大雪封地,北风凛冽,天特别的冷。一夜下雪,从窗缝、门缝往屋里飘满了雪花,屋里没有取暖的炉子,老式窗户上仅贴了一层纸,所以,屋里屋外一个温度。我们住着一排五间房,男同学二间女同学三间,天冷,我们男生将五张单人床排在一起,床上铺上厚厚的一层麦草,上面再铺上席子,来了一个大合铺,还真暖和。女同学见了也效仿。几年的冬天,都是这样度过的。
好不容易公社批给我们小组一吨煤,同学们好高兴。一大早,女同学给备好干粮,男同学拉着排车上路了。从西高都到汤庄45里路,走罗庄、付庄,到汤庄煤矿已是十点钟了,一遍遍的手续,一次次的等,待装好煤,已是下午两点多了。回到知青点天已经很黑了,女同学在家做好饭,等我们回来一起才吃。社员见我们有煤烧,不知有多么的羡慕。
知青生活,有苦有乐。时间一长,劳动累了,想家啊,真是想啊!每个同学都流过泪。晚上,躺在床上,蒙上被子,起初是偷偷地落泪,过一会哭出了声,有的同学就过去安慰,就这样你流泪时我劝你,我流泪时你劝我。几年来,同学们就是这样相互激励、相互鼓舞着走过来的。说乐也真是乐的开怀,当时,哪个村有知青,哪个村的文化生活就“红火”,知青点成了“文化大院”、“文化活动中心”。那时的文化生活少的可怜,村里没有收音机、录音机,更谈不上电视机,家家墙上挂着小喇叭,听支歌就是最大的享受。知青来了,爱说爱唱,老百姓一到晚上就来知青点拉呱儿、说笑话、唱小曲,知青也教他们唱歌、跳舞、拉二胡、吹笛子。村里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村里演,到公社演,还有一支基本的观众队伍,你走到哪里演,他就跟到哪里看,台上台下一家人,演的高兴,看的开心。那是什么样的表演啊,伸伸手,弯弯腰,蹦两蹦,喊两声,可老百姓看得津津有味,他是把我们看成自家的孩儿了。那真诚,朴实的感情,深深的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骨子里。
老百姓有病人,病得不轻,可硬是不上医院看大夫,一是舍不得花钱,二是大老远的不想去,苦苦的熬,我们见了,心里真不是滋味。于是同学发誓要学医、学针灸。五名同学进城买了医书,买了针,对照书本面对面,你给我扎,我给你扎,乡亲们看了心疼啊!半年的自学,对一般的病,如头痛、胃痛、关节痛、扭伤等,还真能见效。后来又到了临沂军分区304独立营医疗队学了新针疗法,打水针(即在穴位上注射葡萄糖),埋羊肠线(专治气管炎),还到了地区医院(今市人民医院)针灸室实习。以后,每天收工回来,小组里就有老百姓早早的等在那里,知青的床也就成了老百姓的“病床”,每次都是先给“病人”下好针,然后再吃饭。时间长了,乡亲们就拿你当亲人待:家里来客人啦,做点好吃的啦,忘不了你;新麦下来了,摊回全麦的煎饼,大娘、大婶特意的抹上猪大油,放上葱花盐,卷起来,热乎乎的送到你手里;你有病了她更是放心不下,拿出过年的面,擀上碗面条、打两个荷包蛋,端到你床前;衣服破了,大娘、大婶争着拿去给你补。乡亲们的那份情,那份爱,今生今世也难忘怀。
文化大革命,村上的老百姓也受了罪、遭了殃,也分了两派闹“革命”,整天地你批我,我整你。我们知青通过一段时间和老百姓接触,觉得都是好人,都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应该团结起来。于是我们找了大队革委会的头头谈,谈团结,谈一碗水端平……,这下可惹恼了这个头头,说我们知青阶级立场有问题,派人在我们大门口站了岗,晚上出门跟哨。他喝上酒,还在喇叭里发酒疯:“你们是知识青年吗?我看是吃屎青年!你们懂什么?你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就得老老实实听我的。”有天半夜,他带一伙人,头戴柳条帽,手拿红缨枪,敲开我们的门,冲进我们的屋,硬说我们有藏的什么东西,一阵乱翻,同学们紧张地缩在了一起。那一夜好冷好冷,谁也没再睡觉,想了许多许多……这一年,他不准我们回家过年,这个年我们过得好孤单,好冷清,家家都在放鞭炮,我们好想家…
难忘的劳动我们12名同学,分到了五个生产小队。乡亲们高髙兴兴地接纳了我们,手把手地教我们插秧、割稻、推小车、耕地、切地瓜干等农活。时间长了,知青和社员也能并肩干活了,插一天秧,也能插上一亩二分田;推小车往地里送粪,一天十二趟,趟趟也能装满篓子。社员们都点头齐叫好。
割了麦子栽稻子,节气不等人,水也不等人。放水、灌田、耙地、插秧,环环相扣不能误。等水灌田是第一件大事,不论是白天晚上都得有人等。有一次我们第五生产小队分在晚上灌稻田,吃过晚饭,我与队长身披蓑衣,手提马灯,肩扛铁锨,来到地里。在地里不停地走,撅埂、放水、灌田,一个稻方一个稻方的灌,一个稻方一个稻方的看。夜深人静,劳动了一天又接着干,真是有点累。我撅开了二个田埂,铺开蓑衣,就躺在了地上,看着晴朗的夜空,数着天上的星星,不知不觉睡着了。一陈凉风吹来,我一个冷颤,醒来一看,已是一身水,一身泥
夏天,生产队种的西瓜、甜瓜下来了,和社员一起拉着排车赶大集。头带一顶草帽,脚穿“沂蒙凉鞋”(用旧推车轮胎自制的鞋),赶罗庄、付庄集,赶册山、塘崖集,赶临沂城里的大集,一车瓜最多卖上十元八元钱。中午太阳偏西了,找个小饭店俩人花去伍角钱,要块大锅饼, 二碗油渣子粉条杂烩菜,这就是外出的最高待遇了。
秋天到了,该秋收了。满场的稻谷和地瓜,又是一个丰收年,老百姓一年就盼着这一季。三夏不折一秋忙,真是黑白昼夜地忙:忙割稻、打稻、刨地瓜,忙耕地、耙地、种小麦,忙切瓜干、晒瓜干、收瓜干。我们知青小组这时歌声少了,笑声少了,互相之间谈天说地少了,饭也吃不到一起了,接连几天白天你不见我,我不见你,晚上回来倒头就睡,真是太累了。早上,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晚饭后,还要到生产队的场上去打稻。满天的星星满场的人,满场的打稻机轰鸣着,一干就是大半夜,天上的“三星”偏过了正中才收工。就这样,一个半月过去了,晚上该穿棉袄了,可场上的稻谷还是没有打完。
春节就要来临,生产队也得给社员忙年。组织一伙壮劳力,推上大米去东海、连云港换大豆。那时,粮食不准流通,不准卖,路上查得紧,只好白天住店晚上走。我们几个男知青也都参加了换大豆的行列。吃饱了饭,攒足了劲,两夜的急行军,赶到东海县。挨门挨户换,一斤二两大米换一斤大豆。回来之后按人分到社员家,家家磨豆子,做豆腐,忙忙活活过大年。
一年过去了,生产队又该选生产队长、会计、保管员、计工员了。知青有文化,办事公道,有的选上小队会计,有的选上保管员、计工员。那个年代,其实干什么也不容易,小队会计就是当家人,“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可那时任你怎么算计也是穷。当保管员,你一大早就得起床,称上饲料,看着磨好,拌到牲口槽里,这才放心,怕得是饲养员和牲口争粮食。当记工员更是不能马虎,“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我干过生产小队的保管员、记工员。记得当记工员时,半年下来,一公布帐,张三找,李四找,这个找,那个找,都说少记了,弄得不可开交。后来在记分的时候,我就用英文字母来替代,早上A,中午B,下午C,干什么活,赶什么集,也用字母来代替,如:推小车是X,赶册山集是W,上午干了一半活去赶册山集,我就记:BXW。年终兑帐,社员拿着我记的帐本,左看右看不明白,我却说得头头是道,社员高兴啦,都说:“知识青年就是有知识,记帐也和咱不一样,可记得一点不错。”
1970年年底,济南来招工,大部分知青招工返回济南了,我招工没有走,留在了临沂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为临沂县吕剧团,现兰山区歌舞团)。临走那几天,大娘大爷都来看我们,流着眼泪送了一程又一程,都说:“这些孩子来俺这里可吃了大苦了。”1973年小组又有二名知青上了临沂师范、临沂卫校,1974年最后一名知青也上了学。至此,从济南来到临沂西高都村的知识青年全部离开了知青点,其他点上的知青也都陆续的走了,走向了工厂,走向了学校,走向了各自的工作岗位,遍布全国各地。
知青这段生活,有苦有乐,有酸有甜,平平凡凡,朴朴实实。多年来对这段历史,许多的人写书撰文,有褒有贬。我从来不去议论它,不管怎么说,经历过上山下乡那段生活的人,在今天的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是能咬咬牙挺过去的。
(吉敦洁撰文)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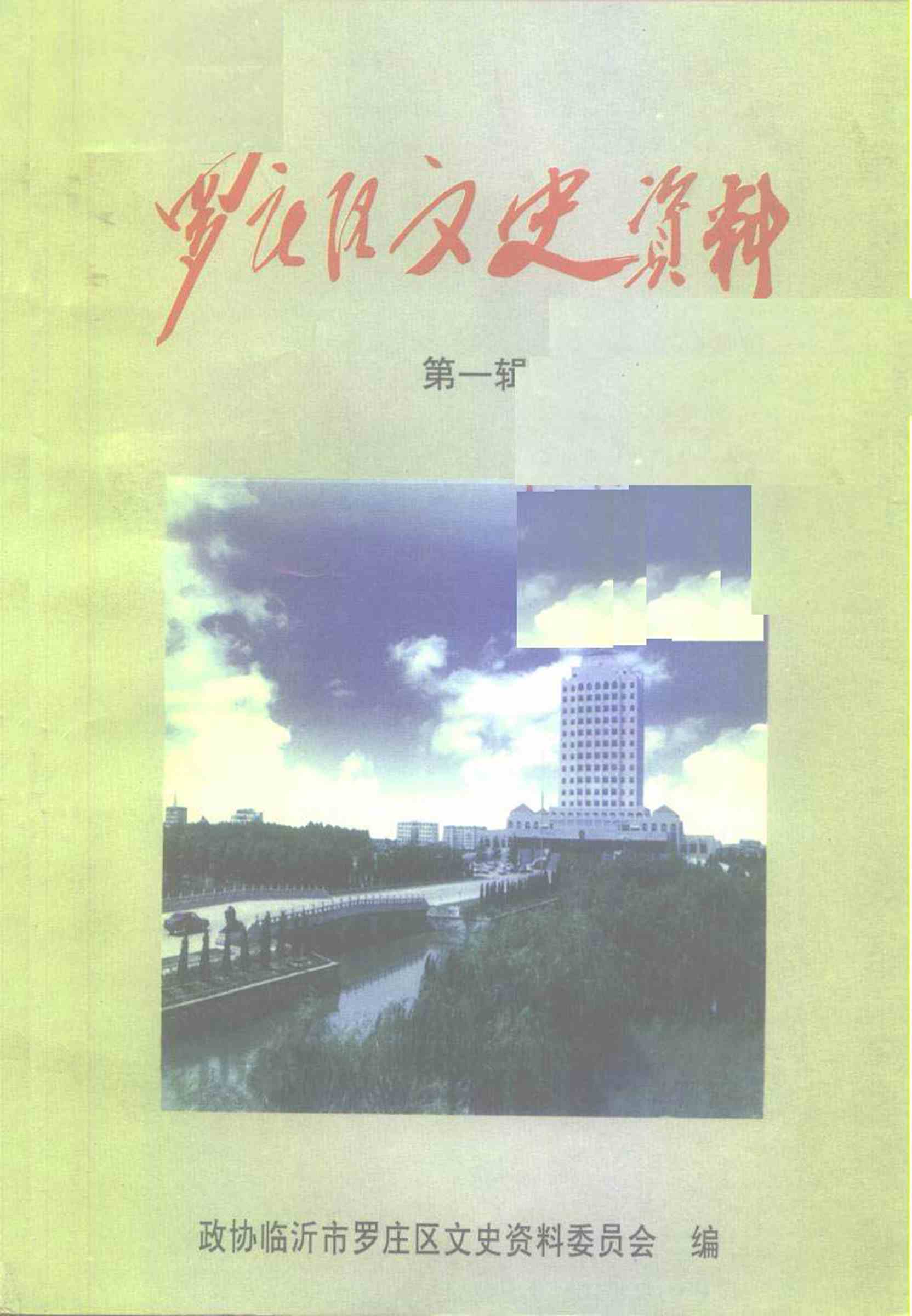
相关人物
吉敦洁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