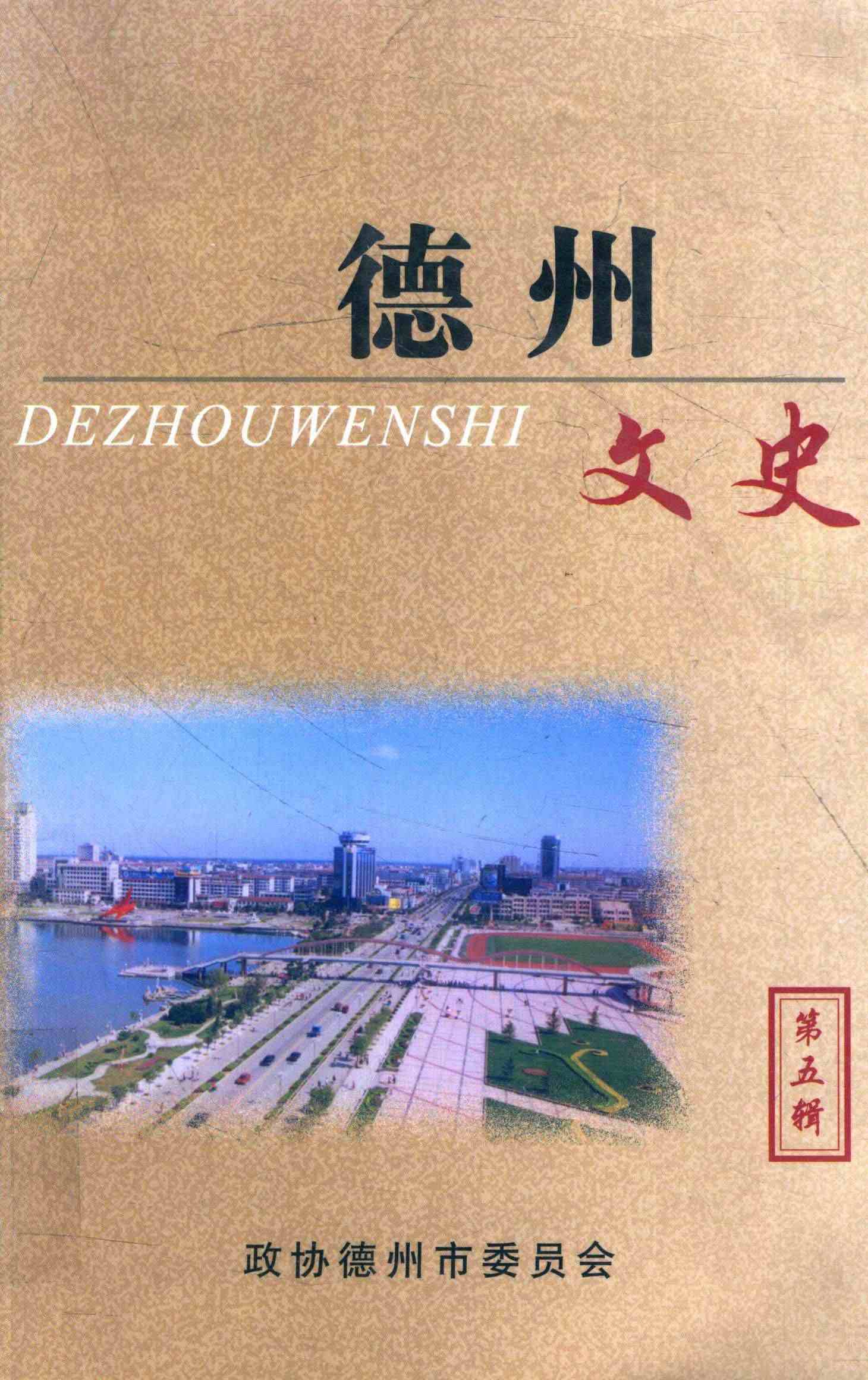“杂技之乡”的一枝花
| 内容出处: | 《德州文史》 图书 |
| 唯一号: | 150020020220007983 |
| 颗粒名称: | “杂技之乡”的一枝花 |
| 其他题名: | 访“杂技之乡”野竹李村 |
| 分类号: | K250.652 |
| 页数: | 5 |
| 页码: | 339-343 |
| 摘要: | 根据《中国杂技》一书记述:“解放前各处杂技之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贫穷落后,农民终年劳累不得温饱,那里的土地贫瘠,无法生存。因此在冬闲的日子里便三五成群,或各家各户,或左邻右舍,成群结队外出卖艺糊口。等到来年春播或秋收,才赶回来参加农忙。半农半艺的传统存在了一千一百多年”。原属河北吴桥,六四年划归山东宁津县张傲乡的野竹李村,自然也不会例外。野竹李村是“杂技之乡”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被誉为“杂技之乡的一枝花”。艺人们在长期的杂技艺术活动中,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迫害,创造了一种共同的语言,在全国杂技界通用,门外人称之为“黑话”,门里人叫“行话”,学名叫“春典”。 |
| 关键词: | 德州市 杂技之乡 一枝花 |
内容
根据《中国杂技》一书记述:“解放前各处杂技之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贫穷落后,农民终年劳累不得温饱,那里的土地贫瘠,无法生存。因此在冬闲的日子里便三五成群,或各家各户,或左邻右舍,成群结队外出卖艺糊口。等到来年春播或秋收,才赶回来参加农忙。半农半艺的传统存在了一千一百多年”。原属河北吴桥,六四年划归山东宁津县张傲乡的野竹李村,自然也不会例外。
所以在去该村前,从我脑海中呈现出的是“盐碱涝洼、土房破屋”的“鲁北农村小景”。万万没有想到,当我们踏进该村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却是宽阔平坦的街道,成行的高压电杆,红砖瓦房林立,排场的水刷石大门……面对这欣欣向荣的农村新景,简直使我们有点目瞪口呆了。
野竹李村是“杂技之乡”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被誉为“杂技之乡的一枝花”。该村的杂技艺术活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相传早在汉代,这里就有被称做“角抵”的杂技艺术活动。清朝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大摆七十二道皇会,第一道就是野竹李村的顶竹杆过城门,即现在的杂技节目“古老中帆”。解放以后,宁(津)、吴(桥)边境更是杂技活动盛行,故有“杂技之乡”的美称。艺人们在长期的杂技艺术活动中,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迫害,创造了一种共同的语言,在全国杂技界通用,门外人称之为“黑话”,门里人叫“行话”,学名叫“春典”。村民主任领我们去房东家的途中,遇一老年妇女,他们之间开玩笑用的都是“春典”。他们管老年妇女叫“苍帼”,不经翻译,外人是无法听懂的。而这种“春典”,在这个村子里,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并视为该村的骄傲。他们常对外村人讲:“进了野竹李你就‘搁念’吧(别说春典),若动春典,连狗都知道”。意思是说,你来野竹李动“春典”,就等于“班门弄斧”,非出洋相不可。
这里被誉为“杂技之乡的一枝花”是当之无愧的。要论杂技艺术,那真是“上至九十九,下到刚会走,说到变戏法,人人有两手”。生活耕作,乡里民俗,无不闪烁着“杂技之乡”的异彩。路边庭院,场间地头,到处都是“练功用具”,打麦场上的车技表演,吸引着过往行人;瓜棚小憩,顺手捡几个土坷垃来个“仙人摘豆”,地头上,两把大镐一并来个“拐子顶”;小学生放学路上,“蝎子爬”的队伍到处可见;谁家办喜事,一凑就是个“专场义演”。刚刚举行过结婚典礼的新郎也会马上跑出洞房;飞身上马来个“蹬里藏身”、“马上倒立”等。
马戏和杂技艺术,在这里不仅仅是一项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化艺术活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开放、搞活”的政策以来,却成了野竹李村村民脱贫致富的一条重要门路。根据八四年高潮时期的统计,全村共有马戏、杂技、飞车走壁、动物展训等六个民间杂技团队,一百多个杂技魔术小组,村民从艺者三百多人。其中能够独立经营演出的“杂技之家”三十五户;三代以上从事杂技艺术活动的“杂技世家”八户。他们都是半农半艺,农忙务农,农闲从艺。全村每年从艺收入可达十余万元。通过“以艺养农”来发展农业,成了该村一个突出的特点。
在野竹李我们共采访了二十多人次,重要访问了刚刚演出归来不久的一个杂技马戏团和一个杂技魔术小组。杂技马戏团的领班人是杨宗治。这个团是由杨宗治和三代杂技世家的孙新民两家为主,并吸收本村和外村部分村民组成的,有二十五名演职员的联合体。孙新民的次子孙国军(长子孙国庆是西安市杂技团演员),三子孙国营及三子的未婚妻小兰为该团的骨干演员。主要节目有:空中飞人、秋千倒立、空中双人体操、高车踢碗等节目。演出路线是以跑乡镇为主,兼跑部分县城。今春外出演出,历时六十三天,主要活动在胶东的招远、蓬莱、栖霞一带。演出两个月,纯收入两万四千多元,平均每人收入千元左右。根据孙新民一家反映,几年来他们全家从艺的收入,可占全家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左右。他们团现有棚圈一个、马两匹,下一步还准备上大棚。
杨宝海杂技魔术小组,去年秋收后去东北,春季农忙时返回,在外演出四个多月。这个小组由四人组成,近三年来一直在东北各地活动。这次历时四个多月,主要活动在大连、丹东、盖平、复县等地的农村基层。他们每到一地,三把号一齐吹响,奏乐集合观众,然后进行宣传工作。平均每天三、四场,收入五、六十元。他们把春季期间视为演出活动的“黄金季节”。在演出中,他们凭技术、讲文明、讲信誉,注意演出质量,深受人民群众欢迎。四个多月,每人平均收入两千多元。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他们每年的从艺收入要高出农业收入的两倍以上。
从采访过程中发现:杂技艺人们不仅在旧社会都有一本血泪账,而且一提起十年浩劫,无不怒气骤生。他们气愤地说:
“文化大革命可把我们折腾苦了。横一个‘破四旧’,竖一个‘割尾巴’,而且我们比其他地方又多了一条‘尾巴’,光杂技魔术道具就烧了几千件,这些道具有些还是我们祖辈留下的传家宝啊!想出去躲躲吧,又被当做‘盲流’、‘黑五类’押送回来,戴高帽子游街。”当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情况时,艺人们个个笑逐颜开。三代杂技世家,七十七岁的孙宪元高兴地说:“我经历了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朝代’,还没碰上这样的好时候。咱的事,电台也播,电视也放,报上也登,听说画报上还有咱的照片。出去演出,到那里都是高接远迎。所以我常嘱咐孩子们一定要好好练、好好演,绝不能给祖辈丢人。”
当问到他们在从艺活动中还有啥困难时,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就是‘婆婆’太多了,‘税收’也太重了。办演出证要化钱,开介绍信要化钱,每到一地都有‘地皮捐’,还有交不完的‘人情费’等等。靠技术、靠劳动挣几个钱,也真不容易啊!”对于他们的苦衷,我们深表同情。
这里土地并不肥沃,但就在这片不足三千亩的土地上,杂技艺术之花却长盛不衰,杂技艺术人才却层出不穷。他们为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据统计,解放以来,从这个村向全国各地专业杂技艺术团体输送的杂技艺术人才已达八十九人之多。由于身怀绝技,解放后被吸收到国家杂技艺术团体的人员中,有些还多次参加出国访问演出,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在这个村子里,如果上查三代,没干过杂技的户,极为罕见。杂技艺术在这个村子里的广泛性与群众性,由此可见一斑。野竹李村的杂技艺术,源远流长,世代相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犹如天涯芳草,在春风吹拂下,更加生机盎
然。
(此文写于1988年,曾发表于文化部主办的《群众文化》1989年第一期上)
所以在去该村前,从我脑海中呈现出的是“盐碱涝洼、土房破屋”的“鲁北农村小景”。万万没有想到,当我们踏进该村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却是宽阔平坦的街道,成行的高压电杆,红砖瓦房林立,排场的水刷石大门……面对这欣欣向荣的农村新景,简直使我们有点目瞪口呆了。
野竹李村是“杂技之乡”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被誉为“杂技之乡的一枝花”。该村的杂技艺术活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相传早在汉代,这里就有被称做“角抵”的杂技艺术活动。清朝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大摆七十二道皇会,第一道就是野竹李村的顶竹杆过城门,即现在的杂技节目“古老中帆”。解放以后,宁(津)、吴(桥)边境更是杂技活动盛行,故有“杂技之乡”的美称。艺人们在长期的杂技艺术活动中,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迫害,创造了一种共同的语言,在全国杂技界通用,门外人称之为“黑话”,门里人叫“行话”,学名叫“春典”。村民主任领我们去房东家的途中,遇一老年妇女,他们之间开玩笑用的都是“春典”。他们管老年妇女叫“苍帼”,不经翻译,外人是无法听懂的。而这种“春典”,在这个村子里,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并视为该村的骄傲。他们常对外村人讲:“进了野竹李你就‘搁念’吧(别说春典),若动春典,连狗都知道”。意思是说,你来野竹李动“春典”,就等于“班门弄斧”,非出洋相不可。
这里被誉为“杂技之乡的一枝花”是当之无愧的。要论杂技艺术,那真是“上至九十九,下到刚会走,说到变戏法,人人有两手”。生活耕作,乡里民俗,无不闪烁着“杂技之乡”的异彩。路边庭院,场间地头,到处都是“练功用具”,打麦场上的车技表演,吸引着过往行人;瓜棚小憩,顺手捡几个土坷垃来个“仙人摘豆”,地头上,两把大镐一并来个“拐子顶”;小学生放学路上,“蝎子爬”的队伍到处可见;谁家办喜事,一凑就是个“专场义演”。刚刚举行过结婚典礼的新郎也会马上跑出洞房;飞身上马来个“蹬里藏身”、“马上倒立”等。
马戏和杂技艺术,在这里不仅仅是一项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化艺术活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开放、搞活”的政策以来,却成了野竹李村村民脱贫致富的一条重要门路。根据八四年高潮时期的统计,全村共有马戏、杂技、飞车走壁、动物展训等六个民间杂技团队,一百多个杂技魔术小组,村民从艺者三百多人。其中能够独立经营演出的“杂技之家”三十五户;三代以上从事杂技艺术活动的“杂技世家”八户。他们都是半农半艺,农忙务农,农闲从艺。全村每年从艺收入可达十余万元。通过“以艺养农”来发展农业,成了该村一个突出的特点。
在野竹李我们共采访了二十多人次,重要访问了刚刚演出归来不久的一个杂技马戏团和一个杂技魔术小组。杂技马戏团的领班人是杨宗治。这个团是由杨宗治和三代杂技世家的孙新民两家为主,并吸收本村和外村部分村民组成的,有二十五名演职员的联合体。孙新民的次子孙国军(长子孙国庆是西安市杂技团演员),三子孙国营及三子的未婚妻小兰为该团的骨干演员。主要节目有:空中飞人、秋千倒立、空中双人体操、高车踢碗等节目。演出路线是以跑乡镇为主,兼跑部分县城。今春外出演出,历时六十三天,主要活动在胶东的招远、蓬莱、栖霞一带。演出两个月,纯收入两万四千多元,平均每人收入千元左右。根据孙新民一家反映,几年来他们全家从艺的收入,可占全家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左右。他们团现有棚圈一个、马两匹,下一步还准备上大棚。
杨宝海杂技魔术小组,去年秋收后去东北,春季农忙时返回,在外演出四个多月。这个小组由四人组成,近三年来一直在东北各地活动。这次历时四个多月,主要活动在大连、丹东、盖平、复县等地的农村基层。他们每到一地,三把号一齐吹响,奏乐集合观众,然后进行宣传工作。平均每天三、四场,收入五、六十元。他们把春季期间视为演出活动的“黄金季节”。在演出中,他们凭技术、讲文明、讲信誉,注意演出质量,深受人民群众欢迎。四个多月,每人平均收入两千多元。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他们每年的从艺收入要高出农业收入的两倍以上。
从采访过程中发现:杂技艺人们不仅在旧社会都有一本血泪账,而且一提起十年浩劫,无不怒气骤生。他们气愤地说:
“文化大革命可把我们折腾苦了。横一个‘破四旧’,竖一个‘割尾巴’,而且我们比其他地方又多了一条‘尾巴’,光杂技魔术道具就烧了几千件,这些道具有些还是我们祖辈留下的传家宝啊!想出去躲躲吧,又被当做‘盲流’、‘黑五类’押送回来,戴高帽子游街。”当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情况时,艺人们个个笑逐颜开。三代杂技世家,七十七岁的孙宪元高兴地说:“我经历了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朝代’,还没碰上这样的好时候。咱的事,电台也播,电视也放,报上也登,听说画报上还有咱的照片。出去演出,到那里都是高接远迎。所以我常嘱咐孩子们一定要好好练、好好演,绝不能给祖辈丢人。”
当问到他们在从艺活动中还有啥困难时,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就是‘婆婆’太多了,‘税收’也太重了。办演出证要化钱,开介绍信要化钱,每到一地都有‘地皮捐’,还有交不完的‘人情费’等等。靠技术、靠劳动挣几个钱,也真不容易啊!”对于他们的苦衷,我们深表同情。
这里土地并不肥沃,但就在这片不足三千亩的土地上,杂技艺术之花却长盛不衰,杂技艺术人才却层出不穷。他们为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据统计,解放以来,从这个村向全国各地专业杂技艺术团体输送的杂技艺术人才已达八十九人之多。由于身怀绝技,解放后被吸收到国家杂技艺术团体的人员中,有些还多次参加出国访问演出,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在这个村子里,如果上查三代,没干过杂技的户,极为罕见。杂技艺术在这个村子里的广泛性与群众性,由此可见一斑。野竹李村的杂技艺术,源远流长,世代相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犹如天涯芳草,在春风吹拂下,更加生机盎
然。
(此文写于1988年,曾发表于文化部主办的《群众文化》1989年第一期上)
相关地名
德州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