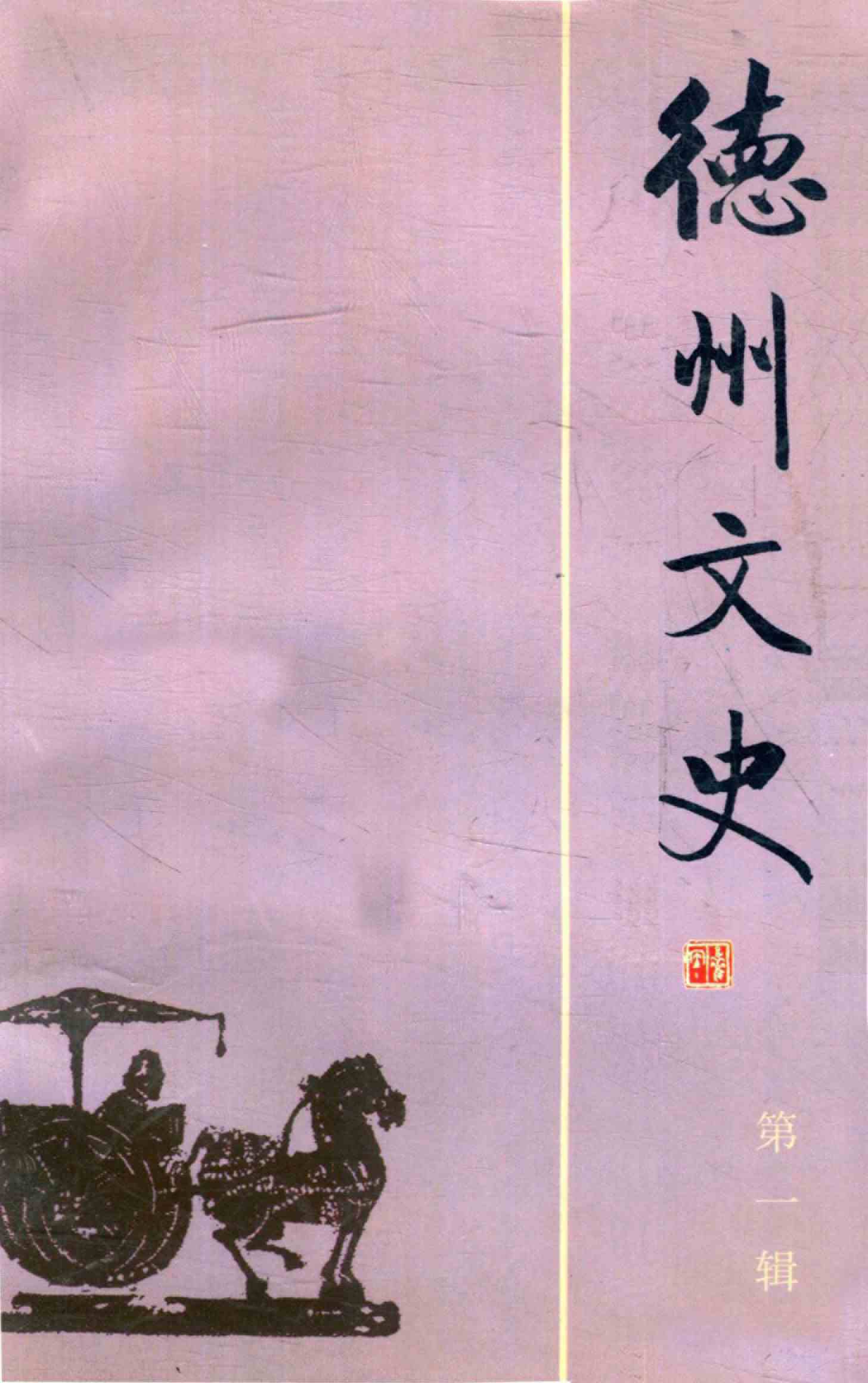日本军国主义者掳掠禹城劳动力纪实
| 内容出处: | 《德州文史》 图书 |
| 唯一号: | 150020020220007760 |
| 颗粒名称: | 日本军国主义者掳掠禹城劳动力纪实 |
| 分类号: | K265 |
| 页数: | 19 |
| 页码: | 183-201 |
| 摘要: | 自从日寇的铁蹄踏进禹城县境,禹城人民就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丰收年景,农民也只是半年糠菜半年粮。1940年至1943年,禹城县连年大旱,最高气温40℃以上,禹城县的田野一片赤土。除地主富农少数人有粮食外,贫苦农民只能以草木为食。有的吃槐花中毒,通身浮肿,皮裂肉绽。道殣相望,死者相藉,逃荒乞讨者随处可见,卖儿鬻女者时有发生,少女仅斗粮的身价即卖为人妻,劳动人民生活在凄风苦雨之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对外侵略和扩张,致使日本青壮年男子均被应征入伍,国内的生产劳动者,除妇女外非老即小。所以,从1943年起,日本侵略者连续在华掳掠廉价劳动力。这次做押解的全是日本兵。摁过手印的第三天,就由门寺坐上闷罐货车北去。 |
| 关键词: | 抗日时期 日军 禹城县 |
内容
自从日寇的铁蹄踏进禹城县境,禹城人民就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丰收年景,农民也只是半年糠菜半年粮。1940年至1943年,禹城县连年大旱,最高气温40℃以上,禹城县的田野一片赤土。除地主富农少数人有粮食外,贫苦农民只能以草木为食。有的吃槐花中毒,通身浮肿,皮裂肉绽。道殣相望,死者相藉,逃荒乞讨者随处可见,卖儿鬻女者时有发生,少女仅斗粮的身价即卖为人妻,劳动人民生活在凄风苦雨之中。
被骗的人们
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对外侵略和扩张,致使日本青壮年男子均被应征入伍,国内的生产劳动者,除妇女外非老即小。所以,从1943年起,日本侵略者连续在华掳掠廉价劳动力。1943年和1944年,他们乘禹城灾荒,以欺骗、诬陷等手段,两次从禹城掠走青壮年劳动力300人。
1943年秋后,日军和伪县公署谎称“张店铝厂招工”,要抽调150名壮丁,说是“管吃管穿,每天工作八小时,工资按产量,多劳多得,每月能剩半斗粮食钱,临走还给八斗粮食(约250公斤)的安家费”。农民虽然故土难离,但为了全家人的生计,一些敦厚善良的农民就报了名。其实日本劳工协会在禹城县招募工人已不是新鲜事,早在1940年就已经开始,也是八斗谷子或高粱的安家费,大都是去东北抚顺市千金寨煤矿。农民也乐意春冬两闲出去做几个月的工,到农忙时就开小差逃回来,虽挣不到钱,家庭也能得到八斗粮食度荒,所以这次仍有部分农民报名。然而,善良的农民却不知道,这一次不是去东北,而是远离故土去日本出卖劳动力。
凡报了名的都集合到城里“山西会馆”待命。过了几天仍凑不足数,就栽赃陷害部分得罪过伪警察的人,说是“八路军的坐探”,抓来充数,总算凑齐了150人。10月份的一天上午,日军用麻绳一连串绑住每个人的一只胳膀,押解到火车站,关进了一辆铁皮“闷罐”车,由伪军警监视,运到济南,押送到原美孚洋行的仓库里。那是一座储存煤油的大房子,由日本兵看管。大家一看势头不对,就乱猜疑。有的说:“这不是去铝厂吧,可能又是下煤窑。”有的说:“是不是让咱们干伪军,去当炮灰呀?”也有的说:“反正没咱们的好果子,说不定让咱上哪里去受罪呢!”有几个曾经当过华工的人有经验,想做逃跑的准备,他们在一处背眼的墙角挖洞,可是挖了半天,怎么也挖不动,原来是水泥石头墙。十来天过去了,又从其他县拉来了许多人,凑足300人,就一齐起了解。仍然是绑着,十人一条绳。这次做押解的全是日本兵。大家被押上一辆铁皮“老闷罐”,迷迷糊糊地开了一夜。车停了,下车一看,原来是青岛车站。这时大伙都知道不是去张店铝厂了,但究竟要到哪里去还不清楚。
这时站台上已有日本兵守候在那里。在押送的路上,不但步兵多了,还增加了骑兵,开路在前。断尾在后。这些人被送到一个虽不是监狱,却戒备森严的地方,四周是高墙,墙上挂满了电网,四角都有岗楼,院子顶上还笼罩着铁丝网,房壁也无比坚厚。直待锁了大门,才给人们松了绑。天还未黑,四角上高挂的探照灯就已打开,夜晚,院子里如同白昼。虽然人们被关进天罗地网,只要有机会,大家还是要斗争,要逃亡。过了几天,一批批的青壮年被押送进来,其中有八九个穿着破旧的八路军军装,大伙明白,这是从抗日战场上来的。这几个八路军战士第二天就暗中活动,策划组织暴动,说咱们“炸”出去。有一个战士说:“现有鬼子兵力不足,咱们抢他岗上的枪打出去,就是死几个,也能大部分闯出去,到外边进山去找八路军,我领路!”这办法正符合大家的心意,哪个不想逃出这个火坑。可是只隔了一天,岗哨就增加了,四角岗楼上也架起了机关枪,枪口正对着这座大房子。下午,几百名难友在院子里排成队,一个鬼子官用生涩的汉语对大家说:“你们不要害怕,皇军要你们当工人,皇军大大的好。你的必须服从命令,逃跑的死了死了的!”不管他说什么,大家心里明白,这完全是谎话。要当工人还能捆绑着,比坐牢还严禁吗?就在这天下午,大家换上了半边红半边黑的薄棉囚服,每人还给一床薄薄的红棉被。回到屋里,有一个河南口音的八路军战士说:“咱们里头有汉奸,可能让鬼子发觉了,要不怎么鬼子今天变了样?咱们非找出他来揍死不可!”大家也都很懊丧,痛恨这个告密的,可惜最终也没找出这个人来。
第二天又让大家集合,点了名,报了数,已是600人了。这些人被捆绑着,押解到大港码头。那里早已停着一艘货轮,人们被赶进漆黑的装着煤炭的底舱,才松了绑。随着汽笛的鸣声,轮船启航了,徐徐离开了码头,驶向大海的深处。轮船开足了马力,船体颠簸得厉害,人们头晕脑胀。驶出胶州湾,一会儿就看不见祖国大陆了,轮船却渐渐缓慢下来,并抛了锚。原来日本人听到一点风声,但又不了解真情,就把这些人先运到海中,以防逃亡。
货轮在海里停了一天,又开来两艘货轮,也是每船600人。这样,一次就运走1800人。难友们都是半辈子生活在那二亩地所系的小圈子里,根本没见过海,更不用说坐轮船了。风平浪静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头晕恶心,有的呕吐起来。起初人们吐酸饭,而后吐粘沫,最后吐的是极苦的黄绿色的水,那就是胆液了。被折腾了半个多月的难友们,身体已经是很虚弱了,再经过这一阵呕吐,大多数人躺在船底爬不起来了。有些身体强壮的,虽然也头晕恶心,总算没吐出来。但船舱里那股酸臭味,也使他们难以忍受。于是便有人要求到甲板上去,让清凉的海风吹一吹。经过许可,有的人爬到甲板上去了。只见苍苍茫茫水天一色,不见边际。除了海浪,什么也看不见,除了隆隆的马达声和波涛声,什么也听不到。这是要到哪里去呢,为什么监视这么严呢,还有机会逃跑吗?一连串的问号盘旋在人们的脑海里,谁也找不出答案。由于英美飞机天天在海空巡航,日轮为躲避轰炸,时行时停,难友们才能有喘息的机会。鬼子官也怕出现死亡,就规定在风平浪静时让人们到甲板上放一次风。就这样,大家才逐渐适应了海上生活。
在门深町水银矿
轮船在海上飘泊了十一个昼夜,终于在一个小码头靠了岸。1800名难友被赶下船。大家走出码头,发现这里房舍与中国完全不同,来往行人的服装打扮也不象中国人,特别是脚趿木屐与汉民不同,难友们都惊呆了。一个日本兵见到大家惊异的神色,就奸笑着说:“这是大日本的门寺海港,你们到家了。”人们一听都怔住了,继而有的落泪,有的谩骂,人们绝望了。来到异国他乡,地理不熟,语言不通,怎么办?有的说:“日本鬼子真狠,把咱弄到这天涯海角,比充军发配还厉害呀!”有的说:“再也跑不了啦,听天由命吧。”也有的说:“只要咱能活下去,有这条小命,总会有出头的日子。”大家议论着,歪歪斜斜地被赶进一个大院子的检疫站,要人们都把衣服脱光,到药池里洗了澡,身上再涂了药,然后按十人一班,每三班一个小队,每三个小队一个中队,每三个中队一个大队,加上队长伙夫,每大队300人。第二天,人们被逼着照了单人相,以后又在贴了相片的“印表”上摁了手印。“印表”上虽然是日文,但也有一些汉字,有几个识字的看出是“日本劳工协会合同书”,最后写的是“昭和十八年(即1943年)十月二十五日。”
摁过手印的第三天,就由门寺坐上闷罐货车北去。这是一列刚刚运过牲口的货车,到处是粪便,臭气熏天。火车开开停停,走了五个昼夜,到了一个叫“青森”的车站下了车。这也是一个港口,大家又乘船渡海,到了一个叫“函馆”的地方,再乘火车继续往北开。走了一天一夜,禹城人的这个大队就到北海道的“门深町”下了车。没下车的那部分人有的去“明治矿业株式会社”挖煤,另有100人被派到农场去干活。禹城大队去的是门深町水银矿。
已经被折磨得虚弱不堪的难友们,爬出火车就被一股刺骨的寒风吹了个透心凉。雪粒象砂子一样随风打向脸庞,刀刺一样的疼。抬头四望,一片白茫茫,都是被大雪覆盖的群山。难友们抱头缩颈,东倒西歪地被带到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坳里。这里地处北纬45度,相当于我国的大兴安岭地区。因为北海道四周环海,风雪特大,气温常低于摄氏零下40度。山脚下有一个大雪堆,雪堆的向阳处有一个黑洞,那就是工棚。门口的周围用稻草和席帘子围着,以防大雪堵门。工棚完全用木板搭制,每个中队住一个工棚。这时难友们还穿着在青岛换上的那身薄棉囚服,每人一床小薄被,怎能抵御如此的寒冷?晚上人们就两人通脚睡,把铺草堆厚一点。两床被子摞在一起。开始大家都睡不着,低声谈论着,盼望日本鬼子被打败,好回家团圆。终因多少天来的困乏,后来都睡着了。但由于天气寒冷,不少人又被冻醒了,大家挤在一起苦熬着这漫漫寒夜。
第二天刚放亮,刺耳的哨子就吹响了。大家起来围坐成一个圆圈,点过了名,每人发给一双大草鞋,这是为适应白天外出干活踏雪用的。然后由伙夫在每人面前摆一只碗,每人一勺稀粥,喝完了再添一勺。大家都嚷着吃不饱。伙食管理员是日本人,他说:“咱们矿上粮食是按生产矿石的数量配给,你们还没干活,哪有粮食?现在有吃的就不错了,你们以后生产量大了会多给吃的。”大家还是乱喊,“吃不饱能干活吗?”却也无济于事。大概难友们的不满引起了日本人的警觉,这天中午饭时,来了个身穿军服留着通鼻胡子的瘸腿鬼子,向大家训话。他叫宇宫,日文音是“乌勾”,大家就叫他“母狗”太君。这个军人气派十足,一脸凶相,据说是从侵华战场上退下来的伤员,是一个饱蘸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他退役后就当了水银矿的作业所长。他用不规范的汉语说了一些“日华亲善”、“干活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等骗人鬼话之后,又说:“你们来到大日本干活是走运的,在这里干活多粮食多,大日本不会亏待你们的。”他最后说了些水银矿的作业程序和必须服从命令的话,“不服从也逃跑不了,北海道是个大岛,四周环海。全岛大山多,人烟稀少,山里花脸狗熊、野狼成群结队,即使让你走,你们只能饿死冻死,或被野兽吃掉。凡逃跑抓回来的,统统死了。”中午饭的粥中又加上了一些糖渣,还有两片马铃薯,这也算是大发慈悲了。当时日本施行配给制,一个日本监工每顿一盒饭,半边大米半边青菜马铃薯,虽然比劳工吃得好些多些,但也吃不饱,所以就克扣劳工的口粮。
第三天开始干活,先由日本人爆炸矿山,然后让华工用土篮挑水银矿石。从矿山挑到火车道旁有15町(日制长度单位,一町109米,36町为一日里),这是水银矿上最脏最累的活。干活以后不喝稀粥了,换成了玉米、马铃薯粉和橡子面混合的窝窝头,每人每顿两个。300人每顿20公斤粮食,每人只有1.4两多,小饭量的半饥半饱,大饭量的只能挨饿。有时每人给一片萝卜咸菜,有时每人一箸子叫“海宝狗”的野生海藻咸菜。春节那天,也不过用相当于两个窝窝头的面,包上些“海宝狗”馅,做成大蒸包让大家吃。
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造成本国劳动力不足,管理人员也太少,一个300人的大队,只有三个日本监工。他们懒得呆在矿上受冻,就采用了“以华制华”的办法,从华工中找一个识字的为他们记数落账,禹城人程绍鲁被他们选中了。程绍鲁考虑到这对难友们有利,就满口答应下来,当了副大队长。难友们挨饿受冻,谁愿意给日本人干活。从程绍鲁记帐以后,他们就用消极怠工来对抗,不管土篮里挑了多少矿石,过去一趟就记一担,有时干脆挑着空篮来回走,只要日本监工不在,大家就这样应付。
北海道冬季夜长昼短,白天只有八小时,矿山又无照明设备,所以无法延长工时,因此天天欠产,日本人就想出了规定任务的办法,确定每天的工作量,完不成不给饭吃。人们的工作加重了,但粮食并未增加,饭食质量又差,饭量大的顶不住了,身体弱的熬不过了,渐渐地一个一个倒下去。越是病号多,粮食越少。病号每顿只给一个窝窝头,有的病号饿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去看病也只给几粒极贱的西药片,根本治不好病。病号只吃粮食不生产,成了日本人的累赘。于是他们想出了一条毒计,设了一个重病号房,说是给病号打针,有几个重病号进去打针,刚拨出针头人就咽了气,这显然是让其速死。后来人们情愿在工棚里也不去病号房了。就这样今天死一个,明天死一个,一个冬季就死了百十个人,其中禹城籍的就有30余人。为了让华工服服贴贴地干活,每当死一个劳工,日本人还要假装出一副慈善面孔,请僧侣诵经祈祷,最后每个死者用一公斤煤油点着木柴烧掉算完。
春节时刻,难友们倍加思念家中亲人,背地里就商议逃跑。但是,在冰雪封地时逃跑会留下足迹,也跑不快,很容易被抓回来。到春季冰雪融化,矿场周围的电网就通了电,更难以逃跑了。有两个难友在想,若不逃跑,早晚也得折磨死,跑出去或许能找到条活路。他俩想趁冬季走,为了避免留下足迹,就从铁路上顺着走。两个难友,其中有一个姓刘的禹城人,就于一天夜里逃出矿场,顺铁道奔跑。那北海道的风雪扑到脸上,打得生疼,又睁不开眼,透不出气,能见度也只有20米,所以他俩走的并不快。当矿警发觉时,也不知他俩的去向,由于矿上人员少,他们没有去追。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矿业所长让矿警严密把守工棚绝不能因小失大。这一夜大伙也没睡好,第二天日本人又威吓了大家一番,也就算了事啦。
两难友顺铁路往北跑,遇到车站绕道而过,有火车过路就躲避,艰难地走了半夜。眼看就要天亮了,两人合计:“咱俩穿着这身囚服,被人看见就得抓起来,咱得想办法换衣服。”他俩看见附近有个值班房,就壮着胆子过去,抓住值班员。值班员见是两个蓬头垢面的大汉就吓懵了,“嗷嗷”地呼喊。他俩先塞住值班员的嘴,然后脱下他的外衣,把他绑起来。又抓住另一睡觉的值班员,他俩一人换了一身标制服,穿上毡靴,就逃走了。
两人换了衣服就大胆了,心想往北走或许能走出日本地,就能到关外了,日本人不是有很多在关外的吗?就是走不到关外,走到苏联也好,也许能转回家去。可是走了一天也没走到尽头,问路吧,又语言不通。一天没吃到东西,饿得实在难受。傍晚,他俩走进一个村子,想讨顿饭吃,村头一家门上挂着“军国之家”的牌子,标明这一家是在侵略战争中死亡的士兵家属。他们走进房门,在土间(日本贫民的外室无地板,是土地面,故称土间)听到室内一个妇女和孩子一边吃饭,一边讲话。他俩一人在外了望,一人进屋去讨饭。因为是穿着铁路标制服,那女人还不十分害怕。他俩不会说日语,只能打着手势说“米西米西”。那妇女给他俩各盛了一碗掺有马铃薯的米饭,这在日本称“菜饭”。当时日本人民也是粮食不足,同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他俩虽然没有吃饭,也不忍心再要了。因为这家只有妇女和孩子,不便久留,他俩就告辞走了。
他俩没走多远,就遇见一个50多岁的老汉,即搭讪着想再讨些饭吃,老汉满口答应,把他俩领回家去,安排吃饭住宿。他俩吃完了饭,躺下还没睡着,就有两个警察持枪闯进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他俩抓走了。原来他俩换衣服不久就被铁路当局发现,铁路沿线通过电话布置搜查两个穿铁路标制服的支那人。日本农村也通电话,那老汉就是该村的村长,所以村长一见到他俩,就知道是逃亡华工。他先把他俩稳住,然后通报了当地警察署。经警察署审讯,他俩被押解到扎幌厅(北海道首府)警察本部,以抢劫罪判处徒刑三年,被关进刑务所(大狱)。
转往雄别煤矿
1944年4月,水银矿停止了开采。由于伤亡人数过多,所剩华工被转移到“雄别煤矿”去挖煤,而雄别煤矿的华工伤亡更为惨重。到雄别煤矿后,照例是矿业所长训话。这是一个肥胖的老鬼子,留着仁丹胡,长了一脸横肉,把眼睛挤成一条缝。据说他自幼就在中国哈尔滨,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是个中国通,因为他对统治中国人有一套办法,就让他当了矿业所长。他原名叫成田勇,为拉拢华工,改姓唐,按日语语音难友们称他“挑太君”。他说:“你们如果干得好,干得快,可以提前回家,换另一帮华工来顶替你们。”他是一个笑面虎,不象水银矿的矿业所长那样苦丧着脸。这里的监工也不象水银矿的监工,皮鞭棍子不离手,“八格亚鲁”不离口,从来不见笑模样。不知是日本人接受了去年的教训呢,还是另一种统治办法。不过难友们明白,他们是笑里藏刀,大家还是十分警惕的。
这里是一个老矿区,原煤层早已挖完,只剩下了一段段的薄煤层,用不上机械,只能手工开采,由于劳动条件太差,华工们只能用手挖,用肩运,既苦又累。每天昼夜两班,实际工作超过13小时,比水银矿的工时还长。特别是夜班,作业十几个小时,中间没有加餐,大家实在饿得难熬。因每周一次换工,所以一些体弱者经常病倒。但病号多了必然影响生产。一天,矿业所长成田勇找程绍鲁谈话,“工人病员太多,我们赔本大大的,你有办法解决吧?”程绍鲁说:“在我们中国,病号都是吃好饭调养。工人本来就吃不饱,是饿出来的病。病了不但吃不上好饭,反而减少粮食,病不更重了吗?病号饭换成大米就好了。”成田勇叹了口气说:“大米实在难得啊!我尽量想办法吧。”从此,凡病员就改供大米稀粥了,有时给点海带咸菜,还弄来一点小干鱼片给病员吃。
日本监工有一个叫小松的,按照日文读音,难友们都叫他“三麻子”。在一个夏天夜晚,三麻子找到了程绍鲁,悄悄地说:“我是日本共产党员,你们这些人里有共产党员吗?我想和他们联系一下。”程绍鲁半信半疑,心里想:“是听说日本也有共产党,但不知是真是假,等和难友们商量好了再说。”就回答他说:“我是不知道,待我问好了告诉你”。以后程绍鲁就暗地里与几个被俘的八路军战士商量,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其中有一个河南人是个干部,他说:“日本是有共产党,如果能联络上,组织起来是好,现在日本本土已无精锐部队,到山里去打游击也撤他的后腿。死了也值得。若是骗人就是无谓的牺牲,不如你去报告有八路军没共产党员,看鬼子怎么办?如果鬼子抓人,我就发动大家给鬼子讲理,同时揭露日本人的假面具。”大家都同意了这个办法,程绍鲁就向三麻子报告了几个被俘的八路军战士。
过了些日子,三麻子告诉程绍鲁,他在山里埋着有枪,让程绍鲁联络人去山里打游击。一天,三麻子领着程绍鲁走进一个黑黝黝的山谷里,扒开草丛浮土,看到埋藏着十几支步枪。三麻子随即埋上,说组织好了人员就去打游击。程绍鲁回来,大家就商量着组织起来去打游击。但不久,几个八路军战士和程绍鲁被一齐抓进监狱,而三麻子却仍然干他的监工。
大家知道了这是一场骗局。那个河南籍八路军干部一动员,大家气愤填膺,一致同意罢工。他们拿起锨、镐、木棒、去找三麻子。“工友们没罪,该逮捕三麻子。”这时,三麻子已不知溜到哪里去了。大家找不到三麻子,又拥到矿场大门,喧嚷着去找矿业所长,矿警持枪阻住大门,并鸣枪威胁。人们仍在大门里吵闹着不去上工。另外几个监工也避在一边不敢出来。不久,成田勇坐着汽车赶来,向大家解释说“叫他们去,不过是教育他们不要上共产党的当。教育好了,保证把他们放回来。工友们都回去干活吧!”由于矿上生产很不景气,工伤事故不断发生,上级矿业株式会社曾批评、警告过雄别煤矿。如果再因此事影响了生产,恐怕这矿业所长的位置就不牢固了。所以他不敢激怒全体劳工,第二天就开始放人,最后都放了回来。三麻子又重新出现,仍然当他的监工。
1944年,日本侵略者在各战场连遭失败,军用物资供应不上,故此军需生产部门强行增加任务指标,妄图挽救其败局,雄别煤矿也同样强制劳工多干、快干,在无劳动保护的条件下,工伤事故越来越多。难友们的仇恨压抑在胸中,个个咬牙切齿,怒火中烧,痛恨日本统治者。
是冬,有几个难友冻伤了手指、脚趾,让场医施药,不料却被截肢。禹城籍华工张明,是来凤乡张庄人,他就是因冻伤被截去双脚的。以后再有冻伤手脚的也无人敢去敷药了,但难友们心中埋下了反抗的种子。第二个春节即将到来了,商河县十七岁的孔××因想念家乡亲人,又泛起了逃跑的念头。他听说北海道北端与苏联的库页岛隔海相望,苏联又和中国相连,只要能跑到库页岛,就能回家。即使被抓住,坐牢也不干这活了。就凭这幼稚的想法,他一个人逃出了矿场。也不知他是怎么走的,居然走到了海边。他偷爬上人家的渔船,被赶了下来。后来冻伤了双脚,走不了路,又被送回了煤矿。这次孔××被抓回来,没送他去警察署,而是以治伤为名被截去了双脚,成为终生残废。
这件事激起了难友们的义愤,积压在心底的怒火终于爆发出来。大家手持工具,吵嚷着去找矿业所长。矿警鸣枪威胁,大家就不去上工。这次,连朝鲜劳工也参加了抗议行动。他们打着手势表示“我们是朋友,日本人是敌人,我们要团结,一致对付日本人。”日本监工看到劳工们的愤怒情绪,也不敢压制,只好报告矿业所长。
成田勇找程绍鲁去谈判,程绍鲁根据大家的意见,提出三条要求:一、改善工友的伙食,起码要吃饭;二、降低生产指标,减轻劳动强度;三、华工要同日本人享受一样的待遇,特别是对伤病员要认真负责地治疗,不能打毒针,冻脚不许截肢。成田勇仍然强调其理由,“粮食供应量是按产品数量定的,降低生产指标就降低了粮食供应量。不过我还是尽力想办法把大家的伙食提高一些。”他还狡辩说:“日本工人非老即小,当然只能干轻活,华工都是健壮劳动力,必须干重活,华工有伤病,我们同样治疗,绝对没有打毒药针的事,冻伤截肢是我们的治疗办法,不然也得烂掉。”程绍鲁据理力争,指出了吃粮数量与产量的差距和日本医生用药针毒死中国人的事实,说明冻伤可以治愈而截肢是错误的。在事实面前,日本人也只好做点让步。事后,运来了一部分大米,他们把大米煮熟再做成“饭团子”。华工每人每顿两个,也仅70克,仍然吃不饱。春节时大家吃了一顿小麦面饺子,饺子馅还是“海宝狗”。活还是那么累,治病除不再截肢外,其他病仍是一两片西药。说是和日本工人同等待遇,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胜利返乡
抗日战争胜利的一天终于到来了。不知是谁从日本工人那里见到了《北海道新闻》登载的“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这一喜讯不胫而走。难友们惊喜地感觉到自己精神世界中已经干枯、变形的生命之树,又抽出了新芽,并舒展地伸向太阳。他们奔跑着、叫喊着,顿时沸腾起来。有的用木棒绑上红被面尽情挥舞,有的在空地乱喊乱跑,若痴若狂。这时日本监工都不见面了,再也没人去干活。第二天大家呼喊着到街上看看情况。煤矿大门前有一条小河,河上有桥,桥头设有岗亭,是为平时阻止华工外出而设的。这时矿警还不许大家过桥,大家一时怒不可遏,将矿警打翻在地,并将岗亭推到河里,以后就再也没有矿警站岗了。难友们拥向大街,看见大街上张贴了日本投降的告示。大家剪短了头发,刮光了胡须,昂首挺胸走在大街上,日本人皆让路于一旁。晚上,大家带回白酒,尽情痛饮,有的喝得酩酊大醉。这里距北海道首府扎幌不过几十公里,第二天大家又到扎幌去游玩,在扎幌,大家看到日本人已不再那样骄横。
休息了约两个月,美国驻军通知大家回国,难友们又一阵狂欢,同时也想起了已成为冤魂的难友。经查对共找到禹城人骨灰52具,又找回了因逃亡而被关押的两个难友,已几乎是两具骷髅了,不知他俩在狱中受了多少苦刑。大家心疼地格外照料他俩,又想让其吃好,又不敢让其多吃,真担心他俩是否还能康复。大家面对一具具骨灰盒和两位枯瘦如柴的难友,不由得泪眼模糊,有的已经泣不成声。来时150人,除了死亡和下落不明者,只剩下82人了。
临行前每人换了一身日制军服,发给300元日钞作路费,于11月末乘客车抵达北九州港。在候船时,遇到了1944年被掳掠的禹城籍华工,其中有禹城、故城的陶景山、孟宪志等人。他们是与战俘关在一起的,在东京附近干活,多是装卸火车轮船的货物,无定时定量,比北海道的华工更苦。他们来时也是150人,回国时仅剩70多人了。
很快,运输日本战俘回国的美国兵舰就来到了,日本战俘下船,华工上船,每船300人。美舰行驶很快,仅四个昼夜就到了我国塘沽港。在塘沽港下了船,住在一所大学里。当时天津还是国民党占据,他们把大家集合起来,挑选年轻力壮的,说是给找工作,其实后来都补充了国民党军队。可是大部分人都思念家乡,不愿留下,就偷着开了小差,只有少数独身的留下来当了内战的炮灰。
大家的路费是日本钞票,在国内不能用,大家要求官方给兑换国币。当局以日钞作废为由均予没收,仅以免费乘火车打发回家。
火车行到沧州车站就不通了,往南是解放区,大家又用实物雇了几辆畜力大车,才回到家乡。到家的第二天夜里,1945年12月27日县城就解放了。
日本侵华期间掳掠华工人数,据日本外务省公布是38500人,而日中友好团体调查结果是十几万人。在途中和劳役中死亡者不计,仅被杀害的华工就有6000多人。象雄别煤矿这样的劳役点,全日本有153处,禹城籍华工只不过是一个点的一小部分,也可作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掳掠奴役中国劳动力的罪证之一。
被骗的人们
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对外侵略和扩张,致使日本青壮年男子均被应征入伍,国内的生产劳动者,除妇女外非老即小。所以,从1943年起,日本侵略者连续在华掳掠廉价劳动力。1943年和1944年,他们乘禹城灾荒,以欺骗、诬陷等手段,两次从禹城掠走青壮年劳动力300人。
1943年秋后,日军和伪县公署谎称“张店铝厂招工”,要抽调150名壮丁,说是“管吃管穿,每天工作八小时,工资按产量,多劳多得,每月能剩半斗粮食钱,临走还给八斗粮食(约250公斤)的安家费”。农民虽然故土难离,但为了全家人的生计,一些敦厚善良的农民就报了名。其实日本劳工协会在禹城县招募工人已不是新鲜事,早在1940年就已经开始,也是八斗谷子或高粱的安家费,大都是去东北抚顺市千金寨煤矿。农民也乐意春冬两闲出去做几个月的工,到农忙时就开小差逃回来,虽挣不到钱,家庭也能得到八斗粮食度荒,所以这次仍有部分农民报名。然而,善良的农民却不知道,这一次不是去东北,而是远离故土去日本出卖劳动力。
凡报了名的都集合到城里“山西会馆”待命。过了几天仍凑不足数,就栽赃陷害部分得罪过伪警察的人,说是“八路军的坐探”,抓来充数,总算凑齐了150人。10月份的一天上午,日军用麻绳一连串绑住每个人的一只胳膀,押解到火车站,关进了一辆铁皮“闷罐”车,由伪军警监视,运到济南,押送到原美孚洋行的仓库里。那是一座储存煤油的大房子,由日本兵看管。大家一看势头不对,就乱猜疑。有的说:“这不是去铝厂吧,可能又是下煤窑。”有的说:“是不是让咱们干伪军,去当炮灰呀?”也有的说:“反正没咱们的好果子,说不定让咱上哪里去受罪呢!”有几个曾经当过华工的人有经验,想做逃跑的准备,他们在一处背眼的墙角挖洞,可是挖了半天,怎么也挖不动,原来是水泥石头墙。十来天过去了,又从其他县拉来了许多人,凑足300人,就一齐起了解。仍然是绑着,十人一条绳。这次做押解的全是日本兵。大家被押上一辆铁皮“老闷罐”,迷迷糊糊地开了一夜。车停了,下车一看,原来是青岛车站。这时大伙都知道不是去张店铝厂了,但究竟要到哪里去还不清楚。
这时站台上已有日本兵守候在那里。在押送的路上,不但步兵多了,还增加了骑兵,开路在前。断尾在后。这些人被送到一个虽不是监狱,却戒备森严的地方,四周是高墙,墙上挂满了电网,四角都有岗楼,院子顶上还笼罩着铁丝网,房壁也无比坚厚。直待锁了大门,才给人们松了绑。天还未黑,四角上高挂的探照灯就已打开,夜晚,院子里如同白昼。虽然人们被关进天罗地网,只要有机会,大家还是要斗争,要逃亡。过了几天,一批批的青壮年被押送进来,其中有八九个穿着破旧的八路军军装,大伙明白,这是从抗日战场上来的。这几个八路军战士第二天就暗中活动,策划组织暴动,说咱们“炸”出去。有一个战士说:“现有鬼子兵力不足,咱们抢他岗上的枪打出去,就是死几个,也能大部分闯出去,到外边进山去找八路军,我领路!”这办法正符合大家的心意,哪个不想逃出这个火坑。可是只隔了一天,岗哨就增加了,四角岗楼上也架起了机关枪,枪口正对着这座大房子。下午,几百名难友在院子里排成队,一个鬼子官用生涩的汉语对大家说:“你们不要害怕,皇军要你们当工人,皇军大大的好。你的必须服从命令,逃跑的死了死了的!”不管他说什么,大家心里明白,这完全是谎话。要当工人还能捆绑着,比坐牢还严禁吗?就在这天下午,大家换上了半边红半边黑的薄棉囚服,每人还给一床薄薄的红棉被。回到屋里,有一个河南口音的八路军战士说:“咱们里头有汉奸,可能让鬼子发觉了,要不怎么鬼子今天变了样?咱们非找出他来揍死不可!”大家也都很懊丧,痛恨这个告密的,可惜最终也没找出这个人来。
第二天又让大家集合,点了名,报了数,已是600人了。这些人被捆绑着,押解到大港码头。那里早已停着一艘货轮,人们被赶进漆黑的装着煤炭的底舱,才松了绑。随着汽笛的鸣声,轮船启航了,徐徐离开了码头,驶向大海的深处。轮船开足了马力,船体颠簸得厉害,人们头晕脑胀。驶出胶州湾,一会儿就看不见祖国大陆了,轮船却渐渐缓慢下来,并抛了锚。原来日本人听到一点风声,但又不了解真情,就把这些人先运到海中,以防逃亡。
货轮在海里停了一天,又开来两艘货轮,也是每船600人。这样,一次就运走1800人。难友们都是半辈子生活在那二亩地所系的小圈子里,根本没见过海,更不用说坐轮船了。风平浪静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头晕恶心,有的呕吐起来。起初人们吐酸饭,而后吐粘沫,最后吐的是极苦的黄绿色的水,那就是胆液了。被折腾了半个多月的难友们,身体已经是很虚弱了,再经过这一阵呕吐,大多数人躺在船底爬不起来了。有些身体强壮的,虽然也头晕恶心,总算没吐出来。但船舱里那股酸臭味,也使他们难以忍受。于是便有人要求到甲板上去,让清凉的海风吹一吹。经过许可,有的人爬到甲板上去了。只见苍苍茫茫水天一色,不见边际。除了海浪,什么也看不见,除了隆隆的马达声和波涛声,什么也听不到。这是要到哪里去呢,为什么监视这么严呢,还有机会逃跑吗?一连串的问号盘旋在人们的脑海里,谁也找不出答案。由于英美飞机天天在海空巡航,日轮为躲避轰炸,时行时停,难友们才能有喘息的机会。鬼子官也怕出现死亡,就规定在风平浪静时让人们到甲板上放一次风。就这样,大家才逐渐适应了海上生活。
在门深町水银矿
轮船在海上飘泊了十一个昼夜,终于在一个小码头靠了岸。1800名难友被赶下船。大家走出码头,发现这里房舍与中国完全不同,来往行人的服装打扮也不象中国人,特别是脚趿木屐与汉民不同,难友们都惊呆了。一个日本兵见到大家惊异的神色,就奸笑着说:“这是大日本的门寺海港,你们到家了。”人们一听都怔住了,继而有的落泪,有的谩骂,人们绝望了。来到异国他乡,地理不熟,语言不通,怎么办?有的说:“日本鬼子真狠,把咱弄到这天涯海角,比充军发配还厉害呀!”有的说:“再也跑不了啦,听天由命吧。”也有的说:“只要咱能活下去,有这条小命,总会有出头的日子。”大家议论着,歪歪斜斜地被赶进一个大院子的检疫站,要人们都把衣服脱光,到药池里洗了澡,身上再涂了药,然后按十人一班,每三班一个小队,每三个小队一个中队,每三个中队一个大队,加上队长伙夫,每大队300人。第二天,人们被逼着照了单人相,以后又在贴了相片的“印表”上摁了手印。“印表”上虽然是日文,但也有一些汉字,有几个识字的看出是“日本劳工协会合同书”,最后写的是“昭和十八年(即1943年)十月二十五日。”
摁过手印的第三天,就由门寺坐上闷罐货车北去。这是一列刚刚运过牲口的货车,到处是粪便,臭气熏天。火车开开停停,走了五个昼夜,到了一个叫“青森”的车站下了车。这也是一个港口,大家又乘船渡海,到了一个叫“函馆”的地方,再乘火车继续往北开。走了一天一夜,禹城人的这个大队就到北海道的“门深町”下了车。没下车的那部分人有的去“明治矿业株式会社”挖煤,另有100人被派到农场去干活。禹城大队去的是门深町水银矿。
已经被折磨得虚弱不堪的难友们,爬出火车就被一股刺骨的寒风吹了个透心凉。雪粒象砂子一样随风打向脸庞,刀刺一样的疼。抬头四望,一片白茫茫,都是被大雪覆盖的群山。难友们抱头缩颈,东倒西歪地被带到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坳里。这里地处北纬45度,相当于我国的大兴安岭地区。因为北海道四周环海,风雪特大,气温常低于摄氏零下40度。山脚下有一个大雪堆,雪堆的向阳处有一个黑洞,那就是工棚。门口的周围用稻草和席帘子围着,以防大雪堵门。工棚完全用木板搭制,每个中队住一个工棚。这时难友们还穿着在青岛换上的那身薄棉囚服,每人一床小薄被,怎能抵御如此的寒冷?晚上人们就两人通脚睡,把铺草堆厚一点。两床被子摞在一起。开始大家都睡不着,低声谈论着,盼望日本鬼子被打败,好回家团圆。终因多少天来的困乏,后来都睡着了。但由于天气寒冷,不少人又被冻醒了,大家挤在一起苦熬着这漫漫寒夜。
第二天刚放亮,刺耳的哨子就吹响了。大家起来围坐成一个圆圈,点过了名,每人发给一双大草鞋,这是为适应白天外出干活踏雪用的。然后由伙夫在每人面前摆一只碗,每人一勺稀粥,喝完了再添一勺。大家都嚷着吃不饱。伙食管理员是日本人,他说:“咱们矿上粮食是按生产矿石的数量配给,你们还没干活,哪有粮食?现在有吃的就不错了,你们以后生产量大了会多给吃的。”大家还是乱喊,“吃不饱能干活吗?”却也无济于事。大概难友们的不满引起了日本人的警觉,这天中午饭时,来了个身穿军服留着通鼻胡子的瘸腿鬼子,向大家训话。他叫宇宫,日文音是“乌勾”,大家就叫他“母狗”太君。这个军人气派十足,一脸凶相,据说是从侵华战场上退下来的伤员,是一个饱蘸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他退役后就当了水银矿的作业所长。他用不规范的汉语说了一些“日华亲善”、“干活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等骗人鬼话之后,又说:“你们来到大日本干活是走运的,在这里干活多粮食多,大日本不会亏待你们的。”他最后说了些水银矿的作业程序和必须服从命令的话,“不服从也逃跑不了,北海道是个大岛,四周环海。全岛大山多,人烟稀少,山里花脸狗熊、野狼成群结队,即使让你走,你们只能饿死冻死,或被野兽吃掉。凡逃跑抓回来的,统统死了。”中午饭的粥中又加上了一些糖渣,还有两片马铃薯,这也算是大发慈悲了。当时日本施行配给制,一个日本监工每顿一盒饭,半边大米半边青菜马铃薯,虽然比劳工吃得好些多些,但也吃不饱,所以就克扣劳工的口粮。
第三天开始干活,先由日本人爆炸矿山,然后让华工用土篮挑水银矿石。从矿山挑到火车道旁有15町(日制长度单位,一町109米,36町为一日里),这是水银矿上最脏最累的活。干活以后不喝稀粥了,换成了玉米、马铃薯粉和橡子面混合的窝窝头,每人每顿两个。300人每顿20公斤粮食,每人只有1.4两多,小饭量的半饥半饱,大饭量的只能挨饿。有时每人给一片萝卜咸菜,有时每人一箸子叫“海宝狗”的野生海藻咸菜。春节那天,也不过用相当于两个窝窝头的面,包上些“海宝狗”馅,做成大蒸包让大家吃。
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造成本国劳动力不足,管理人员也太少,一个300人的大队,只有三个日本监工。他们懒得呆在矿上受冻,就采用了“以华制华”的办法,从华工中找一个识字的为他们记数落账,禹城人程绍鲁被他们选中了。程绍鲁考虑到这对难友们有利,就满口答应下来,当了副大队长。难友们挨饿受冻,谁愿意给日本人干活。从程绍鲁记帐以后,他们就用消极怠工来对抗,不管土篮里挑了多少矿石,过去一趟就记一担,有时干脆挑着空篮来回走,只要日本监工不在,大家就这样应付。
北海道冬季夜长昼短,白天只有八小时,矿山又无照明设备,所以无法延长工时,因此天天欠产,日本人就想出了规定任务的办法,确定每天的工作量,完不成不给饭吃。人们的工作加重了,但粮食并未增加,饭食质量又差,饭量大的顶不住了,身体弱的熬不过了,渐渐地一个一个倒下去。越是病号多,粮食越少。病号每顿只给一个窝窝头,有的病号饿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去看病也只给几粒极贱的西药片,根本治不好病。病号只吃粮食不生产,成了日本人的累赘。于是他们想出了一条毒计,设了一个重病号房,说是给病号打针,有几个重病号进去打针,刚拨出针头人就咽了气,这显然是让其速死。后来人们情愿在工棚里也不去病号房了。就这样今天死一个,明天死一个,一个冬季就死了百十个人,其中禹城籍的就有30余人。为了让华工服服贴贴地干活,每当死一个劳工,日本人还要假装出一副慈善面孔,请僧侣诵经祈祷,最后每个死者用一公斤煤油点着木柴烧掉算完。
春节时刻,难友们倍加思念家中亲人,背地里就商议逃跑。但是,在冰雪封地时逃跑会留下足迹,也跑不快,很容易被抓回来。到春季冰雪融化,矿场周围的电网就通了电,更难以逃跑了。有两个难友在想,若不逃跑,早晚也得折磨死,跑出去或许能找到条活路。他俩想趁冬季走,为了避免留下足迹,就从铁路上顺着走。两个难友,其中有一个姓刘的禹城人,就于一天夜里逃出矿场,顺铁道奔跑。那北海道的风雪扑到脸上,打得生疼,又睁不开眼,透不出气,能见度也只有20米,所以他俩走的并不快。当矿警发觉时,也不知他俩的去向,由于矿上人员少,他们没有去追。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矿业所长让矿警严密把守工棚绝不能因小失大。这一夜大伙也没睡好,第二天日本人又威吓了大家一番,也就算了事啦。
两难友顺铁路往北跑,遇到车站绕道而过,有火车过路就躲避,艰难地走了半夜。眼看就要天亮了,两人合计:“咱俩穿着这身囚服,被人看见就得抓起来,咱得想办法换衣服。”他俩看见附近有个值班房,就壮着胆子过去,抓住值班员。值班员见是两个蓬头垢面的大汉就吓懵了,“嗷嗷”地呼喊。他俩先塞住值班员的嘴,然后脱下他的外衣,把他绑起来。又抓住另一睡觉的值班员,他俩一人换了一身标制服,穿上毡靴,就逃走了。
两人换了衣服就大胆了,心想往北走或许能走出日本地,就能到关外了,日本人不是有很多在关外的吗?就是走不到关外,走到苏联也好,也许能转回家去。可是走了一天也没走到尽头,问路吧,又语言不通。一天没吃到东西,饿得实在难受。傍晚,他俩走进一个村子,想讨顿饭吃,村头一家门上挂着“军国之家”的牌子,标明这一家是在侵略战争中死亡的士兵家属。他们走进房门,在土间(日本贫民的外室无地板,是土地面,故称土间)听到室内一个妇女和孩子一边吃饭,一边讲话。他俩一人在外了望,一人进屋去讨饭。因为是穿着铁路标制服,那女人还不十分害怕。他俩不会说日语,只能打着手势说“米西米西”。那妇女给他俩各盛了一碗掺有马铃薯的米饭,这在日本称“菜饭”。当时日本人民也是粮食不足,同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他俩虽然没有吃饭,也不忍心再要了。因为这家只有妇女和孩子,不便久留,他俩就告辞走了。
他俩没走多远,就遇见一个50多岁的老汉,即搭讪着想再讨些饭吃,老汉满口答应,把他俩领回家去,安排吃饭住宿。他俩吃完了饭,躺下还没睡着,就有两个警察持枪闯进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他俩抓走了。原来他俩换衣服不久就被铁路当局发现,铁路沿线通过电话布置搜查两个穿铁路标制服的支那人。日本农村也通电话,那老汉就是该村的村长,所以村长一见到他俩,就知道是逃亡华工。他先把他俩稳住,然后通报了当地警察署。经警察署审讯,他俩被押解到扎幌厅(北海道首府)警察本部,以抢劫罪判处徒刑三年,被关进刑务所(大狱)。
转往雄别煤矿
1944年4月,水银矿停止了开采。由于伤亡人数过多,所剩华工被转移到“雄别煤矿”去挖煤,而雄别煤矿的华工伤亡更为惨重。到雄别煤矿后,照例是矿业所长训话。这是一个肥胖的老鬼子,留着仁丹胡,长了一脸横肉,把眼睛挤成一条缝。据说他自幼就在中国哈尔滨,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是个中国通,因为他对统治中国人有一套办法,就让他当了矿业所长。他原名叫成田勇,为拉拢华工,改姓唐,按日语语音难友们称他“挑太君”。他说:“你们如果干得好,干得快,可以提前回家,换另一帮华工来顶替你们。”他是一个笑面虎,不象水银矿的矿业所长那样苦丧着脸。这里的监工也不象水银矿的监工,皮鞭棍子不离手,“八格亚鲁”不离口,从来不见笑模样。不知是日本人接受了去年的教训呢,还是另一种统治办法。不过难友们明白,他们是笑里藏刀,大家还是十分警惕的。
这里是一个老矿区,原煤层早已挖完,只剩下了一段段的薄煤层,用不上机械,只能手工开采,由于劳动条件太差,华工们只能用手挖,用肩运,既苦又累。每天昼夜两班,实际工作超过13小时,比水银矿的工时还长。特别是夜班,作业十几个小时,中间没有加餐,大家实在饿得难熬。因每周一次换工,所以一些体弱者经常病倒。但病号多了必然影响生产。一天,矿业所长成田勇找程绍鲁谈话,“工人病员太多,我们赔本大大的,你有办法解决吧?”程绍鲁说:“在我们中国,病号都是吃好饭调养。工人本来就吃不饱,是饿出来的病。病了不但吃不上好饭,反而减少粮食,病不更重了吗?病号饭换成大米就好了。”成田勇叹了口气说:“大米实在难得啊!我尽量想办法吧。”从此,凡病员就改供大米稀粥了,有时给点海带咸菜,还弄来一点小干鱼片给病员吃。
日本监工有一个叫小松的,按照日文读音,难友们都叫他“三麻子”。在一个夏天夜晚,三麻子找到了程绍鲁,悄悄地说:“我是日本共产党员,你们这些人里有共产党员吗?我想和他们联系一下。”程绍鲁半信半疑,心里想:“是听说日本也有共产党,但不知是真是假,等和难友们商量好了再说。”就回答他说:“我是不知道,待我问好了告诉你”。以后程绍鲁就暗地里与几个被俘的八路军战士商量,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其中有一个河南人是个干部,他说:“日本是有共产党,如果能联络上,组织起来是好,现在日本本土已无精锐部队,到山里去打游击也撤他的后腿。死了也值得。若是骗人就是无谓的牺牲,不如你去报告有八路军没共产党员,看鬼子怎么办?如果鬼子抓人,我就发动大家给鬼子讲理,同时揭露日本人的假面具。”大家都同意了这个办法,程绍鲁就向三麻子报告了几个被俘的八路军战士。
过了些日子,三麻子告诉程绍鲁,他在山里埋着有枪,让程绍鲁联络人去山里打游击。一天,三麻子领着程绍鲁走进一个黑黝黝的山谷里,扒开草丛浮土,看到埋藏着十几支步枪。三麻子随即埋上,说组织好了人员就去打游击。程绍鲁回来,大家就商量着组织起来去打游击。但不久,几个八路军战士和程绍鲁被一齐抓进监狱,而三麻子却仍然干他的监工。
大家知道了这是一场骗局。那个河南籍八路军干部一动员,大家气愤填膺,一致同意罢工。他们拿起锨、镐、木棒、去找三麻子。“工友们没罪,该逮捕三麻子。”这时,三麻子已不知溜到哪里去了。大家找不到三麻子,又拥到矿场大门,喧嚷着去找矿业所长,矿警持枪阻住大门,并鸣枪威胁。人们仍在大门里吵闹着不去上工。另外几个监工也避在一边不敢出来。不久,成田勇坐着汽车赶来,向大家解释说“叫他们去,不过是教育他们不要上共产党的当。教育好了,保证把他们放回来。工友们都回去干活吧!”由于矿上生产很不景气,工伤事故不断发生,上级矿业株式会社曾批评、警告过雄别煤矿。如果再因此事影响了生产,恐怕这矿业所长的位置就不牢固了。所以他不敢激怒全体劳工,第二天就开始放人,最后都放了回来。三麻子又重新出现,仍然当他的监工。
1944年,日本侵略者在各战场连遭失败,军用物资供应不上,故此军需生产部门强行增加任务指标,妄图挽救其败局,雄别煤矿也同样强制劳工多干、快干,在无劳动保护的条件下,工伤事故越来越多。难友们的仇恨压抑在胸中,个个咬牙切齿,怒火中烧,痛恨日本统治者。
是冬,有几个难友冻伤了手指、脚趾,让场医施药,不料却被截肢。禹城籍华工张明,是来凤乡张庄人,他就是因冻伤被截去双脚的。以后再有冻伤手脚的也无人敢去敷药了,但难友们心中埋下了反抗的种子。第二个春节即将到来了,商河县十七岁的孔××因想念家乡亲人,又泛起了逃跑的念头。他听说北海道北端与苏联的库页岛隔海相望,苏联又和中国相连,只要能跑到库页岛,就能回家。即使被抓住,坐牢也不干这活了。就凭这幼稚的想法,他一个人逃出了矿场。也不知他是怎么走的,居然走到了海边。他偷爬上人家的渔船,被赶了下来。后来冻伤了双脚,走不了路,又被送回了煤矿。这次孔××被抓回来,没送他去警察署,而是以治伤为名被截去了双脚,成为终生残废。
这件事激起了难友们的义愤,积压在心底的怒火终于爆发出来。大家手持工具,吵嚷着去找矿业所长。矿警鸣枪威胁,大家就不去上工。这次,连朝鲜劳工也参加了抗议行动。他们打着手势表示“我们是朋友,日本人是敌人,我们要团结,一致对付日本人。”日本监工看到劳工们的愤怒情绪,也不敢压制,只好报告矿业所长。
成田勇找程绍鲁去谈判,程绍鲁根据大家的意见,提出三条要求:一、改善工友的伙食,起码要吃饭;二、降低生产指标,减轻劳动强度;三、华工要同日本人享受一样的待遇,特别是对伤病员要认真负责地治疗,不能打毒针,冻脚不许截肢。成田勇仍然强调其理由,“粮食供应量是按产品数量定的,降低生产指标就降低了粮食供应量。不过我还是尽力想办法把大家的伙食提高一些。”他还狡辩说:“日本工人非老即小,当然只能干轻活,华工都是健壮劳动力,必须干重活,华工有伤病,我们同样治疗,绝对没有打毒药针的事,冻伤截肢是我们的治疗办法,不然也得烂掉。”程绍鲁据理力争,指出了吃粮数量与产量的差距和日本医生用药针毒死中国人的事实,说明冻伤可以治愈而截肢是错误的。在事实面前,日本人也只好做点让步。事后,运来了一部分大米,他们把大米煮熟再做成“饭团子”。华工每人每顿两个,也仅70克,仍然吃不饱。春节时大家吃了一顿小麦面饺子,饺子馅还是“海宝狗”。活还是那么累,治病除不再截肢外,其他病仍是一两片西药。说是和日本工人同等待遇,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胜利返乡
抗日战争胜利的一天终于到来了。不知是谁从日本工人那里见到了《北海道新闻》登载的“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这一喜讯不胫而走。难友们惊喜地感觉到自己精神世界中已经干枯、变形的生命之树,又抽出了新芽,并舒展地伸向太阳。他们奔跑着、叫喊着,顿时沸腾起来。有的用木棒绑上红被面尽情挥舞,有的在空地乱喊乱跑,若痴若狂。这时日本监工都不见面了,再也没人去干活。第二天大家呼喊着到街上看看情况。煤矿大门前有一条小河,河上有桥,桥头设有岗亭,是为平时阻止华工外出而设的。这时矿警还不许大家过桥,大家一时怒不可遏,将矿警打翻在地,并将岗亭推到河里,以后就再也没有矿警站岗了。难友们拥向大街,看见大街上张贴了日本投降的告示。大家剪短了头发,刮光了胡须,昂首挺胸走在大街上,日本人皆让路于一旁。晚上,大家带回白酒,尽情痛饮,有的喝得酩酊大醉。这里距北海道首府扎幌不过几十公里,第二天大家又到扎幌去游玩,在扎幌,大家看到日本人已不再那样骄横。
休息了约两个月,美国驻军通知大家回国,难友们又一阵狂欢,同时也想起了已成为冤魂的难友。经查对共找到禹城人骨灰52具,又找回了因逃亡而被关押的两个难友,已几乎是两具骷髅了,不知他俩在狱中受了多少苦刑。大家心疼地格外照料他俩,又想让其吃好,又不敢让其多吃,真担心他俩是否还能康复。大家面对一具具骨灰盒和两位枯瘦如柴的难友,不由得泪眼模糊,有的已经泣不成声。来时150人,除了死亡和下落不明者,只剩下82人了。
临行前每人换了一身日制军服,发给300元日钞作路费,于11月末乘客车抵达北九州港。在候船时,遇到了1944年被掳掠的禹城籍华工,其中有禹城、故城的陶景山、孟宪志等人。他们是与战俘关在一起的,在东京附近干活,多是装卸火车轮船的货物,无定时定量,比北海道的华工更苦。他们来时也是150人,回国时仅剩70多人了。
很快,运输日本战俘回国的美国兵舰就来到了,日本战俘下船,华工上船,每船300人。美舰行驶很快,仅四个昼夜就到了我国塘沽港。在塘沽港下了船,住在一所大学里。当时天津还是国民党占据,他们把大家集合起来,挑选年轻力壮的,说是给找工作,其实后来都补充了国民党军队。可是大部分人都思念家乡,不愿留下,就偷着开了小差,只有少数独身的留下来当了内战的炮灰。
大家的路费是日本钞票,在国内不能用,大家要求官方给兑换国币。当局以日钞作废为由均予没收,仅以免费乘火车打发回家。
火车行到沧州车站就不通了,往南是解放区,大家又用实物雇了几辆畜力大车,才回到家乡。到家的第二天夜里,1945年12月27日县城就解放了。
日本侵华期间掳掠华工人数,据日本外务省公布是38500人,而日中友好团体调查结果是十几万人。在途中和劳役中死亡者不计,仅被杀害的华工就有6000多人。象雄别煤矿这样的劳役点,全日本有153处,禹城籍华工只不过是一个点的一小部分,也可作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掳掠奴役中国劳动力的罪证之一。
相关地名
禹城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