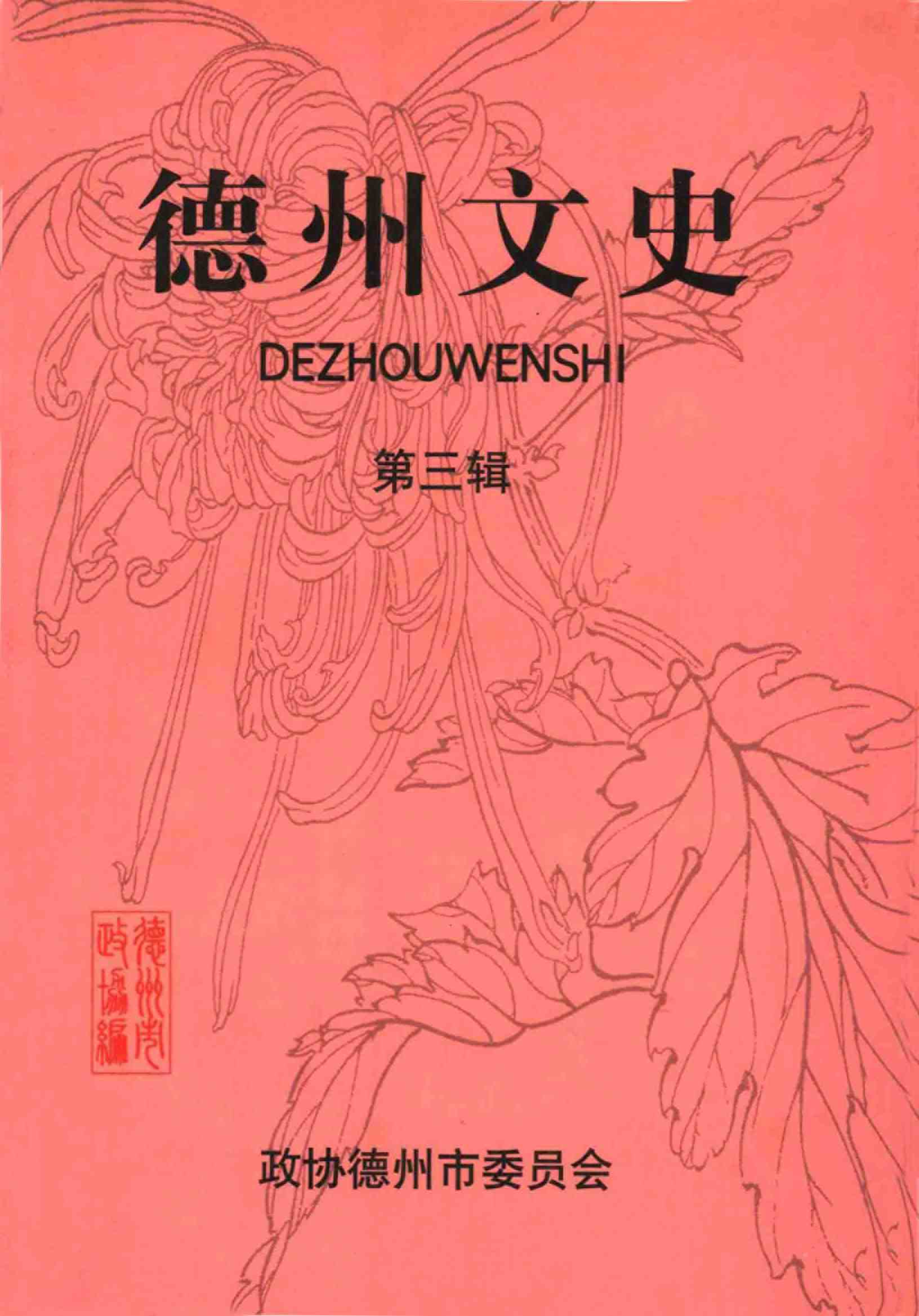内容
1976年,命运之神把我推上段庄村党支部书记的岗位。我当时22岁。那一年秋季,我们这个地区秋雨连绵,低温早霜。记得是八月下的霜,玉米根本没熟,俗话说,“肥不过六月雨,瘦不过八月霜”。历史上有名的金段庄,经过“十年动乱”,穷和乱已经在全县出了名,县委派县法院和县公安局组成工作组在这里坐阵,当时我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粮。一进腊月,全村190户人家已经有70多户断粮了。我一户一户访问断粮户,不知有多少夜晚,翻来覆去不能入睡,那面黄饥瘦、明显缺乏营养的儿童;那一家人围坐在昏暗的油灯下,为柴米而啜泣的情景,使我的心碎了。我当时读了不少马列的书,如《政治经济学》、《列宁全集》、《共产党宣言》,还研究过《中国通史》,但面对现实却束手无策。有一天晚上,我翻身而起,抓着自己的头发往墙壁上碰了三下,大喊了一声“不解决段庄人吃饭的问题,我誓不为人”。当时我已结婚,大女刚刚出生,妻子吓得呆呆发愣,以为我疯了。
好大的雪。1976年的腊月23,正是灶王爷上天的日子。在这一天的下午,我叩开了公社王秀生书记的办公室。门开了,我发现在座的还有许万沂副书记、郭尚廷副书记,好象开什么会。“你们在开会吧?”我连忙又退回来。雪下得正紧,三个书记都出来了,他们把我让进屋里,上下打量着我,好一会没有说话。
因为当时我实在寒酸得很,一件破棉袄,两个袖子上露着棉絮,一双球鞋前面也露着大拇指。也许正是这些感动了这几位老书记,他们静静地听着我的汇报,不时地点点头,结果,正月十五之内10万斤统销粮到户。我踏着风雪回家,天很冷,但我觉得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我心里明白,没有这10万斤统销粮,1977年的春天段庄将不知如何度过。
1977年的春节,段庄没有一户放鞭炮的。当年我高中毕业后,研究过几天古诗,就在这一年的除夕之夜,自斟自饮,面对红烛,心潮起伏,填词一首《满江红》:除夕之夜,独对红烛夜难熬,风也潇潇,雪也潇潇……
探索农村改革之路,我是在1977年春开始的。当时10万斤统销粮上级如期如数分到各家各户,我在正月初六就掀起春季生产高潮。当时我年轻气盛,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我不管你哪个家庭哪个派,不管是横的、楞的、还是不要命的,我只知道春不种,秋不收,不收我们吃什么,谁要是不出来参加劳动,我的拳头可是六亲不认。”这一招也起了作用,只15天,段庄1000亩白茬地普浇一遍水,公社还在段庄开了现场会,表扬了我。乱了十年的段庄一时得到了安定,我好似看到了一线希望。但好景不长,2月2刚过,段庄又乱套了,劳力大部分外出,生产队长连一个人也召集不起来。一个老支部委员找到我说:“九岭啊,这样不行,10万斤统销粮看起来不少,但人们根本没钱买,你知道我正月十五之内是怎么过来的吗?只有60斤萝卜呀!”说到这里老支委已泣不成声了。这件事使我陷入了深思,是啊,分到社员手里的粮食没人买得起,拿出一半到自由市场卖掉,用那一部分差价再买另一半,这样一来,十万斤就成了五万斤,谁也能算出这个帐。生存是人的本能,为一家糊口,他们只有去下苦力,去邯郸拉煤、拉草,到济南造纸厂,全凭一个人拉车步行。当时还过黄河摆渡,有的累得半路吐了血。接连几天,我陷入痛苦地思考中。我召开了支委会,展开讨论,我问一个老支委:“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候用的一人三分保本田,好使吗?”“灵得很!”是啊,三年自然灾害时,我村那年春饿死了18口,可眼下段庄已死了8口,没别的路了,分吧!我立即召开了支部扩大会议,吸收小队长和会计参加,每人2分,用自留地的名子,分好地,离开大路,也就是上级走不到的地块,统一种春玉米。要保密,亲戚家也不准走露消息。有人问:“县公安、县法院就在咱眼皮底下,他们知道了怎么办?”“我已顾不得这些了,路走到哪里算哪里,坐大牢,我去。”事情进行得异常顺利,第二天黎明各队开始活动,一天之内150亩地全部到户,半月之内苗全齐旺。这一招还真灵,段庄又安定下来了,准备下关东的也放下了铺盖卷,人们好象看见了希望,麻木的脸上开始露出一丝笑容。是啊,多好的农民,他们十分听话,大白天在自留地里一个人也不见,只是晚上或黎明之前干这些活,并且没有一个人走露风声。日子一天天过去,有一次工作组长韩敬安同志(当时县法院民厅厅长)和我一块出去转,他故意领我去自留地方向。我发现苗头不对说:“那地方不好走,咱到别处去看看。”他坚持要去,于是我们进入了羊肠小道。真来到自留地了,事也凑巧,一个10多岁的小姑娘正在拿一个小袋子给玉米施肥。韩厅长问:“那小孩在干什么?”那小姑娘看见我们连忙趴下了,但我们却看见了。我说:“可能在拔草。”“我看不是拔草。”“调皮的孩子,不知干什么,不管她。”韩厅长笑了笑,我们又往前走。“我怎么看这地象是一家一户的?”“哪能呀,韩厅长真会说笑话,哪能是一家一户的呀,分明是集体的吗,只不过这块长得好了点。”韩厅长只看着我笑了笑,再也没说什么。实际上韩厅长早就知道了,只是我们之间谁也不挑明罢了。
77年麦收不久,几个队长找到我,说生产队上栽地瓜(麦茬地瓜),没钱买秧子,当时分自留地已尝过甜头,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分下去,让社员自己想办法。队上统一开垅,看上去象集体的一样就行。每人三分地,不要靠大路太近。这次连支部会也没开,更没向工作组汇报。这法子灵得很,以前,这些活最少干5天,分下去之后,两个下午就完成任务。当时几个队长为我担心,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扯了龙袍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是的,反正是豁出去了,人么站着、躺着一样长。这样每人就有半亩地在手,秋后差不多每人就能有400斤粮食,基本够吃的了,劳力在队上还能分一部分,也不违背社会主义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事实证明这一步又走对了。后来自留地被县里人走迷了路无意中发现。我差一点没进大牢,多亏了县公安局、县法院。记得石院长、孙局长、王局长都为我奔走:“九岭有缺点错误让他改就是了,撤了他,谁去段庄收拾乱摊子。”这些话真管用。段庄打派仗远近有名,没有两下子谁也不来段庄找头疼。但是他们也不清楚,自留地的背面还隐藏着一条更可怕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件事没有瞒住韩厅长。有一次韩厅长在工作组和我喝酒,他突然背过身去象背台词一样:“自留地这个问题吗,县委没有《国务院60条》大,有人竟然吃了熊心豹子胆,在法院的眼皮底下走资本主义道路,真的要坐牢的,太年轻啊,太年轻,可惜啊!”我想这下子算完了。他忽然回过身冲我一笑:“我这人有个毛病,就是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天意如何吧!”我放心了,我知韩厅长为人耿直,不会坏我大事,但他也为我捏一把汗,他也有责任。当时我想,地是分了,听天由命吧。说到这里不能不提一下我们的村民,要是当时有一个人告状,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977年一进腊月,奇迹般地听到了鞭炮声,除夕之夜,大街上张灯结彩。我绕大街一周,看到孩子们穿上新衣服,脸上带着笑容,那高高兴兴的样,忍不住热泪盈眶。望着这万家灯火,暗暗说了一句:“衣食足则知耻荣。”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个村子虽小也是一个小小的世界。有人说支部书记是“小国之君”,我认为也不为过。当家人的心是黑是白百姓心中自然有杆称。一个老人对我说:“这一年你只走了两步,一步一层楼。”我对他说我还要走三步、四步,一步一层天。他所说的两步,一步是二分自留地,一步是三分“口粮田”。1978年一开春,我又每人三分春地,全部种春地瓜,当中穿种芝麻,秋种时种麦子,队上只留一少部分,不超过30亩,其余全部分到户,自种自收。1979年粮田地已全部到户,棉田地无论如何还是没有敢动。这时段庄彻底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吃不了还可卖一部分,地瓜加工成粉条,也可卖一部分钱,劳力多的还能分到一部分。我的工作也十分顺手,还经常受到上级的表扬。这一段时间我狠抓了干部的素质教育,使他们廉洁奉公,不多占社员一分钱。事实也是这样,我们村的干部十几年来没一个因贪污多占犯错误的。村里也十分安定,没有一个上访告状的,甚至连打架的、骂大街的也没有。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我敢说当支书十二年没喝过社员一滴酒,没贪过社员一分钱,相反哪一年也要赔进集体几百元。我自己规定:上级来人在我家吃饭一年只领一百元补贴,多了自己掏腰包,其他成员这样的补贴一分也没有。
1979年冬,那时三中全会已开过,我开始考虑在棉田地上作文章。我想:有组织地施行承包,老百姓真能富起来,通过3年来的试验证明是一条可行之路。我是共产党员,应当把这个经验推广出去,让全公社、全县以至全国的老百姓尽快解决温饱问题。但就我自己的力量无论如何也是无能为力的,必须有党委的支持,也就是最起码的一条得公开。有一天县委副书记徐士高来段庄,他是从外地调来的,来夏津后对段庄问题有些耳闻,但具体情况不甚了解,确切地说,当时关于段庄分地的情况,上头只是听到一些传闻,真实情况只有段庄人心里明白。在谈话时我发现徐书记思想开放,为寻求一条农村改革的道路,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只带一个秘书,我把真实情况全盘告诉了他,把下一步实行全盘承包的计划也告诉了他,得到他的充分肯定和赞赏。他临走时吩咐:“你充分做好准备,我向县委汇报,把你的经验推出去。”就在1979年冬天我接连开了几次支部扩大会议,研究如何全部承包的问题。实际上是轻车熟路,一个月的时间关于怎样承包的一系列问题就做好了计划。
1980年初春,县委徐士高副书记来搞责任制试点,在公社的大办公室里,召开了全体脱产干部会议,吸收33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参加,在这次会议上展开了东李公社一次空前的大讨论,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承包责任制符合不符合中央精神。当时中央没有明确规定搞什么分还是包,徐书记讲:“要解放思想,如果只按中央文件办,那是照章办事,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要我们解放思想。”接着大家展开讨论,如现有的集体财产怎么办,军属五保户怎么办,收了棉花不卖给国家怎么办,不在夏津县卖怎么办……。最后竟吵成一锅粥,谁也听不清谁在说什么,有的扯着嗓子喊,有的面红耳赤,瞪着眼呲着牙。我坐在最后面的墙角里静静地听着,最后王秀生书记站起来,挥舞着双手让大家停下来,好一会儿会场才静下来。“让段庄支部书记发表一下意见,看他有没有高招。”我站了起来,手里拿着一个大烟斗,人们把目光都投向我,因为当时我20几岁,是全公社支部书记中最年轻的一个,在我们这个地方年轻人没有一个吸烟用大烟斗的,我赶紧放下烟斗,开始发表我的看法:“三中全会文件上有这么一条,在我国边远地区可以搞承包到组,我认为边远地区是因为贫困,也就是贫困地区可以这样做,我们是贫困地区就等于边远地区,所以说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我说完这些话,有些人觉得有些道理,我听着好象有人说了一句“对!”徐副书记喊了一声:“你接着讲。”“粮田不在计划的可以按人口平均分,国家计划这一块我们可以按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人七劳三,多劳多得’,叫做承包到组,责任到人,不叫包产到户,更不叫分散单干。”“好,有道理。”徐副书记说。我接着说:“关于集体财产如大牲畜、机器什么的,可以折价卖给社员,得来的钱发展再生产,打机井什么的,机井要统一管理,保证每户使上水,这是干部的责任。”关于棉花不卖给国家和不卖给夏津这个问题,我回答得也很风趣,我说:“这个问题不需考虑,哪里给的钱多上哪去卖,就是卖到台湾也出不了中国地盘,还可以卖给美国、日本、加拿大。”有些人笑了,很多人提出的问题我都一一做了回答,像答记者问了。最后有人问:“这样干你觉得段庄秋后向国家交多少皮棉?”“十万斤吧,我准备比去年翻一番。”我说得象讨颗烟那么轻松。在坐的都有些震惊,好大一会儿,一个人也没有吭声。县委徐士高副书记、公社王秀生书记、许万沂副书记几个人好象同时站起来:“分,坚决地分。分不开的,不会分的,让陶九岭教你们。”
散会了,徐士高抓着我的手说:“我喜欢听京剧,今天你演了一出叫诸葛亮舌战群儒,我给你喝彩。”我只是笑了笑,说:“我无古人之风,更无诸葛亮之才,关于喝彩,秋后吧。”“好,秋后你交十万斤,我来给你开庆功大会,就这样。”也就是在这一年,东李公社全面地实行大包干,翻开了农业改革历史上新的一页。
1980年,我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我终于能甩开膀子,施展我的才华了,至于是怎样分或是怎样干的,我想现在已是俗套,不必赘言。但是有一点我需要说,这一年我掉了二十斤肉,但是秋后卖的皮棉超过了十万斤,段庄人均分配一下跃入全县第一。我笑了,哭了,同时也醉了。我没有什么语言,去描绘当时那幸福的情景和心情……
徐士高副书记庆功来了。公社王秀生书记、许万沂副书记、郭尚廷副书记都来了,我们同席而坐,酒杯举得高高的。随之而来的是记者:新华社的、人民日报的。在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县委书记刘风岐听完我的发言之后,高兴得无以言表:“好小陶啊,好小陶啊,全县学小陶啊,学小陶,小陶是何等的好啊……”。当时团县委书记房玉梅问我:“你的感想是什么?”我只说了一句:“我感动了上帝。”房玉梅叹了一口气。我们在一块当过公社团委副书记,她对我是了解的。段庄沸腾了,80年的除夕之夜,鞭炮一直到零点未停,我醉了,但不是自斟自饮的76年了,我邀来了几位支委共度这除夕之夜,良宵美酒,我欣然命笔:“曾几何时,风雨伴我走春秋,风也停了,雨也停了,风雪自此不潇潇……”
是啊,忍饥挨饿的日子,在段庄一去不复返了。我终于胜利了,段庄人终于过上好日子了。
1981年我除了深入完善我的大包干之外,主要是接待记者和作家的采访,再就是给各地介绍落实责任制的经验。1981年开始就成了鲜花盛开的日子了,《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大众日报》、《山东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杂志社、《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文汇报》……先后介绍和报导了段庄实行责任制的情况和取得的成绩。
新闻媒介把段庄的做法迅速传遍全国各地。1980年底或是81年初,陕西省一个大代表团来我县,据说当时陕西省党委书记是山东人,听说老家实行大包干,派了3个地区的3个地委书记,30来个县委书记和报社记者,来老家取经。山东省委派一个粮食厅副厅长带领他们来夏津,县委书记用专车来段庄接我。在县委招待所的大会议室里,徐士高副书记和我接待了他们。记得开会前徐书记嘱咐我:“今天你面对的都是不小的官,不要怕,他们是来学习的,大胆地讲,讲好了,不但露夏津的脸,还给咱山东露脸。”我一笑说:“既然是来学习的,我不管官大小,都是我的学生,世界上那有老师怕学生的道理。”就这样,我详细地介绍了有关怎样分地的情况,然后就是回答他们不明白的问题。整整一个上午,他们很认真,提的问题也很具体,我一一为他们做了满意地答复。最后一个同志问:“用简单的话说,大包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说:“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1981年,段庄人均分配800元以上,段庄用上电,我买来彩电,每天晚上在大街上演,邻近村里的人们来看段庄怎样拥抱现代文明,我不必细讲。房玉梅向团省委汇报了我的情况,受到团省委的重视,孙淑义书记专程来我家看望我,并在全省青年中树我当标兵。
1982年我赴省参加新长征突击手表彰大会,会上我第一个发言,用记者的话说,我得了这次会议的“单打冠军”,在长时间的鼓掌中我再一次向台下鞠躬谢幕。之后我在山东作巡回报告。
1998年底
好大的雪。1976年的腊月23,正是灶王爷上天的日子。在这一天的下午,我叩开了公社王秀生书记的办公室。门开了,我发现在座的还有许万沂副书记、郭尚廷副书记,好象开什么会。“你们在开会吧?”我连忙又退回来。雪下得正紧,三个书记都出来了,他们把我让进屋里,上下打量着我,好一会没有说话。
因为当时我实在寒酸得很,一件破棉袄,两个袖子上露着棉絮,一双球鞋前面也露着大拇指。也许正是这些感动了这几位老书记,他们静静地听着我的汇报,不时地点点头,结果,正月十五之内10万斤统销粮到户。我踏着风雪回家,天很冷,但我觉得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我心里明白,没有这10万斤统销粮,1977年的春天段庄将不知如何度过。
1977年的春节,段庄没有一户放鞭炮的。当年我高中毕业后,研究过几天古诗,就在这一年的除夕之夜,自斟自饮,面对红烛,心潮起伏,填词一首《满江红》:除夕之夜,独对红烛夜难熬,风也潇潇,雪也潇潇……
探索农村改革之路,我是在1977年春开始的。当时10万斤统销粮上级如期如数分到各家各户,我在正月初六就掀起春季生产高潮。当时我年轻气盛,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我不管你哪个家庭哪个派,不管是横的、楞的、还是不要命的,我只知道春不种,秋不收,不收我们吃什么,谁要是不出来参加劳动,我的拳头可是六亲不认。”这一招也起了作用,只15天,段庄1000亩白茬地普浇一遍水,公社还在段庄开了现场会,表扬了我。乱了十年的段庄一时得到了安定,我好似看到了一线希望。但好景不长,2月2刚过,段庄又乱套了,劳力大部分外出,生产队长连一个人也召集不起来。一个老支部委员找到我说:“九岭啊,这样不行,10万斤统销粮看起来不少,但人们根本没钱买,你知道我正月十五之内是怎么过来的吗?只有60斤萝卜呀!”说到这里老支委已泣不成声了。这件事使我陷入了深思,是啊,分到社员手里的粮食没人买得起,拿出一半到自由市场卖掉,用那一部分差价再买另一半,这样一来,十万斤就成了五万斤,谁也能算出这个帐。生存是人的本能,为一家糊口,他们只有去下苦力,去邯郸拉煤、拉草,到济南造纸厂,全凭一个人拉车步行。当时还过黄河摆渡,有的累得半路吐了血。接连几天,我陷入痛苦地思考中。我召开了支委会,展开讨论,我问一个老支委:“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候用的一人三分保本田,好使吗?”“灵得很!”是啊,三年自然灾害时,我村那年春饿死了18口,可眼下段庄已死了8口,没别的路了,分吧!我立即召开了支部扩大会议,吸收小队长和会计参加,每人2分,用自留地的名子,分好地,离开大路,也就是上级走不到的地块,统一种春玉米。要保密,亲戚家也不准走露消息。有人问:“县公安、县法院就在咱眼皮底下,他们知道了怎么办?”“我已顾不得这些了,路走到哪里算哪里,坐大牢,我去。”事情进行得异常顺利,第二天黎明各队开始活动,一天之内150亩地全部到户,半月之内苗全齐旺。这一招还真灵,段庄又安定下来了,准备下关东的也放下了铺盖卷,人们好象看见了希望,麻木的脸上开始露出一丝笑容。是啊,多好的农民,他们十分听话,大白天在自留地里一个人也不见,只是晚上或黎明之前干这些活,并且没有一个人走露风声。日子一天天过去,有一次工作组长韩敬安同志(当时县法院民厅厅长)和我一块出去转,他故意领我去自留地方向。我发现苗头不对说:“那地方不好走,咱到别处去看看。”他坚持要去,于是我们进入了羊肠小道。真来到自留地了,事也凑巧,一个10多岁的小姑娘正在拿一个小袋子给玉米施肥。韩厅长问:“那小孩在干什么?”那小姑娘看见我们连忙趴下了,但我们却看见了。我说:“可能在拔草。”“我看不是拔草。”“调皮的孩子,不知干什么,不管她。”韩厅长笑了笑,我们又往前走。“我怎么看这地象是一家一户的?”“哪能呀,韩厅长真会说笑话,哪能是一家一户的呀,分明是集体的吗,只不过这块长得好了点。”韩厅长只看着我笑了笑,再也没说什么。实际上韩厅长早就知道了,只是我们之间谁也不挑明罢了。
77年麦收不久,几个队长找到我,说生产队上栽地瓜(麦茬地瓜),没钱买秧子,当时分自留地已尝过甜头,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分下去,让社员自己想办法。队上统一开垅,看上去象集体的一样就行。每人三分地,不要靠大路太近。这次连支部会也没开,更没向工作组汇报。这法子灵得很,以前,这些活最少干5天,分下去之后,两个下午就完成任务。当时几个队长为我担心,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扯了龙袍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是的,反正是豁出去了,人么站着、躺着一样长。这样每人就有半亩地在手,秋后差不多每人就能有400斤粮食,基本够吃的了,劳力在队上还能分一部分,也不违背社会主义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事实证明这一步又走对了。后来自留地被县里人走迷了路无意中发现。我差一点没进大牢,多亏了县公安局、县法院。记得石院长、孙局长、王局长都为我奔走:“九岭有缺点错误让他改就是了,撤了他,谁去段庄收拾乱摊子。”这些话真管用。段庄打派仗远近有名,没有两下子谁也不来段庄找头疼。但是他们也不清楚,自留地的背面还隐藏着一条更可怕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件事没有瞒住韩厅长。有一次韩厅长在工作组和我喝酒,他突然背过身去象背台词一样:“自留地这个问题吗,县委没有《国务院60条》大,有人竟然吃了熊心豹子胆,在法院的眼皮底下走资本主义道路,真的要坐牢的,太年轻啊,太年轻,可惜啊!”我想这下子算完了。他忽然回过身冲我一笑:“我这人有个毛病,就是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天意如何吧!”我放心了,我知韩厅长为人耿直,不会坏我大事,但他也为我捏一把汗,他也有责任。当时我想,地是分了,听天由命吧。说到这里不能不提一下我们的村民,要是当时有一个人告状,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977年一进腊月,奇迹般地听到了鞭炮声,除夕之夜,大街上张灯结彩。我绕大街一周,看到孩子们穿上新衣服,脸上带着笑容,那高高兴兴的样,忍不住热泪盈眶。望着这万家灯火,暗暗说了一句:“衣食足则知耻荣。”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个村子虽小也是一个小小的世界。有人说支部书记是“小国之君”,我认为也不为过。当家人的心是黑是白百姓心中自然有杆称。一个老人对我说:“这一年你只走了两步,一步一层楼。”我对他说我还要走三步、四步,一步一层天。他所说的两步,一步是二分自留地,一步是三分“口粮田”。1978年一开春,我又每人三分春地,全部种春地瓜,当中穿种芝麻,秋种时种麦子,队上只留一少部分,不超过30亩,其余全部分到户,自种自收。1979年粮田地已全部到户,棉田地无论如何还是没有敢动。这时段庄彻底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吃不了还可卖一部分,地瓜加工成粉条,也可卖一部分钱,劳力多的还能分到一部分。我的工作也十分顺手,还经常受到上级的表扬。这一段时间我狠抓了干部的素质教育,使他们廉洁奉公,不多占社员一分钱。事实也是这样,我们村的干部十几年来没一个因贪污多占犯错误的。村里也十分安定,没有一个上访告状的,甚至连打架的、骂大街的也没有。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我敢说当支书十二年没喝过社员一滴酒,没贪过社员一分钱,相反哪一年也要赔进集体几百元。我自己规定:上级来人在我家吃饭一年只领一百元补贴,多了自己掏腰包,其他成员这样的补贴一分也没有。
1979年冬,那时三中全会已开过,我开始考虑在棉田地上作文章。我想:有组织地施行承包,老百姓真能富起来,通过3年来的试验证明是一条可行之路。我是共产党员,应当把这个经验推广出去,让全公社、全县以至全国的老百姓尽快解决温饱问题。但就我自己的力量无论如何也是无能为力的,必须有党委的支持,也就是最起码的一条得公开。有一天县委副书记徐士高来段庄,他是从外地调来的,来夏津后对段庄问题有些耳闻,但具体情况不甚了解,确切地说,当时关于段庄分地的情况,上头只是听到一些传闻,真实情况只有段庄人心里明白。在谈话时我发现徐书记思想开放,为寻求一条农村改革的道路,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只带一个秘书,我把真实情况全盘告诉了他,把下一步实行全盘承包的计划也告诉了他,得到他的充分肯定和赞赏。他临走时吩咐:“你充分做好准备,我向县委汇报,把你的经验推出去。”就在1979年冬天我接连开了几次支部扩大会议,研究如何全部承包的问题。实际上是轻车熟路,一个月的时间关于怎样承包的一系列问题就做好了计划。
1980年初春,县委徐士高副书记来搞责任制试点,在公社的大办公室里,召开了全体脱产干部会议,吸收33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参加,在这次会议上展开了东李公社一次空前的大讨论,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承包责任制符合不符合中央精神。当时中央没有明确规定搞什么分还是包,徐书记讲:“要解放思想,如果只按中央文件办,那是照章办事,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要我们解放思想。”接着大家展开讨论,如现有的集体财产怎么办,军属五保户怎么办,收了棉花不卖给国家怎么办,不在夏津县卖怎么办……。最后竟吵成一锅粥,谁也听不清谁在说什么,有的扯着嗓子喊,有的面红耳赤,瞪着眼呲着牙。我坐在最后面的墙角里静静地听着,最后王秀生书记站起来,挥舞着双手让大家停下来,好一会儿会场才静下来。“让段庄支部书记发表一下意见,看他有没有高招。”我站了起来,手里拿着一个大烟斗,人们把目光都投向我,因为当时我20几岁,是全公社支部书记中最年轻的一个,在我们这个地方年轻人没有一个吸烟用大烟斗的,我赶紧放下烟斗,开始发表我的看法:“三中全会文件上有这么一条,在我国边远地区可以搞承包到组,我认为边远地区是因为贫困,也就是贫困地区可以这样做,我们是贫困地区就等于边远地区,所以说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我说完这些话,有些人觉得有些道理,我听着好象有人说了一句“对!”徐副书记喊了一声:“你接着讲。”“粮田不在计划的可以按人口平均分,国家计划这一块我们可以按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人七劳三,多劳多得’,叫做承包到组,责任到人,不叫包产到户,更不叫分散单干。”“好,有道理。”徐副书记说。我接着说:“关于集体财产如大牲畜、机器什么的,可以折价卖给社员,得来的钱发展再生产,打机井什么的,机井要统一管理,保证每户使上水,这是干部的责任。”关于棉花不卖给国家和不卖给夏津这个问题,我回答得也很风趣,我说:“这个问题不需考虑,哪里给的钱多上哪去卖,就是卖到台湾也出不了中国地盘,还可以卖给美国、日本、加拿大。”有些人笑了,很多人提出的问题我都一一做了回答,像答记者问了。最后有人问:“这样干你觉得段庄秋后向国家交多少皮棉?”“十万斤吧,我准备比去年翻一番。”我说得象讨颗烟那么轻松。在坐的都有些震惊,好大一会儿,一个人也没有吭声。县委徐士高副书记、公社王秀生书记、许万沂副书记几个人好象同时站起来:“分,坚决地分。分不开的,不会分的,让陶九岭教你们。”
散会了,徐士高抓着我的手说:“我喜欢听京剧,今天你演了一出叫诸葛亮舌战群儒,我给你喝彩。”我只是笑了笑,说:“我无古人之风,更无诸葛亮之才,关于喝彩,秋后吧。”“好,秋后你交十万斤,我来给你开庆功大会,就这样。”也就是在这一年,东李公社全面地实行大包干,翻开了农业改革历史上新的一页。
1980年,我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我终于能甩开膀子,施展我的才华了,至于是怎样分或是怎样干的,我想现在已是俗套,不必赘言。但是有一点我需要说,这一年我掉了二十斤肉,但是秋后卖的皮棉超过了十万斤,段庄人均分配一下跃入全县第一。我笑了,哭了,同时也醉了。我没有什么语言,去描绘当时那幸福的情景和心情……
徐士高副书记庆功来了。公社王秀生书记、许万沂副书记、郭尚廷副书记都来了,我们同席而坐,酒杯举得高高的。随之而来的是记者:新华社的、人民日报的。在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县委书记刘风岐听完我的发言之后,高兴得无以言表:“好小陶啊,好小陶啊,全县学小陶啊,学小陶,小陶是何等的好啊……”。当时团县委书记房玉梅问我:“你的感想是什么?”我只说了一句:“我感动了上帝。”房玉梅叹了一口气。我们在一块当过公社团委副书记,她对我是了解的。段庄沸腾了,80年的除夕之夜,鞭炮一直到零点未停,我醉了,但不是自斟自饮的76年了,我邀来了几位支委共度这除夕之夜,良宵美酒,我欣然命笔:“曾几何时,风雨伴我走春秋,风也停了,雨也停了,风雪自此不潇潇……”
是啊,忍饥挨饿的日子,在段庄一去不复返了。我终于胜利了,段庄人终于过上好日子了。
1981年我除了深入完善我的大包干之外,主要是接待记者和作家的采访,再就是给各地介绍落实责任制的经验。1981年开始就成了鲜花盛开的日子了,《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大众日报》、《山东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杂志社、《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文汇报》……先后介绍和报导了段庄实行责任制的情况和取得的成绩。
新闻媒介把段庄的做法迅速传遍全国各地。1980年底或是81年初,陕西省一个大代表团来我县,据说当时陕西省党委书记是山东人,听说老家实行大包干,派了3个地区的3个地委书记,30来个县委书记和报社记者,来老家取经。山东省委派一个粮食厅副厅长带领他们来夏津,县委书记用专车来段庄接我。在县委招待所的大会议室里,徐士高副书记和我接待了他们。记得开会前徐书记嘱咐我:“今天你面对的都是不小的官,不要怕,他们是来学习的,大胆地讲,讲好了,不但露夏津的脸,还给咱山东露脸。”我一笑说:“既然是来学习的,我不管官大小,都是我的学生,世界上那有老师怕学生的道理。”就这样,我详细地介绍了有关怎样分地的情况,然后就是回答他们不明白的问题。整整一个上午,他们很认真,提的问题也很具体,我一一为他们做了满意地答复。最后一个同志问:“用简单的话说,大包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说:“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1981年,段庄人均分配800元以上,段庄用上电,我买来彩电,每天晚上在大街上演,邻近村里的人们来看段庄怎样拥抱现代文明,我不必细讲。房玉梅向团省委汇报了我的情况,受到团省委的重视,孙淑义书记专程来我家看望我,并在全省青年中树我当标兵。
1982年我赴省参加新长征突击手表彰大会,会上我第一个发言,用记者的话说,我得了这次会议的“单打冠军”,在长时间的鼓掌中我再一次向台下鞠躬谢幕。之后我在山东作巡回报告。
1998年底
相关人物
陶九岭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