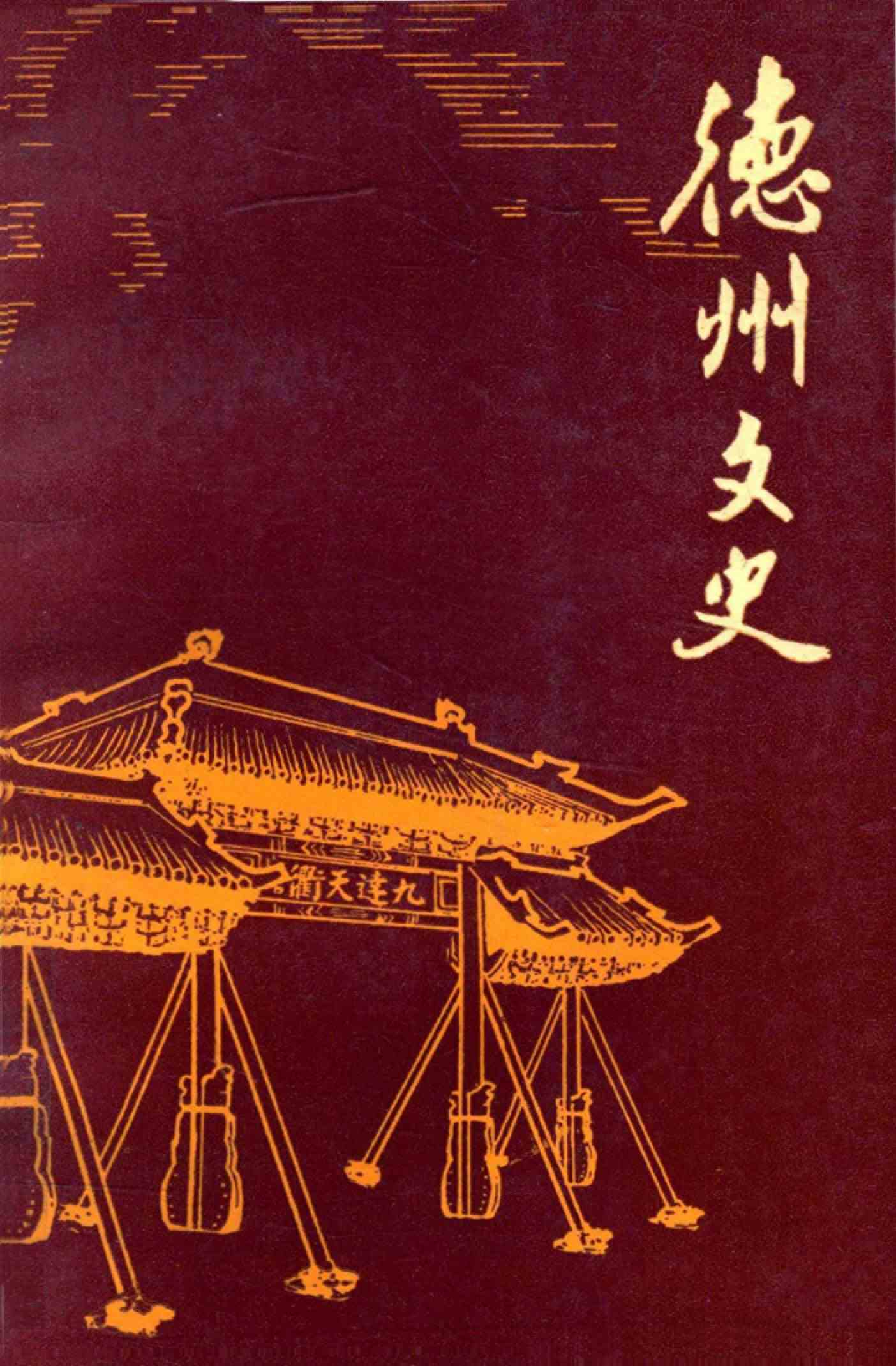内容
19世纪80年代初,以美国基督教公理会(North China Mission of the American Board)教士勾串无赖教民骗取寡妇产业,遭到了德州官绅及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并由此引起重大中外交涉,这就是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德州教案”。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即很快传入了天津,尤其该会传教士山嘉利(C.A.Stanley)等到达天津后,公理会更是加紧了对内地的窥伺。而大运河畔的鲁西北重镇——德州及其附近地区,便成为他们觊觎的主要目标。早在同治六年(1867),公理会即与德州一带民间的秘密会社有了一定的联系。其后,公理会便每年派传教士由天津至德州及附近地区进行传教活动。光绪初年,山东大旱,山嘉利、明恩溥(Arthur H.Smith)、博恒理(Henry D.Porten)、谢卫楼(D.Z.Sheffield)等公理会传教士,见有机可乘,便以办理赈济为名,于光绪三年(1877)先后窜到山东德州、恩县等地活动,很快在一年间收纳教徒150余人。至光绪六年(1880),美国公理会正式作出决定,以运河沿岸的庞庄(属原恩县)为据点,派明恩溥和博恒理两人驻扎,并在庞庄寨里占地建房,很快建立起一个传教中心。从此,公理会便以庞庄为基地,不断向四外扩张,并积极在各地网罗教民,强夺民产,“德州教案”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德州教案”(1880—1882)有两次大的风波。
光绪六年(1880),博恒理进驻庞庄后,在向四周扩充势力的同时,认为运河岸边的鲁西北重镇——德州经济文化发达,交通便利,可作教会传教中心。因而,他久欲在德州或德州附近获得一块地皮,设立教会基地。于是,他勾串德州城南15里第七屯的教民吴长泰,企图骗取吴长泰寡居嫂子吴夏氏的一份产业。他们利用光绪四年(1878)灾年之际吴氏全家曾受公理会赈济而“感恩图报”的心理,哄骗吴夏氏将一所余宅捐与第七屯的公理教会,充作讲堂。在博恒理、吴长泰等人甜言蜜语以至软硬兼施的诱逼下,吴夏氏终于被迫同意将夫兄吴长茂、夫弟吴长安所遗宅院一所,“舍给教会”,并请地方罗大成、本屯先生陆国顺充当中人,于光绪六年九月(1880年10月)间立下了“永不反悔”的捐献字据,其内容如下:
立字人吴长泰暨寡嫂吴夏氏,三弟妇吴潘氏、并次子保成,胞侄双盛,因全信耶稣道理,今同中人地方罗大成、陆国顺(说合),情愿将先兄长茂、亡弟长安所遗宅院一处,北平房三间,西平房四间,平门楼一间,土木相连,舍给教会,作为礼拜堂,永不反悔。东至吴振湖,西至伙道,南至门头地,北至吴瀛洲,四至开清。又有庄东地一段,约二分余,情愿给耶稣教会。恐(空)口无凭,立字为证。光绪六年九月×日立。吴长泰、(吴)夏氏、保成、(吴)潘氏、双盛画押。
为能尽快将房产弄到手,博恒理又唆使吴长泰出面,诱骗吴夏氏于光绪六年十一月十二日(1880年12月13日)立下了正式的捐献文约。文约内容是:
立约人、孀妇吴夏氏与夫胞弟长泰同信“耶稣圣教”有年。既明天上主宰保佑之恩,又蒙荒年赈济之情;因与弟议,愿将自己余宅一所,上带北房三间,小西房四间,大门楼一座,捐输“耶酥堂公会”,以便讲道读书之用。今同教友陆国顺、地方罗大成、催头郑国梁,丈清宅基,共闲地四分九厘八毫二丝。照地应值实价共计银叁两壹钱八分五厘六毫,投报抽税印契过割,恐后无凭,立文约存证。
七屯卫粮三分,吴瑞名下开。新立“耶稣教堂公理会”名下收。光绪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立。
博恒理等人哄骗民产的行为,终于引起了地方官府的注意。光绪七年八月初七日(1881年9月29日),“州官(陈嗣良)为此事传讯地方”。陈嗣良,顺天宛平人,祖籍浙江秀水,同治年间,曾署招远等地知县;光绪四年(1878)起,充任德州知州。他在胶东任职期间,目睹帝国主义者尤其传教士的罪恶行径,抵抗外来侵略的本能,使其很早即与外国侵略者有着强烈的敌对情绪。此次美国传教士在其辖境哄骗民产一事被揭露后,他内心更十分恼火,决意书面阻挡。当他传讯地方时,为博恒理所悉。该传教士“当执其文约,前往州署呈阅”。陈州官压住愤怒,对其“按礼接见”,并“谕其照所立文约,另缮一份送至州署存案,俟查明该孀妇捐输一事,果出情愿,必为盖印”。这样,就很顺利地于八月初九日(10月1日)将其文约内容搞到了手。因查知此宅地基房舍捐输并非情愿,陈州官便计划动员吴夏氏将此宅院捐办官义学,故让来送文约的教徒“将约内所书之耶稣圣教名字改去,并将约内捐输耶稣堂公会等字,改为七屯官义学。又于约后改为官义学陆国顺名下收字样”。事隔不久,陈州官还“传集该州绅士,谕其劝戒该处商民,不可与洋人有任何交接”,防止教会哄骗民产之类事件的再度发生。八月十六日(10月8日),陈州官又出示限制教会的晓谕,并四处张贴。其晓喻的内容如下:
德州正堂陈谕:该地方知悉:查外洋教士在中国传教,原载在和约,奉旨允准,概不禁止。惟习教之人,亦必须严为稽查,以防滋生事端。本州前在招远县任内,曾闻教士言及“凡入教之人,均系正人君子,至匪类小人,一概不许入教”等语。以此谕示闔境军民人等,并地方庄长知悉:凡有愿习教者,既属正人君子,一概不禁;惟责成庄(长)地(保)邻佑等,随时查明习教人名、数目,赴州报名(明),以便稽查。自示以后,若匿不呈报,即系匪类小人,惟利是图,致扰洋教。一经本州查出,或经人告发,必将匿不呈报之邻佑庄地,从严惩办不贷,毋违。特谕。光绪七年八月十六日。
与此同时,德州各阶层民众亦纷纷掀起驱教运动,阻止教会哄骗民产等暴行,很快发展为一场全民性反教斗争。除将七官屯所捐宅院“放火烧毁”外,城内外铺主、雇主还将奉教者解雇。教会势力受到很大冲击。
九月上旬(约11月初)间,博恒理将德州一带情形禀报给美国驻华公使馆,声称:“德州有一孀妇吴夏氏,住该州第七屯地方,因素奉耶稣教,去岁愿将地基及房间捐输与屯内公教会,作为讲经堂,随按其意见办成。该亲族亦俱情愿,并有地方及本屯先生作证”,无奈州官因此传讯地方,强令修改文约,并召集士绅,出示阻教晓谕。据此,九月十四日(11月5日),美国驻京署理公使何天爵(Holcombe,Che-ster)照会总理衙门,告知德州一案情形,认为:奉教之人被其铺主、雇主解雇等情,“皆由州官不按条约,自出己见,张贴示谕而起”;并指出:“该教民在七屯设立讲堂,自应与释道二教之设立寺院无异也。是该孀妇所捐之地,与贵国律例毫无不合。而该州官有所阻挠,殊非合例。至州官所出示谕……不但违例背约,且系最易由此滋生事故”;因此要求总理衙门“转行饬知德州州官,仍按原立文约盖印,毋得按其不公之谕办理;并饬其嗣后格外留心,毋得自出何等意见,以致民教日久相安者,反至多事可也。”
因未接山东巡抚咨文,总理衙门不明事件真相,乃据何天爵来函,于九月十八日(11月9日)照复何天爵:“吴夏氏如实系愿将房间捐作讲堂,按约自应照准……德州(州官)强令改为义学字样,办理自属未合”;但在照会中,总理衙门亦为州官限教示谕加以辩解:“所粘示谕,该州系为便于稽查起见……查其(教民)是否善良之意,并非有所阻挠。”对总理衙门“按约自应照准”的表态,何天爵曾表示“曷胜欣谢”,但对限教示谕的辩解,则十分不满。九月二十五日(11月16日),何天爵又照会总理衙门,仍据《中美天津条约》(1858)第二十九款关于“耶稣基督圣教……原为劝人行善……嗣后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等规定,指责德州陈州官所出之谕,声称:“今德州(州官)出此示谕,显系干预教士,稽察来习教者之权……该处所定办法,不但无故背约,无所得益,且多多有损……”再次要求总理衙门“即行咨饬该处州官,不得按此示谕办理,并饬其于中国教民如非犯法,不得有所阻挠也”。不久,何天爵又为“德州教案”专程前往总理衙门,带去吴夏氏手押及德州卫之戳记阅看。总理衙门亦当面告知“已转饬该地方官,不可稽查入教人名、数目、不可于教民与别项民人有所区别,总须看待入教之民,与奉释道二教一律。”
当时,济南府知府梅启熙、山东巡抚任道镕都支持陈嗣良的限教做法,因而支持他在第七屯开办官义学而息争讼的方案。有上司的默许,陈嗣良的限教措施执行起来较前更为坚决。光绪七年十二月初一日(1882年1月20日),陈嗣良又派差持票,“传教友吴长泰与送教会宅基立约契同人罗大成等,催逼急速赴州”。并声称:“抚台来文,已定准将宅立为官义学,传尔等到案,具字画押。”除吴夏氏不在州境外,其余吴长泰、陆国顺、罗大成及吴夏氏夫弟媳吴潘氏等人,均被押赴州署。当时,吴长泰妻十分恐惶,急忙跑到庞庄送信给博恒理。初二日(21日),博恒理即又“执原文契赴州”,“往见州官,辨此办法”,希望能顺利“税契过割”。陈嗣良却“坚拒不许印契”,并言:“系奉上宪分示如此办理”,并将抚院(任道镕)札文给阅。几经交涉,陈嗣良“仅许吴长泰等讨保回家,候传吴夏氏到案,再来州听讯”。陈嗣良的所作所为,使博恒理恼羞成怒,遂又添枝加叶般禀告给美国署理公使何天爵,最后还危言耸听:“思此威逼改契,立作官义学,又势迫教民,具字画押,不遵和约,不服上宪,恶很(狠)诡诈,一至于斯,若不赶紧调处,圣会教民,祸莫测矣。”
十二月十六日(2月4日),何天爵根据博恒理的一面之词,给总理衙门照会说,德州州官违约有三:“一系强改孀妇捐输房间,为作讲经堂之文约;一系饬令庄地邻佑人等,随时查明教民人(名)数目;一系谕饬绅士,劝谕商民不可与洋人有何交接。”另外,还在照会中附吴夏氏原立字据等件,企图证明吴夏氏是情愿捐输宅地;并指责德州州官并未按总理衙门的饬令办理;要求总理衙门“速行设法,饬禁该州官如此紊乱行为,使其明晰轻视上宪分示,必未干便”。最后,为督促总理衙门“速为查办”,何天爵还威胁说:“此后若无别法按理结办,本署大臣自必另派委员,由本馆前往德州查办”。
尽管美国公使馆屡屡“抗议”、威胁,且总理衙门亦咨行山东巡抚任道镕从速结案,但州官陈嗣良和当地士绅仍凭借广大民众的反抗情绪,不肯让步。当地绅民“为感州官能抑制洋人与传教者,送其匾额与万民伞”。而陈嗣良亦在其召集的士绅会议上表示:“无论有何重事,我在此一年,至于十年,必使洋人来此地不得安。”当地官绅士民反洋教情绪的持续高涨,致使美国公理会占地的企图一直无法实现。
在“德州教案”发生的同时,省城济南亦发生一起重要教案,是由美国长老会(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传教士强买民房引起的。因这起教案久悬不结,光绪八年二月十七日(1882年4月4日),美国署理公使何天爵照会总理衙门,声明:“本署大臣现已特派天津色领事(即色克,JasC.Zuck)及本馆前翻译官德尔乐作为委员,前往济南查办此案。”临行前,何天爵曾特为叮嘱色领事和德翻译,要他们途经德州时,顺便将“德州教案”设法了结。二月廿五日(4月12日),色克、德尔乐一行由北京行抵德州。这一消息很快传遍全城,当地绅民又跃跃欲试,准备痛打洋鬼子。二十六日(13日),色克与德尔乐骑马前往州衙,沿途横冲直撞,很快遭到城内绅民的反抗。当时,参与反抗的除城内李姓店主为首的绅民外,还有不少四邻的乡民。因“适值征收上忙钱粮之时,四乡花户,纷纷进城完粮”;及见色克一行横冲直撞,亦十分气愤,并奋起响应城内绅民的反抗活动。他们嘴里骂着洋鬼子,跟随在马后投掷石块,一直追至州署。色领事一行跑到州衙时,州官陈嗣良也不给其好脸,“不特不为出迎,则至客厅门首,亦不出迎”。会晤时,色领事等“请其(州官)拿办保护,并未肯查拿究惩”,且州官对洋人亦无半句安慰之言。色克等不得要领,不得不灰溜溜地退出州衙,在沿途绅民的唾驾、抛击下,夹着尾巴,前往济南去了。
三月十五日(5月2日),色克、德尔乐一行由济南回德州。这时,德州城内外绅民的反抗情绪仍十分高涨。“彼时城外、城内,民人聚集无数”。所以色领事、德翻译一行再次到达德州时,仍遭到了绅民们的反对。据色领事等事后回忆,“情形与初次相同,其辱骂抛击,则尤甚,且为时甚久”。当时绅民们“将砖石瓦块抛击,计有一点钟之久”。在其未进城前,色领事等“屡告以我等系美国官员,来此办理公事,尔等不必欺凌”,满以为亮出外国牌子,就可吓退民人。但绅民们却“始终弗听”。这次至德州,色领事等“亲见有铺户及街市等人同为辱骂欺凌……由城南至城北,约有六里之遥”。进城后,色领事一行曾请防营汛官派兵保护,深受民众反抗情绪影响的汛官“答以不管,并言不配保护”。至州衙后,陈州官仍不肯给其好脸。当色领事“复面请州官拿办”时,陈州官“亦未行认真查拿”。色领事又告以“此次打骂之人,内有在该处开店者(即李姓店主)”,并认获送案。而陈州官亦不肯究办,“犹任其于署内脱逃”,后经色领事等一再抗议,陈州官虽不得不将李姓店主拿回,但亦“只于该委员等面前虚为责打”而已。色领事还要求出示“禁止商民欺凌教士教民之示”及“谕禁商民欺凌大合众国(美国)委员之示”,陈州官阳为许之,但“亦未即张贴”。结果,使色领事一行仍不得要领,只得悻悻北归。
色领事等北归后,陈州官的限制措施仍未停止。
他曾精心炮制“禁止欺凌教士教民告示仍赋予限教内容告示”,并“遍贴于州属各处”。难怪美国署理公使何天爵见后即照会总理衙门说:“此示词语,甚巧于影射,虽其中未言明不准在境内传教,本署大臣则不能不疑其意在于此—以之煽动百姓,使其忿恨教士与奉教之民。”不仅如此,陈州官在发贴此谕示之际,还再次饬谕各处地保说:“如有传耶稣教者,亦须与别项邪教之人,一律查拿,至拿之如何办法,及有何罪,均有本州作主。”州属各处地保与奉教者有戚者,闻讯告知有关教民“不可在各村传教散书,免至拿去,被其(州官)惩办”。而州官发布晓谕之后,“各处民人已行激动,声称击打洋人,驱逐教士,拆其房屋”,开展多种形式的反洋教活动。在绅民们的打击下,一些平时为非作歹的教民被迫“离家避至天津”。由于上述均属“违约之事”,与州官所出告示有一定关系,因而美国署理公使对这个州官恨之入骨,必欲除去而后快。
在德州的两次“遭遇”,使一向不可一世的色领事、德翻译一行受到当头一击,这是他们所不甘心的。早在第一次被砖石抛击之次日,色领事等便将“在德州被州官轻待及该民欺凌一切情形”报告于美国署理公使何天爵。三月初七日(4月24日),何天爵曾据色领事等人之报亲往总理衙门进行交涉。及色领事一行回京,他们更夸大其辞,向何天爵描述在德州两次被“辱骂欺凌”的经过,并声称在德州“屡与该州(官)会晤,州官甚失礼仪”,不仅不为“出迎”,而且还称委员为“老先生”、“老兄”等等,均属“违约之事”;甚至还说两次被“辱骂欺凌”,系州官与该处“恶人”早有定议故。根据这个片面的汇报,何天爵三番五次照会总理衙门,乘机干涉中国内政,要求撤销州官之职,指名“认真惩办”无罪百姓,压迫清政府就范。
三月二十日(5月7日)何天爵获悉色领事二次被“欺凌辱骂”事后,又亲至总理衙门“将此不合情形,复行缕言”。二十三(5月10日),何天爵正式照会总理衙门:“该委员等系本国官员,因公前往,已为该民所共知,乃于初次赴署晤谈,竟有民人于其出署,胆敢在署前欺凌,实属不合。本署大臣万不疑贵亲王(指恭亲王奕訢)于此案办法不即行切惩该处州官,及该欺凌之民,以全本国体统,以伸委员之辱。”不久,山东巡抚任道镕来函,告知总理衙门:“初次欺凌,系由乡民聚观,未免拥挤;经该州善言抚慰,并许出示禁,”总理衙门一面“咨行山东巡抚严为查办”,一面据实照复何天爵。
四月初一日(5月17日),何天爵再次照会总理衙门,歪曲事实,对山东巡抚咨函加以批驳,告知第二次被“欺凌”等情形,指出:“按此被欺凌一切未合情形,本国足谓该州系有大错。贵亲王现办此案办法,想本国必以为尚未行从重办理。是以请贵亲王再思一重办之法,为此要案伸理,以敦两国睦谊可也。”四月初五日(8月21日),何天爵在致总理衙门照会中,指责州官所出示谕及其限教言行,声称:“德州附近地方,现有洋教士数人居住,该州如此谬妄,违约之事,恐于教士之身家房产,致有危险……如本国商民或致身家房产被伤,想本国必惟贵国是问。”同时声明说:“本国于德州(州官)之事,可谓大有忍耐,贵亲王应设善法,使其不得再有恶行,致烦公牓,并免将来滋事可也。”
四月初八日(5月24日)总理衙门根据何天爵照会,一面“飞函密致山东巡抚,切实筹办妥结”;一面将办理情形照复何天爵。
四月十三日(5月29日),何天爵以闻山东巡抚“尚未办理德州之事”,表示十分不满。至四月二十五日(6月9日),何天爵又照会总理衙门,声称:“该州官从前凌逼教士教民,并轻藐本国委员,唆民肆行凌辱,迄令未经受谴,宜其益无忌惮,依照前此不合者踵而行之……如此迟延,是不惟使该委员一辱愈增,并使本署大臣心疑于山东巡抚不为妥办此案也。”最后还进一步威胁说:“本国委员因公路过德州,系为人所共悉,竟有此等不合之事,非特欺辱委员,直系欺辱本国。按万国公法之议,应惟贵国是问。贵亲王虽已曾咨行山东巡抚办理,请知此要案,本国所与议办者,乃与贵国,非与山东巡抚。若于本国官民被欺,均由该州主谋之案,贵国弗以予之应得之咎,本国必以办法为未妥。本国大臣自再请贵亲王按向来秉公办事之法,不再迟延,以全本国之体也。”
由于美国署理公使何天爵一再威逼,清政府不得不表示妥协,并催促山东巡抚任道镕速将“德州教案”各事妥结。任道镕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将原德州知州陈嗣良“撤调”,另行委派茅方廉署理知州。茅方廉抵任后,仅将参与两次围攻洋人的李姓店主“枷责示惩”,而于其余之人,“当时既未拘获,又不知其姓名”,如“一经妄拿,难免无辜受罪”,乃不了了之。
但清政府的退让,并未使何天爵感到满意。执意干预中国内政的何天爵,又节外生枝,于四月三十日(6月15日)照会总理衙门:“两次滋闹之事,均由该州(陈嗣良)阴主其谋,该民不过听其唆使,故所请严惩者,惟在该州。”因而对四月廿九日(6月14日)总理衙门照会所谈对陈嗣良的“撤调”处分不满:“文内‘撤调’二字,是否即系撤其任,抑系撤之调以别缺。如系因其不合而撤任,本国自必以贵国办理该委员等被欺一事为办法妥协;如系撤之而调往他州,及调补优美之缺,本国亦必以所办为未妥。”
“德州教案”后,虽最终按美国公使之意撤去了知州陈嗣良,枷责了李姓店主,但其结果只能激起德州各阶层民众的强烈义愤,最终迫使美国公理会不仅未获得地皮,而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敢再行侵入德州。
作为德州一带绅民反洋教活动的主要倡导人陈嗣良,虽因美国公使威逼而被清政府免职,但其限制行为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的,也多多少少是受到清政府默许和支持的。因而在其去职未久,清统治者对其仍加录用。光绪九年(1883)以后,他相继署理过曹县知县、蒙阴知县、章邱知县等职,所至皆有政声。至光绪十四年(1888),又得以回德州知州任。
1989.11.18.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即很快传入了天津,尤其该会传教士山嘉利(C.A.Stanley)等到达天津后,公理会更是加紧了对内地的窥伺。而大运河畔的鲁西北重镇——德州及其附近地区,便成为他们觊觎的主要目标。早在同治六年(1867),公理会即与德州一带民间的秘密会社有了一定的联系。其后,公理会便每年派传教士由天津至德州及附近地区进行传教活动。光绪初年,山东大旱,山嘉利、明恩溥(Arthur H.Smith)、博恒理(Henry D.Porten)、谢卫楼(D.Z.Sheffield)等公理会传教士,见有机可乘,便以办理赈济为名,于光绪三年(1877)先后窜到山东德州、恩县等地活动,很快在一年间收纳教徒150余人。至光绪六年(1880),美国公理会正式作出决定,以运河沿岸的庞庄(属原恩县)为据点,派明恩溥和博恒理两人驻扎,并在庞庄寨里占地建房,很快建立起一个传教中心。从此,公理会便以庞庄为基地,不断向四外扩张,并积极在各地网罗教民,强夺民产,“德州教案”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德州教案”(1880—1882)有两次大的风波。
光绪六年(1880),博恒理进驻庞庄后,在向四周扩充势力的同时,认为运河岸边的鲁西北重镇——德州经济文化发达,交通便利,可作教会传教中心。因而,他久欲在德州或德州附近获得一块地皮,设立教会基地。于是,他勾串德州城南15里第七屯的教民吴长泰,企图骗取吴长泰寡居嫂子吴夏氏的一份产业。他们利用光绪四年(1878)灾年之际吴氏全家曾受公理会赈济而“感恩图报”的心理,哄骗吴夏氏将一所余宅捐与第七屯的公理教会,充作讲堂。在博恒理、吴长泰等人甜言蜜语以至软硬兼施的诱逼下,吴夏氏终于被迫同意将夫兄吴长茂、夫弟吴长安所遗宅院一所,“舍给教会”,并请地方罗大成、本屯先生陆国顺充当中人,于光绪六年九月(1880年10月)间立下了“永不反悔”的捐献字据,其内容如下:
立字人吴长泰暨寡嫂吴夏氏,三弟妇吴潘氏、并次子保成,胞侄双盛,因全信耶稣道理,今同中人地方罗大成、陆国顺(说合),情愿将先兄长茂、亡弟长安所遗宅院一处,北平房三间,西平房四间,平门楼一间,土木相连,舍给教会,作为礼拜堂,永不反悔。东至吴振湖,西至伙道,南至门头地,北至吴瀛洲,四至开清。又有庄东地一段,约二分余,情愿给耶稣教会。恐(空)口无凭,立字为证。光绪六年九月×日立。吴长泰、(吴)夏氏、保成、(吴)潘氏、双盛画押。
为能尽快将房产弄到手,博恒理又唆使吴长泰出面,诱骗吴夏氏于光绪六年十一月十二日(1880年12月13日)立下了正式的捐献文约。文约内容是:
立约人、孀妇吴夏氏与夫胞弟长泰同信“耶稣圣教”有年。既明天上主宰保佑之恩,又蒙荒年赈济之情;因与弟议,愿将自己余宅一所,上带北房三间,小西房四间,大门楼一座,捐输“耶酥堂公会”,以便讲道读书之用。今同教友陆国顺、地方罗大成、催头郑国梁,丈清宅基,共闲地四分九厘八毫二丝。照地应值实价共计银叁两壹钱八分五厘六毫,投报抽税印契过割,恐后无凭,立文约存证。
七屯卫粮三分,吴瑞名下开。新立“耶稣教堂公理会”名下收。光绪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立。
博恒理等人哄骗民产的行为,终于引起了地方官府的注意。光绪七年八月初七日(1881年9月29日),“州官(陈嗣良)为此事传讯地方”。陈嗣良,顺天宛平人,祖籍浙江秀水,同治年间,曾署招远等地知县;光绪四年(1878)起,充任德州知州。他在胶东任职期间,目睹帝国主义者尤其传教士的罪恶行径,抵抗外来侵略的本能,使其很早即与外国侵略者有着强烈的敌对情绪。此次美国传教士在其辖境哄骗民产一事被揭露后,他内心更十分恼火,决意书面阻挡。当他传讯地方时,为博恒理所悉。该传教士“当执其文约,前往州署呈阅”。陈州官压住愤怒,对其“按礼接见”,并“谕其照所立文约,另缮一份送至州署存案,俟查明该孀妇捐输一事,果出情愿,必为盖印”。这样,就很顺利地于八月初九日(10月1日)将其文约内容搞到了手。因查知此宅地基房舍捐输并非情愿,陈州官便计划动员吴夏氏将此宅院捐办官义学,故让来送文约的教徒“将约内所书之耶稣圣教名字改去,并将约内捐输耶稣堂公会等字,改为七屯官义学。又于约后改为官义学陆国顺名下收字样”。事隔不久,陈州官还“传集该州绅士,谕其劝戒该处商民,不可与洋人有任何交接”,防止教会哄骗民产之类事件的再度发生。八月十六日(10月8日),陈州官又出示限制教会的晓谕,并四处张贴。其晓喻的内容如下:
德州正堂陈谕:该地方知悉:查外洋教士在中国传教,原载在和约,奉旨允准,概不禁止。惟习教之人,亦必须严为稽查,以防滋生事端。本州前在招远县任内,曾闻教士言及“凡入教之人,均系正人君子,至匪类小人,一概不许入教”等语。以此谕示闔境军民人等,并地方庄长知悉:凡有愿习教者,既属正人君子,一概不禁;惟责成庄(长)地(保)邻佑等,随时查明习教人名、数目,赴州报名(明),以便稽查。自示以后,若匿不呈报,即系匪类小人,惟利是图,致扰洋教。一经本州查出,或经人告发,必将匿不呈报之邻佑庄地,从严惩办不贷,毋违。特谕。光绪七年八月十六日。
与此同时,德州各阶层民众亦纷纷掀起驱教运动,阻止教会哄骗民产等暴行,很快发展为一场全民性反教斗争。除将七官屯所捐宅院“放火烧毁”外,城内外铺主、雇主还将奉教者解雇。教会势力受到很大冲击。
九月上旬(约11月初)间,博恒理将德州一带情形禀报给美国驻华公使馆,声称:“德州有一孀妇吴夏氏,住该州第七屯地方,因素奉耶稣教,去岁愿将地基及房间捐输与屯内公教会,作为讲经堂,随按其意见办成。该亲族亦俱情愿,并有地方及本屯先生作证”,无奈州官因此传讯地方,强令修改文约,并召集士绅,出示阻教晓谕。据此,九月十四日(11月5日),美国驻京署理公使何天爵(Holcombe,Che-ster)照会总理衙门,告知德州一案情形,认为:奉教之人被其铺主、雇主解雇等情,“皆由州官不按条约,自出己见,张贴示谕而起”;并指出:“该教民在七屯设立讲堂,自应与释道二教之设立寺院无异也。是该孀妇所捐之地,与贵国律例毫无不合。而该州官有所阻挠,殊非合例。至州官所出示谕……不但违例背约,且系最易由此滋生事故”;因此要求总理衙门“转行饬知德州州官,仍按原立文约盖印,毋得按其不公之谕办理;并饬其嗣后格外留心,毋得自出何等意见,以致民教日久相安者,反至多事可也。”
因未接山东巡抚咨文,总理衙门不明事件真相,乃据何天爵来函,于九月十八日(11月9日)照复何天爵:“吴夏氏如实系愿将房间捐作讲堂,按约自应照准……德州(州官)强令改为义学字样,办理自属未合”;但在照会中,总理衙门亦为州官限教示谕加以辩解:“所粘示谕,该州系为便于稽查起见……查其(教民)是否善良之意,并非有所阻挠。”对总理衙门“按约自应照准”的表态,何天爵曾表示“曷胜欣谢”,但对限教示谕的辩解,则十分不满。九月二十五日(11月16日),何天爵又照会总理衙门,仍据《中美天津条约》(1858)第二十九款关于“耶稣基督圣教……原为劝人行善……嗣后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等规定,指责德州陈州官所出之谕,声称:“今德州(州官)出此示谕,显系干预教士,稽察来习教者之权……该处所定办法,不但无故背约,无所得益,且多多有损……”再次要求总理衙门“即行咨饬该处州官,不得按此示谕办理,并饬其于中国教民如非犯法,不得有所阻挠也”。不久,何天爵又为“德州教案”专程前往总理衙门,带去吴夏氏手押及德州卫之戳记阅看。总理衙门亦当面告知“已转饬该地方官,不可稽查入教人名、数目、不可于教民与别项民人有所区别,总须看待入教之民,与奉释道二教一律。”
当时,济南府知府梅启熙、山东巡抚任道镕都支持陈嗣良的限教做法,因而支持他在第七屯开办官义学而息争讼的方案。有上司的默许,陈嗣良的限教措施执行起来较前更为坚决。光绪七年十二月初一日(1882年1月20日),陈嗣良又派差持票,“传教友吴长泰与送教会宅基立约契同人罗大成等,催逼急速赴州”。并声称:“抚台来文,已定准将宅立为官义学,传尔等到案,具字画押。”除吴夏氏不在州境外,其余吴长泰、陆国顺、罗大成及吴夏氏夫弟媳吴潘氏等人,均被押赴州署。当时,吴长泰妻十分恐惶,急忙跑到庞庄送信给博恒理。初二日(21日),博恒理即又“执原文契赴州”,“往见州官,辨此办法”,希望能顺利“税契过割”。陈嗣良却“坚拒不许印契”,并言:“系奉上宪分示如此办理”,并将抚院(任道镕)札文给阅。几经交涉,陈嗣良“仅许吴长泰等讨保回家,候传吴夏氏到案,再来州听讯”。陈嗣良的所作所为,使博恒理恼羞成怒,遂又添枝加叶般禀告给美国署理公使何天爵,最后还危言耸听:“思此威逼改契,立作官义学,又势迫教民,具字画押,不遵和约,不服上宪,恶很(狠)诡诈,一至于斯,若不赶紧调处,圣会教民,祸莫测矣。”
十二月十六日(2月4日),何天爵根据博恒理的一面之词,给总理衙门照会说,德州州官违约有三:“一系强改孀妇捐输房间,为作讲经堂之文约;一系饬令庄地邻佑人等,随时查明教民人(名)数目;一系谕饬绅士,劝谕商民不可与洋人有何交接。”另外,还在照会中附吴夏氏原立字据等件,企图证明吴夏氏是情愿捐输宅地;并指责德州州官并未按总理衙门的饬令办理;要求总理衙门“速行设法,饬禁该州官如此紊乱行为,使其明晰轻视上宪分示,必未干便”。最后,为督促总理衙门“速为查办”,何天爵还威胁说:“此后若无别法按理结办,本署大臣自必另派委员,由本馆前往德州查办”。
尽管美国公使馆屡屡“抗议”、威胁,且总理衙门亦咨行山东巡抚任道镕从速结案,但州官陈嗣良和当地士绅仍凭借广大民众的反抗情绪,不肯让步。当地绅民“为感州官能抑制洋人与传教者,送其匾额与万民伞”。而陈嗣良亦在其召集的士绅会议上表示:“无论有何重事,我在此一年,至于十年,必使洋人来此地不得安。”当地官绅士民反洋教情绪的持续高涨,致使美国公理会占地的企图一直无法实现。
在“德州教案”发生的同时,省城济南亦发生一起重要教案,是由美国长老会(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传教士强买民房引起的。因这起教案久悬不结,光绪八年二月十七日(1882年4月4日),美国署理公使何天爵照会总理衙门,声明:“本署大臣现已特派天津色领事(即色克,JasC.Zuck)及本馆前翻译官德尔乐作为委员,前往济南查办此案。”临行前,何天爵曾特为叮嘱色领事和德翻译,要他们途经德州时,顺便将“德州教案”设法了结。二月廿五日(4月12日),色克、德尔乐一行由北京行抵德州。这一消息很快传遍全城,当地绅民又跃跃欲试,准备痛打洋鬼子。二十六日(13日),色克与德尔乐骑马前往州衙,沿途横冲直撞,很快遭到城内绅民的反抗。当时,参与反抗的除城内李姓店主为首的绅民外,还有不少四邻的乡民。因“适值征收上忙钱粮之时,四乡花户,纷纷进城完粮”;及见色克一行横冲直撞,亦十分气愤,并奋起响应城内绅民的反抗活动。他们嘴里骂着洋鬼子,跟随在马后投掷石块,一直追至州署。色领事一行跑到州衙时,州官陈嗣良也不给其好脸,“不特不为出迎,则至客厅门首,亦不出迎”。会晤时,色领事等“请其(州官)拿办保护,并未肯查拿究惩”,且州官对洋人亦无半句安慰之言。色克等不得要领,不得不灰溜溜地退出州衙,在沿途绅民的唾驾、抛击下,夹着尾巴,前往济南去了。
三月十五日(5月2日),色克、德尔乐一行由济南回德州。这时,德州城内外绅民的反抗情绪仍十分高涨。“彼时城外、城内,民人聚集无数”。所以色领事、德翻译一行再次到达德州时,仍遭到了绅民们的反对。据色领事等事后回忆,“情形与初次相同,其辱骂抛击,则尤甚,且为时甚久”。当时绅民们“将砖石瓦块抛击,计有一点钟之久”。在其未进城前,色领事等“屡告以我等系美国官员,来此办理公事,尔等不必欺凌”,满以为亮出外国牌子,就可吓退民人。但绅民们却“始终弗听”。这次至德州,色领事等“亲见有铺户及街市等人同为辱骂欺凌……由城南至城北,约有六里之遥”。进城后,色领事一行曾请防营汛官派兵保护,深受民众反抗情绪影响的汛官“答以不管,并言不配保护”。至州衙后,陈州官仍不肯给其好脸。当色领事“复面请州官拿办”时,陈州官“亦未行认真查拿”。色领事又告以“此次打骂之人,内有在该处开店者(即李姓店主)”,并认获送案。而陈州官亦不肯究办,“犹任其于署内脱逃”,后经色领事等一再抗议,陈州官虽不得不将李姓店主拿回,但亦“只于该委员等面前虚为责打”而已。色领事还要求出示“禁止商民欺凌教士教民之示”及“谕禁商民欺凌大合众国(美国)委员之示”,陈州官阳为许之,但“亦未即张贴”。结果,使色领事一行仍不得要领,只得悻悻北归。
色领事等北归后,陈州官的限制措施仍未停止。
他曾精心炮制“禁止欺凌教士教民告示仍赋予限教内容告示”,并“遍贴于州属各处”。难怪美国署理公使何天爵见后即照会总理衙门说:“此示词语,甚巧于影射,虽其中未言明不准在境内传教,本署大臣则不能不疑其意在于此—以之煽动百姓,使其忿恨教士与奉教之民。”不仅如此,陈州官在发贴此谕示之际,还再次饬谕各处地保说:“如有传耶稣教者,亦须与别项邪教之人,一律查拿,至拿之如何办法,及有何罪,均有本州作主。”州属各处地保与奉教者有戚者,闻讯告知有关教民“不可在各村传教散书,免至拿去,被其(州官)惩办”。而州官发布晓谕之后,“各处民人已行激动,声称击打洋人,驱逐教士,拆其房屋”,开展多种形式的反洋教活动。在绅民们的打击下,一些平时为非作歹的教民被迫“离家避至天津”。由于上述均属“违约之事”,与州官所出告示有一定关系,因而美国署理公使对这个州官恨之入骨,必欲除去而后快。
在德州的两次“遭遇”,使一向不可一世的色领事、德翻译一行受到当头一击,这是他们所不甘心的。早在第一次被砖石抛击之次日,色领事等便将“在德州被州官轻待及该民欺凌一切情形”报告于美国署理公使何天爵。三月初七日(4月24日),何天爵曾据色领事等人之报亲往总理衙门进行交涉。及色领事一行回京,他们更夸大其辞,向何天爵描述在德州两次被“辱骂欺凌”的经过,并声称在德州“屡与该州(官)会晤,州官甚失礼仪”,不仅不为“出迎”,而且还称委员为“老先生”、“老兄”等等,均属“违约之事”;甚至还说两次被“辱骂欺凌”,系州官与该处“恶人”早有定议故。根据这个片面的汇报,何天爵三番五次照会总理衙门,乘机干涉中国内政,要求撤销州官之职,指名“认真惩办”无罪百姓,压迫清政府就范。
三月二十日(5月7日)何天爵获悉色领事二次被“欺凌辱骂”事后,又亲至总理衙门“将此不合情形,复行缕言”。二十三(5月10日),何天爵正式照会总理衙门:“该委员等系本国官员,因公前往,已为该民所共知,乃于初次赴署晤谈,竟有民人于其出署,胆敢在署前欺凌,实属不合。本署大臣万不疑贵亲王(指恭亲王奕訢)于此案办法不即行切惩该处州官,及该欺凌之民,以全本国体统,以伸委员之辱。”不久,山东巡抚任道镕来函,告知总理衙门:“初次欺凌,系由乡民聚观,未免拥挤;经该州善言抚慰,并许出示禁,”总理衙门一面“咨行山东巡抚严为查办”,一面据实照复何天爵。
四月初一日(5月17日),何天爵再次照会总理衙门,歪曲事实,对山东巡抚咨函加以批驳,告知第二次被“欺凌”等情形,指出:“按此被欺凌一切未合情形,本国足谓该州系有大错。贵亲王现办此案办法,想本国必以为尚未行从重办理。是以请贵亲王再思一重办之法,为此要案伸理,以敦两国睦谊可也。”四月初五日(8月21日),何天爵在致总理衙门照会中,指责州官所出示谕及其限教言行,声称:“德州附近地方,现有洋教士数人居住,该州如此谬妄,违约之事,恐于教士之身家房产,致有危险……如本国商民或致身家房产被伤,想本国必惟贵国是问。”同时声明说:“本国于德州(州官)之事,可谓大有忍耐,贵亲王应设善法,使其不得再有恶行,致烦公牓,并免将来滋事可也。”
四月初八日(5月24日)总理衙门根据何天爵照会,一面“飞函密致山东巡抚,切实筹办妥结”;一面将办理情形照复何天爵。
四月十三日(5月29日),何天爵以闻山东巡抚“尚未办理德州之事”,表示十分不满。至四月二十五日(6月9日),何天爵又照会总理衙门,声称:“该州官从前凌逼教士教民,并轻藐本国委员,唆民肆行凌辱,迄令未经受谴,宜其益无忌惮,依照前此不合者踵而行之……如此迟延,是不惟使该委员一辱愈增,并使本署大臣心疑于山东巡抚不为妥办此案也。”最后还进一步威胁说:“本国委员因公路过德州,系为人所共悉,竟有此等不合之事,非特欺辱委员,直系欺辱本国。按万国公法之议,应惟贵国是问。贵亲王虽已曾咨行山东巡抚办理,请知此要案,本国所与议办者,乃与贵国,非与山东巡抚。若于本国官民被欺,均由该州主谋之案,贵国弗以予之应得之咎,本国必以办法为未妥。本国大臣自再请贵亲王按向来秉公办事之法,不再迟延,以全本国之体也。”
由于美国署理公使何天爵一再威逼,清政府不得不表示妥协,并催促山东巡抚任道镕速将“德州教案”各事妥结。任道镕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将原德州知州陈嗣良“撤调”,另行委派茅方廉署理知州。茅方廉抵任后,仅将参与两次围攻洋人的李姓店主“枷责示惩”,而于其余之人,“当时既未拘获,又不知其姓名”,如“一经妄拿,难免无辜受罪”,乃不了了之。
但清政府的退让,并未使何天爵感到满意。执意干预中国内政的何天爵,又节外生枝,于四月三十日(6月15日)照会总理衙门:“两次滋闹之事,均由该州(陈嗣良)阴主其谋,该民不过听其唆使,故所请严惩者,惟在该州。”因而对四月廿九日(6月14日)总理衙门照会所谈对陈嗣良的“撤调”处分不满:“文内‘撤调’二字,是否即系撤其任,抑系撤之调以别缺。如系因其不合而撤任,本国自必以贵国办理该委员等被欺一事为办法妥协;如系撤之而调往他州,及调补优美之缺,本国亦必以所办为未妥。”
“德州教案”后,虽最终按美国公使之意撤去了知州陈嗣良,枷责了李姓店主,但其结果只能激起德州各阶层民众的强烈义愤,最终迫使美国公理会不仅未获得地皮,而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敢再行侵入德州。
作为德州一带绅民反洋教活动的主要倡导人陈嗣良,虽因美国公使威逼而被清政府免职,但其限制行为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的,也多多少少是受到清政府默许和支持的。因而在其去职未久,清统治者对其仍加录用。光绪九年(1883)以后,他相继署理过曹县知县、蒙阴知县、章邱知县等职,所至皆有政声。至光绪十四年(1888),又得以回德州知州任。
1989.11.18.
相关人物
刘晓焕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