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山北亭子“施粥厂”
| 内容出处: | 《山東文史资料选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50020020220002486 |
| 颗粒名称: | 博山北亭子“施粥厂” |
| 分类号: | K295.2 |
| 页数: | 15 |
| 页码: | 229-243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博山北亭子施粥厂骇人听闻的内幕简介。 |
| 关键词: | 博山 北亭子 施粥厂 |
内容
我8岁那年和哥哥刘元文被收容到博山北亭子施粥厂。这个施粥厂也叫“儿童收容所”,看名字应该是个慈善机关,但内幕却骇人听闻。现在我已年过半百,施粥厂那段往事还记忆犹新。
一、歉年
1943年,侵华日军在华北大搞“五次强化治安”,实行惨绝人寰的烧光、杀光和抢光的“三光政策”;同时,对城乡进行经济封锁。博山所出产的陶瓷、琉璃和铁器等,失去了农村市场。农村连年灾荒,就是有粮食也运不进博山城里来。博山城里的一些粮商和富户,趁机把粮食屯积起来,粮价飞涨。博山城里的穷苦人民陷入了严重的饥饉之中,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民国32年大歉年,那时候。大批的穷人被迫下了“关东”,没有下“关东”的都挣扎在死亡线上、卖儿鬻女、沿街乞讨。西冶街口的河滩一带人多,饭铺多,这里是乞丐最集中的地方。他们之中不仅有当地的穷人,还有周围农村被饥饿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不仅有成年人,还有很多未成年的孩子。有的人纵有布施之心,怎奈自己也十分艰难。于是出现了抢饭吃的现象。有人去饭铺买饭时,饥饿的孩子便悄悄地跟在后面,当你付了钱,拿着干粮要走的时候,他抢了就跑。你追,他就往干粮上吐唾沫、擤鼻涕,让你无法再要。有些山里下来的赶集人,回家时往往买一大块强面饼带上,这些饥饿的孩子腿脚跑得快,跟随到路宽人多的地方,从背后抢过来便跑。你紧追,他就掰下一块扔在地上,当你拾起饼来的时候,他已逃得无踪无影了。旁边的人往往都为抢饭的孩子喝彩,从来没人上前拦截。谁不知道这些孩子饿呀!就连观音堂口岗楼里站岗的伪军见了,也只是哈哈大笑而已。抢饭的孩子中也分阶层,有几个较大的孩子被称为“河滩王”。孩子们若抢到大些的干粮,必须首先“孝敬”他们。
当时驻博山的日军是菊池部队,还有为虎作伥的伪保安队伊来灝部以及伪警察。他们倒行逆施,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却偏偏要粉饰太平,维持所谓“东亚新秩序”。他们派出警察将河滩的乞丐一批一批轰出博山城,对饥饿的孩子们无计可施,就委托商会从城内各煤号、商店敛钱,办了个施粥厂,把他们收容起来。
二、上当
施粥厂成立以后,商会便派人整天在河滩观音堂大喊大叫:”小孩们,快到北亭子喝饭呀,尽着喝,进出随便家远的还可以住下!”这样的口号,对那些饥肠辘辘的孩子们是很有诱惑力的;就是那些没有沦为乞丐的孩子,谁愿意呆在家里挨饿!都想到北亭子“喝饭”去,况且是“尽着喝”。
我父亲刘在成是琉璃行业有名的轴子嘴匠。在那饥馑的年月里,他病饿交加,已卧床多日了。指望我母亲每天到姥娘家和大姨家去要几个煎饼,我们一家四口人泡煎饼汤吃。我和哥哥饥饿难忍,经常背着父母,到饭铺桌子底下拾些地瓜巴子和大虾头吃。端午节后的一天,母亲把我们叫过去说:“您爹爹的病越来越重,不能做炉了,外头人都说到北亭子去喝饭挺好,早上去,天黑回来,你俩也去吧,省得在家里饿死。”开始,我和哥哥都怕到那里受人欺侮,不愿去。可是搁不住母亲和大姨流着眼泪劝说,终于由母亲把我们送到北亭子去“喝饭”了。那是在北亭子西面的一个院子,我们是从院子西边的一个单扇门进去的。院子挺大,南院墙外是河,院墙里面不远有棵大洋槐树,院北面有6间大瓦房,靠西头的3间比东头的3间高大,称为北厅房,还有三间西屋。看门的把我们引进西屋登了记,有个30来岁梳着大分头的人对我们说:“你俩就住在北厅房里不要乱窜”。后知此人姓周,我们称他周老师,是施粥厂的主要负责人。
母亲把我们交代下来就走了。我们到北厅房一看,里面有一些小男孩,有的躺着、有的坐着、个个无精打采。我和哥哥呆了一会,觉得非常闷得慌,想到外面去玩玩。走到大门口,就被把门的喝住了:“干什么?”“俺想出去玩玩!”“不行!”我们质问道:“不是说出进随便吗?”“没有的事,来了就别想出去,滚回去!”我和哥哥目瞪口呆,知道上当了。几天以后,在我哥俩的破褂子后面用红土各印上了一个“收”字。
三、瓜干小米饭
我们进施粥厂时,里面已有男女孩子近200人。小的五六岁,大的十几岁。8至10个人编为一个“喝饭”小组,并有两个大一点的担任正副组长。每天喝两次饭。开饭前,几十个小组一一排好队等饭。待西门一开,便由七八个成年人每人挑两铁桶饭,走进来。此时,孩子们立即骚动起来。送饭人把早已摆在地上的一片片大黑碗个个舀满,不问二事,挑起饭桶回头便走。这些饭是商会雇用“马公祠”的农民在“大街商会”里烧作成的。此时,由看守人员(老师)按一组、二组的顺序叫喊,各组的两名组长负责为本组端饭,各人就地喝起来。饭是用粗小米和地瓜干熬成的,喝着有股苦味,饭里的砂子垫得牙疼,糠皮涮嘴刷刷响。饭喝完后,把碗集中到一起,看守人员再指令大一点的女孩子洗刷。
我们才进来的孩子,肚子里都没有食,开头几天喝着,还挺香,再往后就不行了。开始每碗还配有一块辣疙瘩咸菜,后来咸莱没有了,这碗瓜干小米饭就难以咽下去了。我们多么盼望家里的亲人来看看我们,送些咸菜来呀!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母亲和我大姨终于看望我们来了。见了亲人俺泪水盈眶。我迫不及待地问:“娘,你给俺拿来啥?”“杏”!母亲解开一块方形布子,黄橙橙的杏露了出来。接着十多个男孩子围了上来,我和哥哥就把仅有的20多个杏分给了大家十几个。我们这样做并不是新样,别的孩子的父母拿来的东西也给我们吃过。母亲问我们:“一天两碗饭能喝饱吗?”我和哥哥忙说:“碗大、盛的多,喝不了!”母亲离开时,我们再三地恳求:“再来看俺时,多买些咸菜,若无钱买咸菜,就拿些盐来!”以后家长来看望子女,都少不了带些盐来。每到喝饭时,一颗小盐粒就一口饭。盐,成了我们当时救命的仙丹。
四、大地铺
施粥厂刚成立时,是在北亭子两间屋子里,当时只有十多个孩子,行动也较自由。后来喝饭的孩子多了,才搬进了西院。北厅房里住着男孩子,后面的一排房子,东边住着年龄较小的女孩子,西边住着年龄较大的女孩子。我们所住的北厅房,地上铺着破苇席,有的地方什么也没铺,更没有被褥,各屋都一样。睡觉时横躺竖卧,乱七八遭,无法插足。我和哥哥就在西南角找了块地方睡下。白天我们也就在这块地方玩。屋里没有灯,到了夜里,有的咬牙,有的说睡话,也有想娘想哭了的。要是一翻身压到别人身上,便是连打加骂。光这些还不止,北亭子里的庙祝还喂了一只大狗,夜里不时地咬。这些声音使我们不寒而栗!
五、“人口手、刀工尺”
被困在施粥厂的孩子们终日无事干,喝了饭各自找投脾气的说笑玩耍。那些看守员想出了个点子,叫我们跑步,一跑就是十几圈。我们这些孩子大小不一,体质强弱也不同,杂乱的脚步声和带队人员的叫骂声交织在一起,满院子尘土飞扬,乱成一片,直跑得孩子们瘫倒为止。
北厅房里的西山墙上有一块用水泥漫的黑板,这是看守人员教我们识字用的。经常教我们识字的是一个王老师,这人上等个子,白净脸,不笑不说话,但打起“学生”来可是怪吓人的。第一次上课时,我们都很心胜。王老师把“人、口、手”三个字写在黑板上,一遍一遍地教我们念;然后,他用教鞭指谁,谁就站起来念。第二次,还是学“人、口、手”这三个字,可是还有好几个“学生”念不下来。他火了,说:“明日还念这三个字,谁有一个不认得,就挨一教鞭,两个不认得,就挨两教鞭!”结果第三次读“人、口、手”时,有的孩子头上被打起了大疙瘩。接下来,便学了“刀、工、尺”、“山、水、田”、“几、井、斗”、“牙、主、舌”和“皮、毛、衣”等字。有时上课前老师还教我们唱歌,学唱的歌有中国的,也有日本的。有一支歌的歌词开头是:“唱唱唱,亚洲第一大水扬子江……”日本的歌我们不爱唱,因为调子怪难听的。
六、虱子灾
施粥厂里的卫生条件很差,我们住的屋子里到处是烂棉花、破布和垃圾,从不打扫,看守人员从也不督促打扫。孩子们身上穿的破衣服从来没洗过。有的女孩子褂子破了,就从裤腿上撕下块布补在上面;男孩子裤褪烂了,走路不得劲,就干脆撕成半裤。有些小男孩还终日光着腚,因为当时施粥厂光给饭喝,不给衣穿。
由于大家穿的衣服不洗、不换、白天黑夜不离身,虱子就在各人身上繁殖起来。在炎热的夏天里,有些孩子还只好穿着破棉袄,更成了“虱子窝”,我们就叫他“虱子精”。如果走动着,还觉不出虱子咬,只要一住下,就咬得人不得安宁。夜里简直咬得睡不着觉,即使那些光腚“猴”们,尽管身上无虱子,但他们头发里有虱子;加之都在一起睡觉,别人身上的虱子也会咬他们的。一到白天,他们就比穿衣服的孩子挨咬差了。我们在不动或睡觉时,都少不了捉虱子,感到身上某一部位被虱子咬得难受时,就将手伸到那里慢慢地摸;抓住后,就放到嘴里咬死再吐出来。
七、“白媳妇”
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神经不大正常。一天上午,他摸进了后院的山洞里,出来后手里拿着一双沾满灰尘的小脚女人的鞋。他说:“我在洞里看到‘白媳妇’了!”在这之前曾有小孩说,他吃不了的瓜干饭倒在墙根,第二天就一点也没有了。后来有的则说,夜里上厕所时看到了“白媳妇”盘着腿坐在洞口上。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也确实听到过门外有走动的声音。这一切,把孩子们吓坏了,不等天黑就都钻进屋里不敢出来。可是夜里要小便呀,厕所就在山洞的前面,大家都怕碰上“白媳妇”,不敢去。鼓不住了,出屋门就开尿。不多日,北厅房门前的尿就横流成河了。
一天早上,看守人员提前摇铃开饭,说待一会儿上头要来人视察。饭后我们全体在院子里列队等候,约十点多钟,来了七、八个人,有的穿黄军装,有的穿大褂、戴礼帽,都很阔气。有的还用白手帕捂着嘴。一个穿便衣的,手里拿个小照像机,对着我们乱照了一气。那伙人看了一圈就走了。他们走后,那位“周老师”却暴跳如雷,对我们气急败坏地说:“今后不管白天黑夜,也不管男女,一律到厕所尿尿,谁再在门前乱尿,抓住重打十鞭子!”
有天夜里,我被尿鼓得睡不着觉,自己又不敢去厕所,就坐起来,想等别人上厕所时,跟着一起去。不多时,年龄比我大几岁的黄玉刚起来开门走出后,又把门轻轻地关上。我赶紧摸索着向门口走去。这里一条腿,那里一个头,好不容易摸到了门口,开门一看吓了我一大跳:有个象狗一样的东西趴在门外二层台阶上,一动也不动。我便壮了壮胆子喊了声“呔”!那家伙立即抬起头,竖起耳朵,两个蓝蓝发亮的眼睛直盯着我,可把我吓死了!我把门猛一关,回头便向里跑,只踏得那些睡觉的孩子连叫带骂。好歹到了我睡觉的地方,一头扎下就不敢动了。惊慌的心情稳定后,我才发现“尿”早已撒在裤里了!
穿着白鞋、白衣服的“白媳妇”我没见过,山洞里的狐狸夜里出来找东西吃倒是真的。
八、害眼
施粥厂不论男女,多数都害过眼。
起先,孩子们没有害眼的。可是,这里不兴洗手洗脸,我们的手和脸都脏得发黑。一天下午快要吃晚饭了,几个穿便衣的中年人来到施粥厂院内站了一会儿,看到我们这些象小鬼一样的孩子直摇头,然后找上我们的“周老师”,不知说了些什么就走了。次日下午,有伙大人给我们送来了十多个陶瓷大盆。“周老师”把我们召集到一块训话:“看看你们这个脏样,是人是鬼都分不出来!”他指着那些陶瓷大盆说:“从明天开始,就用这些盆洗脸,谁若不洗,我查住后,不客气!”从这以后,每天一早,我们“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洗脸。孩子们不分男女,五人一伙,六人一帮,自愿结成“洗脸小组”,到自来水管上接一盆水,三个人架到宽阔处,大家围起来洗脸。人多盆少,先来后到,轮流着洗。这个办法给眼病的传染创造了条件。几天后,先是在女孩子中间发现了有好几个“害眼”的,大家知道“害眼”传染,就不和她们一起洗脸,她们就在大家用完盆后再洗。没到十天的工夫,男女孩子之间大部分都害起眼来了。我也不例外。“害眼”白天不敢见太阳,晚上睡觉一闭眼就流泪,疼得睡不着觉。第二天醒来时,厚厚的眼眵把两眼粘住睁不开。若用手帮助睁眼,有时会把睫毛拔下来。后来想出了个办法用手指从嘴里抿出唾沫抹在眼上,过一段时间,眼眵就被唾沫泡软了,眼晴也就睁开了。
九、“大肚子病”
施粥厂里生活环境恶劣,孩子们很快就得病了。
我患了一种鼻子流血的病,三两天鼻子就流一次血,一次流一大滩。流完一次后,眼前发黑,头发晕,后来就头疼了,以致留下了一劳累就头疼的终生不治的后遗症。得这种鼻子流血病的孩子是少数,多数孩子患水肿病,每天那两碗霉味的瓜干小米饭,因为难以下咽,有很多人吃不到肚子里去,这对正在发育成长的孩子来说,根本谈不上“营养”。这还不算,整个夏天我们从未喝过一次开水,渴了尽喝凉水。吃上半生不熟的瓜干小米饭,再喝凉水就拉肚子。人越拉越瘦,可肚子却越胀越大,我们称这是“大肚子病”。患这种病的人后来就肿脸、肿腿,没有精神,全身无力。院子里的吵闹声越来越小了。病魔危及着孩子们的生命。
一天中午,从后院传来消息,说有个小女孩快死了,我和哥哥一起跑去看。这个女孩约有七、八岁,长长的头发已成了“毡片”,虱子在头发里钻出钻进。她那已失去血色的脸上,一双单眼皮的眼睛半闭着,上穿一件破条条褂子,下穿青色破半裤,露着肿得发亮的小腿和脚,两手紧攥着,躺在北厅房后面的墙根下,旁边放着一碗落有一层尘土的瓜干小米,是她没吃的早饭。过了一顿饭的时间,这个女孩攥紧的拳头慢慢松开了,一双眼睛完全闭上了,绿头苍蝇在她的鼻子上、嘴上和眼睛上乱爬、乱钻,她死了!不多时,看守人员叫了几个大些的男孩,用一块破席头把她一包,架出去,扔到了铁路东边荒凉的大石头坡上。以后,死的孩子越来越多,凡是要死的都被拖到“白媳妇”洞后面的僻静处去“待死”。死后,照旧扔到大石头坡。也有的家长知道了,抢先把死孩抬回家。后来施粥厂改了章程,死了的孩子不随死随扔了,白天死了,先用块破席头盖上,天黑后再扔出去。经常死人,给我们造成了心理上的恐慌。
十、令人发指的兽行
年龄较大、长相好一点的女孩子,都被安排在北厅房后面靠西头的三间北屋里住。这里的条件好得多,地上铺的是新席,屋里也打扫得比较干净,统共住着她们十多个人。看守对她们也特别优待,有时把自己的干粮给她们吃,泡好的茶也让她们喝,还经常到她们屋里说说笑笑,逗着玩。日久天长,这些女孩产生了一种优越感,总觉得她们比我们要“高贵”些,吃饭不和我们在一起吃,玩也不和我们掺合。而男孩和小女孩也产生了嫉妒心理,见了她们就骂。
在一个天气阴暗的早晨,孩子们还都没“起床”,后院传来了一个女孩呜呜啕啕的哭声,我们赶紧跑去看。这个女孩姓焦,是那些“高贵”女孩中的一员。她头发乱蓬蓬的,一面嚎啕,一面挣着把头往墙上碰,好几个大女孩拚死地拉着她。有的问她为啥,有的劝她别哭,可她好象什么都没听见,只是不要命的哭。大女孩们还是追问为什么?她才泣不成声地说:“俺说不出来,他们不是人!”这下可把我们这些小男孩弄懵了,她为什么会这样伤心?女孩子们苦苦劝她:“要想开点”她却悔恨地说:“这教俺出去咋见人啊,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好!”围观的孩子越来越多,那几个大女孩连拉加推把她拖进屋里,关上了门。
此时,我们这些岁数小的男孩子虽不知这个焦姑娘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但我们已经知道别人给他亏吃了。至此,我们也感到这些“高贵”的大女孩也有说不出的苦处,我们也就不再骂她们了。
十一、不准逃跑
正当施粥厂的孩子们在营养不良、疾病、死亡和遭受污辱的灾难中挣扎的时候,忽然又传来了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消息:日本人要用火车把我们运到别处去!孩子们听了都哭得喝不下饭。不过这个消息没有变成现实。据说,日本人确实有这个计划,把我们运到外地全部枪杀或活埋,以达到“维持社会治安”的目的。由于他们怕引起国内外公众的舆论,没有敢实施,仍然把我们关在施粥厂里,只是不准我们到社会上去。
日本人要把我们用火车运到别处去的消息。尽管当时还是传说,但已使原来就和地狱差不多的施粥厂又增加了浓厚的恐怖气氛。我们虽是孩子,但也懂得,继续待下去只有等死。于是有些大胆的男孩,决心要逃出去。一天夜里,我在矇眬中,听到山洞那里“咕咚”一声,接着北亭里的狗叫了起来,然后就是一阵急跑的脚步声。第二天夜里,这样的事又有几次。一连好几夜都如此。一天上午,有个中等个子胖乎乎的人,头戴礼帽,身着大褂,手执文明棍,由着守人员簇拥着,来到北亭房门前,向我们这些男孩子训话:“你们这些小孩太不知足了,在这里吃不花钱的饭,还学认字,有什么不好,竟敢逃跑!以后谁再逃跑,抓回来往死里打!”后来才知道,这人就是当时商会会长李养之。
李会长走后的第三天,有人扛来了一捆竹篾。这种竹篾约有一公尺长,是粗竹竿劈成的。还有几支黑乎乎的皮鞭和一些细麻绳。我们预感到这一定是用来对付我们的刑具。次日一早,有个看守人员领着几个年龄比较大、好欺负小孩的男孩,拿着一些麻绳走了出来。约十点多钟,他们用麻绳捆来了六、七个男孩子。我们都知道,这是前几天从这里逃跑后又到河滩去要饭被抓回来的。看守人员让他们趴在地上,每人抽了几鞭子,问他们还跑不跑?他们说:“不跑了!”这才饶了他们。过了两天,他们又抓回一个逃跑的男孩,进了门就把他绑在洋槐树上。这个孩子约十一、二岁,发肿的脸皮有点放亮,他是第二次逃跑被抓回来的。在树上绑了大半天,不给吃、不给喝。当看守人员把他放下来时,他一下就瘫坐在树下。问他还跑不跑,他已经无气力回答了。吃晚饭时,他的组长把饭端给他,他摇摇头,慢慢闭上了眼晴。晚上,这个孩子便“失踪”了。
施粥厂的看守人员抓回逃跑的孩子往死里打,但是,逃跑的仍然有增无减。几个看守便想了个鬼点子,让孩子们自己看守自己。刘福州、宋德、蒋力等人,他们都已十几岁,未进施粥厂时就是些“河滩王”,专门欺压小乞丐;到了施粥厂仍是恶性不改。看守们就利用他们,发给他们竹篾、鞭子,让他们看管别人。他们狗仗人势,手持竹篾任意打人。一次有个女孩说丢了一小包盐,刘福州问她:“谁偷去了!”她顺手指了一下坐在北厅房门前的一些有病的小男孩说:“准是他们!”刘福州立即让这些小孩排成一行,趴在地上,在每人的屁股上重打两竹篾,然后问他们偷没偷。凡回答“没偷”的,二番再打,有的被打的尿了裤子。待了不几天,蒋力看着一个叫孙即清的孩子不顺眼,就用竹篾打肿了他的腚。这类横行无忌的事经常发生,我们称为“打遍棍”。
看守出去抓人,就叫刘福州等人跟着。一天他们又去河滩抓从施粥厂逃出去的小孩,还抓进了几个新要饭的孩子。这中间有个六岁的小男孩,个子挺矮,两个耳朵特别大。刘福州等人就拿他开心,经常抓住两个耳朵把他提得老高,说是叫“端提锅”。这孩子哭着求饶,被裂开的耳朵根流出的血液里结成戛碴,第二天又被他们挣裂开……。天天如此,这孩子受不了这样的折磨,终于在一天夜里逃跑了。可是,第二天刚出太阳,他就被刘福州等人抓了回来。在看守的教唆下,刘福州等人把这个孩子捆在一条木凳上,捏住他的鼻子用茶壶往嘴里灌凉水,灌得肚子鼓起后,再用手往下按,凉水从小孩的鼻、口往外冒;然后再灌、再按。反复几次,这孩子快没气了。他们给他松了绑,把他扔到院西南角的墙根下,过了一会,他的嘴唇动了几下,紧闭的眼睛睁开一道缝,不一会就死了。
十二、死里逃生
施粥厂里的孩子们,经过几个月的折磨,已经奄奄一息了,恨不得插翅飞出这高墙大院。这时候家长带食物来探望孩子,把门人就不让进了,叫把东西留下,说他们给送进去。可是家长们拿来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到孩子们的手里。
有位姓吴的看守人员,是博山西域人。施粥厂惨害儿童的悲惨情景他也有些看不下去,便偷偷地把里面的真实情况透露给一些孩子的家长,帮他们出些搭救孩子的主意,知情的家长们,都千方百计地搭救自己的孩子。于春美、于春山姊弟二人病得站不起来,拿饭、上厕所都是在地上爬。他们的母亲对看守人员说:“我这两个孩子让你们操煞心了,他们有病,是自己不长出息,我把他们领回家治好病再送回来!”从早晨哀求到快落太阳了才得到允许。她把女儿背出施粥厂放下,再回来背儿子,这样走来背去往家倒,后遇卖青菜的杨德宏老人,就用担子把他俩挑回了家。我父母商量先把我接出施粥厂,因为我病得比哥哥厉害,若把我兄弟二人一起接出去家里也无法养活。当时我父亲的病更重了,家里生活仍然无着落。我母亲从伪保公所写了个条子去领我。“周老师”问我母亲“怎么保证你的小孩不再出来要饭呢?”我母亲撒了个慌,说“俺掌柜的现在卖鱼,家里有饭吃了!”“周老师”还不放心,威胁我母亲说:“如果发现你的小孩再出来要饭,抓回来就不客气了?”知道要离开施粥厂了,我恨不得一步就迈出大门!这时我哥哥拉住母亲的胳膊喊着:“娘,把我也领走吧,别让我在这里受罪了,再待下去我也会死的?”母亲给我哥哥擦了擦眼泪,自己也含着泪水说:“好孩子,听话,一块接出你们去没啥吃,还不是饿着,过些天我再来接你!”离开了相依为命的哥哥,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施粥厂里有些年龄大的男孩子,等不得家长来接救,他们白天三五成群秘密约好,夜里便互相照应集体逃跑。逃出施粥厂后,为避免被抓,不敢再到河滩要饭,有的干杂工、有的离开博山到外地讨饭,还有的当了小八路。到天冷时,施粥厂里只剩下20多个男孩子了,商会给他们发了用老蓝布做成的棉衣,由喝地瓜干小米饭改成了吃高粱窝窝头。这时,我哥哥仍在施粥厂里。
我母亲没有实现把哥哥领出施粥厂诺言,就与父亲先后饿病而死了。后来我哥哥也逃离了施粥厂。我们一路要着饭向八路军的根据地——高青县一带投奔而去。在那里我俩分别给俩家农民做了义儿,直到博山第五次解放后我和哥哥才先后回到了博山。
只办了六个月的施粥厂,夺去了几十条男女儿童生命。由于施粥厂的折磨,被亲人领回家不几天就死的孩子更多。博山西寨街前往“喝饭”的20多名男女儿童中,从施粥厂接出不几天就死去了5名,他们是昃三章、李二安、刘大麻、大梁妮和刘大妮子。
一、歉年
1943年,侵华日军在华北大搞“五次强化治安”,实行惨绝人寰的烧光、杀光和抢光的“三光政策”;同时,对城乡进行经济封锁。博山所出产的陶瓷、琉璃和铁器等,失去了农村市场。农村连年灾荒,就是有粮食也运不进博山城里来。博山城里的一些粮商和富户,趁机把粮食屯积起来,粮价飞涨。博山城里的穷苦人民陷入了严重的饥饉之中,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民国32年大歉年,那时候。大批的穷人被迫下了“关东”,没有下“关东”的都挣扎在死亡线上、卖儿鬻女、沿街乞讨。西冶街口的河滩一带人多,饭铺多,这里是乞丐最集中的地方。他们之中不仅有当地的穷人,还有周围农村被饥饿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不仅有成年人,还有很多未成年的孩子。有的人纵有布施之心,怎奈自己也十分艰难。于是出现了抢饭吃的现象。有人去饭铺买饭时,饥饿的孩子便悄悄地跟在后面,当你付了钱,拿着干粮要走的时候,他抢了就跑。你追,他就往干粮上吐唾沫、擤鼻涕,让你无法再要。有些山里下来的赶集人,回家时往往买一大块强面饼带上,这些饥饿的孩子腿脚跑得快,跟随到路宽人多的地方,从背后抢过来便跑。你紧追,他就掰下一块扔在地上,当你拾起饼来的时候,他已逃得无踪无影了。旁边的人往往都为抢饭的孩子喝彩,从来没人上前拦截。谁不知道这些孩子饿呀!就连观音堂口岗楼里站岗的伪军见了,也只是哈哈大笑而已。抢饭的孩子中也分阶层,有几个较大的孩子被称为“河滩王”。孩子们若抢到大些的干粮,必须首先“孝敬”他们。
当时驻博山的日军是菊池部队,还有为虎作伥的伪保安队伊来灝部以及伪警察。他们倒行逆施,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却偏偏要粉饰太平,维持所谓“东亚新秩序”。他们派出警察将河滩的乞丐一批一批轰出博山城,对饥饿的孩子们无计可施,就委托商会从城内各煤号、商店敛钱,办了个施粥厂,把他们收容起来。
二、上当
施粥厂成立以后,商会便派人整天在河滩观音堂大喊大叫:”小孩们,快到北亭子喝饭呀,尽着喝,进出随便家远的还可以住下!”这样的口号,对那些饥肠辘辘的孩子们是很有诱惑力的;就是那些没有沦为乞丐的孩子,谁愿意呆在家里挨饿!都想到北亭子“喝饭”去,况且是“尽着喝”。
我父亲刘在成是琉璃行业有名的轴子嘴匠。在那饥馑的年月里,他病饿交加,已卧床多日了。指望我母亲每天到姥娘家和大姨家去要几个煎饼,我们一家四口人泡煎饼汤吃。我和哥哥饥饿难忍,经常背着父母,到饭铺桌子底下拾些地瓜巴子和大虾头吃。端午节后的一天,母亲把我们叫过去说:“您爹爹的病越来越重,不能做炉了,外头人都说到北亭子去喝饭挺好,早上去,天黑回来,你俩也去吧,省得在家里饿死。”开始,我和哥哥都怕到那里受人欺侮,不愿去。可是搁不住母亲和大姨流着眼泪劝说,终于由母亲把我们送到北亭子去“喝饭”了。那是在北亭子西面的一个院子,我们是从院子西边的一个单扇门进去的。院子挺大,南院墙外是河,院墙里面不远有棵大洋槐树,院北面有6间大瓦房,靠西头的3间比东头的3间高大,称为北厅房,还有三间西屋。看门的把我们引进西屋登了记,有个30来岁梳着大分头的人对我们说:“你俩就住在北厅房里不要乱窜”。后知此人姓周,我们称他周老师,是施粥厂的主要负责人。
母亲把我们交代下来就走了。我们到北厅房一看,里面有一些小男孩,有的躺着、有的坐着、个个无精打采。我和哥哥呆了一会,觉得非常闷得慌,想到外面去玩玩。走到大门口,就被把门的喝住了:“干什么?”“俺想出去玩玩!”“不行!”我们质问道:“不是说出进随便吗?”“没有的事,来了就别想出去,滚回去!”我和哥哥目瞪口呆,知道上当了。几天以后,在我哥俩的破褂子后面用红土各印上了一个“收”字。
三、瓜干小米饭
我们进施粥厂时,里面已有男女孩子近200人。小的五六岁,大的十几岁。8至10个人编为一个“喝饭”小组,并有两个大一点的担任正副组长。每天喝两次饭。开饭前,几十个小组一一排好队等饭。待西门一开,便由七八个成年人每人挑两铁桶饭,走进来。此时,孩子们立即骚动起来。送饭人把早已摆在地上的一片片大黑碗个个舀满,不问二事,挑起饭桶回头便走。这些饭是商会雇用“马公祠”的农民在“大街商会”里烧作成的。此时,由看守人员(老师)按一组、二组的顺序叫喊,各组的两名组长负责为本组端饭,各人就地喝起来。饭是用粗小米和地瓜干熬成的,喝着有股苦味,饭里的砂子垫得牙疼,糠皮涮嘴刷刷响。饭喝完后,把碗集中到一起,看守人员再指令大一点的女孩子洗刷。
我们才进来的孩子,肚子里都没有食,开头几天喝着,还挺香,再往后就不行了。开始每碗还配有一块辣疙瘩咸菜,后来咸莱没有了,这碗瓜干小米饭就难以咽下去了。我们多么盼望家里的亲人来看看我们,送些咸菜来呀!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母亲和我大姨终于看望我们来了。见了亲人俺泪水盈眶。我迫不及待地问:“娘,你给俺拿来啥?”“杏”!母亲解开一块方形布子,黄橙橙的杏露了出来。接着十多个男孩子围了上来,我和哥哥就把仅有的20多个杏分给了大家十几个。我们这样做并不是新样,别的孩子的父母拿来的东西也给我们吃过。母亲问我们:“一天两碗饭能喝饱吗?”我和哥哥忙说:“碗大、盛的多,喝不了!”母亲离开时,我们再三地恳求:“再来看俺时,多买些咸菜,若无钱买咸菜,就拿些盐来!”以后家长来看望子女,都少不了带些盐来。每到喝饭时,一颗小盐粒就一口饭。盐,成了我们当时救命的仙丹。
四、大地铺
施粥厂刚成立时,是在北亭子两间屋子里,当时只有十多个孩子,行动也较自由。后来喝饭的孩子多了,才搬进了西院。北厅房里住着男孩子,后面的一排房子,东边住着年龄较小的女孩子,西边住着年龄较大的女孩子。我们所住的北厅房,地上铺着破苇席,有的地方什么也没铺,更没有被褥,各屋都一样。睡觉时横躺竖卧,乱七八遭,无法插足。我和哥哥就在西南角找了块地方睡下。白天我们也就在这块地方玩。屋里没有灯,到了夜里,有的咬牙,有的说睡话,也有想娘想哭了的。要是一翻身压到别人身上,便是连打加骂。光这些还不止,北亭子里的庙祝还喂了一只大狗,夜里不时地咬。这些声音使我们不寒而栗!
五、“人口手、刀工尺”
被困在施粥厂的孩子们终日无事干,喝了饭各自找投脾气的说笑玩耍。那些看守员想出了个点子,叫我们跑步,一跑就是十几圈。我们这些孩子大小不一,体质强弱也不同,杂乱的脚步声和带队人员的叫骂声交织在一起,满院子尘土飞扬,乱成一片,直跑得孩子们瘫倒为止。
北厅房里的西山墙上有一块用水泥漫的黑板,这是看守人员教我们识字用的。经常教我们识字的是一个王老师,这人上等个子,白净脸,不笑不说话,但打起“学生”来可是怪吓人的。第一次上课时,我们都很心胜。王老师把“人、口、手”三个字写在黑板上,一遍一遍地教我们念;然后,他用教鞭指谁,谁就站起来念。第二次,还是学“人、口、手”这三个字,可是还有好几个“学生”念不下来。他火了,说:“明日还念这三个字,谁有一个不认得,就挨一教鞭,两个不认得,就挨两教鞭!”结果第三次读“人、口、手”时,有的孩子头上被打起了大疙瘩。接下来,便学了“刀、工、尺”、“山、水、田”、“几、井、斗”、“牙、主、舌”和“皮、毛、衣”等字。有时上课前老师还教我们唱歌,学唱的歌有中国的,也有日本的。有一支歌的歌词开头是:“唱唱唱,亚洲第一大水扬子江……”日本的歌我们不爱唱,因为调子怪难听的。
六、虱子灾
施粥厂里的卫生条件很差,我们住的屋子里到处是烂棉花、破布和垃圾,从不打扫,看守人员从也不督促打扫。孩子们身上穿的破衣服从来没洗过。有的女孩子褂子破了,就从裤腿上撕下块布补在上面;男孩子裤褪烂了,走路不得劲,就干脆撕成半裤。有些小男孩还终日光着腚,因为当时施粥厂光给饭喝,不给衣穿。
由于大家穿的衣服不洗、不换、白天黑夜不离身,虱子就在各人身上繁殖起来。在炎热的夏天里,有些孩子还只好穿着破棉袄,更成了“虱子窝”,我们就叫他“虱子精”。如果走动着,还觉不出虱子咬,只要一住下,就咬得人不得安宁。夜里简直咬得睡不着觉,即使那些光腚“猴”们,尽管身上无虱子,但他们头发里有虱子;加之都在一起睡觉,别人身上的虱子也会咬他们的。一到白天,他们就比穿衣服的孩子挨咬差了。我们在不动或睡觉时,都少不了捉虱子,感到身上某一部位被虱子咬得难受时,就将手伸到那里慢慢地摸;抓住后,就放到嘴里咬死再吐出来。
七、“白媳妇”
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神经不大正常。一天上午,他摸进了后院的山洞里,出来后手里拿着一双沾满灰尘的小脚女人的鞋。他说:“我在洞里看到‘白媳妇’了!”在这之前曾有小孩说,他吃不了的瓜干饭倒在墙根,第二天就一点也没有了。后来有的则说,夜里上厕所时看到了“白媳妇”盘着腿坐在洞口上。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也确实听到过门外有走动的声音。这一切,把孩子们吓坏了,不等天黑就都钻进屋里不敢出来。可是夜里要小便呀,厕所就在山洞的前面,大家都怕碰上“白媳妇”,不敢去。鼓不住了,出屋门就开尿。不多日,北厅房门前的尿就横流成河了。
一天早上,看守人员提前摇铃开饭,说待一会儿上头要来人视察。饭后我们全体在院子里列队等候,约十点多钟,来了七、八个人,有的穿黄军装,有的穿大褂、戴礼帽,都很阔气。有的还用白手帕捂着嘴。一个穿便衣的,手里拿个小照像机,对着我们乱照了一气。那伙人看了一圈就走了。他们走后,那位“周老师”却暴跳如雷,对我们气急败坏地说:“今后不管白天黑夜,也不管男女,一律到厕所尿尿,谁再在门前乱尿,抓住重打十鞭子!”
有天夜里,我被尿鼓得睡不着觉,自己又不敢去厕所,就坐起来,想等别人上厕所时,跟着一起去。不多时,年龄比我大几岁的黄玉刚起来开门走出后,又把门轻轻地关上。我赶紧摸索着向门口走去。这里一条腿,那里一个头,好不容易摸到了门口,开门一看吓了我一大跳:有个象狗一样的东西趴在门外二层台阶上,一动也不动。我便壮了壮胆子喊了声“呔”!那家伙立即抬起头,竖起耳朵,两个蓝蓝发亮的眼睛直盯着我,可把我吓死了!我把门猛一关,回头便向里跑,只踏得那些睡觉的孩子连叫带骂。好歹到了我睡觉的地方,一头扎下就不敢动了。惊慌的心情稳定后,我才发现“尿”早已撒在裤里了!
穿着白鞋、白衣服的“白媳妇”我没见过,山洞里的狐狸夜里出来找东西吃倒是真的。
八、害眼
施粥厂不论男女,多数都害过眼。
起先,孩子们没有害眼的。可是,这里不兴洗手洗脸,我们的手和脸都脏得发黑。一天下午快要吃晚饭了,几个穿便衣的中年人来到施粥厂院内站了一会儿,看到我们这些象小鬼一样的孩子直摇头,然后找上我们的“周老师”,不知说了些什么就走了。次日下午,有伙大人给我们送来了十多个陶瓷大盆。“周老师”把我们召集到一块训话:“看看你们这个脏样,是人是鬼都分不出来!”他指着那些陶瓷大盆说:“从明天开始,就用这些盆洗脸,谁若不洗,我查住后,不客气!”从这以后,每天一早,我们“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洗脸。孩子们不分男女,五人一伙,六人一帮,自愿结成“洗脸小组”,到自来水管上接一盆水,三个人架到宽阔处,大家围起来洗脸。人多盆少,先来后到,轮流着洗。这个办法给眼病的传染创造了条件。几天后,先是在女孩子中间发现了有好几个“害眼”的,大家知道“害眼”传染,就不和她们一起洗脸,她们就在大家用完盆后再洗。没到十天的工夫,男女孩子之间大部分都害起眼来了。我也不例外。“害眼”白天不敢见太阳,晚上睡觉一闭眼就流泪,疼得睡不着觉。第二天醒来时,厚厚的眼眵把两眼粘住睁不开。若用手帮助睁眼,有时会把睫毛拔下来。后来想出了个办法用手指从嘴里抿出唾沫抹在眼上,过一段时间,眼眵就被唾沫泡软了,眼晴也就睁开了。
九、“大肚子病”
施粥厂里生活环境恶劣,孩子们很快就得病了。
我患了一种鼻子流血的病,三两天鼻子就流一次血,一次流一大滩。流完一次后,眼前发黑,头发晕,后来就头疼了,以致留下了一劳累就头疼的终生不治的后遗症。得这种鼻子流血病的孩子是少数,多数孩子患水肿病,每天那两碗霉味的瓜干小米饭,因为难以下咽,有很多人吃不到肚子里去,这对正在发育成长的孩子来说,根本谈不上“营养”。这还不算,整个夏天我们从未喝过一次开水,渴了尽喝凉水。吃上半生不熟的瓜干小米饭,再喝凉水就拉肚子。人越拉越瘦,可肚子却越胀越大,我们称这是“大肚子病”。患这种病的人后来就肿脸、肿腿,没有精神,全身无力。院子里的吵闹声越来越小了。病魔危及着孩子们的生命。
一天中午,从后院传来消息,说有个小女孩快死了,我和哥哥一起跑去看。这个女孩约有七、八岁,长长的头发已成了“毡片”,虱子在头发里钻出钻进。她那已失去血色的脸上,一双单眼皮的眼睛半闭着,上穿一件破条条褂子,下穿青色破半裤,露着肿得发亮的小腿和脚,两手紧攥着,躺在北厅房后面的墙根下,旁边放着一碗落有一层尘土的瓜干小米,是她没吃的早饭。过了一顿饭的时间,这个女孩攥紧的拳头慢慢松开了,一双眼睛完全闭上了,绿头苍蝇在她的鼻子上、嘴上和眼睛上乱爬、乱钻,她死了!不多时,看守人员叫了几个大些的男孩,用一块破席头把她一包,架出去,扔到了铁路东边荒凉的大石头坡上。以后,死的孩子越来越多,凡是要死的都被拖到“白媳妇”洞后面的僻静处去“待死”。死后,照旧扔到大石头坡。也有的家长知道了,抢先把死孩抬回家。后来施粥厂改了章程,死了的孩子不随死随扔了,白天死了,先用块破席头盖上,天黑后再扔出去。经常死人,给我们造成了心理上的恐慌。
十、令人发指的兽行
年龄较大、长相好一点的女孩子,都被安排在北厅房后面靠西头的三间北屋里住。这里的条件好得多,地上铺的是新席,屋里也打扫得比较干净,统共住着她们十多个人。看守对她们也特别优待,有时把自己的干粮给她们吃,泡好的茶也让她们喝,还经常到她们屋里说说笑笑,逗着玩。日久天长,这些女孩产生了一种优越感,总觉得她们比我们要“高贵”些,吃饭不和我们在一起吃,玩也不和我们掺合。而男孩和小女孩也产生了嫉妒心理,见了她们就骂。
在一个天气阴暗的早晨,孩子们还都没“起床”,后院传来了一个女孩呜呜啕啕的哭声,我们赶紧跑去看。这个女孩姓焦,是那些“高贵”女孩中的一员。她头发乱蓬蓬的,一面嚎啕,一面挣着把头往墙上碰,好几个大女孩拚死地拉着她。有的问她为啥,有的劝她别哭,可她好象什么都没听见,只是不要命的哭。大女孩们还是追问为什么?她才泣不成声地说:“俺说不出来,他们不是人!”这下可把我们这些小男孩弄懵了,她为什么会这样伤心?女孩子们苦苦劝她:“要想开点”她却悔恨地说:“这教俺出去咋见人啊,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好!”围观的孩子越来越多,那几个大女孩连拉加推把她拖进屋里,关上了门。
此时,我们这些岁数小的男孩子虽不知这个焦姑娘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但我们已经知道别人给他亏吃了。至此,我们也感到这些“高贵”的大女孩也有说不出的苦处,我们也就不再骂她们了。
十一、不准逃跑
正当施粥厂的孩子们在营养不良、疾病、死亡和遭受污辱的灾难中挣扎的时候,忽然又传来了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消息:日本人要用火车把我们运到别处去!孩子们听了都哭得喝不下饭。不过这个消息没有变成现实。据说,日本人确实有这个计划,把我们运到外地全部枪杀或活埋,以达到“维持社会治安”的目的。由于他们怕引起国内外公众的舆论,没有敢实施,仍然把我们关在施粥厂里,只是不准我们到社会上去。
日本人要把我们用火车运到别处去的消息。尽管当时还是传说,但已使原来就和地狱差不多的施粥厂又增加了浓厚的恐怖气氛。我们虽是孩子,但也懂得,继续待下去只有等死。于是有些大胆的男孩,决心要逃出去。一天夜里,我在矇眬中,听到山洞那里“咕咚”一声,接着北亭里的狗叫了起来,然后就是一阵急跑的脚步声。第二天夜里,这样的事又有几次。一连好几夜都如此。一天上午,有个中等个子胖乎乎的人,头戴礼帽,身着大褂,手执文明棍,由着守人员簇拥着,来到北亭房门前,向我们这些男孩子训话:“你们这些小孩太不知足了,在这里吃不花钱的饭,还学认字,有什么不好,竟敢逃跑!以后谁再逃跑,抓回来往死里打!”后来才知道,这人就是当时商会会长李养之。
李会长走后的第三天,有人扛来了一捆竹篾。这种竹篾约有一公尺长,是粗竹竿劈成的。还有几支黑乎乎的皮鞭和一些细麻绳。我们预感到这一定是用来对付我们的刑具。次日一早,有个看守人员领着几个年龄比较大、好欺负小孩的男孩,拿着一些麻绳走了出来。约十点多钟,他们用麻绳捆来了六、七个男孩子。我们都知道,这是前几天从这里逃跑后又到河滩去要饭被抓回来的。看守人员让他们趴在地上,每人抽了几鞭子,问他们还跑不跑?他们说:“不跑了!”这才饶了他们。过了两天,他们又抓回一个逃跑的男孩,进了门就把他绑在洋槐树上。这个孩子约十一、二岁,发肿的脸皮有点放亮,他是第二次逃跑被抓回来的。在树上绑了大半天,不给吃、不给喝。当看守人员把他放下来时,他一下就瘫坐在树下。问他还跑不跑,他已经无气力回答了。吃晚饭时,他的组长把饭端给他,他摇摇头,慢慢闭上了眼晴。晚上,这个孩子便“失踪”了。
施粥厂的看守人员抓回逃跑的孩子往死里打,但是,逃跑的仍然有增无减。几个看守便想了个鬼点子,让孩子们自己看守自己。刘福州、宋德、蒋力等人,他们都已十几岁,未进施粥厂时就是些“河滩王”,专门欺压小乞丐;到了施粥厂仍是恶性不改。看守们就利用他们,发给他们竹篾、鞭子,让他们看管别人。他们狗仗人势,手持竹篾任意打人。一次有个女孩说丢了一小包盐,刘福州问她:“谁偷去了!”她顺手指了一下坐在北厅房门前的一些有病的小男孩说:“准是他们!”刘福州立即让这些小孩排成一行,趴在地上,在每人的屁股上重打两竹篾,然后问他们偷没偷。凡回答“没偷”的,二番再打,有的被打的尿了裤子。待了不几天,蒋力看着一个叫孙即清的孩子不顺眼,就用竹篾打肿了他的腚。这类横行无忌的事经常发生,我们称为“打遍棍”。
看守出去抓人,就叫刘福州等人跟着。一天他们又去河滩抓从施粥厂逃出去的小孩,还抓进了几个新要饭的孩子。这中间有个六岁的小男孩,个子挺矮,两个耳朵特别大。刘福州等人就拿他开心,经常抓住两个耳朵把他提得老高,说是叫“端提锅”。这孩子哭着求饶,被裂开的耳朵根流出的血液里结成戛碴,第二天又被他们挣裂开……。天天如此,这孩子受不了这样的折磨,终于在一天夜里逃跑了。可是,第二天刚出太阳,他就被刘福州等人抓了回来。在看守的教唆下,刘福州等人把这个孩子捆在一条木凳上,捏住他的鼻子用茶壶往嘴里灌凉水,灌得肚子鼓起后,再用手往下按,凉水从小孩的鼻、口往外冒;然后再灌、再按。反复几次,这孩子快没气了。他们给他松了绑,把他扔到院西南角的墙根下,过了一会,他的嘴唇动了几下,紧闭的眼睛睁开一道缝,不一会就死了。
十二、死里逃生
施粥厂里的孩子们,经过几个月的折磨,已经奄奄一息了,恨不得插翅飞出这高墙大院。这时候家长带食物来探望孩子,把门人就不让进了,叫把东西留下,说他们给送进去。可是家长们拿来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到孩子们的手里。
有位姓吴的看守人员,是博山西域人。施粥厂惨害儿童的悲惨情景他也有些看不下去,便偷偷地把里面的真实情况透露给一些孩子的家长,帮他们出些搭救孩子的主意,知情的家长们,都千方百计地搭救自己的孩子。于春美、于春山姊弟二人病得站不起来,拿饭、上厕所都是在地上爬。他们的母亲对看守人员说:“我这两个孩子让你们操煞心了,他们有病,是自己不长出息,我把他们领回家治好病再送回来!”从早晨哀求到快落太阳了才得到允许。她把女儿背出施粥厂放下,再回来背儿子,这样走来背去往家倒,后遇卖青菜的杨德宏老人,就用担子把他俩挑回了家。我父母商量先把我接出施粥厂,因为我病得比哥哥厉害,若把我兄弟二人一起接出去家里也无法养活。当时我父亲的病更重了,家里生活仍然无着落。我母亲从伪保公所写了个条子去领我。“周老师”问我母亲“怎么保证你的小孩不再出来要饭呢?”我母亲撒了个慌,说“俺掌柜的现在卖鱼,家里有饭吃了!”“周老师”还不放心,威胁我母亲说:“如果发现你的小孩再出来要饭,抓回来就不客气了?”知道要离开施粥厂了,我恨不得一步就迈出大门!这时我哥哥拉住母亲的胳膊喊着:“娘,把我也领走吧,别让我在这里受罪了,再待下去我也会死的?”母亲给我哥哥擦了擦眼泪,自己也含着泪水说:“好孩子,听话,一块接出你们去没啥吃,还不是饿着,过些天我再来接你!”离开了相依为命的哥哥,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施粥厂里有些年龄大的男孩子,等不得家长来接救,他们白天三五成群秘密约好,夜里便互相照应集体逃跑。逃出施粥厂后,为避免被抓,不敢再到河滩要饭,有的干杂工、有的离开博山到外地讨饭,还有的当了小八路。到天冷时,施粥厂里只剩下20多个男孩子了,商会给他们发了用老蓝布做成的棉衣,由喝地瓜干小米饭改成了吃高粱窝窝头。这时,我哥哥仍在施粥厂里。
我母亲没有实现把哥哥领出施粥厂诺言,就与父亲先后饿病而死了。后来我哥哥也逃离了施粥厂。我们一路要着饭向八路军的根据地——高青县一带投奔而去。在那里我俩分别给俩家农民做了义儿,直到博山第五次解放后我和哥哥才先后回到了博山。
只办了六个月的施粥厂,夺去了几十条男女儿童生命。由于施粥厂的折磨,被亲人领回家不几天就死的孩子更多。博山西寨街前往“喝饭”的20多名男女儿童中,从施粥厂接出不几天就死去了5名,他们是昃三章、李二安、刘大麻、大梁妮和刘大妮子。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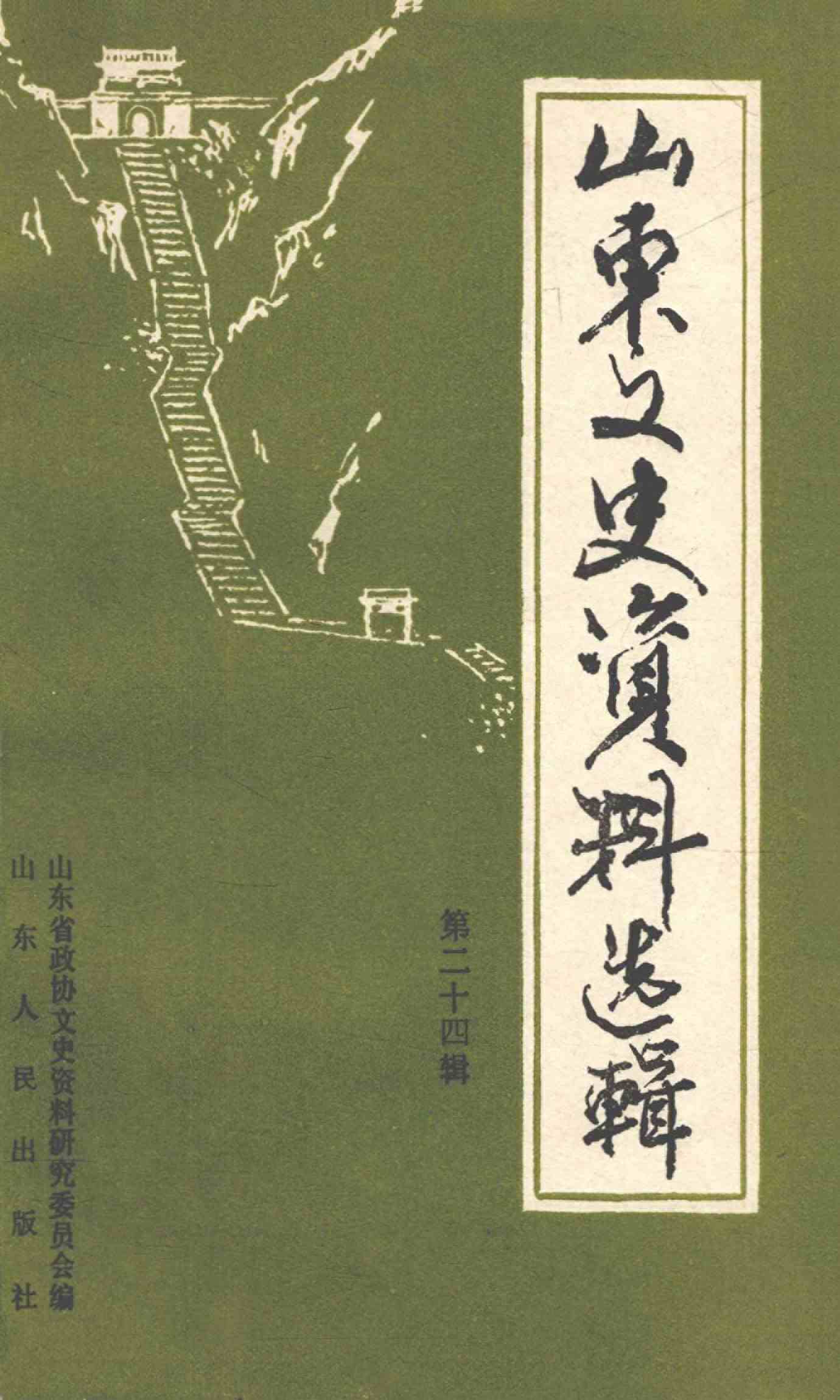
《山東文史资料选辑》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本书内容分述了,回忆抗日战争初期郓城县的统战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斗争中的滨海区、抗日战争初期党对泰山区道会门的统战工作、争取刘子昭部杆子会加入八路军的经过、忆汉斯·希伯参加英模大会片断、沈鸿烈在沂蒙山区、抗日战争时期的李先良、李先良与赵保元角逐的前前后后、忆省立第一乡师老校长鞠思敏先生、刘景良部活动片断等。
阅读
相关人物
刘元武
责任者
相关地名
山东省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