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生活琐记
| 内容出处: | 《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三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50020020220002343 |
| 颗粒名称: | 留日生活琐记 |
| 分类号: | K250.652 |
| 页数: | 14 |
| 页码: | 239-252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叶瑛桐留日生活琐记的内容,包含了我的家世,经营航商,赴日留学等。 |
| 关键词: | 留学 叶瑛桐 日本 |
内容
我的家世
我是山东日照县占子村人,祖父叶汝明水手出身,经商致富集资购船,有大帆船5艘,清末航行日本、朝鲜、东南亚及国内沿海口岸。因抗拒海匪屡次在海上激战成仇,终被海匪绑架杀害。我父兄弟2人,大爷是清末贡生,我父叶春墀清末考取官费留学生,毕业于长崎高等商业学校,纳日女河内花子为妾。归国后任山东商业专门学校校长12年,因政局变化辞职来青岛,任青岛大学教授、青岛取引所(即交易所,系中日合资500万元)常务理事、山东沿海渔航局总局长、青岛地方银行行长等职务,从20年代开始,父亲继承祖业,集资经营航海运输事业。先后购买中、小轮船7艘,成立青岛裕泰轮船公司,成为青岛沿海航商中第二大户,对航运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我中国母亲生7男4女;日本母亲生1男2女共兄弟姊妹14人,现存者只有4人了;二嫂今井芳野是二哥璧桐留日时带回的,二哥早年逝世,遗孤连欣现在日本。
我家与日本人两代通婚,血缘所关我爱日本人。但二三十年代日本人在青岛的所作所为,又使我恨日本人。在尖锐的民族矛盾面前,我父大义凛然地和我日本母亲离了婚;我二哥则因我日本二嫂的关系,血染荒郊,魂归故里。所以轮到我留日的时候,我父临别赠言第一句话就是:永远不能再和日本女性恋爱、结婚。我是恪守了这一庭训的。
经营航商
我的家庭是一个带有浓厚封建意识的资产阶级家庭。又因两世经营的都是较大的航商,所以我自幼就有乘长风,破万里浪的愿望。13岁时,考上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在福建马尾港设立的海军幼年军官学校,因母亲不同意,没有上成。15岁又登定海军舰为见习士官,以后历任三副、二副等职务。18岁又回铁路中学,20岁时,1937年卢沟桥炮声一响,我就考入了洛阳军官学校。在尚未复试期间,我又去考航空学校未取,军校也回不去了,只好回到青岛,学着向军统方面作情报工作。
不久,日寇海军在青岛登陆。我二哥受青岛海关关长之命,乘日寇军舰到石臼所通知当地开关,与青岛通航、通商,被当地商会会长、我父航业方面的竞争对手贺仁庵向当地国民党县政府诬告为汉奸,未经审讯即遭杀害。贺并向当地国民党五十九军军长庞炳勋诬告我父与我二哥内外勾结要献日照投降。庞将举兵来捕,我乃奉父母之命带幼弟弱妹共8口,乘帆船夜间出海逃生。时值腊月,滴水成冰,海上西北狂风连刮了四五个昼夜,小帆船去青岛正是顶头风,3天才走了30多里,以后竟至寸步难行。海上白浪滔天,北风怒吼,小船漏水,全家都泡在冰水之中,食物及饮水即将断绝,母亲要投海。当此生死关头,我毅然决定宁可承担投敌苟活的骂名,也要救出一家老小的性命。于是我拔出手枪威胁帆船老大,径直向正在石臼所港内向岸上开炮的日军军舰驶去。
日舰在查明我们确系我二哥的亲属之后,就把我们装上军舰,送回青岛。这时的青岛已在太阳旗下,我们成了亡国奴。
亡国奴的第一大痛苦就是不自由。中国人都不想当汉奸,但他们非逼着我父亲干不可。我家住无棣一路,路不宽,海军特务部的几辆汽车就摆满了。夜以继日,舌敝唇焦,翻来覆去,喋喋不休,一连20几天。他们摆出了安定市面、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等无数的理由,让我父亲出来维持治安。我父亲的理由只有一条:日没西山,气息奄奄,力不从心,只能来世再效力了。以后他们找到了赵琪(北洋军阀时代的胶澳商埠局总办)任青岛汉奸市长,才把我父亲放了。但又加上一个条件:必须出来组织航运,繁荣市面。我父亲坚决不干,但又怕过分得罪日本人,日子不好过,于是他继续装病,我就代表他出任我家轮船公司总经理。
公司是自己的,一切自己说了算,应当是很神气的,然而不然,上头有鬼子,鬼子说了算。为了胡弄鬼子,就得每天卑躬屈膝、点头哈腰说些假话、胡话,精神上是痛苦的。轮船跑的地方,大都是解放区,几乎每一个船员都免不了要替解放区的亲友捎带一些东西。日本水上宪兵队查得很严,查出来就要逮捕,刑讯,最后大部分都要“保释”,这时就必须由我出马了,到宪兵队去盖章,领人,这个滋味也很不好受。有一次我被宪兵打了两个耳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挨打。
赴宴饮酒本来是一件乐事,但一个人如果天天被逼着吃些肥鱼大肉,喝些过量的酒,那就不但不是享受,而且是一种痛苦了。我就是这样的,每天要接到许多请帖,这是因为当时船少、货多,货主设宴招待,请求我给他们留出舱位的,这些宴会可以不去,但有一些非去不可。如日寇汉奸设下的鸿门宴,叫你去讲条件的;或是公司有求于别人而设的宴会,我是主人,必须带头“欢呼”痛饮,其后果是十分痛苦的,身体也受到影响。在一段时间内,我拼命想办法,如能逃脱一次宴会,就是最大的幸事。
我在小港经营航业几个月,慢慢地就创出了一些名声。“人怕出名猪怕壮”,一点不错。日寇海军特务部找到我父亲说,听说你家四公子日语好,人又能干,请他到部里来,弟继兄“业”吧!于是又一次在我家引起了一场新的震动。最后由母亲决策,父亲出面对日寇回答说:“四子日语还不过关,让他到贵国去深造几年,回国后再为皇军效力不迟。”这样,我由日本海军特务部开具护照,保送去日本留学。我家之规,晚辈外出,长辈向不送行。那次父亲破例送我到大港码头轮船“熊野”丸上,临别郑重宣布3条庭训:
1.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2.为此,所学的内容一定要有利于抗战救国,毕业后立即奔赴后方参加抗战;
3.绝对不许和日本女子谈恋爱、结婚。
历史事实证明:这3条我都做到了。
赴日留学
我在中国看惯了日本的军舰、飞机和军国主义分子的狂妄傲慢,心想日本内地一定是富饶繁盛的,结果是大出意外,我到日本后的第一印象是日本人穷。
我在3年航海生活中,走遍了沿海各大城市,其中西式建筑都占百分之七八十;我国旧式的建筑不过十之二三。日本内地则与此相反,西式高大建筑物不过十之一二,其余十之八九大都是日本传统旧式的小木板房(二层者居多)。虽说是为了防震,但究竟也暴露出国民收入较低、国家财富有限的实底来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不高,四五口之家,一个劳力月收入百元左右,紧紧巴巴过日子,谈不到什么享受。3年之后,我到日本东北地区——山形县去滑雪,在农村住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农村更穷,仅能吃饱而已,并不比中国北方强多少,日本老百姓的钱都叫当官的搜刮去当作军费开支了。
我对日本人的第二个印象是日本大多数人心眼好,也就是善良。他们希望别人都能好起来,遇事能替别人着想,体贴人,同情心强,助人为乐,这些我从我养母身上早已领会到了。这次到日本一看,日本妇女和我养母一样的人几乎是百分之百,男子也有一大半是如此。日本军国主义者及其部下是日本人中的败类,是少数。
我是从我的全体同学中得出这个结论的,除了一个他父亲死在中国战场上的同学对我保持疏远外,所有的同学都很亲切、和蔼、诚恳,难道这些都是假的吗?不是。以后我和他们离别了40多年之后,他们又拿出钱叫我到日本去会面,时间和事实有最后的发言权。
在日本上学,住下宿屋最便宜,这都是一些生活不宽裕的家庭挤出一间屋来租给学生,房租最多不超过10元,加上三餐饭费一二十元,一般三十来元就能解决食宿问题;还能在饭后和家人对话练习日语。但我嫌老太太啰嗦,住了不久,便搬到公寓里去了。
公寓有如我们现在各城市中的集体宿舍的套房。有套一、套二、套三不等,但学生一般都是套一的,很方便,而且可以各行其是,互不干扰。我住公寓时间最长,还曾在房中自炊过,做一些在中华料理店中吃不到的菜,请日本同学来吃,我们一起喝日本酒,唱歌、跳舞、角力、做游戏。只要不闹得太厉害,邻居是不干涉的。
我是3月间到日本的,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考哪个学校,我本来打算考东京高等商船学校,可是来此之后,才知道此校在战时不收外国留学生。原因很清楚,在4年的学习中最后一年是航海实习,而实习又完全是枪炮、鱼雷、扫雷等一套海军军事训练,当然他们是不能让外国人了解他们的军事秘密的。我带来了青岛日军特务部的护照,如果拿出来交涉一下,他们是有可能破例收下我的,但我决心不再蹈我二哥的覆辙,所以我就考入了早稻田大学第二高等学院商科。
早稻田大学是日本5大名门学校之一,是已故首相大隈重信侯爵创办的。大隈侯本人富有自由色彩,所以早大的校风也比较民主自由。按日本当时实行的德日制教育制度:小学6年,中学5年(一贯),高校3年,大学本科3年,共17年,较英美制还多一年,我是高中毕业想上大学本科,所以必须要经过高校阶段。
高校有些象大学预科,文理分科,我选的是商学系,属于第二高院(一院是理科)。课程有国语、汉文、英文、经济学、哲学、逻辑学、心理学、第二外语(对我来说是第三外语)、自然科学等。其中英文时间最多,每周6堂,进度也快,每堂要学一二十页原文文艺小说,每天用于预习、查生字的时间就要一个多小时。其次是经济学概论,难度较大;其实最难的还是国语,这不是我们中国学校中的国语,它名为国语,实际上是日本的古文。它高奥艰深,诘屈聱牙,我自束发读书以来,从来没有不及格的功课,这次碰上这块硬骨头,啃了一年多最后才勉强弄了个及格。
高等学院介于中学和大学之间,功课不象大学那么严格要求,但我可不敢稍有松懈,尽管同学老师都对我很好,但谁知道内心究竟如何?我现在虽已远离战场,但洛阳军校的落日大旗、马鸣箫箫仍然在我心目之中。我抛弃了国民的天职,远逃异国,靦颜事敌,强为欢笑,内心是痛苦的。我拼命用功昼夜不懈,一年之后,除国语和法语之外都达到了优秀水平。
功课压力减轻了,我就参加了早稻田篮球队。以后我又参加了柔道队,虽然没有取得高段位,但也锻炼了不怕苦,不怕死,一拼到底的精神。在柔道场上我认识了东北同学王德成,其实他并不练柔道,只是喜欢看看而已。此人忠实诚恳,我俩一见倾心,说起来才知道他和我是同住在一个学生寮里——千岁乌山明治寮,以后我们经常互访、谈天。他谈到东北人民受日本人的压迫欺凌时,常常落泪。我那年正是21岁,血气方刚,当然是无限同情。有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一个姓于的同学屋内,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姓陈的台湾同学,他拿出了一张写好的誓约书,大意是我们4个人为了抗日反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生死与共,万死不辞,如有违反,甘受最严厉的制裁等,下面的组织名称是“东亚青年抗日联盟”,4个人都签了名之后,就烧了。以后王德成给过我几次抗日传单,叫我分发,我带进电影院之后,也没敢分发,放在座位上就走了。
我是一个心粗胆大之人,也颇能言谈,所以我对中国留学生确实做了不少宣传工作。可惜在抗战时期到日本去上学的留学生大部分是想弄个较高学位,回国后找个挣钱多的工作的,打算抗日的人较少,而且人人都知道日本刑事(便衣警察)很厉害,所以很少有人接我的话碴儿。
和我能谈得来的知心朋友有方旭和吴建。方旭是山东军阀方永昌的弟弟,在一次我俩游山时他告诉我,他是共产党,被捕后在方永昌的压力下,他自首了,但他表示作为一个中国人,一定抗日到底;吴建是山东省高等法院院长的儿子,民族观念很强,我们3人立誓毕业后一定到后方去参加抗日工作。胜利后,我介绍他俩去山东省立医专(即今医学院前身),分别任总务长和训导长,解放后,失去联系。
1940年春,我以优秀成绩毕业于早大二高。本来可以免试进入大学商科,但我想到经过几年奋斗,虽然还不敢和最优秀的日本学生比,但在一般中国留学生中是有一定竞争能力的,于是我又报考了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竟被录取了,我告别了东京,赶到京都上课。
日本有9个帝国大学。这是日本国家的最高学府,学生制服的铜扣上有菊花纹章(皇室纹章)。过去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非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的不能担任大臣职务。我到学校一看,校舍建筑宏伟壮观,设施周全,教官(帝大教授称为教官)人才济济,气宇不凡,学生沉稳肃穆,一副官派,果然和自由民主空气甚浓的早稻田大学有所不同。
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向来以思想进步而闻名于世,但在很早以前进步教授早已被清洗,现在又是战时,思想控制极严。图书馆中虽还有几本《资本论》,但绝对无人敢看,我却从同学梁纫武的口中多少了解到一些进步理论的端倪。我当时认为:从理论中说是对的,但暴力革命对不对呢?我不敢说,在我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中庸之道。
经济学概论讲座是高田保马先生,统计学是蜷川虎二,日本经济史是本庄教官,统制经济学是龙川先生。上课都是讲演式的,老师都有著作,但讲授的与书上不同,因此必须作随堂笔记,我练了半年才能跟上。
1941年12月日军袭击珍珠港,日美英德之间的战争全面爆发了。一开始,我为日军的侥幸成功和近似疯狂的扩大宣传所迷惑而感到有些惶惶不安,但很快我就从大半数日本人民的态度中看透了,这对他们决不是个喜讯。配给(食物)越来越少,而且质量越来越差,一见到街上有人排队就赶紧排进去,不管是什么,只要是食物就买。出征的越来越多了,“护国英灵”也越来越多。日本政府宣布: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半年内就要修完全部课程,作为已经毕业,一律出征。这样算来,我到1942年秋季即可毕业了。日本人个个愁眉苦脸,很少看到笑脸或听到笑声。于是我看透了:日本必败!我怎么办呢?这时恰好有关西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一位教授来问我是否可在秋季毕业后,到关大中国经济研究室去担任助教工作,我认为有请示父亲的必要,就去领了回国许可证,准备回国一次。
被捕羁押
在我准备动身的前一天,有两个刑事到我住的公寓来说,我的回国许可证上的号码写错了,需要到分署去更正一下,我就随他们去了。到了分署之后,他们拿出了一份东京警视厅的来文,上面写着:“叶瑛桐因违反治安维持法,应押解来京。”当下我就被拘留在分署了。
3天之后,由东京来了两个獐头鼠目的刑事把我押解到东京,寄押在六本木警察分署。过了几天,就押送到地方法院,问我:“你认识王德成吗?”“认识。”“什么关系?”“朋友关系。”“你们搞过什么活动?”“没有搞过什么活动。”他冷笑了一声,就把我押还六本木,一直3个月没有再审问。
在这3个月中最大的痛苦是饥饿。我在入狱之前已经在当时的定量分配(每天每人食米2盒3勺,大约可蒸饭3小碗)制度下,饱尝饥饿之苦。现在才知道了真正的饥饿之苦,在狱中的定量又被克扣掉将近一半,再加上几乎没有任何副食,于是把我饿得头昏目眩,四肢无力,身体逐渐衰弱。什么悲观、失望、恐惧、消极等不健康的思想不断出现,需要不断地和这些消极思想作斗争。同监的共党嫌疑分子宫本给了我很大鼓励,他首先同情我的抗日行动,这样我们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他比我寄押的时间长,受刑次数也多,年纪也大(大约有40多岁了),所以他简直就成了我的老师和保护人。他把家中送来的食品分给我吃,把新犯人吃不下的囚粮向看守要来给我吃,在我受了刑伤之后,替我敷药治疗。我从他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磊落胸襟,对共产党有了敬仰(也有恐惧)之心。这对于我以后在1949年拒绝国民党北平市政府让我撤退到台湾的命令留在北平,把市立七中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的行动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他没有向我宣传过共产主义,我也从来没有向他打听过,我不想在抗日罪之上,再加上一个共产罪。所以我在北平解放之前,对于共产党、共产主义几乎是一无所知。
3个月之后提审了。预审员原来就是押解我来东京的那两个刑事:一个是警部端保登治郎;那一个警长叫什么就忘了。讯问是公式似地进行,不承认就打,以后我发现,刑讯是逐渐升级的。例如:
第一次打耳光数十下;第二次,是拳打脚踢;第三次,用灌了铅的簿记棒抽打背部,用脚后跟捣击大腿(受讯人跪着);第四次,用钢钎插进受讯人手指与指甲中间,然后再敲击这些钢钎;第五次,把钢钎通上电,然后跳到我身上唱“爱马进行曲”,呼喊“支那猪万岁!”
痛苦可忍,侮辱难受,我一个右摆拳把端保打得摔倒在地,又举起面前的小桌,向正在拔枪的狗崽子砸去,然后翻身一跳,就从窗户中跳到了街道上。
我忘记了这是在外国——战时的日本,它不会让一个抗日青年逃脱的,不大工夫,我就被毒打一顿之后投进了一个黑暗地狱。
我不知昏过去了有多长时间,只觉得浑身奇痛而且好象被绑紧了一样,丝毫不能转动。等我神志逐渐清醒而且眼睛也适应于黑暗时,这才慢慢弄清楚:我是被塞进了一个仅能容下一个中等身材的日本人的石窟中了。我身高一米七八,当然更加难受,不用说转身、伸腿,连抬一下头都很困难,我心里一着急,又昏就过去了。
当我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只能用在母体中的那种姿势,两手捧头,膝盖顶在胸口上,蜷成一个人肉团。他们用了何种巧妙手术,把我塞进来的,我已来不及思考了,只是看着石缝里的阳光,亮了又暗,暗了又亮,大约是3天或4天过去了。
我的忍耐力已经接近崩溃了,我不想再活下去,于是我慢慢拉紧身上的一件破衬衣,用牙齿固定住一头,那一头用半只手(曲而不能伸的手)揪紧一头,逐渐用力。这是我从柔道中学会的“绞技”(不是用手绞而是用衣襟),平日百发百中,现在倒也管用。我感到神志逐渐模糊,心中有一种超脱感,昏昏如睡之感……忽然爆发了一阵强烈的咳嗽,以致使脖颈突然变得粗起来,一下子就把绞颈的衣襟撑开,于是我也死不成了。这大约是人类的自然保护能力吧。
在清醒过来的时间内,我想:我太软弱了。我的罪不至死.顶多判几年刑罢了,来日方长,我还年轻,父母养育之恩及国难家仇均未报,我不应当求死,应当求生!
说来也巧,又过了一两天之后,就把我放出来了。我已不能行动,瘫在铁笼内几天之后,来人叫我出去,到了办公室,一看不是审讯人员,而是我二嫂在那儿。二嫂一见我就哭了,我也不禁悲从中来。二嫂说:“平日劝你好好读书别问外事,你不听,现在后悔了吧!你也没干什么大事,人家都招认了,你何苦老是替别人受刑呢?”此时此地这些话对我起了很大作用。说实话,我平日对二嫂的感情不算很好,但现在是生死关头,她代表全家来看我,我就不能不好好重新考虑了。
下一次的审讯,审讯员换了一副面孔,不打不骂光捡好听的说。我也早就想好了:死不怕,但死不成的滋味确实太可怕了,不管怎么说,先得保住命,活下去。于是我就把过去和王德成等人订立盟约等活动统统都讲了出来,我想这下子总算过了关了吧!谁知下次提审,他们又换成原来恶狠狠的面孔,说我又隐瞒了重要情节,又把我打了一顿。以后看我实在没有了,也就算了。
以后的狱中生活是比较平静的,我请关押在楼上笼内的老大娘给我缝制一副垫肩,准备判刑后到北海道去干伐木工。
一个秋阳杲杲的上午,一位判事老爷在审讯室出现了,他高坐堂室,神气十足,先问了一下我的身体情况,接着就宣读了判决书。先是列举我的许多严重“罪行”,最后说:“姑念其年幼无知,受人蛊惑,经教育尚能招认,表现了悔改之心,为此特予宽大处理——驱逐出境!”
脱险回国
我收拾简单的行李,向狱中同人告辞,随着押解人员向神户而去。在神户码头派出所又等了好几天。一天夜里星月无光,突然得到命令:秘密登船;但船开出去不久,又停了下来。这样开开停停,走了好几天,还只是在朝鲜南岸岛屿中捉迷藏,打转转。
在旅客们交头接耳的窃窃私语中,我逐渐明白了,在我被关押的半年多的时间里,日军从太平洋上胜利的云端中跌落下来了,日军逐渐后退,美英军步步进逼,上有飞机,下有潜艇,大约日本船只的损失很大,现在这种开开停停的航法,正是在和美国潜艇兜圈子呢。
我听了以后,又是高兴,又是害怕,我偷偷地找了一根半截铁棒和一块木板,心想:船一旦被炸,我先抢上救生艇,谁敢拦挡,我就打死他!
有一天深夜,轮船正在双子群岛内碇泊,忽然传来了船头起锚机轧轧作响的声音,这说明轮船要开始航行了。我兴奋地到甲板上瞭望了一下,从山影、风向、星斗方位看来,船已转向正西——大陆方面,而且是全速航进,心想:不久可看到祖国亲人们了。
第二天早上我刚从朦胧中醒来,就听到外面传来了一阵惊呼声。我急忙来到甲板上一看,只见烟筒上黑烟滚滚,机声轧轧,轮船象一匹受伤的野兽拼命地向左急驶,船身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向左舷倾斜,情况十分危急。在许多人的指点、惊喊下,我才看清了在几百米之外,有一条白色航迹,正在向本船右舷飞驰而来,“不好!鱼雷!”经过了难忍的几十秒钟之后,鱼雷竟从本船右舷后尾远处交叉而过。许多旅客互相拥抱,有的人在跪地祈天,我才感到两只紧握的拳中已冷汗涔涔了。
其后不久又来了一艘日本小型驱逐舰在后护卫,又不知从哪儿冒出了几艘日本商船来,大家结伴同行,十几个小时之后,我就远远望见崂山高角了。
我到家之后,第一个见到的是母亲,母亲见我大哭,说她天天祈祷的菩萨显灵了。我却顾不得哭,母亲身旁放着一盘西式蛋糕,我一下就吃得干干净净。
听说我脱险回青的消息,立刻有许多亲友前来慰问,我无法细谈。先到了湖南路宪兵总队(今档案局址)报到,接见我的副官满面春风首先向我祝贺,并说东京警视厅曾来电征询我们意见,我们认为叶君府上都是亲日的,应当早日放回,使之为建设大东亚而努力,我满口答应。当我回家后不久,海军特务部就送来了港湾部高级嘱托的委任状,联合准备银行送来了经济研究室主任的聘书,我一一表示感谢收下了。
夜间我们全家开会研究,青岛呆不下去了,必须立即奔赴后方参加抗战。3天后我带领刚在东文书院毕业的五弟到了南京。见了过去东文书院院长、现任要人的大汉奸李仲刚,他非常高兴,马上发表我为南京警备司令部少将联络处长。我弟为附员。我回青后向宪兵队报告,他们向我祝贺。此时已将过春节了,我说过了正月十五动身去南京,实际上我初四日就动身了,买的是南京车票。到了徐州,我就转车到商丘,下车住店,次日化装乘地排车到亳县,找到介绍人指定的关系人,护送我到两军交界处再换了一个伪军护送,当天就平安到达界首。当时我看到城墙上国旗飘扬,军号嘹亮,不禁潸然泪下,默诵杜诗: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作者现为青岛华海信息翻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青岛家政艺术学校校长)
我是山东日照县占子村人,祖父叶汝明水手出身,经商致富集资购船,有大帆船5艘,清末航行日本、朝鲜、东南亚及国内沿海口岸。因抗拒海匪屡次在海上激战成仇,终被海匪绑架杀害。我父兄弟2人,大爷是清末贡生,我父叶春墀清末考取官费留学生,毕业于长崎高等商业学校,纳日女河内花子为妾。归国后任山东商业专门学校校长12年,因政局变化辞职来青岛,任青岛大学教授、青岛取引所(即交易所,系中日合资500万元)常务理事、山东沿海渔航局总局长、青岛地方银行行长等职务,从20年代开始,父亲继承祖业,集资经营航海运输事业。先后购买中、小轮船7艘,成立青岛裕泰轮船公司,成为青岛沿海航商中第二大户,对航运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我中国母亲生7男4女;日本母亲生1男2女共兄弟姊妹14人,现存者只有4人了;二嫂今井芳野是二哥璧桐留日时带回的,二哥早年逝世,遗孤连欣现在日本。
我家与日本人两代通婚,血缘所关我爱日本人。但二三十年代日本人在青岛的所作所为,又使我恨日本人。在尖锐的民族矛盾面前,我父大义凛然地和我日本母亲离了婚;我二哥则因我日本二嫂的关系,血染荒郊,魂归故里。所以轮到我留日的时候,我父临别赠言第一句话就是:永远不能再和日本女性恋爱、结婚。我是恪守了这一庭训的。
经营航商
我的家庭是一个带有浓厚封建意识的资产阶级家庭。又因两世经营的都是较大的航商,所以我自幼就有乘长风,破万里浪的愿望。13岁时,考上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在福建马尾港设立的海军幼年军官学校,因母亲不同意,没有上成。15岁又登定海军舰为见习士官,以后历任三副、二副等职务。18岁又回铁路中学,20岁时,1937年卢沟桥炮声一响,我就考入了洛阳军官学校。在尚未复试期间,我又去考航空学校未取,军校也回不去了,只好回到青岛,学着向军统方面作情报工作。
不久,日寇海军在青岛登陆。我二哥受青岛海关关长之命,乘日寇军舰到石臼所通知当地开关,与青岛通航、通商,被当地商会会长、我父航业方面的竞争对手贺仁庵向当地国民党县政府诬告为汉奸,未经审讯即遭杀害。贺并向当地国民党五十九军军长庞炳勋诬告我父与我二哥内外勾结要献日照投降。庞将举兵来捕,我乃奉父母之命带幼弟弱妹共8口,乘帆船夜间出海逃生。时值腊月,滴水成冰,海上西北狂风连刮了四五个昼夜,小帆船去青岛正是顶头风,3天才走了30多里,以后竟至寸步难行。海上白浪滔天,北风怒吼,小船漏水,全家都泡在冰水之中,食物及饮水即将断绝,母亲要投海。当此生死关头,我毅然决定宁可承担投敌苟活的骂名,也要救出一家老小的性命。于是我拔出手枪威胁帆船老大,径直向正在石臼所港内向岸上开炮的日军军舰驶去。
日舰在查明我们确系我二哥的亲属之后,就把我们装上军舰,送回青岛。这时的青岛已在太阳旗下,我们成了亡国奴。
亡国奴的第一大痛苦就是不自由。中国人都不想当汉奸,但他们非逼着我父亲干不可。我家住无棣一路,路不宽,海军特务部的几辆汽车就摆满了。夜以继日,舌敝唇焦,翻来覆去,喋喋不休,一连20几天。他们摆出了安定市面、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等无数的理由,让我父亲出来维持治安。我父亲的理由只有一条:日没西山,气息奄奄,力不从心,只能来世再效力了。以后他们找到了赵琪(北洋军阀时代的胶澳商埠局总办)任青岛汉奸市长,才把我父亲放了。但又加上一个条件:必须出来组织航运,繁荣市面。我父亲坚决不干,但又怕过分得罪日本人,日子不好过,于是他继续装病,我就代表他出任我家轮船公司总经理。
公司是自己的,一切自己说了算,应当是很神气的,然而不然,上头有鬼子,鬼子说了算。为了胡弄鬼子,就得每天卑躬屈膝、点头哈腰说些假话、胡话,精神上是痛苦的。轮船跑的地方,大都是解放区,几乎每一个船员都免不了要替解放区的亲友捎带一些东西。日本水上宪兵队查得很严,查出来就要逮捕,刑讯,最后大部分都要“保释”,这时就必须由我出马了,到宪兵队去盖章,领人,这个滋味也很不好受。有一次我被宪兵打了两个耳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挨打。
赴宴饮酒本来是一件乐事,但一个人如果天天被逼着吃些肥鱼大肉,喝些过量的酒,那就不但不是享受,而且是一种痛苦了。我就是这样的,每天要接到许多请帖,这是因为当时船少、货多,货主设宴招待,请求我给他们留出舱位的,这些宴会可以不去,但有一些非去不可。如日寇汉奸设下的鸿门宴,叫你去讲条件的;或是公司有求于别人而设的宴会,我是主人,必须带头“欢呼”痛饮,其后果是十分痛苦的,身体也受到影响。在一段时间内,我拼命想办法,如能逃脱一次宴会,就是最大的幸事。
我在小港经营航业几个月,慢慢地就创出了一些名声。“人怕出名猪怕壮”,一点不错。日寇海军特务部找到我父亲说,听说你家四公子日语好,人又能干,请他到部里来,弟继兄“业”吧!于是又一次在我家引起了一场新的震动。最后由母亲决策,父亲出面对日寇回答说:“四子日语还不过关,让他到贵国去深造几年,回国后再为皇军效力不迟。”这样,我由日本海军特务部开具护照,保送去日本留学。我家之规,晚辈外出,长辈向不送行。那次父亲破例送我到大港码头轮船“熊野”丸上,临别郑重宣布3条庭训:
1.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2.为此,所学的内容一定要有利于抗战救国,毕业后立即奔赴后方参加抗战;
3.绝对不许和日本女子谈恋爱、结婚。
历史事实证明:这3条我都做到了。
赴日留学
我在中国看惯了日本的军舰、飞机和军国主义分子的狂妄傲慢,心想日本内地一定是富饶繁盛的,结果是大出意外,我到日本后的第一印象是日本人穷。
我在3年航海生活中,走遍了沿海各大城市,其中西式建筑都占百分之七八十;我国旧式的建筑不过十之二三。日本内地则与此相反,西式高大建筑物不过十之一二,其余十之八九大都是日本传统旧式的小木板房(二层者居多)。虽说是为了防震,但究竟也暴露出国民收入较低、国家财富有限的实底来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不高,四五口之家,一个劳力月收入百元左右,紧紧巴巴过日子,谈不到什么享受。3年之后,我到日本东北地区——山形县去滑雪,在农村住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农村更穷,仅能吃饱而已,并不比中国北方强多少,日本老百姓的钱都叫当官的搜刮去当作军费开支了。
我对日本人的第二个印象是日本大多数人心眼好,也就是善良。他们希望别人都能好起来,遇事能替别人着想,体贴人,同情心强,助人为乐,这些我从我养母身上早已领会到了。这次到日本一看,日本妇女和我养母一样的人几乎是百分之百,男子也有一大半是如此。日本军国主义者及其部下是日本人中的败类,是少数。
我是从我的全体同学中得出这个结论的,除了一个他父亲死在中国战场上的同学对我保持疏远外,所有的同学都很亲切、和蔼、诚恳,难道这些都是假的吗?不是。以后我和他们离别了40多年之后,他们又拿出钱叫我到日本去会面,时间和事实有最后的发言权。
在日本上学,住下宿屋最便宜,这都是一些生活不宽裕的家庭挤出一间屋来租给学生,房租最多不超过10元,加上三餐饭费一二十元,一般三十来元就能解决食宿问题;还能在饭后和家人对话练习日语。但我嫌老太太啰嗦,住了不久,便搬到公寓里去了。
公寓有如我们现在各城市中的集体宿舍的套房。有套一、套二、套三不等,但学生一般都是套一的,很方便,而且可以各行其是,互不干扰。我住公寓时间最长,还曾在房中自炊过,做一些在中华料理店中吃不到的菜,请日本同学来吃,我们一起喝日本酒,唱歌、跳舞、角力、做游戏。只要不闹得太厉害,邻居是不干涉的。
我是3月间到日本的,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考哪个学校,我本来打算考东京高等商船学校,可是来此之后,才知道此校在战时不收外国留学生。原因很清楚,在4年的学习中最后一年是航海实习,而实习又完全是枪炮、鱼雷、扫雷等一套海军军事训练,当然他们是不能让外国人了解他们的军事秘密的。我带来了青岛日军特务部的护照,如果拿出来交涉一下,他们是有可能破例收下我的,但我决心不再蹈我二哥的覆辙,所以我就考入了早稻田大学第二高等学院商科。
早稻田大学是日本5大名门学校之一,是已故首相大隈重信侯爵创办的。大隈侯本人富有自由色彩,所以早大的校风也比较民主自由。按日本当时实行的德日制教育制度:小学6年,中学5年(一贯),高校3年,大学本科3年,共17年,较英美制还多一年,我是高中毕业想上大学本科,所以必须要经过高校阶段。
高校有些象大学预科,文理分科,我选的是商学系,属于第二高院(一院是理科)。课程有国语、汉文、英文、经济学、哲学、逻辑学、心理学、第二外语(对我来说是第三外语)、自然科学等。其中英文时间最多,每周6堂,进度也快,每堂要学一二十页原文文艺小说,每天用于预习、查生字的时间就要一个多小时。其次是经济学概论,难度较大;其实最难的还是国语,这不是我们中国学校中的国语,它名为国语,实际上是日本的古文。它高奥艰深,诘屈聱牙,我自束发读书以来,从来没有不及格的功课,这次碰上这块硬骨头,啃了一年多最后才勉强弄了个及格。
高等学院介于中学和大学之间,功课不象大学那么严格要求,但我可不敢稍有松懈,尽管同学老师都对我很好,但谁知道内心究竟如何?我现在虽已远离战场,但洛阳军校的落日大旗、马鸣箫箫仍然在我心目之中。我抛弃了国民的天职,远逃异国,靦颜事敌,强为欢笑,内心是痛苦的。我拼命用功昼夜不懈,一年之后,除国语和法语之外都达到了优秀水平。
功课压力减轻了,我就参加了早稻田篮球队。以后我又参加了柔道队,虽然没有取得高段位,但也锻炼了不怕苦,不怕死,一拼到底的精神。在柔道场上我认识了东北同学王德成,其实他并不练柔道,只是喜欢看看而已。此人忠实诚恳,我俩一见倾心,说起来才知道他和我是同住在一个学生寮里——千岁乌山明治寮,以后我们经常互访、谈天。他谈到东北人民受日本人的压迫欺凌时,常常落泪。我那年正是21岁,血气方刚,当然是无限同情。有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一个姓于的同学屋内,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姓陈的台湾同学,他拿出了一张写好的誓约书,大意是我们4个人为了抗日反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生死与共,万死不辞,如有违反,甘受最严厉的制裁等,下面的组织名称是“东亚青年抗日联盟”,4个人都签了名之后,就烧了。以后王德成给过我几次抗日传单,叫我分发,我带进电影院之后,也没敢分发,放在座位上就走了。
我是一个心粗胆大之人,也颇能言谈,所以我对中国留学生确实做了不少宣传工作。可惜在抗战时期到日本去上学的留学生大部分是想弄个较高学位,回国后找个挣钱多的工作的,打算抗日的人较少,而且人人都知道日本刑事(便衣警察)很厉害,所以很少有人接我的话碴儿。
和我能谈得来的知心朋友有方旭和吴建。方旭是山东军阀方永昌的弟弟,在一次我俩游山时他告诉我,他是共产党,被捕后在方永昌的压力下,他自首了,但他表示作为一个中国人,一定抗日到底;吴建是山东省高等法院院长的儿子,民族观念很强,我们3人立誓毕业后一定到后方去参加抗日工作。胜利后,我介绍他俩去山东省立医专(即今医学院前身),分别任总务长和训导长,解放后,失去联系。
1940年春,我以优秀成绩毕业于早大二高。本来可以免试进入大学商科,但我想到经过几年奋斗,虽然还不敢和最优秀的日本学生比,但在一般中国留学生中是有一定竞争能力的,于是我又报考了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竟被录取了,我告别了东京,赶到京都上课。
日本有9个帝国大学。这是日本国家的最高学府,学生制服的铜扣上有菊花纹章(皇室纹章)。过去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非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的不能担任大臣职务。我到学校一看,校舍建筑宏伟壮观,设施周全,教官(帝大教授称为教官)人才济济,气宇不凡,学生沉稳肃穆,一副官派,果然和自由民主空气甚浓的早稻田大学有所不同。
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向来以思想进步而闻名于世,但在很早以前进步教授早已被清洗,现在又是战时,思想控制极严。图书馆中虽还有几本《资本论》,但绝对无人敢看,我却从同学梁纫武的口中多少了解到一些进步理论的端倪。我当时认为:从理论中说是对的,但暴力革命对不对呢?我不敢说,在我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中庸之道。
经济学概论讲座是高田保马先生,统计学是蜷川虎二,日本经济史是本庄教官,统制经济学是龙川先生。上课都是讲演式的,老师都有著作,但讲授的与书上不同,因此必须作随堂笔记,我练了半年才能跟上。
1941年12月日军袭击珍珠港,日美英德之间的战争全面爆发了。一开始,我为日军的侥幸成功和近似疯狂的扩大宣传所迷惑而感到有些惶惶不安,但很快我就从大半数日本人民的态度中看透了,这对他们决不是个喜讯。配给(食物)越来越少,而且质量越来越差,一见到街上有人排队就赶紧排进去,不管是什么,只要是食物就买。出征的越来越多了,“护国英灵”也越来越多。日本政府宣布: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半年内就要修完全部课程,作为已经毕业,一律出征。这样算来,我到1942年秋季即可毕业了。日本人个个愁眉苦脸,很少看到笑脸或听到笑声。于是我看透了:日本必败!我怎么办呢?这时恰好有关西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一位教授来问我是否可在秋季毕业后,到关大中国经济研究室去担任助教工作,我认为有请示父亲的必要,就去领了回国许可证,准备回国一次。
被捕羁押
在我准备动身的前一天,有两个刑事到我住的公寓来说,我的回国许可证上的号码写错了,需要到分署去更正一下,我就随他们去了。到了分署之后,他们拿出了一份东京警视厅的来文,上面写着:“叶瑛桐因违反治安维持法,应押解来京。”当下我就被拘留在分署了。
3天之后,由东京来了两个獐头鼠目的刑事把我押解到东京,寄押在六本木警察分署。过了几天,就押送到地方法院,问我:“你认识王德成吗?”“认识。”“什么关系?”“朋友关系。”“你们搞过什么活动?”“没有搞过什么活动。”他冷笑了一声,就把我押还六本木,一直3个月没有再审问。
在这3个月中最大的痛苦是饥饿。我在入狱之前已经在当时的定量分配(每天每人食米2盒3勺,大约可蒸饭3小碗)制度下,饱尝饥饿之苦。现在才知道了真正的饥饿之苦,在狱中的定量又被克扣掉将近一半,再加上几乎没有任何副食,于是把我饿得头昏目眩,四肢无力,身体逐渐衰弱。什么悲观、失望、恐惧、消极等不健康的思想不断出现,需要不断地和这些消极思想作斗争。同监的共党嫌疑分子宫本给了我很大鼓励,他首先同情我的抗日行动,这样我们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他比我寄押的时间长,受刑次数也多,年纪也大(大约有40多岁了),所以他简直就成了我的老师和保护人。他把家中送来的食品分给我吃,把新犯人吃不下的囚粮向看守要来给我吃,在我受了刑伤之后,替我敷药治疗。我从他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磊落胸襟,对共产党有了敬仰(也有恐惧)之心。这对于我以后在1949年拒绝国民党北平市政府让我撤退到台湾的命令留在北平,把市立七中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的行动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他没有向我宣传过共产主义,我也从来没有向他打听过,我不想在抗日罪之上,再加上一个共产罪。所以我在北平解放之前,对于共产党、共产主义几乎是一无所知。
3个月之后提审了。预审员原来就是押解我来东京的那两个刑事:一个是警部端保登治郎;那一个警长叫什么就忘了。讯问是公式似地进行,不承认就打,以后我发现,刑讯是逐渐升级的。例如:
第一次打耳光数十下;第二次,是拳打脚踢;第三次,用灌了铅的簿记棒抽打背部,用脚后跟捣击大腿(受讯人跪着);第四次,用钢钎插进受讯人手指与指甲中间,然后再敲击这些钢钎;第五次,把钢钎通上电,然后跳到我身上唱“爱马进行曲”,呼喊“支那猪万岁!”
痛苦可忍,侮辱难受,我一个右摆拳把端保打得摔倒在地,又举起面前的小桌,向正在拔枪的狗崽子砸去,然后翻身一跳,就从窗户中跳到了街道上。
我忘记了这是在外国——战时的日本,它不会让一个抗日青年逃脱的,不大工夫,我就被毒打一顿之后投进了一个黑暗地狱。
我不知昏过去了有多长时间,只觉得浑身奇痛而且好象被绑紧了一样,丝毫不能转动。等我神志逐渐清醒而且眼睛也适应于黑暗时,这才慢慢弄清楚:我是被塞进了一个仅能容下一个中等身材的日本人的石窟中了。我身高一米七八,当然更加难受,不用说转身、伸腿,连抬一下头都很困难,我心里一着急,又昏就过去了。
当我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只能用在母体中的那种姿势,两手捧头,膝盖顶在胸口上,蜷成一个人肉团。他们用了何种巧妙手术,把我塞进来的,我已来不及思考了,只是看着石缝里的阳光,亮了又暗,暗了又亮,大约是3天或4天过去了。
我的忍耐力已经接近崩溃了,我不想再活下去,于是我慢慢拉紧身上的一件破衬衣,用牙齿固定住一头,那一头用半只手(曲而不能伸的手)揪紧一头,逐渐用力。这是我从柔道中学会的“绞技”(不是用手绞而是用衣襟),平日百发百中,现在倒也管用。我感到神志逐渐模糊,心中有一种超脱感,昏昏如睡之感……忽然爆发了一阵强烈的咳嗽,以致使脖颈突然变得粗起来,一下子就把绞颈的衣襟撑开,于是我也死不成了。这大约是人类的自然保护能力吧。
在清醒过来的时间内,我想:我太软弱了。我的罪不至死.顶多判几年刑罢了,来日方长,我还年轻,父母养育之恩及国难家仇均未报,我不应当求死,应当求生!
说来也巧,又过了一两天之后,就把我放出来了。我已不能行动,瘫在铁笼内几天之后,来人叫我出去,到了办公室,一看不是审讯人员,而是我二嫂在那儿。二嫂一见我就哭了,我也不禁悲从中来。二嫂说:“平日劝你好好读书别问外事,你不听,现在后悔了吧!你也没干什么大事,人家都招认了,你何苦老是替别人受刑呢?”此时此地这些话对我起了很大作用。说实话,我平日对二嫂的感情不算很好,但现在是生死关头,她代表全家来看我,我就不能不好好重新考虑了。
下一次的审讯,审讯员换了一副面孔,不打不骂光捡好听的说。我也早就想好了:死不怕,但死不成的滋味确实太可怕了,不管怎么说,先得保住命,活下去。于是我就把过去和王德成等人订立盟约等活动统统都讲了出来,我想这下子总算过了关了吧!谁知下次提审,他们又换成原来恶狠狠的面孔,说我又隐瞒了重要情节,又把我打了一顿。以后看我实在没有了,也就算了。
以后的狱中生活是比较平静的,我请关押在楼上笼内的老大娘给我缝制一副垫肩,准备判刑后到北海道去干伐木工。
一个秋阳杲杲的上午,一位判事老爷在审讯室出现了,他高坐堂室,神气十足,先问了一下我的身体情况,接着就宣读了判决书。先是列举我的许多严重“罪行”,最后说:“姑念其年幼无知,受人蛊惑,经教育尚能招认,表现了悔改之心,为此特予宽大处理——驱逐出境!”
脱险回国
我收拾简单的行李,向狱中同人告辞,随着押解人员向神户而去。在神户码头派出所又等了好几天。一天夜里星月无光,突然得到命令:秘密登船;但船开出去不久,又停了下来。这样开开停停,走了好几天,还只是在朝鲜南岸岛屿中捉迷藏,打转转。
在旅客们交头接耳的窃窃私语中,我逐渐明白了,在我被关押的半年多的时间里,日军从太平洋上胜利的云端中跌落下来了,日军逐渐后退,美英军步步进逼,上有飞机,下有潜艇,大约日本船只的损失很大,现在这种开开停停的航法,正是在和美国潜艇兜圈子呢。
我听了以后,又是高兴,又是害怕,我偷偷地找了一根半截铁棒和一块木板,心想:船一旦被炸,我先抢上救生艇,谁敢拦挡,我就打死他!
有一天深夜,轮船正在双子群岛内碇泊,忽然传来了船头起锚机轧轧作响的声音,这说明轮船要开始航行了。我兴奋地到甲板上瞭望了一下,从山影、风向、星斗方位看来,船已转向正西——大陆方面,而且是全速航进,心想:不久可看到祖国亲人们了。
第二天早上我刚从朦胧中醒来,就听到外面传来了一阵惊呼声。我急忙来到甲板上一看,只见烟筒上黑烟滚滚,机声轧轧,轮船象一匹受伤的野兽拼命地向左急驶,船身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向左舷倾斜,情况十分危急。在许多人的指点、惊喊下,我才看清了在几百米之外,有一条白色航迹,正在向本船右舷飞驰而来,“不好!鱼雷!”经过了难忍的几十秒钟之后,鱼雷竟从本船右舷后尾远处交叉而过。许多旅客互相拥抱,有的人在跪地祈天,我才感到两只紧握的拳中已冷汗涔涔了。
其后不久又来了一艘日本小型驱逐舰在后护卫,又不知从哪儿冒出了几艘日本商船来,大家结伴同行,十几个小时之后,我就远远望见崂山高角了。
我到家之后,第一个见到的是母亲,母亲见我大哭,说她天天祈祷的菩萨显灵了。我却顾不得哭,母亲身旁放着一盘西式蛋糕,我一下就吃得干干净净。
听说我脱险回青的消息,立刻有许多亲友前来慰问,我无法细谈。先到了湖南路宪兵总队(今档案局址)报到,接见我的副官满面春风首先向我祝贺,并说东京警视厅曾来电征询我们意见,我们认为叶君府上都是亲日的,应当早日放回,使之为建设大东亚而努力,我满口答应。当我回家后不久,海军特务部就送来了港湾部高级嘱托的委任状,联合准备银行送来了经济研究室主任的聘书,我一一表示感谢收下了。
夜间我们全家开会研究,青岛呆不下去了,必须立即奔赴后方参加抗战。3天后我带领刚在东文书院毕业的五弟到了南京。见了过去东文书院院长、现任要人的大汉奸李仲刚,他非常高兴,马上发表我为南京警备司令部少将联络处长。我弟为附员。我回青后向宪兵队报告,他们向我祝贺。此时已将过春节了,我说过了正月十五动身去南京,实际上我初四日就动身了,买的是南京车票。到了徐州,我就转车到商丘,下车住店,次日化装乘地排车到亳县,找到介绍人指定的关系人,护送我到两军交界处再换了一个伪军护送,当天就平安到达界首。当时我看到城墙上国旗飘扬,军号嘹亮,不禁潸然泪下,默诵杜诗: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作者现为青岛华海信息翻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青岛家政艺术学校校长)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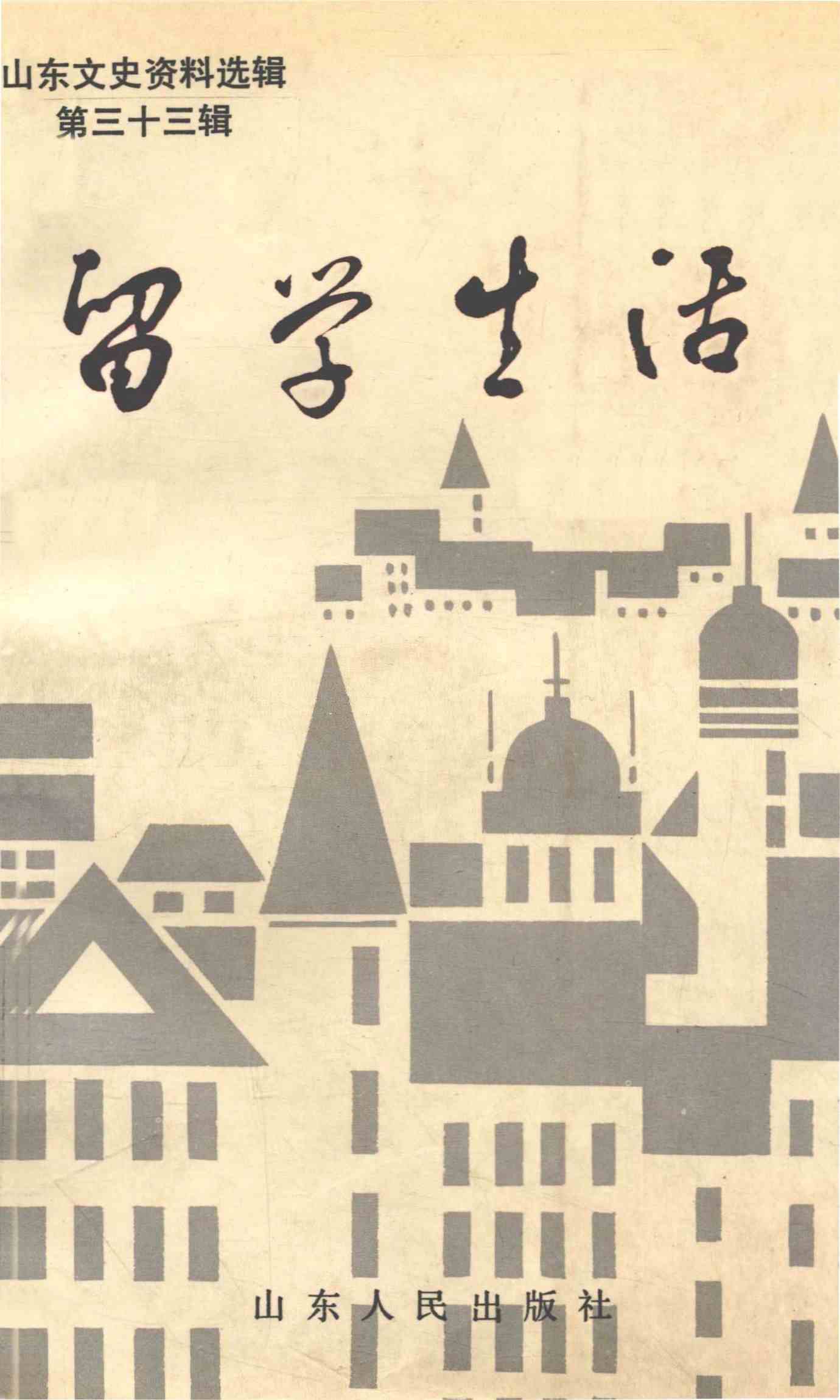
《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三辑》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本书记述了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的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三辑的情况,主要内容为记述我国许多知识分子为了振兴祖国,造福人民,满怀救国之志,远涉重洋,赴异国留学,老一辈知识分子在海外留学的艰苦生活,旨在以生动、翔实的“三亲”资料,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励人们为改革开放、早日实现小康目标而努力学习,勤奋工作。
阅读
相关人物
叶瑛桐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