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私塾学习生活
| 内容出处: | 《山东文史资料选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50020020220002304 |
| 颗粒名称: | 我的私塾学习生活 |
| 分类号: | G629.299;K258 |
| 页数: | 7 |
| 页码: | 225-231 |
| 摘要: | 我曾先后三次脱离学校转入私塾读书。这三次,以其中第二次在私塾读书时间较长,这种私塾,当时都叫它是“野塾”或“散馆”。随着时代的演变,这种私塾在数学内容上有了一番变动,人们也有叫它是“改良私塾”,并且也竟有个别塾学在自己的门边挂上个“改良私塾”的牌子。1934年,我小学毕业后,因为家长要培养我能写会算,够得上到大商店学徒的条件,所以选择了一家认为满意的塾学去学习。这家塾学设在济南南关得胜街东首路南胡同内。 |
| 关键词: | 散馆 私塾 学习生活 |
内容
我曾先后三次脱离学校转入私塾读书。这三次,以其中第二次在私塾读书时间较长,而且就济南南关一带说,虽有几家私塾同时存在,但都不如我所在的这家办学历史久、从学人数多、影响比较大而较为知名。这里写的,就是我在这家私塾就学两年整的学习生活回忆。
这种私塾,当时都叫它是“野塾”或“散馆”。随着时代的演变,这种私塾在数学内容上有了一番变动,人们也有叫它是“改良私塾”,并且也竟有个别塾学在自己的门边挂上个“改良私塾”的牌子。
1934年(民国23年),我小学毕业后,因为家长要培养我能写会算,够得上到大商店学徒的条件,所以选择了一家认为满意的塾学去学习。
这家塾学设在济南南关得胜街东首路南胡同内。大门西旁用红纸写着“郃阳百世堂支”的字样。塾师名叫支元兴,字晓东,排行第四,人都称他是支四爷。那时他年近60岁,据他自己说,他先为生徒,后为人师,将一生的时光,均消磨在“子曰”、“诗云”的塾房里。别人也说他前清无功名,民国来亦未曾在社会上供职,从20几岁便在家设馆教学。因为他教的时间久,教学内容和方法不甚刻板,所以南关一带,同时存在的几家私塾,都不及从他学习的人数多——从学人数,经常保持在20人以上。
塾房设在他家后院北屋里。这座北屋是海青房两间。一间一窗,土墙土地,因已老旧,房顶与四壁皆为炉烟熏黑。窗前有白石榴一株,院约丈半见方,尚有南屋两间,女厕一所。
塾房迎门设大方桌,老师便在桌之右方设座。桌之左上方墙面挂巨幅墨拓“至圣先师”全身像,我们每逢上学下学,都要向这圣像行90度的鞠躬礼。行礼不能草率应付,否则要被斥另行,甚至于像前罚站。
塾房靠四壁安着许多桌子,样子不同,尺寸不一,都是由学生从自己家里搬来的。年龄大的同学坐桌前方,面向壁,年小的坐桌侧,这样大的小的同学平均结合排座,由大学生分担一些“小先生”的责任,于塾房秩序、于功课,都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省却老先生一些力气。
我们这20几个同学所学的功课,根据家长不同的要求,可大体分新、旧两个类型。
有大部分同学是按老的一套学习的。即所读的书,仍从《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或代以《弟子规》、《龙文鞭影》)读起,一直读到《四书》、《五经》,并兼习尺牍、唐宋诗(读本为《唐诗三百首》、《千家诗》)。这些同学因同时要几本书兼习,又要兼带复习旧课,所以到背书时,都要托看一大罗书,放在老师面前桌上,回过头去,一样一样地背。在背诵诗的时候,还要合着韵律、拖着长腔;诵读其他课文,也都习惯地用一种类似诵经的调子读。
塾学强调背诵,几千字或上万字的经书,仍要背通本。为了节约时间和试探背诵的熟练程度,总是由老先生提段去背,提到哪里,背到哪里,稍有生滞,便令重温。重温仍不透熟,轻则把一罗书给抛到地上去,重则要吃手板子。一般地说,15岁以前年龄的同学,是不开讲的,背诵自己所不明白的死东西。这种特殊的锻炼,应该是塾房里独有的硬功夫。这种做法,在科举时代,为了考取功名,趁着年幼记忆力强,倒是一套很重要的“基本功”。
另一种属于新的、所谓“改良”类型的教学课程,便不再让读上述那些书了。才入学的蒙童,读的是当时学校里用的那种国语课本,还认些字块,但是不学算术。老先生教学字块是带讲解的,比如学个“刀”字,总让学生拿着字块,这样大声地喊:“刀——切菜的刀!”记得有一次市教育局的督学去查学,老先生便特意叫上一个姓胡的小同学,如此表演了一番,很得那位督学先生赞许,老先生也乐得逢人便说这件得意的事。
不过对于阿拉伯数字作算术,老先生是极其反对的。老先生曾发过这样的议论,他说:“放弃祖辈相传的算盘不用,反去学人家的洋算学,那真是舍本逐末了”。
对于象我这样上过学校的年龄大些的同学,便学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等所印行的尺牍,以及比较浅近的文言体的短论一类的课本。此外,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兼读《幼学故事琼林》、《东莱博议》或历代选文。如《古文观止》、《古文释义》之类的文章。在读这种选文时,老先生特别重视其中《前出师表》、《后出师表》及《陈情表》这三“表”,老先生称这三篇为“忠孝表”。从意义上说,老先生认为这“表”可以概括历代载道古文的写作精神,是“以文敦教”最好的典范;从应用上说,老先生认为,读透了这样的文章,可以写信,可以撰拟公文,还可以发表议论,又可以写出以情感人之诗。简直是文章中的万能篇什了。
至于作文,我们这两种类型的同学,则大体是一致的,那些深读经书的同学,也不让他们根据所读经书的内容命题写“八股”,我们都学作“家书”,作“酬世函件”或“议论”、“游记”等类的文章。今就我记忆所及,把老先生给我个人出过的作文题目写在下面:
(1)平安家报一封副题是:禀双亲,言公务繁冗,仲秋节不想返家省探……
(2)旱魃为虐说
(3)盂兰会盛况记
(4)喜雨记
(5)三国人物孰可为百世法?试举其言行事实而论之。
老先生出题作文仍延用老办法。将题目写在一张小纸条上,将学生叫到他身边,先让学生把作文题念一遍,然后把要求交代一番,或略作启发。倘逢巧一个题目由几个同学共同来作,便在交代、启发后,传抄题目。在发作文时,同样让学生站在他身边,看着批阅过的作文本子,逐句讲明:为什么这里划上圈,为什么那里批上杠子。不仅错字得由学生自己改,就是有毛病的句子,他只标出,也让自己改。改好誊清(另誊在抄书本子上)让学生把它熟背。
写作文还有一个统一的要求,即不管作哪等题目的文章,统用文言文。关于这一点,老先生的见解是:“白话文”一词是费解的。试问:“既是嘴头上的白话,哪里再可作书面之文?”他还说:“读书作文章,就是学着写规规矩矩的文章。”他给“文言”下了这样一个界说——“文言”者,是唯一表于文章之言词文句也。有多少次,他大斥提倡写语体文为“不学无术”,为“标新立异”,认定是“屑小行劲”,是“行于一时、贻害百世”的事情。
同学中有个写了语体文的,老先生便把他的作文本子抛到地上去,怒叱他不听话,非改过后不给批阅。可是这位同学又偏偏不会写文言文,只好在原来写的语体文句子里胡乱添上些“焉、哉、乎、也”一类的字,重新抄到作文本子上,才勉强被老先生接受批阅。以后这位同学被取消了作文的“资格”。
另外,我们还有共同的功课,那就是练习写大小楷,练习打算盘。
对于写大仿,老先生只许临摹颜、柳、欧、虞等家的楷书。见有写翁方纲、华世奎甚至写曹鸿勋的,他也不反对,但是非常厌忌写篆、隶、六朝碑。他对写篆书的批评是:转(篆)吧,转吧,转糊涂了,连自己姓什么也认不得了。对于隶书,则认定是一种投机取巧、吓唬人的字体,老实向学的人是不屑为的。对于六朝方笔画的字体,按他的说法是一些不认字的石匠,硬刻生造的一些横七竖八、少腿无臂的东西,认为是书法中的邪道。
他认为我国最上乘的书法家,王羲之以下,只有一个柳公权,其余等而下之。老先生的字便是一笔挺拔的柳字。他常为别人写春联、喜对,有时也写写牌匾。当时济南南门外大街上一些商店的匾额,请老先生写的不少。其中济南名食品“赵三糖炒栗子铺——“惠茗斋”三字的匾额,便是由老先生命名并挥写的。
每天功课程序是这样的:早晨读书、背书、以小楷抄书,即放早学。午饭后返塾即磨墨写大、小字。写完盘毕(看写的字叫“盘”),继续读书背书,其余时间,或学习打算盘,或有时静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听老先生发发议论。
老先生教我们打算盘是很有意思的。一般在10岁以后才学算盘,在学完加减“九九歌”以后,便列队学习打账。打账时,让十几个学生按身材高低站一竖行,各将算盘托在胸前,老师戴上铜卡花镜,一手执教鞭,一手拿着他自造的账本子。说一声“开始吧”,便象当时各店家午夜盘账一样,一人疾口念账,几个人抱着算盘便乒乒乓乓地打下去。告一个段落,停下来,让同学从后面开始一一报答数。报对的没话说,倘错了,便吃批评,屡错的,便要吃教鞭了。我打算盘本领很差,怕批评挨打,所以每当停下来的时候,便偷偷地看我后边打得好的同学的答数,或请他低声把答数说一说,作个对照,错了便改过来。可是,站在前边的同学便不能这样,所以因屡错而挨打的,往往都是站在前面的几个小同学。
在私塾中受体罚是常有的。我第一次——八九岁入塾跟一位姓楚的塾师念“学庸”时,挨手板之外,还曾跪过琉渣。同学中有个姓齐的孤儿,他是挨打最狠的一个。他调皮一些,脑子又笨一点,往往因为背不过书,藤竿或木板就常常从他身后击到光脑袋上去(那时还不兴留头发)。他每逢去背书,稍有生滞,便闪着身子用双手抱头,甚至还喊着:“老师,饶过我!”这些动作,常常引起同学大笑,甚至连老先生也忍不住地笑了。
对于打学生,老先生也曾发过议论。他曾这样说:“教必严。不严,无以对你们的父母兄长;而严必打。循循善诱,当然高明,但要看是谁。对牛,不能弹琴,只能给他皮鞭子。”老先生发这样的议论时,我还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时是打过人之后,托着他的水烟袋,坐在他的座位上发的。当时他还咬着牙,不时地把穿着圆口礼服呢便鞋的脚在土地上跺着。
我在这个塾学共待了两年,学来的本领是能写简短的应用函件,能写一笔规矩的字,也会打算盘了,确实学到了可以到大商店学徒的资格,可我并没有到商店去学徒。现在与几位当时的同学,谈起这一阶段的塾学生活情况,大家都有个相同的说法,即:学到一点有用的东西,可是过了一段受罪的生活。
这种私塾,当时都叫它是“野塾”或“散馆”。随着时代的演变,这种私塾在数学内容上有了一番变动,人们也有叫它是“改良私塾”,并且也竟有个别塾学在自己的门边挂上个“改良私塾”的牌子。
1934年(民国23年),我小学毕业后,因为家长要培养我能写会算,够得上到大商店学徒的条件,所以选择了一家认为满意的塾学去学习。
这家塾学设在济南南关得胜街东首路南胡同内。大门西旁用红纸写着“郃阳百世堂支”的字样。塾师名叫支元兴,字晓东,排行第四,人都称他是支四爷。那时他年近60岁,据他自己说,他先为生徒,后为人师,将一生的时光,均消磨在“子曰”、“诗云”的塾房里。别人也说他前清无功名,民国来亦未曾在社会上供职,从20几岁便在家设馆教学。因为他教的时间久,教学内容和方法不甚刻板,所以南关一带,同时存在的几家私塾,都不及从他学习的人数多——从学人数,经常保持在20人以上。
塾房设在他家后院北屋里。这座北屋是海青房两间。一间一窗,土墙土地,因已老旧,房顶与四壁皆为炉烟熏黑。窗前有白石榴一株,院约丈半见方,尚有南屋两间,女厕一所。
塾房迎门设大方桌,老师便在桌之右方设座。桌之左上方墙面挂巨幅墨拓“至圣先师”全身像,我们每逢上学下学,都要向这圣像行90度的鞠躬礼。行礼不能草率应付,否则要被斥另行,甚至于像前罚站。
塾房靠四壁安着许多桌子,样子不同,尺寸不一,都是由学生从自己家里搬来的。年龄大的同学坐桌前方,面向壁,年小的坐桌侧,这样大的小的同学平均结合排座,由大学生分担一些“小先生”的责任,于塾房秩序、于功课,都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省却老先生一些力气。
我们这20几个同学所学的功课,根据家长不同的要求,可大体分新、旧两个类型。
有大部分同学是按老的一套学习的。即所读的书,仍从《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或代以《弟子规》、《龙文鞭影》)读起,一直读到《四书》、《五经》,并兼习尺牍、唐宋诗(读本为《唐诗三百首》、《千家诗》)。这些同学因同时要几本书兼习,又要兼带复习旧课,所以到背书时,都要托看一大罗书,放在老师面前桌上,回过头去,一样一样地背。在背诵诗的时候,还要合着韵律、拖着长腔;诵读其他课文,也都习惯地用一种类似诵经的调子读。
塾学强调背诵,几千字或上万字的经书,仍要背通本。为了节约时间和试探背诵的熟练程度,总是由老先生提段去背,提到哪里,背到哪里,稍有生滞,便令重温。重温仍不透熟,轻则把一罗书给抛到地上去,重则要吃手板子。一般地说,15岁以前年龄的同学,是不开讲的,背诵自己所不明白的死东西。这种特殊的锻炼,应该是塾房里独有的硬功夫。这种做法,在科举时代,为了考取功名,趁着年幼记忆力强,倒是一套很重要的“基本功”。
另一种属于新的、所谓“改良”类型的教学课程,便不再让读上述那些书了。才入学的蒙童,读的是当时学校里用的那种国语课本,还认些字块,但是不学算术。老先生教学字块是带讲解的,比如学个“刀”字,总让学生拿着字块,这样大声地喊:“刀——切菜的刀!”记得有一次市教育局的督学去查学,老先生便特意叫上一个姓胡的小同学,如此表演了一番,很得那位督学先生赞许,老先生也乐得逢人便说这件得意的事。
不过对于阿拉伯数字作算术,老先生是极其反对的。老先生曾发过这样的议论,他说:“放弃祖辈相传的算盘不用,反去学人家的洋算学,那真是舍本逐末了”。
对于象我这样上过学校的年龄大些的同学,便学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等所印行的尺牍,以及比较浅近的文言体的短论一类的课本。此外,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兼读《幼学故事琼林》、《东莱博议》或历代选文。如《古文观止》、《古文释义》之类的文章。在读这种选文时,老先生特别重视其中《前出师表》、《后出师表》及《陈情表》这三“表”,老先生称这三篇为“忠孝表”。从意义上说,老先生认为这“表”可以概括历代载道古文的写作精神,是“以文敦教”最好的典范;从应用上说,老先生认为,读透了这样的文章,可以写信,可以撰拟公文,还可以发表议论,又可以写出以情感人之诗。简直是文章中的万能篇什了。
至于作文,我们这两种类型的同学,则大体是一致的,那些深读经书的同学,也不让他们根据所读经书的内容命题写“八股”,我们都学作“家书”,作“酬世函件”或“议论”、“游记”等类的文章。今就我记忆所及,把老先生给我个人出过的作文题目写在下面:
(1)平安家报一封副题是:禀双亲,言公务繁冗,仲秋节不想返家省探……
(2)旱魃为虐说
(3)盂兰会盛况记
(4)喜雨记
(5)三国人物孰可为百世法?试举其言行事实而论之。
老先生出题作文仍延用老办法。将题目写在一张小纸条上,将学生叫到他身边,先让学生把作文题念一遍,然后把要求交代一番,或略作启发。倘逢巧一个题目由几个同学共同来作,便在交代、启发后,传抄题目。在发作文时,同样让学生站在他身边,看着批阅过的作文本子,逐句讲明:为什么这里划上圈,为什么那里批上杠子。不仅错字得由学生自己改,就是有毛病的句子,他只标出,也让自己改。改好誊清(另誊在抄书本子上)让学生把它熟背。
写作文还有一个统一的要求,即不管作哪等题目的文章,统用文言文。关于这一点,老先生的见解是:“白话文”一词是费解的。试问:“既是嘴头上的白话,哪里再可作书面之文?”他还说:“读书作文章,就是学着写规规矩矩的文章。”他给“文言”下了这样一个界说——“文言”者,是唯一表于文章之言词文句也。有多少次,他大斥提倡写语体文为“不学无术”,为“标新立异”,认定是“屑小行劲”,是“行于一时、贻害百世”的事情。
同学中有个写了语体文的,老先生便把他的作文本子抛到地上去,怒叱他不听话,非改过后不给批阅。可是这位同学又偏偏不会写文言文,只好在原来写的语体文句子里胡乱添上些“焉、哉、乎、也”一类的字,重新抄到作文本子上,才勉强被老先生接受批阅。以后这位同学被取消了作文的“资格”。
另外,我们还有共同的功课,那就是练习写大小楷,练习打算盘。
对于写大仿,老先生只许临摹颜、柳、欧、虞等家的楷书。见有写翁方纲、华世奎甚至写曹鸿勋的,他也不反对,但是非常厌忌写篆、隶、六朝碑。他对写篆书的批评是:转(篆)吧,转吧,转糊涂了,连自己姓什么也认不得了。对于隶书,则认定是一种投机取巧、吓唬人的字体,老实向学的人是不屑为的。对于六朝方笔画的字体,按他的说法是一些不认字的石匠,硬刻生造的一些横七竖八、少腿无臂的东西,认为是书法中的邪道。
他认为我国最上乘的书法家,王羲之以下,只有一个柳公权,其余等而下之。老先生的字便是一笔挺拔的柳字。他常为别人写春联、喜对,有时也写写牌匾。当时济南南门外大街上一些商店的匾额,请老先生写的不少。其中济南名食品“赵三糖炒栗子铺——“惠茗斋”三字的匾额,便是由老先生命名并挥写的。
每天功课程序是这样的:早晨读书、背书、以小楷抄书,即放早学。午饭后返塾即磨墨写大、小字。写完盘毕(看写的字叫“盘”),继续读书背书,其余时间,或学习打算盘,或有时静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听老先生发发议论。
老先生教我们打算盘是很有意思的。一般在10岁以后才学算盘,在学完加减“九九歌”以后,便列队学习打账。打账时,让十几个学生按身材高低站一竖行,各将算盘托在胸前,老师戴上铜卡花镜,一手执教鞭,一手拿着他自造的账本子。说一声“开始吧”,便象当时各店家午夜盘账一样,一人疾口念账,几个人抱着算盘便乒乒乓乓地打下去。告一个段落,停下来,让同学从后面开始一一报答数。报对的没话说,倘错了,便吃批评,屡错的,便要吃教鞭了。我打算盘本领很差,怕批评挨打,所以每当停下来的时候,便偷偷地看我后边打得好的同学的答数,或请他低声把答数说一说,作个对照,错了便改过来。可是,站在前边的同学便不能这样,所以因屡错而挨打的,往往都是站在前面的几个小同学。
在私塾中受体罚是常有的。我第一次——八九岁入塾跟一位姓楚的塾师念“学庸”时,挨手板之外,还曾跪过琉渣。同学中有个姓齐的孤儿,他是挨打最狠的一个。他调皮一些,脑子又笨一点,往往因为背不过书,藤竿或木板就常常从他身后击到光脑袋上去(那时还不兴留头发)。他每逢去背书,稍有生滞,便闪着身子用双手抱头,甚至还喊着:“老师,饶过我!”这些动作,常常引起同学大笑,甚至连老先生也忍不住地笑了。
对于打学生,老先生也曾发过议论。他曾这样说:“教必严。不严,无以对你们的父母兄长;而严必打。循循善诱,当然高明,但要看是谁。对牛,不能弹琴,只能给他皮鞭子。”老先生发这样的议论时,我还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时是打过人之后,托着他的水烟袋,坐在他的座位上发的。当时他还咬着牙,不时地把穿着圆口礼服呢便鞋的脚在土地上跺着。
我在这个塾学共待了两年,学来的本领是能写简短的应用函件,能写一笔规矩的字,也会打算盘了,确实学到了可以到大商店学徒的资格,可我并没有到商店去学徒。现在与几位当时的同学,谈起这一阶段的塾学生活情况,大家都有个相同的说法,即:学到一点有用的东西,可是过了一段受罪的生活。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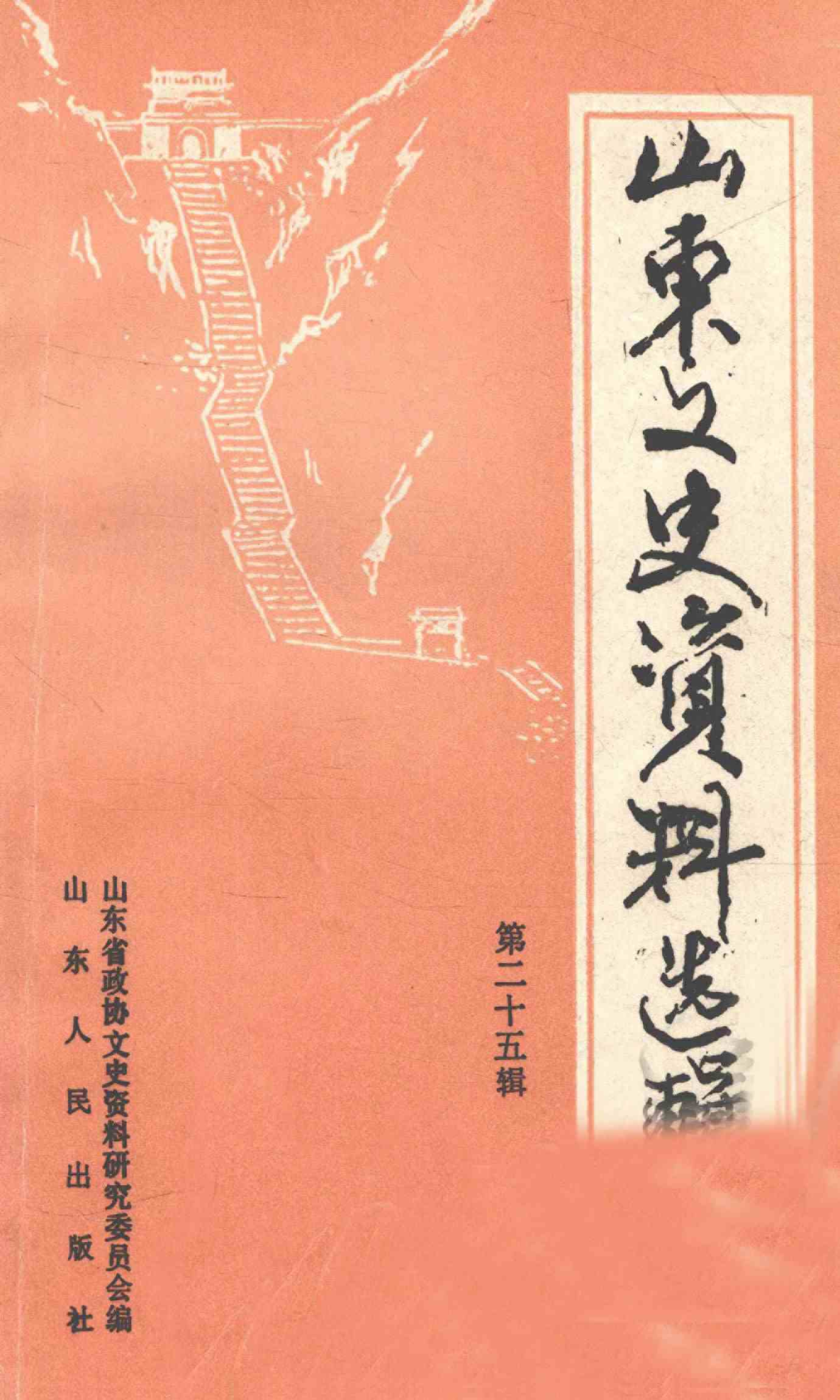
《山东文史资料选辑》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本书记述了秋瑾殉难记、六月六日与李钟岳、忆我的父亲——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忆冯玉祥将军在重庆宴请毛主席、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前前后后、回忆何基沣将军片断、从旧军人到起义将领、我所知道的汪伪政权内幕情况、博山县商会在日伪时期的活动、日军残害中国人民的魔窟——济南“新华院”等资料。
阅读
相关人物
韩文海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