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济南市的金融业
| 内容出处: | 《山东文史集粹工商经济卷》 图书 |
| 唯一号: | 150020020220001760 |
| 颗粒名称: | 解放前济南市的金融业 |
| 分类号: | F832 |
| 页数: | 14 |
| 页码: | 207-220 |
| 摘要: | 本篇记述了清末民初时期、张宗昌主鲁时期、韩复榘统治时期(1930~1937年),解放前济南市的金融业。 |
| 关键词: | 济南市 解放前 金融业 |
内容
解放前济南市的金融业
黄得中
一、清末民初时期
济南的银号起源于清朝康乾年间,最早的有:三合恒、庆泰昌、蚨聚长、协聚泰等,大半成立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还有汇兑钱庄,如大德通、大德恒、晋逢祥等,它们大都是光绪年间山西人来鲁开业的。汇兑钱庄(票庄)专做北京、西北一带的汇兑、贷款生意。此后又有历城、章丘、周村等商人在济南陆续开设的仁和祥、裕茂、同升、广成泰、厚记等银号。
道光年间,在高都司巷成立的福德会馆,为钱业最早的组织,即钱业公会的萌芽组织。会馆设值年,主持会馆一切事务。首任值年为张肇铨(字子衡),系清朝进士。当时银号开业者,并无登记注册之说,只要有师徒关系介绍,到会馆参加交易即可。所谓交易,主要是银两、银元和铜元互相兑换以及存款、放款。由于币制种类复杂,兑换业务占重要部分,钱关每天开关的兑换业务是大头银元兑换铜元。每早到钱业公所(即福德会馆)成交(又名上关)。最早有经纪人从中介绍,后演变为由双方直接交谈成交。公所内有专人负责挂牌,标出当日全市统一执行兑换的标准,关上按成交数字收手续费。后来,钱业公所负责人张子衡和石绍先闹意见,张子衡率领30家较大的银号脱离福德会馆,又在旧军门巷购地建楼,和石派分了家。当时关上业务仍是存款放款,没有汇兑。建立商埠后,土产、粮食等大量农产品来济成交,增加了汇兑业务,每天成交数量很大。这
时又在纬五路北首成立了交易所。从此,钱关分两处,城里关以存放为主,商埠关以汇兑为主。汇兑业务主要是出期票,5天为期,借以调剂头寸(金融业的流动金)。银号按地区分帮派,有山西帮、北京帮、河北帮、章丘帮、周村帮、潍县帮、黄县帮、济宁帮、当地帮等。发行钞票的有四五十家,发行的钞票是钱帖(分1吊、2吊、3吊、5吊、10吊5种);角票(分1角、2角、3角、5角4种);银两票(分1两、2两、5两、10两4种);发行银两的只有几家,大多数以发行钱帖最为通行。继银号之后,济南也出现了银行。最早的银行有大清银行(即中国银行前身),总行设在北京。1909年在济南建山东分行,行址设在旧军门巷。民国2年(即1913年)改为中国银行。资金4000万元,官商各半。1928年山东分行因受军阀压制骚扰,遂迁往青岛,济南改为支行,简称济支行,受青岛管辖。经理人最早为何象百。济支银行的业务主要是存、放、汇等。另一家国家银行是交通银行,创办人是梁士诒,因业务以交通事业为主而得名。1912年在济南建行,最初经理人为陆廷撰。除官办银行外,济南还有商业银行。最早的商业银行有:山东银行,经理人为张子衡。张宗昌时代,为区别于官办的山东省银行,令加商业2字,名山东商业银行。后因受军用票的摧残,被迫倒闭。东莱银行,创办人是青岛有名的烟土大王刘紫珊,1918年在济南建行,经理人原为陶峻南,后改为曹丹庭,业务偏重于房产贷款,从未发行钞票,所以遇有时局不稳,银行挤兑时,它从未受到影响。第三个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为陈光甫,总行设在上海,1915年创办,经营存、放、汇、仓库、外汇等。业务较新,偏重于小额储蓄、旅游,有名的中国旅行社及宝丰保险公司就是该行的附属机构,它在济南建行较晚(1919年),经
理人原为龚祥霖,继任为蔡墨屏。再有,大陆银行,总行在天津,系北四行(中南、大陆、盐业、金城)之一,总经理为谈荔孙。1921年9月在济南建行,经理曹锐岑。此外,还有实业、工商、通惠、齐鲁、泰丰、企业、道生、山左、丰大、周村商业、边业、懋业、中鲁等20余家,大都发行银行钞票。当时,官方虽有银行监理官,但形同虚设。仅于每期决算后,各银行自行造表填报,也不认真考核。当时,外国人在济南也开设了几家银行,如德人开设的德华银行济南支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即撤走。日商的正金、朝鲜、济南银行等,均在济设有分支机构。法国人经营的上海万国储蓄会和比利时经营的义品放款银行也在济南设有分会。前者为小额储蓄存款,后者以经营房地产为主。
1921年后,济南市银行业同业公会和钱业公会相继成立,均订有公会章程。自1921年到1928年,为济南市金融业业务比较繁荣时期。
二、张宗昌主鲁时期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宗昌来济主鲁,设立了山东省银行。钱业公会会长张子衡一心投靠张宗昌,被任命为山东省银行经理。省银行发行纸币,并代理省金库。同时还成立了山东军用款管理局和山东国库善后公债局,发行了军用票和公债票2000万元,并屡向各银行银号强迫借款。济南中国银行经理汪楞伯和交通银行经理陆廷撰均因不同意其借库存现洋20万元充军饷,而被张宗昌扣押在督军署(现在的珍珠泉)内达两三天之久。由于省银行滥发纸币,准备不足,屡有限制兑现之事。倘遇挤兑,就派军警弹压。各商店一开门,就有兵痞拿
军用票来抢购货物,稍一怠慢,就骂声喋喋,拳打脚踢。同时通令中国、交通、山东商业等行予以兑换,以致各家损失甚大,结果省银行票及军用票日益贬值,特别是军用票形同废纸。当时积存该票较多的银行、银号和商号大受亏累,最突出的是山东商业银行和丰年面粉厂被迫倒闭。
在军阀统治时期,当时还出现了不正当的钱业组织,即所谓的“会王钱庄”。先是以摆会为名,30人或50人为一个会,随会的每月交纳会金7吊或8吊(铜元50枚为吊)不等,一月一摆,10个月满期,可得本利100吊。因利息优厚,易于招揽。该会还私设钱庄滥发纸币,在魏家庄及偏僻街巷,栉比林立,俗称“满天飞钱庄”。一般银行、号知道该组织是骗人的而不与之交往,正当的工商业户也没有上当的,受坑害欺骗的多为劳苦大众,如拉洋车的,当保姆的,最初受点小利,就纷纷入会。约二三年后,政府对此予以取缔,各钱庄纷纷倒闭逃亡,所欠之款也无处追索。
这个时期,济南市的银行、号多以存、放、汇、贴现、兑换为主。所有存放利率、汇兑行情、兑换价格,均由关上决定(前已述及)。由于物价平稳,利息涨落亦悬殊不大,因没有法定的利息规定,一般银号放款利率,多超过年息2分。
银行、号的汇兑业务分电汇、票汇、信汇三种。以上海、天津、北京、青岛、烟台为主。电汇、票汇一般数额较大,多由银行承担,以中国、交通、山东商业、东莱、大陆、上海及日商的正金、朝鲜等行最活跃。其他一般银行号,各于每日上关交易时,根据需要头寸程度及资金力量,买卖迟期或即期汇票,以图盈利。当时英美等国的美孚油行、亚细亚煤油公司、英美烟草公司谦信洋行(经营颜料),卜内门洋碱公司,在中国、交
通、上海、山东商业等银行均立有往来账户,常有巨额存款,并做上海电汇。每汇一笔,辄为二三十万元,汇水每千元收费2元。
三、韩复榘统治时期(1930~1937年)
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山东,阻挠北伐,制造了“五三惨案”。日寇侵占济南,济南人民横遭涂炭,全市陷于混乱状态,各银行、号纷纷被迫停业。1929年国民党统治山东,最早来山东的是陈调元,而后是韩复榘。韩统治山东后,原停业的银行、号中,只有部分复业,韩为了控制地方金融,即筹设了山东平市官钱局,经理为汪腾蛟。由财政厅拨资金10万元,并准予发行铜元枚票,发行数额无从查考。继由各县随粮带征股款300万元,筹设山东民生银行,以财政厅原发的金库券300万元拨作该行官股基金。原定资本总额600万元,官民各半,并准予发行角票。总经理为王向荣(伪财政厅长兼),经理为宋福祺。
在此期间,中央银行也来济设立分行。银行业务逐渐活跃,以存、放款为主。凡在本市历史悠久,信誉素著的银行、号,前来存款的极为踊跃。放款方面,资金充裕的银行,直接贷放给较大的工商企业,如中国银行放款给仁丰纱厂(中国银行附设中国保险公司,并兼做火灾保险业务)。仁丰纱厂原由马伯声、穆伯仁(惠丰面粉厂总经理)等集资创办,建成后,仅房地产机器就将资金全部占用,已无活动能力。马伯声到青岛与中国银行经理王仰先联系,由济南中国银行投资200万元,并派人常驻该厂获得了400万元的贷款。经济稳定了,遂从英国购进新机器,从此大干起来。中国银行放款的大工商企业,还有华庆面粉厂和东元盛印染厂等。交通银行放款给鲁丰纱厂(现在的国棉一厂)早在1919年就开始了,先是信用透支。该厂是以
北洋军阀为后台,潘复、王占元为大股东,先由潘复任董事长。后以资金不足,由中、交两行放款,交行为多数,中行为少数,由交行派一总稽核和一名出纳。厂长为李荣萱和祝燮臣,至1932年改选王占元为董事长,来济主持业务。因王和韩复榘关系至好,遂向民生银行贷款,将中、交两行欠款全部还清。1933年因中国向美国做棉麦借款,大批棉麦倾销中国,于是国内物价暴跌。特别是面粉厂、纱厂因物价暴跌而倒闭者有之。鲁丰纱厂因欠债过多(大都是民生银行的贷款),经营困难,于是韩复榘下令让省府参议苗杏村接管,更名为成大纱厂。交通银行业务最发达的时候是1933年后,放款分信用和抵押,也做押汇。业务关系偏重于铁路、邮电系统。其他如纱厂、面粉厂、粮栈、花行、茶庄等,均由各行做抵押放款。
当时中国银行放款均用外仓,即在厂号仓库门前挂牌,标记中国银行仓库第×号,并立有租仓契约,中国银行派有驻厂员或仓库保管员,专管厂内进出货物,凭保管员的通知单,行里掌管放款或还款金额。尽管如此,也不无漏洞。因连年多吃呆账,前后有晋丰茶庄、崇德行、谦兴泰花行等,各欠贷款10万元,无力偿还,亏损很大。至此总行方感到有自建仓库的必要,1934年遂在济南经一路纬六路中国打包公司比邻购地,投资60万元建起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现代仓库。此后,凡用棉花作抵押者,先将棉花送往打包公司打包后,即送仓库领有栈单,再持单去银行办理抵押贷款,从此中国银行业务日渐发达。交通银行见此情况,也不甘落后,遂在经四路纬六路也自建交通仓库,但规模结构远不及中行仓库。此外在官扎营还有杂粮仓库,为了运输方便,有铁路岔道直通仓库内,此仓库属中交两行共用。在小纬北路还有中、交、上海3行仓库。所有这些仓库,连
同几家厂商的仓库,在1937年韩复榘弃城逃窜时,均遭抢掠、焚毁。
在银行、号业务中,兑换占主要部分。各行、号均以银两中的济秤为标准,以凭记账。当时有银两、银元、铜元等在市面流通使用,货币种类繁杂,兑换比率亦不统一。为统一币制,1933年4月6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废两改元条例》,禁止银两在市面流通,限期兑换。但银元和铜元仍照常通用和兑换。同年9月因银元涨价,省令限制铜元入境,并颁布了限制办法。1935年7月,又因各地现洋分歧,并有私运现洋从中渔利者,遂又颁布禁止现洋出境办法。此时银行发行纸币者很多,在济南设行发行纸币,有的不在济南设行的,也有纸币在济南流通,如中南银行,因其属北四行,其发行由大陆银行代理。这时虽已废两改元,但纸币仍极为混乱。且数额无限,难以控制。1935年11月4日国民党财政部又颁布了《统一法币条例》,命令停止使用现金,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币,其他各家纸币,限期收兑,过期一律禁止通用。并规定每币1元兑换铜元240枚。这样铜元银元的门市兑换才绝迹。为了控制现金集中国库,国民党中央又陆续颁布了《交换法币办法》、《银制品用银管理规则》,1937年颁布了《妨害国币惩治条例》。自此之后,银行、号业务才稳步发展。“七七”事变后,日寇攻占济南,本市银行、号有的南迁,有的自行停业,金融业暂时呈现萧条景象。当时只有8家银行,53家银号。
四、日寇统治时期(1937~1945年8月)
卢沟桥事变后,济南银行、号业务不稳,特别是韩复榘无意抗战,闻风逃窜,遂使各银行有了撤退南迁的打算。中央银
行首先撤退,中国银行虽未撤退,但随着经理陈隽人南调广西桂林,济支行的人员也有很多相继调往。至济南沦陷时,在济南的国家银行只剩中、交两行,私营银行有上海、大陆、东莱3家。各家虽未南迁,尚能勉强维持,但营业却已收缩。
1937年北平沦陷后,在日寇控制下,华北政务委员会财政总署署长汪时璟(字翊唐,安徽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原中国银行沈行经理),筹设组织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汪兼任总裁。汪早在军阀时代曾任中国银行汉行经理,因军阀肖耀南将汉行库存准备金现洋(银元)抢走,汉行挤兑,钞票作废。汪与当时副理徐味六等均下台。“九·一八”后,汪任中国银行沈行经理,又请徐味六出来任沈行副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于1938年3月成立后,汪又请徐味六任总稽核。1938年4月汪来济筹设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济南分行,汪带漆日昌(日本留学生)来济,找到当时中国银行济支行襄理徐木天帮助组织,他只由东北带来2人(彭士忱和刘亚宾),其他均由济支行抽调。后因经理漆日昌在济人生地疏,业务不熟,调回总行。济南分行及由交通银行副理黄恂伯任经理。会计主任张敦阜、出纳主任陈衡秋均由总行调来。并在青岛、烟台、龙口、威海等地设立分行,统辖全省金融。
这时期的汇兑业务完全由伪联银掌握,不分公私款项,不限汇额多少,每笔汇款只收汇费1角。至1941年12月1日又改定办法,伪联银专做官厅公款的汇兑调拨事项。从此,其他银行、号才又能承做工商业的汇款,汇出汇入多为北平、天津、青岛、徐州等地,汇额也不甚大,汇水随时变动。
早在1938年3月伪联银即颁布了“旧通货整理办法”。其主要内容是中、交两行钞票,凡印有津、青、鲁等地名者,及
河北省银行、冀东银行钞票,限期一年与联银券等价使用;中央及中国、交通3行未印有地名的钞票,限期3个月,均于限期内迅速兑换联银券。而山东民生银行的山东省库券及山西晋绥业等个别地方银行钞票和角票硬币等,均另行规定。是年8月对旧通货实施第一次贬值(按9折计算流通);1939年2月实施第二次贬值(按6折计算流通)。同时,颁布了禁止旧通货订立契约办法,规定无论任何贷存款契约均以联银券为标准。同年3月明令禁止旧通货流通和停止收兑。1939年4月以后,管理更加严格,颁布了“扰乱金融暂行治罪办法”,这时,虽然早已废两改元,统一了币制,但山东各县银号和一般商号仍多有发行银元券、银角券和铜元券者。伪山东省署公布了《取缔发行私钞及印刷私钞暂行办法》,限期一月,全部收回销毁,至此,市面流通的就只有联银券了。
1939年9月济南商会会长苗兰亭号召全市及全省各大城市筹集资金300万元,在联银扶持下,成立鲁兴银行。苗任董事长,总经理为王稷丞、经理为张铁邨、副理是王雨亭。各重要城市均设立分支机构办事处,统管全省公款收支省库业务。因此,未再筹集官股资金,是当时山东唯一活跃的官商合办银行。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济南中、交两行及所有外商洋行均被日本特务接收,扣押一天,来文没收,不许妄动。然后在北平成立华北中国银行、交通银行。1937年由青岛调来的襄理王兆钰担任了济南中国银行经理,并由北平总行派来会计主任朱季言。开业后,资金无着,不得已遂将纬六路仓库和中国打包分司作价400万元售给华北开发株式会社,以此作为伪中国银行资金。伪中国银行仅做小额外仓抵押贷款。多者5万元,少者一二万元不等。主要行业有:茶叶、粮业、杂货业、百
货业、棉布业等。所谓抵押,实际上就是变相的信用透支。
1938年8月济南沦陷后,原地方性的民生银行和平市官钱局即由敌伪接收,由日人主持,成立整理委员会予以整理。1941年1月1日,划归伪省署财政厅管理。同年11月成立兴农委员会继续整理。1942年3月伪省署又以兴农委员会所清理的民生银行和平市官钱局的部分资金,筹设山东农业银行。由北平联银总行派蒋廷梅来济任董事长,主持全行业务。另设经理魏子厚,副理张会丞,借用原中国银行营业室的主要部分开业。名义上是农业贷款,实际上,农民大众丝毫未得贷款,完全由伪县长贷出领用,或囤积居奇或高利贷出,再度剥削,饱入私囊。开业3年,因亏累过多,于1945年3月停业,移交给鲁兴银行予以清理。这个时期所有联银分行及鲁兴、农业等行,均配备有日本顾问。鲁兴银行顾问为浅井,常驻该行。中、交两行虽无顾问,但每天均有日报表送联银总行审核.联银会计主任还经常到行检查,所有贷款均须经联银总行批准。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实业总署与日寇合办的华北工业银行曾来济设立分行,经理余彬,行址就设在中国银行营业室。但未及营业,日寇就投降了,即行结束,由国民党接收。
至日寇投降前,济南尚有银行14家,银号25家。
日寇统治时期,对金融业的管理方面,于1939年5月颁布了《钱业账庄兑换业监督暂行条例》,至1941年12月11日又明令废止前项条例,另行颁布了《金融机关管理规则》,自颁布此项规定,久无变更。直至1944年12月间,又明令实施第二次增资,规定银号资本为300万元,银行资本为500万元,在6个月以内办理完毕。当时济南所有银号大部申请增资。除晋鲁、聚义、福顺德3家改为银行外,其他未待批回,日寇即宣
布投降,便无形结束。在这一时期济南银钱业对账簿使用进行了改革。
济南银号历史上都沿用旧式账簿,毛边纸竖式红格,用毛笔写的旧式账。记载麻烦,既繁琐又不科学,也不便查核。1933年济南钱业公会在经四路小纬五路会内,举办了簿记学校,每期两年。教师有本市著名会计师李光普、于文甲、阎肯堂等。第一期学员共42人,除各大银号均有人参加外,各大工厂如东元盛等,也都派人参加。以后又继续举办了几期,“七七”事变发生后,就停了。
1943年初,伪华北财政总署颁发了统一会计制度,当时济南市钱业公会为执行这一制度,继事变前的办法,举办会计人员训练班专讲新式簿记。执行统一会计制后,一律改为钢笔横写簿记帐。计有:总分类帐、各科目明细帐、现金日记帐。会计报表计有:日报表、月计表。年度决算有:营业实存状况表、资产负债表、财产目录、负债目录、损益计算表等。决算报表均送联合准备银行审核。
六、抗战后国民党统治时期(1945年8月~1948年8月)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政府财政部1945年10月颁布了《收复区银钱业暂行管理办法》,并举办私营银钱业登记。敌伪时期有几家停业的银号提出复业申请,还有不少早在“七七”事变前就已歇业的银号也乘机申请复业,申请复业继续营业的达60余家。
1945年底国民党省政府主席何思源来济接收敌伪创设的鲁兴银行,将其改组为山东省银行,由吴墉祥任经理,后来改为田叔藩。何来济后,开展了以国民党法币兑换伪联银券的工
作。法币兑换联银最早是1∶9,1945年10月22日又公布对换比率为1∶5。1946年3月由原在重庆任上清寺中央银行支行经理的刘铭善率领人员,随带钞票来济,筹备中央银行复业。刘铭善来济后,接收了日敌的济南银行。随同刘铭善来济的有20多人,其中有副理古质文、文书主任邵光裕、会计主任费同英、营业主任孙岳仙、国库主任姚莹、出纳主任杨〓、交换主任赵玉瑔等。其中绝大部分是山西人,又是刘一手提拔的亲信。唯副理古质文不是山西人,与刘有矛盾。刘来济后想提拔一工友陈某为行员,并假填姓名,为古反对,古以此控告刘欺骗总行,因而陈某未得批准,最后被推荐到东莱银行去,另由东莱银行行长的儿子来中央银行工作,以此作为交换条件。同时古某也被调走,换来副理刘缦卿,他也是刘一手提拔的亲信。因刘是山西人,所以来济后,山西帮的银行很为得利。此时中央银行的业务是发行纸币,代理国库,办理军队存款、汇兑、同业存款活期透支、管理行号存款准备金、核定行号(新建的)资本、办理票据交换等。当时存款主要是军款,由国库拨来,转存活期存款,再转往其他银行或银号。省政府公款则由山东省银行办理,中央银行不做对外放款。票据交换最早只有6家国营银行(中、中、交、农、中央信托局、合作金库)参加,而后全市银行、号均加入,票据交换及同业存款归由营业组掌管。遇有票据交换对轧不平,有欠款的银行、号,这时就要求中央银行帮忙等时间,直等欠款的行、号找军需弄到存款支票,来轧平为止。有时直等到深夜。这就是中央银行对行、号帮大忙的办法。所以济南从未有一家行、号因轧不平而被迫停业的。
1946年3月,中国、交通两行也都由总行派人来接收。中国银行派人来接收的是周寿民,抗战前他是代表中国银行驻仁
丰纱厂的会计主任,这次来济前是四川万县中国银行经理。随同周来济的有襄理张维炜、营业主任吴绍唐、会计主任王鸿鼎、仓库主任颜树东和城内办事处主任周万明等人。来济后除接收了中国银行外,还接收了日敌的正金银行。来济接收交通银行的是季琛。从此中、交两行均相继复业。在济的私营银行东莱、大陆、上海等银行也相继营业。同年下半年,国民党财政部为了控制地方金融,先后在济设立了中央合作金库(经理是陈以铮)、中央信托局(经理吴本仁)及邮政储金汇业局等。同时中国农民银行也在济设立分行,开始营业,但业务限于农贷,未得开展,经理是李祖道。1947年12月济南市政府又筹集资金,开办了官民合营的济南市银行,资金定为10亿元,官股5亿元由市政府拨付,民股5亿元由各区区长负责摊派。但由于货币恶性膨胀,物价飞涨,仅在筹备期间即用掉资金总额的1/5。
至济南解放前夕,全市官办银行共有7家,地方银行两家,私营银行3家。银号在日寇投降前,原有25家,由于国民党规定,凡在战前曾设立而无附逆行为,有证明文件者,均可申请复业。因此,先后共批准银号多达69家,其中尚有第一、第二信用合作社,也属银号性质,由国民党头脑人物组成,专为吸收军队存款,用以投机倒把。但因货币膨胀,物价飞涨,开业不久即宣告停业。所以至解放前夕,尚有12家银行,59家银号。
这个时期的银行号的业务仍以存、放、汇为主。但由于官僚资本投入市场及游资充斥集中,致使一般银钱业务颇为活跃。1946年4月,国民党财政部颁布了《银行管理办法》(包括银号),规定普遍存款应以现款交存准备金,活期15%~20%,定期7%~15%,非经特准不得买卖外汇及生金银;资金运用贷放对象,以工商生产事业及对外贸易之运销事业为限。这时各银
行号在中央银行按存款余额交存准备金,虽有比率规定,据当时主管人说:“并不按比率规定执行,差不离就算了。”
1948年8月国民党币制改革后,山东省府曾颁布《银钱行庄存放利率限制办法》:(1)依中央银行规定之利率。(2)9月1日起放款利率不得超过月息10分,9月16日起放款利率不得超过月息5分,10月1日以后,应压低至民法205条之法定最高利率(即年息2分)。但由于货币恶性膨胀,贬值越来越严重,物价飞涨不可遏止。所以存放利率虽有规定,无人执行,形同虚文。官僚资本大都通过银钱业吸收存款,投入市场,带头投机倒把。一般工商业资金和社会游资,大都做黄金棉纱买卖,囤积居奇,较之敌伪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在法币继续贬值,物价一日数涨的情况下,一般私营银钱业也都兼营了其他副业,借以保本,进而追逐更多利润。国民党政府虽欲严加管理,但各银号均设有“假账”或“两套账”,以备应付官府检查。当时的存、放业务,因受物价波动,私人们愿存货不愿存钱,为吸引存款,当时的存款利率最高达30分,最低也在15分以上,放款(贴现)利率最高达51分,最低24分。尽管如此,各银号存款业务仍不景气。
1948年9月,济南解放前夕,金融业同其他行业一样,人心惶惶,形同停业。许多银行负责人本想逃走,但已买不到飞机票。解放军进城后,马上召集各银行的负责人,宣布共产党的政策,以安定人心。要求原国家银行“办好交待后,留者欢迎,去者欢送”。政策宣布后,人心大为安定。所以各行办理交待,极为顺利。一般私营银行号也人心安定,等待人民政府处理。
(济南市政协供稿)
黄得中
一、清末民初时期
济南的银号起源于清朝康乾年间,最早的有:三合恒、庆泰昌、蚨聚长、协聚泰等,大半成立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还有汇兑钱庄,如大德通、大德恒、晋逢祥等,它们大都是光绪年间山西人来鲁开业的。汇兑钱庄(票庄)专做北京、西北一带的汇兑、贷款生意。此后又有历城、章丘、周村等商人在济南陆续开设的仁和祥、裕茂、同升、广成泰、厚记等银号。
道光年间,在高都司巷成立的福德会馆,为钱业最早的组织,即钱业公会的萌芽组织。会馆设值年,主持会馆一切事务。首任值年为张肇铨(字子衡),系清朝进士。当时银号开业者,并无登记注册之说,只要有师徒关系介绍,到会馆参加交易即可。所谓交易,主要是银两、银元和铜元互相兑换以及存款、放款。由于币制种类复杂,兑换业务占重要部分,钱关每天开关的兑换业务是大头银元兑换铜元。每早到钱业公所(即福德会馆)成交(又名上关)。最早有经纪人从中介绍,后演变为由双方直接交谈成交。公所内有专人负责挂牌,标出当日全市统一执行兑换的标准,关上按成交数字收手续费。后来,钱业公所负责人张子衡和石绍先闹意见,张子衡率领30家较大的银号脱离福德会馆,又在旧军门巷购地建楼,和石派分了家。当时关上业务仍是存款放款,没有汇兑。建立商埠后,土产、粮食等大量农产品来济成交,增加了汇兑业务,每天成交数量很大。这
时又在纬五路北首成立了交易所。从此,钱关分两处,城里关以存放为主,商埠关以汇兑为主。汇兑业务主要是出期票,5天为期,借以调剂头寸(金融业的流动金)。银号按地区分帮派,有山西帮、北京帮、河北帮、章丘帮、周村帮、潍县帮、黄县帮、济宁帮、当地帮等。发行钞票的有四五十家,发行的钞票是钱帖(分1吊、2吊、3吊、5吊、10吊5种);角票(分1角、2角、3角、5角4种);银两票(分1两、2两、5两、10两4种);发行银两的只有几家,大多数以发行钱帖最为通行。继银号之后,济南也出现了银行。最早的银行有大清银行(即中国银行前身),总行设在北京。1909年在济南建山东分行,行址设在旧军门巷。民国2年(即1913年)改为中国银行。资金4000万元,官商各半。1928年山东分行因受军阀压制骚扰,遂迁往青岛,济南改为支行,简称济支行,受青岛管辖。经理人最早为何象百。济支银行的业务主要是存、放、汇等。另一家国家银行是交通银行,创办人是梁士诒,因业务以交通事业为主而得名。1912年在济南建行,最初经理人为陆廷撰。除官办银行外,济南还有商业银行。最早的商业银行有:山东银行,经理人为张子衡。张宗昌时代,为区别于官办的山东省银行,令加商业2字,名山东商业银行。后因受军用票的摧残,被迫倒闭。东莱银行,创办人是青岛有名的烟土大王刘紫珊,1918年在济南建行,经理人原为陶峻南,后改为曹丹庭,业务偏重于房产贷款,从未发行钞票,所以遇有时局不稳,银行挤兑时,它从未受到影响。第三个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为陈光甫,总行设在上海,1915年创办,经营存、放、汇、仓库、外汇等。业务较新,偏重于小额储蓄、旅游,有名的中国旅行社及宝丰保险公司就是该行的附属机构,它在济南建行较晚(1919年),经
理人原为龚祥霖,继任为蔡墨屏。再有,大陆银行,总行在天津,系北四行(中南、大陆、盐业、金城)之一,总经理为谈荔孙。1921年9月在济南建行,经理曹锐岑。此外,还有实业、工商、通惠、齐鲁、泰丰、企业、道生、山左、丰大、周村商业、边业、懋业、中鲁等20余家,大都发行银行钞票。当时,官方虽有银行监理官,但形同虚设。仅于每期决算后,各银行自行造表填报,也不认真考核。当时,外国人在济南也开设了几家银行,如德人开设的德华银行济南支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即撤走。日商的正金、朝鲜、济南银行等,均在济设有分支机构。法国人经营的上海万国储蓄会和比利时经营的义品放款银行也在济南设有分会。前者为小额储蓄存款,后者以经营房地产为主。
1921年后,济南市银行业同业公会和钱业公会相继成立,均订有公会章程。自1921年到1928年,为济南市金融业业务比较繁荣时期。
二、张宗昌主鲁时期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宗昌来济主鲁,设立了山东省银行。钱业公会会长张子衡一心投靠张宗昌,被任命为山东省银行经理。省银行发行纸币,并代理省金库。同时还成立了山东军用款管理局和山东国库善后公债局,发行了军用票和公债票2000万元,并屡向各银行银号强迫借款。济南中国银行经理汪楞伯和交通银行经理陆廷撰均因不同意其借库存现洋20万元充军饷,而被张宗昌扣押在督军署(现在的珍珠泉)内达两三天之久。由于省银行滥发纸币,准备不足,屡有限制兑现之事。倘遇挤兑,就派军警弹压。各商店一开门,就有兵痞拿
军用票来抢购货物,稍一怠慢,就骂声喋喋,拳打脚踢。同时通令中国、交通、山东商业等行予以兑换,以致各家损失甚大,结果省银行票及军用票日益贬值,特别是军用票形同废纸。当时积存该票较多的银行、银号和商号大受亏累,最突出的是山东商业银行和丰年面粉厂被迫倒闭。
在军阀统治时期,当时还出现了不正当的钱业组织,即所谓的“会王钱庄”。先是以摆会为名,30人或50人为一个会,随会的每月交纳会金7吊或8吊(铜元50枚为吊)不等,一月一摆,10个月满期,可得本利100吊。因利息优厚,易于招揽。该会还私设钱庄滥发纸币,在魏家庄及偏僻街巷,栉比林立,俗称“满天飞钱庄”。一般银行、号知道该组织是骗人的而不与之交往,正当的工商业户也没有上当的,受坑害欺骗的多为劳苦大众,如拉洋车的,当保姆的,最初受点小利,就纷纷入会。约二三年后,政府对此予以取缔,各钱庄纷纷倒闭逃亡,所欠之款也无处追索。
这个时期,济南市的银行、号多以存、放、汇、贴现、兑换为主。所有存放利率、汇兑行情、兑换价格,均由关上决定(前已述及)。由于物价平稳,利息涨落亦悬殊不大,因没有法定的利息规定,一般银号放款利率,多超过年息2分。
银行、号的汇兑业务分电汇、票汇、信汇三种。以上海、天津、北京、青岛、烟台为主。电汇、票汇一般数额较大,多由银行承担,以中国、交通、山东商业、东莱、大陆、上海及日商的正金、朝鲜等行最活跃。其他一般银行号,各于每日上关交易时,根据需要头寸程度及资金力量,买卖迟期或即期汇票,以图盈利。当时英美等国的美孚油行、亚细亚煤油公司、英美烟草公司谦信洋行(经营颜料),卜内门洋碱公司,在中国、交
通、上海、山东商业等银行均立有往来账户,常有巨额存款,并做上海电汇。每汇一笔,辄为二三十万元,汇水每千元收费2元。
三、韩复榘统治时期(1930~1937年)
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山东,阻挠北伐,制造了“五三惨案”。日寇侵占济南,济南人民横遭涂炭,全市陷于混乱状态,各银行、号纷纷被迫停业。1929年国民党统治山东,最早来山东的是陈调元,而后是韩复榘。韩统治山东后,原停业的银行、号中,只有部分复业,韩为了控制地方金融,即筹设了山东平市官钱局,经理为汪腾蛟。由财政厅拨资金10万元,并准予发行铜元枚票,发行数额无从查考。继由各县随粮带征股款300万元,筹设山东民生银行,以财政厅原发的金库券300万元拨作该行官股基金。原定资本总额600万元,官民各半,并准予发行角票。总经理为王向荣(伪财政厅长兼),经理为宋福祺。
在此期间,中央银行也来济设立分行。银行业务逐渐活跃,以存、放款为主。凡在本市历史悠久,信誉素著的银行、号,前来存款的极为踊跃。放款方面,资金充裕的银行,直接贷放给较大的工商企业,如中国银行放款给仁丰纱厂(中国银行附设中国保险公司,并兼做火灾保险业务)。仁丰纱厂原由马伯声、穆伯仁(惠丰面粉厂总经理)等集资创办,建成后,仅房地产机器就将资金全部占用,已无活动能力。马伯声到青岛与中国银行经理王仰先联系,由济南中国银行投资200万元,并派人常驻该厂获得了400万元的贷款。经济稳定了,遂从英国购进新机器,从此大干起来。中国银行放款的大工商企业,还有华庆面粉厂和东元盛印染厂等。交通银行放款给鲁丰纱厂(现在的国棉一厂)早在1919年就开始了,先是信用透支。该厂是以
北洋军阀为后台,潘复、王占元为大股东,先由潘复任董事长。后以资金不足,由中、交两行放款,交行为多数,中行为少数,由交行派一总稽核和一名出纳。厂长为李荣萱和祝燮臣,至1932年改选王占元为董事长,来济主持业务。因王和韩复榘关系至好,遂向民生银行贷款,将中、交两行欠款全部还清。1933年因中国向美国做棉麦借款,大批棉麦倾销中国,于是国内物价暴跌。特别是面粉厂、纱厂因物价暴跌而倒闭者有之。鲁丰纱厂因欠债过多(大都是民生银行的贷款),经营困难,于是韩复榘下令让省府参议苗杏村接管,更名为成大纱厂。交通银行业务最发达的时候是1933年后,放款分信用和抵押,也做押汇。业务关系偏重于铁路、邮电系统。其他如纱厂、面粉厂、粮栈、花行、茶庄等,均由各行做抵押放款。
当时中国银行放款均用外仓,即在厂号仓库门前挂牌,标记中国银行仓库第×号,并立有租仓契约,中国银行派有驻厂员或仓库保管员,专管厂内进出货物,凭保管员的通知单,行里掌管放款或还款金额。尽管如此,也不无漏洞。因连年多吃呆账,前后有晋丰茶庄、崇德行、谦兴泰花行等,各欠贷款10万元,无力偿还,亏损很大。至此总行方感到有自建仓库的必要,1934年遂在济南经一路纬六路中国打包公司比邻购地,投资60万元建起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现代仓库。此后,凡用棉花作抵押者,先将棉花送往打包公司打包后,即送仓库领有栈单,再持单去银行办理抵押贷款,从此中国银行业务日渐发达。交通银行见此情况,也不甘落后,遂在经四路纬六路也自建交通仓库,但规模结构远不及中行仓库。此外在官扎营还有杂粮仓库,为了运输方便,有铁路岔道直通仓库内,此仓库属中交两行共用。在小纬北路还有中、交、上海3行仓库。所有这些仓库,连
同几家厂商的仓库,在1937年韩复榘弃城逃窜时,均遭抢掠、焚毁。
在银行、号业务中,兑换占主要部分。各行、号均以银两中的济秤为标准,以凭记账。当时有银两、银元、铜元等在市面流通使用,货币种类繁杂,兑换比率亦不统一。为统一币制,1933年4月6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废两改元条例》,禁止银两在市面流通,限期兑换。但银元和铜元仍照常通用和兑换。同年9月因银元涨价,省令限制铜元入境,并颁布了限制办法。1935年7月,又因各地现洋分歧,并有私运现洋从中渔利者,遂又颁布禁止现洋出境办法。此时银行发行纸币者很多,在济南设行发行纸币,有的不在济南设行的,也有纸币在济南流通,如中南银行,因其属北四行,其发行由大陆银行代理。这时虽已废两改元,但纸币仍极为混乱。且数额无限,难以控制。1935年11月4日国民党财政部又颁布了《统一法币条例》,命令停止使用现金,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币,其他各家纸币,限期收兑,过期一律禁止通用。并规定每币1元兑换铜元240枚。这样铜元银元的门市兑换才绝迹。为了控制现金集中国库,国民党中央又陆续颁布了《交换法币办法》、《银制品用银管理规则》,1937年颁布了《妨害国币惩治条例》。自此之后,银行、号业务才稳步发展。“七七”事变后,日寇攻占济南,本市银行、号有的南迁,有的自行停业,金融业暂时呈现萧条景象。当时只有8家银行,53家银号。
四、日寇统治时期(1937~1945年8月)
卢沟桥事变后,济南银行、号业务不稳,特别是韩复榘无意抗战,闻风逃窜,遂使各银行有了撤退南迁的打算。中央银
行首先撤退,中国银行虽未撤退,但随着经理陈隽人南调广西桂林,济支行的人员也有很多相继调往。至济南沦陷时,在济南的国家银行只剩中、交两行,私营银行有上海、大陆、东莱3家。各家虽未南迁,尚能勉强维持,但营业却已收缩。
1937年北平沦陷后,在日寇控制下,华北政务委员会财政总署署长汪时璟(字翊唐,安徽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原中国银行沈行经理),筹设组织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汪兼任总裁。汪早在军阀时代曾任中国银行汉行经理,因军阀肖耀南将汉行库存准备金现洋(银元)抢走,汉行挤兑,钞票作废。汪与当时副理徐味六等均下台。“九·一八”后,汪任中国银行沈行经理,又请徐味六出来任沈行副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于1938年3月成立后,汪又请徐味六任总稽核。1938年4月汪来济筹设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济南分行,汪带漆日昌(日本留学生)来济,找到当时中国银行济支行襄理徐木天帮助组织,他只由东北带来2人(彭士忱和刘亚宾),其他均由济支行抽调。后因经理漆日昌在济人生地疏,业务不熟,调回总行。济南分行及由交通银行副理黄恂伯任经理。会计主任张敦阜、出纳主任陈衡秋均由总行调来。并在青岛、烟台、龙口、威海等地设立分行,统辖全省金融。
这时期的汇兑业务完全由伪联银掌握,不分公私款项,不限汇额多少,每笔汇款只收汇费1角。至1941年12月1日又改定办法,伪联银专做官厅公款的汇兑调拨事项。从此,其他银行、号才又能承做工商业的汇款,汇出汇入多为北平、天津、青岛、徐州等地,汇额也不甚大,汇水随时变动。
早在1938年3月伪联银即颁布了“旧通货整理办法”。其主要内容是中、交两行钞票,凡印有津、青、鲁等地名者,及
河北省银行、冀东银行钞票,限期一年与联银券等价使用;中央及中国、交通3行未印有地名的钞票,限期3个月,均于限期内迅速兑换联银券。而山东民生银行的山东省库券及山西晋绥业等个别地方银行钞票和角票硬币等,均另行规定。是年8月对旧通货实施第一次贬值(按9折计算流通);1939年2月实施第二次贬值(按6折计算流通)。同时,颁布了禁止旧通货订立契约办法,规定无论任何贷存款契约均以联银券为标准。同年3月明令禁止旧通货流通和停止收兑。1939年4月以后,管理更加严格,颁布了“扰乱金融暂行治罪办法”,这时,虽然早已废两改元,统一了币制,但山东各县银号和一般商号仍多有发行银元券、银角券和铜元券者。伪山东省署公布了《取缔发行私钞及印刷私钞暂行办法》,限期一月,全部收回销毁,至此,市面流通的就只有联银券了。
1939年9月济南商会会长苗兰亭号召全市及全省各大城市筹集资金300万元,在联银扶持下,成立鲁兴银行。苗任董事长,总经理为王稷丞、经理为张铁邨、副理是王雨亭。各重要城市均设立分支机构办事处,统管全省公款收支省库业务。因此,未再筹集官股资金,是当时山东唯一活跃的官商合办银行。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济南中、交两行及所有外商洋行均被日本特务接收,扣押一天,来文没收,不许妄动。然后在北平成立华北中国银行、交通银行。1937年由青岛调来的襄理王兆钰担任了济南中国银行经理,并由北平总行派来会计主任朱季言。开业后,资金无着,不得已遂将纬六路仓库和中国打包分司作价400万元售给华北开发株式会社,以此作为伪中国银行资金。伪中国银行仅做小额外仓抵押贷款。多者5万元,少者一二万元不等。主要行业有:茶叶、粮业、杂货业、百
货业、棉布业等。所谓抵押,实际上就是变相的信用透支。
1938年8月济南沦陷后,原地方性的民生银行和平市官钱局即由敌伪接收,由日人主持,成立整理委员会予以整理。1941年1月1日,划归伪省署财政厅管理。同年11月成立兴农委员会继续整理。1942年3月伪省署又以兴农委员会所清理的民生银行和平市官钱局的部分资金,筹设山东农业银行。由北平联银总行派蒋廷梅来济任董事长,主持全行业务。另设经理魏子厚,副理张会丞,借用原中国银行营业室的主要部分开业。名义上是农业贷款,实际上,农民大众丝毫未得贷款,完全由伪县长贷出领用,或囤积居奇或高利贷出,再度剥削,饱入私囊。开业3年,因亏累过多,于1945年3月停业,移交给鲁兴银行予以清理。这个时期所有联银分行及鲁兴、农业等行,均配备有日本顾问。鲁兴银行顾问为浅井,常驻该行。中、交两行虽无顾问,但每天均有日报表送联银总行审核.联银会计主任还经常到行检查,所有贷款均须经联银总行批准。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实业总署与日寇合办的华北工业银行曾来济设立分行,经理余彬,行址就设在中国银行营业室。但未及营业,日寇就投降了,即行结束,由国民党接收。
至日寇投降前,济南尚有银行14家,银号25家。
日寇统治时期,对金融业的管理方面,于1939年5月颁布了《钱业账庄兑换业监督暂行条例》,至1941年12月11日又明令废止前项条例,另行颁布了《金融机关管理规则》,自颁布此项规定,久无变更。直至1944年12月间,又明令实施第二次增资,规定银号资本为300万元,银行资本为500万元,在6个月以内办理完毕。当时济南所有银号大部申请增资。除晋鲁、聚义、福顺德3家改为银行外,其他未待批回,日寇即宣
布投降,便无形结束。在这一时期济南银钱业对账簿使用进行了改革。
济南银号历史上都沿用旧式账簿,毛边纸竖式红格,用毛笔写的旧式账。记载麻烦,既繁琐又不科学,也不便查核。1933年济南钱业公会在经四路小纬五路会内,举办了簿记学校,每期两年。教师有本市著名会计师李光普、于文甲、阎肯堂等。第一期学员共42人,除各大银号均有人参加外,各大工厂如东元盛等,也都派人参加。以后又继续举办了几期,“七七”事变发生后,就停了。
1943年初,伪华北财政总署颁发了统一会计制度,当时济南市钱业公会为执行这一制度,继事变前的办法,举办会计人员训练班专讲新式簿记。执行统一会计制后,一律改为钢笔横写簿记帐。计有:总分类帐、各科目明细帐、现金日记帐。会计报表计有:日报表、月计表。年度决算有:营业实存状况表、资产负债表、财产目录、负债目录、损益计算表等。决算报表均送联合准备银行审核。
六、抗战后国民党统治时期(1945年8月~1948年8月)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政府财政部1945年10月颁布了《收复区银钱业暂行管理办法》,并举办私营银钱业登记。敌伪时期有几家停业的银号提出复业申请,还有不少早在“七七”事变前就已歇业的银号也乘机申请复业,申请复业继续营业的达60余家。
1945年底国民党省政府主席何思源来济接收敌伪创设的鲁兴银行,将其改组为山东省银行,由吴墉祥任经理,后来改为田叔藩。何来济后,开展了以国民党法币兑换伪联银券的工
作。法币兑换联银最早是1∶9,1945年10月22日又公布对换比率为1∶5。1946年3月由原在重庆任上清寺中央银行支行经理的刘铭善率领人员,随带钞票来济,筹备中央银行复业。刘铭善来济后,接收了日敌的济南银行。随同刘铭善来济的有20多人,其中有副理古质文、文书主任邵光裕、会计主任费同英、营业主任孙岳仙、国库主任姚莹、出纳主任杨〓、交换主任赵玉瑔等。其中绝大部分是山西人,又是刘一手提拔的亲信。唯副理古质文不是山西人,与刘有矛盾。刘来济后想提拔一工友陈某为行员,并假填姓名,为古反对,古以此控告刘欺骗总行,因而陈某未得批准,最后被推荐到东莱银行去,另由东莱银行行长的儿子来中央银行工作,以此作为交换条件。同时古某也被调走,换来副理刘缦卿,他也是刘一手提拔的亲信。因刘是山西人,所以来济后,山西帮的银行很为得利。此时中央银行的业务是发行纸币,代理国库,办理军队存款、汇兑、同业存款活期透支、管理行号存款准备金、核定行号(新建的)资本、办理票据交换等。当时存款主要是军款,由国库拨来,转存活期存款,再转往其他银行或银号。省政府公款则由山东省银行办理,中央银行不做对外放款。票据交换最早只有6家国营银行(中、中、交、农、中央信托局、合作金库)参加,而后全市银行、号均加入,票据交换及同业存款归由营业组掌管。遇有票据交换对轧不平,有欠款的银行、号,这时就要求中央银行帮忙等时间,直等欠款的行、号找军需弄到存款支票,来轧平为止。有时直等到深夜。这就是中央银行对行、号帮大忙的办法。所以济南从未有一家行、号因轧不平而被迫停业的。
1946年3月,中国、交通两行也都由总行派人来接收。中国银行派人来接收的是周寿民,抗战前他是代表中国银行驻仁
丰纱厂的会计主任,这次来济前是四川万县中国银行经理。随同周来济的有襄理张维炜、营业主任吴绍唐、会计主任王鸿鼎、仓库主任颜树东和城内办事处主任周万明等人。来济后除接收了中国银行外,还接收了日敌的正金银行。来济接收交通银行的是季琛。从此中、交两行均相继复业。在济的私营银行东莱、大陆、上海等银行也相继营业。同年下半年,国民党财政部为了控制地方金融,先后在济设立了中央合作金库(经理是陈以铮)、中央信托局(经理吴本仁)及邮政储金汇业局等。同时中国农民银行也在济设立分行,开始营业,但业务限于农贷,未得开展,经理是李祖道。1947年12月济南市政府又筹集资金,开办了官民合营的济南市银行,资金定为10亿元,官股5亿元由市政府拨付,民股5亿元由各区区长负责摊派。但由于货币恶性膨胀,物价飞涨,仅在筹备期间即用掉资金总额的1/5。
至济南解放前夕,全市官办银行共有7家,地方银行两家,私营银行3家。银号在日寇投降前,原有25家,由于国民党规定,凡在战前曾设立而无附逆行为,有证明文件者,均可申请复业。因此,先后共批准银号多达69家,其中尚有第一、第二信用合作社,也属银号性质,由国民党头脑人物组成,专为吸收军队存款,用以投机倒把。但因货币膨胀,物价飞涨,开业不久即宣告停业。所以至解放前夕,尚有12家银行,59家银号。
这个时期的银行号的业务仍以存、放、汇为主。但由于官僚资本投入市场及游资充斥集中,致使一般银钱业务颇为活跃。1946年4月,国民党财政部颁布了《银行管理办法》(包括银号),规定普遍存款应以现款交存准备金,活期15%~20%,定期7%~15%,非经特准不得买卖外汇及生金银;资金运用贷放对象,以工商生产事业及对外贸易之运销事业为限。这时各银
行号在中央银行按存款余额交存准备金,虽有比率规定,据当时主管人说:“并不按比率规定执行,差不离就算了。”
1948年8月国民党币制改革后,山东省府曾颁布《银钱行庄存放利率限制办法》:(1)依中央银行规定之利率。(2)9月1日起放款利率不得超过月息10分,9月16日起放款利率不得超过月息5分,10月1日以后,应压低至民法205条之法定最高利率(即年息2分)。但由于货币恶性膨胀,贬值越来越严重,物价飞涨不可遏止。所以存放利率虽有规定,无人执行,形同虚文。官僚资本大都通过银钱业吸收存款,投入市场,带头投机倒把。一般工商业资金和社会游资,大都做黄金棉纱买卖,囤积居奇,较之敌伪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在法币继续贬值,物价一日数涨的情况下,一般私营银钱业也都兼营了其他副业,借以保本,进而追逐更多利润。国民党政府虽欲严加管理,但各银号均设有“假账”或“两套账”,以备应付官府检查。当时的存、放业务,因受物价波动,私人们愿存货不愿存钱,为吸引存款,当时的存款利率最高达30分,最低也在15分以上,放款(贴现)利率最高达51分,最低24分。尽管如此,各银号存款业务仍不景气。
1948年9月,济南解放前夕,金融业同其他行业一样,人心惶惶,形同停业。许多银行负责人本想逃走,但已买不到飞机票。解放军进城后,马上召集各银行的负责人,宣布共产党的政策,以安定人心。要求原国家银行“办好交待后,留者欢迎,去者欢送”。政策宣布后,人心大为安定。所以各行办理交待,极为顺利。一般私营银行号也人心安定,等待人民政府处理。
(济南市政协供稿)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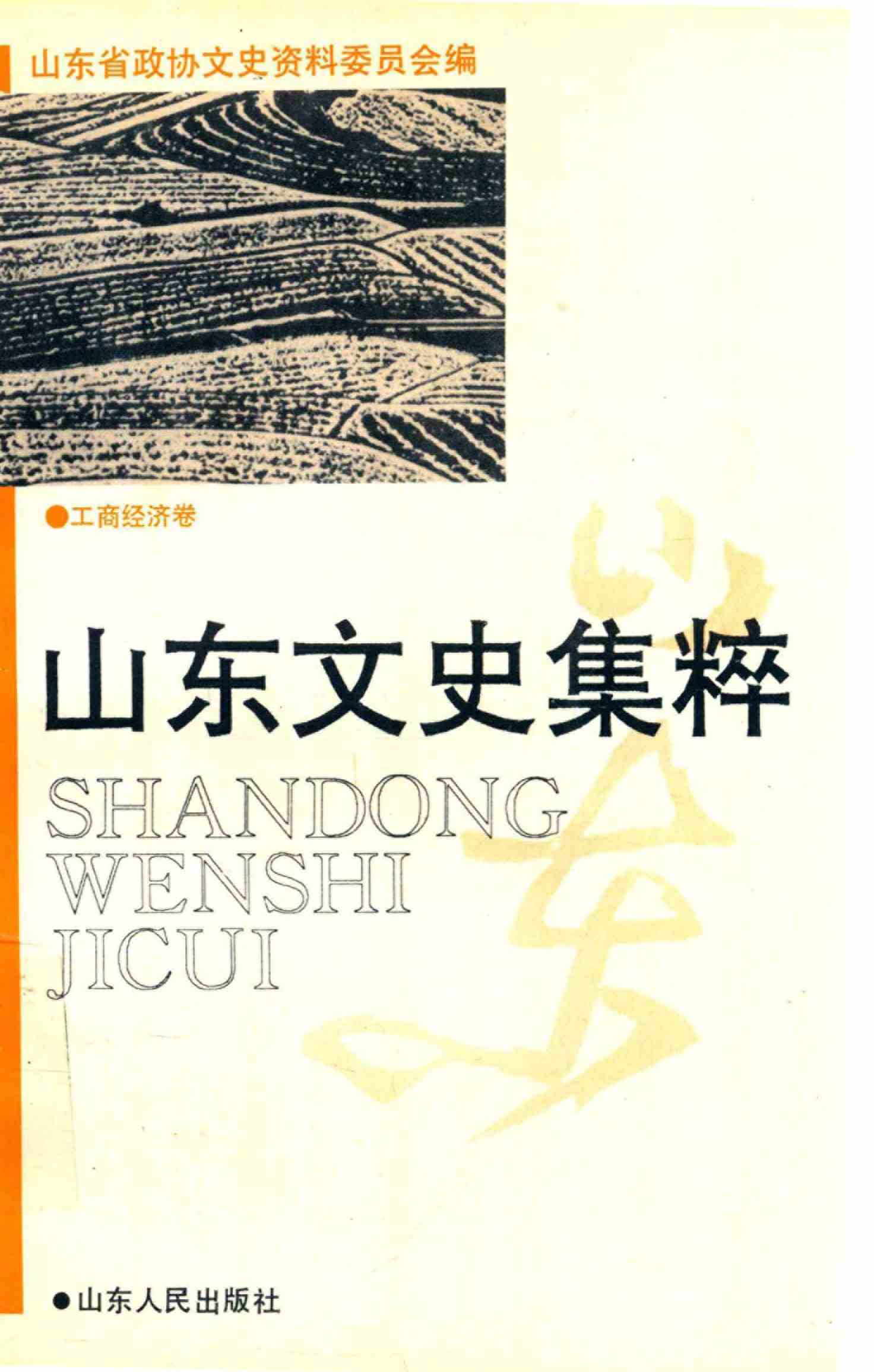
《山东文史集粹工商经济卷》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本书分为政治、军事、革命斗争、工商经济、科技、文化、教育、民族宗教、社会、风物10卷,全书以真实丰富的史料,朴实流畅的文风,重点反映了自戊戌变法至建国前半个多世纪中发生在山东省的重要史实。
阅读
相关人物
黄得中
责任者
相关地名
山东省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