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德顺兴造钟厂
| 内容出处: | 《山东文史集粹工商经济卷》 图书 |
| 唯一号: | 150020020220001707 |
| 颗粒名称: | 烟台德顺兴造钟厂 |
| 分类号: | K295.2 |
| 页数: | 14 |
| 页码: | 85-98 |
| 摘要: | 本篇记述了我于1928年到烟台德顺兴造钟厂学生意,历任会计、经理,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后,烟台德顺兴造钟厂。 |
| 关键词: | 烟台市 德顺兴造钟厂 |
内容
我于1928年到烟台德顺兴造钟厂学生意,历任会计、经理,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后,工作共达46年之久。兹据我个人的经历和见闻,述录成篇,以供有关研究者参考,想亦聊胜于无。如有谬误诚望指正。
一德顺兴的原名叫宝时造钟厂,创办于1915年7月。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次年,英、法、德、意、俄等帝国主义正忙于争夺世界霸权的侵略战争,无暇东顾,我国民族工业稍得长足发展之隙。际此时机,李东山出资,在烟台朝阳街南段东侧创办了一个造钟厂,注册登记为“宝时造钟厂”,商标“宝”字,资金2.5万元。
李东山本名叫李树桐,字东山,原籍威海市人,约生于清季光绪初年,死于1946年10月。此人自幼家道贫穷,不曾入学读书,早年以肩挑小贩为生。他的发迹与烟台当时富商恒兴德丝行是有干系的。最初他独身来烟,腰中仅有200铜钱,投靠他在恒兴德当上海客的堂兄,经堂兄保荐在恒兴德当了一名小伙计。由于他生就乖俐,善于逢迎巴结,不久拜认恒兴德的东家孙文山为干爹。以后他受不了行规约束,自愿退出,仍去从事小贩生涯。在贩卖的市利中,逐渐积起一点资本,就在北大街与太平街南首交会处,开了一个水炉小铺,同时又兼去海关叫行,资本不够向他干爹孙文山告贷。据轶闻,他在叫行买进海关拍卖没收的私货禁物中,发了一笔意外的奇财,于是突为显富而闻。另一说他倒卖了一批船粮,因粮价上涨而得了一笔厚利。总之,他对自己的突富之道一向缄口不宣,讳莫如深,同他共事的人惟感突兀,不解其奥。不过,李东山已握重资确是实事。
俗云,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李东山在握有资本以后,于1892年首先就在他开水炉小铺地址,扩办一爿德顺兴五金行,资本为墨(墨西哥)币300元,至1904年,资本扩大为3万元墨币,主要经营小五金和兼营百货商品。这个五金行成了李东山创办其他事业的本源,也是开办德顺兴造钟厂的母本公司。继之,在烟开办了同志玻璃厂、瑞兴制伞厂,在威海开办了威新花炮厂(后迁烟)、同庆顺镶锡店。以上厂商,在当时的烟威一带均为首创,有独无偶。李东山很善于钻营擘划,长于世故筹谋,时人称之为“李小鬼”。他有句自立的恒言:凡人有之我不干,人无有之我要为。这足以说明他经创事业的特点是,为了无与相争,独得其利,专事缺门,独资独营。
后来,由于德顺兴五金行经销日货马球牌座钟及其零件,引起李东山动意,认为造钟工业是我国的空缺,视为有利可图,于是就以德顺兴五金行为东本,出资办厂。
至于技术,适有一个叫唐志成的人可委其事。唐是掖县人,字逊三,读过私塾,曾在烟台为商户记过帐,因其好钻研小工匠技术,又自办过修理汽灯、钟表的营业,经常到德顺兴五金行购买修表零件结识了李东山。他俩均有创业之好,唐长于李处是略有一点文化知识和修理钟表的技艺。所以双方商定办厂造钟,便一拍即成。李东山自任经理,聘唐志成任厂长兼做技师。
宝时厂创办之初,技术设备十分简陋,曾经数年的筹备、摸索阶段。为了解决技术关,李东山不畏其难,数次亲赴日本大阪马球牌钟表厂观摩套取,并随购一部分机械设备。对于一些日人不肯吐露的重要技术,李东山常以重金送礼请吃贿买。这样由李东山外出学习购置,唐志成苦心孤诣、切磋琢磨钻研,终于在技术设备上草创基础。开厂伊始,仅有工人20多名,大小压力15台,两马力电滚1个,三尺车床1台,设备简陋。许多工序是手工操作,如齿轮是手工冲铣,直到1918年才增设了铣床。唐志成不会计算,主要模拟、拆卸日货马球牌座钟,进行试制。在试制期,为了维持生产收入,还兼制伞铤、汽灯、汽炉、门锁等产品出售。这时因见利甚微,原来恒兴德丝行投入的少量外股,遂中途抽去。历经数年反复试验仿制,第一批座钟终于在1918年制成问世。不过这时生产的钟,除木壳以外,主要零件和原料是从德国人在烟开设的盎斯洋行购进的日货,尚属装配制造阶段。1920年以后逐渐实现钟机自造。但主要原料如铜、铁板、钢丝、钟弦等,仍需从日本或德国进口。
随着钟表生产的进展,职工人数也由20多人增加到50多人,设备也逐步有所增添。但基本上仍以手工操作为主,年产仅一二千只,销路亦只在胶东和东北一带,故而发展较为缓慢。时至1930年,为逃避军阀政府按户头摊捐扩税,始将宝时造钟厂更名为德顺兴造钟厂,在名义上与德顺兴五金行合二为一。
二从1915年建厂到1931年这一阶段,德顺兴造钟厂的经营进程尚为顺利,生产亦确有气色。
除工厂自有一套节简管理的成规外,李东山还有一套笼络用人之法。他用人委事有一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要言。对管理人员的择用,只要能恪职尽责,便委任不疑,并按以后能力和表现,再在工资之外给予几成份子,以此赂取人心。实际任用的管理人员和负责要职的非亲即友。李东山名义是经理,参与实际领导管理的有5人,李殿章(李东山继子)代经理视事,唐志成(原与李有交)任厂长兼技师,戚汇川(李的亲家)任会计,谷钧昌(李的亲戚)负责对外业务联系,还有一名帮账会计。生产组织不设车间,只按工序分为压力、旋铜、旋铁、钻空、铣轮、铆轮、装配、镶钟、木壳、油漆、包装等作业班组,每组设一不脱产的组长。这些组长皆从工人中物色技术较高、顺从肯干者担任,负责组内日常生产、技术管理和产品质量检查等事宜,如有问题可直接请示经理或厂长解决。在每组的生产作业中特别强调节约原料,不出残次品,从基础生产杜绝浪费漏洞。根据当时核算,每生产一只钟的成本4元,卖出5元,能有25%的利润。
对工人的管理使用是严诱相加的。1928年在我入厂前一代工人,学徒期为10年,以后改为8年、6年、5年。严格规定,新徒工入厂至少需有一家商号作保立约,徒期只管伙食,没有工资。但也有例外。当时德顺兴的职工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李东山原籍威海亲友介绍的,一是恒兴德丝行介绍的,这些人进厂不需找保,也不用立约,来去自愿。我是恒兴德介绍去的。徒期5年,第一年发零用钱20吊,第二年30吊,第三年40吊,第四年50吊,第五年100吊(当时约二吊八换一元大洋)。如中途毁约不干,要按入厂时间长短退还伙食等费用。可见徒期之长,立约之严,实属苛厉剥削。所以有的工人忍受不了这种长徒期的无偿劳累,只得丢了行李逃跑了。
德顺兴其时还实行星期日公休制,名义上每星期日让工人休假,实际有半天叫工人清理工厂积存的废物垃圾。但这在当时的烟台各厂商中是唯一的。伙食也比较好,一般每日早馒头、午大米、晚玉米片片,逢年过节还增加酒菜会餐。可是每日的工作时间长达十二三个小时;天不亮就起来,一直干到天黑。对新工人入厂除了要立保外,在徒期死了不管,伤残不管,病了不管,即“三不管”。有的好不容易熬到满徒,竟又以生意不好等理由被解雇。工人干活、说话使资本家稍有不满,动辄就以下工要挟。现在有的老工人还记得,冬天包装屋里从不生炉子,为此几个工人凑了一首打油诗写在墙上:“此屋冷清清,滴水变成冰。工作不能作,炉子不让生。有心买衣服,家中还贫穷;有心要不买,冻的真苦情。”资本家发现后,大事追查,原是老工人陶尊堂写的,非要下他的工不可,经过许多人说情才算息事了。
在产品的经营上,德顺兴主要与日货马球牌钟进行市场竞争,一架座钟的卖价由5元大减至1元多,甚至每卖一架钟外赠毛巾一条。到1928年全国各地学生、工人爱国运动蓬起,出现了一个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新形势。这对民族工业德顺兴的发展是颇为有利的。再加德顺兴注重改进技术和精打细算,出厂的产品质量赶上日货,价格低于日货,并且讲究信誉,保修到底,所以它很快顶退日货,独占市场鳌头。转而价格迅速回升,每架钟提到五六元,销路顺利向东北、华北各大城市开拓,产品闯出声誉,哈尔滨裕昌表店专门经销德顺兴的“宝”字钟。从1928年到1931年间,德顺兴遂达鼎盛时期,共获利十余万元。1928年职工为100多人,迄于1931年最多发展到500余人,年产座钟、挂钟达5.5万多只,销路畅通,生意兴隆。
三但是好景不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已畅的钟表销路,遭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封锁破坏。刚刚开拓的北方市场日趋萎缩,致使产品滞销,积压5万多只,资金周转受限,企业经营困难。资本家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一方面不顾工人失业贫苦,裁减了200多人;另一方面又派出人员,到广州、汕头、上海,杭州、开封、郑州、武汉、重庆等中、南各大商埠,采取先货后款的赊销办法推销。1933年以后,南方市场开通,销路和经营又有了新的转机。当时德顺兴的钟表不但行销沪、宁、穗、渝等大城市,而且也销向香港和国外新加坡南洋群岛等地。在国内爱国斗争高涨的形势影响下,国外爱国华侨也积极相呼应,他们积极宣传购用、推销国货。时有新加坡华侨经办的华兴公司,对德顺兴的钟表自愿承担包销,向南洋群岛各地发售。每次发货后,把货单交中国银行付款划汇结算。1933年出口的钟表约有一万多只,销路开始扩大,产量恢复到年产量4.5万只左右。为了开展业务,在上海、天津等地设立货庄。
由于买卖亨通,销除积压,企业有了增值。自1934年到1935年间,先后投资兴建了新厂楼和包括新中国电影院一排楼房。为使牌名增色,特地花500元托人请书法家华世奎写了“德顺兴”3个颜体大字,镌刻在门楣石匾上。产品也有了改进和增新,仿照日本单铃、双铃两种闹钟,于1936年试制成功并正式投产。这在当时的中国也属首创。
“七七”抗战以后,华北市场全部滞塞。为了摆脱困境,资本家又采取解雇工人的办法,把在厂的职工削减到200多人。1937年的八九月间,国民党的烟台警察局长张奎文闻日帝入侵,首先逃跑,市内秩序骤乱,一部分散兵到德顺兴肆意开枪聚敛,把会计林××的腿打伤,抢了数百元而去。次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烟台。
早在日寇入侵前,烟台已有日人开办的岩城商会等,烟台沦陷之后他们摇身一变为佩刀挂衔的日本军官。这些日商实际是伪装的日特,他们在中国推销日货行商时,就注意搜集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对我国新生的钟表工业德顺兴造钟厂早已觊觎日久。烟台失陷后,日本侵略者就趁机要挟与德顺兴合股经营,阴谋攫为己有。
李东山曾经有言自约,决不与官家交往。起初伪商会要给他一个席位,他坚决谢辞;日本侵略者提出与他合营,又被他婉言谢绝。于是,一场大祸就势所难免了。
日伪以李东山曾经开过花炮厂,所用原料硝磺是经国民党政府的硝磺局批准进货的,日寇硬说他搞硝磺是私通八路军抗日,即把李殿章抓到宪兵队,严刑拷打,羁押数月。后经托人找到政记公司的经理张本政花钱贿赂宪兵队,才得获释。张本政又出主意,从中撮合,终于使李东山就范,与日本人共同开设了一个华兴商行。经营纸张、玉米、杂货等。名义上是合开,实际日本人并未出资,只是设一个空名,李东山虚与委蛇罢了。日本人借此巧取营利,进行公开敲诈,而德顺兴也只得与日本侵略者敷衍。
1939年德商盎斯洋行撤走,德顺兴赖以生产需要的原料从而短缺,产品销路再陷滞塞,许多厂家相继纷纷告歇。为了使企业勉强存立延活,德顺兴把过去积存的下脚铜料,送到化铜厂重新加工成铜板,到天津购进一部分钟弦,左右支绌地维持开工。而钟表销路唯有北京、天津一带,且物价上涨,货币贬值,职工生产没有保障,工人纷纷离厂自谋生计,工厂资金十分拮据,生产基本停顿。1939年末,回厂工人仅有120多人,不及原来职工人数的1/3。维持到1944年,首先由德顺兴五金行的职工提出,把企业的积累按人析分。以当时的通货膨胀的现价扣除原股金6万元,其余均被职工按份分掉了。结果资本家李东山遂将德顺兴五金行关闭报歇。接着德顺兴造钟厂也照此提出析分,因无现金,吃份子的西股职工分了450打钟,约值25万元。此后,李东山取消份子,工厂靠只卖不买来残延苟活。同时对工厂的人事也作了更动,经理由李东山的继子李殿章接任,厂长改由唐志成之子唐绍祥担任,唐志成退居为顾问。其时的德顺兴造钟厂只不过徒有虚名,实已无所生产,处在山穷水尽中挨时度日。
1945年8月24日,烟台首次解放,德顺兴造钟厂幸逢新生。解放初期,有些人想按土改分田的做法去分资本家的厂商。如李东山原籍的来人、街道和厂里的一些人都要分掉德顺兴的设备财产,由于市委正确贯彻执行了党关于城市民族工商业政策,按照实际情况,作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制止了分厂,把德顺兴保存下来,并大力支持其迅速恢复生产。当时烟台总工会主席路唐克同志现在回忆起这个问题,颇有感触地认为,“那时烟台是全国最早解放的沿海城市,我们坚持执行了党的政策,保护了民族工商业,维护广大职工的长远利益,创立了工作经验,对以后解放其他城市工作都有重要意义。”据我所知,李东山为此也很感激人民政府,解除了一些顾虑。
我当时是老职员、主管会计,李东山即特别交待于我:凡人民政府需要用着咱的事,你只管办不用再商议我。以后,市委生产组和公安局到厂里来联系代为往青岛发运钟货,公安局的修械所需要些人力物力支援,我就主持给办了。1946年春,公安局张子江来厂联系代给青岛庄发货,以便为政府买些物资拉回。我给他打配一马车货,开了厂里的介绍信,派李东山之子李继民等两名职工陪同,都作为本厂职工派去青岛。事后我才知道是张子江以此掩护去青岛作敌工。据说在青岛被敌发觉,敲了德顺兴30两金子;李殿章伯父的外甥女(系中学生)被国民党青岛警察分局局长孙聚一强娶为妾才算了事。
经理李殿章、厂长唐绍祥和唐志成等主要人员这时先后去了上海、青岛,李东山年老有病不能出来视事,厂里几乎无人领导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一区区长王琦(原名姜丕忍,后调市公安局任行政秘书)是我本家叔父,他找着我说:“政府要发展生产,经理厂长都走了,你得领头干。”我说我不能干。他进一步给指明:“咱们不干谁干?厂里有那么多人还要吃饭。你是老职员,情况熟,领着发展生产政府是支持的。”以后由王琦的介绍,市委书记滕景禄也表示支持我干,市委统战部领导林一夫、市总工会负责人路唐克亲自到厂鼓励我把生产搞起来。
我接手主持生产,首先买了一台柴油机发电,安置开工生产(因解放初期电力供应不上);另一方面,为了解决资金和原料问题,请示所属五区钟立山区长同意,由我随带十几打钟,乘风船到蒋统区天津推销和采购生产原料。我在天津把货卖出后,先发回一批原料,不幸回船在长岛一带遭到大风,全船人货沉没遇难。接着我又发回第二批原料,生产开始陆续恢复。
1947年春,我由津去沪,找李殿章、唐志成等人回烟,共同把厂里生产搞起来,结果未成。只有李殿章的几个亲属女眷与我同搭救济总署的船,于3月份返烟。《大众报》为我从沪回烟,对生产将作长远打算还作过报道。回烟听说,李东山于1946年10月死去,政府工商登记时,由李的亲家戚汇川做主把我注名为经理。我找市委书记滕景禄要求:“这个经理我不能干,我不是资本家。”滕答复我说:“你怕什么?你当经理是为了领导生产,谁要说什么你告诉他们是我叫你干的。”以后我又找他,他说:“我,你还不相信吗?你只管大胆干。如果工人中有什么问题,你就去找专管工会的路唐克同志。资金有困难,政府帮你解决。”市委还派区委书记孙良朋到厂协助领导恢复生产。这样,资金有困难我到政府去贷款,每次二三千元,随用随借,货销即还。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仅存一息的德顺兴,几度春秋,终于保全下来。
但是1947年的10月,厄运又至,国民党反动派侵占了烟台,烟台的民族工商业再次遭劫。在国民党侵占烟台不久的一天,有个姓曲的妇女来厂秘密交给我一封信,是我们撤出烟台的总工会领导路唐克、辛广义同志写的,主要嘱我一定把厂子和工人维护好。这是党和政府对民族工业的深切关怀,也是对我的莫大信任,我决不能辜负党和政府的重托。因此,当东家李殿章等人从上海回烟想把厂里机器设备卖掉时,我找他们在烟居住的眷属,说明如果卖掉机器,厂子告歇,她们的生活将无着落。李的眷属一听很着急,一齐去苦谏阻拦,终未卖成。
幸存的德顺兴另一方面的最大困难是,原材料非常匮乏,销路不畅;国民党的黑暗统治通货膨胀,捐税繁重,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社会购买力低下,产销异常困难,资金周转不灵,企业处于危机。更加不堪忍受的是国民党任意敲诈,寻衅勒索。有一次国民党刑警队到厂把工人许增文抓去,指控通敌,藉以敲诈,经多方托人说情始才放出。还有一名工人被抓兵,我亲去交涉花了100块银元才把人要回来。为了逃避国民党按户籍点名抓兵派差,厂里的青壮年职工多不敢报户口。像这样荒乱世势,哪有心思和能力去搞什么工业。
四
20世纪初叶,德顺兴造钟厂的创立是我国民族钟表工业之首,当年实在堪称“中国钟表第一家”。它对我国钟表工业的发起和钟表技术的传播是起过重要作用的。到1927年,从德顺兴分离出一部人员,另行独立组建了烟台第二家造钟厂——永康无限公司(后更名为新德造钟厂)。这个公司的正副经理牟成书、牟法典,厂长李吉田等20多人都是从德顺兴造钟厂和德顺兴五金行分离出来的骨干,地址在朝阳街的前首。起初,它名义上号称无限公司,实际仅具有限股金3.6万两白银,其中烟台义昌铁行投股较多。开始职工只有40余人,鼎盛时职工人数增加到300多人;产品以座挂钟为主,商标牌名“永”字。最高年产量为5万多只,行销青岛、济南、厦门、汕头等地。为了与德顺兴竞争,从外抽调它的技术力量和争夺销售市场;而德顺兴则采取折本多销的办法与永康对抗,每只座钟的成本4元,以3.8元向外抛售。结果两败俱伤,但都没有顶垮。1928年罢休修好,双方议定价格统一,每只座钟标价6元销售。此后有4年之久产销畅兴,生意旺盛,都得到了较好的利润。不过双方在经营上犄角暗斗一直未止。
接踵永康之后于1929年,在烟台罗锅桥西又新开了第三家造钟厂——盛利(后改名为胜利)造钟厂。开办人是在朝阳街经营修表店的李汉臣,由原在德顺兴的学徒工陈学元出来担任厂长兼技师。开业初期仅有职工15人,随着企业的发展,于1936年职工人数最多增至近百人。但由于技术力量较差,产品质量一直低下,在市场上总不占要位。继之于1931年又新办一家永业造钟厂,地址在烟台海防营。东家是在烟台太平街北首开饭馆的李永吉,独资5万元;经理赵公敏,技师陈岐鸣,职工100多人,经营力量和规模都不大。1932年开始出产成品,商标牌名为“业”字。最盛时为1933年,职工人数增到270多人,年产座挂钟1.7万多只。后来陈岐鸣从永业厂里出来又开办了岐鸣造钟厂。红卍字会主持办了一个慈业(后改名为红业)造钟厂。总之,到了30年代,在烟台相继创办的造钟厂多至六七家,钟表工人共有1000余人,年产座挂钟16万多只,产品在国内外市场都创出了一定的声誉。
其时的烟台造钟厂是数家并存,已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钟表工业阵容。1933年是解放前烟台钟表工业发展的鼎盛时期。1937年永业造钟厂技师鲁宣民、鞠维祯等人首次试制成功了柔丝挂钟,为我国生产柔丝钟的创始。鲁宣民原是德顺兴造钟厂的技术工人,解放后成为烟台钟表工程师。
此外,从德顺兴分离出去的还有:1932年十几名技工去天津兴办了北洋造钟厂;在沈阳开办了新明造钟厂;在丹东开办了大陆造钟厂。1941年,德顺兴的会计陈玉五又去天津开办了华威造钟厂。后来又去人在青岛开办了一个福祥造钟厂。早在1936年从烟台德顺兴去人到上海开办了忠众造钟厂;1946年又有德顺兴创业技师唐志成、唐绍祥父子等人去上海兴办了时民造钟厂。
以上开办的各个造钟厂的技术力量,几乎都是出自德顺兴造钟厂。解放后担任上海钟表工业公司总工程师张民生、陶尊堂也是来自烟台的德顺兴。
从德顺兴起始,到烟台的钟表工业繁衍形成,并推广到南北其他大城市,确为我国的钟表工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它的发展历程是非常艰难崎岖的。由于频年战乱,地区分割,人民生活无着,钟表工业产销困难,最后烟台的几家造钟厂,有的告歇,有的改产,钟表工人大量失业转业。如胜利、永业等厂都曾改产手推车零件等其他产品维持经营。到1948年烟台第二次解放前夕,全市的造钟厂名为3家,实际仅存德顺兴一家,职工不足百人,年产几千只,钟表工业几临于殁。
五烟台第二次解放初期,由于国民党的统治破坏,遗下一个百业调蔽的残迹,作为受害较重的钟表工业元气大伤,原料和销路仍都成为问题。历史最久的德顺兴只剩下不足百人,因经营不支只得停工两个月。后来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植下,与其他几家一度停业的造钟厂重新复工开业。
1949年春,德顺兴造钟厂为改进产品,特请鲁宣民到厂设计制造柔丝钟。在恢复生产的基础上,很快有了新的生机。1949年烟台各家造钟厂(以德顺兴为主)生产出木钟480多只,闹钟3000多只,产值达到18万余元,钟表工人数恢复到百人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开展销路,我亲自带着柔丝钟新产品到天津推销。在人民政府发展生产的号召下,再加德顺兴一向有信誉,可行先订货付款后发货,以销定产开展经营。因此,资金周转加快,仅有3次,工厂生产就明显地活起来了。到1950年,德顺兴纯收益达3万多元。从此,延蔫将萎的钟表之花又复苏茂发,销路开通,由滞变畅。在3年恢复时期末的1952年,烟台钟表工业产量共有2.3万多只,比1949年提高了6.3倍,产值达到44万多元,比1949年提高了1.3倍多。
1956年秋,德顺兴、新德、永业3家造钟厂实现了全行业合营,成立了综合性的烟台造钟厂。
(本文由张河清整理,烟台市政协供稿)
一德顺兴的原名叫宝时造钟厂,创办于1915年7月。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次年,英、法、德、意、俄等帝国主义正忙于争夺世界霸权的侵略战争,无暇东顾,我国民族工业稍得长足发展之隙。际此时机,李东山出资,在烟台朝阳街南段东侧创办了一个造钟厂,注册登记为“宝时造钟厂”,商标“宝”字,资金2.5万元。
李东山本名叫李树桐,字东山,原籍威海市人,约生于清季光绪初年,死于1946年10月。此人自幼家道贫穷,不曾入学读书,早年以肩挑小贩为生。他的发迹与烟台当时富商恒兴德丝行是有干系的。最初他独身来烟,腰中仅有200铜钱,投靠他在恒兴德当上海客的堂兄,经堂兄保荐在恒兴德当了一名小伙计。由于他生就乖俐,善于逢迎巴结,不久拜认恒兴德的东家孙文山为干爹。以后他受不了行规约束,自愿退出,仍去从事小贩生涯。在贩卖的市利中,逐渐积起一点资本,就在北大街与太平街南首交会处,开了一个水炉小铺,同时又兼去海关叫行,资本不够向他干爹孙文山告贷。据轶闻,他在叫行买进海关拍卖没收的私货禁物中,发了一笔意外的奇财,于是突为显富而闻。另一说他倒卖了一批船粮,因粮价上涨而得了一笔厚利。总之,他对自己的突富之道一向缄口不宣,讳莫如深,同他共事的人惟感突兀,不解其奥。不过,李东山已握重资确是实事。
俗云,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李东山在握有资本以后,于1892年首先就在他开水炉小铺地址,扩办一爿德顺兴五金行,资本为墨(墨西哥)币300元,至1904年,资本扩大为3万元墨币,主要经营小五金和兼营百货商品。这个五金行成了李东山创办其他事业的本源,也是开办德顺兴造钟厂的母本公司。继之,在烟开办了同志玻璃厂、瑞兴制伞厂,在威海开办了威新花炮厂(后迁烟)、同庆顺镶锡店。以上厂商,在当时的烟威一带均为首创,有独无偶。李东山很善于钻营擘划,长于世故筹谋,时人称之为“李小鬼”。他有句自立的恒言:凡人有之我不干,人无有之我要为。这足以说明他经创事业的特点是,为了无与相争,独得其利,专事缺门,独资独营。
后来,由于德顺兴五金行经销日货马球牌座钟及其零件,引起李东山动意,认为造钟工业是我国的空缺,视为有利可图,于是就以德顺兴五金行为东本,出资办厂。
至于技术,适有一个叫唐志成的人可委其事。唐是掖县人,字逊三,读过私塾,曾在烟台为商户记过帐,因其好钻研小工匠技术,又自办过修理汽灯、钟表的营业,经常到德顺兴五金行购买修表零件结识了李东山。他俩均有创业之好,唐长于李处是略有一点文化知识和修理钟表的技艺。所以双方商定办厂造钟,便一拍即成。李东山自任经理,聘唐志成任厂长兼做技师。
宝时厂创办之初,技术设备十分简陋,曾经数年的筹备、摸索阶段。为了解决技术关,李东山不畏其难,数次亲赴日本大阪马球牌钟表厂观摩套取,并随购一部分机械设备。对于一些日人不肯吐露的重要技术,李东山常以重金送礼请吃贿买。这样由李东山外出学习购置,唐志成苦心孤诣、切磋琢磨钻研,终于在技术设备上草创基础。开厂伊始,仅有工人20多名,大小压力15台,两马力电滚1个,三尺车床1台,设备简陋。许多工序是手工操作,如齿轮是手工冲铣,直到1918年才增设了铣床。唐志成不会计算,主要模拟、拆卸日货马球牌座钟,进行试制。在试制期,为了维持生产收入,还兼制伞铤、汽灯、汽炉、门锁等产品出售。这时因见利甚微,原来恒兴德丝行投入的少量外股,遂中途抽去。历经数年反复试验仿制,第一批座钟终于在1918年制成问世。不过这时生产的钟,除木壳以外,主要零件和原料是从德国人在烟开设的盎斯洋行购进的日货,尚属装配制造阶段。1920年以后逐渐实现钟机自造。但主要原料如铜、铁板、钢丝、钟弦等,仍需从日本或德国进口。
随着钟表生产的进展,职工人数也由20多人增加到50多人,设备也逐步有所增添。但基本上仍以手工操作为主,年产仅一二千只,销路亦只在胶东和东北一带,故而发展较为缓慢。时至1930年,为逃避军阀政府按户头摊捐扩税,始将宝时造钟厂更名为德顺兴造钟厂,在名义上与德顺兴五金行合二为一。
二从1915年建厂到1931年这一阶段,德顺兴造钟厂的经营进程尚为顺利,生产亦确有气色。
除工厂自有一套节简管理的成规外,李东山还有一套笼络用人之法。他用人委事有一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要言。对管理人员的择用,只要能恪职尽责,便委任不疑,并按以后能力和表现,再在工资之外给予几成份子,以此赂取人心。实际任用的管理人员和负责要职的非亲即友。李东山名义是经理,参与实际领导管理的有5人,李殿章(李东山继子)代经理视事,唐志成(原与李有交)任厂长兼技师,戚汇川(李的亲家)任会计,谷钧昌(李的亲戚)负责对外业务联系,还有一名帮账会计。生产组织不设车间,只按工序分为压力、旋铜、旋铁、钻空、铣轮、铆轮、装配、镶钟、木壳、油漆、包装等作业班组,每组设一不脱产的组长。这些组长皆从工人中物色技术较高、顺从肯干者担任,负责组内日常生产、技术管理和产品质量检查等事宜,如有问题可直接请示经理或厂长解决。在每组的生产作业中特别强调节约原料,不出残次品,从基础生产杜绝浪费漏洞。根据当时核算,每生产一只钟的成本4元,卖出5元,能有25%的利润。
对工人的管理使用是严诱相加的。1928年在我入厂前一代工人,学徒期为10年,以后改为8年、6年、5年。严格规定,新徒工入厂至少需有一家商号作保立约,徒期只管伙食,没有工资。但也有例外。当时德顺兴的职工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李东山原籍威海亲友介绍的,一是恒兴德丝行介绍的,这些人进厂不需找保,也不用立约,来去自愿。我是恒兴德介绍去的。徒期5年,第一年发零用钱20吊,第二年30吊,第三年40吊,第四年50吊,第五年100吊(当时约二吊八换一元大洋)。如中途毁约不干,要按入厂时间长短退还伙食等费用。可见徒期之长,立约之严,实属苛厉剥削。所以有的工人忍受不了这种长徒期的无偿劳累,只得丢了行李逃跑了。
德顺兴其时还实行星期日公休制,名义上每星期日让工人休假,实际有半天叫工人清理工厂积存的废物垃圾。但这在当时的烟台各厂商中是唯一的。伙食也比较好,一般每日早馒头、午大米、晚玉米片片,逢年过节还增加酒菜会餐。可是每日的工作时间长达十二三个小时;天不亮就起来,一直干到天黑。对新工人入厂除了要立保外,在徒期死了不管,伤残不管,病了不管,即“三不管”。有的好不容易熬到满徒,竟又以生意不好等理由被解雇。工人干活、说话使资本家稍有不满,动辄就以下工要挟。现在有的老工人还记得,冬天包装屋里从不生炉子,为此几个工人凑了一首打油诗写在墙上:“此屋冷清清,滴水变成冰。工作不能作,炉子不让生。有心买衣服,家中还贫穷;有心要不买,冻的真苦情。”资本家发现后,大事追查,原是老工人陶尊堂写的,非要下他的工不可,经过许多人说情才算息事了。
在产品的经营上,德顺兴主要与日货马球牌钟进行市场竞争,一架座钟的卖价由5元大减至1元多,甚至每卖一架钟外赠毛巾一条。到1928年全国各地学生、工人爱国运动蓬起,出现了一个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新形势。这对民族工业德顺兴的发展是颇为有利的。再加德顺兴注重改进技术和精打细算,出厂的产品质量赶上日货,价格低于日货,并且讲究信誉,保修到底,所以它很快顶退日货,独占市场鳌头。转而价格迅速回升,每架钟提到五六元,销路顺利向东北、华北各大城市开拓,产品闯出声誉,哈尔滨裕昌表店专门经销德顺兴的“宝”字钟。从1928年到1931年间,德顺兴遂达鼎盛时期,共获利十余万元。1928年职工为100多人,迄于1931年最多发展到500余人,年产座钟、挂钟达5.5万多只,销路畅通,生意兴隆。
三但是好景不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已畅的钟表销路,遭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封锁破坏。刚刚开拓的北方市场日趋萎缩,致使产品滞销,积压5万多只,资金周转受限,企业经营困难。资本家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一方面不顾工人失业贫苦,裁减了200多人;另一方面又派出人员,到广州、汕头、上海,杭州、开封、郑州、武汉、重庆等中、南各大商埠,采取先货后款的赊销办法推销。1933年以后,南方市场开通,销路和经营又有了新的转机。当时德顺兴的钟表不但行销沪、宁、穗、渝等大城市,而且也销向香港和国外新加坡南洋群岛等地。在国内爱国斗争高涨的形势影响下,国外爱国华侨也积极相呼应,他们积极宣传购用、推销国货。时有新加坡华侨经办的华兴公司,对德顺兴的钟表自愿承担包销,向南洋群岛各地发售。每次发货后,把货单交中国银行付款划汇结算。1933年出口的钟表约有一万多只,销路开始扩大,产量恢复到年产量4.5万只左右。为了开展业务,在上海、天津等地设立货庄。
由于买卖亨通,销除积压,企业有了增值。自1934年到1935年间,先后投资兴建了新厂楼和包括新中国电影院一排楼房。为使牌名增色,特地花500元托人请书法家华世奎写了“德顺兴”3个颜体大字,镌刻在门楣石匾上。产品也有了改进和增新,仿照日本单铃、双铃两种闹钟,于1936年试制成功并正式投产。这在当时的中国也属首创。
“七七”抗战以后,华北市场全部滞塞。为了摆脱困境,资本家又采取解雇工人的办法,把在厂的职工削减到200多人。1937年的八九月间,国民党的烟台警察局长张奎文闻日帝入侵,首先逃跑,市内秩序骤乱,一部分散兵到德顺兴肆意开枪聚敛,把会计林××的腿打伤,抢了数百元而去。次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烟台。
早在日寇入侵前,烟台已有日人开办的岩城商会等,烟台沦陷之后他们摇身一变为佩刀挂衔的日本军官。这些日商实际是伪装的日特,他们在中国推销日货行商时,就注意搜集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对我国新生的钟表工业德顺兴造钟厂早已觊觎日久。烟台失陷后,日本侵略者就趁机要挟与德顺兴合股经营,阴谋攫为己有。
李东山曾经有言自约,决不与官家交往。起初伪商会要给他一个席位,他坚决谢辞;日本侵略者提出与他合营,又被他婉言谢绝。于是,一场大祸就势所难免了。
日伪以李东山曾经开过花炮厂,所用原料硝磺是经国民党政府的硝磺局批准进货的,日寇硬说他搞硝磺是私通八路军抗日,即把李殿章抓到宪兵队,严刑拷打,羁押数月。后经托人找到政记公司的经理张本政花钱贿赂宪兵队,才得获释。张本政又出主意,从中撮合,终于使李东山就范,与日本人共同开设了一个华兴商行。经营纸张、玉米、杂货等。名义上是合开,实际日本人并未出资,只是设一个空名,李东山虚与委蛇罢了。日本人借此巧取营利,进行公开敲诈,而德顺兴也只得与日本侵略者敷衍。
1939年德商盎斯洋行撤走,德顺兴赖以生产需要的原料从而短缺,产品销路再陷滞塞,许多厂家相继纷纷告歇。为了使企业勉强存立延活,德顺兴把过去积存的下脚铜料,送到化铜厂重新加工成铜板,到天津购进一部分钟弦,左右支绌地维持开工。而钟表销路唯有北京、天津一带,且物价上涨,货币贬值,职工生产没有保障,工人纷纷离厂自谋生计,工厂资金十分拮据,生产基本停顿。1939年末,回厂工人仅有120多人,不及原来职工人数的1/3。维持到1944年,首先由德顺兴五金行的职工提出,把企业的积累按人析分。以当时的通货膨胀的现价扣除原股金6万元,其余均被职工按份分掉了。结果资本家李东山遂将德顺兴五金行关闭报歇。接着德顺兴造钟厂也照此提出析分,因无现金,吃份子的西股职工分了450打钟,约值25万元。此后,李东山取消份子,工厂靠只卖不买来残延苟活。同时对工厂的人事也作了更动,经理由李东山的继子李殿章接任,厂长改由唐志成之子唐绍祥担任,唐志成退居为顾问。其时的德顺兴造钟厂只不过徒有虚名,实已无所生产,处在山穷水尽中挨时度日。
1945年8月24日,烟台首次解放,德顺兴造钟厂幸逢新生。解放初期,有些人想按土改分田的做法去分资本家的厂商。如李东山原籍的来人、街道和厂里的一些人都要分掉德顺兴的设备财产,由于市委正确贯彻执行了党关于城市民族工商业政策,按照实际情况,作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制止了分厂,把德顺兴保存下来,并大力支持其迅速恢复生产。当时烟台总工会主席路唐克同志现在回忆起这个问题,颇有感触地认为,“那时烟台是全国最早解放的沿海城市,我们坚持执行了党的政策,保护了民族工商业,维护广大职工的长远利益,创立了工作经验,对以后解放其他城市工作都有重要意义。”据我所知,李东山为此也很感激人民政府,解除了一些顾虑。
我当时是老职员、主管会计,李东山即特别交待于我:凡人民政府需要用着咱的事,你只管办不用再商议我。以后,市委生产组和公安局到厂里来联系代为往青岛发运钟货,公安局的修械所需要些人力物力支援,我就主持给办了。1946年春,公安局张子江来厂联系代给青岛庄发货,以便为政府买些物资拉回。我给他打配一马车货,开了厂里的介绍信,派李东山之子李继民等两名职工陪同,都作为本厂职工派去青岛。事后我才知道是张子江以此掩护去青岛作敌工。据说在青岛被敌发觉,敲了德顺兴30两金子;李殿章伯父的外甥女(系中学生)被国民党青岛警察分局局长孙聚一强娶为妾才算了事。
经理李殿章、厂长唐绍祥和唐志成等主要人员这时先后去了上海、青岛,李东山年老有病不能出来视事,厂里几乎无人领导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一区区长王琦(原名姜丕忍,后调市公安局任行政秘书)是我本家叔父,他找着我说:“政府要发展生产,经理厂长都走了,你得领头干。”我说我不能干。他进一步给指明:“咱们不干谁干?厂里有那么多人还要吃饭。你是老职员,情况熟,领着发展生产政府是支持的。”以后由王琦的介绍,市委书记滕景禄也表示支持我干,市委统战部领导林一夫、市总工会负责人路唐克亲自到厂鼓励我把生产搞起来。
我接手主持生产,首先买了一台柴油机发电,安置开工生产(因解放初期电力供应不上);另一方面,为了解决资金和原料问题,请示所属五区钟立山区长同意,由我随带十几打钟,乘风船到蒋统区天津推销和采购生产原料。我在天津把货卖出后,先发回一批原料,不幸回船在长岛一带遭到大风,全船人货沉没遇难。接着我又发回第二批原料,生产开始陆续恢复。
1947年春,我由津去沪,找李殿章、唐志成等人回烟,共同把厂里生产搞起来,结果未成。只有李殿章的几个亲属女眷与我同搭救济总署的船,于3月份返烟。《大众报》为我从沪回烟,对生产将作长远打算还作过报道。回烟听说,李东山于1946年10月死去,政府工商登记时,由李的亲家戚汇川做主把我注名为经理。我找市委书记滕景禄要求:“这个经理我不能干,我不是资本家。”滕答复我说:“你怕什么?你当经理是为了领导生产,谁要说什么你告诉他们是我叫你干的。”以后我又找他,他说:“我,你还不相信吗?你只管大胆干。如果工人中有什么问题,你就去找专管工会的路唐克同志。资金有困难,政府帮你解决。”市委还派区委书记孙良朋到厂协助领导恢复生产。这样,资金有困难我到政府去贷款,每次二三千元,随用随借,货销即还。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仅存一息的德顺兴,几度春秋,终于保全下来。
但是1947年的10月,厄运又至,国民党反动派侵占了烟台,烟台的民族工商业再次遭劫。在国民党侵占烟台不久的一天,有个姓曲的妇女来厂秘密交给我一封信,是我们撤出烟台的总工会领导路唐克、辛广义同志写的,主要嘱我一定把厂子和工人维护好。这是党和政府对民族工业的深切关怀,也是对我的莫大信任,我决不能辜负党和政府的重托。因此,当东家李殿章等人从上海回烟想把厂里机器设备卖掉时,我找他们在烟居住的眷属,说明如果卖掉机器,厂子告歇,她们的生活将无着落。李的眷属一听很着急,一齐去苦谏阻拦,终未卖成。
幸存的德顺兴另一方面的最大困难是,原材料非常匮乏,销路不畅;国民党的黑暗统治通货膨胀,捐税繁重,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社会购买力低下,产销异常困难,资金周转不灵,企业处于危机。更加不堪忍受的是国民党任意敲诈,寻衅勒索。有一次国民党刑警队到厂把工人许增文抓去,指控通敌,藉以敲诈,经多方托人说情始才放出。还有一名工人被抓兵,我亲去交涉花了100块银元才把人要回来。为了逃避国民党按户籍点名抓兵派差,厂里的青壮年职工多不敢报户口。像这样荒乱世势,哪有心思和能力去搞什么工业。
四
20世纪初叶,德顺兴造钟厂的创立是我国民族钟表工业之首,当年实在堪称“中国钟表第一家”。它对我国钟表工业的发起和钟表技术的传播是起过重要作用的。到1927年,从德顺兴分离出一部人员,另行独立组建了烟台第二家造钟厂——永康无限公司(后更名为新德造钟厂)。这个公司的正副经理牟成书、牟法典,厂长李吉田等20多人都是从德顺兴造钟厂和德顺兴五金行分离出来的骨干,地址在朝阳街的前首。起初,它名义上号称无限公司,实际仅具有限股金3.6万两白银,其中烟台义昌铁行投股较多。开始职工只有40余人,鼎盛时职工人数增加到300多人;产品以座挂钟为主,商标牌名“永”字。最高年产量为5万多只,行销青岛、济南、厦门、汕头等地。为了与德顺兴竞争,从外抽调它的技术力量和争夺销售市场;而德顺兴则采取折本多销的办法与永康对抗,每只座钟的成本4元,以3.8元向外抛售。结果两败俱伤,但都没有顶垮。1928年罢休修好,双方议定价格统一,每只座钟标价6元销售。此后有4年之久产销畅兴,生意旺盛,都得到了较好的利润。不过双方在经营上犄角暗斗一直未止。
接踵永康之后于1929年,在烟台罗锅桥西又新开了第三家造钟厂——盛利(后改名为胜利)造钟厂。开办人是在朝阳街经营修表店的李汉臣,由原在德顺兴的学徒工陈学元出来担任厂长兼技师。开业初期仅有职工15人,随着企业的发展,于1936年职工人数最多增至近百人。但由于技术力量较差,产品质量一直低下,在市场上总不占要位。继之于1931年又新办一家永业造钟厂,地址在烟台海防营。东家是在烟台太平街北首开饭馆的李永吉,独资5万元;经理赵公敏,技师陈岐鸣,职工100多人,经营力量和规模都不大。1932年开始出产成品,商标牌名为“业”字。最盛时为1933年,职工人数增到270多人,年产座挂钟1.7万多只。后来陈岐鸣从永业厂里出来又开办了岐鸣造钟厂。红卍字会主持办了一个慈业(后改名为红业)造钟厂。总之,到了30年代,在烟台相继创办的造钟厂多至六七家,钟表工人共有1000余人,年产座挂钟16万多只,产品在国内外市场都创出了一定的声誉。
其时的烟台造钟厂是数家并存,已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钟表工业阵容。1933年是解放前烟台钟表工业发展的鼎盛时期。1937年永业造钟厂技师鲁宣民、鞠维祯等人首次试制成功了柔丝挂钟,为我国生产柔丝钟的创始。鲁宣民原是德顺兴造钟厂的技术工人,解放后成为烟台钟表工程师。
此外,从德顺兴分离出去的还有:1932年十几名技工去天津兴办了北洋造钟厂;在沈阳开办了新明造钟厂;在丹东开办了大陆造钟厂。1941年,德顺兴的会计陈玉五又去天津开办了华威造钟厂。后来又去人在青岛开办了一个福祥造钟厂。早在1936年从烟台德顺兴去人到上海开办了忠众造钟厂;1946年又有德顺兴创业技师唐志成、唐绍祥父子等人去上海兴办了时民造钟厂。
以上开办的各个造钟厂的技术力量,几乎都是出自德顺兴造钟厂。解放后担任上海钟表工业公司总工程师张民生、陶尊堂也是来自烟台的德顺兴。
从德顺兴起始,到烟台的钟表工业繁衍形成,并推广到南北其他大城市,确为我国的钟表工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它的发展历程是非常艰难崎岖的。由于频年战乱,地区分割,人民生活无着,钟表工业产销困难,最后烟台的几家造钟厂,有的告歇,有的改产,钟表工人大量失业转业。如胜利、永业等厂都曾改产手推车零件等其他产品维持经营。到1948年烟台第二次解放前夕,全市的造钟厂名为3家,实际仅存德顺兴一家,职工不足百人,年产几千只,钟表工业几临于殁。
五烟台第二次解放初期,由于国民党的统治破坏,遗下一个百业调蔽的残迹,作为受害较重的钟表工业元气大伤,原料和销路仍都成为问题。历史最久的德顺兴只剩下不足百人,因经营不支只得停工两个月。后来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植下,与其他几家一度停业的造钟厂重新复工开业。
1949年春,德顺兴造钟厂为改进产品,特请鲁宣民到厂设计制造柔丝钟。在恢复生产的基础上,很快有了新的生机。1949年烟台各家造钟厂(以德顺兴为主)生产出木钟480多只,闹钟3000多只,产值达到18万余元,钟表工人数恢复到百人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开展销路,我亲自带着柔丝钟新产品到天津推销。在人民政府发展生产的号召下,再加德顺兴一向有信誉,可行先订货付款后发货,以销定产开展经营。因此,资金周转加快,仅有3次,工厂生产就明显地活起来了。到1950年,德顺兴纯收益达3万多元。从此,延蔫将萎的钟表之花又复苏茂发,销路开通,由滞变畅。在3年恢复时期末的1952年,烟台钟表工业产量共有2.3万多只,比1949年提高了6.3倍,产值达到44万多元,比1949年提高了1.3倍多。
1956年秋,德顺兴、新德、永业3家造钟厂实现了全行业合营,成立了综合性的烟台造钟厂。
(本文由张河清整理,烟台市政协供稿)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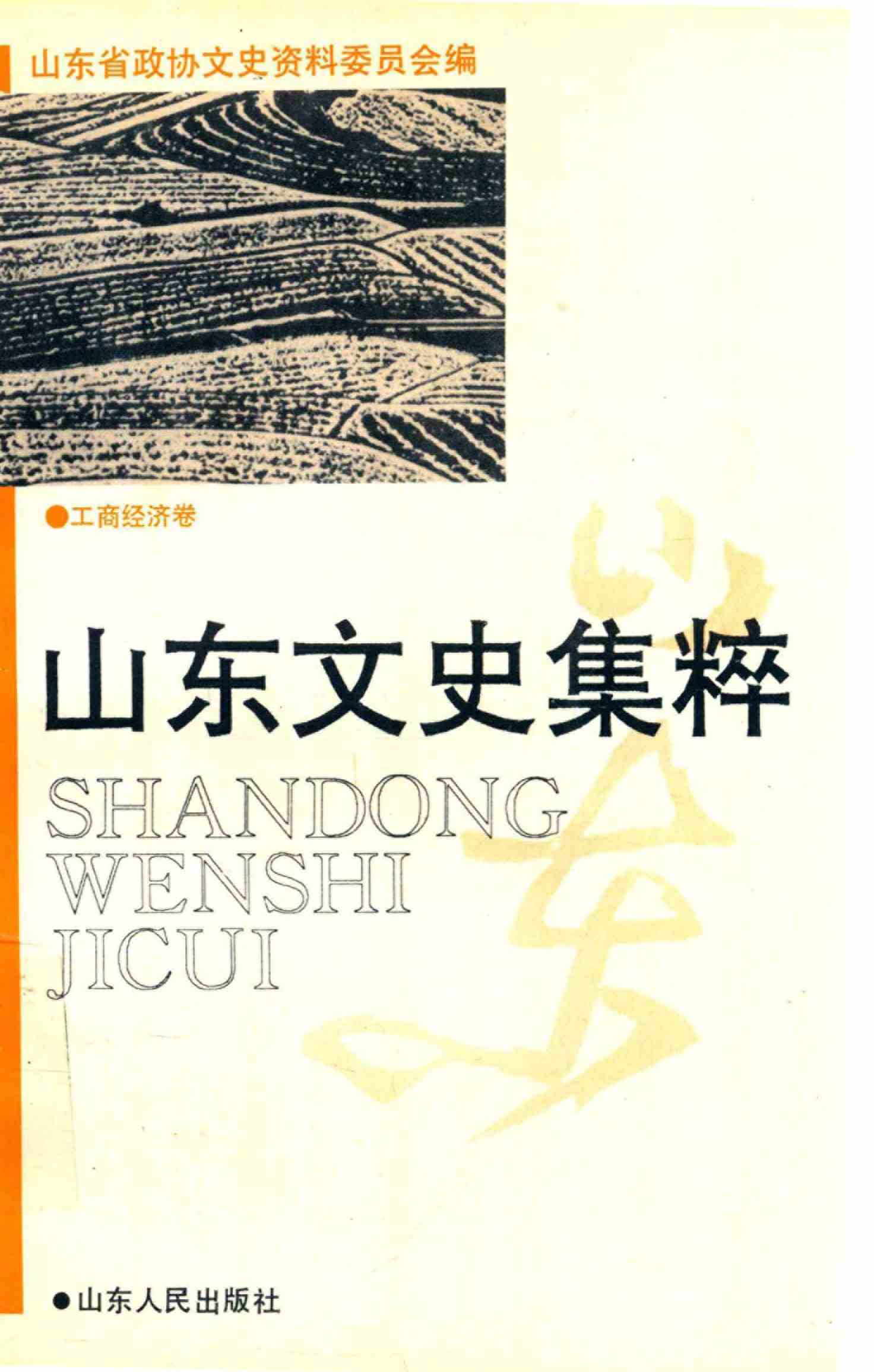
《山东文史集粹工商经济卷》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本书分为政治、军事、革命斗争、工商经济、科技、文化、教育、民族宗教、社会、风物10卷,全书以真实丰富的史料,朴实流畅的文风,重点反映了自戊戌变法至建国前半个多世纪中发生在山东省的重要史实。
阅读
相关地名
山东省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