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的回忆
| 内容出处: | 《山东文史资料选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50020020220000341 |
| 颗粒名称: | 我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的回忆 |
| 分类号: | K250.652 |
| 页数: | 18 |
| 页码: | 63-80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范予遂回忆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时的工作情况的具体内容介绍。 |
| 关键词: | 山东 国民党 委员 |
内容
一
一九四一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沈鸿烈离职,蒋介石委派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所属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继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但不兼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这是因为蒋介石对于学忠所统率的东北军不信任,认为有亲共之嫌,至少也是反共不卖力,故不能把这个专门反共的国民党省党部交给牟中珩。CC派的重要分子何思源,十几年来,一直任山东省教育厅长、民政厅长、鲁北行署主任,为蒋介石所信任,由他继任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本来是很合适的。但由于CC派头子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把持、操纵国民党多年,屡屡遭到国民党其他各派系的反对。在抗战期间,蒋介石为了缓和这种矛盾,就把组织部长CC派头子陈立夫调为教育部长,换上朱家骅。朱家骅本来也是以依附CC派起家的;但是他披着学术界的外衣,以区别于CC派。蒋介石派他作组织部长,对内换汤不换药,对外可以堵住反对者之口。朱家骅秉承蒋介石的意志,也是为了要制造自己的派系,他就不能用CC派分子何思源。
朱家骅为什么找到了我?根子还在蒋介石。一九三八年年底,汪精卫自重庆逃往越南的河内,蒋介石即分别召见了改组派的一些人谈话。十二月三十一日蒋召见了我和邓飞黄,蒋的谈话,主要是劝告我们不要跟汪精卫逃走,并叫我们写信劝汪不要投敌。我们明确表示了态度,坚决反对汪精卫投敌。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日,汪精卫自河内发的艳电和国民党中央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同时在报上发表。我根据这两个文件给汪写了一封信,交彭学沛转去。大意是:(1)绝对不能受日本首相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的欺骗;(2)迅即出国到欧洲去,免受敌人的笼络;(3)对中央给他的处分要以最大忍耐处之,不要同中央翻脸。我这种态度,使蒋相信我不会跟汪投敌。再则,自抗战以来,我在国民参政会的活动和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是始终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蒋也是很清楚的。以此,蒋介石相信,把我派出去,既不会依附汪精卫,也不会勾搭共产党。当朱家骅任组织部长不久,曾要派我作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被我坚决拒绝了。这与我当时对抗战胜利没有信心有关。这次我答应朱家骅回山东,是在珍珠港事件刚刚发生之后。珍珠港事件发生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我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式开始。这时,我国抗战的胜利不仅有希望,而且有把握了。十二月三十一日朱家骅派组织部主任秘书王启江征求我回山东作省党部主任委员的意见,在座的有邓飞黄。未待我说话,他先鼓动我接受这个职务,我也顿时生了政治野心,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朱家骅未待同我见面就签呈给蒋介石,不给我再考虑的机会。
我的政治野心是什么?它是怎么与我对抗战胜利的信心联系在一起的?有必要在这里作一扼要交代。
抗日战争发生之前,国民党的一些失意分子方振武、陈铭枢、黄少谷等都在英国伦敦。我与邓飞黄因汪精卫被刺离开南京,也到了伦敦。他们主张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抗日,把写好的电稿要我与邓飞黄签名,我拒绝签名。我坚持我的反动主张和他们争论。我认为中国不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或接近爆发而单独对日抗战,绝对没有胜利的可能。我说,单独抗战只有一件好处,就是可以削弱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发展民主力量,不过以战争失败为代价,换取民主力量的发展,是万万不可这样作的。后经邓飞黄对我再三劝说,我才签了名。这只是为了朋友的情面,并非我的主张有了改变。
芦沟桥一声炮响,我国对日抗战了,这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全国人民都起来抗战,我自己就不能躲在国外。即于十月间同邓飞黄一起回国参加了抗战。当时我的打算是:在抗战期间,不参加政府工作,不作政府官吏,只想钻进一个类似的民意机构,以便宣传自己对于抗战与民主两个问题的看法。恰好国民参政会成立,就作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除了在会内与进步力量争争吵吵之外,不时在国民党的各种报刊上发表主张。
对于抗战,在初期,总的说不是鼓气而是泄气。记得国民政府退守武汉的时候,我在报上发表的“国际的里面”一文中主张:两国交战,如果一国确信不能在战场上取胜,也不能在外交上取胜,则宁肯在战场上尚未决定胜负之前,承认外交的失败而讲和,比战败到作城下之盟总还好一些。这实际就是鼓吹对日求和投降了。一九三九年,英、法对德宣战,我的失败情绪开始有所转变,一九四一年纳粹德国进攻苏联,觉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越逼越近,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心又始终非常狠毒,中国也就只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日本帝国主义拚到底了。
关于民主政治,当时我坚信资产阶级议会民主那一套,更迷信英国费边社的所谓社会主义。就是说,我坚信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议会的多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我拥护国民党,但我憎恨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及其政府的极端贪污、腐化与无能。而要铲除国民党的这两大祸害,必须改造国民党,而改造国民党的唯一办法,是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宪政。我幻想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再没有理由不履行诺言,结束训政,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宪政。再没有理由不承认共产党这个政治力量,继续维持国共合作,再没有理由不通过政治协商办法解决两党之间的一切争端,而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一旦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国民党在新的政治力量帮助和监督之下,就不可能如从前那样乱搞独裁和贪污,民主政府必然从各方面进行改革,推动进步。这不仅不会削弱国民党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而且会加强这种地位,国民党仍将在很长时期内不失为第一大党的地位。
抗战胜利快要到来,取消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行宪政有了希望,我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久就要召开,我要在这次代表大会争取恢复作为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我是第四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五次被CC派搞掉)的地位,以便在国民党中央有发言权,而回山东作省党部主任委员,正是取得一个中央委员的有利条件。
我也考虑当时山东的军事情况,首先于学忠部受日寇“扫荡”的压力很大,但相信李仙洲的九十二军即将入鲁,它入鲁后即可改变这种情况。再则军政权已统一于苏鲁战区总司令部,于学忠、牟中珩非蒋家嫡系,只要我不同他们闹别扭,他们也不会干涉我的行动,我相信比较容易与他们相处。还有临时省参议会这个所谓民意机关,议长孔繁霨、秘书长王立哉等,也是可以和我合作的。更重要的是,李仙洲与改组派的一些人的关系比较要好,我到山东后,不仅可以得到他的支持,而且我相信可以对李仙洲与于学忠的合作关系起到积极作用。如能达到抗战胜利,这就是我回山东的一个大胜利。同时我也考虑,国民党省党部已成为一个专门反共的机关。在重庆还存在着国共合作关系,我在国民参政会内与进步力量的代表争争吵吵,或写点什么在报刊上发表出来,也只是动口不动手,若作了省党部主任委员,不是亲自动手来反共了吗?但是我又想,我既坚持资产阶级民主,实际就是积极反共,还有什么动口不动手的差别呢?因此,我就不顾一切地要回山东一行。
蒋介石批准我回山东后,就很快约我见了面,冠冕堂皇地说了几句,最重要的是今后有事叫我直接给他报告。临别,叫他的侍卫长林蔚交我一本密电码,要我有事随时拍电报告他。他还写了一张送我路费六千元的纸条给我。这是自汪精卫投敌以来,蒋有意拉拢我,我也有意靠近他的一个具体表现。
我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动身,先到安徽阜阳,住在九十二军司令部约两、三个月。默察九十二军的高级将领,都没有尽速入鲁援助于学忠部解除困境的打算,而李仙洲和汤恩伯之间也存在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对李仙洲入鲁极为不利(现据李仙洲说,当时汤恩伯不支持李仙洲入鲁,而想叫王仲廉代替他)。于学忠是否欢迎李仙洲入鲁?我还不很摸底,但从于学忠、李仙洲之间没有密切联系来看,觉得于学忠对这件事至少不是采取积极态度,而是颇为冷淡的。我还未待进入山东,困难问题就来了。如果九十二军进不了山东,而于学忠的军队又顶不住日寇的“扫荡”,不待敌人总投降就退出山东,那么,我来山东的目的,不就完全落空了吗?后退是不行了,只得进山东,从各方面设法,催九十二军入鲁。
怎样进山东?化装走。“良民证”用樊世昌为代名。省政府派一个职员叫祝廷林来引路。我们于一九四二年五月间自阜阳动身,从宿县乘火车到济南,换胶济路车到张店,再换火车到博山,然后由伪军护送到新四师吴化文的防区,再由吴化文派人送到省府所在地临朐辖境。省府住吕匣店子,省参议会住棘子山,省党部住青崖,三个村庄都相距不远。
一到鲁南山区,顿时感到兴奋愉快。自抗战以来,我一直紧跟着国民政府,由南京退武汉,由武汉退重庆,在重庆呆了四、五年,从未到过前线,这一回可算是到了抗战的最前线了,真觉得不虚此行。
二
到山东来了,怎么办?最重要的问题是想尽一切办法,使九十二军入鲁,但首先必须了解当时山东情况。
国共合作关系,这时连个影子也没有了,这主要由沈鸿烈负责。在于学忠入鲁之前,沈鸿烈以省政府主席兼省党部主任委员的地位,把持山东一切。于学忠入鲁后,沈鸿烈又兼苏鲁战区的副司令,他想以东北军的关系利用于学忠听他使用,而于学忠不听他的,这是他两人矛盾的主要原因。在抗战之初,沈鸿烈在表面上敷衍国共合作,而在骨子里则反其道而行,具体事实不胜枚举。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山东特务头子秦启荣、王尚志杀害共产党四百余人的骇人听闻的“太河惨案”发生后,沈鸿烈竟利用宗教人士作调查来掩盖,诿之为双方误会,足证此人心肠的阴险毒辣。一九三九年五、六月间,省府所在地东里店惨遭日寇飞机轰炸后,沈鸿烈借此把与八路军合作的表面联系也不要了。
于学忠对李仙洲入鲁的态度怎样?这是我急欲知道的。我到日照县境苏鲁战区总司令部会见于学忠时,他对这个问题的表示与我在阜阳所猜测的一样,不是积极而是颇为冷淡的。进来就欢迎,不进来也不要求他进来,态度坚决而不动摇。这就打消了我要求他出名欢迎李仙洲入鲁的意图。在谈话中,他对沈鸿烈很不满意。谈他被刺未中的事,他虽未明言是什么人策动,但嫌疑犯是省党部一个委员李子虔,此案发生后,他逃往重庆,于学忠未追究,此案就不了了之。于学忠还非常不满保安师师长张步云。张步云是一个惯匪,受沈鸿烈改编,驻扎在诸城县境与于学忠部防地相接,完全不听指挥,于学忠莫如之何,认为这是沈鸿烈给他留下的麻烦。从于学忠对李仙洲、沈鸿烈的态度来看,也反映出他对蒋介石的不满。(注一)
关于山东军事情况,除八路军方面我完全不知外,在国民党方面是相当复杂的。正规军有苏鲁战区总司令部直属五十一军的一一三师和一一四师,军长原为牟中珩,牟中珩调任省府主席后,周毓英升为军长。另外有新编第四师,师长为吴化文。暂编三十六师,师长为著名匪首刘桂堂。还有由苏鲁战区总司令部改编的游击部队,第一纵队司令张里元,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第三纵队司令秦启荣,第四纵队司令王尚志。由省政府改编的部队称保安部队,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总司令,其下保安一师师长吴化文兼,保安二师师长张步云,保安三师师长张景月,保安四师师长赵保原等。还有省府所属十六个专区各自改编的保安旅、保安团或特务旅、团等。
这些地方游击部队是由下列三种情况搞起来的。(1)没有逃走的行政专员、县长等,以抗战为名招兵买马,借以扩充自己的势力;(2)区、乡长、恶霸地主、流氓、土匪等,趁机而起接受政府改编的;(3)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直接派人来山东搞起来的,如秦启荣的部队,最初是打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的番号,王立亭的部队是打着别动总队二十八支队的番号,王立亭搞的时间不久就离开了山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组织头子是康泽。这些游击部队总共有多少?据说不下三、四十万人。带兵千人以上的大小头目也有六、七十个。除极少数外,他们都是残害人民,搜括民财,无法无天,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但他们也都是被蒋介石利用来反共的一支别动队。他们反共反人民是一致的,但他们也常常因利害冲突自相火并。如当沈鸿烈主鲁时,鲁东行署主任卢斌属CC派的“学行社”,竟被属“复兴社”的厉文礼的部下所杀害,沈鸿烈也莫如之何,只得不了了之。
这些地方游击部队,在抗战开始之时,也还打过日本侵略军。以后,由于蒋介石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他们就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所谓“曲线救国”的道路。我到鲁南时,就已经有大部分游击部队公开或半明半暗地接受敌人的番号成了伪军,而尚未投敌的只有少数儿个较大的头头。我初到时,吴化文尚未投敌,但不久就知道他与日寇有拉拢,到一九四二年冬,敌伪军有一次大“扫荡”,我与省参议会的孔繁霨等人,转移到吴化文的防区。这次大“扫荡”持续了五、六天,白天移动,夜间有时也得移动。有一天,沿博山、临朐边境向东移动,天拂晓时,被敌伪军围困在一个山峪里,上有飞机,四周炮声隆隆响,进退不得。过了儿个小时,炮声停了,飞机不来了,我们才得安全通过。事后,知道是吴化文的部队派人在山头上用旗语与敌伪军联系才解了围的。这一“扫荡”刚过去,吴化文部队即公开投敌,据说是由一个CC派重要分子牵线的。到一九四三年春,日寇又大举“扫荡”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的防区。厉文礼的司令部住安邱某地,在日伪军四面包围下厉文礼被俘,蒋介石派给于学忠的苏鲁战区总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周复也被击毙。厉文礼被俘后,受日寇的威胁利诱,即公开当了汉奸。这时省党部已移住安邱县的水帘沟,以离交战地区稍远未受影响。
作为一个苏鲁战区总司令的于学忠,在这种军事情况之下,加上蒋介石对他的不信任和他对蒋介石的戒心,就决定了他对敌军不得不采取的战略。在我到山东直到他退出山东的一年间,我觉得他的战略是这样:对敌人绝不主动采取进攻或袭击。敌人如进犯或“扫荡”,即迅速转移,躲避交锋。敌人走后,再回原防。因此,他所控制的地区,只能日益缩小,不能扩大,与八路军相比,正是相反。假设日军不是天天受着八路军的威胁,不敢轻易离开他的据点,于学忠会很快地被敌军赶出山东的。
当我决定来山东时,虽已知山东军事情况,于学忠军是处于不利地位,但绝想不到完全被动挨打到了那种程度。故当我初到山东就遇到一有敌情必须随省府频频转移,曾未有一次进行反击,主观上感觉不能忍耐。在敌众我寡时可以敌来我走,敌去我回,在敌寡我众时,为什么不可以乘机反击?有一次省府通知向悦庄转移,我叫省党部随之转移,但我与秘书一人,勤务兵二人,转移到附近一个小村庄住下来,过了一天并未有敌人来,而五十一军军长周毓英即派人来,一定要我去悦庄。我也觉得作为一种抗议,不能用这种方式,这种单独行动是违犯军纪的,也就随来人一同到了悦庄,住了九天就随省府一同回了原地。从此,我更觉得李仙洲必须迅速入鲁,否则,于学忠必有被敌军逐出山东的一天。但于学忠既无意主动求援于李仙洲,我就不得不积极向李仙洲作工作,先后派阎实甫、潘维芳、李佩贤等到李仙洲处敦促,最后,还直电蒋介石催促,终究未达到目的。
三
省党部的情况怎样呢?我到时:
委员:阎实甫、赵季勋、林鸣九、宋从颐、牟尚斋、刘道元、裴鸣宇、秦启荣、李先良九人(注二)。阎实甫兼秘书长。
三科,一处,一室:
总务科:科长吕学勤。干事、助理干事、录事等共十三人。
组织科:科长张浩然。干事、助理干事共四人。
宣传科:科长李廷俊。干事、助理干事共三人。
交通处:处长夏蔬园。干事及交通员二人。
调统室:主任于仲昆。该室名义上属省党部领导,但他的经费、人事等完全独立,省党部无权过问。
督导员及分住地区:全省共划分二十四个督导区,每区辖四、五个县或六、七个县。
李汉三,菏泽等县;马友三济宁等县;
崔伯鹏,东平等县;黄青云郓城等县;
赵士伟,胶县等县包括青岛市;
赵国栋,莱阳等县;武竹亭,历城等县;
盛伟航,寿光等县;赵光越,潍县等县;
丘青萍,诸城等县;王培祜,沂水等县;
王世和,昌乐等县;刘汝浩,临沂等县;
刘廷简,泰安等县;潘维芳,夏津等县;
栾树青,平原等县;张秀民,临邑等县;
刘同玉,阳信等县;王陶轩,惠民等县;
苏文奇,鲁西等县。
胶济铁路党部:主任委员宋从颐兼,属省党部领导。
九个委员,就派系说,牟尚斋、刘道元、李先良属CC派,赵季勋、林鸣九、宋从颐、裴鸣宇属张苇村派,秦启荣属黄埔派,阎实甫属大同盟。这些人中,秦启荣和李先良都有自己的武力。秦启荣是苏鲁战区所属的第三纵队司令,并兼山东建设厅长,李先良是鲁东行署主任,在崂山地区有保安团队,人数约二、三千人。刘道元兼教育厅长,赵季勋兼财政厅长,裴鸣宇兼省参议会副议长。干部中科长吕学勤、李廷俊属三青团,张浩然、于仲昆属CC派,于仲昆掌管的调统室,就是中央调查统计局在山东设立的一个特务机关。夏蔬园曾经搞过改组派。督导员中CC派、三青团及过去属于改组派和大同盟的人都有,我也不完全知道他们的派系情况。
国民党内各派系的互相倾轧与捣乱,是先天的不治之病。委员九人中,CC派和张苇村派占了绝大多数,他们都是和我不对头的,只有阎实甫和秦启荣二人可以和我合作。我在这种情况之下,也是很感不好应付的。我首先向大家宣布不更动任何一个人,要求大家同心协力,努力工作,争取抗战胜利。这样,至少在表面上大家可以暂时相安。
我在省党部主要作了些什么工作呢?
我到任之初,首先在欢迎我的省级各机关干部职员大会上作了讲话,主要是强调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如果谈到国内政治的话,也必然离不开资产阶级民主那一套。到一九四二年冬,在省府所在地吕匣店子召开了一次省级各机关的党员大会,预先安排了三个人发言,范予遂、何思源和牟中珩。何思源以中央监察委员的身分,牟中珩以军队特别党部主任委员的身分。所以特别要何思源讲话,是在表示我对CC派不存成见之意。我在这次大会上要解释国民党的意义与作用,以提高他们对于组织的观念。在一九四三年,于学忠将退出山东时,召集附近的督导员、县党部书记长等开了一次工作会,主要是给他们打气,以稳定人心。
我同蒋介石直接来往几次电报。第一次是在我到山东后向他报告我所了解的军事情况,第二次大约在一九四二年十月间,省参议会议长孔繁霨等怂恿我,为防止吴化文投敌,叫我打电报给蒋介石,说他抗战有功,请予提升,我也没有征询于学忠总司令的意见,就发了这个电报。经蒋复电,大加申斥,大意说对军队的人事问题,勿得妄事建议。又一次是因为山东局势危急,九十二军迟迟不进山东,打电报催他迅速派兵入鲁挽救危局。蒋复电大意即派大军入鲁,坚持勿馁。省党部即把这个电报转知各有关机关,以安定人心。还有一次是报告苏鲁战区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周复等在安邱被日伪军击毙。
省党部内部工作,组织科主要为吸收党员。因在沦陷区不能发给正式党证,即由省党部发给临时党证,为鲁临字多少号,以便将来调换正式党证。宣传科工作,主要油印一部分小报,叫“简明新闻”,新闻来源是收听的广播录音,再则是颁发由重庆发来的文件等。省党部自己没有一部电台,所有电报都是分送省政府电台和调统室代发。它们常常因电台忙把省党部的电报迟发。特别是调统室不仅迟发,有时积压下来给退回。省党部也莫奈它何。
自吴化文公开投敌,省党部更移动频繁,并向东移动到安邱地区。后厉文礼被俘并公开投敌,省党部又移动到诸城地区。约在一九四三年春节之后,我一个人到北平去治病,因为从阜阳来鲁途中,跌下马来伤了左手,到鲁南山区治疗不得法,致三个指头僵直不能弯曲。到北平住在一个在家习道练拳的友人家,先到周瑞庭医师私设的诊所医疗,又辗转介绍我去找骨科专家孟继懋,他断定可以完全治好。因我不能久居北平,经他告诉了医疗的方法和发给药品,我就回了山东。在上下火车上所见,日本人简直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自己也几乎挨了日本人的揍。我是特意到胶县车站上车的,由一个伪军队长派他的弟弟送我上车,上车的人拥挤不堪,检票时,因为人多拥挤,日本人就用枪托子打和拳击脚踢,我由于有穿伪军装的人送我,才免于遭到拳打脚踢。但上车后挤得如猪仔,动也不能动,又渴又累,受了一夜的罪。回来坐了二等车,但有一个日本强盗军官为了躺卧舒服,竟强占了我的座位,我也只得忍受。
我自北平回来不久,即在一九四三年的四、五月间,苏鲁战区总司令部和省政府决定撤出山东,省党部决定不撤走,我个人也决定暂留在山东,不随省府撤走。在与于学忠和牟中珩送别之后,省党部即移昌乐。听人说,张天佐统治昌乐的办法,是对任何一个有共产党嫌疑的人,不经审讯就秘密处死。
因为于学忠部和省府撤走,省党部召开一次会议,决定派人到附近的游击部队进行联系,委员牟尚斋派到驻安邱的秦启荣部队。适秦启荣部与八路军冲突,为八路军包围,秦启荣被击毙。牟尚斋逃回说,他被俘,诡称在昌乐县当录事而得释放。
自秦启荣被击毙,昌乐突现紧张。张天佐说,为了我的安全,叫我完全保密不与外人接触。我这时考虑,来山东最大目的是希望李仙洲尽早入鲁,于学忠、李仙洲合力保住山东,迎接最后胜利。及自阜阳到了山东,始知于学忠、李仙洲各自所想的并不与我所想的一致,但自己并未因此而灰心,认为九十二军迟早是要进山东的。故当吴化文公开投敌后,曾先后派阎实甫、潘维芳、李佩贤等到李仙洲处催他入鲁,到紧急关头并直电蒋介石催促。孰知事与愿违,九十二军进到半途即已力竭,于学忠也恰在这时顶不住日寇的“扫荡”,而撤离山东。在此情况下,我觉得已没有留在山东的必要,即于八月间由张天佐派人送我到宿县车站,返回重庆。
四
我回到重庆之后,省府撤出山东的CC派分子,对我大肆攻击,这不使我感到意外。攻击我的借口,是说我到北平勾结汉奸。这时我的心情,不在乎他们诬告什么,而在于决心辞掉这个省党部主任委员的职务。但朱家骅不准我辞职,丁惟汾也不同意我辞职。他们说,你辞职正是中了诬告你的人的诡计,他们不是专为攻击你个人,而是想赶走朱家骅夺回组织部。他们攻击我不仅是在口头上,而是上呈文给蒋介石。朱家骅把一份蒋介石署名的代电给我看,是由侍从室第三处发给中央调查统计局的,要它调查我到北平是否有勾结汉奸的事实。而侍从室第三处是陈果夫在那里当家。朱家骅说:“我不相信他们对你的控告,这个代电由我签复‘总裁’就完了,你不要在意。”我又打消了辞职的意思。
一九四四年初,我经西安、洛阳而达阜阳,又与山东省政府住在一起了。朱家骅还再三催我到山东去,我坚决拒绝他这个要求,后来他也就不坚持了。
由于省党部未随省政府撤到阜阳,为了取得联系,省党部在阜阳设立了一个办事处,派于锦荣负责,收转国民党中央拨发的经费及文件。省党部又因不能借用省政府电台拍发电报,而调统室更加多方刁难,不给拍发电报。在我离开山东之后,省党部即在昌乐设法装置了一部电台,从此可以与国民党中央设在阜阳的电台直接通报。省党部阜阳办事处也有一个电台,可以与山东直接取得联系。
在阜阳的多半年期间,比较清闲,无事可作。我两腿发作了急性湿疹,越治越坏,竟至几个月不能走动。幸而日伪“扫荡”的威胁不大,被动转移之事也就减少了。我这时在幻想将来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如何实行宪政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多数与少数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必须多数对少数采取忍让精神,才能得到体现。而我国自民国成立以来,人们所理解和实行的民主,完全是凭借多数压迫少数,因而,也就没有少数服从多数可言,在政治上也就无法取得安定。国民党取消一党专政后,其它各党派在政治上刚刚取得合法平等的权利,国民党更应该对他们采取最大的忍让精神,不能动不动以多数压服他们。而体现忍让精神最好的办法,是“异中求同,同中容异”,此外,不可能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春季,日寇开始了对中原的大“扫荡”,而河南首当其冲。负责保卫中原的蒋介石的嫡系汤恩伯的军队,很快就被日寇打得丢盔弃甲,狼狈溃退。想不到来阜阳又观看了蒋介石的嫡系军队十数万人大溃退的表演。
六月十二日突然接朱家骅辞组织部长职的电报,部长换上了陈果夫。当时很感出乎意外。为什么在即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时,忽然撤了朱家骅换上陈果夫呢?再一想,这是蒋介石仍然相信CC派,叫CC派的头子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包办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即复电朱家骅辞职,也打电报告诉了丁惟汾。这时,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已决定在九月间开会,正好我得早回重庆,不误会期。但因通过平汉铁路有困难,迟至八月十五日才能动身。
我辞职之后,陈果夫即派何思源继任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这时,山东已成为所谓“蒋敌伪合流”的局面,何思源熟悉各方人事关系,确实由他继任省党部主任委员之职,是最适当不过的。
我辞职后不久,省党部就办理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我未被提名为代表候选人,同我有关系的人仅潘维芳(我任内的秘书长,留在山东替我办交代)一人。潘维芳把代表候选人让给了我,我才作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 × ×
写完这一段历史回忆,不仅要问自己:当时为什么认为中国单独抗战,无胜利可能,而必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抗战才能取得胜利?为什么那样迷信资产阶级民主和费边社会主义?回答是:所以那样看抗日战争,是不认识全国人民的力量,惟武器论和极端崇美的结果,而实际上是怕抗日失败,而使国民党政权垮了台。所以那样迷信议会民主和费边社会主义,是幻想以改良主义维护国民党的统治,根子里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当时满脑子里是资产阶级思想,就不可能不按资产阶级世界观办事,也就不可能认识到如现在所认识的:我当时的想法,不仅是反动的,而且是非常愚蠢可笑的了。
当我决定到山东时,对蒋介石、于学忠之间有矛盾不是不知道。但总以为在大敌当前之时,他派九十二军入鲁,是以对敌为重,意在支援于学忠的,故我坚信李仙洲一定能够入鲁,于学忠也一定欢迎李仙洲入鲁,自己也一定能够促成于学忠、李仙洲合作,顶住日寇扫荡,迎接抗战最后胜利。现就周达夫揭露蒋介石、于学忠关系内幕看,李仙洲进不去山东,于学忠不积极欢迎李仙洲进山东,是早为蒋介石、于学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了的,而自己却蒙在这个鼓里而不知,失败不是必然的吗?
附注:
注一:蒋介石与于学忠的关系不很好,我当时只是从表面作推测,内幕并不清楚。在写这篇稿子以前,函询当时于学忠的秘书长周从政,承答复如下:“一九四一年夏,蒋介石和于学忠往返电商多次,鉴于鲁省军政需要统一,明白表示由于兼省主席。蒋介石乃指名派我代表于学忠携鲁省府改组方案到渝就商一切。我八月二十日到渝,见蒋介石后,他说的很好,但后来变了卦。经几次谈话,他明白提出省府主席不由于学忠兼,由于学忠保荐部下二人送请中央选定。于学忠不得已保荐牟中珩和我两人,最后决定为牟中珩。从这件事的经过来看,蒋对于学忠的主要目的,在消灭东北军的五十一军。采取的手段是分化,包括分化人和部队。蒋介石留我在渝不让回鲁,正是分化手段之一。蒋介石认为我是张学良的党羽,接近共产党,不可靠,在当时又为于学忠所信任,更觉可虑。因此,调我去渝,不让回鲁,一面能限制我的活动,一面可减少于的帮手。在这个问题上,沈鸿烈、周复也起到一定的煽惑作用。
“苏鲁战区总部原来未设政治部,过了相当时期,在鲁南站住脚之后,蒋介石才派黄埔一期毕业生周复为政治部主任,成立政治部。表面上是在总部领导下进行抗日的政治工作,实质上是对内而不对外。周复对于学忠及其部队意在监视。而于学忠及其部下对这些人也时常戒备。
“蒋派九十二军入鲁,不是为抗战,乃为争夺地位,想把于学忠的总司令地位取而代之……困难交给杂牌军,权利留给“黄马褂”,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已在二十多年来表现在各个方面了”。
注二:一九四三年七、八月间,委员秦启荣、裴鸣宇出缺,补充李汉三和潘维芳。一九四四年,又增添赵士伟、李廷俊两委员。阎实甫辞秘书长职,派潘维芳兼。
一九四一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沈鸿烈离职,蒋介石委派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所属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继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但不兼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这是因为蒋介石对于学忠所统率的东北军不信任,认为有亲共之嫌,至少也是反共不卖力,故不能把这个专门反共的国民党省党部交给牟中珩。CC派的重要分子何思源,十几年来,一直任山东省教育厅长、民政厅长、鲁北行署主任,为蒋介石所信任,由他继任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本来是很合适的。但由于CC派头子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把持、操纵国民党多年,屡屡遭到国民党其他各派系的反对。在抗战期间,蒋介石为了缓和这种矛盾,就把组织部长CC派头子陈立夫调为教育部长,换上朱家骅。朱家骅本来也是以依附CC派起家的;但是他披着学术界的外衣,以区别于CC派。蒋介石派他作组织部长,对内换汤不换药,对外可以堵住反对者之口。朱家骅秉承蒋介石的意志,也是为了要制造自己的派系,他就不能用CC派分子何思源。
朱家骅为什么找到了我?根子还在蒋介石。一九三八年年底,汪精卫自重庆逃往越南的河内,蒋介石即分别召见了改组派的一些人谈话。十二月三十一日蒋召见了我和邓飞黄,蒋的谈话,主要是劝告我们不要跟汪精卫逃走,并叫我们写信劝汪不要投敌。我们明确表示了态度,坚决反对汪精卫投敌。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日,汪精卫自河内发的艳电和国民党中央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同时在报上发表。我根据这两个文件给汪写了一封信,交彭学沛转去。大意是:(1)绝对不能受日本首相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的欺骗;(2)迅即出国到欧洲去,免受敌人的笼络;(3)对中央给他的处分要以最大忍耐处之,不要同中央翻脸。我这种态度,使蒋相信我不会跟汪投敌。再则,自抗战以来,我在国民参政会的活动和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是始终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蒋也是很清楚的。以此,蒋介石相信,把我派出去,既不会依附汪精卫,也不会勾搭共产党。当朱家骅任组织部长不久,曾要派我作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被我坚决拒绝了。这与我当时对抗战胜利没有信心有关。这次我答应朱家骅回山东,是在珍珠港事件刚刚发生之后。珍珠港事件发生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我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式开始。这时,我国抗战的胜利不仅有希望,而且有把握了。十二月三十一日朱家骅派组织部主任秘书王启江征求我回山东作省党部主任委员的意见,在座的有邓飞黄。未待我说话,他先鼓动我接受这个职务,我也顿时生了政治野心,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朱家骅未待同我见面就签呈给蒋介石,不给我再考虑的机会。
我的政治野心是什么?它是怎么与我对抗战胜利的信心联系在一起的?有必要在这里作一扼要交代。
抗日战争发生之前,国民党的一些失意分子方振武、陈铭枢、黄少谷等都在英国伦敦。我与邓飞黄因汪精卫被刺离开南京,也到了伦敦。他们主张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抗日,把写好的电稿要我与邓飞黄签名,我拒绝签名。我坚持我的反动主张和他们争论。我认为中国不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或接近爆发而单独对日抗战,绝对没有胜利的可能。我说,单独抗战只有一件好处,就是可以削弱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发展民主力量,不过以战争失败为代价,换取民主力量的发展,是万万不可这样作的。后经邓飞黄对我再三劝说,我才签了名。这只是为了朋友的情面,并非我的主张有了改变。
芦沟桥一声炮响,我国对日抗战了,这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全国人民都起来抗战,我自己就不能躲在国外。即于十月间同邓飞黄一起回国参加了抗战。当时我的打算是:在抗战期间,不参加政府工作,不作政府官吏,只想钻进一个类似的民意机构,以便宣传自己对于抗战与民主两个问题的看法。恰好国民参政会成立,就作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除了在会内与进步力量争争吵吵之外,不时在国民党的各种报刊上发表主张。
对于抗战,在初期,总的说不是鼓气而是泄气。记得国民政府退守武汉的时候,我在报上发表的“国际的里面”一文中主张:两国交战,如果一国确信不能在战场上取胜,也不能在外交上取胜,则宁肯在战场上尚未决定胜负之前,承认外交的失败而讲和,比战败到作城下之盟总还好一些。这实际就是鼓吹对日求和投降了。一九三九年,英、法对德宣战,我的失败情绪开始有所转变,一九四一年纳粹德国进攻苏联,觉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越逼越近,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心又始终非常狠毒,中国也就只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日本帝国主义拚到底了。
关于民主政治,当时我坚信资产阶级议会民主那一套,更迷信英国费边社的所谓社会主义。就是说,我坚信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议会的多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我拥护国民党,但我憎恨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及其政府的极端贪污、腐化与无能。而要铲除国民党的这两大祸害,必须改造国民党,而改造国民党的唯一办法,是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宪政。我幻想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再没有理由不履行诺言,结束训政,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宪政。再没有理由不承认共产党这个政治力量,继续维持国共合作,再没有理由不通过政治协商办法解决两党之间的一切争端,而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一旦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国民党在新的政治力量帮助和监督之下,就不可能如从前那样乱搞独裁和贪污,民主政府必然从各方面进行改革,推动进步。这不仅不会削弱国民党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而且会加强这种地位,国民党仍将在很长时期内不失为第一大党的地位。
抗战胜利快要到来,取消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行宪政有了希望,我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久就要召开,我要在这次代表大会争取恢复作为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我是第四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五次被CC派搞掉)的地位,以便在国民党中央有发言权,而回山东作省党部主任委员,正是取得一个中央委员的有利条件。
我也考虑当时山东的军事情况,首先于学忠部受日寇“扫荡”的压力很大,但相信李仙洲的九十二军即将入鲁,它入鲁后即可改变这种情况。再则军政权已统一于苏鲁战区总司令部,于学忠、牟中珩非蒋家嫡系,只要我不同他们闹别扭,他们也不会干涉我的行动,我相信比较容易与他们相处。还有临时省参议会这个所谓民意机关,议长孔繁霨、秘书长王立哉等,也是可以和我合作的。更重要的是,李仙洲与改组派的一些人的关系比较要好,我到山东后,不仅可以得到他的支持,而且我相信可以对李仙洲与于学忠的合作关系起到积极作用。如能达到抗战胜利,这就是我回山东的一个大胜利。同时我也考虑,国民党省党部已成为一个专门反共的机关。在重庆还存在着国共合作关系,我在国民参政会内与进步力量的代表争争吵吵,或写点什么在报刊上发表出来,也只是动口不动手,若作了省党部主任委员,不是亲自动手来反共了吗?但是我又想,我既坚持资产阶级民主,实际就是积极反共,还有什么动口不动手的差别呢?因此,我就不顾一切地要回山东一行。
蒋介石批准我回山东后,就很快约我见了面,冠冕堂皇地说了几句,最重要的是今后有事叫我直接给他报告。临别,叫他的侍卫长林蔚交我一本密电码,要我有事随时拍电报告他。他还写了一张送我路费六千元的纸条给我。这是自汪精卫投敌以来,蒋有意拉拢我,我也有意靠近他的一个具体表现。
我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动身,先到安徽阜阳,住在九十二军司令部约两、三个月。默察九十二军的高级将领,都没有尽速入鲁援助于学忠部解除困境的打算,而李仙洲和汤恩伯之间也存在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对李仙洲入鲁极为不利(现据李仙洲说,当时汤恩伯不支持李仙洲入鲁,而想叫王仲廉代替他)。于学忠是否欢迎李仙洲入鲁?我还不很摸底,但从于学忠、李仙洲之间没有密切联系来看,觉得于学忠对这件事至少不是采取积极态度,而是颇为冷淡的。我还未待进入山东,困难问题就来了。如果九十二军进不了山东,而于学忠的军队又顶不住日寇的“扫荡”,不待敌人总投降就退出山东,那么,我来山东的目的,不就完全落空了吗?后退是不行了,只得进山东,从各方面设法,催九十二军入鲁。
怎样进山东?化装走。“良民证”用樊世昌为代名。省政府派一个职员叫祝廷林来引路。我们于一九四二年五月间自阜阳动身,从宿县乘火车到济南,换胶济路车到张店,再换火车到博山,然后由伪军护送到新四师吴化文的防区,再由吴化文派人送到省府所在地临朐辖境。省府住吕匣店子,省参议会住棘子山,省党部住青崖,三个村庄都相距不远。
一到鲁南山区,顿时感到兴奋愉快。自抗战以来,我一直紧跟着国民政府,由南京退武汉,由武汉退重庆,在重庆呆了四、五年,从未到过前线,这一回可算是到了抗战的最前线了,真觉得不虚此行。
二
到山东来了,怎么办?最重要的问题是想尽一切办法,使九十二军入鲁,但首先必须了解当时山东情况。
国共合作关系,这时连个影子也没有了,这主要由沈鸿烈负责。在于学忠入鲁之前,沈鸿烈以省政府主席兼省党部主任委员的地位,把持山东一切。于学忠入鲁后,沈鸿烈又兼苏鲁战区的副司令,他想以东北军的关系利用于学忠听他使用,而于学忠不听他的,这是他两人矛盾的主要原因。在抗战之初,沈鸿烈在表面上敷衍国共合作,而在骨子里则反其道而行,具体事实不胜枚举。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山东特务头子秦启荣、王尚志杀害共产党四百余人的骇人听闻的“太河惨案”发生后,沈鸿烈竟利用宗教人士作调查来掩盖,诿之为双方误会,足证此人心肠的阴险毒辣。一九三九年五、六月间,省府所在地东里店惨遭日寇飞机轰炸后,沈鸿烈借此把与八路军合作的表面联系也不要了。
于学忠对李仙洲入鲁的态度怎样?这是我急欲知道的。我到日照县境苏鲁战区总司令部会见于学忠时,他对这个问题的表示与我在阜阳所猜测的一样,不是积极而是颇为冷淡的。进来就欢迎,不进来也不要求他进来,态度坚决而不动摇。这就打消了我要求他出名欢迎李仙洲入鲁的意图。在谈话中,他对沈鸿烈很不满意。谈他被刺未中的事,他虽未明言是什么人策动,但嫌疑犯是省党部一个委员李子虔,此案发生后,他逃往重庆,于学忠未追究,此案就不了了之。于学忠还非常不满保安师师长张步云。张步云是一个惯匪,受沈鸿烈改编,驻扎在诸城县境与于学忠部防地相接,完全不听指挥,于学忠莫如之何,认为这是沈鸿烈给他留下的麻烦。从于学忠对李仙洲、沈鸿烈的态度来看,也反映出他对蒋介石的不满。(注一)
关于山东军事情况,除八路军方面我完全不知外,在国民党方面是相当复杂的。正规军有苏鲁战区总司令部直属五十一军的一一三师和一一四师,军长原为牟中珩,牟中珩调任省府主席后,周毓英升为军长。另外有新编第四师,师长为吴化文。暂编三十六师,师长为著名匪首刘桂堂。还有由苏鲁战区总司令部改编的游击部队,第一纵队司令张里元,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第三纵队司令秦启荣,第四纵队司令王尚志。由省政府改编的部队称保安部队,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总司令,其下保安一师师长吴化文兼,保安二师师长张步云,保安三师师长张景月,保安四师师长赵保原等。还有省府所属十六个专区各自改编的保安旅、保安团或特务旅、团等。
这些地方游击部队是由下列三种情况搞起来的。(1)没有逃走的行政专员、县长等,以抗战为名招兵买马,借以扩充自己的势力;(2)区、乡长、恶霸地主、流氓、土匪等,趁机而起接受政府改编的;(3)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直接派人来山东搞起来的,如秦启荣的部队,最初是打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的番号,王立亭的部队是打着别动总队二十八支队的番号,王立亭搞的时间不久就离开了山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组织头子是康泽。这些游击部队总共有多少?据说不下三、四十万人。带兵千人以上的大小头目也有六、七十个。除极少数外,他们都是残害人民,搜括民财,无法无天,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但他们也都是被蒋介石利用来反共的一支别动队。他们反共反人民是一致的,但他们也常常因利害冲突自相火并。如当沈鸿烈主鲁时,鲁东行署主任卢斌属CC派的“学行社”,竟被属“复兴社”的厉文礼的部下所杀害,沈鸿烈也莫如之何,只得不了了之。
这些地方游击部队,在抗战开始之时,也还打过日本侵略军。以后,由于蒋介石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他们就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所谓“曲线救国”的道路。我到鲁南时,就已经有大部分游击部队公开或半明半暗地接受敌人的番号成了伪军,而尚未投敌的只有少数儿个较大的头头。我初到时,吴化文尚未投敌,但不久就知道他与日寇有拉拢,到一九四二年冬,敌伪军有一次大“扫荡”,我与省参议会的孔繁霨等人,转移到吴化文的防区。这次大“扫荡”持续了五、六天,白天移动,夜间有时也得移动。有一天,沿博山、临朐边境向东移动,天拂晓时,被敌伪军围困在一个山峪里,上有飞机,四周炮声隆隆响,进退不得。过了儿个小时,炮声停了,飞机不来了,我们才得安全通过。事后,知道是吴化文的部队派人在山头上用旗语与敌伪军联系才解了围的。这一“扫荡”刚过去,吴化文部队即公开投敌,据说是由一个CC派重要分子牵线的。到一九四三年春,日寇又大举“扫荡”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的防区。厉文礼的司令部住安邱某地,在日伪军四面包围下厉文礼被俘,蒋介石派给于学忠的苏鲁战区总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周复也被击毙。厉文礼被俘后,受日寇的威胁利诱,即公开当了汉奸。这时省党部已移住安邱县的水帘沟,以离交战地区稍远未受影响。
作为一个苏鲁战区总司令的于学忠,在这种军事情况之下,加上蒋介石对他的不信任和他对蒋介石的戒心,就决定了他对敌军不得不采取的战略。在我到山东直到他退出山东的一年间,我觉得他的战略是这样:对敌人绝不主动采取进攻或袭击。敌人如进犯或“扫荡”,即迅速转移,躲避交锋。敌人走后,再回原防。因此,他所控制的地区,只能日益缩小,不能扩大,与八路军相比,正是相反。假设日军不是天天受着八路军的威胁,不敢轻易离开他的据点,于学忠会很快地被敌军赶出山东的。
当我决定来山东时,虽已知山东军事情况,于学忠军是处于不利地位,但绝想不到完全被动挨打到了那种程度。故当我初到山东就遇到一有敌情必须随省府频频转移,曾未有一次进行反击,主观上感觉不能忍耐。在敌众我寡时可以敌来我走,敌去我回,在敌寡我众时,为什么不可以乘机反击?有一次省府通知向悦庄转移,我叫省党部随之转移,但我与秘书一人,勤务兵二人,转移到附近一个小村庄住下来,过了一天并未有敌人来,而五十一军军长周毓英即派人来,一定要我去悦庄。我也觉得作为一种抗议,不能用这种方式,这种单独行动是违犯军纪的,也就随来人一同到了悦庄,住了九天就随省府一同回了原地。从此,我更觉得李仙洲必须迅速入鲁,否则,于学忠必有被敌军逐出山东的一天。但于学忠既无意主动求援于李仙洲,我就不得不积极向李仙洲作工作,先后派阎实甫、潘维芳、李佩贤等到李仙洲处敦促,最后,还直电蒋介石催促,终究未达到目的。
三
省党部的情况怎样呢?我到时:
委员:阎实甫、赵季勋、林鸣九、宋从颐、牟尚斋、刘道元、裴鸣宇、秦启荣、李先良九人(注二)。阎实甫兼秘书长。
三科,一处,一室:
总务科:科长吕学勤。干事、助理干事、录事等共十三人。
组织科:科长张浩然。干事、助理干事共四人。
宣传科:科长李廷俊。干事、助理干事共三人。
交通处:处长夏蔬园。干事及交通员二人。
调统室:主任于仲昆。该室名义上属省党部领导,但他的经费、人事等完全独立,省党部无权过问。
督导员及分住地区:全省共划分二十四个督导区,每区辖四、五个县或六、七个县。
李汉三,菏泽等县;马友三济宁等县;
崔伯鹏,东平等县;黄青云郓城等县;
赵士伟,胶县等县包括青岛市;
赵国栋,莱阳等县;武竹亭,历城等县;
盛伟航,寿光等县;赵光越,潍县等县;
丘青萍,诸城等县;王培祜,沂水等县;
王世和,昌乐等县;刘汝浩,临沂等县;
刘廷简,泰安等县;潘维芳,夏津等县;
栾树青,平原等县;张秀民,临邑等县;
刘同玉,阳信等县;王陶轩,惠民等县;
苏文奇,鲁西等县。
胶济铁路党部:主任委员宋从颐兼,属省党部领导。
九个委员,就派系说,牟尚斋、刘道元、李先良属CC派,赵季勋、林鸣九、宋从颐、裴鸣宇属张苇村派,秦启荣属黄埔派,阎实甫属大同盟。这些人中,秦启荣和李先良都有自己的武力。秦启荣是苏鲁战区所属的第三纵队司令,并兼山东建设厅长,李先良是鲁东行署主任,在崂山地区有保安团队,人数约二、三千人。刘道元兼教育厅长,赵季勋兼财政厅长,裴鸣宇兼省参议会副议长。干部中科长吕学勤、李廷俊属三青团,张浩然、于仲昆属CC派,于仲昆掌管的调统室,就是中央调查统计局在山东设立的一个特务机关。夏蔬园曾经搞过改组派。督导员中CC派、三青团及过去属于改组派和大同盟的人都有,我也不完全知道他们的派系情况。
国民党内各派系的互相倾轧与捣乱,是先天的不治之病。委员九人中,CC派和张苇村派占了绝大多数,他们都是和我不对头的,只有阎实甫和秦启荣二人可以和我合作。我在这种情况之下,也是很感不好应付的。我首先向大家宣布不更动任何一个人,要求大家同心协力,努力工作,争取抗战胜利。这样,至少在表面上大家可以暂时相安。
我在省党部主要作了些什么工作呢?
我到任之初,首先在欢迎我的省级各机关干部职员大会上作了讲话,主要是强调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如果谈到国内政治的话,也必然离不开资产阶级民主那一套。到一九四二年冬,在省府所在地吕匣店子召开了一次省级各机关的党员大会,预先安排了三个人发言,范予遂、何思源和牟中珩。何思源以中央监察委员的身分,牟中珩以军队特别党部主任委员的身分。所以特别要何思源讲话,是在表示我对CC派不存成见之意。我在这次大会上要解释国民党的意义与作用,以提高他们对于组织的观念。在一九四三年,于学忠将退出山东时,召集附近的督导员、县党部书记长等开了一次工作会,主要是给他们打气,以稳定人心。
我同蒋介石直接来往几次电报。第一次是在我到山东后向他报告我所了解的军事情况,第二次大约在一九四二年十月间,省参议会议长孔繁霨等怂恿我,为防止吴化文投敌,叫我打电报给蒋介石,说他抗战有功,请予提升,我也没有征询于学忠总司令的意见,就发了这个电报。经蒋复电,大加申斥,大意说对军队的人事问题,勿得妄事建议。又一次是因为山东局势危急,九十二军迟迟不进山东,打电报催他迅速派兵入鲁挽救危局。蒋复电大意即派大军入鲁,坚持勿馁。省党部即把这个电报转知各有关机关,以安定人心。还有一次是报告苏鲁战区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周复等在安邱被日伪军击毙。
省党部内部工作,组织科主要为吸收党员。因在沦陷区不能发给正式党证,即由省党部发给临时党证,为鲁临字多少号,以便将来调换正式党证。宣传科工作,主要油印一部分小报,叫“简明新闻”,新闻来源是收听的广播录音,再则是颁发由重庆发来的文件等。省党部自己没有一部电台,所有电报都是分送省政府电台和调统室代发。它们常常因电台忙把省党部的电报迟发。特别是调统室不仅迟发,有时积压下来给退回。省党部也莫奈它何。
自吴化文公开投敌,省党部更移动频繁,并向东移动到安邱地区。后厉文礼被俘并公开投敌,省党部又移动到诸城地区。约在一九四三年春节之后,我一个人到北平去治病,因为从阜阳来鲁途中,跌下马来伤了左手,到鲁南山区治疗不得法,致三个指头僵直不能弯曲。到北平住在一个在家习道练拳的友人家,先到周瑞庭医师私设的诊所医疗,又辗转介绍我去找骨科专家孟继懋,他断定可以完全治好。因我不能久居北平,经他告诉了医疗的方法和发给药品,我就回了山东。在上下火车上所见,日本人简直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自己也几乎挨了日本人的揍。我是特意到胶县车站上车的,由一个伪军队长派他的弟弟送我上车,上车的人拥挤不堪,检票时,因为人多拥挤,日本人就用枪托子打和拳击脚踢,我由于有穿伪军装的人送我,才免于遭到拳打脚踢。但上车后挤得如猪仔,动也不能动,又渴又累,受了一夜的罪。回来坐了二等车,但有一个日本强盗军官为了躺卧舒服,竟强占了我的座位,我也只得忍受。
我自北平回来不久,即在一九四三年的四、五月间,苏鲁战区总司令部和省政府决定撤出山东,省党部决定不撤走,我个人也决定暂留在山东,不随省府撤走。在与于学忠和牟中珩送别之后,省党部即移昌乐。听人说,张天佐统治昌乐的办法,是对任何一个有共产党嫌疑的人,不经审讯就秘密处死。
因为于学忠部和省府撤走,省党部召开一次会议,决定派人到附近的游击部队进行联系,委员牟尚斋派到驻安邱的秦启荣部队。适秦启荣部与八路军冲突,为八路军包围,秦启荣被击毙。牟尚斋逃回说,他被俘,诡称在昌乐县当录事而得释放。
自秦启荣被击毙,昌乐突现紧张。张天佐说,为了我的安全,叫我完全保密不与外人接触。我这时考虑,来山东最大目的是希望李仙洲尽早入鲁,于学忠、李仙洲合力保住山东,迎接最后胜利。及自阜阳到了山东,始知于学忠、李仙洲各自所想的并不与我所想的一致,但自己并未因此而灰心,认为九十二军迟早是要进山东的。故当吴化文公开投敌后,曾先后派阎实甫、潘维芳、李佩贤等到李仙洲处催他入鲁,到紧急关头并直电蒋介石催促。孰知事与愿违,九十二军进到半途即已力竭,于学忠也恰在这时顶不住日寇的“扫荡”,而撤离山东。在此情况下,我觉得已没有留在山东的必要,即于八月间由张天佐派人送我到宿县车站,返回重庆。
四
我回到重庆之后,省府撤出山东的CC派分子,对我大肆攻击,这不使我感到意外。攻击我的借口,是说我到北平勾结汉奸。这时我的心情,不在乎他们诬告什么,而在于决心辞掉这个省党部主任委员的职务。但朱家骅不准我辞职,丁惟汾也不同意我辞职。他们说,你辞职正是中了诬告你的人的诡计,他们不是专为攻击你个人,而是想赶走朱家骅夺回组织部。他们攻击我不仅是在口头上,而是上呈文给蒋介石。朱家骅把一份蒋介石署名的代电给我看,是由侍从室第三处发给中央调查统计局的,要它调查我到北平是否有勾结汉奸的事实。而侍从室第三处是陈果夫在那里当家。朱家骅说:“我不相信他们对你的控告,这个代电由我签复‘总裁’就完了,你不要在意。”我又打消了辞职的意思。
一九四四年初,我经西安、洛阳而达阜阳,又与山东省政府住在一起了。朱家骅还再三催我到山东去,我坚决拒绝他这个要求,后来他也就不坚持了。
由于省党部未随省政府撤到阜阳,为了取得联系,省党部在阜阳设立了一个办事处,派于锦荣负责,收转国民党中央拨发的经费及文件。省党部又因不能借用省政府电台拍发电报,而调统室更加多方刁难,不给拍发电报。在我离开山东之后,省党部即在昌乐设法装置了一部电台,从此可以与国民党中央设在阜阳的电台直接通报。省党部阜阳办事处也有一个电台,可以与山东直接取得联系。
在阜阳的多半年期间,比较清闲,无事可作。我两腿发作了急性湿疹,越治越坏,竟至几个月不能走动。幸而日伪“扫荡”的威胁不大,被动转移之事也就减少了。我这时在幻想将来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如何实行宪政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多数与少数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必须多数对少数采取忍让精神,才能得到体现。而我国自民国成立以来,人们所理解和实行的民主,完全是凭借多数压迫少数,因而,也就没有少数服从多数可言,在政治上也就无法取得安定。国民党取消一党专政后,其它各党派在政治上刚刚取得合法平等的权利,国民党更应该对他们采取最大的忍让精神,不能动不动以多数压服他们。而体现忍让精神最好的办法,是“异中求同,同中容异”,此外,不可能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春季,日寇开始了对中原的大“扫荡”,而河南首当其冲。负责保卫中原的蒋介石的嫡系汤恩伯的军队,很快就被日寇打得丢盔弃甲,狼狈溃退。想不到来阜阳又观看了蒋介石的嫡系军队十数万人大溃退的表演。
六月十二日突然接朱家骅辞组织部长职的电报,部长换上了陈果夫。当时很感出乎意外。为什么在即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时,忽然撤了朱家骅换上陈果夫呢?再一想,这是蒋介石仍然相信CC派,叫CC派的头子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包办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即复电朱家骅辞职,也打电报告诉了丁惟汾。这时,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已决定在九月间开会,正好我得早回重庆,不误会期。但因通过平汉铁路有困难,迟至八月十五日才能动身。
我辞职之后,陈果夫即派何思源继任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这时,山东已成为所谓“蒋敌伪合流”的局面,何思源熟悉各方人事关系,确实由他继任省党部主任委员之职,是最适当不过的。
我辞职后不久,省党部就办理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我未被提名为代表候选人,同我有关系的人仅潘维芳(我任内的秘书长,留在山东替我办交代)一人。潘维芳把代表候选人让给了我,我才作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 × ×
写完这一段历史回忆,不仅要问自己:当时为什么认为中国单独抗战,无胜利可能,而必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抗战才能取得胜利?为什么那样迷信资产阶级民主和费边社会主义?回答是:所以那样看抗日战争,是不认识全国人民的力量,惟武器论和极端崇美的结果,而实际上是怕抗日失败,而使国民党政权垮了台。所以那样迷信议会民主和费边社会主义,是幻想以改良主义维护国民党的统治,根子里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当时满脑子里是资产阶级思想,就不可能不按资产阶级世界观办事,也就不可能认识到如现在所认识的:我当时的想法,不仅是反动的,而且是非常愚蠢可笑的了。
当我决定到山东时,对蒋介石、于学忠之间有矛盾不是不知道。但总以为在大敌当前之时,他派九十二军入鲁,是以对敌为重,意在支援于学忠的,故我坚信李仙洲一定能够入鲁,于学忠也一定欢迎李仙洲入鲁,自己也一定能够促成于学忠、李仙洲合作,顶住日寇扫荡,迎接抗战最后胜利。现就周达夫揭露蒋介石、于学忠关系内幕看,李仙洲进不去山东,于学忠不积极欢迎李仙洲进山东,是早为蒋介石、于学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了的,而自己却蒙在这个鼓里而不知,失败不是必然的吗?
附注:
注一:蒋介石与于学忠的关系不很好,我当时只是从表面作推测,内幕并不清楚。在写这篇稿子以前,函询当时于学忠的秘书长周从政,承答复如下:“一九四一年夏,蒋介石和于学忠往返电商多次,鉴于鲁省军政需要统一,明白表示由于兼省主席。蒋介石乃指名派我代表于学忠携鲁省府改组方案到渝就商一切。我八月二十日到渝,见蒋介石后,他说的很好,但后来变了卦。经几次谈话,他明白提出省府主席不由于学忠兼,由于学忠保荐部下二人送请中央选定。于学忠不得已保荐牟中珩和我两人,最后决定为牟中珩。从这件事的经过来看,蒋对于学忠的主要目的,在消灭东北军的五十一军。采取的手段是分化,包括分化人和部队。蒋介石留我在渝不让回鲁,正是分化手段之一。蒋介石认为我是张学良的党羽,接近共产党,不可靠,在当时又为于学忠所信任,更觉可虑。因此,调我去渝,不让回鲁,一面能限制我的活动,一面可减少于的帮手。在这个问题上,沈鸿烈、周复也起到一定的煽惑作用。
“苏鲁战区总部原来未设政治部,过了相当时期,在鲁南站住脚之后,蒋介石才派黄埔一期毕业生周复为政治部主任,成立政治部。表面上是在总部领导下进行抗日的政治工作,实质上是对内而不对外。周复对于学忠及其部队意在监视。而于学忠及其部下对这些人也时常戒备。
“蒋派九十二军入鲁,不是为抗战,乃为争夺地位,想把于学忠的总司令地位取而代之……困难交给杂牌军,权利留给“黄马褂”,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已在二十多年来表现在各个方面了”。
注二:一九四三年七、八月间,委员秦启荣、裴鸣宇出缺,补充李汉三和潘维芳。一九四四年,又增添赵士伟、李廷俊两委员。阎实甫辞秘书长职,派潘维芳兼。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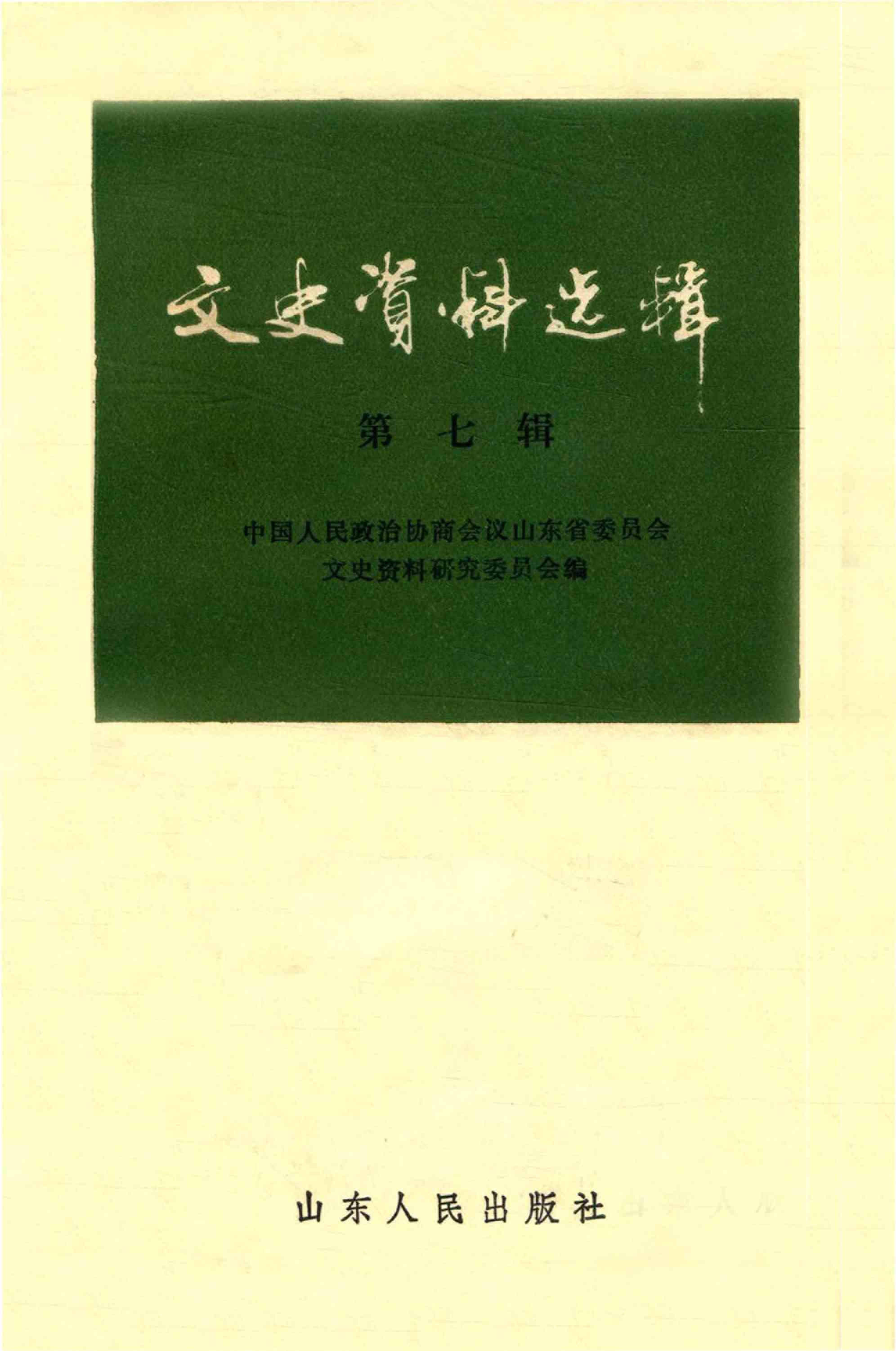
相关人物
范予遂
责任者
相关地名
山东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