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要”(童养媳)
| 内容出处: | 《畲族妇女口述史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920020230007433 |
| 颗粒名称: | “白要”(童养媳) |
| 分类号: | K892.22 |
| 页数: | 21 |
| 页码: | 21-41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畲族地区存在四种婚俗方式,其中“女嫁男方”最常见。家境贫寒的畲族女童常被迫成为童养媳,这是一种非正式和不合法的婚姻形式。这些女童在婆家受到虐待和歧视,地位低下,生命安全和人生权利没有保障。童养媳婚姻中,女孩与主家儿子圆房之前,双方家长不存在确定的亲戚关系,导致“白要”们地位低下,命运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 |
| 关键词: | 武义县 民俗 童养媳 |
内容
按畲族旧时的传统,畲民婚俗方式有“女嫁男方”、“男嫁女方”、“做两头家”和“子媳缘亲”四种,这四种婚俗方式决定了一个畲族女性的婚姻状况。“女嫁男方”最为常见,即女人长大后嫁到男方,这是畲民婚配的主要形式;“男嫁女方”又称“招儿子”,即女方家庭招女婿上门,上门赘婿生育的长子须随母姓;“做两头家”指一般婚配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婚后男女双方干两家活,赡养两家老人;“子媳缘亲”是指家庭经济生活困难的畲民,生有儿子,怕长大成人后娶不上媳妇,就抱他人幼女作童养媳①,待女童长大后与儿子婚配。这四种婚俗中唯有“子媳缘亲”这种婚俗方式不举行婚嫁仪式,因为这种婚姻形式不需要说媒,也不需要聘金和彩礼。这种婚姻在旧社会颇为常见。
武义县当地上了岁数的畲族老妇称童养媳为“白要”或“白要骨”,这是一种蔑称或贱称。“白要”指童养媳就像是一件不值钱的物品,谁需要谁白拿。而称“某某”为“骨”,通常在蔑称或贱称的语境中,类似于“贼骨头”、“贱骨”等意思。解放前家境贫寒的畲族女童,通常有做“白要”,即童养媳的经历,她们既有到汉族家庭当“白要”的,也有到畲族家庭当“白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童养婚俗已被明令禁止。
童养媳婚姻不受法律保护,只是一种中国民间的婚姻习俗。日本学者认为,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婚姻的成立无需获得宗教(即教会)或者世俗(即国家)公共权威的见证或认证,实行的是非法律婚主义,因此婚姻完全是民间行为。①一般来讲,只要未婚男女有人主婚,有人为媒,就可视为合法婚姻。因此,“子媳缘亲”这种婚姻形式只要有中间人说合,双方大人(即女童生身父母与收养她的主家)达成意愿即可。招赘婚尚立相关的婚姻文书,而童养媳婚姻往往不立契约,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童养媳婚姻的非正式性和随意可变性。由于童养媳尚未成年,其命运在相当程度上掌握在公婆手中,非法律婚主义使得童养媳婚姻中的女童生命安全与人生权利没有得到任何保障。
童养媳是指女婴或幼女由其公婆家养育,待其成年后正式结婚。童养媳到夫家后,在夫家经历两个阶段:非正式婚姻阶段和正式婚姻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她们的身份是双重的,既是夫家的一个成员,又是一个候补媳妇,年幼的夫妻以兄妹相称,两人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在第二个阶段,她们既是夫家的一个成员,又是一个正式的媳妇。童养媳在两个阶段的经历尤以第一个阶段最为悲惨。当童养媳的女童地位低下,名义上她是收养人家的准儿媳,可是变数很大。从笔者了解的情况来看,当事人一般都自幼被生身父母送到别人家当童养媳。如娘家在溪口台山脚下一个小村的雷新兰,出生于1934年,由于母亲生育了6个孩子,怕养不活这么多,因此家中排行最小的她不到满月就被一个蓝姓家庭抱走,开始了做“白要”的经历。也有女童在十余岁出头才被生身父母送走去做“白要”。从生理方面来看,无论是年幼还是稍长的童养媳,通常要在收养她的主家度过少则三四年,多则十几年的时间才能婚配。
一部分童养媳在长大后,得以与原定的丈夫正常婚配。还有部分童养媳在主家生活期间,可能会出现如下的情况:第一种情况,童养媳未能长大成人,夭折了。第二种情况,童养媳忍受不了婆家的虐待而逃跑。如娘家为柳城周处村的蓝新妹,在做了两年“白要”后,终于忍受不了“白要”的生活而逃回了娘家。第三种情况,童养媳原先婚配的男方在长大后移情别恋,继而与“原配”分手。如娘家为柳城内潘村的蓝舍爱,8岁时被送到桃溪镇大路山的姑姑家做“白要骨”,原打算许配给大她4岁的表哥,后来表哥和一个女孩好上了,于是蓝舍爱在16岁时又被送回了娘家。这样,名义上有过婚配的蓝舍爱在19岁时,嫁给一个比她大10岁的男人,并且做了后妈。第四种情况,童养媳在主家生活一段时间后,被主人转卖。如娘家在柳城车门村的蓝宝妹,在夫家待了十五六年后被转卖。可见,童养媳在未正式圆房前与丈夫虽有夫妻名分,但这种关系远不如正式婚配的夫妻关系稳定。
在中国传统家庭生活中,联姻的双方家庭往往存在着稳固的人伦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为联姻双方互称“亲家”。与此不同,在畲族童养媳婚姻中,女孩与主家儿子圆房之前,双方家长不存在因婚姻而缔结的确定的亲戚关系,即收养女童的主家与女童的生身父母之间不存在明确的姻亲关系,所以女童的亲生父母一旦将自己的孩子送给别人做“白要”后,通常就不再过问女孩的一切,双方的家长也并无往来,这导致了“白要”们尴尬而低下的家庭地位,她们的命运因此而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在笔者调查的童养媳婚姻案例中,如果女童生养父母与收养家庭本身有亲戚关系,则逢年过节双方家庭因走亲戚还会有来往(如送至姑母家做“白要”的蓝舍爱),相对而言,夫家会善待这种有亲威关系的童养媳,所以当蓝舍爱的表哥移情别恋后,姑父特地还了蓝家50元钱,并用轿子将蓝舍爱抬回娘家。与此相反,如果女童生养父母与收养家庭不存在亲戚关系,则生养父母将女童送至收养家庭后,一直到女儿与对方儿子圆房前,双方家长往往互不来往。虽然钟发品先生①说,他们村(桃溪镇种子源村)曾有一个童养媳的养父、生父之间以兄弟互称,但这种情况实属个例。
童养媳婚姻在旧社会盛行,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从笔者访谈的对象来看,童养媳婚姻主要是当事人家庭经济贫困所致。首先,畲民多处山区,山多田少,土地贫瘠,度日艰难,一遇荒年,生活更显困顿。故穷苦人家生下了女儿又无力抚养,为不使孩子饿死和缓解家中危困,只能将其送人,可见,生身父母将子女送出去童养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其次,结娃娃亲的双方家庭均可免除结婚的开销,男方抱养童养媳时不需要财礼,女方也不需要陪嫁。在送抱童养媳的过程中,多数买卖关系不明确,一般是婆家象征性地给女方娘家些许财物,等到双方成年后圆房就算正式结婚了,这种结婚仪式要比明媒正娶简单得多。最后,抱养童养媳的家庭可以无偿得到一个劳动力,所得到的回报远远超出所付出的。因此,当童养媳们被家长像一件东西一样“送”给养家之后,她的一切便均可由收养她的家庭随意处置,包括她的身体。在夫家,童养媳可以随意被驱使、奴役、责罚及买卖,还要从事多种家务。一旦童养媳具备了基本的劳动能力,便成为夫家家务的主要承担者,是廉价的劳动力。
“童养媳”婚俗实质上是强制的包办婚姻。这些女孩在远未成年,压根儿不知道何为夫妻、何为妇道之时,就做了童养媳。这一习俗使身为童养媳的幼女身心遭到无情的摧残,她们小小年纪就被迫离开了亲生父母,并经常受到夫家,尤其是婆母的虐待。对她们而言,伴随童年的是超越年龄所能承受的繁重的体力劳动及来自身体的饥饿感。在别人眼中,她们只是生产劳动的机器以及成年后繁衍后代的生育工具,是没有人生自由的可以买卖的商品。她们只需具备做妻子、做母亲、做儿媳所需的奉献与忍受,而女性自身人性的、情感的需求则被遗忘、被压抑。这期间她们角色的转变也均为非自主的选择。从“女儿”身份转换为“准媳妇”,长大后成为人之妻、人之母,甚至还会被转卖。在各种身份的转换中,她们没有自主权力,这种现象正是女性社会人格被歧视与被忽视的反映。
因为童养媳这一婚俗对民俗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等领域均有研究意义,因此不少学者从各个视角加以剖析,学者郭松义指出,清代全国有童养媳记载的州县为561个,而当时清朝州县总数为1724个。①费孝通教授在《江村经济》中虽提及童养媳现象,但只是说有这种风俗,并没有做更深入的探讨,因为这不是该书研究的重点。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武雅士教授(A.Wolf),以研究台湾地区汉族的“童养媳”(媳妇仔)而著名。他在台湾地区北部的“海山”(台北盆地边缘)做人类学研究时,发现该地区闽南系统的汉族家庭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童养媳成婚(称为小婚)的比例极高,有时高达40%以上,几乎要与“正常”的迎娶婚(称为大婚)比例相同了。武雅士教授以此为例,进而延伸讨论了人类婚姻制度以及近亲禁忌(incest taboo)的起源等问题,受到研究家庭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广泛注意。
一般学者都以为养童养媳的主要原因是贫穷,但是武雅士教授发现真实的现象并非如此。一种风俗一旦形成,便会流行起来。他发现在台湾地区北部行小婚的童养媳人家之中有许多是很有钱的富家,而有些富人家中甚至有两个以上的童养媳。武雅士教授借助长期以来对日据时代户籍资料的分析(日据时代户籍资料中有童养媳的记录),形成了一种可称为“婆媳夫妻感情丛结”的假说。他发现由童养媳小婚而形成的家庭中,夫妻关系经常是不好的;至少是冷淡的,然而婆媳关系却较为融洽。他认为在夫妻关系经常冷淡的情况下,却仍然有40%以上的家庭采用童养媳婚,这是传统中国家庭宁愿牺牲夫妻感情,也要维持婆媳融洽关系的因素所致(Wolf,1968,1970)。武雅士教授之所以知道人家夫妻感情不好,除了因为他长期在当地做调查访问(一年以上),对各个家庭细节很熟悉外,还由于他在户口资料中发现,凡是童养媳夫妇其子女必定比行大婚夫妇的子女少,这一数字差别在统计学上有重要意义。由于这一现象的发现,武雅士教授提出几种很有趣的规律性理论来对这种特殊婚姻形态加以阐释:1.传统汉族家庭中,经常是婆媳关系优先于夫妻关系;2.童养媳婚姻中的夫妻通常感情不好,这种情况往往会影响子女人数,因此在盛行童养媳的地区人口成长状况颇不稳定;3.童养媳夫妻感情冷淡的原因可能来自于心理,因为儿童以兄妹的关系在家庭中共同成长,经常会失去“性”的吸引力,易于形成近亲禁忌的心理丛结。因此武雅士教授认为他的这个例子,正可以支持芬兰裔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威斯特马克(EdwardWestermarck)早期所提出的近亲婚姻禁忌是心理学的而非生物学的因素这一理论(Wolf,1970,1994)。后来武雅士教授也因为提出这一假说而得到芬兰科学院的学术勋赏。①
武雅士教授的观点对我们研究畲族童养媳现象虽然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但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性,我们还不能完全套用这一理论来对畲族童养媳现象加以解释。就畲族童养媳婚姻的研究现状而言,迄今为止鲜有这方面的研究性文章发表(笔者尚未找到这方面的资料),也鲜有学者对畲族童养媳婚姻在婚姻中所占比例做深入调查。从笔者了解的情况看,童养媳的婚俗解放前在畲族家庭中并不少见,甚至可以说是常见的婚姻形态,并成为一种社会风俗,这也许与畲族聚居区经济相对落后有关。
童养媳婚姻质量也因人而异,就感情而言,有的夫妇比较冷淡;有的关系开初尚可,后来发生变化;有的是姐弟关系胜于夫妻关系。就夫妻关系与生育子女数的相关度而言,如果童养媳长大后与收养她的家庭的儿子成亲,则子女数的确不多,这似乎印证了武雅士教授的童养媳婚姻中的夫妻通常感情不好会影响子女人数的观点,但如果童养媳长大后被卖或其他原因与另外家庭的男人结婚,生育子女数则另当别论(本篇所附的口述实录可以佐证该结论)。
此外,笔者认为童养婚生育子女数还与生理有关。童养媳婚姻中双方的年龄有一定差距。在武义县畲族的童养媳婚姻中,绝大多数为男方大于女方,这种现象与童养媳产生的方式有关。一般一个家庭只有生下男孩后才会考虑收养童养媳,特别是那些自幼被抱养的童养媳绝大多数会小于其未来丈夫。如桃溪镇种子源村的蓝球妹6岁开始做童养媳,男的比她大5岁,在她未成年时公公婆婆相继过世,所以她11岁时即与16岁的丈夫圆房了,但她到18岁才开始生育。不幸的是孩子很快就夭折了,从此蓝球妹再未生育。当然,童养媳婚姻也有女方年龄大于男方的情况,收养女童的家庭未雨绸缪,在自家没有生育男孩之前,先行收养女童(前面提到的雷新兰,她许配的男孩比她小9岁)。又如笔者曾采访过的一位老人,她18岁成亲时男方只有15岁,她到25岁时方才生育,间隔时间长达7年。这类女比男大的婚姻中的女性,她们的心智往往比男性成熟,因此夫妻关系更像是姐弟关系。通常童养媳夫妇在结婚时,往往一方尚不惜人情,甚至发育尚未成熟,另一方已经成人,因而出现有婚姻之形而无婚姻之实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圆房,他们也很难建立正常的夫妻关系,夫妻往往会在婚后若干年之后才会生育,甚至有的夫妇会终身不育,这种情况与女方的早婚有一定的关系。据一项对印度童婚的调查发现,妇女未成年就已结婚,会有绝育的风险。①学者吴东海在田野调查时发现,畲族领养子女率非常高。他在对畲族4个村27户累计162代的统计中发现:自生儿繁衍后代的有98代,占60.49%;自生女招赘繁衍后代的有20代,占12.34%;领养儿女的有44代,占27.17%。其中领养比例最高的紫阳贯村6户28代中,就有9代领养儿女,占32.14%。所以他认为有的畲族家庭连续4代因没有生育而领养,②这种现象除了经济、体质等原因外,也许与早婚有一定关系。③
与武雅士教授了解的情况不同,笔者了解到在畲族童养媳婚姻中,婆媳关系一般不存在优于夫妻关系的现象,甚至婆媳关系比夫妻关系更为恶劣。笔者调查的有童养媳经历的访谈对象均提到婆婆对她们不好,这种不好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干得苦,二是吃不饱。但笔者认为,这并不能说明婆婆们心狠,而是与生活贫困有关。对于婆婆们来说,童养媳是干活不用付钱的劳力,对靠天靠田里的收成过日子的乡村家庭而言,只有拼命干活才能生存下去,因此婆婆们自己也是每天起早贪黑地苦干。另外,童养媳婚姻中的女童通常在幼年时就被婆家收养,因此,她与婆婆的关系既是婆媳关系也是母女关系,而这一种特殊的母女关系与有血缘关系的母女关系有相当大的差异。事实上,童养媳婚姻中的婆媳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人际关系,是一种绝对的上下级关系。小媳妇必须俯首听命于婆母,没有独立、平等的人格尊严。而从这种特殊的母女关系来看,婆婆与儿媳的情感关系存在着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排斥的现象。作为女性,婆媳对家庭情感的体验会存在一定的相似度,有时需要她们联合起来争取自身的权利。例如,在笔者访谈的对象中就有两代童养媳或三代童养媳现象。因此在童养媳婚姻中,往往三四岁的幼女已经是小媳妇了,而此时她的婆婆也不过30岁左右。过去四五代同堂现象非常普遍,所以通常婆婆上面还有太婆婆、太太婆婆,因此婆婆亦受太婆婆、太太婆婆的支使。某种程度上,婆婆与小媳妇都是受压制的。但是,婆婆的身份毕竟与童养媳不一样,婆婆在家里是有发言权和一定家长权的,而小媳妇在家里只相当于奴婢,在未圆房前,只能以准媳妇身份存在,还不算是家庭的正式一员,因此准媳妇受婆婆排斥就成为正常的事情。菲利斯·切斯勒在其名著《女性的负面》的前言中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女人的竞争对象主要是别的女人,……女人通过诽谤、造谣和躲避相互妒忌、暗中作梗。”①在她看来,女性不仅受男性的压迫,有时女性对女性的压迫更甚,甚至母女之间也是如此。她的观点与早期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地位低是男性压迫的结果并不矛盾,但同时她认为,女性除了遭受男性压迫外,也受到女性本身的压迫,女性(婆婆)无意中成了“男性权威的代理人”②。这种现象在童养媳身上更是显而易见。
附一
“白要”蓝宝珠的口述
2008年夏天,我回武义县作田野调查时,请求居住在柳城乡下的亲戚帮忙寻找上了年纪的曾做过童养媳的畲族妇女。为此,亲戚用摩托车载着我在乡间挨村探访。碰上年龄大的老年妇女,我们就“厚着脸皮”问她有没有做过“白要”。本文的蓝宝妹就是坐在自家门口时,被我们偶遇的。她听到我此行的目的是请她讲讲她的经历,特别是怎么当“白要”的,老人脸上表现出颇不以为然的表情,那意思似乎是说做“白要”不值一提。老人非常瘦削,时年82岁,面容清癯,看得出年轻时相貌不差。以下文字根据其口述整理。
我娘家是柳城车门村(车门距柳城约5里路)的,我3岁就死了父亲。后来我娘改嫁,我跟着娘到了后父家。娘和后父生了三四个弟妹,家里人口多,养不过来,7岁时我被送到白姆下村做“白要”。那户人家家境也不好,住的是茅草屋,为了防屋漏,每年的10月左右要将屋顶的稻草重新铺换一次。我8岁时就要一个人看头大水牯,这牛是从财主家租来的,每年要交租给地主,租量是100斤谷。田也是向财主家租的,冬天种大麦、小麦和米麦。米麦比小麦早半个月收割,这样接得上吃饭。稻子每年种一熟。
我做“白要”这家的儿子比我大4岁,家里送他出去读书。我呢,一天到晚忙着干活。天有一点点亮光就起床,出门割草喂牛,牛要吃饱才有力气耕田。接下来我要拔猪草喂猪,还要做其他农活。不到天黑,基本上没坐下来的时候。就这样卖命做,那家也没把我留下。在我19岁时,他们把我转卖到了石井山村,卖了1000多斤谷。之前我并不知道要卖我,直到双方谈好了,对方来要人的时候我才知道。事情到这地步,你不去也得去,如果不去,那就把你捆在长条凳上像卖猪一样绑好抬你走。
我被卖过来的这户人家的家里只有兄弟两个,我嫁的是老大,他也是苦命人,16岁时父母双亡。19岁时讨了我,我们俩是同岁,他对我还好。我嫁过来时,小叔才12岁,家里只有一间茅草铺。22岁时,我有了第一个孩子,后来陆陆续续生了8个,养活了6个,死了2个。活下来的正好3个儿子,3个女儿,其中2个女儿送给别人了。因为家里困难,除了一个儿子是请人接生的,其他都是我自己包的,怎么包的我请教过村里的老人,小孩生下来以后,先把小孩的脐带拉至小孩的膝盖处,拿剪刀剪断,余下的脐带用苎麻线扎紧,拿些棉花压盖在脐带上,最后用破衣服包裹好就行了。生小孩时,自己将小孩包好就没有力气了,懒在床上,身上发冷,连烧饭的力气都没有,就只好饿着。等丈夫耕田回来后,丈夫烧点吃的我吃吃才起得了床。坐月子期间我照样要下床洗衣服、做饭,只是不用下田干活了。
因为家里没老人,所以,小孩生下来以后也没人照料。有一回,我把大女儿放在床上,自己去地里干活。不料,她从床上掉到地上,自己又爬到门边。结果,我地里回来一推门,正好撞到女儿的鼻子。我当时就“啊呀”了一声,以为鼻子撞坏了,要破相了。后来幸好没什么大的印记。
解放后,当时家里分到6亩田,人均1.2亩。但是田地比较贫薄,加上没什么肥料,产量不高。去除交的公粮,做饭时要掺点其他的东西,这样才能吃八九分饱。我们夫妻俩拼命做,后来开始造房子,慢慢地造了三间瓦房,是儿子大了以后一点一点扩建的。我们后来还帮小叔子娶了妻,一年半以后才分的家。
70岁以后,日子好过了。
附二
“白要”蓝新妹的口述
蓝新妹是我所有访谈对象中年龄最大的畲族女性,89岁(2008年),她身材瘦小,但眼不花,耳不聋,描述起往事来仿佛历历在目。陪同我去的亲戚是该村村长的儿媳,可爱的老太太知道她的身份后,直夸她漂亮、可爱,这也可看出老太太脑子好使。下面文字根据2008年8月期间我所做的访谈笔记整理。
我娘家是柳城周处村的,家里很穷。娘生过七八个孩子,但是只养活了三个:我、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11岁时,被送到柳城白姆下村做了两年“白要”。我去的那户人家住在山头上,婆婆非常厉害。她的儿子比我小一岁,但她从来舍不得打自己的亲生儿子,就打我,用赶牛的毛竹条打。毛竹条上细下粗,婆婆就把它倒过来,用粗的那头打我,我的膝盖、腿上经常被她打得都是血。
婆婆还不让我和他们一家住,他们家有两间房,住得下我但不让我住,让我一个人单独住在一户死光了人的无人居住的茅草屋里。床是用木板搭的,下面垫一些稻草,上面的被子就是几块不成形的破棉絮。一到晚上,婆婆也舍不得让我点灯,屋里黑乎乎的,没有亮光,非常吓人。晚上我好像看见有个东西在我床前摇摇晃晃并发出“嚎嚎”声。我吓得赶快用被子蒙住眼睛,不停安慰自己:眼睛看不见就不怕了。
做“白要”的两年,我每天要放牛、砍柴、割草,从没穿过鞋子,草鞋也没得穿,冬天也一样。下雪天的时候,我身上只有两件单衣。吃的是他们家的剩饭,碗里大都是番薯丝,没几粒米,也没有菜。婆婆不准我和她的儿子玩,怕我玩了不干活。那日子苦啊,我实在吃不消了,就一直想逃,有一天终于下定决心要跑回娘家。离开家两年了,我一下子找不到回家的路。我光着脚从早上一直走到下午,脚磨得很痛,终于到了柳城的北门头,别人告诉我只要一直沿着石板路走,就能找到我自己的娘家所在的村庄,多亏了别人指路,最后我回到了家。
我回娘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自己做了一双布鞋穿。在娘家我还是没得吃,但没人打我了。唉,那时候是饿大的。家里经常只有番薯吃,番薯整钵头地煮,饿了就拿一个吃。在娘家我一直待到17岁,后经一个亲戚做媒,嫁到这边的陈弄村。婚事定下来以后,男方拿了一点钱过来,我家打了一对木箱、一个方桌,另备了可以做五件衣服的布料作为我的陪嫁。我出嫁的那天有鞋子穿了。
我丈夫比我大3岁,是独子,他家里也很穷。往往是有了早饭,就没了中饭,有了中饭,就没了晚饭;常常是水烧上了,米不知在哪里。每顿饭吃多少米由婆婆决定,米快下锅时,婆婆会将盛出来的准备做饭的米又倒回一点到放米的口袋里。因为婆婆经常出去借米,到别人家借多了,她不好意思出去借,就叫我去借。烧饭烧饭,其实那不叫饭,只是杂食,里面掺了番薯丝、野菜之类的东西,而且掺的东西比米多。我刚嫁过来时,夫家的房子是没有板壁的,只有柱子,四处漏风。板壁是后来慢慢添上去的。床算是有的,叫米床。①因为这种床像打米用的水磓一样四周有栏,所以叫米床。这种床的好处是小孩不会掉下床。
我嫁过来的第二年,有了第一个孩子,但没过多久就死了。后来陆陆续续又生了四个,只有19岁那年生的一个孩子活了下来。为了过日子,有饭吃,我们夫妻俩发狠做,到地主那里租田种。租来的田离家很远,在十几里路以外,桃溪的西塘村那边。②我每天天刚见亮光就出门做,晚上看不见了才回家,中午还要回去给孩子喂奶。
辛辛苦苦种田,收割后,除了还债交租,就没剩多少了,所以还是吃番薯。只是在坐月子时家里人照顾我,不用吃番薯饭了,改吃米饭,偶尔还有鸡蛋吃,姜汤喝。月子期间家里的活还是照样要干的,就是不用下田干活。但是小孩满月后就必须做了,今天满月,明天就下地了。
苦是苦,但夫妻感情还可以,有时会为了孩子的事情吵嘴干架。
附三
“白要”蓝陈爱的口述
蓝陈爱与我的亲戚同村,而且是我亲戚的亲戚。辈分上,我的这位亲戚该称呼她为大伯母。因此,我亲戚约了她到自己家里,边吃点东西、喝点自制的烧酒边聊。老太太看上去身体相当不错,时年83岁,个头在同辈里面算高大的。下面文字根据2008年8月期间我所做的访谈笔记整理。
我娘家在柳城内潘村。家里姐妹7个,另外还有一个弟弟,我排行老二。7个姐妹中有两个做“白要”。我四五岁时,就被背走过,送到白姆下村。知道这件事后,叔伯家的姑姑冲我父亲骂道:“给人家不如做水坝!”①父亲被骂后就把我背了回来。但是7岁时我又被背到鲍畈村。
我到的这户人家家里四口人:太奶奶、公公、婆婆及公婆生的一个独养儿子。家里原来有亩把田,但太奶奶过世时,卖了五分田出丧。婆婆有大脖子的毛病(即因缺碘引起的甲状腺肿大),脖子上掉下来的肉要用布条挂起来,头低不下来,粗活特别是吃力的活干不了。公公干活还行,就是有点懒。独养儿子被送出去读书,他与我同年。
我刚过去时还小,重活干不动,但是要拎着篮子出去捡柴火和拔猪草。稍大一点,十来岁的时候,除了要拔猪草,还要下田插秧、上山去砍柴,从那时开始,家里的柴火全是我砍回来的,一个人干活没伙伴,太高的山不敢爬上去,只能在山脚路边砍点矮的灌木丛背回来。爬山砍柴时没有鞋穿,砍柴也很吃力,我经常边砍边哭,哭归哭,没人管你,活还是要干的。
“白要”的地位是很低的,只要家里来客人,我就不能上桌吃饭。一年难得能吃上肉,即使有肉,碗里大部分也是汤,大概只有三四片肉,你也不敢夹过来吃。过年的时候,能吃上三天不掺番薯丝的米饭,但三天后就吃不上了。
我是17岁时圆房,圆房也没什么仪式,就是在公婆家里吃碗面条。公婆给我做了一套新衣服和一双新鞋子,另外给我们准备了婚床,是四周有栏杆的米床。我和那个男的有10年的婚姻,其间,他曾经不肯去读书,婆婆就骂我,我就劝他,读了书就长了本事,这是任何人包括他母亲都拿不走的东西。丈夫在我的劝说之后又回去读书,后来当了老师,而且参加了革命。因为参加革命,曾经被国民党抓到丽水坐牢,一直到解放后才放出来。他被抓的时候,我和婆婆走到丽水去看他,天下着雨,路又不好,走到丽水时我的十个脚趾头的指甲盖已经全部脱掉,翻出来的全是带血的肉。
后来他变心了,要和我离婚。我不肯,哭啊哭,从床上哭得滚到地上,他还是要跟我离。人心变了,没药医的,但是我劝他读书这件事情上,他还是说我好的。与前夫离掉后,经人介绍,我到了这边的锦平村,一直和老伴生活到现在。两次婚姻我都没有孩子。
感想
武义乡间曾经流传过这样一首名为《童养媳》的歌谣:
正月梅花带雪开,想起前景真伤悲,七岁做了童养媳,从此爹娘都分开。
二月杏花开园中,公婆待我真当凶,做牛做马饭不饱,挨打挨骂过春冬。
三月桃花开得红,牵头水牯到山中,水牯一时无踪影,丈夫打我全身痛。
四月蔷薇红墙外,姑娘(指小姑)做人也厉害,公婆面前弄是非,害我天天流眼泪。
五月牡丹开得艳,肚中饿得似熬煎,偷吃一碗生冷饭,婆婆要我饿两天。
六月荷花开水中,病在床上真苦痛,口干无人端茶水,还说偷懒装病痛。
七月水仙盆中开,偷偷摸摸娘家归,路上一把被抓住,拳打脚踢捆起来。
八月桂花满树金,公婆硬逼我成亲,可怜我只十三岁,花还未开被蜂采。
九月菊花开满园,丈夫嫌我长麻脸,一日打我两三次,三餐骂我货真贱。
十月芙蓉花开放,心想离婚再嫁郎,可恨保长没道理,嫁鸡随鸡压一方。
十一月里腊梅香,来了救星共产党,提倡婚姻要自由,不许包办由爹娘。
十二月里雪花飞,离了火坑出苦海,政府做主离了婚,自找对象自己爱。①
这首民谣真实地描绘了童养媳婚前辛酸的生活,以及婚后毫无幸福可言的婚姻状况。人们通常用花来比照女性,但在这首歌谣中,自然界美丽怒放的鲜花与童养媳悲惨境遇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得这首歌谣更具感染力和冲击力。
童养婚是一种畸形的婚姻形态,是正规婚姻的重要补充形式,这种特殊的婚配形式决定了童养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从婚姻目的来看,童养媳婚姻主要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从夫妻关系来看,婚配双方年龄上的不协调会引发诸多问题,男女在不更人事之时便有了夫妻名分,承担起除生育之外的诸多家庭责任,所以童养婚中夫妻恩爱的不多见。由于童养媳的角色由女性来扮演,因此她们的经历让我们对贫困家庭的畲族妇女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与家庭生活形态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武义县当地上了岁数的畲族老妇称童养媳为“白要”或“白要骨”,这是一种蔑称或贱称。“白要”指童养媳就像是一件不值钱的物品,谁需要谁白拿。而称“某某”为“骨”,通常在蔑称或贱称的语境中,类似于“贼骨头”、“贱骨”等意思。解放前家境贫寒的畲族女童,通常有做“白要”,即童养媳的经历,她们既有到汉族家庭当“白要”的,也有到畲族家庭当“白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童养婚俗已被明令禁止。
童养媳婚姻不受法律保护,只是一种中国民间的婚姻习俗。日本学者认为,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婚姻的成立无需获得宗教(即教会)或者世俗(即国家)公共权威的见证或认证,实行的是非法律婚主义,因此婚姻完全是民间行为。①一般来讲,只要未婚男女有人主婚,有人为媒,就可视为合法婚姻。因此,“子媳缘亲”这种婚姻形式只要有中间人说合,双方大人(即女童生身父母与收养她的主家)达成意愿即可。招赘婚尚立相关的婚姻文书,而童养媳婚姻往往不立契约,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童养媳婚姻的非正式性和随意可变性。由于童养媳尚未成年,其命运在相当程度上掌握在公婆手中,非法律婚主义使得童养媳婚姻中的女童生命安全与人生权利没有得到任何保障。
童养媳是指女婴或幼女由其公婆家养育,待其成年后正式结婚。童养媳到夫家后,在夫家经历两个阶段:非正式婚姻阶段和正式婚姻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她们的身份是双重的,既是夫家的一个成员,又是一个候补媳妇,年幼的夫妻以兄妹相称,两人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在第二个阶段,她们既是夫家的一个成员,又是一个正式的媳妇。童养媳在两个阶段的经历尤以第一个阶段最为悲惨。当童养媳的女童地位低下,名义上她是收养人家的准儿媳,可是变数很大。从笔者了解的情况来看,当事人一般都自幼被生身父母送到别人家当童养媳。如娘家在溪口台山脚下一个小村的雷新兰,出生于1934年,由于母亲生育了6个孩子,怕养不活这么多,因此家中排行最小的她不到满月就被一个蓝姓家庭抱走,开始了做“白要”的经历。也有女童在十余岁出头才被生身父母送走去做“白要”。从生理方面来看,无论是年幼还是稍长的童养媳,通常要在收养她的主家度过少则三四年,多则十几年的时间才能婚配。
一部分童养媳在长大后,得以与原定的丈夫正常婚配。还有部分童养媳在主家生活期间,可能会出现如下的情况:第一种情况,童养媳未能长大成人,夭折了。第二种情况,童养媳忍受不了婆家的虐待而逃跑。如娘家为柳城周处村的蓝新妹,在做了两年“白要”后,终于忍受不了“白要”的生活而逃回了娘家。第三种情况,童养媳原先婚配的男方在长大后移情别恋,继而与“原配”分手。如娘家为柳城内潘村的蓝舍爱,8岁时被送到桃溪镇大路山的姑姑家做“白要骨”,原打算许配给大她4岁的表哥,后来表哥和一个女孩好上了,于是蓝舍爱在16岁时又被送回了娘家。这样,名义上有过婚配的蓝舍爱在19岁时,嫁给一个比她大10岁的男人,并且做了后妈。第四种情况,童养媳在主家生活一段时间后,被主人转卖。如娘家在柳城车门村的蓝宝妹,在夫家待了十五六年后被转卖。可见,童养媳在未正式圆房前与丈夫虽有夫妻名分,但这种关系远不如正式婚配的夫妻关系稳定。
在中国传统家庭生活中,联姻的双方家庭往往存在着稳固的人伦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为联姻双方互称“亲家”。与此不同,在畲族童养媳婚姻中,女孩与主家儿子圆房之前,双方家长不存在因婚姻而缔结的确定的亲戚关系,即收养女童的主家与女童的生身父母之间不存在明确的姻亲关系,所以女童的亲生父母一旦将自己的孩子送给别人做“白要”后,通常就不再过问女孩的一切,双方的家长也并无往来,这导致了“白要”们尴尬而低下的家庭地位,她们的命运因此而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在笔者调查的童养媳婚姻案例中,如果女童生养父母与收养家庭本身有亲戚关系,则逢年过节双方家庭因走亲戚还会有来往(如送至姑母家做“白要”的蓝舍爱),相对而言,夫家会善待这种有亲威关系的童养媳,所以当蓝舍爱的表哥移情别恋后,姑父特地还了蓝家50元钱,并用轿子将蓝舍爱抬回娘家。与此相反,如果女童生养父母与收养家庭不存在亲戚关系,则生养父母将女童送至收养家庭后,一直到女儿与对方儿子圆房前,双方家长往往互不来往。虽然钟发品先生①说,他们村(桃溪镇种子源村)曾有一个童养媳的养父、生父之间以兄弟互称,但这种情况实属个例。
童养媳婚姻在旧社会盛行,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从笔者访谈的对象来看,童养媳婚姻主要是当事人家庭经济贫困所致。首先,畲民多处山区,山多田少,土地贫瘠,度日艰难,一遇荒年,生活更显困顿。故穷苦人家生下了女儿又无力抚养,为不使孩子饿死和缓解家中危困,只能将其送人,可见,生身父母将子女送出去童养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其次,结娃娃亲的双方家庭均可免除结婚的开销,男方抱养童养媳时不需要财礼,女方也不需要陪嫁。在送抱童养媳的过程中,多数买卖关系不明确,一般是婆家象征性地给女方娘家些许财物,等到双方成年后圆房就算正式结婚了,这种结婚仪式要比明媒正娶简单得多。最后,抱养童养媳的家庭可以无偿得到一个劳动力,所得到的回报远远超出所付出的。因此,当童养媳们被家长像一件东西一样“送”给养家之后,她的一切便均可由收养她的家庭随意处置,包括她的身体。在夫家,童养媳可以随意被驱使、奴役、责罚及买卖,还要从事多种家务。一旦童养媳具备了基本的劳动能力,便成为夫家家务的主要承担者,是廉价的劳动力。
“童养媳”婚俗实质上是强制的包办婚姻。这些女孩在远未成年,压根儿不知道何为夫妻、何为妇道之时,就做了童养媳。这一习俗使身为童养媳的幼女身心遭到无情的摧残,她们小小年纪就被迫离开了亲生父母,并经常受到夫家,尤其是婆母的虐待。对她们而言,伴随童年的是超越年龄所能承受的繁重的体力劳动及来自身体的饥饿感。在别人眼中,她们只是生产劳动的机器以及成年后繁衍后代的生育工具,是没有人生自由的可以买卖的商品。她们只需具备做妻子、做母亲、做儿媳所需的奉献与忍受,而女性自身人性的、情感的需求则被遗忘、被压抑。这期间她们角色的转变也均为非自主的选择。从“女儿”身份转换为“准媳妇”,长大后成为人之妻、人之母,甚至还会被转卖。在各种身份的转换中,她们没有自主权力,这种现象正是女性社会人格被歧视与被忽视的反映。
因为童养媳这一婚俗对民俗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等领域均有研究意义,因此不少学者从各个视角加以剖析,学者郭松义指出,清代全国有童养媳记载的州县为561个,而当时清朝州县总数为1724个。①费孝通教授在《江村经济》中虽提及童养媳现象,但只是说有这种风俗,并没有做更深入的探讨,因为这不是该书研究的重点。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武雅士教授(A.Wolf),以研究台湾地区汉族的“童养媳”(媳妇仔)而著名。他在台湾地区北部的“海山”(台北盆地边缘)做人类学研究时,发现该地区闽南系统的汉族家庭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童养媳成婚(称为小婚)的比例极高,有时高达40%以上,几乎要与“正常”的迎娶婚(称为大婚)比例相同了。武雅士教授以此为例,进而延伸讨论了人类婚姻制度以及近亲禁忌(incest taboo)的起源等问题,受到研究家庭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广泛注意。
一般学者都以为养童养媳的主要原因是贫穷,但是武雅士教授发现真实的现象并非如此。一种风俗一旦形成,便会流行起来。他发现在台湾地区北部行小婚的童养媳人家之中有许多是很有钱的富家,而有些富人家中甚至有两个以上的童养媳。武雅士教授借助长期以来对日据时代户籍资料的分析(日据时代户籍资料中有童养媳的记录),形成了一种可称为“婆媳夫妻感情丛结”的假说。他发现由童养媳小婚而形成的家庭中,夫妻关系经常是不好的;至少是冷淡的,然而婆媳关系却较为融洽。他认为在夫妻关系经常冷淡的情况下,却仍然有40%以上的家庭采用童养媳婚,这是传统中国家庭宁愿牺牲夫妻感情,也要维持婆媳融洽关系的因素所致(Wolf,1968,1970)。武雅士教授之所以知道人家夫妻感情不好,除了因为他长期在当地做调查访问(一年以上),对各个家庭细节很熟悉外,还由于他在户口资料中发现,凡是童养媳夫妇其子女必定比行大婚夫妇的子女少,这一数字差别在统计学上有重要意义。由于这一现象的发现,武雅士教授提出几种很有趣的规律性理论来对这种特殊婚姻形态加以阐释:1.传统汉族家庭中,经常是婆媳关系优先于夫妻关系;2.童养媳婚姻中的夫妻通常感情不好,这种情况往往会影响子女人数,因此在盛行童养媳的地区人口成长状况颇不稳定;3.童养媳夫妻感情冷淡的原因可能来自于心理,因为儿童以兄妹的关系在家庭中共同成长,经常会失去“性”的吸引力,易于形成近亲禁忌的心理丛结。因此武雅士教授认为他的这个例子,正可以支持芬兰裔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威斯特马克(EdwardWestermarck)早期所提出的近亲婚姻禁忌是心理学的而非生物学的因素这一理论(Wolf,1970,1994)。后来武雅士教授也因为提出这一假说而得到芬兰科学院的学术勋赏。①
武雅士教授的观点对我们研究畲族童养媳现象虽然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但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性,我们还不能完全套用这一理论来对畲族童养媳现象加以解释。就畲族童养媳婚姻的研究现状而言,迄今为止鲜有这方面的研究性文章发表(笔者尚未找到这方面的资料),也鲜有学者对畲族童养媳婚姻在婚姻中所占比例做深入调查。从笔者了解的情况看,童养媳的婚俗解放前在畲族家庭中并不少见,甚至可以说是常见的婚姻形态,并成为一种社会风俗,这也许与畲族聚居区经济相对落后有关。
童养媳婚姻质量也因人而异,就感情而言,有的夫妇比较冷淡;有的关系开初尚可,后来发生变化;有的是姐弟关系胜于夫妻关系。就夫妻关系与生育子女数的相关度而言,如果童养媳长大后与收养她的家庭的儿子成亲,则子女数的确不多,这似乎印证了武雅士教授的童养媳婚姻中的夫妻通常感情不好会影响子女人数的观点,但如果童养媳长大后被卖或其他原因与另外家庭的男人结婚,生育子女数则另当别论(本篇所附的口述实录可以佐证该结论)。
此外,笔者认为童养婚生育子女数还与生理有关。童养媳婚姻中双方的年龄有一定差距。在武义县畲族的童养媳婚姻中,绝大多数为男方大于女方,这种现象与童养媳产生的方式有关。一般一个家庭只有生下男孩后才会考虑收养童养媳,特别是那些自幼被抱养的童养媳绝大多数会小于其未来丈夫。如桃溪镇种子源村的蓝球妹6岁开始做童养媳,男的比她大5岁,在她未成年时公公婆婆相继过世,所以她11岁时即与16岁的丈夫圆房了,但她到18岁才开始生育。不幸的是孩子很快就夭折了,从此蓝球妹再未生育。当然,童养媳婚姻也有女方年龄大于男方的情况,收养女童的家庭未雨绸缪,在自家没有生育男孩之前,先行收养女童(前面提到的雷新兰,她许配的男孩比她小9岁)。又如笔者曾采访过的一位老人,她18岁成亲时男方只有15岁,她到25岁时方才生育,间隔时间长达7年。这类女比男大的婚姻中的女性,她们的心智往往比男性成熟,因此夫妻关系更像是姐弟关系。通常童养媳夫妇在结婚时,往往一方尚不惜人情,甚至发育尚未成熟,另一方已经成人,因而出现有婚姻之形而无婚姻之实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圆房,他们也很难建立正常的夫妻关系,夫妻往往会在婚后若干年之后才会生育,甚至有的夫妇会终身不育,这种情况与女方的早婚有一定的关系。据一项对印度童婚的调查发现,妇女未成年就已结婚,会有绝育的风险。①学者吴东海在田野调查时发现,畲族领养子女率非常高。他在对畲族4个村27户累计162代的统计中发现:自生儿繁衍后代的有98代,占60.49%;自生女招赘繁衍后代的有20代,占12.34%;领养儿女的有44代,占27.17%。其中领养比例最高的紫阳贯村6户28代中,就有9代领养儿女,占32.14%。所以他认为有的畲族家庭连续4代因没有生育而领养,②这种现象除了经济、体质等原因外,也许与早婚有一定关系。③
与武雅士教授了解的情况不同,笔者了解到在畲族童养媳婚姻中,婆媳关系一般不存在优于夫妻关系的现象,甚至婆媳关系比夫妻关系更为恶劣。笔者调查的有童养媳经历的访谈对象均提到婆婆对她们不好,这种不好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干得苦,二是吃不饱。但笔者认为,这并不能说明婆婆们心狠,而是与生活贫困有关。对于婆婆们来说,童养媳是干活不用付钱的劳力,对靠天靠田里的收成过日子的乡村家庭而言,只有拼命干活才能生存下去,因此婆婆们自己也是每天起早贪黑地苦干。另外,童养媳婚姻中的女童通常在幼年时就被婆家收养,因此,她与婆婆的关系既是婆媳关系也是母女关系,而这一种特殊的母女关系与有血缘关系的母女关系有相当大的差异。事实上,童养媳婚姻中的婆媳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人际关系,是一种绝对的上下级关系。小媳妇必须俯首听命于婆母,没有独立、平等的人格尊严。而从这种特殊的母女关系来看,婆婆与儿媳的情感关系存在着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排斥的现象。作为女性,婆媳对家庭情感的体验会存在一定的相似度,有时需要她们联合起来争取自身的权利。例如,在笔者访谈的对象中就有两代童养媳或三代童养媳现象。因此在童养媳婚姻中,往往三四岁的幼女已经是小媳妇了,而此时她的婆婆也不过30岁左右。过去四五代同堂现象非常普遍,所以通常婆婆上面还有太婆婆、太太婆婆,因此婆婆亦受太婆婆、太太婆婆的支使。某种程度上,婆婆与小媳妇都是受压制的。但是,婆婆的身份毕竟与童养媳不一样,婆婆在家里是有发言权和一定家长权的,而小媳妇在家里只相当于奴婢,在未圆房前,只能以准媳妇身份存在,还不算是家庭的正式一员,因此准媳妇受婆婆排斥就成为正常的事情。菲利斯·切斯勒在其名著《女性的负面》的前言中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女人的竞争对象主要是别的女人,……女人通过诽谤、造谣和躲避相互妒忌、暗中作梗。”①在她看来,女性不仅受男性的压迫,有时女性对女性的压迫更甚,甚至母女之间也是如此。她的观点与早期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地位低是男性压迫的结果并不矛盾,但同时她认为,女性除了遭受男性压迫外,也受到女性本身的压迫,女性(婆婆)无意中成了“男性权威的代理人”②。这种现象在童养媳身上更是显而易见。
附一
“白要”蓝宝珠的口述
2008年夏天,我回武义县作田野调查时,请求居住在柳城乡下的亲戚帮忙寻找上了年纪的曾做过童养媳的畲族妇女。为此,亲戚用摩托车载着我在乡间挨村探访。碰上年龄大的老年妇女,我们就“厚着脸皮”问她有没有做过“白要”。本文的蓝宝妹就是坐在自家门口时,被我们偶遇的。她听到我此行的目的是请她讲讲她的经历,特别是怎么当“白要”的,老人脸上表现出颇不以为然的表情,那意思似乎是说做“白要”不值一提。老人非常瘦削,时年82岁,面容清癯,看得出年轻时相貌不差。以下文字根据其口述整理。
我娘家是柳城车门村(车门距柳城约5里路)的,我3岁就死了父亲。后来我娘改嫁,我跟着娘到了后父家。娘和后父生了三四个弟妹,家里人口多,养不过来,7岁时我被送到白姆下村做“白要”。那户人家家境也不好,住的是茅草屋,为了防屋漏,每年的10月左右要将屋顶的稻草重新铺换一次。我8岁时就要一个人看头大水牯,这牛是从财主家租来的,每年要交租给地主,租量是100斤谷。田也是向财主家租的,冬天种大麦、小麦和米麦。米麦比小麦早半个月收割,这样接得上吃饭。稻子每年种一熟。
我做“白要”这家的儿子比我大4岁,家里送他出去读书。我呢,一天到晚忙着干活。天有一点点亮光就起床,出门割草喂牛,牛要吃饱才有力气耕田。接下来我要拔猪草喂猪,还要做其他农活。不到天黑,基本上没坐下来的时候。就这样卖命做,那家也没把我留下。在我19岁时,他们把我转卖到了石井山村,卖了1000多斤谷。之前我并不知道要卖我,直到双方谈好了,对方来要人的时候我才知道。事情到这地步,你不去也得去,如果不去,那就把你捆在长条凳上像卖猪一样绑好抬你走。
我被卖过来的这户人家的家里只有兄弟两个,我嫁的是老大,他也是苦命人,16岁时父母双亡。19岁时讨了我,我们俩是同岁,他对我还好。我嫁过来时,小叔才12岁,家里只有一间茅草铺。22岁时,我有了第一个孩子,后来陆陆续续生了8个,养活了6个,死了2个。活下来的正好3个儿子,3个女儿,其中2个女儿送给别人了。因为家里困难,除了一个儿子是请人接生的,其他都是我自己包的,怎么包的我请教过村里的老人,小孩生下来以后,先把小孩的脐带拉至小孩的膝盖处,拿剪刀剪断,余下的脐带用苎麻线扎紧,拿些棉花压盖在脐带上,最后用破衣服包裹好就行了。生小孩时,自己将小孩包好就没有力气了,懒在床上,身上发冷,连烧饭的力气都没有,就只好饿着。等丈夫耕田回来后,丈夫烧点吃的我吃吃才起得了床。坐月子期间我照样要下床洗衣服、做饭,只是不用下田干活了。
因为家里没老人,所以,小孩生下来以后也没人照料。有一回,我把大女儿放在床上,自己去地里干活。不料,她从床上掉到地上,自己又爬到门边。结果,我地里回来一推门,正好撞到女儿的鼻子。我当时就“啊呀”了一声,以为鼻子撞坏了,要破相了。后来幸好没什么大的印记。
解放后,当时家里分到6亩田,人均1.2亩。但是田地比较贫薄,加上没什么肥料,产量不高。去除交的公粮,做饭时要掺点其他的东西,这样才能吃八九分饱。我们夫妻俩拼命做,后来开始造房子,慢慢地造了三间瓦房,是儿子大了以后一点一点扩建的。我们后来还帮小叔子娶了妻,一年半以后才分的家。
70岁以后,日子好过了。
附二
“白要”蓝新妹的口述
蓝新妹是我所有访谈对象中年龄最大的畲族女性,89岁(2008年),她身材瘦小,但眼不花,耳不聋,描述起往事来仿佛历历在目。陪同我去的亲戚是该村村长的儿媳,可爱的老太太知道她的身份后,直夸她漂亮、可爱,这也可看出老太太脑子好使。下面文字根据2008年8月期间我所做的访谈笔记整理。
我娘家是柳城周处村的,家里很穷。娘生过七八个孩子,但是只养活了三个:我、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11岁时,被送到柳城白姆下村做了两年“白要”。我去的那户人家住在山头上,婆婆非常厉害。她的儿子比我小一岁,但她从来舍不得打自己的亲生儿子,就打我,用赶牛的毛竹条打。毛竹条上细下粗,婆婆就把它倒过来,用粗的那头打我,我的膝盖、腿上经常被她打得都是血。
婆婆还不让我和他们一家住,他们家有两间房,住得下我但不让我住,让我一个人单独住在一户死光了人的无人居住的茅草屋里。床是用木板搭的,下面垫一些稻草,上面的被子就是几块不成形的破棉絮。一到晚上,婆婆也舍不得让我点灯,屋里黑乎乎的,没有亮光,非常吓人。晚上我好像看见有个东西在我床前摇摇晃晃并发出“嚎嚎”声。我吓得赶快用被子蒙住眼睛,不停安慰自己:眼睛看不见就不怕了。
做“白要”的两年,我每天要放牛、砍柴、割草,从没穿过鞋子,草鞋也没得穿,冬天也一样。下雪天的时候,我身上只有两件单衣。吃的是他们家的剩饭,碗里大都是番薯丝,没几粒米,也没有菜。婆婆不准我和她的儿子玩,怕我玩了不干活。那日子苦啊,我实在吃不消了,就一直想逃,有一天终于下定决心要跑回娘家。离开家两年了,我一下子找不到回家的路。我光着脚从早上一直走到下午,脚磨得很痛,终于到了柳城的北门头,别人告诉我只要一直沿着石板路走,就能找到我自己的娘家所在的村庄,多亏了别人指路,最后我回到了家。
我回娘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自己做了一双布鞋穿。在娘家我还是没得吃,但没人打我了。唉,那时候是饿大的。家里经常只有番薯吃,番薯整钵头地煮,饿了就拿一个吃。在娘家我一直待到17岁,后经一个亲戚做媒,嫁到这边的陈弄村。婚事定下来以后,男方拿了一点钱过来,我家打了一对木箱、一个方桌,另备了可以做五件衣服的布料作为我的陪嫁。我出嫁的那天有鞋子穿了。
我丈夫比我大3岁,是独子,他家里也很穷。往往是有了早饭,就没了中饭,有了中饭,就没了晚饭;常常是水烧上了,米不知在哪里。每顿饭吃多少米由婆婆决定,米快下锅时,婆婆会将盛出来的准备做饭的米又倒回一点到放米的口袋里。因为婆婆经常出去借米,到别人家借多了,她不好意思出去借,就叫我去借。烧饭烧饭,其实那不叫饭,只是杂食,里面掺了番薯丝、野菜之类的东西,而且掺的东西比米多。我刚嫁过来时,夫家的房子是没有板壁的,只有柱子,四处漏风。板壁是后来慢慢添上去的。床算是有的,叫米床。①因为这种床像打米用的水磓一样四周有栏,所以叫米床。这种床的好处是小孩不会掉下床。
我嫁过来的第二年,有了第一个孩子,但没过多久就死了。后来陆陆续续又生了四个,只有19岁那年生的一个孩子活了下来。为了过日子,有饭吃,我们夫妻俩发狠做,到地主那里租田种。租来的田离家很远,在十几里路以外,桃溪的西塘村那边。②我每天天刚见亮光就出门做,晚上看不见了才回家,中午还要回去给孩子喂奶。
辛辛苦苦种田,收割后,除了还债交租,就没剩多少了,所以还是吃番薯。只是在坐月子时家里人照顾我,不用吃番薯饭了,改吃米饭,偶尔还有鸡蛋吃,姜汤喝。月子期间家里的活还是照样要干的,就是不用下田干活。但是小孩满月后就必须做了,今天满月,明天就下地了。
苦是苦,但夫妻感情还可以,有时会为了孩子的事情吵嘴干架。
附三
“白要”蓝陈爱的口述
蓝陈爱与我的亲戚同村,而且是我亲戚的亲戚。辈分上,我的这位亲戚该称呼她为大伯母。因此,我亲戚约了她到自己家里,边吃点东西、喝点自制的烧酒边聊。老太太看上去身体相当不错,时年83岁,个头在同辈里面算高大的。下面文字根据2008年8月期间我所做的访谈笔记整理。
我娘家在柳城内潘村。家里姐妹7个,另外还有一个弟弟,我排行老二。7个姐妹中有两个做“白要”。我四五岁时,就被背走过,送到白姆下村。知道这件事后,叔伯家的姑姑冲我父亲骂道:“给人家不如做水坝!”①父亲被骂后就把我背了回来。但是7岁时我又被背到鲍畈村。
我到的这户人家家里四口人:太奶奶、公公、婆婆及公婆生的一个独养儿子。家里原来有亩把田,但太奶奶过世时,卖了五分田出丧。婆婆有大脖子的毛病(即因缺碘引起的甲状腺肿大),脖子上掉下来的肉要用布条挂起来,头低不下来,粗活特别是吃力的活干不了。公公干活还行,就是有点懒。独养儿子被送出去读书,他与我同年。
我刚过去时还小,重活干不动,但是要拎着篮子出去捡柴火和拔猪草。稍大一点,十来岁的时候,除了要拔猪草,还要下田插秧、上山去砍柴,从那时开始,家里的柴火全是我砍回来的,一个人干活没伙伴,太高的山不敢爬上去,只能在山脚路边砍点矮的灌木丛背回来。爬山砍柴时没有鞋穿,砍柴也很吃力,我经常边砍边哭,哭归哭,没人管你,活还是要干的。
“白要”的地位是很低的,只要家里来客人,我就不能上桌吃饭。一年难得能吃上肉,即使有肉,碗里大部分也是汤,大概只有三四片肉,你也不敢夹过来吃。过年的时候,能吃上三天不掺番薯丝的米饭,但三天后就吃不上了。
我是17岁时圆房,圆房也没什么仪式,就是在公婆家里吃碗面条。公婆给我做了一套新衣服和一双新鞋子,另外给我们准备了婚床,是四周有栏杆的米床。我和那个男的有10年的婚姻,其间,他曾经不肯去读书,婆婆就骂我,我就劝他,读了书就长了本事,这是任何人包括他母亲都拿不走的东西。丈夫在我的劝说之后又回去读书,后来当了老师,而且参加了革命。因为参加革命,曾经被国民党抓到丽水坐牢,一直到解放后才放出来。他被抓的时候,我和婆婆走到丽水去看他,天下着雨,路又不好,走到丽水时我的十个脚趾头的指甲盖已经全部脱掉,翻出来的全是带血的肉。
后来他变心了,要和我离婚。我不肯,哭啊哭,从床上哭得滚到地上,他还是要跟我离。人心变了,没药医的,但是我劝他读书这件事情上,他还是说我好的。与前夫离掉后,经人介绍,我到了这边的锦平村,一直和老伴生活到现在。两次婚姻我都没有孩子。
感想
武义乡间曾经流传过这样一首名为《童养媳》的歌谣:
正月梅花带雪开,想起前景真伤悲,七岁做了童养媳,从此爹娘都分开。
二月杏花开园中,公婆待我真当凶,做牛做马饭不饱,挨打挨骂过春冬。
三月桃花开得红,牵头水牯到山中,水牯一时无踪影,丈夫打我全身痛。
四月蔷薇红墙外,姑娘(指小姑)做人也厉害,公婆面前弄是非,害我天天流眼泪。
五月牡丹开得艳,肚中饿得似熬煎,偷吃一碗生冷饭,婆婆要我饿两天。
六月荷花开水中,病在床上真苦痛,口干无人端茶水,还说偷懒装病痛。
七月水仙盆中开,偷偷摸摸娘家归,路上一把被抓住,拳打脚踢捆起来。
八月桂花满树金,公婆硬逼我成亲,可怜我只十三岁,花还未开被蜂采。
九月菊花开满园,丈夫嫌我长麻脸,一日打我两三次,三餐骂我货真贱。
十月芙蓉花开放,心想离婚再嫁郎,可恨保长没道理,嫁鸡随鸡压一方。
十一月里腊梅香,来了救星共产党,提倡婚姻要自由,不许包办由爹娘。
十二月里雪花飞,离了火坑出苦海,政府做主离了婚,自找对象自己爱。①
这首民谣真实地描绘了童养媳婚前辛酸的生活,以及婚后毫无幸福可言的婚姻状况。人们通常用花来比照女性,但在这首歌谣中,自然界美丽怒放的鲜花与童养媳悲惨境遇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得这首歌谣更具感染力和冲击力。
童养婚是一种畸形的婚姻形态,是正规婚姻的重要补充形式,这种特殊的婚配形式决定了童养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从婚姻目的来看,童养媳婚姻主要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从夫妻关系来看,婚配双方年龄上的不协调会引发诸多问题,男女在不更人事之时便有了夫妻名分,承担起除生育之外的诸多家庭责任,所以童养婚中夫妻恩爱的不多见。由于童养媳的角色由女性来扮演,因此她们的经历让我们对贫困家庭的畲族妇女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与家庭生活形态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附注
①当地畲民称童养媳为“白要”,即白给的(女人)。
①滋賀秀三:《中国家族法の原理》,第465页,转引自《卖身文书与婚姻(变例婚)文书所见女性的地位与权利》,载http://www.cctv.com,2009年9月9日。
①钟发品先生为武义县本土著名的畲族文化研究者。
①见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52页。
①见http://www.qzwb.com于2006年8月22日所登的转引自中央文献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的《学术泉州》中的文章:《“泉州学”的新视野》,李亦园。该作者系台北地区“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人类学家。
①见2010年5月26日网易探索新闻:《印度童婚调查:45%的女孩早于十八岁结婚》。
②见吴东海:《略论畲族社会生活中的母系制残余》,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③吴东海的文章没有分析结婚年龄与生育的关系。
①见菲利斯·切斯勒著,汪洪友译:《女性的负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②见李银河:《两性关系的历史与现状》,《李银河自选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李银河在论述中国的父权制时,认为中国传统婚姻中常见的婆婆控制媳妇其实质为婆婆乃“男性权威的代理人”。
①讲述者特别强调米床,是因为当地更穷的家庭结婚时的床,仅仅是几块木板搭就的简陋无比的床。
②解放前的畲民非常贫困,据柳城堰下村的调查:1949年,堰下村有畲户29户、112人,畲民仅有水田2.2亩,人均不到二厘田。除屋基旁零星的几块菜地外,他们没有一块山地,29户畲民均向地主租田租山耕种。原泽村乡黄新村,1949年有畲民15户、53人,只有7亩水田、12亩山地,人均一分田二分地,租种地主土地32亩。水田离该村很远,最远的坐落在10多华里的山陇里,这些水田水利条件差,土地肥力低,一年只能种一熟水稻,亩产也只有250斤左右,而每年交的租谷却有150斤。遇到歉收的年份,交了田租就所剩无几,往往是“镰刀上板壁,肚皮饿瘪瘪”。(资料来自政协武义县文史资料委员会2006年编的《武义畲族史料》,第15页)
①农村一般用石头、泥块做“水坝”。此句“做水坝”意为女孩的命太贱。
①见王群、唐桓臻著:《武川记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6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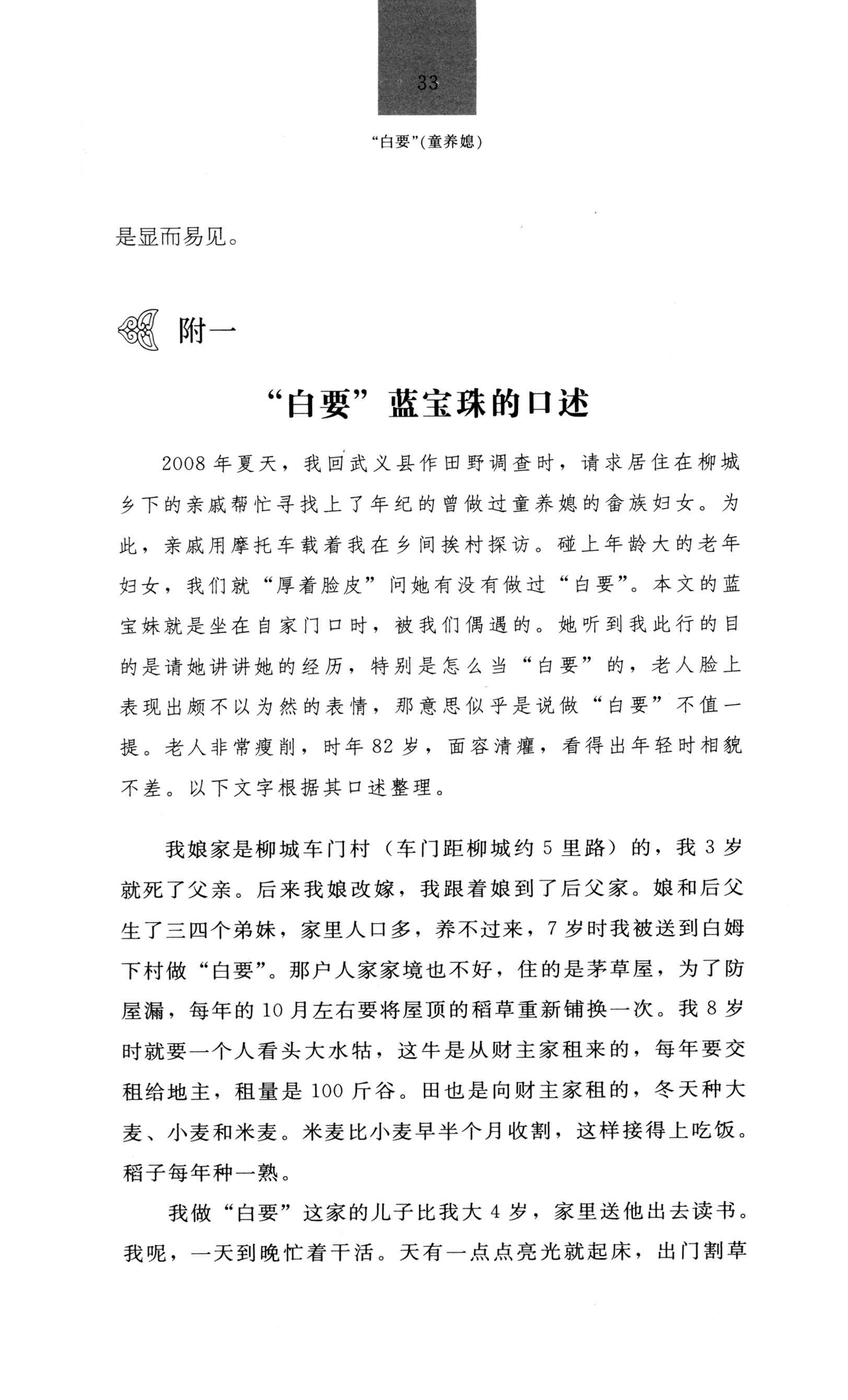
相关机构
美国斯坦福大学
相关机构
相关地名
武义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