畲族乡村发展成效与问题反思
| 内容出处: | 《当代视野下的畲族文化》 图书 |
| 唯一号: | 130920020230005954 |
| 颗粒名称: | 畲族乡村发展成效与问题反思 |
| 分类号: | F592.757 |
| 页数: | 10 |
| 页码: | 412-421 |
| 摘要: | 从乡村发展概念内涵变迁视角而言,现代乡村发展观是乡村社区全面、综合、和谐的可持续发展,而目前我国畲族乡村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特色村寨等方面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从乡村发展模式、发展组织制度、乡村资源开发、乡村发展主体意识以及乡村全面发展等方面仍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因此有必要借鉴中国台湾社区营造经验,通过乡村发展理念转换和社会制度创新,完善知识服务社会的畅通机制等方式来进一步深化畲族乡村发展进程。 |
| 关键词: | 畲族 乡村发展 社区营造 |
内容
畲族是我国东南山区一个历史悠久、散杂居程度较深的山地农耕民族。现今70余万畲族人口中仍有70%以上为乡村人口,且主要集中分布在闽东和浙南一带。自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随着国家对少数民族政策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当今畲族乡村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卓越成效。但由于深受历史文化传统和现有资源禀赋的制约,畲族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仍总体滞后于当地汉族,畲族乡村发展与我国东南发达区域经济尚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基于此,本文从乡村发展概念内涵变迁入手,对畲族乡村发展的既有成效和存在的问题予以分析,旨在总结经验,找出不足,以期寻求进一步发展的新路径[1]。
一、乡村发展概念内涵变迁梳理
要思考畲族乡村发展问题,首先有必要从洞悉乡村发展概念的内涵入手。乡村发展概念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日益丰富和完善。早在1971年,美国经济学家韦茨(Raanan Weitz)在其编印的《变迁世界的乡村发展》(RuralDevelopment in a Changing World)一书中指出:乡村发展着重在低度开发国家寻找能促进发展过程的策略,当前尤为注重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理论方面的研究[2]。从韦茨编印的书中可知,乡村发展的内涵是针对发展滞后国家的人民经济生活贫困,如何寻找促进解决方法。而世界银行在1975年给乡村发展下的定义是:乡村发展是一种策略,拟用为改进乡村贫穷人民的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利益延及在乡村中寻求生活的最贫穷团体,包括小农、佃农及无土地者。其强调乡村发展的目标在增加生产、提高生产力、增加就业、动员可用的土地、劳力及资本,同时也注重消减贫穷及所得的不均[3]。世界银行的乡村发展定义较之韦茨所概述的内容更为丰富,目标更为明确和具体,但二者均属于浅表层次的,主要是针对解决贫困人口的生活困顿问题而言。巴基斯坦学者伊纳亚图拉(Inayatullah)在1979年编印的《乡村发展的研究,亚洲的若干经验》(Approaches To Rural Development,Some Asian Experiences)一书中,其乡村发展内涵着眼于三个方面:(1)传播适当及改进农场技术的过程;(2)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中的人民接触外界而产生新技术与新态度的过程;(3)包含技术、社会、文化与政治等因素的复杂过程[4]。如果说世界银行有关乡村发展的概念主要着眼于消除经济贫困,保障基本生活,显然伊纳亚图拉(Inayatullah)所理解的乡村发展概念内涵要更为丰富,它是由相互联系的三个过程所组成:既包含新技术、新观念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也包括乡村人接受技术的能力、态度及其做出相应的改变这一互动过程,还包括技术、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复杂过程,显然该概念触及到了乡村发展中的多种社会关系。
而澳大利亚学者戴维(David A.M.Lea)和乔德利(D.P.Chaudhri)在20世纪80年代则提出“整合的乡村发展”概念,主要涵盖四个方面的内容:(1)改善乡村大众的生活水准;保障基本安全及对衣、食、住、行和就业等方面的基本需求;(2)增进乡村地区的生产力,免受自然的灾难,并改进与其他部门的互惠关系;(3)提倡自立的发展计划,并使大家都参与发展计划;(4)保障地方的自立性及减少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干扰[5]。这两位有关“整合的乡村发展”的定义虽然总体上仍是着眼于基本的经济生活保障,但他们提出了自我发展和大众参与的发展新内涵,还提出乡村人与社会关系的改进,以及在避免现代化对传统方式干扰的基础上寻求地方的自立性发展。这实际上已经注意到了乡村发展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问题,还将盲目追求现代化而破坏乡村传统的发展区别于真正的乡村发展,这体现了传统与现代和谐并存的宝贵思想。
无论如何,乡村中有待发展的事务是纷繁复杂的,随着众多西方学者的研究,学界逐渐达成共识:乡村发展的内涵既是整合性的,也是多面性的。台湾学者蔡宏进认为:广义的乡村发展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水准之提升。发展的目的除了改善乡村居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条件外,还可以提升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准[6]。从发展人类学的眼光来看:发展是一个综合的指标,包含着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等方面的多层次需求,发展的本质归根到底是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以人为本,人既是发展的主体,也是发展的动力,而发展的方式则是可持续的而非竭泽而渔式的,社会的发展包含着重要的人文发展指数[7]。从现代社会发展观而言,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之一,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发展的意蕴是人类文明以及人与自然状况的改善、进步和提高。发展不同于增长,增长主要表现为量的增加,而发展是指量和质的共同提高;发展也不同于一般的变迁或变化,它是一种朝着更好、更文明和更高方向的变迁。而社会发展是发展的核心内容,其意义在于人类在不断提高生产能力的同时,要使更广泛的人享受到更多的生产成果,要为人们的生活创造可持续的、更美好的环境。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涵盖: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社会福利、生态环境等多个方面,其宗旨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普遍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促进区域的均衡发展和推动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8]。
可见,社会发展既包括物的发展,也包括人的发展,还包括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等多重关系的和谐发展。具体到乡村发展,其内涵也是全面和综合的,不仅仅指的是乡村居民衣食住行等经济指标的增长,还包括其身心健康、闲暇娱乐等精神生活品质的提升,更包括他们享有自由民主和参政议政权利,实现自我价值、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等多方位目标。乡村发展目标,不是以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而是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传统与现代的协调中可持续发展。而乡村发展方式,则是联合国一直强调和鼓励的“以人为中心的内源式发展。”[9]
二、畲族乡村发展成效概览
自新中国成立后,畲族结束了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长期边缘化地位,畲族社会经济文化水准逐渐获得质的飞跃。尤其是近十余年来,随着国家政府对少数民族新农村建设扶持力度的日渐加大,浙、闽、粤、赣、皖等省各级地方政府也对畲族这一世居少数民族的新农村建设尤为重视。正是在各级相关政府部门的财政支持和战略指导下,我国畲族乡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主要体现在:村民自治、能人治村等乡村治理方式的摸索前行;交通道路、民居改造、环境治理等村落基础设施建设的日臻完善;农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山林特色经济资源的产业化;畲族农民人均年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和文化教育程度的普遍提升;文化广场、文化礼堂、畲乡风情广场等村落社区文化空间的修建;“三月三”畲乡风情节等传统节日的普遍复兴;畲族民歌、祭祖、编织、武术、谚语、节日等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逐级申报及对相关传承人的制度保护,等等。
尤其是近五年来,畲族特色村寨建设工作卓有成效。自2009年国家民委和财政部联合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以来,各地畲乡畲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亦紧锣密鼓地跟进,经过5年的努力,至2014年,闽、浙、粤、赣、皖等五省共有19个畲族特色村寨被国家民委列入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单(全国共有340个)。其中,福建省9个:福州市连江县东湖镇天竹村、南平市延平区水南街道岭炳洋村、三明市永安市青水畲族乡沧海村、漳州市漳浦县湖西畲族乡顶坛村、漳州市华安县新圩镇官畲村、宁德市蕉城区金涵畲族乡上金贝村、宁德市蕉城区八都镇猴盾村、宁德市福安市穆云畲族乡溪塔村、宁德市霞浦县溪南镇白露坑村;浙江省6个:杭州市桐庐县莪山畲族乡中门民族村、湖州市安吉县章村镇郎村村、温州市平阳县南雁镇堂基村、丽水市莲都区大港头镇利山村、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东坑镇深垟村、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大均乡李宝村;江西省2个:赣州市赤土畲族乡青塘村大岭背组、吉安市青原区东固畲族乡江口民族村蔡家垅自然村;广东省1个:汕尾市海丰县鹅埠镇红罗畲族村;安徽省1个:宣城市宁国市云梯畲族乡千秋村,以上这些榜上有名的畲族村落被誉为“民居特色突出、产业支撑有力、民族文化浓郁、人居环境优美、民族关系和谐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10]
事实上,除了以上国家民委首批正式命名挂牌的畲族特色村寨以外,闽、浙、粤、赣等地畲乡还有许多成效显著、方兴未艾的畲族特色村寨。诸如:浙江省文成县黄坦镇培头民族村、泰顺县司前畲族镇左溪村和竹里村、景宁畲族自治县鹤溪镇敕木山村、丽水市莲都区老竹畲族镇沙溪村、临安市於潜镇铜山民族村,等等。畲族特色村寨建设项目的试点推进,深化了畲乡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促进了畲乡民俗风情和乡村休闲旅游业的发展,推动了畲族文化与经济的良性互动。
畲族乡村发展上述诸成就的取得,是基于各级政府政策性支持和广大畲族村民积极进取的共同产物。例如,自2003年浙江省政府斥巨资实施村村通公路的康庄工程以来,宽广平坦的公路才逐步延伸至昔日地处僻壤的畲村,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让畲村山林经济资源的开发和畲乡旅游经济的发展具有现实可能性。而各地畲乡新农村建设项目的深入开展,尤其是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试点工作的顺利实施所带来的畲乡巨变,更少不了各级政府所提供的可观的少数民族特扶资金。当然,在畲族乡村发展进程中,广大畲族村民(尤其是那些热心村落发展事务的村落精英们)也为此付出了大量辛勤的汗水,他们充分发挥村落建设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利用区域经济辐射的优势和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优惠,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和超越大山的精神,克服传统的农耕思维模式,淡化族群封闭心理,进而从根本上扭转昔日畲村的贫困局面。
三、畲族乡村发展问题反思
然而,笔者通过在浙南畲村点面结合的田野调查不难发现,畲族乡村的发展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归来起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发展模式而言,自上而下式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是一把双刃剑。长期“以山为基、以农为本”的畲族村落由于受区位环境和历史传统的双重制约,总体上经济基础薄弱、经济结构单一、发展起点低,故其发展大都依赖各级政府的财政支持和民族政策扶持,采取自上而下式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从辩证的观点来看,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具有规划细致、布局全面、资源集中、行动高效等优势。这些优势对低起点的畲族乡村发展的启动和推进尤为重要,事实上,其成就也不菲。但从长远发展来看,该模式也存在着内源性发展动力不足的弊端。一方面,畲族村民因自我发展能力弱而过度依赖政府的财政扶持,另一方面又因长期习惯依赖政府资助而寻求自我发展或社会力量参与的制度创新意愿和动力不足,进而难以发育形成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和个体充分自由表达、实现自我价值的完善机制,最终影响畲村的可持续发展。自我发展能力弱与过度依赖政府两者之间互为因果、恶性循环。尤其是在畲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面对民居新旧杂陈、道路狭窄不平、环境脏乱不堪、改造工程复杂浩大等局面,往往会出现摊子铺得过大和资金缺口严重等窘况,进而陷入如何进一步“向政府要钱”和等待“政府拨款”的被动发展境地。
其次,从发展组织而言,畲族乡村治理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简言之是指对乡村社区的组织管理和制度安排,其宗旨是服务农民、解决民生、推动乡村发展。自1983年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被正式宣告结束后,不久建立了乡(镇)政府、村委会、村民小组这一新的农村建制,凸显了乡镇政权的主体地位,迎来乡村治理新模式。国务院对乡镇组织的职能有着十分明确的界定:除政治职能外,对乡村社区经济活动限于宏观管理范畴,主要是政策指导、统筹规划、组织协调和服务监督。自2002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后,村民自治制度广泛实施,我国广大农村普遍建立了村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村经济联合社、村民代表大会、村民理财小组等多元化基层农民组织,新的乡镇治理机制逐步形成。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业产业化的需要,许多农村还成立了各种类型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以及社会性民间组织[11]。从以上政策法规到组织框架来看,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可谓日臻完善。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各级组织的职能角色却出现了错位、越位和缺位等现象[12]。该现象在少数民族社区因社会发育程度低而表现得更为突出。
就畲族村落而言,乡村治理有待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大分散、小聚居”的地理分布格局,使畲族村落打上了更多的血缘、地缘等传统社区色彩,这与现代社区的适应性和开放性相抵牾;大量中青年农民外出打工经商,村民社会结构复杂、村落基层政权组织力量分散、文化程度总体偏低、村民自治难度大和效能差;随着政府对畲村公共事业投入力度的增大,乡村治理内涵扩大、任务增重,村落基层组织越来越力不从心;随着畲族村民社会流动的日益频繁,其思想观念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政治经济诉求和参与意识日益强烈,但现有的乡村治理模式难以完全满足畲族村民的多元化要求;畲村“能人治村”模式虽有利于推动滞后畲村的发展进程,但能人大都在附近城市经商,村落事务与家庭生意两头兼顾,疲于奔波,也存在着“能人异化”的隐患,“能人与贤人”完美结合治村的理想目标与现实还存在着很大的距离。
此外,各级地方政府有关畲村发展的职能配置还有待优化。近年来,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民宗局、农业局、旅游局、文化局以及乡镇政府各部门等)对畲村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引领,可谓工作出色和成绩不菲,但其工作的重点主要放在项目的推广与实施中,对畲族文化特质和畲族文化心理的了解程度还有所欠缺,因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过走弯路、重复投资等现象,项目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可见,地方政权(尤其是乡镇政府)与畲族村民的互动还有待深化,对畲村发展的指导、协调、服务等职能作用还有待加强。
再者,从资源开发而言,山林资源和人文资源的开发力度还有待深化。近十余年来,许多畲村加大了农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和农业产业化的进程,通过挖掘山林经济资源潜力,逐步实现了畲村由传统生存型农业向现代特色农业产业化的转型,村民经济水准大幅度提升。但山林经济资源潜力还远远挖掘不够,主要表现在品种类型比较单一、缺乏精细化深加工、产业化组织模式不够完善、企业品牌意识不够浓厚等方面。事实上,位处东南山区的畲村山林经济资源十分丰富,可开发的经济林木涵盖十大类型:干果类、水果类、油料类、药材类、调味类、蔬菜类、饮品保健类、编条类、工业用材及其他资源类。但目前各地畲村开发的品种主要为茶叶,以及少量的板栗、油茶、毛竹、青钱柳等,还有大量的经济林木可以开发,诸如:干鲜水果、竹笋、蔬菜、中药材以及食用菌等。此外,目前畲村在山林资源开发中,除茶叶产业化程度相对较深以外,大部分农产品为初加工,附加值较低,即便相对成熟的茶叶企业也存在着产业化组织模式单一、经济合作社名不副实、品牌意识不够深厚等弊端。
近年来,各地畲乡虽然涌现出一批环境优美的畲族特色村寨,彰显了畲族文化魅力,促进了畲乡旅游经济的发展。但总体而言其畲族人文资源潜力挖掘不够充分,畲族文化内涵表现不够丰富,呈现出畲族文化单一化、形式化、符号化、同质化等弊端。例如,畲乡旅游展演主要为婚嫁和对歌习俗,品尝麻糍、乌米饭等特色食品,至于编织蜡染、银饰制作、武术体育、草医药技艺等文化精粹的开发尚涉及不多。还有大量的村落历史、传说故事等人文资源尚未加以整理。在畲家乐旅游经济运营中,畲族文化特色不足,同质化现象明显,文化内涵不够,更缺乏具有文化创意的旅游项目和旅游产品。而且畲村民居以“畲元素上墙”的方式来彰显畲族文化特质,具有形式化和符号化特征。此外,各地普遍兴起的“三月三”畲乡旅游风情节,注重文化展演的形式,而忽略文化的本真意义,对热情热闹和盛大场面的追求,远远胜过对文化意义和经济效益的追求。节日载歌载舞的表演者大都是雇请来的汉族专业演员,大量的畲族村落民间文化艺术人才逐渐被边缘化,而且畲家乐旅游经济受益面总体不广。因此,畲族特色村寨还需要进一步整合山林资源和人文化资源,强化文化创意,凸显民族特色。
再次,从发展本质而言,人的自由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指标。人类发展的理念以20世纪70—80年代为分界点,经历了从传统的发展观到新的发展观的转型。前者将发展片面理解为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经济指标的增长,后者将发展理解为以人为核心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1976年国际劳工组织首次论述了“人”的发展,认为经济发展首先必须满足人的基本需要。随后联合国制定的第三个十年发展计划(1981—1990)不仅规定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量的目标,而且还规定了经济发展的质的目标,即社会进步的目标,如公平分配、充分就业、普及教育、培训劳动力、提高健康水平、改善住房条件、保障妇女儿童的正当权益等。时至1992年,联合国在第一份《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运用人文发展指数(HDI)这一新概念,意即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这三项基础变量按照一定的计算方法组成的综合指标来考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状况,后又补充了生活环境和居民自由程度等两项变量。人文发展指数概念的提出丰富了“发展”的本质内涵。与此同时,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由理论探讨范畴推向人类共同追求的实际目标,从更高的视角寻求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13]。
从新的发展观可知,发展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综合概念,既包括经济生活水准的提高,也包括人的健康理念和文化教育程度及生活品质的提升,还包括基础设施和居住环境的改善以及自由发展和平等参与目标的实现等,更包括既满足当下需求又满足未来需要的可持续发展。就近十余年来畲族乡村发展状况而言,无论是经济生活水准、还是居住环境质量和文化教育水平等方面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从健康理念、居住环境、生活品质、闲暇娱乐以及自由发展、抗风险能力等方面来看,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例如,近十几年来畲族村民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食物结构有了很大的变化,餐桌食物品种日益多样化,但由于健康知识的匮乏,偏好酒肉荤腥和多盐多油食物,加之因“番薯丝吃到老”的痛苦历史记忆而对番薯等粗粮心理排斥,甚至有的上山劳动也以酒解渴,故畲族这个善酒的山居民族,更容易患上心脑血管等疾病。因畲民抗风险能力总体不高,倘若家中有人犯有重大疾病,其家庭生活质量势必一落千丈,少数家庭甚至一蹶不振。再如,畲村垃圾处理排污设施等虽然逐渐完善,但填埋式垃圾处理方式和塑料制品白色污染等对畲乡土地资源的潜在威胁仍不容忽视,大量的城市非安全食品涌入畲村,亦值得警惕。此外,畲村社区文化建设总体投入不足,乡村图书室等文化设施普遍匮乏,畲民的身心健康和精神生活较少关注,畲民精神娱乐生活比较单一,旅游休闲的机会比较少。
最后,从发展主体而言,农户发展与村落发展不平衡性仍较为明显。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国农村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许多畲族农民通过外出打工经商逐步发家致富。然而,中青年的长期外出,不仅导致畲族农户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更导致畲村发展的“空心化”或“半空心化”趋势以及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虽然打工经商发家致富不少,但村落经济基础和集体经济力量依然总体薄弱。事实上,外出打工经商农户的发展并不等于畲族村落经济的发展。尽管并不排除外出打工经商户的发展有助于带动其他农户的家庭发展,但总体而言,外出农户的发展对村落整体发展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相反,畲族村落的整体发展,则必然会提升广大畲民的村落凝聚力和自豪感,同时缩小农户之间的内部差异,尤其有益于保护年老贫病畲民等弱势群体。例如,近三十几年来浙南文成县培头村钟姓畲族村民大都依靠外出打工经商(包括至省内外,甚至国外),获得可观的经济收入和良好的家庭发展,但培头村作为村落整体却长期以贫困面貌和低度发展呈现。直至近年来,随着民族特色村寨的社区营造,培头村犹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享誉四邻八乡,更牵引着无数在外发展的村民回归村落,并主动参与到家乡建设中来。这反映出许多高收入钟姓畲族村民对家乡发展的自豪感远胜于在外面发家致富的成就感。再如,自改革开放之初,景宁、武义等地不少畲族村民陆续至我国各大中城市经营超市而收入不菲,他们大都在家乡修造了气派的新楼房,但仅在春节期间小住几天,平时基本空置。对于这些离乡的富裕畲民而言,其内心升腾的自豪感并非来自自家楼房的引人注目,而是近几年畲族特色村寨建设,村落整体面貌的改观。然而,畲族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村落集体经济的总体薄弱现象仍不容忽视。总之,唯有畲族乡村整体的发展才是畲族发展的关键,也只有畲族乡村的整体发展才是真正和谐、全面的畲族发展,才能从根本上缩小畲村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
结语
乡村发展概念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日渐丰富,既包含着经济指标,也包含着人文指标、环境指标及可持续发展指标等。而近十余年来畲族乡村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经济、文化、教育水平获得大幅度的提升,涌现出一批环境优美、产业活跃、生活富裕的民族特色村寨,但也存在着过度依赖政府、资源潜力开发不足、产业化程度不深、全面发展程度不够、畲汉差距明显、村落内部发展不平衡等诸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深化畲族乡村发展进程,有必要借鉴中国台湾社区营造经验,探索畲族(也适应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自己的乡村社区发展路径与方法。具体措施包括:通过发展理念转换和社会制度创新,建立知识服务社会的畅通机制,整合以高校为核心的知识分子力量,开设社区营造系统课程,增强社区营造整体文化氛围,培育更多关心各民族乡村社区营造的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队伍,组建社区营造专业工作团队,深入各民族乡村社区全程帮扶,鼓励和支持高校及科研机构大学生、硕博研究生们毕业后返乡再造魅力新故乡。唯有通过政府部门的政策指导和制度支持、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引领和体系化的社区专业培训,才能逐步增强村民的公共参与意识、文化自觉意识及社区主体意识,才能不断提高其自我组织和自我发展能力,进而将“一袋马铃薯”[14]式的传统农民蜕变为视野开阔、凝聚合作的现代社区人, 各民族的乡村发展方能获得持续的内生性动力。正如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拉尼(Polanyi,K.)所云:人类的经济,是嵌合并陷于制度、经济的和非经济因素之中的[15]。
一、乡村发展概念内涵变迁梳理
要思考畲族乡村发展问题,首先有必要从洞悉乡村发展概念的内涵入手。乡村发展概念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日益丰富和完善。早在1971年,美国经济学家韦茨(Raanan Weitz)在其编印的《变迁世界的乡村发展》(RuralDevelopment in a Changing World)一书中指出:乡村发展着重在低度开发国家寻找能促进发展过程的策略,当前尤为注重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理论方面的研究[2]。从韦茨编印的书中可知,乡村发展的内涵是针对发展滞后国家的人民经济生活贫困,如何寻找促进解决方法。而世界银行在1975年给乡村发展下的定义是:乡村发展是一种策略,拟用为改进乡村贫穷人民的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利益延及在乡村中寻求生活的最贫穷团体,包括小农、佃农及无土地者。其强调乡村发展的目标在增加生产、提高生产力、增加就业、动员可用的土地、劳力及资本,同时也注重消减贫穷及所得的不均[3]。世界银行的乡村发展定义较之韦茨所概述的内容更为丰富,目标更为明确和具体,但二者均属于浅表层次的,主要是针对解决贫困人口的生活困顿问题而言。巴基斯坦学者伊纳亚图拉(Inayatullah)在1979年编印的《乡村发展的研究,亚洲的若干经验》(Approaches To Rural Development,Some Asian Experiences)一书中,其乡村发展内涵着眼于三个方面:(1)传播适当及改进农场技术的过程;(2)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中的人民接触外界而产生新技术与新态度的过程;(3)包含技术、社会、文化与政治等因素的复杂过程[4]。如果说世界银行有关乡村发展的概念主要着眼于消除经济贫困,保障基本生活,显然伊纳亚图拉(Inayatullah)所理解的乡村发展概念内涵要更为丰富,它是由相互联系的三个过程所组成:既包含新技术、新观念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也包括乡村人接受技术的能力、态度及其做出相应的改变这一互动过程,还包括技术、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复杂过程,显然该概念触及到了乡村发展中的多种社会关系。
而澳大利亚学者戴维(David A.M.Lea)和乔德利(D.P.Chaudhri)在20世纪80年代则提出“整合的乡村发展”概念,主要涵盖四个方面的内容:(1)改善乡村大众的生活水准;保障基本安全及对衣、食、住、行和就业等方面的基本需求;(2)增进乡村地区的生产力,免受自然的灾难,并改进与其他部门的互惠关系;(3)提倡自立的发展计划,并使大家都参与发展计划;(4)保障地方的自立性及减少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干扰[5]。这两位有关“整合的乡村发展”的定义虽然总体上仍是着眼于基本的经济生活保障,但他们提出了自我发展和大众参与的发展新内涵,还提出乡村人与社会关系的改进,以及在避免现代化对传统方式干扰的基础上寻求地方的自立性发展。这实际上已经注意到了乡村发展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问题,还将盲目追求现代化而破坏乡村传统的发展区别于真正的乡村发展,这体现了传统与现代和谐并存的宝贵思想。
无论如何,乡村中有待发展的事务是纷繁复杂的,随着众多西方学者的研究,学界逐渐达成共识:乡村发展的内涵既是整合性的,也是多面性的。台湾学者蔡宏进认为:广义的乡村发展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水准之提升。发展的目的除了改善乡村居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条件外,还可以提升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准[6]。从发展人类学的眼光来看:发展是一个综合的指标,包含着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等方面的多层次需求,发展的本质归根到底是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以人为本,人既是发展的主体,也是发展的动力,而发展的方式则是可持续的而非竭泽而渔式的,社会的发展包含着重要的人文发展指数[7]。从现代社会发展观而言,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之一,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发展的意蕴是人类文明以及人与自然状况的改善、进步和提高。发展不同于增长,增长主要表现为量的增加,而发展是指量和质的共同提高;发展也不同于一般的变迁或变化,它是一种朝着更好、更文明和更高方向的变迁。而社会发展是发展的核心内容,其意义在于人类在不断提高生产能力的同时,要使更广泛的人享受到更多的生产成果,要为人们的生活创造可持续的、更美好的环境。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涵盖: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社会福利、生态环境等多个方面,其宗旨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普遍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促进区域的均衡发展和推动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8]。
可见,社会发展既包括物的发展,也包括人的发展,还包括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等多重关系的和谐发展。具体到乡村发展,其内涵也是全面和综合的,不仅仅指的是乡村居民衣食住行等经济指标的增长,还包括其身心健康、闲暇娱乐等精神生活品质的提升,更包括他们享有自由民主和参政议政权利,实现自我价值、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等多方位目标。乡村发展目标,不是以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而是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传统与现代的协调中可持续发展。而乡村发展方式,则是联合国一直强调和鼓励的“以人为中心的内源式发展。”[9]
二、畲族乡村发展成效概览
自新中国成立后,畲族结束了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长期边缘化地位,畲族社会经济文化水准逐渐获得质的飞跃。尤其是近十余年来,随着国家政府对少数民族新农村建设扶持力度的日渐加大,浙、闽、粤、赣、皖等省各级地方政府也对畲族这一世居少数民族的新农村建设尤为重视。正是在各级相关政府部门的财政支持和战略指导下,我国畲族乡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主要体现在:村民自治、能人治村等乡村治理方式的摸索前行;交通道路、民居改造、环境治理等村落基础设施建设的日臻完善;农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山林特色经济资源的产业化;畲族农民人均年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和文化教育程度的普遍提升;文化广场、文化礼堂、畲乡风情广场等村落社区文化空间的修建;“三月三”畲乡风情节等传统节日的普遍复兴;畲族民歌、祭祖、编织、武术、谚语、节日等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逐级申报及对相关传承人的制度保护,等等。
尤其是近五年来,畲族特色村寨建设工作卓有成效。自2009年国家民委和财政部联合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以来,各地畲乡畲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亦紧锣密鼓地跟进,经过5年的努力,至2014年,闽、浙、粤、赣、皖等五省共有19个畲族特色村寨被国家民委列入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单(全国共有340个)。其中,福建省9个:福州市连江县东湖镇天竹村、南平市延平区水南街道岭炳洋村、三明市永安市青水畲族乡沧海村、漳州市漳浦县湖西畲族乡顶坛村、漳州市华安县新圩镇官畲村、宁德市蕉城区金涵畲族乡上金贝村、宁德市蕉城区八都镇猴盾村、宁德市福安市穆云畲族乡溪塔村、宁德市霞浦县溪南镇白露坑村;浙江省6个:杭州市桐庐县莪山畲族乡中门民族村、湖州市安吉县章村镇郎村村、温州市平阳县南雁镇堂基村、丽水市莲都区大港头镇利山村、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东坑镇深垟村、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大均乡李宝村;江西省2个:赣州市赤土畲族乡青塘村大岭背组、吉安市青原区东固畲族乡江口民族村蔡家垅自然村;广东省1个:汕尾市海丰县鹅埠镇红罗畲族村;安徽省1个:宣城市宁国市云梯畲族乡千秋村,以上这些榜上有名的畲族村落被誉为“民居特色突出、产业支撑有力、民族文化浓郁、人居环境优美、民族关系和谐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10]
事实上,除了以上国家民委首批正式命名挂牌的畲族特色村寨以外,闽、浙、粤、赣等地畲乡还有许多成效显著、方兴未艾的畲族特色村寨。诸如:浙江省文成县黄坦镇培头民族村、泰顺县司前畲族镇左溪村和竹里村、景宁畲族自治县鹤溪镇敕木山村、丽水市莲都区老竹畲族镇沙溪村、临安市於潜镇铜山民族村,等等。畲族特色村寨建设项目的试点推进,深化了畲乡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促进了畲乡民俗风情和乡村休闲旅游业的发展,推动了畲族文化与经济的良性互动。
畲族乡村发展上述诸成就的取得,是基于各级政府政策性支持和广大畲族村民积极进取的共同产物。例如,自2003年浙江省政府斥巨资实施村村通公路的康庄工程以来,宽广平坦的公路才逐步延伸至昔日地处僻壤的畲村,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让畲村山林经济资源的开发和畲乡旅游经济的发展具有现实可能性。而各地畲乡新农村建设项目的深入开展,尤其是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试点工作的顺利实施所带来的畲乡巨变,更少不了各级政府所提供的可观的少数民族特扶资金。当然,在畲族乡村发展进程中,广大畲族村民(尤其是那些热心村落发展事务的村落精英们)也为此付出了大量辛勤的汗水,他们充分发挥村落建设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利用区域经济辐射的优势和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优惠,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和超越大山的精神,克服传统的农耕思维模式,淡化族群封闭心理,进而从根本上扭转昔日畲村的贫困局面。
三、畲族乡村发展问题反思
然而,笔者通过在浙南畲村点面结合的田野调查不难发现,畲族乡村的发展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归来起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发展模式而言,自上而下式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是一把双刃剑。长期“以山为基、以农为本”的畲族村落由于受区位环境和历史传统的双重制约,总体上经济基础薄弱、经济结构单一、发展起点低,故其发展大都依赖各级政府的财政支持和民族政策扶持,采取自上而下式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从辩证的观点来看,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具有规划细致、布局全面、资源集中、行动高效等优势。这些优势对低起点的畲族乡村发展的启动和推进尤为重要,事实上,其成就也不菲。但从长远发展来看,该模式也存在着内源性发展动力不足的弊端。一方面,畲族村民因自我发展能力弱而过度依赖政府的财政扶持,另一方面又因长期习惯依赖政府资助而寻求自我发展或社会力量参与的制度创新意愿和动力不足,进而难以发育形成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和个体充分自由表达、实现自我价值的完善机制,最终影响畲村的可持续发展。自我发展能力弱与过度依赖政府两者之间互为因果、恶性循环。尤其是在畲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面对民居新旧杂陈、道路狭窄不平、环境脏乱不堪、改造工程复杂浩大等局面,往往会出现摊子铺得过大和资金缺口严重等窘况,进而陷入如何进一步“向政府要钱”和等待“政府拨款”的被动发展境地。
其次,从发展组织而言,畲族乡村治理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简言之是指对乡村社区的组织管理和制度安排,其宗旨是服务农民、解决民生、推动乡村发展。自1983年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被正式宣告结束后,不久建立了乡(镇)政府、村委会、村民小组这一新的农村建制,凸显了乡镇政权的主体地位,迎来乡村治理新模式。国务院对乡镇组织的职能有着十分明确的界定:除政治职能外,对乡村社区经济活动限于宏观管理范畴,主要是政策指导、统筹规划、组织协调和服务监督。自2002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后,村民自治制度广泛实施,我国广大农村普遍建立了村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村经济联合社、村民代表大会、村民理财小组等多元化基层农民组织,新的乡镇治理机制逐步形成。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业产业化的需要,许多农村还成立了各种类型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以及社会性民间组织[11]。从以上政策法规到组织框架来看,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可谓日臻完善。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各级组织的职能角色却出现了错位、越位和缺位等现象[12]。该现象在少数民族社区因社会发育程度低而表现得更为突出。
就畲族村落而言,乡村治理有待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大分散、小聚居”的地理分布格局,使畲族村落打上了更多的血缘、地缘等传统社区色彩,这与现代社区的适应性和开放性相抵牾;大量中青年农民外出打工经商,村民社会结构复杂、村落基层政权组织力量分散、文化程度总体偏低、村民自治难度大和效能差;随着政府对畲村公共事业投入力度的增大,乡村治理内涵扩大、任务增重,村落基层组织越来越力不从心;随着畲族村民社会流动的日益频繁,其思想观念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政治经济诉求和参与意识日益强烈,但现有的乡村治理模式难以完全满足畲族村民的多元化要求;畲村“能人治村”模式虽有利于推动滞后畲村的发展进程,但能人大都在附近城市经商,村落事务与家庭生意两头兼顾,疲于奔波,也存在着“能人异化”的隐患,“能人与贤人”完美结合治村的理想目标与现实还存在着很大的距离。
此外,各级地方政府有关畲村发展的职能配置还有待优化。近年来,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民宗局、农业局、旅游局、文化局以及乡镇政府各部门等)对畲村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引领,可谓工作出色和成绩不菲,但其工作的重点主要放在项目的推广与实施中,对畲族文化特质和畲族文化心理的了解程度还有所欠缺,因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过走弯路、重复投资等现象,项目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可见,地方政权(尤其是乡镇政府)与畲族村民的互动还有待深化,对畲村发展的指导、协调、服务等职能作用还有待加强。
再者,从资源开发而言,山林资源和人文资源的开发力度还有待深化。近十余年来,许多畲村加大了农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和农业产业化的进程,通过挖掘山林经济资源潜力,逐步实现了畲村由传统生存型农业向现代特色农业产业化的转型,村民经济水准大幅度提升。但山林经济资源潜力还远远挖掘不够,主要表现在品种类型比较单一、缺乏精细化深加工、产业化组织模式不够完善、企业品牌意识不够浓厚等方面。事实上,位处东南山区的畲村山林经济资源十分丰富,可开发的经济林木涵盖十大类型:干果类、水果类、油料类、药材类、调味类、蔬菜类、饮品保健类、编条类、工业用材及其他资源类。但目前各地畲村开发的品种主要为茶叶,以及少量的板栗、油茶、毛竹、青钱柳等,还有大量的经济林木可以开发,诸如:干鲜水果、竹笋、蔬菜、中药材以及食用菌等。此外,目前畲村在山林资源开发中,除茶叶产业化程度相对较深以外,大部分农产品为初加工,附加值较低,即便相对成熟的茶叶企业也存在着产业化组织模式单一、经济合作社名不副实、品牌意识不够深厚等弊端。
近年来,各地畲乡虽然涌现出一批环境优美的畲族特色村寨,彰显了畲族文化魅力,促进了畲乡旅游经济的发展。但总体而言其畲族人文资源潜力挖掘不够充分,畲族文化内涵表现不够丰富,呈现出畲族文化单一化、形式化、符号化、同质化等弊端。例如,畲乡旅游展演主要为婚嫁和对歌习俗,品尝麻糍、乌米饭等特色食品,至于编织蜡染、银饰制作、武术体育、草医药技艺等文化精粹的开发尚涉及不多。还有大量的村落历史、传说故事等人文资源尚未加以整理。在畲家乐旅游经济运营中,畲族文化特色不足,同质化现象明显,文化内涵不够,更缺乏具有文化创意的旅游项目和旅游产品。而且畲村民居以“畲元素上墙”的方式来彰显畲族文化特质,具有形式化和符号化特征。此外,各地普遍兴起的“三月三”畲乡旅游风情节,注重文化展演的形式,而忽略文化的本真意义,对热情热闹和盛大场面的追求,远远胜过对文化意义和经济效益的追求。节日载歌载舞的表演者大都是雇请来的汉族专业演员,大量的畲族村落民间文化艺术人才逐渐被边缘化,而且畲家乐旅游经济受益面总体不广。因此,畲族特色村寨还需要进一步整合山林资源和人文化资源,强化文化创意,凸显民族特色。
再次,从发展本质而言,人的自由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指标。人类发展的理念以20世纪70—80年代为分界点,经历了从传统的发展观到新的发展观的转型。前者将发展片面理解为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经济指标的增长,后者将发展理解为以人为核心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1976年国际劳工组织首次论述了“人”的发展,认为经济发展首先必须满足人的基本需要。随后联合国制定的第三个十年发展计划(1981—1990)不仅规定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量的目标,而且还规定了经济发展的质的目标,即社会进步的目标,如公平分配、充分就业、普及教育、培训劳动力、提高健康水平、改善住房条件、保障妇女儿童的正当权益等。时至1992年,联合国在第一份《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运用人文发展指数(HDI)这一新概念,意即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这三项基础变量按照一定的计算方法组成的综合指标来考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状况,后又补充了生活环境和居民自由程度等两项变量。人文发展指数概念的提出丰富了“发展”的本质内涵。与此同时,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由理论探讨范畴推向人类共同追求的实际目标,从更高的视角寻求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13]。
从新的发展观可知,发展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综合概念,既包括经济生活水准的提高,也包括人的健康理念和文化教育程度及生活品质的提升,还包括基础设施和居住环境的改善以及自由发展和平等参与目标的实现等,更包括既满足当下需求又满足未来需要的可持续发展。就近十余年来畲族乡村发展状况而言,无论是经济生活水准、还是居住环境质量和文化教育水平等方面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从健康理念、居住环境、生活品质、闲暇娱乐以及自由发展、抗风险能力等方面来看,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例如,近十几年来畲族村民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食物结构有了很大的变化,餐桌食物品种日益多样化,但由于健康知识的匮乏,偏好酒肉荤腥和多盐多油食物,加之因“番薯丝吃到老”的痛苦历史记忆而对番薯等粗粮心理排斥,甚至有的上山劳动也以酒解渴,故畲族这个善酒的山居民族,更容易患上心脑血管等疾病。因畲民抗风险能力总体不高,倘若家中有人犯有重大疾病,其家庭生活质量势必一落千丈,少数家庭甚至一蹶不振。再如,畲村垃圾处理排污设施等虽然逐渐完善,但填埋式垃圾处理方式和塑料制品白色污染等对畲乡土地资源的潜在威胁仍不容忽视,大量的城市非安全食品涌入畲村,亦值得警惕。此外,畲村社区文化建设总体投入不足,乡村图书室等文化设施普遍匮乏,畲民的身心健康和精神生活较少关注,畲民精神娱乐生活比较单一,旅游休闲的机会比较少。
最后,从发展主体而言,农户发展与村落发展不平衡性仍较为明显。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国农村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许多畲族农民通过外出打工经商逐步发家致富。然而,中青年的长期外出,不仅导致畲族农户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更导致畲村发展的“空心化”或“半空心化”趋势以及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虽然打工经商发家致富不少,但村落经济基础和集体经济力量依然总体薄弱。事实上,外出打工经商农户的发展并不等于畲族村落经济的发展。尽管并不排除外出打工经商户的发展有助于带动其他农户的家庭发展,但总体而言,外出农户的发展对村落整体发展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相反,畲族村落的整体发展,则必然会提升广大畲民的村落凝聚力和自豪感,同时缩小农户之间的内部差异,尤其有益于保护年老贫病畲民等弱势群体。例如,近三十几年来浙南文成县培头村钟姓畲族村民大都依靠外出打工经商(包括至省内外,甚至国外),获得可观的经济收入和良好的家庭发展,但培头村作为村落整体却长期以贫困面貌和低度发展呈现。直至近年来,随着民族特色村寨的社区营造,培头村犹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享誉四邻八乡,更牵引着无数在外发展的村民回归村落,并主动参与到家乡建设中来。这反映出许多高收入钟姓畲族村民对家乡发展的自豪感远胜于在外面发家致富的成就感。再如,自改革开放之初,景宁、武义等地不少畲族村民陆续至我国各大中城市经营超市而收入不菲,他们大都在家乡修造了气派的新楼房,但仅在春节期间小住几天,平时基本空置。对于这些离乡的富裕畲民而言,其内心升腾的自豪感并非来自自家楼房的引人注目,而是近几年畲族特色村寨建设,村落整体面貌的改观。然而,畲族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村落集体经济的总体薄弱现象仍不容忽视。总之,唯有畲族乡村整体的发展才是畲族发展的关键,也只有畲族乡村的整体发展才是真正和谐、全面的畲族发展,才能从根本上缩小畲村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
结语
乡村发展概念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日渐丰富,既包含着经济指标,也包含着人文指标、环境指标及可持续发展指标等。而近十余年来畲族乡村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经济、文化、教育水平获得大幅度的提升,涌现出一批环境优美、产业活跃、生活富裕的民族特色村寨,但也存在着过度依赖政府、资源潜力开发不足、产业化程度不深、全面发展程度不够、畲汉差距明显、村落内部发展不平衡等诸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深化畲族乡村发展进程,有必要借鉴中国台湾社区营造经验,探索畲族(也适应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自己的乡村社区发展路径与方法。具体措施包括:通过发展理念转换和社会制度创新,建立知识服务社会的畅通机制,整合以高校为核心的知识分子力量,开设社区营造系统课程,增强社区营造整体文化氛围,培育更多关心各民族乡村社区营造的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队伍,组建社区营造专业工作团队,深入各民族乡村社区全程帮扶,鼓励和支持高校及科研机构大学生、硕博研究生们毕业后返乡再造魅力新故乡。唯有通过政府部门的政策指导和制度支持、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引领和体系化的社区专业培训,才能逐步增强村民的公共参与意识、文化自觉意识及社区主体意识,才能不断提高其自我组织和自我发展能力,进而将“一袋马铃薯”[14]式的传统农民蜕变为视野开阔、凝聚合作的现代社区人, 各民族的乡村发展方能获得持续的内生性动力。正如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拉尼(Polanyi,K.)所云:人类的经济,是嵌合并陷于制度、经济的和非经济因素之中的[15]。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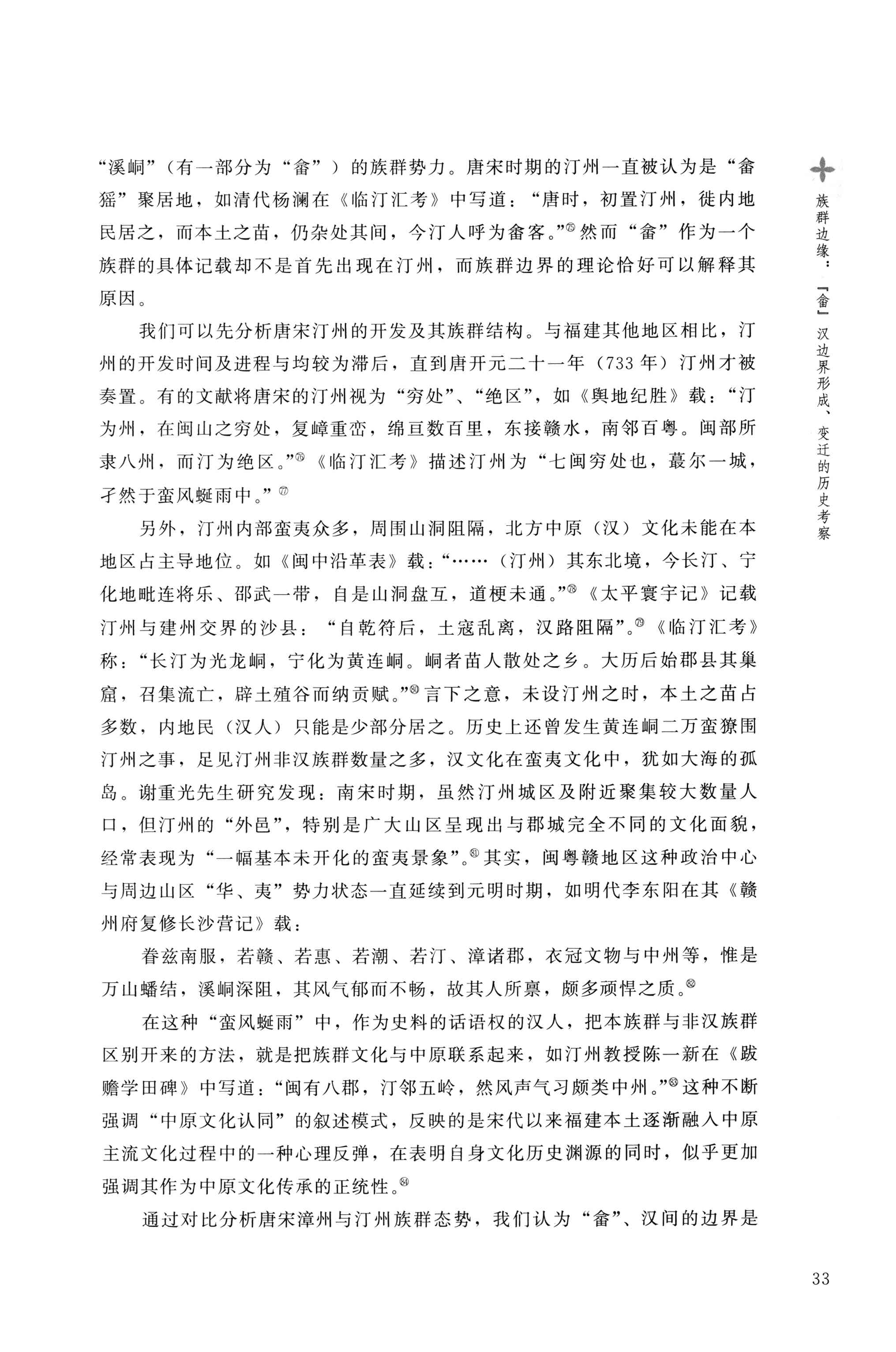
相关人物
王逍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