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 内容出处: | 《当代视野下的畲族文化》 图书 |
| 唯一号: | 130920020230005884 |
| 颗粒名称: | 一、问题的提出 |
| 分类号: | F039 |
| 页数: | 3 |
| 页码: | 344-346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中国少数民族村寨的发展多在政府主导下进行,与政府运作机制密切相关。项目制成为新的治理方式,资金和项目“专项化”、“项目化”。基层政府引入项目,争取资源,服务于本地发展。项目制具有再生产能力,一个项目的“果”往往成为后一项目的“因”,实现项目的再生产。布迪厄的资本理论揭示了资本再生产的重要性,对少数民族村寨的发展有重要启示。 |
| 关键词: | 畲族村 资本再生产 问题 |
内容
当前中国少数民族村寨的发展多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要研究民族村寨的发展逻辑不能离开对政府运作机制的分析。已有学者指出,项目制已成为当前中国新的治理方式(渠敬东,2012),甚至几乎所有的建设和公共服务资金都“专项化”和“项目化”了(折晓叶、陈婴婴,2011)。实际上,中国少数民族村落的发展也已深深地嵌入在政府的各种项目之中,二十世纪末以来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民族村寨和特色乡村正是受益于这种治理方式。基层政府通过打包民族村寨的生态、历史和文化等,获得上级政府发放的项目,给民族村寨带来了各种发展的资源。然而,民族村寨何以引入项目?在一个项目之后又是如何引入下一个项目?村寨引入项目的机制和内在逻辑如何?
已有不少研究指出,引入项目已成为基层政府引进资源的重要方式。折晓叶、陈婴婴提出了项目制运作的形式,国家部门对项目进行“发包”,地方政府则“打包”整合各种项目和资源来向上级政府申请专项资金和项目,而基层政府和村寨则对项目进行“抓包”来主动争取项目,以获取资源,服务于本地发展。他们指出,村庄只有“抓到打包好的项目,才有可能大规模地改变村貌”[2]。渠敬东同样认为“地方政府若不抓项目、跑项目,便无法利用专项资金弥补财政缺口,无法运行公共事务”,地方政府为了引入项目,提出“大跑大项目大发展,小跑小项目小发展,不跑没项目不发展”的口号,以“大项目套小项目”、“一项目生多项目”,尽量“巧立名目,多立名目”,获取更多项目经费来支持地方政府的运作和发展。[3]
项目制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再生产能力。渠敬东指出,“项目在基层社会的输入过程中,并不限于某一专项的输入,而往往表现为多个项目前后承接地连续输入”,体现出强大的繁殖能力[4]。前一项目的“果”往往会成为后一项目的“因”,实现项目的再生产。陈家建也指出项目制会表现出自我扩张效应,项目的“成功经验”往往会使上级部门延续和扩大项目化运作[5],一个部门在一个试点单位项目的成功会吸引其他部门在该试点单位投入新的项目。无论是项目的繁殖还是扩张,其中都有一个项目或资本再生产的机制,这是以往的研究没有予以深入研究的。本研究便欲借布迪厄的资本理论,通过狮墩村的个案尝试去探究这种机制。
布迪厄将资本分为客观资本和象征(符号)资本,客观资本包含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就是经济资源;文化资本是一种信息资本,以身体化的、客观化的和制度化的形式存在,如少数民族的文化;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网络资源,它是“某个个人或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识的关系网,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综合”,如少数民族村寨的宗族网络;象征资本指的是对以上三种资本的感知,“当我们通过各种感知范畴,认可上述三种形式的资本的各自特定逻辑,……从而把握了这几种资本的话,我们就说这些资本采用的形式就是象征(符号)资本”[6],如获得项目这件事和赋予少数民族村寨的各种荣誉称号。象征资本是布迪厄资本理论体系中最富创见的内容,象征资本的特性之一是其再生产性,不仅其本身可以进行再生产,其他资本也会通过各自的象征属性,实现再生产。
检视中国少数民族村寨的发展历程,会发现一些共同的特征:其一,具有特定的荣誉称号;其二,村庄的改变得益于近年来不断引入的各种项目;其三,荣誉与项目多是交替得到的。本研究的个案将表明,在“项目制”的治理方式之下,资本的再生产在中国少数民族村寨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已有不少研究指出,引入项目已成为基层政府引进资源的重要方式。折晓叶、陈婴婴提出了项目制运作的形式,国家部门对项目进行“发包”,地方政府则“打包”整合各种项目和资源来向上级政府申请专项资金和项目,而基层政府和村寨则对项目进行“抓包”来主动争取项目,以获取资源,服务于本地发展。他们指出,村庄只有“抓到打包好的项目,才有可能大规模地改变村貌”[2]。渠敬东同样认为“地方政府若不抓项目、跑项目,便无法利用专项资金弥补财政缺口,无法运行公共事务”,地方政府为了引入项目,提出“大跑大项目大发展,小跑小项目小发展,不跑没项目不发展”的口号,以“大项目套小项目”、“一项目生多项目”,尽量“巧立名目,多立名目”,获取更多项目经费来支持地方政府的运作和发展。[3]
项目制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再生产能力。渠敬东指出,“项目在基层社会的输入过程中,并不限于某一专项的输入,而往往表现为多个项目前后承接地连续输入”,体现出强大的繁殖能力[4]。前一项目的“果”往往会成为后一项目的“因”,实现项目的再生产。陈家建也指出项目制会表现出自我扩张效应,项目的“成功经验”往往会使上级部门延续和扩大项目化运作[5],一个部门在一个试点单位项目的成功会吸引其他部门在该试点单位投入新的项目。无论是项目的繁殖还是扩张,其中都有一个项目或资本再生产的机制,这是以往的研究没有予以深入研究的。本研究便欲借布迪厄的资本理论,通过狮墩村的个案尝试去探究这种机制。
布迪厄将资本分为客观资本和象征(符号)资本,客观资本包含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就是经济资源;文化资本是一种信息资本,以身体化的、客观化的和制度化的形式存在,如少数民族的文化;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网络资源,它是“某个个人或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识的关系网,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综合”,如少数民族村寨的宗族网络;象征资本指的是对以上三种资本的感知,“当我们通过各种感知范畴,认可上述三种形式的资本的各自特定逻辑,……从而把握了这几种资本的话,我们就说这些资本采用的形式就是象征(符号)资本”[6],如获得项目这件事和赋予少数民族村寨的各种荣誉称号。象征资本是布迪厄资本理论体系中最富创见的内容,象征资本的特性之一是其再生产性,不仅其本身可以进行再生产,其他资本也会通过各自的象征属性,实现再生产。
检视中国少数民族村寨的发展历程,会发现一些共同的特征:其一,具有特定的荣誉称号;其二,村庄的改变得益于近年来不断引入的各种项目;其三,荣誉与项目多是交替得到的。本研究的个案将表明,在“项目制”的治理方式之下,资本的再生产在中国少数民族村寨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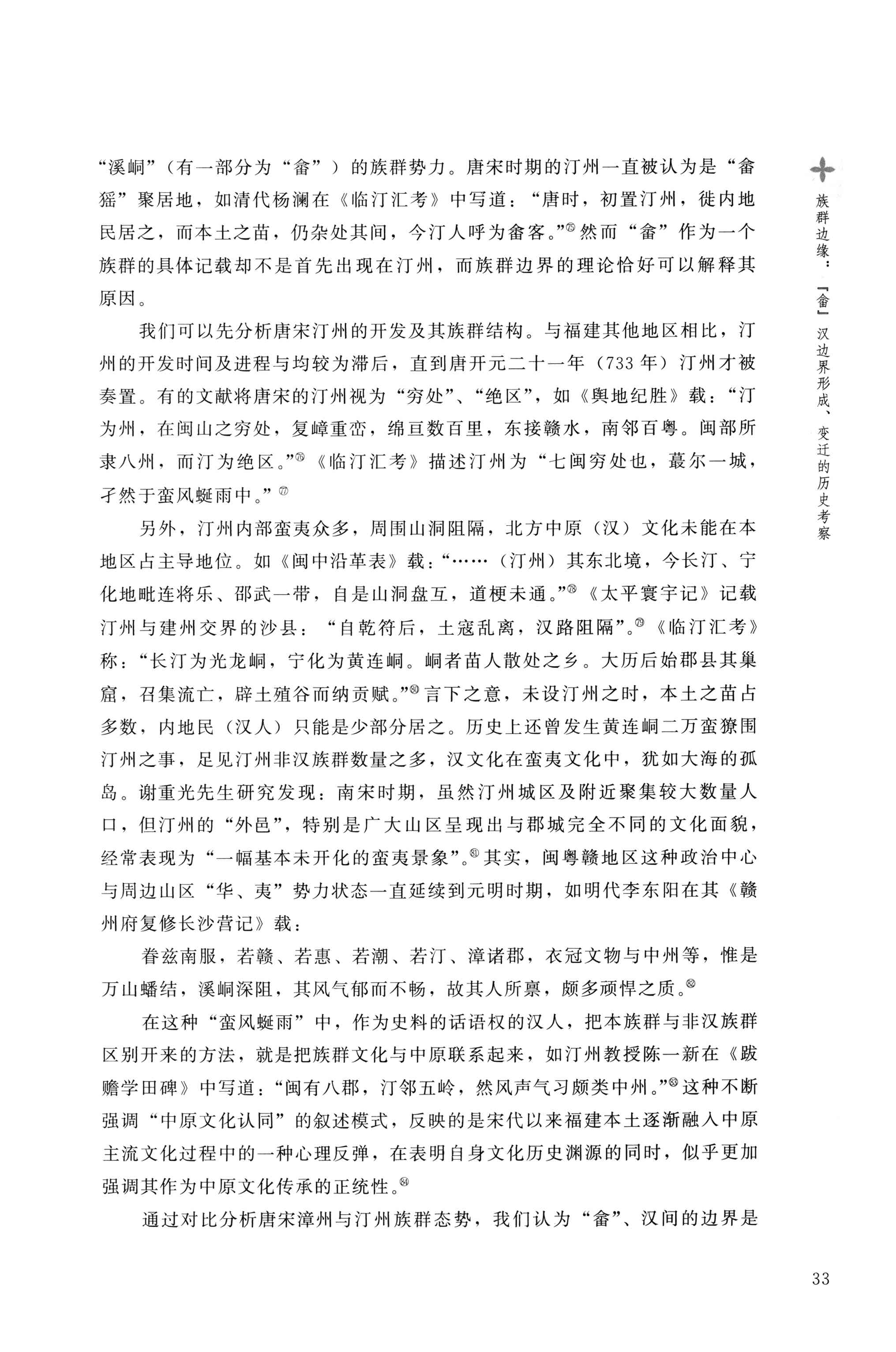
相关人物
雷李洪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