畲族文化共生与畲族多元文化的发展
| 内容出处: | 《当代视野下的畲族文化》 图书 |
| 唯一号: | 130920020230005749 |
| 颗粒名称: | 畲族文化共生与畲族多元文化的发展 |
| 分类号: | G527.57 |
| 页数: | 8 |
| 页码: | 84-91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文化共生是多元文化的共栖、共存的文化状态,其实质是强调群体族群文化在相同地域、空间,通过文化交流与文化接触下充分保持族群文化的独立性,允许异质文化间共存与共荣。民族地区的文化单元受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影响,形成一定历史条件下新的民族文化单元。强调畲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与主流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融互动,畲族文化的发展在坚持畲族文化发展的独立性、独特性、交融性和创新性的发展道路的同时,要主动融入主流文化与周边文化,形成共栖、共存的多元文化样式,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畲族文化。 |
| 关键词: | 民族文化 畲族文化 文化共生 |
内容
文化共生是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历史客观要求,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文化共生单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都是客观存在的文化共生单元,而这些文化共生单元在中华文化母体中相对独立的客观存在构成了文化共生的基本社会条件,各种文化势力的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相互识别与相互融合构成了共生的内在动力,也构成了少数民族特殊的经济社会条件文化共生环境。在文化博弈中,这些文化单元的最终共生走向是相互兼容与吸纳,形成新的文化共生单元和文化合力。在此过程中,坚持畲族文化发展的独立性、独特性、交融性(开放性)和创新性的道路,主动融入主流文化与周边文化,形成多元文化,才能发展特色的畲族文化。
一、畲族文化共生
畲族文化的共生,体现其文化的各个层面,其文化表现方式既有精神层面的文化共生,如宗教信仰、图腾文化等,又有制度层面的文化共生,如宗祀文化、祖图文化、族规与家训文化等,还有物质文化层面的共生,如谱碟文化、音乐文化、契约文化、习俗文化等。通过了解文化共生,了解畲族文化与周边民族与族群关系,特别是与汉民族文化的关系,破解影响畲族文化的主要因素与发展动力,促进畲族文化的当代发展,实现畲族文化的现代性。
(一)共生文化
“共生”源于一个生物学概念,德国著名真菌学奠基人DeBary(1831-1888)首创。其原意为不同生物之间密切生活在一起(LivingTogether)的共栖、共存的一种状态。“共生”从生物之间的共栖、共存引申为指不同种类的一个或更多成员之间的物质联系。它被引入社会科学领域后,用来表示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关系。袁纯清认为:共生是指“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①强调共生关系受共同生存环境、共同生存空间、个体内部和个体间依存关系等因素影响。
文化共生是多元文化的共栖、共存的文化状态。其实质是强调群体(族群)文化在相同地域、空间,通过文化交流与文化接触下,充分保持文化的独立性,允许异质文化间共存与共荣。
文化共生可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文化共生是指文化共生单元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组织结构和作用方式,它是一种相对封闭的共生形式。广义的文化共生是文化共生单元之间的结构模型和作用方式,它反映的是各个文化共生单元之间的相互关系,既包括文化共生单元之间的构成形式,也包括文化共生单元的相互作用方式与强度,还包括各个文化共生单元之间的物质、信息交换关系和能量互换关系。②由于任何完整的文化共生都是行为方式和共生程度的具体结合。因此,民族地区的文化共生应该是广义的文化共生,其共生形式不仅包含物质文化层面的共生,也包含精神文化层面的共生;不仅是指民族之间物质、信息和能量等要素互换关系,也包含文化集团之间构成与相互作用共生关系,即“构成共同体或共生关系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③
(二)畲族文化共生
文化共生是民族地区多元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文化共生关系的发生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文化集团,其在共同区域、空间下,他们之间的文化单元具有一定联系、能够相互作用和影响。因此,任何文化集团文化的传统性、现代性,都会受到外来文化及周边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关系、依存关系和共栖关系的文化共生形态具体表现在文化共生的原生性、冲突性、妥协性与和谐性。
因此,多元文化携手生活在共同的空间和领域,形成一个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多元文化共在、相互尊重、互相兼容、交流互动和协同发展的和谐文化形态。
自明清以来,畲族先民主要生活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西等地,长期游走在南方山区之中。浙江畲族先民最早何时开始耕种现在已无从考证,据在遂昌井头坞村《钟氏族谱》所载的《宋绍熙三年谅公宣公等由广潮始迁各省府州县行程誌》中,记载:“成化十年(1474)十二月二十日,钟三公带子孙移过罗源县徐江里,上炉茅山居住,初学耕田为活,供膳家口。”这说明畲族先民在此时期的已经开始学习农耕生活方式,但也不排除依然处在较为原始的“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说明清时期或更早一些时候,畲族民众已实现从游耕生存到农耕生存方式的转变。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畲族先民在向当地汉族民众学习农耕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带着自身族群“原样”生活样式在异文化的环境和社会中,通过不断的文化接触,使其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价值取向逐渐发生变化,或是部分接受,或是只限定于某个文化侧面,结合自身的文化形态,形成具有“新”的民族文化样式。同样,群族带着“新”的文化方式迁徙到不同的文化环境与社会中,经过相同的文化渗透、同化,重新达到自身文化与区域文化的和谐,这种文化的和谐性或许使其丢掉物质层面的原生文化因素,而且还会丢失精神层面的文化内核,但这种民族间物质、信息和能量等要素的互换,促使文化单元体环境适应性与发展性,从而达到文化的共生。这样的生活样式,一方面来自内部文化发展与改造需要,另一方面是来自外部强势文化的压力。
二、畲族文化共生的因素
根据传统民族的划分其最重要的因素是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特征和共同语言。而使一个民族从单纯的族群意识上升为成民族意识,还需要拥有长期共同生产生活形成的共同文化。民族文化的形成需要经过长期共同生产生活,经过不断地与各群体文化的交融并吸收外来先进文化,最终形成相对成熟、相对稳定的民族文化。在此过程,影响民族文化的变迁与发展不外乎二方面的因素,一是内发性因素,二是外发性因素。对畲族文化共生与发展也可通过共生的内发性因素文化表达与外发性因素的文化表达二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一)畲族文化共生的内发性因素
姓氏是血缘关系的纽带,对一个长期处在迁徙过程的民族而言,姓氏显得更加重要。畲族姓氏相对简单,其原始姓氏只有四大姓氏,即盘、兰、雷、钟,其他姓氏,如李、吴、周、林、千、刘、张、羊、王、宗、世、章、朱、爱、曹、方、康等姓氏是后来融入其群体组织的。畲族社会集团在历史各个阶段的整合过程中,其社会组织及其组织内部的制度性相对不是很严密、很完善,在这种状况下,血缘关系有着极大的凝聚力与影响力,强大血缘关系成为畲族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的重要特征。
作为一种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形式,“姓氏”在我国的发展已历经数千年的历史,并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演进中构筑起一条今人揭示原始氏族状态的通道。而“姓氏是随着图腾名称的产生而产生的,最古的姓氏就是图腾名称;姓氏渊源于图腾名称,是姓氏形成的一条重要途径。”④而这样的论述早在19世纪中期就已出现,如摩尔根在《古代社会》同样简述过此问题。
目前虽然对畲族始祖的考证现在没有公论,在中国历史上,每个部落、民族的始祖都是神话过程,畲族也不例外,但我认为畲族始祖也不能排除与部落首领与中原强在帝国联姻的结果并加以神话处理。而在现实畲族始祖神话处理过程中有些专家认为有不当之处,但无论是从盘瓠传说、高皇歌中四大姓体现畲族文化的核心,还是畲族大姓之盘(大哥地位)的消失或者是融入其他民族,畲族文化共生一开始就发生,并长期存在。畲族在历史上没有产生跨地域性的强有力的社会管理机构,其内部社会整合的传统机制主要由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组织和父系世系群(宗族)组织构成,血缘关系成为畲族内部传统社会关系的主轴。也可从畲族聚居村落上分析,现代畲族村寨多以血缘相近的同姓聚族而居,这一点从现存的宗谱或族谱上可以得到反映⑤。而对根据相关文献、族谱及传说记载,长子姓盘,名自能,受高辛皇帝敕封,敕长子盘自能为南阳郡武骑侯,从广东潮州凤凰山自海路迁徙时,盘姓一族的船被海风吹翻沉没大海,或传说是被告海风吹到“番国”,因此未到达连江登岸,故无盘姓在东南沿海的福建、浙江等地生息。据德国学者哈·史图博在《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中写道:“他们只有四个姓:兰、雷、钟、盘。然而在景宁及其附近地区已没有盘姓氏族了。有人认为他们已改为姓潘而成为汉人了。在景宁有一姓潘的富裕人家,据说是畲民的后裔。”
在畲族文化的起源—畲族盘瓠神话传说中,钟姓是作为盘瓠的女婿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进入畲族族群。在传统的汉文化中,尽管钟姓入赘成为其女婿,也只是半子,其原身份应该是汉族或是其他民族,虽属于这个家族的正式成员,但其血缘关系,按照民间的文化语境解读,钟姓女婿后裔进入畲族群体的记忆反映了他们和畲族其他群体交融的历史真实,站在学术的观点考察,盘瓠传说暗示了钟姓其与汉族的关联。许多钟氏宗谱也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对钟氏“女婿”表述方式是盘瓠传说对畲族历史和文化共生的最好表达。
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调查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畲族于1956年正式成为一个我国民族统一大家庭中的独立一员。在民族识别的过程中,畲族的姓氏组成也成为众多学者的关注对象,就目前的事实而言,浙江的畲族共有蓝、雷、钟、李、吴、罗、杨、娄等姓,在福建闽东地区,畲族也有李、吴、周、林、千、刘、张、羊、王、宗、世、章、朱、爱、曹、方、康等姓氏,除盘、蓝、雷、钟四姓为畲族上古姓氏传承,其他姓氏均年代较后,且多为汉人入赘加入畲族而保留原姓者。其他姓氏的加盟,促使畲族文化在区域内文化共生,促进文化集团的交流与融合。
畲族文化共生的内发性因素就是畲族语言。畲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因其长期与汉族及汉族的客家群体生活在一起,语言汉化已经非常明显。台湾学者吴中杰在畬族语言研究中,通过对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五省畲话,以及广东增城畲语进行实地田野调查研究,通过畲语内部语音系统、畲语与畲话关系、畲语及畲话的语法现象、声韵组合及基本词汇等,提出内部分片的标准,以呈现各方言点之间的异同及远近关系;通过横向的比较研究,如探讨畲话和客家话关系和畲语与各地方言的关系,提出畬话的几项条件音变。并指出:
畲话表层固然有当地汉语方言成分,但就所有汉语方言来说,客家话无疑是跟畲话最接近的,两者重叠现象甚多。然而畲话也有若干虽属于汉语方言成分、却并非来自客家的特色。畲语固有层和畲话有关系,不过这样的词项极其有限,许多畲话的非汉语成分跟畲语说法无从衔接。因此,畲话绝不等于‘客家话跟若干畲语残存成分的相加。⑥
2015年9月,与学院吕立汉、王闰吉、雷艳萍等语言文字专家到开化畲族村落考察,也同样发现此问题。雷艳萍通过畲民讲话与个别字的发音,并与松阳客家话进行对比,开化畲族群体其主要语音语调与客家方言非常接近。另一方面,雷艳萍通过请其导师对畲族语言进行录音分析,其语音比较乱,且古音较多,这进一步说明畲族民众在长期迁徙过程中,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主动接触汉文化,融入当地的语言环境,用汉语文字、汉语语法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诉求。
(二)畲族文化的外发性因素
由于历代封建王朝与社会势力的影响,加上畲族自身游耕生产生活要求等因素,畲族陆续从闽、粤、赣交界地区向闽、浙、赣、粤、皖的一些偏僻山区迁移。在长期的迁移过程中,与汉族文化进行深度接触,不断地吸收汉族先进生产技术,采用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力有了提高,明清时代逐渐由游耕和狩猎经济发展方式向定居农业经济转变,分布上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亦告形成。畲族定居聚落一般都与汉族村落交错分布,既与汉族村落保持一定的距离,又相距不远,既有相对独立性,又有密切的依存关系。这种依存关系具体体现在商品交易,如进行必要的农副产品和生活必需品交易等,畲族生活地区与周围的汉族构成了相互依赖互为补充的共生依存格局,也构成了两族间的共生关系。
这种关系不仅促进了畲族生活水平的提高,提高了生产力,更主要的是使畲族文化与当地文化形成共栖、依存格局。有些是主动接受,有些是被动接受与融合。但在这过程,更多是主动融入,形成共栖、依存的文化关系。彩带文化、服饰文化、祖图文化、契约文化等是最好的见证。
在畲族文化里面,祭祀已经形成畲民家族群体的文化象征符号,作为家族祭祀神圣之地,已深烙于畲民心中,成为一种不容抹煞的精神文化。特别是明清以来,畲族十分热衷兴建祠堂,这一方面体现畲族家族文化发达,另一方面体现畲族受生活在东南沿海汉文化的影响。畲族兴建祠堂文化活动过程中,通过吸收当地汉家祠堂文化的同时,根据自身文化特点有着比较明显的民族特色,在具体兴建祠堂时,就有着从想象到具象的发展过程。祠堂文化或者祭祀文化是畲族主动融入,形成共栖、依存的民族文化表达。
祠堂文化的发展也是一个逐渐发展过程。祠堂文化的萌芽是香炉代替祠堂。畲民初到某地,由于家族人力、财力、物力所限,不能有鼎建祠堂之举。香炉便代表家族的存在进行祭拜。《云和县志》载:“云和畲族没有祠堂。蓝姓香炉置于安溪青石岩,雷姓香炉置于黄处鬼岩。”随之,又以一种特殊的祖籍替代香炉,这种文化形式称为“祖担”。“祖担”是二只箱子或箩筐,箱子里装着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祭祖香炉、祖牌、龙头祖仗、铃刀、龙角、祖图与宗谱等祖籍是畲民流动的祠堂。浙江《建德县志》载:“畲客之祠以竹箱为之,内贮祖牌及香炉。”祖箱来往于畲族乡村,主要用于畲民家族的祭祀,其中尤其是畲民醮明祭,更必须将祖籍请进家门,醮明祭却指传师学师。可以说,传师学师是祖籍文化形式发展而来的。在随祖籍进门的有家族父老,还有畲族巫师。祖籍中除了祖牌、香炉处,还有祖图、祖杖等器物。蓝、雷、钟诸姓的香炉的个数是不同的,蓝姓6只香炉,雷、钟诸姓为5只香炉,祖籍中的祖杖长度也不同于祠堂中的祖杖。
随着家族的繁衍,房屋的增建,村落的扩展,家族经济实力的提升,才能考虑到建祠。在祠堂未建之时,往往会把祖屋当成族从祭祀、议事之所。即使祠堂建成后,祖屋仍是族人缅怀先祖,激励后人的教化之区。祠堂建成后便成为畲民议事、祭祀和红白喜事设宴的公共场所,这与汉族姓氏祠堂的功能相差无几。畲民称为“众厅”,是家族联建的大房屋中预留的大厅,产权属家族公有。汉民姓氏祠堂只是某一姓氏的祠堂,其他姓氏是不能在祠堂中进行各种祭祀、议事和红白喜事设宴的。而畲民的祠堂与不是单姓祠堂,可以是多姓祠堂。
总之,畲民的祠堂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形态。现代意义上畲族祠堂,业已成为畲族“民族即家族”理念的标志。而从香炉—祖籍—祖屋—众厅—祠堂,则是家族历史沧桑的反映以及族人文化变迁集中展示。其功能与汉族的祠堂功能没有区别之外,在此过程畲族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即传师学师文化。传师学师文化产生与发展是随着畲族活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逐步形成的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样式,也是迁徙到浙江畲民对畲族文化内涵的丰富与发展。正是由于其吸收了外来文化样式,才有今天畲族的祭祀文化、祠堂文化及传师学师文化。
三、畲族多元文化发展基本路径
民族文化的发展既要满足民族内在的文化需要,同时也要考虑文化发展的外部动力一条件,也要符合人自身的需要。畲族文化多元性发展既要遵循共生的生物学要求,也要符合民族共生文化的历史因素与现实,为畲族文化发展提供一种恒常性的人文精神资源,为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注入一种持续性的文化驱动力。
在当代文化大融合、大发展的文化多元化道路上,畲族文化的发展,在坚持自身传统文化发展路径外,一是通过坚持文化发展的现代性,即融入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指引畲族文化共生模式建构;二是通过超越畲族文化固有的文化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实践中推进畲族文化的开拓创新,即坚持传统又有创新思维发展民族文化;三是通过坚持和谐共生的价值取向,正确处理畲族传统文化与汉族文化及现代文化的关系,并塑造良好的畲族传统文化发展环境,深化畲族多元文化发展。
为此,畲族多元文化的基本路径要坚持四个原则,即“独立性、交融性、独特性与创新性”原则。独立性原则强调文化发展有自己的空间与环境,根据自己的文化发展规律传承与发展,不仅要依靠政府,而且要依靠民间与社会团体做文化事业,推进畲族文化的发展。现在畲族文化存在一种现象,则在畲族文化发展过程中政府推动畲族文化发展占主导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不是真正的畲族文化的发展与民族文化的繁荣,只是给人、给社会一种假象,其文化张力不强,很多文化样式生命力很快被社会淘汰,被人们所遗忘。只有畲族自身文化需要,通过畲族自身挖掘与深化,并通过政府引导,这样的文化才能有长期性与生命力;二是交融性原则,也可叫互动性原则。强调民族文化发展的依存关系,则通过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才能了解自身文化的短板,才能知道其他民族文化的长处,才能有针对性地改造民族文化这不足,提升畲族文化核心竞争;三是独特性原则。强调畲族文化发展独一无二性,不受周边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发展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要有自己的文化个性与性格;四创新性原则,也叫可持续性原则。这里特别强调要有畲族文化研发与保护基地。畲族文化产品的开发,离不开文化研究团队支撑,离不开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合理利用,因为开发文化产品的目的不仅在于传承与弘扬传统畲族文化,在于使畲民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要重视畲族文化研发团队建设,重视畲族传统非遗传承人的保护与利用,保护畲族传统文化资源,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做到畲族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一、畲族文化共生
畲族文化的共生,体现其文化的各个层面,其文化表现方式既有精神层面的文化共生,如宗教信仰、图腾文化等,又有制度层面的文化共生,如宗祀文化、祖图文化、族规与家训文化等,还有物质文化层面的共生,如谱碟文化、音乐文化、契约文化、习俗文化等。通过了解文化共生,了解畲族文化与周边民族与族群关系,特别是与汉民族文化的关系,破解影响畲族文化的主要因素与发展动力,促进畲族文化的当代发展,实现畲族文化的现代性。
(一)共生文化
“共生”源于一个生物学概念,德国著名真菌学奠基人DeBary(1831-1888)首创。其原意为不同生物之间密切生活在一起(LivingTogether)的共栖、共存的一种状态。“共生”从生物之间的共栖、共存引申为指不同种类的一个或更多成员之间的物质联系。它被引入社会科学领域后,用来表示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关系。袁纯清认为:共生是指“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①强调共生关系受共同生存环境、共同生存空间、个体内部和个体间依存关系等因素影响。
文化共生是多元文化的共栖、共存的文化状态。其实质是强调群体(族群)文化在相同地域、空间,通过文化交流与文化接触下,充分保持文化的独立性,允许异质文化间共存与共荣。
文化共生可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文化共生是指文化共生单元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组织结构和作用方式,它是一种相对封闭的共生形式。广义的文化共生是文化共生单元之间的结构模型和作用方式,它反映的是各个文化共生单元之间的相互关系,既包括文化共生单元之间的构成形式,也包括文化共生单元的相互作用方式与强度,还包括各个文化共生单元之间的物质、信息交换关系和能量互换关系。②由于任何完整的文化共生都是行为方式和共生程度的具体结合。因此,民族地区的文化共生应该是广义的文化共生,其共生形式不仅包含物质文化层面的共生,也包含精神文化层面的共生;不仅是指民族之间物质、信息和能量等要素互换关系,也包含文化集团之间构成与相互作用共生关系,即“构成共同体或共生关系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③
(二)畲族文化共生
文化共生是民族地区多元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文化共生关系的发生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文化集团,其在共同区域、空间下,他们之间的文化单元具有一定联系、能够相互作用和影响。因此,任何文化集团文化的传统性、现代性,都会受到外来文化及周边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关系、依存关系和共栖关系的文化共生形态具体表现在文化共生的原生性、冲突性、妥协性与和谐性。
因此,多元文化携手生活在共同的空间和领域,形成一个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多元文化共在、相互尊重、互相兼容、交流互动和协同发展的和谐文化形态。
自明清以来,畲族先民主要生活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西等地,长期游走在南方山区之中。浙江畲族先民最早何时开始耕种现在已无从考证,据在遂昌井头坞村《钟氏族谱》所载的《宋绍熙三年谅公宣公等由广潮始迁各省府州县行程誌》中,记载:“成化十年(1474)十二月二十日,钟三公带子孙移过罗源县徐江里,上炉茅山居住,初学耕田为活,供膳家口。”这说明畲族先民在此时期的已经开始学习农耕生活方式,但也不排除依然处在较为原始的“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说明清时期或更早一些时候,畲族民众已实现从游耕生存到农耕生存方式的转变。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畲族先民在向当地汉族民众学习农耕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带着自身族群“原样”生活样式在异文化的环境和社会中,通过不断的文化接触,使其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价值取向逐渐发生变化,或是部分接受,或是只限定于某个文化侧面,结合自身的文化形态,形成具有“新”的民族文化样式。同样,群族带着“新”的文化方式迁徙到不同的文化环境与社会中,经过相同的文化渗透、同化,重新达到自身文化与区域文化的和谐,这种文化的和谐性或许使其丢掉物质层面的原生文化因素,而且还会丢失精神层面的文化内核,但这种民族间物质、信息和能量等要素的互换,促使文化单元体环境适应性与发展性,从而达到文化的共生。这样的生活样式,一方面来自内部文化发展与改造需要,另一方面是来自外部强势文化的压力。
二、畲族文化共生的因素
根据传统民族的划分其最重要的因素是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特征和共同语言。而使一个民族从单纯的族群意识上升为成民族意识,还需要拥有长期共同生产生活形成的共同文化。民族文化的形成需要经过长期共同生产生活,经过不断地与各群体文化的交融并吸收外来先进文化,最终形成相对成熟、相对稳定的民族文化。在此过程,影响民族文化的变迁与发展不外乎二方面的因素,一是内发性因素,二是外发性因素。对畲族文化共生与发展也可通过共生的内发性因素文化表达与外发性因素的文化表达二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一)畲族文化共生的内发性因素
姓氏是血缘关系的纽带,对一个长期处在迁徙过程的民族而言,姓氏显得更加重要。畲族姓氏相对简单,其原始姓氏只有四大姓氏,即盘、兰、雷、钟,其他姓氏,如李、吴、周、林、千、刘、张、羊、王、宗、世、章、朱、爱、曹、方、康等姓氏是后来融入其群体组织的。畲族社会集团在历史各个阶段的整合过程中,其社会组织及其组织内部的制度性相对不是很严密、很完善,在这种状况下,血缘关系有着极大的凝聚力与影响力,强大血缘关系成为畲族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的重要特征。
作为一种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形式,“姓氏”在我国的发展已历经数千年的历史,并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演进中构筑起一条今人揭示原始氏族状态的通道。而“姓氏是随着图腾名称的产生而产生的,最古的姓氏就是图腾名称;姓氏渊源于图腾名称,是姓氏形成的一条重要途径。”④而这样的论述早在19世纪中期就已出现,如摩尔根在《古代社会》同样简述过此问题。
目前虽然对畲族始祖的考证现在没有公论,在中国历史上,每个部落、民族的始祖都是神话过程,畲族也不例外,但我认为畲族始祖也不能排除与部落首领与中原强在帝国联姻的结果并加以神话处理。而在现实畲族始祖神话处理过程中有些专家认为有不当之处,但无论是从盘瓠传说、高皇歌中四大姓体现畲族文化的核心,还是畲族大姓之盘(大哥地位)的消失或者是融入其他民族,畲族文化共生一开始就发生,并长期存在。畲族在历史上没有产生跨地域性的强有力的社会管理机构,其内部社会整合的传统机制主要由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组织和父系世系群(宗族)组织构成,血缘关系成为畲族内部传统社会关系的主轴。也可从畲族聚居村落上分析,现代畲族村寨多以血缘相近的同姓聚族而居,这一点从现存的宗谱或族谱上可以得到反映⑤。而对根据相关文献、族谱及传说记载,长子姓盘,名自能,受高辛皇帝敕封,敕长子盘自能为南阳郡武骑侯,从广东潮州凤凰山自海路迁徙时,盘姓一族的船被海风吹翻沉没大海,或传说是被告海风吹到“番国”,因此未到达连江登岸,故无盘姓在东南沿海的福建、浙江等地生息。据德国学者哈·史图博在《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中写道:“他们只有四个姓:兰、雷、钟、盘。然而在景宁及其附近地区已没有盘姓氏族了。有人认为他们已改为姓潘而成为汉人了。在景宁有一姓潘的富裕人家,据说是畲民的后裔。”
在畲族文化的起源—畲族盘瓠神话传说中,钟姓是作为盘瓠的女婿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进入畲族族群。在传统的汉文化中,尽管钟姓入赘成为其女婿,也只是半子,其原身份应该是汉族或是其他民族,虽属于这个家族的正式成员,但其血缘关系,按照民间的文化语境解读,钟姓女婿后裔进入畲族群体的记忆反映了他们和畲族其他群体交融的历史真实,站在学术的观点考察,盘瓠传说暗示了钟姓其与汉族的关联。许多钟氏宗谱也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对钟氏“女婿”表述方式是盘瓠传说对畲族历史和文化共生的最好表达。
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调查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畲族于1956年正式成为一个我国民族统一大家庭中的独立一员。在民族识别的过程中,畲族的姓氏组成也成为众多学者的关注对象,就目前的事实而言,浙江的畲族共有蓝、雷、钟、李、吴、罗、杨、娄等姓,在福建闽东地区,畲族也有李、吴、周、林、千、刘、张、羊、王、宗、世、章、朱、爱、曹、方、康等姓氏,除盘、蓝、雷、钟四姓为畲族上古姓氏传承,其他姓氏均年代较后,且多为汉人入赘加入畲族而保留原姓者。其他姓氏的加盟,促使畲族文化在区域内文化共生,促进文化集团的交流与融合。
畲族文化共生的内发性因素就是畲族语言。畲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因其长期与汉族及汉族的客家群体生活在一起,语言汉化已经非常明显。台湾学者吴中杰在畬族语言研究中,通过对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五省畲话,以及广东增城畲语进行实地田野调查研究,通过畲语内部语音系统、畲语与畲话关系、畲语及畲话的语法现象、声韵组合及基本词汇等,提出内部分片的标准,以呈现各方言点之间的异同及远近关系;通过横向的比较研究,如探讨畲话和客家话关系和畲语与各地方言的关系,提出畬话的几项条件音变。并指出:
畲话表层固然有当地汉语方言成分,但就所有汉语方言来说,客家话无疑是跟畲话最接近的,两者重叠现象甚多。然而畲话也有若干虽属于汉语方言成分、却并非来自客家的特色。畲语固有层和畲话有关系,不过这样的词项极其有限,许多畲话的非汉语成分跟畲语说法无从衔接。因此,畲话绝不等于‘客家话跟若干畲语残存成分的相加。⑥
2015年9月,与学院吕立汉、王闰吉、雷艳萍等语言文字专家到开化畲族村落考察,也同样发现此问题。雷艳萍通过畲民讲话与个别字的发音,并与松阳客家话进行对比,开化畲族群体其主要语音语调与客家方言非常接近。另一方面,雷艳萍通过请其导师对畲族语言进行录音分析,其语音比较乱,且古音较多,这进一步说明畲族民众在长期迁徙过程中,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主动接触汉文化,融入当地的语言环境,用汉语文字、汉语语法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诉求。
(二)畲族文化的外发性因素
由于历代封建王朝与社会势力的影响,加上畲族自身游耕生产生活要求等因素,畲族陆续从闽、粤、赣交界地区向闽、浙、赣、粤、皖的一些偏僻山区迁移。在长期的迁移过程中,与汉族文化进行深度接触,不断地吸收汉族先进生产技术,采用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力有了提高,明清时代逐渐由游耕和狩猎经济发展方式向定居农业经济转变,分布上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亦告形成。畲族定居聚落一般都与汉族村落交错分布,既与汉族村落保持一定的距离,又相距不远,既有相对独立性,又有密切的依存关系。这种依存关系具体体现在商品交易,如进行必要的农副产品和生活必需品交易等,畲族生活地区与周围的汉族构成了相互依赖互为补充的共生依存格局,也构成了两族间的共生关系。
这种关系不仅促进了畲族生活水平的提高,提高了生产力,更主要的是使畲族文化与当地文化形成共栖、依存格局。有些是主动接受,有些是被动接受与融合。但在这过程,更多是主动融入,形成共栖、依存的文化关系。彩带文化、服饰文化、祖图文化、契约文化等是最好的见证。
在畲族文化里面,祭祀已经形成畲民家族群体的文化象征符号,作为家族祭祀神圣之地,已深烙于畲民心中,成为一种不容抹煞的精神文化。特别是明清以来,畲族十分热衷兴建祠堂,这一方面体现畲族家族文化发达,另一方面体现畲族受生活在东南沿海汉文化的影响。畲族兴建祠堂文化活动过程中,通过吸收当地汉家祠堂文化的同时,根据自身文化特点有着比较明显的民族特色,在具体兴建祠堂时,就有着从想象到具象的发展过程。祠堂文化或者祭祀文化是畲族主动融入,形成共栖、依存的民族文化表达。
祠堂文化的发展也是一个逐渐发展过程。祠堂文化的萌芽是香炉代替祠堂。畲民初到某地,由于家族人力、财力、物力所限,不能有鼎建祠堂之举。香炉便代表家族的存在进行祭拜。《云和县志》载:“云和畲族没有祠堂。蓝姓香炉置于安溪青石岩,雷姓香炉置于黄处鬼岩。”随之,又以一种特殊的祖籍替代香炉,这种文化形式称为“祖担”。“祖担”是二只箱子或箩筐,箱子里装着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祭祖香炉、祖牌、龙头祖仗、铃刀、龙角、祖图与宗谱等祖籍是畲民流动的祠堂。浙江《建德县志》载:“畲客之祠以竹箱为之,内贮祖牌及香炉。”祖箱来往于畲族乡村,主要用于畲民家族的祭祀,其中尤其是畲民醮明祭,更必须将祖籍请进家门,醮明祭却指传师学师。可以说,传师学师是祖籍文化形式发展而来的。在随祖籍进门的有家族父老,还有畲族巫师。祖籍中除了祖牌、香炉处,还有祖图、祖杖等器物。蓝、雷、钟诸姓的香炉的个数是不同的,蓝姓6只香炉,雷、钟诸姓为5只香炉,祖籍中的祖杖长度也不同于祠堂中的祖杖。
随着家族的繁衍,房屋的增建,村落的扩展,家族经济实力的提升,才能考虑到建祠。在祠堂未建之时,往往会把祖屋当成族从祭祀、议事之所。即使祠堂建成后,祖屋仍是族人缅怀先祖,激励后人的教化之区。祠堂建成后便成为畲民议事、祭祀和红白喜事设宴的公共场所,这与汉族姓氏祠堂的功能相差无几。畲民称为“众厅”,是家族联建的大房屋中预留的大厅,产权属家族公有。汉民姓氏祠堂只是某一姓氏的祠堂,其他姓氏是不能在祠堂中进行各种祭祀、议事和红白喜事设宴的。而畲民的祠堂与不是单姓祠堂,可以是多姓祠堂。
总之,畲民的祠堂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形态。现代意义上畲族祠堂,业已成为畲族“民族即家族”理念的标志。而从香炉—祖籍—祖屋—众厅—祠堂,则是家族历史沧桑的反映以及族人文化变迁集中展示。其功能与汉族的祠堂功能没有区别之外,在此过程畲族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即传师学师文化。传师学师文化产生与发展是随着畲族活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逐步形成的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样式,也是迁徙到浙江畲民对畲族文化内涵的丰富与发展。正是由于其吸收了外来文化样式,才有今天畲族的祭祀文化、祠堂文化及传师学师文化。
三、畲族多元文化发展基本路径
民族文化的发展既要满足民族内在的文化需要,同时也要考虑文化发展的外部动力一条件,也要符合人自身的需要。畲族文化多元性发展既要遵循共生的生物学要求,也要符合民族共生文化的历史因素与现实,为畲族文化发展提供一种恒常性的人文精神资源,为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注入一种持续性的文化驱动力。
在当代文化大融合、大发展的文化多元化道路上,畲族文化的发展,在坚持自身传统文化发展路径外,一是通过坚持文化发展的现代性,即融入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指引畲族文化共生模式建构;二是通过超越畲族文化固有的文化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实践中推进畲族文化的开拓创新,即坚持传统又有创新思维发展民族文化;三是通过坚持和谐共生的价值取向,正确处理畲族传统文化与汉族文化及现代文化的关系,并塑造良好的畲族传统文化发展环境,深化畲族多元文化发展。
为此,畲族多元文化的基本路径要坚持四个原则,即“独立性、交融性、独特性与创新性”原则。独立性原则强调文化发展有自己的空间与环境,根据自己的文化发展规律传承与发展,不仅要依靠政府,而且要依靠民间与社会团体做文化事业,推进畲族文化的发展。现在畲族文化存在一种现象,则在畲族文化发展过程中政府推动畲族文化发展占主导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不是真正的畲族文化的发展与民族文化的繁荣,只是给人、给社会一种假象,其文化张力不强,很多文化样式生命力很快被社会淘汰,被人们所遗忘。只有畲族自身文化需要,通过畲族自身挖掘与深化,并通过政府引导,这样的文化才能有长期性与生命力;二是交融性原则,也可叫互动性原则。强调民族文化发展的依存关系,则通过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才能了解自身文化的短板,才能知道其他民族文化的长处,才能有针对性地改造民族文化这不足,提升畲族文化核心竞争;三是独特性原则。强调畲族文化发展独一无二性,不受周边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发展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要有自己的文化个性与性格;四创新性原则,也叫可持续性原则。这里特别强调要有畲族文化研发与保护基地。畲族文化产品的开发,离不开文化研究团队支撑,离不开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合理利用,因为开发文化产品的目的不仅在于传承与弘扬传统畲族文化,在于使畲民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要重视畲族文化研发团队建设,重视畲族传统非遗传承人的保护与利用,保护畲族传统文化资源,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做到畲族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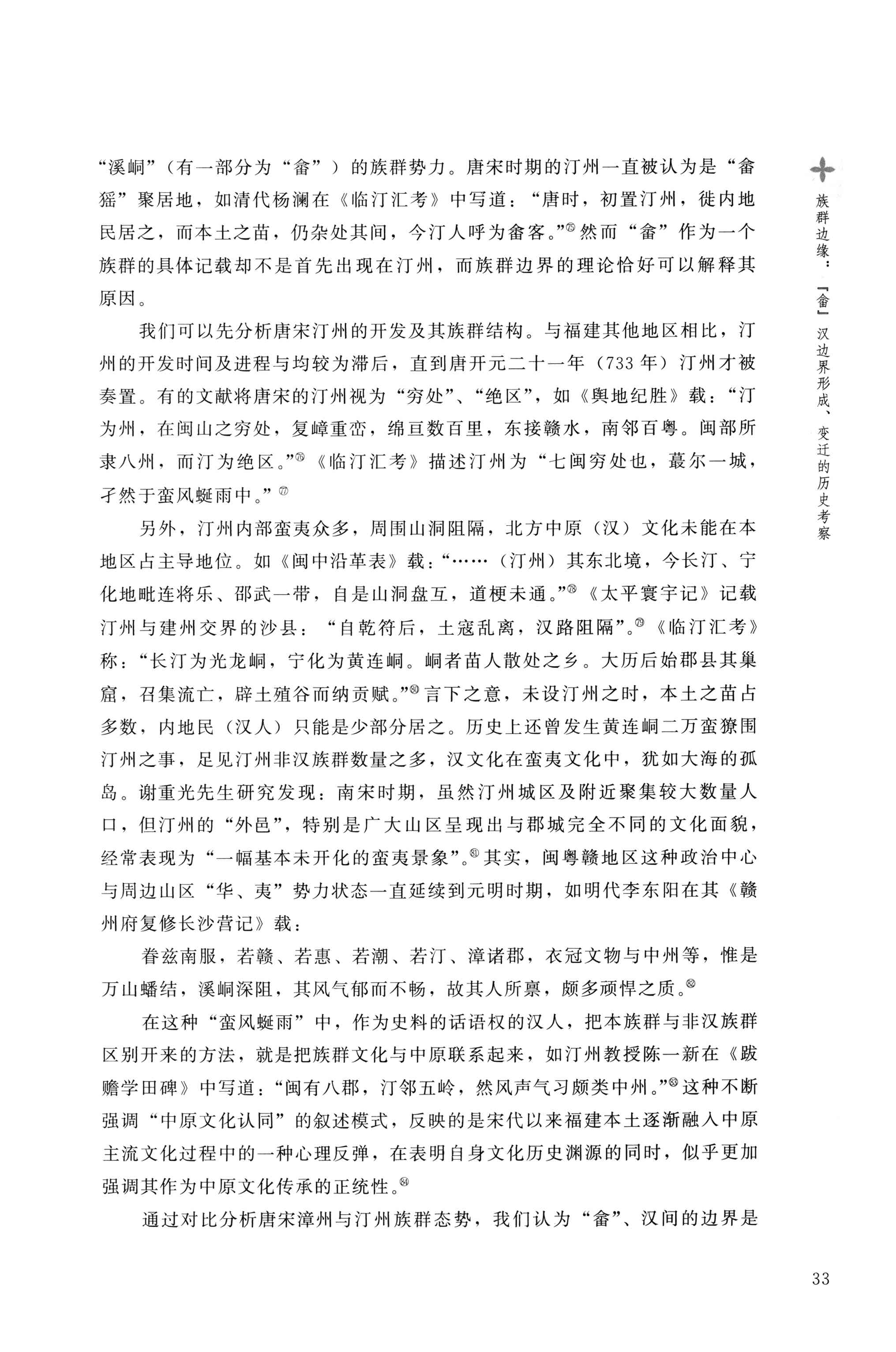
相关地名
宁德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