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经济
| 内容出处: | 《畲族福建罗源县八井村调查》 图书 |
| 唯一号: | 130920020230005140 |
| 颗粒名称: | 第三章 经济 |
| 分类号: | F127.57 |
| 页数: | 36 |
| 页码: | 43-78 |
| 摘要: | 本章介绍了八井村畲民在建国前经济状况困苦,多依赖租佃和借贷为生,受到地主和高利贷者的严重剥削。 |
| 关键词: | 八井村 地方经济 畲族 |
内容
八井村的经济从迁徙定居此地后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但历史上的“刀耕火种”和狩猎经济已难以寻觅,直至今日,八井畲民的经济仍以农业经济为主,与周围的汉族差别很小;其他的经济活动,例如手工业、畜牧业、养殖业、林业虽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因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多数已成为村民的个人行为,也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1949年以后的集体经济同样历经了反复,今天,八井畲村的集体经济相对较弱。
第一节 生产关系的变化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生产关系
(一)生产资料占有情况
根据我们在八井村收集到的清代土地买卖文书看,在乾隆年间,八井村福房的雷君恒(又名雷洪溪)是一位受到罗源县政府旌奖的“耆宾”(地方豪绅),①他从县城和附近汉族手中买进了许多土地,并建了两座占地面积很大、雕琢精细的“八扇房”瓦寮。至清代末年和民国初年,原还拥有不少土地的畲民如雷坤照等开始没落,不断把自己的土地典当和卖出。到新中国建立前夕,八井村的畲民几乎都成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土地几乎都集中在汉族地主手中,畲民的土地多是从汉族地主那里租佃来的,得付出高额的实物地租。畲民族中虽有1户地主,但他仅占地5亩多,系高利贷地主。畲族农民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少又因租谷、借贷无法清还,年复一年,利上加利,只得把土地先典当给地主,随后又可能因无钱还债而把土地的田根断卖给地主,而使自己所拥有的本来就很少的土地流入地主手中。地主土地日渐增多,而农民一天天失去了土地。
根据土地改革时所评的成分,也可以看出当时八井村生产资料占有的情况。在当时八井行政村的189户中,贫农有104户,雇农23户,中农58户,富农2户,半地主1户,地主1户,贫雇农占了一半以上。①由于八井行政村的土地册丧失了一部分,无法全部统计,仅根据该行政村中163户人家的占地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163户中,贫雇农有106户,中农为53户,富农2户,半地主1户,地主1户。他们所拥有的全部自耕田为185.53亩,农地62.07亩,共计247.6亩。租入的土地有:田1053.33亩,农地20.1亩,共计1073.43亩。自耕的与租入的田地共有1321.03亩,其中租入的田地占了81%。这清楚地表明,土地都集中在地主手中。
如果以每户占地的情况来看,也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畲族农民都是无地或少地的,其情况详见表3-1:
在这163户畲族家中,只有1户“半地主”占有田地10亩多,是八井畲村中占地最多的1户。其次,八井村有户人家被划为地主成分,但其占田很少,其主要是靠与城关的地主合作放高利贷剥削畲民,因此当时的土地都集中在汉族地主手中。
(二)租佃关系与借贷
从上面的生产资料占有情况来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八井村的畲民多数是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绝大部分都向汉族地主租佃土地耕种。所付的地租,一般都采用固定的实物地租。由于土质有好坏,地租也有不同,但多寡都由地主确定。地主可以任意抬高租价,甚至坏田也要当好田出租。畲族农民因为无地,为了生活,也只得接受高额的地租。一般每亩地租是300斤、250斤、200斤不等。在新中国建立前,畲民习惯的计算法都是以湿谷计算,合干谷8成。以村长雷兴连为例,他租种2亩田,每年要付给地主地租550斤,牛租谷子30斤,而这2亩田半年可收850斤,地租就占总收获量的32.6%,牛租、种子、肥料还不包括在内。这是丰年的情况,如果遇到歉收或病虫害,地租也是1斤不减,畲民往往把全年的收成用于纳租还不够。如租到坏的田地,畲民就要赔得更多,如村长雷林曾向地主租了1亩坏田,1年的全部收成还不到1担,却要交租2担。若当年的地租无法交清,地主就把这些租谷直接转成高利贷,每季以利息50%计算;或强迫畲民到其他高利贷者处借高利贷来还地租。
(三)借贷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八井村民普遍都很贫困,经常需要靠借贷来维持低下标准的生活,因此在村里存在各种借贷形式多,其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1.借谷:如果正月借谷100斤,六月早稻收成时,就需还谷150斤,利息为50%;如果一季无法还清,下一季的利息为本利的50%,因此到年底就要还225斤,年利率为125%。如1年无法还清,同样再以本利按每季度50%计算,年复一年滚下去,农民就得卖掉自己的土地来还债。
2.借钱:在八井地区,早期的借款一般是年利50%或30%,以年利50%较为普遍。但在新中国建立前的几年内,利息特别高。借款不是以年息计算,而是用月利计算,一般的月利为30%,而且还要利上加利。例如正月借10元,二月就需还13元,三月再以13元加上利息的30%,就需还16.9元,以此类推,等等。
3.青苗钱:青苗钱又称谷贷,它以钱贷出,收入以谷。这是地主、高利贷者利用人们在青黄不接急需用钱之机,乘人之危抛出的一种高利贷形式。如本地地主雷世琪与罗源县城李大玉相互勾结,常利用这种形式剥削畲民。例如当时一担谷价9.6元,李大玉贷给雷世琪每担7元,其中每担赚了2.6元,而雷世琪再以每担3.5元贷给农民,利息为100%。一般贷出时间是4月或7月青黄不接时,而在6月或10月收成后就要马上清还,前后只有4个月时间。这种剥削最为残酷,地主牟利最大。①
4.实物代役租:即向地主借谷子来吃,而在农忙时到地主家里做短工,以所得的工资还给地主的借贷形式。
5.货币贷役金:就是向地主借钱来使用,然后同样在农忙时到地主家里给地主做工,以所得的工资还地主的借贷形式。
后两种形式虽然看起来没计算利息,但地主、富农放出这些钱时,必须事先选好对象,一般是选择劳动力强,技术样样全的人为对象。地主们的剥削,主要是在工作中给他们增加劳动强度,一般他们都要比平常的工作多付出1/3的时间,同时,地主、富农只付给低廉的工资,因此其剥削量并不亚于以上几种。
农民借贷都是向地主、富农和奸商告贷。地主、富农放贷时也不是盲目的,要视债户家里是否有财产,如果债户家无立锥之地,即使愿意出高额利息也难以借到,如雷明节因为家贫如洗,地主就不肯借给他。
(四)雇佣关系
在1949年以前,由于畲族农民家庭普遍贫困,所以许多人家不得不出卖劳力。而在当时,因本民族的地主、富农少,他们占有的土地也少,因此八井畲民一般都是受雇于汉族地主。据统计,在新中国建立以前的几年中,八井畲村的畲民,被人雇为长工、短工和零杂工的有33人。
1.短工:一般被雇佣为短工的,是因他与地主有借贷关系。地主是利用债务和他家庭困穷,不得不出卖劳力,然后直接到他家来雇,或通过其他人的接洽。由于债户家穷困非接受雇用不可,所以地主把工资压得很低,根据雷明节1949年临解放几个月的情况看,他每个月工资仅30斤谷子,折算为1.8元,即每天1斤谷子。以他的劳动量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和他所得的低微工资相比,这种剥削是很重的。
2.长工:如雷任传在1928年~1934年前后7年时间,被外乡汉族地主雇为长工,工资最初是每年300斤谷子,后来提到了600斤。他除了生病外,每天都得朝出暮归,除了耕种田地外,还得帮地主家做些砍柴等杂务。他每年要耕作八九亩田,可收入谷子40担。与之工资相比较,这种剥削是极其残酷的。①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生产关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从此八井村畲族的生产活动就与党中央与国家的政策息息相关。首先是减租减息,这使畲民受地主阶级的剥削程度大大减轻。其次是1950年6月县里开始,10月八井村开始的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富农的多余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贫、雇农以及中农,使得耕者有其田。如根据1952年2月罗源县政府颁发给八井村村民雷益母的“福建省罗源县土地房产所有证”(罗字第02163号)的情况看,雷益母在土改后分到了3.3亩田地和1间占地约0.34亩的房屋,其中水田2.9亩,农地0.4亩,其分布的情况为“七斗洋一丘,0.7亩,东至雷信开田,南至己田,西至雷川美田,北至雷信仁田。”“南山洋一丘,1.4亩,东至蓝顺意田,南至溪,西至雷志兴田,北至雷兴桂田。”“溪骨一丘,0.5亩,东至雷炉佐田,南至路,西至雷炉佐田,北至溪。”“扶楼边一丘,0.3亩,东至路,南至雷典蛋田,西至雷信仁田,北至路。”农地为“溪坂一丘,0.4亩,东至雷为顺田,南至荒冢,西至路,北至雷金和园。”当时还规定“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保护农民已得土地所有权’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之规定”,确定雷益母所得这3.64亩田地、房产为其“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与、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①这一均贫富,使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八井畲村畲民的劳动积极性,并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政府还针对畲民们积贫太久,在生产上遇到的困难,给予积极的救济及资金上的支持,使得畲民们的生产收入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1958年民族调查时,调查人员记录了八井村的一个个案,现照录如下:“雷章文,雇农,解放前一家五口人,自有农地一亩二分,收入茹米(即地瓜米)五百斤;租耕田一亩,年产三百斤谷子,交纳地租一百二十斤。自己买不起农具,在农忙时都向别人租用。苛捐什税每年得交18元。一年砍柴做短工,辛勤劳动,但得不到暖饱,全家只有破棉被一床,睡觉多半盖蓑衣,衣服不能蔽体,破烂不堪。解放后五口人分到八亩水田,原有一亩二分农地也保存,并分到耕牛1头,每年收入谷子三千二百斤,茹米八百斤,养毛猪收入55元。粮食收入除交公粮五百斤外,还卖余粮一千一百斤,几年来添置毛衣三件,箩二挑,谷屏一块,犁一张,耙一张,棉被一床,茶壶酒瓶,每年每人新制单衣一套、布鞋一双,1953年用了58.8元买了一头耕牛,生活改善很大。至今本人回忆解放前后生活情况,他感慨地说:‘过去(指解放前)没吃没穿,天天砍柴过活;解放后生活根本改善,感到非常满意,对党和毛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谢!’”①
1952年,新建立的八井乡中,也组织了几个常年和临时的互助组,1953年在合作社化运动过程中,12月八井乡的八井村中有18户人家首先出来建立起“建新”初级社,有的人还积极参与区的供销合作社的建立,购买供销合作社的股票,开始走合作化的道路,生产关系发生了一次变革。在这次调查中,我们有幸地发现了两张“罗源县第七区供销合作社”1953年12月26日发行的“股票”(图3-1)。这两张股票的持有者为八井村民雷木杉与雷志森父子,他们各购买了“壹万伍仟元”(相当于15元)。
1955年12月,在合作化高潮中,八井乡成立了高级社,八井、横埭、竹里等畲村的初级社和互助组及单干户,全被组织进“八井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中。1958年,在公社化的高潮中,八井高级社的所有人也报名参加人民公社。在1958年10月1日成为罗源县城关人民公社八井营。八井地区的畲民把原先的土地及生产资料全部转为集体所有,由集体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至此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建立起来。八井畲村的生产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由于“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的折腾,群众生活也出现了困难。1961年贯彻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精神,实行按劳分配后,人民的生活逐步有所好转。1961年5月,县里增设人民公社,八井大队隶属城关区小获人民公社。1962年2月调整社队规模,并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固定到队。实行粮食分配与实际投工、投肥挂钩的分配办法,社员的生产积极性逐渐提高。1966年6月,八井大队归属松山人民公社,仍管辖竹里、横埭村。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运动中,八井畲民又经历了一次折腾。
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推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公社体制发生重大变化。1984年9月,实行政社分设,取消人民公社,恢复乡镇建制,八井村的经济体制再次发生了重大的变革。1982年底全面实行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再次极大地唤醒了畲民的生产积极性,至20世纪80年代末,已基本解决了粮食口粮问题,农村经济再次发生了飞跃,生产关系中也开始了新的变化,随着承包期限的延长,生产经营的个体化与自主权已成了时代的主旋律。而在这以后的20年发展中,为了应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八井畲村的冲击,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变化,如三五户,七八户不等的联户,甚至跨越了本村的界限的联户也开始出现;民间的土地租种和“轮租”等形式也开始出现。所有这些新时期、新形势下出现的事物,它们在农村生产关系变革中的作用和地位,还有待我们更深入、细致的观察和研究。
第二节 劳动生产方式的变化
在八井畲村,过去拥有适合水稻耕种的田亩并不多,水利条件差是问题的关键。所以,旱地杂粮耕作始终与水稻耕作具有差不多同等重要的作用,所谓“地瓜丰年粮”的俗话便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但随着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对兴修水利的重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种状况得到改变。
新中国建立前八井村的农作物有:水稻、地瓜(番薯、甘薯、红薯)、小麦、黄豆、花生、油菜、苎麻等,其中以水稻面积最大,地瓜居次,除了这两种作物之外,其他并非每家每户普遍种植,数量也很少。水稻有单季,也有双季,以双季为多。早稻种子有“流山余早”、“早仔”、“软亭早”,其中以“软亭早”为主,占早稻播种数量的70%。晚稻有“黄尖”、“红谷”、“莳谷”、“术谷”等五种,尤以“黄尖”为主,占晚稻播种面积的80%以上,“红谷”、“南旱”主要种在山田中。八井畲村虽地处山腰上,但河谷平原地居多,梯田仅有1/3,双季稻一般都种在土质较好,水源充足的平原水田中,而贫瘠土质的水田一般只种单季稻。在1949年以前畲民很少种小麦,大麦更少,因为畲民喜欢种小麦而不喜欢种大麦。虽然以产量来说,大麦可以多产,但由于价格低于小麦一半,同时也很难卖,所以畲民只种少量供自己食用。
水田稻种平均每亩5斤,但有的晚稻只下4斤。地瓜每亩平均2500株,植单行。小麦每亩平均下种子3.5斤,大麦2.5斤多。根据土壤的质地,1958年土改时,八井村对土地进行了等级评定,农田可分四等,产量不一,水田以收成最好的双季稻为例:甲等每亩年产量可收成500斤,乙等420斤,丙等350斤,丁等250斤。晚稻收获量一般要比早稻多收成50%,而旱田单季稻每亩平均150斤左右。农地以地瓜米计算(每百斤干的地瓜米合400斤生地瓜),甲等亩产500斤,乙等400斤,丙等300斤,丁等200斤。
小麦最好的可收130斤左右,一般是100斤,差的只能收成80斤;大麦最好的亩产可达200斤,中等有120斤,差的100斤,这是一般情况,荒年不在此数,且由于各家庭经济情况不同,如遇家境困难,肥料缺,那收成就会减少,如果是较富裕的农户,因肥料充足,还可以多收。①
八井村民使用的生产工具有:犁、耙、山锄、田刀、耘草耙等。犁耙用于犁耙水田,但也可以犁地瓜园,山锄用于开荒及耕种山地,田刀用来割田埂草,锄头可农、田通用,耘草耙适宜在农地使用。
这些工具的构造样式与附近汉族的无异,都是汉族铁匠打制的,或从县里买来的铁农具,所以这些生产工具都是模仿汉族的,唯有锄头与其他地方的畲族有异,其刃部不是平的,而是圆锥形的,这种锄头用来翻稻头较为方便,但也与附近汉族相同。所以,从生产工具的相互仿样可以看出畲汉两族人民生产工具的交流。耕畜方面主要是牛,有黄牛和水牛两种,根据1949年统计,全村有牛40头,平均每4.5户有1头牛,它们全部用于耕田。在农业运输上,新中国建立之前这里尽是些羊肠小道,出门就需要登山越岭,加上山区道路崎岖不平,不可能应用任何交通运输工具,全部靠人用肩挑。
勤劳是八井村民的传统美德,全村男女都参加劳动,没有很严格的分工,但在过去犁耙田由男人来承担。新中国成立以后,妇女也开始学犁田和插秧,而且完全可以胜任。过去拔秧是妇女的专业,男子很少会拔秧,现男子也干拔秧的活。男子还兼搞手工业,而妇女则管家务多。老年人干些轻活、零工和指导生产等工作。由于劳力缺乏的缘故,八井村许多小孩从小就参加劳动。
在1949年以前,八井畲民每人平均要耕种2亩多田地,但因无劳动力的畲家占多数,因此形成地多劳力少的状况,而且山区的地比平原的需要更多的劳力,因而,显得八井村劳力不足,在生产上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农民自发组织帮工来解决劳力不足的困难。一般在农忙时,除了插秧外,其他事都可帮工,几家人互相换工、轮流收割、耕种。一般都是以工代工,不计男女劳力,帮一天工主人只给一餐饭,不计工资。这种季节性帮工在1949年以前是普遍存在的,也形成为一种惯例,彼此间没有剥削存在,纯是一种互助性质。在家庭劳力组织上,过去都是个体单干,所有农事由各家自行安排,没有其他生产管理上的共同组织。
据统计,在八井村1个劳动力全年的田间劳动最多能达280天,最低也有160天,劳动力强的女人可耕9亩田,最低也可耕5亩地。1949年前,雷志华给地主当雇工,他们2人共耕作地主田地20亩。其中1.5亩是地瓜田,全年可收成120担左右。如果每人每年的口粮平均以480斤计算,可供给25人吃1年。如以自耕农计算,在八井村这个地方,只要耕作1亩上等田即可维持1个人全年的食粮,但由于1949年前绝大部分土地都是向地主租佃的,需要付给地主以高额地租,因此,即使是丰年,绝大部分畲民还是不能维持最低的生活。
八井畲民在常年劳动中,已掌握了各种农作物生长过程的知识。如他们习惯用农历计算,一年24个节气一般的老农都能对答如流,播种、收割、施肥等农活,都是根据24个节气来安排的,其安排详见下表:
耕作技术方面:水田一般是二犁三耙,即在秋收后,有的田种上麦子;有的先把稻头挖起来烧后作肥料,约在十二月把田犁好晒土,明年三月临春耕时,再引水来溶田,并施1次人畜肥约20担作基肥,然后耙平;其后不久,再翻犁1次,插秧时再耙1次,然后再用“木梯”把田耙平,就可以插秧了;插秧的同时,再施1次草木灰肥,每亩用量约15担。早稻一般不用除草,但在播种时需把田埂草铲除掉。早稻插秧后15天左右,再间插晚稻。早稻一般只要65~70天就可以收割。早稻收割后,挖去稻根15天后,晚稻除草1次,施肥数量一般与早稻相同,施肥与除草同时进行,这样到了十月立冬时就可收割晚稻。
旱田都种单季稻。旱田的耕作比较粗放,一般只一犁二耙。先挖起稻根,然后翻犁晒干,下种时再引水进来,耙二次即行。旱田大部分不施肥,如果施肥,每亩约施人畜肥5~6担,并除草1次。旱田的产量比水田低,亩产才100斤。有的单季山田还施用牛骨肥1次,每亩每下1斤种子施1斤牛骨。牛骨肥的制作是把牛骨压成粉,掺和进稻草灰和人粪;其分量大约是牛骨5斤和人粪半担、稻草灰1担一起拌搅作肥。施肥后产量较高,这是畲民在长期农作摸索中作为增产的一种经验。
地瓜最早在芒种时种下,最迟不能超过夏至。种地瓜的耕作技术简单,首先进行翻犁,然后用锄头敲碎土块,搞成一畦一畦后,把地瓜苗插下去。1949年以前一畦通常只种一行。种地瓜的肥料以草木灰为主,方法是挖洞施肥,即在每株旁挖一个洞盛肥料。第一次下肥,大约每亩需草木灰20多担;约半个月后,除草1次;1个多月后,再下第二次肥,施人畜肥约20担。过去种地瓜不割藤,也不再翻土。
过去种麦子不用犁,用锄头把稻根挖出来,把地挖得一畦一畦的,上面有一层薄薄的松土,能盖埋住种子就行。1949年以前不用条播,采用的方法是挖洞点种,把种子和肥料放进洞里,盖上松土即可。种小麦每亩需肥料约32担,以草木灰居多数;而大麦则仅需15担,其肥料也是以草木灰、土粪居多。
在新中国建立前,选育种办法很简单,只要选择一丘长势比较好,没受过灾害的就选为种子。育种时,先把谷种浸在木桶里,把浮在水面的捞起来,沉下去的即作为秧苗种子。
早晚稻的行距都在33厘米左右,根据老农的经验,凡是水田土质好的秧要插得稀些,土质差的田秧则要插得密些,但相差也只是5~6厘米。因为他们认为,土质好的田,秧苗插稀些,秧可以长得茁壮;而土壤差些的田,插密些,秧苗多长些也可以多得收获。
八井村水利灌溉设施只有两条10米宽的水沟,没有池、潭建设,更没有水坝蓄水的设施,因此,水利灌溉方面,都是利用天然的山水,对水资源无力控制,有水整天流,无水则干旱。而旱地都是靠天下雨来灌溉,名为“靠天田”。
新中国建立前,农业的病虫害很厉害,而且种类又多。稻子以蜉流子最厉害,其宿于稻根,吃掉稻根茎使之枯萎。此外,还有螟虫、琉球虫等。地瓜以九节虫、金龟子最厉害,尤以九节虫更凶,把根茎咬断,使之枯萎而无收。由于当时畲民科学知识极端贫乏,认为这是天灾、气候的关系,因而通常把防止虫害的唯一办法寄托在神灵身上,拜神求佛以求防治。
1949年以后,农业生产技术不断革新,全面推广水稻新产品和连作制,耕作技术改由一犁一耙为二犁二耙甚至三犁三耙,改旧式步犁为新式深耕犁。犁分为犁辕、犁底、犁板、犁箭、犁把、犁头、犁铧、犁弓八部分,犁头、犁铧是铸铁的,其余均为木质,一般重24公斤左右。耙分为耙身、耙架、耙梁、耙齿、龙楸等五部分,耙梁是用木连成的,重18公斤左右。田刀分为田刀和田刀柄,柄木质,重2.5公斤左右。五齿耙分为耙齿和耙把两部分,柄木质,重1.8公斤左右。其余还有斗笠、谷桶、扁挑、草刀、箩筐、风车、谷砻、石臼和石杵槌、筛、磨、簸箕等。利器有大柴刀、镰刀、斧头、锯子等。这些工具与汉族无差异,都是从市场上或汉族铁匠处购买来的。
自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生产劳动的个体化和农业工具的改革,过去集体化时期使用过的插秧机、切薯机、电动打谷机、手扶拖拉机等都不用或很少使用了,但一些适应于山区和个体劳动的机械化、半机械化的小型农业生产工具仍继续使用。八井村畲族普遍使用脱粒机代替了以前的稻楻、稻梯;除病虫害则用喷雾器。现在田间管理也有改进,在普遍进行三翻三耙的同时,也进行同次数的除草;除虫主要靠掌握好虫期,用农药来治灭;水稻品种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通常都选用各个时代最好的杂交水稻品种,例如“闽优一号”、“威化二号”等;地瓜的情况也一样。水田翻耕过去为20厘米左右,现在则28厘米左右;深耕后便于密植,1亩田可以增播秧苗2万株以上,如肥足和管理得当,密植能增产。种子的使用量与收获量因土质的不同而有差别。大致是水稻、地瓜1∶21;小麦1∶17;大麦1∶19;京豆1∶13;田豆1∶10;黄豆1∶9;马铃薯1∶19;芋头1∶12;玉米1∶6;高粱1∶7;豌豆1∶8;四季豆1∶16。不适宜种双季的水田逐步改回种单季;在适宜种双季的田地中,多实行两熟制(稻—稻,稻—菜,经济作物如西瓜—稻等)或三熟制(稻—稻—蔬菜等)。蔬菜种植一般不外售,自己食用。蔬菜主要有萝卜、南瓜、茄子、冬瓜、菠菜、扁豆、老虎豆、辣椒、白菜、芥菜、葱、蒜、韭菜、芋头、胡瓜、空心菜等。但近几年也种一些批量卖于市场。此外,近年来还有人把闲置的旱田与山地用来种植龙眼、橄榄、柿子、柑橘、柚子等果树,生产水果供应市场。
现在八井村已很少使用如牛骨粉、兽骨粉、草木灰、垃圾灰、山灰、沟土、沃土烧熏、人粪肥、禽畜粪肥、饼肥等农家肥和天然肥,普遍是到市场上购买硫酸铵、钾镁肥、尿素、碳铵、氯化钾、复合肥等化肥。除虫一般常用的农药有甲铵磷、乐果、敌百虫、敌敌畏、稻瘟净等。化学肥料与农药的大量使用,造成土质弱退,瘦瘠情况逐年深化;化学农药的喷洒,也污染了空气,致使天然的灭虫、除虫的能手青蛙、蛤蟆、田蛙、水蛇等大量消失。干粉农药的喷洒,随风吹散四方,也殃及山林中的黄鹂、啄木鸟、夜鹰子等,造成了其负面的环境问题。
第三节 经济结构的变迁及各行业发展状况
1978年党中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八井村推行了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体制得到改革,生产结构发生了变化,初步实现了农村经济由纯粹的粮食增长型向综合发展型转化,改变了千百年来的种养品种单一的状况,在粮食生产稳步发展的情况下,水果、畜牧业养殖等生产有了飞速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初步改变了落后状况。这一变化的总体情况可用下面表格反映出来:
另外,我们可以根据1995年和2002年福建省农村经济基本情况的统计表,对八井村的各行业进行对比,以考察当前八井村各行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从上表可以看到,随着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各行业都有明显的进步与发展,但林业因环境保护的影响,其收入减少。农业经济收入特别是种植业收入的增长速度缓慢,其中谷物收入没有增加反而大幅减少。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受粮食价格下降的影响外,农产品的深加工无疑是促使农业收入以其他形式得以实现的因素。由上表还可以看到,除了牧业等传统副业继续成倍的增长外,1995年以来的这七八年中,第二、三产业有了迅猛的发展,建筑业的收入增长了5倍,运输业收入增长2倍,工业收入增长了4倍,商饮业收入增长13倍,服务业收入增长了7倍,很显然,这些行业已逐渐成为八井村畲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综合上表的情况还可以看到,八井畲村的经济结构,经由近2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变化,已从原来的单一粮食种植结构,逐渐趋向于多元结构,畲民的市场愿望和市场意识得到了加强。根据2002年福建省农村经济基本情况统计表可以看到,2002年八井畲村总劳动力221人中,外出打工的劳动力有85人,占总劳力的38.5%;其中常年在外打工的达到了50人,占总劳力的22.6%,这些也是影响八井畲村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除了表格反映出的几大经济类型外,八井畲村的手工业和一些传统经济行业的变迁也值得我们关注,特别是畲医和土木建筑、裁缝等传统行业在商品经济的驱动下,有了新的发展。
新中国建立前,八井畲民从事很多行业的手工业生产,如有缝衣、制竹器、细木、土木、理发、制棺、做桶等,但是从业的人数并不多,仍紧紧与农业结合在一起,虽然也有一部分人开始脱离了农业生产,专门从事于某种手工业劳作,但人数却很少。
裁缝:新中国建立前,全村裁缝的从业人员有9人,其中3人是专业的。要想成为一名裁缝师傅,一般需要经过3年的学徒学习,而后才能独立工作。在学徒期间,其所做的一切收入归师傅所有。过去做衣裤都用手工缝纫,专门制作畲女的绣花民族服装、围裙和男人的汉装,每件衣服平均需要工作4天,每年平均可以做90天,每天5角,年平均最少收入为45元,折谷子7担。有的出工较多,则可以收入9担左右。有的1年最多可以做260天,全家的生活全靠裁缝的手工来维持。
做土木:1949年以前,全村从事做土木业的人员有9个,每年平均可做半年时间,主要是兴修四扇房、六扇房之类的传统木结构房子,每天的工资约18斤谷子,每年收入可达20多担,而技术差些的工匠每天也有12斤谷子的收入。
制竹器:1949年以前,全村制竹器的从业人员有7人。他们当学徒的时间也是3年,在学徒期间,学徒的一切收入为师傅所有。他们平均每年有半年工作时间,编制箩、筐、土箕、簸箕、谷筛、米筛、谷笪、竹匾(俗称“薯屏”)、篮子、盖篮、果盘、竹枕头、竹凳、竹椅、竹刷,甚至竹榻等。在农忙时,通常由雇主来此雇请,而在农闲时节,则自己外出接受雇工。如雷世兴在1949年前就到连江等地去干制作竹器的工作。制竹器每工的工资为谷子10斤,每年平均有15担谷子的收入。
做棺木:1949年以前,八井村做棺木的从业人员有2个。他们都是到城里跟长乐人学习的,需当3年的学徒,工资以件计算,每年平均可做85天,每个棺木工资1.2元,相当于谷子20斤。由于八井畲村的情况是有钱人才有可能事先做棺木而备用,而一般穷人,都是在人死后才到城里买几块木板雇人加工。这些做棺木者的工作就是专门做加工的。
理发:1949年以前,八井有2个剃头师傅,最初都是向小获的汉人学习的,需当3年的学徒,农忙时返家生产,3年期满,师傅发给1套理发工具,自己去为人理发挣钱。在新中国建立之前,理发都是包全年的,16岁以上者,每人每年6斤谷子,16岁以下者则供给一顿饭而不必付工资。例如村民雷兴连在1940年理发收入了800斤谷子,而他同年所种的地,除了纳租外只剩下400斤。全家人粮食不够,主要都是靠理发所得来的谷子补贴,其占总收入的66%。
造桶:1949年以前的从业人员有2个,他们专门制作木桶,平均每人每年有80元的收入。
由此看来,八井的手工业从业者虽不多,但其收入,占家庭经济总收入的比重却很大。另外,当时的手工业具有下面几个特点:
1.手工业大多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八井村的手工业者几乎都是半工半农的。
2.普遍存在师徒间的剥削关系,学徒期一般要3年或4年,在这期间,学徒的收入归师傅所有。
3.同行业者彼此间并没有任何组织和规章制度。
4.他们所做的工作都是单纯的手工加工性质,因为原料都是雇主提供的。
5.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流动性很大,膳食一般由雇主供应。①
1949年之后,在“以粮为纲”的几十年中,传统手工行业并没有什么新的发展,但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近几年中,村民普遍感到粮食已不成为其家庭经济的主要收入来源后,“粮食不值钱”,“我们不愁粮食但我们却缺钱花”。虽然有的手工业行业已消失,如制棺木和理发、缝衣等,但有些行业在现代仍有用武之地,因此,那些有手艺的畲民们纷纷利用现在仍有用的传统行业,变通后以适应当前的商品化社会。如由于现在建房已用钢筋混凝土、砖石等材料,传统从事木构房屋建筑的大木工匠只好改行,做起细木来。村民雷有金在1949年后是村里有名的大木师傅,20世纪90年代以前,八井畲村所建的传统式样的木构或土木结构的四扇房、六扇房或假八扇房,大部分都是经由他手设计建造的。此外他也设计建造了小获村的观音庙。现在木工们都使用上了电动的木工工具,如手机刨、电钻、切割机、刨床等,他也只能在家里做一些锅盖、饭甑之类的日常木制用品,拿到罗源市场上卖,没有再参与房屋的建筑。不过即便这样,因他有手艺,其家庭的收入也比单纯靠田地收入的人家要好许多。另一方面,由于时代变了,具体的生活内容也变了,有的人适应了这种变化,而去外面学习做石匠和泥水匠的本领,成了村里建筑现代民居的主力,并以此来养家糊口。村民蓝水盛1975年17岁时就外出跟着莆田人金弟学习打石头和建砖石、钢筋混凝土材料的建筑。至2003年已从业28年,他多数在福州、罗源一带做建筑包工头,有时也在村里帮人建房,其收入在村里算是比较好的一位,他一次性地把自己的两层楼的住宅建好。而他哥哥蓝水银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虽也在近年建了新房,但他只能先建一层,待以后存下更多的收入后,再续建第二层。
在相关统计报表中,数字所显现出来的副业在八井畲村经济中的影响似乎很小。但根据入户调查,我们却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即在口粮得到保证的前提下,以副业为中心的传统手工业的收入,在每户的家庭收入中,其比重已越来越重要。因为,这是他们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源;而对某些畲民家庭来说,也许就是唯一的重要资源。因为在粮食自耕自食的情况下,现金收入是使村民的生活“商品化”和“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因此这些能挣回现金的传统行业已经越来越受到畲民的重视。
八井村的企业情况如下:
1.八井水厂。1996年,罗源县水利局和自来水公司投资,在八井的碗窑里建造水厂,供县城城区用水。与八井村的直接联系只是购买村民的土地,每亩是6000元。但是间接的好处是为八井村的公路改善带来了福音。当然,像2003年夏天的这种罕见的干旱,八井的村民就感觉到缺水的困难了,村民说,没有水厂时,这种情形是没有的。因为它截断了八井村的水源,并对小获溪有一定的污染。
2.养鳗场。1994年由外地私人投资开办的,租用村民的土地,每亩每年给1000斤谷子。养鳗场前几年效益很好,因此后来有个别村民也入股,但却没有一个村民在里面当工人。尽管如此,养鳗场也为村里的发展作了一些贡献,比如村里电话线的安装,交通的改善等。
3.八井水电站。八井水电站是由罗源县开发区1996年投资开办的,所发的电供给开发区使用。开发区购买八井村民的土地,每亩6000元。但留下一个问题,卖了的土地依然在村里应交纳公粮的总面积之内,因此,原土地的主人虽然拿走了钱,但每年还得向国家交纳公粮。这样,该村民以及他的后代就面临无期限的给国家交公粮的问题。
自从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以后,八井村的集体经济已基本不复存在了。在八井村,村里的财政收入每年经常只有几千元,因此,农村经济总收入几乎百分之百是由农民家庭的个体经营收入构成的,如2002年农村经济总收入为288万元,而农民家庭经营的收入也是288万元。这就清楚地表明,八井村现今并没有集体性的经济与经济收入,主要收入是村民家庭的个体经济。从表3-5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农业种植业的收入只有112万元,只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38.7%。由此看来,八井畲民的家庭经营收入大都转向了副业或第三产业。而根据下面的表格,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各行业收入的“商品化”程度,这样也许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几年来八井畲村的第二、第三产业为什么会有迅速发展的原因。
从上表也可看出,种植业出售产品收入仅占种植业收入的21.43%,林业出售产品的收入占林业收入的89.47%,牧业出售产品的收入占牧业收入的92.31%,而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饮业的产品出售收入都占其收入的100%,由此看来除了种植业外,其他行业的商品化程度都比较高,其获得现金的可能性都比种植业强。因此,随着产品商品化以及市场意识的加强和发展,以农业为中心的种植业已经发展到了停滞阶段,在农产品无法自己进行深加工的情况下,其他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商饮、运输、服务业等就飞速发展起来,逐步成为农民现金收入,特别是家庭现金收入的重要来源。
现在八井村的畲民在不放弃种田,保证满足自家口粮需要的基础上,纷纷在农闲时投入种植业外的行业。掌握畲族传统技艺与手艺的人,就有挣钱的优势。除了上述提及的木匠、泥水匠之外,八井村有的畲民具备有畲族传统的医药、医疗技术,而且在罗源、连江甚至福州市都有些名气,他们农闲时纷纷外出行医,或者病人慕名找上门来看病。据我们入户调查,全村以各种形式行医的人员有十几人,据他们说,有的人行医的年收入可达万元以上,甚至更高。这种行医收入都占据他们家庭可支配收入的绝大部分。新任村主任雷桃俤在罗源连江一带是小有名气的畲医,据他自己说,他家2002年的总收入为15000元,除去收获稻谷20担值1000元,水果收入1000元(龙眼收入200元,橄榄收入800元)外,剩下的13000元都是他家行医的收入。而据他人估计,由于雷桃俤和他祖母都是有些名气的畲医,因此他们行医的收入应不止这些,而应该达两万元以上。另外,村中的法师(道士)也可以以自己的一技之长,维持一家的生计,收入与行医不相上下。雷某某家4口人,主要靠他从事法师维持生活,据他自己估计,2002年的总收入大约是1~1.2万元。
没有传统技艺的人,就设法从事商饮业或其他行业来增加现金收入。在500多人的八井村中,现已开有8家食杂店,他们分布在村中主干道路两侧的各处,尽管竞争激烈,但也都能维持。据他们讲,一间店铺每天的营业额大概是从20~30元至200~300元不等。他们各有自己不同的进货渠道,各有自己相对固定的消费群体,村民们常聚集在不同的小店周围聊天和看电视,形成一个个不同的舆论中心和青年娱乐中心。食杂店中经营的种类很多,品种良莠不齐。有的小店的店主除了经营杂货的买卖外,也经营蔬菜、水果、肉禽、蛋,甚至早点的运输贩卖,以供应全村人甚至邻村竹里、横埭人的食用,即方便了村民的生活,也为自己挣得些许利益。村民雷知国在八井畲族小学门口开了一间杂货店,经营的商品除吃的外,还经营些文具之类;此外,每天清晨四点,他还要骑着摩托车到县城的蔬菜批发市场购一些肉、鱼、菜甚至油条等早点,然后回到村里,在村委会门口的大榕树旁贩卖,如卖不完,他还要骑着摩托车到八井老村那里叫卖或到横埭、竹里去叫卖。而据他说,他这样没日没夜地干,2002年的总收入才约1.3~1.5万元。
有的村民则从事畜牧业养殖,养殖的牲畜主要是羊、兔以及少量耕牛。据我们入户调查,村民养殖的羊主要是肉用山羊,销售对象主要是县城的居民。1头羊全年的净收入大约是1000元左右。一般每个养殖户养50头左右,全村共有10户左右的山羊养殖户。八井村虽有人养耕牛,但却养得很少,全村只有3户人家养了4头耕牛,其中1头还是小牛。农忙时,他们把耕牛租给村民们耕种,也可以连人带牛代人犁耙田,后者每犁耙好1亩田地可收入35~45元左右,价格因田地有别而有差异。此外,八井畲村也有4~5户人家养殖蜜蜂,如雷进玉就是一位养蜂的专业户,他养了70箱蜜蜂。据他说收成好时,这70箱蜜蜂1年可以收入1万多元,而收成不好时大约是7000元,平均的年收入多在七八千元左右。
在罗源县大力发展石材加工业的刺激下,近年来八井村的运输业发展得较快。2003年,从事运输业的家庭有4家,经改装可载重7~8吨的四轮的拖拉机有5部,主要都是到附近的石材加工厂和到采石场工地上拉石头。如雷知禄、雷贤寿父子都以此为生。由于竞争激烈,收入起伏不稳定,每户人家拉石头的净收入,大约每天从60~70元到200~300元不等。但由于需贷款买拖拉机、改装和驾驶培训,因此前期投入较大,同时也由于这一行业的竞争激烈,有的人家甚至很长时间没有净收入。根据我们入户调查的数据估算,每个从事运输业家庭的年收入一般都在2~3万元之间。
在包产到户时,八井村还有大量山地,可由村民自由承包种植。在八井村,有很多家庭都有10亩左右的林地,承包早的,其山上种植的树木已成材,承包晚的,其所种植的林木还小,此外,还要受到《林业法》的约束,无法随意售卖,难以变现,因此除少量种植的橄榄、枇杷、龙眼、蜜柚等果树有收益外,林业这方面的收入比较少。近几年来,在种植业方面也有变化,有的人也轮种西瓜和其他经济作物,希冀通过此增加现金收入,但由于市场饱和,价格一直走低,以及遇到气候、技术等原因,所以经营此的村民收入并不高,其种植的积极性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还有一些剩余劳力则采取外出打工的方式来挣取现金。根据2002年福建省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表的数字看,2002年八井畲村的劳动力有221人,其中外出劳动力178人,而常年在外打工的劳动力为50人,分别占劳力总数的80.54%和22.62%。2002年,八井畲民外出的劳务收入为24万元,而2002年八井的农村经济总收入是288万元,可分配净收入为178.4万元,外出劳务收入所占的比例分别为8.4%和13.5%。由此可见,外出劳工对八井畲村的收入与消费所起的作用都将逐年增大与加强。
第四节 消费特点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八井村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全村盖了30多座新房,许多人家从半山腰搬到了平地,其中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屋有十几座,结束了住草木房的历史,家用电器和高档家具也开始进入八井畲民家中,根据50户畲民的入户调查,在这50户人家中,共有彩色电视机18台,电冰箱3台,洗衣机2台,影碟机6台,电话28部,摩托车8台,手提电话25台,拖拉机5台,碾米机1台。固定资产拥有量已与过去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从收入与消费的对比看,抽样调查的50户畲民家庭中,年收入支出达到平衡有24户,占48%,年收入超过支出的有10户,占20%,而年收入不敷支出的有16户,占32%。后者的主要原因有三种情况,首先有几户是前几年计划生育超生而被罚,家庭经济因此受影响。其次是有家庭成员遭遇重大疾患,医疗费用太大,无力承担。其三是家庭成员中有好几个小孩正在读书,花费很大,而自家的经济来源太少、太单一地依靠农业种植业。
从调查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年收入超过年支出的家庭中,全部是以副业或第三产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土地往往仅种单季,或将土地租给别人,收取口粮,够吃就行;其他两类家庭普遍感到收入来源太少,很多收入一时无法变成现金,致使他们不得不压缩开支,甚至借贷。后者往往还要因为高额的利息而背负更重的负担。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八井畲村近几年家庭中的生产性投入在家庭消费中所占比例并不大,尤其是经济收入较少的家庭,他们家庭消费开支中除了固定比例的吃用迎送外,绝大部分的投资是投入到下一代孩子的教育上,用于增殖性的生产投入比例很小。因此,找到增加家庭收入的方法,已成为他们最迫切也是最困难的事。在没有特殊技艺的情况下,他们选择的方法往往是,农闲时到城里打工。从入户调查的50户人家的经济收支统计可以看到,当地村民在吃、用方面的消费相对固定,家庭会依收入情况调节在40%%~60%之间,而科技、教育、文化娱乐和疾患治疗等方面的支出则变数较大,超支主要发生在这些方面。作为农村社区,八井畲村的迎送礼仪消费的比例虽然依年份而有所变化,但基本上都维持在5%~10%左右。当然,因各家的交往情况不同而有不同的支出,但每家在这方面的支出数额,近几年都维持在1000元左右。
以下为八井村几个家庭的具体情况:
个案1
雷知禄家是属于村中经济比较富裕的人家之一。雷知禄,男,2003年41岁,家庭成员5人,其中劳动力3人,女性1人,小孩1人。妻子春桃33岁,在家务农,是雷知禄再婚的妻子。大儿子雷贤寿22岁,为其前妻所生,初中文化程度,在家务农,帮助其父开拖拉机;二儿子雷贤华,15岁,正念初二。其家有水田3亩,建房换地后只剩1.5亩,另有干田0.5亩,山林5~6亩。近几年,自己种双季稻的只有0.5亩,其他的田,春季给其兄弟种西瓜,夏季自己再种水稻,收成每百斤西瓜,其兄弟给予15元作为土地的报酬。因此他们春季所种的0.5亩田只收300斤稻谷,而夏季种的3亩田共收1800斤。春季2.5亩给兄弟种西瓜可收获2500斤,他有375元租借收入。雷知禄家养了3只鸡,8只鸭,没养猪。家中有黑白和彩电各1台,录音机、影碟机各1台,固定电话1部,手机2部,家中没有从事其他手工制品生产。雷知禄原是村里二队的拖拉机手,16岁开始驾驶拖拉机,已有25年驾龄。自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级经济解体,他就不再为村里开拖拉机。1995年开始自己开拖拉机,2001年购买了第一部手扶拖拉机,2003年又购买了一部,每部价格约在16000元左右,基本上都是用自己的积蓄所购。儿子雷贤寿16岁开始开三轮摩托,2003年雷知禄为他购买了一部新的拖拉机让他驾驶。拖拉机既可载石头也可拉砖头。过去他们经常到西兰乡去拉石头或砖头,罗源经济开发区成立后,他们就在开发区里载石头或砖头搞基建,生意并不稳定。据他们介绍,开拖拉机的成本大约有以下几项:养路费每月150元;油费平均每天需5~6元(每公升1.75元);损耗最多的是轮胎,每只轮胎需300元,1~2周就需更换一个。据他们说,最多时一天可赚280~300元,少时则20~30元或60~70元都有可能,而且也不是每天都有活干。2002年全家开拖拉机共赚纯收入25000元,外加租地给人家种西瓜的报酬有375元,年纯收入为25375元,人均纯收入约5075元,所种的稻谷均作为口粮。
雷知禄家的总支出为:每月用于购买肉、菜等食物用350元;香烟150元/月,电费30元/月,水费75元/年,液化煤气350元/年,电话费350元/年,移动话费100元/月,日用品约700元/年,学费及教育费用中学1350元/年,小学300元/年,用于迎送礼仪的费用为2800元/年,其他支出1000元/年左右,总支出共计14485元/年,人均支出2897元/年。
个案2
雷炳金,男,1962年出生,2003年41岁,小学文化程度。家庭成员6人,其中劳动力3人,男劳动力2人。妻子雷智钗,1968年出生,35岁;母亲雷莲香,1933年出生,70岁;长子雷建华1987年出生,16岁,小学毕业,现在城关作厨师;女儿雷建英1989年出生,14岁,初中学生;次子雷贤武1994年出生,9岁,小学二年级学生。雷炳金有水田2.8亩,干田0.5亩,旱地0.2亩,山林8亩,自留菜地0.4亩;家中饲养有6只鸡,3只鸭,没养猪。家中有彩电和影碟机各1台,电话1部。雷炳金除了种稻谷外,还种有橄榄树130余棵(至今还未有收入),柿子树8棵,枇杷树7棵,芭蕉树6棵(尚未有收入),龙眼树6棵(尚未结果);其次,他在干田、旱地和自留菜地里种有芋头500株,地瓜3亩,春季轮种西瓜3亩。农闲时也外出务工,务工的地点有时在城关,有时在八井附近的水厂。据雷炳金说:2002年其家庭总收入的情况大体为:稻谷自给,西瓜纯收入2000元左右、芋头1500元、地瓜2700元,自己外出务工约挣2000元,大儿子雷建华在福州的工厂中做“元宝”(金纸)所得的收入1000元,共计9200元,人均纯收入约为1533元。
他们家的总支出为,食物方面:菜金每年支出3600元左右;日用方面:液化煤气费300元/年,水费50元/年,电费350元/年,日用品300元/年,电话费80元/年;教育费用:中学1300元/年,小学350元/年,孩子零花钱1000元/年;迎送礼仪费用:约1500元/年。另外,因为超生曾被罚款30000元,当时借高利贷还了9000元,现每年还需要还高利贷的本息,但具体数目不详。所以他家可知的总支出共计8830元/年,人均1470元/年。其收支情况在本村属于中等偏下,因为超生被罚款,因而对此颇多怨言。
个案3
雷信春,男,40岁,小学文化程度。家庭成员5人,其中劳动力4个;妻子雷月梅,39岁,小学毕业,在家务农;大女儿灼英,20岁,初中文化,在家务农;二女儿卓燕,17岁,初中文化,在罗源城关一家超市里务工;三女儿雷灼银,15岁,小学四年级学生。雷信春拥有水田2.5亩,干田0.8亩,山林30亩(用于种松树,尚未带来收入),鸡2只。家中有彩色电视机、电冰箱、影碟机各1台,电话1部,自行车1辆,缝纫机1架(雷信春10年前是当地的裁缝之一,会裁制“凤凰装”,当时每套凤凰装的价格在100元左右,现已放弃)。雷信春2002年家庭总收入基本来自其做油漆工的收入,共计8000元左右,人均1600元。
其家庭的总支出如下:粮食自给,其他菜金3000元/年;日用方面为:煤气费100元/年,电费120元/年,水费20元/年,零用1200元/年,科技教育投入(小学费用)400元/年,迎送礼仪费用约600元/年,化肥800元/年,文化娱乐20元/年,共计总支出6260元,人均1252元。其收支情况在本村属于中等偏下。
个案4
雷信伙,男,43岁,小学文化程度。家庭人口6人,其中劳动力4人。其妻雷翠英,40岁,小学文化;大女儿雷桃金,19岁,现在中南民族大学外语系就读。大儿子雷可法,17岁,初中毕业,在罗源城关务工;小儿子雷可财,15岁,小学毕业,在福州务工;母亲雷喜珠,77岁。家有水田4亩,干田1.6亩,家中没有任何耐用消费品,只有一张犁和一张耙。春季没有种地,家人多外出务工,因此也不饲养任何家禽家畜。家庭总收入基本来自外出务工所得。雷信伙本人到罗源打杂工,每天收入20~30元左右;2002年差不多有4个月时间在外打杂工,收入有2500元左右。妻子雷翠英在罗源当保姆,年收入在1500元左右。两个儿子在外务工仅能自保。因此,其家庭的纯收入在4000元左右,人均收入667元。他家的总支出为:粮食自给,菜金2000元/年,日用方面约2000元/年左右,支付大女儿生活费200元/月,迎送礼仪费用2500元,共计总支出8900元,人均支出1483元。此外,他家的总支出中,还没有包括历年所借1万多元高利贷的本息。他们家庭的收支严重入不敷出,家庭经济情况在本村中是属于很差的。
第五节 经济发展趋势
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几十年发展,八井村的农村总体经济水平、人民消费水平都有巨大发展与飞跃,他们已基本摆脱了贫困,正逐步利用相对完善的农村基础设施,寻求更加富裕的生活。八井村产业结构在20世纪90年代已发生了一些变化,二、三产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村民的市场和商品化意识有了很大的加强,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八井村与周围其他村庄相比显得贫弱些。
首先的主要问题是经济结构还比较单一,产业结构调整仍未到位,二、三产业的发展缺乏引导与市场支持。八井村仍以种植业为主,本村并没有企业,仅有的一家养鳗场也是外地人来办的。他们仅向本村人租用田地,付租金而已,也没给八井村提供什么工作机会,难以对本村的经济形成效益和帮助,却占用了农村耕地用水。本村有少数经济能人,虽然到外地参股办养鳗场、虾池,但这只是对其家庭有利,而对八井畲村整体的经济发展起不了什么帮助作用。
其次是多年来八井畲村的集体经济十分脆弱,村财政几乎没有收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八井村经济的基础历来就很脆弱,结构比较单一,又没有村办企业,收入渠道极其狭窄,除了农村特产税返还和“三提五统”外,根本没有其他收入渠道,村财政收入的稀少,反过来又影响了村集体经济的核心作用与引导作用。八井畲村的集体事业、公益事业的发展,基本都是依靠上级扶贫办、老区办,特别是各级民委的支持,才有了相对完善的农村基础设施和居民社区环境。八井畲村并非没有相对出色的经济能人,但破碎的集体经济,难以使个体的力量形成“合力”,为共同的“社区经济”服务。近几年来,八井村的资金和劳动力的外流已开始慢慢显现,而这些对八井村来说都是稀缺的资源,也是村落社区进一步走向全面富裕和发展的基础。
再次是村民人均纯收入仍然偏低,特别是可支配性的消费收入偏低,影响了农村生产性投入的比例,更影响了二、三产业的发展。文教卫生事业的落后,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村民文化科技的相对缺乏,使他们难以找到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的办法。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经济收入相对较高的村民,其所受的教育程度往往也较高,而且会说普通话,善于与外人沟通。教育水平低使得村民们往往不愿投入太多的资金给下一代做“智力投资”,而越是如此,教育水平就越难提高,如此恶性循环势必使教育成为八井村经济发展的瓶颈。近几年来,由于医药费上涨过快,村民因无力支付医药费而“小病磨,大病拖”,一些农户因病背上沉重的债务,陷入贫困而无力自拔。八井村因病致贫、返贫的农户,据村民们自己估计约占贫困户的40%左右。
八井村的经济在逐步加快前进的同时出现的这些问题,反映了其经济发展趋势中逆向的可变因素,保存和发展、完善村落社区经济要素,引进合适的经济增长要素,可能才是最大限度地为本社区经济服务的关键。
第一节 生产关系的变化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生产关系
(一)生产资料占有情况
根据我们在八井村收集到的清代土地买卖文书看,在乾隆年间,八井村福房的雷君恒(又名雷洪溪)是一位受到罗源县政府旌奖的“耆宾”(地方豪绅),①他从县城和附近汉族手中买进了许多土地,并建了两座占地面积很大、雕琢精细的“八扇房”瓦寮。至清代末年和民国初年,原还拥有不少土地的畲民如雷坤照等开始没落,不断把自己的土地典当和卖出。到新中国建立前夕,八井村的畲民几乎都成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土地几乎都集中在汉族地主手中,畲民的土地多是从汉族地主那里租佃来的,得付出高额的实物地租。畲民族中虽有1户地主,但他仅占地5亩多,系高利贷地主。畲族农民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少又因租谷、借贷无法清还,年复一年,利上加利,只得把土地先典当给地主,随后又可能因无钱还债而把土地的田根断卖给地主,而使自己所拥有的本来就很少的土地流入地主手中。地主土地日渐增多,而农民一天天失去了土地。
根据土地改革时所评的成分,也可以看出当时八井村生产资料占有的情况。在当时八井行政村的189户中,贫农有104户,雇农23户,中农58户,富农2户,半地主1户,地主1户,贫雇农占了一半以上。①由于八井行政村的土地册丧失了一部分,无法全部统计,仅根据该行政村中163户人家的占地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163户中,贫雇农有106户,中农为53户,富农2户,半地主1户,地主1户。他们所拥有的全部自耕田为185.53亩,农地62.07亩,共计247.6亩。租入的土地有:田1053.33亩,农地20.1亩,共计1073.43亩。自耕的与租入的田地共有1321.03亩,其中租入的田地占了81%。这清楚地表明,土地都集中在地主手中。
如果以每户占地的情况来看,也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畲族农民都是无地或少地的,其情况详见表3-1:
在这163户畲族家中,只有1户“半地主”占有田地10亩多,是八井畲村中占地最多的1户。其次,八井村有户人家被划为地主成分,但其占田很少,其主要是靠与城关的地主合作放高利贷剥削畲民,因此当时的土地都集中在汉族地主手中。
(二)租佃关系与借贷
从上面的生产资料占有情况来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八井村的畲民多数是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绝大部分都向汉族地主租佃土地耕种。所付的地租,一般都采用固定的实物地租。由于土质有好坏,地租也有不同,但多寡都由地主确定。地主可以任意抬高租价,甚至坏田也要当好田出租。畲族农民因为无地,为了生活,也只得接受高额的地租。一般每亩地租是300斤、250斤、200斤不等。在新中国建立前,畲民习惯的计算法都是以湿谷计算,合干谷8成。以村长雷兴连为例,他租种2亩田,每年要付给地主地租550斤,牛租谷子30斤,而这2亩田半年可收850斤,地租就占总收获量的32.6%,牛租、种子、肥料还不包括在内。这是丰年的情况,如果遇到歉收或病虫害,地租也是1斤不减,畲民往往把全年的收成用于纳租还不够。如租到坏的田地,畲民就要赔得更多,如村长雷林曾向地主租了1亩坏田,1年的全部收成还不到1担,却要交租2担。若当年的地租无法交清,地主就把这些租谷直接转成高利贷,每季以利息50%计算;或强迫畲民到其他高利贷者处借高利贷来还地租。
(三)借贷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八井村民普遍都很贫困,经常需要靠借贷来维持低下标准的生活,因此在村里存在各种借贷形式多,其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1.借谷:如果正月借谷100斤,六月早稻收成时,就需还谷150斤,利息为50%;如果一季无法还清,下一季的利息为本利的50%,因此到年底就要还225斤,年利率为125%。如1年无法还清,同样再以本利按每季度50%计算,年复一年滚下去,农民就得卖掉自己的土地来还债。
2.借钱:在八井地区,早期的借款一般是年利50%或30%,以年利50%较为普遍。但在新中国建立前的几年内,利息特别高。借款不是以年息计算,而是用月利计算,一般的月利为30%,而且还要利上加利。例如正月借10元,二月就需还13元,三月再以13元加上利息的30%,就需还16.9元,以此类推,等等。
3.青苗钱:青苗钱又称谷贷,它以钱贷出,收入以谷。这是地主、高利贷者利用人们在青黄不接急需用钱之机,乘人之危抛出的一种高利贷形式。如本地地主雷世琪与罗源县城李大玉相互勾结,常利用这种形式剥削畲民。例如当时一担谷价9.6元,李大玉贷给雷世琪每担7元,其中每担赚了2.6元,而雷世琪再以每担3.5元贷给农民,利息为100%。一般贷出时间是4月或7月青黄不接时,而在6月或10月收成后就要马上清还,前后只有4个月时间。这种剥削最为残酷,地主牟利最大。①
4.实物代役租:即向地主借谷子来吃,而在农忙时到地主家里做短工,以所得的工资还给地主的借贷形式。
5.货币贷役金:就是向地主借钱来使用,然后同样在农忙时到地主家里给地主做工,以所得的工资还地主的借贷形式。
后两种形式虽然看起来没计算利息,但地主、富农放出这些钱时,必须事先选好对象,一般是选择劳动力强,技术样样全的人为对象。地主们的剥削,主要是在工作中给他们增加劳动强度,一般他们都要比平常的工作多付出1/3的时间,同时,地主、富农只付给低廉的工资,因此其剥削量并不亚于以上几种。
农民借贷都是向地主、富农和奸商告贷。地主、富农放贷时也不是盲目的,要视债户家里是否有财产,如果债户家无立锥之地,即使愿意出高额利息也难以借到,如雷明节因为家贫如洗,地主就不肯借给他。
(四)雇佣关系
在1949年以前,由于畲族农民家庭普遍贫困,所以许多人家不得不出卖劳力。而在当时,因本民族的地主、富农少,他们占有的土地也少,因此八井畲民一般都是受雇于汉族地主。据统计,在新中国建立以前的几年中,八井畲村的畲民,被人雇为长工、短工和零杂工的有33人。
1.短工:一般被雇佣为短工的,是因他与地主有借贷关系。地主是利用债务和他家庭困穷,不得不出卖劳力,然后直接到他家来雇,或通过其他人的接洽。由于债户家穷困非接受雇用不可,所以地主把工资压得很低,根据雷明节1949年临解放几个月的情况看,他每个月工资仅30斤谷子,折算为1.8元,即每天1斤谷子。以他的劳动量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和他所得的低微工资相比,这种剥削是很重的。
2.长工:如雷任传在1928年~1934年前后7年时间,被外乡汉族地主雇为长工,工资最初是每年300斤谷子,后来提到了600斤。他除了生病外,每天都得朝出暮归,除了耕种田地外,还得帮地主家做些砍柴等杂务。他每年要耕作八九亩田,可收入谷子40担。与之工资相比较,这种剥削是极其残酷的。①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生产关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从此八井村畲族的生产活动就与党中央与国家的政策息息相关。首先是减租减息,这使畲民受地主阶级的剥削程度大大减轻。其次是1950年6月县里开始,10月八井村开始的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富农的多余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贫、雇农以及中农,使得耕者有其田。如根据1952年2月罗源县政府颁发给八井村村民雷益母的“福建省罗源县土地房产所有证”(罗字第02163号)的情况看,雷益母在土改后分到了3.3亩田地和1间占地约0.34亩的房屋,其中水田2.9亩,农地0.4亩,其分布的情况为“七斗洋一丘,0.7亩,东至雷信开田,南至己田,西至雷川美田,北至雷信仁田。”“南山洋一丘,1.4亩,东至蓝顺意田,南至溪,西至雷志兴田,北至雷兴桂田。”“溪骨一丘,0.5亩,东至雷炉佐田,南至路,西至雷炉佐田,北至溪。”“扶楼边一丘,0.3亩,东至路,南至雷典蛋田,西至雷信仁田,北至路。”农地为“溪坂一丘,0.4亩,东至雷为顺田,南至荒冢,西至路,北至雷金和园。”当时还规定“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保护农民已得土地所有权’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之规定”,确定雷益母所得这3.64亩田地、房产为其“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与、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①这一均贫富,使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八井畲村畲民的劳动积极性,并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政府还针对畲民们积贫太久,在生产上遇到的困难,给予积极的救济及资金上的支持,使得畲民们的生产收入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1958年民族调查时,调查人员记录了八井村的一个个案,现照录如下:“雷章文,雇农,解放前一家五口人,自有农地一亩二分,收入茹米(即地瓜米)五百斤;租耕田一亩,年产三百斤谷子,交纳地租一百二十斤。自己买不起农具,在农忙时都向别人租用。苛捐什税每年得交18元。一年砍柴做短工,辛勤劳动,但得不到暖饱,全家只有破棉被一床,睡觉多半盖蓑衣,衣服不能蔽体,破烂不堪。解放后五口人分到八亩水田,原有一亩二分农地也保存,并分到耕牛1头,每年收入谷子三千二百斤,茹米八百斤,养毛猪收入55元。粮食收入除交公粮五百斤外,还卖余粮一千一百斤,几年来添置毛衣三件,箩二挑,谷屏一块,犁一张,耙一张,棉被一床,茶壶酒瓶,每年每人新制单衣一套、布鞋一双,1953年用了58.8元买了一头耕牛,生活改善很大。至今本人回忆解放前后生活情况,他感慨地说:‘过去(指解放前)没吃没穿,天天砍柴过活;解放后生活根本改善,感到非常满意,对党和毛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谢!’”①
1952年,新建立的八井乡中,也组织了几个常年和临时的互助组,1953年在合作社化运动过程中,12月八井乡的八井村中有18户人家首先出来建立起“建新”初级社,有的人还积极参与区的供销合作社的建立,购买供销合作社的股票,开始走合作化的道路,生产关系发生了一次变革。在这次调查中,我们有幸地发现了两张“罗源县第七区供销合作社”1953年12月26日发行的“股票”(图3-1)。这两张股票的持有者为八井村民雷木杉与雷志森父子,他们各购买了“壹万伍仟元”(相当于15元)。
1955年12月,在合作化高潮中,八井乡成立了高级社,八井、横埭、竹里等畲村的初级社和互助组及单干户,全被组织进“八井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中。1958年,在公社化的高潮中,八井高级社的所有人也报名参加人民公社。在1958年10月1日成为罗源县城关人民公社八井营。八井地区的畲民把原先的土地及生产资料全部转为集体所有,由集体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至此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建立起来。八井畲村的生产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由于“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的折腾,群众生活也出现了困难。1961年贯彻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精神,实行按劳分配后,人民的生活逐步有所好转。1961年5月,县里增设人民公社,八井大队隶属城关区小获人民公社。1962年2月调整社队规模,并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固定到队。实行粮食分配与实际投工、投肥挂钩的分配办法,社员的生产积极性逐渐提高。1966年6月,八井大队归属松山人民公社,仍管辖竹里、横埭村。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运动中,八井畲民又经历了一次折腾。
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推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公社体制发生重大变化。1984年9月,实行政社分设,取消人民公社,恢复乡镇建制,八井村的经济体制再次发生了重大的变革。1982年底全面实行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再次极大地唤醒了畲民的生产积极性,至20世纪80年代末,已基本解决了粮食口粮问题,农村经济再次发生了飞跃,生产关系中也开始了新的变化,随着承包期限的延长,生产经营的个体化与自主权已成了时代的主旋律。而在这以后的20年发展中,为了应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八井畲村的冲击,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变化,如三五户,七八户不等的联户,甚至跨越了本村的界限的联户也开始出现;民间的土地租种和“轮租”等形式也开始出现。所有这些新时期、新形势下出现的事物,它们在农村生产关系变革中的作用和地位,还有待我们更深入、细致的观察和研究。
第二节 劳动生产方式的变化
在八井畲村,过去拥有适合水稻耕种的田亩并不多,水利条件差是问题的关键。所以,旱地杂粮耕作始终与水稻耕作具有差不多同等重要的作用,所谓“地瓜丰年粮”的俗话便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但随着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对兴修水利的重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种状况得到改变。
新中国建立前八井村的农作物有:水稻、地瓜(番薯、甘薯、红薯)、小麦、黄豆、花生、油菜、苎麻等,其中以水稻面积最大,地瓜居次,除了这两种作物之外,其他并非每家每户普遍种植,数量也很少。水稻有单季,也有双季,以双季为多。早稻种子有“流山余早”、“早仔”、“软亭早”,其中以“软亭早”为主,占早稻播种数量的70%。晚稻有“黄尖”、“红谷”、“莳谷”、“术谷”等五种,尤以“黄尖”为主,占晚稻播种面积的80%以上,“红谷”、“南旱”主要种在山田中。八井畲村虽地处山腰上,但河谷平原地居多,梯田仅有1/3,双季稻一般都种在土质较好,水源充足的平原水田中,而贫瘠土质的水田一般只种单季稻。在1949年以前畲民很少种小麦,大麦更少,因为畲民喜欢种小麦而不喜欢种大麦。虽然以产量来说,大麦可以多产,但由于价格低于小麦一半,同时也很难卖,所以畲民只种少量供自己食用。
水田稻种平均每亩5斤,但有的晚稻只下4斤。地瓜每亩平均2500株,植单行。小麦每亩平均下种子3.5斤,大麦2.5斤多。根据土壤的质地,1958年土改时,八井村对土地进行了等级评定,农田可分四等,产量不一,水田以收成最好的双季稻为例:甲等每亩年产量可收成500斤,乙等420斤,丙等350斤,丁等250斤。晚稻收获量一般要比早稻多收成50%,而旱田单季稻每亩平均150斤左右。农地以地瓜米计算(每百斤干的地瓜米合400斤生地瓜),甲等亩产500斤,乙等400斤,丙等300斤,丁等200斤。
小麦最好的可收130斤左右,一般是100斤,差的只能收成80斤;大麦最好的亩产可达200斤,中等有120斤,差的100斤,这是一般情况,荒年不在此数,且由于各家庭经济情况不同,如遇家境困难,肥料缺,那收成就会减少,如果是较富裕的农户,因肥料充足,还可以多收。①
八井村民使用的生产工具有:犁、耙、山锄、田刀、耘草耙等。犁耙用于犁耙水田,但也可以犁地瓜园,山锄用于开荒及耕种山地,田刀用来割田埂草,锄头可农、田通用,耘草耙适宜在农地使用。
这些工具的构造样式与附近汉族的无异,都是汉族铁匠打制的,或从县里买来的铁农具,所以这些生产工具都是模仿汉族的,唯有锄头与其他地方的畲族有异,其刃部不是平的,而是圆锥形的,这种锄头用来翻稻头较为方便,但也与附近汉族相同。所以,从生产工具的相互仿样可以看出畲汉两族人民生产工具的交流。耕畜方面主要是牛,有黄牛和水牛两种,根据1949年统计,全村有牛40头,平均每4.5户有1头牛,它们全部用于耕田。在农业运输上,新中国建立之前这里尽是些羊肠小道,出门就需要登山越岭,加上山区道路崎岖不平,不可能应用任何交通运输工具,全部靠人用肩挑。
勤劳是八井村民的传统美德,全村男女都参加劳动,没有很严格的分工,但在过去犁耙田由男人来承担。新中国成立以后,妇女也开始学犁田和插秧,而且完全可以胜任。过去拔秧是妇女的专业,男子很少会拔秧,现男子也干拔秧的活。男子还兼搞手工业,而妇女则管家务多。老年人干些轻活、零工和指导生产等工作。由于劳力缺乏的缘故,八井村许多小孩从小就参加劳动。
在1949年以前,八井畲民每人平均要耕种2亩多田地,但因无劳动力的畲家占多数,因此形成地多劳力少的状况,而且山区的地比平原的需要更多的劳力,因而,显得八井村劳力不足,在生产上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农民自发组织帮工来解决劳力不足的困难。一般在农忙时,除了插秧外,其他事都可帮工,几家人互相换工、轮流收割、耕种。一般都是以工代工,不计男女劳力,帮一天工主人只给一餐饭,不计工资。这种季节性帮工在1949年以前是普遍存在的,也形成为一种惯例,彼此间没有剥削存在,纯是一种互助性质。在家庭劳力组织上,过去都是个体单干,所有农事由各家自行安排,没有其他生产管理上的共同组织。
据统计,在八井村1个劳动力全年的田间劳动最多能达280天,最低也有160天,劳动力强的女人可耕9亩田,最低也可耕5亩地。1949年前,雷志华给地主当雇工,他们2人共耕作地主田地20亩。其中1.5亩是地瓜田,全年可收成120担左右。如果每人每年的口粮平均以480斤计算,可供给25人吃1年。如以自耕农计算,在八井村这个地方,只要耕作1亩上等田即可维持1个人全年的食粮,但由于1949年前绝大部分土地都是向地主租佃的,需要付给地主以高额地租,因此,即使是丰年,绝大部分畲民还是不能维持最低的生活。
八井畲民在常年劳动中,已掌握了各种农作物生长过程的知识。如他们习惯用农历计算,一年24个节气一般的老农都能对答如流,播种、收割、施肥等农活,都是根据24个节气来安排的,其安排详见下表:
耕作技术方面:水田一般是二犁三耙,即在秋收后,有的田种上麦子;有的先把稻头挖起来烧后作肥料,约在十二月把田犁好晒土,明年三月临春耕时,再引水来溶田,并施1次人畜肥约20担作基肥,然后耙平;其后不久,再翻犁1次,插秧时再耙1次,然后再用“木梯”把田耙平,就可以插秧了;插秧的同时,再施1次草木灰肥,每亩用量约15担。早稻一般不用除草,但在播种时需把田埂草铲除掉。早稻插秧后15天左右,再间插晚稻。早稻一般只要65~70天就可以收割。早稻收割后,挖去稻根15天后,晚稻除草1次,施肥数量一般与早稻相同,施肥与除草同时进行,这样到了十月立冬时就可收割晚稻。
旱田都种单季稻。旱田的耕作比较粗放,一般只一犁二耙。先挖起稻根,然后翻犁晒干,下种时再引水进来,耙二次即行。旱田大部分不施肥,如果施肥,每亩约施人畜肥5~6担,并除草1次。旱田的产量比水田低,亩产才100斤。有的单季山田还施用牛骨肥1次,每亩每下1斤种子施1斤牛骨。牛骨肥的制作是把牛骨压成粉,掺和进稻草灰和人粪;其分量大约是牛骨5斤和人粪半担、稻草灰1担一起拌搅作肥。施肥后产量较高,这是畲民在长期农作摸索中作为增产的一种经验。
地瓜最早在芒种时种下,最迟不能超过夏至。种地瓜的耕作技术简单,首先进行翻犁,然后用锄头敲碎土块,搞成一畦一畦后,把地瓜苗插下去。1949年以前一畦通常只种一行。种地瓜的肥料以草木灰为主,方法是挖洞施肥,即在每株旁挖一个洞盛肥料。第一次下肥,大约每亩需草木灰20多担;约半个月后,除草1次;1个多月后,再下第二次肥,施人畜肥约20担。过去种地瓜不割藤,也不再翻土。
过去种麦子不用犁,用锄头把稻根挖出来,把地挖得一畦一畦的,上面有一层薄薄的松土,能盖埋住种子就行。1949年以前不用条播,采用的方法是挖洞点种,把种子和肥料放进洞里,盖上松土即可。种小麦每亩需肥料约32担,以草木灰居多数;而大麦则仅需15担,其肥料也是以草木灰、土粪居多。
在新中国建立前,选育种办法很简单,只要选择一丘长势比较好,没受过灾害的就选为种子。育种时,先把谷种浸在木桶里,把浮在水面的捞起来,沉下去的即作为秧苗种子。
早晚稻的行距都在33厘米左右,根据老农的经验,凡是水田土质好的秧要插得稀些,土质差的田秧则要插得密些,但相差也只是5~6厘米。因为他们认为,土质好的田,秧苗插稀些,秧可以长得茁壮;而土壤差些的田,插密些,秧苗多长些也可以多得收获。
八井村水利灌溉设施只有两条10米宽的水沟,没有池、潭建设,更没有水坝蓄水的设施,因此,水利灌溉方面,都是利用天然的山水,对水资源无力控制,有水整天流,无水则干旱。而旱地都是靠天下雨来灌溉,名为“靠天田”。
新中国建立前,农业的病虫害很厉害,而且种类又多。稻子以蜉流子最厉害,其宿于稻根,吃掉稻根茎使之枯萎。此外,还有螟虫、琉球虫等。地瓜以九节虫、金龟子最厉害,尤以九节虫更凶,把根茎咬断,使之枯萎而无收。由于当时畲民科学知识极端贫乏,认为这是天灾、气候的关系,因而通常把防止虫害的唯一办法寄托在神灵身上,拜神求佛以求防治。
1949年以后,农业生产技术不断革新,全面推广水稻新产品和连作制,耕作技术改由一犁一耙为二犁二耙甚至三犁三耙,改旧式步犁为新式深耕犁。犁分为犁辕、犁底、犁板、犁箭、犁把、犁头、犁铧、犁弓八部分,犁头、犁铧是铸铁的,其余均为木质,一般重24公斤左右。耙分为耙身、耙架、耙梁、耙齿、龙楸等五部分,耙梁是用木连成的,重18公斤左右。田刀分为田刀和田刀柄,柄木质,重2.5公斤左右。五齿耙分为耙齿和耙把两部分,柄木质,重1.8公斤左右。其余还有斗笠、谷桶、扁挑、草刀、箩筐、风车、谷砻、石臼和石杵槌、筛、磨、簸箕等。利器有大柴刀、镰刀、斧头、锯子等。这些工具与汉族无差异,都是从市场上或汉族铁匠处购买来的。
自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生产劳动的个体化和农业工具的改革,过去集体化时期使用过的插秧机、切薯机、电动打谷机、手扶拖拉机等都不用或很少使用了,但一些适应于山区和个体劳动的机械化、半机械化的小型农业生产工具仍继续使用。八井村畲族普遍使用脱粒机代替了以前的稻楻、稻梯;除病虫害则用喷雾器。现在田间管理也有改进,在普遍进行三翻三耙的同时,也进行同次数的除草;除虫主要靠掌握好虫期,用农药来治灭;水稻品种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通常都选用各个时代最好的杂交水稻品种,例如“闽优一号”、“威化二号”等;地瓜的情况也一样。水田翻耕过去为20厘米左右,现在则28厘米左右;深耕后便于密植,1亩田可以增播秧苗2万株以上,如肥足和管理得当,密植能增产。种子的使用量与收获量因土质的不同而有差别。大致是水稻、地瓜1∶21;小麦1∶17;大麦1∶19;京豆1∶13;田豆1∶10;黄豆1∶9;马铃薯1∶19;芋头1∶12;玉米1∶6;高粱1∶7;豌豆1∶8;四季豆1∶16。不适宜种双季的水田逐步改回种单季;在适宜种双季的田地中,多实行两熟制(稻—稻,稻—菜,经济作物如西瓜—稻等)或三熟制(稻—稻—蔬菜等)。蔬菜种植一般不外售,自己食用。蔬菜主要有萝卜、南瓜、茄子、冬瓜、菠菜、扁豆、老虎豆、辣椒、白菜、芥菜、葱、蒜、韭菜、芋头、胡瓜、空心菜等。但近几年也种一些批量卖于市场。此外,近年来还有人把闲置的旱田与山地用来种植龙眼、橄榄、柿子、柑橘、柚子等果树,生产水果供应市场。
现在八井村已很少使用如牛骨粉、兽骨粉、草木灰、垃圾灰、山灰、沟土、沃土烧熏、人粪肥、禽畜粪肥、饼肥等农家肥和天然肥,普遍是到市场上购买硫酸铵、钾镁肥、尿素、碳铵、氯化钾、复合肥等化肥。除虫一般常用的农药有甲铵磷、乐果、敌百虫、敌敌畏、稻瘟净等。化学肥料与农药的大量使用,造成土质弱退,瘦瘠情况逐年深化;化学农药的喷洒,也污染了空气,致使天然的灭虫、除虫的能手青蛙、蛤蟆、田蛙、水蛇等大量消失。干粉农药的喷洒,随风吹散四方,也殃及山林中的黄鹂、啄木鸟、夜鹰子等,造成了其负面的环境问题。
第三节 经济结构的变迁及各行业发展状况
1978年党中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八井村推行了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体制得到改革,生产结构发生了变化,初步实现了农村经济由纯粹的粮食增长型向综合发展型转化,改变了千百年来的种养品种单一的状况,在粮食生产稳步发展的情况下,水果、畜牧业养殖等生产有了飞速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初步改变了落后状况。这一变化的总体情况可用下面表格反映出来:
另外,我们可以根据1995年和2002年福建省农村经济基本情况的统计表,对八井村的各行业进行对比,以考察当前八井村各行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从上表可以看到,随着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各行业都有明显的进步与发展,但林业因环境保护的影响,其收入减少。农业经济收入特别是种植业收入的增长速度缓慢,其中谷物收入没有增加反而大幅减少。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受粮食价格下降的影响外,农产品的深加工无疑是促使农业收入以其他形式得以实现的因素。由上表还可以看到,除了牧业等传统副业继续成倍的增长外,1995年以来的这七八年中,第二、三产业有了迅猛的发展,建筑业的收入增长了5倍,运输业收入增长2倍,工业收入增长了4倍,商饮业收入增长13倍,服务业收入增长了7倍,很显然,这些行业已逐渐成为八井村畲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综合上表的情况还可以看到,八井畲村的经济结构,经由近2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变化,已从原来的单一粮食种植结构,逐渐趋向于多元结构,畲民的市场愿望和市场意识得到了加强。根据2002年福建省农村经济基本情况统计表可以看到,2002年八井畲村总劳动力221人中,外出打工的劳动力有85人,占总劳力的38.5%;其中常年在外打工的达到了50人,占总劳力的22.6%,这些也是影响八井畲村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除了表格反映出的几大经济类型外,八井畲村的手工业和一些传统经济行业的变迁也值得我们关注,特别是畲医和土木建筑、裁缝等传统行业在商品经济的驱动下,有了新的发展。
新中国建立前,八井畲民从事很多行业的手工业生产,如有缝衣、制竹器、细木、土木、理发、制棺、做桶等,但是从业的人数并不多,仍紧紧与农业结合在一起,虽然也有一部分人开始脱离了农业生产,专门从事于某种手工业劳作,但人数却很少。
裁缝:新中国建立前,全村裁缝的从业人员有9人,其中3人是专业的。要想成为一名裁缝师傅,一般需要经过3年的学徒学习,而后才能独立工作。在学徒期间,其所做的一切收入归师傅所有。过去做衣裤都用手工缝纫,专门制作畲女的绣花民族服装、围裙和男人的汉装,每件衣服平均需要工作4天,每年平均可以做90天,每天5角,年平均最少收入为45元,折谷子7担。有的出工较多,则可以收入9担左右。有的1年最多可以做260天,全家的生活全靠裁缝的手工来维持。
做土木:1949年以前,全村从事做土木业的人员有9个,每年平均可做半年时间,主要是兴修四扇房、六扇房之类的传统木结构房子,每天的工资约18斤谷子,每年收入可达20多担,而技术差些的工匠每天也有12斤谷子的收入。
制竹器:1949年以前,全村制竹器的从业人员有7人。他们当学徒的时间也是3年,在学徒期间,学徒的一切收入为师傅所有。他们平均每年有半年工作时间,编制箩、筐、土箕、簸箕、谷筛、米筛、谷笪、竹匾(俗称“薯屏”)、篮子、盖篮、果盘、竹枕头、竹凳、竹椅、竹刷,甚至竹榻等。在农忙时,通常由雇主来此雇请,而在农闲时节,则自己外出接受雇工。如雷世兴在1949年前就到连江等地去干制作竹器的工作。制竹器每工的工资为谷子10斤,每年平均有15担谷子的收入。
做棺木:1949年以前,八井村做棺木的从业人员有2个。他们都是到城里跟长乐人学习的,需当3年的学徒,工资以件计算,每年平均可做85天,每个棺木工资1.2元,相当于谷子20斤。由于八井畲村的情况是有钱人才有可能事先做棺木而备用,而一般穷人,都是在人死后才到城里买几块木板雇人加工。这些做棺木者的工作就是专门做加工的。
理发:1949年以前,八井有2个剃头师傅,最初都是向小获的汉人学习的,需当3年的学徒,农忙时返家生产,3年期满,师傅发给1套理发工具,自己去为人理发挣钱。在新中国建立之前,理发都是包全年的,16岁以上者,每人每年6斤谷子,16岁以下者则供给一顿饭而不必付工资。例如村民雷兴连在1940年理发收入了800斤谷子,而他同年所种的地,除了纳租外只剩下400斤。全家人粮食不够,主要都是靠理发所得来的谷子补贴,其占总收入的66%。
造桶:1949年以前的从业人员有2个,他们专门制作木桶,平均每人每年有80元的收入。
由此看来,八井的手工业从业者虽不多,但其收入,占家庭经济总收入的比重却很大。另外,当时的手工业具有下面几个特点:
1.手工业大多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八井村的手工业者几乎都是半工半农的。
2.普遍存在师徒间的剥削关系,学徒期一般要3年或4年,在这期间,学徒的收入归师傅所有。
3.同行业者彼此间并没有任何组织和规章制度。
4.他们所做的工作都是单纯的手工加工性质,因为原料都是雇主提供的。
5.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流动性很大,膳食一般由雇主供应。①
1949年之后,在“以粮为纲”的几十年中,传统手工行业并没有什么新的发展,但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近几年中,村民普遍感到粮食已不成为其家庭经济的主要收入来源后,“粮食不值钱”,“我们不愁粮食但我们却缺钱花”。虽然有的手工业行业已消失,如制棺木和理发、缝衣等,但有些行业在现代仍有用武之地,因此,那些有手艺的畲民们纷纷利用现在仍有用的传统行业,变通后以适应当前的商品化社会。如由于现在建房已用钢筋混凝土、砖石等材料,传统从事木构房屋建筑的大木工匠只好改行,做起细木来。村民雷有金在1949年后是村里有名的大木师傅,20世纪90年代以前,八井畲村所建的传统式样的木构或土木结构的四扇房、六扇房或假八扇房,大部分都是经由他手设计建造的。此外他也设计建造了小获村的观音庙。现在木工们都使用上了电动的木工工具,如手机刨、电钻、切割机、刨床等,他也只能在家里做一些锅盖、饭甑之类的日常木制用品,拿到罗源市场上卖,没有再参与房屋的建筑。不过即便这样,因他有手艺,其家庭的收入也比单纯靠田地收入的人家要好许多。另一方面,由于时代变了,具体的生活内容也变了,有的人适应了这种变化,而去外面学习做石匠和泥水匠的本领,成了村里建筑现代民居的主力,并以此来养家糊口。村民蓝水盛1975年17岁时就外出跟着莆田人金弟学习打石头和建砖石、钢筋混凝土材料的建筑。至2003年已从业28年,他多数在福州、罗源一带做建筑包工头,有时也在村里帮人建房,其收入在村里算是比较好的一位,他一次性地把自己的两层楼的住宅建好。而他哥哥蓝水银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虽也在近年建了新房,但他只能先建一层,待以后存下更多的收入后,再续建第二层。
在相关统计报表中,数字所显现出来的副业在八井畲村经济中的影响似乎很小。但根据入户调查,我们却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即在口粮得到保证的前提下,以副业为中心的传统手工业的收入,在每户的家庭收入中,其比重已越来越重要。因为,这是他们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源;而对某些畲民家庭来说,也许就是唯一的重要资源。因为在粮食自耕自食的情况下,现金收入是使村民的生活“商品化”和“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因此这些能挣回现金的传统行业已经越来越受到畲民的重视。
八井村的企业情况如下:
1.八井水厂。1996年,罗源县水利局和自来水公司投资,在八井的碗窑里建造水厂,供县城城区用水。与八井村的直接联系只是购买村民的土地,每亩是6000元。但是间接的好处是为八井村的公路改善带来了福音。当然,像2003年夏天的这种罕见的干旱,八井的村民就感觉到缺水的困难了,村民说,没有水厂时,这种情形是没有的。因为它截断了八井村的水源,并对小获溪有一定的污染。
2.养鳗场。1994年由外地私人投资开办的,租用村民的土地,每亩每年给1000斤谷子。养鳗场前几年效益很好,因此后来有个别村民也入股,但却没有一个村民在里面当工人。尽管如此,养鳗场也为村里的发展作了一些贡献,比如村里电话线的安装,交通的改善等。
3.八井水电站。八井水电站是由罗源县开发区1996年投资开办的,所发的电供给开发区使用。开发区购买八井村民的土地,每亩6000元。但留下一个问题,卖了的土地依然在村里应交纳公粮的总面积之内,因此,原土地的主人虽然拿走了钱,但每年还得向国家交纳公粮。这样,该村民以及他的后代就面临无期限的给国家交公粮的问题。
自从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以后,八井村的集体经济已基本不复存在了。在八井村,村里的财政收入每年经常只有几千元,因此,农村经济总收入几乎百分之百是由农民家庭的个体经营收入构成的,如2002年农村经济总收入为288万元,而农民家庭经营的收入也是288万元。这就清楚地表明,八井村现今并没有集体性的经济与经济收入,主要收入是村民家庭的个体经济。从表3-5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农业种植业的收入只有112万元,只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38.7%。由此看来,八井畲民的家庭经营收入大都转向了副业或第三产业。而根据下面的表格,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各行业收入的“商品化”程度,这样也许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几年来八井畲村的第二、第三产业为什么会有迅速发展的原因。
从上表也可看出,种植业出售产品收入仅占种植业收入的21.43%,林业出售产品的收入占林业收入的89.47%,牧业出售产品的收入占牧业收入的92.31%,而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饮业的产品出售收入都占其收入的100%,由此看来除了种植业外,其他行业的商品化程度都比较高,其获得现金的可能性都比种植业强。因此,随着产品商品化以及市场意识的加强和发展,以农业为中心的种植业已经发展到了停滞阶段,在农产品无法自己进行深加工的情况下,其他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商饮、运输、服务业等就飞速发展起来,逐步成为农民现金收入,特别是家庭现金收入的重要来源。
现在八井村的畲民在不放弃种田,保证满足自家口粮需要的基础上,纷纷在农闲时投入种植业外的行业。掌握畲族传统技艺与手艺的人,就有挣钱的优势。除了上述提及的木匠、泥水匠之外,八井村有的畲民具备有畲族传统的医药、医疗技术,而且在罗源、连江甚至福州市都有些名气,他们农闲时纷纷外出行医,或者病人慕名找上门来看病。据我们入户调查,全村以各种形式行医的人员有十几人,据他们说,有的人行医的年收入可达万元以上,甚至更高。这种行医收入都占据他们家庭可支配收入的绝大部分。新任村主任雷桃俤在罗源连江一带是小有名气的畲医,据他自己说,他家2002年的总收入为15000元,除去收获稻谷20担值1000元,水果收入1000元(龙眼收入200元,橄榄收入800元)外,剩下的13000元都是他家行医的收入。而据他人估计,由于雷桃俤和他祖母都是有些名气的畲医,因此他们行医的收入应不止这些,而应该达两万元以上。另外,村中的法师(道士)也可以以自己的一技之长,维持一家的生计,收入与行医不相上下。雷某某家4口人,主要靠他从事法师维持生活,据他自己估计,2002年的总收入大约是1~1.2万元。
没有传统技艺的人,就设法从事商饮业或其他行业来增加现金收入。在500多人的八井村中,现已开有8家食杂店,他们分布在村中主干道路两侧的各处,尽管竞争激烈,但也都能维持。据他们讲,一间店铺每天的营业额大概是从20~30元至200~300元不等。他们各有自己不同的进货渠道,各有自己相对固定的消费群体,村民们常聚集在不同的小店周围聊天和看电视,形成一个个不同的舆论中心和青年娱乐中心。食杂店中经营的种类很多,品种良莠不齐。有的小店的店主除了经营杂货的买卖外,也经营蔬菜、水果、肉禽、蛋,甚至早点的运输贩卖,以供应全村人甚至邻村竹里、横埭人的食用,即方便了村民的生活,也为自己挣得些许利益。村民雷知国在八井畲族小学门口开了一间杂货店,经营的商品除吃的外,还经营些文具之类;此外,每天清晨四点,他还要骑着摩托车到县城的蔬菜批发市场购一些肉、鱼、菜甚至油条等早点,然后回到村里,在村委会门口的大榕树旁贩卖,如卖不完,他还要骑着摩托车到八井老村那里叫卖或到横埭、竹里去叫卖。而据他说,他这样没日没夜地干,2002年的总收入才约1.3~1.5万元。
有的村民则从事畜牧业养殖,养殖的牲畜主要是羊、兔以及少量耕牛。据我们入户调查,村民养殖的羊主要是肉用山羊,销售对象主要是县城的居民。1头羊全年的净收入大约是1000元左右。一般每个养殖户养50头左右,全村共有10户左右的山羊养殖户。八井村虽有人养耕牛,但却养得很少,全村只有3户人家养了4头耕牛,其中1头还是小牛。农忙时,他们把耕牛租给村民们耕种,也可以连人带牛代人犁耙田,后者每犁耙好1亩田地可收入35~45元左右,价格因田地有别而有差异。此外,八井畲村也有4~5户人家养殖蜜蜂,如雷进玉就是一位养蜂的专业户,他养了70箱蜜蜂。据他说收成好时,这70箱蜜蜂1年可以收入1万多元,而收成不好时大约是7000元,平均的年收入多在七八千元左右。
在罗源县大力发展石材加工业的刺激下,近年来八井村的运输业发展得较快。2003年,从事运输业的家庭有4家,经改装可载重7~8吨的四轮的拖拉机有5部,主要都是到附近的石材加工厂和到采石场工地上拉石头。如雷知禄、雷贤寿父子都以此为生。由于竞争激烈,收入起伏不稳定,每户人家拉石头的净收入,大约每天从60~70元到200~300元不等。但由于需贷款买拖拉机、改装和驾驶培训,因此前期投入较大,同时也由于这一行业的竞争激烈,有的人家甚至很长时间没有净收入。根据我们入户调查的数据估算,每个从事运输业家庭的年收入一般都在2~3万元之间。
在包产到户时,八井村还有大量山地,可由村民自由承包种植。在八井村,有很多家庭都有10亩左右的林地,承包早的,其山上种植的树木已成材,承包晚的,其所种植的林木还小,此外,还要受到《林业法》的约束,无法随意售卖,难以变现,因此除少量种植的橄榄、枇杷、龙眼、蜜柚等果树有收益外,林业这方面的收入比较少。近几年来,在种植业方面也有变化,有的人也轮种西瓜和其他经济作物,希冀通过此增加现金收入,但由于市场饱和,价格一直走低,以及遇到气候、技术等原因,所以经营此的村民收入并不高,其种植的积极性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还有一些剩余劳力则采取外出打工的方式来挣取现金。根据2002年福建省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表的数字看,2002年八井畲村的劳动力有221人,其中外出劳动力178人,而常年在外打工的劳动力为50人,分别占劳力总数的80.54%和22.62%。2002年,八井畲民外出的劳务收入为24万元,而2002年八井的农村经济总收入是288万元,可分配净收入为178.4万元,外出劳务收入所占的比例分别为8.4%和13.5%。由此可见,外出劳工对八井畲村的收入与消费所起的作用都将逐年增大与加强。
第四节 消费特点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八井村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全村盖了30多座新房,许多人家从半山腰搬到了平地,其中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屋有十几座,结束了住草木房的历史,家用电器和高档家具也开始进入八井畲民家中,根据50户畲民的入户调查,在这50户人家中,共有彩色电视机18台,电冰箱3台,洗衣机2台,影碟机6台,电话28部,摩托车8台,手提电话25台,拖拉机5台,碾米机1台。固定资产拥有量已与过去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从收入与消费的对比看,抽样调查的50户畲民家庭中,年收入支出达到平衡有24户,占48%,年收入超过支出的有10户,占20%,而年收入不敷支出的有16户,占32%。后者的主要原因有三种情况,首先有几户是前几年计划生育超生而被罚,家庭经济因此受影响。其次是有家庭成员遭遇重大疾患,医疗费用太大,无力承担。其三是家庭成员中有好几个小孩正在读书,花费很大,而自家的经济来源太少、太单一地依靠农业种植业。
从调查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年收入超过年支出的家庭中,全部是以副业或第三产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土地往往仅种单季,或将土地租给别人,收取口粮,够吃就行;其他两类家庭普遍感到收入来源太少,很多收入一时无法变成现金,致使他们不得不压缩开支,甚至借贷。后者往往还要因为高额的利息而背负更重的负担。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八井畲村近几年家庭中的生产性投入在家庭消费中所占比例并不大,尤其是经济收入较少的家庭,他们家庭消费开支中除了固定比例的吃用迎送外,绝大部分的投资是投入到下一代孩子的教育上,用于增殖性的生产投入比例很小。因此,找到增加家庭收入的方法,已成为他们最迫切也是最困难的事。在没有特殊技艺的情况下,他们选择的方法往往是,农闲时到城里打工。从入户调查的50户人家的经济收支统计可以看到,当地村民在吃、用方面的消费相对固定,家庭会依收入情况调节在40%%~60%之间,而科技、教育、文化娱乐和疾患治疗等方面的支出则变数较大,超支主要发生在这些方面。作为农村社区,八井畲村的迎送礼仪消费的比例虽然依年份而有所变化,但基本上都维持在5%~10%左右。当然,因各家的交往情况不同而有不同的支出,但每家在这方面的支出数额,近几年都维持在1000元左右。
以下为八井村几个家庭的具体情况:
个案1
雷知禄家是属于村中经济比较富裕的人家之一。雷知禄,男,2003年41岁,家庭成员5人,其中劳动力3人,女性1人,小孩1人。妻子春桃33岁,在家务农,是雷知禄再婚的妻子。大儿子雷贤寿22岁,为其前妻所生,初中文化程度,在家务农,帮助其父开拖拉机;二儿子雷贤华,15岁,正念初二。其家有水田3亩,建房换地后只剩1.5亩,另有干田0.5亩,山林5~6亩。近几年,自己种双季稻的只有0.5亩,其他的田,春季给其兄弟种西瓜,夏季自己再种水稻,收成每百斤西瓜,其兄弟给予15元作为土地的报酬。因此他们春季所种的0.5亩田只收300斤稻谷,而夏季种的3亩田共收1800斤。春季2.5亩给兄弟种西瓜可收获2500斤,他有375元租借收入。雷知禄家养了3只鸡,8只鸭,没养猪。家中有黑白和彩电各1台,录音机、影碟机各1台,固定电话1部,手机2部,家中没有从事其他手工制品生产。雷知禄原是村里二队的拖拉机手,16岁开始驾驶拖拉机,已有25年驾龄。自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级经济解体,他就不再为村里开拖拉机。1995年开始自己开拖拉机,2001年购买了第一部手扶拖拉机,2003年又购买了一部,每部价格约在16000元左右,基本上都是用自己的积蓄所购。儿子雷贤寿16岁开始开三轮摩托,2003年雷知禄为他购买了一部新的拖拉机让他驾驶。拖拉机既可载石头也可拉砖头。过去他们经常到西兰乡去拉石头或砖头,罗源经济开发区成立后,他们就在开发区里载石头或砖头搞基建,生意并不稳定。据他们介绍,开拖拉机的成本大约有以下几项:养路费每月150元;油费平均每天需5~6元(每公升1.75元);损耗最多的是轮胎,每只轮胎需300元,1~2周就需更换一个。据他们说,最多时一天可赚280~300元,少时则20~30元或60~70元都有可能,而且也不是每天都有活干。2002年全家开拖拉机共赚纯收入25000元,外加租地给人家种西瓜的报酬有375元,年纯收入为25375元,人均纯收入约5075元,所种的稻谷均作为口粮。
雷知禄家的总支出为:每月用于购买肉、菜等食物用350元;香烟150元/月,电费30元/月,水费75元/年,液化煤气350元/年,电话费350元/年,移动话费100元/月,日用品约700元/年,学费及教育费用中学1350元/年,小学300元/年,用于迎送礼仪的费用为2800元/年,其他支出1000元/年左右,总支出共计14485元/年,人均支出2897元/年。
个案2
雷炳金,男,1962年出生,2003年41岁,小学文化程度。家庭成员6人,其中劳动力3人,男劳动力2人。妻子雷智钗,1968年出生,35岁;母亲雷莲香,1933年出生,70岁;长子雷建华1987年出生,16岁,小学毕业,现在城关作厨师;女儿雷建英1989年出生,14岁,初中学生;次子雷贤武1994年出生,9岁,小学二年级学生。雷炳金有水田2.8亩,干田0.5亩,旱地0.2亩,山林8亩,自留菜地0.4亩;家中饲养有6只鸡,3只鸭,没养猪。家中有彩电和影碟机各1台,电话1部。雷炳金除了种稻谷外,还种有橄榄树130余棵(至今还未有收入),柿子树8棵,枇杷树7棵,芭蕉树6棵(尚未有收入),龙眼树6棵(尚未结果);其次,他在干田、旱地和自留菜地里种有芋头500株,地瓜3亩,春季轮种西瓜3亩。农闲时也外出务工,务工的地点有时在城关,有时在八井附近的水厂。据雷炳金说:2002年其家庭总收入的情况大体为:稻谷自给,西瓜纯收入2000元左右、芋头1500元、地瓜2700元,自己外出务工约挣2000元,大儿子雷建华在福州的工厂中做“元宝”(金纸)所得的收入1000元,共计9200元,人均纯收入约为1533元。
他们家的总支出为,食物方面:菜金每年支出3600元左右;日用方面:液化煤气费300元/年,水费50元/年,电费350元/年,日用品300元/年,电话费80元/年;教育费用:中学1300元/年,小学350元/年,孩子零花钱1000元/年;迎送礼仪费用:约1500元/年。另外,因为超生曾被罚款30000元,当时借高利贷还了9000元,现每年还需要还高利贷的本息,但具体数目不详。所以他家可知的总支出共计8830元/年,人均1470元/年。其收支情况在本村属于中等偏下,因为超生被罚款,因而对此颇多怨言。
个案3
雷信春,男,40岁,小学文化程度。家庭成员5人,其中劳动力4个;妻子雷月梅,39岁,小学毕业,在家务农;大女儿灼英,20岁,初中文化,在家务农;二女儿卓燕,17岁,初中文化,在罗源城关一家超市里务工;三女儿雷灼银,15岁,小学四年级学生。雷信春拥有水田2.5亩,干田0.8亩,山林30亩(用于种松树,尚未带来收入),鸡2只。家中有彩色电视机、电冰箱、影碟机各1台,电话1部,自行车1辆,缝纫机1架(雷信春10年前是当地的裁缝之一,会裁制“凤凰装”,当时每套凤凰装的价格在100元左右,现已放弃)。雷信春2002年家庭总收入基本来自其做油漆工的收入,共计8000元左右,人均1600元。
其家庭的总支出如下:粮食自给,其他菜金3000元/年;日用方面为:煤气费100元/年,电费120元/年,水费20元/年,零用1200元/年,科技教育投入(小学费用)400元/年,迎送礼仪费用约600元/年,化肥800元/年,文化娱乐20元/年,共计总支出6260元,人均1252元。其收支情况在本村属于中等偏下。
个案4
雷信伙,男,43岁,小学文化程度。家庭人口6人,其中劳动力4人。其妻雷翠英,40岁,小学文化;大女儿雷桃金,19岁,现在中南民族大学外语系就读。大儿子雷可法,17岁,初中毕业,在罗源城关务工;小儿子雷可财,15岁,小学毕业,在福州务工;母亲雷喜珠,77岁。家有水田4亩,干田1.6亩,家中没有任何耐用消费品,只有一张犁和一张耙。春季没有种地,家人多外出务工,因此也不饲养任何家禽家畜。家庭总收入基本来自外出务工所得。雷信伙本人到罗源打杂工,每天收入20~30元左右;2002年差不多有4个月时间在外打杂工,收入有2500元左右。妻子雷翠英在罗源当保姆,年收入在1500元左右。两个儿子在外务工仅能自保。因此,其家庭的纯收入在4000元左右,人均收入667元。他家的总支出为:粮食自给,菜金2000元/年,日用方面约2000元/年左右,支付大女儿生活费200元/月,迎送礼仪费用2500元,共计总支出8900元,人均支出1483元。此外,他家的总支出中,还没有包括历年所借1万多元高利贷的本息。他们家庭的收支严重入不敷出,家庭经济情况在本村中是属于很差的。
第五节 经济发展趋势
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几十年发展,八井村的农村总体经济水平、人民消费水平都有巨大发展与飞跃,他们已基本摆脱了贫困,正逐步利用相对完善的农村基础设施,寻求更加富裕的生活。八井村产业结构在20世纪90年代已发生了一些变化,二、三产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村民的市场和商品化意识有了很大的加强,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八井村与周围其他村庄相比显得贫弱些。
首先的主要问题是经济结构还比较单一,产业结构调整仍未到位,二、三产业的发展缺乏引导与市场支持。八井村仍以种植业为主,本村并没有企业,仅有的一家养鳗场也是外地人来办的。他们仅向本村人租用田地,付租金而已,也没给八井村提供什么工作机会,难以对本村的经济形成效益和帮助,却占用了农村耕地用水。本村有少数经济能人,虽然到外地参股办养鳗场、虾池,但这只是对其家庭有利,而对八井畲村整体的经济发展起不了什么帮助作用。
其次是多年来八井畲村的集体经济十分脆弱,村财政几乎没有收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八井村经济的基础历来就很脆弱,结构比较单一,又没有村办企业,收入渠道极其狭窄,除了农村特产税返还和“三提五统”外,根本没有其他收入渠道,村财政收入的稀少,反过来又影响了村集体经济的核心作用与引导作用。八井畲村的集体事业、公益事业的发展,基本都是依靠上级扶贫办、老区办,特别是各级民委的支持,才有了相对完善的农村基础设施和居民社区环境。八井畲村并非没有相对出色的经济能人,但破碎的集体经济,难以使个体的力量形成“合力”,为共同的“社区经济”服务。近几年来,八井村的资金和劳动力的外流已开始慢慢显现,而这些对八井村来说都是稀缺的资源,也是村落社区进一步走向全面富裕和发展的基础。
再次是村民人均纯收入仍然偏低,特别是可支配性的消费收入偏低,影响了农村生产性投入的比例,更影响了二、三产业的发展。文教卫生事业的落后,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村民文化科技的相对缺乏,使他们难以找到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的办法。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经济收入相对较高的村民,其所受的教育程度往往也较高,而且会说普通话,善于与外人沟通。教育水平低使得村民们往往不愿投入太多的资金给下一代做“智力投资”,而越是如此,教育水平就越难提高,如此恶性循环势必使教育成为八井村经济发展的瓶颈。近几年来,由于医药费上涨过快,村民因无力支付医药费而“小病磨,大病拖”,一些农户因病背上沉重的债务,陷入贫困而无力自拔。八井村因病致贫、返贫的农户,据村民们自己估计约占贫困户的40%左右。
八井村的经济在逐步加快前进的同时出现的这些问题,反映了其经济发展趋势中逆向的可变因素,保存和发展、完善村落社区经济要素,引进合适的经济增长要素,可能才是最大限度地为本社区经济服务的关键。
附注
①雷君恒墓碑上镌刻的衔头为:“旌奖祖考耆宾洪溪雷公”。
①当时八井行政村中的189户人家,包括横埭村与竹里村的。
①蒋炳钊等人,“福建罗源县八井村畲族社会情况调查”,《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126页。
① 蒋炳钊等人,“福建罗源县八井村畲族社会情况调查”,《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125页。
①罗字第02163号《福建省罗源县土地房产所有证》(1952年2月)。
①《罗源县城关人民公社八井营畲族调查报告》,(1958年油印本),35页。
①参见蒋炳钊等《福建罗源县八井村畲族社会情况调查》,载《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123页。
①参见《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127~128页。
①罗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罗源县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891~892页。
②《罗源年鉴》编委会编:《罗源年鉴(1998年)》。
①《罗源县城关人民公社八井营畲族调查报告》(调查时间: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七日至二十四日)第1页:“本村位于罗源城南,相距约二十华里,属于城关人民公社八井营一、二、三连。共有三个自然村:八井、横埭、竹里,竹里又分上、下竹里,合为一个自然村。”
②蒋炳钊、林玉山、袁钟秀、陈自昭调查整理:《福建罗源县八井村畲族社会情况调查》,《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18页。
①以上资料、数据根据八井村《流入人口登记簿·流入人口登记表》(1995年、1996年)统计。
②资料来源于《福州市基层计生信息变动报告单(村级2)》(2000年)。
① 参见八井村《计划生育台账登记簿》(2003年)及丛云飞调查笔记(2003年)。
①以上资料源自八井村《计生台账登记簿》及笔者实地调查。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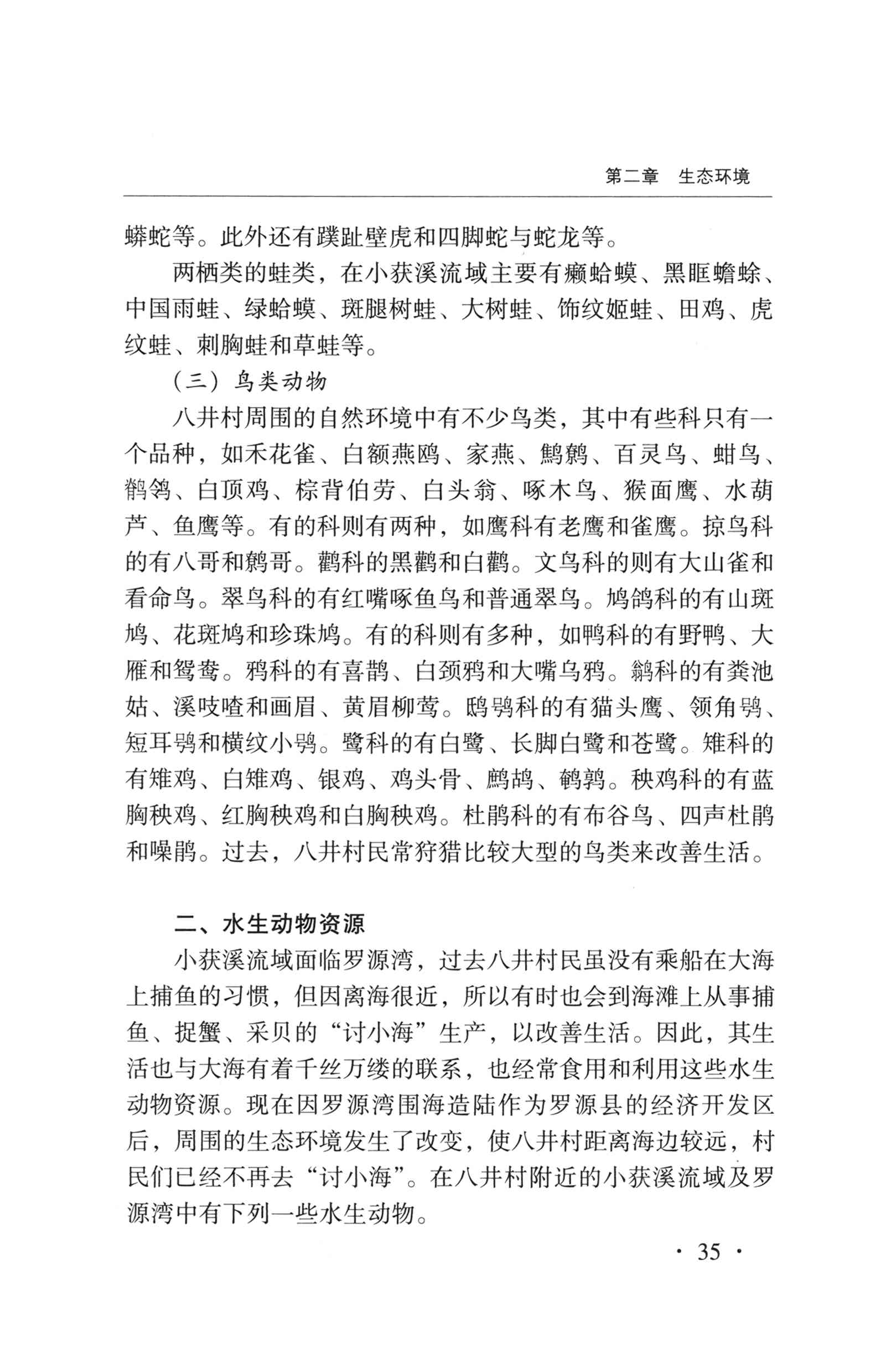
《畲族福建罗源县八井村调查》
出版者:云南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对福建省罗源县八井村畲族的调查,依次介绍了其概况与历史、生态环境、经济、人口、婚姻家庭、宗族、社区管理、法律、民居建筑、风俗习惯、口传文化、教育等。
阅读
相关地名
八井村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