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概况与历史
| 内容出处: | 《畲族福建罗源县八井村调查》 图书 |
| 唯一号: | 130920020230005109 |
| 颗粒名称: | 第一章 概况与历史 |
| 分类号: | K928.5 |
| 页数: | 21 |
| 页码: | 1-21 |
| 摘要: | 本章介绍了八井村行政隶属沿革、族称演变、畲族传说、畲族源流、以及八井村概况。 |
| 关键词: | 八井村 行政隶属 行政区划 |
内容
畲族是中国东南地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广东、江西、安徽、贵州、湖南等地。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有709592人,福建的闽东大约聚居有十九万人,是畲族大分散、小聚居的主要地区。八井村所属的罗源县就是闽东的一个有着畲族分布的县份。
第一节 八井村行政隶属沿革
八井村所在的罗源县别号罗川,位于福建省东北部沿海,地处北纬26°23'~26°39'和东经119°07'~119°54'之间,面积有1081.2平方公里。辖6个镇、5个乡(含1个畲族自治乡),人口25.29万,其中畲族约两万多人,占全县人口的8%,罗源通行闽东方言福州土话中的罗源话,八井村畲族除了会讲罗源话外,在其内部还使用畲语。
在宋代,罗源县分为崇德、常熟、同乐3个乡,17个里(隅)。其中崇德乡辖县城及其附近地区。划东隅、西隅、南隅、北隅、新顺里、梅溪里、安金里、拜井里、善化里9个里(隅)。现松山镇所属的村落,除了北山、巽屿外,包括碗窑里、八井村在内的制瓷繁荣地带的其他村落都属于拜井里。元代沿用宋代制度,但分罗平、霍口、招贤、黄重各为上下2里,里(隅)数增至21个。但碗窑里、八井村等现在松山镇所属的村落仍属于崇德乡拜井里。
明代洪武十四年(1381年)撤乡的建制,改实行以里辖图制,仍保持有21里,但把霍口上下2里合并为1里,而把新丰里分为上下2里。永乐元年(1403年)裁去南隅、北隅和霍口,并把罗平上下2里合并为1里,罗源县的里数剩下17个。永乐十年(1412年)又裁去新顺和安金2里,罗源县剩下15里。天顺六年(1462年)裁掉罗平里,并把新丰上下2里合并为1里,同时,在善化里中增加1图,罗源剩下13里14图。成化八年(1472年),除了恢复罗平里外,还把新丰里改为上下里,并在善化里中增加1图,罗源县成了15里16图。万历年间(1573年~1619年)以成化八年形成的16图为16里,除了将善化2图改名为化一、化二,招贤2图改名为贤一、贤二,新丰2图改名为丰上、丰下,黄重2图改名为重上、重下外,其余均依原来的里名。尽管明代有如此多的变化,但松山镇内的这些村落如八井村等都属于拜井里。
清代罗源县仍沿用明代万历年间的划分,分为16里,但也有些变化,这个变化就是里下设铺,铺下辖村。在清代,现松山镇的几乎所有村落仍属于拜井里。当时的拜井里分松山、泥田、大获和小获四个铺。松山铺辖上吕洞、下吕洞、牛洋、进山、歧前、歧后、树柄、马鞍、白柯(白花)9个村落。泥田铺辖泥田、迹头、可湖、泥港、白水5个村。大获铺辖大获、山头、坑里、林里、下井洋、叶洋、下坑7个村落。小获铺辖小获、深港、芝堂前、桥下、新村下、陈厝头、林下尾、后山、罗厝里、陈伯井(八井)、横埭、碗窑里12个村落。而在乾隆年间,陈伯井曾一度属于化一里。
民国初,基本上沿袭清代的行政区划。民国二十年(1931年),罗源县分为5个区,其中第二区区公所驻地在碧里乡,其管辖29个乡镇,八井村属之。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九月,实行保甲制度,将5个区并为3个区,改区公所为区署。区以下设19个联保办事处,统辖166保。当时,第一区区署驻地为松山,下属9个联保。八井村和牛洋村属于第一区大小获联保竹里保。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改联保为乡镇,八井村属于第一区大小获乡的小获保。民国三十年(1941年)二月,新从连江县划入的巽屿、北山与大小获乡合并组成获巽乡。全县也改为2个区、1个县辖镇,12个乡。八井村属于第一区的获巽乡小获保。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二月,罗源把乡镇增设至19个,但八井村仍属于获巽乡小获保。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乡镇缩编为7个,松山乡和获巽乡合并为松获乡,公所驻地为大获村,下辖歧后、歧前、小获、大获、外剩、巽屿、北山、白湖、泥田9个保,八井村属于小获保。
1949年8月14日,罗源县解放。8月28日,县人民民主政府接管了旧政权的7个乡镇公所,建立了7个区人民民主政府,并沿用原乡镇名称,区以下仍保留保甲建制。八井村属于松获区小获保。1949年9月,将凤山、凤寿两区合并为第一区;洪林、河阳两区并为第二区;鉴碧、松获两区合并为第三区;福丰区则改为第四区。因此,八井村属于第三区小获保。
1950年3月,废除保甲制度。6月,增设第五区;9月,增设第六区,至此,全县划为6个区、64个乡和4个街。其中第一区包括白塔、南门外、歧余、松山、小获、大获、泥田、巽屿、北山、起步、长治、港头、兰田、桂林、护国15个乡,八井村属于小获乡。1952年4月,将松山等地增设为第七区,将洋头等地增设为第八区,乡镇也做了调整。这时的第七区辖有泥田、白水、松山、小获、大获、巽屿、北山7个乡。7月,县人民政府把八井从小获乡划分出来,单独成立一个乡,其辖有八井村、竹里村和横埭村等。1954年,又增设乡镇,第七区又增加了外洋、迹头、歧后、上杭4个乡。1955年8月,撤销第七区,并入第六区,9月,第六区改名为城关区,下辖八井、横埭、竹里的八井乡隶属城关区。1958年5月撤区并乡,八井乡被撤,八井村属于歧余区小获乡。
1958年9月大办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全县建立6个人民公社,98个生产大队。10月1日,八井高级社成为隶属城关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因公社用军队团的建制,故八井生产大队建制为八井营,下辖八井(一连)、横埭(二连)、竹里(三连)等村。1961年5月,恢复区一级建制,下辖几个人民公社。其次,增设人民公社至37个,缩小其各自的管辖范围。此时,八井大队隶属城关区小获人民公社。
1965年7月裁区并社,全县划分为城郊、松山、起步、洪洋、中房、西兰、飞竹、霍口、碧里、鉴江10个人民公社,原城关镇建制不变。1966年6月,城关镇改为城镇公社;城郊公社除划归松山、城镇公社的8个大队外,其余的15个大队另组成白塔公社,同年11月则更名为红塔公社。至此,全县划为11个人民公社。其中八井大队归属松山人民公社,仍管辖竹里、横埭村。
1984年9月,全县的人民公社都改为乡镇,各生产大队改为村,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从1990年以后,除了松山乡改为松山镇外,其所统辖的村落一直保持不变。其辖有北山、巽屿、外洋、剩头、大获、上杭、小获、八井、竹里、歧后、歧头、南歧、树柄、吕洞、前房、渡头、泥田、迹头、乘风、白水、上土港、下土港22个行政村;而在八井行政村中则有八井与牛洋两个自然村。①
第二节 族称演变
畲族主要集中分布在福建闽东地区,八井村的畲族多自称为“sanha”(山哈)。但“sanha”(山哈)的意思,各地的解释则有不同,有的地方如霞浦县崇儒乡的畲族认为:“sanha”(山哈)既是“山客”,也是“三吓”,前者的意思为居住在山里的客人、外地人;后者的意思为畲民有“怕抓、怕打、怕苦”“三怕”之意。②后者这种说法,可能是解放前在大汉族主义的歧视下而形成的一种解释。有的地方认为“sanha”(山哈)是“三合”,意指畲族蓝姓、雷姓、钟姓三者联合之意。罗源县八井村的畲民认为畲语的“哈”即是“客”,“山哈”指的就是“山客”,意思是居住在山中的客人或山里迁徙的客人,而没有或不代表其他意思。
有的地方的畲族也谦称自己为“小姓人”,而尊称汉族为“大姓人”;或者称自己为“三姓人”,称汉族为“百姓人”;或者在本族中互相称呼“zigeying”,即“自家人”、“自个人”、“自己人”,而称汉族为“holou”,即“华老(佬)”、“汉老(佬)”,在一些畲族的歌本中,“holou”也写作“阜老(佬)”、“河老(佬)”或“福老(佬)”。③
此外,在过去,有的地方的畲族也自称自己为“siha”,汉字可写成“食客”或“吃客”。畲族有的老人自己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忠勇王盘瓠帮助高辛皇帝征讨番邦有功劳,所以高辛皇帝恩准盘瓠忠勇王的子孙免纳粮税,免派徭役,可以傍山吃山,靠海吃海,走到哪里就可以吃到哪里,故有此自称。后来,由于汉族中有些人用这一称呼来污蔑、歧视他们的祖先好吃懒做,所以就逐渐弃之不用。①
还有,过去有的地方的畲族也自称自己为“瑶人”、“苗民”。在有些地方如霞浦县的有些畲民也自称自己为“畲家人民”,不过他们认为此“畲”字,应由“入田米”三个字组合而成为“畬”字,并自我认为这是汉顺帝赐封的,如霞浦县崇儒乡霞坪村保存的《汝南郡蓝氏宗谱》中的《释明畲字义》说:“汉顺帝时,有钟姓、雷姓官员同奏:盘、蓝、雷、钟四姓原是上古忠勇王功臣后裔,仕廊庙无不致身尽忠,农草野无不尽力耕作,高山无水之处,栽种奢禾,遇欠岁能济饥,请封名号。上准奏,旨谕:盘、蓝、雷、钟四姓,种奢禾济饥有功,山米助田米,就以入田米成一字,曰‘〓’,四姓子孙封曰‘〓家人民’。”②故有时他们也自称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实行的是民族平等政策。1952年7月,为了了解本省内的民族情况,福建省人民政府组织了民族调查组,在闽东地区调查,曾编写《畲族福安县仙岭洋村调查情况》等调查报考,对畲族的情况有初步的了解,并发现过去对畲族的称呼中有歧视现象。因此在1952年7~9月间,闽东各县都召开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各界人民代表都做出决议,统一以“少数民族”暂时作为畲族的代称,并严禁使用任何带有侮辱性的族称。受此影响,这以后,畲民也有自称“少数民族”的。如这次我们在八井村调查时,就常有人跟我们说:我们少数民族如何如何等。
目前政府法定的族称——畲族主要来自被称,但这种称呼也是诸多称呼中的一种。在历史上,汉族称畲族有多种称呼,如畲民、畲客、畲人、瑶民、畲瑶、苗夷、山民、棚民等。
对这些被称,八井村畲族同胞比较反感的是“畲民”、“畲人”等,因为,在闽东各地的方言中,“畲”的发音与“蛇”、“邪”的发音相近。在新中国建立前,闽东汉族中有些人恶意利用这种谐音曲解其义,有的甚至用侮辱性字眼编成顺口溜,对畲民横加歧视、欺凌、唾骂,并因此常挑起民族纠纷,故闽东地区有的畲族同胞如八井村的畲民认为“蛇族”、“邪族”是一种忌语。
1953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派出由中央民族学院、华东民政事务委员会和福建、浙江、广东省民政厅等人员组成的民族识别调查组,赴福建、浙江、广东等畲族地区进行识别调查。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的定义,结合我国民族的实际情况与历史情况,认为“畲民”的称谓出现得较早,有历史的基础;同时,“畲”字没有贬义,其为“三岁治田”或“烧榛种田”之意,民以“畲”命名,只说明他们是“山居为农”、“耕山而食”的善田者也。其次,民族识别调查组也尊重本民族人民的意愿和遵从“名从主人”的原则,即同一些畲族同胞进行了充分讨论与协商,最后确定用“畲族”这一称谓来命名,并确认畲族是一个具有自我特征的单一少数民族。1956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并正式公布确认:畲族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平等成员,从此,畲族就成为法定的族称,从根本上结束了历史上族称混乱的现象,也在某种程度增强了畲族内部的凝聚力。
然而,正因为在闽东方言中,“畲”字与“蛇”、“邪”谐音,历史上又常有以后两者称呼侮辱畲族的事件发生,所以,畲族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因此忌讳而不太愿意自称畲族,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还有人要求改变这一法定的族称。不过,由于民族政策的实施一步步深入和民族关系的根本改善,现在绝大多数畲族同胞都接受和拥护这一族称了,包括八井村的村民,他们也自豪地说,他们是畲族。
第三节 八井村畲族传说中的始祖
各地的畲族多认为他们是上古忠勇王盘瓠的子孙。盘瓠王和畲族几个主要姓氏祖先的传说,或保留在畲族同胞的记忆中,或保留在所谓记录历史记忆的族谱中。过去居住在八井村对面大山座山腰中,多与八井雷姓畲族通婚的树楼村蓝姓畲族的《蓝氏族谱》,其修于清代光绪十八年(1892年),其中的《敕书姓氏封》就记述了盘瓠的传说,其曰:“自昔盘古分天地,伏羲画八卦,造书契,神农艺五谷,尝百草,黄帝设井分州,调音律,备器用。爰乃高辛氏正宫德成刘帝后,此娄金星所由降生也。于是高辛在位四十五年五月初五,正宫皇后夜梦娄金星降凡,因是惊醒,陟然耳痛,宣令太医院调治,取出一物如蚕形,形样稀奇,以盘贮养,变为龙狗,金鳞珠点,眼光四射,颇会人言,帝见喜之,取名龙期,号曰盘瓠。时方平静,国家安宁,突有西番率党倡叛,行妖使术,无敢与敌,帝心忧虑,宣令有人退敌,许以三公主为婚,举朝默然,莫敢承命。龙期一见,进前折榜,啣奉帝前。帝命尔能成功,加封敕赐。龙期承旨,漂洋过海,历尽寒冰,直至西番。番王一见此兽,锦色奇形,因命纳在帐内,随从出入。一日番王集群臣欢乐畅饮,各已告退,王醉睡沉迷,夜半首级被龙期咬断,星夜攀城滚浪回朝,及番朝审觉,军前虎将万吉等统兵追赶,已无踪迹。龙期将番王首级跪献帝前,验其首无异,大喜曰:‘彼苍有灵,生此靖邦,天下定矣!’龙期谢恩,即请敕赐。帝悔前言,因以宫女谬称公主,赐以盘瓠为亲。龙期不悦,进入内宫,暗认公主,身隐望恩楼金钟下,期以七日夜成人完亲。已至六日,皇后私心窃视,身体以备,但头未成形。本是中幽北斗禄存刘隆星君脱化生,几助国安民,帝恩曩恩令既出,宜敕赐加封,即命群臣置酒笙歌,招龙期为驸马,敕封忠勇王,敕忠勇二大将军,左将军邓从成、右将军邹定施带领部众,听其差令。因准会稽山七弦洞优游林泉,并建王府,时御林军千余人护卫,举朝官员备酒饯送,给牒刊颁,永存为照者。诏下:驸马忠勇王除寇有功,给赐敕书,继世相传,长垂不朽,并赐世代免征差费,逢山逢田任其耕种,凡经过各省府州县,供奉夫役,支给俸薪,仰该部知悉,御旨敕书,统付刊颁存照。”还说:“驸马王生三男,长名自能,仍姓本姓盘;次男以蓝(篮)盛至殿前,因蓝为姓,赐名光辉;三男裹至殿前问姓,适雷鸣应声,因以雷为姓,赐名巨祐。帝以东夷贡三女长奇珍配盘自能,封为开混柱国侯;次奇珠配蓝光辉,封为护国侯;三奇配雷巨祐,封为武骑侯;盘瓠王生一女,名龙郎,匹配钟志清,与以敌勇侯之封,于斯时也。三株竞秀,百世流芳,螽斯衍庆,瓜瓞绵长矣。”
在八井村,据说还存有光绪年间修的《雷氏族谱》,然而,现不知流失在哪里,这次调查虽经多方查找,仍没能见到,甚是遗憾。不过,1958年从事福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当时的调查人员见过,他们根据《雷氏族谱》中的记载,概述了关于盘瓠王和畲族的来源,“在盘古开天辟地以后,出现个高辛皇帝,皇后刘氏耳痛三年,从耳中取出一虫,放在盘里养活。一日,虫变成一条龙,一说似麒麟。满身花斑,皇帝认为不祥,欲驱逐出去。大臣劝止,留在宫中饲养,取名盘瓠。当时有番王作乱,扰乱天下,皇帝出了告示说,如有打败番王者,赐三公主为妻,当时无人敢应,只有盘瓠撕下布告到皇帝面前,表示能收拾番王。于是盘瓠领旨跨海而去,到番王处约有三年,侍候番王,百顺百依。一日,盘瓠乘番王酒醉,取下番王头,奔回见皇帝,皇帝大喜,但不愿以三公主给盘瓠为妻,拟以一宫女代替,盘瓠不肯,竟以人语说:将我放在钟下,七日七夜变成人形,七日后,果然变成人。亦有六日后公主掀钟看,身已变人头未变好一说。和三公主成了亲,居住在深山中,共生三子一女。高辛皇帝赐姓,长子姓盘,次子姓蓝,三子姓雷,女儿嫁与钟姓为妻。此后,盘、蓝、雷、钟四姓为盘瓠后代,是为本民族起源。”①
从上述两篇记述看,虽细节上有些差异,如《蓝氏族谱》说高辛帝见到“龙期”“喜之”,盘瓠在金钟内变人时,是因刘皇后等不及偷看,而使“龙期”头没有变成人形;而雷姓族谱中所说,初见到“龙期”时,高辛帝认为不祥,后在大臣的劝阻下,才留下“龙期”饲养;另外,盘瓠在金钟中变人时不是刘皇后去看,而是三公主去掀钟观看,等等。然而,虽然有细节上的不同,但这些文字所表述的主题与社会记忆、历史记忆却都是基本一致的,即认为盘瓠是畲族的始祖,并以此为象征,作为团结畲族的唯一纽带。
尽管这些神话传说与其他地方畲族的传说基本一致,也具备上述的社会功能,但八井村雷姓在光绪年间重修族谱时,似乎也对谱中所刊载的这一民族来源的神话传说不以为然,他们在族谱中这样写道:“……今人见其妇女异妆音响殊俗而以为盘瓠之遗类者,毋乃谬乎?”②从而对这一有关其民族来源的传说表示了异议。
第四节 八井村畲族的源流
关于八井村畲族的源流,有着几种看法。首先根据《罗源县志》畲族篇迁徙一节记载,八井村雷姓畲族属于松山镇牛洋支派。该书说,牛洋支派的雷姓祖居广东潮州如东县,明弘治年间(1488年~1505年)入迁现松山镇牛洋村,并分衍八井村。清代顺治十八年(1661年)因迁界的缘故,分别迁吕洞、溪(即南洋)、尖山。康熙二十年复界回迁。其后裔分衍牛坪(现已废)、横埭、杨家里、经布岩等地。①这表明牛洋、八井、横埭、杨家里、经布岩、牛坪的雷姓畲族均出于同一来源,而且他们的始祖是在明成化年间先迁入罗源牛洋,以后再分衍八井,到了迁界结束后才分衍到横埭等地。不过,在这里,没有指出牛洋支派的始祖是谁。然而,在同一篇的武术一节中该书在介绍“八井拳”时说,“八井拳是在明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由雷居安、雷安和两兄弟传到牛洋村,其后裔迁居八井后逐渐出名,故称‘八井拳’。”②在这段话中,虽指出了牛洋支派两位先祖的名讳,但表述得比较含糊,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从其叙述中马上确定雷居安和雷安和就是牛洋支派的开基祖。因为其表述的是由两个人在成化年间把拳术传到牛洋村。因此,如果雷居安和雷安和不是牛洋村雷姓的开基祖的话,这段话可以理解为雷姓畲族在成化年间以前就早已经迁入牛洋,而在成化年间,由雷居安和雷安和这两个人把拳术传到牛洋村来。但是如果雷居安和雷安和的确是牛洋支派的开基祖的话,那么,牛洋这两位开基祖原本就懂得武术,所以当他们于成化年间迁入牛洋村时,也就自然而然地将武术技能带到牛洋村来。同时,也表明牛洋支派是在明代成化年间迁入罗源的。显然,这两段记载有着某些矛盾,即武术一节中所记载的时间,无论我们如何理解,它都要早于迁徙一节中所记载的年代。换言之,这两条记载中,有一条记载的始迁时间是错的。其次,这两条记载还有一个共同的弊病,即它们都没有把牛洋支派雷姓始祖的迁徙路线说得明白些。不过,如果我们综合上述两条记载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牛洋支派的雷氏畲族始祖始迁罗源的年代为弘治到成化年间,或者迁到牛洋为成化年间,而从牛洋分衍八井则是弘治年间。因为通常在一个地方,不会有同一支派的某个人来此开基后,又有一个同一支派的人再来开基一次的现象,所以宁可像上面那样理解,似乎可以比较顺理成章地得到解释。此外,综合上述记载看,牛洋支派的始祖应为雷居安与雷安和两人,他们先开基牛洋,其后裔分迁八井,迁界后,再迁横埭等地。
在这次田野调查中,我们从八井村畲民的记忆中了解到一些关于其祖先来源与迁徙的情况。根据八井村畲民的口述,其开基祖为雷安居与雷安和,这与《罗源县志》中“雷居安”的说法有些不同。他们祖居广东潮州凤凰山,先迁居兴化府的莆田,而后又迁居罗源县白花,接着又迁牛洋(吾洋、五羊),然后又迁居现起步镇的白岩,接着又迁回牛洋定居,定居以后,再从牛洋迁到八井村,在八井形成福、禄两房,后来又有人从八井村迁居到横埭。换言之,安居与安和迁徙来迁徙去,最后定居在牛洋,并在此开基散叶,然后,分迁八井,在八井形成福、禄两房,以后,又有人迁到横埭去,故横埭现既有福房的人,又有禄房的人。
然而,1958年,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八井调查后所写的报告说:“分布在八井、横埭的雷姓畲族,传说祖先在广东潮州,后迁入福建兴化的莆田一带,明朝成化年间迁至罗源,先住在罗源城西南的笔架山,后迁至八井一带,最初分福、禄两房,福房住在牛洋、八井,禄房住在横埭。传说来到这里已经住了十一代。”①换言之,根据这样的说法,八井、牛洋、横埭的雷姓畲族始祖在成化年间先迁入的是八井一带,而不是牛洋。其分为两房,八井、牛洋均为福房,而横埭的则为禄房。看来与《县志》和现在八井畲民的口传又有不同。
在这次调查中,通过口头调查和早期土地买卖文书、墓碑文字等的验证,我们了解到八井畲村的字辈似乎有两个系统,第一为“安—邦—民—飞—永—君—子—辅—朝—廷—乾—坤—志—信—可—知—贤”,第二为“安—邦—民—飞—永—君—子—辅—枝—大—向—章—传—世—德—恒—开”。从这两个系统中,我们可以看到“安”字辈都是八井雷氏的第一代,因此安居或居安与安和的确是牛洋、八井雷氏的开基祖。
在调查中,我们也看到,现八井村确实有两个房头,福房的祠堂已破烂不堪,但还屹立在祠堂厝那里。原先禄房的祠堂现已不见踪影,但禄房的派下现在当中厝祠堂原址上,建了一间三面墙的小屋来摆放祖先牌位等。而且从这两房的人取名的情况看,两房的人多数都以第一系统的字辈来取名;而福房中的有些人则用第二系统来取名,如德明、德育等,并且其儿子辈的人又用第一系统来取名,如德明的儿子叫知文,德育的儿子叫知钦,孙子叫贤华、贤斌。
我们还看到,八井雷姓与横埭的雷姓关系密切些,而与牛洋的雷姓似乎关系疏远些,即牛洋的雷姓都不属于八井的福、禄两房,他们另为一房支。这表明,八井雷姓与牛洋雷姓在比较早期就已经分支了,而与横埭雷姓则互相纠缠不清,即横埭雷姓即有八井福房的人,也有八井禄房的人,所以与八井的福、禄两房关系都比较近。
由此看来,1958年调查时所说的牛洋与八井为福房,而横埭为禄房的说法似乎与现存的实际不同。其次,《县志》中所说的开基祖的后裔再迁八井的说法也有问题,因为,如果这样,那么牛洋支派福、禄两房应该是从居安与安和两人算起,这两房应该在牛洋形成,而后他们的派下人迁到八井,这才导致八井形成福、禄两房,然而,八井雷姓似乎与牛洋雷姓关系都不密切,因此,事实似乎与《县志》所说的也有差异。
因此,综合上述种种情况加以建构的话,我们认为,比较合理的雷姓畲族牛洋支派的宗族变迁应该是:成化年间,居安与安和开基牛洋,并在牛洋形成两房。到弘治年间或者后来,安和迁徙八井村,是为八井的开基祖,并在其派下中形成了八井的福、禄两房。清初的迁界,八井畲民迁居吕洞等处,康熙二十年复界,八井畲民回迁后,福、禄两房中均有人再迁徙横埭,并发展至今。所以,才会形成八井福、禄两房的雷姓与牛洋雷姓的疏远,与横埭雷姓比较亲近的现象。否则,则有许多地方解释不通。
第五节 八井村概况
一、八井村的自然与社会环境
八井村位于小获溪的中游地带,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其老村背靠双髻山,海拔60~75米,有祠堂厝、墘头厝、打石厝、当中厝、水井巷等角落,福房的祠堂在祠堂厝,禄房的简陋祠堂在当中厝,老村东边通往公路的村口则有白马王庙;新村位于山脚下海拔7~10米的谷地上,有七斗洋、铁厂、新厝等几个角落。畲族小学建在小获溪汊流形成的溪坂上。新村的南边隔着小获溪为竹里行政村的横埭畲村,其村后为虎头山、大山座、荔枝栏、狮山等山,大山座的山脚下过去有一个名叫树楼的小村落,但现在已成遗址。翻过虎头山则为竹里村。八井村的西边为由层层叠叠的小山与大山构成的狭窄谷地,其两旁有连绵不断的层层山岭,幽谷中的小获溪水九曲十八弯,碧水盈盈,流水潺潺;龙潭、师公潭潭水幽幽,宛如项链上的吊坠,幽深的峡谷,风景如诗如画。根据村民讲,在这一幽谷中,离八井村最近的有罗汉山、观音垵、狮坂、灯模山、对面山、平盖山、山罗盖、安折下等,灯模山后,剃刀梁下即为碗窑里废村,在那里,现建有县属的自来水厂和水电站,其后有剃刀梁、母发山头、岗头山、天山梁、白鹭坑等,再远些则为俗称“三十六炮”的连绵大山,它已在凤山镇的境内。在八井村畲民的观念中,所谓的“炮”,实指大山的峰峦,所以“三十六炮”即为36峰。八井村背靠双髻山,面对虎头山、大山座,这些山岭的走向均为东西向,它们西高东低,一直延伸到罗源湾海边。两条山脉之间,为罗源湾海积与小获溪冲积出来的平地。村民说:从西边的高山上鸟瞰,其地势为“五鲤朝天门”,民间也称这块谷地为“鲤鱼埠”。因此,八井村的东面是一眼可以望到罗源湾的一片较大的海积与冲积平地。原先八井村向东走两里地,就到了罗源湾海边,现由于县里围垦部分罗源湾作为经济开发区的用地,罗源湾已退到开发区的堤坝之外,因此,从八井延伸至海边的谷地现也与围垦形成的开发区连为一体。
八井村向东约一里地的山边,为小获行政村的罗厝里自然村,再继续往东一里地则为原在海边的小获、埭头店、桥下、新村下等自然村,它们在未围海修建开发区时,都散布在罗源湾的海边。小获村再向东一里多,为鹤屿,过去其为罗源湾中的小岛,现在因围海造陆作为罗源县的经济开发区,而成为围垦区中一部分,所以鹤屿与小获等过去的滨海村落现在可以由陆路交通。
1958年前,八井村到县城有两条路,一条是向北翻越双髻山到牛洋村,再到前房、吕洞、五里桥等地而达县城,这条路要翻山越岭,小路上上下下,崎岖不平。另一条路则先向东,经罗厝里、小获,然后沿着罗源湾边过芝堂前等村,在歧后村等处拐弯到吕洞,到五里桥,再到县城,这条路多沿着罗源湾海边走,比较平缓,但需要绕弯。现在则通公路,它是在沿海这条小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其从渡头到小获、北山一段为省道,而从小获经罗厝里到八井村的一段则为八井村的村公路。
八井村村公路是解放后该村几代领导班子在不同时期共同努力的结果。1958年以前,八井村只有一条小路通向村外;1958年4月,在“农村通大道,田头车子化”的号召下,时任大队支书雷志岳及其他村干部带领八井村群众在两个月之内修通了村公路,改善了当时的交通,也为现在的水泥路打下了路基。1984年,八井村在村支书雷信银、村主任雷志銮的组织下,从县民委争取到拨款,重新对路面进行了整修,使村公路的路面变得更宽、更平,改善了当时的交通条件。1996年,罗源县自来水公司在八井村投资建水厂,供全县城饮用水。2002年,由八井水厂投资将从小获村到八井水厂的一段村公路翻修成沥青路面。同时,村支书雷可华、村主任雷可木从2001年开始多方筹集经费,其中有民宗委的拨款5000元,水厂赞助20000元,开发区水电站赞助部分,于2002年把村子里的主干公路修成水泥路面。经过这次全面翻修,八井村的交通条件就更为方便了。只可惜从松山镇到小获村的那条被称为省道的公路坑洼不平,影响了周围乡村的交通条件。在松山镇,省道没有村道好,这是一大特色。不过据当地村民说,政府不久将要改造这条高低不平的省道了。
现在从八井到县城约有十公里,有一部分人经营的中巴专跑八井村,此外,从县城到北山的中巴,如果没有人到罗厝里或八井村,就不弯进去,但如果有八井村的乘客,往北山的中巴也会将他们送到八井村委会前,再原路返回到小获,再驶往最终目的地北山。所以,把这些专走八井村和附带也走八井村的中巴全计算在内,大约每隔半个多小时,就有一班中巴可以到八井村。此外,有时也有“面的”和摩托车载客。
二、八井村社会环境的变迁
在八井村的碗窑里、灯模山、对面山、平盖山山上的许多地方,现在还可以看到许多处由变形匣钵、瓷碗、瓷碟、瓷壶、灯架等的残片堆积的遗物裸露,它们都是古代瓷窑的遗址。根据《罗源县志》载:碗窑里窑址位于松山乡小获村碗窑里剃刀梁山脚下。窑址残片堆积层厚约0.5~1米。碗帮平直,座小露胎,表面灰白色,内底绘有卷云式、莲花式条纹或密而短的篦纹。经鉴定属宋代瓷窑。①然而,上述记载似乎有些错误,如碗窑里废村现属于八井村,而不是属于小获村。其次,其遗物也不止一种“直口碗”,而是有多种。其三,碗窑里出土的瓷器,不仅有宋代的,也有元、明、清的。因为1978年4月,国家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省博物馆考古组和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在罗源县作文物普查时,曾调查和鉴定了碗窑里等地所出土的遗物,他们发现的碗窑里出土物不仅有碗,还有碟、花瓶、灯架等瓷制品和匣钵等,年代不仅有南宋的,还有元代、明代、清代的。如敞口的偏绿色青瓷浅碗是南宋的,而青白色的小瓷碗则是明代以后的。
另外,据八井村民传说,在宋代以前,现双髻山、大山座之间的小获溪中下游冲积平地还是罗源湾的一部分,海水涨潮时,海船可以直接溯流到达八井村的碗窑里一带码头停泊。由于碗窑里一带有优质的、制瓷器用的高岭土资源,所以也就在这个有着优质高岭土的产地逐步形成制瓷业,陆续建造起许多瓷窑,烧制瓷碗等,并以此作为海上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海运大江南北和出口海外。
到明末清初间,碗窑里的制瓷业盛况空前,据称灯模山、对面山、平盖山的山坡上瓷窑林立;碗窑里村中,工棚、仓库、商店、住宅鳞次栉比,夹道而立,形成首尾约里许的一条街。从闽清、古田、宁德等地招聘来的瓷工汇集于此。其中有位来自古田的制瓷师傅名叫林东扬,他所制造的碗、瓮、瓶、杯等瓷器,纵使盛水结冰,也绝不会造成容器爆裂。因此,其制作的这种瓷器很受东北、华北等寒冷地区消费者的欢迎,经常有那里的瓷器商人前来采购,附载于本县运载“海纸”(即外运土纸)的巨型木帆船经罗源湾出口北上。那时,由于围垦如横埭,和河流淤积等的关系,海运码头已经转移到了小获埭头店村面对湾中小岛鹤屿的岸边。每逢夜潮,岸上船上灯火辉煌,路旁街口一箱箱的瓷器、一捆捆海纸堆积如山,装卸工肩挑背负忙个不停,海上瓷器、土纸贸易十分繁忙。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为了防止沿海民众对郑成功抗清军队的支持,颁布了“迁海令”,强迫包括碗窑里瓷村、八井村等在内苏、浙、闽、粤沿海的民众,离乡背井内迁30里以上,八井村畲民在这样的情况下,被迫迁徙到吕洞一带。碗窑里的瓷窑也被尽毁,制瓷工棚被烧光,人员内迁。到了康熙二十年(1681年),碗窑里瓷村、八井畲村等的民众才获准重返家园,瓷村的民众在废墟中重新建造起窑炉,招收瓷工,戳力经营,不数年就拥有瓷窑、制坯车间、成品仓库各6座(所)。在发展的高峰时,瓷工甚至达到400多人。这以后又持续经营了200多年,产品有青瓷大小碗、碟、瓶以及白瓷的高脚小碟、碗等。民国十七年(1928年)农历七月一日,老天连下三昼夜的暴雨,山洪暴发,并导致山崩,泥石流淹没了整个碗窑里,仅两户人家幸免于难,从此碗窑里瓷村终于一蹶不振,仅存废墟供后人凭吊。①
此外,据八井村畲民讲,八井村村名的来历主要有两种。一是因该地原有八口水井而得名,如祠堂厝边上有一口,雷志森家边上有一口,水井坊的路口有一口等。由于该地有这八口水井,所以该村才命名为八井村。一是由“陈伯井”这个地名转化来的。相传过去因碗窑里盛产瓷器,所以有许多人来此地讨生活,因此碗窑里的附近也逐渐建立起一些村落来。据说首先来现在八井村这里建立村落的为汉族的陈姓人家。他在此落脚后,挖了一口井,建立村落,后来人们就称此地为“陈伯井”。明代中晚期,畲族的先民才迁进来,以后慢慢发展,终于成了“陈伯井”村的主人,这以后再慢慢将“陈伯井”转化为“八井营”、“八井村”。然而,我们在村口的白马宫边上见到一块清代同治元年(1862年)刻的“盛世共享”石碑,它记录了嘉庆十年(1805年)一份县衙告示的内容。碑文中提到了现在八井所在地及附近几个村落的地名,如“本年七月二十三日,丁居小获铺地保罗为闻、畲总雷君侯、乡老辅灼、禁长明发、枝秀等词称,窃闻住居小获、陈拜井、横埭、竹里处,均系农民耕种田山。”其中出现的地名有小获铺和小获、陈拜井、横埭、竹里等几个村。除了“八井”写为“陈拜井”外,其余都与现代的名称相同。换言之,在嘉庆年间,八井被人称为“陈拜井”,而非“陈伯井”。其次,我们在八井村找到一些清代的土地买卖文书,其中有一份清代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文书记载:“王永茂原父手向雷君恒处承有屯田叁号,坐属小获地方土名陈八井及磘口仓埕,共栽租谷贰千觔大秤。”看来,“陈拜井”也以谐音简写成“陈八井”。由此可知,“陈伯井”、“陈八井”都是“陈拜井”的谐音,或音变。而《罗源县志》记载,在宋代,全县划为三个乡,17个里(隅),辖38图时,在现在的松山镇的范围中,就设有“拜井里”,并辖3图。明代洪武十四年(1381年)延续上述宋代的建制,只是改辖3图为辖2图;到了成化八年(1472年)又改为辖1图。清代“拜井里”的建制仍存在,只不过改“图”为“铺”,拜井里下辖有松山(包括上吕洞、下吕洞、牛洋、进山、歧前、树柄、歧后、马鞍、白柯等9个村落)、小获(包括小获、深港、芝堂前、横埭、罗厝里、陈拜井、碗窑里、陈厝头、林下尾、桥下、新村下、后山等12个村落)、大获(包括大获、山头、坑里、林里、下井洋、叶洋、下坑等7个村落)、泥田(包括泥田、迹头、可湖、泥港、白水5个村落)四个铺。
因此,根据以上各种点滴情况汇集起来看,在宋代,罗源县东部就有“拜井里”地名,宋代时期,现松山镇一带临海,有不少村落有码头、港口,既是海上贸易的繁荣地带,也由于是高岭土的产地之一而为制瓷业繁荣的地带,较大型的海船甚至可以溯小获溪流而上,直达制瓷业的中心碗窑里,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蠡测,宋代拜井里这个里社的所在村落,应在现在的八井一带。其最初应由陈姓居民开拓的,他们在那里挖井建房,形成村落,所以人们称该地为“陈拜井”,意为陈姓的“拜井”,而官方则把里社设于此,故称“拜井里”。明代成化年之后,畲民也迁入该村,他们也延续先人的称呼,称该村为“陈拜井”、“陈伯井”或“陈八井”。在这些变异中,“伯”、“八”应该都是“拜”之谐音。到了近代,才去掉“陈”字,简称为“八井”。简称为八井的时间,很可能是在20世纪初,因为我们在八井村发现一份宣统元年的土地文书上有:“雷坤照自己手置有右卫屯田壹号,坐属拜井里小获地方,土名八井,俗叫口口木臭下”的记载,根据此,我们大体可以推断,在宣统元年(1908年)前后,就已经开始有人称“陈拜井”为“八井”了。
综上所述,包括碗窑里在内的八井村这个地方,在宋代前后就已经十分繁荣,当时罗源湾到现在八井村、碗窑里的山脚下,八井村这里既是制瓷繁荣的工场,也是瓷器等贸易的码头与海港。但到了明清以后,由于小获溪的逐渐淤塞,地理环境发生了变迁。虽然,八井村的附近,因有高岭土的制瓷资源,仍然还是制瓷业繁忙的地方,但贸易的码头与海港则因溪流的淤塞而外迁到东面距八井村二里的小获村一带。1928年农历七月,由于连续3天暴雨导致的泥石流淹没了碗窑里后,八井村这里的制瓷业才寿终正寝,这个原本有过制瓷业的地方,才慢慢地变成了比较单纯的农业社会。
第一节 八井村行政隶属沿革
八井村所在的罗源县别号罗川,位于福建省东北部沿海,地处北纬26°23'~26°39'和东经119°07'~119°54'之间,面积有1081.2平方公里。辖6个镇、5个乡(含1个畲族自治乡),人口25.29万,其中畲族约两万多人,占全县人口的8%,罗源通行闽东方言福州土话中的罗源话,八井村畲族除了会讲罗源话外,在其内部还使用畲语。
在宋代,罗源县分为崇德、常熟、同乐3个乡,17个里(隅)。其中崇德乡辖县城及其附近地区。划东隅、西隅、南隅、北隅、新顺里、梅溪里、安金里、拜井里、善化里9个里(隅)。现松山镇所属的村落,除了北山、巽屿外,包括碗窑里、八井村在内的制瓷繁荣地带的其他村落都属于拜井里。元代沿用宋代制度,但分罗平、霍口、招贤、黄重各为上下2里,里(隅)数增至21个。但碗窑里、八井村等现在松山镇所属的村落仍属于崇德乡拜井里。
明代洪武十四年(1381年)撤乡的建制,改实行以里辖图制,仍保持有21里,但把霍口上下2里合并为1里,而把新丰里分为上下2里。永乐元年(1403年)裁去南隅、北隅和霍口,并把罗平上下2里合并为1里,罗源县的里数剩下17个。永乐十年(1412年)又裁去新顺和安金2里,罗源县剩下15里。天顺六年(1462年)裁掉罗平里,并把新丰上下2里合并为1里,同时,在善化里中增加1图,罗源剩下13里14图。成化八年(1472年),除了恢复罗平里外,还把新丰里改为上下里,并在善化里中增加1图,罗源县成了15里16图。万历年间(1573年~1619年)以成化八年形成的16图为16里,除了将善化2图改名为化一、化二,招贤2图改名为贤一、贤二,新丰2图改名为丰上、丰下,黄重2图改名为重上、重下外,其余均依原来的里名。尽管明代有如此多的变化,但松山镇内的这些村落如八井村等都属于拜井里。
清代罗源县仍沿用明代万历年间的划分,分为16里,但也有些变化,这个变化就是里下设铺,铺下辖村。在清代,现松山镇的几乎所有村落仍属于拜井里。当时的拜井里分松山、泥田、大获和小获四个铺。松山铺辖上吕洞、下吕洞、牛洋、进山、歧前、歧后、树柄、马鞍、白柯(白花)9个村落。泥田铺辖泥田、迹头、可湖、泥港、白水5个村。大获铺辖大获、山头、坑里、林里、下井洋、叶洋、下坑7个村落。小获铺辖小获、深港、芝堂前、桥下、新村下、陈厝头、林下尾、后山、罗厝里、陈伯井(八井)、横埭、碗窑里12个村落。而在乾隆年间,陈伯井曾一度属于化一里。
民国初,基本上沿袭清代的行政区划。民国二十年(1931年),罗源县分为5个区,其中第二区区公所驻地在碧里乡,其管辖29个乡镇,八井村属之。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九月,实行保甲制度,将5个区并为3个区,改区公所为区署。区以下设19个联保办事处,统辖166保。当时,第一区区署驻地为松山,下属9个联保。八井村和牛洋村属于第一区大小获联保竹里保。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改联保为乡镇,八井村属于第一区大小获乡的小获保。民国三十年(1941年)二月,新从连江县划入的巽屿、北山与大小获乡合并组成获巽乡。全县也改为2个区、1个县辖镇,12个乡。八井村属于第一区的获巽乡小获保。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二月,罗源把乡镇增设至19个,但八井村仍属于获巽乡小获保。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乡镇缩编为7个,松山乡和获巽乡合并为松获乡,公所驻地为大获村,下辖歧后、歧前、小获、大获、外剩、巽屿、北山、白湖、泥田9个保,八井村属于小获保。
1949年8月14日,罗源县解放。8月28日,县人民民主政府接管了旧政权的7个乡镇公所,建立了7个区人民民主政府,并沿用原乡镇名称,区以下仍保留保甲建制。八井村属于松获区小获保。1949年9月,将凤山、凤寿两区合并为第一区;洪林、河阳两区并为第二区;鉴碧、松获两区合并为第三区;福丰区则改为第四区。因此,八井村属于第三区小获保。
1950年3月,废除保甲制度。6月,增设第五区;9月,增设第六区,至此,全县划为6个区、64个乡和4个街。其中第一区包括白塔、南门外、歧余、松山、小获、大获、泥田、巽屿、北山、起步、长治、港头、兰田、桂林、护国15个乡,八井村属于小获乡。1952年4月,将松山等地增设为第七区,将洋头等地增设为第八区,乡镇也做了调整。这时的第七区辖有泥田、白水、松山、小获、大获、巽屿、北山7个乡。7月,县人民政府把八井从小获乡划分出来,单独成立一个乡,其辖有八井村、竹里村和横埭村等。1954年,又增设乡镇,第七区又增加了外洋、迹头、歧后、上杭4个乡。1955年8月,撤销第七区,并入第六区,9月,第六区改名为城关区,下辖八井、横埭、竹里的八井乡隶属城关区。1958年5月撤区并乡,八井乡被撤,八井村属于歧余区小获乡。
1958年9月大办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全县建立6个人民公社,98个生产大队。10月1日,八井高级社成为隶属城关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因公社用军队团的建制,故八井生产大队建制为八井营,下辖八井(一连)、横埭(二连)、竹里(三连)等村。1961年5月,恢复区一级建制,下辖几个人民公社。其次,增设人民公社至37个,缩小其各自的管辖范围。此时,八井大队隶属城关区小获人民公社。
1965年7月裁区并社,全县划分为城郊、松山、起步、洪洋、中房、西兰、飞竹、霍口、碧里、鉴江10个人民公社,原城关镇建制不变。1966年6月,城关镇改为城镇公社;城郊公社除划归松山、城镇公社的8个大队外,其余的15个大队另组成白塔公社,同年11月则更名为红塔公社。至此,全县划为11个人民公社。其中八井大队归属松山人民公社,仍管辖竹里、横埭村。
1984年9月,全县的人民公社都改为乡镇,各生产大队改为村,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从1990年以后,除了松山乡改为松山镇外,其所统辖的村落一直保持不变。其辖有北山、巽屿、外洋、剩头、大获、上杭、小获、八井、竹里、歧后、歧头、南歧、树柄、吕洞、前房、渡头、泥田、迹头、乘风、白水、上土港、下土港22个行政村;而在八井行政村中则有八井与牛洋两个自然村。①
第二节 族称演变
畲族主要集中分布在福建闽东地区,八井村的畲族多自称为“sanha”(山哈)。但“sanha”(山哈)的意思,各地的解释则有不同,有的地方如霞浦县崇儒乡的畲族认为:“sanha”(山哈)既是“山客”,也是“三吓”,前者的意思为居住在山里的客人、外地人;后者的意思为畲民有“怕抓、怕打、怕苦”“三怕”之意。②后者这种说法,可能是解放前在大汉族主义的歧视下而形成的一种解释。有的地方认为“sanha”(山哈)是“三合”,意指畲族蓝姓、雷姓、钟姓三者联合之意。罗源县八井村的畲民认为畲语的“哈”即是“客”,“山哈”指的就是“山客”,意思是居住在山中的客人或山里迁徙的客人,而没有或不代表其他意思。
有的地方的畲族也谦称自己为“小姓人”,而尊称汉族为“大姓人”;或者称自己为“三姓人”,称汉族为“百姓人”;或者在本族中互相称呼“zigeying”,即“自家人”、“自个人”、“自己人”,而称汉族为“holou”,即“华老(佬)”、“汉老(佬)”,在一些畲族的歌本中,“holou”也写作“阜老(佬)”、“河老(佬)”或“福老(佬)”。③
此外,在过去,有的地方的畲族也自称自己为“siha”,汉字可写成“食客”或“吃客”。畲族有的老人自己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忠勇王盘瓠帮助高辛皇帝征讨番邦有功劳,所以高辛皇帝恩准盘瓠忠勇王的子孙免纳粮税,免派徭役,可以傍山吃山,靠海吃海,走到哪里就可以吃到哪里,故有此自称。后来,由于汉族中有些人用这一称呼来污蔑、歧视他们的祖先好吃懒做,所以就逐渐弃之不用。①
还有,过去有的地方的畲族也自称自己为“瑶人”、“苗民”。在有些地方如霞浦县的有些畲民也自称自己为“畲家人民”,不过他们认为此“畲”字,应由“入田米”三个字组合而成为“畬”字,并自我认为这是汉顺帝赐封的,如霞浦县崇儒乡霞坪村保存的《汝南郡蓝氏宗谱》中的《释明畲字义》说:“汉顺帝时,有钟姓、雷姓官员同奏:盘、蓝、雷、钟四姓原是上古忠勇王功臣后裔,仕廊庙无不致身尽忠,农草野无不尽力耕作,高山无水之处,栽种奢禾,遇欠岁能济饥,请封名号。上准奏,旨谕:盘、蓝、雷、钟四姓,种奢禾济饥有功,山米助田米,就以入田米成一字,曰‘〓’,四姓子孙封曰‘〓家人民’。”②故有时他们也自称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实行的是民族平等政策。1952年7月,为了了解本省内的民族情况,福建省人民政府组织了民族调查组,在闽东地区调查,曾编写《畲族福安县仙岭洋村调查情况》等调查报考,对畲族的情况有初步的了解,并发现过去对畲族的称呼中有歧视现象。因此在1952年7~9月间,闽东各县都召开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各界人民代表都做出决议,统一以“少数民族”暂时作为畲族的代称,并严禁使用任何带有侮辱性的族称。受此影响,这以后,畲民也有自称“少数民族”的。如这次我们在八井村调查时,就常有人跟我们说:我们少数民族如何如何等。
目前政府法定的族称——畲族主要来自被称,但这种称呼也是诸多称呼中的一种。在历史上,汉族称畲族有多种称呼,如畲民、畲客、畲人、瑶民、畲瑶、苗夷、山民、棚民等。
对这些被称,八井村畲族同胞比较反感的是“畲民”、“畲人”等,因为,在闽东各地的方言中,“畲”的发音与“蛇”、“邪”的发音相近。在新中国建立前,闽东汉族中有些人恶意利用这种谐音曲解其义,有的甚至用侮辱性字眼编成顺口溜,对畲民横加歧视、欺凌、唾骂,并因此常挑起民族纠纷,故闽东地区有的畲族同胞如八井村的畲民认为“蛇族”、“邪族”是一种忌语。
1953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派出由中央民族学院、华东民政事务委员会和福建、浙江、广东省民政厅等人员组成的民族识别调查组,赴福建、浙江、广东等畲族地区进行识别调查。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的定义,结合我国民族的实际情况与历史情况,认为“畲民”的称谓出现得较早,有历史的基础;同时,“畲”字没有贬义,其为“三岁治田”或“烧榛种田”之意,民以“畲”命名,只说明他们是“山居为农”、“耕山而食”的善田者也。其次,民族识别调查组也尊重本民族人民的意愿和遵从“名从主人”的原则,即同一些畲族同胞进行了充分讨论与协商,最后确定用“畲族”这一称谓来命名,并确认畲族是一个具有自我特征的单一少数民族。1956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并正式公布确认:畲族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平等成员,从此,畲族就成为法定的族称,从根本上结束了历史上族称混乱的现象,也在某种程度增强了畲族内部的凝聚力。
然而,正因为在闽东方言中,“畲”字与“蛇”、“邪”谐音,历史上又常有以后两者称呼侮辱畲族的事件发生,所以,畲族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因此忌讳而不太愿意自称畲族,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还有人要求改变这一法定的族称。不过,由于民族政策的实施一步步深入和民族关系的根本改善,现在绝大多数畲族同胞都接受和拥护这一族称了,包括八井村的村民,他们也自豪地说,他们是畲族。
第三节 八井村畲族传说中的始祖
各地的畲族多认为他们是上古忠勇王盘瓠的子孙。盘瓠王和畲族几个主要姓氏祖先的传说,或保留在畲族同胞的记忆中,或保留在所谓记录历史记忆的族谱中。过去居住在八井村对面大山座山腰中,多与八井雷姓畲族通婚的树楼村蓝姓畲族的《蓝氏族谱》,其修于清代光绪十八年(1892年),其中的《敕书姓氏封》就记述了盘瓠的传说,其曰:“自昔盘古分天地,伏羲画八卦,造书契,神农艺五谷,尝百草,黄帝设井分州,调音律,备器用。爰乃高辛氏正宫德成刘帝后,此娄金星所由降生也。于是高辛在位四十五年五月初五,正宫皇后夜梦娄金星降凡,因是惊醒,陟然耳痛,宣令太医院调治,取出一物如蚕形,形样稀奇,以盘贮养,变为龙狗,金鳞珠点,眼光四射,颇会人言,帝见喜之,取名龙期,号曰盘瓠。时方平静,国家安宁,突有西番率党倡叛,行妖使术,无敢与敌,帝心忧虑,宣令有人退敌,许以三公主为婚,举朝默然,莫敢承命。龙期一见,进前折榜,啣奉帝前。帝命尔能成功,加封敕赐。龙期承旨,漂洋过海,历尽寒冰,直至西番。番王一见此兽,锦色奇形,因命纳在帐内,随从出入。一日番王集群臣欢乐畅饮,各已告退,王醉睡沉迷,夜半首级被龙期咬断,星夜攀城滚浪回朝,及番朝审觉,军前虎将万吉等统兵追赶,已无踪迹。龙期将番王首级跪献帝前,验其首无异,大喜曰:‘彼苍有灵,生此靖邦,天下定矣!’龙期谢恩,即请敕赐。帝悔前言,因以宫女谬称公主,赐以盘瓠为亲。龙期不悦,进入内宫,暗认公主,身隐望恩楼金钟下,期以七日夜成人完亲。已至六日,皇后私心窃视,身体以备,但头未成形。本是中幽北斗禄存刘隆星君脱化生,几助国安民,帝恩曩恩令既出,宜敕赐加封,即命群臣置酒笙歌,招龙期为驸马,敕封忠勇王,敕忠勇二大将军,左将军邓从成、右将军邹定施带领部众,听其差令。因准会稽山七弦洞优游林泉,并建王府,时御林军千余人护卫,举朝官员备酒饯送,给牒刊颁,永存为照者。诏下:驸马忠勇王除寇有功,给赐敕书,继世相传,长垂不朽,并赐世代免征差费,逢山逢田任其耕种,凡经过各省府州县,供奉夫役,支给俸薪,仰该部知悉,御旨敕书,统付刊颁存照。”还说:“驸马王生三男,长名自能,仍姓本姓盘;次男以蓝(篮)盛至殿前,因蓝为姓,赐名光辉;三男裹至殿前问姓,适雷鸣应声,因以雷为姓,赐名巨祐。帝以东夷贡三女长奇珍配盘自能,封为开混柱国侯;次奇珠配蓝光辉,封为护国侯;三奇配雷巨祐,封为武骑侯;盘瓠王生一女,名龙郎,匹配钟志清,与以敌勇侯之封,于斯时也。三株竞秀,百世流芳,螽斯衍庆,瓜瓞绵长矣。”
在八井村,据说还存有光绪年间修的《雷氏族谱》,然而,现不知流失在哪里,这次调查虽经多方查找,仍没能见到,甚是遗憾。不过,1958年从事福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当时的调查人员见过,他们根据《雷氏族谱》中的记载,概述了关于盘瓠王和畲族的来源,“在盘古开天辟地以后,出现个高辛皇帝,皇后刘氏耳痛三年,从耳中取出一虫,放在盘里养活。一日,虫变成一条龙,一说似麒麟。满身花斑,皇帝认为不祥,欲驱逐出去。大臣劝止,留在宫中饲养,取名盘瓠。当时有番王作乱,扰乱天下,皇帝出了告示说,如有打败番王者,赐三公主为妻,当时无人敢应,只有盘瓠撕下布告到皇帝面前,表示能收拾番王。于是盘瓠领旨跨海而去,到番王处约有三年,侍候番王,百顺百依。一日,盘瓠乘番王酒醉,取下番王头,奔回见皇帝,皇帝大喜,但不愿以三公主给盘瓠为妻,拟以一宫女代替,盘瓠不肯,竟以人语说:将我放在钟下,七日七夜变成人形,七日后,果然变成人。亦有六日后公主掀钟看,身已变人头未变好一说。和三公主成了亲,居住在深山中,共生三子一女。高辛皇帝赐姓,长子姓盘,次子姓蓝,三子姓雷,女儿嫁与钟姓为妻。此后,盘、蓝、雷、钟四姓为盘瓠后代,是为本民族起源。”①
从上述两篇记述看,虽细节上有些差异,如《蓝氏族谱》说高辛帝见到“龙期”“喜之”,盘瓠在金钟内变人时,是因刘皇后等不及偷看,而使“龙期”头没有变成人形;而雷姓族谱中所说,初见到“龙期”时,高辛帝认为不祥,后在大臣的劝阻下,才留下“龙期”饲养;另外,盘瓠在金钟中变人时不是刘皇后去看,而是三公主去掀钟观看,等等。然而,虽然有细节上的不同,但这些文字所表述的主题与社会记忆、历史记忆却都是基本一致的,即认为盘瓠是畲族的始祖,并以此为象征,作为团结畲族的唯一纽带。
尽管这些神话传说与其他地方畲族的传说基本一致,也具备上述的社会功能,但八井村雷姓在光绪年间重修族谱时,似乎也对谱中所刊载的这一民族来源的神话传说不以为然,他们在族谱中这样写道:“……今人见其妇女异妆音响殊俗而以为盘瓠之遗类者,毋乃谬乎?”②从而对这一有关其民族来源的传说表示了异议。
第四节 八井村畲族的源流
关于八井村畲族的源流,有着几种看法。首先根据《罗源县志》畲族篇迁徙一节记载,八井村雷姓畲族属于松山镇牛洋支派。该书说,牛洋支派的雷姓祖居广东潮州如东县,明弘治年间(1488年~1505年)入迁现松山镇牛洋村,并分衍八井村。清代顺治十八年(1661年)因迁界的缘故,分别迁吕洞、溪(即南洋)、尖山。康熙二十年复界回迁。其后裔分衍牛坪(现已废)、横埭、杨家里、经布岩等地。①这表明牛洋、八井、横埭、杨家里、经布岩、牛坪的雷姓畲族均出于同一来源,而且他们的始祖是在明成化年间先迁入罗源牛洋,以后再分衍八井,到了迁界结束后才分衍到横埭等地。不过,在这里,没有指出牛洋支派的始祖是谁。然而,在同一篇的武术一节中该书在介绍“八井拳”时说,“八井拳是在明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由雷居安、雷安和两兄弟传到牛洋村,其后裔迁居八井后逐渐出名,故称‘八井拳’。”②在这段话中,虽指出了牛洋支派两位先祖的名讳,但表述得比较含糊,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从其叙述中马上确定雷居安和雷安和就是牛洋支派的开基祖。因为其表述的是由两个人在成化年间把拳术传到牛洋村。因此,如果雷居安和雷安和不是牛洋村雷姓的开基祖的话,这段话可以理解为雷姓畲族在成化年间以前就早已经迁入牛洋,而在成化年间,由雷居安和雷安和这两个人把拳术传到牛洋村来。但是如果雷居安和雷安和的确是牛洋支派的开基祖的话,那么,牛洋这两位开基祖原本就懂得武术,所以当他们于成化年间迁入牛洋村时,也就自然而然地将武术技能带到牛洋村来。同时,也表明牛洋支派是在明代成化年间迁入罗源的。显然,这两段记载有着某些矛盾,即武术一节中所记载的时间,无论我们如何理解,它都要早于迁徙一节中所记载的年代。换言之,这两条记载中,有一条记载的始迁时间是错的。其次,这两条记载还有一个共同的弊病,即它们都没有把牛洋支派雷姓始祖的迁徙路线说得明白些。不过,如果我们综合上述两条记载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牛洋支派的雷氏畲族始祖始迁罗源的年代为弘治到成化年间,或者迁到牛洋为成化年间,而从牛洋分衍八井则是弘治年间。因为通常在一个地方,不会有同一支派的某个人来此开基后,又有一个同一支派的人再来开基一次的现象,所以宁可像上面那样理解,似乎可以比较顺理成章地得到解释。此外,综合上述记载看,牛洋支派的始祖应为雷居安与雷安和两人,他们先开基牛洋,其后裔分迁八井,迁界后,再迁横埭等地。
在这次田野调查中,我们从八井村畲民的记忆中了解到一些关于其祖先来源与迁徙的情况。根据八井村畲民的口述,其开基祖为雷安居与雷安和,这与《罗源县志》中“雷居安”的说法有些不同。他们祖居广东潮州凤凰山,先迁居兴化府的莆田,而后又迁居罗源县白花,接着又迁牛洋(吾洋、五羊),然后又迁居现起步镇的白岩,接着又迁回牛洋定居,定居以后,再从牛洋迁到八井村,在八井形成福、禄两房,后来又有人从八井村迁居到横埭。换言之,安居与安和迁徙来迁徙去,最后定居在牛洋,并在此开基散叶,然后,分迁八井,在八井形成福、禄两房,以后,又有人迁到横埭去,故横埭现既有福房的人,又有禄房的人。
然而,1958年,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八井调查后所写的报告说:“分布在八井、横埭的雷姓畲族,传说祖先在广东潮州,后迁入福建兴化的莆田一带,明朝成化年间迁至罗源,先住在罗源城西南的笔架山,后迁至八井一带,最初分福、禄两房,福房住在牛洋、八井,禄房住在横埭。传说来到这里已经住了十一代。”①换言之,根据这样的说法,八井、牛洋、横埭的雷姓畲族始祖在成化年间先迁入的是八井一带,而不是牛洋。其分为两房,八井、牛洋均为福房,而横埭的则为禄房。看来与《县志》和现在八井畲民的口传又有不同。
在这次调查中,通过口头调查和早期土地买卖文书、墓碑文字等的验证,我们了解到八井畲村的字辈似乎有两个系统,第一为“安—邦—民—飞—永—君—子—辅—朝—廷—乾—坤—志—信—可—知—贤”,第二为“安—邦—民—飞—永—君—子—辅—枝—大—向—章—传—世—德—恒—开”。从这两个系统中,我们可以看到“安”字辈都是八井雷氏的第一代,因此安居或居安与安和的确是牛洋、八井雷氏的开基祖。
在调查中,我们也看到,现八井村确实有两个房头,福房的祠堂已破烂不堪,但还屹立在祠堂厝那里。原先禄房的祠堂现已不见踪影,但禄房的派下现在当中厝祠堂原址上,建了一间三面墙的小屋来摆放祖先牌位等。而且从这两房的人取名的情况看,两房的人多数都以第一系统的字辈来取名;而福房中的有些人则用第二系统来取名,如德明、德育等,并且其儿子辈的人又用第一系统来取名,如德明的儿子叫知文,德育的儿子叫知钦,孙子叫贤华、贤斌。
我们还看到,八井雷姓与横埭的雷姓关系密切些,而与牛洋的雷姓似乎关系疏远些,即牛洋的雷姓都不属于八井的福、禄两房,他们另为一房支。这表明,八井雷姓与牛洋雷姓在比较早期就已经分支了,而与横埭雷姓则互相纠缠不清,即横埭雷姓即有八井福房的人,也有八井禄房的人,所以与八井的福、禄两房关系都比较近。
由此看来,1958年调查时所说的牛洋与八井为福房,而横埭为禄房的说法似乎与现存的实际不同。其次,《县志》中所说的开基祖的后裔再迁八井的说法也有问题,因为,如果这样,那么牛洋支派福、禄两房应该是从居安与安和两人算起,这两房应该在牛洋形成,而后他们的派下人迁到八井,这才导致八井形成福、禄两房,然而,八井雷姓似乎与牛洋雷姓关系都不密切,因此,事实似乎与《县志》所说的也有差异。
因此,综合上述种种情况加以建构的话,我们认为,比较合理的雷姓畲族牛洋支派的宗族变迁应该是:成化年间,居安与安和开基牛洋,并在牛洋形成两房。到弘治年间或者后来,安和迁徙八井村,是为八井的开基祖,并在其派下中形成了八井的福、禄两房。清初的迁界,八井畲民迁居吕洞等处,康熙二十年复界,八井畲民回迁后,福、禄两房中均有人再迁徙横埭,并发展至今。所以,才会形成八井福、禄两房的雷姓与牛洋雷姓的疏远,与横埭雷姓比较亲近的现象。否则,则有许多地方解释不通。
第五节 八井村概况
一、八井村的自然与社会环境
八井村位于小获溪的中游地带,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其老村背靠双髻山,海拔60~75米,有祠堂厝、墘头厝、打石厝、当中厝、水井巷等角落,福房的祠堂在祠堂厝,禄房的简陋祠堂在当中厝,老村东边通往公路的村口则有白马王庙;新村位于山脚下海拔7~10米的谷地上,有七斗洋、铁厂、新厝等几个角落。畲族小学建在小获溪汊流形成的溪坂上。新村的南边隔着小获溪为竹里行政村的横埭畲村,其村后为虎头山、大山座、荔枝栏、狮山等山,大山座的山脚下过去有一个名叫树楼的小村落,但现在已成遗址。翻过虎头山则为竹里村。八井村的西边为由层层叠叠的小山与大山构成的狭窄谷地,其两旁有连绵不断的层层山岭,幽谷中的小获溪水九曲十八弯,碧水盈盈,流水潺潺;龙潭、师公潭潭水幽幽,宛如项链上的吊坠,幽深的峡谷,风景如诗如画。根据村民讲,在这一幽谷中,离八井村最近的有罗汉山、观音垵、狮坂、灯模山、对面山、平盖山、山罗盖、安折下等,灯模山后,剃刀梁下即为碗窑里废村,在那里,现建有县属的自来水厂和水电站,其后有剃刀梁、母发山头、岗头山、天山梁、白鹭坑等,再远些则为俗称“三十六炮”的连绵大山,它已在凤山镇的境内。在八井村畲民的观念中,所谓的“炮”,实指大山的峰峦,所以“三十六炮”即为36峰。八井村背靠双髻山,面对虎头山、大山座,这些山岭的走向均为东西向,它们西高东低,一直延伸到罗源湾海边。两条山脉之间,为罗源湾海积与小获溪冲积出来的平地。村民说:从西边的高山上鸟瞰,其地势为“五鲤朝天门”,民间也称这块谷地为“鲤鱼埠”。因此,八井村的东面是一眼可以望到罗源湾的一片较大的海积与冲积平地。原先八井村向东走两里地,就到了罗源湾海边,现由于县里围垦部分罗源湾作为经济开发区的用地,罗源湾已退到开发区的堤坝之外,因此,从八井延伸至海边的谷地现也与围垦形成的开发区连为一体。
八井村向东约一里地的山边,为小获行政村的罗厝里自然村,再继续往东一里地则为原在海边的小获、埭头店、桥下、新村下等自然村,它们在未围海修建开发区时,都散布在罗源湾的海边。小获村再向东一里多,为鹤屿,过去其为罗源湾中的小岛,现在因围海造陆作为罗源县的经济开发区,而成为围垦区中一部分,所以鹤屿与小获等过去的滨海村落现在可以由陆路交通。
1958年前,八井村到县城有两条路,一条是向北翻越双髻山到牛洋村,再到前房、吕洞、五里桥等地而达县城,这条路要翻山越岭,小路上上下下,崎岖不平。另一条路则先向东,经罗厝里、小获,然后沿着罗源湾边过芝堂前等村,在歧后村等处拐弯到吕洞,到五里桥,再到县城,这条路多沿着罗源湾海边走,比较平缓,但需要绕弯。现在则通公路,它是在沿海这条小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其从渡头到小获、北山一段为省道,而从小获经罗厝里到八井村的一段则为八井村的村公路。
八井村村公路是解放后该村几代领导班子在不同时期共同努力的结果。1958年以前,八井村只有一条小路通向村外;1958年4月,在“农村通大道,田头车子化”的号召下,时任大队支书雷志岳及其他村干部带领八井村群众在两个月之内修通了村公路,改善了当时的交通,也为现在的水泥路打下了路基。1984年,八井村在村支书雷信银、村主任雷志銮的组织下,从县民委争取到拨款,重新对路面进行了整修,使村公路的路面变得更宽、更平,改善了当时的交通条件。1996年,罗源县自来水公司在八井村投资建水厂,供全县城饮用水。2002年,由八井水厂投资将从小获村到八井水厂的一段村公路翻修成沥青路面。同时,村支书雷可华、村主任雷可木从2001年开始多方筹集经费,其中有民宗委的拨款5000元,水厂赞助20000元,开发区水电站赞助部分,于2002年把村子里的主干公路修成水泥路面。经过这次全面翻修,八井村的交通条件就更为方便了。只可惜从松山镇到小获村的那条被称为省道的公路坑洼不平,影响了周围乡村的交通条件。在松山镇,省道没有村道好,这是一大特色。不过据当地村民说,政府不久将要改造这条高低不平的省道了。
现在从八井到县城约有十公里,有一部分人经营的中巴专跑八井村,此外,从县城到北山的中巴,如果没有人到罗厝里或八井村,就不弯进去,但如果有八井村的乘客,往北山的中巴也会将他们送到八井村委会前,再原路返回到小获,再驶往最终目的地北山。所以,把这些专走八井村和附带也走八井村的中巴全计算在内,大约每隔半个多小时,就有一班中巴可以到八井村。此外,有时也有“面的”和摩托车载客。
二、八井村社会环境的变迁
在八井村的碗窑里、灯模山、对面山、平盖山山上的许多地方,现在还可以看到许多处由变形匣钵、瓷碗、瓷碟、瓷壶、灯架等的残片堆积的遗物裸露,它们都是古代瓷窑的遗址。根据《罗源县志》载:碗窑里窑址位于松山乡小获村碗窑里剃刀梁山脚下。窑址残片堆积层厚约0.5~1米。碗帮平直,座小露胎,表面灰白色,内底绘有卷云式、莲花式条纹或密而短的篦纹。经鉴定属宋代瓷窑。①然而,上述记载似乎有些错误,如碗窑里废村现属于八井村,而不是属于小获村。其次,其遗物也不止一种“直口碗”,而是有多种。其三,碗窑里出土的瓷器,不仅有宋代的,也有元、明、清的。因为1978年4月,国家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省博物馆考古组和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在罗源县作文物普查时,曾调查和鉴定了碗窑里等地所出土的遗物,他们发现的碗窑里出土物不仅有碗,还有碟、花瓶、灯架等瓷制品和匣钵等,年代不仅有南宋的,还有元代、明代、清代的。如敞口的偏绿色青瓷浅碗是南宋的,而青白色的小瓷碗则是明代以后的。
另外,据八井村民传说,在宋代以前,现双髻山、大山座之间的小获溪中下游冲积平地还是罗源湾的一部分,海水涨潮时,海船可以直接溯流到达八井村的碗窑里一带码头停泊。由于碗窑里一带有优质的、制瓷器用的高岭土资源,所以也就在这个有着优质高岭土的产地逐步形成制瓷业,陆续建造起许多瓷窑,烧制瓷碗等,并以此作为海上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海运大江南北和出口海外。
到明末清初间,碗窑里的制瓷业盛况空前,据称灯模山、对面山、平盖山的山坡上瓷窑林立;碗窑里村中,工棚、仓库、商店、住宅鳞次栉比,夹道而立,形成首尾约里许的一条街。从闽清、古田、宁德等地招聘来的瓷工汇集于此。其中有位来自古田的制瓷师傅名叫林东扬,他所制造的碗、瓮、瓶、杯等瓷器,纵使盛水结冰,也绝不会造成容器爆裂。因此,其制作的这种瓷器很受东北、华北等寒冷地区消费者的欢迎,经常有那里的瓷器商人前来采购,附载于本县运载“海纸”(即外运土纸)的巨型木帆船经罗源湾出口北上。那时,由于围垦如横埭,和河流淤积等的关系,海运码头已经转移到了小获埭头店村面对湾中小岛鹤屿的岸边。每逢夜潮,岸上船上灯火辉煌,路旁街口一箱箱的瓷器、一捆捆海纸堆积如山,装卸工肩挑背负忙个不停,海上瓷器、土纸贸易十分繁忙。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为了防止沿海民众对郑成功抗清军队的支持,颁布了“迁海令”,强迫包括碗窑里瓷村、八井村等在内苏、浙、闽、粤沿海的民众,离乡背井内迁30里以上,八井村畲民在这样的情况下,被迫迁徙到吕洞一带。碗窑里的瓷窑也被尽毁,制瓷工棚被烧光,人员内迁。到了康熙二十年(1681年),碗窑里瓷村、八井畲村等的民众才获准重返家园,瓷村的民众在废墟中重新建造起窑炉,招收瓷工,戳力经营,不数年就拥有瓷窑、制坯车间、成品仓库各6座(所)。在发展的高峰时,瓷工甚至达到400多人。这以后又持续经营了200多年,产品有青瓷大小碗、碟、瓶以及白瓷的高脚小碟、碗等。民国十七年(1928年)农历七月一日,老天连下三昼夜的暴雨,山洪暴发,并导致山崩,泥石流淹没了整个碗窑里,仅两户人家幸免于难,从此碗窑里瓷村终于一蹶不振,仅存废墟供后人凭吊。①
此外,据八井村畲民讲,八井村村名的来历主要有两种。一是因该地原有八口水井而得名,如祠堂厝边上有一口,雷志森家边上有一口,水井坊的路口有一口等。由于该地有这八口水井,所以该村才命名为八井村。一是由“陈伯井”这个地名转化来的。相传过去因碗窑里盛产瓷器,所以有许多人来此地讨生活,因此碗窑里的附近也逐渐建立起一些村落来。据说首先来现在八井村这里建立村落的为汉族的陈姓人家。他在此落脚后,挖了一口井,建立村落,后来人们就称此地为“陈伯井”。明代中晚期,畲族的先民才迁进来,以后慢慢发展,终于成了“陈伯井”村的主人,这以后再慢慢将“陈伯井”转化为“八井营”、“八井村”。然而,我们在村口的白马宫边上见到一块清代同治元年(1862年)刻的“盛世共享”石碑,它记录了嘉庆十年(1805年)一份县衙告示的内容。碑文中提到了现在八井所在地及附近几个村落的地名,如“本年七月二十三日,丁居小获铺地保罗为闻、畲总雷君侯、乡老辅灼、禁长明发、枝秀等词称,窃闻住居小获、陈拜井、横埭、竹里处,均系农民耕种田山。”其中出现的地名有小获铺和小获、陈拜井、横埭、竹里等几个村。除了“八井”写为“陈拜井”外,其余都与现代的名称相同。换言之,在嘉庆年间,八井被人称为“陈拜井”,而非“陈伯井”。其次,我们在八井村找到一些清代的土地买卖文书,其中有一份清代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文书记载:“王永茂原父手向雷君恒处承有屯田叁号,坐属小获地方土名陈八井及磘口仓埕,共栽租谷贰千觔大秤。”看来,“陈拜井”也以谐音简写成“陈八井”。由此可知,“陈伯井”、“陈八井”都是“陈拜井”的谐音,或音变。而《罗源县志》记载,在宋代,全县划为三个乡,17个里(隅),辖38图时,在现在的松山镇的范围中,就设有“拜井里”,并辖3图。明代洪武十四年(1381年)延续上述宋代的建制,只是改辖3图为辖2图;到了成化八年(1472年)又改为辖1图。清代“拜井里”的建制仍存在,只不过改“图”为“铺”,拜井里下辖有松山(包括上吕洞、下吕洞、牛洋、进山、歧前、树柄、歧后、马鞍、白柯等9个村落)、小获(包括小获、深港、芝堂前、横埭、罗厝里、陈拜井、碗窑里、陈厝头、林下尾、桥下、新村下、后山等12个村落)、大获(包括大获、山头、坑里、林里、下井洋、叶洋、下坑等7个村落)、泥田(包括泥田、迹头、可湖、泥港、白水5个村落)四个铺。
因此,根据以上各种点滴情况汇集起来看,在宋代,罗源县东部就有“拜井里”地名,宋代时期,现松山镇一带临海,有不少村落有码头、港口,既是海上贸易的繁荣地带,也由于是高岭土的产地之一而为制瓷业繁荣的地带,较大型的海船甚至可以溯小获溪流而上,直达制瓷业的中心碗窑里,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蠡测,宋代拜井里这个里社的所在村落,应在现在的八井一带。其最初应由陈姓居民开拓的,他们在那里挖井建房,形成村落,所以人们称该地为“陈拜井”,意为陈姓的“拜井”,而官方则把里社设于此,故称“拜井里”。明代成化年之后,畲民也迁入该村,他们也延续先人的称呼,称该村为“陈拜井”、“陈伯井”或“陈八井”。在这些变异中,“伯”、“八”应该都是“拜”之谐音。到了近代,才去掉“陈”字,简称为“八井”。简称为八井的时间,很可能是在20世纪初,因为我们在八井村发现一份宣统元年的土地文书上有:“雷坤照自己手置有右卫屯田壹号,坐属拜井里小获地方,土名八井,俗叫口口木臭下”的记载,根据此,我们大体可以推断,在宣统元年(1908年)前后,就已经开始有人称“陈拜井”为“八井”了。
综上所述,包括碗窑里在内的八井村这个地方,在宋代前后就已经十分繁荣,当时罗源湾到现在八井村、碗窑里的山脚下,八井村这里既是制瓷繁荣的工场,也是瓷器等贸易的码头与海港。但到了明清以后,由于小获溪的逐渐淤塞,地理环境发生了变迁。虽然,八井村的附近,因有高岭土的制瓷资源,仍然还是制瓷业繁忙的地方,但贸易的码头与海港则因溪流的淤塞而外迁到东面距八井村二里的小获村一带。1928年农历七月,由于连续3天暴雨导致的泥石流淹没了碗窑里后,八井村这里的制瓷业才寿终正寝,这个原本有过制瓷业的地方,才慢慢地变成了比较单纯的农业社会。
附注
①参见《罗源县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56~72页
②《福建省霞浦县崇儒公社畲族调查报告》(油印本),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等1983年编印。
③《霞浦县畲族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46页。
① 《福建省霞浦县崇儒公社畲族调查报告》(油印本),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等1983年编印,5页。
② 《福建省霞浦县崇儒公社畲族调查报告》(油印本),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等1983年编印,6页。
①《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119页。
②《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119页。
①《罗源县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889页。
②《罗源县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899页。
①《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118~119页。
①《罗源县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842页。
①陈承群:《罗源陶瓷业琐记》,《罗源文史资料》第七辑(1996年),9~10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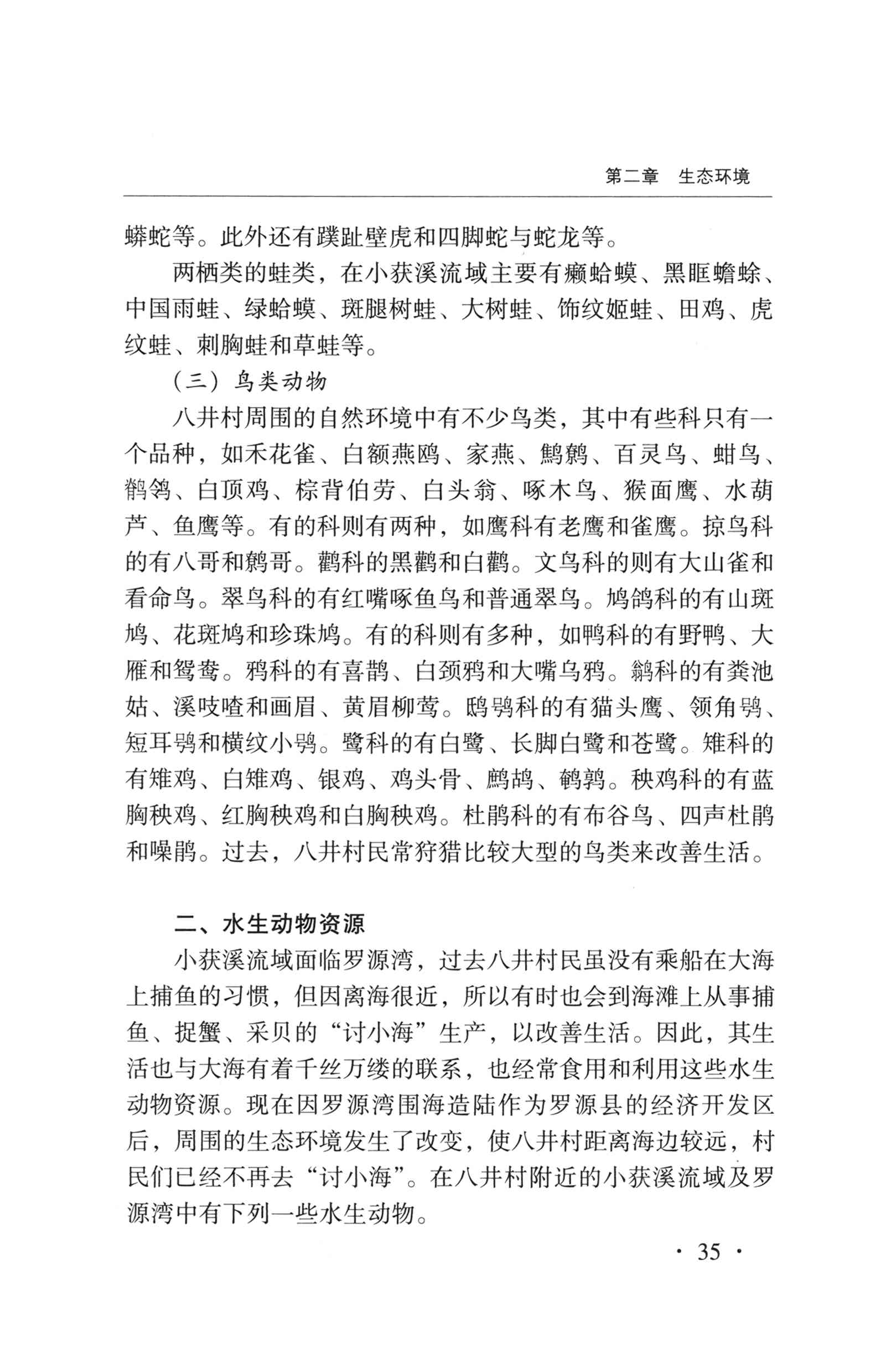
《畲族福建罗源县八井村调查》
出版者:云南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对福建省罗源县八井村畲族的调查,依次介绍了其概况与历史、生态环境、经济、人口、婚姻家庭、宗族、社区管理、法律、民居建筑、风俗习惯、口传文化、教育等。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