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近代以来畲汉族群边界的再造
| 内容出处: |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图书 |
| 唯一号: | 130920020230003827 |
| 颗粒名称: | 四、近代以来畲汉族群边界的再造 |
| 分类号: | K288.3 |
| 页数: | 7 |
| 页码: | 258-264 |
| 摘要: | 本文探讨了近代以来畲汉族群边界的再造过程。在明清时期,畲民逐渐融入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特征与周边汉族相似。 |
| 关键词: | 畲族 民国时期 民族同化 |
内容
明清以后,定居后的畲民慢慢地融入当地社会,其经济、文化等特征越来越多地与周边汉族没有太大差别。清代至民国,文献对各地畲民记载呈现出减少的趋向,本身也表明了各地畲汉族群边界有移动和消失的迹象。
在民国时期,官方对福建等地的畲民统称为“苗民”或“苗族”,这种族称的转变与当时政府的民族思想与民族政策是分不开的,同时与清末以后的民族主义思潮不无关系。
清末民初,在巨大的民族危机下,许多知识分子寻求“国族”建构,如梁启超提出史学的任务就是要激发民众的国家意识,①“炎黄子孙”“黄帝世胄”“五族统一”成为当时的流行话语。政府和一些学者主张“同化”(所谓的“五族统一”即是该思想的表现),认为“少数民族”的调查和研究不能“刺激国族分化”,因此,当时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主要是以“安边”“治边”为要的“边政”研究。②
这种“五族统一”“五族共和”的思想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颇为流行,在民国初期修纂的畲族族谱中体现了这种思想。如上杭《雷氏梓福公家谱》在“凡例”中写道:“此谱议修于光复前一年,购工庀材,择吉开雕,越十有五月而告成。五族适于是年统一,是此谱诚为民国成立一大纪念,故于卷首敬刊国旗,用志盛事。”③一些接受新思想的畲族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在族谱中宣扬“五族共和”思想,如上杭雷氏第十九代裔孙雷熙春、雷晓春在“序”中称:
岁辛亥(1911年,笔者注),吾族有修谱之举……且此谱之作与民国之成立固有绝大关系者。吾族得姓实在黄帝纪元之世,源流最古。远祖方雷氏佐黄帝南征北伐,纯然民族主义,功德留荫,历世已四千六百余年,虽期间丧乱频仍,叠经变故,而忠孝节义之士犹复昶望于史册。方吾一世祖梓福公之生也,当赵宋末造,时适胡元入主中夏,窃据神器,因挚眷避地卜居于此,优游金山摺水间者九十载。追明太祖定鼎金陵,汉族光复,始考终牗下。迄明、清二代,族中科名仕宦于今为盛,而士大夫博学识能文章者,先后修谱两次,曾未昌言民族主义。为详考吾族得姓之缘,纪以志诸谱牒,知其慑服于专制余威者为已殁矣。乃者五族统一,政更共和,举黄帝手定之锦绣河山悉以还诸黄帝世胄,而此谱适于是年秋月以成。由是濡毫吮墨,畅所欲言,俾吾祖吾宗萦抱民族思想,得于序录中表白一二。①
该序描述了黄帝征伐异族、胡元入主中夏、明代汉族光复、民国政更共和等历史事件,反映的是清末民初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想,这种社会思潮经知识分子的宣传慢慢渗透到一般家族中,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民国元年,上杭雷赞明在“序”中称“今民国新立,治尚共和,神明之胄四万万皆同胞矣。”雷庭瑞在《重修梓福公新谱告成序》也称:“今岁五月开局编印,新谱告成值民国新纪元,谨进一言以志盛举。曰,共和成立,五族大同,汉满蒙回藏为一家,是亲爱家族之观念尤当推而远之,不仅在一姓一族也。五族者千万姓之所积,人人各亲爱其同姓,思扶掖而促进之,知非保五族则一族姓不能独立,于是互相扶掖,互相促进,此爱同胞、爱祖国者所不能违之公例也。”②
当时国民政府主张民族同化,鼓励边疆非汉人群汉化。在这种民族政策的指导下,官方并未将分布在福建等地区的畲民视为一个比较独立的、具有政治意义的民族,而是笼统地以苗族称之。实际上,关于对南方民族以“苗”“瑶(徭)”等族称泛称,在明清以前十分常见,这大概类似于更早之前,中原王朝将南方地区的族群泛称为“蛮”“越”“獠”等。应该来讲,这些族群内部存在较大差异,族群间具有一定的族群边界,如“越”又称“百越”,足以说明各个地区的族群是有一定区别的人群集团。将这些族群泛称为“蛮”“越”等,说明对于华夏族而言,或者是由于族群的接触与认识还不够,无法对这些族群内部的差别进行更详细地分,或者即使其群体内部有一些区别,但在华夏族心目中,这些差异可以忽略不计。即在“华夷之辨”的语境中,所谓的“蛮”“越”“苗”等无非是作为“华”的对立面而存在,二者形成了“文明”—“野蛮”的文化政治结构。杨志强在分析近代苗族形成问题时指出,明清以后,常将“苗”“苗种”作为南方各省非汉系族群的泛称,而“作为一种汉民族对于异族的称谓,这里所说的‘种’代表的是一种‘华’与‘夷’区别的模糊的文化境界,而并不是现今意义上所看到的‘种族’或‘民族’。”①
在民国时期,福建各地的畲民在官方上被称为“苗族”,如1937年《各县区苗夷民族概况》描述了连江、福鼎、顺昌三地“苗夷民族”情况,这些“苗夷民族”实际上多为畲民,其中连江有23个畲民村落,主要是迁徙自漳浦蓝、雷畲民,这些畲民在女子服饰上具有与汉族不同的装束特征,“清初与汉人通婚,在咸丰时代,苗族生活颇裕,中有田租收至三千余担者,今则已衰落。”到民国时代畲民业已与汉人同化。②
成立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山民会馆(后改为三明会馆),是闽东浙南“山民”联络议事之所。1946年,闽东畲族宗人商议重兴三明会馆,蓝玉轩等向所在地霞浦县政府提交申请报告,业经县长刘仇签署,呈报省政府核准在案,成为官方〓册认定的“苗夷民族”(按当时《福建年鉴》之称)“公益团体组织”。③由此可见,当时的闽东畲民被官方认定为“苗夷民族”,而不被认为是“畲族”。
1947年12月8日《福建省政府关于送边疆民族及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状况调查表给内政部电》关于苗族连江、罗源、顺昌、漳平、周宁等县,人口也相应增加。同时在注明备考注明:“苗族俗称畲民,间有与汉人同化者。”④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30—40年代,政府也将水上居民(疍民)作为“边疆民族及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上报国家有关部门。⑤苗族作为畲族的称呼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年时间还在官方的报告中出现,如1952年7月8日写成的《畲族福安县仙岭洋村调查情况》中,认为国民党大汉族主义进行民族压迫、歧视和侮辱,故意歪曲其历史,而另一方面,畲族限于文化,对本民族历史也不甚了解,“只认为苗民称号较臭畲人(臭蛇人)好,这是畲族改称苗族之始。”又称:
解放后来自北方干部,过去接触少数民族不多,对当地畲族未曾详尽调查,了解该民族历史,以及民族特征,只因他们语言不同,妇女装饰奇异,居住高山,称之苗民……在国民党大汉族主义消灭同化政策压迫下,曾经强迫改变民族服装,于民国十二三年间改穿汉服,藉以躲避欺视,不易辨别他们是畲民。女的虽略有改变,但仍然保持民族装饰。①
1952—1953年,漳平县、闽侯县提交的报告也均把本地畲民称为“苗族”②。1953年12月9日,在一份由福安地委统战部提交的报告中,还显示了当地畲民对于要将本族命名为“畲族”存在不满的情绪。报告称当时畲民有“苗族”“瑶族”“山宅”“三民”等名称,但畲民本身不承认自己为“畲族”,原因主要是历代反动统治(国民政府采取的是同化政策)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残存的民族隔阂没有彻底消除,加上当时南下干部不了解情况称畲民为“苗族”,福安地委统战部根据1951年在福安仙岩乡从该族家谱调查后认为“畲族”名称是正确的,这引起了当时畲族百姓的反对。③直到1956年9月9日《中共福安县委统战部关于少数民族名称问题的报告》仍坚持不使用畲族这个民族称号。④随着1956年中央统战部下发《关于确定畲民民族成分问题》,关于畲民名称的争论才渐渐停息下来。⑤并在1956年12月8日经中共中央统战部最后确定畲族的民族成份和民族名称。⑥至此,畲族作为一个族称在国家的政策下推行,而关于畲族的民族认同的过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闽西南一些地区接受程度较快,①而闽东一些地区则经历较长一段时间磨合,才最终接受,如在确定族称的两年多以后的1958年10月1日的《宁德县南山片畲族调查报告》仍在讨论畲族民族名称的几个来源与畲民态度。②1958年10月5日的《罗源县苗民情况报告》仍将畲族称为苗民③。而一些地区,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对畲民族称表示不满。④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称畲民为“苗民”与国民党政府的民族政策有一定关系,另外一些因畲汉矛盾给畲民带来情感伤害的地区,也希望用“苗族”等泛称替代原来被标签化了的“畲”族。笔者大胆推论,假如没有后来学术界的努力和国家政策的推行,部分畲民将可能被官方划分为“苗族”,也有可能在提倡“五族共和”以及民族同化的政策下,更多的畲民走向汉化,从而导致族群意识不彰显。正如疍民融入汉人之中,而在此之前,畲、疍均作为福建地区比较特殊的族群一并被论述⑤。当然,历史无法推论。在新中国民族政策的推行下,地方政府、学术界、各地的畲民(或疑似畲民)精英参与了新的族群边界的制造。
就国家和学术界而言,他们希望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标准来开展民族识别、民族身份恢复工作。民族学者施联朱参加了畲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他在《解放以来畲族研究综述》指出,“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为畲族识别工作重要因素。”①并强调不能单以民族姓氏定民族成分,他说:“我们说畲族主要有盘、蓝、雷、钟四大姓,不等于说四大姓全是畲族,姓氏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共同体,而民族则是以地缘为基础的人们共同体,把姓氏视为民族特征的主要标志之一,是错误的。”②
这种看似科学的民族识别标准却不能完全解决民族识别和民族恢复中的实际困难如何判断一个地方族群的民族特点是否足以被认定为畲族,需要当地族人支持与材料证明、地方政府的调研与申报以及相应政府部门审批与认定。但如果在一些地方原畲民住区的居民对被认定为畲族热情不高,或者当地民族部门投入不足,或者国家认定族群身份根据上报材料与若干调研,其中也不能保证完全做到十分客观。因此,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在族谱记载中有较为亲近血缘关系的姓氏,存在着一个地方宗姓被认定为畲族,而另一个地方宗姓却未被认定为畲族的情况。③
但是,在族群认同工具主义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的地区人群为能被确认为畲族而努力。1964年9月5日《福安专署关于政和、松溪少数民族称谓问题的调查报告》说明了政和县雷姓族人要求恢复畲族族称的由来,该文写道:
政和县雷华泉于1953年参加建阳专区少数民族代表会,体会到党的民族政策的英明:1963年他堂兄雷成寿从建阳籍到政和来谈起有关历年来闽北地区党对畲族人民的关怀以及闽东地区民族工作情况,他们得到很大启发,所以积极要求恢复族称。松溪县畲族曾向区里要求解决族称问题。①
从这份报告,可以看出政和县雷华泉通过了解国家的民族政策积极要求恢复族称,族群内部精英的运作使得该地区的畲民得以确认为畲族的政治身份。
近年来的一些研究也证明,一些畲民为了被确定畲族的政治身份,不断对本民族的历史进行重构。如周大鸣在赣南地区田野调查中发现,一些原属客家的蓝、雷、钟姓在20世纪80年代恢复成畲族后进行族群重构,他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恢复成赣南畲族的族谱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在1985年以前的族谱中,每一次族谱的序言有一个逐步‘汉化’‘正统化’的过程,受‘大传统’影响的烙印不断明显。而1985年后修的族谱则是‘畲化’的过程,透过这些‘精英文化’的变化历程,可以再现一个族群的变迁。”②杨晋涛在研究闽西蓝姓居民的“畲族意识”时也提出:“就武平的情况来看,没有国家民族平等的理念和政策,一个已经汉化,其身份已被周围汉人认可,并且一度以汉人自认的群体,不会无端重提祖先,并力求恢复先民身份;同时,未能掌握相当的历史文化资源,就要求国家对自己的特殊身份给予认可,势必也不可能。”③
如果说历史上畲民为了淡化畲汉边界不断建构族群历史向汉文化靠拢的话,那么,在新的民族政策下,更多的畲民为争取被确定为畲族的政治身份做出不懈努力,而由国家、地方、学术界以及民间多方合力推行的文化展演,无不都是在强化业已形成的族群边界,这种看似截然相反的族群现象,却是各个族群在不同历史情境下做出的相同反应。
在民国时期,官方对福建等地的畲民统称为“苗民”或“苗族”,这种族称的转变与当时政府的民族思想与民族政策是分不开的,同时与清末以后的民族主义思潮不无关系。
清末民初,在巨大的民族危机下,许多知识分子寻求“国族”建构,如梁启超提出史学的任务就是要激发民众的国家意识,①“炎黄子孙”“黄帝世胄”“五族统一”成为当时的流行话语。政府和一些学者主张“同化”(所谓的“五族统一”即是该思想的表现),认为“少数民族”的调查和研究不能“刺激国族分化”,因此,当时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主要是以“安边”“治边”为要的“边政”研究。②
这种“五族统一”“五族共和”的思想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颇为流行,在民国初期修纂的畲族族谱中体现了这种思想。如上杭《雷氏梓福公家谱》在“凡例”中写道:“此谱议修于光复前一年,购工庀材,择吉开雕,越十有五月而告成。五族适于是年统一,是此谱诚为民国成立一大纪念,故于卷首敬刊国旗,用志盛事。”③一些接受新思想的畲族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在族谱中宣扬“五族共和”思想,如上杭雷氏第十九代裔孙雷熙春、雷晓春在“序”中称:
岁辛亥(1911年,笔者注),吾族有修谱之举……且此谱之作与民国之成立固有绝大关系者。吾族得姓实在黄帝纪元之世,源流最古。远祖方雷氏佐黄帝南征北伐,纯然民族主义,功德留荫,历世已四千六百余年,虽期间丧乱频仍,叠经变故,而忠孝节义之士犹复昶望于史册。方吾一世祖梓福公之生也,当赵宋末造,时适胡元入主中夏,窃据神器,因挚眷避地卜居于此,优游金山摺水间者九十载。追明太祖定鼎金陵,汉族光复,始考终牗下。迄明、清二代,族中科名仕宦于今为盛,而士大夫博学识能文章者,先后修谱两次,曾未昌言民族主义。为详考吾族得姓之缘,纪以志诸谱牒,知其慑服于专制余威者为已殁矣。乃者五族统一,政更共和,举黄帝手定之锦绣河山悉以还诸黄帝世胄,而此谱适于是年秋月以成。由是濡毫吮墨,畅所欲言,俾吾祖吾宗萦抱民族思想,得于序录中表白一二。①
该序描述了黄帝征伐异族、胡元入主中夏、明代汉族光复、民国政更共和等历史事件,反映的是清末民初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想,这种社会思潮经知识分子的宣传慢慢渗透到一般家族中,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民国元年,上杭雷赞明在“序”中称“今民国新立,治尚共和,神明之胄四万万皆同胞矣。”雷庭瑞在《重修梓福公新谱告成序》也称:“今岁五月开局编印,新谱告成值民国新纪元,谨进一言以志盛举。曰,共和成立,五族大同,汉满蒙回藏为一家,是亲爱家族之观念尤当推而远之,不仅在一姓一族也。五族者千万姓之所积,人人各亲爱其同姓,思扶掖而促进之,知非保五族则一族姓不能独立,于是互相扶掖,互相促进,此爱同胞、爱祖国者所不能违之公例也。”②
当时国民政府主张民族同化,鼓励边疆非汉人群汉化。在这种民族政策的指导下,官方并未将分布在福建等地区的畲民视为一个比较独立的、具有政治意义的民族,而是笼统地以苗族称之。实际上,关于对南方民族以“苗”“瑶(徭)”等族称泛称,在明清以前十分常见,这大概类似于更早之前,中原王朝将南方地区的族群泛称为“蛮”“越”“獠”等。应该来讲,这些族群内部存在较大差异,族群间具有一定的族群边界,如“越”又称“百越”,足以说明各个地区的族群是有一定区别的人群集团。将这些族群泛称为“蛮”“越”等,说明对于华夏族而言,或者是由于族群的接触与认识还不够,无法对这些族群内部的差别进行更详细地分,或者即使其群体内部有一些区别,但在华夏族心目中,这些差异可以忽略不计。即在“华夷之辨”的语境中,所谓的“蛮”“越”“苗”等无非是作为“华”的对立面而存在,二者形成了“文明”—“野蛮”的文化政治结构。杨志强在分析近代苗族形成问题时指出,明清以后,常将“苗”“苗种”作为南方各省非汉系族群的泛称,而“作为一种汉民族对于异族的称谓,这里所说的‘种’代表的是一种‘华’与‘夷’区别的模糊的文化境界,而并不是现今意义上所看到的‘种族’或‘民族’。”①
在民国时期,福建各地的畲民在官方上被称为“苗族”,如1937年《各县区苗夷民族概况》描述了连江、福鼎、顺昌三地“苗夷民族”情况,这些“苗夷民族”实际上多为畲民,其中连江有23个畲民村落,主要是迁徙自漳浦蓝、雷畲民,这些畲民在女子服饰上具有与汉族不同的装束特征,“清初与汉人通婚,在咸丰时代,苗族生活颇裕,中有田租收至三千余担者,今则已衰落。”到民国时代畲民业已与汉人同化。②
成立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山民会馆(后改为三明会馆),是闽东浙南“山民”联络议事之所。1946年,闽东畲族宗人商议重兴三明会馆,蓝玉轩等向所在地霞浦县政府提交申请报告,业经县长刘仇签署,呈报省政府核准在案,成为官方〓册认定的“苗夷民族”(按当时《福建年鉴》之称)“公益团体组织”。③由此可见,当时的闽东畲民被官方认定为“苗夷民族”,而不被认为是“畲族”。
1947年12月8日《福建省政府关于送边疆民族及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状况调查表给内政部电》关于苗族连江、罗源、顺昌、漳平、周宁等县,人口也相应增加。同时在注明备考注明:“苗族俗称畲民,间有与汉人同化者。”④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30—40年代,政府也将水上居民(疍民)作为“边疆民族及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上报国家有关部门。⑤苗族作为畲族的称呼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年时间还在官方的报告中出现,如1952年7月8日写成的《畲族福安县仙岭洋村调查情况》中,认为国民党大汉族主义进行民族压迫、歧视和侮辱,故意歪曲其历史,而另一方面,畲族限于文化,对本民族历史也不甚了解,“只认为苗民称号较臭畲人(臭蛇人)好,这是畲族改称苗族之始。”又称:
解放后来自北方干部,过去接触少数民族不多,对当地畲族未曾详尽调查,了解该民族历史,以及民族特征,只因他们语言不同,妇女装饰奇异,居住高山,称之苗民……在国民党大汉族主义消灭同化政策压迫下,曾经强迫改变民族服装,于民国十二三年间改穿汉服,藉以躲避欺视,不易辨别他们是畲民。女的虽略有改变,但仍然保持民族装饰。①
1952—1953年,漳平县、闽侯县提交的报告也均把本地畲民称为“苗族”②。1953年12月9日,在一份由福安地委统战部提交的报告中,还显示了当地畲民对于要将本族命名为“畲族”存在不满的情绪。报告称当时畲民有“苗族”“瑶族”“山宅”“三民”等名称,但畲民本身不承认自己为“畲族”,原因主要是历代反动统治(国民政府采取的是同化政策)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残存的民族隔阂没有彻底消除,加上当时南下干部不了解情况称畲民为“苗族”,福安地委统战部根据1951年在福安仙岩乡从该族家谱调查后认为“畲族”名称是正确的,这引起了当时畲族百姓的反对。③直到1956年9月9日《中共福安县委统战部关于少数民族名称问题的报告》仍坚持不使用畲族这个民族称号。④随着1956年中央统战部下发《关于确定畲民民族成分问题》,关于畲民名称的争论才渐渐停息下来。⑤并在1956年12月8日经中共中央统战部最后确定畲族的民族成份和民族名称。⑥至此,畲族作为一个族称在国家的政策下推行,而关于畲族的民族认同的过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闽西南一些地区接受程度较快,①而闽东一些地区则经历较长一段时间磨合,才最终接受,如在确定族称的两年多以后的1958年10月1日的《宁德县南山片畲族调查报告》仍在讨论畲族民族名称的几个来源与畲民态度。②1958年10月5日的《罗源县苗民情况报告》仍将畲族称为苗民③。而一些地区,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对畲民族称表示不满。④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称畲民为“苗民”与国民党政府的民族政策有一定关系,另外一些因畲汉矛盾给畲民带来情感伤害的地区,也希望用“苗族”等泛称替代原来被标签化了的“畲”族。笔者大胆推论,假如没有后来学术界的努力和国家政策的推行,部分畲民将可能被官方划分为“苗族”,也有可能在提倡“五族共和”以及民族同化的政策下,更多的畲民走向汉化,从而导致族群意识不彰显。正如疍民融入汉人之中,而在此之前,畲、疍均作为福建地区比较特殊的族群一并被论述⑤。当然,历史无法推论。在新中国民族政策的推行下,地方政府、学术界、各地的畲民(或疑似畲民)精英参与了新的族群边界的制造。
就国家和学术界而言,他们希望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标准来开展民族识别、民族身份恢复工作。民族学者施联朱参加了畲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他在《解放以来畲族研究综述》指出,“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为畲族识别工作重要因素。”①并强调不能单以民族姓氏定民族成分,他说:“我们说畲族主要有盘、蓝、雷、钟四大姓,不等于说四大姓全是畲族,姓氏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共同体,而民族则是以地缘为基础的人们共同体,把姓氏视为民族特征的主要标志之一,是错误的。”②
这种看似科学的民族识别标准却不能完全解决民族识别和民族恢复中的实际困难如何判断一个地方族群的民族特点是否足以被认定为畲族,需要当地族人支持与材料证明、地方政府的调研与申报以及相应政府部门审批与认定。但如果在一些地方原畲民住区的居民对被认定为畲族热情不高,或者当地民族部门投入不足,或者国家认定族群身份根据上报材料与若干调研,其中也不能保证完全做到十分客观。因此,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在族谱记载中有较为亲近血缘关系的姓氏,存在着一个地方宗姓被认定为畲族,而另一个地方宗姓却未被认定为畲族的情况。③
但是,在族群认同工具主义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的地区人群为能被确认为畲族而努力。1964年9月5日《福安专署关于政和、松溪少数民族称谓问题的调查报告》说明了政和县雷姓族人要求恢复畲族族称的由来,该文写道:
政和县雷华泉于1953年参加建阳专区少数民族代表会,体会到党的民族政策的英明:1963年他堂兄雷成寿从建阳籍到政和来谈起有关历年来闽北地区党对畲族人民的关怀以及闽东地区民族工作情况,他们得到很大启发,所以积极要求恢复族称。松溪县畲族曾向区里要求解决族称问题。①
从这份报告,可以看出政和县雷华泉通过了解国家的民族政策积极要求恢复族称,族群内部精英的运作使得该地区的畲民得以确认为畲族的政治身份。
近年来的一些研究也证明,一些畲民为了被确定畲族的政治身份,不断对本民族的历史进行重构。如周大鸣在赣南地区田野调查中发现,一些原属客家的蓝、雷、钟姓在20世纪80年代恢复成畲族后进行族群重构,他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恢复成赣南畲族的族谱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在1985年以前的族谱中,每一次族谱的序言有一个逐步‘汉化’‘正统化’的过程,受‘大传统’影响的烙印不断明显。而1985年后修的族谱则是‘畲化’的过程,透过这些‘精英文化’的变化历程,可以再现一个族群的变迁。”②杨晋涛在研究闽西蓝姓居民的“畲族意识”时也提出:“就武平的情况来看,没有国家民族平等的理念和政策,一个已经汉化,其身份已被周围汉人认可,并且一度以汉人自认的群体,不会无端重提祖先,并力求恢复先民身份;同时,未能掌握相当的历史文化资源,就要求国家对自己的特殊身份给予认可,势必也不可能。”③
如果说历史上畲民为了淡化畲汉边界不断建构族群历史向汉文化靠拢的话,那么,在新的民族政策下,更多的畲民为争取被确定为畲族的政治身份做出不懈努力,而由国家、地方、学术界以及民间多方合力推行的文化展演,无不都是在强化业已形成的族群边界,这种看似截然相反的族群现象,却是各个族群在不同历史情境下做出的相同反应。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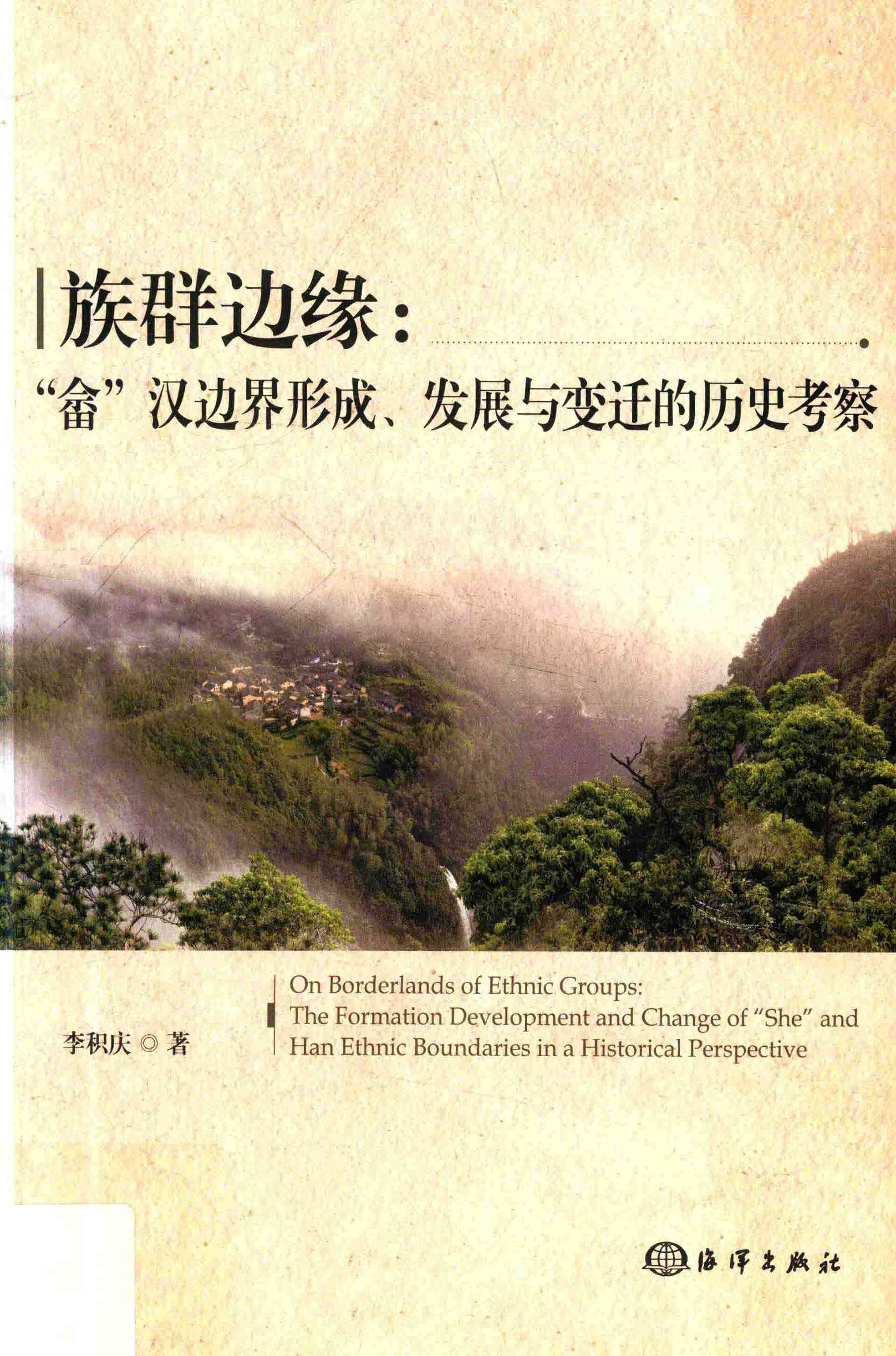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出版者:海洋出版社
本书从族群边界的理论角度,重新审视畲族形成、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在承认族群客观历史文化的同时,重点研究历史上“他者”(主要是汉族)对“畲”的社会定义以及“自者”(主要为南方非汉族群)自我族群认同的过程,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现实意义。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