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族群边界与文化认同
| 内容出处: |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图书 |
| 唯一号: | 130920020230003825 |
| 颗粒名称: | 二、族群边界与文化认同 |
| 分类号: | K288.3 |
| 页数: | 7 |
| 页码: | 249-255 |
| 摘要: | 本文从生态文化语境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历史上族群互动和族群边界的形成。 |
| 关键词: | 畲族 生态文化 族群分类 |
内容
在生态边界冲突激烈地区,族群互动更为频繁,历史上许多新的族群,往往是在族群边界地区中孕育产生的。张之恒将中国划分为四个截然不同的经济文化区,除四个经济文化区之外,还存在着三个过渡地带或称文化交汇地带。①张之恒的“过渡地带”理论不仅仅在考古学上有创新意义,对族群理论研究也有借鉴意义。如张氏所提出的三个史前文化过渡地带,一直是各民族文化互动比较频繁地方,如阴山南侧及河套地区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交汇地带,后来著名的河湟民族走廊地区即产生于此。而本书研究重点区域闽粤赣交界地区,其处于南岭以北和武夷山以西地区过渡地带,在该区域中,多种族群文化交流频繁,这使得该地区成为新族群孕育的温床。从历史上看,唐宋时期的闽粤赣地区,其族群结构变化最为明显,学术界普遍认为,福佬、畲族、客家等族群均是在这一时期孕育形成的。②
按照传统的民族史观点,随着族群互动与融合,各个族群吸收对方的文化,继而形成了迥异于原族群组成部分的新族群。实际上,新的族群诞生于族群边界互动地带,不仅仅在于各种族群文化的融合的客观结果,还在于族群间主观认同的情况。这里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我群”对“他群”认识程度与情感;二是“我群”如何通过“他群”看待本族群。
春秋以后,华夏族形成了“天下—四方”“华—夷”的民族观。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华夏族经历了漫长的华夏化进程。华夏族对外扩张的过程,同时也是对“异族”不断接触与认识的过程。在以往研究中,学者常以某个族群出现于某文献中的时间作为该族群存在的标志,确切来讲,各类族群称谓的出现,更多的体现以华夏族为代表的主流人群对周边非主流人群的认识程度。因为,早在记载之前,这些族群的实体人口可能已经存在,但作为“异己”的共同体,是以华夏族为参照物后才形成的。
笔者以闽粤赣边区的一些非汉族群为例。如文献中曾载,在西晋至唐的闽粤赣地区,活跃着一类被称为“山都”“木客”的人群,这类人群在文献中的出现时间顺序,恰恰与中原王朝开疆拓土的时间顺序相一致。就当时的各种记载而言,“山都”“木客”作为一种“异类”而存在,其具有神秘的特性,按现在人种学观点来看,几乎可以将其归为“非人类”中。但是,作为文本记载中的文化事象,“山都”“木客”却是华夏族向南扩展时对一些非汉族群的一种历史记忆,其中可能包含着对“异族”的想象,这种想象是南下汉人对土著真实情况的一种误读,是对异族的不了解,或者接触后的形成的恐惧、厌恶等心理的一种投射。唐代以后“山都”“木客”的消亡,客观原因是其族群实体融入华夏族;而从主观认识角度看,其原因则为:随着华夏族对闽粤赣非汉族群认识水平的提高,原来一些想象的部分已无从考究,故不予记载。
因帝国深入边陲以及南方次第开发而引起思想认识变迁,这种现象多有存在,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古人关于瘴气、蛊毒等文化事象的认识。学者认为,文献中大量记载瘴气与区域开发程度有关,瘴气与其说是一种病理现象,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其中体现的是以汉人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南方各地区的认识情况。张文认为,所谓的“瘴气”或“瘴病”,更多反映的是中原文化对南方地区的地域偏见与族群歧视,①左鹏则认为“各地区瘴情的轻重差异,反映了此地为中原文化所涵化的深浅程度。”②再如“蓄蛊”现象,于赓哲认为关于“蛊毒”流行地的记载,其经历了从中原地区到南方土著地区移动的过程,并且,开发程度越早的南方土著地区越早脱离“蓄蛊之地”的恶名。③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中原地区对“南土卑湿”认识的变迁上,“南土卑湿”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其反映的是族群边界的动摇与移动。④
以上的研究说明,作为主流文化话语权的华夏族群,其对周边族群的认识程度是随着帝国开发而逐渐深入。不同族群开始接触后,族群意识渐渐产生,族群的自我认同由此增强。一般来讲,在族群接触较多地区,不同族群文化带来的文化冲击(cultureshock)使得双方族群意识到对方与我方差异的存在。这种意识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当中,能被文献记载下来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我们发现,文献记载在描述“他者”的文化特征时,总是要体现其与“我者”差异,而这种差异往往会被放大。这种以“他者”之“异”,来反衬“我者”之“同”的描述,体现的是族群的自我认同,是在华夷之别的民族观指导下的一种自觉的实践。
笔者在书中探讨了“畲”作为一种族群称谓首先出现在漳州、潮州地区的原因。南宋时期的漳州与潮州等地以“畲”为代表的溪洞种类活动的场所,但这些区域应该不是溪洞种类(与省民相对)的中心区域,而是族群边界地区。按照宋人刘克庄的描述,溪洞种类分布在漳、潮、梅、汀、赣等区域,从当时的族群格局看,漳州、潮州等地的溪峒种类位于与省民交错的地带,也就是在族群边界的地区。按照王明珂先生的研究,在族群边界地带,族群意识比族群中心地带更为强烈。漳州、潮州的边界区域地位使其成为“畲”、汉双方观察并认识对方族群的“前哨”;而在溪洞种类的中心地带之一的汀州,这些族群仍沿用唐代以来的对南方非汉族群的泛称,如“(峒)蛮”等称谓。南宋时期的漳州、潮州“畲”的族群文化特色比较明显,而随着族群边界的移动,原来的族群边界地区可能成为某族群的中心地区,明清以后,“畲”汉族群边界转移到闽东、浙南等地区,此时该地区的畲民族群意识比漳州、潮州等地畲民强烈得多。
可见,族群边界并非一成不变,其呈现出多变性、复杂性、重合性等特点。判断族群边界变化的情况,可以从族群边界双方的族群认同的变化的情况进行考察。宋元以后,闽粤赣地区的“畲”汉边界呈现飘忽不定的状态:其中既有畲民通过获得版籍成为编户齐民的情况,也有汉人通过“入山洞”,脱籍成为“畲”“瑶”族群的情况。这种族群边界的流动,一方面是社会人群的政治或文化身份发生变化,体现了官方关于族群分类的标准,以及如何对非汉族群进行社会定义;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各族群自我认同变化的一种结果。具体来讲,就官方而言,“峒”与“非峒”“畲”与“非畲”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纳税服役,是否接受教化,以及是否编入国家版籍。因此,在许多历史语境下,“畲”与“非畲”并不是严格的种族区分标准,其中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政治身份、文化身份的差别。
笔者在文中还以宋元以来的“畲乱”记载为例说明官方社会分类标准问题。实际上,在众多的“畲军”“畲寇”中,并不是全部由非汉族群组成,其中有不少人群通过打着“畲”的旗号,以此号召人群、凝聚人心、增加认同。也就是说,这群人在种族特征中,并非都是刘克庄的《漳州谕畲》文中所指的溪洞种类,但是,在特定社会情境或历史语境中,这个群体的人或者被官方以一定标准——通常是不纳赋税,不服从国家管理——认定为“畲”,或者这个群体的人在文化上转变了族群认同,从而自我认同为“畲”。
当然,在宋元“畲乱”中,畲民在与国家互动中,其文化认同常常出现反复性:或者归顺朝廷、被收编军队、安排屯田、获得版籍以及融入汉族等;或者反抗或归降后复叛,“依山险阻”“亡入畲洞”。以上两种选择显示了在华夏化运动过程中,以畲民为代表的南方非汉族群的不同文化认同取向。文化认同取向不同,其族群边界也会发生变化:其一,成为编户齐民的畲民,即所谓的“日山獠将化编氓”,这些原被称作“山獠”的非汉族群,久而久之成为了国家子民,这些成为“编氓”非汉族群与汉人之间的族群文化差别随着族群的融合慢慢缩小,这种趋势使得“汉”与“非汉”的族群边界开始变得模糊甚至消失殆尽;其二,那些不与政府合作的非汉族群,国家仍以“化外之民”视之,将其与“化内之民”严格区分开来,而这些非汉族群通常也以“化外之民”自居,或退守“山洞”,或迁移到更偏远的山区,这种情况下,“汉”与“非汉”的族群边界也因这类群体而存在,并随着这些非汉居民的活动轨迹而发生移动。
明中叶时期,华南地区进入了社会转型时期。该阶段畲汉边界的显著变化,成为畲族发展史中值得关注的内容。从明中叶开始,畲民的核心聚居区逐渐从闽粤赣地区转移至闽浙赣地区,这种变化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形成的。王阳明成功平定“畲乱”,闽粤赣地区开始由“乱”入“治”,大量的畲民或迁徙外地,或融入当地汉人之中。除了王阳明平定“畲乱”的推力外,明清时期的商业化进程起了拉力作用,区域经济分工使得大量的“畲客”在此期间迁入闽浙赣地区进行经济作物种植。另外,明末清初的“倭乱”与“迁界”为畲民迁居并扎根于闽东浙南地区提供了又一历史契机。
林校生根据畲民的历史记忆(主要以歌谣、族谱为载体)和畲民现代人口分布现状,将畲族族群的核心集居地按时间顺序分为“潮州中心期”“汀、漳中心期”“福宁府中心期”三个重要阶段。①实际上,这种所谓的“地区中心说”,是以某一历史时期该地区的畲族文化特征或者文化认同情况作为判断标准。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其一,在明清时期,从闽粤赣地区迁往闽浙赣地区的畲民,这些迁徙的人口占输出地畲民人口总数的比例到底有多大?其二,在明清以后,闽浙赣地区畲民文化特征、族群意识为何比闽粤赣地区畲民更为显著?
首先,在明清以后,在闽西南许多原为“畲区”的地方,后来慢慢变为“客区”,这种变化不能单纯地以畲民实质性的人口外迁来解释。实际上,汀州、漳州地区在明清时期,仍存在着许多(或疑似)畲民姓氏的巨家大族,有的成为当地望族。一些文献也表明,明清时期有大量畲民融入当地汉人,并逐渐成为土著,许多甚至“忘其所自来”。谢重光先生指出,明中叶以后,原来的赣闽粤交界地区畲族住区,如今几乎清一色是客家人的住区,①与以畲族外迁来解释此现象观点不同的是,谢先生认为更重要的因素应是畲民大部分转化为客家人了。②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需通过文化来解释,“应将其视为在汉文化认同的过程中,汉族的边界逐渐扩大、华夏边缘在东南的进一步扩张的结果。”③即:在强势的汉文化语境中,闽西南地区的许多畲民家族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汉文化,在明清时期,畲、汉族群文化认同趋于一致,导致了该地区的畲汉边界的模糊、偏移乃至消失。
其次,闽浙赣地区畲民的族群意识是在族群边界冲突中凸显出来的。明清时期,许多来自汀州等地的“畲客”大量迁入闽浙赣地区,成为蓝靛、苎麻等经济作物种植的主力军。这种人口的流动是地区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导致的必然结果,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对于流动人口输入地而言,大量的移民为本地增加了劳动力,尤其对于未开发地带或战后的地区,移民在地区开发以及恢复地方经济方面作用巨大。而流动人口的弊端在于其可能成为社会秩序的威胁者和破坏者。一方面,在古代中国,官方奉行重本抑末经济思想,大量土地用于经济作物种植可能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日益紧张的资源竞争使得“土”“客”矛盾愈发紧张。“畲客”作为一种流动人口,在某些地区一度受到土著的排挤,当地土著(主要是汉人)中的一些人主张严格区分土客边界,试图将“畲客”边缘化,在清代中期发生在闽东、浙南地区的“学额之争”,标志着土客矛盾达到顶点。与闽浙赣地区有着显著畲汉边界不同的是,在闽粤赣地区的一些畲民家族渐渐融入当地汉人社会之中,一些家族甚至出现了诸如雷鋐、蓝鼎元的知识分子。这些畲民家族在文教上取得的成绩不亚于周边汉人家族,其文化认同也显示出与当地汉人无特别大的差别。因此,在闽浙赣地区,其畲民的文化特色之所以比闽粤赣地区更鲜明,离不开两个因素:一是当地土著的族群分类及对当地畲民的社会定义(体现在对畲民的各种歧视称谓);二是当地畲民利用族群文化以凝聚人心,并对当地大汉族主义予以反抗与回击。
尽管在明清时期,闽浙赣地区的畲民体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征,但是在强势的汉文化以及华夏化进程的持续影响下,畲民的文化认同呈现出向汉文化靠拢总的趋势。这个趋势直到新的民族政策实行后被扭转过来,国家按照一定的民族识别标准,通过政治权力重新划定族群边界,畲族在1956年成为政治意义上的民族,自此之后,原来一些地区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畲族族群认同在各方的操作下变得越来越强烈,一度出现了恢复畲族身份的热潮。
畲客的共生关系和族群分野也体现了文化认同与族群边界的关系。竹村卓二引用鲍曼(BaumannHermann)的民族理论①后认为,畲民之所以被汉族称为“畲客”或“輋客”,说明畲、汉族的关系本来就非同一般。他称:“至少在中国对华中、华南非汉民族的称呼中,用‘客’这一概念来表示的,别无他例。这一点显示了畲民与边境尚未开化的原住民苗族和彝族略有不同,当然,对于土著汉族(主民)的社会来说,畲民是处于外来客民的地位。畲民对于汉族来说,现在与其说是应征服或驱逐的蛮夷,莫如说是保持一定社会距离,处于互通有无共生关系中的同伴的地位。”②王东先生也认为,在较长的历史时间中,畲汉族群融合,二者形成了密切的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同时是一种共变关系。“伴随着这种互动与共变,畲、汉双方在各自改变自己的同时,也在改变着对方。”③
在早期迁入的闽浙赣地区“畲客”中,既有畲民,也有客家人,他们统称为“客”。但是不管是政府,还是当地土著,对“客”的认识比较一致:或者以“客”称之,其中并没有清晰的畲族与客家身份的区分;或者统一以地名称之,如汀州人,借以区分籍贯。另外,也没有证据表明,来自汀州等地区的“畲客”之间形成了严格的“畲族”与“客家”的族群分类关系。这说明在明清之际初迁至闽浙赣地区的“畲客”,其不仅在经济方式等客观文化特征无太大差别,其主观的文化认同也比较一致。而当这些“畲客”慢慢安顿下来并定居,土、客矛盾逐渐升级后,“畲客”中的“畲”特征被凸显出来。
与以往闽浙赣地区迁徙的“畲客”文化认同有所区别的是,迁往两广等地区的“畲客”,“畲”特征并没有被凸显,其反映的更多是客家文化认同。这种现象的产生既与广府、客文化差异产生敌意有关,如广府人把客家人称为“匪”“犵”“獠”“猺”等,“或是直接在‘客’字上加上污辱性的‘犬’字偏旁,以示客家为野蛮民族,自以为与之水火不容。”①咸治同丰年间,广东一带爆发了大规模的土客大械斗,此后,客家运动逐渐在广东等地蓬勃兴起,“畲客”中的客家文化认同达到顶点,畲族认同反而不被彰显。直到20世纪80年代,整个广东地区的畲民文化认同总体仍不是特别强烈,对此周大鸣论述道:
广东东部是畲族传说中的文化中心,其凤凰山更被认同为畲族的发源地,可是在这场恢复畲族的运动中,广东反而没有其强烈。究其原因,首先与广东省政府没有强力推行恢复族属相关,其次粤东北是客家文化的中心,对客家文化的认同超越了其他族群的认同。②
我们认为,不同地区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对族群的特质具有重要决定作用。谢重光先生曾指出:“有什么样的生态环境(包括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就会有什么特质的人群,这个人群的文化也会鲜明地打上其生态环境的烙印。”③在不同区域中,生态、人文环境不同,族群的认同取向也可能有所不同,正如笔者前文所指出的,不同的文化取向最终导致了“畲”“客”成为两个比较独立的族群。一些特殊的历史事件,如明中叶社会转型加速了“畲”“客”族群的分离趋势。畲族与客家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紧密的关系,由于文化认同的差异,二者之间形成一道鲜明的族群边界,这也再一次证明文化取向对于区分族群的重要性。④
按照传统的民族史观点,随着族群互动与融合,各个族群吸收对方的文化,继而形成了迥异于原族群组成部分的新族群。实际上,新的族群诞生于族群边界互动地带,不仅仅在于各种族群文化的融合的客观结果,还在于族群间主观认同的情况。这里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我群”对“他群”认识程度与情感;二是“我群”如何通过“他群”看待本族群。
春秋以后,华夏族形成了“天下—四方”“华—夷”的民族观。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华夏族经历了漫长的华夏化进程。华夏族对外扩张的过程,同时也是对“异族”不断接触与认识的过程。在以往研究中,学者常以某个族群出现于某文献中的时间作为该族群存在的标志,确切来讲,各类族群称谓的出现,更多的体现以华夏族为代表的主流人群对周边非主流人群的认识程度。因为,早在记载之前,这些族群的实体人口可能已经存在,但作为“异己”的共同体,是以华夏族为参照物后才形成的。
笔者以闽粤赣边区的一些非汉族群为例。如文献中曾载,在西晋至唐的闽粤赣地区,活跃着一类被称为“山都”“木客”的人群,这类人群在文献中的出现时间顺序,恰恰与中原王朝开疆拓土的时间顺序相一致。就当时的各种记载而言,“山都”“木客”作为一种“异类”而存在,其具有神秘的特性,按现在人种学观点来看,几乎可以将其归为“非人类”中。但是,作为文本记载中的文化事象,“山都”“木客”却是华夏族向南扩展时对一些非汉族群的一种历史记忆,其中可能包含着对“异族”的想象,这种想象是南下汉人对土著真实情况的一种误读,是对异族的不了解,或者接触后的形成的恐惧、厌恶等心理的一种投射。唐代以后“山都”“木客”的消亡,客观原因是其族群实体融入华夏族;而从主观认识角度看,其原因则为:随着华夏族对闽粤赣非汉族群认识水平的提高,原来一些想象的部分已无从考究,故不予记载。
因帝国深入边陲以及南方次第开发而引起思想认识变迁,这种现象多有存在,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古人关于瘴气、蛊毒等文化事象的认识。学者认为,文献中大量记载瘴气与区域开发程度有关,瘴气与其说是一种病理现象,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其中体现的是以汉人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南方各地区的认识情况。张文认为,所谓的“瘴气”或“瘴病”,更多反映的是中原文化对南方地区的地域偏见与族群歧视,①左鹏则认为“各地区瘴情的轻重差异,反映了此地为中原文化所涵化的深浅程度。”②再如“蓄蛊”现象,于赓哲认为关于“蛊毒”流行地的记载,其经历了从中原地区到南方土著地区移动的过程,并且,开发程度越早的南方土著地区越早脱离“蓄蛊之地”的恶名。③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中原地区对“南土卑湿”认识的变迁上,“南土卑湿”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其反映的是族群边界的动摇与移动。④
以上的研究说明,作为主流文化话语权的华夏族群,其对周边族群的认识程度是随着帝国开发而逐渐深入。不同族群开始接触后,族群意识渐渐产生,族群的自我认同由此增强。一般来讲,在族群接触较多地区,不同族群文化带来的文化冲击(cultureshock)使得双方族群意识到对方与我方差异的存在。这种意识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当中,能被文献记载下来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我们发现,文献记载在描述“他者”的文化特征时,总是要体现其与“我者”差异,而这种差异往往会被放大。这种以“他者”之“异”,来反衬“我者”之“同”的描述,体现的是族群的自我认同,是在华夷之别的民族观指导下的一种自觉的实践。
笔者在书中探讨了“畲”作为一种族群称谓首先出现在漳州、潮州地区的原因。南宋时期的漳州与潮州等地以“畲”为代表的溪洞种类活动的场所,但这些区域应该不是溪洞种类(与省民相对)的中心区域,而是族群边界地区。按照宋人刘克庄的描述,溪洞种类分布在漳、潮、梅、汀、赣等区域,从当时的族群格局看,漳州、潮州等地的溪峒种类位于与省民交错的地带,也就是在族群边界的地区。按照王明珂先生的研究,在族群边界地带,族群意识比族群中心地带更为强烈。漳州、潮州的边界区域地位使其成为“畲”、汉双方观察并认识对方族群的“前哨”;而在溪洞种类的中心地带之一的汀州,这些族群仍沿用唐代以来的对南方非汉族群的泛称,如“(峒)蛮”等称谓。南宋时期的漳州、潮州“畲”的族群文化特色比较明显,而随着族群边界的移动,原来的族群边界地区可能成为某族群的中心地区,明清以后,“畲”汉族群边界转移到闽东、浙南等地区,此时该地区的畲民族群意识比漳州、潮州等地畲民强烈得多。
可见,族群边界并非一成不变,其呈现出多变性、复杂性、重合性等特点。判断族群边界变化的情况,可以从族群边界双方的族群认同的变化的情况进行考察。宋元以后,闽粤赣地区的“畲”汉边界呈现飘忽不定的状态:其中既有畲民通过获得版籍成为编户齐民的情况,也有汉人通过“入山洞”,脱籍成为“畲”“瑶”族群的情况。这种族群边界的流动,一方面是社会人群的政治或文化身份发生变化,体现了官方关于族群分类的标准,以及如何对非汉族群进行社会定义;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各族群自我认同变化的一种结果。具体来讲,就官方而言,“峒”与“非峒”“畲”与“非畲”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纳税服役,是否接受教化,以及是否编入国家版籍。因此,在许多历史语境下,“畲”与“非畲”并不是严格的种族区分标准,其中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政治身份、文化身份的差别。
笔者在文中还以宋元以来的“畲乱”记载为例说明官方社会分类标准问题。实际上,在众多的“畲军”“畲寇”中,并不是全部由非汉族群组成,其中有不少人群通过打着“畲”的旗号,以此号召人群、凝聚人心、增加认同。也就是说,这群人在种族特征中,并非都是刘克庄的《漳州谕畲》文中所指的溪洞种类,但是,在特定社会情境或历史语境中,这个群体的人或者被官方以一定标准——通常是不纳赋税,不服从国家管理——认定为“畲”,或者这个群体的人在文化上转变了族群认同,从而自我认同为“畲”。
当然,在宋元“畲乱”中,畲民在与国家互动中,其文化认同常常出现反复性:或者归顺朝廷、被收编军队、安排屯田、获得版籍以及融入汉族等;或者反抗或归降后复叛,“依山险阻”“亡入畲洞”。以上两种选择显示了在华夏化运动过程中,以畲民为代表的南方非汉族群的不同文化认同取向。文化认同取向不同,其族群边界也会发生变化:其一,成为编户齐民的畲民,即所谓的“日山獠将化编氓”,这些原被称作“山獠”的非汉族群,久而久之成为了国家子民,这些成为“编氓”非汉族群与汉人之间的族群文化差别随着族群的融合慢慢缩小,这种趋势使得“汉”与“非汉”的族群边界开始变得模糊甚至消失殆尽;其二,那些不与政府合作的非汉族群,国家仍以“化外之民”视之,将其与“化内之民”严格区分开来,而这些非汉族群通常也以“化外之民”自居,或退守“山洞”,或迁移到更偏远的山区,这种情况下,“汉”与“非汉”的族群边界也因这类群体而存在,并随着这些非汉居民的活动轨迹而发生移动。
明中叶时期,华南地区进入了社会转型时期。该阶段畲汉边界的显著变化,成为畲族发展史中值得关注的内容。从明中叶开始,畲民的核心聚居区逐渐从闽粤赣地区转移至闽浙赣地区,这种变化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形成的。王阳明成功平定“畲乱”,闽粤赣地区开始由“乱”入“治”,大量的畲民或迁徙外地,或融入当地汉人之中。除了王阳明平定“畲乱”的推力外,明清时期的商业化进程起了拉力作用,区域经济分工使得大量的“畲客”在此期间迁入闽浙赣地区进行经济作物种植。另外,明末清初的“倭乱”与“迁界”为畲民迁居并扎根于闽东浙南地区提供了又一历史契机。
林校生根据畲民的历史记忆(主要以歌谣、族谱为载体)和畲民现代人口分布现状,将畲族族群的核心集居地按时间顺序分为“潮州中心期”“汀、漳中心期”“福宁府中心期”三个重要阶段。①实际上,这种所谓的“地区中心说”,是以某一历史时期该地区的畲族文化特征或者文化认同情况作为判断标准。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其一,在明清时期,从闽粤赣地区迁往闽浙赣地区的畲民,这些迁徙的人口占输出地畲民人口总数的比例到底有多大?其二,在明清以后,闽浙赣地区畲民文化特征、族群意识为何比闽粤赣地区畲民更为显著?
首先,在明清以后,在闽西南许多原为“畲区”的地方,后来慢慢变为“客区”,这种变化不能单纯地以畲民实质性的人口外迁来解释。实际上,汀州、漳州地区在明清时期,仍存在着许多(或疑似)畲民姓氏的巨家大族,有的成为当地望族。一些文献也表明,明清时期有大量畲民融入当地汉人,并逐渐成为土著,许多甚至“忘其所自来”。谢重光先生指出,明中叶以后,原来的赣闽粤交界地区畲族住区,如今几乎清一色是客家人的住区,①与以畲族外迁来解释此现象观点不同的是,谢先生认为更重要的因素应是畲民大部分转化为客家人了。②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需通过文化来解释,“应将其视为在汉文化认同的过程中,汉族的边界逐渐扩大、华夏边缘在东南的进一步扩张的结果。”③即:在强势的汉文化语境中,闽西南地区的许多畲民家族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汉文化,在明清时期,畲、汉族群文化认同趋于一致,导致了该地区的畲汉边界的模糊、偏移乃至消失。
其次,闽浙赣地区畲民的族群意识是在族群边界冲突中凸显出来的。明清时期,许多来自汀州等地的“畲客”大量迁入闽浙赣地区,成为蓝靛、苎麻等经济作物种植的主力军。这种人口的流动是地区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导致的必然结果,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对于流动人口输入地而言,大量的移民为本地增加了劳动力,尤其对于未开发地带或战后的地区,移民在地区开发以及恢复地方经济方面作用巨大。而流动人口的弊端在于其可能成为社会秩序的威胁者和破坏者。一方面,在古代中国,官方奉行重本抑末经济思想,大量土地用于经济作物种植可能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日益紧张的资源竞争使得“土”“客”矛盾愈发紧张。“畲客”作为一种流动人口,在某些地区一度受到土著的排挤,当地土著(主要是汉人)中的一些人主张严格区分土客边界,试图将“畲客”边缘化,在清代中期发生在闽东、浙南地区的“学额之争”,标志着土客矛盾达到顶点。与闽浙赣地区有着显著畲汉边界不同的是,在闽粤赣地区的一些畲民家族渐渐融入当地汉人社会之中,一些家族甚至出现了诸如雷鋐、蓝鼎元的知识分子。这些畲民家族在文教上取得的成绩不亚于周边汉人家族,其文化认同也显示出与当地汉人无特别大的差别。因此,在闽浙赣地区,其畲民的文化特色之所以比闽粤赣地区更鲜明,离不开两个因素:一是当地土著的族群分类及对当地畲民的社会定义(体现在对畲民的各种歧视称谓);二是当地畲民利用族群文化以凝聚人心,并对当地大汉族主义予以反抗与回击。
尽管在明清时期,闽浙赣地区的畲民体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征,但是在强势的汉文化以及华夏化进程的持续影响下,畲民的文化认同呈现出向汉文化靠拢总的趋势。这个趋势直到新的民族政策实行后被扭转过来,国家按照一定的民族识别标准,通过政治权力重新划定族群边界,畲族在1956年成为政治意义上的民族,自此之后,原来一些地区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畲族族群认同在各方的操作下变得越来越强烈,一度出现了恢复畲族身份的热潮。
畲客的共生关系和族群分野也体现了文化认同与族群边界的关系。竹村卓二引用鲍曼(BaumannHermann)的民族理论①后认为,畲民之所以被汉族称为“畲客”或“輋客”,说明畲、汉族的关系本来就非同一般。他称:“至少在中国对华中、华南非汉民族的称呼中,用‘客’这一概念来表示的,别无他例。这一点显示了畲民与边境尚未开化的原住民苗族和彝族略有不同,当然,对于土著汉族(主民)的社会来说,畲民是处于外来客民的地位。畲民对于汉族来说,现在与其说是应征服或驱逐的蛮夷,莫如说是保持一定社会距离,处于互通有无共生关系中的同伴的地位。”②王东先生也认为,在较长的历史时间中,畲汉族群融合,二者形成了密切的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同时是一种共变关系。“伴随着这种互动与共变,畲、汉双方在各自改变自己的同时,也在改变着对方。”③
在早期迁入的闽浙赣地区“畲客”中,既有畲民,也有客家人,他们统称为“客”。但是不管是政府,还是当地土著,对“客”的认识比较一致:或者以“客”称之,其中并没有清晰的畲族与客家身份的区分;或者统一以地名称之,如汀州人,借以区分籍贯。另外,也没有证据表明,来自汀州等地区的“畲客”之间形成了严格的“畲族”与“客家”的族群分类关系。这说明在明清之际初迁至闽浙赣地区的“畲客”,其不仅在经济方式等客观文化特征无太大差别,其主观的文化认同也比较一致。而当这些“畲客”慢慢安顿下来并定居,土、客矛盾逐渐升级后,“畲客”中的“畲”特征被凸显出来。
与以往闽浙赣地区迁徙的“畲客”文化认同有所区别的是,迁往两广等地区的“畲客”,“畲”特征并没有被凸显,其反映的更多是客家文化认同。这种现象的产生既与广府、客文化差异产生敌意有关,如广府人把客家人称为“匪”“犵”“獠”“猺”等,“或是直接在‘客’字上加上污辱性的‘犬’字偏旁,以示客家为野蛮民族,自以为与之水火不容。”①咸治同丰年间,广东一带爆发了大规模的土客大械斗,此后,客家运动逐渐在广东等地蓬勃兴起,“畲客”中的客家文化认同达到顶点,畲族认同反而不被彰显。直到20世纪80年代,整个广东地区的畲民文化认同总体仍不是特别强烈,对此周大鸣论述道:
广东东部是畲族传说中的文化中心,其凤凰山更被认同为畲族的发源地,可是在这场恢复畲族的运动中,广东反而没有其强烈。究其原因,首先与广东省政府没有强力推行恢复族属相关,其次粤东北是客家文化的中心,对客家文化的认同超越了其他族群的认同。②
我们认为,不同地区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对族群的特质具有重要决定作用。谢重光先生曾指出:“有什么样的生态环境(包括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就会有什么特质的人群,这个人群的文化也会鲜明地打上其生态环境的烙印。”③在不同区域中,生态、人文环境不同,族群的认同取向也可能有所不同,正如笔者前文所指出的,不同的文化取向最终导致了“畲”“客”成为两个比较独立的族群。一些特殊的历史事件,如明中叶社会转型加速了“畲”“客”族群的分离趋势。畲族与客家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紧密的关系,由于文化认同的差异,二者之间形成一道鲜明的族群边界,这也再一次证明文化取向对于区分族群的重要性。④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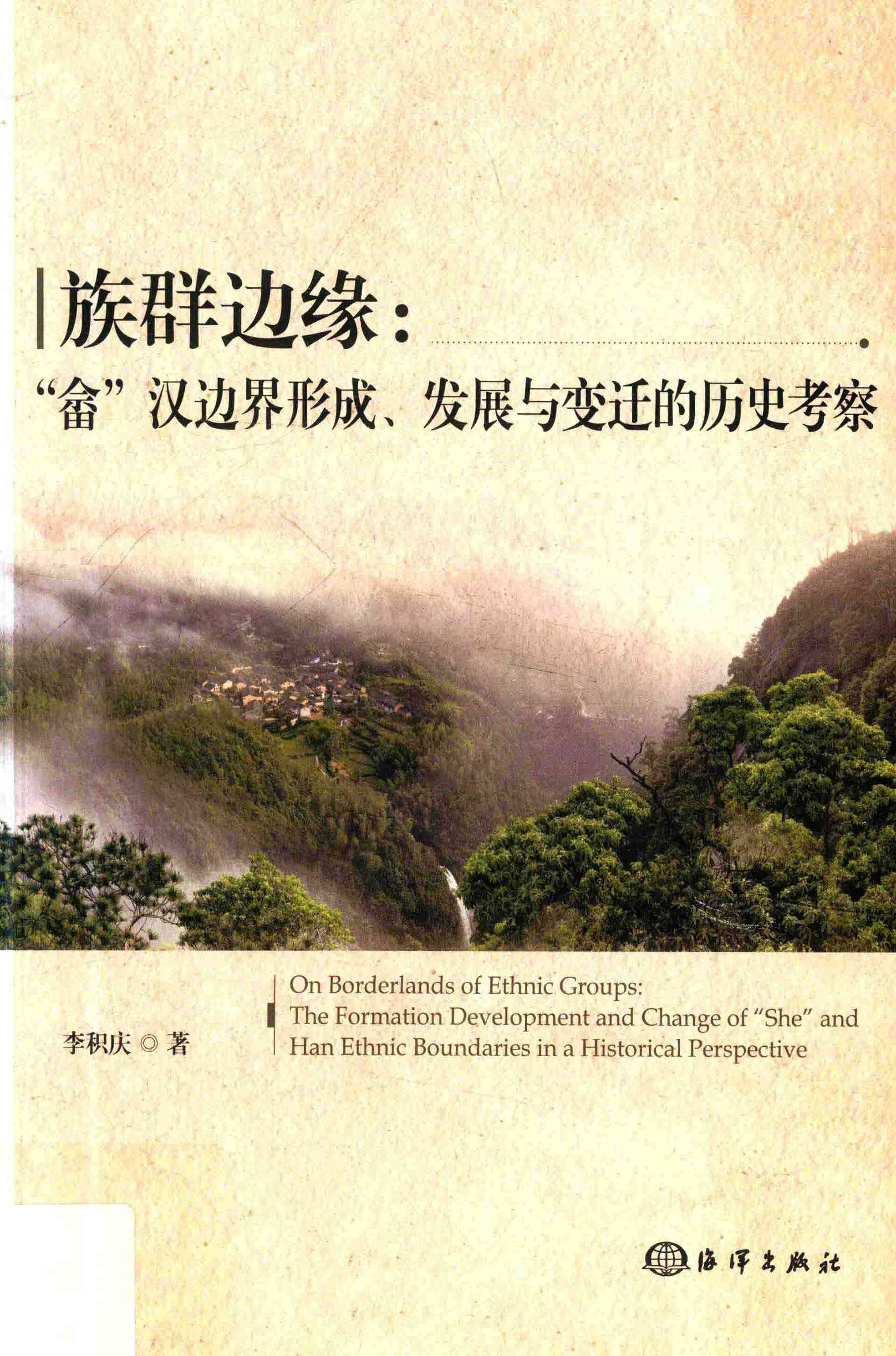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出版者:海洋出版社
本书从族群边界的理论角度,重新审视畲族形成、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在承认族群客观历史文化的同时,重点研究历史上“他者”(主要是汉族)对“畲”的社会定义以及“自者”(主要为南方非汉族群)自我族群认同的过程,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现实意义。
阅读
相关地名
宁德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