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余论
| 内容出处: |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图书 |
| 唯一号: | 130920020230003823 |
| 颗粒名称: | 第六章 余论 |
| 分类号: | K288.3 |
| 页数: | 19 |
| 页码: | 246-264 |
| 摘要: | 这段文本主要讨论了“畲”族群的形成、变迁历史以及与汉族的关系。 |
| 关键词: | 畲族 汉族 变迁历史 |
内容
现代族群理论认为,一个族群的形成,离不开“他者”族群的存在,也就说,如果没有“他族”的存在,就谈不上有“我族”的族群意识,族群认同也就无从说起。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书从族群边界理论的角度,探讨了“畲”的形成、变迁历史以及“畲”汉族群的关系,重点说明以下四个问题。
一、生态文化语境与族群分类
在古代中国,由于受到大一统观念的影响,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民族史的撰述,都体现出了诸如“夷夏同祖认同、华夷一家认同、共属中国认同、华夏文化认同”的大一统意识。①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华夏文化在几千年的民族史撰述中一直处于被表述的中心,四方“夷狄”则处于从属地位。而在具体实践中,华夏民族自春秋战国以后,在与周边非华夏民族的互动过程中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表现为华夏族及其文化不断向边陲扩张,最终使得各个非华夏民族淹没在华夏族的“海洋”中,或者成为“华夏海洋”中的“非华夏孤岛”。
因此,在重新审视我国古代民族史时,我们必须将历代有关于“非华夏”族群的文字记载置于当时的社会情境来分析,具体来说:一是在汉文化语境下,这种记载多大程度反映了文字记载者的立场、态度及情感,而作为文本的历史记忆,其又反映了当时什么样的历史心性?二是这种记载中的文化特征,是否能够反映“异族”的实际情况,即这种客观的文化特征描述能否与“异族”的实际认同情况相一致?或者说,对“他者”只是文字记载者单方面的认同?
本书认为,“畲”作为一个南方非汉族群,其在历史上出现并非偶然,需要在生态语境和文化语境下对其作一番考察。
首先,自然生态是任何一种族群和文化产生的最基础因素。正如我国历史上形成的游牧—农耕文明的生态界线,自然生态上差异导致了文化的差异,从而形成了文化特色截然不同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畲”作为原始的、粗放的耕作方式,与精耕细作的汉族农业也存在一条若隐若现的生态边界,这种自然生态的差异在族群文化特征上打上鲜明的烙印,这种迥异于“他者”的文化特征,成为“他者”族群观察另一个族群的切入点。根据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给文化所作的定义,文化应该包含了人类经历的各个方面①。按照这种定义,一个族群的文化特征应该包罗万象,而作为文字记载的族群,其呈现给后人的文化特征,充其量不过是一些静态的、被认为的诸多特征中较为典型的、有异于他者的特征。
笔者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农业的变迁认为,“畬(畲)田”的耕作方式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历史上除了那些被称为“畬田”民族外,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在某一历史阶段,也都曾经从事“畬田”农业“畬(烧)田”农业。之所以有“畬田”民族的称谓,其主要原因在于:随着汉族农业技术的发展,在汉族社会中,“畬田”的耕作方式逐渐被精耕细作农业所取代;而在一些非汉族群中,“畬田”农业作为一种技术要求不高、较易实施的粗放农业,仍一直被沿用。
随着代表农业文明的汉族文化不断扩张,“畬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在一定的区域内遭遇,由此产生了生态的冲突。这种冲突首先发生在两种生态文化的锋线,即在两种生态文化的边界地区是生态矛盾最集中的地方。在中国古代,长城沿线被视为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冲突最集中的地方,长城的分布与走向基本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生态系统的分界线。生态的冲突带来族群文化的冲突,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在历史上曾发生过族群冲突,长城正是这种族群文化冲突中的历史产物。“畬田”农业与精耕细作的冲突在唐宋时期成为一个显著问题,其中的一个表现是唐宋时期,许多有关“畬(畲)”的诗文中大量出现。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唐宋时期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不无关系:随着帝国华夏化进程加快,中国南方各个地区得到不同程度地开发,北方汉人带来的先进农业与被认为是原始农业残余的“畬田”农业遭遇时,这种文化冲击(cultureshock)使得“畬(畲)”作为一种猎奇、述异、诗化见诸汉人知识分子的笔端。
尽管也有大量诗人对“畬(畲)”不吝溢美之词,但无法改变整个主流文化对“畬(畲)”及从事该经济方式人群的看法,特别是当“畬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在资源上发生冲突且有所加剧时,“畬(畲)”作为一种文化标签常贴在那些从事“畬(畲)”田农业的非汉族群身上,目的就是将其边缘化,从而使其在生态、文化资源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正如韩起澜(EmilyHonig)在研究上海的苏北人时指出,历史上许多苏北人是移居上海的难民,棚户区居民或苦力劳工,但并不是每个被称为苏北人的都是来自江苏北部,精英集团曾对苏北人这个社会类别进行建构,“对于江南人来说,苏北身份的建构和归属部分地确立了一个类别,对照这个类别,他们就能界定自己并最终以上海人身份自诩。”①当然,也有一些苏北人不断建构自己在上海的身份,并有一些人对这种地域歧视进行抗争和抵制。刘志伟在对珠江三角洲“沙田一民田”族群格局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结论。②可以说,这种类似由“农村—城市”籍贯而产生的社会分层,并以某类人作为标签贴在一个族群上的社会现象,在各个时空中均能发现。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标签并不是刚开始就存在,我们以“农村—城市”分析:
第一,甲群体和乙群体刚开始均在农村地区,二者的经济文化特征差别不大,二者不存在较大的资源竞争关系;第二,甲群体所在区域由于自然生态、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原因,区域经济发展,成为城市;乙群体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变迁不大,仍是延续着农村的经济社会形态;第三,大量的乙群体进入甲群体所在区域,占用了甲群体所在区域的资源,并对甲群体资源占有造成一定的威胁;为了将乙群体边缘化,削弱其竞争力,甲群体建构乙群体的“标签”身份。这种构建其他群体社会类别的行为,目的在于提升甲群体的族群认同,从而达到对乙群体的控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甲群体对乙群体分类是基于其籍贯。殊不知,在本群体的数代或更早以前,自己的先祖也是与乙群体同类。当然,可能存在甲群体对本族先祖进行建构的问题,关于这点笔者将在稍后论述。
通过“农村—城市”结构转换的分析,反观“畬田农业—精耕细作农业”结构,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生态文化语境对于人群分类的重要性。掌握了发达农业技术的汉人,早已经将先祖曾从事的“畬田农业”选择性地失忆了,将南方一些非汉族群称之为“畲”,是汉文化语境下的产物。同样的,将聚落形态的“洞(峒)”作为一种族群分类,同样是文化建构的产物。
二、族群边界与文化认同
在生态边界冲突激烈地区,族群互动更为频繁,历史上许多新的族群,往往是在族群边界地区中孕育产生的。张之恒将中国划分为四个截然不同的经济文化区,除四个经济文化区之外,还存在着三个过渡地带或称文化交汇地带。①张之恒的“过渡地带”理论不仅仅在考古学上有创新意义,对族群理论研究也有借鉴意义。如张氏所提出的三个史前文化过渡地带,一直是各民族文化互动比较频繁地方,如阴山南侧及河套地区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交汇地带,后来著名的河湟民族走廊地区即产生于此。而本书研究重点区域闽粤赣交界地区,其处于南岭以北和武夷山以西地区过渡地带,在该区域中,多种族群文化交流频繁,这使得该地区成为新族群孕育的温床。从历史上看,唐宋时期的闽粤赣地区,其族群结构变化最为明显,学术界普遍认为,福佬、畲族、客家等族群均是在这一时期孕育形成的。②
按照传统的民族史观点,随着族群互动与融合,各个族群吸收对方的文化,继而形成了迥异于原族群组成部分的新族群。实际上,新的族群诞生于族群边界互动地带,不仅仅在于各种族群文化的融合的客观结果,还在于族群间主观认同的情况。这里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我群”对“他群”认识程度与情感;二是“我群”如何通过“他群”看待本族群。
春秋以后,华夏族形成了“天下—四方”“华—夷”的民族观。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华夏族经历了漫长的华夏化进程。华夏族对外扩张的过程,同时也是对“异族”不断接触与认识的过程。在以往研究中,学者常以某个族群出现于某文献中的时间作为该族群存在的标志,确切来讲,各类族群称谓的出现,更多的体现以华夏族为代表的主流人群对周边非主流人群的认识程度。因为,早在记载之前,这些族群的实体人口可能已经存在,但作为“异己”的共同体,是以华夏族为参照物后才形成的。
笔者以闽粤赣边区的一些非汉族群为例。如文献中曾载,在西晋至唐的闽粤赣地区,活跃着一类被称为“山都”“木客”的人群,这类人群在文献中的出现时间顺序,恰恰与中原王朝开疆拓土的时间顺序相一致。就当时的各种记载而言,“山都”“木客”作为一种“异类”而存在,其具有神秘的特性,按现在人种学观点来看,几乎可以将其归为“非人类”中。但是,作为文本记载中的文化事象,“山都”“木客”却是华夏族向南扩展时对一些非汉族群的一种历史记忆,其中可能包含着对“异族”的想象,这种想象是南下汉人对土著真实情况的一种误读,是对异族的不了解,或者接触后的形成的恐惧、厌恶等心理的一种投射。唐代以后“山都”“木客”的消亡,客观原因是其族群实体融入华夏族;而从主观认识角度看,其原因则为:随着华夏族对闽粤赣非汉族群认识水平的提高,原来一些想象的部分已无从考究,故不予记载。
因帝国深入边陲以及南方次第开发而引起思想认识变迁,这种现象多有存在,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古人关于瘴气、蛊毒等文化事象的认识。学者认为,文献中大量记载瘴气与区域开发程度有关,瘴气与其说是一种病理现象,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其中体现的是以汉人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南方各地区的认识情况。张文认为,所谓的“瘴气”或“瘴病”,更多反映的是中原文化对南方地区的地域偏见与族群歧视,①左鹏则认为“各地区瘴情的轻重差异,反映了此地为中原文化所涵化的深浅程度。”②再如“蓄蛊”现象,于赓哲认为关于“蛊毒”流行地的记载,其经历了从中原地区到南方土著地区移动的过程,并且,开发程度越早的南方土著地区越早脱离“蓄蛊之地”的恶名。③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中原地区对“南土卑湿”认识的变迁上,“南土卑湿”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其反映的是族群边界的动摇与移动。④
以上的研究说明,作为主流文化话语权的华夏族群,其对周边族群的认识程度是随着帝国开发而逐渐深入。不同族群开始接触后,族群意识渐渐产生,族群的自我认同由此增强。一般来讲,在族群接触较多地区,不同族群文化带来的文化冲击(cultureshock)使得双方族群意识到对方与我方差异的存在。这种意识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当中,能被文献记载下来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我们发现,文献记载在描述“他者”的文化特征时,总是要体现其与“我者”差异,而这种差异往往会被放大。这种以“他者”之“异”,来反衬“我者”之“同”的描述,体现的是族群的自我认同,是在华夷之别的民族观指导下的一种自觉的实践。
笔者在书中探讨了“畲”作为一种族群称谓首先出现在漳州、潮州地区的原因。南宋时期的漳州与潮州等地以“畲”为代表的溪洞种类活动的场所,但这些区域应该不是溪洞种类(与省民相对)的中心区域,而是族群边界地区。按照宋人刘克庄的描述,溪洞种类分布在漳、潮、梅、汀、赣等区域,从当时的族群格局看,漳州、潮州等地的溪峒种类位于与省民交错的地带,也就是在族群边界的地区。按照王明珂先生的研究,在族群边界地带,族群意识比族群中心地带更为强烈。漳州、潮州的边界区域地位使其成为“畲”、汉双方观察并认识对方族群的“前哨”;而在溪洞种类的中心地带之一的汀州,这些族群仍沿用唐代以来的对南方非汉族群的泛称,如“(峒)蛮”等称谓。南宋时期的漳州、潮州“畲”的族群文化特色比较明显,而随着族群边界的移动,原来的族群边界地区可能成为某族群的中心地区,明清以后,“畲”汉族群边界转移到闽东、浙南等地区,此时该地区的畲民族群意识比漳州、潮州等地畲民强烈得多。
可见,族群边界并非一成不变,其呈现出多变性、复杂性、重合性等特点。判断族群边界变化的情况,可以从族群边界双方的族群认同的变化的情况进行考察。宋元以后,闽粤赣地区的“畲”汉边界呈现飘忽不定的状态:其中既有畲民通过获得版籍成为编户齐民的情况,也有汉人通过“入山洞”,脱籍成为“畲”“瑶”族群的情况。这种族群边界的流动,一方面是社会人群的政治或文化身份发生变化,体现了官方关于族群分类的标准,以及如何对非汉族群进行社会定义;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各族群自我认同变化的一种结果。具体来讲,就官方而言,“峒”与“非峒”“畲”与“非畲”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纳税服役,是否接受教化,以及是否编入国家版籍。因此,在许多历史语境下,“畲”与“非畲”并不是严格的种族区分标准,其中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政治身份、文化身份的差别。
笔者在文中还以宋元以来的“畲乱”记载为例说明官方社会分类标准问题。实际上,在众多的“畲军”“畲寇”中,并不是全部由非汉族群组成,其中有不少人群通过打着“畲”的旗号,以此号召人群、凝聚人心、增加认同。也就是说,这群人在种族特征中,并非都是刘克庄的《漳州谕畲》文中所指的溪洞种类,但是,在特定社会情境或历史语境中,这个群体的人或者被官方以一定标准——通常是不纳赋税,不服从国家管理——认定为“畲”,或者这个群体的人在文化上转变了族群认同,从而自我认同为“畲”。
当然,在宋元“畲乱”中,畲民在与国家互动中,其文化认同常常出现反复性:或者归顺朝廷、被收编军队、安排屯田、获得版籍以及融入汉族等;或者反抗或归降后复叛,“依山险阻”“亡入畲洞”。以上两种选择显示了在华夏化运动过程中,以畲民为代表的南方非汉族群的不同文化认同取向。文化认同取向不同,其族群边界也会发生变化:其一,成为编户齐民的畲民,即所谓的“日山獠将化编氓”,这些原被称作“山獠”的非汉族群,久而久之成为了国家子民,这些成为“编氓”非汉族群与汉人之间的族群文化差别随着族群的融合慢慢缩小,这种趋势使得“汉”与“非汉”的族群边界开始变得模糊甚至消失殆尽;其二,那些不与政府合作的非汉族群,国家仍以“化外之民”视之,将其与“化内之民”严格区分开来,而这些非汉族群通常也以“化外之民”自居,或退守“山洞”,或迁移到更偏远的山区,这种情况下,“汉”与“非汉”的族群边界也因这类群体而存在,并随着这些非汉居民的活动轨迹而发生移动。
明中叶时期,华南地区进入了社会转型时期。该阶段畲汉边界的显著变化,成为畲族发展史中值得关注的内容。从明中叶开始,畲民的核心聚居区逐渐从闽粤赣地区转移至闽浙赣地区,这种变化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形成的。王阳明成功平定“畲乱”,闽粤赣地区开始由“乱”入“治”,大量的畲民或迁徙外地,或融入当地汉人之中。除了王阳明平定“畲乱”的推力外,明清时期的商业化进程起了拉力作用,区域经济分工使得大量的“畲客”在此期间迁入闽浙赣地区进行经济作物种植。另外,明末清初的“倭乱”与“迁界”为畲民迁居并扎根于闽东浙南地区提供了又一历史契机。
林校生根据畲民的历史记忆(主要以歌谣、族谱为载体)和畲民现代人口分布现状,将畲族族群的核心集居地按时间顺序分为“潮州中心期”“汀、漳中心期”“福宁府中心期”三个重要阶段。①实际上,这种所谓的“地区中心说”,是以某一历史时期该地区的畲族文化特征或者文化认同情况作为判断标准。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其一,在明清时期,从闽粤赣地区迁往闽浙赣地区的畲民,这些迁徙的人口占输出地畲民人口总数的比例到底有多大?其二,在明清以后,闽浙赣地区畲民文化特征、族群意识为何比闽粤赣地区畲民更为显著?
首先,在明清以后,在闽西南许多原为“畲区”的地方,后来慢慢变为“客区”,这种变化不能单纯地以畲民实质性的人口外迁来解释。实际上,汀州、漳州地区在明清时期,仍存在着许多(或疑似)畲民姓氏的巨家大族,有的成为当地望族。一些文献也表明,明清时期有大量畲民融入当地汉人,并逐渐成为土著,许多甚至“忘其所自来”。谢重光先生指出,明中叶以后,原来的赣闽粤交界地区畲族住区,如今几乎清一色是客家人的住区,①与以畲族外迁来解释此现象观点不同的是,谢先生认为更重要的因素应是畲民大部分转化为客家人了。②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需通过文化来解释,“应将其视为在汉文化认同的过程中,汉族的边界逐渐扩大、华夏边缘在东南的进一步扩张的结果。”③即:在强势的汉文化语境中,闽西南地区的许多畲民家族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汉文化,在明清时期,畲、汉族群文化认同趋于一致,导致了该地区的畲汉边界的模糊、偏移乃至消失。
其次,闽浙赣地区畲民的族群意识是在族群边界冲突中凸显出来的。明清时期,许多来自汀州等地的“畲客”大量迁入闽浙赣地区,成为蓝靛、苎麻等经济作物种植的主力军。这种人口的流动是地区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导致的必然结果,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对于流动人口输入地而言,大量的移民为本地增加了劳动力,尤其对于未开发地带或战后的地区,移民在地区开发以及恢复地方经济方面作用巨大。而流动人口的弊端在于其可能成为社会秩序的威胁者和破坏者。一方面,在古代中国,官方奉行重本抑末经济思想,大量土地用于经济作物种植可能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日益紧张的资源竞争使得“土”“客”矛盾愈发紧张。“畲客”作为一种流动人口,在某些地区一度受到土著的排挤,当地土著(主要是汉人)中的一些人主张严格区分土客边界,试图将“畲客”边缘化,在清代中期发生在闽东、浙南地区的“学额之争”,标志着土客矛盾达到顶点。与闽浙赣地区有着显著畲汉边界不同的是,在闽粤赣地区的一些畲民家族渐渐融入当地汉人社会之中,一些家族甚至出现了诸如雷鋐、蓝鼎元的知识分子。这些畲民家族在文教上取得的成绩不亚于周边汉人家族,其文化认同也显示出与当地汉人无特别大的差别。因此,在闽浙赣地区,其畲民的文化特色之所以比闽粤赣地区更鲜明,离不开两个因素:一是当地土著的族群分类及对当地畲民的社会定义(体现在对畲民的各种歧视称谓);二是当地畲民利用族群文化以凝聚人心,并对当地大汉族主义予以反抗与回击。
尽管在明清时期,闽浙赣地区的畲民体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征,但是在强势的汉文化以及华夏化进程的持续影响下,畲民的文化认同呈现出向汉文化靠拢总的趋势。这个趋势直到新的民族政策实行后被扭转过来,国家按照一定的民族识别标准,通过政治权力重新划定族群边界,畲族在1956年成为政治意义上的民族,自此之后,原来一些地区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畲族族群认同在各方的操作下变得越来越强烈,一度出现了恢复畲族身份的热潮。
畲客的共生关系和族群分野也体现了文化认同与族群边界的关系。竹村卓二引用鲍曼(BaumannHermann)的民族理论①后认为,畲民之所以被汉族称为“畲客”或“輋客”,说明畲、汉族的关系本来就非同一般。他称:“至少在中国对华中、华南非汉民族的称呼中,用‘客’这一概念来表示的,别无他例。这一点显示了畲民与边境尚未开化的原住民苗族和彝族略有不同,当然,对于土著汉族(主民)的社会来说,畲民是处于外来客民的地位。畲民对于汉族来说,现在与其说是应征服或驱逐的蛮夷,莫如说是保持一定社会距离,处于互通有无共生关系中的同伴的地位。”②王东先生也认为,在较长的历史时间中,畲汉族群融合,二者形成了密切的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同时是一种共变关系。“伴随着这种互动与共变,畲、汉双方在各自改变自己的同时,也在改变着对方。”③
在早期迁入的闽浙赣地区“畲客”中,既有畲民,也有客家人,他们统称为“客”。但是不管是政府,还是当地土著,对“客”的认识比较一致:或者以“客”称之,其中并没有清晰的畲族与客家身份的区分;或者统一以地名称之,如汀州人,借以区分籍贯。另外,也没有证据表明,来自汀州等地区的“畲客”之间形成了严格的“畲族”与“客家”的族群分类关系。这说明在明清之际初迁至闽浙赣地区的“畲客”,其不仅在经济方式等客观文化特征无太大差别,其主观的文化认同也比较一致。而当这些“畲客”慢慢安顿下来并定居,土、客矛盾逐渐升级后,“畲客”中的“畲”特征被凸显出来。
与以往闽浙赣地区迁徙的“畲客”文化认同有所区别的是,迁往两广等地区的“畲客”,“畲”特征并没有被凸显,其反映的更多是客家文化认同。这种现象的产生既与广府、客文化差异产生敌意有关,如广府人把客家人称为“匪”“犵”“獠”“猺”等,“或是直接在‘客’字上加上污辱性的‘犬’字偏旁,以示客家为野蛮民族,自以为与之水火不容。”①咸治同丰年间,广东一带爆发了大规模的土客大械斗,此后,客家运动逐渐在广东等地蓬勃兴起,“畲客”中的客家文化认同达到顶点,畲族认同反而不被彰显。直到20世纪80年代,整个广东地区的畲民文化认同总体仍不是特别强烈,对此周大鸣论述道:
广东东部是畲族传说中的文化中心,其凤凰山更被认同为畲族的发源地,可是在这场恢复畲族的运动中,广东反而没有其强烈。究其原因,首先与广东省政府没有强力推行恢复族属相关,其次粤东北是客家文化的中心,对客家文化的认同超越了其他族群的认同。②
我们认为,不同地区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对族群的特质具有重要决定作用。谢重光先生曾指出:“有什么样的生态环境(包括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就会有什么特质的人群,这个人群的文化也会鲜明地打上其生态环境的烙印。”③在不同区域中,生态、人文环境不同,族群的认同取向也可能有所不同,正如笔者前文所指出的,不同的文化取向最终导致了“畲”“客”成为两个比较独立的族群。一些特殊的历史事件,如明中叶社会转型加速了“畲”“客”族群的分离趋势。畲族与客家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紧密的关系,由于文化认同的差异,二者之间形成一道鲜明的族群边界,这也再一次证明文化取向对于区分族群的重要性。④
三、历史记忆与文化建构
费孝通先生在论述中国人际关系时,曾提出“差序格局”理论,这种差序格局类似“水波纹”。他说:“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①水波向外越推越远,一圈比一圈薄。在传统中国,用差序格局理论可以较为有效地解释其中复杂而又独特的人际网络关系。如果将每个族群看作一个人,差序格局理论在一定场合中也起作用,传统的华夏民族观正是这种差序格局的其中一个体现。也就是说,在传统华夏族心目中,以“中国”为中心,越往外层的区域越蛮荒,其所在地区的族群也更难被教化。这种以地理区域作为划分族群类别的标准,在中国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存在着,诸如对“南蛮”的族群印象曾长期存在于古代中原人历史记忆中。
然而,这种族群印象可能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生移动和变迁。如春秋以前,位于长江中游的楚人、长江下游的吴人和越人均不在华夏集团之内,随着楚、吴、越三个南方政治集团完成华夏化,华夏的边缘移至这三个族群势力的外缘。换句话说,当楚人等族群完成华夏化,华夏边缘外移,原来用作楚人族群称谓的“蛮夷”,此时已不再适用,而是套用于更偏远边陲地区的非华夏人群中。就此而言,华夏边缘的移动,并不一定是华夏族人口实质性的迁移,有可能是非华夏人群通过文化认同的转变成为华夏族成员,从而导致华夏族心目中的“异族”向外扩展。正如王明珂指出,一些非华夏人群通过攀附实现手段,将本族血缘与“黄帝子孙”联系起来,或者是将迁居祖先的地域与中原发生联系,建构出“英雄徙边”或“弟兄民族”的历史。②就华南地区汉人而言,其历史建构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南方土著或南迁汉人关于“汉人”正统身份的建构。在以华夏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中,华南地区长期处于帝国的边缘,其所在地区的居民在文化阶序上从属于中原地区的人群。为了提升当地土著的族群身份,最重要的是证明自己与中原汉人的联系。在与国家、地方社会的互动中,当地土著通过主动向中原王朝靠拢,协助政府在该地区建立政治机构,使地区完成华夏化进程。于是在帝国“差序格局”中,该地区离帝国的中心又近了一圈,本地居民借此完成了从“化外”向“化内”的转变。除了将本地区与中原中心发生联系外,在家族层面,本地土著或南迁汉人还通过“攀附”的手段对先祖进行建构,将本家族的迁居地、迁居祖先与中原发生联系,向本族和外界宣称“黄帝后裔”的中原正统身份,这也是许多南方汉人族谱在追溯祖源时较为普遍的叙述模式。
其二,对本地区的“蛮夷”族群进行分类与建构。唐宋以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福建等南方地区的政治地位较以前的“蛮荒之地”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与之同时进行的是该地区“汉人”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体现在此时该地区出现了大量关于“蛮”“蜑”等非汉族群的记载,即作为“他者”的“蛮”“蜑”,其出现证明了“我族”意识的存在。南方土著或南迁汉人通过建构“蛮夷”的族群分类,将“蛮夷”边缘化,并与“蛮夷”划清界限,目的也是想证明本族群正统的“汉人”身份,如前文所指出的,陈元光平蛮正是这种族群分类建构的产物。
在华夏化进程中,畲民也通过两种途径维护本族群利益。其一,利用本族文化,增强族群认同,与大汉族主义进行抗争。这种抗争可以体现在畲民关于盘瓠传说以及其衍生物如《开山公据》《高皇歌》、龙头杖、祖图等文化的理解、坚持与传承上。如畲民对历史上的盘瓠传说进行二次加工,认为本族具有三公主高贵的血统,还有王朝恩赐的特权等,借此宣扬本族光辉历史与传统;再如《高皇歌》通过对“阜老”(福佬或汉人)“恶”的形象的塑造,还告诫本族不能与“阜老”交往等,借此建构了“阜老”与本族严格的族群边界。在这种文化解释体系中,畲民通过夸大族群差异,来激发本民族的族群意识,从而增强文化认同感。
另一方面,在强势的汉文化中,特别是在华夏化进程中,畲民不得不进行族群历史的建构,以提升族群地位。如在明清以后,畲民有意识地对盘瓠的形象进行改造,盘瓠以“龙”“麒麟”“凤凰”等形象出现,并回避“犬”的形象;再如,畲民将一些历史人物进行塑造,如雷海青、雷万春、南霁云、钟景期等,使其成为本民族的英雄祖先。随着畲民族谱修撰的流行,畲民同周围汉民一样,对祖源进行建构,使其在血缘上与“黄帝子孙”发生联系,在地缘上打通与中原的关系。通过这种族群建构,一些地区畲民在文化认同上渐渐发生变化,表现出国家的认同与对汉文化的认同。畲汉之间的族群界线进一步发生漂移、模糊化甚至消失。
四、近代以来畲汉族群边界的再造
明清以后,定居后的畲民慢慢地融入当地社会,其经济、文化等特征越来越多地与周边汉族没有太大差别。清代至民国,文献对各地畲民记载呈现出减少的趋向,本身也表明了各地畲汉族群边界有移动和消失的迹象。
在民国时期,官方对福建等地的畲民统称为“苗民”或“苗族”,这种族称的转变与当时政府的民族思想与民族政策是分不开的,同时与清末以后的民族主义思潮不无关系。
清末民初,在巨大的民族危机下,许多知识分子寻求“国族”建构,如梁启超提出史学的任务就是要激发民众的国家意识,①“炎黄子孙”“黄帝世胄”“五族统一”成为当时的流行话语。政府和一些学者主张“同化”(所谓的“五族统一”即是该思想的表现),认为“少数民族”的调查和研究不能“刺激国族分化”,因此,当时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主要是以“安边”“治边”为要的“边政”研究。②
这种“五族统一”“五族共和”的思想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颇为流行,在民国初期修纂的畲族族谱中体现了这种思想。如上杭《雷氏梓福公家谱》在“凡例”中写道:“此谱议修于光复前一年,购工庀材,择吉开雕,越十有五月而告成。五族适于是年统一,是此谱诚为民国成立一大纪念,故于卷首敬刊国旗,用志盛事。”③一些接受新思想的畲族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在族谱中宣扬“五族共和”思想,如上杭雷氏第十九代裔孙雷熙春、雷晓春在“序”中称:
岁辛亥(1911年,笔者注),吾族有修谱之举……且此谱之作与民国之成立固有绝大关系者。吾族得姓实在黄帝纪元之世,源流最古。远祖方雷氏佐黄帝南征北伐,纯然民族主义,功德留荫,历世已四千六百余年,虽期间丧乱频仍,叠经变故,而忠孝节义之士犹复昶望于史册。方吾一世祖梓福公之生也,当赵宋末造,时适胡元入主中夏,窃据神器,因挚眷避地卜居于此,优游金山摺水间者九十载。追明太祖定鼎金陵,汉族光复,始考终牗下。迄明、清二代,族中科名仕宦于今为盛,而士大夫博学识能文章者,先后修谱两次,曾未昌言民族主义。为详考吾族得姓之缘,纪以志诸谱牒,知其慑服于专制余威者为已殁矣。乃者五族统一,政更共和,举黄帝手定之锦绣河山悉以还诸黄帝世胄,而此谱适于是年秋月以成。由是濡毫吮墨,畅所欲言,俾吾祖吾宗萦抱民族思想,得于序录中表白一二。①
该序描述了黄帝征伐异族、胡元入主中夏、明代汉族光复、民国政更共和等历史事件,反映的是清末民初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想,这种社会思潮经知识分子的宣传慢慢渗透到一般家族中,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民国元年,上杭雷赞明在“序”中称“今民国新立,治尚共和,神明之胄四万万皆同胞矣。”雷庭瑞在《重修梓福公新谱告成序》也称:“今岁五月开局编印,新谱告成值民国新纪元,谨进一言以志盛举。曰,共和成立,五族大同,汉满蒙回藏为一家,是亲爱家族之观念尤当推而远之,不仅在一姓一族也。五族者千万姓之所积,人人各亲爱其同姓,思扶掖而促进之,知非保五族则一族姓不能独立,于是互相扶掖,互相促进,此爱同胞、爱祖国者所不能违之公例也。”②
当时国民政府主张民族同化,鼓励边疆非汉人群汉化。在这种民族政策的指导下,官方并未将分布在福建等地区的畲民视为一个比较独立的、具有政治意义的民族,而是笼统地以苗族称之。实际上,关于对南方民族以“苗”“瑶(徭)”等族称泛称,在明清以前十分常见,这大概类似于更早之前,中原王朝将南方地区的族群泛称为“蛮”“越”“獠”等。应该来讲,这些族群内部存在较大差异,族群间具有一定的族群边界,如“越”又称“百越”,足以说明各个地区的族群是有一定区别的人群集团。将这些族群泛称为“蛮”“越”等,说明对于华夏族而言,或者是由于族群的接触与认识还不够,无法对这些族群内部的差别进行更详细地分,或者即使其群体内部有一些区别,但在华夏族心目中,这些差异可以忽略不计。即在“华夷之辨”的语境中,所谓的“蛮”“越”“苗”等无非是作为“华”的对立面而存在,二者形成了“文明”—“野蛮”的文化政治结构。杨志强在分析近代苗族形成问题时指出,明清以后,常将“苗”“苗种”作为南方各省非汉系族群的泛称,而“作为一种汉民族对于异族的称谓,这里所说的‘种’代表的是一种‘华’与‘夷’区别的模糊的文化境界,而并不是现今意义上所看到的‘种族’或‘民族’。”①
在民国时期,福建各地的畲民在官方上被称为“苗族”,如1937年《各县区苗夷民族概况》描述了连江、福鼎、顺昌三地“苗夷民族”情况,这些“苗夷民族”实际上多为畲民,其中连江有23个畲民村落,主要是迁徙自漳浦蓝、雷畲民,这些畲民在女子服饰上具有与汉族不同的装束特征,“清初与汉人通婚,在咸丰时代,苗族生活颇裕,中有田租收至三千余担者,今则已衰落。”到民国时代畲民业已与汉人同化。②
成立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山民会馆(后改为三明会馆),是闽东浙南“山民”联络议事之所。1946年,闽东畲族宗人商议重兴三明会馆,蓝玉轩等向所在地霞浦县政府提交申请报告,业经县长刘仇签署,呈报省政府核准在案,成为官方〓册认定的“苗夷民族”(按当时《福建年鉴》之称)“公益团体组织”。③由此可见,当时的闽东畲民被官方认定为“苗夷民族”,而不被认为是“畲族”。
1947年12月8日《福建省政府关于送边疆民族及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状况调查表给内政部电》关于苗族连江、罗源、顺昌、漳平、周宁等县,人口也相应增加。同时在注明备考注明:“苗族俗称畲民,间有与汉人同化者。”④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30—40年代,政府也将水上居民(疍民)作为“边疆民族及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上报国家有关部门。⑤苗族作为畲族的称呼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年时间还在官方的报告中出现,如1952年7月8日写成的《畲族福安县仙岭洋村调查情况》中,认为国民党大汉族主义进行民族压迫、歧视和侮辱,故意歪曲其历史,而另一方面,畲族限于文化,对本民族历史也不甚了解,“只认为苗民称号较臭畲人(臭蛇人)好,这是畲族改称苗族之始。”又称:
解放后来自北方干部,过去接触少数民族不多,对当地畲族未曾详尽调查,了解该民族历史,以及民族特征,只因他们语言不同,妇女装饰奇异,居住高山,称之苗民……在国民党大汉族主义消灭同化政策压迫下,曾经强迫改变民族服装,于民国十二三年间改穿汉服,藉以躲避欺视,不易辨别他们是畲民。女的虽略有改变,但仍然保持民族装饰。①
1952—1953年,漳平县、闽侯县提交的报告也均把本地畲民称为“苗族”②。1953年12月9日,在一份由福安地委统战部提交的报告中,还显示了当地畲民对于要将本族命名为“畲族”存在不满的情绪。报告称当时畲民有“苗族”“瑶族”“山宅”“三民”等名称,但畲民本身不承认自己为“畲族”,原因主要是历代反动统治(国民政府采取的是同化政策)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残存的民族隔阂没有彻底消除,加上当时南下干部不了解情况称畲民为“苗族”,福安地委统战部根据1951年在福安仙岩乡从该族家谱调查后认为“畲族”名称是正确的,这引起了当时畲族百姓的反对。③直到1956年9月9日《中共福安县委统战部关于少数民族名称问题的报告》仍坚持不使用畲族这个民族称号。④随着1956年中央统战部下发《关于确定畲民民族成分问题》,关于畲民名称的争论才渐渐停息下来。⑤并在1956年12月8日经中共中央统战部最后确定畲族的民族成份和民族名称。⑥至此,畲族作为一个族称在国家的政策下推行,而关于畲族的民族认同的过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闽西南一些地区接受程度较快,①而闽东一些地区则经历较长一段时间磨合,才最终接受,如在确定族称的两年多以后的1958年10月1日的《宁德县南山片畲族调查报告》仍在讨论畲族民族名称的几个来源与畲民态度。②1958年10月5日的《罗源县苗民情况报告》仍将畲族称为苗民③。而一些地区,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对畲民族称表示不满。④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称畲民为“苗民”与国民党政府的民族政策有一定关系,另外一些因畲汉矛盾给畲民带来情感伤害的地区,也希望用“苗族”等泛称替代原来被标签化了的“畲”族。笔者大胆推论,假如没有后来学术界的努力和国家政策的推行,部分畲民将可能被官方划分为“苗族”,也有可能在提倡“五族共和”以及民族同化的政策下,更多的畲民走向汉化,从而导致族群意识不彰显。正如疍民融入汉人之中,而在此之前,畲、疍均作为福建地区比较特殊的族群一并被论述⑤。当然,历史无法推论。在新中国民族政策的推行下,地方政府、学术界、各地的畲民(或疑似畲民)精英参与了新的族群边界的制造。
就国家和学术界而言,他们希望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标准来开展民族识别、民族身份恢复工作。民族学者施联朱参加了畲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他在《解放以来畲族研究综述》指出,“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为畲族识别工作重要因素。”①并强调不能单以民族姓氏定民族成分,他说:“我们说畲族主要有盘、蓝、雷、钟四大姓,不等于说四大姓全是畲族,姓氏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共同体,而民族则是以地缘为基础的人们共同体,把姓氏视为民族特征的主要标志之一,是错误的。”②
这种看似科学的民族识别标准却不能完全解决民族识别和民族恢复中的实际困难如何判断一个地方族群的民族特点是否足以被认定为畲族,需要当地族人支持与材料证明、地方政府的调研与申报以及相应政府部门审批与认定。但如果在一些地方原畲民住区的居民对被认定为畲族热情不高,或者当地民族部门投入不足,或者国家认定族群身份根据上报材料与若干调研,其中也不能保证完全做到十分客观。因此,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在族谱记载中有较为亲近血缘关系的姓氏,存在着一个地方宗姓被认定为畲族,而另一个地方宗姓却未被认定为畲族的情况。③
但是,在族群认同工具主义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的地区人群为能被确认为畲族而努力。1964年9月5日《福安专署关于政和、松溪少数民族称谓问题的调查报告》说明了政和县雷姓族人要求恢复畲族族称的由来,该文写道:
政和县雷华泉于1953年参加建阳专区少数民族代表会,体会到党的民族政策的英明:1963年他堂兄雷成寿从建阳籍到政和来谈起有关历年来闽北地区党对畲族人民的关怀以及闽东地区民族工作情况,他们得到很大启发,所以积极要求恢复族称。松溪县畲族曾向区里要求解决族称问题。①
从这份报告,可以看出政和县雷华泉通过了解国家的民族政策积极要求恢复族称,族群内部精英的运作使得该地区的畲民得以确认为畲族的政治身份。
近年来的一些研究也证明,一些畲民为了被确定畲族的政治身份,不断对本民族的历史进行重构。如周大鸣在赣南地区田野调查中发现,一些原属客家的蓝、雷、钟姓在20世纪80年代恢复成畲族后进行族群重构,他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恢复成赣南畲族的族谱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在1985年以前的族谱中,每一次族谱的序言有一个逐步‘汉化’‘正统化’的过程,受‘大传统’影响的烙印不断明显。而1985年后修的族谱则是‘畲化’的过程,透过这些‘精英文化’的变化历程,可以再现一个族群的变迁。”②杨晋涛在研究闽西蓝姓居民的“畲族意识”时也提出:“就武平的情况来看,没有国家民族平等的理念和政策,一个已经汉化,其身份已被周围汉人认可,并且一度以汉人自认的群体,不会无端重提祖先,并力求恢复先民身份;同时,未能掌握相当的历史文化资源,就要求国家对自己的特殊身份给予认可,势必也不可能。”③
如果说历史上畲民为了淡化畲汉边界不断建构族群历史向汉文化靠拢的话,那么,在新的民族政策下,更多的畲民为争取被确定为畲族的政治身份做出不懈努力,而由国家、地方、学术界以及民间多方合力推行的文化展演,无不都是在强化业已形成的族群边界,这种看似截然相反的族群现象,却是各个族群在不同历史情境下做出的相同反应。
一、生态文化语境与族群分类
在古代中国,由于受到大一统观念的影响,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民族史的撰述,都体现出了诸如“夷夏同祖认同、华夷一家认同、共属中国认同、华夏文化认同”的大一统意识。①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华夏文化在几千年的民族史撰述中一直处于被表述的中心,四方“夷狄”则处于从属地位。而在具体实践中,华夏民族自春秋战国以后,在与周边非华夏民族的互动过程中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表现为华夏族及其文化不断向边陲扩张,最终使得各个非华夏民族淹没在华夏族的“海洋”中,或者成为“华夏海洋”中的“非华夏孤岛”。
因此,在重新审视我国古代民族史时,我们必须将历代有关于“非华夏”族群的文字记载置于当时的社会情境来分析,具体来说:一是在汉文化语境下,这种记载多大程度反映了文字记载者的立场、态度及情感,而作为文本的历史记忆,其又反映了当时什么样的历史心性?二是这种记载中的文化特征,是否能够反映“异族”的实际情况,即这种客观的文化特征描述能否与“异族”的实际认同情况相一致?或者说,对“他者”只是文字记载者单方面的认同?
本书认为,“畲”作为一个南方非汉族群,其在历史上出现并非偶然,需要在生态语境和文化语境下对其作一番考察。
首先,自然生态是任何一种族群和文化产生的最基础因素。正如我国历史上形成的游牧—农耕文明的生态界线,自然生态上差异导致了文化的差异,从而形成了文化特色截然不同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畲”作为原始的、粗放的耕作方式,与精耕细作的汉族农业也存在一条若隐若现的生态边界,这种自然生态的差异在族群文化特征上打上鲜明的烙印,这种迥异于“他者”的文化特征,成为“他者”族群观察另一个族群的切入点。根据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给文化所作的定义,文化应该包含了人类经历的各个方面①。按照这种定义,一个族群的文化特征应该包罗万象,而作为文字记载的族群,其呈现给后人的文化特征,充其量不过是一些静态的、被认为的诸多特征中较为典型的、有异于他者的特征。
笔者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农业的变迁认为,“畬(畲)田”的耕作方式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历史上除了那些被称为“畬田”民族外,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在某一历史阶段,也都曾经从事“畬田”农业“畬(烧)田”农业。之所以有“畬田”民族的称谓,其主要原因在于:随着汉族农业技术的发展,在汉族社会中,“畬田”的耕作方式逐渐被精耕细作农业所取代;而在一些非汉族群中,“畬田”农业作为一种技术要求不高、较易实施的粗放农业,仍一直被沿用。
随着代表农业文明的汉族文化不断扩张,“畬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在一定的区域内遭遇,由此产生了生态的冲突。这种冲突首先发生在两种生态文化的锋线,即在两种生态文化的边界地区是生态矛盾最集中的地方。在中国古代,长城沿线被视为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冲突最集中的地方,长城的分布与走向基本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生态系统的分界线。生态的冲突带来族群文化的冲突,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在历史上曾发生过族群冲突,长城正是这种族群文化冲突中的历史产物。“畬田”农业与精耕细作的冲突在唐宋时期成为一个显著问题,其中的一个表现是唐宋时期,许多有关“畬(畲)”的诗文中大量出现。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唐宋时期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不无关系:随着帝国华夏化进程加快,中国南方各个地区得到不同程度地开发,北方汉人带来的先进农业与被认为是原始农业残余的“畬田”农业遭遇时,这种文化冲击(cultureshock)使得“畬(畲)”作为一种猎奇、述异、诗化见诸汉人知识分子的笔端。
尽管也有大量诗人对“畬(畲)”不吝溢美之词,但无法改变整个主流文化对“畬(畲)”及从事该经济方式人群的看法,特别是当“畬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在资源上发生冲突且有所加剧时,“畬(畲)”作为一种文化标签常贴在那些从事“畬(畲)”田农业的非汉族群身上,目的就是将其边缘化,从而使其在生态、文化资源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正如韩起澜(EmilyHonig)在研究上海的苏北人时指出,历史上许多苏北人是移居上海的难民,棚户区居民或苦力劳工,但并不是每个被称为苏北人的都是来自江苏北部,精英集团曾对苏北人这个社会类别进行建构,“对于江南人来说,苏北身份的建构和归属部分地确立了一个类别,对照这个类别,他们就能界定自己并最终以上海人身份自诩。”①当然,也有一些苏北人不断建构自己在上海的身份,并有一些人对这种地域歧视进行抗争和抵制。刘志伟在对珠江三角洲“沙田一民田”族群格局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结论。②可以说,这种类似由“农村—城市”籍贯而产生的社会分层,并以某类人作为标签贴在一个族群上的社会现象,在各个时空中均能发现。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标签并不是刚开始就存在,我们以“农村—城市”分析:
第一,甲群体和乙群体刚开始均在农村地区,二者的经济文化特征差别不大,二者不存在较大的资源竞争关系;第二,甲群体所在区域由于自然生态、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原因,区域经济发展,成为城市;乙群体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变迁不大,仍是延续着农村的经济社会形态;第三,大量的乙群体进入甲群体所在区域,占用了甲群体所在区域的资源,并对甲群体资源占有造成一定的威胁;为了将乙群体边缘化,削弱其竞争力,甲群体建构乙群体的“标签”身份。这种构建其他群体社会类别的行为,目的在于提升甲群体的族群认同,从而达到对乙群体的控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甲群体对乙群体分类是基于其籍贯。殊不知,在本群体的数代或更早以前,自己的先祖也是与乙群体同类。当然,可能存在甲群体对本族先祖进行建构的问题,关于这点笔者将在稍后论述。
通过“农村—城市”结构转换的分析,反观“畬田农业—精耕细作农业”结构,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生态文化语境对于人群分类的重要性。掌握了发达农业技术的汉人,早已经将先祖曾从事的“畬田农业”选择性地失忆了,将南方一些非汉族群称之为“畲”,是汉文化语境下的产物。同样的,将聚落形态的“洞(峒)”作为一种族群分类,同样是文化建构的产物。
二、族群边界与文化认同
在生态边界冲突激烈地区,族群互动更为频繁,历史上许多新的族群,往往是在族群边界地区中孕育产生的。张之恒将中国划分为四个截然不同的经济文化区,除四个经济文化区之外,还存在着三个过渡地带或称文化交汇地带。①张之恒的“过渡地带”理论不仅仅在考古学上有创新意义,对族群理论研究也有借鉴意义。如张氏所提出的三个史前文化过渡地带,一直是各民族文化互动比较频繁地方,如阴山南侧及河套地区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交汇地带,后来著名的河湟民族走廊地区即产生于此。而本书研究重点区域闽粤赣交界地区,其处于南岭以北和武夷山以西地区过渡地带,在该区域中,多种族群文化交流频繁,这使得该地区成为新族群孕育的温床。从历史上看,唐宋时期的闽粤赣地区,其族群结构变化最为明显,学术界普遍认为,福佬、畲族、客家等族群均是在这一时期孕育形成的。②
按照传统的民族史观点,随着族群互动与融合,各个族群吸收对方的文化,继而形成了迥异于原族群组成部分的新族群。实际上,新的族群诞生于族群边界互动地带,不仅仅在于各种族群文化的融合的客观结果,还在于族群间主观认同的情况。这里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我群”对“他群”认识程度与情感;二是“我群”如何通过“他群”看待本族群。
春秋以后,华夏族形成了“天下—四方”“华—夷”的民族观。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华夏族经历了漫长的华夏化进程。华夏族对外扩张的过程,同时也是对“异族”不断接触与认识的过程。在以往研究中,学者常以某个族群出现于某文献中的时间作为该族群存在的标志,确切来讲,各类族群称谓的出现,更多的体现以华夏族为代表的主流人群对周边非主流人群的认识程度。因为,早在记载之前,这些族群的实体人口可能已经存在,但作为“异己”的共同体,是以华夏族为参照物后才形成的。
笔者以闽粤赣边区的一些非汉族群为例。如文献中曾载,在西晋至唐的闽粤赣地区,活跃着一类被称为“山都”“木客”的人群,这类人群在文献中的出现时间顺序,恰恰与中原王朝开疆拓土的时间顺序相一致。就当时的各种记载而言,“山都”“木客”作为一种“异类”而存在,其具有神秘的特性,按现在人种学观点来看,几乎可以将其归为“非人类”中。但是,作为文本记载中的文化事象,“山都”“木客”却是华夏族向南扩展时对一些非汉族群的一种历史记忆,其中可能包含着对“异族”的想象,这种想象是南下汉人对土著真实情况的一种误读,是对异族的不了解,或者接触后的形成的恐惧、厌恶等心理的一种投射。唐代以后“山都”“木客”的消亡,客观原因是其族群实体融入华夏族;而从主观认识角度看,其原因则为:随着华夏族对闽粤赣非汉族群认识水平的提高,原来一些想象的部分已无从考究,故不予记载。
因帝国深入边陲以及南方次第开发而引起思想认识变迁,这种现象多有存在,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古人关于瘴气、蛊毒等文化事象的认识。学者认为,文献中大量记载瘴气与区域开发程度有关,瘴气与其说是一种病理现象,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其中体现的是以汉人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南方各地区的认识情况。张文认为,所谓的“瘴气”或“瘴病”,更多反映的是中原文化对南方地区的地域偏见与族群歧视,①左鹏则认为“各地区瘴情的轻重差异,反映了此地为中原文化所涵化的深浅程度。”②再如“蓄蛊”现象,于赓哲认为关于“蛊毒”流行地的记载,其经历了从中原地区到南方土著地区移动的过程,并且,开发程度越早的南方土著地区越早脱离“蓄蛊之地”的恶名。③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中原地区对“南土卑湿”认识的变迁上,“南土卑湿”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其反映的是族群边界的动摇与移动。④
以上的研究说明,作为主流文化话语权的华夏族群,其对周边族群的认识程度是随着帝国开发而逐渐深入。不同族群开始接触后,族群意识渐渐产生,族群的自我认同由此增强。一般来讲,在族群接触较多地区,不同族群文化带来的文化冲击(cultureshock)使得双方族群意识到对方与我方差异的存在。这种意识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当中,能被文献记载下来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我们发现,文献记载在描述“他者”的文化特征时,总是要体现其与“我者”差异,而这种差异往往会被放大。这种以“他者”之“异”,来反衬“我者”之“同”的描述,体现的是族群的自我认同,是在华夷之别的民族观指导下的一种自觉的实践。
笔者在书中探讨了“畲”作为一种族群称谓首先出现在漳州、潮州地区的原因。南宋时期的漳州与潮州等地以“畲”为代表的溪洞种类活动的场所,但这些区域应该不是溪洞种类(与省民相对)的中心区域,而是族群边界地区。按照宋人刘克庄的描述,溪洞种类分布在漳、潮、梅、汀、赣等区域,从当时的族群格局看,漳州、潮州等地的溪峒种类位于与省民交错的地带,也就是在族群边界的地区。按照王明珂先生的研究,在族群边界地带,族群意识比族群中心地带更为强烈。漳州、潮州的边界区域地位使其成为“畲”、汉双方观察并认识对方族群的“前哨”;而在溪洞种类的中心地带之一的汀州,这些族群仍沿用唐代以来的对南方非汉族群的泛称,如“(峒)蛮”等称谓。南宋时期的漳州、潮州“畲”的族群文化特色比较明显,而随着族群边界的移动,原来的族群边界地区可能成为某族群的中心地区,明清以后,“畲”汉族群边界转移到闽东、浙南等地区,此时该地区的畲民族群意识比漳州、潮州等地畲民强烈得多。
可见,族群边界并非一成不变,其呈现出多变性、复杂性、重合性等特点。判断族群边界变化的情况,可以从族群边界双方的族群认同的变化的情况进行考察。宋元以后,闽粤赣地区的“畲”汉边界呈现飘忽不定的状态:其中既有畲民通过获得版籍成为编户齐民的情况,也有汉人通过“入山洞”,脱籍成为“畲”“瑶”族群的情况。这种族群边界的流动,一方面是社会人群的政治或文化身份发生变化,体现了官方关于族群分类的标准,以及如何对非汉族群进行社会定义;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各族群自我认同变化的一种结果。具体来讲,就官方而言,“峒”与“非峒”“畲”与“非畲”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纳税服役,是否接受教化,以及是否编入国家版籍。因此,在许多历史语境下,“畲”与“非畲”并不是严格的种族区分标准,其中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政治身份、文化身份的差别。
笔者在文中还以宋元以来的“畲乱”记载为例说明官方社会分类标准问题。实际上,在众多的“畲军”“畲寇”中,并不是全部由非汉族群组成,其中有不少人群通过打着“畲”的旗号,以此号召人群、凝聚人心、增加认同。也就是说,这群人在种族特征中,并非都是刘克庄的《漳州谕畲》文中所指的溪洞种类,但是,在特定社会情境或历史语境中,这个群体的人或者被官方以一定标准——通常是不纳赋税,不服从国家管理——认定为“畲”,或者这个群体的人在文化上转变了族群认同,从而自我认同为“畲”。
当然,在宋元“畲乱”中,畲民在与国家互动中,其文化认同常常出现反复性:或者归顺朝廷、被收编军队、安排屯田、获得版籍以及融入汉族等;或者反抗或归降后复叛,“依山险阻”“亡入畲洞”。以上两种选择显示了在华夏化运动过程中,以畲民为代表的南方非汉族群的不同文化认同取向。文化认同取向不同,其族群边界也会发生变化:其一,成为编户齐民的畲民,即所谓的“日山獠将化编氓”,这些原被称作“山獠”的非汉族群,久而久之成为了国家子民,这些成为“编氓”非汉族群与汉人之间的族群文化差别随着族群的融合慢慢缩小,这种趋势使得“汉”与“非汉”的族群边界开始变得模糊甚至消失殆尽;其二,那些不与政府合作的非汉族群,国家仍以“化外之民”视之,将其与“化内之民”严格区分开来,而这些非汉族群通常也以“化外之民”自居,或退守“山洞”,或迁移到更偏远的山区,这种情况下,“汉”与“非汉”的族群边界也因这类群体而存在,并随着这些非汉居民的活动轨迹而发生移动。
明中叶时期,华南地区进入了社会转型时期。该阶段畲汉边界的显著变化,成为畲族发展史中值得关注的内容。从明中叶开始,畲民的核心聚居区逐渐从闽粤赣地区转移至闽浙赣地区,这种变化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形成的。王阳明成功平定“畲乱”,闽粤赣地区开始由“乱”入“治”,大量的畲民或迁徙外地,或融入当地汉人之中。除了王阳明平定“畲乱”的推力外,明清时期的商业化进程起了拉力作用,区域经济分工使得大量的“畲客”在此期间迁入闽浙赣地区进行经济作物种植。另外,明末清初的“倭乱”与“迁界”为畲民迁居并扎根于闽东浙南地区提供了又一历史契机。
林校生根据畲民的历史记忆(主要以歌谣、族谱为载体)和畲民现代人口分布现状,将畲族族群的核心集居地按时间顺序分为“潮州中心期”“汀、漳中心期”“福宁府中心期”三个重要阶段。①实际上,这种所谓的“地区中心说”,是以某一历史时期该地区的畲族文化特征或者文化认同情况作为判断标准。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其一,在明清时期,从闽粤赣地区迁往闽浙赣地区的畲民,这些迁徙的人口占输出地畲民人口总数的比例到底有多大?其二,在明清以后,闽浙赣地区畲民文化特征、族群意识为何比闽粤赣地区畲民更为显著?
首先,在明清以后,在闽西南许多原为“畲区”的地方,后来慢慢变为“客区”,这种变化不能单纯地以畲民实质性的人口外迁来解释。实际上,汀州、漳州地区在明清时期,仍存在着许多(或疑似)畲民姓氏的巨家大族,有的成为当地望族。一些文献也表明,明清时期有大量畲民融入当地汉人,并逐渐成为土著,许多甚至“忘其所自来”。谢重光先生指出,明中叶以后,原来的赣闽粤交界地区畲族住区,如今几乎清一色是客家人的住区,①与以畲族外迁来解释此现象观点不同的是,谢先生认为更重要的因素应是畲民大部分转化为客家人了。②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需通过文化来解释,“应将其视为在汉文化认同的过程中,汉族的边界逐渐扩大、华夏边缘在东南的进一步扩张的结果。”③即:在强势的汉文化语境中,闽西南地区的许多畲民家族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汉文化,在明清时期,畲、汉族群文化认同趋于一致,导致了该地区的畲汉边界的模糊、偏移乃至消失。
其次,闽浙赣地区畲民的族群意识是在族群边界冲突中凸显出来的。明清时期,许多来自汀州等地的“畲客”大量迁入闽浙赣地区,成为蓝靛、苎麻等经济作物种植的主力军。这种人口的流动是地区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导致的必然结果,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对于流动人口输入地而言,大量的移民为本地增加了劳动力,尤其对于未开发地带或战后的地区,移民在地区开发以及恢复地方经济方面作用巨大。而流动人口的弊端在于其可能成为社会秩序的威胁者和破坏者。一方面,在古代中国,官方奉行重本抑末经济思想,大量土地用于经济作物种植可能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日益紧张的资源竞争使得“土”“客”矛盾愈发紧张。“畲客”作为一种流动人口,在某些地区一度受到土著的排挤,当地土著(主要是汉人)中的一些人主张严格区分土客边界,试图将“畲客”边缘化,在清代中期发生在闽东、浙南地区的“学额之争”,标志着土客矛盾达到顶点。与闽浙赣地区有着显著畲汉边界不同的是,在闽粤赣地区的一些畲民家族渐渐融入当地汉人社会之中,一些家族甚至出现了诸如雷鋐、蓝鼎元的知识分子。这些畲民家族在文教上取得的成绩不亚于周边汉人家族,其文化认同也显示出与当地汉人无特别大的差别。因此,在闽浙赣地区,其畲民的文化特色之所以比闽粤赣地区更鲜明,离不开两个因素:一是当地土著的族群分类及对当地畲民的社会定义(体现在对畲民的各种歧视称谓);二是当地畲民利用族群文化以凝聚人心,并对当地大汉族主义予以反抗与回击。
尽管在明清时期,闽浙赣地区的畲民体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征,但是在强势的汉文化以及华夏化进程的持续影响下,畲民的文化认同呈现出向汉文化靠拢总的趋势。这个趋势直到新的民族政策实行后被扭转过来,国家按照一定的民族识别标准,通过政治权力重新划定族群边界,畲族在1956年成为政治意义上的民族,自此之后,原来一些地区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畲族族群认同在各方的操作下变得越来越强烈,一度出现了恢复畲族身份的热潮。
畲客的共生关系和族群分野也体现了文化认同与族群边界的关系。竹村卓二引用鲍曼(BaumannHermann)的民族理论①后认为,畲民之所以被汉族称为“畲客”或“輋客”,说明畲、汉族的关系本来就非同一般。他称:“至少在中国对华中、华南非汉民族的称呼中,用‘客’这一概念来表示的,别无他例。这一点显示了畲民与边境尚未开化的原住民苗族和彝族略有不同,当然,对于土著汉族(主民)的社会来说,畲民是处于外来客民的地位。畲民对于汉族来说,现在与其说是应征服或驱逐的蛮夷,莫如说是保持一定社会距离,处于互通有无共生关系中的同伴的地位。”②王东先生也认为,在较长的历史时间中,畲汉族群融合,二者形成了密切的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同时是一种共变关系。“伴随着这种互动与共变,畲、汉双方在各自改变自己的同时,也在改变着对方。”③
在早期迁入的闽浙赣地区“畲客”中,既有畲民,也有客家人,他们统称为“客”。但是不管是政府,还是当地土著,对“客”的认识比较一致:或者以“客”称之,其中并没有清晰的畲族与客家身份的区分;或者统一以地名称之,如汀州人,借以区分籍贯。另外,也没有证据表明,来自汀州等地区的“畲客”之间形成了严格的“畲族”与“客家”的族群分类关系。这说明在明清之际初迁至闽浙赣地区的“畲客”,其不仅在经济方式等客观文化特征无太大差别,其主观的文化认同也比较一致。而当这些“畲客”慢慢安顿下来并定居,土、客矛盾逐渐升级后,“畲客”中的“畲”特征被凸显出来。
与以往闽浙赣地区迁徙的“畲客”文化认同有所区别的是,迁往两广等地区的“畲客”,“畲”特征并没有被凸显,其反映的更多是客家文化认同。这种现象的产生既与广府、客文化差异产生敌意有关,如广府人把客家人称为“匪”“犵”“獠”“猺”等,“或是直接在‘客’字上加上污辱性的‘犬’字偏旁,以示客家为野蛮民族,自以为与之水火不容。”①咸治同丰年间,广东一带爆发了大规模的土客大械斗,此后,客家运动逐渐在广东等地蓬勃兴起,“畲客”中的客家文化认同达到顶点,畲族认同反而不被彰显。直到20世纪80年代,整个广东地区的畲民文化认同总体仍不是特别强烈,对此周大鸣论述道:
广东东部是畲族传说中的文化中心,其凤凰山更被认同为畲族的发源地,可是在这场恢复畲族的运动中,广东反而没有其强烈。究其原因,首先与广东省政府没有强力推行恢复族属相关,其次粤东北是客家文化的中心,对客家文化的认同超越了其他族群的认同。②
我们认为,不同地区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对族群的特质具有重要决定作用。谢重光先生曾指出:“有什么样的生态环境(包括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就会有什么特质的人群,这个人群的文化也会鲜明地打上其生态环境的烙印。”③在不同区域中,生态、人文环境不同,族群的认同取向也可能有所不同,正如笔者前文所指出的,不同的文化取向最终导致了“畲”“客”成为两个比较独立的族群。一些特殊的历史事件,如明中叶社会转型加速了“畲”“客”族群的分离趋势。畲族与客家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紧密的关系,由于文化认同的差异,二者之间形成一道鲜明的族群边界,这也再一次证明文化取向对于区分族群的重要性。④
三、历史记忆与文化建构
费孝通先生在论述中国人际关系时,曾提出“差序格局”理论,这种差序格局类似“水波纹”。他说:“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①水波向外越推越远,一圈比一圈薄。在传统中国,用差序格局理论可以较为有效地解释其中复杂而又独特的人际网络关系。如果将每个族群看作一个人,差序格局理论在一定场合中也起作用,传统的华夏民族观正是这种差序格局的其中一个体现。也就是说,在传统华夏族心目中,以“中国”为中心,越往外层的区域越蛮荒,其所在地区的族群也更难被教化。这种以地理区域作为划分族群类别的标准,在中国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存在着,诸如对“南蛮”的族群印象曾长期存在于古代中原人历史记忆中。
然而,这种族群印象可能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生移动和变迁。如春秋以前,位于长江中游的楚人、长江下游的吴人和越人均不在华夏集团之内,随着楚、吴、越三个南方政治集团完成华夏化,华夏的边缘移至这三个族群势力的外缘。换句话说,当楚人等族群完成华夏化,华夏边缘外移,原来用作楚人族群称谓的“蛮夷”,此时已不再适用,而是套用于更偏远边陲地区的非华夏人群中。就此而言,华夏边缘的移动,并不一定是华夏族人口实质性的迁移,有可能是非华夏人群通过文化认同的转变成为华夏族成员,从而导致华夏族心目中的“异族”向外扩展。正如王明珂指出,一些非华夏人群通过攀附实现手段,将本族血缘与“黄帝子孙”联系起来,或者是将迁居祖先的地域与中原发生联系,建构出“英雄徙边”或“弟兄民族”的历史。②就华南地区汉人而言,其历史建构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南方土著或南迁汉人关于“汉人”正统身份的建构。在以华夏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中,华南地区长期处于帝国的边缘,其所在地区的居民在文化阶序上从属于中原地区的人群。为了提升当地土著的族群身份,最重要的是证明自己与中原汉人的联系。在与国家、地方社会的互动中,当地土著通过主动向中原王朝靠拢,协助政府在该地区建立政治机构,使地区完成华夏化进程。于是在帝国“差序格局”中,该地区离帝国的中心又近了一圈,本地居民借此完成了从“化外”向“化内”的转变。除了将本地区与中原中心发生联系外,在家族层面,本地土著或南迁汉人还通过“攀附”的手段对先祖进行建构,将本家族的迁居地、迁居祖先与中原发生联系,向本族和外界宣称“黄帝后裔”的中原正统身份,这也是许多南方汉人族谱在追溯祖源时较为普遍的叙述模式。
其二,对本地区的“蛮夷”族群进行分类与建构。唐宋以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福建等南方地区的政治地位较以前的“蛮荒之地”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与之同时进行的是该地区“汉人”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体现在此时该地区出现了大量关于“蛮”“蜑”等非汉族群的记载,即作为“他者”的“蛮”“蜑”,其出现证明了“我族”意识的存在。南方土著或南迁汉人通过建构“蛮夷”的族群分类,将“蛮夷”边缘化,并与“蛮夷”划清界限,目的也是想证明本族群正统的“汉人”身份,如前文所指出的,陈元光平蛮正是这种族群分类建构的产物。
在华夏化进程中,畲民也通过两种途径维护本族群利益。其一,利用本族文化,增强族群认同,与大汉族主义进行抗争。这种抗争可以体现在畲民关于盘瓠传说以及其衍生物如《开山公据》《高皇歌》、龙头杖、祖图等文化的理解、坚持与传承上。如畲民对历史上的盘瓠传说进行二次加工,认为本族具有三公主高贵的血统,还有王朝恩赐的特权等,借此宣扬本族光辉历史与传统;再如《高皇歌》通过对“阜老”(福佬或汉人)“恶”的形象的塑造,还告诫本族不能与“阜老”交往等,借此建构了“阜老”与本族严格的族群边界。在这种文化解释体系中,畲民通过夸大族群差异,来激发本民族的族群意识,从而增强文化认同感。
另一方面,在强势的汉文化中,特别是在华夏化进程中,畲民不得不进行族群历史的建构,以提升族群地位。如在明清以后,畲民有意识地对盘瓠的形象进行改造,盘瓠以“龙”“麒麟”“凤凰”等形象出现,并回避“犬”的形象;再如,畲民将一些历史人物进行塑造,如雷海青、雷万春、南霁云、钟景期等,使其成为本民族的英雄祖先。随着畲民族谱修撰的流行,畲民同周围汉民一样,对祖源进行建构,使其在血缘上与“黄帝子孙”发生联系,在地缘上打通与中原的关系。通过这种族群建构,一些地区畲民在文化认同上渐渐发生变化,表现出国家的认同与对汉文化的认同。畲汉之间的族群界线进一步发生漂移、模糊化甚至消失。
四、近代以来畲汉族群边界的再造
明清以后,定居后的畲民慢慢地融入当地社会,其经济、文化等特征越来越多地与周边汉族没有太大差别。清代至民国,文献对各地畲民记载呈现出减少的趋向,本身也表明了各地畲汉族群边界有移动和消失的迹象。
在民国时期,官方对福建等地的畲民统称为“苗民”或“苗族”,这种族称的转变与当时政府的民族思想与民族政策是分不开的,同时与清末以后的民族主义思潮不无关系。
清末民初,在巨大的民族危机下,许多知识分子寻求“国族”建构,如梁启超提出史学的任务就是要激发民众的国家意识,①“炎黄子孙”“黄帝世胄”“五族统一”成为当时的流行话语。政府和一些学者主张“同化”(所谓的“五族统一”即是该思想的表现),认为“少数民族”的调查和研究不能“刺激国族分化”,因此,当时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主要是以“安边”“治边”为要的“边政”研究。②
这种“五族统一”“五族共和”的思想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颇为流行,在民国初期修纂的畲族族谱中体现了这种思想。如上杭《雷氏梓福公家谱》在“凡例”中写道:“此谱议修于光复前一年,购工庀材,择吉开雕,越十有五月而告成。五族适于是年统一,是此谱诚为民国成立一大纪念,故于卷首敬刊国旗,用志盛事。”③一些接受新思想的畲族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在族谱中宣扬“五族共和”思想,如上杭雷氏第十九代裔孙雷熙春、雷晓春在“序”中称:
岁辛亥(1911年,笔者注),吾族有修谱之举……且此谱之作与民国之成立固有绝大关系者。吾族得姓实在黄帝纪元之世,源流最古。远祖方雷氏佐黄帝南征北伐,纯然民族主义,功德留荫,历世已四千六百余年,虽期间丧乱频仍,叠经变故,而忠孝节义之士犹复昶望于史册。方吾一世祖梓福公之生也,当赵宋末造,时适胡元入主中夏,窃据神器,因挚眷避地卜居于此,优游金山摺水间者九十载。追明太祖定鼎金陵,汉族光复,始考终牗下。迄明、清二代,族中科名仕宦于今为盛,而士大夫博学识能文章者,先后修谱两次,曾未昌言民族主义。为详考吾族得姓之缘,纪以志诸谱牒,知其慑服于专制余威者为已殁矣。乃者五族统一,政更共和,举黄帝手定之锦绣河山悉以还诸黄帝世胄,而此谱适于是年秋月以成。由是濡毫吮墨,畅所欲言,俾吾祖吾宗萦抱民族思想,得于序录中表白一二。①
该序描述了黄帝征伐异族、胡元入主中夏、明代汉族光复、民国政更共和等历史事件,反映的是清末民初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想,这种社会思潮经知识分子的宣传慢慢渗透到一般家族中,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民国元年,上杭雷赞明在“序”中称“今民国新立,治尚共和,神明之胄四万万皆同胞矣。”雷庭瑞在《重修梓福公新谱告成序》也称:“今岁五月开局编印,新谱告成值民国新纪元,谨进一言以志盛举。曰,共和成立,五族大同,汉满蒙回藏为一家,是亲爱家族之观念尤当推而远之,不仅在一姓一族也。五族者千万姓之所积,人人各亲爱其同姓,思扶掖而促进之,知非保五族则一族姓不能独立,于是互相扶掖,互相促进,此爱同胞、爱祖国者所不能违之公例也。”②
当时国民政府主张民族同化,鼓励边疆非汉人群汉化。在这种民族政策的指导下,官方并未将分布在福建等地区的畲民视为一个比较独立的、具有政治意义的民族,而是笼统地以苗族称之。实际上,关于对南方民族以“苗”“瑶(徭)”等族称泛称,在明清以前十分常见,这大概类似于更早之前,中原王朝将南方地区的族群泛称为“蛮”“越”“獠”等。应该来讲,这些族群内部存在较大差异,族群间具有一定的族群边界,如“越”又称“百越”,足以说明各个地区的族群是有一定区别的人群集团。将这些族群泛称为“蛮”“越”等,说明对于华夏族而言,或者是由于族群的接触与认识还不够,无法对这些族群内部的差别进行更详细地分,或者即使其群体内部有一些区别,但在华夏族心目中,这些差异可以忽略不计。即在“华夷之辨”的语境中,所谓的“蛮”“越”“苗”等无非是作为“华”的对立面而存在,二者形成了“文明”—“野蛮”的文化政治结构。杨志强在分析近代苗族形成问题时指出,明清以后,常将“苗”“苗种”作为南方各省非汉系族群的泛称,而“作为一种汉民族对于异族的称谓,这里所说的‘种’代表的是一种‘华’与‘夷’区别的模糊的文化境界,而并不是现今意义上所看到的‘种族’或‘民族’。”①
在民国时期,福建各地的畲民在官方上被称为“苗族”,如1937年《各县区苗夷民族概况》描述了连江、福鼎、顺昌三地“苗夷民族”情况,这些“苗夷民族”实际上多为畲民,其中连江有23个畲民村落,主要是迁徙自漳浦蓝、雷畲民,这些畲民在女子服饰上具有与汉族不同的装束特征,“清初与汉人通婚,在咸丰时代,苗族生活颇裕,中有田租收至三千余担者,今则已衰落。”到民国时代畲民业已与汉人同化。②
成立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山民会馆(后改为三明会馆),是闽东浙南“山民”联络议事之所。1946年,闽东畲族宗人商议重兴三明会馆,蓝玉轩等向所在地霞浦县政府提交申请报告,业经县长刘仇签署,呈报省政府核准在案,成为官方〓册认定的“苗夷民族”(按当时《福建年鉴》之称)“公益团体组织”。③由此可见,当时的闽东畲民被官方认定为“苗夷民族”,而不被认为是“畲族”。
1947年12月8日《福建省政府关于送边疆民族及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状况调查表给内政部电》关于苗族连江、罗源、顺昌、漳平、周宁等县,人口也相应增加。同时在注明备考注明:“苗族俗称畲民,间有与汉人同化者。”④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30—40年代,政府也将水上居民(疍民)作为“边疆民族及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上报国家有关部门。⑤苗族作为畲族的称呼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年时间还在官方的报告中出现,如1952年7月8日写成的《畲族福安县仙岭洋村调查情况》中,认为国民党大汉族主义进行民族压迫、歧视和侮辱,故意歪曲其历史,而另一方面,畲族限于文化,对本民族历史也不甚了解,“只认为苗民称号较臭畲人(臭蛇人)好,这是畲族改称苗族之始。”又称:
解放后来自北方干部,过去接触少数民族不多,对当地畲族未曾详尽调查,了解该民族历史,以及民族特征,只因他们语言不同,妇女装饰奇异,居住高山,称之苗民……在国民党大汉族主义消灭同化政策压迫下,曾经强迫改变民族服装,于民国十二三年间改穿汉服,藉以躲避欺视,不易辨别他们是畲民。女的虽略有改变,但仍然保持民族装饰。①
1952—1953年,漳平县、闽侯县提交的报告也均把本地畲民称为“苗族”②。1953年12月9日,在一份由福安地委统战部提交的报告中,还显示了当地畲民对于要将本族命名为“畲族”存在不满的情绪。报告称当时畲民有“苗族”“瑶族”“山宅”“三民”等名称,但畲民本身不承认自己为“畲族”,原因主要是历代反动统治(国民政府采取的是同化政策)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残存的民族隔阂没有彻底消除,加上当时南下干部不了解情况称畲民为“苗族”,福安地委统战部根据1951年在福安仙岩乡从该族家谱调查后认为“畲族”名称是正确的,这引起了当时畲族百姓的反对。③直到1956年9月9日《中共福安县委统战部关于少数民族名称问题的报告》仍坚持不使用畲族这个民族称号。④随着1956年中央统战部下发《关于确定畲民民族成分问题》,关于畲民名称的争论才渐渐停息下来。⑤并在1956年12月8日经中共中央统战部最后确定畲族的民族成份和民族名称。⑥至此,畲族作为一个族称在国家的政策下推行,而关于畲族的民族认同的过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闽西南一些地区接受程度较快,①而闽东一些地区则经历较长一段时间磨合,才最终接受,如在确定族称的两年多以后的1958年10月1日的《宁德县南山片畲族调查报告》仍在讨论畲族民族名称的几个来源与畲民态度。②1958年10月5日的《罗源县苗民情况报告》仍将畲族称为苗民③。而一些地区,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对畲民族称表示不满。④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称畲民为“苗民”与国民党政府的民族政策有一定关系,另外一些因畲汉矛盾给畲民带来情感伤害的地区,也希望用“苗族”等泛称替代原来被标签化了的“畲”族。笔者大胆推论,假如没有后来学术界的努力和国家政策的推行,部分畲民将可能被官方划分为“苗族”,也有可能在提倡“五族共和”以及民族同化的政策下,更多的畲民走向汉化,从而导致族群意识不彰显。正如疍民融入汉人之中,而在此之前,畲、疍均作为福建地区比较特殊的族群一并被论述⑤。当然,历史无法推论。在新中国民族政策的推行下,地方政府、学术界、各地的畲民(或疑似畲民)精英参与了新的族群边界的制造。
就国家和学术界而言,他们希望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标准来开展民族识别、民族身份恢复工作。民族学者施联朱参加了畲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他在《解放以来畲族研究综述》指出,“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为畲族识别工作重要因素。”①并强调不能单以民族姓氏定民族成分,他说:“我们说畲族主要有盘、蓝、雷、钟四大姓,不等于说四大姓全是畲族,姓氏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共同体,而民族则是以地缘为基础的人们共同体,把姓氏视为民族特征的主要标志之一,是错误的。”②
这种看似科学的民族识别标准却不能完全解决民族识别和民族恢复中的实际困难如何判断一个地方族群的民族特点是否足以被认定为畲族,需要当地族人支持与材料证明、地方政府的调研与申报以及相应政府部门审批与认定。但如果在一些地方原畲民住区的居民对被认定为畲族热情不高,或者当地民族部门投入不足,或者国家认定族群身份根据上报材料与若干调研,其中也不能保证完全做到十分客观。因此,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在族谱记载中有较为亲近血缘关系的姓氏,存在着一个地方宗姓被认定为畲族,而另一个地方宗姓却未被认定为畲族的情况。③
但是,在族群认同工具主义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的地区人群为能被确认为畲族而努力。1964年9月5日《福安专署关于政和、松溪少数民族称谓问题的调查报告》说明了政和县雷姓族人要求恢复畲族族称的由来,该文写道:
政和县雷华泉于1953年参加建阳专区少数民族代表会,体会到党的民族政策的英明:1963年他堂兄雷成寿从建阳籍到政和来谈起有关历年来闽北地区党对畲族人民的关怀以及闽东地区民族工作情况,他们得到很大启发,所以积极要求恢复族称。松溪县畲族曾向区里要求解决族称问题。①
从这份报告,可以看出政和县雷华泉通过了解国家的民族政策积极要求恢复族称,族群内部精英的运作使得该地区的畲民得以确认为畲族的政治身份。
近年来的一些研究也证明,一些畲民为了被确定畲族的政治身份,不断对本民族的历史进行重构。如周大鸣在赣南地区田野调查中发现,一些原属客家的蓝、雷、钟姓在20世纪80年代恢复成畲族后进行族群重构,他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恢复成赣南畲族的族谱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在1985年以前的族谱中,每一次族谱的序言有一个逐步‘汉化’‘正统化’的过程,受‘大传统’影响的烙印不断明显。而1985年后修的族谱则是‘畲化’的过程,透过这些‘精英文化’的变化历程,可以再现一个族群的变迁。”②杨晋涛在研究闽西蓝姓居民的“畲族意识”时也提出:“就武平的情况来看,没有国家民族平等的理念和政策,一个已经汉化,其身份已被周围汉人认可,并且一度以汉人自认的群体,不会无端重提祖先,并力求恢复先民身份;同时,未能掌握相当的历史文化资源,就要求国家对自己的特殊身份给予认可,势必也不可能。”③
如果说历史上畲民为了淡化畲汉边界不断建构族群历史向汉文化靠拢的话,那么,在新的民族政策下,更多的畲民为争取被确定为畲族的政治身份做出不懈努力,而由国家、地方、学术界以及民间多方合力推行的文化展演,无不都是在强化业已形成的族群边界,这种看似截然相反的族群现象,却是各个族群在不同历史情境下做出的相同反应。
附注
①马卫东:《大一统与民族史撰述》,《史学集刊》,2011年第6期,第53页。
①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定义,他说:“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和习惯。”载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9-20页。
①[美]韩起澜(EmilyHonig)著,卢明华译:《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上海史研究译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11-112页。
②刘志伟:《地域空间中的国家秩序——珠江三角洲“沙田—民田”格局的形成》,《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14页。
①四个截然不同经济文化区分别为:一是武夷山至南岭一线以南地区,即狭义的华南地区;二是长江流域;三是黄河流域;四是北方沙漠草原地区以上各个区域由于生态环境不同,其经济文化也因此截然不同。在以上各个不同经济文化区还存在着三个过渡地带或称文化交汇地带:一是南岭以北和武夷山以西地区过渡地带;二是秦岭南侧至淮河一线过渡地带;三是阴山南侧及河套地区过渡地带。参见张之恒:《生态环境对史前文化的影响和中国史前文化的三个过渡地带》,《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2期,第33-37页
②谢重光:《客家文化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9-129页。
①张文:《地域偏见和族群歧视:中国古代瘴气与瘴病的文化学解读》,《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第68-77页。
②左鹏:《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194-204页
③于赓哲:《蓄蛊之地——一项文化歧视符号的迁转流移》,《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194-204页。
④于赓哲:《疾病、卑湿与中古族群边界》,《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第63-71页。
①林校生:《“滨海畲族”:中国东南族群分布格局的一大变动》,《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7页。
①谢重光:《客家文化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41页。
②谢重光:《新民向化——王阳明巡抚南赣对畲民汉化的推动》,《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36-37页。
③李积庆:《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变迁的历史考察》,《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10-11页。
①鲍曼认为民族的共生是一种文化变化的特殊形态,并将其定义为:“不同文化类型并且互不触犯的两个民族共同体,以各自生产不同生活必需品的传统性交换为基础的和平的共生”[日]竹村卓二著,金少萍,朱桂昌译:《瑶族的历史和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76页
②[日]竹村卓二著,金少萍,朱桂昌译:《瑶族的历史和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85页。
③王东:《那山那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5-57页。
①刘平:《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0页。
②David Y.H.Wu:Ethnicity,Identity and Culture,The Hmmanities Bulletin,voJume 4 December 1995,Faculty of Arts.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P.17.转引自周大鸣:《从“客家”到“畲族”——以赣南畲族为例看畲客关系》,《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09年第6辑,第5页。
③谢重光:《客家文化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88-489页。
④早在20世纪40年代,陈寅恪先生在探讨文化与血统对于区别北朝胡人、汉人各自不同地位时,曾有精到的论述:“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比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共血统如何,在所不论……此为北朝汉人、胡人之分别,不论其血统,只视其教化为汉抑或为胡而定之确证,诚可谓‘有教无类’矣。又此典为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若不明此,必致无谓之纠纷。”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6-17页。
①费孝通著:《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23页。
②参见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①梁启超:《新史学》,1902年,第7-8页,收入《饮冰室文集》第4册第9卷,第1-11页。
②如傅斯年曾反对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在云南正在进行的边疆民族调查研究。他在写信给朱家骅、杭立武称:“此地正在同化中,来了此辈‘学者’,不特以此等议论对同化加以打击,而且专刺激国族分化之意识……夫学问不应受政治之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想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转引自王明珂:《由族群到民族:中国西南历史经验》,《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1期,第1页。
③雷熙春,雷国瑞纂修:《上杭雷氏梓福公家谱》,民国元年(1912年)刻本,载《家族谱牒——畲族卷》(下),福州:海风出版社,2011年,第122页。
①雷熙春,雷国瑞纂修:《上杭雷氏梓福公家谱》,民国元年(1912年)刻本,载《家族谱牒——畲族卷》(下),福州:海风出版社,2011年,第111页。
②同②,第111页、第113-114页。
①杨志强:《从“苗”到“苗族”——论近代民族集团形成的“他者性”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4页。
②《各县区苗夷民族概况》(1937年),载福建省档案馆、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编:《福建畲族档案资料选编(1937—1990)》,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7页。
③俞郁田编纂,霞浦县民族事务委员会,《霞浦县畲族志》编写组编:《霞浦县畲族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1-105页。
④《福建省政府关于送边疆民族及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状况调查表给内政部电》(1947年12月8日),载《福建畲族档案资料选编(1937—1990)》,第11页。
⑤《边疆民族及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状况调查表》(1948年3月11日)、《福建省政府为续编边疆异族调查表送请查核给内政部的代电》,载《福建畲族档案资料选编(1937—1990)》,第12页。
①《畲族福安县仙岭洋村调查情况》(1952年7月8日),载《福建畲族档案资料选编(1937—1990)》,第30-31页。
②参见《漳平县少数民族情况》(1952年10月16日),《闽侯县人民政府关于少数民族情况报告》(1951—1953年),载《福建畲族档案资料选编(1937—1990)》,第50页、第22-23页。
③《中共福安地委统战部关于畲族人民对本民族名称意见的一些问题》(1953年12月9日),载《福建畲族档案资料选编(1937—1990)》,第177-178页。
④该报告称:“我据下逢乡调查,他们自称‘苗族’但渊源无处查考……为了正确贯彻民族政策,慎重处理这一问题,我县特于今年8月底县三级扩干会议期中,召开一次少数民族干部座谈会,征求他们对本民族名称的意见,会上大家一致不同意称‘畲族’,认为他们祖传‘天下有山民’一语,应称为‘山民族’,也可称为‘瑶族’‘民族’或‘苗族’较为适当。根据以上情况,我县经过研究,初步意见认为以上几种名称都没有足够的根据,但其中以‘山民’族在我县流传较广、较深。因此拟改为‘山民’族较为适当。此外,根据该族人民意见,改为‘瑶’族、‘民’族或‘苗’族也可以。如何决定特报请核示”参见《中共福安县委统战部关于少数民族名称问题的报告》(1956年9月9日),载《福建畲族档案资料选编(1937—1990)》,第179页。
⑤《福建省委统战部转发“关于确定畲民民族成分问题”的电报》(1956年8月21日),载《福建畲族档案资料选编(1937—1990)》,第180页。
⑥《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确定畲族的民族成分和民族名称问题的电报》(1956年12月8日),载《福建畲族档案资料选编(1937—1990)》,第181页。
①华安等地畲民表示认同。中共龙溪地委统战部对“华安县关于贯彻畲族名称情况补充报告”的意见(1957年5月28日)称:“畲民居住于彭水、官畲二个自然村,混居在汉族二个乡自搬到华安彭水、官畲居住有十四代之久,计四百廿多年,系姓蓝、雷、钟三姓,没有其他性别混合,家居一贯业农为生活来源,其饮食起居很简,俗话说:‘吃无油菜汤,睡无脚眠床’(意思说吃很简单,睡的是在地板上)该族自历以来,并无文,所用文字都以汉文,只是在语言上的差别,以往其种族的称呼,自古以来本族群众也不知道是什么,只是知道本族人口稀少,曾有一段说是苗族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土改时,该乡工作组(苏六官),根据该族语言差别,就给予说你们是苗族。自此以来群众就有这种传说,认为自己是苗族。可是去年漳平少数民族确定为畲民,漳平系与华安少数民族同宗同姓,因此就产生矛盾。认为漳平是同宗同姓为什么没有同族,这样少数民族对苗族称呼是不大相信,通过这次确定为畲族,畲民非常满意。”参见《中共龙溪地委统战部对“华安县关于贯彻畲族名称情况补充报告”的意见》,载《福建畲族档案资料选编(1937—1990)》,第183页。
②《宁德县南山片畲族调查报告》(1958年10月1日),载《福建畲族档案资料选编(1937—1990)》,第107-108页。
③《罗源县苗民情况报告》,载《福建畲族档案资料选编(1937—1990)》,第105-106贞。
④如1983年6月《罗源县福湖大队畲族综合调查报告》记载:“在(罗源)福湖等地的调查,本地畲族干部和群众对民族称呼问题反映非常强烈因根据福建等地的方言,‘畲’与‘蛇’谐音,有的汉族也就借此污蔑少数民族,他们说,畲族称呼是强加的,在以前自己都没有听到过,这是难以接受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几次民族调查和《畲族简史》征求定稿中,不知反映过多少次,这是引起当地民族问题的症结之一。他们坚决要求改变族称.有的说改成凤凰族(因祖先源于广东凤凰山),或‘山哈族’并要求在全畲族同胞中进行民意测验,尊重本民族人民自己的意愿。”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79级社会调查实习队:《福建省罗源县畲族历史与现状调查报告选编》,载《福建畲族档案资料选编(1937—1990)》,第164页。
⑤20世纪50年代初,水上居民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也成为全国性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的对象之一。根据文献和实地考察,调查组写成了《粤桂疍民情况调查报告》《疍民简史和概况》《疍民由来问题》等专题报告,尽管研究者反映了部分疍民要求作为一个单独民族的意见,但是,自到1956年底,关于疍民是否是一个少数民族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出结论。以后,疍民被确定为汉族的一部分。参见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下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20-121页。
①施联朱:《解放以来畲族研究综述》,载施联朱主编:《畲族研究论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9页。
②同①,第9-10页
③如在20世纪80年代民族识别恢复阶段,福建云霄县下河乡坡兜、圳头、安后、安前村钟姓,永春县下洋镇长溪村雷姓,永春逢壶乡西昌村、八乡村等章姓,在申请恢复(畲族)民族身份时,尽管他们努力证明本族与已经被认定为畲族民族身份的同族姓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政府仍以其“民族的明显特点消失”等原因,不予变更民族身份。参见:《云霄县民政局关于坡兜、圳头、安后、安前村钟姓要求恢复畲族问题的调查报告及漳州市民政局的答复》《永春县人民政府关于申请恢复少数民族成分的报告及泉州市民政局的批复》,载《福建畲族档案资料选编(1937—1990)》,第192-194页,第201-202页。
①《福安专署关于政和、松溪少数民族称谓问题的调查报告》,载《福建畲族档案资料选编(1937—1990)》,第184页。
②周大鸣:《从“客家”到“畲族”——以赣南畲族为例看畲客关系》,《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09年第6辑,第3页。
③杨晋涛:《闽西蓝姓居民的“畲族意识”——一个族群建构的例子》,《畲族文化研究》(上册),第168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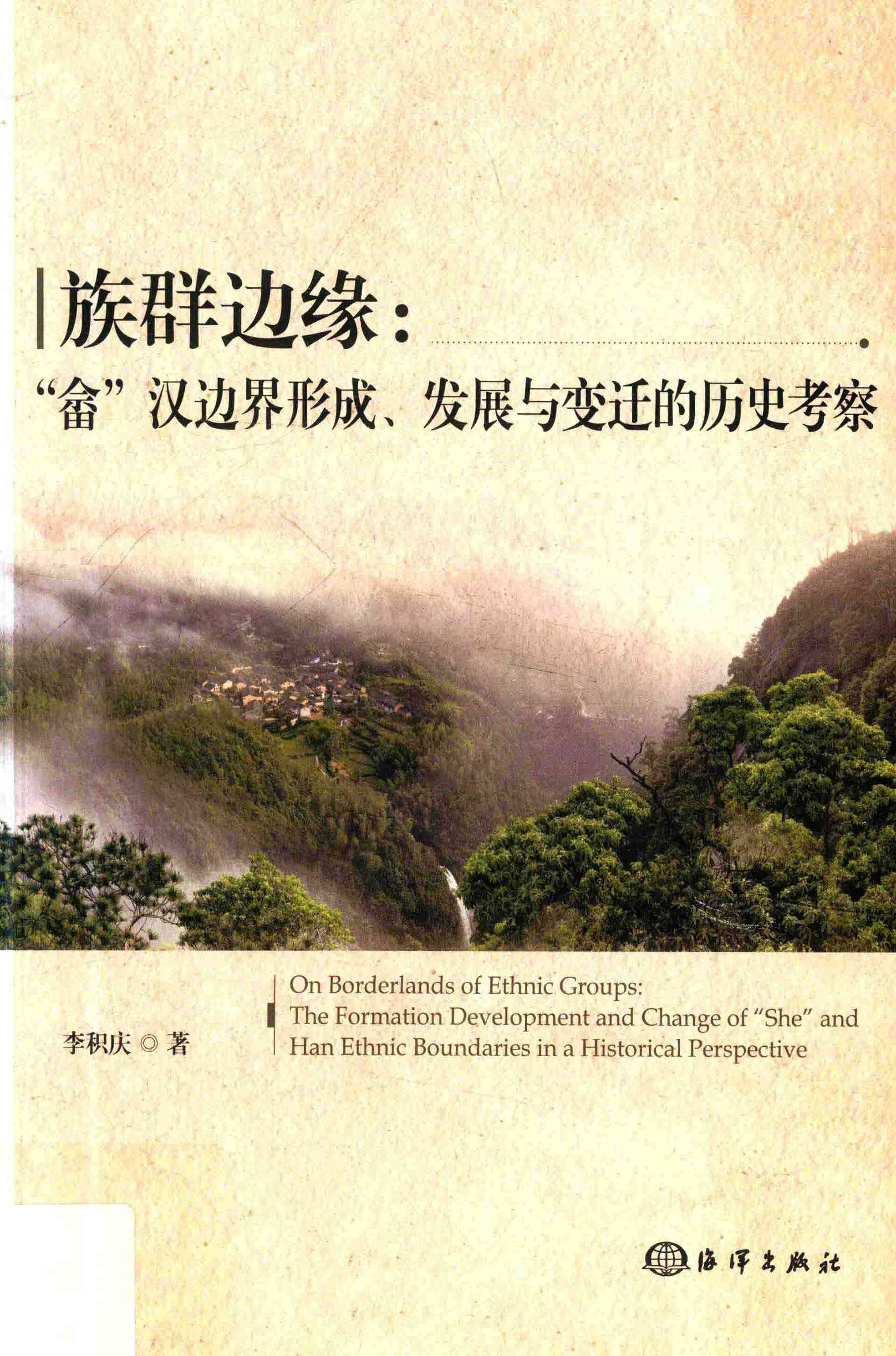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出版者:海洋出版社
本书从族群边界的理论角度,重新审视畲族形成、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在承认族群客观历史文化的同时,重点研究历史上“他者”(主要是汉族)对“畲”的社会定义以及“自者”(主要为南方非汉族群)自我族群认同的过程,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现实意义。
阅读
相关地名
宁德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