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明清以来畲民族群历史的建构
| 内容出处: |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图书 |
| 唯一号: | 130920020230003819 |
| 颗粒名称: | 第四节 明清以来畲民族群历史的建构 |
| 分类号: | K288.3 |
| 页数: | 18 |
| 页码: | 226-243 |
| 摘要: | 这段文本主要讨论了畲族的历史和文化建构,特别是他们如何通过盘瓠传说来塑造自己的族群认同和历史记忆。 |
| 关键词: | 畲族 盘瓠传说 族群 |
内容
王明珂在论述近代“苗族”与“瑶族”形成问题时指出:“与世界其他各‘民族’之形成一样,皆经由一‘历史化’过程——包括华夏知识分子对‘苗、瑶’的历史建构,也包括‘苗、瑶’族群中知识分子之我族历史建构。”③在汉族强势优势文化下,畲族通过改造盘瓠形象、建构族源记忆、塑造本民族英雄等手段,对本民族的历史进行建构,用以加强或淡化族群边界。
一、畲民精英分子的反思与“非畲化”思潮
盘瓠传说或盘瓠信仰对于畲族来说极其重要。畲民关于盘瓠迁徙传说的历史记忆与叙事,一定意义上属于王明珂所说的“英雄徙边记”。④也就是说,盘瓠及三公主作为高贵血统以及高贵地位的祖先,迁徙到各地,成为畲瑶的祖先。清光绪元年(1875年)福安春雷云《冯翊雷氏宗谱·谱序》:“雷氏先世,非即高辛所封之盘瓠我王乎!……而敕封立国侯之巨祐公即雷氏开基之鼻祖。”①《冯翊雷氏宗谱》载有《御偈》曰:“念尔祖宗德泽深,名垂万古受封荣。原为前朝除匪寇,莫将券牒视非真。享镇名山多乐趣,何烦鸟语动幽情。自从敕赐恩膏厚,世代相承及古今。”又有《御赐封联》曰:“功建前朝,帝譬高辛亲救赐;名垂后裔,皇孙公子免差徭。”②这些所谓御赐的偈子或对联应该是畲民根据《开山公据》等传说二次加工。
日本学者村松一弥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和现状》一书中,分析畲民的文献和传说,并判断称:“据说居住在罗源县(福建省)山地的畲族(畲民),是自尊心非常强,富有优越感的集团,而且自信惟有本部族才是高贵民族,蔑视周围的汉族,决不与汉族通婚。”③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畲民在与汉族交流过程中,借用盘瓠传说以维持本民族的边界,其具有强烈自尊心和族群优越感,夸耀本族为“高贵民族”,蔑视周围民族,这正是族群认同感强,族群意识高涨的说明。这种自尊心和优越感同清代以后客家运动中体现出来的优越感有着历史的相似性,正是由于本族群在与其他族群交往中产生的摩擦,促使族群激发出强烈的自我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主要表现为以己为是,而以他族为非,具有强烈的排他性。
在闽东浙南地区,除了部分地方志记载畲民为盘瓠后裔外,还有一些畲族谱也宣称本族为盘瓠后裔者。在福鼎市牛埕下《冯翊雷氏宗谱》中,录有《纂修雷氏族谱序》,该序中作者以本族为盘瓠后裔为荣,认为霞浦、福安以及福鼎等地的畲民均为盘瓠后裔。该序文称:“……他如霞浦是居者瑞发,福安是处者孔亲以及福安之鼻各穆洋溪塔、岩前、老虎岩井白路三坪等处。地名孔多,难以枚举,均是盘瓠王后裔。”④民国四年(1915年)福鼎枇杷坑《钟氏族谱》中载有钟氏后人对盘瓠祖先的追述,如:
藐躬生幸太平时,谱帙未修最系思。莫学崇韬忘己祖,盘瓠以降即宗支。裔孙鸣登谨志。
家乘由来贵晰详,程门旧训最堪尝。本源我溯高辛氏,谱学何须羡盛唐。裔孙起勉谨志。①
由此可见,闽东地区的畲民家族倾向于宣扬盘瓠信仰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并不断宣称本族高贵的血统以及免差徭的政治权力,以此来凝聚族群。清同治九年(1870年),福鼎《蓝氏宗谱》载:“现在闽省连江、罗源、侯官等俱蒙示禁勒石永革,畲黎得安耕凿。”②因此,有学者指出,即使到了清中期以后,各地畲民均纳税服役,畲民还不断通过盘瓠传说及其文本或实物宣称“免差徭”,这可以认为是畲民对政治身份的一种追求,用以与汉人相区别。③
随着畲汉族群交流的加深,族群间关于社会资源的竞争更加激烈,因此,一些畲民家族希望通过传统文化来维持族群边界。如一些畲民希望通过盘瓠传说及其相应的一些文本、实物及口述材料,如《高皇歌》《开山公据》、龙头杖、祖图等,来维护及合理化畲人对华夏边缘资源之拥有与使用,并以此成为解释族群来源、姓氏构成的重要依据。④但是,在强势的汉文化中,一些汉人将畲民的盘瓠传说污名化,使其成为汉人贬低、排斥畲民的工具。而实际上,关于族群的起源,基本上都加入神话的成分,这种神话成分在现实社会中有时会显示出幼稚、夸张、荒谬等特性。正如陈登原在《国史旧闻》所论:“槃瓠之说……至于此事,自属荒昧之记。如太昊蛇形,炎帝蛇首(原注:《北堂书钞》卷一),汤之先世,出于燕卵(原注:《诗·玄鸟篇》郑氏注),可知即在汉族,固亦往往而有,存而弗论可也。”⑤
因此,即使是汉族,也有“蛇首”“燕卵”的祖源传说。在人类社会演进中,每个民族均会创造出一些神话或传说,其中包含了人类“童年时代”的思想,这种认识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特定产物。盘瓠之所以被污名化,不在于其故事的荒谬性,更多的原因在于汉人掌握着话语权。反过来说,假如畲族掌握主流文化的话语权,那么汉人可能因为“蛇首”“燕卵”的祖源传说而被讥笑,当然,这种假设只能是推论而已。
在一些南方非汉族群中,对待“盘瓠”的祖源故事,其情感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受到历代汉族文字记载的影响,他们接受“盘瓠”的祖源传说并神圣化“盘瓠”的形象;另一方面,相对汉族而言,南方非汉族群政治、文化处于劣势地位,在强势汉文化下,非汉族群中的精英分子,特别是一些深受汉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纷纷对本族的“盘瓠”传说进行辩证,并试图对此现状进行改变,有“去盘瓠化”的思想倾向。另外,有一些族群,如瑶族①等,采取与盘瓠有联系②、但又有区别③的“盘古”作为本族始祖,用以宣称自身有比华夏之“黄帝”更古老的起源。④
因此,畲民家族对盘瓠传说进行了有意识地改造、理会与解说,如突出盘瓠的,龙与麒麟或麒麟与凤凰的形象。⑤杨正军认为造成盘瓠形象改变的原因与畲、汉在科举领域的竞争,以及畲族知识分子对本族文化的反思有关。⑥
有些出身畲族的文人开始批驳“盘瓠遗种”说的荒谬无稽,在文字书写的历史记忆重构中表现出强烈的“去盘瓠”意识。钟大焜,福州府侯官县人,同治九年(1870年)中举,光绪三年(1877年)成进士,曾任四品衔刑部主事。光绪二十年(1894年)钟大焜试图纂修《颍川钟氏总谱》。《颍川钟氏支谱》谱成,曾请广西太平府知府吴徴鳌作序,该文对钟姓的畲民身份进行考辨,其文曰:
……余维其先出于颍川四长皓公,后徙于各省,以闽之汀州为盛。其由粤复迁于闽之福宁者,揆其所自,亦由汀而来。福宁族亦繁盛,咸以明洪武进士知浙江天台县音公为始祖。音公后六七传,多山居力农,只与蓝、雷二姓联姻,而人遂称为畲民。考《说文》烧榛种田为畲,入六麻韵音斜,其人七虞韵者为甾,〓之畲音佘,本一字二音,并无〓字。今福宁土民俗书为佘,即官府案赎亦从俗为畲。然考其字义并非恶
劣之称,不过为山居农民而已。①
明清以来,闽东蓝、雷、钟三姓多“山居力农”,并且三姓相互通婚,比较好地保留了畲民的文化传统,正是有这些文化差异,于是“人遂称为畲民”。说明畲民与“土民”之间存在族群边界,“土民”对畲民的称谓,影响到官方对畲民的界定,所谓的“官府案赎亦从俗为畲”。吴徴鳌称畲民只不过是山居的农民,从字、义上说并非“恶劣之称”,这恰恰说明了当时有很大一部分“土民”或官府以“恶劣之称”对“畲”进行认识。
吴徴鳌在“序”中又对畲民中广泛流传的盘瓠传说进行考辨,他认为盘瓠传说是“荒远无稽之言”,因为旧谱中明代之前的世系尚且不能说明详尽,突然将四千余年的祖先源流置于谱端,因此不能令人信服,并对福宁府中畲民攀附盘瓠传说进行批评,他说:
考福宁府属妇人皆裹脚,不裹脚者则髻上加流苏,或加冠,有高及尺余者。即衣服亦与平民稍殊,以为此当时高辛所赐也,初不知外人转因此而目为畲。且近日妇人为此妆饰者不独蓝、雷二姓,渐延及十余姓,所以乐为此者,皆以妇人不裹脚利耕作耳。乃因耕作之便,遂不恤他人之称为畲,又因其先有联姻高辛之荣,遂忘其有盘瓠之辱,且尽将盘瓠事实弁于谱端,复绘图立说张为屏幛,以自别于平民。岂知联姻帝室事属无稽,而盘瓠之辱则已群指而目之,而平民反不与联姻矣。置近代洪武进士天台知县子孙之荣于不顾,而独有取于四千年以前盘瓠之辱以为荣,非由于山民无知不识字不读书,何以至此哉!②
裹脚,亦称缠足,是古代中国特有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明清时期最为兴盛③,上至士大夫,下至编户百姓人家,皆有裹足,这是儒家文化成为主流思想的结果。清代钱泳《履园丛话》就曾议论道:“大凡女人之德,自以性情柔和为第一义,容貌端庄为第二义,至足之大小,本无足重轻。然元、明以来,士大夫家,以至编户小民,莫不裹足,似足之不能不裹,而为容貌之一助……(裹足)并无益于民生,实有关于世教。”①
可见,在明清时期,女子裹脚符合主流文化的审美标准,在某些场合成为区别百姓是否得到教化的一个标准。显然,在福宁府中,不裹脚者不在少数,这些不裹脚者装束与“平民”有较大差别,因此,外人(主要是汉人)将这些装束作为畲民的一种文化特征,实际上,因为不裹脚且服饰适合耕作,所以不仅蓝雷钟三姓为此妆饰,这种衣着装束习俗“渐延及十余姓”,说明许多汉人也采用这种装束,甚至不担心其他人“称之为畲”。从以上材料,不仅可以看出畲民文化影响闽东汉人的文化,甚至可以推及唐宋时期,南迁汉人进入闽粤赣地区时,采借了土著居民的文化习俗,可能在认同上也如闽东汉人,“不恤他人之称为畲”。
就畲族而言,此时他们采用盘瓠传说,作为现有文化习俗的存在作合理的解释,如上文所称的“髻上加流苏,或加冠,有高及尺余者”。关于这种头饰的来源,一些畲民根据盘瓠传说将其与三公主联系起来,或称为“凤冠”。如此看来,这种不裹足、类似“凤冠”的头饰,虽然在外人看来不符合主流文化,却可以成为畲民自我标榜曾联姻高辛帝、有着“自别于平民”的高贵血统,这种历史记忆成为一种对抗主流文化的资本。
还有一些畲族族谱的作者也对盘瓠传说的来源表示怀疑。如修于民国九年(1920年)的霞浦县青皎畲族村《冯翊郡雷氏宗谱》将始祖追溯至轩辕赐姓的西陵氏螺祖,本姓因“雷电而受姓”,认为盘瓠传说是不合理的,该文写道:“谬传帝以女妻盘瓠者,岂不碍于圣门,而同别类乎?能无污蔑古帝,妄读圣经?当人犁舌地狱,以为狂谬无知极矣!……杜君卿《通典》与范蔚宗《后汉书》论沙黔中,五溪蛮僻处苗、徭、黎、壮西南蛮界。东南何所考据以‘菑民’为‘畲民’?亦指盘瓠之后裔也耶?致令无识之徒,借资口实,群相诟骂,漫侮圣经。”②
修谱者认为,盘瓠之说有污蔑圣贤,另外认为,盘瓠之说原属于五溪地区以及西南蛮界,而将东南地区的畲民称为“盘瓠之后裔”,是他者用以互相诟骂的一种说法。依作者看来,盘瓠实际上是外人强加给畲民的,这不符合事实,应该重新审视。作者目的是为了澄清雷氏的祖源,虽然关于畲民的盘瓠祖源传说来源解释不一定符合事实,但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说明了盘瓠传说的其中一个途径是由汉人传入非汉人群中,从而固化为一个族群的印象。
当然,以上只是闽东部分畲民关于本族文化的解释,体现了本族的文化认同。然而畲民文化在汉文化犹如海洋中的孤岛,一些汉族知识分子认为主要原因是教化不够,如吴徴鳌认为钟姓族人将盘瓠事实全部写在谱端,并且“绘图立说张为屏幛”,主要是“由于山民无知不识字不读书”的结果,所以他在谱序中提出设想,这也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普遍思想观念。他说:“宗族既盛则殷实或多,何如广兴乡塾,倡设书院,率子弟而教之。庶他年文教大兴,科名鼎盛,方知前此之愚陋,而有以敦劝其乡人,而渐改其敝俗,以继绳天台公之祖武,且克振颍川之家声,是则余之所厚望也夫。”①
在强势的儒家文化,一些畲族识分子也开始反思,并力图重新建构文化,以扭转外人对本族的偏见。如光绪二十四年福建提刑按察使司的告示,该告示实际上是应钟大焜的要求而发布,称“古来槃弧之说本属不经”,要求畲民改变服式乖习俗,以免“授人口实”。其全文为:
署福建等处提刑按察使司兼管骚传事盐法道余为示谕事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据家丁林添禀称,家主刑部主事钟大焜因修谱到福宁所属各县,见有一种山民,纳粮考试与百姓无异,惟装束不同,群呼为畲。山民不服,时起争端。家主向山民劝改粧束与众一律,便可免此称谓,无不踊跃乐从。惟各山民散处甚多,禀请出示晓谕,等情到司。
据此本署司查,薄海苍生莫非天朝赤子,即闽粤之蛋户、江浙之惰民,雍正年间曾奉谕旨,准其一体编入民籍,况此种山民完粮、纳税、与考、服官,一切与齐民相同,并非身操贱业者。比在国家有包含遍覆之仁,在百姓岂可存尔诈我虞之见。但其粧束诡异,未免动人惊疑,且因僻处山陬,罔知体制,子仪节亦多僭越,自非剀切晓谕,则陋俗相沿不革,即群疑亦解释无由。除禀批示并通饬外,合亟示谕,为此示仰閤省军民诸色人等知悉:
古来槃弧之说本属不经,当今中外一家,何可于同乡并井之人而故别其族类!自示之后,该山民男妇人等务将服式改从民俗,不得稍涉奇衺。所有冠丧婚嫁,应遵通礼及朱子家礼为法,均无稍有僭踰,授人口实。百姓亦各屏除畛域,等类齐观,勿仍以畲民相诟病。喁喁向化,耦俱无猜,以成大同之治,本署司有厚望焉。其各凛遵毋违,特示。①
从文告可知三个信息:
一是告示的缘由为钟大焜所见所感,根据告示,当时存在族群间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冲突,钟大焜在同宗族的感情驱使以及士大夫教化一方的使命下,力推改良风俗。
二是清雍正以后,闽、浙、粤的“化外”族群,基本上已“编入民籍”,“完粮、纳税、与考、服官,一切与齐民相同”,然而,因为畲民“僻处山陬,罔知体制”,所以“陋俗相沿不革”,以至“妆束诡异”,畲民应“将服式改从民俗”,以免“授人口实”。
三是认为流传在闽东的“槃弧之说”荒诞不经,百姓应当消除偏见,“屏除畛域,等类齐观”“以成大同之治”,反映士大夫所提倡的“民胞物与”的思想。
钟大焜发布此文告是为了给闽东畲民正名,然而,正如蓝炯熹所指出的,单纯地改变装束等,以机械同化并不能改变当时的汉、畲的族群态势。②
从上述文告可知,钟大焜一方面认为,闽东畲族已经是国家编户齐民了,不能因为其服装和礼仪的不同,就视他们为异类。同时,也劝说闽东畲族改装易服,同时以朱子家礼为礼法,即接受儒家文化传统。我们会发现,随着与汉人接触更多,随着畲族社会变迁,其对盘瓠的理解以及对盘瓠的态度呈现出不一致的地方,表现出复杂的感情。
可以看出,在吴徴鳌的《序言》和文告放置于谱牒之中,对崇奉盘瓠先祖的闽东畲民带来了相当大的思想观念冲击,其文化认同必定受到动摇。
再如福安溪塔村《蓝氏宗谱》畲族知识分子雷一声认为盘瓠之说“历代史籍均无考”,是“腐儒因之,遂以弁诸谱首作鼻祖,并杜撰三代以下之官职而指为三代上之头衔与历朝敕赠封诰,俚言鄙词一串,迂腐卑劣,令人喷饭不已。斯谱之作,本拟删之,但以误传误已深入脑根,牢不可破,姑依原谱存之,虽属鲁鱼亥豕,不胜其弊,然夏王郭公仍阙其文,以符春秋之遗旨。于是,有感而为之,构缀数语,以弁其首云”。③
随着畲民学习更多的汉文化,儒家思想也对畲民的日常行为起了约束的作用。
如罗源松山镇上土港村蓝氏支谱纂修于清咸丰八年(1858年),由该家族蓝大奎的家塾教师、连江县丹阳林光灿撰修并手书,他在《附录议约于后》写道:“……且治家男女更须分别,男正乎外,女正乎内,齐家有道而家道兴焉。即在田园山场耕种,决不许男女无别,与乡人唱和俚歌,语多污秽,恐贻败伦乱俗之讥。”①
这段话反映当时在田园山场耕种时,畲民“男女无别,与乡人唱和俚歌”。所谓俚歌,应该就是畲族或客家山歌。修谱者站在儒家知识分子的角度,认为山歌“语多污秽,恐贻败伦乱俗之讥”。这种观念与当时儒家社会主流思想是分不开的,同时也反映了儒家知识分子改造畲族文化的愿望。
可见,畲族知识分子在面对本族的传统文化时的矛盾心理:一方面由于该人群深受汉文化影响,有去盘瓠化的意愿;另一方面,盘瓠传说已经深入畲民人心,难以一时改变,只能默认该事实的存在。在本族群的文化建构中,不管是畲民还是汉人,都有一部分精英分子在其中起作用,他们的目的就是通过文化建构以本族群在资源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
二、畲民对本族群历史的建构
许多学者认为关于畲族族谱追溯远祖的文字记载实际上是汉化以后的产物。②宋代以来家族修谱之风逐渐渗透到中国边缘底层社会,族谱几乎成了每个家族、宗族的“标配”。前文已经论述到,明清以后,定居后的畲民家族已经向宗族社会发展,有的甚至成为当地的巨家大族。此时大量出现的畲民族谱正是这种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宋明以后族谱编撰,一般以苏洵、欧阳修所撰之谱为典范。正如王明珂指出正史、方志、族谱均可以视为“规范化的书写、阅读与编辑体例”的文类。而这种文类大量出现了“范式化情节”,这些都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和历史心性下的产物。③也就是说,族谱的修撰及其内容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及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苏洵在其《嘉祐集》对族谱论述曰:“盖自唐衰,谱牒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于是乎,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而谱遂大废。”④谱牒在苏洵生活的时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应该视作唐宋的社会变革在文化上的一个表现,其中反映了庶人出身的新兴士大夫家族关于先祖的历史记忆。可以想见,“由贱而贵”或“由贫而富”的家族在本族的族源具有很大的虚构成分。后世族谱基本上会用较大篇幅来追溯祖源,形成了“帝王作之祖,将相为之宗”一种社会风尚。①
畲族族谱也常将历史上同姓氏的历史人物载入本族族谱。福鼎岭兜《冯翊郡雷氏族谱》在记述盘瓠传说之后,又按照时间顺序,记载了本族的历史人物,该谱的《加敕历代世祖荣封列左》称:
敕封盘护忠勇王;受姓始祖、立国侯雷巨祐;夏太康,雷孟初,安阳太守;少康,雷施震,持(特)科侍郎;帝槐,雷俨誉,镇国将军;帝不降,雷金声,巡游御史;商成汤,雷起龙,都督使;太甲,雷行伟,内阁主事;太戌,雷纲厉,安定太守;祖丁,雷遇震,京兆大夫;殷盘庚,雷四勤,黎阳太守;武丁,雷共文,御史大夫;帝乙,雷通奋,宝定太守;周文王,雷勃然,上大夫;东周惠王,雷横,真定太守;汉高祖,雷腾廷,蜀郡太守;高祖,雷义,京兆尚书并仕黎州太守,雷知时,雷州太守;平帝,雷无我,尚书、左仆射;章帝,雷动雨,博州太守;晋,雷炳五,濮阳太守;晋孝武,雷焕,沂州太守;陈太建,雷发嵩,镇国将军;陈,雷霆,中牟令;开皇,雷荣,京兆大夫等。奉侄德清传递部本,赴各处分存,俾我族人按籍观览,以不忘其祖耳。
大清乾隆五十二年丁未桂月谷旦
钦命礼部左侍郎、浙江督学部院雷鋐顿首谨录②
族谱的修撰者记载了从夏、商、周直至隋代开皇年间③二十三位被荣封官爵的祖先。主要是由于如族传说在开皇年间盘瓠之后从有名有姓,时间人物官名。以上将历代如作者十分精确地描述了历代祖先的生活时代、姓名、官职,这种过于精确的描述,恰恰说明了该本族族源的虚构成分。且不说一些地名、官职错漏百出,比如秦朝才开始设置御史大夫,明朝才开始设置内阁等,这些官名不可能出现在夏商周之际;就连《加敕历代世祖荣封列左》的撰述者也可能是伪托:族谱称该段文字为理学名臣雷鋐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所录,然而按宁化《冯翊郡雷氏家谱-世系图》记载,雷鋐“生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二月初四日,卒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月廿五日。”①因此,雷鋐不可能在去世二十余年后还能撰述文字。出现这种谬误,或者是族谱抄录文字时出错,或者是族谱借用雷鋐的影响力,伪托制造了以上的文字。②
该族谱在随后又载有《附列历代名人》,将本族的名人系谱从隋唐时代连接到修谱时代,其文如下:
唐贞观,雷观,京兆大夫、雷州京兆大夫;开元,雷万春,欧州刺史;开元,雷汝升,南郡太守;雷可敬,尚书左仆射;雷纲,洪州都督使;雷建,洪州刺史;后唐同光,雷震兴,军功守府;后汉乾祐,雷琳,黎州太守;雷仁,汴州都御史;后周显德,雷玉光,内阁主事;宋大中祥符,雷应春,吏部侍郎;雷次宗,大学士;雷德逊,理问;南宋绍定,雷石进,奉政大夫;雷化雨,镇国将军;元皇庆,雷尚腾,军功守府;明洪武,雷玉霖,礼部左侍郎;永乐,雷厥因,举人;嘉靖,雷在天,军功守府;崇祯,雷朝斗,进士,雷起云,提督军务;国朝顺治,雷有祥,军功守府;康熙,雷魁,进士;雍正,雷文招,军功守府;乾隆,雷鋐,浙江督学政;嘉庆,雷泽远,福宁州镇州;道光,雷轮,进士、仕江西镇州道;道光,雷学海,任处州府。
道光乙酉科举人雷声华谨录咸丰,雷云,例授文林郎;雷榜荣,进士;同治,雷天兴,壬戌科举人,浙江处州;雷嘉澍,丙午举人,任衢州府县使。
儒童雷宗功、庠生宗显、宗洲谨录③
从史学的角度来看,越接近作者写作年代的内容可信度相对越高一些,如雷云本人就是该谱的撰修者,例授文林郎也是史实。但是,远至唐代的雷万春,族谱称其曾任欧州刺史,正史并无此方面内容的记载,《新唐书》仅提及雷万春是睢阳守城将领张巡的一位偏将。①雷万春本人也被闽东等地畲民纳入本族祖先系谱之中,成为一位家族的保护神,笔者稍后将详细论述。
明清以来,一些家族祖源记忆在具体情节虽然存在许多的虚构成分,但刘志伟认为这种历史的虚构“却与历史大势的真实是统一的,这是明代中期以后知识分子的历史记忆渐次模式化的一种表现”。②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畲民家族在修撰族谱时,也必定遵循了这种“规范化的书写体例”。
首先,是将本宗族与“黄帝后裔”直接或间接牵上了血缘关系。如闽西上杭蓝氏族人认为本族先祖因有熊国君贡秀蓝一株而得姓,一世祖蓝昌奇为炎帝神农氏之后。这种传说颇为流行,也引起本族族人对此种联系的怀疑,如民国时期上杭庐丰蓝氏族谱撰稿人蓝映奎对本族旧谱关于姓氏来源表示怀疑,他引证《辞源》《尚友录》《氏族笺释》《百家姓考略》等关于蓝姓源流的记载,“均以旧谱所载异”他在《闽杭庐丰蓝氏族谱卷末之——溯源志》称:“考我族旧谱称,受姓自昌奇公始,公即炎帝十一世孙,乃帝榆罔之子也。族先哲溯源及此远矣……旧谱称‘昌奇公生,适有熊国以秀蓝入贡,遂赐蓝姓,封汝南郡,火旺公’按我国分郡自秦始皇始,旧谱所称未知何据?但遍查各谱都经详载,累累如贯珠,只得疑以传疑,留待后贤之考定,作溯源志。”③
也就是说,汝南郡在秦以前不存在,然而旧谱却言之凿凿,“累累如贯珠”,作者虽生疑惑,仍“只得疑以传疑”。这种矛盾心态显示了历史记忆建构在族人中一些精英分子的反思,然而却无力转变,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畲民攀附现象的普遍性还有一些畲民族谱叙述先祖时,罗列了唐宋以来有官职的祖先,这些都说明畲民家族在文化认同上,有向主流文化靠拢的趋势。
既然每个家族均将先祖归于“黄帝后裔”,因此,不论是汉族还是畲族,这种具有“规范化书写”模式的族谱在祖源上就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并且社会环境描述、先祖人物言行等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也就是王明珂先生所指出的所谓的“范式化情节”。于是,在社会上以统谱来“联天下为一家”的企图与实践。如明代凌迪知在《万姓统谱》序言中称:“夫天下,家积也,谱可联家矣,则联天下为一家者,盍以天下之姓谱之……岂知万干一本、万派一源,考之世谱,曰五帝三王,无非出于黄帝之后,黄帝一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异者姓异。则知凡有生者,皆一人之身所分也,分而以嗣以续,愈远愈繁,由一人而百姓而千姓而万姓。”①
在此序言中,作者将万姓的一家之起始归于黄帝。在这种“黄帝后裔”历史心性的指引下,“愈来愈多华夏之域的社会中、下层人群,由于获得一些‘历史’(家族史)而成为‘黄帝子孙’。”②
以客家族群为例。原来与畲族有密切关系的客家族群,其在族谱中均将本族的历史与中原发生联系,如出现大量的“石壁”迁居地传说正是这种历史现象的反映。在南方地区同一个姓氏的族谱在祖源的记载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性,这是由于移民需要建构新的集体记忆的结果。③
正是以上这种历史背景下,在清代光绪年间,福州府侯官县人钟大焜在查阅数地族谱后,产生了全国钟姓联谱的想法。光绪二十年钟大焜试图纂修《颍川钟氏总谱》,他在《谱序》中写道:“苟遍考各府县直省,或更得善本谱帙为往时所不经见者,博考周稽,期于精审,则远祖名字世系必可彼此同符,而此之始祖某由某迁来,即彼之裔孙某由某迁去,抄录既广,考核随之,知于支分派衍中必能蝉联巧合,脉络贯通,而世次长幼乌有不别哉!惟远省骤难传抄,兹先以闽省为始,聘请同宗某某负笈遍历抄录,再加修辑、期以二岁藏事,再以余力兼及他省。”④
可见,钟大焜希望通过对各府县谱牒中先祖名字世系来贯通脉络,从本省入手,然后遍及外省,从而形成全国性的钟姓总谱。由于工程过于浩大,力不从心,延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只汇集了福建福州府和福宁府以及江西萍乡的数十部家谱,编成五卷本《颍川钟氏支谱》刊行面世。
其次,将本族与中原在地域上发生联系。在南方地区,汉族将本族姓氏与某一郡望发生联系,其逻辑为先祖曾是中原地区迁来,畲族的这种“攀附”显然受到汉族的思想观念影响,是典型的“门第观念”“中原正统观念”①的体现。乾隆《龙溪县志》论述闽人中原认同时称:“陈元光光州固始人,王审知亦光州固始人,而漳人多祖元光,泉人多祖审知,皆称固始。按郑樵家谱后序云:吾祖出荥阳,过江入闽,皆有源流,孰为光州固始人哉!夫(今)闽人称祖,皆曰光州固始来。实由王潮兄弟王绪入闽,审知因其众,克定闽中,以桑梓故,独优固始。故闽人至今言氏族本之,以当审知之时,重固始也,其实谬滥。”②
从宋代郑樵起就对闽人“光州固始”情结提出疑问,到了清代在一些知识分子中更是对这种“文化建构”有了清醒的认识,然而在大部分的群众中,却以此为文化资本,“重固始”——即将本族祖先与中原联系——成为争夺文化资源的重要策略。正如学者指出,福佬人的“河南光州固始”、客家的“宁化石壁”、广府人的珠玑巷,再包括明清壮族土司谱牒中的南京传说,畲族中的凤凰山传说等,这些都可以被称之为“祖先同乡说”。③
畲民在此思想观念影响下,也将代表华夏地缘符号的“郡邑”与本族联系起来,具体为冯翊雷姓、汝南蓝姓、颍川钟姓,这种符号广泛出现在畲民的宗祠、族谱上。如福安坂中井口《汝南郡蓝氏宗谱》《咏蓝族历代显宦》称:“汝南德望久称隆,食采曾分楚地中。东莞余芳繁子姓,西征伟绩纪凉公。宾师位重衡文选,蹇直人传御史风。缅厥芳徽均足述,固应流泽永无穷”④《跋蓝氏宗谱后》又记载到:“汝南蓝氏昔本望族,自迁闽疆,事耕乍者多,业诗书者少,故其宗谱久未订正。”⑤
族谱说明了本族的郡望所在,并先验地认为本族原来也是官宦世家,只不过到了闽疆以后,主要从事农业,而知识分子少,故而宗谱久未订正。实际上应该是相反,主要从事农业,随着少部分知识分子或族内精英提倡,加上汉族修谱风气的影响,所以宗谱才兴盛起来。
再次,通过攀附某些历史人物间接说明本族来源。如闽东浙南的族谱常有盘王漂失的记载。从严格意义上说,盘王漂失并非历史的真实,应该将其视为畲民对本族群早期迁徙的一种历史解释。①在这个传说中,其中将本族与闽王王审知联系起来,如福鼎《蓝氏宗谱》写道:“唐光启二年(886年),盘、蓝、雷、钟、李有三百六十余丁口,从闽王王审知为乡导,由海来闽,至连江马鼻道登岸,时徙罗源大坝头居焉。盘王碧一船被风漂流,不知去向,故盘姓于今无传。”②
再如修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的福安春雷云村《冯翊雷氏宗谱》,其《谱序》写道:“山东巢贼作乱,士民咸归,惟王审知不从,率河南之众入闽。雷氏祖正礼公同审知入闽,为闽王乡导官,乃迁福州府罗源县大垻头,遂为通闽之祠祖。闽中雷氏由祖而兴,越传至雷公斌,遭兵燹之迫,由罗源转迁本邑穆洋牛石坂,再传至赐公,迁西院,继由西院迁坑下楼,乃讳起凤行香五公是也。”③以上材料均写道本族祖先作为王审知的乡导官。
按照清代梁章钜在《称谓录》中称:“乡导,《宋史·太宗纪》:‘自将伐契丹,次金台,顿募民为乡导者百人。’《孙武子》:‘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④乡导主要为当地居民。族谱中常表述为“随王审知入闽”,应该是王审知“率河南之众入闽”中的一员,然而其身份却是乡导官。从以上表述,我们似乎可以推理,如果王审知等代表的是唐末南下的中原汉人,那么,畲民显然不是与王审知从迁居地一道出发的族群,否则就不可能成为熟悉当地情况的乡导官。如何解释畲民这种矛盾的表述呢?我们似乎可以从《资治通鉴》的记载看出一些端倪,该书《唐纪》曰:“(昭宗景福元年)王潮以从弟彦福为军统、弟审知为都监,将兵攻福州。民自请输米饷军,平湖洞及滨海蛮夷皆以兵船助之。”①
如果从文化学传播的角度来看,“蛮夷兵船相助”的记载应该对畲民族谱中的“闽王乡导官”传说有一定的影响,其中均反映了在华夏化进程中的某一历史时段,华夏族与非华夏民族之间曾有的合作关系。区别在于:前者为宋代汉族知识分子记载,后者则是宋代以后,确切来讲应该是在明清以后畲民的一种历史记忆。汉族知识分子称这些“他者”为“平湖洞及滨海蛮夷”,在明清时期的社会环境下,畲民在表述这段历史时,肯定不会以“蛮夷”自居。因此,如果说“同审知入闽”显示其攀附王审知中原正统身份的话,那么“乡导官”则间接暗示了畲民关于本族为“土著”的一种思维模式。这种复杂心态,正是文化建构中畲民关于本族不同历史来源思想激烈碰撞的产物。
再如,平和县部分钟姓畲族中流传本族祖先钟法兴的故事,也可以将这个故事视为建构的族群历史。在1986—1987年间,福建、广东、江西等省重新识别了一批畲族,平和县南胜、山格、芦溪、九峰、崎岭等乡的蓝姓、钟姓族人正是在此时被恢复为畲族的。为了顺利被恢复为畲族,当地族人特别是一些精英分子奔走其中,如钟姓畲民撰写并向上级递交了《关于迫切要求吾钟氏汉族恢复为畲族申请报告》,该报告介绍了当前的民族政策背景时称:“松州大庙……建庙的目的,在于当时朝廷为纪念杨文广平南时阵亡的所有大小将领。因此,在庙中雕有大小神像四十多尊,其中一尊便是法兴(即钟氏字招,名法兴)系平南有功之臣。为了光宗耀祖,钟氏定以每年正月十四至十六日为祭祖。”②
《平闽十八洞》书中记载,杨文广代表中原王朝平定南闽诸洞“蛮夷”,即叛乱的南方非汉族群。叶国庆先生认为杨文广平闽历史上虽无其事,但该书“演唐陈元光平闽之事无疑。”③郭志超不同意该观点,认为“所谓早唐陈元光在漳州地区平蛮之事不曾发生。”④显然,不管历史上陈元光漳州平蛮是否发生,但杨文广平闽乃是虚构的历史。因此,可以肯定的是,畲民将钟法兴与杨文广平蛮相联系肯定是一种历史的建构。
应该来讲,这种历史建构具有其特殊意义。在明清以后,漳州当地普遍流传着陈元光漳州平蛮的传说。当地畲民被称为“蓝雷仔”,其中也包括钟姓,这些畲民常常被表述为被征服的对象,其后世显然在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皆不同于汉人。该历史建构的逻辑推理是:既然钟法兴为杨文广的部将,钟也是平蛮的主角之一,本族乃征服者,而并非被征服的对象。因此,钟姓畲民通过这个历史建构,来回应“陈元光漳州平蛮”对本族带来的文化压力。
畲民还将雷海青、雷万春、南霁云等历史人物,纳入本族崇拜神灵系谱,这也是畲族文化建构的结果。应该说,以上三个历史人物或虚构人物,最初都不是畲族人物,但畲民通过历史建构而成为本族的英雄祖先。
田都元帅雷海青,是广泛流行于闽粤台等地区的戏剧神。关于雷海清的乐工身份,主要见于唐郑处诲的《明皇杂录·乐工忠死》一文①,但在正史没有其名。有部分学者认为《旧唐书·王维传》中记载王维所作的《凝碧诗》是唐代雷海青的证据②,但《旧唐书》并未提及雷海青之名。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后人根据唐宋史料,不断枝叶其说,“层累”地丰富了雷海青的人物(神格)形象。叶明生先生曾指出:“把田公元帅信仰与唐乐工以忠烈骂贼被安禄山杀害的雷海青联系在一起,大约是明末清初的事。而这种衍变也是在福州、兴化、泉州之间形成。”③雷海青的人物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丰满,不仅从乐工变为神灵,而且被赋予了司音乐、御敌寇、保百姓等多种功能。
雷万春、南霁云为张巡部将,同于睢阳城陷后遇难,历史上确有其人,《新唐书》④有其记载。也有学者认为雷万春就是田公元帅⑤,其从唐代名将到宋代时变为地方保护神,而且有一个从中原到江南一带传播的过程。叶明生也指出,雷海青与雷万春是同庙奉祭的,形象不同,一文一武,但都被民间称为田公帅。⑥总之,以上三人均为在全国或者区域内较有影响的人物,其开始并非以畲民的身份出现。
在明清以后,畲民渐渐将以上人物纳入本族祖先系谱。雷海青、雷万春与畲民雷姓同姓,畲民通过小说歌《锦香亭》等,将雷万春塑造为本族的打虎英雄,成为畲村也是家喻户晓的故事。再如民间传说将“三月三”吃“乌饭”的习俗来源而与雷万春联系起来,这种说法认为:“祖先雷万春困守睢阳区,‘乌饭’充军粮,以此欺敌兵,免为所劫”。①关于“乌饭”的起源,许多地方民众将其与佛教、道教联系起来②,如浦城畲民中流传着乌饭与“目连救母”的故事。③在畲民的乌饭传说众多版本中,较多的是以唐代畲、汉交战为历史背景进行叙述。④
南霁云则被畲民以“南”“蓝”谐音之故,写作“蓝霁云”。如白露坑村神宫中亦有蓝(南)霁云神像。⑤畲民还塑造了文武双全的畲族英雄钟景期,与雷万春等人有紧密的历史联系。畲民不但在钟姓的祠堂中有专门祭祀钟景期的牌位,甚至很多畲村还建庙祭拜,如蕉城区的忠烈庙也有此钟景期、雷万春、蓝(南)霁云三人的塑像。⑥至今在福安的一些村庄,凡是供奉田公元帅的畲族人家,都要在农历八月二十三日过“元帅节”,即为田公元帅雷海清过生日,当日杀大公鸡一只,连同其他供品摆到元帅坛前供祭。祭罢,全家人喝“元帅酒”以祈平安。⑦
一、畲民精英分子的反思与“非畲化”思潮
盘瓠传说或盘瓠信仰对于畲族来说极其重要。畲民关于盘瓠迁徙传说的历史记忆与叙事,一定意义上属于王明珂所说的“英雄徙边记”。④也就是说,盘瓠及三公主作为高贵血统以及高贵地位的祖先,迁徙到各地,成为畲瑶的祖先。清光绪元年(1875年)福安春雷云《冯翊雷氏宗谱·谱序》:“雷氏先世,非即高辛所封之盘瓠我王乎!……而敕封立国侯之巨祐公即雷氏开基之鼻祖。”①《冯翊雷氏宗谱》载有《御偈》曰:“念尔祖宗德泽深,名垂万古受封荣。原为前朝除匪寇,莫将券牒视非真。享镇名山多乐趣,何烦鸟语动幽情。自从敕赐恩膏厚,世代相承及古今。”又有《御赐封联》曰:“功建前朝,帝譬高辛亲救赐;名垂后裔,皇孙公子免差徭。”②这些所谓御赐的偈子或对联应该是畲民根据《开山公据》等传说二次加工。
日本学者村松一弥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和现状》一书中,分析畲民的文献和传说,并判断称:“据说居住在罗源县(福建省)山地的畲族(畲民),是自尊心非常强,富有优越感的集团,而且自信惟有本部族才是高贵民族,蔑视周围的汉族,决不与汉族通婚。”③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畲民在与汉族交流过程中,借用盘瓠传说以维持本民族的边界,其具有强烈自尊心和族群优越感,夸耀本族为“高贵民族”,蔑视周围民族,这正是族群认同感强,族群意识高涨的说明。这种自尊心和优越感同清代以后客家运动中体现出来的优越感有着历史的相似性,正是由于本族群在与其他族群交往中产生的摩擦,促使族群激发出强烈的自我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主要表现为以己为是,而以他族为非,具有强烈的排他性。
在闽东浙南地区,除了部分地方志记载畲民为盘瓠后裔外,还有一些畲族谱也宣称本族为盘瓠后裔者。在福鼎市牛埕下《冯翊雷氏宗谱》中,录有《纂修雷氏族谱序》,该序中作者以本族为盘瓠后裔为荣,认为霞浦、福安以及福鼎等地的畲民均为盘瓠后裔。该序文称:“……他如霞浦是居者瑞发,福安是处者孔亲以及福安之鼻各穆洋溪塔、岩前、老虎岩井白路三坪等处。地名孔多,难以枚举,均是盘瓠王后裔。”④民国四年(1915年)福鼎枇杷坑《钟氏族谱》中载有钟氏后人对盘瓠祖先的追述,如:
藐躬生幸太平时,谱帙未修最系思。莫学崇韬忘己祖,盘瓠以降即宗支。裔孙鸣登谨志。
家乘由来贵晰详,程门旧训最堪尝。本源我溯高辛氏,谱学何须羡盛唐。裔孙起勉谨志。①
由此可见,闽东地区的畲民家族倾向于宣扬盘瓠信仰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并不断宣称本族高贵的血统以及免差徭的政治权力,以此来凝聚族群。清同治九年(1870年),福鼎《蓝氏宗谱》载:“现在闽省连江、罗源、侯官等俱蒙示禁勒石永革,畲黎得安耕凿。”②因此,有学者指出,即使到了清中期以后,各地畲民均纳税服役,畲民还不断通过盘瓠传说及其文本或实物宣称“免差徭”,这可以认为是畲民对政治身份的一种追求,用以与汉人相区别。③
随着畲汉族群交流的加深,族群间关于社会资源的竞争更加激烈,因此,一些畲民家族希望通过传统文化来维持族群边界。如一些畲民希望通过盘瓠传说及其相应的一些文本、实物及口述材料,如《高皇歌》《开山公据》、龙头杖、祖图等,来维护及合理化畲人对华夏边缘资源之拥有与使用,并以此成为解释族群来源、姓氏构成的重要依据。④但是,在强势的汉文化中,一些汉人将畲民的盘瓠传说污名化,使其成为汉人贬低、排斥畲民的工具。而实际上,关于族群的起源,基本上都加入神话的成分,这种神话成分在现实社会中有时会显示出幼稚、夸张、荒谬等特性。正如陈登原在《国史旧闻》所论:“槃瓠之说……至于此事,自属荒昧之记。如太昊蛇形,炎帝蛇首(原注:《北堂书钞》卷一),汤之先世,出于燕卵(原注:《诗·玄鸟篇》郑氏注),可知即在汉族,固亦往往而有,存而弗论可也。”⑤
因此,即使是汉族,也有“蛇首”“燕卵”的祖源传说。在人类社会演进中,每个民族均会创造出一些神话或传说,其中包含了人类“童年时代”的思想,这种认识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特定产物。盘瓠之所以被污名化,不在于其故事的荒谬性,更多的原因在于汉人掌握着话语权。反过来说,假如畲族掌握主流文化的话语权,那么汉人可能因为“蛇首”“燕卵”的祖源传说而被讥笑,当然,这种假设只能是推论而已。
在一些南方非汉族群中,对待“盘瓠”的祖源故事,其情感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受到历代汉族文字记载的影响,他们接受“盘瓠”的祖源传说并神圣化“盘瓠”的形象;另一方面,相对汉族而言,南方非汉族群政治、文化处于劣势地位,在强势汉文化下,非汉族群中的精英分子,特别是一些深受汉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纷纷对本族的“盘瓠”传说进行辩证,并试图对此现状进行改变,有“去盘瓠化”的思想倾向。另外,有一些族群,如瑶族①等,采取与盘瓠有联系②、但又有区别③的“盘古”作为本族始祖,用以宣称自身有比华夏之“黄帝”更古老的起源。④
因此,畲民家族对盘瓠传说进行了有意识地改造、理会与解说,如突出盘瓠的,龙与麒麟或麒麟与凤凰的形象。⑤杨正军认为造成盘瓠形象改变的原因与畲、汉在科举领域的竞争,以及畲族知识分子对本族文化的反思有关。⑥
有些出身畲族的文人开始批驳“盘瓠遗种”说的荒谬无稽,在文字书写的历史记忆重构中表现出强烈的“去盘瓠”意识。钟大焜,福州府侯官县人,同治九年(1870年)中举,光绪三年(1877年)成进士,曾任四品衔刑部主事。光绪二十年(1894年)钟大焜试图纂修《颍川钟氏总谱》。《颍川钟氏支谱》谱成,曾请广西太平府知府吴徴鳌作序,该文对钟姓的畲民身份进行考辨,其文曰:
……余维其先出于颍川四长皓公,后徙于各省,以闽之汀州为盛。其由粤复迁于闽之福宁者,揆其所自,亦由汀而来。福宁族亦繁盛,咸以明洪武进士知浙江天台县音公为始祖。音公后六七传,多山居力农,只与蓝、雷二姓联姻,而人遂称为畲民。考《说文》烧榛种田为畲,入六麻韵音斜,其人七虞韵者为甾,〓之畲音佘,本一字二音,并无〓字。今福宁土民俗书为佘,即官府案赎亦从俗为畲。然考其字义并非恶
劣之称,不过为山居农民而已。①
明清以来,闽东蓝、雷、钟三姓多“山居力农”,并且三姓相互通婚,比较好地保留了畲民的文化传统,正是有这些文化差异,于是“人遂称为畲民”。说明畲民与“土民”之间存在族群边界,“土民”对畲民的称谓,影响到官方对畲民的界定,所谓的“官府案赎亦从俗为畲”。吴徴鳌称畲民只不过是山居的农民,从字、义上说并非“恶劣之称”,这恰恰说明了当时有很大一部分“土民”或官府以“恶劣之称”对“畲”进行认识。
吴徴鳌在“序”中又对畲民中广泛流传的盘瓠传说进行考辨,他认为盘瓠传说是“荒远无稽之言”,因为旧谱中明代之前的世系尚且不能说明详尽,突然将四千余年的祖先源流置于谱端,因此不能令人信服,并对福宁府中畲民攀附盘瓠传说进行批评,他说:
考福宁府属妇人皆裹脚,不裹脚者则髻上加流苏,或加冠,有高及尺余者。即衣服亦与平民稍殊,以为此当时高辛所赐也,初不知外人转因此而目为畲。且近日妇人为此妆饰者不独蓝、雷二姓,渐延及十余姓,所以乐为此者,皆以妇人不裹脚利耕作耳。乃因耕作之便,遂不恤他人之称为畲,又因其先有联姻高辛之荣,遂忘其有盘瓠之辱,且尽将盘瓠事实弁于谱端,复绘图立说张为屏幛,以自别于平民。岂知联姻帝室事属无稽,而盘瓠之辱则已群指而目之,而平民反不与联姻矣。置近代洪武进士天台知县子孙之荣于不顾,而独有取于四千年以前盘瓠之辱以为荣,非由于山民无知不识字不读书,何以至此哉!②
裹脚,亦称缠足,是古代中国特有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明清时期最为兴盛③,上至士大夫,下至编户百姓人家,皆有裹足,这是儒家文化成为主流思想的结果。清代钱泳《履园丛话》就曾议论道:“大凡女人之德,自以性情柔和为第一义,容貌端庄为第二义,至足之大小,本无足重轻。然元、明以来,士大夫家,以至编户小民,莫不裹足,似足之不能不裹,而为容貌之一助……(裹足)并无益于民生,实有关于世教。”①
可见,在明清时期,女子裹脚符合主流文化的审美标准,在某些场合成为区别百姓是否得到教化的一个标准。显然,在福宁府中,不裹脚者不在少数,这些不裹脚者装束与“平民”有较大差别,因此,外人(主要是汉人)将这些装束作为畲民的一种文化特征,实际上,因为不裹脚且服饰适合耕作,所以不仅蓝雷钟三姓为此妆饰,这种衣着装束习俗“渐延及十余姓”,说明许多汉人也采用这种装束,甚至不担心其他人“称之为畲”。从以上材料,不仅可以看出畲民文化影响闽东汉人的文化,甚至可以推及唐宋时期,南迁汉人进入闽粤赣地区时,采借了土著居民的文化习俗,可能在认同上也如闽东汉人,“不恤他人之称为畲”。
就畲族而言,此时他们采用盘瓠传说,作为现有文化习俗的存在作合理的解释,如上文所称的“髻上加流苏,或加冠,有高及尺余者”。关于这种头饰的来源,一些畲民根据盘瓠传说将其与三公主联系起来,或称为“凤冠”。如此看来,这种不裹足、类似“凤冠”的头饰,虽然在外人看来不符合主流文化,却可以成为畲民自我标榜曾联姻高辛帝、有着“自别于平民”的高贵血统,这种历史记忆成为一种对抗主流文化的资本。
还有一些畲族族谱的作者也对盘瓠传说的来源表示怀疑。如修于民国九年(1920年)的霞浦县青皎畲族村《冯翊郡雷氏宗谱》将始祖追溯至轩辕赐姓的西陵氏螺祖,本姓因“雷电而受姓”,认为盘瓠传说是不合理的,该文写道:“谬传帝以女妻盘瓠者,岂不碍于圣门,而同别类乎?能无污蔑古帝,妄读圣经?当人犁舌地狱,以为狂谬无知极矣!……杜君卿《通典》与范蔚宗《后汉书》论沙黔中,五溪蛮僻处苗、徭、黎、壮西南蛮界。东南何所考据以‘菑民’为‘畲民’?亦指盘瓠之后裔也耶?致令无识之徒,借资口实,群相诟骂,漫侮圣经。”②
修谱者认为,盘瓠之说有污蔑圣贤,另外认为,盘瓠之说原属于五溪地区以及西南蛮界,而将东南地区的畲民称为“盘瓠之后裔”,是他者用以互相诟骂的一种说法。依作者看来,盘瓠实际上是外人强加给畲民的,这不符合事实,应该重新审视。作者目的是为了澄清雷氏的祖源,虽然关于畲民的盘瓠祖源传说来源解释不一定符合事实,但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说明了盘瓠传说的其中一个途径是由汉人传入非汉人群中,从而固化为一个族群的印象。
当然,以上只是闽东部分畲民关于本族文化的解释,体现了本族的文化认同。然而畲民文化在汉文化犹如海洋中的孤岛,一些汉族知识分子认为主要原因是教化不够,如吴徴鳌认为钟姓族人将盘瓠事实全部写在谱端,并且“绘图立说张为屏幛”,主要是“由于山民无知不识字不读书”的结果,所以他在谱序中提出设想,这也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普遍思想观念。他说:“宗族既盛则殷实或多,何如广兴乡塾,倡设书院,率子弟而教之。庶他年文教大兴,科名鼎盛,方知前此之愚陋,而有以敦劝其乡人,而渐改其敝俗,以继绳天台公之祖武,且克振颍川之家声,是则余之所厚望也夫。”①
在强势的儒家文化,一些畲族识分子也开始反思,并力图重新建构文化,以扭转外人对本族的偏见。如光绪二十四年福建提刑按察使司的告示,该告示实际上是应钟大焜的要求而发布,称“古来槃弧之说本属不经”,要求畲民改变服式乖习俗,以免“授人口实”。其全文为:
署福建等处提刑按察使司兼管骚传事盐法道余为示谕事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据家丁林添禀称,家主刑部主事钟大焜因修谱到福宁所属各县,见有一种山民,纳粮考试与百姓无异,惟装束不同,群呼为畲。山民不服,时起争端。家主向山民劝改粧束与众一律,便可免此称谓,无不踊跃乐从。惟各山民散处甚多,禀请出示晓谕,等情到司。
据此本署司查,薄海苍生莫非天朝赤子,即闽粤之蛋户、江浙之惰民,雍正年间曾奉谕旨,准其一体编入民籍,况此种山民完粮、纳税、与考、服官,一切与齐民相同,并非身操贱业者。比在国家有包含遍覆之仁,在百姓岂可存尔诈我虞之见。但其粧束诡异,未免动人惊疑,且因僻处山陬,罔知体制,子仪节亦多僭越,自非剀切晓谕,则陋俗相沿不革,即群疑亦解释无由。除禀批示并通饬外,合亟示谕,为此示仰閤省军民诸色人等知悉:
古来槃弧之说本属不经,当今中外一家,何可于同乡并井之人而故别其族类!自示之后,该山民男妇人等务将服式改从民俗,不得稍涉奇衺。所有冠丧婚嫁,应遵通礼及朱子家礼为法,均无稍有僭踰,授人口实。百姓亦各屏除畛域,等类齐观,勿仍以畲民相诟病。喁喁向化,耦俱无猜,以成大同之治,本署司有厚望焉。其各凛遵毋违,特示。①
从文告可知三个信息:
一是告示的缘由为钟大焜所见所感,根据告示,当时存在族群间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冲突,钟大焜在同宗族的感情驱使以及士大夫教化一方的使命下,力推改良风俗。
二是清雍正以后,闽、浙、粤的“化外”族群,基本上已“编入民籍”,“完粮、纳税、与考、服官,一切与齐民相同”,然而,因为畲民“僻处山陬,罔知体制”,所以“陋俗相沿不革”,以至“妆束诡异”,畲民应“将服式改从民俗”,以免“授人口实”。
三是认为流传在闽东的“槃弧之说”荒诞不经,百姓应当消除偏见,“屏除畛域,等类齐观”“以成大同之治”,反映士大夫所提倡的“民胞物与”的思想。
钟大焜发布此文告是为了给闽东畲民正名,然而,正如蓝炯熹所指出的,单纯地改变装束等,以机械同化并不能改变当时的汉、畲的族群态势。②
从上述文告可知,钟大焜一方面认为,闽东畲族已经是国家编户齐民了,不能因为其服装和礼仪的不同,就视他们为异类。同时,也劝说闽东畲族改装易服,同时以朱子家礼为礼法,即接受儒家文化传统。我们会发现,随着与汉人接触更多,随着畲族社会变迁,其对盘瓠的理解以及对盘瓠的态度呈现出不一致的地方,表现出复杂的感情。
可以看出,在吴徴鳌的《序言》和文告放置于谱牒之中,对崇奉盘瓠先祖的闽东畲民带来了相当大的思想观念冲击,其文化认同必定受到动摇。
再如福安溪塔村《蓝氏宗谱》畲族知识分子雷一声认为盘瓠之说“历代史籍均无考”,是“腐儒因之,遂以弁诸谱首作鼻祖,并杜撰三代以下之官职而指为三代上之头衔与历朝敕赠封诰,俚言鄙词一串,迂腐卑劣,令人喷饭不已。斯谱之作,本拟删之,但以误传误已深入脑根,牢不可破,姑依原谱存之,虽属鲁鱼亥豕,不胜其弊,然夏王郭公仍阙其文,以符春秋之遗旨。于是,有感而为之,构缀数语,以弁其首云”。③
随着畲民学习更多的汉文化,儒家思想也对畲民的日常行为起了约束的作用。
如罗源松山镇上土港村蓝氏支谱纂修于清咸丰八年(1858年),由该家族蓝大奎的家塾教师、连江县丹阳林光灿撰修并手书,他在《附录议约于后》写道:“……且治家男女更须分别,男正乎外,女正乎内,齐家有道而家道兴焉。即在田园山场耕种,决不许男女无别,与乡人唱和俚歌,语多污秽,恐贻败伦乱俗之讥。”①
这段话反映当时在田园山场耕种时,畲民“男女无别,与乡人唱和俚歌”。所谓俚歌,应该就是畲族或客家山歌。修谱者站在儒家知识分子的角度,认为山歌“语多污秽,恐贻败伦乱俗之讥”。这种观念与当时儒家社会主流思想是分不开的,同时也反映了儒家知识分子改造畲族文化的愿望。
可见,畲族知识分子在面对本族的传统文化时的矛盾心理:一方面由于该人群深受汉文化影响,有去盘瓠化的意愿;另一方面,盘瓠传说已经深入畲民人心,难以一时改变,只能默认该事实的存在。在本族群的文化建构中,不管是畲民还是汉人,都有一部分精英分子在其中起作用,他们的目的就是通过文化建构以本族群在资源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
二、畲民对本族群历史的建构
许多学者认为关于畲族族谱追溯远祖的文字记载实际上是汉化以后的产物。②宋代以来家族修谱之风逐渐渗透到中国边缘底层社会,族谱几乎成了每个家族、宗族的“标配”。前文已经论述到,明清以后,定居后的畲民家族已经向宗族社会发展,有的甚至成为当地的巨家大族。此时大量出现的畲民族谱正是这种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宋明以后族谱编撰,一般以苏洵、欧阳修所撰之谱为典范。正如王明珂指出正史、方志、族谱均可以视为“规范化的书写、阅读与编辑体例”的文类。而这种文类大量出现了“范式化情节”,这些都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和历史心性下的产物。③也就是说,族谱的修撰及其内容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及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苏洵在其《嘉祐集》对族谱论述曰:“盖自唐衰,谱牒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于是乎,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而谱遂大废。”④谱牒在苏洵生活的时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应该视作唐宋的社会变革在文化上的一个表现,其中反映了庶人出身的新兴士大夫家族关于先祖的历史记忆。可以想见,“由贱而贵”或“由贫而富”的家族在本族的族源具有很大的虚构成分。后世族谱基本上会用较大篇幅来追溯祖源,形成了“帝王作之祖,将相为之宗”一种社会风尚。①
畲族族谱也常将历史上同姓氏的历史人物载入本族族谱。福鼎岭兜《冯翊郡雷氏族谱》在记述盘瓠传说之后,又按照时间顺序,记载了本族的历史人物,该谱的《加敕历代世祖荣封列左》称:
敕封盘护忠勇王;受姓始祖、立国侯雷巨祐;夏太康,雷孟初,安阳太守;少康,雷施震,持(特)科侍郎;帝槐,雷俨誉,镇国将军;帝不降,雷金声,巡游御史;商成汤,雷起龙,都督使;太甲,雷行伟,内阁主事;太戌,雷纲厉,安定太守;祖丁,雷遇震,京兆大夫;殷盘庚,雷四勤,黎阳太守;武丁,雷共文,御史大夫;帝乙,雷通奋,宝定太守;周文王,雷勃然,上大夫;东周惠王,雷横,真定太守;汉高祖,雷腾廷,蜀郡太守;高祖,雷义,京兆尚书并仕黎州太守,雷知时,雷州太守;平帝,雷无我,尚书、左仆射;章帝,雷动雨,博州太守;晋,雷炳五,濮阳太守;晋孝武,雷焕,沂州太守;陈太建,雷发嵩,镇国将军;陈,雷霆,中牟令;开皇,雷荣,京兆大夫等。奉侄德清传递部本,赴各处分存,俾我族人按籍观览,以不忘其祖耳。
大清乾隆五十二年丁未桂月谷旦
钦命礼部左侍郎、浙江督学部院雷鋐顿首谨录②
族谱的修撰者记载了从夏、商、周直至隋代开皇年间③二十三位被荣封官爵的祖先。主要是由于如族传说在开皇年间盘瓠之后从有名有姓,时间人物官名。以上将历代如作者十分精确地描述了历代祖先的生活时代、姓名、官职,这种过于精确的描述,恰恰说明了该本族族源的虚构成分。且不说一些地名、官职错漏百出,比如秦朝才开始设置御史大夫,明朝才开始设置内阁等,这些官名不可能出现在夏商周之际;就连《加敕历代世祖荣封列左》的撰述者也可能是伪托:族谱称该段文字为理学名臣雷鋐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所录,然而按宁化《冯翊郡雷氏家谱-世系图》记载,雷鋐“生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二月初四日,卒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月廿五日。”①因此,雷鋐不可能在去世二十余年后还能撰述文字。出现这种谬误,或者是族谱抄录文字时出错,或者是族谱借用雷鋐的影响力,伪托制造了以上的文字。②
该族谱在随后又载有《附列历代名人》,将本族的名人系谱从隋唐时代连接到修谱时代,其文如下:
唐贞观,雷观,京兆大夫、雷州京兆大夫;开元,雷万春,欧州刺史;开元,雷汝升,南郡太守;雷可敬,尚书左仆射;雷纲,洪州都督使;雷建,洪州刺史;后唐同光,雷震兴,军功守府;后汉乾祐,雷琳,黎州太守;雷仁,汴州都御史;后周显德,雷玉光,内阁主事;宋大中祥符,雷应春,吏部侍郎;雷次宗,大学士;雷德逊,理问;南宋绍定,雷石进,奉政大夫;雷化雨,镇国将军;元皇庆,雷尚腾,军功守府;明洪武,雷玉霖,礼部左侍郎;永乐,雷厥因,举人;嘉靖,雷在天,军功守府;崇祯,雷朝斗,进士,雷起云,提督军务;国朝顺治,雷有祥,军功守府;康熙,雷魁,进士;雍正,雷文招,军功守府;乾隆,雷鋐,浙江督学政;嘉庆,雷泽远,福宁州镇州;道光,雷轮,进士、仕江西镇州道;道光,雷学海,任处州府。
道光乙酉科举人雷声华谨录咸丰,雷云,例授文林郎;雷榜荣,进士;同治,雷天兴,壬戌科举人,浙江处州;雷嘉澍,丙午举人,任衢州府县使。
儒童雷宗功、庠生宗显、宗洲谨录③
从史学的角度来看,越接近作者写作年代的内容可信度相对越高一些,如雷云本人就是该谱的撰修者,例授文林郎也是史实。但是,远至唐代的雷万春,族谱称其曾任欧州刺史,正史并无此方面内容的记载,《新唐书》仅提及雷万春是睢阳守城将领张巡的一位偏将。①雷万春本人也被闽东等地畲民纳入本族祖先系谱之中,成为一位家族的保护神,笔者稍后将详细论述。
明清以来,一些家族祖源记忆在具体情节虽然存在许多的虚构成分,但刘志伟认为这种历史的虚构“却与历史大势的真实是统一的,这是明代中期以后知识分子的历史记忆渐次模式化的一种表现”。②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畲民家族在修撰族谱时,也必定遵循了这种“规范化的书写体例”。
首先,是将本宗族与“黄帝后裔”直接或间接牵上了血缘关系。如闽西上杭蓝氏族人认为本族先祖因有熊国君贡秀蓝一株而得姓,一世祖蓝昌奇为炎帝神农氏之后。这种传说颇为流行,也引起本族族人对此种联系的怀疑,如民国时期上杭庐丰蓝氏族谱撰稿人蓝映奎对本族旧谱关于姓氏来源表示怀疑,他引证《辞源》《尚友录》《氏族笺释》《百家姓考略》等关于蓝姓源流的记载,“均以旧谱所载异”他在《闽杭庐丰蓝氏族谱卷末之——溯源志》称:“考我族旧谱称,受姓自昌奇公始,公即炎帝十一世孙,乃帝榆罔之子也。族先哲溯源及此远矣……旧谱称‘昌奇公生,适有熊国以秀蓝入贡,遂赐蓝姓,封汝南郡,火旺公’按我国分郡自秦始皇始,旧谱所称未知何据?但遍查各谱都经详载,累累如贯珠,只得疑以传疑,留待后贤之考定,作溯源志。”③
也就是说,汝南郡在秦以前不存在,然而旧谱却言之凿凿,“累累如贯珠”,作者虽生疑惑,仍“只得疑以传疑”。这种矛盾心态显示了历史记忆建构在族人中一些精英分子的反思,然而却无力转变,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畲民攀附现象的普遍性还有一些畲民族谱叙述先祖时,罗列了唐宋以来有官职的祖先,这些都说明畲民家族在文化认同上,有向主流文化靠拢的趋势。
既然每个家族均将先祖归于“黄帝后裔”,因此,不论是汉族还是畲族,这种具有“规范化书写”模式的族谱在祖源上就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并且社会环境描述、先祖人物言行等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也就是王明珂先生所指出的所谓的“范式化情节”。于是,在社会上以统谱来“联天下为一家”的企图与实践。如明代凌迪知在《万姓统谱》序言中称:“夫天下,家积也,谱可联家矣,则联天下为一家者,盍以天下之姓谱之……岂知万干一本、万派一源,考之世谱,曰五帝三王,无非出于黄帝之后,黄帝一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异者姓异。则知凡有生者,皆一人之身所分也,分而以嗣以续,愈远愈繁,由一人而百姓而千姓而万姓。”①
在此序言中,作者将万姓的一家之起始归于黄帝。在这种“黄帝后裔”历史心性的指引下,“愈来愈多华夏之域的社会中、下层人群,由于获得一些‘历史’(家族史)而成为‘黄帝子孙’。”②
以客家族群为例。原来与畲族有密切关系的客家族群,其在族谱中均将本族的历史与中原发生联系,如出现大量的“石壁”迁居地传说正是这种历史现象的反映。在南方地区同一个姓氏的族谱在祖源的记载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性,这是由于移民需要建构新的集体记忆的结果。③
正是以上这种历史背景下,在清代光绪年间,福州府侯官县人钟大焜在查阅数地族谱后,产生了全国钟姓联谱的想法。光绪二十年钟大焜试图纂修《颍川钟氏总谱》,他在《谱序》中写道:“苟遍考各府县直省,或更得善本谱帙为往时所不经见者,博考周稽,期于精审,则远祖名字世系必可彼此同符,而此之始祖某由某迁来,即彼之裔孙某由某迁去,抄录既广,考核随之,知于支分派衍中必能蝉联巧合,脉络贯通,而世次长幼乌有不别哉!惟远省骤难传抄,兹先以闽省为始,聘请同宗某某负笈遍历抄录,再加修辑、期以二岁藏事,再以余力兼及他省。”④
可见,钟大焜希望通过对各府县谱牒中先祖名字世系来贯通脉络,从本省入手,然后遍及外省,从而形成全国性的钟姓总谱。由于工程过于浩大,力不从心,延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只汇集了福建福州府和福宁府以及江西萍乡的数十部家谱,编成五卷本《颍川钟氏支谱》刊行面世。
其次,将本族与中原在地域上发生联系。在南方地区,汉族将本族姓氏与某一郡望发生联系,其逻辑为先祖曾是中原地区迁来,畲族的这种“攀附”显然受到汉族的思想观念影响,是典型的“门第观念”“中原正统观念”①的体现。乾隆《龙溪县志》论述闽人中原认同时称:“陈元光光州固始人,王审知亦光州固始人,而漳人多祖元光,泉人多祖审知,皆称固始。按郑樵家谱后序云:吾祖出荥阳,过江入闽,皆有源流,孰为光州固始人哉!夫(今)闽人称祖,皆曰光州固始来。实由王潮兄弟王绪入闽,审知因其众,克定闽中,以桑梓故,独优固始。故闽人至今言氏族本之,以当审知之时,重固始也,其实谬滥。”②
从宋代郑樵起就对闽人“光州固始”情结提出疑问,到了清代在一些知识分子中更是对这种“文化建构”有了清醒的认识,然而在大部分的群众中,却以此为文化资本,“重固始”——即将本族祖先与中原联系——成为争夺文化资源的重要策略。正如学者指出,福佬人的“河南光州固始”、客家的“宁化石壁”、广府人的珠玑巷,再包括明清壮族土司谱牒中的南京传说,畲族中的凤凰山传说等,这些都可以被称之为“祖先同乡说”。③
畲民在此思想观念影响下,也将代表华夏地缘符号的“郡邑”与本族联系起来,具体为冯翊雷姓、汝南蓝姓、颍川钟姓,这种符号广泛出现在畲民的宗祠、族谱上。如福安坂中井口《汝南郡蓝氏宗谱》《咏蓝族历代显宦》称:“汝南德望久称隆,食采曾分楚地中。东莞余芳繁子姓,西征伟绩纪凉公。宾师位重衡文选,蹇直人传御史风。缅厥芳徽均足述,固应流泽永无穷”④《跋蓝氏宗谱后》又记载到:“汝南蓝氏昔本望族,自迁闽疆,事耕乍者多,业诗书者少,故其宗谱久未订正。”⑤
族谱说明了本族的郡望所在,并先验地认为本族原来也是官宦世家,只不过到了闽疆以后,主要从事农业,而知识分子少,故而宗谱久未订正。实际上应该是相反,主要从事农业,随着少部分知识分子或族内精英提倡,加上汉族修谱风气的影响,所以宗谱才兴盛起来。
再次,通过攀附某些历史人物间接说明本族来源。如闽东浙南的族谱常有盘王漂失的记载。从严格意义上说,盘王漂失并非历史的真实,应该将其视为畲民对本族群早期迁徙的一种历史解释。①在这个传说中,其中将本族与闽王王审知联系起来,如福鼎《蓝氏宗谱》写道:“唐光启二年(886年),盘、蓝、雷、钟、李有三百六十余丁口,从闽王王审知为乡导,由海来闽,至连江马鼻道登岸,时徙罗源大坝头居焉。盘王碧一船被风漂流,不知去向,故盘姓于今无传。”②
再如修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的福安春雷云村《冯翊雷氏宗谱》,其《谱序》写道:“山东巢贼作乱,士民咸归,惟王审知不从,率河南之众入闽。雷氏祖正礼公同审知入闽,为闽王乡导官,乃迁福州府罗源县大垻头,遂为通闽之祠祖。闽中雷氏由祖而兴,越传至雷公斌,遭兵燹之迫,由罗源转迁本邑穆洋牛石坂,再传至赐公,迁西院,继由西院迁坑下楼,乃讳起凤行香五公是也。”③以上材料均写道本族祖先作为王审知的乡导官。
按照清代梁章钜在《称谓录》中称:“乡导,《宋史·太宗纪》:‘自将伐契丹,次金台,顿募民为乡导者百人。’《孙武子》:‘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④乡导主要为当地居民。族谱中常表述为“随王审知入闽”,应该是王审知“率河南之众入闽”中的一员,然而其身份却是乡导官。从以上表述,我们似乎可以推理,如果王审知等代表的是唐末南下的中原汉人,那么,畲民显然不是与王审知从迁居地一道出发的族群,否则就不可能成为熟悉当地情况的乡导官。如何解释畲民这种矛盾的表述呢?我们似乎可以从《资治通鉴》的记载看出一些端倪,该书《唐纪》曰:“(昭宗景福元年)王潮以从弟彦福为军统、弟审知为都监,将兵攻福州。民自请输米饷军,平湖洞及滨海蛮夷皆以兵船助之。”①
如果从文化学传播的角度来看,“蛮夷兵船相助”的记载应该对畲民族谱中的“闽王乡导官”传说有一定的影响,其中均反映了在华夏化进程中的某一历史时段,华夏族与非华夏民族之间曾有的合作关系。区别在于:前者为宋代汉族知识分子记载,后者则是宋代以后,确切来讲应该是在明清以后畲民的一种历史记忆。汉族知识分子称这些“他者”为“平湖洞及滨海蛮夷”,在明清时期的社会环境下,畲民在表述这段历史时,肯定不会以“蛮夷”自居。因此,如果说“同审知入闽”显示其攀附王审知中原正统身份的话,那么“乡导官”则间接暗示了畲民关于本族为“土著”的一种思维模式。这种复杂心态,正是文化建构中畲民关于本族不同历史来源思想激烈碰撞的产物。
再如,平和县部分钟姓畲族中流传本族祖先钟法兴的故事,也可以将这个故事视为建构的族群历史。在1986—1987年间,福建、广东、江西等省重新识别了一批畲族,平和县南胜、山格、芦溪、九峰、崎岭等乡的蓝姓、钟姓族人正是在此时被恢复为畲族的。为了顺利被恢复为畲族,当地族人特别是一些精英分子奔走其中,如钟姓畲民撰写并向上级递交了《关于迫切要求吾钟氏汉族恢复为畲族申请报告》,该报告介绍了当前的民族政策背景时称:“松州大庙……建庙的目的,在于当时朝廷为纪念杨文广平南时阵亡的所有大小将领。因此,在庙中雕有大小神像四十多尊,其中一尊便是法兴(即钟氏字招,名法兴)系平南有功之臣。为了光宗耀祖,钟氏定以每年正月十四至十六日为祭祖。”②
《平闽十八洞》书中记载,杨文广代表中原王朝平定南闽诸洞“蛮夷”,即叛乱的南方非汉族群。叶国庆先生认为杨文广平闽历史上虽无其事,但该书“演唐陈元光平闽之事无疑。”③郭志超不同意该观点,认为“所谓早唐陈元光在漳州地区平蛮之事不曾发生。”④显然,不管历史上陈元光漳州平蛮是否发生,但杨文广平闽乃是虚构的历史。因此,可以肯定的是,畲民将钟法兴与杨文广平蛮相联系肯定是一种历史的建构。
应该来讲,这种历史建构具有其特殊意义。在明清以后,漳州当地普遍流传着陈元光漳州平蛮的传说。当地畲民被称为“蓝雷仔”,其中也包括钟姓,这些畲民常常被表述为被征服的对象,其后世显然在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皆不同于汉人。该历史建构的逻辑推理是:既然钟法兴为杨文广的部将,钟也是平蛮的主角之一,本族乃征服者,而并非被征服的对象。因此,钟姓畲民通过这个历史建构,来回应“陈元光漳州平蛮”对本族带来的文化压力。
畲民还将雷海青、雷万春、南霁云等历史人物,纳入本族崇拜神灵系谱,这也是畲族文化建构的结果。应该说,以上三个历史人物或虚构人物,最初都不是畲族人物,但畲民通过历史建构而成为本族的英雄祖先。
田都元帅雷海青,是广泛流行于闽粤台等地区的戏剧神。关于雷海清的乐工身份,主要见于唐郑处诲的《明皇杂录·乐工忠死》一文①,但在正史没有其名。有部分学者认为《旧唐书·王维传》中记载王维所作的《凝碧诗》是唐代雷海青的证据②,但《旧唐书》并未提及雷海青之名。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后人根据唐宋史料,不断枝叶其说,“层累”地丰富了雷海青的人物(神格)形象。叶明生先生曾指出:“把田公元帅信仰与唐乐工以忠烈骂贼被安禄山杀害的雷海青联系在一起,大约是明末清初的事。而这种衍变也是在福州、兴化、泉州之间形成。”③雷海青的人物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丰满,不仅从乐工变为神灵,而且被赋予了司音乐、御敌寇、保百姓等多种功能。
雷万春、南霁云为张巡部将,同于睢阳城陷后遇难,历史上确有其人,《新唐书》④有其记载。也有学者认为雷万春就是田公元帅⑤,其从唐代名将到宋代时变为地方保护神,而且有一个从中原到江南一带传播的过程。叶明生也指出,雷海青与雷万春是同庙奉祭的,形象不同,一文一武,但都被民间称为田公帅。⑥总之,以上三人均为在全国或者区域内较有影响的人物,其开始并非以畲民的身份出现。
在明清以后,畲民渐渐将以上人物纳入本族祖先系谱。雷海青、雷万春与畲民雷姓同姓,畲民通过小说歌《锦香亭》等,将雷万春塑造为本族的打虎英雄,成为畲村也是家喻户晓的故事。再如民间传说将“三月三”吃“乌饭”的习俗来源而与雷万春联系起来,这种说法认为:“祖先雷万春困守睢阳区,‘乌饭’充军粮,以此欺敌兵,免为所劫”。①关于“乌饭”的起源,许多地方民众将其与佛教、道教联系起来②,如浦城畲民中流传着乌饭与“目连救母”的故事。③在畲民的乌饭传说众多版本中,较多的是以唐代畲、汉交战为历史背景进行叙述。④
南霁云则被畲民以“南”“蓝”谐音之故,写作“蓝霁云”。如白露坑村神宫中亦有蓝(南)霁云神像。⑤畲民还塑造了文武双全的畲族英雄钟景期,与雷万春等人有紧密的历史联系。畲民不但在钟姓的祠堂中有专门祭祀钟景期的牌位,甚至很多畲村还建庙祭拜,如蕉城区的忠烈庙也有此钟景期、雷万春、蓝(南)霁云三人的塑像。⑥至今在福安的一些村庄,凡是供奉田公元帅的畲族人家,都要在农历八月二十三日过“元帅节”,即为田公元帅雷海清过生日,当日杀大公鸡一只,连同其他供品摆到元帅坛前供祭。祭罢,全家人喝“元帅酒”以祈平安。⑦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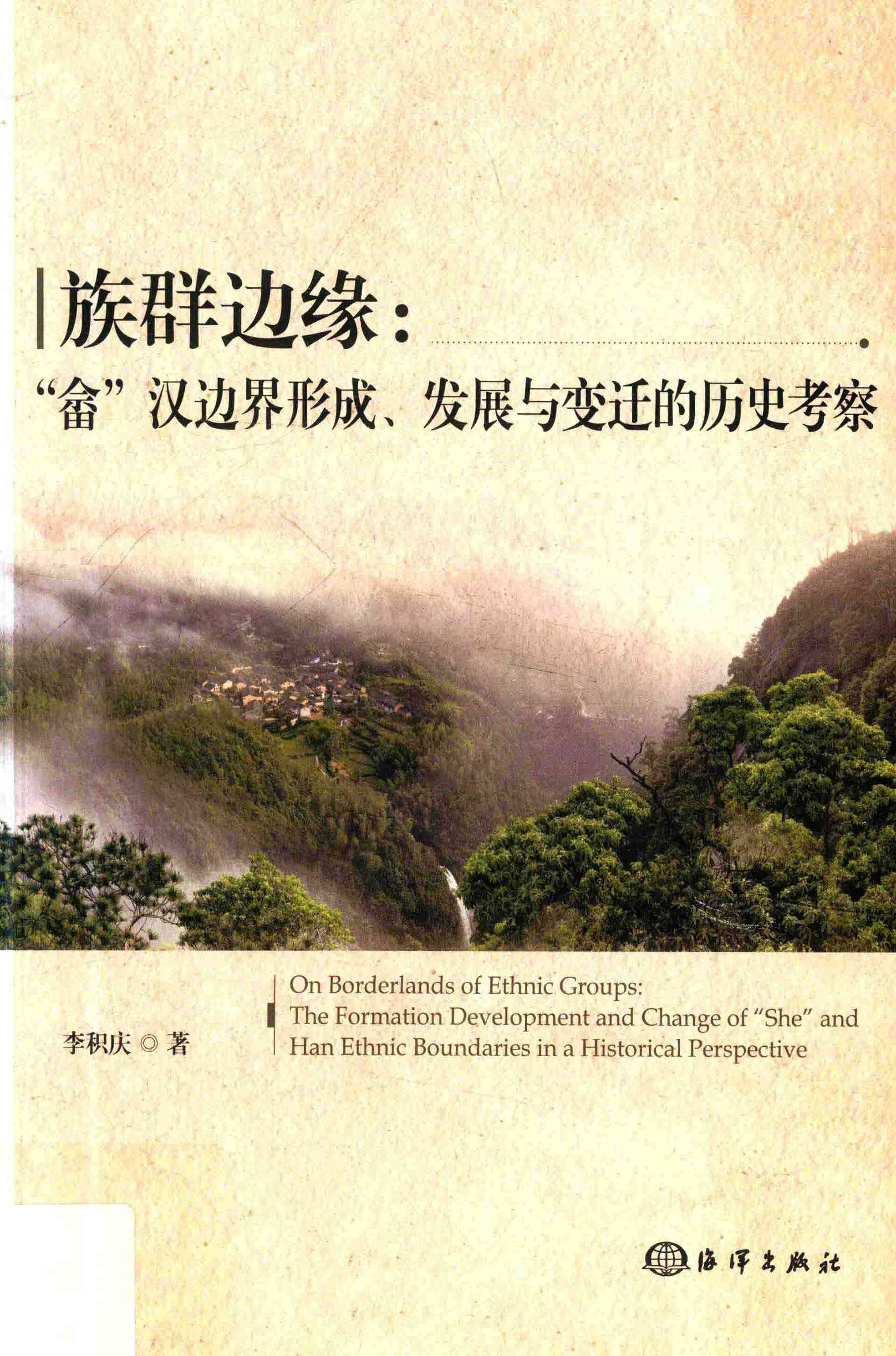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出版者:海洋出版社
本书从族群边界的理论角度,重新审视畲族形成、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在承认族群客观历史文化的同时,重点研究历史上“他者”(主要是汉族)对“畲”的社会定义以及“自者”(主要为南方非汉族群)自我族群认同的过程,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现实意义。
阅读
相关地名
宁德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