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额之争与畲汉边界的强化
| 内容出处: |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图书 |
| 唯一号: | 130920020230003818 |
| 颗粒名称: | 三、学额之争与畲汉边界的强化 |
| 分类号: | K288.3 |
| 页数: | 5 |
| 页码: | 222-226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畲民在历史上受到的族群歧视,特别是在科举考试方面的阻碍。 |
| 关键词: | 畲民 文化 族群 |
内容
如果说在日常接触中,汉人以蔑称称呼畲民是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现象,那么在学额之争中,汉人对畲民的蔑称则将这种畲汉矛盾推向新的高度,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古代科举是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许多百姓希望通过科举实现所谓的“由贱而贵”。换言之,一旦掌握了文化的话语权,就可以提高身份,家族也有可能成为当地望族。因此,科举作为一种文化资源,不仅培养了大量人才,加强了王朝的统治,对于统治者而言,科举所及之处,也是帝国王化的表现,尤其是在边陲地区的非汉民族中实行科举,常常被视为帝国强大,皇恩泽被天下,四方“夷狄”归化的象征。因此,一个地方科举的推行情况常常成为地方治理、官员业绩的重要考核标准之一。明清时期,随着闽东畲民社会的稳定,越来越多的畲民知识分子希望通过科举进入主流文化圈,并实现社会阶层流动。这种文化资源的竞争引起了汉人的警觉,他们通过“种族”区分排除畲民,历史上在闽浙赣地区出现了几次的学额之争,畲民通过抗争,更加强化本族的凝聚力。
吴楚椿在《畲民考》称清初移入浙江的畲民起先多从事佃耕、轿夫等行业,较少有读书者,随着畲民生活的稳定以及家族的发展,也出现了部分读书的畲民。该文称:“顺治间,迁琼海之民于浙,名畲民。而处郡十县尤多,在青田者分钟、雷、蓝、盆、娄五姓,力耕作苦,或佃种田亩,或扛抬山舆。识字者绝少,土民以异类目之,彼亦不能与较。我国家休养生息,人文蔚起,畲民有读书者,入衙门充书吏,未敢考试。间出应试,土人辄攻之,曰:‘畲民系盘瓠遗种’。”①
但这些读书的畲民不敢考试,主要是因为土人的攻击。光绪《处州府志》又称:“近有读书通文义者,巡抚学使谓于朝,得注民籍与考试之列矣。括人顾嗤鄙之,不与通婚姻,辄目为盘瓠遗种。”②
乾隆时期,官府开始对这种族群矛盾进行干预。由于畲民陆续纳税服役,在政治身份上成为编户齐民,所以官方不主张对畲民区别对待,如吴楚椿《畲民考》:“今夫习俗之弊莫甚于党同伐异……我国家中外遐迩,一视同仁,导民为善,惰民乐户皆准改业。僮瑶荒徼,增设苗学,况畲民本属琼海淳良,奉官迁浙,力农务本,已逾百年。合处属计之奚啻千户,而一任土民谬引荒诞不经之说,斥为异类,阻其上进之阶,是草野之横议也。乾隆四十一年秋,署府宪梁命余查办,余已备详在案。又据处属各县均查明,实系农民亦在案,因试期太迫,未暇详请,谨慎为著其大略如此。”③
嘉庆、道光年间,闽东、浙南等地的学额之争达到顶峰。如清嘉庆七年,“福鼎童生钟良弼呈控,县书串通生监诬指畲民不准与试。”时任福建巡抚的李
殿图“饬司道严讯”,并且详细回复,“张示士林”,对“诬指畲民不准与试”的言论进行反驳:“尔等将版图之内曾经输粮纳税,并有入学年分确据者,以为不入版图,阻其向往之路,则又不知是何肺腑也!婚优隶卒三世不习旧业,例尚准其应试,何独畲民有意排击之?……本部院为世道人心风俗起见,不惮与尔等覙缕言之。”①
钟良弼,原名钟鸣云(1780—1842年),福宁府学生员,福鼎丹桥钟氏十田公派下第二十三世。清嘉庆七年(1802年)因民间歧视畲民,钟良弼赴考受阻,遂典卖家产顽强上诉,得福建巡抚李殿图主持正义,终于第二年考取府学生员,名动全省。嗣后其事迹被畲族歌手编成歌谣,在闽、浙畲民中广为传唱。清道光十九年,钟良弼年届六十“闲暇在家”,受家族推崇主持纂修宗谱。其事迹记载在族谱中,并通过小说《钟良弼》等传播,不断强化畲民族群意识,使得原来存在的族群边界维系得更加牢固。畲民外将一些科举得名者不断地记录在族谱,强化该历史记忆,凝聚人心。福鼎枇杷坑《钟氏族谱》的《本支小引》:
始祖士田公由九都新丘迁二十都王佳洋单桥……臣公在单桥创大厦,置膏腆。嘉庆七年,曾孙良弼、良材训闻诗书,志矢上进,廪生陈希尧保结,在岳邑尊与考,八年科试蒙恩宗师取进钟良弼府学生员第二十名,廿一年蒙翰宗师备进佾生钟良材第二名。道光廿一年,王府尊岁试取录前列第六名钟熙,年科试取录前列第八名,廿二年蒙温宗师取进福鼎县学第五名,咸丰己未年乡荐中式贡元第一名,钦加州同知衔候补直隶州。②
另一个例子为平阳人雷云。他在为福鼎岭兜《冯翊郡雷氏族谱》撰谱时,自述了为争得考试资格的过程,其文曰:
予甫七岁则就外傅,累年不辍,学文诵诗,志切上进,弱冠之年遂赴童子之试。溯我祖自明季之徙平也,天荒尚未见破,临场之际竟被妒诬抑阻,缠讼三载,往府造省,涉水陟山,日夜奔驰,风尘劳瘁,经受多少艰辛,子孙方得赴试。抚台提奏此案,载入《学政全书》,云路有自。我系次嗣也,名虽不登于泮水,身既入贡于天家,一门之内,继继①绳绳,咸知耕读实我先君之尊师重道有以报也。
以上的《学政全书》于嘉庆八年(1803年)所作,记录在福鼎岭兜《冯翊郡雷氏族谱》中,该文详细记载了“浙江巡抚臣阮元会同浙江学政臣文宁咨称,处州府属青田县有畲民钟正芳等呈请与土民一体应试一事。”认为畲民意为农民,本来不是恶称,而且畲民在青田等地“置有粮祠庐墓,素行并非秽贱”,只因“畲妇头戴布冠与本处妇女稍有不同,土著者指为异类,廪生等惑于俗说不敢具保,致畲民不得与试。”作者作此《学政全书》目的在于使畲民不因“其妇女服饰稍异,概阻其向上之心”,因此,“咨请部示期明立章程,以免无识愚民藉词攻讦”。②
《学政全书》颁发后,并未能完全消解学额之争。在光绪《处州府志》曾记载温州畲民求考受阻之事,其文曰:
嘉庆八年,仪征阮文达公抚浙,会同学使文宁,咨准一体考试。其(畲民,笔者注)散居温州者,于道光六年援例求考,诸生禀于学使宝应朱文定公云:“照例身家不清白者,不准与考。”泰顺畲民皆作舆台为人役,身家未为清白,奉批不准与考。丽邑畲民亦有与之相类者,当分别观之一也。③
在清代,闽浙等地区的百姓耻于从事轿夫、仆隶等职业,如福安诸生陈上储在《呈福宁府志事实序》说道:“福宁负山环海,浙尾闽头……以风俗言之,五邑淳漓相半,而皆质直好义。富者不与贫争利,贫者矫语贫贱而傲富贵。即室如悬磬,甘守其穷,耻为舆夫、仆隶。”④在这种观念下,一些汉人将泰顺、丽水等地区畲民从事轿夫等下等行业作为阻止畲民应考的借口。官府以客观的立场出面澄清,认为此事不能以偏概全,即部分畲民从事轿夫职业不能等同于所有畲民的身份。
这种争论在随后数十年中仍在持续进行着。道光廿七年(1847年),官方颁布《温州府谕禁阻考告示》,说明当时畲汉学额之争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畲汉族群矛盾也达到了较深的程度。因此,不得不由官方出面发布告示,希望通过告示抑制畲汉矛盾的继续激化。根据《温州府谕禁阻考告示》记载,当时平阳县有廪生及各童“阻挠攻讦”畲民雷云等人赴考。告示做出公允判断,认为“该县各童阻挠显违定例,自应严行查禁”,虽然“县、府两试均已考过”,但是允许“该童雷云并请准其分别补考”。发布此告示,“示仰平阳县廪保生童人等知悉,嗣后如有畲民赴考,应照定例准其一体考试,毋许再行阻挠致滋事端。”①
这个阶段,畲民的抗争得到官方的重视,官方通过一些文告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畲民的部分利益。此外,畲民的抱团抗争行为激发了族群的凝聚力,确实增强了畲民的族群认同。蒋炳钊先生认为,畲民在迁徙到闽东后,需要加强内部的团结,而传统文化是“反抗外族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强化本民族内部团结,加强民族的凝聚力”的一个重要纽带。②然而,文化资源的争取对畲民认同来讲,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因为一些畲族知识分子在吸收了儒家文化后,开始对本民族的族源传说进行反思,在他们的推动下,畲汉的族群边界再次发生漂移。
古代科举是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许多百姓希望通过科举实现所谓的“由贱而贵”。换言之,一旦掌握了文化的话语权,就可以提高身份,家族也有可能成为当地望族。因此,科举作为一种文化资源,不仅培养了大量人才,加强了王朝的统治,对于统治者而言,科举所及之处,也是帝国王化的表现,尤其是在边陲地区的非汉民族中实行科举,常常被视为帝国强大,皇恩泽被天下,四方“夷狄”归化的象征。因此,一个地方科举的推行情况常常成为地方治理、官员业绩的重要考核标准之一。明清时期,随着闽东畲民社会的稳定,越来越多的畲民知识分子希望通过科举进入主流文化圈,并实现社会阶层流动。这种文化资源的竞争引起了汉人的警觉,他们通过“种族”区分排除畲民,历史上在闽浙赣地区出现了几次的学额之争,畲民通过抗争,更加强化本族的凝聚力。
吴楚椿在《畲民考》称清初移入浙江的畲民起先多从事佃耕、轿夫等行业,较少有读书者,随着畲民生活的稳定以及家族的发展,也出现了部分读书的畲民。该文称:“顺治间,迁琼海之民于浙,名畲民。而处郡十县尤多,在青田者分钟、雷、蓝、盆、娄五姓,力耕作苦,或佃种田亩,或扛抬山舆。识字者绝少,土民以异类目之,彼亦不能与较。我国家休养生息,人文蔚起,畲民有读书者,入衙门充书吏,未敢考试。间出应试,土人辄攻之,曰:‘畲民系盘瓠遗种’。”①
但这些读书的畲民不敢考试,主要是因为土人的攻击。光绪《处州府志》又称:“近有读书通文义者,巡抚学使谓于朝,得注民籍与考试之列矣。括人顾嗤鄙之,不与通婚姻,辄目为盘瓠遗种。”②
乾隆时期,官府开始对这种族群矛盾进行干预。由于畲民陆续纳税服役,在政治身份上成为编户齐民,所以官方不主张对畲民区别对待,如吴楚椿《畲民考》:“今夫习俗之弊莫甚于党同伐异……我国家中外遐迩,一视同仁,导民为善,惰民乐户皆准改业。僮瑶荒徼,增设苗学,况畲民本属琼海淳良,奉官迁浙,力农务本,已逾百年。合处属计之奚啻千户,而一任土民谬引荒诞不经之说,斥为异类,阻其上进之阶,是草野之横议也。乾隆四十一年秋,署府宪梁命余查办,余已备详在案。又据处属各县均查明,实系农民亦在案,因试期太迫,未暇详请,谨慎为著其大略如此。”③
嘉庆、道光年间,闽东、浙南等地的学额之争达到顶峰。如清嘉庆七年,“福鼎童生钟良弼呈控,县书串通生监诬指畲民不准与试。”时任福建巡抚的李
殿图“饬司道严讯”,并且详细回复,“张示士林”,对“诬指畲民不准与试”的言论进行反驳:“尔等将版图之内曾经输粮纳税,并有入学年分确据者,以为不入版图,阻其向往之路,则又不知是何肺腑也!婚优隶卒三世不习旧业,例尚准其应试,何独畲民有意排击之?……本部院为世道人心风俗起见,不惮与尔等覙缕言之。”①
钟良弼,原名钟鸣云(1780—1842年),福宁府学生员,福鼎丹桥钟氏十田公派下第二十三世。清嘉庆七年(1802年)因民间歧视畲民,钟良弼赴考受阻,遂典卖家产顽强上诉,得福建巡抚李殿图主持正义,终于第二年考取府学生员,名动全省。嗣后其事迹被畲族歌手编成歌谣,在闽、浙畲民中广为传唱。清道光十九年,钟良弼年届六十“闲暇在家”,受家族推崇主持纂修宗谱。其事迹记载在族谱中,并通过小说《钟良弼》等传播,不断强化畲民族群意识,使得原来存在的族群边界维系得更加牢固。畲民外将一些科举得名者不断地记录在族谱,强化该历史记忆,凝聚人心。福鼎枇杷坑《钟氏族谱》的《本支小引》:
始祖士田公由九都新丘迁二十都王佳洋单桥……臣公在单桥创大厦,置膏腆。嘉庆七年,曾孙良弼、良材训闻诗书,志矢上进,廪生陈希尧保结,在岳邑尊与考,八年科试蒙恩宗师取进钟良弼府学生员第二十名,廿一年蒙翰宗师备进佾生钟良材第二名。道光廿一年,王府尊岁试取录前列第六名钟熙,年科试取录前列第八名,廿二年蒙温宗师取进福鼎县学第五名,咸丰己未年乡荐中式贡元第一名,钦加州同知衔候补直隶州。②
另一个例子为平阳人雷云。他在为福鼎岭兜《冯翊郡雷氏族谱》撰谱时,自述了为争得考试资格的过程,其文曰:
予甫七岁则就外傅,累年不辍,学文诵诗,志切上进,弱冠之年遂赴童子之试。溯我祖自明季之徙平也,天荒尚未见破,临场之际竟被妒诬抑阻,缠讼三载,往府造省,涉水陟山,日夜奔驰,风尘劳瘁,经受多少艰辛,子孙方得赴试。抚台提奏此案,载入《学政全书》,云路有自。我系次嗣也,名虽不登于泮水,身既入贡于天家,一门之内,继继①绳绳,咸知耕读实我先君之尊师重道有以报也。
以上的《学政全书》于嘉庆八年(1803年)所作,记录在福鼎岭兜《冯翊郡雷氏族谱》中,该文详细记载了“浙江巡抚臣阮元会同浙江学政臣文宁咨称,处州府属青田县有畲民钟正芳等呈请与土民一体应试一事。”认为畲民意为农民,本来不是恶称,而且畲民在青田等地“置有粮祠庐墓,素行并非秽贱”,只因“畲妇头戴布冠与本处妇女稍有不同,土著者指为异类,廪生等惑于俗说不敢具保,致畲民不得与试。”作者作此《学政全书》目的在于使畲民不因“其妇女服饰稍异,概阻其向上之心”,因此,“咨请部示期明立章程,以免无识愚民藉词攻讦”。②
《学政全书》颁发后,并未能完全消解学额之争。在光绪《处州府志》曾记载温州畲民求考受阻之事,其文曰:
嘉庆八年,仪征阮文达公抚浙,会同学使文宁,咨准一体考试。其(畲民,笔者注)散居温州者,于道光六年援例求考,诸生禀于学使宝应朱文定公云:“照例身家不清白者,不准与考。”泰顺畲民皆作舆台为人役,身家未为清白,奉批不准与考。丽邑畲民亦有与之相类者,当分别观之一也。③
在清代,闽浙等地区的百姓耻于从事轿夫、仆隶等职业,如福安诸生陈上储在《呈福宁府志事实序》说道:“福宁负山环海,浙尾闽头……以风俗言之,五邑淳漓相半,而皆质直好义。富者不与贫争利,贫者矫语贫贱而傲富贵。即室如悬磬,甘守其穷,耻为舆夫、仆隶。”④在这种观念下,一些汉人将泰顺、丽水等地区畲民从事轿夫等下等行业作为阻止畲民应考的借口。官府以客观的立场出面澄清,认为此事不能以偏概全,即部分畲民从事轿夫职业不能等同于所有畲民的身份。
这种争论在随后数十年中仍在持续进行着。道光廿七年(1847年),官方颁布《温州府谕禁阻考告示》,说明当时畲汉学额之争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畲汉族群矛盾也达到了较深的程度。因此,不得不由官方出面发布告示,希望通过告示抑制畲汉矛盾的继续激化。根据《温州府谕禁阻考告示》记载,当时平阳县有廪生及各童“阻挠攻讦”畲民雷云等人赴考。告示做出公允判断,认为“该县各童阻挠显违定例,自应严行查禁”,虽然“县、府两试均已考过”,但是允许“该童雷云并请准其分别补考”。发布此告示,“示仰平阳县廪保生童人等知悉,嗣后如有畲民赴考,应照定例准其一体考试,毋许再行阻挠致滋事端。”①
这个阶段,畲民的抗争得到官方的重视,官方通过一些文告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畲民的部分利益。此外,畲民的抱团抗争行为激发了族群的凝聚力,确实增强了畲民的族群认同。蒋炳钊先生认为,畲民在迁徙到闽东后,需要加强内部的团结,而传统文化是“反抗外族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强化本民族内部团结,加强民族的凝聚力”的一个重要纽带。②然而,文化资源的争取对畲民认同来讲,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因为一些畲族知识分子在吸收了儒家文化后,开始对本民族的族源传说进行反思,在他们的推动下,畲汉的族群边界再次发生漂移。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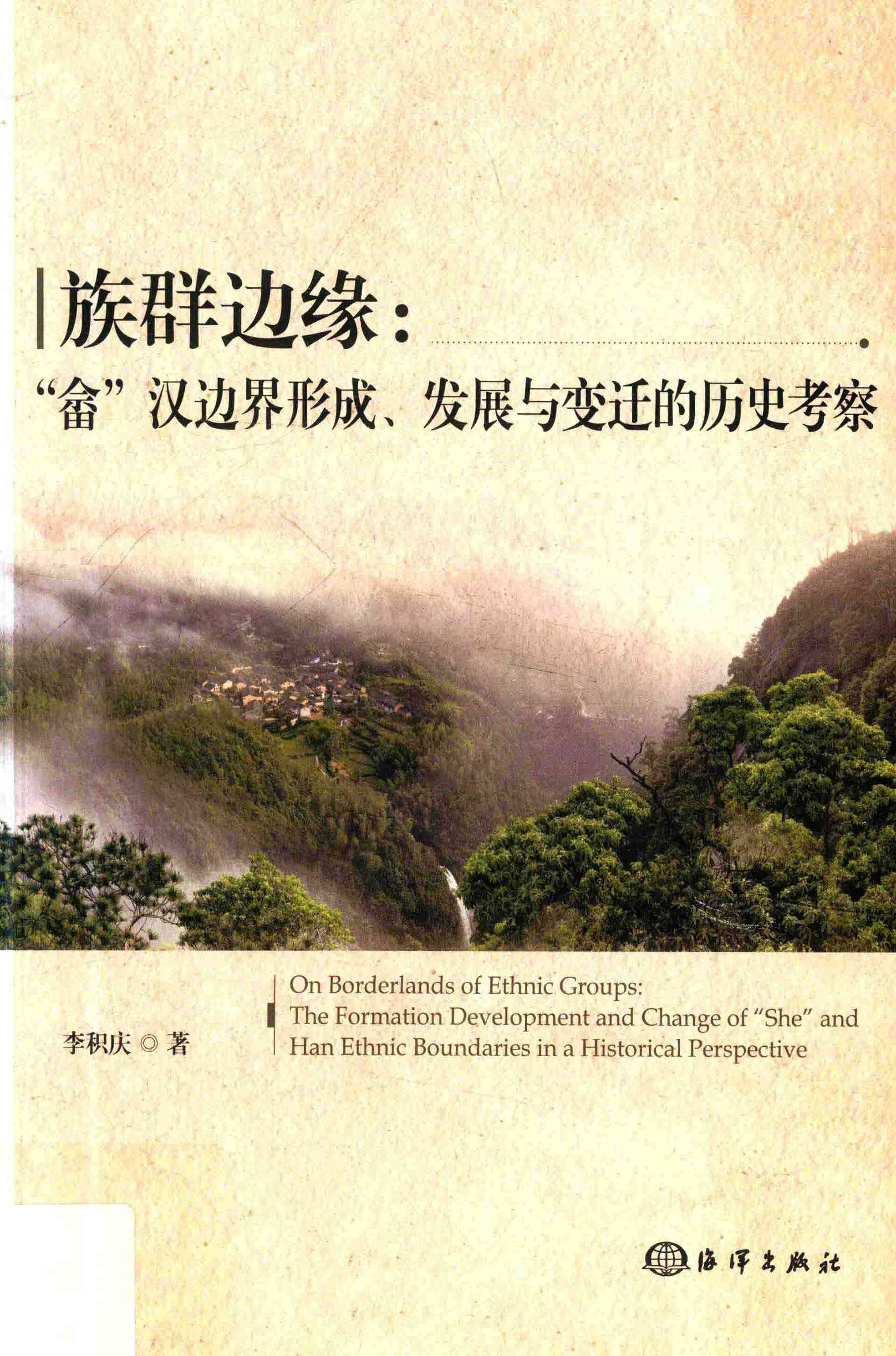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出版者:海洋出版社
本书从族群边界的理论角度,重新审视畲族形成、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在承认族群客观历史文化的同时,重点研究历史上“他者”(主要是汉族)对“畲”的社会定义以及“自者”(主要为南方非汉族群)自我族群认同的过程,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现实意义。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