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认同转变与明清时期“畲”“客”族群身份的分离
| 内容出处: |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图书 |
| 唯一号: | 130920020230003800 |
| 颗粒名称: | 二、文化认同转变与明清时期“畲”“客”族群身份的分离 |
| 分类号: | K288.3 |
| 页数: | 5 |
| 页码: | 146-150 |
| 摘要: | 本文探讨了明清时期畲族和客家人的文化认同转变,以及由此导致的“畲”“客”族群身份的分离。 |
| 关键词: | 畲族 族群边界 明清时期 |
内容
随着客家学的兴起,由于与客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畲族成为客家研究中重要内容之一。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中认为客家曾与畲族发生混化,其结果是越来越多是畲族被汉化,许多畲族的住地成为客家的聚居区①对于过去曾有的“畲客”之说,罗香林写信询问翁国樑:“到底事实上畲民是不是又称‘客家’呢?他们是汉族呢?还是猺族的别支呢?假如是猺族,何以被人称为客家?”②自罗香林先生之后,有些学者在清末以后客家运动兴起背景下,极力辨明或撇清“畲”“客”之间的关系,但随着客家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畲客的关系,因而涌现出一大批的研究成果。
学术界一般认为,客家是南迁汉人与盘瓠蛮、百越互动的过程而形成的新的族群。在较长的历史时间中,畲汉融合,并形成密切的共生③关系,客家与畲族在历史上曾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关系。那么,是什么导致了“畲”“客”之间的分离呢?笔者认为,文化在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谢重光先生所指出的:“客家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④在客家形成的过程中,除了北方汉人南迁的因素起作用外,赣闽粤边原住民的历史与文化等多种因素也在起作用,以上多种文化因子共同促使了客家文化的最终形成。那么“畲”“客”的分离同样也是因为文化的原因,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不同的文化取向导致了“畲”“客”的最终形成两个独立的族群,而历史上出现的“畲”变“客”,或者“客”变“畲”,也均是文化认同在起主要作用。
明代以来,特别是明中叶王阳明巡抚南赣以后,随着国家加强对闽粤赣地区的管理,许多畲民完成了身份的转变。谢重光先生曾高度评价王阳明巡抚南赣对畲民汉化的推动,这种变化体现在族群格局是原为畲族住区的赣闽粤交界地区,“如今几乎清一色是客家人的住区”。①与以畲族外迁来解释此现象观点不同的是,谢先生认为更重要的因素应是畲民大部分转化为客家人了②。陈永海在《一个山区的族群标记:畲“贼”之例》一文中指出,畲民与客家人出现分化的原因主要是文化转向的不同:“有一部分畲瑶人群坚持其盘瓠信仰仍为‘畲’,另一部分人群则接受儒家的礼仪,转为客家人。”③这也再一次印证文化认同在族群边界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此时,闽粤赣的族群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如谢重光所说:“明代以前,福建畲族、客家、福佬三大族群的分布态势是:客家处在西北部的汀江流城,福佬处在西南部的九龙江流域,两者之间的玳瑁山、博平岭东西麓是畲族的天下。”④而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急剧变迁,畲民的边界的移动产生影响,其中畲、客的分离正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其中一个表现。
明清时期,“畲”“客”经常合称均指蓝、雷等畲民,在闽西南地区,与“畲”“客”相区别的,则是福佬,如道光《平和县志》:“和邑深山穷谷中,旧有猺獞,椎髻跣足,以槃、篮、雷为姓……闽省凡深山穷谷之处每多此种,错处汀、潮接壤之间……土人称之曰“客”,彼称土人曰“河老”。⑤再如漳州南靖县南坑高港村《曾氏崇本堂世谱》中,也记载“畲”(客)与汉的区别:
蓝、雷者,即传记所称猺人是也,乃盘瓠之后,楚粤为盛。闽中唐宋以前亦在在有之。然多在深山穷谷中,又迁徙无常,故土人称之曰“客”,而彼称土人为其“河老”,为其自河南光州来,畏之也。凡三团左右有曰“畲客营”者,有曰“客仔寮”者,有曰“番仔寮”者,皆其旧址也。①
顺治年间,潮州地区社会动乱中有称“客贼”的,乾隆《潮州府志》记载:
顺治元年甲申,客贼通福建,闽王老统数千人,突至揭阳县西关,知有备,遁去。三月,山贼邱文德寇兰田,蓝霖寇打石山,官兵御之。贼佯走,弃所劫之物于路,宫兵争取之。贼突出,官兵败绩。②
参照对“客”的定义,蓝霖的姓也颇符合畲族的特征,可以断定客贼部分指的是畲民。清人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也记载道:
徭人楚粤为盛,而闽中山溪高深之处,间有之。漳徭人与虔汀潮接壤错处,亦以槃、雷、蓝为姓……常称城邑人为河老,谓自河南迁来,畏之,繇陈元光将军始也。③
以上说明,福佬(河老)族群作为“畲客”的他者出现。文中称畲民“常称城邑人为河老”,可见“河老”最初应该是他称的。有的学者认为,“河老”或“福佬”是因为北方汉人南迁,以操河洛话,因而被称为河洛人。④笔者认为,这种观点颇有附会的嫌疑。实际上,“老”或“佬”是在南方特定生态、文化环境下的产物,而非“洛”的变音。在南方除了“河老”,还有“斗老”“大佬”等,如傅衣凌在《福建畲姓考》列举宋元史料中关于闽、粤、浙、赣中出现的“大老”⑤,认为大老为畲徭酋长尊称,他说:“凡称大老者,均在闽赣粤诸省,适合肴族之居地,且与蜒族有关,即上引广东黎德为元时著名蜒‘贼’,其同盟军有唐大老等,亦可见两族间之联系。脱欢同漳州路高僳讨平之……盖僮僚民族好称佬,故两粤人民喜欢称人为佬,例如广东佬、广西佬、广佬、白话佬、外江佬之类。又尊称别人为大佬,自己谦称为细佬,称有钱人为财主佬,称有学问人为读书佬。这佬字即獠字的异写。”①
陶希圣曾注意到在元代华南地区起事的徒众之中,有许多首领被称为“大老”②。“大老”的出现,是由于群众间歃血为盟的结拜,进而推举出领袖,即所谓的大哥。
再如,嘉靖《广东通志初稿》记载当时潮州地区的佃户“率依山逞蛮,结党肆志”首领称“斗老”,当地主下乡收租时,“各佃户必告之斗老”结党抗拒佃租。③在广东方言“大”和“斗”谐音,二者或有联系。《石窟一徵》就指出在广州常称“大哥”为“大老”。④“大佬”这种称谓在今天的广东、台湾等地区仍作为常用词使用,意为群体中的首领、头目等。
历史上,畲、客具有密切的共生关系,曹树基也指出汉畲融合形成客家民系,在其后移民过程中与土著抗争导致客家意识的出现。⑤实际上,畲民与客家的分离与华夏化的进程是相同步的。相对福建、广东而言,江西地区的畲瑶等非汉人群更早进入华夏边缘之内,显示出王朝中心向边陲扩张的一个延伸过程。正如王东指出:“就赣南的情况来看,由于其境内的民族成分比较单一,汉族自东汉以来就已成为当地的主体民族,故而,以莫徭为主体的苗瑶族先民在迁入赣南以后,很快融入到汉民族之中,从而成为政府的编户齐民”⑥。
王天鹏根据萨林斯有关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提出用“文化界定历史”来探讨畲族与客家的形成。作者认为,客家与畲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历史的发展,二者因为分别采取了“攀附”与“逃离”截然不同的策略,所以分离成为客家和畲族两个不同的族群。具体来说,畲民族群通过《高皇歌》等载体强化逐渐“逃离”国家统治的历史记忆,并在实践中播迁到中央政府控制相对薄弱的山区,游离于编户齐民之外;而一些畲客通过“攀附”努力保持与中央王权的关系,摆脱边缘地位,而成为客家族群。⑦
直到清代后期,“客”才开始成为客家族群的专用名词,主要因为当时社会经济的急剧变迁,促使闽西、粤东的客家人加强了这种自我意识认同的紧迫性。①这又涉及“畲”(客)与广府、潮汕人族群边界冲突的历史,在族群危机下,客家精英通过不断建构历史记忆,试图证明中原正统文化传承的合理性。
到了民国时代,客家意识进一步觉醒,加速了“客家”与“畲民”在社会定义上的剥离。如当时发生了学者王斤役谈论《云霄厅志》重刊情况提到“客”与“河老”的关系时称:“云霄厅志修于嘉庆廿一年十一月,蠹鱼吞蚀,残肃不完,去年据以重刊,始得复与世学人相见。益‘民元废厅改县议案及呈批各件’为第二十一卷,余仍旧贯。卷三有猺獞一节,猺獞即今之客族:土人称之曰客,彼称土人曰河老。”②
这种将“客”与猺獞相提并论的表述引起了海内外客家对王斤役不满,后《逸经》编辑部妥协,只好再次声明“客”指的是畲民,而非客家,其文称:“但细查王君原文所载,乃引用《云霄县③志》,文中所称‘客族’,乃指当地之畲民,系与土人相对之称,并非泛指其他各地之‘客家人’而言,其义至明,不容误会。”④
从这里也反映了客家与畲的分离,除了族群本身的文化取向、文化认同不一样外,其与本族精英的努力争取族群身份也是分不开的。
可见以上所述的“畲区”变为“客区”,确实不能单纯以人口实质性迁移来解释,而应将其视为在汉文化认同的过程中,汉族的边界逐渐扩大、华夏边缘在东南的进一步扩张的结果。借用王明珂关于“羌在汉藏之间”⑤的概念,我们似乎也可以用“客在畲汉之间”⑥来解释这个历史现象。
学术界一般认为,客家是南迁汉人与盘瓠蛮、百越互动的过程而形成的新的族群。在较长的历史时间中,畲汉融合,并形成密切的共生③关系,客家与畲族在历史上曾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关系。那么,是什么导致了“畲”“客”之间的分离呢?笔者认为,文化在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谢重光先生所指出的:“客家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④在客家形成的过程中,除了北方汉人南迁的因素起作用外,赣闽粤边原住民的历史与文化等多种因素也在起作用,以上多种文化因子共同促使了客家文化的最终形成。那么“畲”“客”的分离同样也是因为文化的原因,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不同的文化取向导致了“畲”“客”的最终形成两个独立的族群,而历史上出现的“畲”变“客”,或者“客”变“畲”,也均是文化认同在起主要作用。
明代以来,特别是明中叶王阳明巡抚南赣以后,随着国家加强对闽粤赣地区的管理,许多畲民完成了身份的转变。谢重光先生曾高度评价王阳明巡抚南赣对畲民汉化的推动,这种变化体现在族群格局是原为畲族住区的赣闽粤交界地区,“如今几乎清一色是客家人的住区”。①与以畲族外迁来解释此现象观点不同的是,谢先生认为更重要的因素应是畲民大部分转化为客家人了②。陈永海在《一个山区的族群标记:畲“贼”之例》一文中指出,畲民与客家人出现分化的原因主要是文化转向的不同:“有一部分畲瑶人群坚持其盘瓠信仰仍为‘畲’,另一部分人群则接受儒家的礼仪,转为客家人。”③这也再一次印证文化认同在族群边界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此时,闽粤赣的族群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如谢重光所说:“明代以前,福建畲族、客家、福佬三大族群的分布态势是:客家处在西北部的汀江流城,福佬处在西南部的九龙江流域,两者之间的玳瑁山、博平岭东西麓是畲族的天下。”④而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急剧变迁,畲民的边界的移动产生影响,其中畲、客的分离正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其中一个表现。
明清时期,“畲”“客”经常合称均指蓝、雷等畲民,在闽西南地区,与“畲”“客”相区别的,则是福佬,如道光《平和县志》:“和邑深山穷谷中,旧有猺獞,椎髻跣足,以槃、篮、雷为姓……闽省凡深山穷谷之处每多此种,错处汀、潮接壤之间……土人称之曰“客”,彼称土人曰“河老”。⑤再如漳州南靖县南坑高港村《曾氏崇本堂世谱》中,也记载“畲”(客)与汉的区别:
蓝、雷者,即传记所称猺人是也,乃盘瓠之后,楚粤为盛。闽中唐宋以前亦在在有之。然多在深山穷谷中,又迁徙无常,故土人称之曰“客”,而彼称土人为其“河老”,为其自河南光州来,畏之也。凡三团左右有曰“畲客营”者,有曰“客仔寮”者,有曰“番仔寮”者,皆其旧址也。①
顺治年间,潮州地区社会动乱中有称“客贼”的,乾隆《潮州府志》记载:
顺治元年甲申,客贼通福建,闽王老统数千人,突至揭阳县西关,知有备,遁去。三月,山贼邱文德寇兰田,蓝霖寇打石山,官兵御之。贼佯走,弃所劫之物于路,宫兵争取之。贼突出,官兵败绩。②
参照对“客”的定义,蓝霖的姓也颇符合畲族的特征,可以断定客贼部分指的是畲民。清人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也记载道:
徭人楚粤为盛,而闽中山溪高深之处,间有之。漳徭人与虔汀潮接壤错处,亦以槃、雷、蓝为姓……常称城邑人为河老,谓自河南迁来,畏之,繇陈元光将军始也。③
以上说明,福佬(河老)族群作为“畲客”的他者出现。文中称畲民“常称城邑人为河老”,可见“河老”最初应该是他称的。有的学者认为,“河老”或“福佬”是因为北方汉人南迁,以操河洛话,因而被称为河洛人。④笔者认为,这种观点颇有附会的嫌疑。实际上,“老”或“佬”是在南方特定生态、文化环境下的产物,而非“洛”的变音。在南方除了“河老”,还有“斗老”“大佬”等,如傅衣凌在《福建畲姓考》列举宋元史料中关于闽、粤、浙、赣中出现的“大老”⑤,认为大老为畲徭酋长尊称,他说:“凡称大老者,均在闽赣粤诸省,适合肴族之居地,且与蜒族有关,即上引广东黎德为元时著名蜒‘贼’,其同盟军有唐大老等,亦可见两族间之联系。脱欢同漳州路高僳讨平之……盖僮僚民族好称佬,故两粤人民喜欢称人为佬,例如广东佬、广西佬、广佬、白话佬、外江佬之类。又尊称别人为大佬,自己谦称为细佬,称有钱人为财主佬,称有学问人为读书佬。这佬字即獠字的异写。”①
陶希圣曾注意到在元代华南地区起事的徒众之中,有许多首领被称为“大老”②。“大老”的出现,是由于群众间歃血为盟的结拜,进而推举出领袖,即所谓的大哥。
再如,嘉靖《广东通志初稿》记载当时潮州地区的佃户“率依山逞蛮,结党肆志”首领称“斗老”,当地主下乡收租时,“各佃户必告之斗老”结党抗拒佃租。③在广东方言“大”和“斗”谐音,二者或有联系。《石窟一徵》就指出在广州常称“大哥”为“大老”。④“大佬”这种称谓在今天的广东、台湾等地区仍作为常用词使用,意为群体中的首领、头目等。
历史上,畲、客具有密切的共生关系,曹树基也指出汉畲融合形成客家民系,在其后移民过程中与土著抗争导致客家意识的出现。⑤实际上,畲民与客家的分离与华夏化的进程是相同步的。相对福建、广东而言,江西地区的畲瑶等非汉人群更早进入华夏边缘之内,显示出王朝中心向边陲扩张的一个延伸过程。正如王东指出:“就赣南的情况来看,由于其境内的民族成分比较单一,汉族自东汉以来就已成为当地的主体民族,故而,以莫徭为主体的苗瑶族先民在迁入赣南以后,很快融入到汉民族之中,从而成为政府的编户齐民”⑥。
王天鹏根据萨林斯有关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提出用“文化界定历史”来探讨畲族与客家的形成。作者认为,客家与畲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历史的发展,二者因为分别采取了“攀附”与“逃离”截然不同的策略,所以分离成为客家和畲族两个不同的族群。具体来说,畲民族群通过《高皇歌》等载体强化逐渐“逃离”国家统治的历史记忆,并在实践中播迁到中央政府控制相对薄弱的山区,游离于编户齐民之外;而一些畲客通过“攀附”努力保持与中央王权的关系,摆脱边缘地位,而成为客家族群。⑦
直到清代后期,“客”才开始成为客家族群的专用名词,主要因为当时社会经济的急剧变迁,促使闽西、粤东的客家人加强了这种自我意识认同的紧迫性。①这又涉及“畲”(客)与广府、潮汕人族群边界冲突的历史,在族群危机下,客家精英通过不断建构历史记忆,试图证明中原正统文化传承的合理性。
到了民国时代,客家意识进一步觉醒,加速了“客家”与“畲民”在社会定义上的剥离。如当时发生了学者王斤役谈论《云霄厅志》重刊情况提到“客”与“河老”的关系时称:“云霄厅志修于嘉庆廿一年十一月,蠹鱼吞蚀,残肃不完,去年据以重刊,始得复与世学人相见。益‘民元废厅改县议案及呈批各件’为第二十一卷,余仍旧贯。卷三有猺獞一节,猺獞即今之客族:土人称之曰客,彼称土人曰河老。”②
这种将“客”与猺獞相提并论的表述引起了海内外客家对王斤役不满,后《逸经》编辑部妥协,只好再次声明“客”指的是畲民,而非客家,其文称:“但细查王君原文所载,乃引用《云霄县③志》,文中所称‘客族’,乃指当地之畲民,系与土人相对之称,并非泛指其他各地之‘客家人’而言,其义至明,不容误会。”④
从这里也反映了客家与畲的分离,除了族群本身的文化取向、文化认同不一样外,其与本族精英的努力争取族群身份也是分不开的。
可见以上所述的“畲区”变为“客区”,确实不能单纯以人口实质性迁移来解释,而应将其视为在汉文化认同的过程中,汉族的边界逐渐扩大、华夏边缘在东南的进一步扩张的结果。借用王明珂关于“羌在汉藏之间”⑤的概念,我们似乎也可以用“客在畲汉之间”⑥来解释这个历史现象。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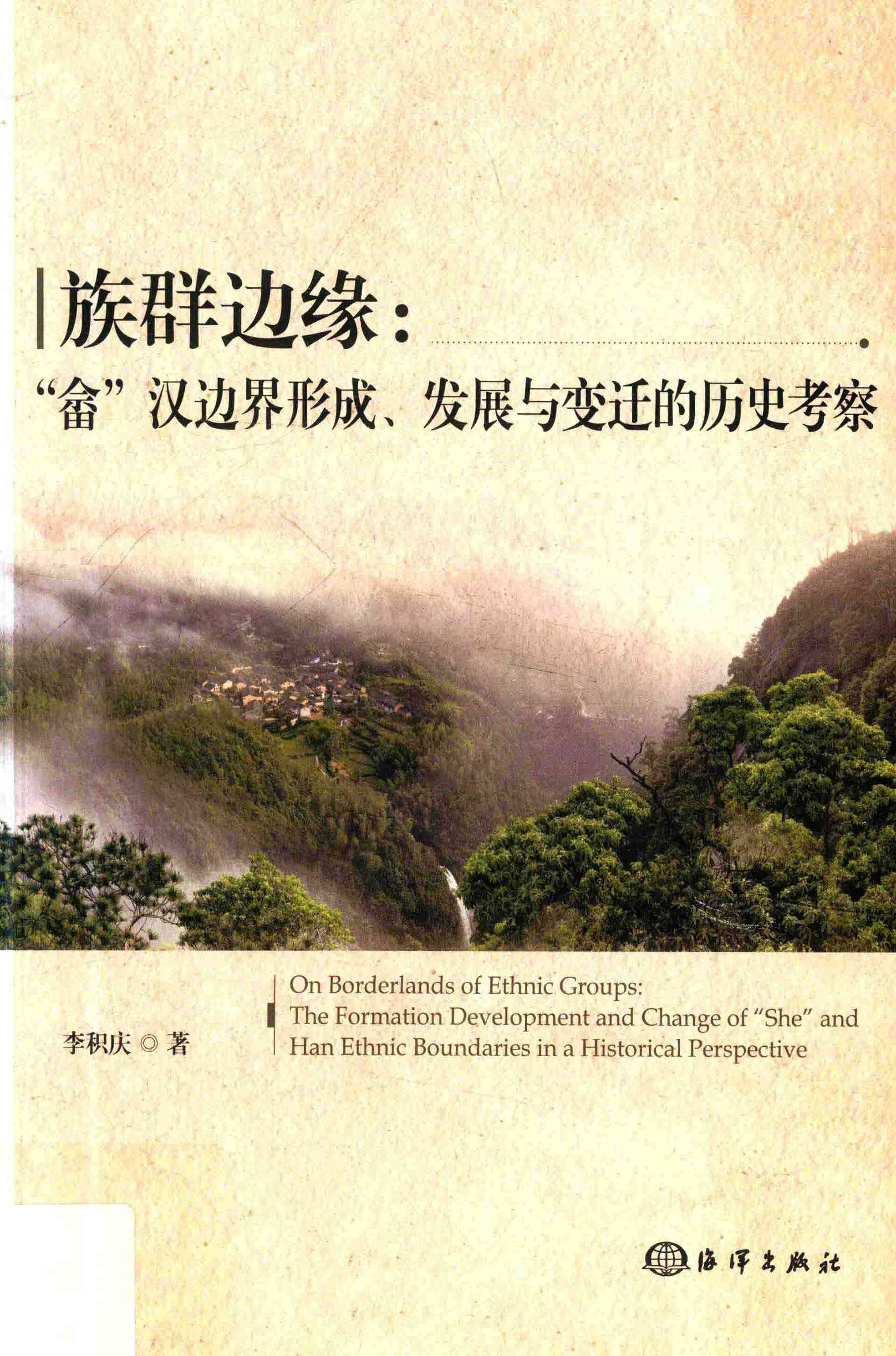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出版者:海洋出版社
本书从族群边界的理论角度,重新审视畲族形成、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在承认族群客观历史文化的同时,重点研究历史上“他者”(主要是汉族)对“畲”的社会定义以及“自者”(主要为南方非汉族群)自我族群认同的过程,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现实意义。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