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畲瑶“盗”“寇”“贼”族群印象的由来
| 内容出处: |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图书 |
| 唯一号: | 130920020230003790 |
| 颗粒名称: | 一、畲瑶“盗”“寇”“贼”族群印象的由来 |
| 分类号: | K288.3 |
| 页数: | 10 |
| 页码: | 113-122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宋明时期闽粤赣地区的“寇乱”现象以及地方社会的文化整合情况。 |
| 关键词: | 畲族 宋明时期 |
内容
宋明时期闽粤赣地区“寇乱”频发,地方社会危机重重,该地区的社会动乱有其自然、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这是一个多种因素叠加、社会矛盾积累到某个临界点时,而后矛盾相继爆发的特殊社会现象。正如《汉书·贾谊传》所称:“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④从文化学的角度,宋元以来的“畲”乱,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再创造的结果,“寇乱”显示了当地族群社会文化整合的情况。
随着以汉人为代表中央王朝日益深入南方地区,南方的非汉族群被定性为“蛮夷”话语之中①,文献中出现的有关“峒”“蛮”“獠”“猺”“獞”等均是这种“华夷之辨”族群话语下的产物。特别是在汉与非汉之间的族群边界冲突发生时,更进一步加深了华夏族对“蛮夷”的“贼”“寇”身份的印象。那么,这些“贼”“盗”“寇”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话语权掌握在统治者手中,因此“贼”“寇”其实就是官方单方面的文化表述的产物,官方的利益成为评判标准的核心。在官方的话语系统中,“贼”“寇”与“民”相对,是合法社会秩序以及帝国权威的挑衅者。“贼”“寇”本有区别,清代梁章钜在《称谓录》中称:“奸宄。《书传》:‘劫人曰寇,杀人曰贼,在外曰奸,在内曰宄。’……盗,《左氏》定公八年经注:盗,谓阳货也。疏:盗者,贱人之称也。”②
随着历史的发展与演变,“贼”“寇”“盗”作为对动乱者的贱称实际上是相通的,可视为一种泛称,专门用以指代社会秩序的叛乱者。统治者用“贼”“盗”“寇”的文化标签来定义社会中某一特定族群,并以此区别族群间“良”与“荞”的边界。王朝以文化阶序来区分“贼”“民”之间的族群边界,其目的在于:宣扬文化等级差异,防止更多民众加入“贼”之中,同时增强普通百姓内部的文化认同感。从历史上看,在多数动乱中,不仅由官方派兵平盗,在民间中,也有许多士绅阶层自发组织乡村民间武装对“贼”“寇”进行剿杀可见,族群边界的区分,有助于维护王朝的统治秩序。如《宋史》载:“(至元十四年)五月……(张)世杰乃奉益王入海,而自将陈吊眼、许夫人诸畲兵攻蒲寿庚,不下。”③
而清代杨澜的《临汀汇考》亦载其事:“宋绍熙中,上杭峒寇结他峒为乱,州判赵师璱擒其渠魁。而宋季张世杰会师讨蒲寿庚,有许夫人统诸峒畲军来会,汀畲亦在军中。”④
这里的表述比较微妙:“峒”民为乱称之为“峒寇”,参与张世杰军队者则称之为“畲军”或“畲兵”。可见,“军”“兵”与“寇”之间的区别,显然是根据是否符合官方利益的标准而作评判的。
刘志伟曾指出“蛮夷”之所以常被冠以“贼”“盗”“寇”蔑称,与其“不受教化”“不税不役”“化外之民”的特征有关系,而所谓“蛮夷”,不仅是一个血统的范畴,更是一个文化和社会的范畴。①对于王朝而言,纳税服役的政治意义远比经济意义大,是否承担赋役、履行国家义务,成为国家区分“民”与“盗”的重要指标。②在一些国家政治管理鞭长莫及的偏远边陲地区,其居民(主要为非汉人群)无法做到或不愿意去履行国家义务,国家因此将这些居民与“盗联系起来”。这种思想体现在文献上,就是常将地理上的边陲与族群“化外”的性格联系起来,即认为一个地区的民风或族群性格往往与地理环境有关,地理越蛮荒险远的地方,居民可能越难教化,也更易发生动乱。
福建山区往往为盗贼渊薮,宋代的周必大称:“七闽地狭,人众甚艰苦,其民亦重犯法,然东际海南接炎峤,西入赣境,风潮出没之奸,山谷集之盗,控御失所,或害吾治。”③到至元年间便有人认为:“闽地山谷之间往往乌合为寇”。④《元一统志》也称:“汀之为郡,山重复而险阻,水迅急浅色涩。民生其间,气刚愎而好斗,心偏迫而浅,亦风土使然。⑤
直到明代闽粤赣仍被认为是畲民聚集的地方,何乔远《闽书》称:“江西之南赣,福建之汀漳,及广东之南、韶、潮、惠,湖广之郴桂,境壤相接,峻谷深山,岭岫缀连,輋贼窟穴其中。”⑥明代时期,上杭溪南地区作为“盗窟”尤为著名,明代兵部尚书杨博称:“闽广之贼所倚重者数巢穴耳,其大者在福建则有上杭峰头、永春蓬壶……”⑦明人郭造卿在《闽中分处郡县议》亦云:
“然近日三省山寇数十年一作,及剿有数十年之安,惟三图百余年,无秋冬间不啸聚,屡扑而不驯服,其山林险密,尤异他区,邻省山寇共推之为主耳。”①
清代杨澜在《临汀汇考》称:“南赣地连闽广,山谷深阻,盗贼易为巢穴。”②《肇域志》记载漳浦县大帽山:“在县北百里,山大而峻……南距檺林延袤数百里,深林丛莽,群不逞多啸聚,其间迤东通溪埔山,菁畲猺獞时出为寇,乡导而直北。”③可见在闽南地区的漳浦大帽山、云霄檺林这些地方“深林丛莽”,成为“盗贼”啸聚的地方,在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人是“菁畲猺獞”,也就是畲民。
除了福建外,广东、江西等地也是畲、猺、峒獠出没之地,如史称“在广东则有猺峒,在江西有輋巢”④,这些族群一般被认为是危险的、狡猾的人群,如元末黄潜记载郴州百姓害怕与当地非汉族群交往,“洞蛮猺獠往来民间,人惮其强猾,莫敢与相贸易”。、⑤这里“民间”应该指的汉人社会,“人”也指汉人,当然这种记载是单方面的反映的是汉人对这些猺獠的看法,我们或许可以推测,猺獠在面对强势的汉人,比上述的汉人更为“忌惮”。
这些非汉族群在汉人眼中之所以是危险群体,与他们时常外出劫掠有关,因此也被称为“盗贼”。明人梁朝宗描述江西龙泉等地有“猺、輋、獠”,这些居民僻居山区,不纳赋税,而且在灾荒之年劫掠百姓,如“龙泉,吉左僻邑也,控郴衡而引虔,猺、輋、獠、恶少出没之地,岁登则自食其力,歉则群聚不逞之徒,大肆劫掠刈人如草菅。”⑥
輋民冠以“贼”字,可见当时畲民的族群印象被打上“盗寇”的烙印,正是有了这种族群印象,所以在文献中谈及闽粤赣边等地区的非汉族群时,常以好斗喜乱来形容其性格,如“畲丁①溪子善惊好斗。”②又如“畬丁洞猺喜惊而嗜斗”③。
实际上,“民”和“贼”的身份并不一定是固定不变的,二者是可以转化的。王慎中在分析上杭县的溪南盗风日炽时,对“民”化为“盗”作过精彩的论述:
风气所限,非性故然,长子育孙,生蕃齿盛,耳目熟习,莫改厥德,少视其壮,壮视其老,蹲危逗幽,乃为盗薮。厥有治者,不揆其性,不闵其习,盗视彼民,忿犷堲凶,攻击铲除,如农疾莠,惟惧不残、民不见德,又弗儆威,既狃于习,且偷其生,鸱张螳怒,攘奋踉跄。吏既雠民,民亦毒吏,雠毒两积,交不得已,于是溪南之民,恶声胶固。④
可见,最初“民”“盗”水火不容,但最后仍皆为盗贼所吸纳。足见一个地方文化对族群塑造的力量。
就官方立场而言,“盗贼”界定主要在于人民的行踪官方是否难以掌握,衡量的标准是以平民的活动是否违法脱序作判别。在古代农业社会价值观念下,只要在土地上安分守己,就不是“盗贼”,否则皆将与“盗贼”无异。“倘若硬性将传统农业社会价值观念,桎梏在逐渐转向于商品经济流通的社会,自然官方会对流民、移民的增多而感到处处皆‘盗’,在此情况下,社会经济的变化造成南赣地区的盗增并不使人意外。当然对于现有秩序与体制而言,官方根本不容许‘盗贼’聚众生事,并强力禁制他们‘倡乱’。”⑤
另一方面,华夏化过程中,王朝势力深入非汉地区,引起了当地族群与其他族群,乃至与政府的矛盾。这本来是政府深入非汉族群的居住地,但如前文所述,在华夏视野的“天下观”中,官方先验地认为土地人口均为国家所有,因而,不服从国家安排的就是“寇”或“贼”。直至明清时期,在全国开展丈量土地运动,在闽粤赣地区就遇到畲民的抵抗,如平和县早在明嘉靖中,知县谢明德就已经开始提议实施土地丈量:
仿古经界之法,就现在田土丈量均产,每田一亩随九等高下会计产钱。而总合一郡诸租税、钱、米之数,以产钱为母,别定等则;一例均敷,分隶若干为省计,若干为职田、学粮之属,令诸乡具籍,条别辖内田额四至。①
这说明是一种边界的推移。应该是加强控制,华夏边缘逐渐延伸,导致了非汉民族的反弹。这种丈量田亩等,名义上是为国家丈量田亩,实际上在此之前均为非汉民族居住,应该会造成关系的紧张,如清道光《平和县志》记载:
(康熙)三十七年七月,贼首钟平鼻,吕扁②党也。因县有丈量田亩之议,人情汹汹,知县奔避郡城。平鼻结盗营大丰社,去县三十里,约期劫县,而自为内应,与弟钟二乘间登城伺探,为营兵所觉。县乡壮乘夜薄贼营,贼知平鼻既遁,皆溃,死者甚众。③
第二,由于中国中国古代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本,常将一些从事非农业的人民称为“轻民”,与“重民”相对。清代梁章钜在《称谓录》中称:“重民,《管子》:‘轻民处而重民散’。注:轻民,谓为盗者,重民,谓务农者。”④轻和重相对,区别在于,重民务农纳税,轻民,逋逃为盗。所以从事商业以及经济作物者均认为是社会不稳定因素。
闽粤赣地区自宋代以后,出现的许多“寇”“贼”,清代杨澜曾考证称:
汀郡……乃稽之往代,则有江寇、虔寇、广寇、漳寇、海寇、洞寇、畲寇、盐寇,种种名色,其故何哉?自王绪引兵入闽,汀郡首婴其锋,地为丹徼喉衿。入宋,则盐徒剽掠,往来汀、虔、漳、梅、循、惠、广之地,官不能禁。①
如果将杨澜列举的“寇”分类,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按照族群身份从事职业区分,如海寇、畲寇、峒寇、盐寇,或者是处在山峒、海边的寇,或者是从事盐业、畲田的寇;二是按照“盗寇”来源地区分,如江寇、虔寇、广寇、漳寇。根据杨澜考证,古代汀州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类型的“寇”,一方面是地理缘故,唐末王绪引兵入闽,汀州因其地理位置首先遭遇战乱而引起“寇乱”;另一方面是经济缘故,如盐徒四处剽掠,官府也无法控制。
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唐五代以后,以王绪为代表的中原汉族势力进入福建地区,引起了当地族群结构的变化,族群边界被打破时,族群冲突而造成的社会动乱屡有发生;另外,唐宋经济重心南移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在地方与中央,地区与地区之间以及不同族群之间的资源分配发生结构性的矛盾,由此产生冲突。②特别是入宋以后,朝廷关于食盐制度的不合理③,一些盐徒趁机剽掠,食盐走私盛行引起地方的连锁动乱反应。如王安石《虔州学记》记载:“虔州江南,地最旷,大山长谷,荒翳险阻,赣、闽、越,铜盐之贩,道所出入,椎埋盗守鼓铸之奸,视天下为多。”④《天下郡国利病书》也称:“汀虽非产盐之区,而实为通盐之路,亦江广之咽喉,为闽西外府也。宋时通之,寇且踵作,而必禁之”⑤南宋绍定年间汀州改食潮盐后,《临汀汇考》载:“惟虔州患苦盐法如故。而汀境食米不敷,半仰给于邻境之肩贩,常有遏粜之恐。于是乃许虔民担米来汀,贸盐而返,以有易无,二州民胥赖之。”⑥
可见各地的经济结构具有不平衡的特性。以汀州为例,该地常常有粮食不足的现象发生,粮食不足自然米价上涨,由此又引起寇乱的产生。有史料证明灾荒引发的米价上涨曾导致了闽西洞民寇乱。清代邱嘉穗在《与翁明府、蒋参戎论洞寇书》曾记载了明代上杭来苏三乡的洞寇因为米价上涨而为盗寇的情况:
窃惟来苏三乡,孤悬天末,不幸复界闽、粤间,西接武平,南邻程乡,无深沟高垒以为之限,有幽岩丛菁以为之巢。其二洞,群不逞之徒倚为窟穴,游奕往来,眈眈视来苏如奇货者,盖匪朝伊夕矣。会日秋收颇歉,谷价上腾,加以赣米弗来,潮米莫上,贫民半菽不饱,并日而炊。于是,二洞之亡命为雄者,至敢阴行招纳之私,大肆攻掠之惨,一呼百应,四方驿骚……诚见年荒米贵,平时汀、潮两地所仰给于西江诸郡县者,近则皆禁绝不甚通,非邻封有遏籴之谋,即当事之过虑,不许贩出境外,而皆必给票盘验,以使之嗷嗷望哺,卒不可得;枵腹难堪,呼吁无门,既不敢擅发河东之粟,复谁能代绘监门之图?彼以为死于饥也,与死于盗也,等一死也;与其捐瘠沟中而长为白骨之鬼也,何如游魂釜底而暂作绿林之豪也。是以奋袂攘臂,不得已而出于此。①
日本学者竹村卓二在研究华南山地民族时也指出:“山地民的粮食自给率十分低下,常常碰到饥荒,从而成为引起暴动的原因,这并非偶然。尤其为维持生命不可缺少的食盐供给,是最为紧要的问题。”②
明清以后,在闽粤赣地区出现大量类似“炭党”“矿徒”“菁客”“麻民”“蓝户”“烟民”“菰农”“畲客”“山贼”“棚民”等称谓的流动人口。“寇、客、党、徒、盗、贼”等通称与“民、户”相对,是在中国古代重本抑末经济体系下,对非粮食生产人口的各种称谓。之所以用“贼”“寇”称之,主要是因为这些流动人口往往与土著族群发生冲突,并对正常农业社会秩序带来巨大的破坏。傅衣凌先生曾论述道:“(明清时期)山区带有商品经济关系性质的农民斗争……是和商品生产有较大联系的山区棚民的斗争。他们以蓝户、菁户、麻民、炭党为主体,此外,还有‘矿盗’‘海盗’的参加……他们多是离开土地的外地人……流动性大,人数多”。③傅先生认为,明清时期的社会动乱与这些从事非农业(从事商品经济关系性质产业)人口有极大关系。
这些流动人口,往往是无籍的人口。无籍之民,按刘志伟研究,在明代广东地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脱离里甲体制的“逋负之徒”(或“逃户”),另一类是未归附于里甲体制的“化外之民”(或“蛮夷”)。①饶伟新曾指出,“无籍之民的社会政治处境和‘化外蛮夷’的族群背景”造成了明代赣南的社会动乱。②也就是说,无籍之民与“蛮夷”共同造成了明代闽粤赣地区的社会动乱。如《虔台志》载惠州府三类无籍之民:
以和平(县)为赣、桂、汀、漳之界,乃大帽山、岑冈地也,挂坑障、香炉峰、看牛坪皆比近,故延蔓相及耳。然惠皆良民耶?徭僮淆焉,鱼蛋伏焉,逋亡集焉,盗所由出也。③
说明在广东惠州在数省交界之地不仅“良民”居住,还生活着许多非汉族群,概括起来有三类人:“徭僮”“鱼蛋”“逋亡”。这三类分别指在山为畲、在水为疍,加上逃避赋税的所谓“奸人”,这些人是汉人,但一般将其视为化外之民。这也说明了随着历史的推移,王朝关于南方化外的非汉族群的泛称,从原来的一类(蛮),变为两类(莫徭—卢艇、蛮—疍、居峒砦—家桴筏),变为三类(“徭僮”—“鱼蛋”—“逋亡”)。从这种泛称分类也进一步说明,对华南社会,特别是内部结构,有了更深的理解。“逋亡”群体的存在,是华夷边界摇摆、流动的重要变量。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广东多地有“山寨瑶贼、蛮贼及倭贼”。同时,“东莞、香山等县逋逃蜑户,附居海岛,遇官军即称捕鱼,遇番贼则同为寇,不时出没,劫掠人民。”④这些“逋逃蜑户”在蜑与倭中身份变换,成为地方不稳定因素之一。
无籍之民与“蛮夷”二者有时候是统一的,即动乱中的叛乱者,既是“蛮夷”,又是无籍之民。福建等地的矿冶,聚集了一些非汉人群,有很大一部分是畲民。如永安御史胡琼《忠洛无银矿记》记载峒民从事银矿开采,而后酿祸的经过:
正德癸酉,民有趋利者,诱浙之峒民,拥众突来,未敢恣发。适郡节推郭姓者摄县事,峒民度其老而贪,得厚啗以利。郭欣然许其开凿,且为之陈于总镇。邑人以其地密迩大帽山,为江、浙、闽、广丛盗之会,虑其闻风袭夺,因以为乱,群情惊惧罔措。时佥宪、睢阳蔡公天佑行部至郡,闻之,乃兼程诣县,数郭之罪,率庶民塞而禁之。峒民方以采无所得,及闻蔡来,众遂宵遁。至是,人心始安,皆德于蔡。然闻总镇,祸已基于此矣①
永安出现从浙江而来的峒民,这些峒民或许是畲族。再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广东畲民成为“矿徒”时称:“畲蛮,岭海随在皆有之……近海则通番,入峒则通猺,凡田(土单)矿场有利者,皆纠合为慝,以欺官府,其害僭于甲兵。”又载广东“惠之归善、海丰,广之从化、香山皆有银矿。畲蛮招集恶少,投托里胥,假为文移,开矿取银,因行劫掠。”②
顾炎武的《肇域志》记载:“金溪山,一作金鸡山,在县西北四十里,连接六洞诸山,旧有银坑,湮塞已久,万历中奉旨开采,商估杂还,豪狷假虎,二都山民岌岌惊变。”③六洞也称“六峒”④,二都“山民”主要是畲民。说明由于矿冶开采,一些富商巨族借以占领盘剥,导致明代周边畲民几乎动乱。从这个记载来看,所谓的动乱,经常是由于资源竞争中,畲民的一种自我反应,常常是被迫叛乱的,然而在叛乱之后,统治者常常冠之以贼、寇等称号,形成了一种族群的印象。
随着以汉人为代表中央王朝日益深入南方地区,南方的非汉族群被定性为“蛮夷”话语之中①,文献中出现的有关“峒”“蛮”“獠”“猺”“獞”等均是这种“华夷之辨”族群话语下的产物。特别是在汉与非汉之间的族群边界冲突发生时,更进一步加深了华夏族对“蛮夷”的“贼”“寇”身份的印象。那么,这些“贼”“盗”“寇”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话语权掌握在统治者手中,因此“贼”“寇”其实就是官方单方面的文化表述的产物,官方的利益成为评判标准的核心。在官方的话语系统中,“贼”“寇”与“民”相对,是合法社会秩序以及帝国权威的挑衅者。“贼”“寇”本有区别,清代梁章钜在《称谓录》中称:“奸宄。《书传》:‘劫人曰寇,杀人曰贼,在外曰奸,在内曰宄。’……盗,《左氏》定公八年经注:盗,谓阳货也。疏:盗者,贱人之称也。”②
随着历史的发展与演变,“贼”“寇”“盗”作为对动乱者的贱称实际上是相通的,可视为一种泛称,专门用以指代社会秩序的叛乱者。统治者用“贼”“盗”“寇”的文化标签来定义社会中某一特定族群,并以此区别族群间“良”与“荞”的边界。王朝以文化阶序来区分“贼”“民”之间的族群边界,其目的在于:宣扬文化等级差异,防止更多民众加入“贼”之中,同时增强普通百姓内部的文化认同感。从历史上看,在多数动乱中,不仅由官方派兵平盗,在民间中,也有许多士绅阶层自发组织乡村民间武装对“贼”“寇”进行剿杀可见,族群边界的区分,有助于维护王朝的统治秩序。如《宋史》载:“(至元十四年)五月……(张)世杰乃奉益王入海,而自将陈吊眼、许夫人诸畲兵攻蒲寿庚,不下。”③
而清代杨澜的《临汀汇考》亦载其事:“宋绍熙中,上杭峒寇结他峒为乱,州判赵师璱擒其渠魁。而宋季张世杰会师讨蒲寿庚,有许夫人统诸峒畲军来会,汀畲亦在军中。”④
这里的表述比较微妙:“峒”民为乱称之为“峒寇”,参与张世杰军队者则称之为“畲军”或“畲兵”。可见,“军”“兵”与“寇”之间的区别,显然是根据是否符合官方利益的标准而作评判的。
刘志伟曾指出“蛮夷”之所以常被冠以“贼”“盗”“寇”蔑称,与其“不受教化”“不税不役”“化外之民”的特征有关系,而所谓“蛮夷”,不仅是一个血统的范畴,更是一个文化和社会的范畴。①对于王朝而言,纳税服役的政治意义远比经济意义大,是否承担赋役、履行国家义务,成为国家区分“民”与“盗”的重要指标。②在一些国家政治管理鞭长莫及的偏远边陲地区,其居民(主要为非汉人群)无法做到或不愿意去履行国家义务,国家因此将这些居民与“盗联系起来”。这种思想体现在文献上,就是常将地理上的边陲与族群“化外”的性格联系起来,即认为一个地区的民风或族群性格往往与地理环境有关,地理越蛮荒险远的地方,居民可能越难教化,也更易发生动乱。
福建山区往往为盗贼渊薮,宋代的周必大称:“七闽地狭,人众甚艰苦,其民亦重犯法,然东际海南接炎峤,西入赣境,风潮出没之奸,山谷集之盗,控御失所,或害吾治。”③到至元年间便有人认为:“闽地山谷之间往往乌合为寇”。④《元一统志》也称:“汀之为郡,山重复而险阻,水迅急浅色涩。民生其间,气刚愎而好斗,心偏迫而浅,亦风土使然。⑤
直到明代闽粤赣仍被认为是畲民聚集的地方,何乔远《闽书》称:“江西之南赣,福建之汀漳,及广东之南、韶、潮、惠,湖广之郴桂,境壤相接,峻谷深山,岭岫缀连,輋贼窟穴其中。”⑥明代时期,上杭溪南地区作为“盗窟”尤为著名,明代兵部尚书杨博称:“闽广之贼所倚重者数巢穴耳,其大者在福建则有上杭峰头、永春蓬壶……”⑦明人郭造卿在《闽中分处郡县议》亦云:
“然近日三省山寇数十年一作,及剿有数十年之安,惟三图百余年,无秋冬间不啸聚,屡扑而不驯服,其山林险密,尤异他区,邻省山寇共推之为主耳。”①
清代杨澜在《临汀汇考》称:“南赣地连闽广,山谷深阻,盗贼易为巢穴。”②《肇域志》记载漳浦县大帽山:“在县北百里,山大而峻……南距檺林延袤数百里,深林丛莽,群不逞多啸聚,其间迤东通溪埔山,菁畲猺獞时出为寇,乡导而直北。”③可见在闽南地区的漳浦大帽山、云霄檺林这些地方“深林丛莽”,成为“盗贼”啸聚的地方,在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人是“菁畲猺獞”,也就是畲民。
除了福建外,广东、江西等地也是畲、猺、峒獠出没之地,如史称“在广东则有猺峒,在江西有輋巢”④,这些族群一般被认为是危险的、狡猾的人群,如元末黄潜记载郴州百姓害怕与当地非汉族群交往,“洞蛮猺獠往来民间,人惮其强猾,莫敢与相贸易”。、⑤这里“民间”应该指的汉人社会,“人”也指汉人,当然这种记载是单方面的反映的是汉人对这些猺獠的看法,我们或许可以推测,猺獠在面对强势的汉人,比上述的汉人更为“忌惮”。
这些非汉族群在汉人眼中之所以是危险群体,与他们时常外出劫掠有关,因此也被称为“盗贼”。明人梁朝宗描述江西龙泉等地有“猺、輋、獠”,这些居民僻居山区,不纳赋税,而且在灾荒之年劫掠百姓,如“龙泉,吉左僻邑也,控郴衡而引虔,猺、輋、獠、恶少出没之地,岁登则自食其力,歉则群聚不逞之徒,大肆劫掠刈人如草菅。”⑥
輋民冠以“贼”字,可见当时畲民的族群印象被打上“盗寇”的烙印,正是有了这种族群印象,所以在文献中谈及闽粤赣边等地区的非汉族群时,常以好斗喜乱来形容其性格,如“畲丁①溪子善惊好斗。”②又如“畬丁洞猺喜惊而嗜斗”③。
实际上,“民”和“贼”的身份并不一定是固定不变的,二者是可以转化的。王慎中在分析上杭县的溪南盗风日炽时,对“民”化为“盗”作过精彩的论述:
风气所限,非性故然,长子育孙,生蕃齿盛,耳目熟习,莫改厥德,少视其壮,壮视其老,蹲危逗幽,乃为盗薮。厥有治者,不揆其性,不闵其习,盗视彼民,忿犷堲凶,攻击铲除,如农疾莠,惟惧不残、民不见德,又弗儆威,既狃于习,且偷其生,鸱张螳怒,攘奋踉跄。吏既雠民,民亦毒吏,雠毒两积,交不得已,于是溪南之民,恶声胶固。④
可见,最初“民”“盗”水火不容,但最后仍皆为盗贼所吸纳。足见一个地方文化对族群塑造的力量。
就官方立场而言,“盗贼”界定主要在于人民的行踪官方是否难以掌握,衡量的标准是以平民的活动是否违法脱序作判别。在古代农业社会价值观念下,只要在土地上安分守己,就不是“盗贼”,否则皆将与“盗贼”无异。“倘若硬性将传统农业社会价值观念,桎梏在逐渐转向于商品经济流通的社会,自然官方会对流民、移民的增多而感到处处皆‘盗’,在此情况下,社会经济的变化造成南赣地区的盗增并不使人意外。当然对于现有秩序与体制而言,官方根本不容许‘盗贼’聚众生事,并强力禁制他们‘倡乱’。”⑤
另一方面,华夏化过程中,王朝势力深入非汉地区,引起了当地族群与其他族群,乃至与政府的矛盾。这本来是政府深入非汉族群的居住地,但如前文所述,在华夏视野的“天下观”中,官方先验地认为土地人口均为国家所有,因而,不服从国家安排的就是“寇”或“贼”。直至明清时期,在全国开展丈量土地运动,在闽粤赣地区就遇到畲民的抵抗,如平和县早在明嘉靖中,知县谢明德就已经开始提议实施土地丈量:
仿古经界之法,就现在田土丈量均产,每田一亩随九等高下会计产钱。而总合一郡诸租税、钱、米之数,以产钱为母,别定等则;一例均敷,分隶若干为省计,若干为职田、学粮之属,令诸乡具籍,条别辖内田额四至。①
这说明是一种边界的推移。应该是加强控制,华夏边缘逐渐延伸,导致了非汉民族的反弹。这种丈量田亩等,名义上是为国家丈量田亩,实际上在此之前均为非汉民族居住,应该会造成关系的紧张,如清道光《平和县志》记载:
(康熙)三十七年七月,贼首钟平鼻,吕扁②党也。因县有丈量田亩之议,人情汹汹,知县奔避郡城。平鼻结盗营大丰社,去县三十里,约期劫县,而自为内应,与弟钟二乘间登城伺探,为营兵所觉。县乡壮乘夜薄贼营,贼知平鼻既遁,皆溃,死者甚众。③
第二,由于中国中国古代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本,常将一些从事非农业的人民称为“轻民”,与“重民”相对。清代梁章钜在《称谓录》中称:“重民,《管子》:‘轻民处而重民散’。注:轻民,谓为盗者,重民,谓务农者。”④轻和重相对,区别在于,重民务农纳税,轻民,逋逃为盗。所以从事商业以及经济作物者均认为是社会不稳定因素。
闽粤赣地区自宋代以后,出现的许多“寇”“贼”,清代杨澜曾考证称:
汀郡……乃稽之往代,则有江寇、虔寇、广寇、漳寇、海寇、洞寇、畲寇、盐寇,种种名色,其故何哉?自王绪引兵入闽,汀郡首婴其锋,地为丹徼喉衿。入宋,则盐徒剽掠,往来汀、虔、漳、梅、循、惠、广之地,官不能禁。①
如果将杨澜列举的“寇”分类,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按照族群身份从事职业区分,如海寇、畲寇、峒寇、盐寇,或者是处在山峒、海边的寇,或者是从事盐业、畲田的寇;二是按照“盗寇”来源地区分,如江寇、虔寇、广寇、漳寇。根据杨澜考证,古代汀州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类型的“寇”,一方面是地理缘故,唐末王绪引兵入闽,汀州因其地理位置首先遭遇战乱而引起“寇乱”;另一方面是经济缘故,如盐徒四处剽掠,官府也无法控制。
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唐五代以后,以王绪为代表的中原汉族势力进入福建地区,引起了当地族群结构的变化,族群边界被打破时,族群冲突而造成的社会动乱屡有发生;另外,唐宋经济重心南移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在地方与中央,地区与地区之间以及不同族群之间的资源分配发生结构性的矛盾,由此产生冲突。②特别是入宋以后,朝廷关于食盐制度的不合理③,一些盐徒趁机剽掠,食盐走私盛行引起地方的连锁动乱反应。如王安石《虔州学记》记载:“虔州江南,地最旷,大山长谷,荒翳险阻,赣、闽、越,铜盐之贩,道所出入,椎埋盗守鼓铸之奸,视天下为多。”④《天下郡国利病书》也称:“汀虽非产盐之区,而实为通盐之路,亦江广之咽喉,为闽西外府也。宋时通之,寇且踵作,而必禁之”⑤南宋绍定年间汀州改食潮盐后,《临汀汇考》载:“惟虔州患苦盐法如故。而汀境食米不敷,半仰给于邻境之肩贩,常有遏粜之恐。于是乃许虔民担米来汀,贸盐而返,以有易无,二州民胥赖之。”⑥
可见各地的经济结构具有不平衡的特性。以汀州为例,该地常常有粮食不足的现象发生,粮食不足自然米价上涨,由此又引起寇乱的产生。有史料证明灾荒引发的米价上涨曾导致了闽西洞民寇乱。清代邱嘉穗在《与翁明府、蒋参戎论洞寇书》曾记载了明代上杭来苏三乡的洞寇因为米价上涨而为盗寇的情况:
窃惟来苏三乡,孤悬天末,不幸复界闽、粤间,西接武平,南邻程乡,无深沟高垒以为之限,有幽岩丛菁以为之巢。其二洞,群不逞之徒倚为窟穴,游奕往来,眈眈视来苏如奇货者,盖匪朝伊夕矣。会日秋收颇歉,谷价上腾,加以赣米弗来,潮米莫上,贫民半菽不饱,并日而炊。于是,二洞之亡命为雄者,至敢阴行招纳之私,大肆攻掠之惨,一呼百应,四方驿骚……诚见年荒米贵,平时汀、潮两地所仰给于西江诸郡县者,近则皆禁绝不甚通,非邻封有遏籴之谋,即当事之过虑,不许贩出境外,而皆必给票盘验,以使之嗷嗷望哺,卒不可得;枵腹难堪,呼吁无门,既不敢擅发河东之粟,复谁能代绘监门之图?彼以为死于饥也,与死于盗也,等一死也;与其捐瘠沟中而长为白骨之鬼也,何如游魂釜底而暂作绿林之豪也。是以奋袂攘臂,不得已而出于此。①
日本学者竹村卓二在研究华南山地民族时也指出:“山地民的粮食自给率十分低下,常常碰到饥荒,从而成为引起暴动的原因,这并非偶然。尤其为维持生命不可缺少的食盐供给,是最为紧要的问题。”②
明清以后,在闽粤赣地区出现大量类似“炭党”“矿徒”“菁客”“麻民”“蓝户”“烟民”“菰农”“畲客”“山贼”“棚民”等称谓的流动人口。“寇、客、党、徒、盗、贼”等通称与“民、户”相对,是在中国古代重本抑末经济体系下,对非粮食生产人口的各种称谓。之所以用“贼”“寇”称之,主要是因为这些流动人口往往与土著族群发生冲突,并对正常农业社会秩序带来巨大的破坏。傅衣凌先生曾论述道:“(明清时期)山区带有商品经济关系性质的农民斗争……是和商品生产有较大联系的山区棚民的斗争。他们以蓝户、菁户、麻民、炭党为主体,此外,还有‘矿盗’‘海盗’的参加……他们多是离开土地的外地人……流动性大,人数多”。③傅先生认为,明清时期的社会动乱与这些从事非农业(从事商品经济关系性质产业)人口有极大关系。
这些流动人口,往往是无籍的人口。无籍之民,按刘志伟研究,在明代广东地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脱离里甲体制的“逋负之徒”(或“逃户”),另一类是未归附于里甲体制的“化外之民”(或“蛮夷”)。①饶伟新曾指出,“无籍之民的社会政治处境和‘化外蛮夷’的族群背景”造成了明代赣南的社会动乱。②也就是说,无籍之民与“蛮夷”共同造成了明代闽粤赣地区的社会动乱。如《虔台志》载惠州府三类无籍之民:
以和平(县)为赣、桂、汀、漳之界,乃大帽山、岑冈地也,挂坑障、香炉峰、看牛坪皆比近,故延蔓相及耳。然惠皆良民耶?徭僮淆焉,鱼蛋伏焉,逋亡集焉,盗所由出也。③
说明在广东惠州在数省交界之地不仅“良民”居住,还生活着许多非汉族群,概括起来有三类人:“徭僮”“鱼蛋”“逋亡”。这三类分别指在山为畲、在水为疍,加上逃避赋税的所谓“奸人”,这些人是汉人,但一般将其视为化外之民。这也说明了随着历史的推移,王朝关于南方化外的非汉族群的泛称,从原来的一类(蛮),变为两类(莫徭—卢艇、蛮—疍、居峒砦—家桴筏),变为三类(“徭僮”—“鱼蛋”—“逋亡”)。从这种泛称分类也进一步说明,对华南社会,特别是内部结构,有了更深的理解。“逋亡”群体的存在,是华夷边界摇摆、流动的重要变量。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广东多地有“山寨瑶贼、蛮贼及倭贼”。同时,“东莞、香山等县逋逃蜑户,附居海岛,遇官军即称捕鱼,遇番贼则同为寇,不时出没,劫掠人民。”④这些“逋逃蜑户”在蜑与倭中身份变换,成为地方不稳定因素之一。
无籍之民与“蛮夷”二者有时候是统一的,即动乱中的叛乱者,既是“蛮夷”,又是无籍之民。福建等地的矿冶,聚集了一些非汉人群,有很大一部分是畲民。如永安御史胡琼《忠洛无银矿记》记载峒民从事银矿开采,而后酿祸的经过:
正德癸酉,民有趋利者,诱浙之峒民,拥众突来,未敢恣发。适郡节推郭姓者摄县事,峒民度其老而贪,得厚啗以利。郭欣然许其开凿,且为之陈于总镇。邑人以其地密迩大帽山,为江、浙、闽、广丛盗之会,虑其闻风袭夺,因以为乱,群情惊惧罔措。时佥宪、睢阳蔡公天佑行部至郡,闻之,乃兼程诣县,数郭之罪,率庶民塞而禁之。峒民方以采无所得,及闻蔡来,众遂宵遁。至是,人心始安,皆德于蔡。然闻总镇,祸已基于此矣①
永安出现从浙江而来的峒民,这些峒民或许是畲族。再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广东畲民成为“矿徒”时称:“畲蛮,岭海随在皆有之……近海则通番,入峒则通猺,凡田(土单)矿场有利者,皆纠合为慝,以欺官府,其害僭于甲兵。”又载广东“惠之归善、海丰,广之从化、香山皆有银矿。畲蛮招集恶少,投托里胥,假为文移,开矿取银,因行劫掠。”②
顾炎武的《肇域志》记载:“金溪山,一作金鸡山,在县西北四十里,连接六洞诸山,旧有银坑,湮塞已久,万历中奉旨开采,商估杂还,豪狷假虎,二都山民岌岌惊变。”③六洞也称“六峒”④,二都“山民”主要是畲民。说明由于矿冶开采,一些富商巨族借以占领盘剥,导致明代周边畲民几乎动乱。从这个记载来看,所谓的动乱,经常是由于资源竞争中,畲民的一种自我反应,常常是被迫叛乱的,然而在叛乱之后,统治者常常冠之以贼、寇等称号,形成了一种族群的印象。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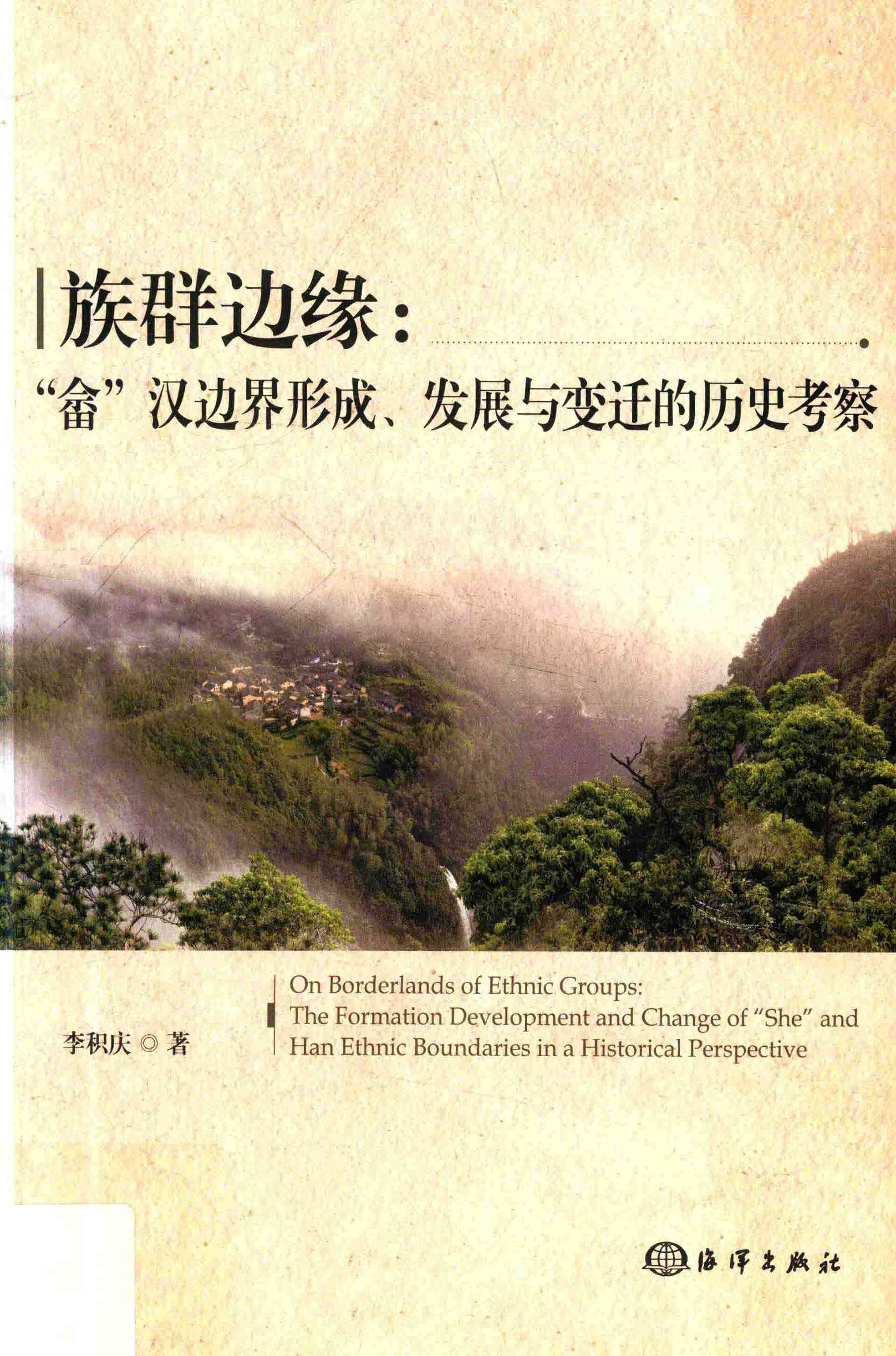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出版者:海洋出版社
本书从族群边界的理论角度,重新审视畲族形成、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在承认族群客观历史文化的同时,重点研究历史上“他者”(主要是汉族)对“畲”的社会定义以及“自者”(主要为南方非汉族群)自我族群认同的过程,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现实意义。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