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宋明时期畲汉族群边界的流动
| 内容出处: |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图书 |
| 唯一号: | 130920020230003785 |
| 颗粒名称: | 第三章 宋明时期畲汉族群边界的流动 |
| 分类号: | K288.3 |
| 页数: | 27 |
| 页码: | 106-132 |
| 摘要: | 本文探讨了宋明时期畲汉族群边界的流动。 |
| 关键词: | 族群文化 称谓 漳州 |
内容
闽粤赣地区是地理边界的缓冲区,也是各类族群互动频繁的地带,成为孕育新的族群的温床。这个地区的族群边界流动频繁,既有畲民通过获得版籍成为编户齐民的情况,也有汉人通过“入山洞”,脱籍成为“畲”“瑶”族群的情况。这种族群边界的流动,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身份或文化身份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是官方对族群社会定义和族群分类的结果,同时也体现了族群自我认同的变迁过程。
第一节 国家认同与畲汉边界的流动
两宋时期,福建人口迅速增长①。户口的增加一方面是经济发展、人口繁殖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一些非汉人群进入国家版籍的结果。
一、族群边界流动:“畲入汉”与“汉入畲”
有关“畲”汉身份转化,在史料多有记载。刘克庄《漳州谕畲》一文描述了漳州地区的畲人不堪“贵家辟产”“豪干诛货”以及“官吏征求土物”而“怙众据险,剽略省地。”在理宗景定三年(1262年),国家派兵对畲民采取“剿捕”策略,然而效果不佳,于是选派卓德庆前往治理畲乱,卓德庆采取招抚策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漳州谕畲》写道:
侯榜山前曰:畲民亦吾民也。前事勿问,许其自新。其中有知书及土人陷畲者,如能挺身来归,当为区处,俾安土著;或畲长能率众归顺,亦补常资。如或不悛,当调大军,尽鉏巢穴乃止。命陈鉴入畲招谕。令下五日,畲长李德纳款。德最反复杰黠者。于是西九畲酋长相继受招。西定,乃并力于南,命统制官彭之才剿捕,龙岩主簿龚镗说谕,且捕且招。彭三捷,龚挺身深入。又选进士张杰、卓度、张椿叟、刘口等与俱。南畲三十余所,酋长各籍户口三十余家,愿为版籍民。二畲既定,漳民始知有土之乐。①
“畲民亦吾民”说明是官方在招抚畲民中采取的一种外交辞令,其中又隐含着华夏民族与非华夏民族不平等地位。如刘克庄在《送方漳浦》也写道:“颇闻送者诗盈轴,我有樵歌子试听。岩邑虽然人所畏,畬民均是物之灵。二升饭了官中事,一字廉真座右铭。见说守侯如召杜,断无走吏至公庭。”②刘克庄以山歌的形式送方漳浦,其中一般认为生活在岩邑(险要的城邑),一般人视之为畏途。“物之灵”用典于《尚书·泰誓上》,其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③畲族应该被看做“物之灵”。侧面反映了当时很多人将“畲”视为非人的看法普遍存在,这是一种族群边界的象征。
一般来讲,非汉民族在华夏化进程中有三个主要特点:
一是畲民内部的汉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具有不平衡性。也就是说,汉化常常从内部集团的上层开始,从刘克庄文中我们发现,畲民的华夏化是从“知书”“土人陷畲者”“畲长”开始的。在明清以后仍是这样,如《天下郡国利病书》描述福建“猺人”时称:“楚粤为盛,而闽中山溪高深之处间有之。漳猺人与虔、汀、潮、循接壤错处……今酋魁亦有辨华文者。”④
正如当年楚、越等国华夏化运动也是从上层开始⑤一样,畲民的华夏化也是从首领开始,所谓的“今酋魁亦有辨华文者”,说明畲族族群首领开始接触汉字并通汉语,为本族畲民的汉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是畲民汉化具有反复性,从中也体现了族群认同工具主义的特性。“畲长”之所以被认为是“最反复杰黠者”,说明畲民在不同社会环境下,根据利益需求,选择不同的认同策略。
三是反映了非汉民族华夏化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在国家意志的强力推行下,部分非华夏民族在强势的华夏文化中或者被迫,或者自愿融入华夏族中,另外,还有部分采取不合作或逃离的策略,他们仍然保持“蛮夷”身份。但是,随着华夏化进程不断进行,在官方“且捕且招”的政策下,将有越来越多的蛮夷融入华夏族中,这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一个大的发展方向与历史趋势。
汉人进入畲区而成为畲民也是当时比较常见的历史现象。在宋代不仅有百姓“入畲”“陷畲”,连一些官员都“隐畲”以求庇佑。如刘埙的《隐居通议》记载南宋赵必岊入畲的情况:
赵必岊,字次山……乡寓公吴允文浚奉密诏以江西招讨使举义反正,结约次山协谋兴复,战不利。允文奔漳州为都督文丞相天祥所杀,次山解兵隐汀州之畬中,踰年以疾终。①
汉人逃入畲洞,即所谓的“边人逃入蛮峒”,大部分原因是为了逃避赋税。《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时,江西行省左丞高兴曾上书请旨言:“江西、福建汀、漳诸处连年盗起,百姓入山以避,乞降旨招谕复业。”皇帝下诏皆以应允。②在元代,由于各地畲乱不断,百姓入畲者比前代更多,如《元一统志》记载道:
汀之为郡,山重复而险阻……西邻赣,南接海湄。山林深密,岩谷阻窃,四境椎埋顽狠之徒,党与相聚,声势相倚,负固保险,动以千百计,号为畲民。时或弄兵,相挻而起,民被其害,官被其扰。盖皆江右、广南游手失业之人逋逃于此,渐染成习。
武平南抵循、梅,西连赣,篁竹之乡、烟岚之地,往往为江广界上逋逃者之所据。或曰“长甲”,或曰“某寨”,或曰“畲峒”,少不如意,则弱肉强食,相挺而起。税之田产,为所占据而不输官。③
在元代汀州“椎埋顽狠之徒”,数量众多,他们“党与相聚,声势相倚,”且“号为畲民”,说明他们中许多是打着“畲”的旗号,弄兵作乱。这类“畲”数量增多的原因是“江右、广南游手失业之人逋逃于此”,这些人原本并非“畲”民,其在汀州所占之地被称为“长甲”“某寨”“畲峒”,被视为化外之民。由此可见,此时族群之间的界限模糊不定,在社会动乱的背景下,畲作为一类人群,其势力得到较大的发展。在元代士大夫眼中,此类逃离本乡聚集于深山幽谷间负隅抗拒官府者,也被称为“畲民”,明显的例子还有“畲民丘大老集众千人寇长泰县”①。
在明代前期,闽粤赣的畲族势力仍较强大,入畲的汉人较多。王阳明治理闽粤赣地区“畲乱”时,曾记载有一些汉人被煽动蛊惑入畲的情况:
其大贼首谢志珊、蓝天凤,各又自称“盘皇子孙”,收有传流宝印画像,蛊惑群贼,悉归约束。即其妖狐酷鼠之辈,固知决无所就;而原其封豕长蛇之心,实已有不可言。②
也有一些是无籍汉人避役入輋的如:“吉安府龙泉、万安、泰和三县并南安所属大庾等三县居民无籍者,往往携带妻女,入輋为盗。”③还有原本非畲的百工技艺游食之人入輋的如:“其初輋贼,原系广东流来。先年,奉巡抚都御史金泽行令安插于此,不过砍山耕活。年深日久,生长日蕃,羽翼渐多;居民受其杀戮,田地被其占据。又且潜引万安、龙泉等县避役逃民并百工技艺游食之人杂处于内,分群聚党,动以万计。”④
以上描述的多为江西一带畲族情况,闽粤其他地方也类似,如“闽潮人叛逃流亡,就地垦荒者谓之畲蛮。”⑤到了清代,仍有此类人员:“雷公岭,距县北(饶平县)三十五里,层冈叠嶂,为潮惠二县(恐为州之误,笔者注)之界,奸民逋赋役者,辄借口邻封,彼此窜避,或托为猺獞逃化外。”⑥“托为瑶僮逃化外”说明畲汉边界在流动。
李调元的《南越笔记》有关于汉人由伪猺变为真猺过程的记载,其文称:乐昌有伪猺,多居九峰司诸山。其始也苦于诛求,以其田产质客户,窜身猺中,规免旦夕,久之性情相习,遂为真猺。相率破犯条要,恣行攻劫,为地夫之害,即善猺亦且畏之。⑦
显然,文献中关于的“畲”“輋”“猺”的记载,其并非作为纯粹的种族区分,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身份或文化身份的区分。也就是说,官方或文人把“入畲”的汉人——这些汉人不管是“为盗”,还是“避役”——均称为“畲民”,目的是用其笼统地称呼那些脱离编户、与政府不合作的各种人群。①
由此可见,“畲民”的形成不仅仅是自我认同的结果,官方或主流文化对其社会定义同样重要。也就是说,有一些畲民认同,乃至“假托”自己为“畲民”;而另外一部分则是官方以单方面标准判断其是否为“畲”。可见,“畲/汉”边界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既可以“入畲为寇”,又可以“籍峒为民”,从而实现“版籍/无籍”和身份的相互转化。②
二、国家认同:版籍作为族群区分的意义
国家常将获得版籍作为区分“溪洞”与“省民”或“畲”与“非畲”的重要标准,其背后体现的是文化认同的因素。国家之所以重视版籍,是因为社会的安定需要对边境进行控制,需要对户口进行管理。如明万历《福州府志》描述洪武到正德到万历年间二百余年户口无所增长时,作者论述道:
夫国家治平,晏然无事,二百年于兹,即前古未有矣……是故豪宗巨家,或百余人,或数十人,县官庸调,曾不得征其寸帛,役其一夫。田夫野人生子,黄口以上,即籍于官,吏索丁银,急于星火。此所以贫者益贫,而富者益富也……不毛之宅,无职事之人,终日美衣甘食,博弈饮酒,市井嬉游,独不可稍举古人以末之政,以纾力本者之困也耶?为今之计,欲使户无匿丁,则莫若凡讼于官者,必稽其版,凡适四方者,必验其襦,则户口可核。户口可核,则赋役可均。不惟足国裕财,驱民于农,亦无便于此者矣。③
明代户税制度不完善,豪宗巨家和一些百姓逃避户税,造成了国家的户税危机,所以要求,欲使户无匿丁,加强户籍的审核,如此可以均赋役,足国裕财,驱民于农。从这个分析,国家十分需要将一些可以纳入版籍的百姓纳入,这是国家安定的重要基础。将畲民纳入编户齐民可以证明一个地方官的政绩,也说明地方教化、文明的象征。
一些百姓如果不入版籍,不纳赋税,也会被视为化外之民。直到明末,所谓的化内化外并不一定指的是少数民族,而指的是有没有接受王化,如冯梦龙的《寿宁待志》称:
至磻溪、西溪二处与泗洲桥素通姻盟,互相应援,一呼百集,目无官府,欠粮拒捕,无所不至。余惩顽民陈百进之事,乃请详上台……而收化外之民于化内也。①
实际上,在早期蛮族华夏化过程中,也常提及纳税情况,如应劭记载长沙武陵蛮称:“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②认为,他们不向中国官府纳赋税,说是因其父盘瓠对中国有功,母亲又是帝王之女事实上,应是当时朝廷尚无力统治这地方的山间人群。《南史》中记载荆雍州蛮为盘瓠之后,这部分蛮夷顺附者向朝廷纳赋税,但无杂税与劳役。也有部分汉人逃入蛮夷,群起为盗,“结党连郡,动有数百千人”③。这些逃入蛮夷中的汉人,逋负钱粮,也被统治者视为化外之民。因此,赋税与其作为经济特征,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特征:是判断汉与非汉的重要标准之一。
再如宋代刘克庄为宁都县丞赵必健写的《英德赵使君墓志铭》称:剧贼陈淮西、罗洞天聚众出没赣、汀、潮、梅数州郡,檄令合官民兵讨之……罗畬峒首黄应德久负固,亦请出谒,公延见,享劳之,感泣辞去。已而邵农至其所,应德曰:“吾父来矣,率妻子部曲罗拜,愿附省民输王租,迄公去,溪峒无反仄者。”④
以上记载中的罗畬峒居民应该是畲民,是否“输王租”,成为“省民”与“峒民”的主要区别之一。郭志超等认为唐代之前畲族尚无纳税,南宋末年才有少部分畲族承担封建赋役,宋元时期畲民入籍和承担赋役并没有大范围进行,而直至清代,畲民才在真正意义上承担封建赋役。⑤从畲民的纳税服役的范围及普遍性情况,可以看出,畲民不断被卷入华夏化进程中,编户齐民身份的获得以及对国家义务的履行,对畲民的国家认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明代一些畲族首领入朝贡献,这种象征性的仪式在国家看来是臣服万民,民心归顺的国家重大事件,因此被记录在史籍当中。如明代《广东通志》记载道:
(永乐五年1407年)冬十一月,畬蛮雷文用等来朝。初,潮州府卫卒谢辅言:海阳县凤凰山诸处畬,遁入山谷中,不供徭赋,乞与耆老陈晚往招之。于是畬长雷文用等,凡百四十九户,俱愿复业。至是辅率文用等来朝,命各赐钞三十锭,彩币表里绸绢衣一袭,赐辅、晚亦如之。①
可见,是否纳税服役是朝廷判断一个地区人群“化内”或“化外”的标准。如崇祯《兴宁县志》曾对当时将“徭蛋”称为“夷狄”的社会偏见进行反驳,其中主要的理由就是当地“徭蛋”获得版籍,并纳税服役,其文曰:
按吴志名徭蛋曰夷狄,令人愕然。求其说而不得。此非山戎氐羌之比,错居中土,衣冠与世同,无复椎结之习,一耕于山,山有粮,一渔河,河有课。既籍其名於版,子孙数十世势能徙居塞外矣乎?出入同乡井,又能区分限域矣乎?王者无外,听其蠉飞蠕动于穹环之间,亦齐民矣。已恶得而狄之。②
明代《广东通志》描写潮州府畲、瑶时称:
民有山輋曰瑶、僮,其种有二:曰平鬃,曰崎鬃。其姓有三:曰盘、曰蓝、曰雷。依山而居,采猎而食,不冠不履,三姓自为婚,有病没,则并焚其室庐而徙居焉。俗有类于夷狄,籍隶县治,岁纳皮张。旧志无所考。我朝设土官以治之,衔曰輋官,所领又有輋,輋当做畲,实录谓之畲蛮。③
从以上记载看出,作者认为輋又称瑶、僮,习俗“有类于夷狄”,即认为畲民与夷狄习俗有相同的地方,从遣词造句中又说明畲民不完全与夷狄相同造成这种认识的根本原因在于“籍隶县治”,这再一次说明国家版籍制度的施行,使得畲民慢慢进入华夏边缘之内,版籍也是判断畲汉边界的一个重要标准。
第二节 “贼”“民”分类与宋代以来的“畲乱”
宋元以后直至明中叶,闽粤赣交界地区一直是族群动乱的中心区域,体现在文献上就是大量有关于“洞寇”“畲寇”“畲军”“畲贼”等记载的出现。
新中国成立以来,畲族动乱(或畲族起义)成为畲族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由于受到当时学术背景的影响,畲族史研究带有明显的“政治意识”,如畲族社会历史调查中,过多地强调阶级斗争内容,从而限制了畲族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①笔者认同王学典先生关于50年来的农民起义研究的反思,即在“学术语境中”对社会动乱进行研究。②近年来,闽粤赣地区的社会动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唐立宗、黄志繁、饶伟新等学者做了有益的探索,给本文研究带来了不少的启发。③笔者从族群边界的角度分析后认为:宋元大量出现的“畲乱”记载,是官方单方面的文化表述,“畲”经常是作为一种“文化标签”,“畲”与“非畲”并非只是纯粹血统的“种族”区别。宋元时期,关于“畲乱”的大量描述,既体现了官方“贼”“民”的族群分类,也可以观察“畲”、汉族群边界的流动情况。
一、畲瑶“盗”“寇”“贼”族群印象的由来
宋明时期闽粤赣地区“寇乱”频发,地方社会危机重重,该地区的社会动乱有其自然、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这是一个多种因素叠加、社会矛盾积累到某个临界点时,而后矛盾相继爆发的特殊社会现象。正如《汉书·贾谊传》所称:“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④从文化学的角度,宋元以来的“畲”乱,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再创造的结果,“寇乱”显示了当地族群社会文化整合的情况。
随着以汉人为代表中央王朝日益深入南方地区,南方的非汉族群被定性为“蛮夷”话语之中①,文献中出现的有关“峒”“蛮”“獠”“猺”“獞”等均是这种“华夷之辨”族群话语下的产物。特别是在汉与非汉之间的族群边界冲突发生时,更进一步加深了华夏族对“蛮夷”的“贼”“寇”身份的印象。那么,这些“贼”“盗”“寇”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话语权掌握在统治者手中,因此“贼”“寇”其实就是官方单方面的文化表述的产物,官方的利益成为评判标准的核心。在官方的话语系统中,“贼”“寇”与“民”相对,是合法社会秩序以及帝国权威的挑衅者。“贼”“寇”本有区别,清代梁章钜在《称谓录》中称:“奸宄。《书传》:‘劫人曰寇,杀人曰贼,在外曰奸,在内曰宄。’……盗,《左氏》定公八年经注:盗,谓阳货也。疏:盗者,贱人之称也。”②
随着历史的发展与演变,“贼”“寇”“盗”作为对动乱者的贱称实际上是相通的,可视为一种泛称,专门用以指代社会秩序的叛乱者。统治者用“贼”“盗”“寇”的文化标签来定义社会中某一特定族群,并以此区别族群间“良”与“荞”的边界。王朝以文化阶序来区分“贼”“民”之间的族群边界,其目的在于:宣扬文化等级差异,防止更多民众加入“贼”之中,同时增强普通百姓内部的文化认同感。从历史上看,在多数动乱中,不仅由官方派兵平盗,在民间中,也有许多士绅阶层自发组织乡村民间武装对“贼”“寇”进行剿杀可见,族群边界的区分,有助于维护王朝的统治秩序。如《宋史》载:“(至元十四年)五月……(张)世杰乃奉益王入海,而自将陈吊眼、许夫人诸畲兵攻蒲寿庚,不下。”③
而清代杨澜的《临汀汇考》亦载其事:“宋绍熙中,上杭峒寇结他峒为乱,州判赵师璱擒其渠魁。而宋季张世杰会师讨蒲寿庚,有许夫人统诸峒畲军来会,汀畲亦在军中。”④
这里的表述比较微妙:“峒”民为乱称之为“峒寇”,参与张世杰军队者则称之为“畲军”或“畲兵”。可见,“军”“兵”与“寇”之间的区别,显然是根据是否符合官方利益的标准而作评判的。
刘志伟曾指出“蛮夷”之所以常被冠以“贼”“盗”“寇”蔑称,与其“不受教化”“不税不役”“化外之民”的特征有关系,而所谓“蛮夷”,不仅是一个血统的范畴,更是一个文化和社会的范畴。①对于王朝而言,纳税服役的政治意义远比经济意义大,是否承担赋役、履行国家义务,成为国家区分“民”与“盗”的重要指标。②在一些国家政治管理鞭长莫及的偏远边陲地区,其居民(主要为非汉人群)无法做到或不愿意去履行国家义务,国家因此将这些居民与“盗联系起来”。这种思想体现在文献上,就是常将地理上的边陲与族群“化外”的性格联系起来,即认为一个地区的民风或族群性格往往与地理环境有关,地理越蛮荒险远的地方,居民可能越难教化,也更易发生动乱。
福建山区往往为盗贼渊薮,宋代的周必大称:“七闽地狭,人众甚艰苦,其民亦重犯法,然东际海南接炎峤,西入赣境,风潮出没之奸,山谷集之盗,控御失所,或害吾治。”③到至元年间便有人认为:“闽地山谷之间往往乌合为寇”。④《元一统志》也称:“汀之为郡,山重复而险阻,水迅急浅色涩。民生其间,气刚愎而好斗,心偏迫而浅,亦风土使然。⑤
直到明代闽粤赣仍被认为是畲民聚集的地方,何乔远《闽书》称:“江西之南赣,福建之汀漳,及广东之南、韶、潮、惠,湖广之郴桂,境壤相接,峻谷深山,岭岫缀连,輋贼窟穴其中。”⑥明代时期,上杭溪南地区作为“盗窟”尤为著名,明代兵部尚书杨博称:“闽广之贼所倚重者数巢穴耳,其大者在福建则有上杭峰头、永春蓬壶……”⑦明人郭造卿在《闽中分处郡县议》亦云:
“然近日三省山寇数十年一作,及剿有数十年之安,惟三图百余年,无秋冬间不啸聚,屡扑而不驯服,其山林险密,尤异他区,邻省山寇共推之为主耳。”①
清代杨澜在《临汀汇考》称:“南赣地连闽广,山谷深阻,盗贼易为巢穴。”②《肇域志》记载漳浦县大帽山:“在县北百里,山大而峻……南距檺林延袤数百里,深林丛莽,群不逞多啸聚,其间迤东通溪埔山,菁畲猺獞时出为寇,乡导而直北。”③可见在闽南地区的漳浦大帽山、云霄檺林这些地方“深林丛莽”,成为“盗贼”啸聚的地方,在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人是“菁畲猺獞”,也就是畲民。
除了福建外,广东、江西等地也是畲、猺、峒獠出没之地,如史称“在广东则有猺峒,在江西有輋巢”④,这些族群一般被认为是危险的、狡猾的人群,如元末黄潜记载郴州百姓害怕与当地非汉族群交往,“洞蛮猺獠往来民间,人惮其强猾,莫敢与相贸易”。、⑤这里“民间”应该指的汉人社会,“人”也指汉人,当然这种记载是单方面的反映的是汉人对这些猺獠的看法,我们或许可以推测,猺獠在面对强势的汉人,比上述的汉人更为“忌惮”。
这些非汉族群在汉人眼中之所以是危险群体,与他们时常外出劫掠有关,因此也被称为“盗贼”。明人梁朝宗描述江西龙泉等地有“猺、輋、獠”,这些居民僻居山区,不纳赋税,而且在灾荒之年劫掠百姓,如“龙泉,吉左僻邑也,控郴衡而引虔,猺、輋、獠、恶少出没之地,岁登则自食其力,歉则群聚不逞之徒,大肆劫掠刈人如草菅。”⑥
輋民冠以“贼”字,可见当时畲民的族群印象被打上“盗寇”的烙印,正是有了这种族群印象,所以在文献中谈及闽粤赣边等地区的非汉族群时,常以好斗喜乱来形容其性格,如“畲丁①溪子善惊好斗。”②又如“畬丁洞猺喜惊而嗜斗”③。
实际上,“民”和“贼”的身份并不一定是固定不变的,二者是可以转化的。王慎中在分析上杭县的溪南盗风日炽时,对“民”化为“盗”作过精彩的论述:
风气所限,非性故然,长子育孙,生蕃齿盛,耳目熟习,莫改厥德,少视其壮,壮视其老,蹲危逗幽,乃为盗薮。厥有治者,不揆其性,不闵其习,盗视彼民,忿犷堲凶,攻击铲除,如农疾莠,惟惧不残、民不见德,又弗儆威,既狃于习,且偷其生,鸱张螳怒,攘奋踉跄。吏既雠民,民亦毒吏,雠毒两积,交不得已,于是溪南之民,恶声胶固。④
可见,最初“民”“盗”水火不容,但最后仍皆为盗贼所吸纳。足见一个地方文化对族群塑造的力量。
就官方立场而言,“盗贼”界定主要在于人民的行踪官方是否难以掌握,衡量的标准是以平民的活动是否违法脱序作判别。在古代农业社会价值观念下,只要在土地上安分守己,就不是“盗贼”,否则皆将与“盗贼”无异。“倘若硬性将传统农业社会价值观念,桎梏在逐渐转向于商品经济流通的社会,自然官方会对流民、移民的增多而感到处处皆‘盗’,在此情况下,社会经济的变化造成南赣地区的盗增并不使人意外。当然对于现有秩序与体制而言,官方根本不容许‘盗贼’聚众生事,并强力禁制他们‘倡乱’。”⑤
另一方面,华夏化过程中,王朝势力深入非汉地区,引起了当地族群与其他族群,乃至与政府的矛盾。这本来是政府深入非汉族群的居住地,但如前文所述,在华夏视野的“天下观”中,官方先验地认为土地人口均为国家所有,因而,不服从国家安排的就是“寇”或“贼”。直至明清时期,在全国开展丈量土地运动,在闽粤赣地区就遇到畲民的抵抗,如平和县早在明嘉靖中,知县谢明德就已经开始提议实施土地丈量:
仿古经界之法,就现在田土丈量均产,每田一亩随九等高下会计产钱。而总合一郡诸租税、钱、米之数,以产钱为母,别定等则;一例均敷,分隶若干为省计,若干为职田、学粮之属,令诸乡具籍,条别辖内田额四至。①
这说明是一种边界的推移。应该是加强控制,华夏边缘逐渐延伸,导致了非汉民族的反弹。这种丈量田亩等,名义上是为国家丈量田亩,实际上在此之前均为非汉民族居住,应该会造成关系的紧张,如清道光《平和县志》记载:
(康熙)三十七年七月,贼首钟平鼻,吕扁②党也。因县有丈量田亩之议,人情汹汹,知县奔避郡城。平鼻结盗营大丰社,去县三十里,约期劫县,而自为内应,与弟钟二乘间登城伺探,为营兵所觉。县乡壮乘夜薄贼营,贼知平鼻既遁,皆溃,死者甚众。③
第二,由于中国中国古代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本,常将一些从事非农业的人民称为“轻民”,与“重民”相对。清代梁章钜在《称谓录》中称:“重民,《管子》:‘轻民处而重民散’。注:轻民,谓为盗者,重民,谓务农者。”④轻和重相对,区别在于,重民务农纳税,轻民,逋逃为盗。所以从事商业以及经济作物者均认为是社会不稳定因素。
闽粤赣地区自宋代以后,出现的许多“寇”“贼”,清代杨澜曾考证称:
汀郡……乃稽之往代,则有江寇、虔寇、广寇、漳寇、海寇、洞寇、畲寇、盐寇,种种名色,其故何哉?自王绪引兵入闽,汀郡首婴其锋,地为丹徼喉衿。入宋,则盐徒剽掠,往来汀、虔、漳、梅、循、惠、广之地,官不能禁。①
如果将杨澜列举的“寇”分类,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按照族群身份从事职业区分,如海寇、畲寇、峒寇、盐寇,或者是处在山峒、海边的寇,或者是从事盐业、畲田的寇;二是按照“盗寇”来源地区分,如江寇、虔寇、广寇、漳寇。根据杨澜考证,古代汀州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类型的“寇”,一方面是地理缘故,唐末王绪引兵入闽,汀州因其地理位置首先遭遇战乱而引起“寇乱”;另一方面是经济缘故,如盐徒四处剽掠,官府也无法控制。
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唐五代以后,以王绪为代表的中原汉族势力进入福建地区,引起了当地族群结构的变化,族群边界被打破时,族群冲突而造成的社会动乱屡有发生;另外,唐宋经济重心南移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在地方与中央,地区与地区之间以及不同族群之间的资源分配发生结构性的矛盾,由此产生冲突。②特别是入宋以后,朝廷关于食盐制度的不合理③,一些盐徒趁机剽掠,食盐走私盛行引起地方的连锁动乱反应。如王安石《虔州学记》记载:“虔州江南,地最旷,大山长谷,荒翳险阻,赣、闽、越,铜盐之贩,道所出入,椎埋盗守鼓铸之奸,视天下为多。”④《天下郡国利病书》也称:“汀虽非产盐之区,而实为通盐之路,亦江广之咽喉,为闽西外府也。宋时通之,寇且踵作,而必禁之”⑤南宋绍定年间汀州改食潮盐后,《临汀汇考》载:“惟虔州患苦盐法如故。而汀境食米不敷,半仰给于邻境之肩贩,常有遏粜之恐。于是乃许虔民担米来汀,贸盐而返,以有易无,二州民胥赖之。”⑥
可见各地的经济结构具有不平衡的特性。以汀州为例,该地常常有粮食不足的现象发生,粮食不足自然米价上涨,由此又引起寇乱的产生。有史料证明灾荒引发的米价上涨曾导致了闽西洞民寇乱。清代邱嘉穗在《与翁明府、蒋参戎论洞寇书》曾记载了明代上杭来苏三乡的洞寇因为米价上涨而为盗寇的情况:
窃惟来苏三乡,孤悬天末,不幸复界闽、粤间,西接武平,南邻程乡,无深沟高垒以为之限,有幽岩丛菁以为之巢。其二洞,群不逞之徒倚为窟穴,游奕往来,眈眈视来苏如奇货者,盖匪朝伊夕矣。会日秋收颇歉,谷价上腾,加以赣米弗来,潮米莫上,贫民半菽不饱,并日而炊。于是,二洞之亡命为雄者,至敢阴行招纳之私,大肆攻掠之惨,一呼百应,四方驿骚……诚见年荒米贵,平时汀、潮两地所仰给于西江诸郡县者,近则皆禁绝不甚通,非邻封有遏籴之谋,即当事之过虑,不许贩出境外,而皆必给票盘验,以使之嗷嗷望哺,卒不可得;枵腹难堪,呼吁无门,既不敢擅发河东之粟,复谁能代绘监门之图?彼以为死于饥也,与死于盗也,等一死也;与其捐瘠沟中而长为白骨之鬼也,何如游魂釜底而暂作绿林之豪也。是以奋袂攘臂,不得已而出于此。①
日本学者竹村卓二在研究华南山地民族时也指出:“山地民的粮食自给率十分低下,常常碰到饥荒,从而成为引起暴动的原因,这并非偶然。尤其为维持生命不可缺少的食盐供给,是最为紧要的问题。”②
明清以后,在闽粤赣地区出现大量类似“炭党”“矿徒”“菁客”“麻民”“蓝户”“烟民”“菰农”“畲客”“山贼”“棚民”等称谓的流动人口。“寇、客、党、徒、盗、贼”等通称与“民、户”相对,是在中国古代重本抑末经济体系下,对非粮食生产人口的各种称谓。之所以用“贼”“寇”称之,主要是因为这些流动人口往往与土著族群发生冲突,并对正常农业社会秩序带来巨大的破坏。傅衣凌先生曾论述道:“(明清时期)山区带有商品经济关系性质的农民斗争……是和商品生产有较大联系的山区棚民的斗争。他们以蓝户、菁户、麻民、炭党为主体,此外,还有‘矿盗’‘海盗’的参加……他们多是离开土地的外地人……流动性大,人数多”。③傅先生认为,明清时期的社会动乱与这些从事非农业(从事商品经济关系性质产业)人口有极大关系。
这些流动人口,往往是无籍的人口。无籍之民,按刘志伟研究,在明代广东地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脱离里甲体制的“逋负之徒”(或“逃户”),另一类是未归附于里甲体制的“化外之民”(或“蛮夷”)。①饶伟新曾指出,“无籍之民的社会政治处境和‘化外蛮夷’的族群背景”造成了明代赣南的社会动乱。②也就是说,无籍之民与“蛮夷”共同造成了明代闽粤赣地区的社会动乱。如《虔台志》载惠州府三类无籍之民:
以和平(县)为赣、桂、汀、漳之界,乃大帽山、岑冈地也,挂坑障、香炉峰、看牛坪皆比近,故延蔓相及耳。然惠皆良民耶?徭僮淆焉,鱼蛋伏焉,逋亡集焉,盗所由出也。③
说明在广东惠州在数省交界之地不仅“良民”居住,还生活着许多非汉族群,概括起来有三类人:“徭僮”“鱼蛋”“逋亡”。这三类分别指在山为畲、在水为疍,加上逃避赋税的所谓“奸人”,这些人是汉人,但一般将其视为化外之民。这也说明了随着历史的推移,王朝关于南方化外的非汉族群的泛称,从原来的一类(蛮),变为两类(莫徭—卢艇、蛮—疍、居峒砦—家桴筏),变为三类(“徭僮”—“鱼蛋”—“逋亡”)。从这种泛称分类也进一步说明,对华南社会,特别是内部结构,有了更深的理解。“逋亡”群体的存在,是华夷边界摇摆、流动的重要变量。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广东多地有“山寨瑶贼、蛮贼及倭贼”。同时,“东莞、香山等县逋逃蜑户,附居海岛,遇官军即称捕鱼,遇番贼则同为寇,不时出没,劫掠人民。”④这些“逋逃蜑户”在蜑与倭中身份变换,成为地方不稳定因素之一。
无籍之民与“蛮夷”二者有时候是统一的,即动乱中的叛乱者,既是“蛮夷”,又是无籍之民。福建等地的矿冶,聚集了一些非汉人群,有很大一部分是畲民。如永安御史胡琼《忠洛无银矿记》记载峒民从事银矿开采,而后酿祸的经过:
正德癸酉,民有趋利者,诱浙之峒民,拥众突来,未敢恣发。适郡节推郭姓者摄县事,峒民度其老而贪,得厚啗以利。郭欣然许其开凿,且为之陈于总镇。邑人以其地密迩大帽山,为江、浙、闽、广丛盗之会,虑其闻风袭夺,因以为乱,群情惊惧罔措。时佥宪、睢阳蔡公天佑行部至郡,闻之,乃兼程诣县,数郭之罪,率庶民塞而禁之。峒民方以采无所得,及闻蔡来,众遂宵遁。至是,人心始安,皆德于蔡。然闻总镇,祸已基于此矣①
永安出现从浙江而来的峒民,这些峒民或许是畲族。再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广东畲民成为“矿徒”时称:“畲蛮,岭海随在皆有之……近海则通番,入峒则通猺,凡田(土单)矿场有利者,皆纠合为慝,以欺官府,其害僭于甲兵。”又载广东“惠之归善、海丰,广之从化、香山皆有银矿。畲蛮招集恶少,投托里胥,假为文移,开矿取银,因行劫掠。”②
顾炎武的《肇域志》记载:“金溪山,一作金鸡山,在县西北四十里,连接六洞诸山,旧有银坑,湮塞已久,万历中奉旨开采,商估杂还,豪狷假虎,二都山民岌岌惊变。”③六洞也称“六峒”④,二都“山民”主要是畲民。说明由于矿冶开采,一些富商巨族借以占领盘剥,导致明代周边畲民几乎动乱。从这个记载来看,所谓的动乱,经常是由于资源竞争中,畲民的一种自我反应,常常是被迫叛乱的,然而在叛乱之后,统治者常常冠之以贼、寇等称号,形成了一种族群的印象。
二、“贼”“民”转化与畲汉边界的流动
根据官方对“贼”“寇”的定义,“贼”“民”之间具有动态流动性,二者既是对立的,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⑤换言之,有一些当地的土豪和良民在特殊情况下也转化为“盗贼”。如《宋史》记载绍兴十五年(1145年),福建安抚莫将上言称:“汀、漳、泉、剑四州,与广东、江西接壤,比年寇盗剽劫居民,土豪备私钱集社户防捍有劳,有司不为上闻推恩,破家无所依归,势必从贼。官军不习山险,且瘴疠侵加,不能穷追。管属良民,悉转为盗。”①这里说明一些土豪本为本地区防御付出努力,但是地方官存在不作为的现象,使其得不到应有的封赏,致使这些土豪家破财尽,只好从贼;一些处于“山险”地方的良民,由于官方军队无法制约盗寇,这些良民也转为盗寇。
在“贼”“寇”,其族群成分也具有动态性,有一些则将寇乱的部众与非汉族群攀上联系。如《宋史》称:“漳州之东,去海甚迩,大山深阻,虽有采矾之利,而潮、梅、汀、赣四州之奸民聚焉,其魁杰者号大洞主、小洞主,土著与负贩者,皆盗贼也。”②在这里,“洞主”既可以解释为矾矿的洞主,也可以解释“山洞”洞主。因为在唐宋以后,常将非汉族群聚落称为“洞”,洞主指其首领或酋长。如果后者推论成立的话,则说明当时有许多“潮、梅、汀、赣四州之奸民”以及当地“土著”与“负贩者”均打着“洞”的旗号进行寇乱剽劫。这不仅说明了在动乱中,一些“民”向“贼”的流动,也说明了从“夷”到“夏”的族群边界的流动。
再如至元十四年,“元军进至潮阳县,宋都统陈懿等兄弟五人以畲兵七千人降。”③陈懿家族拥有一支船队,其主要功绩为海上军事活动④。谢重光先生认为陈懿所率领的畲兵应源于蜑民,与山居耕畲的山民不属于同一系统,也就是说,这些畲兵是“海盗”,而不是“山寇”。⑤按照刘克庄的《漳州谕畲》记载,是在漳州等地溪峒种类的一支,他说:“凡溪峒种类不一:曰蛮、曰猺、曰黎、曰蜑,在漳者曰畲。”⑥可见在南宋以后,畲、蜑均属于“溪峒种类”,但由于所处区域不同,二者仍有区别。如果将蜑民军队称为“畲兵”,那么,说明在南宋刘克庄所处时代,“畲”还专指漳州的一支“溪峒种类”,而到了元代已经被用来泛称南方的一些“溪峒种类”了。也就是说,在宋元时期出现的畲军,其中的非汉族群,除了“畲”外,可能还有一些被称为“蛮”“猺”“黎”“蜑”的族群。
在宋元时期,“畲”不仅内涵变得丰富,包含了南方一些非汉族群,其在外延上似乎也有扩大的趋势。文献中出现的各类“畲军”,其部众并非全由畲民或“溪峒种类”组成,其中有很多是汉人。这些汉人在叛乱起兵时,常借助“畲”的旗号以壮大声势,如宋绍定二年(1229年),宁化的晏头陀在潭飞磜起义,即是此例。按傅衣凌考证,头陀不是人名,而是畲族中的一种尊号。①其部众多达数万人,②成分却并非均是“溪峒种类”而被认为是盐寇,《宋史》载:“盐寇起宁化,居安以书谕汀守曰:土瘠民贫,业于盐可尽禁耶?且彼执三首恶以自赎,宜治此三人,他可勿治。”③在宋代,江淮、赣、闽一带的盐夫、盐寇很多都为汉人,《宋史》又称:“不逞无赖盗贩(盐)者众。捕之急则起为盗贼,江淮间虽衣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贩盐为事。江西则虔州地连广南,而福建之汀州亦与虔接,虔盐弗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④
宋元以后,号称“头陀军”还有黄华⑤、陈吊眼等⑥。与晏头陀一样,这些“头陀军”有许多是汉人,如黄华畲军中主要是盐夫。《元史·世祖纪》载:至元十五年“建宁政和县人黄华,集盐夫,联络建宁、括苍及畲民妇自称许夫人为乱。”⑦到至元二十年,黄华的头陀军部众达几十万人⑧,这些人都被称为“畲军”。《元史》称,至元二十二年“九月,诏福建黄华畲军,有恒产者放为民,无恒产与妻子者编为守城军。”⑨而与黄华互为呼应的远不止几十万,至元二十六年,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王恽进言于朝说:
福建所辖郡县五十余,连山距海,实为边徼重地。而民情轻诡,由平定以来官吏贪残,故山寇往往啸聚,愚民因而蚁附,剽掠村落,官兵致讨,复蹂践之甚,非朝廷一视同仁之意也……福建归附之民户几百万,黄华一变,十去四五。今剧贼猖獗,又酷于华,其可以寻常草窃视之?况其地有溪山之险,东击西走,出没难测,招之不降,攻之不克,宜选精兵,申明号令,专命重臣节制,以计讨之,使彼势穷力竭,庶可取也。①
王恽分析福建寇乱的原因有几个:一是地理原因:“连山距海”“边徼重地”;二是族群原因:“民情轻诡”;三是“官吏贪残”;四是“山寇啸聚”后“愚民蚁附”。“福建归附之民户几百万,黄华一变,十去四五”的“十去四五”,可能有两种意思:一是百姓逃离十之四五;二是原来归附的百姓,又成为脱籍贯之民的有十之四五。如果是后者,则说明华夏边缘是向中心内缩,而非向边陲扩张,也就是说原来为华夏边缘内的百姓,现在又返回为边缘之外的百姓。但不管怎样一种后果,都说明了动乱对当地社会——尤其是汉族社会,带来巨大的打击。由此可见,“畲”在宋元成为一个泛称,许多参与地方动乱的人群打着畲的名号,统治者也将这些动乱称之为畲,这有文化标签的意味,而非全部均有“溪峒种类”的血统。
明代文献常将“畲”“猺”两类族群并称,二者具有一定联系。如《明武宗实录》记载道:
先是,江西、广东、湖广之交,溪峒阻深,江西上犹等县輋贼谢志山等据横水、桶冈诸巢;广东龙川县贼池仲容据三浰头诸巢,与猺贼龚福全等联络。亘千百里,时出攻剽,势甚猖獗,将连兵乘虚入广。②
可见畲、瑶互相联络支援,“连兵”作乱,形成了“四省輋贼、猺贼及峒贼蟠纠流劫”③的情况。王阳明称:“三省贼巢,联络千里,虽声势相因,而其间亦自有种类之分、界限之隔。利则争趋,患不相顾,乃其性习。”④这段话说明,闽浙赣三省这些所谓的輋、猺、峒的贼寇实际上是有种族之间的区分,聚居地有所区别,也就是说,族群间是有族群边界的,即所谓的“自有种类之分、界限之隔”。但是在利益驱动之下,这些族群会联合起来,“声势相因”,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但在患难的时候,互不相顾,族群认同感消退。这符合族群认同“工具论”或“情境论”的观点,即:在不同的社会情境,或者为了本族群的利益,族群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族群认同,以求得本族的生存与发展。
在明清时期,还有一些族群打着畲、瑶族群的旗号,如谢志珊、蓝天凤等领导的“桶冈之乱”,他们自称为“盘皇子孙”,目的就是为了纠集各路不同人群:“其大贼首谢志珊、蓝天凤,各又自称‘盘皇子孙’,收有传流宝印画像,蛊惑群贼,悉归约束。即其妖狐酷鼠之辈,固知决无所就;而原其封豕长蛇之心,实已有不可言。”①
再如正德年间,原来迁往南安府的广东移民“称輋为寇”②,在江西本地也有入輋为盗的现象,王阳明称:“及有吉安府龙泉、万安、泰和三县,并南安府所属大庾等三县居民,无籍者往往携带妻女,入輋为盗;行劫则指引道路,征剿则通报消息,尤为可恶。”③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许多无籍者“入輋”后成为畲民,这些“入輋”的人群常常被官方视作“盗”。前文笔者曾论述,峒与非峒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受到国家的控制,而是否入籍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在官方视野中,不受国家控制的作乱就是“盗”,没有版籍的移民往往与化外之民没有太大区别,而在南方,官方又往往以“畲”“瑶”“峒”等称谓泛称这些化外之民。笔者推测,这些号称为“輋”,一方面可能是自称,由于畲瑶历来号称本族群具有“免差徭”的特权,一些人为了逃避赋役,或者如上述所说,为了互相得到支援联络,于是自号为輋,而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汉人;另一方面可能是他称,由于汉人迁徙到偏远地区后,族群得到发展,生产生活方式受到当地土著影响,其文化发生部分变化。由于这些人群地处偏远地区,官方往往控制不到,而当这部分人作乱时,官方将这些“失控”的人群统一归为“輋”人,至于这些人的族源,对于官方而言,已经不那么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明清时期闽粤赣一些地区的“移民”“畲”“盗贼”三者有着相当微妙的共生关系。
三、边界的消失:宋至明“畲寇”减少的原因分析
在宋元时期,许多南方非汉族群的动乱,均冠以“畲乱”“畲军”“畲寇”,随着畲汉融合以及畲汉边界的模糊,在明代以后,这种以“畲”作为寇乱主体的记载减少,而取而代之的是族群特征不明显的“山寇”。这种变化从侧面反映了族群边界的模糊,也说明大量畲民在认同上发生转变,逐步融入汉族之中。
宋元时期,朝廷对畲民武装进行剿抚,导致“畲军”“畲兵”“畲寇”大量减少。由于招抚畲军既能平息叛乱,又能加强统治,所以朝廷尽力招抚。《元史》记载至元十六年,蒲寿庚请求朝廷下诏并得到应允:“诏谕漳、泉、汀、邵武等处暨八十四畲官吏军民,若能举众来降,官吏例加迁赏,军民按堵如故。以泉州经张世杰兵,减今年租赋之半。”①元代苏天爵的《元文类》载:“福建之畬军则皆不出戍他方,盖乡兵也。”②《元史》称:“福建之畲军,则皆不出戍他方者,盖乡兵也。又有以技名者曰炮军、弩军、水手军,应募而集者曰答拉罕军”。③可见畲军用于地方防守。除此之外,朝廷也将其作为征服其他溪洞的工具,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元朝王恽的诗写道:“蛮陬溪洞既荒远,颠枿其间不无孽。畬军新附用得宜,以彼为攻易摧折”。④
一些不接受招降的或复叛者,则逃入山洞,继续“依阻山险”,“负固”顽抗,最终招致朝廷的新一轮镇压。如《元经世大典序录》记载:“至元十六年五月,降旨招闽地八十四畲来降者。十七年八月,陈桂龙父子反漳州,据山寨,桂龙在九层际畲、陈吊眼在漳浦蜂山寨、陈三官水篆畲、罗半天梅泷长窑、陈大妇客寮畲,余不尽录。十八年十月,官军讨桂龙,方元帅守上饶,完者都屯中饶,时桂龙众尚万余,拒三饶,寻捕得其父子斩之。”⑤再如至元十九年,“黄华急攻建宁……华走江山洞,追至赤岩,华败走,赴火死。”⑥平和县乌泥洞“在坂仔。岩险异常,相传畲寇李志甫据此作乱,四帅征之,兵不能进。陈君用侦知洞后有间道,乃募壮士数十人潜人,猝遇志甫,地狭,兵器不得用,因手格杀之,余党悉平。”①
明清以后,随着族群的融合,华夏族对边陲各族群有更深入的了解,一些寇乱不再以“畲”来泛称,而有更细的划分,如林大春在《论海寇必诛状》将南方寇乱分为三类,其文称:“为今岭海患者,不过曰山寇、海寇、倭寇三者而已……夫是三者,势相倚而祸相因者也……夫山寇非他也,盖多村里恶少,与夫愚蠢编氓,非有奇谋异能,特见间而起。又其所居,多负险易以伏匿。急之则啸聚岩谷间,州郡亡命闻而争奔走焉。”②可见,山寇主要是“村里恶少”“愚蠢编氓”以及“州郡亡命”组成,这些人很大一部分人应该是汉人,其因为“聚岩谷间”而被统称为山寇。在统治者眼中,这些山寇应该与历来“啸聚畲峒”的化外之民无别。只不过是无法具体区分族群差异,所以以山寇称之应该是比较恰当的表述。明代何乔远在《闽书》中则对明中叶以来福建“寇乱”发展变迁进行论述,他说:
闽中成、弘以前,山寇多而海寇少;正、嘉以来,山寇少而海寇多。国初,州县仍宋、元旧,山林深阻,荆棘蒙密,奸宄时窃发,至乎蔓不可图。今其地芟夷之后,悉置县司,即欲啸聚,靡所藏寄。此山寇多少所由异也。③
这段文字说明了寇乱由山变海变化趋势,同时对山寇变少原因作了解释。关于山寇变少的原因,或许与国家权力深入山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逐渐加强有关,随着归入版籍的人变多,山寇自然变少。《世烈录》记载了明朝潮州等地受到山海之间的贼寇骚扰的情形:
潮郡自正统、天顺以来,海寇山瑶,迭出劫掠,陷城杀吏,肆毒连年。本官按行郡邑,抚戢残余,励志救民,奋身犯难,初平海寇,继讨畲蛮,累破峒贼于程乡、黄岗,穷捣窘巢于上杭、安远,兵威所及,如火燎毛,遂使疮痍得反衽席,老弱得保天年④
所谓的山寇是哪一些人?就汉人角度观察,无非是住在山里为乱的,其常常为陌生人,至于这些陌生人是哪个族类反倒不太重要。当时普遍的情况是,近于郡县城镇地方多是汉民所移住定居,而长期居于乡野山谷之间的则多为非汉族住民。因此,有学者认为,山寇与畲、瑶之间必有联系,陈森甫曾指出,直到明代,有许多山寇为乱与瑶、畲等少数民族活动有很大的关系。①谢重光认为,明代闽粤赣地区民变的主体有部分人是客家百姓,也有畲族人民。②李荣村、林天蔚等学者认为,这些非汉族群动乱的主要原因是地方的经济政治无法改善。③也就是说,地方经济政治结构的变动(主要是对非汉族群经济社会的冲击),造成了非汉族群对社会做出反应,在官方或汉人的表述中,就是“寇乱”。
康熙《漳浦县志》则将当地的“寇”分为五类,其文写道:“(漳浦)地连潮广,蛮獠杂居,反叛不常,为寇一;扶桑日出,风烟咫尺,倭入内地,为寇二;崇严巨浸,林木啸聚,潢池窃弄,山海之际,伏莽为灾,为寇三,为寇四;更姓易朔,妄指义旗,借衣冠为盗薮,流毒乡里,为寇五。”④可见,在明清漳州地区的寇乱的成分有五大类:一是“蛮獠”,主要是指畲瑶等族群;二是倭寇;三、四是山海之间的寇,可称之为山寇、海寇;五是指由豪强发起,旨在反抗朝廷的叛乱者。《平和县志》:“邑(平和县)居边徼,寇盗滋多;地连瓯粤,蛮僚难化。况崇岩巨浸,林木啸聚,山隅海曲,伏莽多虞乎!至于乘时藉势,妄指义旗,又有倚衣冠为盗薮,以荼毒乡里者,无怪乎叛乱相寻。”⑤明清仍有“倚衣冠为盗薮”者,应该是地方地主组织发动的一些地方叛乱,而非完全是底层百姓的自发叛乱。
在元代,将一些族群身份不是特别明确的寇乱,常以“畲寇”称之;在明代,常将其统称为山寇、山贼等。当然,明清山寇并非全是非汉族群的寇乱,也可以指其他族群叛乱者。正如吴震方在《岭南杂记》称:“明通志凡山寇皆谓之獠,盖山寇亡命乌合,未必种传,无从究考。”⑥明代以来,这些“盗寇”,在血统上不好辨认族群属性,所以官方笼统将其划入山寇、峒寇一类,强调的是生活地理位置以及不受政府羁縻,荒忽无常的共同特点。①
因此,针对文献中出现的“山寇”,应该分析其出现的具体语境。有时候山寇特指畲民,如杨澜《临汀汇考》:“今汀中畲客所占之地……想郡治初开时,乡村平衍处亦都如是。故《唐书》谓汀郡多山寇也。”②山寇在此应指特指“畲客”或其先民。再如乾隆《汀州府志》载罗良:“元至正间,散资募士,捕杀漳州山寇。”③漳州山寇就是李志甫。
关于史志对李志甫记载的分歧,谢重光先生认为:“可能缘于李志甫本是汉人,但所聚之众有汉人、也有不少是畲民,李本身也已畲化,故或笼统称之为‘反贼’‘山贼’‘南胜贼’,或迳称为‘畲贼’。”④我们认为畲倒是一种名号,而不在于族群内部血统成分之多寡,也不在于是否被畲化,而在于统治者对其看法,入峒则为畲,出峒则为汉,这就是族群边界的解释。
元明之间,畲寇减少在文献表述上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两个文献对比来说明,一份是元代陈志方《元右丞相晋国公罗公墓志铭》,其文称:
值元季之乱,每叹曰:大丈夫当扫除天下,安集四境,今举世纷乱,安事毛锥为也。因廪募乡民从大将,击平南胜畲贼李志甫,功居最,奏授长汀尉,未几,畲寇吴仰海、江西贼詹天骥发公奉命讨平之,陞漳新翼万户。至正十三年,福安贼康子政犯福州,帅宪两府以礼币致公……其后,南胜畲寇陈角车、李国祥,安溪贼李大,同安贼吴肥,潮贼王猛虎,江西贼林国庸,先后窃发。西林贼陈世民攻陷南诏、长汀、龙岩、漳浦诸邑,公悉削平。降其众,复其邑。⑤
我们再来看明代《闽书·罗良传》的表述,其文曰:
罗良,字彦温,负俊才,善谋略。至正四年(1344年),漳贼李志甫围守将战败,良倾家募兵,从江浙平章百花讨平之,以功授长汀尉。十一年(1351年)……贼吴仲海等杀千户福留,陷南胜等县,对比以上两则材料,前者将李志甫、吴仲海记载畲贼、畲寇;后者则写为漳贼、贼等。这种表述的微妙变化,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元代以后,大量的“畲军”被安排入政府统治,人数大量减少;二是“畲”的内涵在元明之间发生变化:即元代凡是寇乱的,均可冠以畲寇;明代随着畲的进一步明确,畲更倾向于指代具有盘瓠信仰的非汉人群。到了明中叶,王阳明巡抚南赣,对闽粤赣地区“畲乱”进行治理,特别是大量新县的设立,闽粤赣地区许多地方由“盗区”转为“治区”,更多的畲民转化为新民,明中叶以后,文献中就更少有关于“畲寇”的记载。本书将在下一章对此进行论述。
第三节 小结
本章论述了宋元以后至明初期闽粤赣地区畲汉边界移动的情况,主要论点有:
(1)根据官方的族群分类方法,常将边陲地区不纳税服役的非汉民族称为“盗”“贼”“寇”等,是否成为国家管控范围之内的居民成为“贼”与“民”的重要区分标志。宋元常出现有关“畲军”“畲丁”“畲乱”,其中“畲”作为一种蛮夷语境被表述,其不应该认为完全是种族血统的概念,而应该将其视为一种文化的范畴。也就是说,“畲军”“峒丁”中的畲或峒,均是官方对南方地区非汉族群笼统的概称。畲乱中显示了华夏边缘的移动过程。从官方的角度来看,其将参加动乱视为化外之民,目的在于区别“贼”与“民”、“良”与“莠”,显示的是官方心目中异族的移动过程;从叛乱当事人角度来看,他们打着“畲”的旗号,目的在于壮大声势、联合更多民众参与斗争,显示的则是主观上向“异族”认同的转变。以上两个共同制造了“畲”在宋元时期从内涵到外延的转变。就此而言,如黄华、李志甫等所谓的“畲寇”“畲贼”“畲军”,其被认为是畲,与其从血统、种族上去寻找根源,不如从文化上去说明其成因。其作为非汉民族,更多的是官方,以汉人为代表的政府认为这些人为未开化人群之一,称之为畲,有贬义的意思。所以既可以称之为畲贼,又称之为山贼,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是一种文化的称谓,而非完全以血统来区分人群。
(2)随着闽粤赣地区族群频繁互动,族群边界也显示出变化不定的状况,具有流动性。既有畲民通过获得版籍成为编户齐民的情况,也有汉人通过“入山洞”,脱籍成为“畲”“瑶”族群的情况。
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历史情境下,社会中出现了一股反社会的潜力,并在宋元时期迅速形成合力,爆发了空前的动乱,畲乱在东南一地尤为明显。畲乱引起了朝廷的重视,因而在文献上留下了大量与之有关的记载。“畲乱”本质上是社会秩序破坏下,华夏心目中异族迁移中的体现。也就是畲乱与盐寇、地方寇(潮寇、广寇、赣寇)是一致的,只不过冠以异族的名号。与其将其视为种族区别,更多的是文化上来考量。也就是说畲军、畲寇、畲贼不一定是溪峒民族,有些人打着“畲”的名号起兵,此其一;另外华夏视野中,将一些寇乱冠以畲名,是化外之民的象征。
(3)族群的文化认同是族群边界的一个重要指标。当各族群刻意强调族群间的文化差异、文化认同迥异时,族群边界越明显;而当族群不自觉淡化族群间的差异、文化趋同,族群边界逐渐模糊,直至消失或漂移。
这种族群边界的移动还可以通过政治文化教化来实现。在地方动乱中,各个族群被卷入其中,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族群或联合,或对抗,动乱深刻打上族群斗争烙印①。中央政府通过军事压制、设置县治、加强教化等手段进一步加强对闽粤赣地区的控制,使“盗区”变为“治区”,一些畲民或者逃避战乱或者被军事驱赶迁徙其他地区,这对畲民迁徙起着推动的作用。另外一些畲民仍生活在闽粤赣地区,他们被编入版籍,成为纳税服役的王朝子民。族群边界在动乱中不断移动,总的方向是华夏化运动螺旋式、曲折前进,宋元以来的畲乱使得“畲”作为一个族群登上历史舞台,进入人们视野,为畲族族群社会发展与变迁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 国家认同与畲汉边界的流动
两宋时期,福建人口迅速增长①。户口的增加一方面是经济发展、人口繁殖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一些非汉人群进入国家版籍的结果。
一、族群边界流动:“畲入汉”与“汉入畲”
有关“畲”汉身份转化,在史料多有记载。刘克庄《漳州谕畲》一文描述了漳州地区的畲人不堪“贵家辟产”“豪干诛货”以及“官吏征求土物”而“怙众据险,剽略省地。”在理宗景定三年(1262年),国家派兵对畲民采取“剿捕”策略,然而效果不佳,于是选派卓德庆前往治理畲乱,卓德庆采取招抚策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漳州谕畲》写道:
侯榜山前曰:畲民亦吾民也。前事勿问,许其自新。其中有知书及土人陷畲者,如能挺身来归,当为区处,俾安土著;或畲长能率众归顺,亦补常资。如或不悛,当调大军,尽鉏巢穴乃止。命陈鉴入畲招谕。令下五日,畲长李德纳款。德最反复杰黠者。于是西九畲酋长相继受招。西定,乃并力于南,命统制官彭之才剿捕,龙岩主簿龚镗说谕,且捕且招。彭三捷,龚挺身深入。又选进士张杰、卓度、张椿叟、刘口等与俱。南畲三十余所,酋长各籍户口三十余家,愿为版籍民。二畲既定,漳民始知有土之乐。①
“畲民亦吾民”说明是官方在招抚畲民中采取的一种外交辞令,其中又隐含着华夏民族与非华夏民族不平等地位。如刘克庄在《送方漳浦》也写道:“颇闻送者诗盈轴,我有樵歌子试听。岩邑虽然人所畏,畬民均是物之灵。二升饭了官中事,一字廉真座右铭。见说守侯如召杜,断无走吏至公庭。”②刘克庄以山歌的形式送方漳浦,其中一般认为生活在岩邑(险要的城邑),一般人视之为畏途。“物之灵”用典于《尚书·泰誓上》,其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③畲族应该被看做“物之灵”。侧面反映了当时很多人将“畲”视为非人的看法普遍存在,这是一种族群边界的象征。
一般来讲,非汉民族在华夏化进程中有三个主要特点:
一是畲民内部的汉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具有不平衡性。也就是说,汉化常常从内部集团的上层开始,从刘克庄文中我们发现,畲民的华夏化是从“知书”“土人陷畲者”“畲长”开始的。在明清以后仍是这样,如《天下郡国利病书》描述福建“猺人”时称:“楚粤为盛,而闽中山溪高深之处间有之。漳猺人与虔、汀、潮、循接壤错处……今酋魁亦有辨华文者。”④
正如当年楚、越等国华夏化运动也是从上层开始⑤一样,畲民的华夏化也是从首领开始,所谓的“今酋魁亦有辨华文者”,说明畲族族群首领开始接触汉字并通汉语,为本族畲民的汉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是畲民汉化具有反复性,从中也体现了族群认同工具主义的特性。“畲长”之所以被认为是“最反复杰黠者”,说明畲民在不同社会环境下,根据利益需求,选择不同的认同策略。
三是反映了非汉民族华夏化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在国家意志的强力推行下,部分非华夏民族在强势的华夏文化中或者被迫,或者自愿融入华夏族中,另外,还有部分采取不合作或逃离的策略,他们仍然保持“蛮夷”身份。但是,随着华夏化进程不断进行,在官方“且捕且招”的政策下,将有越来越多的蛮夷融入华夏族中,这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一个大的发展方向与历史趋势。
汉人进入畲区而成为畲民也是当时比较常见的历史现象。在宋代不仅有百姓“入畲”“陷畲”,连一些官员都“隐畲”以求庇佑。如刘埙的《隐居通议》记载南宋赵必岊入畲的情况:
赵必岊,字次山……乡寓公吴允文浚奉密诏以江西招讨使举义反正,结约次山协谋兴复,战不利。允文奔漳州为都督文丞相天祥所杀,次山解兵隐汀州之畬中,踰年以疾终。①
汉人逃入畲洞,即所谓的“边人逃入蛮峒”,大部分原因是为了逃避赋税。《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时,江西行省左丞高兴曾上书请旨言:“江西、福建汀、漳诸处连年盗起,百姓入山以避,乞降旨招谕复业。”皇帝下诏皆以应允。②在元代,由于各地畲乱不断,百姓入畲者比前代更多,如《元一统志》记载道:
汀之为郡,山重复而险阻……西邻赣,南接海湄。山林深密,岩谷阻窃,四境椎埋顽狠之徒,党与相聚,声势相倚,负固保险,动以千百计,号为畲民。时或弄兵,相挻而起,民被其害,官被其扰。盖皆江右、广南游手失业之人逋逃于此,渐染成习。
武平南抵循、梅,西连赣,篁竹之乡、烟岚之地,往往为江广界上逋逃者之所据。或曰“长甲”,或曰“某寨”,或曰“畲峒”,少不如意,则弱肉强食,相挺而起。税之田产,为所占据而不输官。③
在元代汀州“椎埋顽狠之徒”,数量众多,他们“党与相聚,声势相倚,”且“号为畲民”,说明他们中许多是打着“畲”的旗号,弄兵作乱。这类“畲”数量增多的原因是“江右、广南游手失业之人逋逃于此”,这些人原本并非“畲”民,其在汀州所占之地被称为“长甲”“某寨”“畲峒”,被视为化外之民。由此可见,此时族群之间的界限模糊不定,在社会动乱的背景下,畲作为一类人群,其势力得到较大的发展。在元代士大夫眼中,此类逃离本乡聚集于深山幽谷间负隅抗拒官府者,也被称为“畲民”,明显的例子还有“畲民丘大老集众千人寇长泰县”①。
在明代前期,闽粤赣的畲族势力仍较强大,入畲的汉人较多。王阳明治理闽粤赣地区“畲乱”时,曾记载有一些汉人被煽动蛊惑入畲的情况:
其大贼首谢志珊、蓝天凤,各又自称“盘皇子孙”,收有传流宝印画像,蛊惑群贼,悉归约束。即其妖狐酷鼠之辈,固知决无所就;而原其封豕长蛇之心,实已有不可言。②
也有一些是无籍汉人避役入輋的如:“吉安府龙泉、万安、泰和三县并南安所属大庾等三县居民无籍者,往往携带妻女,入輋为盗。”③还有原本非畲的百工技艺游食之人入輋的如:“其初輋贼,原系广东流来。先年,奉巡抚都御史金泽行令安插于此,不过砍山耕活。年深日久,生长日蕃,羽翼渐多;居民受其杀戮,田地被其占据。又且潜引万安、龙泉等县避役逃民并百工技艺游食之人杂处于内,分群聚党,动以万计。”④
以上描述的多为江西一带畲族情况,闽粤其他地方也类似,如“闽潮人叛逃流亡,就地垦荒者谓之畲蛮。”⑤到了清代,仍有此类人员:“雷公岭,距县北(饶平县)三十五里,层冈叠嶂,为潮惠二县(恐为州之误,笔者注)之界,奸民逋赋役者,辄借口邻封,彼此窜避,或托为猺獞逃化外。”⑥“托为瑶僮逃化外”说明畲汉边界在流动。
李调元的《南越笔记》有关于汉人由伪猺变为真猺过程的记载,其文称:乐昌有伪猺,多居九峰司诸山。其始也苦于诛求,以其田产质客户,窜身猺中,规免旦夕,久之性情相习,遂为真猺。相率破犯条要,恣行攻劫,为地夫之害,即善猺亦且畏之。⑦
显然,文献中关于的“畲”“輋”“猺”的记载,其并非作为纯粹的种族区分,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身份或文化身份的区分。也就是说,官方或文人把“入畲”的汉人——这些汉人不管是“为盗”,还是“避役”——均称为“畲民”,目的是用其笼统地称呼那些脱离编户、与政府不合作的各种人群。①
由此可见,“畲民”的形成不仅仅是自我认同的结果,官方或主流文化对其社会定义同样重要。也就是说,有一些畲民认同,乃至“假托”自己为“畲民”;而另外一部分则是官方以单方面标准判断其是否为“畲”。可见,“畲/汉”边界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既可以“入畲为寇”,又可以“籍峒为民”,从而实现“版籍/无籍”和身份的相互转化。②
二、国家认同:版籍作为族群区分的意义
国家常将获得版籍作为区分“溪洞”与“省民”或“畲”与“非畲”的重要标准,其背后体现的是文化认同的因素。国家之所以重视版籍,是因为社会的安定需要对边境进行控制,需要对户口进行管理。如明万历《福州府志》描述洪武到正德到万历年间二百余年户口无所增长时,作者论述道:
夫国家治平,晏然无事,二百年于兹,即前古未有矣……是故豪宗巨家,或百余人,或数十人,县官庸调,曾不得征其寸帛,役其一夫。田夫野人生子,黄口以上,即籍于官,吏索丁银,急于星火。此所以贫者益贫,而富者益富也……不毛之宅,无职事之人,终日美衣甘食,博弈饮酒,市井嬉游,独不可稍举古人以末之政,以纾力本者之困也耶?为今之计,欲使户无匿丁,则莫若凡讼于官者,必稽其版,凡适四方者,必验其襦,则户口可核。户口可核,则赋役可均。不惟足国裕财,驱民于农,亦无便于此者矣。③
明代户税制度不完善,豪宗巨家和一些百姓逃避户税,造成了国家的户税危机,所以要求,欲使户无匿丁,加强户籍的审核,如此可以均赋役,足国裕财,驱民于农。从这个分析,国家十分需要将一些可以纳入版籍的百姓纳入,这是国家安定的重要基础。将畲民纳入编户齐民可以证明一个地方官的政绩,也说明地方教化、文明的象征。
一些百姓如果不入版籍,不纳赋税,也会被视为化外之民。直到明末,所谓的化内化外并不一定指的是少数民族,而指的是有没有接受王化,如冯梦龙的《寿宁待志》称:
至磻溪、西溪二处与泗洲桥素通姻盟,互相应援,一呼百集,目无官府,欠粮拒捕,无所不至。余惩顽民陈百进之事,乃请详上台……而收化外之民于化内也。①
实际上,在早期蛮族华夏化过程中,也常提及纳税情况,如应劭记载长沙武陵蛮称:“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②认为,他们不向中国官府纳赋税,说是因其父盘瓠对中国有功,母亲又是帝王之女事实上,应是当时朝廷尚无力统治这地方的山间人群。《南史》中记载荆雍州蛮为盘瓠之后,这部分蛮夷顺附者向朝廷纳赋税,但无杂税与劳役。也有部分汉人逃入蛮夷,群起为盗,“结党连郡,动有数百千人”③。这些逃入蛮夷中的汉人,逋负钱粮,也被统治者视为化外之民。因此,赋税与其作为经济特征,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特征:是判断汉与非汉的重要标准之一。
再如宋代刘克庄为宁都县丞赵必健写的《英德赵使君墓志铭》称:剧贼陈淮西、罗洞天聚众出没赣、汀、潮、梅数州郡,檄令合官民兵讨之……罗畬峒首黄应德久负固,亦请出谒,公延见,享劳之,感泣辞去。已而邵农至其所,应德曰:“吾父来矣,率妻子部曲罗拜,愿附省民输王租,迄公去,溪峒无反仄者。”④
以上记载中的罗畬峒居民应该是畲民,是否“输王租”,成为“省民”与“峒民”的主要区别之一。郭志超等认为唐代之前畲族尚无纳税,南宋末年才有少部分畲族承担封建赋役,宋元时期畲民入籍和承担赋役并没有大范围进行,而直至清代,畲民才在真正意义上承担封建赋役。⑤从畲民的纳税服役的范围及普遍性情况,可以看出,畲民不断被卷入华夏化进程中,编户齐民身份的获得以及对国家义务的履行,对畲民的国家认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明代一些畲族首领入朝贡献,这种象征性的仪式在国家看来是臣服万民,民心归顺的国家重大事件,因此被记录在史籍当中。如明代《广东通志》记载道:
(永乐五年1407年)冬十一月,畬蛮雷文用等来朝。初,潮州府卫卒谢辅言:海阳县凤凰山诸处畬,遁入山谷中,不供徭赋,乞与耆老陈晚往招之。于是畬长雷文用等,凡百四十九户,俱愿复业。至是辅率文用等来朝,命各赐钞三十锭,彩币表里绸绢衣一袭,赐辅、晚亦如之。①
可见,是否纳税服役是朝廷判断一个地区人群“化内”或“化外”的标准。如崇祯《兴宁县志》曾对当时将“徭蛋”称为“夷狄”的社会偏见进行反驳,其中主要的理由就是当地“徭蛋”获得版籍,并纳税服役,其文曰:
按吴志名徭蛋曰夷狄,令人愕然。求其说而不得。此非山戎氐羌之比,错居中土,衣冠与世同,无复椎结之习,一耕于山,山有粮,一渔河,河有课。既籍其名於版,子孙数十世势能徙居塞外矣乎?出入同乡井,又能区分限域矣乎?王者无外,听其蠉飞蠕动于穹环之间,亦齐民矣。已恶得而狄之。②
明代《广东通志》描写潮州府畲、瑶时称:
民有山輋曰瑶、僮,其种有二:曰平鬃,曰崎鬃。其姓有三:曰盘、曰蓝、曰雷。依山而居,采猎而食,不冠不履,三姓自为婚,有病没,则并焚其室庐而徙居焉。俗有类于夷狄,籍隶县治,岁纳皮张。旧志无所考。我朝设土官以治之,衔曰輋官,所领又有輋,輋当做畲,实录谓之畲蛮。③
从以上记载看出,作者认为輋又称瑶、僮,习俗“有类于夷狄”,即认为畲民与夷狄习俗有相同的地方,从遣词造句中又说明畲民不完全与夷狄相同造成这种认识的根本原因在于“籍隶县治”,这再一次说明国家版籍制度的施行,使得畲民慢慢进入华夏边缘之内,版籍也是判断畲汉边界的一个重要标准。
第二节 “贼”“民”分类与宋代以来的“畲乱”
宋元以后直至明中叶,闽粤赣交界地区一直是族群动乱的中心区域,体现在文献上就是大量有关于“洞寇”“畲寇”“畲军”“畲贼”等记载的出现。
新中国成立以来,畲族动乱(或畲族起义)成为畲族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由于受到当时学术背景的影响,畲族史研究带有明显的“政治意识”,如畲族社会历史调查中,过多地强调阶级斗争内容,从而限制了畲族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①笔者认同王学典先生关于50年来的农民起义研究的反思,即在“学术语境中”对社会动乱进行研究。②近年来,闽粤赣地区的社会动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唐立宗、黄志繁、饶伟新等学者做了有益的探索,给本文研究带来了不少的启发。③笔者从族群边界的角度分析后认为:宋元大量出现的“畲乱”记载,是官方单方面的文化表述,“畲”经常是作为一种“文化标签”,“畲”与“非畲”并非只是纯粹血统的“种族”区别。宋元时期,关于“畲乱”的大量描述,既体现了官方“贼”“民”的族群分类,也可以观察“畲”、汉族群边界的流动情况。
一、畲瑶“盗”“寇”“贼”族群印象的由来
宋明时期闽粤赣地区“寇乱”频发,地方社会危机重重,该地区的社会动乱有其自然、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这是一个多种因素叠加、社会矛盾积累到某个临界点时,而后矛盾相继爆发的特殊社会现象。正如《汉书·贾谊传》所称:“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④从文化学的角度,宋元以来的“畲”乱,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再创造的结果,“寇乱”显示了当地族群社会文化整合的情况。
随着以汉人为代表中央王朝日益深入南方地区,南方的非汉族群被定性为“蛮夷”话语之中①,文献中出现的有关“峒”“蛮”“獠”“猺”“獞”等均是这种“华夷之辨”族群话语下的产物。特别是在汉与非汉之间的族群边界冲突发生时,更进一步加深了华夏族对“蛮夷”的“贼”“寇”身份的印象。那么,这些“贼”“盗”“寇”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话语权掌握在统治者手中,因此“贼”“寇”其实就是官方单方面的文化表述的产物,官方的利益成为评判标准的核心。在官方的话语系统中,“贼”“寇”与“民”相对,是合法社会秩序以及帝国权威的挑衅者。“贼”“寇”本有区别,清代梁章钜在《称谓录》中称:“奸宄。《书传》:‘劫人曰寇,杀人曰贼,在外曰奸,在内曰宄。’……盗,《左氏》定公八年经注:盗,谓阳货也。疏:盗者,贱人之称也。”②
随着历史的发展与演变,“贼”“寇”“盗”作为对动乱者的贱称实际上是相通的,可视为一种泛称,专门用以指代社会秩序的叛乱者。统治者用“贼”“盗”“寇”的文化标签来定义社会中某一特定族群,并以此区别族群间“良”与“荞”的边界。王朝以文化阶序来区分“贼”“民”之间的族群边界,其目的在于:宣扬文化等级差异,防止更多民众加入“贼”之中,同时增强普通百姓内部的文化认同感。从历史上看,在多数动乱中,不仅由官方派兵平盗,在民间中,也有许多士绅阶层自发组织乡村民间武装对“贼”“寇”进行剿杀可见,族群边界的区分,有助于维护王朝的统治秩序。如《宋史》载:“(至元十四年)五月……(张)世杰乃奉益王入海,而自将陈吊眼、许夫人诸畲兵攻蒲寿庚,不下。”③
而清代杨澜的《临汀汇考》亦载其事:“宋绍熙中,上杭峒寇结他峒为乱,州判赵师璱擒其渠魁。而宋季张世杰会师讨蒲寿庚,有许夫人统诸峒畲军来会,汀畲亦在军中。”④
这里的表述比较微妙:“峒”民为乱称之为“峒寇”,参与张世杰军队者则称之为“畲军”或“畲兵”。可见,“军”“兵”与“寇”之间的区别,显然是根据是否符合官方利益的标准而作评判的。
刘志伟曾指出“蛮夷”之所以常被冠以“贼”“盗”“寇”蔑称,与其“不受教化”“不税不役”“化外之民”的特征有关系,而所谓“蛮夷”,不仅是一个血统的范畴,更是一个文化和社会的范畴。①对于王朝而言,纳税服役的政治意义远比经济意义大,是否承担赋役、履行国家义务,成为国家区分“民”与“盗”的重要指标。②在一些国家政治管理鞭长莫及的偏远边陲地区,其居民(主要为非汉人群)无法做到或不愿意去履行国家义务,国家因此将这些居民与“盗联系起来”。这种思想体现在文献上,就是常将地理上的边陲与族群“化外”的性格联系起来,即认为一个地区的民风或族群性格往往与地理环境有关,地理越蛮荒险远的地方,居民可能越难教化,也更易发生动乱。
福建山区往往为盗贼渊薮,宋代的周必大称:“七闽地狭,人众甚艰苦,其民亦重犯法,然东际海南接炎峤,西入赣境,风潮出没之奸,山谷集之盗,控御失所,或害吾治。”③到至元年间便有人认为:“闽地山谷之间往往乌合为寇”。④《元一统志》也称:“汀之为郡,山重复而险阻,水迅急浅色涩。民生其间,气刚愎而好斗,心偏迫而浅,亦风土使然。⑤
直到明代闽粤赣仍被认为是畲民聚集的地方,何乔远《闽书》称:“江西之南赣,福建之汀漳,及广东之南、韶、潮、惠,湖广之郴桂,境壤相接,峻谷深山,岭岫缀连,輋贼窟穴其中。”⑥明代时期,上杭溪南地区作为“盗窟”尤为著名,明代兵部尚书杨博称:“闽广之贼所倚重者数巢穴耳,其大者在福建则有上杭峰头、永春蓬壶……”⑦明人郭造卿在《闽中分处郡县议》亦云:
“然近日三省山寇数十年一作,及剿有数十年之安,惟三图百余年,无秋冬间不啸聚,屡扑而不驯服,其山林险密,尤异他区,邻省山寇共推之为主耳。”①
清代杨澜在《临汀汇考》称:“南赣地连闽广,山谷深阻,盗贼易为巢穴。”②《肇域志》记载漳浦县大帽山:“在县北百里,山大而峻……南距檺林延袤数百里,深林丛莽,群不逞多啸聚,其间迤东通溪埔山,菁畲猺獞时出为寇,乡导而直北。”③可见在闽南地区的漳浦大帽山、云霄檺林这些地方“深林丛莽”,成为“盗贼”啸聚的地方,在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人是“菁畲猺獞”,也就是畲民。
除了福建外,广东、江西等地也是畲、猺、峒獠出没之地,如史称“在广东则有猺峒,在江西有輋巢”④,这些族群一般被认为是危险的、狡猾的人群,如元末黄潜记载郴州百姓害怕与当地非汉族群交往,“洞蛮猺獠往来民间,人惮其强猾,莫敢与相贸易”。、⑤这里“民间”应该指的汉人社会,“人”也指汉人,当然这种记载是单方面的反映的是汉人对这些猺獠的看法,我们或许可以推测,猺獠在面对强势的汉人,比上述的汉人更为“忌惮”。
这些非汉族群在汉人眼中之所以是危险群体,与他们时常外出劫掠有关,因此也被称为“盗贼”。明人梁朝宗描述江西龙泉等地有“猺、輋、獠”,这些居民僻居山区,不纳赋税,而且在灾荒之年劫掠百姓,如“龙泉,吉左僻邑也,控郴衡而引虔,猺、輋、獠、恶少出没之地,岁登则自食其力,歉则群聚不逞之徒,大肆劫掠刈人如草菅。”⑥
輋民冠以“贼”字,可见当时畲民的族群印象被打上“盗寇”的烙印,正是有了这种族群印象,所以在文献中谈及闽粤赣边等地区的非汉族群时,常以好斗喜乱来形容其性格,如“畲丁①溪子善惊好斗。”②又如“畬丁洞猺喜惊而嗜斗”③。
实际上,“民”和“贼”的身份并不一定是固定不变的,二者是可以转化的。王慎中在分析上杭县的溪南盗风日炽时,对“民”化为“盗”作过精彩的论述:
风气所限,非性故然,长子育孙,生蕃齿盛,耳目熟习,莫改厥德,少视其壮,壮视其老,蹲危逗幽,乃为盗薮。厥有治者,不揆其性,不闵其习,盗视彼民,忿犷堲凶,攻击铲除,如农疾莠,惟惧不残、民不见德,又弗儆威,既狃于习,且偷其生,鸱张螳怒,攘奋踉跄。吏既雠民,民亦毒吏,雠毒两积,交不得已,于是溪南之民,恶声胶固。④
可见,最初“民”“盗”水火不容,但最后仍皆为盗贼所吸纳。足见一个地方文化对族群塑造的力量。
就官方立场而言,“盗贼”界定主要在于人民的行踪官方是否难以掌握,衡量的标准是以平民的活动是否违法脱序作判别。在古代农业社会价值观念下,只要在土地上安分守己,就不是“盗贼”,否则皆将与“盗贼”无异。“倘若硬性将传统农业社会价值观念,桎梏在逐渐转向于商品经济流通的社会,自然官方会对流民、移民的增多而感到处处皆‘盗’,在此情况下,社会经济的变化造成南赣地区的盗增并不使人意外。当然对于现有秩序与体制而言,官方根本不容许‘盗贼’聚众生事,并强力禁制他们‘倡乱’。”⑤
另一方面,华夏化过程中,王朝势力深入非汉地区,引起了当地族群与其他族群,乃至与政府的矛盾。这本来是政府深入非汉族群的居住地,但如前文所述,在华夏视野的“天下观”中,官方先验地认为土地人口均为国家所有,因而,不服从国家安排的就是“寇”或“贼”。直至明清时期,在全国开展丈量土地运动,在闽粤赣地区就遇到畲民的抵抗,如平和县早在明嘉靖中,知县谢明德就已经开始提议实施土地丈量:
仿古经界之法,就现在田土丈量均产,每田一亩随九等高下会计产钱。而总合一郡诸租税、钱、米之数,以产钱为母,别定等则;一例均敷,分隶若干为省计,若干为职田、学粮之属,令诸乡具籍,条别辖内田额四至。①
这说明是一种边界的推移。应该是加强控制,华夏边缘逐渐延伸,导致了非汉民族的反弹。这种丈量田亩等,名义上是为国家丈量田亩,实际上在此之前均为非汉民族居住,应该会造成关系的紧张,如清道光《平和县志》记载:
(康熙)三十七年七月,贼首钟平鼻,吕扁②党也。因县有丈量田亩之议,人情汹汹,知县奔避郡城。平鼻结盗营大丰社,去县三十里,约期劫县,而自为内应,与弟钟二乘间登城伺探,为营兵所觉。县乡壮乘夜薄贼营,贼知平鼻既遁,皆溃,死者甚众。③
第二,由于中国中国古代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本,常将一些从事非农业的人民称为“轻民”,与“重民”相对。清代梁章钜在《称谓录》中称:“重民,《管子》:‘轻民处而重民散’。注:轻民,谓为盗者,重民,谓务农者。”④轻和重相对,区别在于,重民务农纳税,轻民,逋逃为盗。所以从事商业以及经济作物者均认为是社会不稳定因素。
闽粤赣地区自宋代以后,出现的许多“寇”“贼”,清代杨澜曾考证称:
汀郡……乃稽之往代,则有江寇、虔寇、广寇、漳寇、海寇、洞寇、畲寇、盐寇,种种名色,其故何哉?自王绪引兵入闽,汀郡首婴其锋,地为丹徼喉衿。入宋,则盐徒剽掠,往来汀、虔、漳、梅、循、惠、广之地,官不能禁。①
如果将杨澜列举的“寇”分类,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按照族群身份从事职业区分,如海寇、畲寇、峒寇、盐寇,或者是处在山峒、海边的寇,或者是从事盐业、畲田的寇;二是按照“盗寇”来源地区分,如江寇、虔寇、广寇、漳寇。根据杨澜考证,古代汀州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类型的“寇”,一方面是地理缘故,唐末王绪引兵入闽,汀州因其地理位置首先遭遇战乱而引起“寇乱”;另一方面是经济缘故,如盐徒四处剽掠,官府也无法控制。
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唐五代以后,以王绪为代表的中原汉族势力进入福建地区,引起了当地族群结构的变化,族群边界被打破时,族群冲突而造成的社会动乱屡有发生;另外,唐宋经济重心南移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在地方与中央,地区与地区之间以及不同族群之间的资源分配发生结构性的矛盾,由此产生冲突。②特别是入宋以后,朝廷关于食盐制度的不合理③,一些盐徒趁机剽掠,食盐走私盛行引起地方的连锁动乱反应。如王安石《虔州学记》记载:“虔州江南,地最旷,大山长谷,荒翳险阻,赣、闽、越,铜盐之贩,道所出入,椎埋盗守鼓铸之奸,视天下为多。”④《天下郡国利病书》也称:“汀虽非产盐之区,而实为通盐之路,亦江广之咽喉,为闽西外府也。宋时通之,寇且踵作,而必禁之”⑤南宋绍定年间汀州改食潮盐后,《临汀汇考》载:“惟虔州患苦盐法如故。而汀境食米不敷,半仰给于邻境之肩贩,常有遏粜之恐。于是乃许虔民担米来汀,贸盐而返,以有易无,二州民胥赖之。”⑥
可见各地的经济结构具有不平衡的特性。以汀州为例,该地常常有粮食不足的现象发生,粮食不足自然米价上涨,由此又引起寇乱的产生。有史料证明灾荒引发的米价上涨曾导致了闽西洞民寇乱。清代邱嘉穗在《与翁明府、蒋参戎论洞寇书》曾记载了明代上杭来苏三乡的洞寇因为米价上涨而为盗寇的情况:
窃惟来苏三乡,孤悬天末,不幸复界闽、粤间,西接武平,南邻程乡,无深沟高垒以为之限,有幽岩丛菁以为之巢。其二洞,群不逞之徒倚为窟穴,游奕往来,眈眈视来苏如奇货者,盖匪朝伊夕矣。会日秋收颇歉,谷价上腾,加以赣米弗来,潮米莫上,贫民半菽不饱,并日而炊。于是,二洞之亡命为雄者,至敢阴行招纳之私,大肆攻掠之惨,一呼百应,四方驿骚……诚见年荒米贵,平时汀、潮两地所仰给于西江诸郡县者,近则皆禁绝不甚通,非邻封有遏籴之谋,即当事之过虑,不许贩出境外,而皆必给票盘验,以使之嗷嗷望哺,卒不可得;枵腹难堪,呼吁无门,既不敢擅发河东之粟,复谁能代绘监门之图?彼以为死于饥也,与死于盗也,等一死也;与其捐瘠沟中而长为白骨之鬼也,何如游魂釜底而暂作绿林之豪也。是以奋袂攘臂,不得已而出于此。①
日本学者竹村卓二在研究华南山地民族时也指出:“山地民的粮食自给率十分低下,常常碰到饥荒,从而成为引起暴动的原因,这并非偶然。尤其为维持生命不可缺少的食盐供给,是最为紧要的问题。”②
明清以后,在闽粤赣地区出现大量类似“炭党”“矿徒”“菁客”“麻民”“蓝户”“烟民”“菰农”“畲客”“山贼”“棚民”等称谓的流动人口。“寇、客、党、徒、盗、贼”等通称与“民、户”相对,是在中国古代重本抑末经济体系下,对非粮食生产人口的各种称谓。之所以用“贼”“寇”称之,主要是因为这些流动人口往往与土著族群发生冲突,并对正常农业社会秩序带来巨大的破坏。傅衣凌先生曾论述道:“(明清时期)山区带有商品经济关系性质的农民斗争……是和商品生产有较大联系的山区棚民的斗争。他们以蓝户、菁户、麻民、炭党为主体,此外,还有‘矿盗’‘海盗’的参加……他们多是离开土地的外地人……流动性大,人数多”。③傅先生认为,明清时期的社会动乱与这些从事非农业(从事商品经济关系性质产业)人口有极大关系。
这些流动人口,往往是无籍的人口。无籍之民,按刘志伟研究,在明代广东地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脱离里甲体制的“逋负之徒”(或“逃户”),另一类是未归附于里甲体制的“化外之民”(或“蛮夷”)。①饶伟新曾指出,“无籍之民的社会政治处境和‘化外蛮夷’的族群背景”造成了明代赣南的社会动乱。②也就是说,无籍之民与“蛮夷”共同造成了明代闽粤赣地区的社会动乱。如《虔台志》载惠州府三类无籍之民:
以和平(县)为赣、桂、汀、漳之界,乃大帽山、岑冈地也,挂坑障、香炉峰、看牛坪皆比近,故延蔓相及耳。然惠皆良民耶?徭僮淆焉,鱼蛋伏焉,逋亡集焉,盗所由出也。③
说明在广东惠州在数省交界之地不仅“良民”居住,还生活着许多非汉族群,概括起来有三类人:“徭僮”“鱼蛋”“逋亡”。这三类分别指在山为畲、在水为疍,加上逃避赋税的所谓“奸人”,这些人是汉人,但一般将其视为化外之民。这也说明了随着历史的推移,王朝关于南方化外的非汉族群的泛称,从原来的一类(蛮),变为两类(莫徭—卢艇、蛮—疍、居峒砦—家桴筏),变为三类(“徭僮”—“鱼蛋”—“逋亡”)。从这种泛称分类也进一步说明,对华南社会,特别是内部结构,有了更深的理解。“逋亡”群体的存在,是华夷边界摇摆、流动的重要变量。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广东多地有“山寨瑶贼、蛮贼及倭贼”。同时,“东莞、香山等县逋逃蜑户,附居海岛,遇官军即称捕鱼,遇番贼则同为寇,不时出没,劫掠人民。”④这些“逋逃蜑户”在蜑与倭中身份变换,成为地方不稳定因素之一。
无籍之民与“蛮夷”二者有时候是统一的,即动乱中的叛乱者,既是“蛮夷”,又是无籍之民。福建等地的矿冶,聚集了一些非汉人群,有很大一部分是畲民。如永安御史胡琼《忠洛无银矿记》记载峒民从事银矿开采,而后酿祸的经过:
正德癸酉,民有趋利者,诱浙之峒民,拥众突来,未敢恣发。适郡节推郭姓者摄县事,峒民度其老而贪,得厚啗以利。郭欣然许其开凿,且为之陈于总镇。邑人以其地密迩大帽山,为江、浙、闽、广丛盗之会,虑其闻风袭夺,因以为乱,群情惊惧罔措。时佥宪、睢阳蔡公天佑行部至郡,闻之,乃兼程诣县,数郭之罪,率庶民塞而禁之。峒民方以采无所得,及闻蔡来,众遂宵遁。至是,人心始安,皆德于蔡。然闻总镇,祸已基于此矣①
永安出现从浙江而来的峒民,这些峒民或许是畲族。再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广东畲民成为“矿徒”时称:“畲蛮,岭海随在皆有之……近海则通番,入峒则通猺,凡田(土单)矿场有利者,皆纠合为慝,以欺官府,其害僭于甲兵。”又载广东“惠之归善、海丰,广之从化、香山皆有银矿。畲蛮招集恶少,投托里胥,假为文移,开矿取银,因行劫掠。”②
顾炎武的《肇域志》记载:“金溪山,一作金鸡山,在县西北四十里,连接六洞诸山,旧有银坑,湮塞已久,万历中奉旨开采,商估杂还,豪狷假虎,二都山民岌岌惊变。”③六洞也称“六峒”④,二都“山民”主要是畲民。说明由于矿冶开采,一些富商巨族借以占领盘剥,导致明代周边畲民几乎动乱。从这个记载来看,所谓的动乱,经常是由于资源竞争中,畲民的一种自我反应,常常是被迫叛乱的,然而在叛乱之后,统治者常常冠之以贼、寇等称号,形成了一种族群的印象。
二、“贼”“民”转化与畲汉边界的流动
根据官方对“贼”“寇”的定义,“贼”“民”之间具有动态流动性,二者既是对立的,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⑤换言之,有一些当地的土豪和良民在特殊情况下也转化为“盗贼”。如《宋史》记载绍兴十五年(1145年),福建安抚莫将上言称:“汀、漳、泉、剑四州,与广东、江西接壤,比年寇盗剽劫居民,土豪备私钱集社户防捍有劳,有司不为上闻推恩,破家无所依归,势必从贼。官军不习山险,且瘴疠侵加,不能穷追。管属良民,悉转为盗。”①这里说明一些土豪本为本地区防御付出努力,但是地方官存在不作为的现象,使其得不到应有的封赏,致使这些土豪家破财尽,只好从贼;一些处于“山险”地方的良民,由于官方军队无法制约盗寇,这些良民也转为盗寇。
在“贼”“寇”,其族群成分也具有动态性,有一些则将寇乱的部众与非汉族群攀上联系。如《宋史》称:“漳州之东,去海甚迩,大山深阻,虽有采矾之利,而潮、梅、汀、赣四州之奸民聚焉,其魁杰者号大洞主、小洞主,土著与负贩者,皆盗贼也。”②在这里,“洞主”既可以解释为矾矿的洞主,也可以解释“山洞”洞主。因为在唐宋以后,常将非汉族群聚落称为“洞”,洞主指其首领或酋长。如果后者推论成立的话,则说明当时有许多“潮、梅、汀、赣四州之奸民”以及当地“土著”与“负贩者”均打着“洞”的旗号进行寇乱剽劫。这不仅说明了在动乱中,一些“民”向“贼”的流动,也说明了从“夷”到“夏”的族群边界的流动。
再如至元十四年,“元军进至潮阳县,宋都统陈懿等兄弟五人以畲兵七千人降。”③陈懿家族拥有一支船队,其主要功绩为海上军事活动④。谢重光先生认为陈懿所率领的畲兵应源于蜑民,与山居耕畲的山民不属于同一系统,也就是说,这些畲兵是“海盗”,而不是“山寇”。⑤按照刘克庄的《漳州谕畲》记载,是在漳州等地溪峒种类的一支,他说:“凡溪峒种类不一:曰蛮、曰猺、曰黎、曰蜑,在漳者曰畲。”⑥可见在南宋以后,畲、蜑均属于“溪峒种类”,但由于所处区域不同,二者仍有区别。如果将蜑民军队称为“畲兵”,那么,说明在南宋刘克庄所处时代,“畲”还专指漳州的一支“溪峒种类”,而到了元代已经被用来泛称南方的一些“溪峒种类”了。也就是说,在宋元时期出现的畲军,其中的非汉族群,除了“畲”外,可能还有一些被称为“蛮”“猺”“黎”“蜑”的族群。
在宋元时期,“畲”不仅内涵变得丰富,包含了南方一些非汉族群,其在外延上似乎也有扩大的趋势。文献中出现的各类“畲军”,其部众并非全由畲民或“溪峒种类”组成,其中有很多是汉人。这些汉人在叛乱起兵时,常借助“畲”的旗号以壮大声势,如宋绍定二年(1229年),宁化的晏头陀在潭飞磜起义,即是此例。按傅衣凌考证,头陀不是人名,而是畲族中的一种尊号。①其部众多达数万人,②成分却并非均是“溪峒种类”而被认为是盐寇,《宋史》载:“盐寇起宁化,居安以书谕汀守曰:土瘠民贫,业于盐可尽禁耶?且彼执三首恶以自赎,宜治此三人,他可勿治。”③在宋代,江淮、赣、闽一带的盐夫、盐寇很多都为汉人,《宋史》又称:“不逞无赖盗贩(盐)者众。捕之急则起为盗贼,江淮间虽衣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贩盐为事。江西则虔州地连广南,而福建之汀州亦与虔接,虔盐弗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④
宋元以后,号称“头陀军”还有黄华⑤、陈吊眼等⑥。与晏头陀一样,这些“头陀军”有许多是汉人,如黄华畲军中主要是盐夫。《元史·世祖纪》载:至元十五年“建宁政和县人黄华,集盐夫,联络建宁、括苍及畲民妇自称许夫人为乱。”⑦到至元二十年,黄华的头陀军部众达几十万人⑧,这些人都被称为“畲军”。《元史》称,至元二十二年“九月,诏福建黄华畲军,有恒产者放为民,无恒产与妻子者编为守城军。”⑨而与黄华互为呼应的远不止几十万,至元二十六年,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王恽进言于朝说:
福建所辖郡县五十余,连山距海,实为边徼重地。而民情轻诡,由平定以来官吏贪残,故山寇往往啸聚,愚民因而蚁附,剽掠村落,官兵致讨,复蹂践之甚,非朝廷一视同仁之意也……福建归附之民户几百万,黄华一变,十去四五。今剧贼猖獗,又酷于华,其可以寻常草窃视之?况其地有溪山之险,东击西走,出没难测,招之不降,攻之不克,宜选精兵,申明号令,专命重臣节制,以计讨之,使彼势穷力竭,庶可取也。①
王恽分析福建寇乱的原因有几个:一是地理原因:“连山距海”“边徼重地”;二是族群原因:“民情轻诡”;三是“官吏贪残”;四是“山寇啸聚”后“愚民蚁附”。“福建归附之民户几百万,黄华一变,十去四五”的“十去四五”,可能有两种意思:一是百姓逃离十之四五;二是原来归附的百姓,又成为脱籍贯之民的有十之四五。如果是后者,则说明华夏边缘是向中心内缩,而非向边陲扩张,也就是说原来为华夏边缘内的百姓,现在又返回为边缘之外的百姓。但不管怎样一种后果,都说明了动乱对当地社会——尤其是汉族社会,带来巨大的打击。由此可见,“畲”在宋元成为一个泛称,许多参与地方动乱的人群打着畲的名号,统治者也将这些动乱称之为畲,这有文化标签的意味,而非全部均有“溪峒种类”的血统。
明代文献常将“畲”“猺”两类族群并称,二者具有一定联系。如《明武宗实录》记载道:
先是,江西、广东、湖广之交,溪峒阻深,江西上犹等县輋贼谢志山等据横水、桶冈诸巢;广东龙川县贼池仲容据三浰头诸巢,与猺贼龚福全等联络。亘千百里,时出攻剽,势甚猖獗,将连兵乘虚入广。②
可见畲、瑶互相联络支援,“连兵”作乱,形成了“四省輋贼、猺贼及峒贼蟠纠流劫”③的情况。王阳明称:“三省贼巢,联络千里,虽声势相因,而其间亦自有种类之分、界限之隔。利则争趋,患不相顾,乃其性习。”④这段话说明,闽浙赣三省这些所谓的輋、猺、峒的贼寇实际上是有种族之间的区分,聚居地有所区别,也就是说,族群间是有族群边界的,即所谓的“自有种类之分、界限之隔”。但是在利益驱动之下,这些族群会联合起来,“声势相因”,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但在患难的时候,互不相顾,族群认同感消退。这符合族群认同“工具论”或“情境论”的观点,即:在不同的社会情境,或者为了本族群的利益,族群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族群认同,以求得本族的生存与发展。
在明清时期,还有一些族群打着畲、瑶族群的旗号,如谢志珊、蓝天凤等领导的“桶冈之乱”,他们自称为“盘皇子孙”,目的就是为了纠集各路不同人群:“其大贼首谢志珊、蓝天凤,各又自称‘盘皇子孙’,收有传流宝印画像,蛊惑群贼,悉归约束。即其妖狐酷鼠之辈,固知决无所就;而原其封豕长蛇之心,实已有不可言。”①
再如正德年间,原来迁往南安府的广东移民“称輋为寇”②,在江西本地也有入輋为盗的现象,王阳明称:“及有吉安府龙泉、万安、泰和三县,并南安府所属大庾等三县居民,无籍者往往携带妻女,入輋为盗;行劫则指引道路,征剿则通报消息,尤为可恶。”③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许多无籍者“入輋”后成为畲民,这些“入輋”的人群常常被官方视作“盗”。前文笔者曾论述,峒与非峒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受到国家的控制,而是否入籍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在官方视野中,不受国家控制的作乱就是“盗”,没有版籍的移民往往与化外之民没有太大区别,而在南方,官方又往往以“畲”“瑶”“峒”等称谓泛称这些化外之民。笔者推测,这些号称为“輋”,一方面可能是自称,由于畲瑶历来号称本族群具有“免差徭”的特权,一些人为了逃避赋役,或者如上述所说,为了互相得到支援联络,于是自号为輋,而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汉人;另一方面可能是他称,由于汉人迁徙到偏远地区后,族群得到发展,生产生活方式受到当地土著影响,其文化发生部分变化。由于这些人群地处偏远地区,官方往往控制不到,而当这部分人作乱时,官方将这些“失控”的人群统一归为“輋”人,至于这些人的族源,对于官方而言,已经不那么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明清时期闽粤赣一些地区的“移民”“畲”“盗贼”三者有着相当微妙的共生关系。
三、边界的消失:宋至明“畲寇”减少的原因分析
在宋元时期,许多南方非汉族群的动乱,均冠以“畲乱”“畲军”“畲寇”,随着畲汉融合以及畲汉边界的模糊,在明代以后,这种以“畲”作为寇乱主体的记载减少,而取而代之的是族群特征不明显的“山寇”。这种变化从侧面反映了族群边界的模糊,也说明大量畲民在认同上发生转变,逐步融入汉族之中。
宋元时期,朝廷对畲民武装进行剿抚,导致“畲军”“畲兵”“畲寇”大量减少。由于招抚畲军既能平息叛乱,又能加强统治,所以朝廷尽力招抚。《元史》记载至元十六年,蒲寿庚请求朝廷下诏并得到应允:“诏谕漳、泉、汀、邵武等处暨八十四畲官吏军民,若能举众来降,官吏例加迁赏,军民按堵如故。以泉州经张世杰兵,减今年租赋之半。”①元代苏天爵的《元文类》载:“福建之畬军则皆不出戍他方,盖乡兵也。”②《元史》称:“福建之畲军,则皆不出戍他方者,盖乡兵也。又有以技名者曰炮军、弩军、水手军,应募而集者曰答拉罕军”。③可见畲军用于地方防守。除此之外,朝廷也将其作为征服其他溪洞的工具,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元朝王恽的诗写道:“蛮陬溪洞既荒远,颠枿其间不无孽。畬军新附用得宜,以彼为攻易摧折”。④
一些不接受招降的或复叛者,则逃入山洞,继续“依阻山险”,“负固”顽抗,最终招致朝廷的新一轮镇压。如《元经世大典序录》记载:“至元十六年五月,降旨招闽地八十四畲来降者。十七年八月,陈桂龙父子反漳州,据山寨,桂龙在九层际畲、陈吊眼在漳浦蜂山寨、陈三官水篆畲、罗半天梅泷长窑、陈大妇客寮畲,余不尽录。十八年十月,官军讨桂龙,方元帅守上饶,完者都屯中饶,时桂龙众尚万余,拒三饶,寻捕得其父子斩之。”⑤再如至元十九年,“黄华急攻建宁……华走江山洞,追至赤岩,华败走,赴火死。”⑥平和县乌泥洞“在坂仔。岩险异常,相传畲寇李志甫据此作乱,四帅征之,兵不能进。陈君用侦知洞后有间道,乃募壮士数十人潜人,猝遇志甫,地狭,兵器不得用,因手格杀之,余党悉平。”①
明清以后,随着族群的融合,华夏族对边陲各族群有更深入的了解,一些寇乱不再以“畲”来泛称,而有更细的划分,如林大春在《论海寇必诛状》将南方寇乱分为三类,其文称:“为今岭海患者,不过曰山寇、海寇、倭寇三者而已……夫是三者,势相倚而祸相因者也……夫山寇非他也,盖多村里恶少,与夫愚蠢编氓,非有奇谋异能,特见间而起。又其所居,多负险易以伏匿。急之则啸聚岩谷间,州郡亡命闻而争奔走焉。”②可见,山寇主要是“村里恶少”“愚蠢编氓”以及“州郡亡命”组成,这些人很大一部分人应该是汉人,其因为“聚岩谷间”而被统称为山寇。在统治者眼中,这些山寇应该与历来“啸聚畲峒”的化外之民无别。只不过是无法具体区分族群差异,所以以山寇称之应该是比较恰当的表述。明代何乔远在《闽书》中则对明中叶以来福建“寇乱”发展变迁进行论述,他说:
闽中成、弘以前,山寇多而海寇少;正、嘉以来,山寇少而海寇多。国初,州县仍宋、元旧,山林深阻,荆棘蒙密,奸宄时窃发,至乎蔓不可图。今其地芟夷之后,悉置县司,即欲啸聚,靡所藏寄。此山寇多少所由异也。③
这段文字说明了寇乱由山变海变化趋势,同时对山寇变少原因作了解释。关于山寇变少的原因,或许与国家权力深入山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逐渐加强有关,随着归入版籍的人变多,山寇自然变少。《世烈录》记载了明朝潮州等地受到山海之间的贼寇骚扰的情形:
潮郡自正统、天顺以来,海寇山瑶,迭出劫掠,陷城杀吏,肆毒连年。本官按行郡邑,抚戢残余,励志救民,奋身犯难,初平海寇,继讨畲蛮,累破峒贼于程乡、黄岗,穷捣窘巢于上杭、安远,兵威所及,如火燎毛,遂使疮痍得反衽席,老弱得保天年④
所谓的山寇是哪一些人?就汉人角度观察,无非是住在山里为乱的,其常常为陌生人,至于这些陌生人是哪个族类反倒不太重要。当时普遍的情况是,近于郡县城镇地方多是汉民所移住定居,而长期居于乡野山谷之间的则多为非汉族住民。因此,有学者认为,山寇与畲、瑶之间必有联系,陈森甫曾指出,直到明代,有许多山寇为乱与瑶、畲等少数民族活动有很大的关系。①谢重光认为,明代闽粤赣地区民变的主体有部分人是客家百姓,也有畲族人民。②李荣村、林天蔚等学者认为,这些非汉族群动乱的主要原因是地方的经济政治无法改善。③也就是说,地方经济政治结构的变动(主要是对非汉族群经济社会的冲击),造成了非汉族群对社会做出反应,在官方或汉人的表述中,就是“寇乱”。
康熙《漳浦县志》则将当地的“寇”分为五类,其文写道:“(漳浦)地连潮广,蛮獠杂居,反叛不常,为寇一;扶桑日出,风烟咫尺,倭入内地,为寇二;崇严巨浸,林木啸聚,潢池窃弄,山海之际,伏莽为灾,为寇三,为寇四;更姓易朔,妄指义旗,借衣冠为盗薮,流毒乡里,为寇五。”④可见,在明清漳州地区的寇乱的成分有五大类:一是“蛮獠”,主要是指畲瑶等族群;二是倭寇;三、四是山海之间的寇,可称之为山寇、海寇;五是指由豪强发起,旨在反抗朝廷的叛乱者。《平和县志》:“邑(平和县)居边徼,寇盗滋多;地连瓯粤,蛮僚难化。况崇岩巨浸,林木啸聚,山隅海曲,伏莽多虞乎!至于乘时藉势,妄指义旗,又有倚衣冠为盗薮,以荼毒乡里者,无怪乎叛乱相寻。”⑤明清仍有“倚衣冠为盗薮”者,应该是地方地主组织发动的一些地方叛乱,而非完全是底层百姓的自发叛乱。
在元代,将一些族群身份不是特别明确的寇乱,常以“畲寇”称之;在明代,常将其统称为山寇、山贼等。当然,明清山寇并非全是非汉族群的寇乱,也可以指其他族群叛乱者。正如吴震方在《岭南杂记》称:“明通志凡山寇皆谓之獠,盖山寇亡命乌合,未必种传,无从究考。”⑥明代以来,这些“盗寇”,在血统上不好辨认族群属性,所以官方笼统将其划入山寇、峒寇一类,强调的是生活地理位置以及不受政府羁縻,荒忽无常的共同特点。①
因此,针对文献中出现的“山寇”,应该分析其出现的具体语境。有时候山寇特指畲民,如杨澜《临汀汇考》:“今汀中畲客所占之地……想郡治初开时,乡村平衍处亦都如是。故《唐书》谓汀郡多山寇也。”②山寇在此应指特指“畲客”或其先民。再如乾隆《汀州府志》载罗良:“元至正间,散资募士,捕杀漳州山寇。”③漳州山寇就是李志甫。
关于史志对李志甫记载的分歧,谢重光先生认为:“可能缘于李志甫本是汉人,但所聚之众有汉人、也有不少是畲民,李本身也已畲化,故或笼统称之为‘反贼’‘山贼’‘南胜贼’,或迳称为‘畲贼’。”④我们认为畲倒是一种名号,而不在于族群内部血统成分之多寡,也不在于是否被畲化,而在于统治者对其看法,入峒则为畲,出峒则为汉,这就是族群边界的解释。
元明之间,畲寇减少在文献表述上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两个文献对比来说明,一份是元代陈志方《元右丞相晋国公罗公墓志铭》,其文称:
值元季之乱,每叹曰:大丈夫当扫除天下,安集四境,今举世纷乱,安事毛锥为也。因廪募乡民从大将,击平南胜畲贼李志甫,功居最,奏授长汀尉,未几,畲寇吴仰海、江西贼詹天骥发公奉命讨平之,陞漳新翼万户。至正十三年,福安贼康子政犯福州,帅宪两府以礼币致公……其后,南胜畲寇陈角车、李国祥,安溪贼李大,同安贼吴肥,潮贼王猛虎,江西贼林国庸,先后窃发。西林贼陈世民攻陷南诏、长汀、龙岩、漳浦诸邑,公悉削平。降其众,复其邑。⑤
我们再来看明代《闽书·罗良传》的表述,其文曰:
罗良,字彦温,负俊才,善谋略。至正四年(1344年),漳贼李志甫围守将战败,良倾家募兵,从江浙平章百花讨平之,以功授长汀尉。十一年(1351年)……贼吴仲海等杀千户福留,陷南胜等县,对比以上两则材料,前者将李志甫、吴仲海记载畲贼、畲寇;后者则写为漳贼、贼等。这种表述的微妙变化,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元代以后,大量的“畲军”被安排入政府统治,人数大量减少;二是“畲”的内涵在元明之间发生变化:即元代凡是寇乱的,均可冠以畲寇;明代随着畲的进一步明确,畲更倾向于指代具有盘瓠信仰的非汉人群。到了明中叶,王阳明巡抚南赣,对闽粤赣地区“畲乱”进行治理,特别是大量新县的设立,闽粤赣地区许多地方由“盗区”转为“治区”,更多的畲民转化为新民,明中叶以后,文献中就更少有关于“畲寇”的记载。本书将在下一章对此进行论述。
第三节 小结
本章论述了宋元以后至明初期闽粤赣地区畲汉边界移动的情况,主要论点有:
(1)根据官方的族群分类方法,常将边陲地区不纳税服役的非汉民族称为“盗”“贼”“寇”等,是否成为国家管控范围之内的居民成为“贼”与“民”的重要区分标志。宋元常出现有关“畲军”“畲丁”“畲乱”,其中“畲”作为一种蛮夷语境被表述,其不应该认为完全是种族血统的概念,而应该将其视为一种文化的范畴。也就是说,“畲军”“峒丁”中的畲或峒,均是官方对南方地区非汉族群笼统的概称。畲乱中显示了华夏边缘的移动过程。从官方的角度来看,其将参加动乱视为化外之民,目的在于区别“贼”与“民”、“良”与“莠”,显示的是官方心目中异族的移动过程;从叛乱当事人角度来看,他们打着“畲”的旗号,目的在于壮大声势、联合更多民众参与斗争,显示的则是主观上向“异族”认同的转变。以上两个共同制造了“畲”在宋元时期从内涵到外延的转变。就此而言,如黄华、李志甫等所谓的“畲寇”“畲贼”“畲军”,其被认为是畲,与其从血统、种族上去寻找根源,不如从文化上去说明其成因。其作为非汉民族,更多的是官方,以汉人为代表的政府认为这些人为未开化人群之一,称之为畲,有贬义的意思。所以既可以称之为畲贼,又称之为山贼,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是一种文化的称谓,而非完全以血统来区分人群。
(2)随着闽粤赣地区族群频繁互动,族群边界也显示出变化不定的状况,具有流动性。既有畲民通过获得版籍成为编户齐民的情况,也有汉人通过“入山洞”,脱籍成为“畲”“瑶”族群的情况。
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历史情境下,社会中出现了一股反社会的潜力,并在宋元时期迅速形成合力,爆发了空前的动乱,畲乱在东南一地尤为明显。畲乱引起了朝廷的重视,因而在文献上留下了大量与之有关的记载。“畲乱”本质上是社会秩序破坏下,华夏心目中异族迁移中的体现。也就是畲乱与盐寇、地方寇(潮寇、广寇、赣寇)是一致的,只不过冠以异族的名号。与其将其视为种族区别,更多的是文化上来考量。也就是说畲军、畲寇、畲贼不一定是溪峒民族,有些人打着“畲”的名号起兵,此其一;另外华夏视野中,将一些寇乱冠以畲名,是化外之民的象征。
(3)族群的文化认同是族群边界的一个重要指标。当各族群刻意强调族群间的文化差异、文化认同迥异时,族群边界越明显;而当族群不自觉淡化族群间的差异、文化趋同,族群边界逐渐模糊,直至消失或漂移。
这种族群边界的移动还可以通过政治文化教化来实现。在地方动乱中,各个族群被卷入其中,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族群或联合,或对抗,动乱深刻打上族群斗争烙印①。中央政府通过军事压制、设置县治、加强教化等手段进一步加强对闽粤赣地区的控制,使“盗区”变为“治区”,一些畲民或者逃避战乱或者被军事驱赶迁徙其他地区,这对畲民迁徙起着推动的作用。另外一些畲民仍生活在闽粤赣地区,他们被编入版籍,成为纳税服役的王朝子民。族群边界在动乱中不断移动,总的方向是华夏化运动螺旋式、曲折前进,宋元以来的畲乱使得“畲”作为一个族群登上历史舞台,进入人们视野,为畲族族群社会发展与变迁奠定了基础。
附注
①根据梁方仲先生统计,从唐元和年间(806—820年),福建登记在册的有户口分别为:74467户,315740人;而到了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户口分别是1599214户,3230578人,400年间,户口分别增长到21.5倍、10.2倍。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4页。
①[宋]刘克庄:《漳州谕畲》,载《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三《记》。
②[宋]刘克庄:《送方漳浦》,载《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三十四《诗》。
③[春秋]孔子:《尚书》,《泰誓上》,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3页。
④[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下册),第26册,《福建备录·防闽山寇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56页。
⑤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5页。
①[元]刘埙:《隐居通议》,卷九《诗歌四·云舍赵公诗》,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172杂家类,第866册,第97页。
②[明]宋濂:《元史》,卷十七《本纪·世祖十四》。
③赵万里辑:《元一统志》(下册),卷八《汀州路·风俗形胜》,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629-631页。
①[明]宋濂:《元史》,卷十五《本纪·世祖十二》
②[明]王守仁:《横水桶冈捷音疏》,载《王文成公全书》,卷之十《别录二》。
③[明]王守仁:《咨报湖广巡抚右副都循史秦夹攻事宜》,载《王文成公全书》卷之十六《别录八》。
④[明]王守仁:《立崇义县治疏》,载《王文成公全书》,卷之十《别录二》。
⑤[清]祝淮:《香山县志》,卷八《前事略》,道光八年(1828年)刻本。
⑥[清]周硕勋:《潮州府志》,卷十六《山川》,中国方志丛书第46号,据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重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204页。
⑦[清]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七,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第309-311页。
①黄挺,陈占山:《潮汕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41页。
②黄向春:《“畲/汉”边界的流动与历史记忆的重构——以东南地方文献中的“蛮獠——畲”叙事为例》,《学术月刊》,2009年第6期,第139-140页。
③[明]喻政主修:万历《福州府志》,卷二十六《食货志一·户口》,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年。
①[明]冯梦龙著,陈煜奎校点:《寿宁待志》,卷上《铺递》,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39页。
②[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佚文·四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③[唐]李延寿:《南史》,卷七九《夷貊下·荆雍州蛮》,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④[宋]刘克庄:《英德赵使君墓志铭》,载《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六.《墓志铭》。
⑤郭志超、董建辉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畲族的赋役状况进行了考证辨识,认为畲族地区的封建赋役制始于南宋末,局部扩张于元明,普遍实行于清代。早在明代,粤东大部分畲族地区已推行赋役制度,而到清代,闽西、闽南(九龙江以西)及赣南畲族地区赋役制度亦得到普遍推行。参见郭志超,董建辉:《畲族赋役史考辨——与蒋炳钊先生商榷》,《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第94-100页。
①[明]黄佐纂修:《广东通志》,卷六十七外志四《猺獞》,第1760页。
②[明]刘熙祚修,李永茂纂:《兴宁县志》,卷六《杂记·徭蛋》,北京:中国书店,1992年。
③[明]黄佐纂修:《广东通志》,卷六十七外志四《猺獞》,第1765页。
①新中国成立以后,畲族起义(畲乱)作为历史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的一部分,许多学者对畲族各类起义进行了认真细致地梳理、考证,多层面多角度地论述,推动了畲族研究的深入发展;这种研究很大程度受到“阶级斗争论”的学术背景影响,带有明显的“政治意识”如畲族社会历史调查中,报告常将畲族阶级斗争作为重要内容来论述,对畲民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反抗历史也着墨甚多。如编于1980年的《畲族简史》,有一半以上篇幅在描述畲族的抗争参见《畲族简史》编写组:《畲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②王学典:《意识形态与历史:近50年来农战史研究之检讨》,《史学月刊》.2005年第7期,第15页。
③参见唐立宗:《在“盗区”与“政区”之间——明代闽粤赣湘交界的秩序变动与地方行政演化》,“国立”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18),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2年;饶伟新:《明代赣南族群关系与社会秩序的演变:以移民与流寇为中心》,厦门: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9年;黄志繁:《“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④[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
①温春香:《明清之际畲族民风的改变——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11期。
②[清]梁章钜撰,王释非,许振轩点校:《称谓录》(校注本),卷三十《盗贼》,第564-565页、第621页。
③[元]脱脱:《宋史》,卷四百五十一《列传第二百一十·忠义六·张世杰》,第13273页
④[清]杨澜:《临汀汇考》,卷三《畲民附》,第29b页。
①刘志伟通过比较两部《广东通志》关于广东地区“蛮夷”的记载,发现除了提到了一些文化上的特征以外,特别用了“不服政化”“不可羁摩”“不属于官”“无版籍”“无赋役”之类的字眼来描述他们的社会身份他们不仅在文化上属于“椎结卉服之民”,在社会身份上更是区别于“良民”“编户”齐民”,是民属于所谓的“化外之民”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户籍赋税制度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01-102页。
②温春香:《明清以来闽粤赣交界区畲民的族谱书写与族群意识》,《贵州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第178-179页。
③[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直敷文阁福建运判吕企中除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填赵子英召赴行在阙候任满前来奏事》,第11a页
④[元]胡翰:《墓志铭》,收入[元]王毅:《木讷斋文集》附卷,转引自陈高华等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4页。
⑤赵万里辑:《元一统志》,卷八《汀州路风俗形胜》,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629-630页。
⑥[明]何乔远:《名山藏》,卷八十五《儒林记·王守仁》,续修四库全书,427,史部杂史类,据明崇祯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95页。
⑦[明]杨博:《杨襄毅公本兵疏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1册,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师真堂刻本,卷七《请催江西守臣依限平贼起副使谭纶统兵疏》,第35b页。
①[明]郭造卿:《海岳山房存稿》(明万历间谷城于氏刊本),卷十二《闽中分处郡县议》,第27b-28a页。
②[清]杨澜:《临汀汇考》,卷三《兵寇考》。
③[清]顾炎武撰,王文楚等校点:《肇域志》,《福建一》,第341页。
④[明]毛伯温:《毛襄懋先生奏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诏令奏议第59册,清乾隆三十七年恩堂刻《毛襄懋公全集本影印》,卷四《弭盗疏》,第23a页。
⑤[元]黄潜:《黄学士文集》,收入放胡宗楙辑《擅金华丛书》18,影钞元至正刊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70年,卷三一《正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省知政事王公墓志铭》,第7b页。
⑥[清]刘坤一等修,趟之谦等纂:《重修江西通志》,卷七五《建置略·坛庙三》,根据清光绪六年(1880年)刊本影印,台北:台湾华文书局,1967年,第54a页。
①这里的畲丁指的南方非汉族群中的一种。清代梁章钜将畬丁归为“农”类,他在《称谓录》中称:“《元史·博尔忽传》:‘畬丁溪子’,案畬丁,务农者也。”[清]梁章钜撰,王释非,许振轩点校:《称谓录(校注本)》,卷二十七《农》,第513页。
②[元]元明善:《太师淇阳忠武王碑》,载《清河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1323集部·别集类,据清光绪刻本藕香零拾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页。
③[元]许有壬:《送苏伯修赴湖广参政序》,载《至正集》,卷三十四,据清抄本影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95集部,元别集类,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75页。
④[明]王慎中:《玩芳堂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88册,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蔡克廉刻本,卷四,《抚寇碑记》,第33b页。
⑤唐立宗:《在“盗区”与“政区”之间——明代闽粤赣湘交界的秩序变动与地方行政演化》,2002年,第101-102页。
①[清]黄许桂修,曾泮水纂:《平和县志》,卷一,《山川志》,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修,第72页。
②钟先、钟平鼻钟姓在诏安应属畲姓。吕扁是康熙年间聚集在诏安县寇乱头目。道光《平和县志》卷三《武功志》:“(康熙)三十六年,诏安县城吕扁聚党于白叶渠。渠深险,与广东大埔县山谷连界,数日之间,众至七百余人。劫掠村落,渐逼县城,居民各依乡堡固守,贼无所得。间道夜趋南靖之山城墟,会沮雨,既至,天已明,贼争夺食.汛防千总曾高捷击走之。后入(平和)县境,聚高磜,约正吴元臣纠乡壮击杀百余人,生擒者数十,枭吕扁首,余党俱散。”同上书,卷三《武功志》。
③同②,卷十《士习》,第157-158页。
④[清]梁章钜撰,王释非,许振轩点校:《称谓录》(校注本),卷二十七《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13页。
①[清]杨澜:《临汀汇考》卷一,《方域考》,第14a页。
②黄志繁《“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59-261页。
③宋代食盐由国家统销,汀州食福建盐,由闽江溯流经南平、邵武运至;赣州食淮盐,又须过长江。溯赣江运至。因路途遥远,盐价既高,质量也差。相比之下,潮盐优质廉价,汀、赣二州百姓都喜食潮盐。为打破政府食盐的垄断和科派,汀、赣二州出现贩运私盐现象,从而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详见周琍:《明清时期闽粤赣边区的“盐粮流通”》,《盐业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34-35页。
④[清]魏瀛等修,钟音鸿等纂:《赣州府志》,卷二三《经政志》,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刊本。
⑤[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下册),第26册《福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90页。
⑥[清]杨澜:《临汀汇考》卷三,《盐法》。
①[清]邱嘉穗:《与翁明府、蒋参戎论洞寇书》,载[清]曾曰瑛等修,李绂等纂:《汀州府志》,乾隆十七年(1752年)修,卷四十三《艺文五》,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579-581页。
②[日]竹村卓二著,金少萍,朱桂昌译:《瑶族的历史和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14-115页。
③傅衣凌:《从农民斗争到资本主义萌芽看中国封建社会的弹性》,《学术研究》,1983年第2期。
①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8-109页。
②饶伟新:《明代赣南的社会动乱与闽粤移民的族群背景》,《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第133-139页。
③[明]谈恺修纂:《虔台续志》,卷一《舆图志》,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刊刻,台北:台北图书馆韩雪研究中心影印本,第31页。
④[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下册),原第二十七册广东二引《通志》,第316页。
①[明]胡琼:《忠洛无银矿记》,载顺治《永安县志》卷九《艺文志》
②[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下册),原书第二十九册《广东下·峒獠》,第395页。
③[清]顾炎武:《肇域志》,《福建二·诏安》,第446页。
④康熙《诏安县志》记载六峒“在县西北六十里,连接金溪诸山,旧有银矿,奸民藉官射利,往往生事呈采……万历年间奉敕合开采陵谷为墟,商贾杂还,豪民假虎,鸱张更甚,二都之民岌岌惊变,后奉旨停革,民乃安堵。”载[清]秦炯纂修:《诏安县志》,卷之七《武备志·关隘》,康熙三十年(1691年)修,据同治十三年(1874年)刻本影印。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31,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92页。
⑤黄志繁:《“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温春来:《咸同年间广东高明县的土客械斗》,载胡春惠,周惠民主编:《两岸三地研究生视野下的近代中国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2000年。
①[元]脱脱:《宋史》,卷一九三《兵志七》,第4819页
②同①,卷一八五《食货下七》,第4537页。
③[明]宋濂:《元史》,卷一三二《哈喇岱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④《元史》,卷十《本纪·世祖七》载:“庚寅,张弘范以降臣陈懿兄弟破贼有功,且出战船百艘从征宋二王,请授懿招讨使兼潮州路军民总管,及其弟忠、义、勇三人为管军总管,千夫长塔剌海获文天祥有功,请授总管军千户,佩符,并从之。”《元史》,卷一五《本纪·世祖十二》,称元朝准备进攻日本时,“陈义愿自备海船三十艘以备征进”《元史》,卷一三一《忙兀台传》谓:“初,宋降将五虎陈义尝助张弘范擒文天祥,助鄂勒哲图讨陈大举,又资安塔哈征日本战舰三千。”参见[明]宋濂:《元史》,卷十《本纪·世祖七》,卷十五《本纪·世祖十二》,卷一三一《忙兀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⑤谢重光:《客家文化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51-152页。
⑥[宋]刘克庄:《漳州谕畲》,载《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三《记》。
①傅衣凌认为一些族群因为禁忌的原因,喜欢借用假名,以避灾害,畲民中的晏头陀就是这种习俗的表现,史称:“人见其自号头陀,遂习用之,致其本名彪反隐而不彰。”参见傅衣凌:《福建畲姓考》,载《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75页。
②[元]脱脱:《宋史》,卷四一九《陈韡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61页。
③[元]脱脱:《宋史》,卷四零五《王居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255页
④[元]脱脱:《宋史》,卷一八二《食货下四·盐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441页
⑤黄华起兵,降而复叛,两次都是号称陀头军。《元史》称至元十七年,黄华“聚党三万人,扰建宁,号头陀军”;《元经世大典序录》又称:“至元二十年八月,建宁招讨使黄华反,集亡命十余万,剪发文面,号陀头军。”见[明]宋濂:《元史》,卷一三一《完者都传》;《元经世大典序录·政典》,卷四一《国朝文类》。
⑥《新元史》称:“庆元贼陈吊眼聚众叛,自称头陀军”。参见柯劭忞等撰,余大钧标点:《新元史》,卷165,《吕德传》,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85页。
⑦[明]宋濂:《元史》,卷七《本纪·世祖七》。
⑧[明]宋濂:《元史》,卷一五《本纪·世祖十二》。
⑨[明]宋濂:《元史》,卷九八《兵志一》。
①[明]宋濂:《元史》,卷一六七《列传第五十四·王恽》,第3932-3933页。
②《明武宗寅缘》,卷一六四,第12b页,正德十三年七月己酉条。
③[明]邹守益等撰:《王阳明先生图谱》(《四库未收书辑刊》史部四辑十九册,清抄本),第477贞
④[明]王守仁:《议夹剿方略疏》,载《王文成公全书》,卷之十《别录二》,第333页。
①[明]王守仁:《横水桶冈捷音疏》,载《王文成公全书》,卷之十《别录二》。
②[明]嘉靖《南安府志》原文载:“南安接壤闽、广、湖、郴之间,实惟四塞之地,去城北数十里,狗脚岭而下曰横水者,迤逦石磴而入,草木丛深,别一区域。往岁广之迁民安插,至正德间复叛,称輋为寇,犯大庾,攻南康,侵上犹,肆为剽掠,荼毒生灵,良善苦之。”参见[明]刘节撰:《南安府志》,卷十二《秩祀志二·庙祠》,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1年版,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510页。
③[明]王守仁:《咨报湖广巡抚右副都御史秦夹攻事宜》,载《王文成公全书》,卷之十六《别录八》,第547页。
①[明]宋濂:《元史》,卷十《本纪第十·世祖七》,第211页。
②[元]苏天爵编:《元文类》,卷四十一《杂著·军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367-540页。
③[明]宋濂:《元史》,卷九八《兵志一》。
④[元]王恽:《南楼行送信御史佐鄂岳行院》,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第十一《七言古诗》,四部丛刊初编224集部,据上海涵芬楼借江南图书馆藏明弘治翻元本景印,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重印影印,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
⑤《元经世大典序录·政典》,《国朝文类》卷四一。
⑥[明]宋濂:《元史》,卷一六二《高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①[清]黄许桂修,曾泮水纂:《平和县志》,卷一《山川志》,道光十三年(1833年)修。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3-54页。
②[明]林大舂:《井丹诗文集》,卷八《论海寇必诛状》,《潮州文献丛刊》3,1935年练江郭氏双百鹿斋据明万历版本暨林家刻藏祖本相互参校,香港:香港潮州会馆,1980年,第3b-4a页。
③[明]何乔远:《闽书》,卷四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03页。
④《世烈录》,卷四《补遗·崇祀潮州府名宦姑》,转引自朱洪,姜永兴:《广东畲族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2页。
①陈森甫:《宋元以来江西西南山地之畲蛮》,《国立编译馆馆刊》,第1卷第4期,1972年,第169-184页。
②谢重光推论如溪南盗钟子人、清流贼蓝得隆、永定渠魁钟三,从其姓氏和地域来看,可断定其属畲族无疑谢重光:《客家文化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70页。
③李荣村:《黑风峒变乱始末——南宋中叶湘粤赣间峒民的变乱》,第497-545页;林天蔚:《宋代猺乱编年纪事》,载《宋史研究集》第六辑,台北:“国立编译馆”出版,1986年,第437-486页。
④[清]陈汝咸修,林登虎纂:《漳浦县志》,卷十一《兵防志》,第783-784页。
⑤[清]吕天锦等纂:《平和县志》,卷十二,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刊本。
⑥[清]吴震方:《岭南杂记》(复印本),丛书集成初编,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8页。
①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户籍赋税制度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01-102页。
②[清]杨澜:《临汀汇考》,卷四《山鬼淫祠考》。
③[清]曾曰瑛等修,李绂等纂:《汀州府志》,乾隆十七年(1752年)修,卷之二十八《选举八》,第332页。
④谢重光:《客家文化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47页。
⑤[元]陈志方:《元右丞相晋国公罗公墓志铭》,载[清]李维钰原本,沈定均续修,吴联熏增纂:《漳州府志》,卷四六.第1118页。
又平之。
①[明]何乔远:《闽书》,卷一二四《罗良传》,第3719-3720页。
①谢重光:《客家文化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49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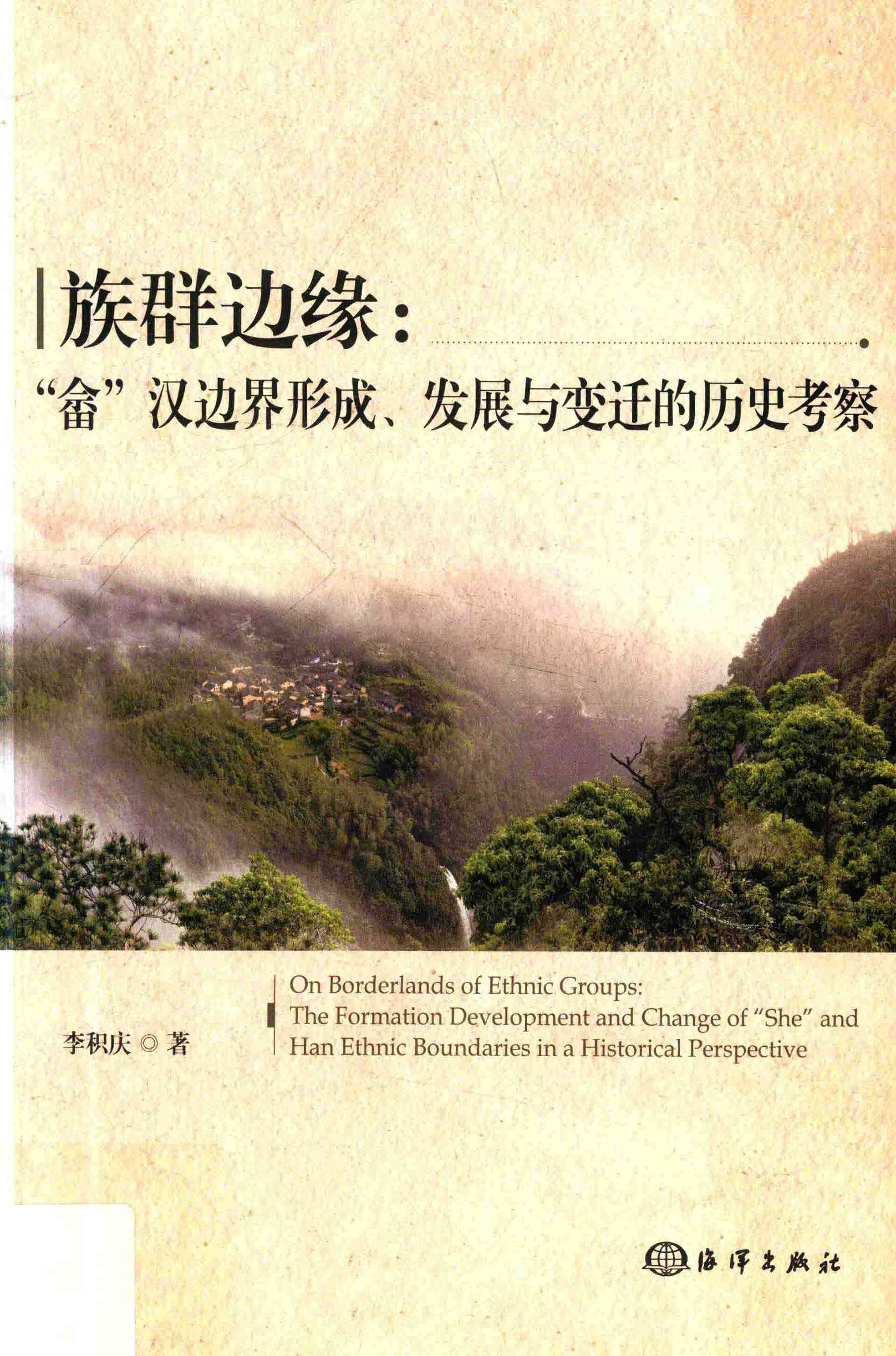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出版者:海洋出版社
本书从族群边界的理论角度,重新审视畲族形成、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在承认族群客观历史文化的同时,重点研究历史上“他者”(主要是汉族)对“畲”的社会定义以及“自者”(主要为南方非汉族群)自我族群认同的过程,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现实意义。
阅读
相关地名
宁德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