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洞:从洞穴居址到“蛮夷”聚落称谓的转变
| 内容出处: |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图书 |
| 唯一号: | 130920020230003764 |
| 颗粒名称: | 一、山洞:从洞穴居址到“蛮夷”聚落称谓的转变 |
| 分类号: | K288.3 |
| 页数: | 7 |
| 页码: | 36-42 |
| 摘要: | 本文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和总结,探讨了“山洞”从作为自然环境到非汉民族聚落称谓的转变过程。 |
| 关键词: | 山洞 人类聚落 非汉民族 |
内容
“畲”和“峒”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学界常将历史上出现在南方地区“山洞”“溪洞”“峒蛮”“峒獠”等族群与畲民联系起来。峒,也称“洞”,或“山洞”,关于山洞的解释,学术界上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自然环境说,指原来未设政区的偏远之处的山间溪谷;①二是民族构成说,专门指南方山区非汉族土著民族;②三是地方组织说,指随着中原王朝政治在华南社会的扩展,在国家行政统治未能到达的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由土豪势力建立起来的具有实质性的地域统治体制或特殊的军政单位。③以上观点将“溪洞”并称,各观点并不完全矛盾,只不过是将山洞放置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中讨论而已。如李荣村指出:“唐宋时凡近山的蛮夷住地、聚落或羁縻州洞等都可称作峒,又称溪峒,也就是蛮洞的意思,但绝不当作狭义的洞穴解释。”④李氏强调以特定历史条件来考察“洞”的含义,这是十分有道理的,但至于“洞”为何从表示“岩洞”“窟穴”的原意,变为少数民族“聚落”或组织,那还是得探寻洞的本源,方可做出解释。
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旧石器时代,洞穴居址作为人类聚落形态就已经存在。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就曾指出:“洞穴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者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⑤古代人类有选择寻找居住的洞穴,留下各个时代的洞穴堆积,在我国的华南、华北地区均分布着具有代表性的各时代洞穴。⑥一般来讲,这个时期的洞穴并非孤立、静态的存在,而是作为一个聚落系统发挥生产生活的功能。这一阶段的聚落形态主要为“洞穴-旷野”模式,也就是说,人类选择在洞穴,既要考虑洞穴作为遮蔽所的功能,又要考虑到以洞穴为中心的周围自然环境,尤其是食物资源的获取情况。⑦到了中石器时代⑧,随着原始农业的萌芽,人类社会开始由采集渐进到农业,由狩猎发展为畜牧⑨,在生产、生活技术水平提高的基础之上,人类从洞穴向更广阔的台地、平原、山冈进发。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建造技术高度发展,人们已经不再依赖洞穴,在各个适合人类生产生活的地形建造居所,形成聚落,并在不同地区发展出多元化的人类居住体系。在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华南地区所占数量不少,比较集中地分布在广东、广西、江西、云南等地区,浙江、福建、湖南等地也有少量分布,大概可以将遗址分为洞穴遗址、贝丘遗址、台地遗址三种类型。①从后两种类型足以证明人类的居址向多元化发展。在新石器晚期,人们已经大量建造公共广场、祭坛等建筑,聚落居址成为文明的标志。随着聚落的发展,中国个别地区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进入城邦模式。②
可见,早期人类由于生产生活技术水平较低,只能依赖洞穴作为庇护所,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对获取自然资源的需求,人类从“山洞”走向“旷野”,形成聚落,创造出越来越丰富的人类文明。那么可以想见,随着地区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提前进入“文明社会”、居住在城邦村落的族群在看待仍在“洞穴”居住的族群时,必定占有相对的心理优越感。而正是这种优越感带来的人们观念的变化,使得洞的意义开始延伸,也就是说“洞”在“文化先进”地区的人群看来,开始成为一种文化落后、野蛮未开化的象征。这种象征逐渐被“标签化”或“模式化”,形成了某一人群对另外一个人群的固有印象,如唐代刘禹锡称“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桴筏者,与华言不通。”③“居洞砦”是野蛮、未开化族群的重要特征之一。唐代以后,这些“居洞砦”的非汉人群一般被称为“峒民”或“峒獠”,其广泛分布于南方地区,如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写道:“峒獠者,岭表溪峒之民,古称山越,唐宋以来,开拓寝繁,自邕州以东,广州以西,皆推其雄长者为首领,籍其民为壮丁。”④这些分布广泛的“洞”,其地理环境、自然生态、社会组织特征又是如何呢?笔者拟以闽西象洞和海南黎峒作为例子进行分析。
宋开庆年间由胡太初所修的《临汀志》记载了有关象洞的情况,其文曰:
象洞,在武平县南一百里,接潮、梅界。林木蓊翳,旧传象出其间,故名。后渐刊木诛茅,遇萦纡怀抱之地,即为一聚落,如是者九十有九,故俗号“九十九洞”。其地膏沃,家善酝酿,邑人之象洞酒。洪刍有《老酒赋》,正谓此。但僻远负固,多不乐输,故置巡检寨以镇焉。①
按照作者的描述,象洞应该可以被认为是南方非汉民族居住的“山洞”的一种。以上材料可以说明:
第一,从自然生态上看,象洞原先是人迹罕至、丛箐林密的原始山林地带,在未开发之前,此地乃象群出没之地②,象洞因此而得名。
第二,从聚落形态看,象洞从原始森林变为人类聚居地的过程大概有三个步骤:首先,开辟山林,“刊木诛茅”;其次,选择“萦纡怀抱”的地理环境,在中间平坦、土地肥沃的地方开发成一个聚落;再次,随着山林开发的深入,各个“洞”被次第开发,如象洞形成了“九十九洞”的规模。笔者推论,“九十九”如此巧妙的数字,在此语境下应该不是实指,而是虚数,描述者只是想表达“洞”之数量极多而已。关于各洞之间的关系,应该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以地形看,各个“洞”周围山林林阻隔,交通不便,各洞之间可以保持相对独立的状态;而以名称看,象洞统称为“九十九洞”,说明各洞在“类型”上是相似的,不仅地理环境相似,族群多有相通,所以可以统称。
第三,从人文生态上看,洞中有平坦且肥沃土地可供“洞民”从事农业,并善于酿酒,其“象洞酒”在闻名于武平一邑;象洞早期居民不纳赋税,“僻远负固,多不乐输”,被认为是“化外之民”。随着王朝势力深入边陲,国家在非汉族群的地区驻兵,以控制当地“负固”之徒。
周去非《岭外代答》“海外黎蛮条”记载当地“黎峒”的情况,颇具代表性,可以看做是唐宋“蛮夷”聚落的一个典型,其文曰:
海南有黎母山,内为生黎,去州县远,不供赋役;外为熟黎,耕省地,供赋役,而各以所迩隶于四军州。生黎质直犷悍,不受欺触,本不为人患。熟黎多湖广、福建之奸民也,狡悍祸贼,外虽供赋于官,而阴结生黎以侵省地,邀掠行旅、居民,官吏经由村峒,多舍其家。峒中有王二娘者,黎之酋也,夫之名不闻。家饶于财,善用其众,力能制服群黎,朝廷赐封宜人,琼管有令于黎峒,必下王宜人,无不帖然。二娘死,女亦能继其业。昔崇宁中,王祖道经略广西,抚定黎贼九百七峒,结丁口六万四千,开通道路一千二百余里,自以为汉唐以来所不臣之地,皆入版图。①
本文记载了海南岛黎峒居民情况以及朝廷“开山洞”接管黎峒的过程,从该文可以较为直接了解被宋朝直接统治前的“峒”的基本情况:
第一,海南岛黎母山的居民成分有生黎、熟黎两种。海南峒中居民也是非汉族群,被分生黎、熟黎两种②,二者区别主要有两处:一是居住地理位置的远近,生黎住深山内,离政治中心远;熟黎住山外,耕种“省地”,与“省民”接壤;二是是否供赋役,“熟黎”多数来自湖广、福建地区(笔者猜测这些“熟黎”应多为汉人),然而在政府看来,他们却是“奸民”,因为他们暗自勾结生黎侵吞“省地”,目的在于以生黎身份占有“省地”后,可以逃避赋税,这也是他们被称为“黎”的根本原因。由此看来,汉人从“良民”变为“奸民”的评判标准在于这些百姓是否接受国家统一管理,并承担相应的服役纳税的义务,“良民”一旦变为“奸民”后,其与蛮夷常常是混淆不清的,并没有十分清楚的界限。如宋代《诸蕃志》也记载道:“黎,海南四郡岛上蛮也……去省地远者为生黎,近者为熟黎……黎之峒落日以繁滋,不知其几千百也,咸无统属,峒自为雄长,止于王、符、张、李数姓。”③
第二,“峒”是一个非汉族群的自治组织单位。海南黎母山峒中文中提到,“黎酋”王二娘凭借其家族势力和个人能力对“群黎”进行管理,并受到朝廷的赐封。这是朝廷的一种“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而“洞”就属于其中的一个基层组织。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称:“自唐宋以来内附,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洞”。④所谓的“种落”,指一个种族的聚落,也可以理解为族群的聚居区。族群人口数量不一,聚落的大小也不同,国家将聚落大的设州县,小的则称为“洞”。可见,宋代的“峒”是少数民族基层组织的一种,作为量词的“峒”,相当于现在一个村落或一个山区。
第三,海南黎峒有一定的人口数量。该文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峒中聚居人口概况,按文中所称的“抚定九百七峒,结丁口六万四千”计算,每个峒的丁口(成年男性)约为71人,如果将妇女儿童包括进去,可以推论宋代海南岛黎母山地区每个峒大约为二三百人。当然,各地的峒有大有小,各个种群有兴有衰,不能一概而论。如清代徐家干在《苗疆闻见录》描述西南苗人情况,也具体谈到聚落的大概人口数量:“苗人聚种而居,窟宅之地皆呼为寨,或二三百为一寨,或百数十家为一寨,依山傍涧,火种刀耕,其生性之蛮野,洵非政教所可及”①。所谓的“窟宅之地”“寨”,其意思应该与我们所分析的作为聚落形态的“峒”相似。另外,按照文中描述,清代的西南苗民与其他地方的“峒”民在生产、生活以及文化习性有着相似之处。
综合闽西象洞和海南黎峒两个典型个案,再结合其他文献,我们基本上可以理解唐宋以来“洞(峒)”作为聚落形态的基本特征:
第一,在地理位置上,“洞(峒)”多处于远离政治中心的偏远山区,经常处于万山之中,这些地区处于在南方的帝国边陲地带,山林阻隔,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多为非汉族群所居住。
第二,在村落特征上,经常表现为四周山峰(山林)环抱,中间有山坳平地。这种村落形态,一方面以有利的地形一定程度上阻隔或延缓了外族(朝廷)势力侵入;另一方面,中间平坳地区特别适合农业生产,保证了本地居民的物资供给。
第三,“洞(峒)”民的族群特征表现为,洞(峒)中居民基本上为非汉民族居住,具有“僻远负固,多不乐输”的特性,即不受朝廷控制,不承担纳税服役的义务。峒中有部分居民为汉族,这部分人经常是“逋负逃役”之人,因此也被政府认为“化外之民”。由此可见,“峒”与“非峒”的区别除了由种族区分的因素外,还在于是否纳税服役,是否接受教化,是否编入版籍。
第四,“洞(峒)”的政治特征:由于各洞(峒)远离政治中心,根据情况有的实行羁縻政策,有的则完全没有管理。随着帝国深入边陲以及各族群互动加深,朝廷或派兵镇守、镇压,或进行招抚,总体上山洞逐渐减少。这与历朝政府开边经略,对山洞进行治理有关。随着山洞渐次被开发,许多原来是“山洞”的地方不再称为“山洞”,而被称为“峒民”“峒僚”“洞寇”的人群,除了有种族的含义外,还具有政治的含义(或文化含义)。
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旧石器时代,洞穴居址作为人类聚落形态就已经存在。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就曾指出:“洞穴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者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⑤古代人类有选择寻找居住的洞穴,留下各个时代的洞穴堆积,在我国的华南、华北地区均分布着具有代表性的各时代洞穴。⑥一般来讲,这个时期的洞穴并非孤立、静态的存在,而是作为一个聚落系统发挥生产生活的功能。这一阶段的聚落形态主要为“洞穴-旷野”模式,也就是说,人类选择在洞穴,既要考虑洞穴作为遮蔽所的功能,又要考虑到以洞穴为中心的周围自然环境,尤其是食物资源的获取情况。⑦到了中石器时代⑧,随着原始农业的萌芽,人类社会开始由采集渐进到农业,由狩猎发展为畜牧⑨,在生产、生活技术水平提高的基础之上,人类从洞穴向更广阔的台地、平原、山冈进发。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建造技术高度发展,人们已经不再依赖洞穴,在各个适合人类生产生活的地形建造居所,形成聚落,并在不同地区发展出多元化的人类居住体系。在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华南地区所占数量不少,比较集中地分布在广东、广西、江西、云南等地区,浙江、福建、湖南等地也有少量分布,大概可以将遗址分为洞穴遗址、贝丘遗址、台地遗址三种类型。①从后两种类型足以证明人类的居址向多元化发展。在新石器晚期,人们已经大量建造公共广场、祭坛等建筑,聚落居址成为文明的标志。随着聚落的发展,中国个别地区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进入城邦模式。②
可见,早期人类由于生产生活技术水平较低,只能依赖洞穴作为庇护所,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对获取自然资源的需求,人类从“山洞”走向“旷野”,形成聚落,创造出越来越丰富的人类文明。那么可以想见,随着地区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提前进入“文明社会”、居住在城邦村落的族群在看待仍在“洞穴”居住的族群时,必定占有相对的心理优越感。而正是这种优越感带来的人们观念的变化,使得洞的意义开始延伸,也就是说“洞”在“文化先进”地区的人群看来,开始成为一种文化落后、野蛮未开化的象征。这种象征逐渐被“标签化”或“模式化”,形成了某一人群对另外一个人群的固有印象,如唐代刘禹锡称“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桴筏者,与华言不通。”③“居洞砦”是野蛮、未开化族群的重要特征之一。唐代以后,这些“居洞砦”的非汉人群一般被称为“峒民”或“峒獠”,其广泛分布于南方地区,如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写道:“峒獠者,岭表溪峒之民,古称山越,唐宋以来,开拓寝繁,自邕州以东,广州以西,皆推其雄长者为首领,籍其民为壮丁。”④这些分布广泛的“洞”,其地理环境、自然生态、社会组织特征又是如何呢?笔者拟以闽西象洞和海南黎峒作为例子进行分析。
宋开庆年间由胡太初所修的《临汀志》记载了有关象洞的情况,其文曰:
象洞,在武平县南一百里,接潮、梅界。林木蓊翳,旧传象出其间,故名。后渐刊木诛茅,遇萦纡怀抱之地,即为一聚落,如是者九十有九,故俗号“九十九洞”。其地膏沃,家善酝酿,邑人之象洞酒。洪刍有《老酒赋》,正谓此。但僻远负固,多不乐输,故置巡检寨以镇焉。①
按照作者的描述,象洞应该可以被认为是南方非汉民族居住的“山洞”的一种。以上材料可以说明:
第一,从自然生态上看,象洞原先是人迹罕至、丛箐林密的原始山林地带,在未开发之前,此地乃象群出没之地②,象洞因此而得名。
第二,从聚落形态看,象洞从原始森林变为人类聚居地的过程大概有三个步骤:首先,开辟山林,“刊木诛茅”;其次,选择“萦纡怀抱”的地理环境,在中间平坦、土地肥沃的地方开发成一个聚落;再次,随着山林开发的深入,各个“洞”被次第开发,如象洞形成了“九十九洞”的规模。笔者推论,“九十九”如此巧妙的数字,在此语境下应该不是实指,而是虚数,描述者只是想表达“洞”之数量极多而已。关于各洞之间的关系,应该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以地形看,各个“洞”周围山林林阻隔,交通不便,各洞之间可以保持相对独立的状态;而以名称看,象洞统称为“九十九洞”,说明各洞在“类型”上是相似的,不仅地理环境相似,族群多有相通,所以可以统称。
第三,从人文生态上看,洞中有平坦且肥沃土地可供“洞民”从事农业,并善于酿酒,其“象洞酒”在闻名于武平一邑;象洞早期居民不纳赋税,“僻远负固,多不乐输”,被认为是“化外之民”。随着王朝势力深入边陲,国家在非汉族群的地区驻兵,以控制当地“负固”之徒。
周去非《岭外代答》“海外黎蛮条”记载当地“黎峒”的情况,颇具代表性,可以看做是唐宋“蛮夷”聚落的一个典型,其文曰:
海南有黎母山,内为生黎,去州县远,不供赋役;外为熟黎,耕省地,供赋役,而各以所迩隶于四军州。生黎质直犷悍,不受欺触,本不为人患。熟黎多湖广、福建之奸民也,狡悍祸贼,外虽供赋于官,而阴结生黎以侵省地,邀掠行旅、居民,官吏经由村峒,多舍其家。峒中有王二娘者,黎之酋也,夫之名不闻。家饶于财,善用其众,力能制服群黎,朝廷赐封宜人,琼管有令于黎峒,必下王宜人,无不帖然。二娘死,女亦能继其业。昔崇宁中,王祖道经略广西,抚定黎贼九百七峒,结丁口六万四千,开通道路一千二百余里,自以为汉唐以来所不臣之地,皆入版图。①
本文记载了海南岛黎峒居民情况以及朝廷“开山洞”接管黎峒的过程,从该文可以较为直接了解被宋朝直接统治前的“峒”的基本情况:
第一,海南岛黎母山的居民成分有生黎、熟黎两种。海南峒中居民也是非汉族群,被分生黎、熟黎两种②,二者区别主要有两处:一是居住地理位置的远近,生黎住深山内,离政治中心远;熟黎住山外,耕种“省地”,与“省民”接壤;二是是否供赋役,“熟黎”多数来自湖广、福建地区(笔者猜测这些“熟黎”应多为汉人),然而在政府看来,他们却是“奸民”,因为他们暗自勾结生黎侵吞“省地”,目的在于以生黎身份占有“省地”后,可以逃避赋税,这也是他们被称为“黎”的根本原因。由此看来,汉人从“良民”变为“奸民”的评判标准在于这些百姓是否接受国家统一管理,并承担相应的服役纳税的义务,“良民”一旦变为“奸民”后,其与蛮夷常常是混淆不清的,并没有十分清楚的界限。如宋代《诸蕃志》也记载道:“黎,海南四郡岛上蛮也……去省地远者为生黎,近者为熟黎……黎之峒落日以繁滋,不知其几千百也,咸无统属,峒自为雄长,止于王、符、张、李数姓。”③
第二,“峒”是一个非汉族群的自治组织单位。海南黎母山峒中文中提到,“黎酋”王二娘凭借其家族势力和个人能力对“群黎”进行管理,并受到朝廷的赐封。这是朝廷的一种“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而“洞”就属于其中的一个基层组织。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称:“自唐宋以来内附,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洞”。④所谓的“种落”,指一个种族的聚落,也可以理解为族群的聚居区。族群人口数量不一,聚落的大小也不同,国家将聚落大的设州县,小的则称为“洞”。可见,宋代的“峒”是少数民族基层组织的一种,作为量词的“峒”,相当于现在一个村落或一个山区。
第三,海南黎峒有一定的人口数量。该文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峒中聚居人口概况,按文中所称的“抚定九百七峒,结丁口六万四千”计算,每个峒的丁口(成年男性)约为71人,如果将妇女儿童包括进去,可以推论宋代海南岛黎母山地区每个峒大约为二三百人。当然,各地的峒有大有小,各个种群有兴有衰,不能一概而论。如清代徐家干在《苗疆闻见录》描述西南苗人情况,也具体谈到聚落的大概人口数量:“苗人聚种而居,窟宅之地皆呼为寨,或二三百为一寨,或百数十家为一寨,依山傍涧,火种刀耕,其生性之蛮野,洵非政教所可及”①。所谓的“窟宅之地”“寨”,其意思应该与我们所分析的作为聚落形态的“峒”相似。另外,按照文中描述,清代的西南苗民与其他地方的“峒”民在生产、生活以及文化习性有着相似之处。
综合闽西象洞和海南黎峒两个典型个案,再结合其他文献,我们基本上可以理解唐宋以来“洞(峒)”作为聚落形态的基本特征:
第一,在地理位置上,“洞(峒)”多处于远离政治中心的偏远山区,经常处于万山之中,这些地区处于在南方的帝国边陲地带,山林阻隔,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多为非汉族群所居住。
第二,在村落特征上,经常表现为四周山峰(山林)环抱,中间有山坳平地。这种村落形态,一方面以有利的地形一定程度上阻隔或延缓了外族(朝廷)势力侵入;另一方面,中间平坳地区特别适合农业生产,保证了本地居民的物资供给。
第三,“洞(峒)”民的族群特征表现为,洞(峒)中居民基本上为非汉民族居住,具有“僻远负固,多不乐输”的特性,即不受朝廷控制,不承担纳税服役的义务。峒中有部分居民为汉族,这部分人经常是“逋负逃役”之人,因此也被政府认为“化外之民”。由此可见,“峒”与“非峒”的区别除了由种族区分的因素外,还在于是否纳税服役,是否接受教化,是否编入版籍。
第四,“洞(峒)”的政治特征:由于各洞(峒)远离政治中心,根据情况有的实行羁縻政策,有的则完全没有管理。随着帝国深入边陲以及各族群互动加深,朝廷或派兵镇守、镇压,或进行招抚,总体上山洞逐渐减少。这与历朝政府开边经略,对山洞进行治理有关。随着山洞渐次被开发,许多原来是“山洞”的地方不再称为“山洞”,而被称为“峒民”“峒僚”“洞寇”的人群,除了有种族的含义外,还具有政治的含义(或文化含义)。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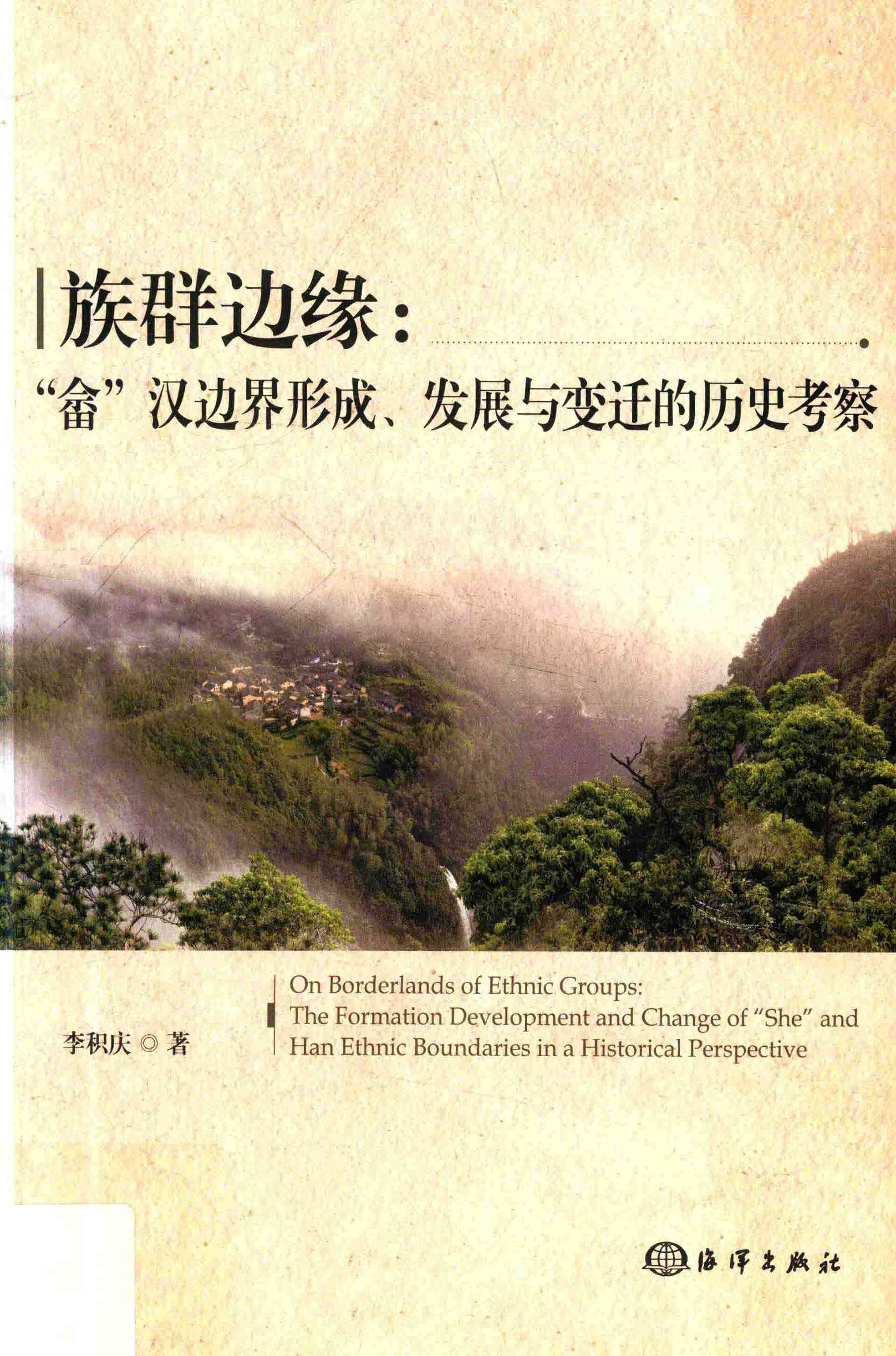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出版者:海洋出版社
本书从族群边界的理论角度,重新审视畲族形成、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在承认族群客观历史文化的同时,重点研究历史上“他者”(主要是汉族)对“畲”的社会定义以及“自者”(主要为南方非汉族群)自我族群认同的过程,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现实意义。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