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语境下的南方“畲洞”及其聚落人文
| 内容出处: |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图书 |
| 唯一号: | 130920020230003763 |
| 颗粒名称: | 第二节 文化语境下的南方“畲洞”及其聚落人文 |
| 分类号: | K288.3 |
| 页数: | 13 |
| 页码: | 36-48 |
| 摘要: | 本文分析了唐宋时期南方“畲洞”及其聚落人文的演变。 |
| 关键词: | 人文 畲洞 宋代 |
内容
历史上常将唐代以后“峒蛮”“峒獠”与畲族联系起来。“畲”不仅仅是一种耕作方式,还具有聚落的含义。“畲”从一种经济形式或聚落形态的称谓演变为一类族群的称谓,其与汉文化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畲”作为一种溪峒地区或部落基层组织存在,其与“洞(峒)”一样,均经历过本义——聚落称谓——族群称谓的转变过程。在以华夏为中心的民族观指导下,畲、峒的文化特征成为汉族对南方非汉族群分类的重要依据。
一、山洞:从洞穴居址到“蛮夷”聚落称谓的转变
“畲”和“峒”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学界常将历史上出现在南方地区“山洞”“溪洞”“峒蛮”“峒獠”等族群与畲民联系起来。峒,也称“洞”,或“山洞”,关于山洞的解释,学术界上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自然环境说,指原来未设政区的偏远之处的山间溪谷;①二是民族构成说,专门指南方山区非汉族土著民族;②三是地方组织说,指随着中原王朝政治在华南社会的扩展,在国家行政统治未能到达的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由土豪势力建立起来的具有实质性的地域统治体制或特殊的军政单位。③以上观点将“溪洞”并称,各观点并不完全矛盾,只不过是将山洞放置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中讨论而已。如李荣村指出:“唐宋时凡近山的蛮夷住地、聚落或羁縻州洞等都可称作峒,又称溪峒,也就是蛮洞的意思,但绝不当作狭义的洞穴解释。”④李氏强调以特定历史条件来考察“洞”的含义,这是十分有道理的,但至于“洞”为何从表示“岩洞”“窟穴”的原意,变为少数民族“聚落”或组织,那还是得探寻洞的本源,方可做出解释。
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旧石器时代,洞穴居址作为人类聚落形态就已经存在。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就曾指出:“洞穴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者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⑤古代人类有选择寻找居住的洞穴,留下各个时代的洞穴堆积,在我国的华南、华北地区均分布着具有代表性的各时代洞穴。⑥一般来讲,这个时期的洞穴并非孤立、静态的存在,而是作为一个聚落系统发挥生产生活的功能。这一阶段的聚落形态主要为“洞穴-旷野”模式,也就是说,人类选择在洞穴,既要考虑洞穴作为遮蔽所的功能,又要考虑到以洞穴为中心的周围自然环境,尤其是食物资源的获取情况。⑦到了中石器时代⑧,随着原始农业的萌芽,人类社会开始由采集渐进到农业,由狩猎发展为畜牧⑨,在生产、生活技术水平提高的基础之上,人类从洞穴向更广阔的台地、平原、山冈进发。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建造技术高度发展,人们已经不再依赖洞穴,在各个适合人类生产生活的地形建造居所,形成聚落,并在不同地区发展出多元化的人类居住体系。在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华南地区所占数量不少,比较集中地分布在广东、广西、江西、云南等地区,浙江、福建、湖南等地也有少量分布,大概可以将遗址分为洞穴遗址、贝丘遗址、台地遗址三种类型。①从后两种类型足以证明人类的居址向多元化发展。在新石器晚期,人们已经大量建造公共广场、祭坛等建筑,聚落居址成为文明的标志。随着聚落的发展,中国个别地区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进入城邦模式。②
可见,早期人类由于生产生活技术水平较低,只能依赖洞穴作为庇护所,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对获取自然资源的需求,人类从“山洞”走向“旷野”,形成聚落,创造出越来越丰富的人类文明。那么可以想见,随着地区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提前进入“文明社会”、居住在城邦村落的族群在看待仍在“洞穴”居住的族群时,必定占有相对的心理优越感。而正是这种优越感带来的人们观念的变化,使得洞的意义开始延伸,也就是说“洞”在“文化先进”地区的人群看来,开始成为一种文化落后、野蛮未开化的象征。这种象征逐渐被“标签化”或“模式化”,形成了某一人群对另外一个人群的固有印象,如唐代刘禹锡称“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桴筏者,与华言不通。”③“居洞砦”是野蛮、未开化族群的重要特征之一。唐代以后,这些“居洞砦”的非汉人群一般被称为“峒民”或“峒獠”,其广泛分布于南方地区,如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写道:“峒獠者,岭表溪峒之民,古称山越,唐宋以来,开拓寝繁,自邕州以东,广州以西,皆推其雄长者为首领,籍其民为壮丁。”④这些分布广泛的“洞”,其地理环境、自然生态、社会组织特征又是如何呢?笔者拟以闽西象洞和海南黎峒作为例子进行分析。
宋开庆年间由胡太初所修的《临汀志》记载了有关象洞的情况,其文曰:
象洞,在武平县南一百里,接潮、梅界。林木蓊翳,旧传象出其间,故名。后渐刊木诛茅,遇萦纡怀抱之地,即为一聚落,如是者九十有九,故俗号“九十九洞”。其地膏沃,家善酝酿,邑人之象洞酒。洪刍有《老酒赋》,正谓此。但僻远负固,多不乐输,故置巡检寨以镇焉。①
按照作者的描述,象洞应该可以被认为是南方非汉民族居住的“山洞”的一种。以上材料可以说明:
第一,从自然生态上看,象洞原先是人迹罕至、丛箐林密的原始山林地带,在未开发之前,此地乃象群出没之地②,象洞因此而得名。
第二,从聚落形态看,象洞从原始森林变为人类聚居地的过程大概有三个步骤:首先,开辟山林,“刊木诛茅”;其次,选择“萦纡怀抱”的地理环境,在中间平坦、土地肥沃的地方开发成一个聚落;再次,随着山林开发的深入,各个“洞”被次第开发,如象洞形成了“九十九洞”的规模。笔者推论,“九十九”如此巧妙的数字,在此语境下应该不是实指,而是虚数,描述者只是想表达“洞”之数量极多而已。关于各洞之间的关系,应该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以地形看,各个“洞”周围山林林阻隔,交通不便,各洞之间可以保持相对独立的状态;而以名称看,象洞统称为“九十九洞”,说明各洞在“类型”上是相似的,不仅地理环境相似,族群多有相通,所以可以统称。
第三,从人文生态上看,洞中有平坦且肥沃土地可供“洞民”从事农业,并善于酿酒,其“象洞酒”在闻名于武平一邑;象洞早期居民不纳赋税,“僻远负固,多不乐输”,被认为是“化外之民”。随着王朝势力深入边陲,国家在非汉族群的地区驻兵,以控制当地“负固”之徒。
周去非《岭外代答》“海外黎蛮条”记载当地“黎峒”的情况,颇具代表性,可以看做是唐宋“蛮夷”聚落的一个典型,其文曰:
海南有黎母山,内为生黎,去州县远,不供赋役;外为熟黎,耕省地,供赋役,而各以所迩隶于四军州。生黎质直犷悍,不受欺触,本不为人患。熟黎多湖广、福建之奸民也,狡悍祸贼,外虽供赋于官,而阴结生黎以侵省地,邀掠行旅、居民,官吏经由村峒,多舍其家。峒中有王二娘者,黎之酋也,夫之名不闻。家饶于财,善用其众,力能制服群黎,朝廷赐封宜人,琼管有令于黎峒,必下王宜人,无不帖然。二娘死,女亦能继其业。昔崇宁中,王祖道经略广西,抚定黎贼九百七峒,结丁口六万四千,开通道路一千二百余里,自以为汉唐以来所不臣之地,皆入版图。①
本文记载了海南岛黎峒居民情况以及朝廷“开山洞”接管黎峒的过程,从该文可以较为直接了解被宋朝直接统治前的“峒”的基本情况:
第一,海南岛黎母山的居民成分有生黎、熟黎两种。海南峒中居民也是非汉族群,被分生黎、熟黎两种②,二者区别主要有两处:一是居住地理位置的远近,生黎住深山内,离政治中心远;熟黎住山外,耕种“省地”,与“省民”接壤;二是是否供赋役,“熟黎”多数来自湖广、福建地区(笔者猜测这些“熟黎”应多为汉人),然而在政府看来,他们却是“奸民”,因为他们暗自勾结生黎侵吞“省地”,目的在于以生黎身份占有“省地”后,可以逃避赋税,这也是他们被称为“黎”的根本原因。由此看来,汉人从“良民”变为“奸民”的评判标准在于这些百姓是否接受国家统一管理,并承担相应的服役纳税的义务,“良民”一旦变为“奸民”后,其与蛮夷常常是混淆不清的,并没有十分清楚的界限。如宋代《诸蕃志》也记载道:“黎,海南四郡岛上蛮也……去省地远者为生黎,近者为熟黎……黎之峒落日以繁滋,不知其几千百也,咸无统属,峒自为雄长,止于王、符、张、李数姓。”③
第二,“峒”是一个非汉族群的自治组织单位。海南黎母山峒中文中提到,“黎酋”王二娘凭借其家族势力和个人能力对“群黎”进行管理,并受到朝廷的赐封。这是朝廷的一种“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而“洞”就属于其中的一个基层组织。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称:“自唐宋以来内附,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洞”。④所谓的“种落”,指一个种族的聚落,也可以理解为族群的聚居区。族群人口数量不一,聚落的大小也不同,国家将聚落大的设州县,小的则称为“洞”。可见,宋代的“峒”是少数民族基层组织的一种,作为量词的“峒”,相当于现在一个村落或一个山区。
第三,海南黎峒有一定的人口数量。该文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峒中聚居人口概况,按文中所称的“抚定九百七峒,结丁口六万四千”计算,每个峒的丁口(成年男性)约为71人,如果将妇女儿童包括进去,可以推论宋代海南岛黎母山地区每个峒大约为二三百人。当然,各地的峒有大有小,各个种群有兴有衰,不能一概而论。如清代徐家干在《苗疆闻见录》描述西南苗人情况,也具体谈到聚落的大概人口数量:“苗人聚种而居,窟宅之地皆呼为寨,或二三百为一寨,或百数十家为一寨,依山傍涧,火种刀耕,其生性之蛮野,洵非政教所可及”①。所谓的“窟宅之地”“寨”,其意思应该与我们所分析的作为聚落形态的“峒”相似。另外,按照文中描述,清代的西南苗民与其他地方的“峒”民在生产、生活以及文化习性有着相似之处。
综合闽西象洞和海南黎峒两个典型个案,再结合其他文献,我们基本上可以理解唐宋以来“洞(峒)”作为聚落形态的基本特征:
第一,在地理位置上,“洞(峒)”多处于远离政治中心的偏远山区,经常处于万山之中,这些地区处于在南方的帝国边陲地带,山林阻隔,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多为非汉族群所居住。
第二,在村落特征上,经常表现为四周山峰(山林)环抱,中间有山坳平地。这种村落形态,一方面以有利的地形一定程度上阻隔或延缓了外族(朝廷)势力侵入;另一方面,中间平坳地区特别适合农业生产,保证了本地居民的物资供给。
第三,“洞(峒)”民的族群特征表现为,洞(峒)中居民基本上为非汉民族居住,具有“僻远负固,多不乐输”的特性,即不受朝廷控制,不承担纳税服役的义务。峒中有部分居民为汉族,这部分人经常是“逋负逃役”之人,因此也被政府认为“化外之民”。由此可见,“峒”与“非峒”的区别除了由种族区分的因素外,还在于是否纳税服役,是否接受教化,是否编入版籍。
第四,“洞(峒)”的政治特征:由于各洞(峒)远离政治中心,根据情况有的实行羁縻政策,有的则完全没有管理。随着帝国深入边陲以及各族群互动加深,朝廷或派兵镇守、镇压,或进行招抚,总体上山洞逐渐减少。这与历朝政府开边经略,对山洞进行治理有关。随着山洞渐次被开发,许多原来是“山洞”的地方不再称为“山洞”,而被称为“峒民”“峒僚”“洞寇”的人群,除了有种族的含义外,还具有政治的含义(或文化含义)。
二、作为地名和聚落形态的“畲”
宋元时期,畲作为地名常被文献记载。《宋史·许应龙传》记载“距州(潮州)六七十里曰山斜,峒獠所聚,匄耕土田,不输赋,禁兵与哄,应龙平决之。”①可见“山斜(畲)”作为一个地区的名称,其距离潮州城有六七十里,该“山斜”为“峒獠”聚居、耕作的地区。在广东,“輋”字是非汉民族的一种居住形式,清代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称:“粤人以山林中结竹木障覆居息为輋,故称瑶所止曰輋”②赵希璜也在《横輋》一文中对輋进行解释:“(輋)音斜,粤呼山居者为輋客。”③清代《浮山志》中为张九钺的罗浮诗后作注曰:“畲、輋,俗皆读如斜”。④
实际上,在广东一些地区,“輋”也指山脊,如民国《龙门县志》记载:“土人谓山低缺处为凹,谓山谷为迳,谓山脊为輋。”⑤由此可见,畲、輋、斜等在许多情境下并不作某一类人群的称谓来解释。
再如南宋刘克庄的《漳州谕畲》,该文是畲族史研究中极具地位的一篇重要文献。该篇正文其“畬(畲)”字共出现23次,笔者认为关于这些“畬(畲)”字的解释,根据上下文意思,可分为三类。由表1-1可以看出《漳州谕畲》中并非每一个“畬(畲)”字都作“畲民”解释,有一些应该用类似“溪洞地区”聚落名称来解释,还有一些二者均解释得通的。
第一类“畬(畲)”用族群称谓解释比较合理。如“凡溪洞种类不一:曰蛮、曰猺、曰黎、曰蜑,在漳者曰畬。”此处的畲应该与蛮、猺、黎、蜑并称,说明他们是溪洞种类下属的一类叫“畲”的人;再如“彼畬曷尝读范史”,应该解释为:那些“畲人”何尝读过范晔的《后汉书》呢?
第二类“畬(畲)”用溪峒地区或部落基层组织解释比较合理。如“汀赣贼入畬者”应该解释为,一些汀赣贼逃入畲洞地区;再如“南畬三十余所酋长各籍户口三十余家”,合理解释是:隶属南畲地区或组织的三十多个部落,其酋长分别将本所三十余家编入户籍;又如“清白之吏,固畬之所贵欤”,其合理解释是:清廉正直的官员,乃是巩固畲峒地区珍贵的人才。
第三类就是既可以将“畬(畲)”理解为溪洞地区,又可以解释为溪洞种类、如“二畬既定”可以解释为平定二处畲峒地区,也可以解释为平定二处畲峒地区的族群;再如“畬田”“畬长”可以解释为畲峒地区的田地、酋长,也可以解释为畲人的田地、酋长。
畲作为一种聚落或基层组织解释,还可以在一些文献中体现。如南宋时的赵必岊,字次山,“乡寓公吴允文浚奉密诏以江西招讨使举义反正,结约次山协谋兴复,战不利。允文奔漳州为都督文丞相天祥所杀,次山解兵隐汀州之畬中,踰年以疾终。”②畲作为地名普遍出现在闽粤一些地区中,如《元经世大典序录》载:“(至元)十七年八月,陈桂龙父子反漳州,据山砦,桂龙在九层漈畲,陈吊眼在漳浦山砦,陈三官水篆畲,罗半天梅泷长窖,陈大妇客寮畲。”①上文所称“九层漈畲”“水篆畲”“客寮畲”与“漳浦山砦”“梅泷长窖”并称,均指闽南的一些地名。元代有“畲洞”并称的记载,如《元史》称:“至元十七年,陈桂龙据漳州反,唆都率兵讨之,桂龙亡入畲洞。”②按民国《诏安县志》解释称:“按吊眼贼巢及桂龙所逃畲洞,即诏之乌山十八洞等处,南胜畲寇系其余党,寇乱数十年间。”③陈吊眼、陈桂龙等畲洞为诏安的“乌山十八洞”,所谓的“十八洞”应该是十几个村落(洞)组成一个地区,统称“畲洞”。
畲和洞联系起来作为聚居区的典型例子莫过于百家畲洞。《明史》载:“漳平,(漳州)府西北……东南有象湖山。南有百家畲洞,踞龙岩、安溪、龙溪、南靖、漳平五县之交。”④明代黄仲昭在《八闽通志》中将百家畲洞的地理、人文介绍得更为详细:
百家畲洞,在县南永福里。界龙岩、安溪、龙溪、南靖、漳平五县间。万山环抱,四面阻塞。洞口陡隘,仅通人行。其中深邃宽广,可容百余家。畲田播种,足给衣食。四方亡命者多逋聚其间。凭恃险远,易于为乱。宣德正统间,尝有江志贤、李乌觜、卢赤须、罗兴进者,乌合郡(恐为群之误,笔者注)丑,跳梁出没,至动方岳。守臣连年剿捕,仅得宁息。然服则人,叛则兽,无常性也。自漳平设县以来,官政易及,不复反侧。然尤在司民社者控御得其道云。⑤
清代方志龙岩、漳平等地方志关于百家畲洞的记载,均沿袭《八闽通志》,仅在个别字句稍作增删。⑥另据清道光《漳平县志》记载:
永福(漳平县下的一个里)自为一区,其山之名者有双髻山、猛虎山、大壮山,与百家畲洞于环阻之中又复有平者,然其细已甚不胜纪。①
综合弘治《八闽通志》和道光《漳平县志》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第一,百家畲洞,又称百家畲,这里的“畲”指的是地名。也就是说,畲与洞可以合称,也可以分开单独作为地名。
第二,百家畲洞具有典型的南方少数民族“山洞”特征,表现出“万山环抱,四面阻塞”、中间“深邃宽广”的自然地理特征以及“四方亡命者多逋聚其间”的“化外之民”聚居地的人文特征。
第三,按照“百家畲洞”字面意思,结合象洞有“九十九洞”的特点,我们估计百家畲洞也是由多个洞组合而成。而在漳平一地,与百家畲洞所具有的“于环阻之中又复有平者”地理人文特征的畲洞还有很多,只是无法一一道来,所谓的“其细已甚不胜纪”。
清代以来,许多地方还保存畲(輋)的地名,如李调元《南越笔记》记载广东地区輋人及其聚居地区的情况:“輋人:澄海山中有輋户……輋巢居也;猺所止曰屳、曰峒、亦曰輋。海丰之地,有曰罗輋,曰葫芦輋,曰大溪輋。兴宁有大信輋,归善有窑輋。”②
直到现在,闽粤赣地区仍有许多地名带有“畲”字,③如福建连城带有“畲”字的地名就有19个,而武平也有17个。④其余的如长汀的下畲;上杭的大畲;龙岩的郭畲、小高畲、畲背、洋畲、下经畲;漳平的谢畲、罗畲、百种畲,东下畲;华安的官畲、南靖的桂竹畲、后畲、上麻畲;云霄的桃畲、上梨畲、下梨畲、坝头畲,等等。
学者推论这些地区与畲瑶等非汉族群有一定的联系。清代温仲和在光绪《嘉应州志》中,曾对有关“畲”的地名与族群关系作一番论述,他说:“今地以畲名者尚多有之,而所谓猺獠则绝无其人,盖日久皆化为熟户,而风俗与居民无异矣。”①
在作者看来,带有“畲”字的地名与“猺獠”存在着某种关系,只不过这些非汉民族变为“熟户”后,不再称为“畲”,但地名仍存于今。
再如著名学者徐松石先生也提出:“畲瑶即古代所谓山越。在广东东部散布甚广。平远、蕉岭、梅县、河源、惠来、丰顺、新安等地,现在还有许多畲字或輋字的地名。”②陈龙、吴炳奎、刘大可等学者也对闽粤赣一些地区内带有“畲”字的地名进行考证,以证明历史上畲瑶等族群在该地存在的可能性。③因此,有学者将这些带“畲”字的地名视为闽粤边地区畲族活动史的活“化石”。④
需要指出的是,带有“畲(輋)”地名的出现时间与“猺獠”族群在该地的居住时间,孰先孰后,目前仍无法考证。我们或许可以推论:古代汉人常将“猺獠”生活的地方称为“畲”,正如将南方非汉族群聚居区称为“山洞”一样。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畲”地名的命名与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遗存有关系。司徒尚纪认为在广东等地区,“没有水利工程灌溉的丘陵、山地,其被开发利用土地通名为畬地或畬田,实为梯田,过去实行刀耕火种,至今在海南、粤北黎、瑶地区仍有残存,故以畬为首尾地名在内陆山区较普遍。”广东客家人聚居平远县就有许多以畲命名的地名,反映的是“山区梯田文化景观”。⑤
因此,我们认为“畲”的地名未必一定和非汉族群聚落有关,即:“畲”作为一种地名的命名方式在闽粤赣地区已经形成一种传统,人们用其称呼一些“山脊”或山地地名,而这并不一定和“猺獠”族群有必然的联系。
三、“畲”“峒”生态文化语境下的一种族群分类
在古代中国,由于受到大一统观念的影响,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民族史的撰述,都体现出了诸如“夷夏同祖认同、华夷一家认同、共属中国认同、华夏文化认同”的大一统意识。①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华夏文化在几千年的民族史撰述中一直处于被表述的中心,四方“夷狄”则处于从属地位。而在具体实践中,华夏民族自春秋战国以后,在与周边非华夏民族的互动过程中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表现出华夏族及其文化不断向边陲扩张,最终使得各非华夏民族淹没在华夏族的“海洋”中或成为“华夏海洋”中的“非华夏孤岛”。
因此,在重新审视我国古代民族史时,我们必须将历代有关于“非华夏”族群的文字记载置于当时的社会情境来分析,具体来说:一是在汉文化语境下,这种记载多大程度反映了文字记载者的立场、态度及情感,而作为文本的历史记忆又反映了当时什么样的历史心性?二是这种记载中的文化特征,是否能够反映“异族”的实际情况,即这种客观的文化特征描述能否与“异族”的实际认同情况相一致?或者说,对“他者”只是文字记载者单方面的认同?
“畲”作为一种族群的出现,需要在生态语境和文化语境下考察。首先,自然生态无疑是任何一种族群和文化产生的最基础因素。正如我国历史上形成的游牧与农耕文明的生态界线,自然生态上差异导致了文化的差异,从而形成了文化特色截然不同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畲”作为原始的、粗放的耕作方式,与精耕细作的汉族农业也存在一条若隐若现的生态边界,这种自然生态的差异在族群文化特征上打上鲜明的烙印,这种迥异于“他者”的文化特征,成为“他者”族群观察另一个族群的切入点。根据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给文化所作的定义,文化应该包含了人类经历的各个方面②。按照这种定义,一个族群的文化特征应该包罗万象,而作为文字记载的族群,其呈现给后人的文化特征,充其量不过是一些静态的、被认为的诸多特征中较为典型的、有异于他者的特征。
笔者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农业的变迁认为,“畬(畲)田”的耕作方式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历史上从事“畬田”农业的族群,除了被称为“畬田”民族外,实际上,在某一历史阶段,汉族也从事“畬(烧)田”农业。③主要区别在于:随着汉族农业技术的发展,在汉族社会中,“畬田”的耕作方式逐渐被精耕细作农业所取代;而在一些非汉族群中,“畬田”农业作为一种技术要求不高、较易实施的粗放农业,仍一直被沿用。
随着代表农业文明的汉族文化不断扩张,“畬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遭遇,并产生了生态冲突。这种冲突首先发生在两种生态文化的锋线,也就是在两种生态文化的边界地区是生态矛盾最集中的地方。正如在古代中国,长城沿线被视为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冲突最集中的地方,长城的分布与走向基本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生态系统的分界线。生态文化的冲突带来族群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唐宋时期特别明显。“畬(畲)”之所以在唐宋时期的诗文中大量出现,与唐宋时期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时期,随着帝国华夏化进程加快,中国南方各个地区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北方汉人带来的先进农业与被认为是原始农业残余的“畬田”农业遭遇时,这种文化冲击(cultureshock)使得“畬(畲)”作为一种猎奇、述异、诗化见诸汉人知识分子的笔端。
尽管也有大量诗人对“畬(畲)”不吝溢美之词,但无法改变整个主流文化对“畲”的看法,特别是当“畲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在资源上冲突加剧时,“畲”一种文化标签常贴在非汉族群身上,目的就是将其边缘化。
第三节 小结
本章从生态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唐宋以来与畲族及其先民相关的自然生态和聚落人文情况。本章的主要论点有:
(1)“畲”作为一种古老的耕作方式,不仅在时间维度上,并且在空间广度上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中。要探讨“畲”如何成为一个族群的称谓,必须将其放置于特定的生态语境和文化语境中考察。
(2)在历史上中国中部、南方地区,曾存在畬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的生态冲突。畬田农业是一种较为古老的耕作方式,其在文化特征与日本学者提出的“照叶树林文化”特征相似。唐宋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中心南移,以精耕细作为代表的汉人农业在中国南方地区迅速发展,畬田农业呈现出明显的退缩趋势,宋代以后南方地区梯田的增多,说明了这个现象。随着对生态资源的需求,代表汉人农业的精耕细作与代表古代农耕方式的残存形态的畬田农业开始发生冲突,其生态边界恰好为汉族与非汉族群的边界大部分吻合。
(3)“畲”不仅仅是一种耕作方式,还具有带有聚落的含义。“畲”之所以从一种经济形式或聚落形态的称谓演变为一类族群的称谓.这与汉文化语境有着
密切的关系。“畲(輋)”或“山洞”,起先是作为人类居址称谓而存在的,这种特定的自然生态造就了特殊的聚落文化,从而成为生活在该地区人群的一种人文特征。
(4)在以华夏为中心的民族观指导下,汉人以从事特殊耕作方式(畲、輋),或居住在特殊聚落形态(洞、峒)作为文化特征,将南方非汉族群标签化。本章通过考察闽西象洞和海南黎峒两个个案,总结出作为聚落形态的“畲”“峒”的村落形态特征、族群构成、地方组织方式以及政治人文特征等。以此证明:“畲”或“峒”作为非汉人群的聚落、组织或族群称谓,均是在汉文化语境中产生的。在这种文化语境中,畲(輋)、峒(洞)除了具有区分种族的意义外,还具有政治和文化的意义。
一、山洞:从洞穴居址到“蛮夷”聚落称谓的转变
“畲”和“峒”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学界常将历史上出现在南方地区“山洞”“溪洞”“峒蛮”“峒獠”等族群与畲民联系起来。峒,也称“洞”,或“山洞”,关于山洞的解释,学术界上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自然环境说,指原来未设政区的偏远之处的山间溪谷;①二是民族构成说,专门指南方山区非汉族土著民族;②三是地方组织说,指随着中原王朝政治在华南社会的扩展,在国家行政统治未能到达的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由土豪势力建立起来的具有实质性的地域统治体制或特殊的军政单位。③以上观点将“溪洞”并称,各观点并不完全矛盾,只不过是将山洞放置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中讨论而已。如李荣村指出:“唐宋时凡近山的蛮夷住地、聚落或羁縻州洞等都可称作峒,又称溪峒,也就是蛮洞的意思,但绝不当作狭义的洞穴解释。”④李氏强调以特定历史条件来考察“洞”的含义,这是十分有道理的,但至于“洞”为何从表示“岩洞”“窟穴”的原意,变为少数民族“聚落”或组织,那还是得探寻洞的本源,方可做出解释。
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旧石器时代,洞穴居址作为人类聚落形态就已经存在。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就曾指出:“洞穴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者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⑤古代人类有选择寻找居住的洞穴,留下各个时代的洞穴堆积,在我国的华南、华北地区均分布着具有代表性的各时代洞穴。⑥一般来讲,这个时期的洞穴并非孤立、静态的存在,而是作为一个聚落系统发挥生产生活的功能。这一阶段的聚落形态主要为“洞穴-旷野”模式,也就是说,人类选择在洞穴,既要考虑洞穴作为遮蔽所的功能,又要考虑到以洞穴为中心的周围自然环境,尤其是食物资源的获取情况。⑦到了中石器时代⑧,随着原始农业的萌芽,人类社会开始由采集渐进到农业,由狩猎发展为畜牧⑨,在生产、生活技术水平提高的基础之上,人类从洞穴向更广阔的台地、平原、山冈进发。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建造技术高度发展,人们已经不再依赖洞穴,在各个适合人类生产生活的地形建造居所,形成聚落,并在不同地区发展出多元化的人类居住体系。在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华南地区所占数量不少,比较集中地分布在广东、广西、江西、云南等地区,浙江、福建、湖南等地也有少量分布,大概可以将遗址分为洞穴遗址、贝丘遗址、台地遗址三种类型。①从后两种类型足以证明人类的居址向多元化发展。在新石器晚期,人们已经大量建造公共广场、祭坛等建筑,聚落居址成为文明的标志。随着聚落的发展,中国个别地区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进入城邦模式。②
可见,早期人类由于生产生活技术水平较低,只能依赖洞穴作为庇护所,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对获取自然资源的需求,人类从“山洞”走向“旷野”,形成聚落,创造出越来越丰富的人类文明。那么可以想见,随着地区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提前进入“文明社会”、居住在城邦村落的族群在看待仍在“洞穴”居住的族群时,必定占有相对的心理优越感。而正是这种优越感带来的人们观念的变化,使得洞的意义开始延伸,也就是说“洞”在“文化先进”地区的人群看来,开始成为一种文化落后、野蛮未开化的象征。这种象征逐渐被“标签化”或“模式化”,形成了某一人群对另外一个人群的固有印象,如唐代刘禹锡称“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桴筏者,与华言不通。”③“居洞砦”是野蛮、未开化族群的重要特征之一。唐代以后,这些“居洞砦”的非汉人群一般被称为“峒民”或“峒獠”,其广泛分布于南方地区,如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写道:“峒獠者,岭表溪峒之民,古称山越,唐宋以来,开拓寝繁,自邕州以东,广州以西,皆推其雄长者为首领,籍其民为壮丁。”④这些分布广泛的“洞”,其地理环境、自然生态、社会组织特征又是如何呢?笔者拟以闽西象洞和海南黎峒作为例子进行分析。
宋开庆年间由胡太初所修的《临汀志》记载了有关象洞的情况,其文曰:
象洞,在武平县南一百里,接潮、梅界。林木蓊翳,旧传象出其间,故名。后渐刊木诛茅,遇萦纡怀抱之地,即为一聚落,如是者九十有九,故俗号“九十九洞”。其地膏沃,家善酝酿,邑人之象洞酒。洪刍有《老酒赋》,正谓此。但僻远负固,多不乐输,故置巡检寨以镇焉。①
按照作者的描述,象洞应该可以被认为是南方非汉民族居住的“山洞”的一种。以上材料可以说明:
第一,从自然生态上看,象洞原先是人迹罕至、丛箐林密的原始山林地带,在未开发之前,此地乃象群出没之地②,象洞因此而得名。
第二,从聚落形态看,象洞从原始森林变为人类聚居地的过程大概有三个步骤:首先,开辟山林,“刊木诛茅”;其次,选择“萦纡怀抱”的地理环境,在中间平坦、土地肥沃的地方开发成一个聚落;再次,随着山林开发的深入,各个“洞”被次第开发,如象洞形成了“九十九洞”的规模。笔者推论,“九十九”如此巧妙的数字,在此语境下应该不是实指,而是虚数,描述者只是想表达“洞”之数量极多而已。关于各洞之间的关系,应该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以地形看,各个“洞”周围山林林阻隔,交通不便,各洞之间可以保持相对独立的状态;而以名称看,象洞统称为“九十九洞”,说明各洞在“类型”上是相似的,不仅地理环境相似,族群多有相通,所以可以统称。
第三,从人文生态上看,洞中有平坦且肥沃土地可供“洞民”从事农业,并善于酿酒,其“象洞酒”在闻名于武平一邑;象洞早期居民不纳赋税,“僻远负固,多不乐输”,被认为是“化外之民”。随着王朝势力深入边陲,国家在非汉族群的地区驻兵,以控制当地“负固”之徒。
周去非《岭外代答》“海外黎蛮条”记载当地“黎峒”的情况,颇具代表性,可以看做是唐宋“蛮夷”聚落的一个典型,其文曰:
海南有黎母山,内为生黎,去州县远,不供赋役;外为熟黎,耕省地,供赋役,而各以所迩隶于四军州。生黎质直犷悍,不受欺触,本不为人患。熟黎多湖广、福建之奸民也,狡悍祸贼,外虽供赋于官,而阴结生黎以侵省地,邀掠行旅、居民,官吏经由村峒,多舍其家。峒中有王二娘者,黎之酋也,夫之名不闻。家饶于财,善用其众,力能制服群黎,朝廷赐封宜人,琼管有令于黎峒,必下王宜人,无不帖然。二娘死,女亦能继其业。昔崇宁中,王祖道经略广西,抚定黎贼九百七峒,结丁口六万四千,开通道路一千二百余里,自以为汉唐以来所不臣之地,皆入版图。①
本文记载了海南岛黎峒居民情况以及朝廷“开山洞”接管黎峒的过程,从该文可以较为直接了解被宋朝直接统治前的“峒”的基本情况:
第一,海南岛黎母山的居民成分有生黎、熟黎两种。海南峒中居民也是非汉族群,被分生黎、熟黎两种②,二者区别主要有两处:一是居住地理位置的远近,生黎住深山内,离政治中心远;熟黎住山外,耕种“省地”,与“省民”接壤;二是是否供赋役,“熟黎”多数来自湖广、福建地区(笔者猜测这些“熟黎”应多为汉人),然而在政府看来,他们却是“奸民”,因为他们暗自勾结生黎侵吞“省地”,目的在于以生黎身份占有“省地”后,可以逃避赋税,这也是他们被称为“黎”的根本原因。由此看来,汉人从“良民”变为“奸民”的评判标准在于这些百姓是否接受国家统一管理,并承担相应的服役纳税的义务,“良民”一旦变为“奸民”后,其与蛮夷常常是混淆不清的,并没有十分清楚的界限。如宋代《诸蕃志》也记载道:“黎,海南四郡岛上蛮也……去省地远者为生黎,近者为熟黎……黎之峒落日以繁滋,不知其几千百也,咸无统属,峒自为雄长,止于王、符、张、李数姓。”③
第二,“峒”是一个非汉族群的自治组织单位。海南黎母山峒中文中提到,“黎酋”王二娘凭借其家族势力和个人能力对“群黎”进行管理,并受到朝廷的赐封。这是朝廷的一种“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而“洞”就属于其中的一个基层组织。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称:“自唐宋以来内附,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洞”。④所谓的“种落”,指一个种族的聚落,也可以理解为族群的聚居区。族群人口数量不一,聚落的大小也不同,国家将聚落大的设州县,小的则称为“洞”。可见,宋代的“峒”是少数民族基层组织的一种,作为量词的“峒”,相当于现在一个村落或一个山区。
第三,海南黎峒有一定的人口数量。该文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峒中聚居人口概况,按文中所称的“抚定九百七峒,结丁口六万四千”计算,每个峒的丁口(成年男性)约为71人,如果将妇女儿童包括进去,可以推论宋代海南岛黎母山地区每个峒大约为二三百人。当然,各地的峒有大有小,各个种群有兴有衰,不能一概而论。如清代徐家干在《苗疆闻见录》描述西南苗人情况,也具体谈到聚落的大概人口数量:“苗人聚种而居,窟宅之地皆呼为寨,或二三百为一寨,或百数十家为一寨,依山傍涧,火种刀耕,其生性之蛮野,洵非政教所可及”①。所谓的“窟宅之地”“寨”,其意思应该与我们所分析的作为聚落形态的“峒”相似。另外,按照文中描述,清代的西南苗民与其他地方的“峒”民在生产、生活以及文化习性有着相似之处。
综合闽西象洞和海南黎峒两个典型个案,再结合其他文献,我们基本上可以理解唐宋以来“洞(峒)”作为聚落形态的基本特征:
第一,在地理位置上,“洞(峒)”多处于远离政治中心的偏远山区,经常处于万山之中,这些地区处于在南方的帝国边陲地带,山林阻隔,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多为非汉族群所居住。
第二,在村落特征上,经常表现为四周山峰(山林)环抱,中间有山坳平地。这种村落形态,一方面以有利的地形一定程度上阻隔或延缓了外族(朝廷)势力侵入;另一方面,中间平坳地区特别适合农业生产,保证了本地居民的物资供给。
第三,“洞(峒)”民的族群特征表现为,洞(峒)中居民基本上为非汉民族居住,具有“僻远负固,多不乐输”的特性,即不受朝廷控制,不承担纳税服役的义务。峒中有部分居民为汉族,这部分人经常是“逋负逃役”之人,因此也被政府认为“化外之民”。由此可见,“峒”与“非峒”的区别除了由种族区分的因素外,还在于是否纳税服役,是否接受教化,是否编入版籍。
第四,“洞(峒)”的政治特征:由于各洞(峒)远离政治中心,根据情况有的实行羁縻政策,有的则完全没有管理。随着帝国深入边陲以及各族群互动加深,朝廷或派兵镇守、镇压,或进行招抚,总体上山洞逐渐减少。这与历朝政府开边经略,对山洞进行治理有关。随着山洞渐次被开发,许多原来是“山洞”的地方不再称为“山洞”,而被称为“峒民”“峒僚”“洞寇”的人群,除了有种族的含义外,还具有政治的含义(或文化含义)。
二、作为地名和聚落形态的“畲”
宋元时期,畲作为地名常被文献记载。《宋史·许应龙传》记载“距州(潮州)六七十里曰山斜,峒獠所聚,匄耕土田,不输赋,禁兵与哄,应龙平决之。”①可见“山斜(畲)”作为一个地区的名称,其距离潮州城有六七十里,该“山斜”为“峒獠”聚居、耕作的地区。在广东,“輋”字是非汉民族的一种居住形式,清代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称:“粤人以山林中结竹木障覆居息为輋,故称瑶所止曰輋”②赵希璜也在《横輋》一文中对輋进行解释:“(輋)音斜,粤呼山居者为輋客。”③清代《浮山志》中为张九钺的罗浮诗后作注曰:“畲、輋,俗皆读如斜”。④
实际上,在广东一些地区,“輋”也指山脊,如民国《龙门县志》记载:“土人谓山低缺处为凹,谓山谷为迳,谓山脊为輋。”⑤由此可见,畲、輋、斜等在许多情境下并不作某一类人群的称谓来解释。
再如南宋刘克庄的《漳州谕畲》,该文是畲族史研究中极具地位的一篇重要文献。该篇正文其“畬(畲)”字共出现23次,笔者认为关于这些“畬(畲)”字的解释,根据上下文意思,可分为三类。由表1-1可以看出《漳州谕畲》中并非每一个“畬(畲)”字都作“畲民”解释,有一些应该用类似“溪洞地区”聚落名称来解释,还有一些二者均解释得通的。
第一类“畬(畲)”用族群称谓解释比较合理。如“凡溪洞种类不一:曰蛮、曰猺、曰黎、曰蜑,在漳者曰畬。”此处的畲应该与蛮、猺、黎、蜑并称,说明他们是溪洞种类下属的一类叫“畲”的人;再如“彼畬曷尝读范史”,应该解释为:那些“畲人”何尝读过范晔的《后汉书》呢?
第二类“畬(畲)”用溪峒地区或部落基层组织解释比较合理。如“汀赣贼入畬者”应该解释为,一些汀赣贼逃入畲洞地区;再如“南畬三十余所酋长各籍户口三十余家”,合理解释是:隶属南畲地区或组织的三十多个部落,其酋长分别将本所三十余家编入户籍;又如“清白之吏,固畬之所贵欤”,其合理解释是:清廉正直的官员,乃是巩固畲峒地区珍贵的人才。
第三类就是既可以将“畬(畲)”理解为溪洞地区,又可以解释为溪洞种类、如“二畬既定”可以解释为平定二处畲峒地区,也可以解释为平定二处畲峒地区的族群;再如“畬田”“畬长”可以解释为畲峒地区的田地、酋长,也可以解释为畲人的田地、酋长。
畲作为一种聚落或基层组织解释,还可以在一些文献中体现。如南宋时的赵必岊,字次山,“乡寓公吴允文浚奉密诏以江西招讨使举义反正,结约次山协谋兴复,战不利。允文奔漳州为都督文丞相天祥所杀,次山解兵隐汀州之畬中,踰年以疾终。”②畲作为地名普遍出现在闽粤一些地区中,如《元经世大典序录》载:“(至元)十七年八月,陈桂龙父子反漳州,据山砦,桂龙在九层漈畲,陈吊眼在漳浦山砦,陈三官水篆畲,罗半天梅泷长窖,陈大妇客寮畲。”①上文所称“九层漈畲”“水篆畲”“客寮畲”与“漳浦山砦”“梅泷长窖”并称,均指闽南的一些地名。元代有“畲洞”并称的记载,如《元史》称:“至元十七年,陈桂龙据漳州反,唆都率兵讨之,桂龙亡入畲洞。”②按民国《诏安县志》解释称:“按吊眼贼巢及桂龙所逃畲洞,即诏之乌山十八洞等处,南胜畲寇系其余党,寇乱数十年间。”③陈吊眼、陈桂龙等畲洞为诏安的“乌山十八洞”,所谓的“十八洞”应该是十几个村落(洞)组成一个地区,统称“畲洞”。
畲和洞联系起来作为聚居区的典型例子莫过于百家畲洞。《明史》载:“漳平,(漳州)府西北……东南有象湖山。南有百家畲洞,踞龙岩、安溪、龙溪、南靖、漳平五县之交。”④明代黄仲昭在《八闽通志》中将百家畲洞的地理、人文介绍得更为详细:
百家畲洞,在县南永福里。界龙岩、安溪、龙溪、南靖、漳平五县间。万山环抱,四面阻塞。洞口陡隘,仅通人行。其中深邃宽广,可容百余家。畲田播种,足给衣食。四方亡命者多逋聚其间。凭恃险远,易于为乱。宣德正统间,尝有江志贤、李乌觜、卢赤须、罗兴进者,乌合郡(恐为群之误,笔者注)丑,跳梁出没,至动方岳。守臣连年剿捕,仅得宁息。然服则人,叛则兽,无常性也。自漳平设县以来,官政易及,不复反侧。然尤在司民社者控御得其道云。⑤
清代方志龙岩、漳平等地方志关于百家畲洞的记载,均沿袭《八闽通志》,仅在个别字句稍作增删。⑥另据清道光《漳平县志》记载:
永福(漳平县下的一个里)自为一区,其山之名者有双髻山、猛虎山、大壮山,与百家畲洞于环阻之中又复有平者,然其细已甚不胜纪。①
综合弘治《八闽通志》和道光《漳平县志》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第一,百家畲洞,又称百家畲,这里的“畲”指的是地名。也就是说,畲与洞可以合称,也可以分开单独作为地名。
第二,百家畲洞具有典型的南方少数民族“山洞”特征,表现出“万山环抱,四面阻塞”、中间“深邃宽广”的自然地理特征以及“四方亡命者多逋聚其间”的“化外之民”聚居地的人文特征。
第三,按照“百家畲洞”字面意思,结合象洞有“九十九洞”的特点,我们估计百家畲洞也是由多个洞组合而成。而在漳平一地,与百家畲洞所具有的“于环阻之中又复有平者”地理人文特征的畲洞还有很多,只是无法一一道来,所谓的“其细已甚不胜纪”。
清代以来,许多地方还保存畲(輋)的地名,如李调元《南越笔记》记载广东地区輋人及其聚居地区的情况:“輋人:澄海山中有輋户……輋巢居也;猺所止曰屳、曰峒、亦曰輋。海丰之地,有曰罗輋,曰葫芦輋,曰大溪輋。兴宁有大信輋,归善有窑輋。”②
直到现在,闽粤赣地区仍有许多地名带有“畲”字,③如福建连城带有“畲”字的地名就有19个,而武平也有17个。④其余的如长汀的下畲;上杭的大畲;龙岩的郭畲、小高畲、畲背、洋畲、下经畲;漳平的谢畲、罗畲、百种畲,东下畲;华安的官畲、南靖的桂竹畲、后畲、上麻畲;云霄的桃畲、上梨畲、下梨畲、坝头畲,等等。
学者推论这些地区与畲瑶等非汉族群有一定的联系。清代温仲和在光绪《嘉应州志》中,曾对有关“畲”的地名与族群关系作一番论述,他说:“今地以畲名者尚多有之,而所谓猺獠则绝无其人,盖日久皆化为熟户,而风俗与居民无异矣。”①
在作者看来,带有“畲”字的地名与“猺獠”存在着某种关系,只不过这些非汉民族变为“熟户”后,不再称为“畲”,但地名仍存于今。
再如著名学者徐松石先生也提出:“畲瑶即古代所谓山越。在广东东部散布甚广。平远、蕉岭、梅县、河源、惠来、丰顺、新安等地,现在还有许多畲字或輋字的地名。”②陈龙、吴炳奎、刘大可等学者也对闽粤赣一些地区内带有“畲”字的地名进行考证,以证明历史上畲瑶等族群在该地存在的可能性。③因此,有学者将这些带“畲”字的地名视为闽粤边地区畲族活动史的活“化石”。④
需要指出的是,带有“畲(輋)”地名的出现时间与“猺獠”族群在该地的居住时间,孰先孰后,目前仍无法考证。我们或许可以推论:古代汉人常将“猺獠”生活的地方称为“畲”,正如将南方非汉族群聚居区称为“山洞”一样。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畲”地名的命名与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遗存有关系。司徒尚纪认为在广东等地区,“没有水利工程灌溉的丘陵、山地,其被开发利用土地通名为畬地或畬田,实为梯田,过去实行刀耕火种,至今在海南、粤北黎、瑶地区仍有残存,故以畬为首尾地名在内陆山区较普遍。”广东客家人聚居平远县就有许多以畲命名的地名,反映的是“山区梯田文化景观”。⑤
因此,我们认为“畲”的地名未必一定和非汉族群聚落有关,即:“畲”作为一种地名的命名方式在闽粤赣地区已经形成一种传统,人们用其称呼一些“山脊”或山地地名,而这并不一定和“猺獠”族群有必然的联系。
三、“畲”“峒”生态文化语境下的一种族群分类
在古代中国,由于受到大一统观念的影响,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民族史的撰述,都体现出了诸如“夷夏同祖认同、华夷一家认同、共属中国认同、华夏文化认同”的大一统意识。①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华夏文化在几千年的民族史撰述中一直处于被表述的中心,四方“夷狄”则处于从属地位。而在具体实践中,华夏民族自春秋战国以后,在与周边非华夏民族的互动过程中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表现出华夏族及其文化不断向边陲扩张,最终使得各非华夏民族淹没在华夏族的“海洋”中或成为“华夏海洋”中的“非华夏孤岛”。
因此,在重新审视我国古代民族史时,我们必须将历代有关于“非华夏”族群的文字记载置于当时的社会情境来分析,具体来说:一是在汉文化语境下,这种记载多大程度反映了文字记载者的立场、态度及情感,而作为文本的历史记忆又反映了当时什么样的历史心性?二是这种记载中的文化特征,是否能够反映“异族”的实际情况,即这种客观的文化特征描述能否与“异族”的实际认同情况相一致?或者说,对“他者”只是文字记载者单方面的认同?
“畲”作为一种族群的出现,需要在生态语境和文化语境下考察。首先,自然生态无疑是任何一种族群和文化产生的最基础因素。正如我国历史上形成的游牧与农耕文明的生态界线,自然生态上差异导致了文化的差异,从而形成了文化特色截然不同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畲”作为原始的、粗放的耕作方式,与精耕细作的汉族农业也存在一条若隐若现的生态边界,这种自然生态的差异在族群文化特征上打上鲜明的烙印,这种迥异于“他者”的文化特征,成为“他者”族群观察另一个族群的切入点。根据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给文化所作的定义,文化应该包含了人类经历的各个方面②。按照这种定义,一个族群的文化特征应该包罗万象,而作为文字记载的族群,其呈现给后人的文化特征,充其量不过是一些静态的、被认为的诸多特征中较为典型的、有异于他者的特征。
笔者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农业的变迁认为,“畬(畲)田”的耕作方式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历史上从事“畬田”农业的族群,除了被称为“畬田”民族外,实际上,在某一历史阶段,汉族也从事“畬(烧)田”农业。③主要区别在于:随着汉族农业技术的发展,在汉族社会中,“畬田”的耕作方式逐渐被精耕细作农业所取代;而在一些非汉族群中,“畬田”农业作为一种技术要求不高、较易实施的粗放农业,仍一直被沿用。
随着代表农业文明的汉族文化不断扩张,“畬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遭遇,并产生了生态冲突。这种冲突首先发生在两种生态文化的锋线,也就是在两种生态文化的边界地区是生态矛盾最集中的地方。正如在古代中国,长城沿线被视为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冲突最集中的地方,长城的分布与走向基本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生态系统的分界线。生态文化的冲突带来族群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唐宋时期特别明显。“畬(畲)”之所以在唐宋时期的诗文中大量出现,与唐宋时期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时期,随着帝国华夏化进程加快,中国南方各个地区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北方汉人带来的先进农业与被认为是原始农业残余的“畬田”农业遭遇时,这种文化冲击(cultureshock)使得“畬(畲)”作为一种猎奇、述异、诗化见诸汉人知识分子的笔端。
尽管也有大量诗人对“畬(畲)”不吝溢美之词,但无法改变整个主流文化对“畲”的看法,特别是当“畲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在资源上冲突加剧时,“畲”一种文化标签常贴在非汉族群身上,目的就是将其边缘化。
第三节 小结
本章从生态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唐宋以来与畲族及其先民相关的自然生态和聚落人文情况。本章的主要论点有:
(1)“畲”作为一种古老的耕作方式,不仅在时间维度上,并且在空间广度上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中。要探讨“畲”如何成为一个族群的称谓,必须将其放置于特定的生态语境和文化语境中考察。
(2)在历史上中国中部、南方地区,曾存在畬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的生态冲突。畬田农业是一种较为古老的耕作方式,其在文化特征与日本学者提出的“照叶树林文化”特征相似。唐宋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中心南移,以精耕细作为代表的汉人农业在中国南方地区迅速发展,畬田农业呈现出明显的退缩趋势,宋代以后南方地区梯田的增多,说明了这个现象。随着对生态资源的需求,代表汉人农业的精耕细作与代表古代农耕方式的残存形态的畬田农业开始发生冲突,其生态边界恰好为汉族与非汉族群的边界大部分吻合。
(3)“畲”不仅仅是一种耕作方式,还具有带有聚落的含义。“畲”之所以从一种经济形式或聚落形态的称谓演变为一类族群的称谓.这与汉文化语境有着
密切的关系。“畲(輋)”或“山洞”,起先是作为人类居址称谓而存在的,这种特定的自然生态造就了特殊的聚落文化,从而成为生活在该地区人群的一种人文特征。
(4)在以华夏为中心的民族观指导下,汉人以从事特殊耕作方式(畲、輋),或居住在特殊聚落形态(洞、峒)作为文化特征,将南方非汉族群标签化。本章通过考察闽西象洞和海南黎峒两个个案,总结出作为聚落形态的“畲”“峒”的村落形态特征、族群构成、地方组织方式以及政治人文特征等。以此证明:“畲”或“峒”作为非汉人群的聚落、组织或族群称谓,均是在汉文化语境中产生的。在这种文化语境中,畲(輋)、峒(洞)除了具有区分种族的意义外,还具有政治和文化的意义。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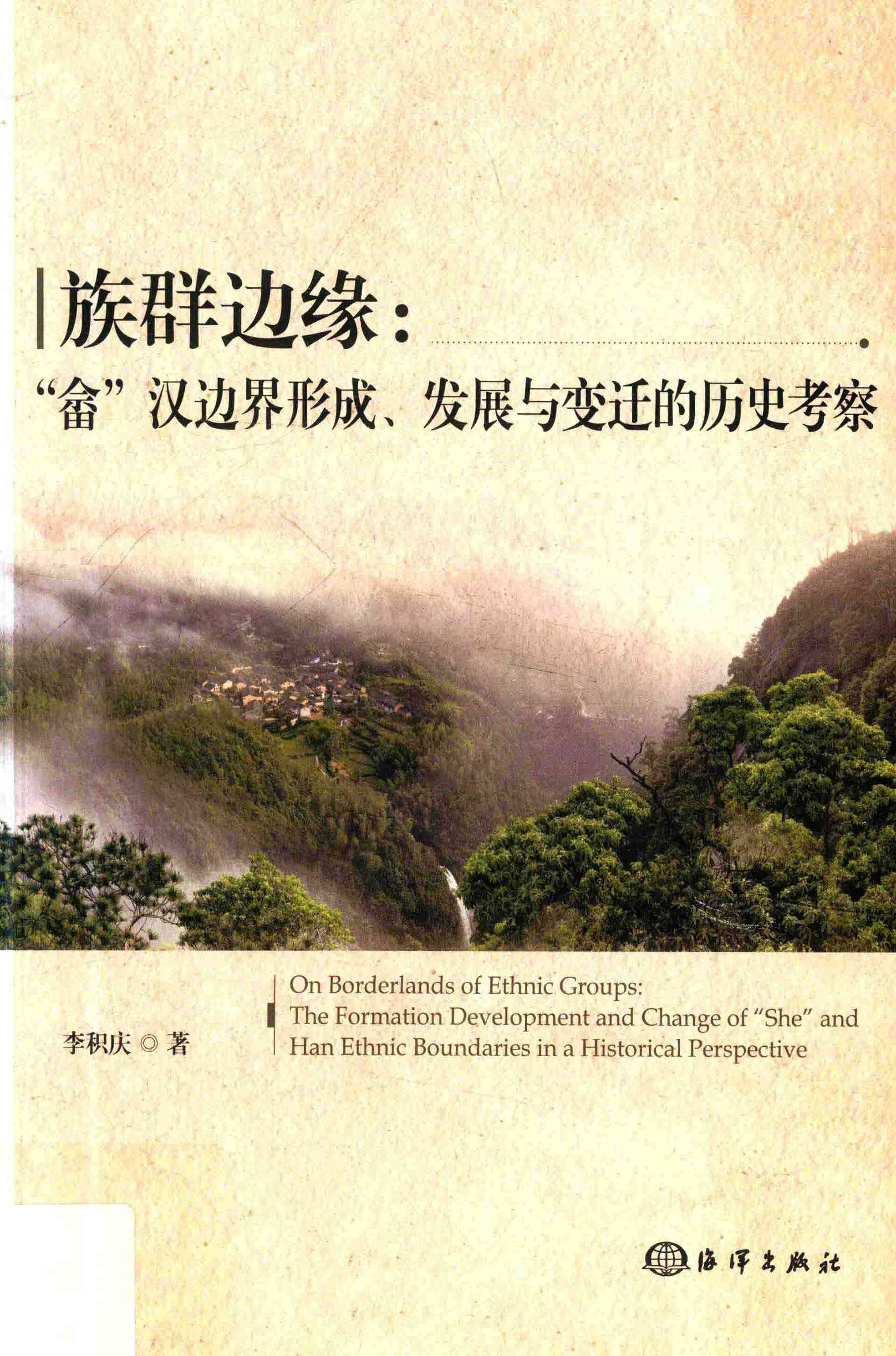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出版者:海洋出版社
本书从族群边界的理论角度,重新审视畲族形成、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在承认族群客观历史文化的同时,重点研究历史上“他者”(主要是汉族)对“畲”的社会定义以及“自者”(主要为南方非汉族群)自我族群认同的过程,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现实意义。
阅读
相关地名
宁德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