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宋时期“畲”汉族群的文化生态边界
| 内容出处: |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图书 |
| 唯一号: | 130920020230003759 |
| 颗粒名称: | 第一章 宋时期“畲”汉族群的文化生态边界 |
| 分类号: | K288.3 |
| 页数: | 26 |
| 页码: | 24-49 |
| 摘要: | 本文考察了宋时期“畲”汉族群的文化生态边界。通过对畬田农业的生态语境及分布情况的分析,揭示了族群边界的复杂性和多维性。文章指出,在界定族群边界时,经济因素如畬田农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应考虑到政治、文化等多重因素。通过对“畲”的词义演变和畬田农业的分布情况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理解宋时期“畲”汉族群的边界特征和文化生态。 |
| 关键词: | 族群边界 畬田农业 宋代 |
内容
族群边界的界定,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一般认为,畲民之得名与该族群“烧山种畲”的经济方式存在较大关系,畲民就是烧山种畲的人。①就此而言,经济因素在某一历史时期“畲”汉族群边界的界定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畲”在本义上不仅仅是一种耕作方式,还带有聚落的含义,也就是“畲”不仅仅具有经济的意义,还带有文化或政治的意义,这种意义的需要放在一定的语境下进行分析。本章先分析“畲”是如何从一种经济形式或聚落形态的称谓演变为一类族群的称谓的过程,进而说明在界定族群边界中起作用的相关因素。
第一节 生态语境下的畬田农业与边界冲突
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休斯(J.Donald Hughes)曾指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们依赖于生态系统,并且不能完全操纵自己的命运……历史叙述必须把人类事件置于地方和地区生态语境之中。”②因此,在考察畲族及其先民的族群文化之前,先对与之相关的地区自然生态进行考察是十分必要的。
一、唐宋时期的畬田农业及其分布情况
畬田农业作为一种粗放的耕作方式早在春秋以前就已经存在,唐宋以后仍在中国南方地区广泛存在。“畲”在唐以前一般写作“畬”,其作为原始农业经济方式最早是指开垦出来的两年或三年田地①,反映的是春秋时期以前我国广泛存在的一种休闲耕作制度。从战国到隋唐,中国古代农业从精耕细作农业成型时期转入精耕细作农业扩展时期,②由于休闲耕作制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畬”在隋唐时期增加了新的音和义:读“YU”时是指开垦两三年的田,读“SHE”时则为“畬田”(烧田)的含义。③
畬田是一种区别于精耕农业的耕作方式,如《魏书·崔辩列传附模弟楷传》记载:“遥途远运,惟用舟舻,南亩畬菑,微事耒耜。”④唐宋以来,畬田农业大量出现于文献中,如刘禹锡的《畬田行》曾具体介绍了畬田的耕作过程:
何处好畬田,团团缦山腹。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惊麏走且
顾,群雉声咿喔。红焰远成霞,轻煤飞入郭。风引上高岑,猎猎度青
林。青林望靡靡,赤光低复起。照潭出老蛟,爆竹惊山鬼。夜色不见
山,孤明星汉间。如星复如月,俱逐晓风灭。本从敲石光,遂至烘天
热。下种暖灰中,乘阳拆牙孽。苍苍一雨后,苕颖如云发。巴人拱手
吟,耕耨不关心。由来得地势,径寸有余金。⑤
文章描写了“畬田”前卜“雨卦”、烧山、种畬等一系列过程,并指出“畬田”的主人为巴人,是西南一带的非汉族群。温庭筠《烧歌》也详细描写了带有“楚越”之地风俗的烧田(畬田)情况,“畬田”的主人也应是非汉人群。⑥
唐代或有一些汉人也从事畬田农业。如唐代韩鄂的《四时纂要》描写的七月开荒田,其耕作方式与畬田有相似之处。将这种耕作方式写入其文曰:
开荒田。凡开荒山泽田,皆以此月芟其草,干,放火烧,至春而开
之,则根朽而省工。若林木绝大者,〓杀之,叶死不扇,便任耕种。三
年之后,根枯茎朽,烧之则入地尽矣。耕荒必以铁爬漏凑之,遍爬之,
漫掷黍稷,再遍耢。明年乃于其中种谷也。①
相对于刘禹锡《畬田行》一文中粗放的畬田耕作方式,开荒田似乎比较精细,这意味着或者开荒田借鉴了畬田的方法;或者可以认为畬田开始慢慢向汉人精细农业转变。韩鄂的《四时纂要》是一本按照四时及月份列举出应做农事的月令式农书,开荒田被列为七月应做的农事,间接说明在唐代仍有许多地区实行畬田或与之相近的农业耕作方式。只不过在非汉人群中,畬田更为流行而已。如唐代黔州之西的东谢蛮地区,“土宜五谷,不以牛耕,但为畬田,每岁易。”②而南蛮地区也是“宜五谷,为畬田,岁一易之。”③
到了宋代,在一些偏远的山区多有“畬田”农业的记载,如宋代王禹偁《小畜集》卷八《畬田词并序》描写了西北地区居民刀耕火种的情况:
上雒郡南六百里,属邑有丰阳、上津,皆深山穷谷,不通辙迹。其民刀耕火种,大底先斫山田,虽悬崖绝岭,树木尽仆,俟其干且燥,乃行火焉。火尚炽,即以种播之。然后酿黍稷、烹鸡豚,先约曰某家某日有事于畬田,虽数百里如期而集,锄斧随焉。至则行酒啖炙,鼓噪而作,盖劚而掩其土也。劚毕则生,不复耘矣。援桴者,有勉励督课之语,若歌曲然。且其俗更互力田,人人自勉。仆爱其有义,作《畬田》五首,以侑其气。亦欲采诗官闻之,传于执政者,苟择良二千石暨贤百里,使化天下之民如斯民之义,庶乎污莱尽辟矣。其词则取乎俚,盖欲山民之易晓也。④
从序言中可以看出山民“畬田”的斫山田、烧林木、播种、盖土的劳作程序,同时也看出在“畬田”时,不同地区人们互相协作,主人酒菜待客,同时伴有宛如歌声的“劳动号子”。作者显然被这种热烈的气氛感染,写了五首简单易懂的《畲田词》①,希望能进一步推广“畬田”,将其用于各地山林的开辟。
在中国南方各地,“畬田”的耕作方式普遍存在。如《宋史》记载西南地区抚水州一些“聚山险”的蛮夷从事畲田农业,但是由于耕作方式粗放,“收谷粟甚少”②而宋代张淏在《云谷杂记》中提到湖南等地区的畲田收成较好:
沅湘闻多山,农家惟种粟,且多在冈阜,每欲布种时,则先伐其林木,纵火焚之,俟其成灰,即布种于其间。如是则所收必倍,盖史所谓刀耕火种也。③
朱胜非在《绀珠集》中则记载宋代江南畬田:
江南人多畬田,先纵火谓之熂炉,俟经雨下,种历三岁,土脉竭不可种,复生草木。宋西阳王子尚云:山湖之俗,熂山封水以种,名疁田,即谓此也。《尔雅》田一岁曰菑,田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畬。田凡三岁,不可复种,故名畬。熂音饩,疁音留。④
这里提到的“种历三岁,土脉竭不可种,复生草木”,说明了从事畬田的民族必须常常迁徙,以获得新的山地用以烧山种畲。
华南地区的福建也实行畬田。早在唐代,诗人贯休曾在《怀武夷红石子》写有“竹鞘畲刀缺,松枝猎箭牢”⑤诗句,依稀可以了解唐代建州或存在畲田农业;《全唐文》收入唐代陈元光的《请建州县表》,其文称:“况兹镇地极七闽,境连百粤,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⑥虽然陈元光的《请建州县表》被考证是伪作①,但至少说明在某一历史时段,漳州的“蛮僚”或当地居民曾从事有关“火田”(畬田的别称)的耕作活动,其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在后人建构该篇伪作的时候仍被重新提起。宋人杨杰在《故温州录事参军陈君墓志铭》中记载当时宁化军有盗寇持畲刀盗割粮食,其文称:“再调汀州司理参军,宁化军有盗六人,持畲刀,夜割人禾,田主逐之,五人逸去,其一独留,且杀主人。”②这则材料比较肯定地说明宋代或更早福建存在畲田农业。
明清以后,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仍是南方一些非汉民族主要耕作方式。如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曾记载:“南方多畬田,种之极易。春粒细香美,少虚怯,只于灰中种之,又不锄治,故也。”③明代谢肇淛记载闽东畲人烧畲“……过湖坪,值畲人纵火焚山,西风甚急,竹木迸爆霹雳。舆者犯烈炎而驰下山,回望十里为灰矣。”④清代杨澜《临汀汇考》描述汀州地区畲客刀耕火种情况:“此外又有棱米,又名畲米,畲客开山种树,掘烧乱草,乘土暖种之,分粘和不粘二种,四月种,九月收。”⑤范绍质在《徭民纪略》也称:“汀东南百余里,有猺民焉……糞田以火土,草木黄落,烈山泽,雨瀑灰浏,田遂肥饶,播种布谷,不耘耔而获。”⑥
在广东的粤东等地的輋(畲)民也存在类似的耕作方式,如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七:“輋人……其人耕无犁锄,率以刀治土,种五谷,曰刀耕;燔林木,使灰入土,土暖而蛇蛊死,以为肥,曰火耨。是为畬蛮之类。《志》所称伐山而甾蓻草而播,依山谷采猎,不冠不屦者是也。”⑦吴震方《岭南杂记》则写道:“潮之西北山中有畲户者……刀耕火种,不供赋也。”⑧
总之,唐代以来,南方许多地区存在刀耕火种的“畬田”耕作方式.这种相对粗放的耕作方式常常作为非汉族群文化特征被大量记载在文献中①。有关畲田的耕作技术,大泽正昭以及周尚兵等学者均作了详细的考证,②兹不赘述。
实际上,“畬田”(或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很长时间存在于人类社会中,而不仅仅局限于上述几个地区。自20世纪40—50年代起,由日本学者中尾佐助、上山春平、佐佐木高明等提出了“照叶树林③文化论”。该理论认为:从喜马拉雅山南麓东经不丹、阿萨姆、缅甸、中国云南南部、泰国、老挝、越南北部、中国长江南岸直至日本西部的辽阔地域存在一个地域广阔的照叶树林文化带“照叶树林带”(见图1-1)。这一地带的文化具有相通性,其最基本、最重要的文化特征是以栽种水稻、杂粮(包括旱稻)、薯类为主的烧田农业。④照叶树林地带上的少数民族众多,有许多民族都曾从事或者至今仍在延续传统刀耕火种的农耕生产方式。⑤
根据“照叶树林带”的分布情况,结合有关新石器时期区系划分,可以看出中国南部两个中心文化区,即华南地区及长江流域部分地区属于照叶树林的分布范围;而二者之间的过渡带,即南岭以北和武夷山以西地区过渡地带则恰好处于东亚半月弧中心的东缘和南缘。⑥这也间接说明了该地区在历史上广泛存在刀耕火种(畬田农业)的经济方式。
日本学者大泽正昭发现,唐宋时期实行畬田分布的地域一度相当广大,⑦并且与獠、蛮、氐、羌、山棚、山越等“少数民族”的居住区域有相当程度的重合,曾雄生将这些以畬田(刀耕火种)为主要特征的农耕民族定义为“畬田民族”。①实际上,畬田的耕作方式曾广泛存在于包括汉族在内的各个族群中,只不过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畬田作为中国古代农耕方式的残存形态被主流农业生产者所淘汰。如果以更广阔的时空来考察畬田(刀耕火种),笔者更愿意将所谓的“畬田民族”认定为特定时期某一人群的特定称谓。唐宋以后,畬田耕作方式逐渐被边缘化,自唐代以后,随着江南的开发更进一步,畬田区域呈缩小的趋势,大泽先生因此认为畬田是中国古代农耕方式的残存形态。②
将大泽正昭的“畬田分布图”(见图1-2)与东亚地区“照叶树林带”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唐宋的畬田基本在照叶树林带的范围内,少部分畬田在“照叶树林带”偏北地域,这反映了中国古代自然生态的变化:即烧田农业有向南、向西偏移的趋势。
由此可以说明:一是畬田的生态环境分布在中国的中南部,随着历史的变迁,烧田农业有向南、向西偏移的趋势;二是烧田农业的缩小与走向,与帝国开边进程(中国地方区域经济渐次开发)的趋势和走向是相一致的。随着帝国权力的深入和经济的开发,主流农业势力在地域上逐渐由北向南,在地区上逐渐由中心平原盆地向偏远山区扩张,这也意味着主流农业的生产者(主要是汉族)族群势力与之同步扩张。而造成唐宋时期畬田地区与獠、蛮、氐、羌、山棚、山越等族群分布区域高度重合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上述族群较多分布在中国中南部及偏远山区的历史事实;二是汉族在农业扩张过程中,与固守畬田农业耕作方式族群产生的生态冲突而留下的历史印记。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畬”作为原始农业经济方式早已存在,唐宋以后的社会经济转型,使得畬田农业呈缩小和偏移的趋势,畬田与精耕细作农业的生态矛盾随着社会发展与族群扩张逐渐显现。
二、畬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之间的冲突
竹村卓二先生在研究东南亚的农业形态时给出,山间坡面粗放的刀耕火种农业的生态系统受到要素的制约:一是局部地区的自然环境;二是与其内部的社会组织、技术、人口动态有关;三是与外部社会有关。①也就是说,刀耕火种的生态系统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在资源竞争比较激烈的地方,刀耕火种的生态系统往往因为某一要素的缺失而受到破坏。文献中常将刀耕火种的特点描述为“随山种插,去瘠就腴”①“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它徙”②“耕山而食,去瘠就腴,率数岁一徙”③等,这种粗放型的耕作方式要求在自然生态中,必须有相应的大片的山地资源供其耕作。在外部社会中,随着汉民族“华夏化”④进程的加快,不同族群所代表的不同经济方式存在着竞争关系。显然,畬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二者之间在生态资源上存在的竞争关系慢慢突显,并逐渐引起生态冲突。早在唐宋以前,这种冲突就已存在,如《晋书·食货志》就载了东南地区水田与陆田的冲突:
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非不尔也,然此事施于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顷户口日增,而陂堰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水雨,辄复横流,延及陆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陆种。⑤
唐宋以后,大部分汉族地区农业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进入精耕细作农业扩张时期。⑥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更是加剧了畬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的冲突。这种冲突可以从《五灯会元》的一则记载看出:
南岳玄泰禅师……尝以衡山多被山民斩伐烧畬,为害滋甚,乃作畬山谣曰:“畬山儿,畬山儿,无所知。年年斫断青山嵋。就中最好衡岳色,杉松利斧摧贞枝。灵禽野鹤无因依,白云回避青烟飞猿猱路绝岩崖出,芝术失根茆草肥。年年斫罢仍再锄,千秋终是难复初。又道今年种不多,来年更斫当阳坡。国家寿岳尚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远迩传播,达于九重,有诏禁止。故岳中兰若无复延燎,师之力也。①
玄泰禅师显然十分反对在南岳地区畬山“斩伐烧畬”,他将这些“斩伐烧畬”的“山民莫徭辈”②蔑称为“畬山儿”。③玄泰禅师所提到的从事“刀耕火种”的莫徭,被认为是一种“承盘瓠之后”的“夷蜒”族群,“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④因此,学者经常将其与后世的畲、瑶等族群联系起来。
唐末五代以后,在中国南方各地开始出现梯田,这是一种与畬田有所不同的山田梯田的兴起,是精耕细作农业从平地延伸到山地的表现,这是中国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的重要表现。元代王祯在其《农书》上对梯田的地理环境、耕作情况、作物及收成等进行介绍,其文曰:
梯田,谓梯山为田也。夫山多地少之处,除磊石及峭壁,例同不毛,其余所在土山,下自横麓,上及危巅,一体之间,裁作重磴,即可种艺。如土石相半,则必叠石相次,包土成田。又有山势峻极,不可展足,播殖之际,人则伛偻蚁沿而上,耨土而种,蹑坎而耘,此山田不等,自下登陟,俱若梯磴,故总曰梯田。上有水源,则可种杭林。如止陆种,亦宜粟麦,盖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乡细民,必求垦佃,犹胜不稼。其人力所致,雨露所养,不无少获。然力日至此,夫免艰食,又复租税随之,良可悯也。⑤
可见,梯田付出更多的人力劳动成本,这是对山地最大限度地利用,收获也比刀耕火种来得多。学者认为,南方梯田的产生与唐宋以后经济重心南移及大量北人南迁有一定关系。①应该讲,梯田耕作技术比畬田要求更高,虽然梯田和畬田二者并非前后继替的关系,但有史料证明很多的梯田是由畬田转化而来的。
最早出现“梯田”一词,就目前发现的史料应该出自于南宋范成大在乾道七年(1172年)以后几年所作《骖鸾录》,该书主要讲述范成大在乾道壬辰十二月,以中书舍人出知静江府途中的所见所闻。在乾道八年闰二月,范成大到达江西宜春,由于慕仰山之名,特意逗留几日,其文写道:
泊袁州(今江西宜春),闻仰山之胜久矣,去城虽远,今日特往游之。二十五里,先至孚惠庙……旧传二龙昔居仰山中,以其地施仰山祖师,迁居于此……出庙三十里,至仰山,缘山腹乔松之磴,甚危。岭阪之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建寺之祖仰山师者,事具《传灯录》中,号小释迦。始入山求地,一獭前引,今有獭桥。至谷中,即二龙所居,化为白衣,逊其地焉。大仰之名,遂闻天下。②
文中的提到的“仰山祖师”就是伪仰宗的创始人慧寂禅师(815—891年)。慧寂禅师曾于唐会昌元年(841年)从湖南伪山来到仰山脚下“创庵以居”,③至唐宣宗年间正式建寺,并由宣宗赐名“栖隐寺”。当时的仰山并非如范成大所描述的“禾田层层”,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在仰山可能大部分还是畬田耕作方式。《五灯会元》卷九《南岳下四世·仰山慧寂禅师》记载了仰山慧寂禅师生平,并载有大篇幅的师(沩山灵祐禅师)、徒(仰山慧寂禅师)对话,其中谈论到仰山烧山种畲的情况:
师在沩山,为直岁,作务归,沩问:“甚么处去来?”师曰:“田中来。”沩曰:“田中多少人?”师插锹叉手。沩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师拔锹便行……师夏末问讯沩山次,沩曰:“子一夏不见上来,在下面作何所务?”师曰:“某甲在下面,鉏得一片畬,下得一箩种。”沩曰:“子今夏不虚过。”④
另外,在《袁州仰山慧寂禅师语录》中也记载了慧寂禅师与师兄弟谈论烧畲自种自食的事:“山僧与汝诸人说着:‘开得一片畲,绵绵密密。两顿粥饭,其道自办’。”①
其中提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中的“刈茅”应该也与烧山种畬活动有关。由此可见,唐代后期的湖南、江西等南方地区都广泛分布着畬田,而社会上对畬田的态度不尽相同。但总的趋势是,畬田的地域慢慢地缩小,以仰山为例,唐末还可以“〓得一片畬”,过了一两百年的范成大生活的南宋时代,仰山就全部被开垦为梯田了。
在宋代以后,在南方的一些丘陵山地开垦梯田,已经成为比较普遍的事了。如宋代方勺《泊宅编》曾记载福建地区因地理环境垦造梯田的情况:
七闽地狭瘠,而水源浅远,其人虽至勤俭,而所以为生之具,比他处终无有甚富者。垦山陇为田,层起如阶级。然每远引溪谷水以灌溉,中途必为之硙,不唯碓米,亦能播精。朱行中知泉州,有“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之诗,盖纪实也。②
明代谢肇淛在《五杂俎》中也有类似的记载:“闽中自高山至平地,截截为田,远望如梯。真昔人所云‘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者,可谓无余地也。”谢肇涮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闽之福塘,地狭而人众,四民之业无远不届,即遐陬穷发髪、人迹不到之处往往有之,诚有不可解者,盖地狭则无田以自食,而人众则射利之途愈广故也。”③清初学者周亮工在《闽小纪》也记载道:“闽中壤狭田少,山麓皆治为陇亩,昔人所谓磳田也。”④梯田的耕作更为辛苦,收获却不多,道光《永定县志》称:“地斗隘厥土骍刚,山田五倍于平野,层累十余级不盈一亩。”⑤梯田之所以流行于南方地区,原因有二:其一是南方多山地丘陵的地理环境;其二是随着当地人口的增加,平原土地开垦殆尽,迫使人们往山地丘陵寻求土地,因地制宜地开垦梯田,最大限度利用土地进行生产。相对于畬田农业的粗放管理,梯田在土地利用率上更高效,因此,也更适用于人地关系紧张的地区。
宋代以后,畬田农业在一定区域受到限制,如北宋政府开始实行“火田之禁”,《宋史·食货志》载:
大中祥符四年,诏曰:“火田之禁,著在《礼经》,山林之间,合顺时令。其或昆虫未蛰,草木犹蕃,辄纵燎原,则伤生类。诸州县人畬田,并如乡土旧例,自馀焚烧野草,须十月后方得纵火。其行路野宿人,所在检察,毋使延燔。①
诏令反映了两点:一是“诸州县”存在畬田现象,二是对畬田进行时间(“须十月后”)和地点(“毋使延燔”,即不让火势蔓延到畬田以外的地方)的限制。这种限制是在确保主流农耕文化的利益:要求畬田要“合顺时令”实际上是合顺精耕细作的“时令”;要求畬田不要“伤生类”实际上是不要损害以汉人为代表的利益。直到明清,这种生态的冲突依然存在,如王阳明在《平輋》一诗中写道:“处处山田尽入輋(畬),可怜黎庶半无家”②,描述的是赣闽粤部分地方百姓的田园为畬田所占的情况。
总之,“畬”作为原始农业经济方式早已存在,包括汉族在内的许多族群都曾从事“畬田”农业方式。唐宋以后,随着经济的开发,由于在生态资源上存在竞争关系,畬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的生态边界凸显。
第二节 文化语境下的南方“畲洞”及其聚落人文
历史上常将唐代以后“峒蛮”“峒獠”与畲族联系起来。“畲”不仅仅是一种耕作方式,还具有聚落的含义。“畲”从一种经济形式或聚落形态的称谓演变为一类族群的称谓,其与汉文化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畲”作为一种溪峒地区或部落基层组织存在,其与“洞(峒)”一样,均经历过本义——聚落称谓——族群称谓的转变过程。在以华夏为中心的民族观指导下,畲、峒的文化特征成为汉族对南方非汉族群分类的重要依据。
一、山洞:从洞穴居址到“蛮夷”聚落称谓的转变
“畲”和“峒”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学界常将历史上出现在南方地区“山洞”“溪洞”“峒蛮”“峒獠”等族群与畲民联系起来。峒,也称“洞”,或“山洞”,关于山洞的解释,学术界上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自然环境说,指原来未设政区的偏远之处的山间溪谷;①二是民族构成说,专门指南方山区非汉族土著民族;②三是地方组织说,指随着中原王朝政治在华南社会的扩展,在国家行政统治未能到达的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由土豪势力建立起来的具有实质性的地域统治体制或特殊的军政单位。③以上观点将“溪洞”并称,各观点并不完全矛盾,只不过是将山洞放置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中讨论而已。如李荣村指出:“唐宋时凡近山的蛮夷住地、聚落或羁縻州洞等都可称作峒,又称溪峒,也就是蛮洞的意思,但绝不当作狭义的洞穴解释。”④李氏强调以特定历史条件来考察“洞”的含义,这是十分有道理的,但至于“洞”为何从表示“岩洞”“窟穴”的原意,变为少数民族“聚落”或组织,那还是得探寻洞的本源,方可做出解释。
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旧石器时代,洞穴居址作为人类聚落形态就已经存在。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就曾指出:“洞穴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者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⑤古代人类有选择寻找居住的洞穴,留下各个时代的洞穴堆积,在我国的华南、华北地区均分布着具有代表性的各时代洞穴。⑥一般来讲,这个时期的洞穴并非孤立、静态的存在,而是作为一个聚落系统发挥生产生活的功能。这一阶段的聚落形态主要为“洞穴-旷野”模式,也就是说,人类选择在洞穴,既要考虑洞穴作为遮蔽所的功能,又要考虑到以洞穴为中心的周围自然环境,尤其是食物资源的获取情况。⑦到了中石器时代⑧,随着原始农业的萌芽,人类社会开始由采集渐进到农业,由狩猎发展为畜牧⑨,在生产、生活技术水平提高的基础之上,人类从洞穴向更广阔的台地、平原、山冈进发。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建造技术高度发展,人们已经不再依赖洞穴,在各个适合人类生产生活的地形建造居所,形成聚落,并在不同地区发展出多元化的人类居住体系。在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华南地区所占数量不少,比较集中地分布在广东、广西、江西、云南等地区,浙江、福建、湖南等地也有少量分布,大概可以将遗址分为洞穴遗址、贝丘遗址、台地遗址三种类型。①从后两种类型足以证明人类的居址向多元化发展。在新石器晚期,人们已经大量建造公共广场、祭坛等建筑,聚落居址成为文明的标志。随着聚落的发展,中国个别地区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进入城邦模式。②
可见,早期人类由于生产生活技术水平较低,只能依赖洞穴作为庇护所,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对获取自然资源的需求,人类从“山洞”走向“旷野”,形成聚落,创造出越来越丰富的人类文明。那么可以想见,随着地区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提前进入“文明社会”、居住在城邦村落的族群在看待仍在“洞穴”居住的族群时,必定占有相对的心理优越感。而正是这种优越感带来的人们观念的变化,使得洞的意义开始延伸,也就是说“洞”在“文化先进”地区的人群看来,开始成为一种文化落后、野蛮未开化的象征。这种象征逐渐被“标签化”或“模式化”,形成了某一人群对另外一个人群的固有印象,如唐代刘禹锡称“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桴筏者,与华言不通。”③“居洞砦”是野蛮、未开化族群的重要特征之一。唐代以后,这些“居洞砦”的非汉人群一般被称为“峒民”或“峒獠”,其广泛分布于南方地区,如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写道:“峒獠者,岭表溪峒之民,古称山越,唐宋以来,开拓寝繁,自邕州以东,广州以西,皆推其雄长者为首领,籍其民为壮丁。”④这些分布广泛的“洞”,其地理环境、自然生态、社会组织特征又是如何呢?笔者拟以闽西象洞和海南黎峒作为例子进行分析。
宋开庆年间由胡太初所修的《临汀志》记载了有关象洞的情况,其文曰:
象洞,在武平县南一百里,接潮、梅界。林木蓊翳,旧传象出其间,故名。后渐刊木诛茅,遇萦纡怀抱之地,即为一聚落,如是者九十有九,故俗号“九十九洞”。其地膏沃,家善酝酿,邑人之象洞酒。洪刍有《老酒赋》,正谓此。但僻远负固,多不乐输,故置巡检寨以镇焉。①
按照作者的描述,象洞应该可以被认为是南方非汉民族居住的“山洞”的一种。以上材料可以说明:
第一,从自然生态上看,象洞原先是人迹罕至、丛箐林密的原始山林地带,在未开发之前,此地乃象群出没之地②,象洞因此而得名。
第二,从聚落形态看,象洞从原始森林变为人类聚居地的过程大概有三个步骤:首先,开辟山林,“刊木诛茅”;其次,选择“萦纡怀抱”的地理环境,在中间平坦、土地肥沃的地方开发成一个聚落;再次,随着山林开发的深入,各个“洞”被次第开发,如象洞形成了“九十九洞”的规模。笔者推论,“九十九”如此巧妙的数字,在此语境下应该不是实指,而是虚数,描述者只是想表达“洞”之数量极多而已。关于各洞之间的关系,应该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以地形看,各个“洞”周围山林林阻隔,交通不便,各洞之间可以保持相对独立的状态;而以名称看,象洞统称为“九十九洞”,说明各洞在“类型”上是相似的,不仅地理环境相似,族群多有相通,所以可以统称。
第三,从人文生态上看,洞中有平坦且肥沃土地可供“洞民”从事农业,并善于酿酒,其“象洞酒”在闻名于武平一邑;象洞早期居民不纳赋税,“僻远负固,多不乐输”,被认为是“化外之民”。随着王朝势力深入边陲,国家在非汉族群的地区驻兵,以控制当地“负固”之徒。
周去非《岭外代答》“海外黎蛮条”记载当地“黎峒”的情况,颇具代表性,可以看做是唐宋“蛮夷”聚落的一个典型,其文曰:
海南有黎母山,内为生黎,去州县远,不供赋役;外为熟黎,耕省地,供赋役,而各以所迩隶于四军州。生黎质直犷悍,不受欺触,本不为人患。熟黎多湖广、福建之奸民也,狡悍祸贼,外虽供赋于官,而阴结生黎以侵省地,邀掠行旅、居民,官吏经由村峒,多舍其家。峒中有王二娘者,黎之酋也,夫之名不闻。家饶于财,善用其众,力能制服群黎,朝廷赐封宜人,琼管有令于黎峒,必下王宜人,无不帖然。二娘死,女亦能继其业。昔崇宁中,王祖道经略广西,抚定黎贼九百七峒,结丁口六万四千,开通道路一千二百余里,自以为汉唐以来所不臣之地,皆入版图。①
本文记载了海南岛黎峒居民情况以及朝廷“开山洞”接管黎峒的过程,从该文可以较为直接了解被宋朝直接统治前的“峒”的基本情况:
第一,海南岛黎母山的居民成分有生黎、熟黎两种。海南峒中居民也是非汉族群,被分生黎、熟黎两种②,二者区别主要有两处:一是居住地理位置的远近,生黎住深山内,离政治中心远;熟黎住山外,耕种“省地”,与“省民”接壤;二是是否供赋役,“熟黎”多数来自湖广、福建地区(笔者猜测这些“熟黎”应多为汉人),然而在政府看来,他们却是“奸民”,因为他们暗自勾结生黎侵吞“省地”,目的在于以生黎身份占有“省地”后,可以逃避赋税,这也是他们被称为“黎”的根本原因。由此看来,汉人从“良民”变为“奸民”的评判标准在于这些百姓是否接受国家统一管理,并承担相应的服役纳税的义务,“良民”一旦变为“奸民”后,其与蛮夷常常是混淆不清的,并没有十分清楚的界限。如宋代《诸蕃志》也记载道:“黎,海南四郡岛上蛮也……去省地远者为生黎,近者为熟黎……黎之峒落日以繁滋,不知其几千百也,咸无统属,峒自为雄长,止于王、符、张、李数姓。”③
第二,“峒”是一个非汉族群的自治组织单位。海南黎母山峒中文中提到,“黎酋”王二娘凭借其家族势力和个人能力对“群黎”进行管理,并受到朝廷的赐封。这是朝廷的一种“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而“洞”就属于其中的一个基层组织。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称:“自唐宋以来内附,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洞”。④所谓的“种落”,指一个种族的聚落,也可以理解为族群的聚居区。族群人口数量不一,聚落的大小也不同,国家将聚落大的设州县,小的则称为“洞”。可见,宋代的“峒”是少数民族基层组织的一种,作为量词的“峒”,相当于现在一个村落或一个山区。
第三,海南黎峒有一定的人口数量。该文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峒中聚居人口概况,按文中所称的“抚定九百七峒,结丁口六万四千”计算,每个峒的丁口(成年男性)约为71人,如果将妇女儿童包括进去,可以推论宋代海南岛黎母山地区每个峒大约为二三百人。当然,各地的峒有大有小,各个种群有兴有衰,不能一概而论。如清代徐家干在《苗疆闻见录》描述西南苗人情况,也具体谈到聚落的大概人口数量:“苗人聚种而居,窟宅之地皆呼为寨,或二三百为一寨,或百数十家为一寨,依山傍涧,火种刀耕,其生性之蛮野,洵非政教所可及”①。所谓的“窟宅之地”“寨”,其意思应该与我们所分析的作为聚落形态的“峒”相似。另外,按照文中描述,清代的西南苗民与其他地方的“峒”民在生产、生活以及文化习性有着相似之处。
综合闽西象洞和海南黎峒两个典型个案,再结合其他文献,我们基本上可以理解唐宋以来“洞(峒)”作为聚落形态的基本特征:
第一,在地理位置上,“洞(峒)”多处于远离政治中心的偏远山区,经常处于万山之中,这些地区处于在南方的帝国边陲地带,山林阻隔,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多为非汉族群所居住。
第二,在村落特征上,经常表现为四周山峰(山林)环抱,中间有山坳平地。这种村落形态,一方面以有利的地形一定程度上阻隔或延缓了外族(朝廷)势力侵入;另一方面,中间平坳地区特别适合农业生产,保证了本地居民的物资供给。
第三,“洞(峒)”民的族群特征表现为,洞(峒)中居民基本上为非汉民族居住,具有“僻远负固,多不乐输”的特性,即不受朝廷控制,不承担纳税服役的义务。峒中有部分居民为汉族,这部分人经常是“逋负逃役”之人,因此也被政府认为“化外之民”。由此可见,“峒”与“非峒”的区别除了由种族区分的因素外,还在于是否纳税服役,是否接受教化,是否编入版籍。
第四,“洞(峒)”的政治特征:由于各洞(峒)远离政治中心,根据情况有的实行羁縻政策,有的则完全没有管理。随着帝国深入边陲以及各族群互动加深,朝廷或派兵镇守、镇压,或进行招抚,总体上山洞逐渐减少。这与历朝政府开边经略,对山洞进行治理有关。随着山洞渐次被开发,许多原来是“山洞”的地方不再称为“山洞”,而被称为“峒民”“峒僚”“洞寇”的人群,除了有种族的含义外,还具有政治的含义(或文化含义)。
二、作为地名和聚落形态的“畲”
宋元时期,畲作为地名常被文献记载。《宋史·许应龙传》记载“距州(潮州)六七十里曰山斜,峒獠所聚,匄耕土田,不输赋,禁兵与哄,应龙平决之。”①可见“山斜(畲)”作为一个地区的名称,其距离潮州城有六七十里,该“山斜”为“峒獠”聚居、耕作的地区。在广东,“輋”字是非汉民族的一种居住形式,清代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称:“粤人以山林中结竹木障覆居息为輋,故称瑶所止曰輋”②赵希璜也在《横輋》一文中对輋进行解释:“(輋)音斜,粤呼山居者为輋客。”③清代《浮山志》中为张九钺的罗浮诗后作注曰:“畲、輋,俗皆读如斜”。④
实际上,在广东一些地区,“輋”也指山脊,如民国《龙门县志》记载:“土人谓山低缺处为凹,谓山谷为迳,谓山脊为輋。”⑤由此可见,畲、輋、斜等在许多情境下并不作某一类人群的称谓来解释。
再如南宋刘克庄的《漳州谕畲》,该文是畲族史研究中极具地位的一篇重要文献。该篇正文其“畬(畲)”字共出现23次,笔者认为关于这些“畬(畲)”字的解释,根据上下文意思,可分为三类。由表1-1可以看出《漳州谕畲》中并非每一个“畬(畲)”字都作“畲民”解释,有一些应该用类似“溪洞地区”聚落名称来解释,还有一些二者均解释得通的。
第一类“畬(畲)”用族群称谓解释比较合理。如“凡溪洞种类不一:曰蛮、曰猺、曰黎、曰蜑,在漳者曰畬。”此处的畲应该与蛮、猺、黎、蜑并称,说明他们是溪洞种类下属的一类叫“畲”的人;再如“彼畬曷尝读范史”,应该解释为:那些“畲人”何尝读过范晔的《后汉书》呢?
第二类“畬(畲)”用溪峒地区或部落基层组织解释比较合理。如“汀赣贼入畬者”应该解释为,一些汀赣贼逃入畲洞地区;再如“南畬三十余所酋长各籍户口三十余家”,合理解释是:隶属南畲地区或组织的三十多个部落,其酋长分别将本所三十余家编入户籍;又如“清白之吏,固畬之所贵欤”,其合理解释是:清廉正直的官员,乃是巩固畲峒地区珍贵的人才。
第三类就是既可以将“畬(畲)”理解为溪洞地区,又可以解释为溪洞种类、如“二畬既定”可以解释为平定二处畲峒地区,也可以解释为平定二处畲峒地区的族群;再如“畬田”“畬长”可以解释为畲峒地区的田地、酋长,也可以解释为畲人的田地、酋长。
畲作为一种聚落或基层组织解释,还可以在一些文献中体现。如南宋时的赵必岊,字次山,“乡寓公吴允文浚奉密诏以江西招讨使举义反正,结约次山协谋兴复,战不利。允文奔漳州为都督文丞相天祥所杀,次山解兵隐汀州之畬中,踰年以疾终。”②畲作为地名普遍出现在闽粤一些地区中,如《元经世大典序录》载:“(至元)十七年八月,陈桂龙父子反漳州,据山砦,桂龙在九层漈畲,陈吊眼在漳浦山砦,陈三官水篆畲,罗半天梅泷长窖,陈大妇客寮畲。”①上文所称“九层漈畲”“水篆畲”“客寮畲”与“漳浦山砦”“梅泷长窖”并称,均指闽南的一些地名。元代有“畲洞”并称的记载,如《元史》称:“至元十七年,陈桂龙据漳州反,唆都率兵讨之,桂龙亡入畲洞。”②按民国《诏安县志》解释称:“按吊眼贼巢及桂龙所逃畲洞,即诏之乌山十八洞等处,南胜畲寇系其余党,寇乱数十年间。”③陈吊眼、陈桂龙等畲洞为诏安的“乌山十八洞”,所谓的“十八洞”应该是十几个村落(洞)组成一个地区,统称“畲洞”。
畲和洞联系起来作为聚居区的典型例子莫过于百家畲洞。《明史》载:“漳平,(漳州)府西北……东南有象湖山。南有百家畲洞,踞龙岩、安溪、龙溪、南靖、漳平五县之交。”④明代黄仲昭在《八闽通志》中将百家畲洞的地理、人文介绍得更为详细:
百家畲洞,在县南永福里。界龙岩、安溪、龙溪、南靖、漳平五县间。万山环抱,四面阻塞。洞口陡隘,仅通人行。其中深邃宽广,可容百余家。畲田播种,足给衣食。四方亡命者多逋聚其间。凭恃险远,易于为乱。宣德正统间,尝有江志贤、李乌觜、卢赤须、罗兴进者,乌合郡(恐为群之误,笔者注)丑,跳梁出没,至动方岳。守臣连年剿捕,仅得宁息。然服则人,叛则兽,无常性也。自漳平设县以来,官政易及,不复反侧。然尤在司民社者控御得其道云。⑤
清代方志龙岩、漳平等地方志关于百家畲洞的记载,均沿袭《八闽通志》,仅在个别字句稍作增删。⑥另据清道光《漳平县志》记载:
永福(漳平县下的一个里)自为一区,其山之名者有双髻山、猛虎山、大壮山,与百家畲洞于环阻之中又复有平者,然其细已甚不胜纪。①
综合弘治《八闽通志》和道光《漳平县志》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第一,百家畲洞,又称百家畲,这里的“畲”指的是地名。也就是说,畲与洞可以合称,也可以分开单独作为地名。
第二,百家畲洞具有典型的南方少数民族“山洞”特征,表现出“万山环抱,四面阻塞”、中间“深邃宽广”的自然地理特征以及“四方亡命者多逋聚其间”的“化外之民”聚居地的人文特征。
第三,按照“百家畲洞”字面意思,结合象洞有“九十九洞”的特点,我们估计百家畲洞也是由多个洞组合而成。而在漳平一地,与百家畲洞所具有的“于环阻之中又复有平者”地理人文特征的畲洞还有很多,只是无法一一道来,所谓的“其细已甚不胜纪”。
清代以来,许多地方还保存畲(輋)的地名,如李调元《南越笔记》记载广东地区輋人及其聚居地区的情况:“輋人:澄海山中有輋户……輋巢居也;猺所止曰屳、曰峒、亦曰輋。海丰之地,有曰罗輋,曰葫芦輋,曰大溪輋。兴宁有大信輋,归善有窑輋。”②
直到现在,闽粤赣地区仍有许多地名带有“畲”字,③如福建连城带有“畲”字的地名就有19个,而武平也有17个。④其余的如长汀的下畲;上杭的大畲;龙岩的郭畲、小高畲、畲背、洋畲、下经畲;漳平的谢畲、罗畲、百种畲,东下畲;华安的官畲、南靖的桂竹畲、后畲、上麻畲;云霄的桃畲、上梨畲、下梨畲、坝头畲,等等。
学者推论这些地区与畲瑶等非汉族群有一定的联系。清代温仲和在光绪《嘉应州志》中,曾对有关“畲”的地名与族群关系作一番论述,他说:“今地以畲名者尚多有之,而所谓猺獠则绝无其人,盖日久皆化为熟户,而风俗与居民无异矣。”①
在作者看来,带有“畲”字的地名与“猺獠”存在着某种关系,只不过这些非汉民族变为“熟户”后,不再称为“畲”,但地名仍存于今。
再如著名学者徐松石先生也提出:“畲瑶即古代所谓山越。在广东东部散布甚广。平远、蕉岭、梅县、河源、惠来、丰顺、新安等地,现在还有许多畲字或輋字的地名。”②陈龙、吴炳奎、刘大可等学者也对闽粤赣一些地区内带有“畲”字的地名进行考证,以证明历史上畲瑶等族群在该地存在的可能性。③因此,有学者将这些带“畲”字的地名视为闽粤边地区畲族活动史的活“化石”。④
需要指出的是,带有“畲(輋)”地名的出现时间与“猺獠”族群在该地的居住时间,孰先孰后,目前仍无法考证。我们或许可以推论:古代汉人常将“猺獠”生活的地方称为“畲”,正如将南方非汉族群聚居区称为“山洞”一样。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畲”地名的命名与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遗存有关系。司徒尚纪认为在广东等地区,“没有水利工程灌溉的丘陵、山地,其被开发利用土地通名为畬地或畬田,实为梯田,过去实行刀耕火种,至今在海南、粤北黎、瑶地区仍有残存,故以畬为首尾地名在内陆山区较普遍。”广东客家人聚居平远县就有许多以畲命名的地名,反映的是“山区梯田文化景观”。⑤
因此,我们认为“畲”的地名未必一定和非汉族群聚落有关,即:“畲”作为一种地名的命名方式在闽粤赣地区已经形成一种传统,人们用其称呼一些“山脊”或山地地名,而这并不一定和“猺獠”族群有必然的联系。
三、“畲”“峒”生态文化语境下的一种族群分类
在古代中国,由于受到大一统观念的影响,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民族史的撰述,都体现出了诸如“夷夏同祖认同、华夷一家认同、共属中国认同、华夏文化认同”的大一统意识。①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华夏文化在几千年的民族史撰述中一直处于被表述的中心,四方“夷狄”则处于从属地位。而在具体实践中,华夏民族自春秋战国以后,在与周边非华夏民族的互动过程中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表现出华夏族及其文化不断向边陲扩张,最终使得各非华夏民族淹没在华夏族的“海洋”中或成为“华夏海洋”中的“非华夏孤岛”。
因此,在重新审视我国古代民族史时,我们必须将历代有关于“非华夏”族群的文字记载置于当时的社会情境来分析,具体来说:一是在汉文化语境下,这种记载多大程度反映了文字记载者的立场、态度及情感,而作为文本的历史记忆又反映了当时什么样的历史心性?二是这种记载中的文化特征,是否能够反映“异族”的实际情况,即这种客观的文化特征描述能否与“异族”的实际认同情况相一致?或者说,对“他者”只是文字记载者单方面的认同?
“畲”作为一种族群的出现,需要在生态语境和文化语境下考察。首先,自然生态无疑是任何一种族群和文化产生的最基础因素。正如我国历史上形成的游牧与农耕文明的生态界线,自然生态上差异导致了文化的差异,从而形成了文化特色截然不同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畲”作为原始的、粗放的耕作方式,与精耕细作的汉族农业也存在一条若隐若现的生态边界,这种自然生态的差异在族群文化特征上打上鲜明的烙印,这种迥异于“他者”的文化特征,成为“他者”族群观察另一个族群的切入点。根据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给文化所作的定义,文化应该包含了人类经历的各个方面②。按照这种定义,一个族群的文化特征应该包罗万象,而作为文字记载的族群,其呈现给后人的文化特征,充其量不过是一些静态的、被认为的诸多特征中较为典型的、有异于他者的特征。
笔者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农业的变迁认为,“畬(畲)田”的耕作方式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历史上从事“畬田”农业的族群,除了被称为“畬田”民族外,实际上,在某一历史阶段,汉族也从事“畬(烧)田”农业。③主要区别在于:随着汉族农业技术的发展,在汉族社会中,“畬田”的耕作方式逐渐被精耕细作农业所取代;而在一些非汉族群中,“畬田”农业作为一种技术要求不高、较易实施的粗放农业,仍一直被沿用。
随着代表农业文明的汉族文化不断扩张,“畬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遭遇,并产生了生态冲突。这种冲突首先发生在两种生态文化的锋线,也就是在两种生态文化的边界地区是生态矛盾最集中的地方。正如在古代中国,长城沿线被视为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冲突最集中的地方,长城的分布与走向基本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生态系统的分界线。生态文化的冲突带来族群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唐宋时期特别明显。“畬(畲)”之所以在唐宋时期的诗文中大量出现,与唐宋时期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时期,随着帝国华夏化进程加快,中国南方各个地区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北方汉人带来的先进农业与被认为是原始农业残余的“畬田”农业遭遇时,这种文化冲击(cultureshock)使得“畬(畲)”作为一种猎奇、述异、诗化见诸汉人知识分子的笔端。
尽管也有大量诗人对“畬(畲)”不吝溢美之词,但无法改变整个主流文化对“畲”的看法,特别是当“畲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在资源上冲突加剧时,“畲”一种文化标签常贴在非汉族群身上,目的就是将其边缘化。
第三节 小结
本章从生态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唐宋以来与畲族及其先民相关的自然生态和聚落人文情况。本章的主要论点有:
(1)“畲”作为一种古老的耕作方式,不仅在时间维度上,并且在空间广度上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中。要探讨“畲”如何成为一个族群的称谓,必须将其放置于特定的生态语境和文化语境中考察。
(2)在历史上中国中部、南方地区,曾存在畬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的生态冲突。畬田农业是一种较为古老的耕作方式,其在文化特征与日本学者提出的“照叶树林文化”特征相似。唐宋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中心南移,以精耕细作为代表的汉人农业在中国南方地区迅速发展,畬田农业呈现出明显的退缩趋势,宋代以后南方地区梯田的增多,说明了这个现象。随着对生态资源的需求,代表汉人农业的精耕细作与代表古代农耕方式的残存形态的畬田农业开始发生冲突,其生态边界恰好为汉族与非汉族群的边界大部分吻合。
(3)“畲”不仅仅是一种耕作方式,还具有带有聚落的含义。“畲”之所以从一种经济形式或聚落形态的称谓演变为一类族群的称谓.这与汉文化语境有着
密切的关系。“畲(輋)”或“山洞”,起先是作为人类居址称谓而存在的,这种特定的自然生态造就了特殊的聚落文化,从而成为生活在该地区人群的一种人文特征。
(4)在以华夏为中心的民族观指导下,汉人以从事特殊耕作方式(畲、輋),或居住在特殊聚落形态(洞、峒)作为文化特征,将南方非汉族群标签化。本章通过考察闽西象洞和海南黎峒两个个案,总结出作为聚落形态的“畲”“峒”的村落形态特征、族群构成、地方组织方式以及政治人文特征等。以此证明:“畲”或“峒”作为非汉人群的聚落、组织或族群称谓,均是在汉文化语境中产生的。在这种文化语境中,畲(輋)、峒(洞)除了具有区分种族的意义外,还具有政治和文化的意义。
第一节 生态语境下的畬田农业与边界冲突
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休斯(J.Donald Hughes)曾指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们依赖于生态系统,并且不能完全操纵自己的命运……历史叙述必须把人类事件置于地方和地区生态语境之中。”②因此,在考察畲族及其先民的族群文化之前,先对与之相关的地区自然生态进行考察是十分必要的。
一、唐宋时期的畬田农业及其分布情况
畬田农业作为一种粗放的耕作方式早在春秋以前就已经存在,唐宋以后仍在中国南方地区广泛存在。“畲”在唐以前一般写作“畬”,其作为原始农业经济方式最早是指开垦出来的两年或三年田地①,反映的是春秋时期以前我国广泛存在的一种休闲耕作制度。从战国到隋唐,中国古代农业从精耕细作农业成型时期转入精耕细作农业扩展时期,②由于休闲耕作制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畬”在隋唐时期增加了新的音和义:读“YU”时是指开垦两三年的田,读“SHE”时则为“畬田”(烧田)的含义。③
畬田是一种区别于精耕农业的耕作方式,如《魏书·崔辩列传附模弟楷传》记载:“遥途远运,惟用舟舻,南亩畬菑,微事耒耜。”④唐宋以来,畬田农业大量出现于文献中,如刘禹锡的《畬田行》曾具体介绍了畬田的耕作过程:
何处好畬田,团团缦山腹。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惊麏走且
顾,群雉声咿喔。红焰远成霞,轻煤飞入郭。风引上高岑,猎猎度青
林。青林望靡靡,赤光低复起。照潭出老蛟,爆竹惊山鬼。夜色不见
山,孤明星汉间。如星复如月,俱逐晓风灭。本从敲石光,遂至烘天
热。下种暖灰中,乘阳拆牙孽。苍苍一雨后,苕颖如云发。巴人拱手
吟,耕耨不关心。由来得地势,径寸有余金。⑤
文章描写了“畬田”前卜“雨卦”、烧山、种畬等一系列过程,并指出“畬田”的主人为巴人,是西南一带的非汉族群。温庭筠《烧歌》也详细描写了带有“楚越”之地风俗的烧田(畬田)情况,“畬田”的主人也应是非汉人群。⑥
唐代或有一些汉人也从事畬田农业。如唐代韩鄂的《四时纂要》描写的七月开荒田,其耕作方式与畬田有相似之处。将这种耕作方式写入其文曰:
开荒田。凡开荒山泽田,皆以此月芟其草,干,放火烧,至春而开
之,则根朽而省工。若林木绝大者,〓杀之,叶死不扇,便任耕种。三
年之后,根枯茎朽,烧之则入地尽矣。耕荒必以铁爬漏凑之,遍爬之,
漫掷黍稷,再遍耢。明年乃于其中种谷也。①
相对于刘禹锡《畬田行》一文中粗放的畬田耕作方式,开荒田似乎比较精细,这意味着或者开荒田借鉴了畬田的方法;或者可以认为畬田开始慢慢向汉人精细农业转变。韩鄂的《四时纂要》是一本按照四时及月份列举出应做农事的月令式农书,开荒田被列为七月应做的农事,间接说明在唐代仍有许多地区实行畬田或与之相近的农业耕作方式。只不过在非汉人群中,畬田更为流行而已。如唐代黔州之西的东谢蛮地区,“土宜五谷,不以牛耕,但为畬田,每岁易。”②而南蛮地区也是“宜五谷,为畬田,岁一易之。”③
到了宋代,在一些偏远的山区多有“畬田”农业的记载,如宋代王禹偁《小畜集》卷八《畬田词并序》描写了西北地区居民刀耕火种的情况:
上雒郡南六百里,属邑有丰阳、上津,皆深山穷谷,不通辙迹。其民刀耕火种,大底先斫山田,虽悬崖绝岭,树木尽仆,俟其干且燥,乃行火焉。火尚炽,即以种播之。然后酿黍稷、烹鸡豚,先约曰某家某日有事于畬田,虽数百里如期而集,锄斧随焉。至则行酒啖炙,鼓噪而作,盖劚而掩其土也。劚毕则生,不复耘矣。援桴者,有勉励督课之语,若歌曲然。且其俗更互力田,人人自勉。仆爱其有义,作《畬田》五首,以侑其气。亦欲采诗官闻之,传于执政者,苟择良二千石暨贤百里,使化天下之民如斯民之义,庶乎污莱尽辟矣。其词则取乎俚,盖欲山民之易晓也。④
从序言中可以看出山民“畬田”的斫山田、烧林木、播种、盖土的劳作程序,同时也看出在“畬田”时,不同地区人们互相协作,主人酒菜待客,同时伴有宛如歌声的“劳动号子”。作者显然被这种热烈的气氛感染,写了五首简单易懂的《畲田词》①,希望能进一步推广“畬田”,将其用于各地山林的开辟。
在中国南方各地,“畬田”的耕作方式普遍存在。如《宋史》记载西南地区抚水州一些“聚山险”的蛮夷从事畲田农业,但是由于耕作方式粗放,“收谷粟甚少”②而宋代张淏在《云谷杂记》中提到湖南等地区的畲田收成较好:
沅湘闻多山,农家惟种粟,且多在冈阜,每欲布种时,则先伐其林木,纵火焚之,俟其成灰,即布种于其间。如是则所收必倍,盖史所谓刀耕火种也。③
朱胜非在《绀珠集》中则记载宋代江南畬田:
江南人多畬田,先纵火谓之熂炉,俟经雨下,种历三岁,土脉竭不可种,复生草木。宋西阳王子尚云:山湖之俗,熂山封水以种,名疁田,即谓此也。《尔雅》田一岁曰菑,田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畬。田凡三岁,不可复种,故名畬。熂音饩,疁音留。④
这里提到的“种历三岁,土脉竭不可种,复生草木”,说明了从事畬田的民族必须常常迁徙,以获得新的山地用以烧山种畲。
华南地区的福建也实行畬田。早在唐代,诗人贯休曾在《怀武夷红石子》写有“竹鞘畲刀缺,松枝猎箭牢”⑤诗句,依稀可以了解唐代建州或存在畲田农业;《全唐文》收入唐代陈元光的《请建州县表》,其文称:“况兹镇地极七闽,境连百粤,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⑥虽然陈元光的《请建州县表》被考证是伪作①,但至少说明在某一历史时段,漳州的“蛮僚”或当地居民曾从事有关“火田”(畬田的别称)的耕作活动,其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在后人建构该篇伪作的时候仍被重新提起。宋人杨杰在《故温州录事参军陈君墓志铭》中记载当时宁化军有盗寇持畲刀盗割粮食,其文称:“再调汀州司理参军,宁化军有盗六人,持畲刀,夜割人禾,田主逐之,五人逸去,其一独留,且杀主人。”②这则材料比较肯定地说明宋代或更早福建存在畲田农业。
明清以后,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仍是南方一些非汉民族主要耕作方式。如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曾记载:“南方多畬田,种之极易。春粒细香美,少虚怯,只于灰中种之,又不锄治,故也。”③明代谢肇淛记载闽东畲人烧畲“……过湖坪,值畲人纵火焚山,西风甚急,竹木迸爆霹雳。舆者犯烈炎而驰下山,回望十里为灰矣。”④清代杨澜《临汀汇考》描述汀州地区畲客刀耕火种情况:“此外又有棱米,又名畲米,畲客开山种树,掘烧乱草,乘土暖种之,分粘和不粘二种,四月种,九月收。”⑤范绍质在《徭民纪略》也称:“汀东南百余里,有猺民焉……糞田以火土,草木黄落,烈山泽,雨瀑灰浏,田遂肥饶,播种布谷,不耘耔而获。”⑥
在广东的粤东等地的輋(畲)民也存在类似的耕作方式,如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七:“輋人……其人耕无犁锄,率以刀治土,种五谷,曰刀耕;燔林木,使灰入土,土暖而蛇蛊死,以为肥,曰火耨。是为畬蛮之类。《志》所称伐山而甾蓻草而播,依山谷采猎,不冠不屦者是也。”⑦吴震方《岭南杂记》则写道:“潮之西北山中有畲户者……刀耕火种,不供赋也。”⑧
总之,唐代以来,南方许多地区存在刀耕火种的“畬田”耕作方式.这种相对粗放的耕作方式常常作为非汉族群文化特征被大量记载在文献中①。有关畲田的耕作技术,大泽正昭以及周尚兵等学者均作了详细的考证,②兹不赘述。
实际上,“畬田”(或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很长时间存在于人类社会中,而不仅仅局限于上述几个地区。自20世纪40—50年代起,由日本学者中尾佐助、上山春平、佐佐木高明等提出了“照叶树林③文化论”。该理论认为:从喜马拉雅山南麓东经不丹、阿萨姆、缅甸、中国云南南部、泰国、老挝、越南北部、中国长江南岸直至日本西部的辽阔地域存在一个地域广阔的照叶树林文化带“照叶树林带”(见图1-1)。这一地带的文化具有相通性,其最基本、最重要的文化特征是以栽种水稻、杂粮(包括旱稻)、薯类为主的烧田农业。④照叶树林地带上的少数民族众多,有许多民族都曾从事或者至今仍在延续传统刀耕火种的农耕生产方式。⑤
根据“照叶树林带”的分布情况,结合有关新石器时期区系划分,可以看出中国南部两个中心文化区,即华南地区及长江流域部分地区属于照叶树林的分布范围;而二者之间的过渡带,即南岭以北和武夷山以西地区过渡地带则恰好处于东亚半月弧中心的东缘和南缘。⑥这也间接说明了该地区在历史上广泛存在刀耕火种(畬田农业)的经济方式。
日本学者大泽正昭发现,唐宋时期实行畬田分布的地域一度相当广大,⑦并且与獠、蛮、氐、羌、山棚、山越等“少数民族”的居住区域有相当程度的重合,曾雄生将这些以畬田(刀耕火种)为主要特征的农耕民族定义为“畬田民族”。①实际上,畬田的耕作方式曾广泛存在于包括汉族在内的各个族群中,只不过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畬田作为中国古代农耕方式的残存形态被主流农业生产者所淘汰。如果以更广阔的时空来考察畬田(刀耕火种),笔者更愿意将所谓的“畬田民族”认定为特定时期某一人群的特定称谓。唐宋以后,畬田耕作方式逐渐被边缘化,自唐代以后,随着江南的开发更进一步,畬田区域呈缩小的趋势,大泽先生因此认为畬田是中国古代农耕方式的残存形态。②
将大泽正昭的“畬田分布图”(见图1-2)与东亚地区“照叶树林带”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唐宋的畬田基本在照叶树林带的范围内,少部分畬田在“照叶树林带”偏北地域,这反映了中国古代自然生态的变化:即烧田农业有向南、向西偏移的趋势。
由此可以说明:一是畬田的生态环境分布在中国的中南部,随着历史的变迁,烧田农业有向南、向西偏移的趋势;二是烧田农业的缩小与走向,与帝国开边进程(中国地方区域经济渐次开发)的趋势和走向是相一致的。随着帝国权力的深入和经济的开发,主流农业势力在地域上逐渐由北向南,在地区上逐渐由中心平原盆地向偏远山区扩张,这也意味着主流农业的生产者(主要是汉族)族群势力与之同步扩张。而造成唐宋时期畬田地区与獠、蛮、氐、羌、山棚、山越等族群分布区域高度重合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上述族群较多分布在中国中南部及偏远山区的历史事实;二是汉族在农业扩张过程中,与固守畬田农业耕作方式族群产生的生态冲突而留下的历史印记。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畬”作为原始农业经济方式早已存在,唐宋以后的社会经济转型,使得畬田农业呈缩小和偏移的趋势,畬田与精耕细作农业的生态矛盾随着社会发展与族群扩张逐渐显现。
二、畬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之间的冲突
竹村卓二先生在研究东南亚的农业形态时给出,山间坡面粗放的刀耕火种农业的生态系统受到要素的制约:一是局部地区的自然环境;二是与其内部的社会组织、技术、人口动态有关;三是与外部社会有关。①也就是说,刀耕火种的生态系统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在资源竞争比较激烈的地方,刀耕火种的生态系统往往因为某一要素的缺失而受到破坏。文献中常将刀耕火种的特点描述为“随山种插,去瘠就腴”①“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它徙”②“耕山而食,去瘠就腴,率数岁一徙”③等,这种粗放型的耕作方式要求在自然生态中,必须有相应的大片的山地资源供其耕作。在外部社会中,随着汉民族“华夏化”④进程的加快,不同族群所代表的不同经济方式存在着竞争关系。显然,畬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二者之间在生态资源上存在的竞争关系慢慢突显,并逐渐引起生态冲突。早在唐宋以前,这种冲突就已存在,如《晋书·食货志》就载了东南地区水田与陆田的冲突:
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非不尔也,然此事施于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顷户口日增,而陂堰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水雨,辄复横流,延及陆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陆种。⑤
唐宋以后,大部分汉族地区农业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进入精耕细作农业扩张时期。⑥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更是加剧了畬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的冲突。这种冲突可以从《五灯会元》的一则记载看出:
南岳玄泰禅师……尝以衡山多被山民斩伐烧畬,为害滋甚,乃作畬山谣曰:“畬山儿,畬山儿,无所知。年年斫断青山嵋。就中最好衡岳色,杉松利斧摧贞枝。灵禽野鹤无因依,白云回避青烟飞猿猱路绝岩崖出,芝术失根茆草肥。年年斫罢仍再锄,千秋终是难复初。又道今年种不多,来年更斫当阳坡。国家寿岳尚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远迩传播,达于九重,有诏禁止。故岳中兰若无复延燎,师之力也。①
玄泰禅师显然十分反对在南岳地区畬山“斩伐烧畬”,他将这些“斩伐烧畬”的“山民莫徭辈”②蔑称为“畬山儿”。③玄泰禅师所提到的从事“刀耕火种”的莫徭,被认为是一种“承盘瓠之后”的“夷蜒”族群,“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④因此,学者经常将其与后世的畲、瑶等族群联系起来。
唐末五代以后,在中国南方各地开始出现梯田,这是一种与畬田有所不同的山田梯田的兴起,是精耕细作农业从平地延伸到山地的表现,这是中国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的重要表现。元代王祯在其《农书》上对梯田的地理环境、耕作情况、作物及收成等进行介绍,其文曰:
梯田,谓梯山为田也。夫山多地少之处,除磊石及峭壁,例同不毛,其余所在土山,下自横麓,上及危巅,一体之间,裁作重磴,即可种艺。如土石相半,则必叠石相次,包土成田。又有山势峻极,不可展足,播殖之际,人则伛偻蚁沿而上,耨土而种,蹑坎而耘,此山田不等,自下登陟,俱若梯磴,故总曰梯田。上有水源,则可种杭林。如止陆种,亦宜粟麦,盖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乡细民,必求垦佃,犹胜不稼。其人力所致,雨露所养,不无少获。然力日至此,夫免艰食,又复租税随之,良可悯也。⑤
可见,梯田付出更多的人力劳动成本,这是对山地最大限度地利用,收获也比刀耕火种来得多。学者认为,南方梯田的产生与唐宋以后经济重心南移及大量北人南迁有一定关系。①应该讲,梯田耕作技术比畬田要求更高,虽然梯田和畬田二者并非前后继替的关系,但有史料证明很多的梯田是由畬田转化而来的。
最早出现“梯田”一词,就目前发现的史料应该出自于南宋范成大在乾道七年(1172年)以后几年所作《骖鸾录》,该书主要讲述范成大在乾道壬辰十二月,以中书舍人出知静江府途中的所见所闻。在乾道八年闰二月,范成大到达江西宜春,由于慕仰山之名,特意逗留几日,其文写道:
泊袁州(今江西宜春),闻仰山之胜久矣,去城虽远,今日特往游之。二十五里,先至孚惠庙……旧传二龙昔居仰山中,以其地施仰山祖师,迁居于此……出庙三十里,至仰山,缘山腹乔松之磴,甚危。岭阪之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建寺之祖仰山师者,事具《传灯录》中,号小释迦。始入山求地,一獭前引,今有獭桥。至谷中,即二龙所居,化为白衣,逊其地焉。大仰之名,遂闻天下。②
文中的提到的“仰山祖师”就是伪仰宗的创始人慧寂禅师(815—891年)。慧寂禅师曾于唐会昌元年(841年)从湖南伪山来到仰山脚下“创庵以居”,③至唐宣宗年间正式建寺,并由宣宗赐名“栖隐寺”。当时的仰山并非如范成大所描述的“禾田层层”,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在仰山可能大部分还是畬田耕作方式。《五灯会元》卷九《南岳下四世·仰山慧寂禅师》记载了仰山慧寂禅师生平,并载有大篇幅的师(沩山灵祐禅师)、徒(仰山慧寂禅师)对话,其中谈论到仰山烧山种畲的情况:
师在沩山,为直岁,作务归,沩问:“甚么处去来?”师曰:“田中来。”沩曰:“田中多少人?”师插锹叉手。沩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师拔锹便行……师夏末问讯沩山次,沩曰:“子一夏不见上来,在下面作何所务?”师曰:“某甲在下面,鉏得一片畬,下得一箩种。”沩曰:“子今夏不虚过。”④
另外,在《袁州仰山慧寂禅师语录》中也记载了慧寂禅师与师兄弟谈论烧畲自种自食的事:“山僧与汝诸人说着:‘开得一片畲,绵绵密密。两顿粥饭,其道自办’。”①
其中提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中的“刈茅”应该也与烧山种畬活动有关。由此可见,唐代后期的湖南、江西等南方地区都广泛分布着畬田,而社会上对畬田的态度不尽相同。但总的趋势是,畬田的地域慢慢地缩小,以仰山为例,唐末还可以“〓得一片畬”,过了一两百年的范成大生活的南宋时代,仰山就全部被开垦为梯田了。
在宋代以后,在南方的一些丘陵山地开垦梯田,已经成为比较普遍的事了。如宋代方勺《泊宅编》曾记载福建地区因地理环境垦造梯田的情况:
七闽地狭瘠,而水源浅远,其人虽至勤俭,而所以为生之具,比他处终无有甚富者。垦山陇为田,层起如阶级。然每远引溪谷水以灌溉,中途必为之硙,不唯碓米,亦能播精。朱行中知泉州,有“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之诗,盖纪实也。②
明代谢肇淛在《五杂俎》中也有类似的记载:“闽中自高山至平地,截截为田,远望如梯。真昔人所云‘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者,可谓无余地也。”谢肇涮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闽之福塘,地狭而人众,四民之业无远不届,即遐陬穷发髪、人迹不到之处往往有之,诚有不可解者,盖地狭则无田以自食,而人众则射利之途愈广故也。”③清初学者周亮工在《闽小纪》也记载道:“闽中壤狭田少,山麓皆治为陇亩,昔人所谓磳田也。”④梯田的耕作更为辛苦,收获却不多,道光《永定县志》称:“地斗隘厥土骍刚,山田五倍于平野,层累十余级不盈一亩。”⑤梯田之所以流行于南方地区,原因有二:其一是南方多山地丘陵的地理环境;其二是随着当地人口的增加,平原土地开垦殆尽,迫使人们往山地丘陵寻求土地,因地制宜地开垦梯田,最大限度利用土地进行生产。相对于畬田农业的粗放管理,梯田在土地利用率上更高效,因此,也更适用于人地关系紧张的地区。
宋代以后,畬田农业在一定区域受到限制,如北宋政府开始实行“火田之禁”,《宋史·食货志》载:
大中祥符四年,诏曰:“火田之禁,著在《礼经》,山林之间,合顺时令。其或昆虫未蛰,草木犹蕃,辄纵燎原,则伤生类。诸州县人畬田,并如乡土旧例,自馀焚烧野草,须十月后方得纵火。其行路野宿人,所在检察,毋使延燔。①
诏令反映了两点:一是“诸州县”存在畬田现象,二是对畬田进行时间(“须十月后”)和地点(“毋使延燔”,即不让火势蔓延到畬田以外的地方)的限制。这种限制是在确保主流农耕文化的利益:要求畬田要“合顺时令”实际上是合顺精耕细作的“时令”;要求畬田不要“伤生类”实际上是不要损害以汉人为代表的利益。直到明清,这种生态的冲突依然存在,如王阳明在《平輋》一诗中写道:“处处山田尽入輋(畬),可怜黎庶半无家”②,描述的是赣闽粤部分地方百姓的田园为畬田所占的情况。
总之,“畬”作为原始农业经济方式早已存在,包括汉族在内的许多族群都曾从事“畬田”农业方式。唐宋以后,随着经济的开发,由于在生态资源上存在竞争关系,畬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的生态边界凸显。
第二节 文化语境下的南方“畲洞”及其聚落人文
历史上常将唐代以后“峒蛮”“峒獠”与畲族联系起来。“畲”不仅仅是一种耕作方式,还具有聚落的含义。“畲”从一种经济形式或聚落形态的称谓演变为一类族群的称谓,其与汉文化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畲”作为一种溪峒地区或部落基层组织存在,其与“洞(峒)”一样,均经历过本义——聚落称谓——族群称谓的转变过程。在以华夏为中心的民族观指导下,畲、峒的文化特征成为汉族对南方非汉族群分类的重要依据。
一、山洞:从洞穴居址到“蛮夷”聚落称谓的转变
“畲”和“峒”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学界常将历史上出现在南方地区“山洞”“溪洞”“峒蛮”“峒獠”等族群与畲民联系起来。峒,也称“洞”,或“山洞”,关于山洞的解释,学术界上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自然环境说,指原来未设政区的偏远之处的山间溪谷;①二是民族构成说,专门指南方山区非汉族土著民族;②三是地方组织说,指随着中原王朝政治在华南社会的扩展,在国家行政统治未能到达的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由土豪势力建立起来的具有实质性的地域统治体制或特殊的军政单位。③以上观点将“溪洞”并称,各观点并不完全矛盾,只不过是将山洞放置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中讨论而已。如李荣村指出:“唐宋时凡近山的蛮夷住地、聚落或羁縻州洞等都可称作峒,又称溪峒,也就是蛮洞的意思,但绝不当作狭义的洞穴解释。”④李氏强调以特定历史条件来考察“洞”的含义,这是十分有道理的,但至于“洞”为何从表示“岩洞”“窟穴”的原意,变为少数民族“聚落”或组织,那还是得探寻洞的本源,方可做出解释。
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旧石器时代,洞穴居址作为人类聚落形态就已经存在。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就曾指出:“洞穴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者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⑤古代人类有选择寻找居住的洞穴,留下各个时代的洞穴堆积,在我国的华南、华北地区均分布着具有代表性的各时代洞穴。⑥一般来讲,这个时期的洞穴并非孤立、静态的存在,而是作为一个聚落系统发挥生产生活的功能。这一阶段的聚落形态主要为“洞穴-旷野”模式,也就是说,人类选择在洞穴,既要考虑洞穴作为遮蔽所的功能,又要考虑到以洞穴为中心的周围自然环境,尤其是食物资源的获取情况。⑦到了中石器时代⑧,随着原始农业的萌芽,人类社会开始由采集渐进到农业,由狩猎发展为畜牧⑨,在生产、生活技术水平提高的基础之上,人类从洞穴向更广阔的台地、平原、山冈进发。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建造技术高度发展,人们已经不再依赖洞穴,在各个适合人类生产生活的地形建造居所,形成聚落,并在不同地区发展出多元化的人类居住体系。在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华南地区所占数量不少,比较集中地分布在广东、广西、江西、云南等地区,浙江、福建、湖南等地也有少量分布,大概可以将遗址分为洞穴遗址、贝丘遗址、台地遗址三种类型。①从后两种类型足以证明人类的居址向多元化发展。在新石器晚期,人们已经大量建造公共广场、祭坛等建筑,聚落居址成为文明的标志。随着聚落的发展,中国个别地区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进入城邦模式。②
可见,早期人类由于生产生活技术水平较低,只能依赖洞穴作为庇护所,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对获取自然资源的需求,人类从“山洞”走向“旷野”,形成聚落,创造出越来越丰富的人类文明。那么可以想见,随着地区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提前进入“文明社会”、居住在城邦村落的族群在看待仍在“洞穴”居住的族群时,必定占有相对的心理优越感。而正是这种优越感带来的人们观念的变化,使得洞的意义开始延伸,也就是说“洞”在“文化先进”地区的人群看来,开始成为一种文化落后、野蛮未开化的象征。这种象征逐渐被“标签化”或“模式化”,形成了某一人群对另外一个人群的固有印象,如唐代刘禹锡称“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桴筏者,与华言不通。”③“居洞砦”是野蛮、未开化族群的重要特征之一。唐代以后,这些“居洞砦”的非汉人群一般被称为“峒民”或“峒獠”,其广泛分布于南方地区,如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写道:“峒獠者,岭表溪峒之民,古称山越,唐宋以来,开拓寝繁,自邕州以东,广州以西,皆推其雄长者为首领,籍其民为壮丁。”④这些分布广泛的“洞”,其地理环境、自然生态、社会组织特征又是如何呢?笔者拟以闽西象洞和海南黎峒作为例子进行分析。
宋开庆年间由胡太初所修的《临汀志》记载了有关象洞的情况,其文曰:
象洞,在武平县南一百里,接潮、梅界。林木蓊翳,旧传象出其间,故名。后渐刊木诛茅,遇萦纡怀抱之地,即为一聚落,如是者九十有九,故俗号“九十九洞”。其地膏沃,家善酝酿,邑人之象洞酒。洪刍有《老酒赋》,正谓此。但僻远负固,多不乐输,故置巡检寨以镇焉。①
按照作者的描述,象洞应该可以被认为是南方非汉民族居住的“山洞”的一种。以上材料可以说明:
第一,从自然生态上看,象洞原先是人迹罕至、丛箐林密的原始山林地带,在未开发之前,此地乃象群出没之地②,象洞因此而得名。
第二,从聚落形态看,象洞从原始森林变为人类聚居地的过程大概有三个步骤:首先,开辟山林,“刊木诛茅”;其次,选择“萦纡怀抱”的地理环境,在中间平坦、土地肥沃的地方开发成一个聚落;再次,随着山林开发的深入,各个“洞”被次第开发,如象洞形成了“九十九洞”的规模。笔者推论,“九十九”如此巧妙的数字,在此语境下应该不是实指,而是虚数,描述者只是想表达“洞”之数量极多而已。关于各洞之间的关系,应该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以地形看,各个“洞”周围山林林阻隔,交通不便,各洞之间可以保持相对独立的状态;而以名称看,象洞统称为“九十九洞”,说明各洞在“类型”上是相似的,不仅地理环境相似,族群多有相通,所以可以统称。
第三,从人文生态上看,洞中有平坦且肥沃土地可供“洞民”从事农业,并善于酿酒,其“象洞酒”在闻名于武平一邑;象洞早期居民不纳赋税,“僻远负固,多不乐输”,被认为是“化外之民”。随着王朝势力深入边陲,国家在非汉族群的地区驻兵,以控制当地“负固”之徒。
周去非《岭外代答》“海外黎蛮条”记载当地“黎峒”的情况,颇具代表性,可以看做是唐宋“蛮夷”聚落的一个典型,其文曰:
海南有黎母山,内为生黎,去州县远,不供赋役;外为熟黎,耕省地,供赋役,而各以所迩隶于四军州。生黎质直犷悍,不受欺触,本不为人患。熟黎多湖广、福建之奸民也,狡悍祸贼,外虽供赋于官,而阴结生黎以侵省地,邀掠行旅、居民,官吏经由村峒,多舍其家。峒中有王二娘者,黎之酋也,夫之名不闻。家饶于财,善用其众,力能制服群黎,朝廷赐封宜人,琼管有令于黎峒,必下王宜人,无不帖然。二娘死,女亦能继其业。昔崇宁中,王祖道经略广西,抚定黎贼九百七峒,结丁口六万四千,开通道路一千二百余里,自以为汉唐以来所不臣之地,皆入版图。①
本文记载了海南岛黎峒居民情况以及朝廷“开山洞”接管黎峒的过程,从该文可以较为直接了解被宋朝直接统治前的“峒”的基本情况:
第一,海南岛黎母山的居民成分有生黎、熟黎两种。海南峒中居民也是非汉族群,被分生黎、熟黎两种②,二者区别主要有两处:一是居住地理位置的远近,生黎住深山内,离政治中心远;熟黎住山外,耕种“省地”,与“省民”接壤;二是是否供赋役,“熟黎”多数来自湖广、福建地区(笔者猜测这些“熟黎”应多为汉人),然而在政府看来,他们却是“奸民”,因为他们暗自勾结生黎侵吞“省地”,目的在于以生黎身份占有“省地”后,可以逃避赋税,这也是他们被称为“黎”的根本原因。由此看来,汉人从“良民”变为“奸民”的评判标准在于这些百姓是否接受国家统一管理,并承担相应的服役纳税的义务,“良民”一旦变为“奸民”后,其与蛮夷常常是混淆不清的,并没有十分清楚的界限。如宋代《诸蕃志》也记载道:“黎,海南四郡岛上蛮也……去省地远者为生黎,近者为熟黎……黎之峒落日以繁滋,不知其几千百也,咸无统属,峒自为雄长,止于王、符、张、李数姓。”③
第二,“峒”是一个非汉族群的自治组织单位。海南黎母山峒中文中提到,“黎酋”王二娘凭借其家族势力和个人能力对“群黎”进行管理,并受到朝廷的赐封。这是朝廷的一种“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而“洞”就属于其中的一个基层组织。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称:“自唐宋以来内附,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洞”。④所谓的“种落”,指一个种族的聚落,也可以理解为族群的聚居区。族群人口数量不一,聚落的大小也不同,国家将聚落大的设州县,小的则称为“洞”。可见,宋代的“峒”是少数民族基层组织的一种,作为量词的“峒”,相当于现在一个村落或一个山区。
第三,海南黎峒有一定的人口数量。该文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峒中聚居人口概况,按文中所称的“抚定九百七峒,结丁口六万四千”计算,每个峒的丁口(成年男性)约为71人,如果将妇女儿童包括进去,可以推论宋代海南岛黎母山地区每个峒大约为二三百人。当然,各地的峒有大有小,各个种群有兴有衰,不能一概而论。如清代徐家干在《苗疆闻见录》描述西南苗人情况,也具体谈到聚落的大概人口数量:“苗人聚种而居,窟宅之地皆呼为寨,或二三百为一寨,或百数十家为一寨,依山傍涧,火种刀耕,其生性之蛮野,洵非政教所可及”①。所谓的“窟宅之地”“寨”,其意思应该与我们所分析的作为聚落形态的“峒”相似。另外,按照文中描述,清代的西南苗民与其他地方的“峒”民在生产、生活以及文化习性有着相似之处。
综合闽西象洞和海南黎峒两个典型个案,再结合其他文献,我们基本上可以理解唐宋以来“洞(峒)”作为聚落形态的基本特征:
第一,在地理位置上,“洞(峒)”多处于远离政治中心的偏远山区,经常处于万山之中,这些地区处于在南方的帝国边陲地带,山林阻隔,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多为非汉族群所居住。
第二,在村落特征上,经常表现为四周山峰(山林)环抱,中间有山坳平地。这种村落形态,一方面以有利的地形一定程度上阻隔或延缓了外族(朝廷)势力侵入;另一方面,中间平坳地区特别适合农业生产,保证了本地居民的物资供给。
第三,“洞(峒)”民的族群特征表现为,洞(峒)中居民基本上为非汉民族居住,具有“僻远负固,多不乐输”的特性,即不受朝廷控制,不承担纳税服役的义务。峒中有部分居民为汉族,这部分人经常是“逋负逃役”之人,因此也被政府认为“化外之民”。由此可见,“峒”与“非峒”的区别除了由种族区分的因素外,还在于是否纳税服役,是否接受教化,是否编入版籍。
第四,“洞(峒)”的政治特征:由于各洞(峒)远离政治中心,根据情况有的实行羁縻政策,有的则完全没有管理。随着帝国深入边陲以及各族群互动加深,朝廷或派兵镇守、镇压,或进行招抚,总体上山洞逐渐减少。这与历朝政府开边经略,对山洞进行治理有关。随着山洞渐次被开发,许多原来是“山洞”的地方不再称为“山洞”,而被称为“峒民”“峒僚”“洞寇”的人群,除了有种族的含义外,还具有政治的含义(或文化含义)。
二、作为地名和聚落形态的“畲”
宋元时期,畲作为地名常被文献记载。《宋史·许应龙传》记载“距州(潮州)六七十里曰山斜,峒獠所聚,匄耕土田,不输赋,禁兵与哄,应龙平决之。”①可见“山斜(畲)”作为一个地区的名称,其距离潮州城有六七十里,该“山斜”为“峒獠”聚居、耕作的地区。在广东,“輋”字是非汉民族的一种居住形式,清代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称:“粤人以山林中结竹木障覆居息为輋,故称瑶所止曰輋”②赵希璜也在《横輋》一文中对輋进行解释:“(輋)音斜,粤呼山居者为輋客。”③清代《浮山志》中为张九钺的罗浮诗后作注曰:“畲、輋,俗皆读如斜”。④
实际上,在广东一些地区,“輋”也指山脊,如民国《龙门县志》记载:“土人谓山低缺处为凹,谓山谷为迳,谓山脊为輋。”⑤由此可见,畲、輋、斜等在许多情境下并不作某一类人群的称谓来解释。
再如南宋刘克庄的《漳州谕畲》,该文是畲族史研究中极具地位的一篇重要文献。该篇正文其“畬(畲)”字共出现23次,笔者认为关于这些“畬(畲)”字的解释,根据上下文意思,可分为三类。由表1-1可以看出《漳州谕畲》中并非每一个“畬(畲)”字都作“畲民”解释,有一些应该用类似“溪洞地区”聚落名称来解释,还有一些二者均解释得通的。
第一类“畬(畲)”用族群称谓解释比较合理。如“凡溪洞种类不一:曰蛮、曰猺、曰黎、曰蜑,在漳者曰畬。”此处的畲应该与蛮、猺、黎、蜑并称,说明他们是溪洞种类下属的一类叫“畲”的人;再如“彼畬曷尝读范史”,应该解释为:那些“畲人”何尝读过范晔的《后汉书》呢?
第二类“畬(畲)”用溪峒地区或部落基层组织解释比较合理。如“汀赣贼入畬者”应该解释为,一些汀赣贼逃入畲洞地区;再如“南畬三十余所酋长各籍户口三十余家”,合理解释是:隶属南畲地区或组织的三十多个部落,其酋长分别将本所三十余家编入户籍;又如“清白之吏,固畬之所贵欤”,其合理解释是:清廉正直的官员,乃是巩固畲峒地区珍贵的人才。
第三类就是既可以将“畬(畲)”理解为溪洞地区,又可以解释为溪洞种类、如“二畬既定”可以解释为平定二处畲峒地区,也可以解释为平定二处畲峒地区的族群;再如“畬田”“畬长”可以解释为畲峒地区的田地、酋长,也可以解释为畲人的田地、酋长。
畲作为一种聚落或基层组织解释,还可以在一些文献中体现。如南宋时的赵必岊,字次山,“乡寓公吴允文浚奉密诏以江西招讨使举义反正,结约次山协谋兴复,战不利。允文奔漳州为都督文丞相天祥所杀,次山解兵隐汀州之畬中,踰年以疾终。”②畲作为地名普遍出现在闽粤一些地区中,如《元经世大典序录》载:“(至元)十七年八月,陈桂龙父子反漳州,据山砦,桂龙在九层漈畲,陈吊眼在漳浦山砦,陈三官水篆畲,罗半天梅泷长窖,陈大妇客寮畲。”①上文所称“九层漈畲”“水篆畲”“客寮畲”与“漳浦山砦”“梅泷长窖”并称,均指闽南的一些地名。元代有“畲洞”并称的记载,如《元史》称:“至元十七年,陈桂龙据漳州反,唆都率兵讨之,桂龙亡入畲洞。”②按民国《诏安县志》解释称:“按吊眼贼巢及桂龙所逃畲洞,即诏之乌山十八洞等处,南胜畲寇系其余党,寇乱数十年间。”③陈吊眼、陈桂龙等畲洞为诏安的“乌山十八洞”,所谓的“十八洞”应该是十几个村落(洞)组成一个地区,统称“畲洞”。
畲和洞联系起来作为聚居区的典型例子莫过于百家畲洞。《明史》载:“漳平,(漳州)府西北……东南有象湖山。南有百家畲洞,踞龙岩、安溪、龙溪、南靖、漳平五县之交。”④明代黄仲昭在《八闽通志》中将百家畲洞的地理、人文介绍得更为详细:
百家畲洞,在县南永福里。界龙岩、安溪、龙溪、南靖、漳平五县间。万山环抱,四面阻塞。洞口陡隘,仅通人行。其中深邃宽广,可容百余家。畲田播种,足给衣食。四方亡命者多逋聚其间。凭恃险远,易于为乱。宣德正统间,尝有江志贤、李乌觜、卢赤须、罗兴进者,乌合郡(恐为群之误,笔者注)丑,跳梁出没,至动方岳。守臣连年剿捕,仅得宁息。然服则人,叛则兽,无常性也。自漳平设县以来,官政易及,不复反侧。然尤在司民社者控御得其道云。⑤
清代方志龙岩、漳平等地方志关于百家畲洞的记载,均沿袭《八闽通志》,仅在个别字句稍作增删。⑥另据清道光《漳平县志》记载:
永福(漳平县下的一个里)自为一区,其山之名者有双髻山、猛虎山、大壮山,与百家畲洞于环阻之中又复有平者,然其细已甚不胜纪。①
综合弘治《八闽通志》和道光《漳平县志》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第一,百家畲洞,又称百家畲,这里的“畲”指的是地名。也就是说,畲与洞可以合称,也可以分开单独作为地名。
第二,百家畲洞具有典型的南方少数民族“山洞”特征,表现出“万山环抱,四面阻塞”、中间“深邃宽广”的自然地理特征以及“四方亡命者多逋聚其间”的“化外之民”聚居地的人文特征。
第三,按照“百家畲洞”字面意思,结合象洞有“九十九洞”的特点,我们估计百家畲洞也是由多个洞组合而成。而在漳平一地,与百家畲洞所具有的“于环阻之中又复有平者”地理人文特征的畲洞还有很多,只是无法一一道来,所谓的“其细已甚不胜纪”。
清代以来,许多地方还保存畲(輋)的地名,如李调元《南越笔记》记载广东地区輋人及其聚居地区的情况:“輋人:澄海山中有輋户……輋巢居也;猺所止曰屳、曰峒、亦曰輋。海丰之地,有曰罗輋,曰葫芦輋,曰大溪輋。兴宁有大信輋,归善有窑輋。”②
直到现在,闽粤赣地区仍有许多地名带有“畲”字,③如福建连城带有“畲”字的地名就有19个,而武平也有17个。④其余的如长汀的下畲;上杭的大畲;龙岩的郭畲、小高畲、畲背、洋畲、下经畲;漳平的谢畲、罗畲、百种畲,东下畲;华安的官畲、南靖的桂竹畲、后畲、上麻畲;云霄的桃畲、上梨畲、下梨畲、坝头畲,等等。
学者推论这些地区与畲瑶等非汉族群有一定的联系。清代温仲和在光绪《嘉应州志》中,曾对有关“畲”的地名与族群关系作一番论述,他说:“今地以畲名者尚多有之,而所谓猺獠则绝无其人,盖日久皆化为熟户,而风俗与居民无异矣。”①
在作者看来,带有“畲”字的地名与“猺獠”存在着某种关系,只不过这些非汉民族变为“熟户”后,不再称为“畲”,但地名仍存于今。
再如著名学者徐松石先生也提出:“畲瑶即古代所谓山越。在广东东部散布甚广。平远、蕉岭、梅县、河源、惠来、丰顺、新安等地,现在还有许多畲字或輋字的地名。”②陈龙、吴炳奎、刘大可等学者也对闽粤赣一些地区内带有“畲”字的地名进行考证,以证明历史上畲瑶等族群在该地存在的可能性。③因此,有学者将这些带“畲”字的地名视为闽粤边地区畲族活动史的活“化石”。④
需要指出的是,带有“畲(輋)”地名的出现时间与“猺獠”族群在该地的居住时间,孰先孰后,目前仍无法考证。我们或许可以推论:古代汉人常将“猺獠”生活的地方称为“畲”,正如将南方非汉族群聚居区称为“山洞”一样。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畲”地名的命名与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遗存有关系。司徒尚纪认为在广东等地区,“没有水利工程灌溉的丘陵、山地,其被开发利用土地通名为畬地或畬田,实为梯田,过去实行刀耕火种,至今在海南、粤北黎、瑶地区仍有残存,故以畬为首尾地名在内陆山区较普遍。”广东客家人聚居平远县就有许多以畲命名的地名,反映的是“山区梯田文化景观”。⑤
因此,我们认为“畲”的地名未必一定和非汉族群聚落有关,即:“畲”作为一种地名的命名方式在闽粤赣地区已经形成一种传统,人们用其称呼一些“山脊”或山地地名,而这并不一定和“猺獠”族群有必然的联系。
三、“畲”“峒”生态文化语境下的一种族群分类
在古代中国,由于受到大一统观念的影响,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民族史的撰述,都体现出了诸如“夷夏同祖认同、华夷一家认同、共属中国认同、华夏文化认同”的大一统意识。①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华夏文化在几千年的民族史撰述中一直处于被表述的中心,四方“夷狄”则处于从属地位。而在具体实践中,华夏民族自春秋战国以后,在与周边非华夏民族的互动过程中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表现出华夏族及其文化不断向边陲扩张,最终使得各非华夏民族淹没在华夏族的“海洋”中或成为“华夏海洋”中的“非华夏孤岛”。
因此,在重新审视我国古代民族史时,我们必须将历代有关于“非华夏”族群的文字记载置于当时的社会情境来分析,具体来说:一是在汉文化语境下,这种记载多大程度反映了文字记载者的立场、态度及情感,而作为文本的历史记忆又反映了当时什么样的历史心性?二是这种记载中的文化特征,是否能够反映“异族”的实际情况,即这种客观的文化特征描述能否与“异族”的实际认同情况相一致?或者说,对“他者”只是文字记载者单方面的认同?
“畲”作为一种族群的出现,需要在生态语境和文化语境下考察。首先,自然生态无疑是任何一种族群和文化产生的最基础因素。正如我国历史上形成的游牧与农耕文明的生态界线,自然生态上差异导致了文化的差异,从而形成了文化特色截然不同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畲”作为原始的、粗放的耕作方式,与精耕细作的汉族农业也存在一条若隐若现的生态边界,这种自然生态的差异在族群文化特征上打上鲜明的烙印,这种迥异于“他者”的文化特征,成为“他者”族群观察另一个族群的切入点。根据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给文化所作的定义,文化应该包含了人类经历的各个方面②。按照这种定义,一个族群的文化特征应该包罗万象,而作为文字记载的族群,其呈现给后人的文化特征,充其量不过是一些静态的、被认为的诸多特征中较为典型的、有异于他者的特征。
笔者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农业的变迁认为,“畬(畲)田”的耕作方式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历史上从事“畬田”农业的族群,除了被称为“畬田”民族外,实际上,在某一历史阶段,汉族也从事“畬(烧)田”农业。③主要区别在于:随着汉族农业技术的发展,在汉族社会中,“畬田”的耕作方式逐渐被精耕细作农业所取代;而在一些非汉族群中,“畬田”农业作为一种技术要求不高、较易实施的粗放农业,仍一直被沿用。
随着代表农业文明的汉族文化不断扩张,“畬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遭遇,并产生了生态冲突。这种冲突首先发生在两种生态文化的锋线,也就是在两种生态文化的边界地区是生态矛盾最集中的地方。正如在古代中国,长城沿线被视为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冲突最集中的地方,长城的分布与走向基本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生态系统的分界线。生态文化的冲突带来族群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唐宋时期特别明显。“畬(畲)”之所以在唐宋时期的诗文中大量出现,与唐宋时期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时期,随着帝国华夏化进程加快,中国南方各个地区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北方汉人带来的先进农业与被认为是原始农业残余的“畬田”农业遭遇时,这种文化冲击(cultureshock)使得“畬(畲)”作为一种猎奇、述异、诗化见诸汉人知识分子的笔端。
尽管也有大量诗人对“畬(畲)”不吝溢美之词,但无法改变整个主流文化对“畲”的看法,特别是当“畲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在资源上冲突加剧时,“畲”一种文化标签常贴在非汉族群身上,目的就是将其边缘化。
第三节 小结
本章从生态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唐宋以来与畲族及其先民相关的自然生态和聚落人文情况。本章的主要论点有:
(1)“畲”作为一种古老的耕作方式,不仅在时间维度上,并且在空间广度上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中。要探讨“畲”如何成为一个族群的称谓,必须将其放置于特定的生态语境和文化语境中考察。
(2)在历史上中国中部、南方地区,曾存在畬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的生态冲突。畬田农业是一种较为古老的耕作方式,其在文化特征与日本学者提出的“照叶树林文化”特征相似。唐宋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中心南移,以精耕细作为代表的汉人农业在中国南方地区迅速发展,畬田农业呈现出明显的退缩趋势,宋代以后南方地区梯田的增多,说明了这个现象。随着对生态资源的需求,代表汉人农业的精耕细作与代表古代农耕方式的残存形态的畬田农业开始发生冲突,其生态边界恰好为汉族与非汉族群的边界大部分吻合。
(3)“畲”不仅仅是一种耕作方式,还具有带有聚落的含义。“畲”之所以从一种经济形式或聚落形态的称谓演变为一类族群的称谓.这与汉文化语境有着
密切的关系。“畲(輋)”或“山洞”,起先是作为人类居址称谓而存在的,这种特定的自然生态造就了特殊的聚落文化,从而成为生活在该地区人群的一种人文特征。
(4)在以华夏为中心的民族观指导下,汉人以从事特殊耕作方式(畲、輋),或居住在特殊聚落形态(洞、峒)作为文化特征,将南方非汉族群标签化。本章通过考察闽西象洞和海南黎峒两个个案,总结出作为聚落形态的“畲”“峒”的村落形态特征、族群构成、地方组织方式以及政治人文特征等。以此证明:“畲”或“峒”作为非汉人群的聚落、组织或族群称谓,均是在汉文化语境中产生的。在这种文化语境中,畲(輋)、峒(洞)除了具有区分种族的意义外,还具有政治和文化的意义。
附注
①傅衣凌:《福建畲姓考》,原载《福建文化》,第2卷第1期,1944年,收入《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77页。关于畲之得名还有“入番”说“蛇”音说等,以上观点流行并不普遍,不是主流观点,兹不赘述详见[德]史图博,李化民:《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武汉: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84年,第2-6页。
②[美]J.唐纳德·休斯(J.Donald Hughes)著,梅雪芹译:《什么是环境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译者序》第3页。
①陈元煦:《浅谈“畲”字含义与畲族名称》,《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第118-120页。
②李根蟠把中国古代农业史分为五个阶段:原始农业时期(原始社会,实行抛荒耕作制),沟恤农业时期(虞—春秋,实行休闲耕作制),精耕细作农业成型时期(战国—魏晋南北朝,连种制),精耕细作农业扩展时期(隋—元,轮作倒茬),精耕细作农业持续发展时期(明、清,复种制)。参见李根蟠:《中国古代耕作制度的若干问题》,《古今农业》,1989年第2期,第1页。
③[日]大泽正昭著,亿里译:《论唐宋时代的烧田(畬田)农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期,第226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五六,列传第四四《崔辩列传附模弟楷传》,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55页。
⑤[唐]刘禹锡:《畲田行》,载《刘梦得文集》,卷九《乐府》,四部丛刊初编118集部,据上海涵芬楼景印董氏景宋本影印,商务印书馆1926年重印影印,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
⑥温庭筠《烧歌》记载:“起来望南山,山火烧山田。微红夕如灭,短焰复相连。差差向岩石,冉冉凌青壁。低随回风尽,远照檐茅赤。邻翁能楚言,倚锸欲潸然。自言楚越俗,烧畬为早田。豆苗虫促促,篱上花当屋。废栈豕归栏,广场鸡啄粟。新年春雨晴,处处赛神声。持钱就人卜,敲瓦隔林鸣。卜得山上卦,归来桑枣下。吹火向白茅,腰镰映赪蔗。风驱槲叶烟,槲树连平山。迸星拂霞外,飞烬落阶前。仰面呻复嚏,鸦娘咒丰岁。谁知苍翠容,尽作官家税。”参见温庭筠:《温飞卿集笺注》四部备要卷三,《烧歌》。
①[唐]韩鄂撰,缪愉样释:《四时纂要校释》,《秋令》卷之四,北京:农业出版社,1979年,第173页。
②[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七,列传第一四七.《南蛮西南蛮传·东谢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74页。
③[宋]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列传第一四七下,《南蛮传下·两爨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317页。
④[宋]王禹偁:《王黄州小畜集》,卷八《畲田词并序》,四部丛刊初编集部133,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576页。
①《畬田词》分别从田歌、待客、斫山、协作、收获等高度赞扬了畬田的行为,五首词其一:“大家齐力劚孱颜,耳听田歌手莫闲。各愿种成千百索,(自注:山田不知畎亩,但以百尺绳量之,曰某家今年种得若干索,以为田数。)豆萁禾穗满青山。”其二:“杀尽鸡豚唤劚畲,由来递互作生涯。莫言火种无多利,林树明年似乱麻。(自注:种谷之明年,自然生木,山民获济。)”其三:“谷声猎猎酒醺醺,斫上高山入乱云自种自收还自足,不知尧舜是吾君。”其四:“北山种了种南山,相助力耕岂有偏。愿得人间皆似我,也应四海少荒田。”其五:“畬田鼓笛乐熙熙,空有歌声未有词。从此商于为故事,满山皆唱舍人诗。”[宋]王禹偁:《王黄州小畜集》,卷八《畲田词并序》,四部丛刊初编集部133,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576-577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五,列传第二五四,《蛮夷传三·抚水州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205页。
③[宋]张淏:《云谷杂记》,补编卷二“刀耕火种”条,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04页。
④[宋]朱胜非:《绀珠集》,卷十一,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子部178杂家类,第872册,第501-502页。
⑤[唐]贯休撰,[明]毛晋编:《禅月集》卷八《怀武夷红石子》,据明虞山毛氏汲古阁刊本影印,台湾明文书局,1981年,第60页。
⑥[清]董浩辑:《全唐文》,卷一六四,陈元光《请建州县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74-1675页。
①谢重光:《〈全唐文〉所收陈元光表文两篇系伪作考》,载《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第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85-307页。
②[宋]杨杰,曹小雲校笺:《无为集校笺》卷一四,《故温州录事参军陈君墓志铭》,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
③[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十三《谷之二·稷粟类》,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79医家类,第773册,第459页。
④[明]谢肇淛:《太姆山志》,卷中《游太姆山记》,福州慕园书屋,嘉庆五年(1800年)重刊本。
⑤[清]杨澜:《临汀汇考》,卷四,《物产考》,光绪四年(1878年)刊本,福建师大古籍室藏,第15a页。
⑥[清]曾曰瑛等修,李绂等纂:《汀州府志》,乾隆十七年(1752年)修,卷四十一《艺文三》,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527-528页
⑦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七,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第309-311页。
⑧[清]吴震方:《岭南杂记》卷五,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复印本),第28页。
①李剑农列举了唐代有关火耕畲田的诗文共30例,这些诗文大都出现在唐后期。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19-23页。
②有关畲田技术详见[日]大泽正昭著,亿里译:《论唐宋时代的烧田(畬田)农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期,第223-249页;周尚兵:《唐代南方畲田耕作技术的再考察》,《农业考古》,2006年第1期,第145-149页。
③所谓的照叶树林,指的是在东亚温暖带中,其森林以柞、柯、楠、山茶等树种为主,由于树叶的表面反射阳光,因此称之为“照叶树林”。[日]佐佐木高明著,刘愚山译:《照叶树林文化之路—从布丹、云南到日本》,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④有关照叶树林文化论参见[日]中尾佐助著,赵玉蕙译:《照叶树林的农业文明之光》,《农业考古》,2009年第4期;[日]佐佐木高明著,刘愚山译:《照叶树林文化之路——从布丹,云南到日本》,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⑤在西南地区照叶树林地带的民族有苗瑶语族、藏缅语族、孟高棉语族、壮侗语族等语族,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云南地区的一些民族仍存在刀耕火种,总体呈现出消退的趋向。参见金少萍:《云南少数民族与照叶树林——地域、民族、文化》,《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80页,第82页。
⑥陈有贝:《照叶树林文化理论——史前两岸文化传播研究的另一个线索》,《田野考古》,2000年第7卷第1、2期合刊。
⑦大泽正昭统计了唐宋30余篇与地域有关的诗文史料并制成地图,认为唐代畬田应该包括有山南、江南两道的大部分以及剑南道的东部,以上地区畬田实施区域仅是这些州县周边的山间地,并没有包括山地的全部范围。[日]大泽正昭著,亿里译:《论唐宋时代的烧田(畬田)农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期,第233页。
①参见曾雄生:《唐宋时期的畬田与畬田民族的历史走向》,《古今农业》,2005年第4期,第30页。
②李剑农先生在《宋元明经济史稿》中,将唐代“畬田”作为唐宋时代江南开发进展的例证,笔者同意大泽正昭的观点。[日]大泽正昭著,亿里译:《论唐宋时代的烧田(畬田)农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期,第237页。
①[日]竹村卓二著,金少萍,朱桂昌译:《瑶族的历史和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①[清]曾曰瑛等修,李绂等纂:《汀州府志》,卷之四十四《艺文六·丛谈》,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修,同治六年(1867年)刊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七十五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650-651页。
②[明]良弼修,杨宗甫纂:《惠州府志》,卷十四《外志·猺疍》,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影印本,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第14b页。
③[清]卞宝第:《闽峤輶轩录》,卷一,清刻本,厦门大学古籍室藏,第10b页。
④华夏化指的是华夏民族为代表的中原势力向帝国边陲不断扩展的过程,其中不仅仅包括华夏民族实质性的人口迁移和华夏文化的传播,还包括非汉民族华夏文化认同的转变。关于“华夏化”的有关内容,笔者在后文将做详细论述。
⑤[唐]房玄龄:《晋书》,卷二六《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88页。
⑥春秋战国时期,汉族地区铁器和牛耕开始广泛使用,开始连作复种制;秦汉时期,进入精耕细作农业时期;唐宋以后,南方农业进步,水田不再“火耕而水耨”,开始使用水稻移栽法等参见曾雄生:《唐宋时期的畬田与畬田民族的历史走向》,《古今农业》,2005年第4期,第31页。
①[宋]普济:《五灯会元》,卷六《青原下五世·南岳玄泰禅师》,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14页
②[宋]释赞宁:《宋高僧传》,卷十七《唐南岳七宝台寺玄泰传》,中国佛教典籍选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③笔者认为“畬山儿”中的“儿”应属蔑称。用作“他称”的“某某儿”或“某某仔”经常是蔑称,民国黄仲琴先生考察华安仙字潭古迹时曾有此论:“蓝雷钟系,或瑶、或苗,溯源不异,名称则淆,按闽南人对于蓝雷人,名之曰:‘蓝雷仔’。‘仔’者轻之之辞,盖弱小民族之称谓也。”黄仲琴:《汰溪古文》,《岭南大学学报》四卷二期,1935年,载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编:《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16页。
④[唐]魏征:《隋书》,卷三一《地理下》,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87页。
⑤[元]王祯撰,缪启愉译注:《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99页。
①杨抑先生就曾指出:“只有当北民南徙,农业生产重心转移到江南,尤其唐代中叶以后,平地人口多,田地不敷耕种,或者是战乱人们在平原地区不得安生才会逃赴山区、半山区垦复种植换而言之,梯田的建造,必定是在人口的增长与耕地资源不足这一矛盾中才有可能产生。”杨抑:《中国南方丘陵山区水土保持史考略》,《农业考古》,1995年第1期,第112页。
②[宋]范成大:《骖鸾录》(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2页。
③[民国]谢祖安修,苏玉贤纂:《宜春县志》,卷二十《艺文》,民国二十九年石印本。
④[宋]普济:《五灯会元》,卷九《南岳下四世·仰山慧寂禅师》,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26-530页。
①[明]语风圆信,郭凝之编:《袁州仰山慧寂禅师语录》,载《六重新修大藏经》No.1990,卷四十七,第582页。
②[宋]方勺:《泊宅编》,卷三(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5页。
③[明]谢肇涮:《五杂俎》,卷四《地部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78页。
④[清]周亮工:《闽小记》,卷一《磳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8-39页。
⑤[清]方履篯修,巫宜福纂:《永定县志》,卷一六《风俗》,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刻本。
①[元]脱脱:《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162页。
②[明]王守仁:《桶冈和邢太守韵二首》,载《王文成公全书》,卷之二十《外集二》,四部丛刊初编259集部,据上海涵芬楼景印明隆庆刊本,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重印形印,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
①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82页。
②李荣村指出:“唐宋时凡近山的蛮夷住地、聚落或羁縻州洞等都可称作峒,又称溪峒,也就是蛮洞的意思,但绝不当作狭义的洞穴解释。”参见李荣村:《溪峒溯源》,《“国立编译馆”馆刊》第1卷,1971年第1期,第20-23页。
③佟珊:《华南“洞蛮”聚落人文的民族考古考察》,《南方文物》,2010年第2期,第81页。
④李荣村:《溪峒溯源》,《“国立编译馆”馆刊》,1981年第1卷第1期,第20-23页。
⑤裴文中:《洞穴的知识》,《文物春秋》,2004年第3期,第1页。
⑥同⑤,第1-4页。
⑦为了在核心洞穴周围更大半径中获取食物,用旷野居址来控制资源是人类探索出的一种策略,如王社江、沈辰借鉴考古学家艾萨克(Isaac),甘博(Gamlbe)的理论,对洛南盆地旧石器早期遗址聚落形态进行研究,印证了“核心洞穴与旷野居址”模式的存在。参见王社江,沈辰:《洛南盆地旧石器早期遗址聚落形态解析》,《考古》,2006年第4期,第54-57页。
⑧中石器时代(Mesolitnic),该概念最早由法国学者韦斯托普(H.Westropp)在1866年提出,主要指处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的一个时期,学术界关于中国的中石器时代仍有争议。参见赵朝洪:《试论中石器时代》,《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第73-83页。
⑨樊志民:《试论中国中石器时代的原始农业萌芽》,《中国农史》,1993年第2期,第1页。
①彭适凡:《试论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兼论有关的几个问题》,《文物》,1976年12期,第15-16页。
②郑韬凯:《从洞穴到聚落——中国石器时代先民的居住模式和居住观念研究》,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4页。
③[唐]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卷三《唐故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赠左散骑常侍薛公神道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下·峒獠》,续修四库全书597史部地理类,据上海图书馆清抄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59页。
①[宋]胡太初修,赵与沐纂:《临汀志·山川》,宋开庆元年(1259年)修,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2页
②唐宋以前,南方一些生态比较原始的地区,常有象群出没,如北宋彭乘《墨客挥犀》载:“漳州漳浦县,地连潮阳,素多象,往往十数为群,然不为害,惟独象遇之,逐人蹂践,至骨肉糜碎乃止。盖独象乃众象中之最犷悍者,不为群象所容,故遇之则蹂而害人。”再如漳州平和有象湖山,传闻是大象出没的地方参见[宋]彭乘:《墨客挥犀》卷三,“潮阳象”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06页:[清]黄许桂修,曾泮水纂:《山川志》卷一,道光十三年(1833年)修,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0页。
①[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外国门上》,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第62-64页。
②一般来讲,见诸古代汉文史籍的“生黎”“熟黎”词汇,反映的是古代文人士大夫对当时黎族内部族群的划分与认识。参见王献军:《黎族历史上的“生黎”和“熟黎”》,载陆勤毅,吴春明主编:《百越研究》(第二辑),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7页。
③[宋]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19-220页。
④[清]徐家干,吴一文校注:《苗疆闻见录》,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2页。
①[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6页。
①[元]脱脱:《宋史》,卷四百一十九,列传第一百七十八《许应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54页。
②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第十七册《广东上》引《博罗县志》,第359页。
③[清]赵希璜:《横輋》,载《峰草堂诗钞》,卷二《古今体诗五十八首》,续修四库全书1471集部·别集类,据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年安阳县署刻增修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90页。
④[清]陈铭珪:《浮山志》,卷四《诗上》,清光绪七年(1881年)荔庄刻本,厦门大学古籍室藏,第29b页。
⑤[民国]招念慈,邬庆时纂修:《龙门县志》,卷四《县地志四·山川》,民国二十五(1936年)年广州南关增沙街汉元楼铅印本,厦门大学古籍室藏,第42b页。
①[宋]刘克庄:《漳州谕畲》,载《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三《记》,四部丛刊初编213集部,据上二海涵芬楼景印旧抄本,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重印影印,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
②[元]刘埙:《隐居通议》,卷九《诗歌四·云舍赵公诗》,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172杂家类,第866册,第97页。
①[元]苏天爵:《元文类》,卷四十一《杂著·招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367-537页。
②[明]宋濂:《元史》,卷十一《本纪第十一·世祖八》,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28页。
③陈荫祖修,吴名世纂:《诏安县志》,上编卷五《大事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31,据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诏安青年印务公司铅印本影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678页。
④[清]张廷玉等著:《明史》,卷四五《地理》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⑤[明]黄仲昭:弘治《八闽通志》,卷八《地理·山川》“漳平县”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0页。
⑥参见[清]彭衍堂修,陈文衡纂:《龙岩州志》,卷一《封域志·山川》,据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修,光绪十六年(1890)重刊本影印,中国方志丛书,第85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26页;[清]蔡世钹等撰:[道光]《漳平县志》,卷一《舆地·山川》,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专辑34,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54-355页。
①[清]蔡世钹等撰:道光《漳平县志》,卷一《舆地·山川》,第354-355页
②[清]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七,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第309-311页。
③据陈龙统计,福建全省有231处带“畲”字的地名,另外广东有带“畲”字的地名有793处。参见陈龙:《福建“畲”字地名考略》,福建省地名委员会、福建省地名学研究会编:《地名》,1981年第2期。
④如连城曲溪的岭背畲、胡畲,姑田的大畲、尧家畲、河畲,赖源的杨公畲,朋口的余家畲、官畲、赖家畲、下畲峡,宣和的傅家畲,江公畲,新泉的李家畲、儒畲、畲部,庙前的江畲、西江畲,园畲村;武平的黄畲塘、落畲、黄心畲、黎畲、袁畲,上畲、苏畲、蓝畲、中畲、黄畲、大畲、雷公畲、饶畲、坪畲、乐畲、洋畲、畲窝里等。参见陈百流:《连城县乡村的演变略考》,《连城文史资料》第13辑,第130页;福建省武平县地名办公室编:《武平县地名录》(内部资料),1983年,第224-240页。
①[清]吴宗焯等修,温仲和纂:《嘉应州志》,卷三十二《丛谈》,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刻本。
②徐松石:《民族学术研究著作五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4-145页。
③陈龙:《福建“畲”字地名考略》,福建省地名委员会、福建省地名学研究会编:《地名》1981年第2期;吴炳奎:《畲字地名考》,《梅县文史资料》第13辑;刘大可:《客家与畲族关系再认识——闽西武平县村落的田野调查研究》,《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12期,第56页。
④周雪香:《明清闽粤边客家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1页。
⑤司徒尚纪:《广东地名的历史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期,第50-51页。
①马卫东:《大一统与民族史撰述》,《史学集刊》,2011年第6期,第53页。
②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定义,他说:“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和习惯。”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9-20页。
③李积庆:《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变迁的历史考察》,《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5-16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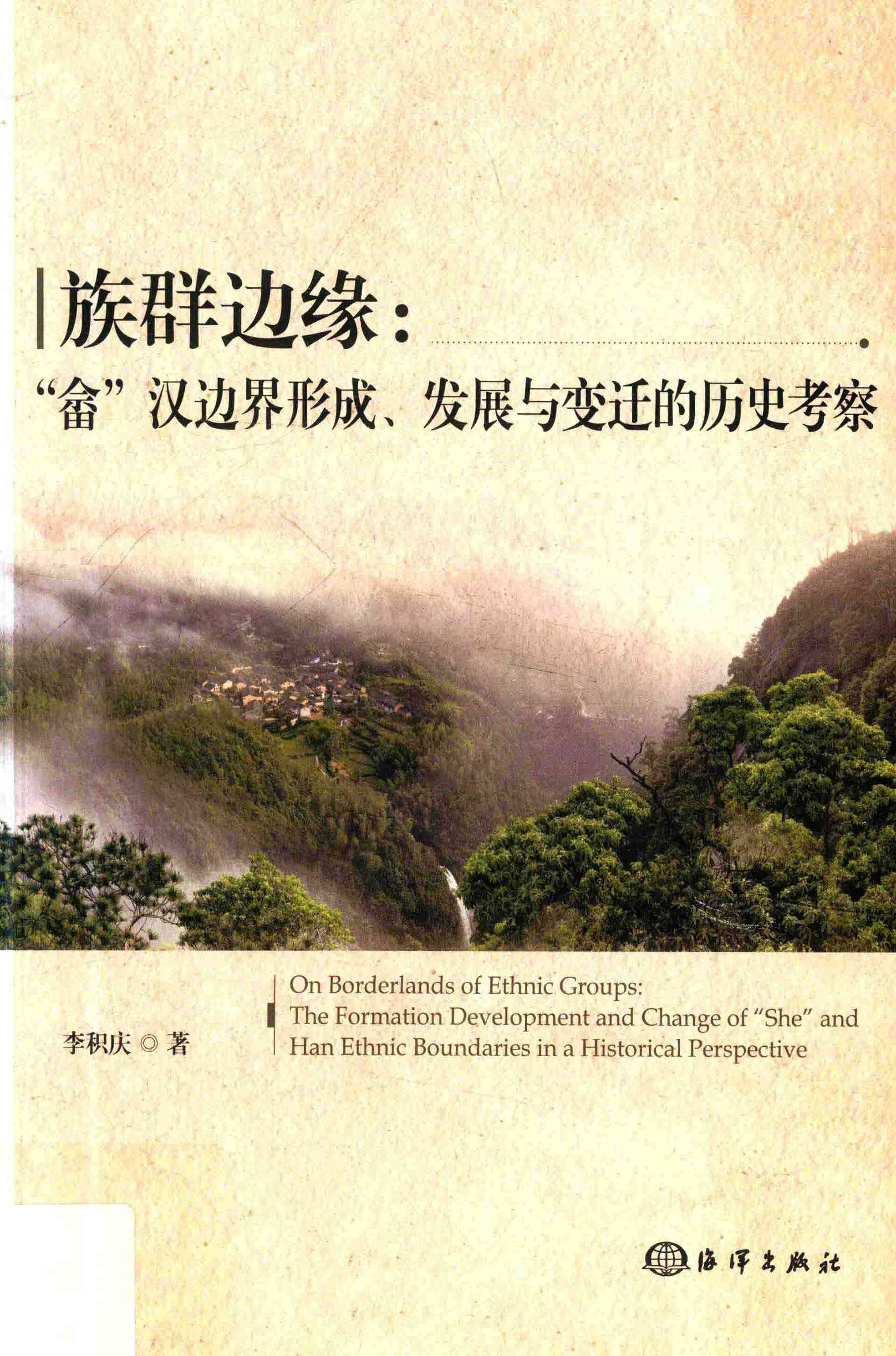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出版者:海洋出版社
本书从族群边界的理论角度,重新审视畲族形成、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在承认族群客观历史文化的同时,重点研究历史上“他者”(主要是汉族)对“畲”的社会定义以及“自者”(主要为南方非汉族群)自我族群认同的过程,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现实意义。
阅读
相关地名
宁德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