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 内容出处: |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图书 |
| 唯一号: | 130920020230003758 |
| 颗粒名称: | 绪论 |
| 分类号: | K288.3 |
| 页数: | 23 |
| 页码: | 1-23 |
| 摘要: | 本文主要探讨了美、族群等哲学命题,以及不同学科对族群的不同认识。 |
| 关键词: | 宁德市 畲族 哲学 |
内容
美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感受?其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成为千百年来人们争论不休的对象。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认为:美既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同时也人们对客观事物做了一番主观的选择。关于“族群”(ethnic group)的定义,至今仍有很多争议,其中也涉及类似上述的争辩:族群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主观认同的结果?
由于学科不同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学者对族群的认识也是不同的:一般来讲,考古学、历史学以及传统民族学研究更倾向于将族群视为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不同族群具有不同的客观文化特征,其表现为体质、语言、习俗等文化的不同;而人类学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研究开始更多转向族群主观认同的研究。
事实上,关于族群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认同的结果,二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有学者把族群定义为:“族群是人们在交往互动和参照对比过程中自认为和被认为具有共同的起源或世系,从而具有某些共同文化特征的人群范畴。”①这种观点既承认族群事实存在的共同文化特征,同时也不否认主观认同在族群存在中扮演的角色,该观点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
“畲”②民作为中国东南地区族群特征比较明显的族群,常见诸历代文献中,作为一种族群称谓,“畲”最早出现于南宋末期③。学者一般认定该时期的“畲”就是当代畲族的前身,而在南宋之前及之后,“畲”不会凭空出现,也不会突然消失,作为一个与周围民族有着清晰界线的民族,畲族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脉络。
自20世纪初起,学者开始对畲族进行研究,在畲族源流、族群迁徙、畲族客观文化、畲汉族群互动、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等领域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并在百年的探索中,形成了畲族研究比较固定的范式。以畲族源流研究为例,在2004年出版的《福州畲族志》一书中写道:
早在公元7世纪初,对居住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包括畲族先民在内)的少数民族泛称“蛮”“蛮獠”“峒蛮”或“峒獠”。直至公元13世纪中叶的南宋末年,汉文史书上出现“畲民”和“輋民”两词并用的族称。前者指的闽西南汀漳地区的畲族,后者指的是广东潮州地区的畲族,二者字异音同,指的都是同一个民族……宋末元初,畲族人民纷纷加入抗元武装……当时对畲族人民所组织的抗元武装队伍,史书都称“畲军”……到了元代,“畲”字被普遍使用。明代,对“畲民”“輋民”“輋瑶”等称呼都有使用。在清代的一些地方志中,往往把畲族称为“畲民”“苗瑶”,或合称为“畲瑶”“畲蛮”。不过,“畲民”一词比较多见。民国时期,有的把畲族统称为“苗夷”或“苗族”,直到50年代,一批南下干部仍把畲族称为“苗族”,甚至畲族干部和群众也自认为是“苗族”,至今福州郊区和城区约有1000人还自报“苗族”。①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学术思想的形成,既与我国古代民族史记载的传统有关,也与中国学术史思潮有关。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斯大林的民族学理论一度成为我国民族学的指导思想。根据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即所谓的“四个共同”的标准②,学者认定畲族及其先民共享有相同的、具有显著特征的族群文化。因此,学者更多地将畲族研究的重点放在畲族客观文化特征的发现与对比研究上。通过分析畲族文化的构成要素,概括畲族的核心文化特征,继而按照文化特征的同异分辨各类族群。这使得历史上或现实中的有共同文化特征的族群产生联系,以此建立起畲族历史的系谱。唐代的“蛮”“獠”—宋代的“畲”“輋”—明清以后的“畲瑶”“畲蛮”—当代的畲族就是传统民族史研究中畲族系谱的主要脉络。
传统民族学研究对于厘清历史上纷繁复杂的族群以及界定当代民族成分,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正是由于传统民族学研究提供了的理论基础,使得畲族的认定工作得以顺利推进。及至当代,是否具有显著的民族特征甚至成为某一人群能否被识别①或被恢复为畲族的主要依据之一。
尽管“客观特征论”在族群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学术界也发现:“客观特征论”具有理论局限性,仅仅以此理论是无法解释复杂多变的族群现象。如,在20世纪80年代民族识别恢复阶段,福建省云霄县下河乡坡兜、圳头、安后、安前村钟姓,永春县下洋镇长溪村雷姓,永春县逢壶乡西昌村、八乡村等章姓,在申请恢复(畲族)民族身份时,尽管他们努力证明本族与已经被认定为畲族民族身份的同族姓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政府仍以其“民族的明显特点消失”等原因,不予变更民族身份。②与其相反的一个的例子是,贵州省麻江县东家人被认定为畲族,而这些畲族在族群文化特征上,显然与东南一带传统意义上的畲族大异其趣。③随着交叉学科的发展以及新理论、新方法的引入,学界也开始对“客观文化特征论”的研究范式进行反思,并指出其理论局限性的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客观特征论”的理论前提是先验地假定“文化变异是不连续的”。也就是说,我们将一个社会中人群分为“分享着共同文化”和“具有独立文化”两类集合体。之所以说是“先验地假定”,是因为任何一种族群和文化都不是静态的,而是变迁的。正如有学者将族群的发展比作“组织化的动脉”,就像血液流经人体动脉的各个位置,族群在不同社会文化体系中,被赋予内涵的数量和形式也均有不同。④清人吴震方在《岭南杂记》对南方非汉族群称呼变化不定曾做过一番论述,他说:
獠即蛮之种,出自梁益之间,其在岭南,则隋唐时为患,然是时不言有猺,宋以后又不言獠,意其类合分无定,故随代异名。明通志凡山
寇皆谓之獠,盖山寇亡命乌合,未必种传,无从究考。①
按照吴震方对“獠”的源流考证,各个时代分合不定的族称,不仅形式(称呼)不同,而且内涵(族群成分)也变化很大:如明代文献直接将族群成分来源不一的“山寇”统统都称为“獠”。因此,若以某一些静态的文化特征作为区分或追溯某一族群的标准,常常会出现“以今溯古”“刻舟求剑”的民族学研究困境,从而陷入“表述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②。
另一方面,“客观特征论”以文化之间的同异来区分不同的族群,注重族群“本质的”“核心的”“典型的”文化特征。但是,在历史上或现实中常常出现一些不同族群享有相同的文化特征,而所谓的相同的“族群”“民族”在许多文化特征中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正如学者指出:“在以文化作为族群区分标志时,人们只是挑选那些能够反映其世系或族源的文化特征来作为族群区分标志,对于那些不能反映其族源共同文化的特征往往视而不见。而且,为了标明族界,人们常常是在复活或发明据信是自己祖先曾有的传统文化。”③也就是说,为了证明某族群是同一族群时,人们强调族群整体的同一性、延续性,不能看到或有意忽略了族群内部的差异性与复杂性;而当想证明某两族群为不同族群时,人们又往往忽略族群间共有的文化,转而强调不同族群间的文化差异,在此过程中,可能有一些文化还存在刻意被“制造”(被建构)的情况。
自挪威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克·巴斯在《族群与边界》一书中提出族群边界理论④后,一些学者就将这个理论运用到中国族群的研究中,其中以台湾学者王明珂的华夏边缘研究为代表⑤。这些持族群边界理论的学者对传统民族研究进行反思,他们不认同“族群是一个有共同的客观体质、文化特征的人群”的观点,①族群边界地区的主观异己感之所以比族群核心地区更为强烈,按王明珂的解释是:“在族群关系中,一旦以某种主观范准界定了族群边缘,族群内部的人不用经常强调自己的文化内涵,反而是在族群边缘,族群特征被强调出来”,而“需要强调族群文化特征的人,常是有族群认同危机的人”。王明珂因此认为:“族群边缘是观察、理解族群现象的最佳位置。”②这也解释了历史和现实中时常出现的族群现象:族群认同越强烈、族群文化特征越是被强调的地区有可能不是族群的核心地区,反而是在族群的边界地区。
关于这种认识,我们还可以从日本学者濑川昌久的研究得到启示。濑川先生在研究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族谱时,发现宁化石壁传说③和南雄珠矶巷传说具有大量的相似性,他将二者比较分析后推测:“不管哪一个传说之所以都选择这类场所作为故事发生的舞台,也许是因为曾经有过一个时期,那里是从江西一侧的汉族‘华’界,进入福建、广东一侧‘夷’界的最前线,因此,这类场所就以明确的形式体现出了汉族与原住民之间的族群分界。”④
学界一般认为,“石壁”作为祖先移居传说的移居地,更多的应该被视为一个建构的文化符号。⑤华南的各个族群通过“石壁”传说等历史记忆的建构来强调文化认同,从而达到维持族群边界的目的。就此而言,与其将“石壁”看成某一历史时期某个族群祖先移居地(或集居地)中心,不如将其视作该历史时期的族群边界(或文化边界)的象征符号。也就是说,原来认为所谓的祖源地或族群的中心地带.有可能只是族群边缘地带。如果这种推论成立的话,那么有关畲族历史记忆中的移居地传说,如“凤凰山传说”“河南传说”“南京传说”①等,可能可以对其进行重新解读,这对畲族的族群形成发展史研究显然具有重大意义。
基于对传统民族学研究范式的反思,本书拟从族群边界的角度,重新审视畲族族群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希望在新理论、新方法的观照下,对畲族史研究作一番有益的探索。
一
本书从族群边界的理论角度,重新审视畲族形成、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在承认族群客观历史文化的同时,重点研究历史上“他者”(主要是汉族)对“畲”的社会定义以及“自者”(主要为南方非汉族群)自我族群认同的过程。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现实意义。
第一,本研究在研究视角上与传统民族史具有一定的区别。传统民族史研究认为历史上的畲族具有“一以贯之”的文化与传统,尽管在不同时代,畲族及其先民的族群称呼有所不同,但在客观特征上是“一脉相承”的。传统的畲族研究侧重对畲族的族源、客观文化进行研究,本书从族群边界的角度,重新审视畲族发展中的生态、文化语境,特别是重视作为“他者”存在的“畲”族群如何被建构,以及畲民族群如何对本族群的历史进行建构,以此探讨畲族文化认同转变的情况。本书除了承认族群客观文化存在的同时,同时也指出:历史上的“畲”,其文化具有不连续性,这种不连续性体现在客观文化特征的差异。比如唐宋的“蛮”“獠”、宋元的“畲军”与明清的畲民,乃至当代的畲族在文化内涵上有着较大的差异。之所以能将这些族群联系起来,在于“畲”、汉族群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进行了族群历史的建构,并形成了一定的族群的文化认同。本书在叙述与畲族有关的历史事件时,不仅关注历史事件本身,更注重历史事件背后的语境的分析,特别是一定区域内生态语境、文化语境对族群塑造的影响。历史上的“畲”族群,其自身存在一个自我发展、演变的过程,同时也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在汉文化语境中,“畲”族群存在被建构
①“河南传说”“凤凰山传说”“南京传说”为畲族的祖源或迁居地的传说,具体内容详见蓝炯熹:《畲民家族文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55页。
和自我文化建构的过程。从外因角度分析,在帝国的“华夏化”进程中,作为中国的非汉民族,“畲”不断被标签化,而成为众多非汉族群名称中的一种;从内因角度分析,一些族群通过祖源传说等历史记忆将本族与历史上的相关族群联系起来,形成特定的族群认同,建构起族群发展的历史脉络。
第二,本研究借鉴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将族群历史与地域社会发展结合研究。本文将畲族历史置于区域社会发展史特定的“语境”和历史脉络之中分析,这对于研究畲族的族群迁徙、族际交往以及自身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文化变迁更具说服力。一定的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都深刻影响着族群的发展。这种生态环境对“畲”的影响体现在多方面,如在自然生态方面,历史上曾发生畲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的生态冲突;在社会经济发面,唐宋政治经济中心南移,明代中期社会转型均带来区域族群格局的变迁;在政治文化方面,唐宋以后对南方地区的开发,越来越多的非汉民族卷入“王化”和“儒化”的社会进程中,特定时期政府的民族政策对族群的认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下的“畲”族群,其族群的文化内涵及特征可能因时因地产生变化,即各地的畲族既有历史文化的某种共性,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加入不同地域的文化因子,形成了各自地区的族群特征。可以说,各地的畲族文化的发展各有自身的特点区域畲族史研究的目的,一方面,将区域畲族的发展置于大的历史背景下,注重畲族形成的整体性与延续性;另一方面,兼顾不同地区畲族的共性与个性的比较。在特定生态社会背景下对该族群一些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从中找寻畲族发展的历史遗迹和其他信息,以此达到“一叶知秋”的效果。
通过整合畲族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学科的学术资源,就畲族族源、族际互动、文化习俗等若干专题进行专门讨论。在区域社会发展史的视野下,将不同省区,如将闽粤赣地区和闽浙赣地区的畲族进行比较研究,在梳理畲族社会发展脉络的同时,把握各个地区的畲族共性与个性。
借鉴人类学、知识考古学等方法,在理论上将畲族研究推进一步。首先,运用社会史研究方法,既重视畲族历史的宏大叙事,又重视个案的研究,特别对族群赖以生存的生态、社会、文化背景进行多方位的考察。其次,突破传统民族史框架,引入族群边界、族群认同理论,强调“畲、汉”在特殊语境下,具有流动性,在此理论下更强调历史的文化解释,强调历史的意义,强调记忆与认同在历史建构中的作用。再次,借鉴“知识考古学”等理论,对各种与畲民有关的文献或民间传说进行重新解读,更注重“文本”之后的社会情境与历史心性的研究。特别是对材料(包括文献材料与口述材料)的分析上,更注重文本所体
现出作者的立场、态度及情感。在历史上,不管是汉族或者非汉民族,其对“我群”或“他群”历史的表述,均带有一定的情感。一般而言,历史上留存的文献,多为汉族知识分子所撰写,学者通常根据其中有关非汉民族的记载来论述这些族群的历史。实际上,畲民族群中也流传着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口传材料,及至明清还有一些畲民知识分子对本族族谱进行修纂。这些有着丰富内容的文本背后,其作者的立场、写作的目的,乃至虚构族群历史的情感,均值得进一步考察。我们不仅要考察文本与历史事实的相符程度,即历史材料的真伪,还要进一步考察这些材料如何真伪、为何真伪。
第三,研究区域畲族史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华夷秩序”下和强势的汉文化中,历史上的畲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处于边缘化地位,表现为“经济的弱势、政治的异类、文化的边缘”。①新中国成立以后,畲族边缘地位得到较大改观,但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心理和文化习惯仍存留于当代,另外,相比较汉族聚集地区而言,畲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总体上比较落后。就此而言,研究区域畲族史,目的在于对畲族的生存与发展加入现实的关怀。在历史或现实中,常出现一些以划分族群边界而带来的族群冲突或族际纠纷。王明珂曾指出,之所以出现以上各种族际边界纷争,皆由所谓的“历史”造成,其背后的人类社会本性不外是资源竞争,“历史学者深入研究、争论一些表象化的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s as representation),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因各据其认同立场,选择性的取材、编织与诠释历史;如此之‘历史’经常鼓动民族情绪,导致更多的人群冲突。”②研究畲族历史,特别是对历史上的畲族与客家、福佬等民系关系进行研究,厘清族群之间融合、冲突与合作的情况,这在当下提倡和谐社会建设、消弭族群矛盾具有借鉴意义。
二
有关畲族及其先民的情况,唐宋以来的正史、方志、文人文集及笔记等文献多有记载,而近代学术意义上的畲族研究应是始于20世纪初。关于畲族研究综述,郭志超先生在其著作《闽台民族史辨》作了专题论述,他按新中国成立前
(一)新中国成立前畲族研究情况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传入中国,一些学者在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影响下,开始对中国的民族史进行研究。一般认为,刘师培在1903年完成的《中国民族志》是中国学者运用新的民族学对我国少数民族研究的开端②,而畲民和疍民③作为东南比较有特色的族群理所应当地进入学者的研究范围。1906年浙南云和县的学人魏兰(笔名浮云)发表的《畲客风俗》一书④,1911年日本学者山崎直方发表《畲族》一文⑤,成为中外学者研究畲族的开端。此后,沈作乾(1924年)⑥、董作宾(1926—1927年)⑦等也开始留意畲族的研究。如董作宾在《福建畬民考略》所说:“近著以国学门周刊所载沈作乾《括苍畬民调查记》为详……至云和某君《畬民风俗谈》,犹未见也。岁乙丑,余游学闽垣,颇留意于风俗习惯语言民族之考察。乃就披览所及,凡闽中地志笔记,有关畬民之记载,辄撮要录之,以供研究畬民者之参考焉。”⑧
此后史图博(H.Stubel)和李化民(1933年)①、何子星(1933年)②、何联奎(1936—1937年)③、凌纯声、芮逸夫、勇士衡(1947年)④、胡先骕、胡传楷、管长墉⑤、罗香林⑥、林惠祥、钟敬文、林耀华等在研究华南社会及族群文化时,也涉及畲族的研究。这些学者从畲族族源、族属、族称、族群迁徙、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广泛研究,为新中国成立后畲族的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
一些研究机构,如福建协和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前身),成立了闽学会(1926—1931年)、福建文化研究会(1931—1949年),据汪毅夫统计,福建协和大学的福建民族研究成果有20种⑦,其中与畲族有关系的有12篇,如董作宾的《畬语十八名》⑧《说畬》《福建畬民考略》;克立鹄的《福建省的“山达”》(The San Tak of Fukien Province)⑨;克立鹄、江鼎伊的《对福建土著的进一步研究》(Further Notes on Aborigines of Fukien)⑩等。除了刊在《福建文化》的研究成果外,其他作品还有:魏应麒的《畲民之起源与“畲”字之商订》、沈骥的《福建省几个特殊民族的研究》、翁绍耳的《福州北岭黄土岗特种部族人民生活》、管长墉的《福建之畲民》、陈锡襄的《畲民与客家》以及傅衣凌的《福建畲姓考》等。⑩
当时的畲族研究的状况与当时的学术关怀有着密切的关系。从19世纪中叶以后,维持了几千年的“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在西方坚船利炮和优势文化的冲击下,逐步动摇。在这种背景下,许多知识分子开始转而寻求“国族”建构,在“炎黄子孙”“黄帝世胄”“五族统一”“政更共和”①成为当时的流行话语。政府和一些学者主张“同化”(所谓的“五族统一”即是该思想的表现),认为“少数民族”的调查和研究不能刺“激作国族分化”,因此,当时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主要是以“安边”“治边”为要的“边政”研究。②在20世纪30—40年代,边疆学、边政学热潮兴起,大量中外民族学者纷纷赴边陲地区民族调查,其中又以西南地区为最多③。如1928—1949年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将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西南地区,参与这一阶段民族调查研究的学者,其研究主旨并非想刻意、任意创造一些民族范畴,而是希望通过在新学科理论和知识的指导下,结合传统华夏民族观(即以华夏为核心、四夷为边缘的“中国”观念),借着国家民族政策的施行,对民族分类、识别并且再造华夏边缘。④
相对西南地区而言,这一阶段的东南地区民族研究相对薄弱,因此,畲族研究的成果并不能算为丰富,且论著多属介绍性文章。1935年,岭南大学黄仲琴教授在《汰溪古文》一文中对福建华安仙字潭“古文”及其族属(畲民)进行研究,他在“引言”中称:“西南民族于我国古代文化有重要之关系,在今日学术界已成为一个研究之问题。学术机关以及学者个人,多往川滇各处为实地之考察;又如云南罗罗⑤及其他古族之文字,亦有为专门之研究者。川滇之外,如粤如湘如闽,尚有古代民族之遗留,若盘、蓝、雷之类是也。兹述往年在闽南所发现之古代遗文一种,以供学者参考。”⑥
该文结尾又写道:“若得译其(指汰溪古文)词意,且加以较长之时间应需之费用,尽拓其地所有刻石,且相择处所,为发掘之工作,当必续有发现,使沈埋史迹,复见光明,于研究我国西南民族文化者,有所裨益也。”①由此可见,当时西南民族研究成为中国民族学的研究中心,畲族的研究常作为西南民族研究的补充、参考或个案印证来研究。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畲族研究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国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民族识别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斯大林的五阶段论的指导下,有关单位对中国各民族的社会形态进行调查。畲族研究在此背景的推动下形成了热潮,也取得了较多的调查成果。在1953年和1955年,中央分别组织畲族调查小组进行实地调查,调查组获得许多畲族珍贵的文献、民俗、语言等资料②,并认定畲民既不是汉族,也不是瑶族的一支,而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在1956年12月,经国务院正式公布,畲族作为单一民族最终被确认。自1958年起,国家又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形成29篇、共40万字的调查报告,并编成《畲族简史简志合编》。
这一阶段的畲族社会历史调查,调查组深入畲民住区,通过挖掘历史文献材料以及民间传说等口述材料,在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等方法的指导下,试图从各个侧面证明畲民文化的特殊性,从而为畲族被识别为单一的民族提供客观依据。而国家或调查人员也致力于规范民族划分的标准,试图以一种更为客观、稳定、科学的理论及方法推进国家的民族识别工作,并以国家的意志确定民族身份,以此代替长期混乱、流动的地方族群认同。③当然,这一阶段的畲族研究,明显还带有政治性的味道。“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至1978年,畲族研究则处于停顿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交叉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发展,我国的畲族研究更加多元,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多学科参与其中,许多新理论、新方法也被引入,如许多学者注重通过田野调查获取材料。在多学科的介入以及国际学术界的参与下,畲族研究进入更加系统和深入的阶段,一批重要的著作陆续出版,①一些地方或机构也开始组织编写相关地区的畲族志②。2002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畲族研究书系”③将畲族研究推向高潮。
近十年来,畲族研究又体现了新资料、新理论、新问题、新思路、新领域④的特点。一大批研究成果面世,如郭志超的《闽台民族史辨》⑤《畲族文化述论》⑥两部著作对畲族文化进行了较好梳理和总结;邱国珍的《浙江畲族史》⑦,按省区研究畲族的历史和文化,这种以区域的视角关照畲族史研究是一创举;由钟雷兴主编的《闽东畲族文化全书》(套装全12册)⑧,则是对闽东地区的畲族文物、乡村、民俗、民间信仰、谱牒祠堂、语言、民间故事、医药、体育、服饰、工艺美术、现代文明等方面进行系统的论述。
近年来许多学者引入族群认同、族群边界、社会记忆、近代建构论等理论来做推理和解释,涌现了一批作品。如周大鸣以实地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分析,探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畲族族群重构、畲客转化的一个个案,以此说明族群认同的内涵所在以及变迁动力来源,并说明“根基论”与“工具论”(或“情境论”)在族群认同中的不同作用①;万建中的《传说记忆与族群认同——以盘瓠传说为考察对象》运用族群的集体记忆来解释这些族群的族源②;黄向春在《“畲/汉”边界的流动与历史记忆的重构——以东南地方文献中的“蛮獠—畲”叙事为例》将边界理论运用到畲族研究上,文章对南宋以来“畲/汉”边界流动以及“畲/汉”如何通过历史记忆建构来塑造族群分类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开拓了畲族研究的新视野。③杨晋涛在《闽西蓝姓居民的“畲族意识”——一个族群建构的例子》一文中注意到,官方和民间共同致力于族群边界的建构,目的在于获得政治承认,这种族群边界建构过程中,族群认同因此发生变化;④董建辉、林宏杰的《工具主义考量与民族身份的界定——一个畲族乡的成立所引发的理论思考》一文以一个畲族乡的成立为个案,认为工具主义在构建新的民族认同中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⑤方清云的《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精英意识与民族认同——以当代畲族文化重构为例》一文注意到当代畲族文化建构中精英分子所起的作用,作者认为精英分子决定了族群文化重构的方向,而其中经济利益和民族共同情感是文化重构的重要考量因素;⑥曹大明的《重塑“畲人”:赣南畲族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以族群认同的理论分析了赣南畲族族群认同的变化,其理论取向以“根基论”为主导,兼采“工具论”,同时也论述了当代民族政策所建构的社会语境以及赣南畲族如何进行文化展示。⑦
一些硕士、博士论文也以畲族为研究对象,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如温春香在其博士论文《文化表述与地域社会:宋元以来闽粤赣毗邻区的族群研究》中,从文化表述角度审视汉人意识与汉人身份在东南的形成过程,审视族群之边界的问题,作者认为闽粤赣毗邻区乃至东南地区的汉人社会的出现,这种社会现象不能简单地用“汉化”作解释,而与对畲民典范书写的转变有关;①董波的硕士论文《从东家人到畲族——贵州麻江县六堡村畲族的人类学考察东家》则探讨了一个有趣的族群现象:一个在族群文化特征迥异于东南地区的西南族群,慢慢向畲族族群认同的转变的过程,这种研究所展现出来的新视角为畲族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②陈雍的硕士学位论文《族群与族群边界:以畲族为中心的探讨》探讨了盘瓠建构、畲民的社会定义,以及对新中国成立后族群边界的重新划定等问题进行讨论,作者认为,注意从群体内部的自我认同与群体所处的社会情景——社会定义来分析族群边界的形成,作者还提出不论是历史上还是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畲族的族群边界都是不清晰的③,但是造成这种族群边界模糊的原因及过程,作者没有深入研究。此外,还有许多博士、硕士论文从畲族的社会经济变迁、教育、文化以及个案调查等方面进行研究。④
总之,学界经过近百年的探索,畲族研究在研究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畲族研究已经成为我国民族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然而,当前的畲族研究也存在许多不足,比如,有的学者不注重史料的分析,而历史上有关畲族的史料常存在相互抄袭的情况,如不加以甄别就会陷入“以讹证讹”的困境。⑤另外,一些学者在使用理论时,存在“过度解释”之嫌,如不重视历史文献的价值,虽注意到畲族是国族主义下的近代建构,却忽略了畲族之存在,自有其近代以前之历史基础或延续性,过度地割裂了该民族本身的发展脉络,被批评为“对传统过度割裂”。在畲族史的研究中,必须重视既有的研究成果的利用,同时也要兼顾研究方法的创新,只有把畲族史置于整体的社会文化史脉络中来加以考察和把握,研究的结论才会更具说服力。
本书拟以“畲”汉边界为切入点,考察在自然(生态)史、社会史、事件史时间视野下,中国东南区域社会“畲”汉族群边界如何形成与演变,以此了解在多重语境下的“畲”民族群形成、发展与变迁历史。
(一)理论方法
1.族群与族群边界
首先,畲族是本书的讨论对象,现对本书的所论述“畲族”内涵与外延进行说明。本书支持畲族是文化概念的观点,认为不能以血统上认识或识别畲族。①关于畲族的概念,谢重光先生曾作过深入地探讨,他将“畲族”概念表述为:“畲族是历史上在赣闽粤交界区域形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它的来源很复杂,包括自五溪地区迁移至此的武陵蛮、长沙蛮后裔,当地土生土长的百越种族和山都、木客等原始居民,也包括自中原、江淮迁来的汉族移民即客家先民和福佬先民。这些不同来源的居民以赣闽粤边的广大山区为舞台,经过长期的互相接触、互相斗争、互相交流、互相融合,最后形成一种以经常移徙的粗放山林经济和狩猎经济相结合为主要经济特征,以盘瓠崇拜和相关文化事象为主要文化特征,椎髻左衽、结木架棚而居为主要生活特征的特殊文化,这种文化的载体就是畲族。”谢先生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历史畲族所具有的内涵。
本书认为,除了以这些客观文化特征来定义畲族外,还有两个重要条件需要注意:一是族群社会定义,即站在“他者”的角度,定义另外一个族群,就此而言,以汉族为代表的他者对“畲族”的形成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宋元时期,官方常将一些动乱分子不加区别地称为“畲”,而如果按血统上讲,这些所谓的“畲”,许多都是汉人;二是族群的自我定义,即族群的认同。按客观文化特征上看,历史上具备畲族某些文化特征的族群很多,然而并非所有与之
①谢重光:《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11页。
有关的族群最终都发展成为畲族,除了“他者”的定义外,本族的自我认同无疑对畲族的形成发展与变迁起着很大的作用。
因此本书认为:畲族不仅表现为具有共同客观文化特征的族群,还表现为族群的主观文化认同,这种认同不仅仅是自我认同,还包括他者的定义。畲族是客观文化特征和主观认同的统一体。客观文化特征与主观认同并非截然对立,二者常常是统一的:当本族认为他族为“异己”时,常常会放大他族的异文化;当本族认同于他者时,常常不察觉或忽略他族的异文化。
其次,通过畲族边界探讨畲族的发展与变迁是本书的主要目的。现对边界理论进行梳理。1969年,挪威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th)在其主编的论文集《族群与边界》(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中首先提出了族群边界的概念。按照巴斯对族群边界的定义,他认为造成族群的主要因素不在于核心的文化特征或文化内涵,而在于它的边界。族群边界的划定,是一个族群在生态性的资源竞争中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这种行为是动态的、多变的,它不是客观的地理边界,更多的是一种主观排他性的边界。族群的边界的表现形式既包括看得见的符号和标志,如语言、住房、生产生活方式等,也包括一些看不见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胡明文等的研究也证实,畲民姓氏、语言、风俗信仰等成为当代一些地区畲民被他族称为畲族或自我认定是畲族的依据,正是这些族群特征成为畲族族群边界得以存续。①
巴斯还指出,“族群”并不是在一种社会文化的孤立状态中发展起来的,相反,它是在不同的社会群体发生交互作用(interaction)之后才形成的,这与美国学者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的研究有共通之处。帕特森提出了“文化群”(the cultural group)概念和“族群”划分理论。他认为当一个“文化群”因为人口迁移而与周边的其他“文化群”发生接触的时候,彼此间往往会在生存资源方面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竞争,并由竞争而导致冲突(conflflict)。一旦这种竞争和冲突的局面形成,身处冲突前沿的成员就会形成越来越强固的自我认同意识。随着这种自我认同意识的不断强化,“我群”与“他群”之间的无形边界就会越来越清晰。②由于“边界”总是在不同群体间发生交互作用的前沿地带才会产生,因此,某一“族群”的形成,并非意味着某一“文化群”的所有成员都变成这
2.考古学理论
首先是考古学的区系理论。中国自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以后,开始形成了区域的文化传统,而到了新石器时代时,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各考古学者根据不同理论和方法,将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划分为不同区系。④由于各地区的自然地理的不同,这也造成了考古学意义上的各区域在文化面貌、社会结构、发展阶段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也有学者将考古文化视为一个文化地理的概念。⑤
这种区系理论应用到族群研究中,就是考察自然生态在族群及其文化塑造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证据显示,从新石器时代后期开始,在考古学意义上的华北区,就逐渐形成了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野。这种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的生态边界,最终也导致了农耕民族文化与游牧民族文化的差别。①由于生态环境不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耕民族与长城线以外的游牧民族或半农半牧民族在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进而在华夏族中形成了严格的“夷夏”观念,最后,中原地区比较有效地限制了边地民族实体、民族思想的南下或东进。
将考古学的区系理论引入族群研究,还体现在将族群历史与地域社会的发展史结合起来探讨,探讨在“大历史”背景下族群的发展与变迁,尤其注重分析在族群发展中不同生态与文化语境。更加强调历史的多元特征及历史的文化解释功能,并强调记忆与认同在历史建构中的作用。
其次是“知识考古学”理论及方法。法国学者福柯(MichelFoucault,1926—1984年)提出“知识考古学”理论,试图用考古学方法来梳理人类知识的历史,对社会主流知识进行寻根究底,②并对当代、近代和历史的知识进行再观察与再诠释,因此,有学者也将“知识考古学”称为“考古学的考古”,或者“反思性考古”。③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理论强调“话语-实践”的关系,它颠覆了试图通过知识去再现历史的传统史学方法,而希望通过社会史、思想史、科学史的考证,探讨形成这种历史知识的话语本身是如何产生的。④按照知识考古学的观点,话语不仅是一个实践过程,还内在包含着权力,而知识是话语形式表现和展开的,话语的存在形式和实践过程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中存在的,都受与某种历史条件统一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所制约,所以话语摆脱不了某种支配力量的作用。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了社会史研究关于史料的审①
3.社会记忆理论
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系统论述了社会记忆理论。②保罗·康纳顿认同社会记忆的存在,指出社会记忆有三种类型:个人记忆、认知记忆和习惯记忆。在论述社会记忆时,保罗·康纳顿提出历史重构的概念,同时指出权力在社会记忆的形成和保持过程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他认为“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等级。”掌握社会记忆的人,可以证明一个社会的合法化,并且具有了改变社会的力量,“旨在废除一种制度的仪式,只有通过反过来回忆另一些迄今为止确认那个制度的仪式,才有意义。”③以一种记忆取代另一种记忆,又称“结构性失忆”,该概念由英国人类学家古立佛(P.H.Gulliver)提出。古立佛注意到,非洲Jie族通过特别记得一些祖先,并且忘记另一些祖先来达到家族的发展(融合或分裂)的目的。④
在族群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族群常通过社会记忆才重构本族历史,目的在于使本族群在族群竞争中获取到优势地位,越是掌握社会话语权力的族群,控制社会记忆的能力越强。这种社会记忆既包括“结构性失忆”,即遗忘一些记忆,选择性地记忆某些历史;同时也包括重构历史,即建构一些与本族本来无关的记忆,最后成为本族历史的一部分。
当然,社会记忆的选择并不是无端地、任意地形成,这与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关。王明珂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历史记忆与社会情境、历史心性三者的关系,他认“非洲Jie族”在原文中如此写法,此处保留不变。
为文献或口述材料作为一种“历史事实”,实际上的一种“历史记忆”,而各种历史记忆必定忠实地反映了特定的“社会性境”和“历史心性”。所谓的社会情境是指“社会人群的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与相关的族群、性别或阶级认同与区分”,所谓的“历史心性”,是指“人们由社会中得到的一种有关历史与时间的文化概念……在此文化概念下,人们循一固定模式去回忆与建构‘历史’”①,是在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下,人类对族群“起源”(历史)之思考与建构模式。②在这种理论下,我们可以了解族群是如何通过历史书写、文化表述来建构自己的历史,同时也提醒我们对产生各类“历史记忆”的历史背景、他者的眼光以及表述者的态度、情感等需要进一步分析。
(二)资料来源
本书探讨的是族群与地域社会的关系,所采用的资料采集方面侧重于地方志、族谱、碑刻等民间资料,部分来自田野调查。历代政府重视对非汉民族的记载,在历朝的正史、实录、政书中均有体现。唐宋以后,出现了大量的文人文集、笔记记载了非汉族群的活动情况。本书采用历史文献法,对历史上的文献进行了搜集和运用。如宋代刘克庄的《后村先生大全集》③、周去非的《岭外代答》④、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⑤;元代刘埙的《水云村稿》⑥;明代王守仁的《王文成公全书》⑦、谢肇涮的《五杂俎》;清代吴震方的《岭南杂志》⑧;各代的地理志书、地方志都提供了有关的民族史材料,如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⑨;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⑩、王象之的《舆地纪胜》⑪、祝穆的《方舆胜览》①、欧阳忞的《舆地广记》②;赵万里的《元一统志》③;清代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④,等等。各省、府、县的地方志,如弘治《八闽通志》⑤、崇祯《兴化县志》、乾隆《汀州府志》⑥、乾隆《龙溪县志》⑦、乾隆《福宁府志》⑧、道光《平和县志》⑨、清代杨澜《临汀汇考》⑩、光绪《福安县志》⑪等提供了许多有关畲族的资料。
清朝以来,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各地畲民纷纷对本族的族谱进行修撰,直到目前还保存数量不少的畲民家族谱牒资料。一些机构和学者在畲民谱牒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上做出了不少努力,如福建省少数民族古籍丛书编委会编纂的《家族谱牒——畲族卷》⑩上、下两册,共收入福建各地畲民族谱22部;陈支平、刘婷玉对漳州、宁德、浙南、台湾等地的数百种的畲族族谱进行收集和整理⑬。与地方志、文集对畲民“客位”记载有所不同的是,畲民族谱的主持修纂工作主要由本族族人承担,实际撰写者除延请汉人知识分子参与外,也有部分本族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因此,畲民的族谱中加入了畲民“主位”的思考。通过梳理这些文献资料,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当时东南地区畲民族群活动情况以及畲汉族群关系情况,而且通过畲民对本族历史与传说的有意识地改造,考察畲族文化的变迁与畲族文化认同转变过程。①当然,地方志、谱牒等都有其资料的局限性,在应用这些材料的时候需加以辨别②。
民国时期以来的各类报刊、档案文件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对福建、广东、浙江等地的畲族调研报告都是畲族历史研究重要的材料。如福建省档案馆、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选编《福建畲族档案资料选编》③分综合类、政治类、经济类、文教类、附录5部分,收录省、市、县有关畲民的各类档案材料109份,为了解近当代以来的畲族历史提供了绝佳观察视角。
如谢重光、邹文清指出,明清闽粤的漳、汀、潮、惠等地地方志有关猺人、畲客的记载存在相互抄袭的情况,作者认为在使用文献要注意甄别。参见谢重光,邹文清:《试论明清粤闽畲民文献源流——从〈猺民纪略〉“中兽立毙”之类描述谈起》,《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由于学科不同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学者对族群的认识也是不同的:一般来讲,考古学、历史学以及传统民族学研究更倾向于将族群视为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不同族群具有不同的客观文化特征,其表现为体质、语言、习俗等文化的不同;而人类学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研究开始更多转向族群主观认同的研究。
事实上,关于族群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认同的结果,二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有学者把族群定义为:“族群是人们在交往互动和参照对比过程中自认为和被认为具有共同的起源或世系,从而具有某些共同文化特征的人群范畴。”①这种观点既承认族群事实存在的共同文化特征,同时也不否认主观认同在族群存在中扮演的角色,该观点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
“畲”②民作为中国东南地区族群特征比较明显的族群,常见诸历代文献中,作为一种族群称谓,“畲”最早出现于南宋末期③。学者一般认定该时期的“畲”就是当代畲族的前身,而在南宋之前及之后,“畲”不会凭空出现,也不会突然消失,作为一个与周围民族有着清晰界线的民族,畲族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脉络。
自20世纪初起,学者开始对畲族进行研究,在畲族源流、族群迁徙、畲族客观文化、畲汉族群互动、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等领域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并在百年的探索中,形成了畲族研究比较固定的范式。以畲族源流研究为例,在2004年出版的《福州畲族志》一书中写道:
早在公元7世纪初,对居住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包括畲族先民在内)的少数民族泛称“蛮”“蛮獠”“峒蛮”或“峒獠”。直至公元13世纪中叶的南宋末年,汉文史书上出现“畲民”和“輋民”两词并用的族称。前者指的闽西南汀漳地区的畲族,后者指的是广东潮州地区的畲族,二者字异音同,指的都是同一个民族……宋末元初,畲族人民纷纷加入抗元武装……当时对畲族人民所组织的抗元武装队伍,史书都称“畲军”……到了元代,“畲”字被普遍使用。明代,对“畲民”“輋民”“輋瑶”等称呼都有使用。在清代的一些地方志中,往往把畲族称为“畲民”“苗瑶”,或合称为“畲瑶”“畲蛮”。不过,“畲民”一词比较多见。民国时期,有的把畲族统称为“苗夷”或“苗族”,直到50年代,一批南下干部仍把畲族称为“苗族”,甚至畲族干部和群众也自认为是“苗族”,至今福州郊区和城区约有1000人还自报“苗族”。①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学术思想的形成,既与我国古代民族史记载的传统有关,也与中国学术史思潮有关。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斯大林的民族学理论一度成为我国民族学的指导思想。根据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即所谓的“四个共同”的标准②,学者认定畲族及其先民共享有相同的、具有显著特征的族群文化。因此,学者更多地将畲族研究的重点放在畲族客观文化特征的发现与对比研究上。通过分析畲族文化的构成要素,概括畲族的核心文化特征,继而按照文化特征的同异分辨各类族群。这使得历史上或现实中的有共同文化特征的族群产生联系,以此建立起畲族历史的系谱。唐代的“蛮”“獠”—宋代的“畲”“輋”—明清以后的“畲瑶”“畲蛮”—当代的畲族就是传统民族史研究中畲族系谱的主要脉络。
传统民族学研究对于厘清历史上纷繁复杂的族群以及界定当代民族成分,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正是由于传统民族学研究提供了的理论基础,使得畲族的认定工作得以顺利推进。及至当代,是否具有显著的民族特征甚至成为某一人群能否被识别①或被恢复为畲族的主要依据之一。
尽管“客观特征论”在族群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学术界也发现:“客观特征论”具有理论局限性,仅仅以此理论是无法解释复杂多变的族群现象。如,在20世纪80年代民族识别恢复阶段,福建省云霄县下河乡坡兜、圳头、安后、安前村钟姓,永春县下洋镇长溪村雷姓,永春县逢壶乡西昌村、八乡村等章姓,在申请恢复(畲族)民族身份时,尽管他们努力证明本族与已经被认定为畲族民族身份的同族姓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政府仍以其“民族的明显特点消失”等原因,不予变更民族身份。②与其相反的一个的例子是,贵州省麻江县东家人被认定为畲族,而这些畲族在族群文化特征上,显然与东南一带传统意义上的畲族大异其趣。③随着交叉学科的发展以及新理论、新方法的引入,学界也开始对“客观文化特征论”的研究范式进行反思,并指出其理论局限性的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客观特征论”的理论前提是先验地假定“文化变异是不连续的”。也就是说,我们将一个社会中人群分为“分享着共同文化”和“具有独立文化”两类集合体。之所以说是“先验地假定”,是因为任何一种族群和文化都不是静态的,而是变迁的。正如有学者将族群的发展比作“组织化的动脉”,就像血液流经人体动脉的各个位置,族群在不同社会文化体系中,被赋予内涵的数量和形式也均有不同。④清人吴震方在《岭南杂记》对南方非汉族群称呼变化不定曾做过一番论述,他说:
獠即蛮之种,出自梁益之间,其在岭南,则隋唐时为患,然是时不言有猺,宋以后又不言獠,意其类合分无定,故随代异名。明通志凡山
寇皆谓之獠,盖山寇亡命乌合,未必种传,无从究考。①
按照吴震方对“獠”的源流考证,各个时代分合不定的族称,不仅形式(称呼)不同,而且内涵(族群成分)也变化很大:如明代文献直接将族群成分来源不一的“山寇”统统都称为“獠”。因此,若以某一些静态的文化特征作为区分或追溯某一族群的标准,常常会出现“以今溯古”“刻舟求剑”的民族学研究困境,从而陷入“表述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②。
另一方面,“客观特征论”以文化之间的同异来区分不同的族群,注重族群“本质的”“核心的”“典型的”文化特征。但是,在历史上或现实中常常出现一些不同族群享有相同的文化特征,而所谓的相同的“族群”“民族”在许多文化特征中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正如学者指出:“在以文化作为族群区分标志时,人们只是挑选那些能够反映其世系或族源的文化特征来作为族群区分标志,对于那些不能反映其族源共同文化的特征往往视而不见。而且,为了标明族界,人们常常是在复活或发明据信是自己祖先曾有的传统文化。”③也就是说,为了证明某族群是同一族群时,人们强调族群整体的同一性、延续性,不能看到或有意忽略了族群内部的差异性与复杂性;而当想证明某两族群为不同族群时,人们又往往忽略族群间共有的文化,转而强调不同族群间的文化差异,在此过程中,可能有一些文化还存在刻意被“制造”(被建构)的情况。
自挪威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克·巴斯在《族群与边界》一书中提出族群边界理论④后,一些学者就将这个理论运用到中国族群的研究中,其中以台湾学者王明珂的华夏边缘研究为代表⑤。这些持族群边界理论的学者对传统民族研究进行反思,他们不认同“族群是一个有共同的客观体质、文化特征的人群”的观点,①族群边界地区的主观异己感之所以比族群核心地区更为强烈,按王明珂的解释是:“在族群关系中,一旦以某种主观范准界定了族群边缘,族群内部的人不用经常强调自己的文化内涵,反而是在族群边缘,族群特征被强调出来”,而“需要强调族群文化特征的人,常是有族群认同危机的人”。王明珂因此认为:“族群边缘是观察、理解族群现象的最佳位置。”②这也解释了历史和现实中时常出现的族群现象:族群认同越强烈、族群文化特征越是被强调的地区有可能不是族群的核心地区,反而是在族群的边界地区。
关于这种认识,我们还可以从日本学者濑川昌久的研究得到启示。濑川先生在研究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族谱时,发现宁化石壁传说③和南雄珠矶巷传说具有大量的相似性,他将二者比较分析后推测:“不管哪一个传说之所以都选择这类场所作为故事发生的舞台,也许是因为曾经有过一个时期,那里是从江西一侧的汉族‘华’界,进入福建、广东一侧‘夷’界的最前线,因此,这类场所就以明确的形式体现出了汉族与原住民之间的族群分界。”④
学界一般认为,“石壁”作为祖先移居传说的移居地,更多的应该被视为一个建构的文化符号。⑤华南的各个族群通过“石壁”传说等历史记忆的建构来强调文化认同,从而达到维持族群边界的目的。就此而言,与其将“石壁”看成某一历史时期某个族群祖先移居地(或集居地)中心,不如将其视作该历史时期的族群边界(或文化边界)的象征符号。也就是说,原来认为所谓的祖源地或族群的中心地带.有可能只是族群边缘地带。如果这种推论成立的话,那么有关畲族历史记忆中的移居地传说,如“凤凰山传说”“河南传说”“南京传说”①等,可能可以对其进行重新解读,这对畲族的族群形成发展史研究显然具有重大意义。
基于对传统民族学研究范式的反思,本书拟从族群边界的角度,重新审视畲族族群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希望在新理论、新方法的观照下,对畲族史研究作一番有益的探索。
一
本书从族群边界的理论角度,重新审视畲族形成、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在承认族群客观历史文化的同时,重点研究历史上“他者”(主要是汉族)对“畲”的社会定义以及“自者”(主要为南方非汉族群)自我族群认同的过程。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现实意义。
第一,本研究在研究视角上与传统民族史具有一定的区别。传统民族史研究认为历史上的畲族具有“一以贯之”的文化与传统,尽管在不同时代,畲族及其先民的族群称呼有所不同,但在客观特征上是“一脉相承”的。传统的畲族研究侧重对畲族的族源、客观文化进行研究,本书从族群边界的角度,重新审视畲族发展中的生态、文化语境,特别是重视作为“他者”存在的“畲”族群如何被建构,以及畲民族群如何对本族群的历史进行建构,以此探讨畲族文化认同转变的情况。本书除了承认族群客观文化存在的同时,同时也指出:历史上的“畲”,其文化具有不连续性,这种不连续性体现在客观文化特征的差异。比如唐宋的“蛮”“獠”、宋元的“畲军”与明清的畲民,乃至当代的畲族在文化内涵上有着较大的差异。之所以能将这些族群联系起来,在于“畲”、汉族群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进行了族群历史的建构,并形成了一定的族群的文化认同。本书在叙述与畲族有关的历史事件时,不仅关注历史事件本身,更注重历史事件背后的语境的分析,特别是一定区域内生态语境、文化语境对族群塑造的影响。历史上的“畲”族群,其自身存在一个自我发展、演变的过程,同时也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在汉文化语境中,“畲”族群存在被建构
①“河南传说”“凤凰山传说”“南京传说”为畲族的祖源或迁居地的传说,具体内容详见蓝炯熹:《畲民家族文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55页。
和自我文化建构的过程。从外因角度分析,在帝国的“华夏化”进程中,作为中国的非汉民族,“畲”不断被标签化,而成为众多非汉族群名称中的一种;从内因角度分析,一些族群通过祖源传说等历史记忆将本族与历史上的相关族群联系起来,形成特定的族群认同,建构起族群发展的历史脉络。
第二,本研究借鉴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将族群历史与地域社会发展结合研究。本文将畲族历史置于区域社会发展史特定的“语境”和历史脉络之中分析,这对于研究畲族的族群迁徙、族际交往以及自身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文化变迁更具说服力。一定的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都深刻影响着族群的发展。这种生态环境对“畲”的影响体现在多方面,如在自然生态方面,历史上曾发生畲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的生态冲突;在社会经济发面,唐宋政治经济中心南移,明代中期社会转型均带来区域族群格局的变迁;在政治文化方面,唐宋以后对南方地区的开发,越来越多的非汉民族卷入“王化”和“儒化”的社会进程中,特定时期政府的民族政策对族群的认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下的“畲”族群,其族群的文化内涵及特征可能因时因地产生变化,即各地的畲族既有历史文化的某种共性,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加入不同地域的文化因子,形成了各自地区的族群特征。可以说,各地的畲族文化的发展各有自身的特点区域畲族史研究的目的,一方面,将区域畲族的发展置于大的历史背景下,注重畲族形成的整体性与延续性;另一方面,兼顾不同地区畲族的共性与个性的比较。在特定生态社会背景下对该族群一些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从中找寻畲族发展的历史遗迹和其他信息,以此达到“一叶知秋”的效果。
通过整合畲族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学科的学术资源,就畲族族源、族际互动、文化习俗等若干专题进行专门讨论。在区域社会发展史的视野下,将不同省区,如将闽粤赣地区和闽浙赣地区的畲族进行比较研究,在梳理畲族社会发展脉络的同时,把握各个地区的畲族共性与个性。
借鉴人类学、知识考古学等方法,在理论上将畲族研究推进一步。首先,运用社会史研究方法,既重视畲族历史的宏大叙事,又重视个案的研究,特别对族群赖以生存的生态、社会、文化背景进行多方位的考察。其次,突破传统民族史框架,引入族群边界、族群认同理论,强调“畲、汉”在特殊语境下,具有流动性,在此理论下更强调历史的文化解释,强调历史的意义,强调记忆与认同在历史建构中的作用。再次,借鉴“知识考古学”等理论,对各种与畲民有关的文献或民间传说进行重新解读,更注重“文本”之后的社会情境与历史心性的研究。特别是对材料(包括文献材料与口述材料)的分析上,更注重文本所体
现出作者的立场、态度及情感。在历史上,不管是汉族或者非汉民族,其对“我群”或“他群”历史的表述,均带有一定的情感。一般而言,历史上留存的文献,多为汉族知识分子所撰写,学者通常根据其中有关非汉民族的记载来论述这些族群的历史。实际上,畲民族群中也流传着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口传材料,及至明清还有一些畲民知识分子对本族族谱进行修纂。这些有着丰富内容的文本背后,其作者的立场、写作的目的,乃至虚构族群历史的情感,均值得进一步考察。我们不仅要考察文本与历史事实的相符程度,即历史材料的真伪,还要进一步考察这些材料如何真伪、为何真伪。
第三,研究区域畲族史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华夷秩序”下和强势的汉文化中,历史上的畲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处于边缘化地位,表现为“经济的弱势、政治的异类、文化的边缘”。①新中国成立以后,畲族边缘地位得到较大改观,但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心理和文化习惯仍存留于当代,另外,相比较汉族聚集地区而言,畲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总体上比较落后。就此而言,研究区域畲族史,目的在于对畲族的生存与发展加入现实的关怀。在历史或现实中,常出现一些以划分族群边界而带来的族群冲突或族际纠纷。王明珂曾指出,之所以出现以上各种族际边界纷争,皆由所谓的“历史”造成,其背后的人类社会本性不外是资源竞争,“历史学者深入研究、争论一些表象化的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s as representation),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因各据其认同立场,选择性的取材、编织与诠释历史;如此之‘历史’经常鼓动民族情绪,导致更多的人群冲突。”②研究畲族历史,特别是对历史上的畲族与客家、福佬等民系关系进行研究,厘清族群之间融合、冲突与合作的情况,这在当下提倡和谐社会建设、消弭族群矛盾具有借鉴意义。
二
有关畲族及其先民的情况,唐宋以来的正史、方志、文人文集及笔记等文献多有记载,而近代学术意义上的畲族研究应是始于20世纪初。关于畲族研究综述,郭志超先生在其著作《闽台民族史辨》作了专题论述,他按新中国成立前
(一)新中国成立前畲族研究情况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传入中国,一些学者在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影响下,开始对中国的民族史进行研究。一般认为,刘师培在1903年完成的《中国民族志》是中国学者运用新的民族学对我国少数民族研究的开端②,而畲民和疍民③作为东南比较有特色的族群理所应当地进入学者的研究范围。1906年浙南云和县的学人魏兰(笔名浮云)发表的《畲客风俗》一书④,1911年日本学者山崎直方发表《畲族》一文⑤,成为中外学者研究畲族的开端。此后,沈作乾(1924年)⑥、董作宾(1926—1927年)⑦等也开始留意畲族的研究。如董作宾在《福建畬民考略》所说:“近著以国学门周刊所载沈作乾《括苍畬民调查记》为详……至云和某君《畬民风俗谈》,犹未见也。岁乙丑,余游学闽垣,颇留意于风俗习惯语言民族之考察。乃就披览所及,凡闽中地志笔记,有关畬民之记载,辄撮要录之,以供研究畬民者之参考焉。”⑧
此后史图博(H.Stubel)和李化民(1933年)①、何子星(1933年)②、何联奎(1936—1937年)③、凌纯声、芮逸夫、勇士衡(1947年)④、胡先骕、胡传楷、管长墉⑤、罗香林⑥、林惠祥、钟敬文、林耀华等在研究华南社会及族群文化时,也涉及畲族的研究。这些学者从畲族族源、族属、族称、族群迁徙、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广泛研究,为新中国成立后畲族的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
一些研究机构,如福建协和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前身),成立了闽学会(1926—1931年)、福建文化研究会(1931—1949年),据汪毅夫统计,福建协和大学的福建民族研究成果有20种⑦,其中与畲族有关系的有12篇,如董作宾的《畬语十八名》⑧《说畬》《福建畬民考略》;克立鹄的《福建省的“山达”》(The San Tak of Fukien Province)⑨;克立鹄、江鼎伊的《对福建土著的进一步研究》(Further Notes on Aborigines of Fukien)⑩等。除了刊在《福建文化》的研究成果外,其他作品还有:魏应麒的《畲民之起源与“畲”字之商订》、沈骥的《福建省几个特殊民族的研究》、翁绍耳的《福州北岭黄土岗特种部族人民生活》、管长墉的《福建之畲民》、陈锡襄的《畲民与客家》以及傅衣凌的《福建畲姓考》等。⑩
当时的畲族研究的状况与当时的学术关怀有着密切的关系。从19世纪中叶以后,维持了几千年的“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在西方坚船利炮和优势文化的冲击下,逐步动摇。在这种背景下,许多知识分子开始转而寻求“国族”建构,在“炎黄子孙”“黄帝世胄”“五族统一”“政更共和”①成为当时的流行话语。政府和一些学者主张“同化”(所谓的“五族统一”即是该思想的表现),认为“少数民族”的调查和研究不能刺“激作国族分化”,因此,当时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主要是以“安边”“治边”为要的“边政”研究。②在20世纪30—40年代,边疆学、边政学热潮兴起,大量中外民族学者纷纷赴边陲地区民族调查,其中又以西南地区为最多③。如1928—1949年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将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西南地区,参与这一阶段民族调查研究的学者,其研究主旨并非想刻意、任意创造一些民族范畴,而是希望通过在新学科理论和知识的指导下,结合传统华夏民族观(即以华夏为核心、四夷为边缘的“中国”观念),借着国家民族政策的施行,对民族分类、识别并且再造华夏边缘。④
相对西南地区而言,这一阶段的东南地区民族研究相对薄弱,因此,畲族研究的成果并不能算为丰富,且论著多属介绍性文章。1935年,岭南大学黄仲琴教授在《汰溪古文》一文中对福建华安仙字潭“古文”及其族属(畲民)进行研究,他在“引言”中称:“西南民族于我国古代文化有重要之关系,在今日学术界已成为一个研究之问题。学术机关以及学者个人,多往川滇各处为实地之考察;又如云南罗罗⑤及其他古族之文字,亦有为专门之研究者。川滇之外,如粤如湘如闽,尚有古代民族之遗留,若盘、蓝、雷之类是也。兹述往年在闽南所发现之古代遗文一种,以供学者参考。”⑥
该文结尾又写道:“若得译其(指汰溪古文)词意,且加以较长之时间应需之费用,尽拓其地所有刻石,且相择处所,为发掘之工作,当必续有发现,使沈埋史迹,复见光明,于研究我国西南民族文化者,有所裨益也。”①由此可见,当时西南民族研究成为中国民族学的研究中心,畲族的研究常作为西南民族研究的补充、参考或个案印证来研究。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畲族研究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国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民族识别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斯大林的五阶段论的指导下,有关单位对中国各民族的社会形态进行调查。畲族研究在此背景的推动下形成了热潮,也取得了较多的调查成果。在1953年和1955年,中央分别组织畲族调查小组进行实地调查,调查组获得许多畲族珍贵的文献、民俗、语言等资料②,并认定畲民既不是汉族,也不是瑶族的一支,而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在1956年12月,经国务院正式公布,畲族作为单一民族最终被确认。自1958年起,国家又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形成29篇、共40万字的调查报告,并编成《畲族简史简志合编》。
这一阶段的畲族社会历史调查,调查组深入畲民住区,通过挖掘历史文献材料以及民间传说等口述材料,在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等方法的指导下,试图从各个侧面证明畲民文化的特殊性,从而为畲族被识别为单一的民族提供客观依据。而国家或调查人员也致力于规范民族划分的标准,试图以一种更为客观、稳定、科学的理论及方法推进国家的民族识别工作,并以国家的意志确定民族身份,以此代替长期混乱、流动的地方族群认同。③当然,这一阶段的畲族研究,明显还带有政治性的味道。“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至1978年,畲族研究则处于停顿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交叉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发展,我国的畲族研究更加多元,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多学科参与其中,许多新理论、新方法也被引入,如许多学者注重通过田野调查获取材料。在多学科的介入以及国际学术界的参与下,畲族研究进入更加系统和深入的阶段,一批重要的著作陆续出版,①一些地方或机构也开始组织编写相关地区的畲族志②。2002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畲族研究书系”③将畲族研究推向高潮。
近十年来,畲族研究又体现了新资料、新理论、新问题、新思路、新领域④的特点。一大批研究成果面世,如郭志超的《闽台民族史辨》⑤《畲族文化述论》⑥两部著作对畲族文化进行了较好梳理和总结;邱国珍的《浙江畲族史》⑦,按省区研究畲族的历史和文化,这种以区域的视角关照畲族史研究是一创举;由钟雷兴主编的《闽东畲族文化全书》(套装全12册)⑧,则是对闽东地区的畲族文物、乡村、民俗、民间信仰、谱牒祠堂、语言、民间故事、医药、体育、服饰、工艺美术、现代文明等方面进行系统的论述。
近年来许多学者引入族群认同、族群边界、社会记忆、近代建构论等理论来做推理和解释,涌现了一批作品。如周大鸣以实地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分析,探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畲族族群重构、畲客转化的一个个案,以此说明族群认同的内涵所在以及变迁动力来源,并说明“根基论”与“工具论”(或“情境论”)在族群认同中的不同作用①;万建中的《传说记忆与族群认同——以盘瓠传说为考察对象》运用族群的集体记忆来解释这些族群的族源②;黄向春在《“畲/汉”边界的流动与历史记忆的重构——以东南地方文献中的“蛮獠—畲”叙事为例》将边界理论运用到畲族研究上,文章对南宋以来“畲/汉”边界流动以及“畲/汉”如何通过历史记忆建构来塑造族群分类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开拓了畲族研究的新视野。③杨晋涛在《闽西蓝姓居民的“畲族意识”——一个族群建构的例子》一文中注意到,官方和民间共同致力于族群边界的建构,目的在于获得政治承认,这种族群边界建构过程中,族群认同因此发生变化;④董建辉、林宏杰的《工具主义考量与民族身份的界定——一个畲族乡的成立所引发的理论思考》一文以一个畲族乡的成立为个案,认为工具主义在构建新的民族认同中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⑤方清云的《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精英意识与民族认同——以当代畲族文化重构为例》一文注意到当代畲族文化建构中精英分子所起的作用,作者认为精英分子决定了族群文化重构的方向,而其中经济利益和民族共同情感是文化重构的重要考量因素;⑥曹大明的《重塑“畲人”:赣南畲族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以族群认同的理论分析了赣南畲族族群认同的变化,其理论取向以“根基论”为主导,兼采“工具论”,同时也论述了当代民族政策所建构的社会语境以及赣南畲族如何进行文化展示。⑦
一些硕士、博士论文也以畲族为研究对象,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如温春香在其博士论文《文化表述与地域社会:宋元以来闽粤赣毗邻区的族群研究》中,从文化表述角度审视汉人意识与汉人身份在东南的形成过程,审视族群之边界的问题,作者认为闽粤赣毗邻区乃至东南地区的汉人社会的出现,这种社会现象不能简单地用“汉化”作解释,而与对畲民典范书写的转变有关;①董波的硕士论文《从东家人到畲族——贵州麻江县六堡村畲族的人类学考察东家》则探讨了一个有趣的族群现象:一个在族群文化特征迥异于东南地区的西南族群,慢慢向畲族族群认同的转变的过程,这种研究所展现出来的新视角为畲族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②陈雍的硕士学位论文《族群与族群边界:以畲族为中心的探讨》探讨了盘瓠建构、畲民的社会定义,以及对新中国成立后族群边界的重新划定等问题进行讨论,作者认为,注意从群体内部的自我认同与群体所处的社会情景——社会定义来分析族群边界的形成,作者还提出不论是历史上还是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畲族的族群边界都是不清晰的③,但是造成这种族群边界模糊的原因及过程,作者没有深入研究。此外,还有许多博士、硕士论文从畲族的社会经济变迁、教育、文化以及个案调查等方面进行研究。④
总之,学界经过近百年的探索,畲族研究在研究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畲族研究已经成为我国民族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然而,当前的畲族研究也存在许多不足,比如,有的学者不注重史料的分析,而历史上有关畲族的史料常存在相互抄袭的情况,如不加以甄别就会陷入“以讹证讹”的困境。⑤另外,一些学者在使用理论时,存在“过度解释”之嫌,如不重视历史文献的价值,虽注意到畲族是国族主义下的近代建构,却忽略了畲族之存在,自有其近代以前之历史基础或延续性,过度地割裂了该民族本身的发展脉络,被批评为“对传统过度割裂”。在畲族史的研究中,必须重视既有的研究成果的利用,同时也要兼顾研究方法的创新,只有把畲族史置于整体的社会文化史脉络中来加以考察和把握,研究的结论才会更具说服力。
本书拟以“畲”汉边界为切入点,考察在自然(生态)史、社会史、事件史时间视野下,中国东南区域社会“畲”汉族群边界如何形成与演变,以此了解在多重语境下的“畲”民族群形成、发展与变迁历史。
(一)理论方法
1.族群与族群边界
首先,畲族是本书的讨论对象,现对本书的所论述“畲族”内涵与外延进行说明。本书支持畲族是文化概念的观点,认为不能以血统上认识或识别畲族。①关于畲族的概念,谢重光先生曾作过深入地探讨,他将“畲族”概念表述为:“畲族是历史上在赣闽粤交界区域形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它的来源很复杂,包括自五溪地区迁移至此的武陵蛮、长沙蛮后裔,当地土生土长的百越种族和山都、木客等原始居民,也包括自中原、江淮迁来的汉族移民即客家先民和福佬先民。这些不同来源的居民以赣闽粤边的广大山区为舞台,经过长期的互相接触、互相斗争、互相交流、互相融合,最后形成一种以经常移徙的粗放山林经济和狩猎经济相结合为主要经济特征,以盘瓠崇拜和相关文化事象为主要文化特征,椎髻左衽、结木架棚而居为主要生活特征的特殊文化,这种文化的载体就是畲族。”谢先生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历史畲族所具有的内涵。
本书认为,除了以这些客观文化特征来定义畲族外,还有两个重要条件需要注意:一是族群社会定义,即站在“他者”的角度,定义另外一个族群,就此而言,以汉族为代表的他者对“畲族”的形成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宋元时期,官方常将一些动乱分子不加区别地称为“畲”,而如果按血统上讲,这些所谓的“畲”,许多都是汉人;二是族群的自我定义,即族群的认同。按客观文化特征上看,历史上具备畲族某些文化特征的族群很多,然而并非所有与之
①谢重光:《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11页。
有关的族群最终都发展成为畲族,除了“他者”的定义外,本族的自我认同无疑对畲族的形成发展与变迁起着很大的作用。
因此本书认为:畲族不仅表现为具有共同客观文化特征的族群,还表现为族群的主观文化认同,这种认同不仅仅是自我认同,还包括他者的定义。畲族是客观文化特征和主观认同的统一体。客观文化特征与主观认同并非截然对立,二者常常是统一的:当本族认为他族为“异己”时,常常会放大他族的异文化;当本族认同于他者时,常常不察觉或忽略他族的异文化。
其次,通过畲族边界探讨畲族的发展与变迁是本书的主要目的。现对边界理论进行梳理。1969年,挪威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th)在其主编的论文集《族群与边界》(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中首先提出了族群边界的概念。按照巴斯对族群边界的定义,他认为造成族群的主要因素不在于核心的文化特征或文化内涵,而在于它的边界。族群边界的划定,是一个族群在生态性的资源竞争中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这种行为是动态的、多变的,它不是客观的地理边界,更多的是一种主观排他性的边界。族群的边界的表现形式既包括看得见的符号和标志,如语言、住房、生产生活方式等,也包括一些看不见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胡明文等的研究也证实,畲民姓氏、语言、风俗信仰等成为当代一些地区畲民被他族称为畲族或自我认定是畲族的依据,正是这些族群特征成为畲族族群边界得以存续。①
巴斯还指出,“族群”并不是在一种社会文化的孤立状态中发展起来的,相反,它是在不同的社会群体发生交互作用(interaction)之后才形成的,这与美国学者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的研究有共通之处。帕特森提出了“文化群”(the cultural group)概念和“族群”划分理论。他认为当一个“文化群”因为人口迁移而与周边的其他“文化群”发生接触的时候,彼此间往往会在生存资源方面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竞争,并由竞争而导致冲突(conflflict)。一旦这种竞争和冲突的局面形成,身处冲突前沿的成员就会形成越来越强固的自我认同意识。随着这种自我认同意识的不断强化,“我群”与“他群”之间的无形边界就会越来越清晰。②由于“边界”总是在不同群体间发生交互作用的前沿地带才会产生,因此,某一“族群”的形成,并非意味着某一“文化群”的所有成员都变成这
2.考古学理论
首先是考古学的区系理论。中国自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以后,开始形成了区域的文化传统,而到了新石器时代时,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各考古学者根据不同理论和方法,将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划分为不同区系。④由于各地区的自然地理的不同,这也造成了考古学意义上的各区域在文化面貌、社会结构、发展阶段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也有学者将考古文化视为一个文化地理的概念。⑤
这种区系理论应用到族群研究中,就是考察自然生态在族群及其文化塑造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证据显示,从新石器时代后期开始,在考古学意义上的华北区,就逐渐形成了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野。这种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的生态边界,最终也导致了农耕民族文化与游牧民族文化的差别。①由于生态环境不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耕民族与长城线以外的游牧民族或半农半牧民族在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进而在华夏族中形成了严格的“夷夏”观念,最后,中原地区比较有效地限制了边地民族实体、民族思想的南下或东进。
将考古学的区系理论引入族群研究,还体现在将族群历史与地域社会的发展史结合起来探讨,探讨在“大历史”背景下族群的发展与变迁,尤其注重分析在族群发展中不同生态与文化语境。更加强调历史的多元特征及历史的文化解释功能,并强调记忆与认同在历史建构中的作用。
其次是“知识考古学”理论及方法。法国学者福柯(MichelFoucault,1926—1984年)提出“知识考古学”理论,试图用考古学方法来梳理人类知识的历史,对社会主流知识进行寻根究底,②并对当代、近代和历史的知识进行再观察与再诠释,因此,有学者也将“知识考古学”称为“考古学的考古”,或者“反思性考古”。③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理论强调“话语-实践”的关系,它颠覆了试图通过知识去再现历史的传统史学方法,而希望通过社会史、思想史、科学史的考证,探讨形成这种历史知识的话语本身是如何产生的。④按照知识考古学的观点,话语不仅是一个实践过程,还内在包含着权力,而知识是话语形式表现和展开的,话语的存在形式和实践过程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中存在的,都受与某种历史条件统一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所制约,所以话语摆脱不了某种支配力量的作用。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了社会史研究关于史料的审①
3.社会记忆理论
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系统论述了社会记忆理论。②保罗·康纳顿认同社会记忆的存在,指出社会记忆有三种类型:个人记忆、认知记忆和习惯记忆。在论述社会记忆时,保罗·康纳顿提出历史重构的概念,同时指出权力在社会记忆的形成和保持过程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他认为“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等级。”掌握社会记忆的人,可以证明一个社会的合法化,并且具有了改变社会的力量,“旨在废除一种制度的仪式,只有通过反过来回忆另一些迄今为止确认那个制度的仪式,才有意义。”③以一种记忆取代另一种记忆,又称“结构性失忆”,该概念由英国人类学家古立佛(P.H.Gulliver)提出。古立佛注意到,非洲Jie族通过特别记得一些祖先,并且忘记另一些祖先来达到家族的发展(融合或分裂)的目的。④
在族群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族群常通过社会记忆才重构本族历史,目的在于使本族群在族群竞争中获取到优势地位,越是掌握社会话语权力的族群,控制社会记忆的能力越强。这种社会记忆既包括“结构性失忆”,即遗忘一些记忆,选择性地记忆某些历史;同时也包括重构历史,即建构一些与本族本来无关的记忆,最后成为本族历史的一部分。
当然,社会记忆的选择并不是无端地、任意地形成,这与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关。王明珂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历史记忆与社会情境、历史心性三者的关系,他认“非洲Jie族”在原文中如此写法,此处保留不变。
为文献或口述材料作为一种“历史事实”,实际上的一种“历史记忆”,而各种历史记忆必定忠实地反映了特定的“社会性境”和“历史心性”。所谓的社会情境是指“社会人群的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与相关的族群、性别或阶级认同与区分”,所谓的“历史心性”,是指“人们由社会中得到的一种有关历史与时间的文化概念……在此文化概念下,人们循一固定模式去回忆与建构‘历史’”①,是在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下,人类对族群“起源”(历史)之思考与建构模式。②在这种理论下,我们可以了解族群是如何通过历史书写、文化表述来建构自己的历史,同时也提醒我们对产生各类“历史记忆”的历史背景、他者的眼光以及表述者的态度、情感等需要进一步分析。
(二)资料来源
本书探讨的是族群与地域社会的关系,所采用的资料采集方面侧重于地方志、族谱、碑刻等民间资料,部分来自田野调查。历代政府重视对非汉民族的记载,在历朝的正史、实录、政书中均有体现。唐宋以后,出现了大量的文人文集、笔记记载了非汉族群的活动情况。本书采用历史文献法,对历史上的文献进行了搜集和运用。如宋代刘克庄的《后村先生大全集》③、周去非的《岭外代答》④、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⑤;元代刘埙的《水云村稿》⑥;明代王守仁的《王文成公全书》⑦、谢肇涮的《五杂俎》;清代吴震方的《岭南杂志》⑧;各代的地理志书、地方志都提供了有关的民族史材料,如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⑨;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⑩、王象之的《舆地纪胜》⑪、祝穆的《方舆胜览》①、欧阳忞的《舆地广记》②;赵万里的《元一统志》③;清代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④,等等。各省、府、县的地方志,如弘治《八闽通志》⑤、崇祯《兴化县志》、乾隆《汀州府志》⑥、乾隆《龙溪县志》⑦、乾隆《福宁府志》⑧、道光《平和县志》⑨、清代杨澜《临汀汇考》⑩、光绪《福安县志》⑪等提供了许多有关畲族的资料。
清朝以来,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各地畲民纷纷对本族的族谱进行修撰,直到目前还保存数量不少的畲民家族谱牒资料。一些机构和学者在畲民谱牒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上做出了不少努力,如福建省少数民族古籍丛书编委会编纂的《家族谱牒——畲族卷》⑩上、下两册,共收入福建各地畲民族谱22部;陈支平、刘婷玉对漳州、宁德、浙南、台湾等地的数百种的畲族族谱进行收集和整理⑬。与地方志、文集对畲民“客位”记载有所不同的是,畲民族谱的主持修纂工作主要由本族族人承担,实际撰写者除延请汉人知识分子参与外,也有部分本族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因此,畲民的族谱中加入了畲民“主位”的思考。通过梳理这些文献资料,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当时东南地区畲民族群活动情况以及畲汉族群关系情况,而且通过畲民对本族历史与传说的有意识地改造,考察畲族文化的变迁与畲族文化认同转变过程。①当然,地方志、谱牒等都有其资料的局限性,在应用这些材料的时候需加以辨别②。
民国时期以来的各类报刊、档案文件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对福建、广东、浙江等地的畲族调研报告都是畲族历史研究重要的材料。如福建省档案馆、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选编《福建畲族档案资料选编》③分综合类、政治类、经济类、文教类、附录5部分,收录省、市、县有关畲民的各类档案材料109份,为了解近当代以来的畲族历史提供了绝佳观察视角。
如谢重光、邹文清指出,明清闽粤的漳、汀、潮、惠等地地方志有关猺人、畲客的记载存在相互抄袭的情况,作者认为在使用文献要注意甄别。参见谢重光,邹文清:《试论明清粤闽畲民文献源流——从〈猺民纪略〉“中兽立毙”之类描述谈起》,《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附注
①潘蛟:《勃罗姆列伊的民族分类及其关联的问题》,《民族研究》,1995年第4期,第17-18页;又见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39页
②本书所论的“畲”不完全等同于现代民族概念的畲族笔者认为,“畲”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不断丰富的族群,历史上的“畬”现代的畲族在外延与内涵上均有不同,另外本书论述的“畲”溯及畲族的可能族源,而不是真正的畲民,为了不引起歧义及行文方便,特加上引号。
③学界一般将刘克庄的《漳州谕畲》一文的问世[该文成于南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年)],作为“畲”民在文献上出现的最早时间。谢重光先生则认为,南宋《舆地纪胜》中记载的“山客輋”,是一种广东梅州地区特定族群的称谓,该志书是“輋”(“畲”)文献上的最早记载,其成书于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比刘克庄《漳州谕畲》一文早问世35年另外,最迟不晚于端平元年(1234年),在潮州地区出现“山斜(畲)”的称谓(《宋史》卷四一九《许应龙传》),也比刘克庄《漳州谕畲》早了30年左右参见谢重光:《客家文化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77页。
①福州市畲族志编委会:《福州畲族志》,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29页。
②斯大林将民族定义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与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参见[苏联]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94页。
①黄光学,施联朱:《中国的民族识别》,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175页。
②参见《云霄县民政局关于坡兜、圳头、安后、安前村钟姓要求恢复畲族问题的调查报告及漳州市民政局的答复》《永春县人民政府关于申请恢复少数民族成分的报告及泉州市民政局的批复》,载福建省档案馆、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编:《福建畲族档案资料选编(1937—1990)》,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92-194页,第201-202页。
③董波:《从东家人到畲族——贵州麻江县六堡村畲族的人类学考察东家》,厦门: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④[挪威]费雷德里克·巴斯著;高崇译,周大鸣校,李远龙复校:《族群与边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第16页,第18页。
①[清]吴震方:《岭南杂记》,丛书集成初编,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复印本),第28页。
②[美]马尔库斯(George E.Marcus),费彻尔(Michael M.J.Fischer)著,王铭铭,蓝达居译:《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3-36页
③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39页。
④族群边界理论参见[挪威]弗里德里克·巴斯主编:《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挪威]费雷德里克·巴斯著;高崇译,周大鸣校,李远龙复校:《族群与边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第16-27页;[挪威]费雷德里克·巴斯著,李丽琴译:《族群与边界》(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⑤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而是认为族群由族群边界维持,“造成族群边界的是一群人主观上对外的异己感(the sense of otherness),以及对内的基本情感联系(primordial attachment)。”
①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页。
②同①,第17页,第45页。
③濑川昌久根据《畲族历史社会调查》发现,在福建宁德县丹头、福安县甘棠乡山头庄,江西省铅山县,贵溪县,广东省潮州凤凰山区李公坑、碗窑,丰顺县凤坪等地的畲族中流传着与宁化石壁相关联的祖先移居传说,进而论证了牧野巽关于“汉族祖先移居传说是伴随着少数民族汉化同步传播的结果”推测的正确性。参见[日]濑川昌久著,钱杭译:《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221-222页、第226页。
④同③,第228页。
⑤持有类似观点的文章如谢重光:《客家普遍溯源于宁化石壁的文化意蕴》,《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9年第1期;谢重光:《南方少数民族汉化的典型模式——“石壁现象”和“固始现象”透视》,《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9期;余达忠,曾念强:《一个文化符号的形成与演变——基于宁化石壁的个案研究》,《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6期。
①王逍:《文化透镜下的畲族历史》,《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第169页。
②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46页。
与新中国成立后、分专题对畲族研究进行详细介绍①,研究综述时间截至成书前(2006年)。近十年来,畲族研究取得了许多新成果,研究出现新动态,需要进行重新整理与反思。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畲族研究进行简单回顾,重点论述研究背景及十年来的新趋势。
①郭志超:《闽台民族史辨》,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第451-531页。
②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1-69页、第73-84页。
③疍民,也写作蜑民、蜒民、蛋民等,为历代文人对各地水上居民的称呼。疍民在历史上广泛分布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是一个以舟居水处及水上作业为主要生活、生产特征的族群,其中又以福建、广东、广西三省区沿海及江河港市最为集中。历史文献关于东南地区族群的记载,经常将畲、疍并称。近代学术界关于疍民的研究,几乎与畲族研究同时进行,都是我国民族史与族群研究的一个缩影。参见黄向春:《从疍民研究看中国民族史与族群研究的百年探索》,《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第55-65页。
④浮云:《畲客风俗》。该书版本有争议,沈作乾在《畲民调查记》中称:“此书于民国前三四年脱稿,由其本人石印千本,分送戚友,并未出版”;而德国学者史图博(H.Stubel)在撰写《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一文时,引用《畲客风俗》内容,并注明其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出版,由上海会文堂发行。参见[德]史图博,李化民:《浙江景宁县敕木山畲民调查记》(“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六号,1932年德文版),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84年,第13-17页。
⑤[日]山崎直方:《畲族》,《人类学杂志》,1911年第27卷第1号,第24-25页。
⑥沈作乾:《畲民调查记》,《东方杂志》,第21卷第7号,1924年。
⑦董作宾:《说“畲”》,《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6年;董作宾:《畲语十八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1926年;董作宾:《福建畲民考略》,《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集刊》,1927年。
⑧董作宾:《福建畬民考略》,《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集刊》,第一集第二期,1927年11月,第21页。
①[德]史图博,李化民:《浙江景宁县敕木山畲民调查记》,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84年
②何子星:《畲民问题》,《东方杂志》,第30卷第13号,1933年。
③何联奎:《畲民地理分布》,《民族学研究集刊》,第2集,1937年。
④凌纯声:《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16本,1947年,第127-172页。
⑤管长墉:《福建之畲民——社会学的研究与史料的整理》,《福建文化》,第1卷第4期,1941年
⑥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广东兴宁希山书藏社1933年初版;台北古亭书屋于1975年、台北众文图书有限公司于1981年、台北南天书局于199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92年再版发行。
⑦统计主要根据各个时期福建协和大学校内教员和学生在校内外刊物发表的论文,以及校内刊物发表的校内外学者的论文检索而得。参见汪毅夫:《福建协和大学与福建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35页。
⑧董作宾:《畲语十八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1926年。
⑨克立鹄:《福建省的“山达”》(The San Tak of Fukien Province),载《中国文理杂志》(The China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ls),第4卷第5期,1926年5月。
⑩克立鹄,江鼎伊:《对福建土著的进一步研究》(Further Notes on Aborigines of Fukkien),载《中国文理杂志》(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第5卷第2期,1927年2月。
⑪参见汪毅夫:《福建协和大学与福建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35-36页。
①如民国元年(1912年)上杭雷氏撰修族谱时,该族知识分子雷熙春、雷晓春在《序》中写道:“迄明、清二代,族中科名仕宦于今为盛,而士大夫博学识能文章者,先后修谱两次,曾未昌言民族主义。为详考吾族得姓之缘,纪以志诸谱牒,知其慑服于专制余威者为已殁矣。乃者五族统一,政更共和,举黄帝手定之锦绣河山悉以还诸黄帝世胄,而此谱适于是年秋月以成。由是濡毫吮墨,畅所欲言,俾吾祖吾宗萦抱民族思想,得于序录中表白一二。”参见雷熙春,雷国瑞纂修:《上杭雷氏梓福公家谱》,民国元年(1912年)刻本,载《家族谱牒——畲族卷》(下),福州:海风出版社,2011年,第111页。
②王明珂:《由族群到民族:中国西南历史经验》,《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1期,第1页。
③20世纪30—40年代的民族调查以西南为重点,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等地区的民族田野调查也各有侧重地展开。详见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7-181页。
④王明珂:《由族群到民族:中国西南历史经验》,《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1期,第1页,第6页。
⑤罗罗系彝族旧称,新中国成立后废弃不用,姑存原文。
⑥黄仲琴:《汰溪古文》,《岭南大学学报》,第四卷第二期,1935年,载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编:《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11页。
①黄仲琴:《汰溪古文》,《岭南大学学报》,第四卷第二期,1935年,载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编:《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16页。
②相关情况可参阅宋蜀华,满都尔图主编:《中国民族学五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③王建民等著:《中国民族学史》(下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26页。
①这时期的代表作主要有《畲族简史》编写组:《畲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福建省编辑组:《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州:福建省人民出版社,1986年;蒋炳钊:《畲族史稿》,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施联朱著:《畲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年;施联朱编著:《畲族风俗志》,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等等
②这些畲族志如俞郁田编纂:《霞浦县畲族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黄集良主编:《上杭县畲族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福安畲族志》编纂委员会编,蓝炯熹总纂:《福安畲族志》,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蓝运全,缪品枚主编:《闽东畲族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蓝存干:《宁德市畲族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陈国强等主编:《崇儒乡畲族》,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陈国强:《霞浦水门畲族》,中国人类学会编,1999年;蓝炯喜著:《猴墩茶人:畲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州市畲族志》,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石奕龙,张实主编:《畲族:福建罗源县八井村调查》,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穆云畲族乡志》编委会,蓝炯熹主编:《穆云畲族乡志》,福州:海峡书局,2014年
③主要有吴永章的《畲族与苗瑶比较研究》,谢重光的《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游文良的《畲语研究》,蓝雪霏的《畲族音乐文化》,蓝炯熹的《畲民家族文化》和雷弯山的《畲族风情》。
④谢重光,张春兰:《畲族文化研究的新收获——2009年全国畲族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⑤郭志超:《闽台民族史辨》,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
⑥郭志超:《畲族文化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⑦邱国珍:《浙江畲族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10年。
⑧钟雷兴主编:《闽东畲族文化全书》(1-12册),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
①周大鸣:《从“客家”到“畲族”——以赣南畲族为例看畲客关系》,《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09年第6辑,第1-6页。
②万建中:《传说记忆与族群认同——以盘瓠传说为考察对象》,《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③黄向春:《“畲/汉”边界的流动与历史记忆的重构——以东南地方文献中的“蛮獠—畲”叙事为例》,《学术月刊》,2009年第6期,第138页。
④杨晋涛:《闽西蓝姓居民的“畲族意识”——一个族群建构的例子》,载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编:《畲族文化研究》(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168页。
⑤董建辉,林宏杰:《工具主义考量与民族身份的界定——一个畲族乡的成立所引发的理论思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27页。
⑥方清云:《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精英意识与民族认同——以当代畲族文化重构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81-84页。
⑦曹大明:《重塑“畲人”:赣南畲族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广州:中国出版集团,2014年。
①温春香:《文化表述与地域社会:宋元以来闽粤赣毗邻区的族群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②董波:《从东家人到畲族——贵州麻江县六堡村畲族的人类学考察东家》,厦门: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③陈雍:《族群与族群边界:以畲族为中心的探讨》,武汉:湖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④谢彪:《畲汉文化互动下的畲族古代教育研究》,福州: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张小椿:《清代以来畲族教育研究》,福州: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蓝美芬:《闽北畲族社会经济文化变迁考察——松溪民间契约文书研究》,厦门: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牛玉西:《畲族与客家的文化互动研究——以平和县秀峰乡龙岭村为例》,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周慧慧:《闽东畲族汉化进程中的文化发展与遗失》,福州: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谢琳:《闽东畲村谢岭下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厦门: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葛赢超:《金贝:一个东南畲村的社会与文化》,厦门: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张镇升:《宋末与元初闽粤赣边畲汉民变比较研究》,广州: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等等。
⑤如谢重光、邹文清指出,明清闽粤的漳、汀、潮、惠等地地方志有关猺人、畲客的记载存在相互抄袭的情况,作者认为在使用文献要予以甄别。参见谢重光,邹文清:《试论明清粤闽畲民文献源流——从〈猺民纪略〉“中兽立毙”之类描述谈起》,《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①胡明文,古新仁:《移民孤岛与族群边界存续——江西“两江”畲族移民村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62页。
②梁肇庭著,冷剑波,周云水译:《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族群性:客家、棚民及其邻居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个“族群”,而是意味着只有那些与其他“文化群”发生交互作用的成员,才会凝聚成为一个“族群”。①
族群边界的消解则与族群隔离的消除以及不同族群间文化趋同的加剧有着密切的关系。学术界关于族群认同形成的解释,大体可以分为原生论和工具论②两种观点,这两种观点从不同角度,较好地解释了族群的认同起源及转向等问题。
因此,族群认同在族群边界的形成和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族群认同是人们在交往互动和参照对比过程中构建的一种关系,族群范畴会跟随与它交往互动和参照对比的对象的变换而伸缩。”③比如说,古代中国“华”的族群认同是在与“夷”交往互动中产生,而“华”中又有南方汉人北方汉人的认同;南方人中又有多种民系的认同,如福佬、客家、广府等民系认同的区别,这种认同是建立在一定的参照对象中产生的。换句话说,没有“他者”的存在,就没有“我族”意识的产生。
①王东:《那山那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②根基论或原生论(primordialist approach)强调族群认同原生性、非理性;工具论(intrumentalist approach)或情境论(Circumstantialist approach)则强调族群认同的趋利性、工具性。以上理论参见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6-352页。
③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39-340页。
④代表性的观点有严文明的“三区”说、苏秉琦的“六区”说、佟柱臣的“七区”说、陈剩勇的“七大文化圈”说、侯甬坚的“九区”说、周廷儒的“十区”说等,以上观点参见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25-234页;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规律和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86年第2期;陈剩勇:《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之谜破译》,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年,第264页;侯甬坚:《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3-36页;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16-221页。关于新石器遗址的“文化区系”观点的综述还可以参见郑韬凯:《从洞穴到聚落——中国石器时代先民的居住模式和居住观念研究》,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40-41页。
⑤王妙发:《黄河流域聚落论稿——从史前聚落到早期都市》,北京: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5页。
①在黄河长江中下游的平原地区(中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发生了农业文化,与这一片平原上的宜耕土地在北方与内蒙古高原的草地和戈壁相接,在西方却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相连。这些高原除了一部分黄土地带和一些盆地外都不宜耕种,而适于牧业。而划分农牧两区的地理界线大体上就是从战国时开始建筑直到现在还存在的长城。参见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9-10页。
②[法]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③曹兵武:《知识考古:现代考古学知识和概念的梳理与重构——〈南方文物〉“知识考古”专栏开栏辞》,《南方文物》,2011年第2期,第74-75页。
④项晓敏:《福柯考古学话语体系探微》,《浙江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3期,第37页。
视与使用,并形成了社会史研究新的范式。这种研究方法认为,一些文献或口述材料可能存在着时间或空间的错位,但是作为某种历史记忆,却包含着反映某种社会情境的历史真实,通过史料的考古,口头传说与正史、野史、文献等材料具有某种同等的含义。因此,解释、辨伪文献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了,而揭示一定历史时期的不同性质话语形成的原因、过程可能更值得挖掘。可以说,如果传统史学观点的焦点在于探究何为真、何为假,那么新的研究方法则重点考察“如何”真、假,并且“为何”真、假的问题。
①户华为:《虚构与真实——民间传说、历史记忆与社会史“知识考古”》,《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162-163页。
②[美]保罗·康纳顿(PaulConnerton):《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③同②,第1页,第5页。
④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①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143页。
②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36页
③[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初编216集部,据上海涵芬楼景印旧钞本,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重印影印,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
④[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
⑤[宋]范成大撰:《桂海虞衡志》(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⑥[元]刘埙:《水云村稿》,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134别集类,第1195册。
⑦[明]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四部丛刊初编259集部;据上海涵芬楼景印明隆庆刊本,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重印影印,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
⑧[清]吴震方:《岭南杂志》卷五,明新堂藏版,嘉庆五年重刊本。
⑨[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⑩[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⑪[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①[宋]祝穆撰,施和金校:《方舆胜览》,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②[宋]欧阳忞撰,李勇先,王小红校注:《舆地广记》(宋元地理志丛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③赵万里辑:《元一统志》,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
④[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续修四库全书597史部地理类,据上海图书馆清抄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⑤[明]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⑥[清]曾曰瑛等修,李绂等纂:《汀州府志》,乾隆十七年(1752年)修,同治六年刊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七十五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
⑦[清]吴宜燮修,黄惠,李畴纂:《龙溪县志》,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⑧[清]朱珪修,李绂纂:《福宁府志》,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修,光绪六年重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
⑨[清]黄许桂修,曾泮水纂:《平和县志》,道光十三年(1833年)修,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⑩[清]杨澜:《临汀汇考》,光绪四年(1878年)刊本,福建师大古籍室藏。
⑪[清]张景祁等纂修:《福安县志》,据清光绪十年(1884年)刊本影印,中国方志丛书第78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
⑫福建省少数民族古籍丛书编委会:《家族谱牒——畲族卷》(上、下),福州:海风出版社,2010—2011年。
⑬陈支平,刘婷玉:《闽台畲族族谱搜集整理札记》,《人民论坛》,2011年第12期。
①温春香认为,随着新材料、新方法的引入,传统的单纯地以汉文献入手的“客位”畲族研究,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诟病,由于文献中不可避免地渗透了本族群的意识与立场,因此可以更多地探讨文献作者(包括畲民自身)的立场和情感,以此探讨动态的族群发展及有趣的族群认同变迁过程。温春香:《明清以来闽粤赣交界区畲民的族谱书写与族群意识》,《贵州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
②谢重光在《客家源流新探》一书中,就专门列有“谱牒资料在客家研究中的价值和局限”一节,批评罗香林客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4-20页。
③福建省档案馆、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编:《福建畲族档案资料选编(1937—1990)》,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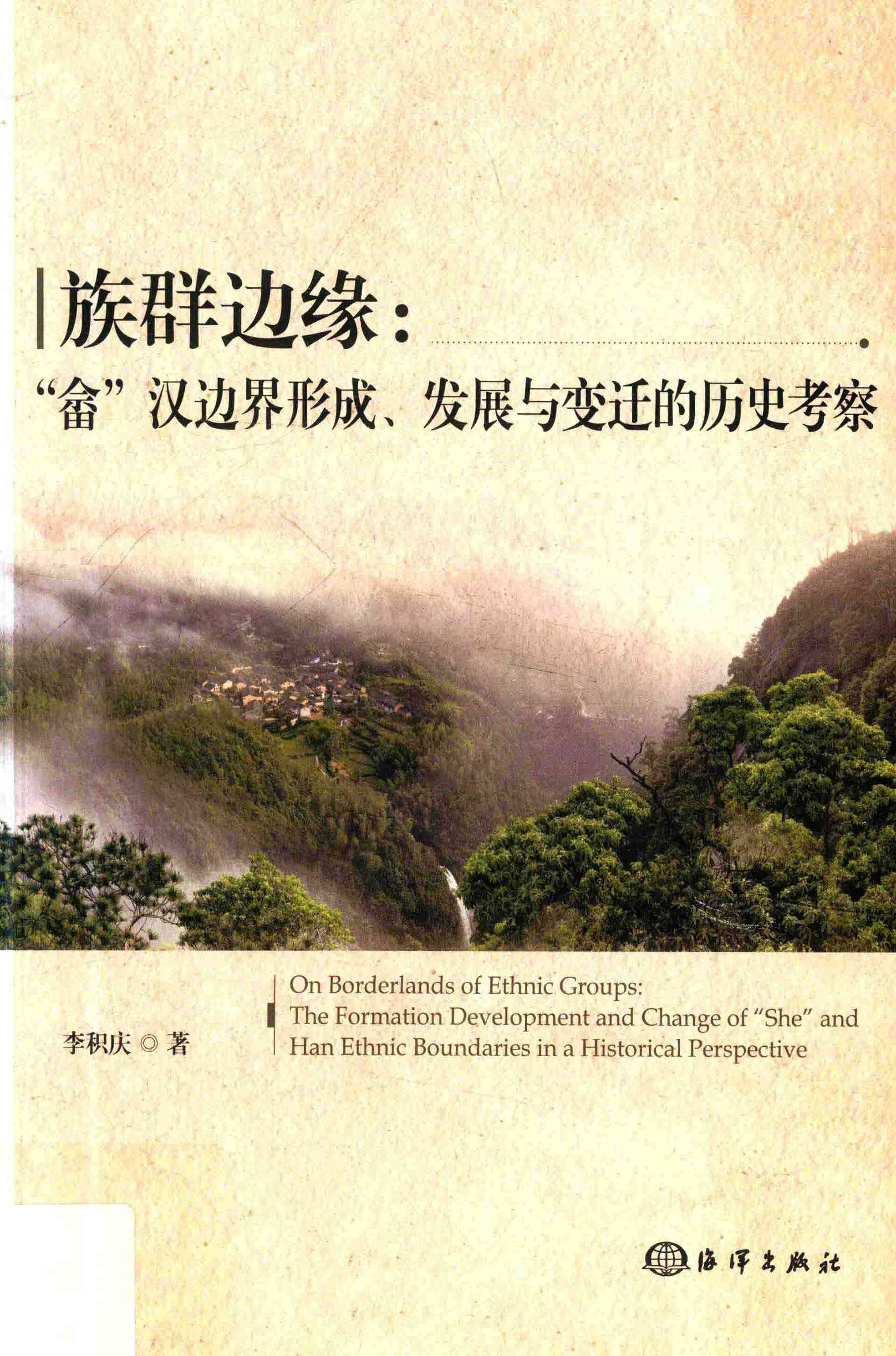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出版者:海洋出版社
本书从族群边界的理论角度,重新审视畲族形成、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在承认族群客观历史文化的同时,重点研究历史上“他者”(主要是汉族)对“畲”的社会定义以及“自者”(主要为南方非汉族群)自我族群认同的过程,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现实意义。
阅读
相关地名
宁德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