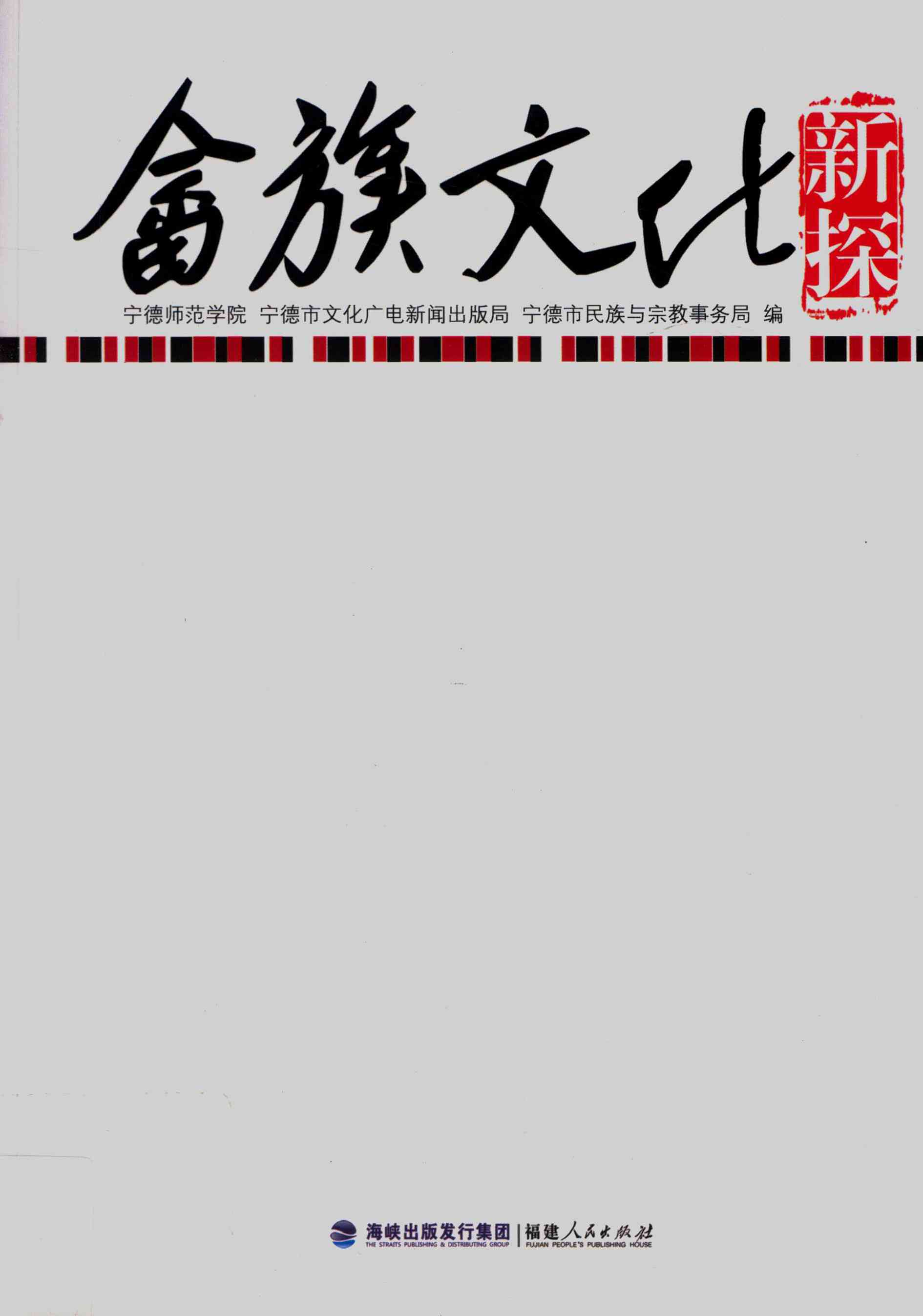内容
作为素有撰史传统的国度,传统知识精英在很早以前就非常关注生活于其周边的“异己”人群。畲民作为唐宋以来中国东南颇为独特的人群,其习俗、信仰、劳作方式等都备受时人关注。关于畲民的记载,自宋、元至明、清屡见不鲜。然而时间越往后,关于畲民的记载也变得越是淡化,或是承袭旧说,或作无从考证之叹。及至如今,闽粤赣毗邻地区,人们很难从日常生活中立刻分辨出畲与汉。这是由于这个曾经明显异于汉文化的人群渐渐“化为土著”,而这个过程事实上也是双向的,而非仅仅单向进行,畲汉的融合也有多条途径可达,这其中既有畲的汉化,也有汉的畲化。
一、作为“异己”的书写——文献记载中所见之畲民
活跃于中国东南的土著人群,早者有山都木客之说,或作兽类,或作鬼类,皆为异己记载之开端。但因其去向不明,后人亦只作“姑妄”之说。而畲民的记载,则自宋、元以来,及至明、清、民国,皆有连续见证。自南宋刘克庄《漳州谕畲》一文明确提出畲民名称,畲民便作为一个有别于华夏之人群见诸笔端,作为猎奇也好,作为华夷之防也好,甚至于作为“与齐民无别”的强调也好,其实皆反映出畲民作为“异己”的存在与汉族知识精英的看法。
检视现存史料,南宋刘克庄之《漳州谕畲》是最早明确提出“畲民”称呼的。在该文中,我们可知漳州之畲民分为西畲、南畲两种,“凡溪洞种类不一,曰蛮、曰猺、曰黎、曰蜑,在漳者曰畲。西畲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他们有自已独特的劳作方式,通行刀耕火种,以狩猎为生,不事赋役,“二畲皆刀耕火耘,厓栖谷汲,如猱升鼠伏,有国者以不治治之。畲民不悦,畲田不税,其来久矣”。且有自己集团独特的祖先崇拜,即崇拜盘瓠,“余读诸畲款状,有自称盘护孙者”。①
在刘克庄之后,关于畲民的记载不绝于书,其中尤多见于地方志。作为具官方色彩的地方志书,普遍地将畲民问题纳入到视野中,在广东多见于惠潮二府,如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所修之《惠州府志》有详细记载:“其在惠者俱来自别境,椎结跣足,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它徙。粤人以山林中结竹木障覆居息为,故称猺,所止曰。……其姓为盘、蓝、雷、钟、苟,自相婚姻,土人与邻者亦不与通婚。猺有长有丁,国初设抚猺土官领之,俾略输山赋,赋论刀为准,羁糜而已。又之稍稍听征调,长枪劲弩,时亦效功,然此猺颇驯伏,下山见耆老士人皆拜俯,知礼敬云。”②
在记载中,畲字亦作“畬、”书写,畲人又称猺人。在此,人们可清楚地知道畲民刀耕火种,善于射猎,以采集为生活的辅助,食尽一山则迁徙,祭祀盘瓠,与汉族人不通婚姻。即便有所谓输山赋,亦只是象征性的。在此我们可大胆地猜测,作者对于畲民自相婚姻的强调,一方面是作为畲民习俗的介绍,而更深层次似乎是在将畲民与汉族人作血统上的区别。而以上引文中所涉及的基本要素在别处记载中也时常可见。
如潮州府的畲民就极相似,“其曰户者,男女皆椎发跣足,依山而居,迁徙无常,刀耕火种,不供赋役,善射猎,以毒药涂弩矢,中兽立毙”③。
他们有两个种类,“潮州府,民有山,曰猺獞,其种有二,曰平鬃,曰崎鬃。姓有三,曰盘曰蓝曰雷。依山而居,采猎而食,不冠不履,三姓自为婚,有病殁则并焚其室庐而徙居焉。俗有类于夷狄,籍隶县治,岁纳皮张,旧态无所考,我朝设土官以治之,衔曰官”①。畲民的这些特征与前文记载皆大同小异,在程式化的描述之余,其简短的评论——“俗有类于夷狄”却让我们窥见汉人知识精英所流露出的华夷之别。
而更为甚者,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所修的《兴宁县志》则从祖源上将其与汉族人作了“明确”区分。将“猺人”祖图所言之图腾传说作为信史解读,以污名手段将其与汉族人决裂。认为畲人与汉族人祖源不同,血统不同,言语不同,甚至于劳作方式也不同。“猺人亦多种,传记多载。余尝得其世出图观之,大抵祖槃瓠,亦有次第……然散处南粤,在在皆有之,大抵依聚山林,斫树为。”②
也许是见了不少诸如此类的记载,一些汉族人开始反省前人对畲民的描述。崇祯《兴宁县志》的修纂者或许是意识到自己有责任为“王化”作些什么,于是在论及“徭疍”时,表现得颇为语惊四座。“按吴志名徭疍曰夷狄,令人愕然。求其说而不得。此非山戎氐羌之比,错居中土,衣冠与世同,无复椎结之习,一耕于山,山有粮,一渔河,河有课。既籍其名于版,子孙数十世势能徙居塞外矣乎?出入同乡井,又能区分限域矣乎?王者无外,听其蠉飞蠕动于穹环之间,亦齐民矣。已恶得而狄之。”③
然而,所需强调者,往往亦是存在危机者。纂修者这一用心良苦的强调,更明确地反映当时汉族人将畲民“狄化”之普遍。
非但知识精英如此,与畲民毗临而居的下层百姓亦无例外地“异化”畲民。
范绍质撰写于清初的《猺民纪略》对福建畲民的状况作了详细的交代。从记载中我们可知,作为普通百姓的“乡人”与畲民之间有明显的族群界线,乡人有专门对这一群人的称呼,即“畲客”,其独特的生活劳作方式也作为族群的外显标识为汉族人知识精英所一再强调。“汀东南百余里有猺民焉,结庐山谷,诛茅为瓦,编竹为篱,伐荻为户牖,临清溪,棲茂树,阴翳蓊郁,宵然深曲。其男子不巾帽,短衫阔袖,椎髻跣足,黎而青眼,长身猿臂,声哑哑如鸟,乡人呼其名曰畲客。”①
而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修纂的《福州府志》中所引《连江县志》,我们同样可看到的是,在汉族人视其为“异种”的同时,畲民对于“我者”与“他者”亦有明确区分,这从其对汉族人的称呼上可一目了然。“连深山中有异种者曰畲民……其民短衫跣足,妇人高髻,蒙布加饰如璎珞状,亦跣而杂作。以其远近为伍,性多淳朴,亦受民田以耕,谓平民曰百姓。”②
江西兴国的畲民则被人们称为“山野子”,并被邻郡之汉族人讥笑为“异类”。
“太平乡崇贤里有山民户。……号为‘山野子’,其人多雷、蓝、毕三姓……邻郡皆哂兴邑山民为异类,与徭僮狼黎比。”③
作为“异类”的畲民即便与汉族人有少量的接触,也是不受礼敬的。“福建、江西、广东深山中有畲民,同于猺獞,不与平民相接。有作工于民家者,食之阶石,不以人礼待之。”④
因此,无论是汉族人知识精英也好,平民百姓也好,皆把畲民视为有别于己的“异类”,这一现象是广泛存在于历史上的,甚至是把其作为低自己一等的人群存在的。
从历史上看,中国东南这片地区历史上确曾生活着一批与汉族人迥异的人群。在长期的生活中,他们形成了明显有别于当地汉族人的劳作方式,日常习俗,乃至信仰。随着山区的开发,这些与汉族人有如此殊别的人群与汉族人何以相安无事,他们又为何渐渐消失于人们的视线?“迁徙论”是不是足以解释这些问题?这就是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
二、“异己”的消失——明清时期畲汉融合
随着山区的日益开发和人群的日渐交融,畲民慢慢的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那些早期对畲民的记载渐渐地变成一种奇异的印象,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甚至已从人们记忆中消失。而所谓的消失,并非指这一人群事实上的消亡,而是指曾经作为指认该人群明显异于汉族人的外显标识的消融。
对于明显有别于汉族人的畲民去向何处,当时人多认为是其皆化为土著。
从万历时所修《广东通志》中已见端倪:“畲蛮,岭海随在皆有之,以刀耕火种为名者也,衣服言语渐同齐民。”①
而修于康熙年间(1662—1722年)的《平和县志》对此给出了较详细的答案:“今则太平既入,声教日讫,和邑诸山木拔道通,瑶僮安在哉?盖传流渐远,言语相通,饮食衣服起居往来多与人同,瑶僮而化为齐民,亦相与忘其所自来矣。”②
光绪温仲和所修之《嘉应州志》所言亦同,“今地以畲名者尚多有之,而所谓猺獠则绝无其人,盖日久皆化为熟户,而风俗与居民无异矣”③。
民国的闽西畲民与汉族人也无从分辨,“今则男子衣帽、发辫如乡人……虽峒瑶有亦无异于乡里中编氓也”④。
更为甚者,那些曾经作为人们谈资的畲民故事也无人再提起,如民国郑丰稔所言:“余在儿童时代,蓝雷故事,尚为童话中之时行材料,今则未闻有谈及者,盖式微矣。”⑤
此外,从修纂于不同年代的五个版本的兴宁地方志中我们可梳理出畲民与汉族人融合的大概历程。
修纂于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的《兴宁县志》载:“瑶之属颇多,大抵聚处山林,斫树为,刀耕火种,采山猎食,嗜欲不类,语言不通,土人与之邻者不相往来,不为婚姻。本县瑶民亦众,随山散处,岁输山粮七石正。”①就如我们上面已谈及的,类似的记载在当时还可找出很多。如果没错,这段记载至少反映了明中前期畲民的基本状况,或者至少反映了当时知识精英的一种普遍的记忆。
而时隔几十年后,修纂于嘉靖年间(1522—1566年)的《兴宁县志》则添加了一些内容:“猺人亦多种,传记多载。余尝得其世出图观之,大抵祖槃瓠,亦有次第……然散处南粤,在在皆有之,大抵依聚山林,斫树为。”②以上添加的这些内容为作者所见,无论其表述背后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这时,人们对畲民还并不陌生。
然而,这种印象也就此停留在人们的意象之中了,约在百年之后所修的《兴宁县志》,就明确表示以前并不陌生的这群畲民皆化为土著了。“徭本盘瓠之种,亦有次第……散处南粤,在在有之。大抵依聚山林,斫树为,刀耕火种,采实猎毛,嗜欲言语不同土人,与之邻者亦不为婚姻。随山散处,岁输出粮,事同羁縻而已。……今皆化为土著。”③
再时隔约半个世纪,重修的《兴宁县志》在述及畲民皆化为土著时所作的按语中,更发出前事无从考的概叹:“宁赋有徭人山米,即徭僮之岁输山粮也。然久无。徭人输糠者,据前志云今皆化为土著,独不记其何年始将山米并归民粮,其化为土著亦不记其承籍与否,卒不可考,一阙事也。”④由此可知,此时人们对畲民之印象全靠前人所记,无此,便无从知晓了。
及至清末,兴宁学者罗献所修之《兴宁乡土志》再一次表明:“猺之别种曰畲,刀耕火种,采实猎毛……种族泯灭,不可考耳。”⑤
在此,百年、半个世纪并不能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时段来探讨,百年或半个世纪并不反映当时人们对畲民的意象变化的实际时间。但其所表现的时序先后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所反映的正是时间上继替与人们认识间的变化。故而,在此,时间序列的“先后”变得格外重要。也正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从《兴宁县志》的时序中窥见人们意象的变化。
但是,如果仅从正史或地方志等文来探讨的话,以上所反映的现象确实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汉族人知识精英的这种记忆所持续的时间也有长期的延续性。但这却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畲汉融合只是单纯的畲融于汉的过程。事实上,不同人群的融合绝非以单线进行,当我们转而关注畲民自身的叙事时,我们发现,问题远不止这么简单。或者说,所谓的“化为土著”远不是一句话就可以概括的。畲民与汉族人的交流与混化有多种途径可达,他们的融合也是双向的,生活于民间的人们有他们自己的运作模式与方法。
三、历史上畲汉融合的几种途径
两种界线分明的人群何以混化至无分彼此,其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人群间的日常交往了,比如日常生活、经济的往来。而对于特殊的历史时期而言,还包括共同抵抗外来势力所导致的合作。
畲民虽主要以耕山游猎为生,但亦有不得不与汉族人发生接触时。“大抵瑶抵峒皆依山负险,性情鲁莽,与良颇异,然衣食器皿悉取给于近县村落。”①因此,畲民也常入市贸易。“入市贸布易丝,率俯首不敢睥睨”②。道光《建阳县志》也说明畲民“与汉人交接历有年”③。这一接触的过程本身就是双向的流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经济的日益依赖,文化与习俗亦日渐互染。
与此同时,在时局动荡的年代,畲民与汉族人之间的界线时时飘移,许多汉族人也逃入畲民之中,以求庇佑。如南宋时的赵必岊,字次山,“乡寓公吴允文浚奉密诏以江西招讨使举义反正,结约次山协谋兴复,战不利。允文奔漳州为都督文丞相天祥所杀,次山解兵隐汀州之畬中,踰年以疾终”①。
这一方面固然因为战争或动乱等原因,同时也是由于畲民不赋不役的诱惑,使众多汉族人隐于畲中。如明代江西“吉安府龙泉、万安、泰和三县并南安府所属大庾等三县居民无籍者,往往携带妻女,入为盗”②。而清朝广东潮州府则有“雷公岭……层冈叠嶂,为潮惠二县之界,奸民逋赋役者,辄藉口邻封,彼此窜避,或托为猺獞逃化外”③。
其次,血缘上的混化是最直接的方式。
畲民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群之所以成为可能,其最主要的原因即在于他们不与汉族人通婚,从血统上保持其内部的独立性与稳定性。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畲民亦与汉族人互相通婚。在这方面,郭志超先生打破传统研究的樊篱,利用畲民族谱资料作了专门论述,认为在历史上其实存在不少畲民与汉族人通婚的情况,导致人们误以为畲族只与本族通婚的原因是,那些方志、文集的作者没有将汉化较高的定居畲民包括在畲民里。④此外,我们也可从地方志所见,在乾隆年间(1736—1795年)畲民已开始和汉族人通婚。“邑有畲民……近又与土民联婚,并改其焚尸浮葬之习,亦足见一道同风之化云”⑤。从晚清建阳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出,畲民与汉族人通婚,多遵汉族人习俗。“近唯嘉和一带畲民,半染华风。欲与汉人为婚,则先为其幼女缠足,稍长,令学针黹坐闺中,不与习农事,奁资亦略如华人。”⑥
在通婚方面,族谱的记载应是较可靠细致的材料,而方志记载的重要性在于,它所反映的是当时较为流行与普遍的一种行为。
相对于通婚,收养则是另一条血统混化的途径。下面的一段记载就是平和何仓蓝氏畲民收养汉族人何氏之子,这是对畲汉血统混化的一个很好的诠释。
平和蓝氏入漳始祖蓝琛曾仕元,元亡之际,从江西避乱至漳。蓝琛公五世孙源泰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迁居平和县南胜何仓,为开基何仓一世祖,汉族人何姓彦璋公出嗣源泰公为子,为二世祖。“添河公三子彦璋公出嗣何仓蓝家,为蓝源泰之子,后裔为蓝氏。”①但事实上,根据何仓蓝木龙所提供的资料表明,彦璋公后裔也有返归汉族人何氏家族的。
“彦璋公配蔡氏,生七子。文琛、文其、文清、文生、文乐、文林、文树。文琛、文清、文乐后裔居何仓;文其后裔居漳浦大南坂;文生、文林后裔居平和县山格镇,文树返归何氏,居何地何空楼。”②
谱中所提到的何仓今作禾仓,上面的这一记载收录于福建云霄、平和《何氏族谱》中。而彦璋公后裔分布简况的资料则由何仓蓝木龙提供。历史上,这种畲民收养汉族人的例子虽不常见,但在民间实际上也还是存在的。而且,在畲民作为一个独立民族被识别后的今天,这样的例子也是屡见不鲜。③
最后,作为外力之国家在这一融合过程中起了巨大作用。
明朝闽粤赣边区新县的大量设置及国家教化的推行使畲民归于王化。由唐以来,闽粤赣边区就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盐寇”、“峒寇”、流民等时时引发动乱,作为国家触角未深入之地,族群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而历史上随山散处的畲民也是构成地方板荡的一股力量。不仅畲民、流寇,当地民人也会身不由已地卷入斗争中,这将使事态更为严重。南赣巡抚就是为处理闽粤赣湘交界地区事务而设。在南赣巡抚设置前后,闽粤赣交界区共设新县达22个之多,其中4县为南赣巡抚设置前所添。①经过这一规模浩大的新县设置,闽粤赣交界地区人民活动直接为王朝所控制,昔日的“盗区”变成国家统治下的“政区”。
随着县治的建立,政府也积极地推行国家教化,对畲民也进行编保甲,把畲民纳入国家主流文化体系。这在许多方志里都有体现,如道光《龙岩州志》中记载:“今畲客固安分,许其编甲完粮,视土著之民一例。”②民国《德化县志》也说入清后,畲民“遂编保甲,从力役,视平民无别”③。
族群最本质的内容即是有一个异己的对立面的存的,通过对比反观自己有别于他者,当自己与这种参照物渐渐趋同时,文化的界线与族群的界线也就慢慢消失。当然,上引史料也反映了汉族人知识精英过于简化的表达,在他们眼中,王朝的力量大于一切,因为这种对王朝力量的无限放大,导致他们看不到更多复杂的历史过程,那些存在于民间的互动过程。
对于众多汉族人知识分子来说,对于“异己”的记载,一方面固然出于好奇之心,将畲民视为一个异己人群,将其奇风异俗作为一种谈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汉族人知识精英历来所具有的为王朝统治服务的思想,记载这些畲民,是为了便于统治者更好地对其进行统治。因为有如此重要的“使命”,只要有“异己”的存在,便有关于“异己”的书写。而随着日益的交流与接触,当“异己”群体不再有明显的可认之处时,便没有太多强调的必要。因而渐渐作为“拾遗”来书写,将其视为宣扬王化的见证。这一表达明显的体现在“化为土著、与齐民无别”这一说法上。然而事实上,随着地区的开发与国家的直接进入,即使是像畲民这样“自相为婚,不与齐民往来”的人群,也最终难免与汉族人融合。畲汉的这种融合途径是多样的,也是畲汉双向的,其中既有通婚、收养等血缘上的混化,也有互相隐匿的地缘上的融合,更有国家等外力作用下的推进,因此历史上既存在畲融于汉的可能,也有汉融于畲的可能。而畲汉这种跨民族融合所形成的独特文化,也是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重要原因。
一、作为“异己”的书写——文献记载中所见之畲民
活跃于中国东南的土著人群,早者有山都木客之说,或作兽类,或作鬼类,皆为异己记载之开端。但因其去向不明,后人亦只作“姑妄”之说。而畲民的记载,则自宋、元以来,及至明、清、民国,皆有连续见证。自南宋刘克庄《漳州谕畲》一文明确提出畲民名称,畲民便作为一个有别于华夏之人群见诸笔端,作为猎奇也好,作为华夷之防也好,甚至于作为“与齐民无别”的强调也好,其实皆反映出畲民作为“异己”的存在与汉族知识精英的看法。
检视现存史料,南宋刘克庄之《漳州谕畲》是最早明确提出“畲民”称呼的。在该文中,我们可知漳州之畲民分为西畲、南畲两种,“凡溪洞种类不一,曰蛮、曰猺、曰黎、曰蜑,在漳者曰畲。西畲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他们有自已独特的劳作方式,通行刀耕火种,以狩猎为生,不事赋役,“二畲皆刀耕火耘,厓栖谷汲,如猱升鼠伏,有国者以不治治之。畲民不悦,畲田不税,其来久矣”。且有自己集团独特的祖先崇拜,即崇拜盘瓠,“余读诸畲款状,有自称盘护孙者”。①
在刘克庄之后,关于畲民的记载不绝于书,其中尤多见于地方志。作为具官方色彩的地方志书,普遍地将畲民问题纳入到视野中,在广东多见于惠潮二府,如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所修之《惠州府志》有详细记载:“其在惠者俱来自别境,椎结跣足,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它徙。粤人以山林中结竹木障覆居息为,故称猺,所止曰。……其姓为盘、蓝、雷、钟、苟,自相婚姻,土人与邻者亦不与通婚。猺有长有丁,国初设抚猺土官领之,俾略输山赋,赋论刀为准,羁糜而已。又之稍稍听征调,长枪劲弩,时亦效功,然此猺颇驯伏,下山见耆老士人皆拜俯,知礼敬云。”②
在记载中,畲字亦作“畬、”书写,畲人又称猺人。在此,人们可清楚地知道畲民刀耕火种,善于射猎,以采集为生活的辅助,食尽一山则迁徙,祭祀盘瓠,与汉族人不通婚姻。即便有所谓输山赋,亦只是象征性的。在此我们可大胆地猜测,作者对于畲民自相婚姻的强调,一方面是作为畲民习俗的介绍,而更深层次似乎是在将畲民与汉族人作血统上的区别。而以上引文中所涉及的基本要素在别处记载中也时常可见。
如潮州府的畲民就极相似,“其曰户者,男女皆椎发跣足,依山而居,迁徙无常,刀耕火种,不供赋役,善射猎,以毒药涂弩矢,中兽立毙”③。
他们有两个种类,“潮州府,民有山,曰猺獞,其种有二,曰平鬃,曰崎鬃。姓有三,曰盘曰蓝曰雷。依山而居,采猎而食,不冠不履,三姓自为婚,有病殁则并焚其室庐而徙居焉。俗有类于夷狄,籍隶县治,岁纳皮张,旧态无所考,我朝设土官以治之,衔曰官”①。畲民的这些特征与前文记载皆大同小异,在程式化的描述之余,其简短的评论——“俗有类于夷狄”却让我们窥见汉人知识精英所流露出的华夷之别。
而更为甚者,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所修的《兴宁县志》则从祖源上将其与汉族人作了“明确”区分。将“猺人”祖图所言之图腾传说作为信史解读,以污名手段将其与汉族人决裂。认为畲人与汉族人祖源不同,血统不同,言语不同,甚至于劳作方式也不同。“猺人亦多种,传记多载。余尝得其世出图观之,大抵祖槃瓠,亦有次第……然散处南粤,在在皆有之,大抵依聚山林,斫树为。”②
也许是见了不少诸如此类的记载,一些汉族人开始反省前人对畲民的描述。崇祯《兴宁县志》的修纂者或许是意识到自己有责任为“王化”作些什么,于是在论及“徭疍”时,表现得颇为语惊四座。“按吴志名徭疍曰夷狄,令人愕然。求其说而不得。此非山戎氐羌之比,错居中土,衣冠与世同,无复椎结之习,一耕于山,山有粮,一渔河,河有课。既籍其名于版,子孙数十世势能徙居塞外矣乎?出入同乡井,又能区分限域矣乎?王者无外,听其蠉飞蠕动于穹环之间,亦齐民矣。已恶得而狄之。”③
然而,所需强调者,往往亦是存在危机者。纂修者这一用心良苦的强调,更明确地反映当时汉族人将畲民“狄化”之普遍。
非但知识精英如此,与畲民毗临而居的下层百姓亦无例外地“异化”畲民。
范绍质撰写于清初的《猺民纪略》对福建畲民的状况作了详细的交代。从记载中我们可知,作为普通百姓的“乡人”与畲民之间有明显的族群界线,乡人有专门对这一群人的称呼,即“畲客”,其独特的生活劳作方式也作为族群的外显标识为汉族人知识精英所一再强调。“汀东南百余里有猺民焉,结庐山谷,诛茅为瓦,编竹为篱,伐荻为户牖,临清溪,棲茂树,阴翳蓊郁,宵然深曲。其男子不巾帽,短衫阔袖,椎髻跣足,黎而青眼,长身猿臂,声哑哑如鸟,乡人呼其名曰畲客。”①
而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修纂的《福州府志》中所引《连江县志》,我们同样可看到的是,在汉族人视其为“异种”的同时,畲民对于“我者”与“他者”亦有明确区分,这从其对汉族人的称呼上可一目了然。“连深山中有异种者曰畲民……其民短衫跣足,妇人高髻,蒙布加饰如璎珞状,亦跣而杂作。以其远近为伍,性多淳朴,亦受民田以耕,谓平民曰百姓。”②
江西兴国的畲民则被人们称为“山野子”,并被邻郡之汉族人讥笑为“异类”。
“太平乡崇贤里有山民户。……号为‘山野子’,其人多雷、蓝、毕三姓……邻郡皆哂兴邑山民为异类,与徭僮狼黎比。”③
作为“异类”的畲民即便与汉族人有少量的接触,也是不受礼敬的。“福建、江西、广东深山中有畲民,同于猺獞,不与平民相接。有作工于民家者,食之阶石,不以人礼待之。”④
因此,无论是汉族人知识精英也好,平民百姓也好,皆把畲民视为有别于己的“异类”,这一现象是广泛存在于历史上的,甚至是把其作为低自己一等的人群存在的。
从历史上看,中国东南这片地区历史上确曾生活着一批与汉族人迥异的人群。在长期的生活中,他们形成了明显有别于当地汉族人的劳作方式,日常习俗,乃至信仰。随着山区的开发,这些与汉族人有如此殊别的人群与汉族人何以相安无事,他们又为何渐渐消失于人们的视线?“迁徙论”是不是足以解释这些问题?这就是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
二、“异己”的消失——明清时期畲汉融合
随着山区的日益开发和人群的日渐交融,畲民慢慢的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那些早期对畲民的记载渐渐地变成一种奇异的印象,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甚至已从人们记忆中消失。而所谓的消失,并非指这一人群事实上的消亡,而是指曾经作为指认该人群明显异于汉族人的外显标识的消融。
对于明显有别于汉族人的畲民去向何处,当时人多认为是其皆化为土著。
从万历时所修《广东通志》中已见端倪:“畲蛮,岭海随在皆有之,以刀耕火种为名者也,衣服言语渐同齐民。”①
而修于康熙年间(1662—1722年)的《平和县志》对此给出了较详细的答案:“今则太平既入,声教日讫,和邑诸山木拔道通,瑶僮安在哉?盖传流渐远,言语相通,饮食衣服起居往来多与人同,瑶僮而化为齐民,亦相与忘其所自来矣。”②
光绪温仲和所修之《嘉应州志》所言亦同,“今地以畲名者尚多有之,而所谓猺獠则绝无其人,盖日久皆化为熟户,而风俗与居民无异矣”③。
民国的闽西畲民与汉族人也无从分辨,“今则男子衣帽、发辫如乡人……虽峒瑶有亦无异于乡里中编氓也”④。
更为甚者,那些曾经作为人们谈资的畲民故事也无人再提起,如民国郑丰稔所言:“余在儿童时代,蓝雷故事,尚为童话中之时行材料,今则未闻有谈及者,盖式微矣。”⑤
此外,从修纂于不同年代的五个版本的兴宁地方志中我们可梳理出畲民与汉族人融合的大概历程。
修纂于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的《兴宁县志》载:“瑶之属颇多,大抵聚处山林,斫树为,刀耕火种,采山猎食,嗜欲不类,语言不通,土人与之邻者不相往来,不为婚姻。本县瑶民亦众,随山散处,岁输山粮七石正。”①就如我们上面已谈及的,类似的记载在当时还可找出很多。如果没错,这段记载至少反映了明中前期畲民的基本状况,或者至少反映了当时知识精英的一种普遍的记忆。
而时隔几十年后,修纂于嘉靖年间(1522—1566年)的《兴宁县志》则添加了一些内容:“猺人亦多种,传记多载。余尝得其世出图观之,大抵祖槃瓠,亦有次第……然散处南粤,在在皆有之,大抵依聚山林,斫树为。”②以上添加的这些内容为作者所见,无论其表述背后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这时,人们对畲民还并不陌生。
然而,这种印象也就此停留在人们的意象之中了,约在百年之后所修的《兴宁县志》,就明确表示以前并不陌生的这群畲民皆化为土著了。“徭本盘瓠之种,亦有次第……散处南粤,在在有之。大抵依聚山林,斫树为,刀耕火种,采实猎毛,嗜欲言语不同土人,与之邻者亦不为婚姻。随山散处,岁输出粮,事同羁縻而已。……今皆化为土著。”③
再时隔约半个世纪,重修的《兴宁县志》在述及畲民皆化为土著时所作的按语中,更发出前事无从考的概叹:“宁赋有徭人山米,即徭僮之岁输山粮也。然久无。徭人输糠者,据前志云今皆化为土著,独不记其何年始将山米并归民粮,其化为土著亦不记其承籍与否,卒不可考,一阙事也。”④由此可知,此时人们对畲民之印象全靠前人所记,无此,便无从知晓了。
及至清末,兴宁学者罗献所修之《兴宁乡土志》再一次表明:“猺之别种曰畲,刀耕火种,采实猎毛……种族泯灭,不可考耳。”⑤
在此,百年、半个世纪并不能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时段来探讨,百年或半个世纪并不反映当时人们对畲民的意象变化的实际时间。但其所表现的时序先后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所反映的正是时间上继替与人们认识间的变化。故而,在此,时间序列的“先后”变得格外重要。也正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从《兴宁县志》的时序中窥见人们意象的变化。
但是,如果仅从正史或地方志等文来探讨的话,以上所反映的现象确实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汉族人知识精英的这种记忆所持续的时间也有长期的延续性。但这却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畲汉融合只是单纯的畲融于汉的过程。事实上,不同人群的融合绝非以单线进行,当我们转而关注畲民自身的叙事时,我们发现,问题远不止这么简单。或者说,所谓的“化为土著”远不是一句话就可以概括的。畲民与汉族人的交流与混化有多种途径可达,他们的融合也是双向的,生活于民间的人们有他们自己的运作模式与方法。
三、历史上畲汉融合的几种途径
两种界线分明的人群何以混化至无分彼此,其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人群间的日常交往了,比如日常生活、经济的往来。而对于特殊的历史时期而言,还包括共同抵抗外来势力所导致的合作。
畲民虽主要以耕山游猎为生,但亦有不得不与汉族人发生接触时。“大抵瑶抵峒皆依山负险,性情鲁莽,与良颇异,然衣食器皿悉取给于近县村落。”①因此,畲民也常入市贸易。“入市贸布易丝,率俯首不敢睥睨”②。道光《建阳县志》也说明畲民“与汉人交接历有年”③。这一接触的过程本身就是双向的流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经济的日益依赖,文化与习俗亦日渐互染。
与此同时,在时局动荡的年代,畲民与汉族人之间的界线时时飘移,许多汉族人也逃入畲民之中,以求庇佑。如南宋时的赵必岊,字次山,“乡寓公吴允文浚奉密诏以江西招讨使举义反正,结约次山协谋兴复,战不利。允文奔漳州为都督文丞相天祥所杀,次山解兵隐汀州之畬中,踰年以疾终”①。
这一方面固然因为战争或动乱等原因,同时也是由于畲民不赋不役的诱惑,使众多汉族人隐于畲中。如明代江西“吉安府龙泉、万安、泰和三县并南安府所属大庾等三县居民无籍者,往往携带妻女,入为盗”②。而清朝广东潮州府则有“雷公岭……层冈叠嶂,为潮惠二县之界,奸民逋赋役者,辄藉口邻封,彼此窜避,或托为猺獞逃化外”③。
其次,血缘上的混化是最直接的方式。
畲民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群之所以成为可能,其最主要的原因即在于他们不与汉族人通婚,从血统上保持其内部的独立性与稳定性。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畲民亦与汉族人互相通婚。在这方面,郭志超先生打破传统研究的樊篱,利用畲民族谱资料作了专门论述,认为在历史上其实存在不少畲民与汉族人通婚的情况,导致人们误以为畲族只与本族通婚的原因是,那些方志、文集的作者没有将汉化较高的定居畲民包括在畲民里。④此外,我们也可从地方志所见,在乾隆年间(1736—1795年)畲民已开始和汉族人通婚。“邑有畲民……近又与土民联婚,并改其焚尸浮葬之习,亦足见一道同风之化云”⑤。从晚清建阳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出,畲民与汉族人通婚,多遵汉族人习俗。“近唯嘉和一带畲民,半染华风。欲与汉人为婚,则先为其幼女缠足,稍长,令学针黹坐闺中,不与习农事,奁资亦略如华人。”⑥
在通婚方面,族谱的记载应是较可靠细致的材料,而方志记载的重要性在于,它所反映的是当时较为流行与普遍的一种行为。
相对于通婚,收养则是另一条血统混化的途径。下面的一段记载就是平和何仓蓝氏畲民收养汉族人何氏之子,这是对畲汉血统混化的一个很好的诠释。
平和蓝氏入漳始祖蓝琛曾仕元,元亡之际,从江西避乱至漳。蓝琛公五世孙源泰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迁居平和县南胜何仓,为开基何仓一世祖,汉族人何姓彦璋公出嗣源泰公为子,为二世祖。“添河公三子彦璋公出嗣何仓蓝家,为蓝源泰之子,后裔为蓝氏。”①但事实上,根据何仓蓝木龙所提供的资料表明,彦璋公后裔也有返归汉族人何氏家族的。
“彦璋公配蔡氏,生七子。文琛、文其、文清、文生、文乐、文林、文树。文琛、文清、文乐后裔居何仓;文其后裔居漳浦大南坂;文生、文林后裔居平和县山格镇,文树返归何氏,居何地何空楼。”②
谱中所提到的何仓今作禾仓,上面的这一记载收录于福建云霄、平和《何氏族谱》中。而彦璋公后裔分布简况的资料则由何仓蓝木龙提供。历史上,这种畲民收养汉族人的例子虽不常见,但在民间实际上也还是存在的。而且,在畲民作为一个独立民族被识别后的今天,这样的例子也是屡见不鲜。③
最后,作为外力之国家在这一融合过程中起了巨大作用。
明朝闽粤赣边区新县的大量设置及国家教化的推行使畲民归于王化。由唐以来,闽粤赣边区就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盐寇”、“峒寇”、流民等时时引发动乱,作为国家触角未深入之地,族群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而历史上随山散处的畲民也是构成地方板荡的一股力量。不仅畲民、流寇,当地民人也会身不由已地卷入斗争中,这将使事态更为严重。南赣巡抚就是为处理闽粤赣湘交界地区事务而设。在南赣巡抚设置前后,闽粤赣交界区共设新县达22个之多,其中4县为南赣巡抚设置前所添。①经过这一规模浩大的新县设置,闽粤赣交界地区人民活动直接为王朝所控制,昔日的“盗区”变成国家统治下的“政区”。
随着县治的建立,政府也积极地推行国家教化,对畲民也进行编保甲,把畲民纳入国家主流文化体系。这在许多方志里都有体现,如道光《龙岩州志》中记载:“今畲客固安分,许其编甲完粮,视土著之民一例。”②民国《德化县志》也说入清后,畲民“遂编保甲,从力役,视平民无别”③。
族群最本质的内容即是有一个异己的对立面的存的,通过对比反观自己有别于他者,当自己与这种参照物渐渐趋同时,文化的界线与族群的界线也就慢慢消失。当然,上引史料也反映了汉族人知识精英过于简化的表达,在他们眼中,王朝的力量大于一切,因为这种对王朝力量的无限放大,导致他们看不到更多复杂的历史过程,那些存在于民间的互动过程。
对于众多汉族人知识分子来说,对于“异己”的记载,一方面固然出于好奇之心,将畲民视为一个异己人群,将其奇风异俗作为一种谈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汉族人知识精英历来所具有的为王朝统治服务的思想,记载这些畲民,是为了便于统治者更好地对其进行统治。因为有如此重要的“使命”,只要有“异己”的存在,便有关于“异己”的书写。而随着日益的交流与接触,当“异己”群体不再有明显的可认之处时,便没有太多强调的必要。因而渐渐作为“拾遗”来书写,将其视为宣扬王化的见证。这一表达明显的体现在“化为土著、与齐民无别”这一说法上。然而事实上,随着地区的开发与国家的直接进入,即使是像畲民这样“自相为婚,不与齐民往来”的人群,也最终难免与汉族人融合。畲汉的这种融合途径是多样的,也是畲汉双向的,其中既有通婚、收养等血缘上的混化,也有互相隐匿的地缘上的融合,更有国家等外力作用下的推进,因此历史上既存在畲融于汉的可能,也有汉融于畲的可能。而畲汉这种跨民族融合所形成的独特文化,也是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重要原因。
附注
①(宋)刘克庄:《后村集》卷93《记》,四部丛刊本。
②(明)姚良弼修、杨宗甫纂:《惠州府志》卷14《外志·猺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③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18《风俗·潮州》。
①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35《猺獞》。
②(明)黄国奎等篡:《兴宁县志》卷3《人事部·猺蛋》,上海书店,1990年版。
③(明)刘熙祚修、李永茂纂:《兴宁县志》卷6《杂纪·徭蛋》,中国书店1992年版。
①(清)曾日瑛等修、李绂等篡:《汀州府志》卷41《艺文》,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
②乾隆《福州府志》卷76《外纪二》。
③(清)张尚瑗纂:《潋水志林》卷17《志事·近录》,康熙五十年(1711年),2001年重印本。
④(清)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卷十五《渌水亭杂识一》,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徐乾学刻本。
①(明)郭棐纂修:《广东通志》卷70《外志五》,齐鲁书社1996年版。
②(清)吕天锦:《平和县志》卷12杂《览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
③光绪《嘉应州志》卷32《丛谈》。
④民国《长汀县志》卷35《杂录·畲客》。
⑤民国《龙岩县志》卷4《氏族》。
①正德《兴宁县志》。
②(明)黄国奎等纂:《兴宁县志》卷3《人事部·猺蛋》,上海书店1990年版。
③(明)刘熙祚修、李永茂纂:《兴宁县志》卷6《杂纪·徭蛋》,中国书店1992年版。
④(清)王纶部纂修:《兴宁县志》卷6《人物志》,中国书店1992年版。
⑤(清)罗献编:《兴宁乡土志·人类》,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抄本。
①崇祯《东莞县志·瑶》。
②(清)曾日瑛等修、李绂等篡:《汀州府志》卷41《艺文记·猺民纪略》,成文出版社。
③道光《建阳县志》卷2《舆地志·附畲民风俗》道光十二年(1832年)刊本。
①(元)刘埙:《隐居通议》卷9《诗歌四·云舍赵公诗》,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同治《南安府志》卷24《艺文七》。
③光绪《潮州府志》卷16《山川》。
④郭志超:《从谱牒资料看畲汉通婚》,《闽台民族史辨》,黄山书社2006年版,212—244页。
⑤乾隆《永春州志》,卷7《风土志》,五十二年(1787年)刊本。
⑥道光《建阳县志》卷2《舆地志·附畲民风俗》。
①云霄、平和《何氏族谱》(内部版)2005年10月17日。
②云霄、平和《何氏族谱》(内部版)2005年10月17日。
③王逍:《收养与继嗣:畲汉互动的特殊纽带》,“畲族文化研究论丛”,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8—211页。
①唐立宗:《在“盗区”与“政区”之间——明代闽粤赣湘交界的秩序变动与地方行政演化》,“国立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18),“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2年版,第367—368页。
②光绪《龙岩州志》卷20《杂记》。
③民国《德化县志》卷3《风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