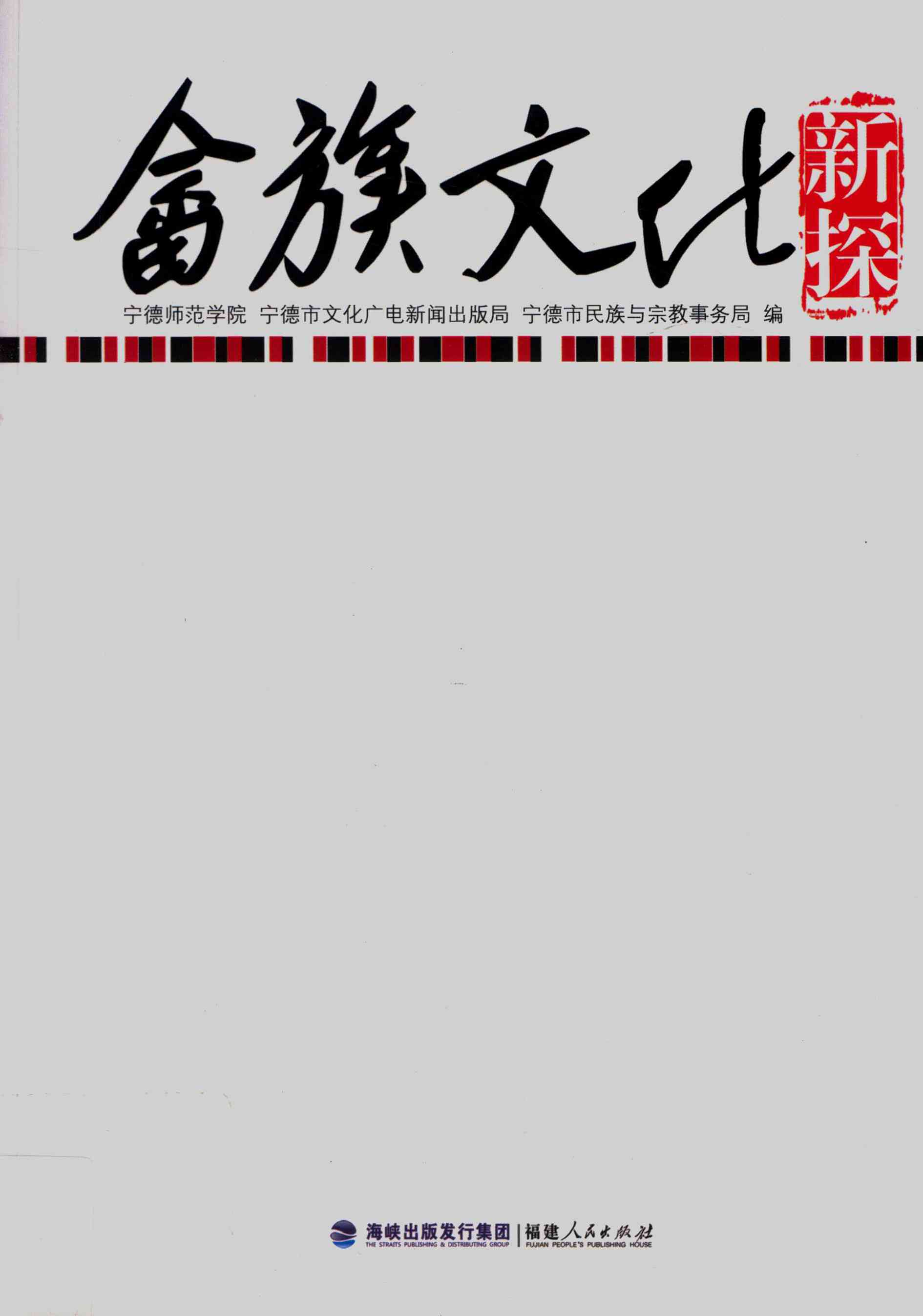内容
畲族与汉族在长期的互动交往中,形成了两个缓冲地带——汉化畲族与“畲化”汉族。我们将原本是汉族,后被畲族同化,在民族成分认定时被认定为是畲族的这批人称为汉姓畲族。为何汉族作为一个主体民族能被畲族同化,被同化后的汉族对畲族的认同情况如何?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了解到汉姓畲族在语言、服装、通婚等方面的认同情况,并结合对族谱、墓碑、石碑等资料的分析,认为通婚、生存、共同的语言是其“畲化”的主要原因并在交互起作用。在文章最后还对“畲化”与汉化、吴姓畲族与钟姓畲族、双重地位的选择三方面进行了讨论。
一、“畲化”的界定
1.族群认同理论小引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指出:“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利条件,然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径指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言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又‘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后来,费孝通先生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和阐述,他提出“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所谓民族意识,所以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①。梁启超先生和费孝通先生在他们的论述中都提到了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来说的重要性,但在两个长期通婚、关系融洽的民族之间,这种民族意识则有可能慢慢消融,共同的经济生活则成了两个民族之间的主要内容。
李济先生在《中国民族的形成》中提出,对于两个混居的民族而言,“交往一旦开始,两个民族群体之间的这种关系就只有三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群要么被同化,要么被剿灭,要么不断与入主的我群发生冲突”②。前两种意味着一个民族消弭于另一个民族之中,成为一个民族,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存在一种势力较强的文化,能将另一个民族同化或剿灭;第三种则意味着如果两个民族的势力相当,无法相互取代,陷入相互对立的局面。作者这种论述并不全面,两个民族在不断的接触过程中,还有存在第四种可能,那就是两个民族的人民都建立起对彼此的认同,两个民族长期和睦相处。
在汉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历史证明了汉族作为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核心,将周围各民族凝聚成一个整体,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在一些地方汉民族可能同化他民族,在另一些地方,其他民族也可能同化汉民族。费孝通先生就曾提到汉族融入他民族的两种情形:“一种是被迫的,有如被匈奴、西羌、突厥掳掠去的,有如被中原统治者派遣去边去屯垦的士兵、贫民或罪犯;另一种是由于天灾人祸自愿流亡去的”③。这些“移入其他民族地区的汉人很多就和当地民族通婚,并且为了适应当地社会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也会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发生改变,过若干代以后,就融合于当地民族了”④。公元399年高昌国原是一个由汉魏逃亡到这里的汉人建立的国家,后被胡化;公元866年被回鹘占领后的西州,当地汉人的后裔融合于维吾尔族;“迁居于云南洱海地区的汉人成了白族中的一个重要部分”①。这些都可以作为汉族被他民族同化的例证。
就族群认同本身而言,学术界一般有“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观点。前者强调认同是处在内在根植的天然血缘、情感的认同,个体在此获得归属感;后者强调认同是出于工具理性的考量,从现实利益、生存的角度,选择特定的认同。也有一些理论试图将两者综合。而学者王明珂则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个人或人群都经常借着改变原有的祖源记忆,来加入、接纳或脱离一个族群;造成族群边界的变迁,也就是族群认同变迁(ethnic change)”②。即族群认同存在着一定的塑造,乃至想象。处在资源竞争的情境中,族群以此选择安全、有利的族群身份。在考察族群认同时,如果我们能将血缘、生存及族群记忆三个因素结合,则能较全面地考察一个族群认同的转变过程。
2.“畲化”的界定
学术界对于“汉化”的研究文字非常之多,但对少数民族同化汉族的研究则很少。但是民族之间相互混杂,借鉴吸收各自文化中优秀的成分是自然发生的,中华民族也正是经过了这样的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③。因此,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纯粹的自立于其他民族之外的民族,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模糊界限则让界定一个民族是否被另一个民族同化变成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对于畲族和汉族,他们之间存在两个缓冲地带,即“畲化”汉族与“汉化”畲族。有人认为“汉化畲族就是保持传统蓝、雷、钟姓氏,并通过姓氏来表现出民族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畲化汉族就是保持汉族姓氏,丧失汉族文化特征,同化于畲族,风俗习惯、信仰崇拜、行为方式、生产生活同于畲族。”①这里,将姓氏符号作为区分这两个群体的标志,并没有对“畲化”和“汉化”提出一个具体的标准,因此很难让人信服。
傅衣凌先生和郭志超先生都曾对畲姓的变化进行了考析。他们根据史料记载先将某个姓氏认定为是畲姓,然后再进行考察,但对于怎样才算是“畲姓”也没有一个标准。我们认为某个姓氏是畲姓的前提是这批人具有畲族特征并被认定为畲族,因此在未确定他们是否是畲族前将他们的姓氏归为畲姓进行考察则显得不够严谨。为了避免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出现歧义,在本文中我们将除了畲族传统的盘、蓝、雷、钟四大姓氏外,畲族拥有的其他姓氏都归为汉姓。
那么我们是根据什么将“汉姓”畲族认定为畲族?他们怎样才算是被“畲化”?下面我们将以虎头村为例,从三方面进行论证。
一是政府的认定。20世纪50年代政府进行民族成分认定时将虎头吴姓村民认定为畲族。当年的“民族识别”工作有四个特点:第一,当年在收集各类材料以判定群体差别是否可以定义为“民族”差别时,主要的资料是历史、语言文字、服饰习俗等基本上属于文化层面的内容;第二,行政区划和管辖边界等政治层面的内容并不是当时的重点;第三,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各群体的体质差异并不明显,所以体质差别也没有成为识别工作的主要内容;第四,在“识别”过程中,对于当地群众的愿望给予特别的重视。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虎头村吴氏被认定为畲族是双向选择的结果,他们无论是在文化层面还是在心理层面对畲族都已经建立了深深的认同感。
二是虎头村吴氏族谱、墓碑对其与畲族通婚的记载。虎头村现存四本(道光、同治、光绪、1953年)族谱,族谱里对每一代人的通婚情况大都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从族谱里可以看出吴氏世代都娶畲族女子为妻,且他们的女儿大都嫁给附近村庄的畲民。正是通过这样一代又一代的通婚,吴氏血统渐渐稀释,而畲族血统则不断增加,二者的血缘联系不断加强,通过血缘联系进而加强了文化方面对畲族的认同。在虎头村下辖的一个岔头自然村有该地开基始祖及其儿子的墓,开基始祖幸公的墓建成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其儿子的墓具体年代则已看不清。据墓碑记载,该地开基始祖娶的便是钟氏妻子,而他的儿子娶的则是雷氏妻子。这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吴氏从迁移至岔头开始便与畲族通婚,通婚历史悠久。、
三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当地村民说畲语、唱畲歌、穿畲族衣服、过畲族节日。问卷调查表明,有81.6%吴氏村民会讲畲语,有36.4%吴氏村民在家庭中讲畲语,有52.8%吴氏村民喜欢穿畲族服饰,没有村民反对畲汉通婚。这些说明,虎头吴氏畲族村民已经具备了非常明显的畲族特征,不仅他们认定自己是畲族而且附近村庄的村民也都认为这批人是畲族。
二、吴姓畲族认同现状
1.迁徙
福安吴姓畲族的始祖谱名为知几公,原籍浙江泰顺县兰溪东门外九堡大路边,于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从浙江泰顺九堡大路边村迁入福安九都社口桐湾村。①据《清同治八年延陵吴氏宗谱重修序》载:“源公迁浙江泰顺县九堡大路边,于明嘉靖间为金陵太守,后致仕归卒。又传五世至知几公,字法度,由泰顺卜筑于安邑九都桐壪,配妣彭氏生九子。长法吉,次法正,三法辛,四法显,五法清,六法生,七法东,八法传,九法德,分为九房。迨明季,遭兵燹之乱,谱牒遗忘,散处离居。而法吉、法正二公同迁安邑岭下,法辛公回泰顺梓里,法显公迁泰顺峩洋金丝岗,法清公迁澹溪,法生公迁甯德吴洞里,法东公迁后坑承天至留洋,法传公迁桐湾。迨国朝,法东公三世孙辛公兄弟二人长平公由留洋迁居溪塔墓亭,幸公由留洋而迁岔头,为岔头之开创祖也。”这里描绘了法东公及其后裔的迁徙路线大致是泰顺→九都桐湾→后坑承天→留洋,其中一支平公由留洋迁往墓亭,另一支幸公则迁往岔头,成为岔头的开基始祖。但族谱里里并没有虎头吴氏迁徙的记载,《福安畲族志》记载虎头吴氏是由岔头村迁徙而来,但据当地年逾70、曾管过吴氏族谱的吴大爷所说,虎头吴氏是从墓亭迁徙而来,可见《福安畲族志》的记载与当地的说法也有一些出入。
至于迁徙的原因,族谱里提到“迨明季,遭兵燹之乱,谱牒遗忘,散处离居”。可见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对吴氏的迁徙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当地民众之间还流行另外一种说法,说是因为当时发生水灾,知几公九个儿子分散各地,只有法东公和法传公仍留在桐湾,成为吴姓畲族始祖,其他七兄弟迁移他处,仍为汉族。也正因为这个原因,部分族谱遗失。那么吴氏究竟出于什么原因而迁徙,现在我们也难以断定,但可以明确的一点是他们都是逃难而来。
地域的变动创造了新的族群环境,环境的改变意味着文化习俗、族群关系等一系列的改变,需要对旧有的许多习俗作出改变以适应新的生存地域。吴氏迁入人口较为聚集的福安,这种改变则尤为明显。但我们也可以找到与吴姓类似的例子,如有学者研究一个李土司家族的个案中,其身份由突厥变为土族,“族群身份改变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其祖先所处的战乱频仍的时代背景,加之频繁迁徙的经历、族际接触与通婚的历史等,其所处的地域特点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①。
一般来说,迁徙意味着对迁徙地原有资源分配格局的改变,势必会遭到当地原住民不同程度的排斥。但闽东却有其特殊之处,这是一个来自不同族群的移民构成的社会,当地原有居民大多处于分散未定居状态,这也有史料为证,李济考察历史记载中的城垣数目,到公元1644年为止各省的分布情况中,福建仅为69座,而全国总记载有4478座。“在中国本部之内,只要在任何地方发现城墙,就意味着我们中国人已经以某种定居的状况存在于当地。”②说明至少在吴姓畲族迁徙至福建前后,当地依然是一个尚待开发、地域排他意识不强的区域,没有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有绝对的优越感,这无疑为吴姓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当然,城池的未建并不意味着当地是处于未开化的地区,也可能由于当地人民的开放程度和接纳程度较高。畲族非常善于吸收汉族的文化。在走访中,发现畲族本身就有诸多汉文化的因子,比如畲族的男装大抵与汉族的长袍相似,以汉字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等,其本身的存在就依托于汉文化的诸多创设,反映着畲族本身并不是封闭的,他有个自我调节的机制。畲族在吸收了汉族文化的同时又在其中加入了畲族本身的元素,最基本的核心的东西他没有变,他用这种机制来强化了族群之间的联系。我们再来看看当时中国东南的民族,“在所有的你群诸民族中,操掸语的民族是最易于吸收外来文化的。这显示在如下事实中:中国东南各地的越人,对于入境的我群很少持长久的敌视态度”①。这种对进入当地的族群采取的包容态度,有利于外来族群融入,因此东南区域也是民族关系较为复杂的一块地方。
总之,从吴姓畲族的迁徙来看,一个族群的身份变迁要成为可能,需要合适的生存空间以及可接纳他们的当地族群,二者缺一不可。
2.基于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分析
本次调查所取样本来自我们随机碰到的且愿意接受我们采访的村民。有21.6%的样本来自溪塔村,其余样本来自虎头村。虎头村有吴姓畲族217户、1083人,是调查的核心。两村样本总数为51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入户走访,选择家庭中某一家庭成员作为调查的对象。
我们是以清华的学生身份进入调查,且有村长的推荐,以及溪塔当地的大学生陪伴调查,以消除语言障碍和陌生感,保证了调查的质量和可信度。
(1)调查样本特征
在51份问卷中,雷姓有4人;钟姓有3人;蓝姓2人;陈姓汉族1人;缪姓汉族3人;谢姓畲族1人;吴姓畲族37人。即样本的主体为吴姓畲族。其中,唯一的陈姓是从相邻的乡镇嫁至钟姓畲族人家的媳妇,缪姓汉族父母也均为汉族,不会说畲语,是居住在当地的汉族人家,是没有被“畲化”的样本。谢姓畲族由于样本较小,在当地不具代表性,故不做具体分析。因此,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吴姓畲族占72.54%,四大姓畲族占17.64%,汉族占7.8%。
表一是我们调查中受访者的年龄分布,以青壮年为主,同时各个年龄段都有,可以视为当地人口年龄段的大体分布。这样,使得我们的调查有了近60年的时间跨度,可以相应分析代际之间畲化的程度以及认同比较。
在访谈中,一位年逾六旬的吴姓畲族因为小时候经常听畲族受歧视的故事,对自己的畲族身份并不很认同,他不说畲语、不穿畲服也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畲族身份。即畲族的身份对他实质是一种外在的赋与,缺少内心的认同。这可以视为“汉化”的一个例子,即是社会身份决定了他处在汉畲的中间地带,但是若从心理上选择,则倾向于文化、经济更为强势的汉族。同时,由于老者幼年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家的民族政策并未实行,少数民族弱势地位并未改观,以致他的先辈们对于族群身份并不认同,进而影响到他的观念形成,这应该也是原因之一。一位32岁的吴姓受访者遇到的情况则与此相反,他表示这个“畲族”的成分没有对他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没有受到歧视。但是他给出的理由是“也许因为我的汉族朋友比较多”。相比而言,他则被汉族所接纳,对于本民族正面的认同就多些。由此可以看出,他民族对本民族的态度不仅会影响一个民族对他民族的认同情况,也会影响一个民族对本民族的认同。
(2)语言使用情况分析
我们以四大姓畲族、汉姓畲族、汉族三个族群作为数据分析的对象,从表二中可以看出,畲语掌握程度最好的是四大姓畲族,汉姓畲族和汉族次之,从这里可以发现“畲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汉姓畲族处于中间状态。居住在畲族村落边缘的汉族也受到影响,但是相对很轻,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畲语,反映了畲语在当地依然是族群内部的交流工具。而当地方言则是三个族群掌握情况最好的语言,被作为当地交往的公共语言。普通话则是在更广阔的地域内交往、沟通的工具,往往与阅历、职业、教育程度相关。在此项数据中,汉姓畲族为普通话掌握最好的族群,在某种程度也反映其开放程度。
而表三则是在自然情境中,家庭内部语言的选择,可以更真切地反映出语言的传承与内心认同。在汉族中,家庭内部不再使用畲语,表面畲语纯粹是对外交往的工具,没有内心的认同。而畲语在四大姓畲族中使用的比例最高,且为首选语言。汉姓畲族与之相差并不大,他们由于长期与四大姓畲族通婚,家庭成员有习得畲语的环境,现在仍然有36.4%的汉姓畲族在家中用畲语交流,这使得畲语得到良好的传承,这就不单是工具理性了。但是,汉族方言仍然是汉姓畲族家庭内部交流的首选语言,畲语处于下风,似乎也可折射出当下情境中“汉化”与“畲化”的角力结果。
在访谈中有受访者说到现在畲汉已分不清,因为现在会讲畲语的未必是畲族群众,而有可能是畲家的汉族媳妇或当地长期与畲族居住在一起而会说畲语的汉族群众;不会讲畲话的未必不是畲族群众,而有可能是被汉化的畲民。以前畲族人上街做买卖会被人歧视,导致一部分家庭改用当地方言交流,而他们的儿女因长期在县城读书,失去了学习畲语最好的环境,因此他们不会讲畲语,畲语这种断裂的状态出现在新老一辈的传承中。这一方面说明畲语作为区别汉畲族群的功能在模糊,另一方面说明畲语在与当地福安话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这与畲语缺乏文字载体,只在小范围内交流也有关系,而在现代经济背景下,不同地域、文化的交往日益加深,畲语受到的地域限制则成为弱势经济地位的表征。
(3)各族群对畲族民族服装的态度
表四中,四大姓畲族有时和经常穿畲族服装的为33.3%,汉姓畲族为13.8%,而汉族则为零。从服饰上看,四大姓畲族民族服装的穿着比例也并不高。在访谈中,有一个25岁村民提到,小时候经常穿着畲服,在家、劳动、节日都穿(节日穿新衣服),原因是经济困难,畲服便于劳作。现在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穿的和汉族差不多,有官员来访时才穿。他“小时候”大致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将近20年过去了,经济社会条件都有改善,这也是畲族服装变迁的时代因素。也有村民提到,穿畲衣在以前会受到歧视,为了避免遭受偏见,选择不穿。以前穿的比较多,慢慢地男的穿的少了,女的照穿;现在经济好起来了,男女都不穿畲服了。
在现代化浪潮的席卷下,各个民族大抵都遇到类似的情境,不单是畲族。如在羌族中,羌寨里女性必须要穿本民族的服饰,而男性则不必。出门办事时,一般穿汉族人常穿的服饰。表明了服饰“它不是界定一个族群客观特征之一,而是主观上强调或掩饰族群身份的工具”①。因为民族服饰往往意味着封闭、保守。尽管这样,对民族服饰的认同并不低,四大姓畲族群众和汉姓畲族群众对畲族服装的正面态度分别为88.9%和83.3%,民族服饰在加强民族认同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4)各族群对畲汉通婚的态度
从两表来看,各族群对畲汉通婚都不持反对态度,认为畲汉都一样,抛却了民族偏见。但是实际的族群间通婚情况中,一方面四大姓畲族与畲族通婚的比例要略高于汉姓畲族,某种程度反映了其族群认同要高于汉姓畲族;另一方面,两大族群与畲族通婚都远大于和汉族通婚比例,说明汉姓畲族是在畲族的“我群”之内,畲族已真正接纳了汉姓畲族。
三、“畲化”原因分析
1.通婚
族群间通婚无疑是驱动族群融合、同化极为重要的因素。有学者指出:“族际通婚本身是一个可统计计算的客观指标,同时这个指标最集中地体现出两个族群作为整体是否真正地在相互交往中处于融合状态,即是否出现两个族群的血缘融合,因此族际通婚是衡量族群关系最重要的、总结性的指标。”①
在以家族为基本社群单位的传统时代里,通婚就成为碾平族群间隔阂的力量。虎头村吴氏当时便是一个家族迁入虎头村的,那么最初的吴姓汉族先民们是如何以通婚的形式融入当地的?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一种解释,“婚姻的关系固然是取得地缘的门路……‘外客’却并不容易娶得本地人做妻子,使他的儿女有个进入当地社区的机会。事实上大概先得有了土地,才能在血缘网中生根”②。这与先前关于迁徙中的部分分析吻合,即当地有着相对富余的生存空间,这是通婚的经济基础。
另外,在走访中,最先人们介绍吴姓时说他们祖上出过皇帝。在查看了吴氏家谱后才明白,虎头吴氏以太伯为祖先,而他们的远古祖先则是帝喾,但这已无法考证。有学者指出,“句吴王室成为太伯后裔……使他们在华夏历史记忆中找到太伯传说,以合理化自己的华夏身份。华夏在族群利益抉择下,也以‘太伯奔吴’的历史记忆来证实句吴王室的华夏身份”①。即吴氏太伯之后,可能是对历史记忆的重新建构,虎头吴氏的祖先也很有可能是这种构建的结果。从这里可以看到,即使吴姓已经被认定为畲族,但是依然在强调其祖先的正统性来彰显其血统的高贵,通过溯源暗示其与强势的中原文化的亲缘关系,这在与畲族通婚中无疑增加了被接纳的筹码。因为尽管在当地畲族村落中,畲族是处在强势有利的地位,但在更广阔的地缘文化中,畲族仍是弱势的族群。吴氏以姻亲关系建立起与周边畲族族群的往来关系,在时间的更替中,逐渐在文化表征中被畲化,但同时并未完全认同自己的畲民身份,而是保留着遥远的关于祖先血脉的乡愁。通过问卷调查我们也证实,吴氏对畲族的认同度并没有畲族传统四大姓氏对畲族的认同高。
通过对吴氏族谱的分析,我们发现吴氏世代与畲族通婚,这无疑加速了吴氏融入畲族的进程。“畲族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且还是血缘的概念。”②吴氏对畲族认同是在不断与畲族的通婚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因此这种认同更多是建立在血缘的基础上的,文化上的认同也是由这种血缘关系带来的。与畲族血缘关系的建立,使之嵌入了畲族原有族群的“差序格局”,淡化了“我群”与“你群”的界限。同时,畲族女性进入汉族的家庭内部,对子女的社会化起着关键的作用,子嗣一代对于畲族文化比之最初汉族的父辈们有着更大的亲近。于是,通过代际的传承和族际通婚的不断强化,原有汉族的血统、文化被稀释,相应地,畲族的血缘、文化在增加,并逐渐取代汉族成为主流,“畲化”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
2.生存
畲族和汉族人民当年迁移的目的都是为了谋生,因此吴氏迁居虎头村的时候,首要考虑的应该是如何在这片土地生根发芽。而虎头村附近村庄的村民都是在吴氏迁入虎头村的同一时期迁入这片地区的,相隔不远的溪塔村便是在吴氏迁入65年之后的1588年才迁入的①。
据《吴氏统谱》载“肇基祖法东公,祖居浙江平邑莒溪(今属苍南),于明嘉靖壬午(公元1523年)迁入闽省福安穆阳虎头定居,至公侯申戌,历四七二年,传一十六世”②。而最早徙居浙江泰顺的是在1575年,雷元山从平阳青街白岩村迁泰顺八都莲头金沙垟。③虎头村吴氏开基始祖的迁徙发生在畲族进入其迁出地之前,也就是说他们在迁入福安之前并没有同畲族同胞有过多交往,他们对畲族的认同是在迁入福安以后才建立起来的。那为何在刚迁入畲族地区时就会与畲族通婚呢?我们只能将其归为出于生存的考虑。由于虎头地区属偏远山区,为了更好地生存,需要畲汉人民共同努力进行开发。
畲汉人民共同的遭遇、迁徙,共同的经济生活都有利于加强彼此的认同。同时,统治者的政策也在扮演着催化剂的角色,推动畲汉关系的进一步深入。据《福安畲族志》载,自乾隆十七年(1752年)始,统治阶级的统治才渐渐触及到畲族地区,“编图隶籍”和“编甲完粮”的经济政策逐渐实行于畲族地区。④统治阶级对畲族的统治政策大都与当地汉族一样,正因为如此,使得畲、汉民族关系进一步密切,畲族社会经济生活同汉族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⑤
从畲族族谱所载,畲族迁徙多是一家一户由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因此畲族聚落一般较小,且以单姓聚居为常。⑥畲族是实行民族内婚制的,同姓一般不通婚,因此地处偏远的畲族在寻找异姓通婚时则会遇到一些困难,虎头吴氏则成了他们的一个选择,且相隔不远的吴氏与畲族通婚更有利于其共同开发这块地区,因此这是畲汉人民双向选择的结果。
以下的两个例子则与这种情况类似。“福建宁德县南岗斗村畲民在康熙年间迁到这里居住,便同当地汉族通婚,而且关系十分融洽。福鼎县伏柳乡的高厝里和蓝厝里二村,是汉族高姓和畲族蓝姓于清代迁居于此,他们共同开发了这块土地,两族之间不仅通婚,而且关系十分融洽。”①即我们在虎头族谱中见到的畲族与汉族通婚并非孤例。
两个族群的通婚也是经济往来的一种相互依附。面对超出少量人力之外的自然力,需要协作以应对。而通婚则是将相互的血脉交互,接纳进各自的谱系,插入各自的亲缘差序格局中,经济的协作就是题中之义了。这往往超越了单个民族的自闭,而是走向了合作。如同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格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乃至被归化。这种生存的双向选择使畲汉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共同的经济生活促进了民族的交往,彼此的认同也在不断的交往与合作中慢慢建立起来,而在这种互动中民族因素的考虑则居于次要地位。
3.共同的语言
在访谈中发现,一个嫁至当地的汉族妇女也会许多畲语,以致被当地人误以为是畲族,她解释原因,说为了和其街坊交流,就得懂一些畲语,否则很难融入。在问卷中,有25%的汉族受访者也会畲语。当地是一个畲族聚集的山区,环境相对封闭,群体间往来大多限于街邻,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并且从人口分布上看,畲族无疑处于强势地位。因此掌握日常互动的公共语言就成为必须,尤其是在交流方式非常局限的乡村,在这里畲语变为一种生存的工具。这无疑为解释几百年前吴姓祖先迁居当地而被同化的过程提供了一个解释的维度。
虎头村的吴姓村民们共同的祖先是吴氏法东一支,历经几百年而繁衍成村落。最初迁徙当地的只限于所在家庭几个成员,与原有的畲族居民相比,人数上无疑处于劣势。而要在特定环境生存,就需要与其他的社群进行生产合作,交流成为必要,这就需要采纳已有的公共语言,于是对畲语的习得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了。而“语言是群体加强凝聚力、产生群体自我认同的有力工具。民族语言除了特定的人际交流、沟通、文化传承等功能外,还是重要而必不可少的群体心理凝固剂和聚合物”①。语言不只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所在族群文化的载体。吴氏在语言的习得中,也在吸收着当地族群的文化,在文化意义上与畲族趋同。
同时,畲语的习得,对吴氏而言是表示对畲族的认同,这使得他们得以在当地定居生存,获得安全、有利的族群身份。
这种社群互动导致了族群边界的模糊。这里既有“根基论”的影子,也有“工具论”的影子。比如出于日常的交往需要而习得畲语,从而被外部认可、接纳,是工具理性的。而即使在今天畲语受到冲击的背景下,在家庭内部,也依然有36.4%的家庭将畲语作为家庭成员间交流的工具。说明他们在历史的演替中,已经将畲语融入了他们的潜意识中,不仅仅是一种工具需要,而真正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4.多因素交错起作用
以上我们提到的生存、通婚、共同的语言多个因素并不是单独起作用的,而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虎头吴氏出于生存的考虑选择了与当地畲族女子通婚,通过通婚又促进了他们对这片地区的共同开发,在长期的通婚与共同的经济生活中,语言的习得是自然而然的事,而当畲语变为其生活的一部分时,他们对畲族的认同也在不断加深,通过认同的加深又强化了通婚和经济合作。这种民族的同化就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生了。
总之,“畲化”的过程是多个因素共同起作用的,一面在瓦解着原有汉族文化的力量,又在根植进新的畲族文化因子。当然,族群身份变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处在多种力量的此消彼长中,不同的时代又处在畲化的不同阶段。尽管历时三百多年,但是也无法说我们研究中的吴姓畲族已经是完全的畲族,比如在对于语言、服饰、通婚等统计中,吴姓畲族对于畲族的认同要低于四大姓原有的畲族。这种不完全性,说明其依然有残留的汉文化的痕迹,即使历时长久,依然未完全消失。在特定的情境中,被记忆或者遗忘。
四、讨论
1.“畲化”与“汉化”
在对于“畲化”的分析中,一直有一个疑问。作为正统的畲族,在诸多方面的考察分析中,已经和汉族足够相似。体质无从辨别,没有本民族文字,衣服已经汉化,乃至现今普及使用最广的语言是当地汉族方言。即使在家庭中,使用畲语交流的比例也仅占45.4%。畲族本民族的文化标示已经处在自然的消亡中。那么我们界定的“汉姓”畲族,在何种意义上属于畲族,又在何种意义上属于汉族?在虎头村,这两个民族的界限已经如此模糊,已很难给出一个绝对的标准。或者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说,在畲汉自然的交融过程中,这种标准已不显得那么重要了。
四大姓畲族就像是搁在吴姓畲族与外部更大的汉族族群中间的围墙,当吴姓迁至畲族族群周围时,便趋同于畲族,与之融为一体;但是当这道围墙本身已经变得低矮,并且逐渐与汉族社群混为一体时,此时的吴姓畲族被“畲化”中,或许还夹杂着“汉化”,因为畲族本身的文化中就有汉文化的大量影子。于是“畲化”与“汉化”两者间就不是完全对立和相互取代的两种过程,而是相互渗透的。因此,我们在说吴姓畲族时,他们应是“畲化”和“汉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当文化的因素此时已经不再能够完全界定族群时,心理的认同就被凸显。尤其在这样一个商业化、信息化的时代里,整个世界都在趋同,变得平坦。于是也就在质疑,衡量一个族群被同化的表示里,文化是否已经无足轻重?因为没有办法说清混杂的元素里有多少是纯粹属于一个民族所有的,因此民族的识别问题也显得更为复杂。
2.吴姓与钟姓畲族
姓氏作为畲族民族认同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是标识其民族特征的一个属性。在畲族的盘瓠传说中,钟姓是以女婿身份进入畲族族群的。根据钟毅锋先生的研究,钟姓具有亦畲亦汉的特点,“钟姓的源流有两支,一支畲族一支汉族,他们本来是没有血缘关系,属于两个不同文化的群体,因为有共同的姓氏符号,使他们构建了共同的祖先源流。”①既然钟姓有两个源流,那么将钟姓作为两个民族交融的切入点则是不太妥当的。既然他们构建了同一个祖先,那么在这种人为的造祖运动中钟氏加强对畲族的认同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此可以说明他们就不是畲汉自然交融而成,也不属于民族融合的典型产物,或者说他们中仅有一部分是民族交融而成的。而虎头吴姓畲族则可视为民族交融的典型例子。对畲族来说,吴姓和部分钟姓都是外来的,那么为何钟姓畲族现已完全被认同为畲族,而吴姓尚处畲汉之间徘徊呢?
抛去地域等诸多变量的差异,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不容忽视,即两者的历史与族源记忆的差别,钟姓已经被整合进入畲族的族群记忆当中了,而吴氏则没有。由于畲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所以口耳相传的历史传说就显得深入人心,成为认同建构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虎头吴姓畲族对自己祖先的记忆则非常的统一明确,这种祖先的记忆成为吴姓完全进入畲族的无形力量。
我们调查中有一个例子是吴姓老者提及自己在县城出生的孙子,由于不被认为是畲族,所以民族成分里填的是汉族,而这位老者的儿子却是畲族。这便是姓氏认同面临的尴尬结果,这种尴尬的处境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我们也不得而知。
对于吴氏和钟氏面临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处境,我们是否可以作出这样的比喻和推断:如果钟氏是“畲化”的完成时的话,那么吴氏是否是“畲化”的进行时呢?吴氏是否终究有一天也会变成完成时呢?结果究竟如何,我们有待历史进行验证。
3.双重地位的选择
吴氏畲族在与汉族交往中,因其自身的文化符号与汉族无异而往往被视为汉族,而在畲族族群中出现时,因其会说畲语而又被视为畲族。吴氏这种摇摆于畲族与汉族之间的这种特殊身份,可以使他们具有双重优势,至今这种优势仍然在发挥着作用。从民族政策上来说,畲族会享受一定的照顾政策。从具体情境来看,当吴氏出现在畲族群体时由于其会讲畲话、懂得畲族的一些传统而被认为是畲族,从而获得畲族同胞的认同;当其出现在汉族群体时,他们则可以借自己原有的汉族姓氏掩饰自己的畲族身份,取得民族认同。这种状况可以使其自由活动于畲汉之间,对其生存、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尤其在当时艰难的生存背景条件下这种身份更是获得人们的青睐。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吴氏选择与畲族通婚的动机。
既然民族融合能让一个族群享受如此有利的生存地位,那么为何这种情况没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存在?这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民族与他民族交融时作出的良好选择呢?这或许可以为我们研究民族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畲化”的界定
1.族群认同理论小引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指出:“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利条件,然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径指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言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又‘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后来,费孝通先生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和阐述,他提出“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所谓民族意识,所以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①。梁启超先生和费孝通先生在他们的论述中都提到了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来说的重要性,但在两个长期通婚、关系融洽的民族之间,这种民族意识则有可能慢慢消融,共同的经济生活则成了两个民族之间的主要内容。
李济先生在《中国民族的形成》中提出,对于两个混居的民族而言,“交往一旦开始,两个民族群体之间的这种关系就只有三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群要么被同化,要么被剿灭,要么不断与入主的我群发生冲突”②。前两种意味着一个民族消弭于另一个民族之中,成为一个民族,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存在一种势力较强的文化,能将另一个民族同化或剿灭;第三种则意味着如果两个民族的势力相当,无法相互取代,陷入相互对立的局面。作者这种论述并不全面,两个民族在不断的接触过程中,还有存在第四种可能,那就是两个民族的人民都建立起对彼此的认同,两个民族长期和睦相处。
在汉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历史证明了汉族作为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核心,将周围各民族凝聚成一个整体,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在一些地方汉民族可能同化他民族,在另一些地方,其他民族也可能同化汉民族。费孝通先生就曾提到汉族融入他民族的两种情形:“一种是被迫的,有如被匈奴、西羌、突厥掳掠去的,有如被中原统治者派遣去边去屯垦的士兵、贫民或罪犯;另一种是由于天灾人祸自愿流亡去的”③。这些“移入其他民族地区的汉人很多就和当地民族通婚,并且为了适应当地社会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也会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发生改变,过若干代以后,就融合于当地民族了”④。公元399年高昌国原是一个由汉魏逃亡到这里的汉人建立的国家,后被胡化;公元866年被回鹘占领后的西州,当地汉人的后裔融合于维吾尔族;“迁居于云南洱海地区的汉人成了白族中的一个重要部分”①。这些都可以作为汉族被他民族同化的例证。
就族群认同本身而言,学术界一般有“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观点。前者强调认同是处在内在根植的天然血缘、情感的认同,个体在此获得归属感;后者强调认同是出于工具理性的考量,从现实利益、生存的角度,选择特定的认同。也有一些理论试图将两者综合。而学者王明珂则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个人或人群都经常借着改变原有的祖源记忆,来加入、接纳或脱离一个族群;造成族群边界的变迁,也就是族群认同变迁(ethnic change)”②。即族群认同存在着一定的塑造,乃至想象。处在资源竞争的情境中,族群以此选择安全、有利的族群身份。在考察族群认同时,如果我们能将血缘、生存及族群记忆三个因素结合,则能较全面地考察一个族群认同的转变过程。
2.“畲化”的界定
学术界对于“汉化”的研究文字非常之多,但对少数民族同化汉族的研究则很少。但是民族之间相互混杂,借鉴吸收各自文化中优秀的成分是自然发生的,中华民族也正是经过了这样的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③。因此,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纯粹的自立于其他民族之外的民族,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模糊界限则让界定一个民族是否被另一个民族同化变成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对于畲族和汉族,他们之间存在两个缓冲地带,即“畲化”汉族与“汉化”畲族。有人认为“汉化畲族就是保持传统蓝、雷、钟姓氏,并通过姓氏来表现出民族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畲化汉族就是保持汉族姓氏,丧失汉族文化特征,同化于畲族,风俗习惯、信仰崇拜、行为方式、生产生活同于畲族。”①这里,将姓氏符号作为区分这两个群体的标志,并没有对“畲化”和“汉化”提出一个具体的标准,因此很难让人信服。
傅衣凌先生和郭志超先生都曾对畲姓的变化进行了考析。他们根据史料记载先将某个姓氏认定为是畲姓,然后再进行考察,但对于怎样才算是“畲姓”也没有一个标准。我们认为某个姓氏是畲姓的前提是这批人具有畲族特征并被认定为畲族,因此在未确定他们是否是畲族前将他们的姓氏归为畲姓进行考察则显得不够严谨。为了避免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出现歧义,在本文中我们将除了畲族传统的盘、蓝、雷、钟四大姓氏外,畲族拥有的其他姓氏都归为汉姓。
那么我们是根据什么将“汉姓”畲族认定为畲族?他们怎样才算是被“畲化”?下面我们将以虎头村为例,从三方面进行论证。
一是政府的认定。20世纪50年代政府进行民族成分认定时将虎头吴姓村民认定为畲族。当年的“民族识别”工作有四个特点:第一,当年在收集各类材料以判定群体差别是否可以定义为“民族”差别时,主要的资料是历史、语言文字、服饰习俗等基本上属于文化层面的内容;第二,行政区划和管辖边界等政治层面的内容并不是当时的重点;第三,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各群体的体质差异并不明显,所以体质差别也没有成为识别工作的主要内容;第四,在“识别”过程中,对于当地群众的愿望给予特别的重视。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虎头村吴氏被认定为畲族是双向选择的结果,他们无论是在文化层面还是在心理层面对畲族都已经建立了深深的认同感。
二是虎头村吴氏族谱、墓碑对其与畲族通婚的记载。虎头村现存四本(道光、同治、光绪、1953年)族谱,族谱里对每一代人的通婚情况大都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从族谱里可以看出吴氏世代都娶畲族女子为妻,且他们的女儿大都嫁给附近村庄的畲民。正是通过这样一代又一代的通婚,吴氏血统渐渐稀释,而畲族血统则不断增加,二者的血缘联系不断加强,通过血缘联系进而加强了文化方面对畲族的认同。在虎头村下辖的一个岔头自然村有该地开基始祖及其儿子的墓,开基始祖幸公的墓建成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其儿子的墓具体年代则已看不清。据墓碑记载,该地开基始祖娶的便是钟氏妻子,而他的儿子娶的则是雷氏妻子。这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吴氏从迁移至岔头开始便与畲族通婚,通婚历史悠久。、
三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当地村民说畲语、唱畲歌、穿畲族衣服、过畲族节日。问卷调查表明,有81.6%吴氏村民会讲畲语,有36.4%吴氏村民在家庭中讲畲语,有52.8%吴氏村民喜欢穿畲族服饰,没有村民反对畲汉通婚。这些说明,虎头吴氏畲族村民已经具备了非常明显的畲族特征,不仅他们认定自己是畲族而且附近村庄的村民也都认为这批人是畲族。
二、吴姓畲族认同现状
1.迁徙
福安吴姓畲族的始祖谱名为知几公,原籍浙江泰顺县兰溪东门外九堡大路边,于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从浙江泰顺九堡大路边村迁入福安九都社口桐湾村。①据《清同治八年延陵吴氏宗谱重修序》载:“源公迁浙江泰顺县九堡大路边,于明嘉靖间为金陵太守,后致仕归卒。又传五世至知几公,字法度,由泰顺卜筑于安邑九都桐壪,配妣彭氏生九子。长法吉,次法正,三法辛,四法显,五法清,六法生,七法东,八法传,九法德,分为九房。迨明季,遭兵燹之乱,谱牒遗忘,散处离居。而法吉、法正二公同迁安邑岭下,法辛公回泰顺梓里,法显公迁泰顺峩洋金丝岗,法清公迁澹溪,法生公迁甯德吴洞里,法东公迁后坑承天至留洋,法传公迁桐湾。迨国朝,法东公三世孙辛公兄弟二人长平公由留洋迁居溪塔墓亭,幸公由留洋而迁岔头,为岔头之开创祖也。”这里描绘了法东公及其后裔的迁徙路线大致是泰顺→九都桐湾→后坑承天→留洋,其中一支平公由留洋迁往墓亭,另一支幸公则迁往岔头,成为岔头的开基始祖。但族谱里里并没有虎头吴氏迁徙的记载,《福安畲族志》记载虎头吴氏是由岔头村迁徙而来,但据当地年逾70、曾管过吴氏族谱的吴大爷所说,虎头吴氏是从墓亭迁徙而来,可见《福安畲族志》的记载与当地的说法也有一些出入。
至于迁徙的原因,族谱里提到“迨明季,遭兵燹之乱,谱牒遗忘,散处离居”。可见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对吴氏的迁徙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当地民众之间还流行另外一种说法,说是因为当时发生水灾,知几公九个儿子分散各地,只有法东公和法传公仍留在桐湾,成为吴姓畲族始祖,其他七兄弟迁移他处,仍为汉族。也正因为这个原因,部分族谱遗失。那么吴氏究竟出于什么原因而迁徙,现在我们也难以断定,但可以明确的一点是他们都是逃难而来。
地域的变动创造了新的族群环境,环境的改变意味着文化习俗、族群关系等一系列的改变,需要对旧有的许多习俗作出改变以适应新的生存地域。吴氏迁入人口较为聚集的福安,这种改变则尤为明显。但我们也可以找到与吴姓类似的例子,如有学者研究一个李土司家族的个案中,其身份由突厥变为土族,“族群身份改变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其祖先所处的战乱频仍的时代背景,加之频繁迁徙的经历、族际接触与通婚的历史等,其所处的地域特点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①。
一般来说,迁徙意味着对迁徙地原有资源分配格局的改变,势必会遭到当地原住民不同程度的排斥。但闽东却有其特殊之处,这是一个来自不同族群的移民构成的社会,当地原有居民大多处于分散未定居状态,这也有史料为证,李济考察历史记载中的城垣数目,到公元1644年为止各省的分布情况中,福建仅为69座,而全国总记载有4478座。“在中国本部之内,只要在任何地方发现城墙,就意味着我们中国人已经以某种定居的状况存在于当地。”②说明至少在吴姓畲族迁徙至福建前后,当地依然是一个尚待开发、地域排他意识不强的区域,没有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有绝对的优越感,这无疑为吴姓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当然,城池的未建并不意味着当地是处于未开化的地区,也可能由于当地人民的开放程度和接纳程度较高。畲族非常善于吸收汉族的文化。在走访中,发现畲族本身就有诸多汉文化的因子,比如畲族的男装大抵与汉族的长袍相似,以汉字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等,其本身的存在就依托于汉文化的诸多创设,反映着畲族本身并不是封闭的,他有个自我调节的机制。畲族在吸收了汉族文化的同时又在其中加入了畲族本身的元素,最基本的核心的东西他没有变,他用这种机制来强化了族群之间的联系。我们再来看看当时中国东南的民族,“在所有的你群诸民族中,操掸语的民族是最易于吸收外来文化的。这显示在如下事实中:中国东南各地的越人,对于入境的我群很少持长久的敌视态度”①。这种对进入当地的族群采取的包容态度,有利于外来族群融入,因此东南区域也是民族关系较为复杂的一块地方。
总之,从吴姓畲族的迁徙来看,一个族群的身份变迁要成为可能,需要合适的生存空间以及可接纳他们的当地族群,二者缺一不可。
2.基于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分析
本次调查所取样本来自我们随机碰到的且愿意接受我们采访的村民。有21.6%的样本来自溪塔村,其余样本来自虎头村。虎头村有吴姓畲族217户、1083人,是调查的核心。两村样本总数为51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入户走访,选择家庭中某一家庭成员作为调查的对象。
我们是以清华的学生身份进入调查,且有村长的推荐,以及溪塔当地的大学生陪伴调查,以消除语言障碍和陌生感,保证了调查的质量和可信度。
(1)调查样本特征
在51份问卷中,雷姓有4人;钟姓有3人;蓝姓2人;陈姓汉族1人;缪姓汉族3人;谢姓畲族1人;吴姓畲族37人。即样本的主体为吴姓畲族。其中,唯一的陈姓是从相邻的乡镇嫁至钟姓畲族人家的媳妇,缪姓汉族父母也均为汉族,不会说畲语,是居住在当地的汉族人家,是没有被“畲化”的样本。谢姓畲族由于样本较小,在当地不具代表性,故不做具体分析。因此,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吴姓畲族占72.54%,四大姓畲族占17.64%,汉族占7.8%。
表一是我们调查中受访者的年龄分布,以青壮年为主,同时各个年龄段都有,可以视为当地人口年龄段的大体分布。这样,使得我们的调查有了近60年的时间跨度,可以相应分析代际之间畲化的程度以及认同比较。
在访谈中,一位年逾六旬的吴姓畲族因为小时候经常听畲族受歧视的故事,对自己的畲族身份并不很认同,他不说畲语、不穿畲服也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畲族身份。即畲族的身份对他实质是一种外在的赋与,缺少内心的认同。这可以视为“汉化”的一个例子,即是社会身份决定了他处在汉畲的中间地带,但是若从心理上选择,则倾向于文化、经济更为强势的汉族。同时,由于老者幼年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家的民族政策并未实行,少数民族弱势地位并未改观,以致他的先辈们对于族群身份并不认同,进而影响到他的观念形成,这应该也是原因之一。一位32岁的吴姓受访者遇到的情况则与此相反,他表示这个“畲族”的成分没有对他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没有受到歧视。但是他给出的理由是“也许因为我的汉族朋友比较多”。相比而言,他则被汉族所接纳,对于本民族正面的认同就多些。由此可以看出,他民族对本民族的态度不仅会影响一个民族对他民族的认同情况,也会影响一个民族对本民族的认同。
(2)语言使用情况分析
我们以四大姓畲族、汉姓畲族、汉族三个族群作为数据分析的对象,从表二中可以看出,畲语掌握程度最好的是四大姓畲族,汉姓畲族和汉族次之,从这里可以发现“畲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汉姓畲族处于中间状态。居住在畲族村落边缘的汉族也受到影响,但是相对很轻,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畲语,反映了畲语在当地依然是族群内部的交流工具。而当地方言则是三个族群掌握情况最好的语言,被作为当地交往的公共语言。普通话则是在更广阔的地域内交往、沟通的工具,往往与阅历、职业、教育程度相关。在此项数据中,汉姓畲族为普通话掌握最好的族群,在某种程度也反映其开放程度。
而表三则是在自然情境中,家庭内部语言的选择,可以更真切地反映出语言的传承与内心认同。在汉族中,家庭内部不再使用畲语,表面畲语纯粹是对外交往的工具,没有内心的认同。而畲语在四大姓畲族中使用的比例最高,且为首选语言。汉姓畲族与之相差并不大,他们由于长期与四大姓畲族通婚,家庭成员有习得畲语的环境,现在仍然有36.4%的汉姓畲族在家中用畲语交流,这使得畲语得到良好的传承,这就不单是工具理性了。但是,汉族方言仍然是汉姓畲族家庭内部交流的首选语言,畲语处于下风,似乎也可折射出当下情境中“汉化”与“畲化”的角力结果。
在访谈中有受访者说到现在畲汉已分不清,因为现在会讲畲语的未必是畲族群众,而有可能是畲家的汉族媳妇或当地长期与畲族居住在一起而会说畲语的汉族群众;不会讲畲话的未必不是畲族群众,而有可能是被汉化的畲民。以前畲族人上街做买卖会被人歧视,导致一部分家庭改用当地方言交流,而他们的儿女因长期在县城读书,失去了学习畲语最好的环境,因此他们不会讲畲语,畲语这种断裂的状态出现在新老一辈的传承中。这一方面说明畲语作为区别汉畲族群的功能在模糊,另一方面说明畲语在与当地福安话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这与畲语缺乏文字载体,只在小范围内交流也有关系,而在现代经济背景下,不同地域、文化的交往日益加深,畲语受到的地域限制则成为弱势经济地位的表征。
(3)各族群对畲族民族服装的态度
表四中,四大姓畲族有时和经常穿畲族服装的为33.3%,汉姓畲族为13.8%,而汉族则为零。从服饰上看,四大姓畲族民族服装的穿着比例也并不高。在访谈中,有一个25岁村民提到,小时候经常穿着畲服,在家、劳动、节日都穿(节日穿新衣服),原因是经济困难,畲服便于劳作。现在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穿的和汉族差不多,有官员来访时才穿。他“小时候”大致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将近20年过去了,经济社会条件都有改善,这也是畲族服装变迁的时代因素。也有村民提到,穿畲衣在以前会受到歧视,为了避免遭受偏见,选择不穿。以前穿的比较多,慢慢地男的穿的少了,女的照穿;现在经济好起来了,男女都不穿畲服了。
在现代化浪潮的席卷下,各个民族大抵都遇到类似的情境,不单是畲族。如在羌族中,羌寨里女性必须要穿本民族的服饰,而男性则不必。出门办事时,一般穿汉族人常穿的服饰。表明了服饰“它不是界定一个族群客观特征之一,而是主观上强调或掩饰族群身份的工具”①。因为民族服饰往往意味着封闭、保守。尽管这样,对民族服饰的认同并不低,四大姓畲族群众和汉姓畲族群众对畲族服装的正面态度分别为88.9%和83.3%,民族服饰在加强民族认同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4)各族群对畲汉通婚的态度
从两表来看,各族群对畲汉通婚都不持反对态度,认为畲汉都一样,抛却了民族偏见。但是实际的族群间通婚情况中,一方面四大姓畲族与畲族通婚的比例要略高于汉姓畲族,某种程度反映了其族群认同要高于汉姓畲族;另一方面,两大族群与畲族通婚都远大于和汉族通婚比例,说明汉姓畲族是在畲族的“我群”之内,畲族已真正接纳了汉姓畲族。
三、“畲化”原因分析
1.通婚
族群间通婚无疑是驱动族群融合、同化极为重要的因素。有学者指出:“族际通婚本身是一个可统计计算的客观指标,同时这个指标最集中地体现出两个族群作为整体是否真正地在相互交往中处于融合状态,即是否出现两个族群的血缘融合,因此族际通婚是衡量族群关系最重要的、总结性的指标。”①
在以家族为基本社群单位的传统时代里,通婚就成为碾平族群间隔阂的力量。虎头村吴氏当时便是一个家族迁入虎头村的,那么最初的吴姓汉族先民们是如何以通婚的形式融入当地的?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一种解释,“婚姻的关系固然是取得地缘的门路……‘外客’却并不容易娶得本地人做妻子,使他的儿女有个进入当地社区的机会。事实上大概先得有了土地,才能在血缘网中生根”②。这与先前关于迁徙中的部分分析吻合,即当地有着相对富余的生存空间,这是通婚的经济基础。
另外,在走访中,最先人们介绍吴姓时说他们祖上出过皇帝。在查看了吴氏家谱后才明白,虎头吴氏以太伯为祖先,而他们的远古祖先则是帝喾,但这已无法考证。有学者指出,“句吴王室成为太伯后裔……使他们在华夏历史记忆中找到太伯传说,以合理化自己的华夏身份。华夏在族群利益抉择下,也以‘太伯奔吴’的历史记忆来证实句吴王室的华夏身份”①。即吴氏太伯之后,可能是对历史记忆的重新建构,虎头吴氏的祖先也很有可能是这种构建的结果。从这里可以看到,即使吴姓已经被认定为畲族,但是依然在强调其祖先的正统性来彰显其血统的高贵,通过溯源暗示其与强势的中原文化的亲缘关系,这在与畲族通婚中无疑增加了被接纳的筹码。因为尽管在当地畲族村落中,畲族是处在强势有利的地位,但在更广阔的地缘文化中,畲族仍是弱势的族群。吴氏以姻亲关系建立起与周边畲族族群的往来关系,在时间的更替中,逐渐在文化表征中被畲化,但同时并未完全认同自己的畲民身份,而是保留着遥远的关于祖先血脉的乡愁。通过问卷调查我们也证实,吴氏对畲族的认同度并没有畲族传统四大姓氏对畲族的认同高。
通过对吴氏族谱的分析,我们发现吴氏世代与畲族通婚,这无疑加速了吴氏融入畲族的进程。“畲族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且还是血缘的概念。”②吴氏对畲族认同是在不断与畲族的通婚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因此这种认同更多是建立在血缘的基础上的,文化上的认同也是由这种血缘关系带来的。与畲族血缘关系的建立,使之嵌入了畲族原有族群的“差序格局”,淡化了“我群”与“你群”的界限。同时,畲族女性进入汉族的家庭内部,对子女的社会化起着关键的作用,子嗣一代对于畲族文化比之最初汉族的父辈们有着更大的亲近。于是,通过代际的传承和族际通婚的不断强化,原有汉族的血统、文化被稀释,相应地,畲族的血缘、文化在增加,并逐渐取代汉族成为主流,“畲化”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
2.生存
畲族和汉族人民当年迁移的目的都是为了谋生,因此吴氏迁居虎头村的时候,首要考虑的应该是如何在这片土地生根发芽。而虎头村附近村庄的村民都是在吴氏迁入虎头村的同一时期迁入这片地区的,相隔不远的溪塔村便是在吴氏迁入65年之后的1588年才迁入的①。
据《吴氏统谱》载“肇基祖法东公,祖居浙江平邑莒溪(今属苍南),于明嘉靖壬午(公元1523年)迁入闽省福安穆阳虎头定居,至公侯申戌,历四七二年,传一十六世”②。而最早徙居浙江泰顺的是在1575年,雷元山从平阳青街白岩村迁泰顺八都莲头金沙垟。③虎头村吴氏开基始祖的迁徙发生在畲族进入其迁出地之前,也就是说他们在迁入福安之前并没有同畲族同胞有过多交往,他们对畲族的认同是在迁入福安以后才建立起来的。那为何在刚迁入畲族地区时就会与畲族通婚呢?我们只能将其归为出于生存的考虑。由于虎头地区属偏远山区,为了更好地生存,需要畲汉人民共同努力进行开发。
畲汉人民共同的遭遇、迁徙,共同的经济生活都有利于加强彼此的认同。同时,统治者的政策也在扮演着催化剂的角色,推动畲汉关系的进一步深入。据《福安畲族志》载,自乾隆十七年(1752年)始,统治阶级的统治才渐渐触及到畲族地区,“编图隶籍”和“编甲完粮”的经济政策逐渐实行于畲族地区。④统治阶级对畲族的统治政策大都与当地汉族一样,正因为如此,使得畲、汉民族关系进一步密切,畲族社会经济生活同汉族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⑤
从畲族族谱所载,畲族迁徙多是一家一户由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因此畲族聚落一般较小,且以单姓聚居为常。⑥畲族是实行民族内婚制的,同姓一般不通婚,因此地处偏远的畲族在寻找异姓通婚时则会遇到一些困难,虎头吴氏则成了他们的一个选择,且相隔不远的吴氏与畲族通婚更有利于其共同开发这块地区,因此这是畲汉人民双向选择的结果。
以下的两个例子则与这种情况类似。“福建宁德县南岗斗村畲民在康熙年间迁到这里居住,便同当地汉族通婚,而且关系十分融洽。福鼎县伏柳乡的高厝里和蓝厝里二村,是汉族高姓和畲族蓝姓于清代迁居于此,他们共同开发了这块土地,两族之间不仅通婚,而且关系十分融洽。”①即我们在虎头族谱中见到的畲族与汉族通婚并非孤例。
两个族群的通婚也是经济往来的一种相互依附。面对超出少量人力之外的自然力,需要协作以应对。而通婚则是将相互的血脉交互,接纳进各自的谱系,插入各自的亲缘差序格局中,经济的协作就是题中之义了。这往往超越了单个民族的自闭,而是走向了合作。如同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格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乃至被归化。这种生存的双向选择使畲汉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共同的经济生活促进了民族的交往,彼此的认同也在不断的交往与合作中慢慢建立起来,而在这种互动中民族因素的考虑则居于次要地位。
3.共同的语言
在访谈中发现,一个嫁至当地的汉族妇女也会许多畲语,以致被当地人误以为是畲族,她解释原因,说为了和其街坊交流,就得懂一些畲语,否则很难融入。在问卷中,有25%的汉族受访者也会畲语。当地是一个畲族聚集的山区,环境相对封闭,群体间往来大多限于街邻,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并且从人口分布上看,畲族无疑处于强势地位。因此掌握日常互动的公共语言就成为必须,尤其是在交流方式非常局限的乡村,在这里畲语变为一种生存的工具。这无疑为解释几百年前吴姓祖先迁居当地而被同化的过程提供了一个解释的维度。
虎头村的吴姓村民们共同的祖先是吴氏法东一支,历经几百年而繁衍成村落。最初迁徙当地的只限于所在家庭几个成员,与原有的畲族居民相比,人数上无疑处于劣势。而要在特定环境生存,就需要与其他的社群进行生产合作,交流成为必要,这就需要采纳已有的公共语言,于是对畲语的习得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了。而“语言是群体加强凝聚力、产生群体自我认同的有力工具。民族语言除了特定的人际交流、沟通、文化传承等功能外,还是重要而必不可少的群体心理凝固剂和聚合物”①。语言不只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所在族群文化的载体。吴氏在语言的习得中,也在吸收着当地族群的文化,在文化意义上与畲族趋同。
同时,畲语的习得,对吴氏而言是表示对畲族的认同,这使得他们得以在当地定居生存,获得安全、有利的族群身份。
这种社群互动导致了族群边界的模糊。这里既有“根基论”的影子,也有“工具论”的影子。比如出于日常的交往需要而习得畲语,从而被外部认可、接纳,是工具理性的。而即使在今天畲语受到冲击的背景下,在家庭内部,也依然有36.4%的家庭将畲语作为家庭成员间交流的工具。说明他们在历史的演替中,已经将畲语融入了他们的潜意识中,不仅仅是一种工具需要,而真正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4.多因素交错起作用
以上我们提到的生存、通婚、共同的语言多个因素并不是单独起作用的,而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虎头吴氏出于生存的考虑选择了与当地畲族女子通婚,通过通婚又促进了他们对这片地区的共同开发,在长期的通婚与共同的经济生活中,语言的习得是自然而然的事,而当畲语变为其生活的一部分时,他们对畲族的认同也在不断加深,通过认同的加深又强化了通婚和经济合作。这种民族的同化就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生了。
总之,“畲化”的过程是多个因素共同起作用的,一面在瓦解着原有汉族文化的力量,又在根植进新的畲族文化因子。当然,族群身份变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处在多种力量的此消彼长中,不同的时代又处在畲化的不同阶段。尽管历时三百多年,但是也无法说我们研究中的吴姓畲族已经是完全的畲族,比如在对于语言、服饰、通婚等统计中,吴姓畲族对于畲族的认同要低于四大姓原有的畲族。这种不完全性,说明其依然有残留的汉文化的痕迹,即使历时长久,依然未完全消失。在特定的情境中,被记忆或者遗忘。
四、讨论
1.“畲化”与“汉化”
在对于“畲化”的分析中,一直有一个疑问。作为正统的畲族,在诸多方面的考察分析中,已经和汉族足够相似。体质无从辨别,没有本民族文字,衣服已经汉化,乃至现今普及使用最广的语言是当地汉族方言。即使在家庭中,使用畲语交流的比例也仅占45.4%。畲族本民族的文化标示已经处在自然的消亡中。那么我们界定的“汉姓”畲族,在何种意义上属于畲族,又在何种意义上属于汉族?在虎头村,这两个民族的界限已经如此模糊,已很难给出一个绝对的标准。或者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说,在畲汉自然的交融过程中,这种标准已不显得那么重要了。
四大姓畲族就像是搁在吴姓畲族与外部更大的汉族族群中间的围墙,当吴姓迁至畲族族群周围时,便趋同于畲族,与之融为一体;但是当这道围墙本身已经变得低矮,并且逐渐与汉族社群混为一体时,此时的吴姓畲族被“畲化”中,或许还夹杂着“汉化”,因为畲族本身的文化中就有汉文化的大量影子。于是“畲化”与“汉化”两者间就不是完全对立和相互取代的两种过程,而是相互渗透的。因此,我们在说吴姓畲族时,他们应是“畲化”和“汉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当文化的因素此时已经不再能够完全界定族群时,心理的认同就被凸显。尤其在这样一个商业化、信息化的时代里,整个世界都在趋同,变得平坦。于是也就在质疑,衡量一个族群被同化的表示里,文化是否已经无足轻重?因为没有办法说清混杂的元素里有多少是纯粹属于一个民族所有的,因此民族的识别问题也显得更为复杂。
2.吴姓与钟姓畲族
姓氏作为畲族民族认同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是标识其民族特征的一个属性。在畲族的盘瓠传说中,钟姓是以女婿身份进入畲族族群的。根据钟毅锋先生的研究,钟姓具有亦畲亦汉的特点,“钟姓的源流有两支,一支畲族一支汉族,他们本来是没有血缘关系,属于两个不同文化的群体,因为有共同的姓氏符号,使他们构建了共同的祖先源流。”①既然钟姓有两个源流,那么将钟姓作为两个民族交融的切入点则是不太妥当的。既然他们构建了同一个祖先,那么在这种人为的造祖运动中钟氏加强对畲族的认同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此可以说明他们就不是畲汉自然交融而成,也不属于民族融合的典型产物,或者说他们中仅有一部分是民族交融而成的。而虎头吴姓畲族则可视为民族交融的典型例子。对畲族来说,吴姓和部分钟姓都是外来的,那么为何钟姓畲族现已完全被认同为畲族,而吴姓尚处畲汉之间徘徊呢?
抛去地域等诸多变量的差异,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不容忽视,即两者的历史与族源记忆的差别,钟姓已经被整合进入畲族的族群记忆当中了,而吴氏则没有。由于畲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所以口耳相传的历史传说就显得深入人心,成为认同建构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虎头吴姓畲族对自己祖先的记忆则非常的统一明确,这种祖先的记忆成为吴姓完全进入畲族的无形力量。
我们调查中有一个例子是吴姓老者提及自己在县城出生的孙子,由于不被认为是畲族,所以民族成分里填的是汉族,而这位老者的儿子却是畲族。这便是姓氏认同面临的尴尬结果,这种尴尬的处境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我们也不得而知。
对于吴氏和钟氏面临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处境,我们是否可以作出这样的比喻和推断:如果钟氏是“畲化”的完成时的话,那么吴氏是否是“畲化”的进行时呢?吴氏是否终究有一天也会变成完成时呢?结果究竟如何,我们有待历史进行验证。
3.双重地位的选择
吴氏畲族在与汉族交往中,因其自身的文化符号与汉族无异而往往被视为汉族,而在畲族族群中出现时,因其会说畲语而又被视为畲族。吴氏这种摇摆于畲族与汉族之间的这种特殊身份,可以使他们具有双重优势,至今这种优势仍然在发挥着作用。从民族政策上来说,畲族会享受一定的照顾政策。从具体情境来看,当吴氏出现在畲族群体时由于其会讲畲话、懂得畲族的一些传统而被认为是畲族,从而获得畲族同胞的认同;当其出现在汉族群体时,他们则可以借自己原有的汉族姓氏掩饰自己的畲族身份,取得民族认同。这种状况可以使其自由活动于畲汉之间,对其生存、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尤其在当时艰难的生存背景条件下这种身份更是获得人们的青睐。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吴氏选择与畲族通婚的动机。
既然民族融合能让一个族群享受如此有利的生存地位,那么为何这种情况没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存在?这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民族与他民族交融时作出的良好选择呢?这或许可以为我们研究民族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附注
①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②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1671—68页。
③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19页。
④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20页。
①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20页。
②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③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①蓝万清:《从汉化畲族与畲化汉族谈畲汉之辨》,http://blog.sina.com.cn/s/blog48bac99e0100053s.html,2006年8月10日。
②菅志翔:《族群归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义》,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①蓝运全、缪品枚主编:《闽东畲族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①祁进玉:《群体身份与多元认同:基于三个土族社区的人类学对比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98页。
②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61页。
受访者样本年龄分布①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178页。
各个族群掌握方言情况样本中成员在家庭中使用语言情况各族群对畲族民族服装的态度注:受访者中有3个描述在家中男的很少穿,而女性穿的较多些,未计入数据统计中,占数据总数的5.9%。
各族群间通婚态度注:由于部分受访者为未成年人或者未被问及该问题,关于入赘、通婚的态度为部分受访者态度的反映。在统计时根据已作出回答的人数作为基数的,同时汉族样本较少,所以数据显得绝对。
①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族群间通婚情况①马戎序、梁茂春撰:《跨越族群边界:社会学视野下的大瑶山族群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版,第5页。
②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年,第68页。
①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页。
②钟毅峰:《亦畲亦汉——钟姓复杂民族性研究》,http://www.minzuonline.com/shezu/LiShi/47810/1.htm,2008年5月29日。
①龙远蔚等撰:《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福安市畲族卷》,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页。
②《吴氏统谱》,1994年修,第198页。
③《泰顺畲族大事记》,《泰顺县文史资料》1994年第3辑,第118页。
④蓝炯熹总纂:《福安畲族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⑤蒋炳钊、吴绵吉、辛土城:《中国东南民族关系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9页。
⑥郭志超:《闽台民族史辨》,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181页。
①蒋炳钊、吴绵吉、辛土城:《中国东南民族关系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97页。
①祁进玉:《群体身份与多元认同:基于三个土族社区的人类学对比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页。
①钟毅峰:《亦畲亦汉——钟姓复杂民族性研究》,http://www.minzuonline.com/shezu/LiShi/47810/1.htm,2008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