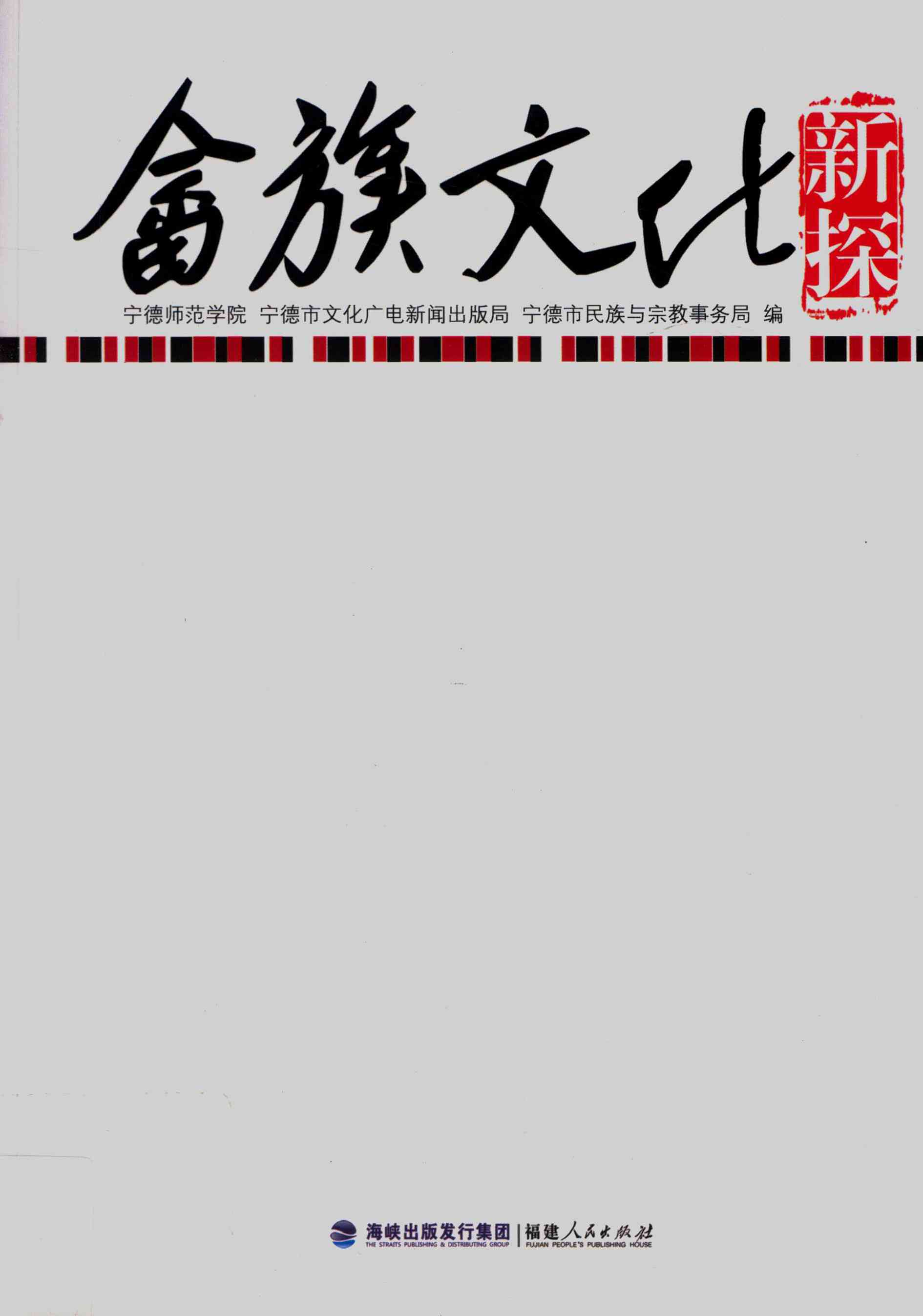内容
畲族是我国东南沿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畲族先民很早就聚居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那时这一带尚未开发,社会经济处于以“刀耕火种”为基本特征的原始游耕阶段。
唐总章年间(668—669年),封建王朝的军队进入畲族聚居的漳潮地区,造成了畲族社区的第一次大震荡。这场政治剧变对畲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造成了强烈的反响,也开启了日后畲族大迁徙的漫漫历程。
一、入迁闽东——招民垦荒政策带动移民热
根据闽东现有畲族谱谍统计,从唐至清,畲族蓝、雷、钟三大主姓共有74支迁入闽东,其中唐代2支,明代30支,清代42支;蓝姓26支,雷姓25支,钟姓23支。②
唐代的2支,最早的是唐乾符三年(876年),有蓝姓畲民从侯官县(闽侯)迁入古田县的水竹洋(今富达村);其次是唐五代时期,有钟姓畲民从汀州上杭迁入福安韩阳坂五十三都钟莆坑,其后裔又于北宋大观四年(1110年)移迁今福安市坂中畲族乡的大林村。
还有一些是语焉不详的“来历不明”者。如北宋时就有雷姓畲族迁住福安金斗洋村。《福安畲族志》有这样的记述:“坂中和安钟谱载,‘大林钟’始祖飞公之女适金斗量(金斗洋)雷谓礼。时为北宋末年。”现今在金斗洋畲民中还流传着类似的说法。这也是有关闽东雷姓畲民的最早记述。
畲民大批迁入闽东是在明清时期,尤以万历至乾隆中期的200年最为集中。这与明清时期封建政府招民垦荒的政策密切相关。
明初,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因长期战乱而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以“招集流民,劝农兴学”为基本国策,规定“凡开垦荒田……各处人民先因兵燹遗下田土,他人开垦成熟者,听为己业,有司于附近荒田拨补”①,还规定“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②。明代赋出于土田,役出于丁口,二者皆归于户。游耕畲民因尚未纳入官府的编甲管理,无需承担赋役。加上闽东依山际海的地理特点,使当地许多滨海临江的汉民家族更多地热衷于通过围海造田来缓解因人口增殖带来的吃饭问题③,空余出更多偏远的山区荒野,给畲民的移迁提供了较为广阔的接纳空间。
清代闽东的社会经济状况与明代大抵相当,清初也经历过较大的社会动荡。为了恢复生产,顺治六年(1649年)清政府规定了一系列招民垦荒的措施:“凡各处逃亡民人,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俾之安居乐业。察本地方无主荒田,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④清政府还以招徕流民的数量作为考核黜陟地方官的重要标准。这些措施有效地为广大流徙各地、住无定处的畲民提供了一个落籍安居的政策背景,而闽东广袤的尚未充分开发的山区“余地”则使封建官府招民垦荒的初衷得以成为现实。于是,这许多勤劳勇敢、酷爱自由的族群,怀抱着“功建前朝帝喾高辛亲敕赐,名垂后裔皇子王孙免差徭”⑤的信念,络绎不绝地到闽东来做“山客”,进而定居落籍成为这里的新主人。
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有雷姓畲民由罗源北岭迁至福鼎十四都白琳大旗坑牛埕下,这是有明确时间记载的进入闽东的第一支雷姓畲民。此外,比较重要的还有福安后门坪雷姓,明成化二年(1466年)从福州方向转迁而来;宁德猴墩雷姓,明万历元年(1573年)从罗源迁入;霞浦水门茶岗雷姓,清乾隆元年(1736年)从浙南迁入。
闽东最主要的一支钟姓畲族是“大林钟”。该支派于明正德十一年 (1516年)迁至福安大林,后来闽东钟氏就奉大林钟的开基祖为钟熙侯王,大林钟氏宗祠成为福宁府钟氏畲民共祀的祖祠。
明中期以后蓝姓开始大批进入闽东。较早的有宁德飞鸾葡萄坑蓝姓,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自罗源八角井迁入。此外,比较重要的还有福安穆云溪塔蓝姓,于万历年间(1573—1619年)自寿宁迁入;霞浦青皎牛岭蓝姓,于天启元年(1621年)自罗源迁入;霞浦崇儒上水蓝姓,于崇祯九年(1636年)自浙江泰顺迁入。
可知最后一支钟姓畲族是于清雍正三年(1725年)从闽西的武平县迁入宁德县斑竹村。这时雷、蓝两姓的入迁仍在继续。直到乾隆后期(18世纪后期)还有雷、蓝两姓畲民分别从南面的罗源、连江和浙江平阳、泰顺等地迁入闽东。
此后畲族入迁闽东的历史基本结束,仅有零星的畲民从浙江回迁。
闽东畲族内部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唐末盘、蓝、雷、钟等姓畲民共三百六十余口随王审知为向导官从海路入闽,其中盘姓一船被大风漂流不知去向,其余在连江马鼻登岸,经罗源大坝头后分迁各地。尽管在诸多的畲族谱谍中都有类似的记述,但是此说与各支系族谱中普遍比较明确的开基祖肇迁时间相去甚远,也得不到其他史料的有力印证,所以目前只能将其视为传说。
二、告别游耕——一曲感动历史的山地情歌
明清时期畲族入迁闽东的内因与以往的迁徙是大不相同的。
以往畲民的迁徙都带有明显的军事性质。如南宋末年,畲族人民组成“畲军”,参加文天祥、张世杰等领导的闽浙沿海地区的抗元武装斗争,宋亡后被迫流徙各地。最典型的当属元代陈吊眼、许夫人、钟明亮等以畲族为主体的反元义军,以万为计的造反大军转战于闽粤赣三省的漳、潮、泉、汀、赣诸州,起义军被镇压后,这些畲族勇士或留居当地,或散迁他处。
明清时代大批畲族向北迁徙是原始游耕的继续。刀耕火种、去瘠就腴,是畲民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集韵·麻韵》:“畲,火种也。”《广韵·麻韵》:“畲,烧榛种田。”“畲”字还指开垦过二三年的田地。《尔雅·释地》:“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畲。”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互为因果。畲民食尽一山,两三年后则他徙。因为他们靠山吃山,所以自称山哈、山客;因为刀耕火种,所以又称“畲客”。“畲”字还有一个写法作“”(广东俗字),檀萃《说蛮》解释说:“,巢居也。”所谓巢居就是在山林中搭寮架棚为居所。从粤东到闽西,再到闽中,再到闽东,畲族这种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在粤东,畲民“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①。
在闽西,畲民“随山种插,去瘠就腴,多于深山中编荻架茅为居,善射猎”②。
在闽中,“畲民巢居崖处,射猎其业,耕山而食,率二三岁一徙”③。
在闽东,“畲民崖处巢居,耕山而食,去瘠就腴,率数岁一徙”④。
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进士、长乐人谢肇涮为我们留下了一段关于畲民烧山的现场记录:“既过胡坪(今霞浦水门武坪),值畲人纵火焚山,西风急甚,竹木迸爆如霹雳。舆者犯裂〔烈〕焰而驰,下山回望,十里为灰矣。”⑤
其实烧山火耕的生产方式汉族也有。古诗中早有汉民烧畲的佳句,如“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陶潜《和刘柴桑》);“煮酒为盐速,烧畲度地偏”(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宝客一百韵》);“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刘禹锡《竹枝词之九》)。直到20世纪70年代,笔者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时还多次与当地村民一道烧过“畲”,当地村民叫做“烧园坪”:在离村落偏远的山上,烧出“园坪”一片,以所烧的草木灰为肥,种植薯类或其他耐旱作物(多是杂粮),两三年后地力衰退,就抛荒了。不同的是谢肇淛笔下的畲人烧山是将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捆绑在一起,待地力退后,他们就会弃寮迁移,另择新地。
进入闽东后,畲民仍然在继续频繁地流徙。有在县内,也有在县际;还有一部分继续北上浙江,或不久后又回迁闽东。《丽水畲族志》记述:“今调查统计,由福建入迁处州的蓝、雷、钟三姓有35支,由福建迁居浙江平阳、瑞安、杭州钱塘(今萧山县)等地后分迁来的7支,共计42支,他们散居于丽水地区的9个县市。……另有9支族返迁福建。”⑥
畲民“在漫长的流徙过程中,每经过一个地方并没有全数迁走,迁走的只是一部分,其余仍在原处安居下来,故迁移沿线都有畲民住居”①。这样一来,畲族的分布越来越分散,后来的许多畲村大多是由一人一户发族。福安“山头庄钟姓畲族……原有5个兄弟,一个来山头庄,一个在双江坑门里,一个住林洋,另外两个去宁德。山头庄雷姓畲族系自穆阳迁来的。小岭钟姓畲族系从宁德城郊附近的金村迁来。有三兄弟,一住金,一来小岭,一住头里”②。畲族就是这样形成了今天的“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
畲族进入闽东后,与当地汉族的交往日益频繁。他们从汉族农民身上学到了许多农耕技术,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于是不再留恋昔日的游耕,从而开始了择地定居、以农为业的尝试。这样,一部分畲民依靠自己开垦的少量土地得以生存,更多无地、少地的畲民只好租种汉族地主的田地和官山,成为佃农。
史志上记述,“古田、连江、罗源、福宁、宁德、福安”畲民“布散山泽间,亦受民田以耕,谓平民曰百姓”③,“附近民居在邑之四都上洋等村,(畲民)与民往来交易,亦有承佃民业为生业者”。④租种汉族地主土地者日益增多。山有山租,田有田租,租额一般按其收获量“主佃均分”。付不起地租、无田可耕者只好“仰给于富户雇工”,成为地主的长工、短工。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钟大焜纂修的《颍川钟氏宗谱》载福安正堂准给大林钟姓畲民官山一号的山场执照,申明“五都大林官山一号断归钟盛九等久住管守,山场艺植竹木,栽种生理,岁纳官租银二两加给栖云寺渡夫工食”。该山场历经明清两朝,从万历到光绪共三次更换执照,可谓一脉相承。
畲民定居之后,官府对他们实行了有效管理,并且逐步编甲入籍。“康熙年间钤印州示,内有‘畲民居住山野,专责畲民保长保固地方,烟差照例豁免……’”①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更定清初编置户口牌甲之令,规定“各省山居棚民,按户编册”②。从此以后,清政府对畲民全面实行编甲管理,并且和汉民一样承担照章完粮义务,标志着畲民从此彻底告别了游耕,封建关系在畲族社区完全确立。
三、垦荒种山——融入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
根据推算,乾隆中期(18世纪后期)福安县畲民约有1.4万人,在今之闽东范围内当有畲民4万多人。③
人数如此之多的新移民,怀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景,散布在闽东的茫茫山野,无疑对这一片土地的进一步开发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尤其必须指出的是由于畲族妇女和男子一样参加劳动,使畲族的劳动生产能力大大超过周边相同户数的汉族原住民。史料中关于畲族妇女参加劳动的记述可谓比比皆是:“吾族本畲民,男女耕作,自古如斯。”④“畲民……男女杂作,以远近为伍,性多淳朴,短衫跣足。”⑤“畲民……男耕女磕,恪守法纪,其风俗近古。”⑥……
广大畲民定居闽东以后,主动融入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垦荒种山是他们最基本的谋生手段,和周边的汉民一样,他们主要是种植禾稻、蓝靛、苎麻、甘薯等。
南宋以后,随着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南移、北方汉人大批南迁,福建人口在原有的基础上迅速膨胀,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人们在围海造田的同时也更加重视山区的进一步开发。“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尽力耕”①,“深山穷谷,人迹所不到,往往有民居,田园水竹,鸡犬之音相闻”②是当时的写照。到了明清,闽东大地已经开发得很充分。许多新到的畲民只好到自然条件更为艰苦的高寒山区,开山辟田。这些地方山高水冷,路途遥远,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畲民多居住高山斜坡上,耕种着梯田。耕地分水田和农地二种,水田较农地为多。水田约占耕地总面积的90%—95%。……梯田山高水冷,土浅砂多,山道崎岖,交通不便,因此种植农作物花工大,产量低。据了解,一亩水稻从种到收,需要30—40个工作日,而每亩水稻产谷200—250斤,300斤以上也有,差的不到100斤。”③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所以“农田耕作,极为粗放,水田都只二犁二耙……原始刀耕火种的残余尚留存在耕种之中。1亩水田,种子6斤,插1300株秧苗,故当时就以1300株为1亩。……畲民田园,多为梯田,靠近溪涧能经常灌溉的不多……‘久晴则怕旱,久雨则怕涝’。水利设备极差,无水坝,亦无水渠,顶多只在溪涧水源地方安上竹筒,疏导灌溉,其法十分原始”④。
为解高山梯田水冷、地瘠、耗工、低产之虞,山区农民培植了一种称作山稻或园稻的旱稻。明万历《福安县志》云:福安“又有一种山稻,畲人种于山坞”⑤。这种稻谷适合在山上旱地种植,因多为畲民所种,所以又被称作“畲稻”。畲民“所开土地,叫做‘畲田’……当地群众多称他们为‘畲客’或‘山客’,本无恶意”⑥。
蓝靛也叫青靛,闽东人又叫“菁”。这是一种可以提取蓝色染料的草本植物。明代以来,东南沿海的纺织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对蓝靛的需求激增;“福建菁”已名闻全国,尤以汀州为最,所以有“福州西南,蓝甲天下”之说。因社会生活需要,而且种菁获利颇丰,闽东各县早有种植。万历《福安县志》在《土产》目下就列有“靛”。乾隆《宁德县志》云:“邑以种菁为业者,大抵汀人也”,“如西乡几都,菁客盈千”。①说明当时有大批汀州人到闽东种菁,其中应该有许多畲民。入迁闽东的畲民,因擅种蓝靛,也被称为“菁客”,他们居住的村落被称为“菁寮”;今福鼎前岐还有一个叫做“菁寮”的畲村。
苎麻纤维细长,平滑而又有丝光,质轻而拉力强,吸湿易干又易散热,染色容易褪色难,历来是闽东山区寻常百姓主要的衣着用料,社会需求量相当大。直到20世纪70年代,闽东广大的山乡农民无论畲汉,每人至少还有一两件苎麻布制成的被称作“粗衫”的劳动服。由于气候和土质的原因,闽东和浙南广袤的山区成了苎麻的理想家园,山民都擅此业。种苎,制苎,直至织成苎布,“一条龙”做到底,自给自足。明末寿宁知县冯梦龙曾有过如此的描述:(寿民)“近得苎麻之利,走龙泉、庆元、云和之境如鹜。……苎山亦称麻山,一年三熟,谓之‘三季’。富者买山,贫者为佣,中人则自力其地”②。
种苎与种菁关系甚大,种菁种苎之利数倍于种粮,不少乡民因而致富。清代闽东靛菁除为本地所产苎布着色外,大多销往江浙。此业乾嘉年间(1736—1820年)最盛,同光(1862—1908年)以后,“西洋之靛竞进,力比土靛强二十倍。土靛十二斤半仅当彼之十两,色泽较鲜而价较廉,而土靛遂一败涂地”③。传统的种苎和种靛业遂走向败落。
和汉族山民一样,畲民也擅苎业。差不多每家每户都有织布机,畲民称为“楠机”(nóng gū)。“织麻布是畲族妇女的专长,家庭人口多的一年要织70—80尺,人口少的织30—40尺,原料都是自己种的苎麻,有少量黄麻。麻布都是作外衣备户外劳动之用。……没有出卖的,穿时都染成青、蓝色。”④苎麻丝织成的布叫做“苎布”、“緕布”、“夏布”。乾隆《福宁府志》称:“夏布之属以福安为上。”①这恐怕与福安畲族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种苎者最多不无关系。
清初,抗清英雄、福安进士刘中藻“选练精兵”,“取于苎寮、菁寮、畲寮”,在“崎岖山谷,聚众万人,遂复庆元、泰顺、寿宁、宁德、福安、古田、罗源诸县”。②此“三寮”之民的主体应是畲族,收复的庆元等七县都是畲族聚居的区域。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畲民所从事的生产劳动内容、基本的生活状况。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长乐华侨陈振龙父子从菲律宾引进甘薯(番薯)苗,经福建巡抚金学曾的大力提倡,开始在福建各地普遍种植。甘薯初一传入便充分表现出耐旱高产的优秀品质,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成为山区人民(包括畲民)的主粮。《福安县志》云:“山田硗确,不任菑畲者,悉种薯蓣以佐粒食,贫民尤利赖焉。”③“薯蓣”即甘薯,“粒食”指米谷。闽东大地山多地少,从此甘薯成为山区人民的主粮,在粮食作物中其地位仅次于水稻。畲汉人民不断地对甘薯品种进行改良,以保证持续高产。到民国时期福安就有李薯、蕹菜薯、苦瓜薯、红薯、牛底薯、冰糖薯、台湾薯等品种。④
畲民靠山吃山。除种植业外,采薪烧炭也是畲民的一项重要的生产劳动内容和经济来源。20世纪前期的闽东,每50公斤柴片大约可换2.5公斤稻谷,每50公斤木炭大约可换10公斤稻谷。畲民常以采薪烧炭换取生活所需。柴薪除松木、杂木片外还有杂木树枝和“细芒”(覆盖山体的芒萁草)。直到20世纪后期“厨房革命”(告别柴草,以液化石油汽或电力为燃料)之前,每天上午在城镇的集市上依然可以看到成群的山民(主要是畲民)挑着薪炭待沽的身影。
定居的农耕生活使畲民与当地汉族融为一体,并且在保留自己主要传统的同时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在政治和文教方面与汉族有了相同的追求。
在耕读文化的氛围中,一些畲族村落也设立私塾,延师授课;一些畲族知识分子经过自身的刻苦努力,取得了令人刮目的成就,跻身于上流社会;还出现了像古田的富达、霞浦的白露坑等畲族文化名村。封建社会的主流观念和价值取向深深地影响着畲民,众多畲族宗谱中的“族规”、“家范”都对子孙后代规定了许多充满儒家理念的处世原则,下面这则被称为“圣谕十六条”的教训①颇具代表性:
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里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
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律法以警愚顽;
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
戒逃匿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
畲族同胞就是这样以自己的聪明智慧和超人的吃苦耐劳为闽东山区的进一步开发和文明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并以千年的时光,和当地汉族一道谱写了一曲民族大团结、大融合的壮丽乐章。
唐总章年间(668—669年),封建王朝的军队进入畲族聚居的漳潮地区,造成了畲族社区的第一次大震荡。这场政治剧变对畲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造成了强烈的反响,也开启了日后畲族大迁徙的漫漫历程。
一、入迁闽东——招民垦荒政策带动移民热
根据闽东现有畲族谱谍统计,从唐至清,畲族蓝、雷、钟三大主姓共有74支迁入闽东,其中唐代2支,明代30支,清代42支;蓝姓26支,雷姓25支,钟姓23支。②
唐代的2支,最早的是唐乾符三年(876年),有蓝姓畲民从侯官县(闽侯)迁入古田县的水竹洋(今富达村);其次是唐五代时期,有钟姓畲民从汀州上杭迁入福安韩阳坂五十三都钟莆坑,其后裔又于北宋大观四年(1110年)移迁今福安市坂中畲族乡的大林村。
还有一些是语焉不详的“来历不明”者。如北宋时就有雷姓畲族迁住福安金斗洋村。《福安畲族志》有这样的记述:“坂中和安钟谱载,‘大林钟’始祖飞公之女适金斗量(金斗洋)雷谓礼。时为北宋末年。”现今在金斗洋畲民中还流传着类似的说法。这也是有关闽东雷姓畲民的最早记述。
畲民大批迁入闽东是在明清时期,尤以万历至乾隆中期的200年最为集中。这与明清时期封建政府招民垦荒的政策密切相关。
明初,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因长期战乱而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以“招集流民,劝农兴学”为基本国策,规定“凡开垦荒田……各处人民先因兵燹遗下田土,他人开垦成熟者,听为己业,有司于附近荒田拨补”①,还规定“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②。明代赋出于土田,役出于丁口,二者皆归于户。游耕畲民因尚未纳入官府的编甲管理,无需承担赋役。加上闽东依山际海的地理特点,使当地许多滨海临江的汉民家族更多地热衷于通过围海造田来缓解因人口增殖带来的吃饭问题③,空余出更多偏远的山区荒野,给畲民的移迁提供了较为广阔的接纳空间。
清代闽东的社会经济状况与明代大抵相当,清初也经历过较大的社会动荡。为了恢复生产,顺治六年(1649年)清政府规定了一系列招民垦荒的措施:“凡各处逃亡民人,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俾之安居乐业。察本地方无主荒田,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④清政府还以招徕流民的数量作为考核黜陟地方官的重要标准。这些措施有效地为广大流徙各地、住无定处的畲民提供了一个落籍安居的政策背景,而闽东广袤的尚未充分开发的山区“余地”则使封建官府招民垦荒的初衷得以成为现实。于是,这许多勤劳勇敢、酷爱自由的族群,怀抱着“功建前朝帝喾高辛亲敕赐,名垂后裔皇子王孙免差徭”⑤的信念,络绎不绝地到闽东来做“山客”,进而定居落籍成为这里的新主人。
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有雷姓畲民由罗源北岭迁至福鼎十四都白琳大旗坑牛埕下,这是有明确时间记载的进入闽东的第一支雷姓畲民。此外,比较重要的还有福安后门坪雷姓,明成化二年(1466年)从福州方向转迁而来;宁德猴墩雷姓,明万历元年(1573年)从罗源迁入;霞浦水门茶岗雷姓,清乾隆元年(1736年)从浙南迁入。
闽东最主要的一支钟姓畲族是“大林钟”。该支派于明正德十一年 (1516年)迁至福安大林,后来闽东钟氏就奉大林钟的开基祖为钟熙侯王,大林钟氏宗祠成为福宁府钟氏畲民共祀的祖祠。
明中期以后蓝姓开始大批进入闽东。较早的有宁德飞鸾葡萄坑蓝姓,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自罗源八角井迁入。此外,比较重要的还有福安穆云溪塔蓝姓,于万历年间(1573—1619年)自寿宁迁入;霞浦青皎牛岭蓝姓,于天启元年(1621年)自罗源迁入;霞浦崇儒上水蓝姓,于崇祯九年(1636年)自浙江泰顺迁入。
可知最后一支钟姓畲族是于清雍正三年(1725年)从闽西的武平县迁入宁德县斑竹村。这时雷、蓝两姓的入迁仍在继续。直到乾隆后期(18世纪后期)还有雷、蓝两姓畲民分别从南面的罗源、连江和浙江平阳、泰顺等地迁入闽东。
此后畲族入迁闽东的历史基本结束,仅有零星的畲民从浙江回迁。
闽东畲族内部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唐末盘、蓝、雷、钟等姓畲民共三百六十余口随王审知为向导官从海路入闽,其中盘姓一船被大风漂流不知去向,其余在连江马鼻登岸,经罗源大坝头后分迁各地。尽管在诸多的畲族谱谍中都有类似的记述,但是此说与各支系族谱中普遍比较明确的开基祖肇迁时间相去甚远,也得不到其他史料的有力印证,所以目前只能将其视为传说。
二、告别游耕——一曲感动历史的山地情歌
明清时期畲族入迁闽东的内因与以往的迁徙是大不相同的。
以往畲民的迁徙都带有明显的军事性质。如南宋末年,畲族人民组成“畲军”,参加文天祥、张世杰等领导的闽浙沿海地区的抗元武装斗争,宋亡后被迫流徙各地。最典型的当属元代陈吊眼、许夫人、钟明亮等以畲族为主体的反元义军,以万为计的造反大军转战于闽粤赣三省的漳、潮、泉、汀、赣诸州,起义军被镇压后,这些畲族勇士或留居当地,或散迁他处。
明清时代大批畲族向北迁徙是原始游耕的继续。刀耕火种、去瘠就腴,是畲民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集韵·麻韵》:“畲,火种也。”《广韵·麻韵》:“畲,烧榛种田。”“畲”字还指开垦过二三年的田地。《尔雅·释地》:“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畲。”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互为因果。畲民食尽一山,两三年后则他徙。因为他们靠山吃山,所以自称山哈、山客;因为刀耕火种,所以又称“畲客”。“畲”字还有一个写法作“”(广东俗字),檀萃《说蛮》解释说:“,巢居也。”所谓巢居就是在山林中搭寮架棚为居所。从粤东到闽西,再到闽中,再到闽东,畲族这种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在粤东,畲民“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①。
在闽西,畲民“随山种插,去瘠就腴,多于深山中编荻架茅为居,善射猎”②。
在闽中,“畲民巢居崖处,射猎其业,耕山而食,率二三岁一徙”③。
在闽东,“畲民崖处巢居,耕山而食,去瘠就腴,率数岁一徙”④。
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进士、长乐人谢肇涮为我们留下了一段关于畲民烧山的现场记录:“既过胡坪(今霞浦水门武坪),值畲人纵火焚山,西风急甚,竹木迸爆如霹雳。舆者犯裂〔烈〕焰而驰,下山回望,十里为灰矣。”⑤
其实烧山火耕的生产方式汉族也有。古诗中早有汉民烧畲的佳句,如“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陶潜《和刘柴桑》);“煮酒为盐速,烧畲度地偏”(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宝客一百韵》);“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刘禹锡《竹枝词之九》)。直到20世纪70年代,笔者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时还多次与当地村民一道烧过“畲”,当地村民叫做“烧园坪”:在离村落偏远的山上,烧出“园坪”一片,以所烧的草木灰为肥,种植薯类或其他耐旱作物(多是杂粮),两三年后地力衰退,就抛荒了。不同的是谢肇淛笔下的畲人烧山是将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捆绑在一起,待地力退后,他们就会弃寮迁移,另择新地。
进入闽东后,畲民仍然在继续频繁地流徙。有在县内,也有在县际;还有一部分继续北上浙江,或不久后又回迁闽东。《丽水畲族志》记述:“今调查统计,由福建入迁处州的蓝、雷、钟三姓有35支,由福建迁居浙江平阳、瑞安、杭州钱塘(今萧山县)等地后分迁来的7支,共计42支,他们散居于丽水地区的9个县市。……另有9支族返迁福建。”⑥
畲民“在漫长的流徙过程中,每经过一个地方并没有全数迁走,迁走的只是一部分,其余仍在原处安居下来,故迁移沿线都有畲民住居”①。这样一来,畲族的分布越来越分散,后来的许多畲村大多是由一人一户发族。福安“山头庄钟姓畲族……原有5个兄弟,一个来山头庄,一个在双江坑门里,一个住林洋,另外两个去宁德。山头庄雷姓畲族系自穆阳迁来的。小岭钟姓畲族系从宁德城郊附近的金村迁来。有三兄弟,一住金,一来小岭,一住头里”②。畲族就是这样形成了今天的“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
畲族进入闽东后,与当地汉族的交往日益频繁。他们从汉族农民身上学到了许多农耕技术,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于是不再留恋昔日的游耕,从而开始了择地定居、以农为业的尝试。这样,一部分畲民依靠自己开垦的少量土地得以生存,更多无地、少地的畲民只好租种汉族地主的田地和官山,成为佃农。
史志上记述,“古田、连江、罗源、福宁、宁德、福安”畲民“布散山泽间,亦受民田以耕,谓平民曰百姓”③,“附近民居在邑之四都上洋等村,(畲民)与民往来交易,亦有承佃民业为生业者”。④租种汉族地主土地者日益增多。山有山租,田有田租,租额一般按其收获量“主佃均分”。付不起地租、无田可耕者只好“仰给于富户雇工”,成为地主的长工、短工。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钟大焜纂修的《颍川钟氏宗谱》载福安正堂准给大林钟姓畲民官山一号的山场执照,申明“五都大林官山一号断归钟盛九等久住管守,山场艺植竹木,栽种生理,岁纳官租银二两加给栖云寺渡夫工食”。该山场历经明清两朝,从万历到光绪共三次更换执照,可谓一脉相承。
畲民定居之后,官府对他们实行了有效管理,并且逐步编甲入籍。“康熙年间钤印州示,内有‘畲民居住山野,专责畲民保长保固地方,烟差照例豁免……’”①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更定清初编置户口牌甲之令,规定“各省山居棚民,按户编册”②。从此以后,清政府对畲民全面实行编甲管理,并且和汉民一样承担照章完粮义务,标志着畲民从此彻底告别了游耕,封建关系在畲族社区完全确立。
三、垦荒种山——融入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
根据推算,乾隆中期(18世纪后期)福安县畲民约有1.4万人,在今之闽东范围内当有畲民4万多人。③
人数如此之多的新移民,怀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景,散布在闽东的茫茫山野,无疑对这一片土地的进一步开发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尤其必须指出的是由于畲族妇女和男子一样参加劳动,使畲族的劳动生产能力大大超过周边相同户数的汉族原住民。史料中关于畲族妇女参加劳动的记述可谓比比皆是:“吾族本畲民,男女耕作,自古如斯。”④“畲民……男女杂作,以远近为伍,性多淳朴,短衫跣足。”⑤“畲民……男耕女磕,恪守法纪,其风俗近古。”⑥……
广大畲民定居闽东以后,主动融入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垦荒种山是他们最基本的谋生手段,和周边的汉民一样,他们主要是种植禾稻、蓝靛、苎麻、甘薯等。
南宋以后,随着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南移、北方汉人大批南迁,福建人口在原有的基础上迅速膨胀,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人们在围海造田的同时也更加重视山区的进一步开发。“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尽力耕”①,“深山穷谷,人迹所不到,往往有民居,田园水竹,鸡犬之音相闻”②是当时的写照。到了明清,闽东大地已经开发得很充分。许多新到的畲民只好到自然条件更为艰苦的高寒山区,开山辟田。这些地方山高水冷,路途遥远,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畲民多居住高山斜坡上,耕种着梯田。耕地分水田和农地二种,水田较农地为多。水田约占耕地总面积的90%—95%。……梯田山高水冷,土浅砂多,山道崎岖,交通不便,因此种植农作物花工大,产量低。据了解,一亩水稻从种到收,需要30—40个工作日,而每亩水稻产谷200—250斤,300斤以上也有,差的不到100斤。”③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所以“农田耕作,极为粗放,水田都只二犁二耙……原始刀耕火种的残余尚留存在耕种之中。1亩水田,种子6斤,插1300株秧苗,故当时就以1300株为1亩。……畲民田园,多为梯田,靠近溪涧能经常灌溉的不多……‘久晴则怕旱,久雨则怕涝’。水利设备极差,无水坝,亦无水渠,顶多只在溪涧水源地方安上竹筒,疏导灌溉,其法十分原始”④。
为解高山梯田水冷、地瘠、耗工、低产之虞,山区农民培植了一种称作山稻或园稻的旱稻。明万历《福安县志》云:福安“又有一种山稻,畲人种于山坞”⑤。这种稻谷适合在山上旱地种植,因多为畲民所种,所以又被称作“畲稻”。畲民“所开土地,叫做‘畲田’……当地群众多称他们为‘畲客’或‘山客’,本无恶意”⑥。
蓝靛也叫青靛,闽东人又叫“菁”。这是一种可以提取蓝色染料的草本植物。明代以来,东南沿海的纺织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对蓝靛的需求激增;“福建菁”已名闻全国,尤以汀州为最,所以有“福州西南,蓝甲天下”之说。因社会生活需要,而且种菁获利颇丰,闽东各县早有种植。万历《福安县志》在《土产》目下就列有“靛”。乾隆《宁德县志》云:“邑以种菁为业者,大抵汀人也”,“如西乡几都,菁客盈千”。①说明当时有大批汀州人到闽东种菁,其中应该有许多畲民。入迁闽东的畲民,因擅种蓝靛,也被称为“菁客”,他们居住的村落被称为“菁寮”;今福鼎前岐还有一个叫做“菁寮”的畲村。
苎麻纤维细长,平滑而又有丝光,质轻而拉力强,吸湿易干又易散热,染色容易褪色难,历来是闽东山区寻常百姓主要的衣着用料,社会需求量相当大。直到20世纪70年代,闽东广大的山乡农民无论畲汉,每人至少还有一两件苎麻布制成的被称作“粗衫”的劳动服。由于气候和土质的原因,闽东和浙南广袤的山区成了苎麻的理想家园,山民都擅此业。种苎,制苎,直至织成苎布,“一条龙”做到底,自给自足。明末寿宁知县冯梦龙曾有过如此的描述:(寿民)“近得苎麻之利,走龙泉、庆元、云和之境如鹜。……苎山亦称麻山,一年三熟,谓之‘三季’。富者买山,贫者为佣,中人则自力其地”②。
种苎与种菁关系甚大,种菁种苎之利数倍于种粮,不少乡民因而致富。清代闽东靛菁除为本地所产苎布着色外,大多销往江浙。此业乾嘉年间(1736—1820年)最盛,同光(1862—1908年)以后,“西洋之靛竞进,力比土靛强二十倍。土靛十二斤半仅当彼之十两,色泽较鲜而价较廉,而土靛遂一败涂地”③。传统的种苎和种靛业遂走向败落。
和汉族山民一样,畲民也擅苎业。差不多每家每户都有织布机,畲民称为“楠机”(nóng gū)。“织麻布是畲族妇女的专长,家庭人口多的一年要织70—80尺,人口少的织30—40尺,原料都是自己种的苎麻,有少量黄麻。麻布都是作外衣备户外劳动之用。……没有出卖的,穿时都染成青、蓝色。”④苎麻丝织成的布叫做“苎布”、“緕布”、“夏布”。乾隆《福宁府志》称:“夏布之属以福安为上。”①这恐怕与福安畲族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种苎者最多不无关系。
清初,抗清英雄、福安进士刘中藻“选练精兵”,“取于苎寮、菁寮、畲寮”,在“崎岖山谷,聚众万人,遂复庆元、泰顺、寿宁、宁德、福安、古田、罗源诸县”。②此“三寮”之民的主体应是畲族,收复的庆元等七县都是畲族聚居的区域。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畲民所从事的生产劳动内容、基本的生活状况。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长乐华侨陈振龙父子从菲律宾引进甘薯(番薯)苗,经福建巡抚金学曾的大力提倡,开始在福建各地普遍种植。甘薯初一传入便充分表现出耐旱高产的优秀品质,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成为山区人民(包括畲民)的主粮。《福安县志》云:“山田硗确,不任菑畲者,悉种薯蓣以佐粒食,贫民尤利赖焉。”③“薯蓣”即甘薯,“粒食”指米谷。闽东大地山多地少,从此甘薯成为山区人民的主粮,在粮食作物中其地位仅次于水稻。畲汉人民不断地对甘薯品种进行改良,以保证持续高产。到民国时期福安就有李薯、蕹菜薯、苦瓜薯、红薯、牛底薯、冰糖薯、台湾薯等品种。④
畲民靠山吃山。除种植业外,采薪烧炭也是畲民的一项重要的生产劳动内容和经济来源。20世纪前期的闽东,每50公斤柴片大约可换2.5公斤稻谷,每50公斤木炭大约可换10公斤稻谷。畲民常以采薪烧炭换取生活所需。柴薪除松木、杂木片外还有杂木树枝和“细芒”(覆盖山体的芒萁草)。直到20世纪后期“厨房革命”(告别柴草,以液化石油汽或电力为燃料)之前,每天上午在城镇的集市上依然可以看到成群的山民(主要是畲民)挑着薪炭待沽的身影。
定居的农耕生活使畲民与当地汉族融为一体,并且在保留自己主要传统的同时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在政治和文教方面与汉族有了相同的追求。
在耕读文化的氛围中,一些畲族村落也设立私塾,延师授课;一些畲族知识分子经过自身的刻苦努力,取得了令人刮目的成就,跻身于上流社会;还出现了像古田的富达、霞浦的白露坑等畲族文化名村。封建社会的主流观念和价值取向深深地影响着畲民,众多畲族宗谱中的“族规”、“家范”都对子孙后代规定了许多充满儒家理念的处世原则,下面这则被称为“圣谕十六条”的教训①颇具代表性:
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里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
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律法以警愚顽;
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
戒逃匿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
畲族同胞就是这样以自己的聪明智慧和超人的吃苦耐劳为闽东山区的进一步开发和文明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并以千年的时光,和当地汉族一道谱写了一曲民族大团结、大融合的壮丽乐章。
附注
①闽东在1971年以前称福安专区,此后称宁德地区;2000年11月以后称宁德市。1983年以前的闽东曾包括罗源、连江两县。本文所称“闽东”一般指1983年以后的宁德地区(市)范围。
②宁德地区方志委:《宁德地区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8页。
①《明会典》卷17《户部·田土》。
②《洪武实录》卷243。
③李健民:《闽东畲族村居分布格局的形成》,《畲族文化研究论丛:2005全国畲族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5页。
④《清世祖实录》卷43。
⑤这是一副被称为“御赐”的畲族专用对联,浓缩了畲民对始祖传说的认知传承,表达了畲民的民族自豪感和为中华帝国建功立业的价值取向。多见于畲族宗谱和祠堂、民居的中堂。
蓝、雷、钟三姓最后一个支系迁入闽东的情况(不含在闽东县际县内的迁移)如下表:福安霞浦福鼎宁德蓝姓迁入时间清康熙年间清乾隆年间清乾隆三十一年清乾隆年间迁出地汀州庐丰浙江平阳朱山浙江平阳祭头罗源梅树坑村连江外窑村迁入地上白石聚仙岗村牙城第一层桐山麻坑里七都三阳镇飞鸾新岩村雷迁入时间明成化二年清乾隆初年清乾隆五十六年清乾隆年间迁出地福州方向浙江南部浙江泰顺吴家墩罗源文院、松山半山村姓迁入地十都官湖 (后转迁后门坪)福宁下四都草岗 (今水门茶岗)白琳棋盘坑虎三际坑院后,飞鸾南山向阳里钟迁入时间明景泰年间明万历十四年清雍正三年迁出地金溪玉林浙江平阳三十三都凤池溪边汀州武平姓迁入地西门外五都眠山岗 (后转迁大林)桥亭洋心宁德县斑竹村资料来源 《福安畲族志》《霞浦县畲族志》《福鼎县畲族志》《宁德市畲族志》①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十七册《广东上·博罗县》。
②(清)李拔:《汀州府志》卷45《丛谈附》。
③明万历《永春县志》卷2《风俗》。
④卞宝第:《闽峤〓轩录》卷1《霞浦县》。
⑤(明)谢肇淛:《长溪琐语》。
⑥《丽水地区畲族志》,电子工业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0页。
①陈元煦、蒋炳钊等:《福建福鼎县畲族情况调查,1958年》,《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8页。
②施联朱等:《福建福安县甘棠乡山岭联社畲族,1958年》,《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3页。
③(清)张景祁:《福安县志》卷38《杂记》。
④(清)辛竟可:《古田县志》卷2《风俗·畲民附》。
①乾隆三十九年福宁府告示,见福安甘棠田螺园畲族村《雷氏宗谱》。
②《清史稿》卷120。
③ 李健明:《闽东畲族村居分布格局的形成》,《畲族文化研究论丛:2005全国畲族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3页。
④福安康厝东山畲族村《雷氏族谱》。
⑤(清)张景祁:《福安县志》卷38《杂记》。
⑥福鼎《蓝氏宗谱》,《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3页。
①(宋)方勺:《泊宅编》卷中引朱行中知泉州诗。
②(宋)李纲:《桃源行诗序》,《梁溪集》卷12。
③《福建福安县畲族情况调查,1958年》,《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36页。
④《福建福鼎县畲族情况调查,1958年》,《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66页。
⑤(明)陆以载:《福安县志》第1卷《舆地志·土产》。
⑥《福建福安县畲族情况调查,1958年》,《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34页。
①(清)卢建其:《宁德县志》卷1《舆地志·物产》。
②(明)冯梦龙:《寿宁待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页。
③民国《霞浦县志》。
④《畲族社会历史调查》,转引自俞郁田《霞浦畲族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①(清)李拔:《福宁府志》卷14下《学校·风俗》。
②《思文大纪》卷6《痛史》第六种;又见张景祁《福安县志》卷22《人物》。
③(清)张景祁:《福安县志》卷7《物产》。
④〔西〕冯意纳爵(Ignacio Ibanez)、高大涵(Blas Cornejo):《班华字典·福安方言》“Camote”条,商务印书馆1941—1943年版。
①福安甘棠田螺园畲族村《雷氏宗谱》。
相关地名
闽侯县
相关地名
汀州镇
相关地名
上杭县
相关地名
北宋镇
相关地名
坂中畲族乡
相关地名
滨海县
相关地名
临江市
相关地名
福鼎市
相关地名
福州市
相关地名
宁德市
相关地名
罗源县
相关地名
霞浦县
相关地名
大林镇
相关地名
寿宁县
相关地名
崇儒畲族乡
相关地名
浙江省
相关地名
泰顺县
相关地名
武平县
相关地名
连江县
相关地名
平阳县
相关地名
马鼻镇
相关地名
南宋乡
相关地名
新田县
相关地名
广东省
相关地名
长乐区
相关地名
福建省
相关地名
瑞安市
相关地名
杭州市
相关地名
钱塘区
相关地名
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
相关地名
穆阳镇
相关地名
官山镇
相关地名
西乡县
相关地名
前岐镇
相关地名
龙泉市
相关地名
庆元县
相关地名
云和县
相关地名
台湾省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