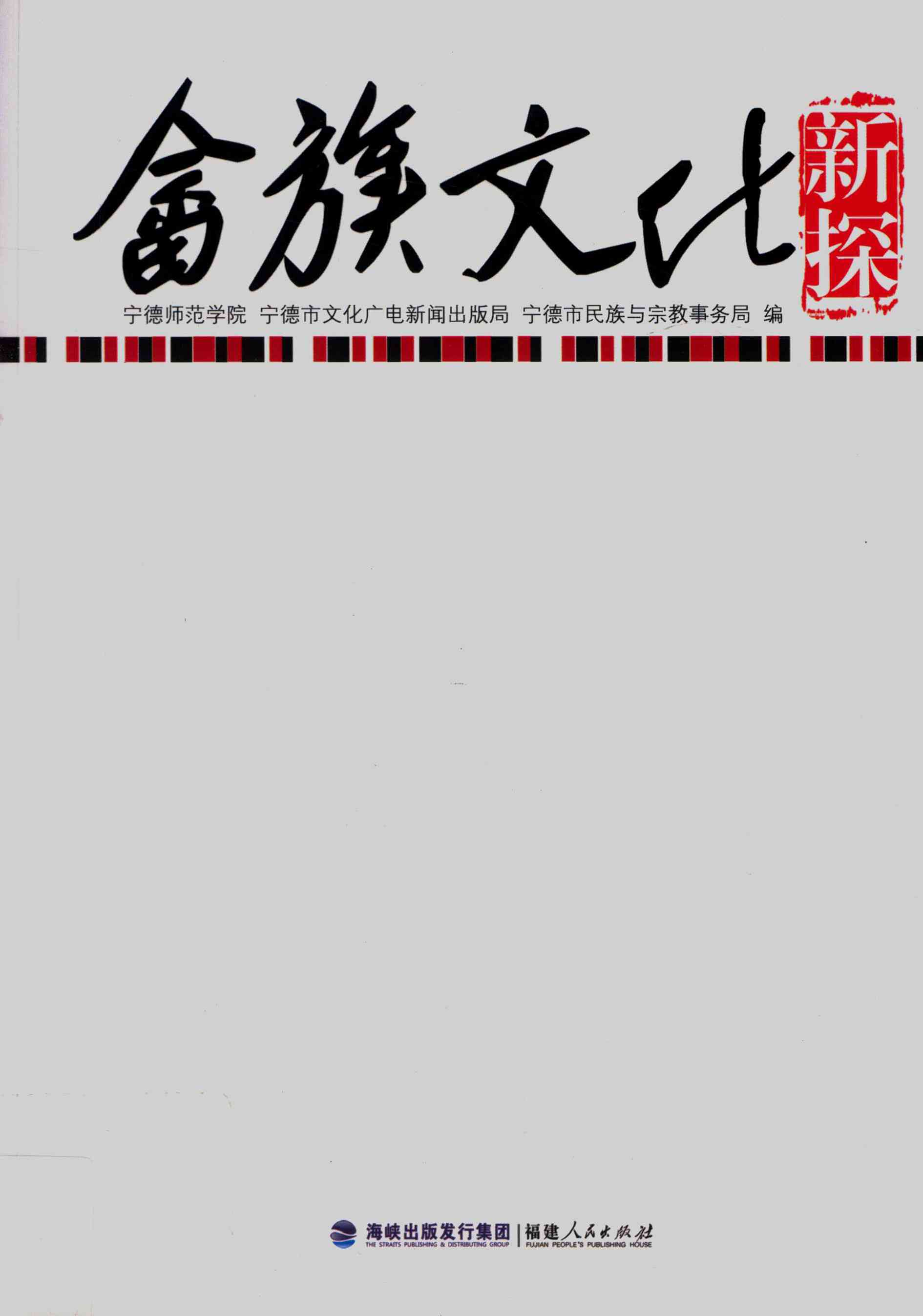内容
从明嘉靖“倭寇”的大肆侵掠到清初迁界的巨大反复,促成畲民大量入迁闽东北滨海丘陵地区,形成“滨海畲族”。这是中国东南族群分布格局的一大变动。在新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中,畲族文化逐渐展现若干新质,如生产生活方式中海元素的渗入;原有信仰体系与陈靖姑信仰的交相作用;儒家思想的浸润和牵引;民族—家族企业运营的新经验;族群权益意识和维权实践的初步表现等等,都是很值得注意的。
一、“滨海畲族”概念的提出
清初以来,畲族分布格局发生一个显著变化,闽东北逐渐成为这个族群的最集中的栖息地。闽东北共有11个畲族乡,从南至北分属连江、罗源、宁德(今蕉城区)、霞浦、福安、福鼎等6个沿海县份。现在的宁德市9个县(市、区),其中4个在沿海。宁德市有9个畲族乡,全部分布在沿海县份。蕉城(原为宁德县)的金涵,福鼎的硖门和佳阳,霞浦的盐田和水门,就在海边。福安的坂中、康厝和穆云,离海边有点距离,但也在长溪中游的主支流(穆阳溪)上,与长溪在福安入海处的几个港口大镇水路相通,情况有些类似于福州疍民之沿闽江而一路迁徙到上游的南平、建瓯、邵武和将乐(参见“维基百科”网的“福州疍民分布图”),只是他们离海比闽北疍民近得多。崇儒畲族乡距海稍远,但它所在霞浦县正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县份。
宁德市现有234个畲族村委会,其中沿海4个县份共有215个,占总数的91.88%;即使扣除沿海县份中离海稍远的畲族建制村,包括蕉城赤溪镇(2村),福安潭头、上白石和社口三镇(12村),霞浦崇儒、柏洋二乡(10村),福鼎管阳、蟠溪二镇(5村),仍有186个建制村,占总数的79.49%。①
如果从最为散漫的人口自然分布角度看,缪品枚在《畲族与闽东传统文化》一文中指出,沿海畲族人口占闽东畲族人口总数的44.26%。②缪文未交代统计口径,这里不便复核。新近发表的赖艳华《闽东畲族居住格局初探》一文,把闽东畲族人口分布划分为三大聚居区:福安交溪(应称作长溪)流域,福鼎、霞浦、蕉城(原宁德县)沿海一带,古田溪水库周边及水口水库上游;指出鼎(福鼎)、霞(霞浦)、蕉(宁德蕉城)三县(市)沿海一带畲族人口为70533人(已扣除崇儒),占闽东畲族人口的44.48%。③但拙文只就“滨海畲族”一点来考察,应当将赖文中长溪下半段5个乡镇的畲族人口划入统计范围(包括赛岐镇1919人,溪柄镇3349人,甘棠镇6324人,下白石镇4944人,湾坞乡2852人),则为89921人,所占百分比为57.13%。而按笔者的视角,如前文所述,长溪中游的坂中(7400人)、韩阳(2106人)、城阳(2928人)三地和其主要支流穆阳溪中段的穆云(7286人)、康厝(5503人)、溪潭(4285人)三乡镇都距海口不远,旧时通航条件很好,海船的客、货换乘溪船,可以顺利运抵长溪中游两岸④,这里的畲族其实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滨海性”,如果把这29508人也作为“准滨海人”来理解,所占比例就更高了。
据此,笔者提出“滨海畲族”这一概念。
当然,仅仅止于这些“事实”,还不足以籀绎出科学概念。我们并不必要在“畲族”之外再杜撰诸如“山地畲族”、“游耕畲族”之类新名词。我们创设概念,是要标示事物的分异和新质。现在大家常说全国畲族一半以上在福建,福建畲族一半以上在宁德市。“滨海畲族”则意在凸显这个散居民族的最大聚居区的地理特征,如上文所述,不仅宁德市是一个滨海城市,而且从人口自然分布到畲村聚落分布再到畲族乡行政性分布,统计单位的层级越高,畲族滨海意味越强(57.13%→79.49%→100%)。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有关民政、民族领导部门便以福建沿海为汉族地区等理由而对原为少数民族的“疍民”作出已经“汉化”、不再是少数民族的认定。民族政策对民族发展有很强的规整导向作用,疍民渐渐地而又很快地真的不成其为少数民族了。在这种形势下,“滨海畲族”更可谓是我国东南地区族群生态结构的一个巨大异数。
应当说明的是,本文本节及下一节的阐述,受手头材料限制,侧重于分析现在宁德市的情形,特别是对于乡村、人口、河流的数据使用方面,尤其如此。实际上,闽东北“滨海畲族”的指称范围,应当包括宁德邻境的罗源、连江二县,它们在孙吴至初唐四百多年间本同属一县,现在的地表形态和族群生态仍具有很大的一致性。
二、造就“滨海畲族”的历史机缘
“滨海畲族”的形成,或者说相对弱势、落后的畲族人口竟然在相对强势、先进的汉族地区,在汉族本身人地关系已显紧张的福建沿海地区大规模集结,与其强调它的必然性,不如说这需要一种很特殊的历史机缘。这个特殊历史机缘,笔者以为主要是明嘉靖后半叶二十余年“倭寇”连续大肆侵掠和清顺治、康熙之交二三十年间从禁海迁界到复界招徕的巨大反复。
关于晚明倭患与畲民入迁闽东北滨海丘陵的关系,由于史料欠缺,此前学界不见涉及。本文也无力深究,只是提出一个初步的考察,希望能够引起注意。
检读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刊本《宁德县志》卷一《舆地志·物产·货属》,发现在“菁靛”目下引有一条“旧志”的按语:
本县山场,无论城郭乡村,除附近庐舍坟墓者始为民业,高山深谷俱官山也。嘉靖初年,外郡人来县境栽菁,俱告于官,官则随山按户,置簿收租。自辛酉(公元1561年)倭变之后,官簿无存,土豪年估其租。今考本县州籍,民山并无分抄,悉属官山,尚存官山三顷二十亩九分之税匀派于通县,而利独归于数家。种菁之户,若仿故事,召各乡菁牙、菁客,随其众寡;置簿收租,归之公家,未为不可。然
在当时,则属豪强私占。而此日,承平已久,彼此授受买山者多矣。检核旧志,至“利独归于数家”之前,文字大抵照抄万历十七年(1589年)旧志;之后,掺入新志编纂者的意思;末句则为乾隆年间(1736—1795年)的地权状况。闽东北的菁客中,有不少畲民。他们在官山垦植,必须向官府办理登记手续,按章交纳租税。根据这则记事,嘉靖四十年辛酉年(1561年)“倭寇”攻陷宁德县城,税收档案被毁无存,改由地方豪强粗估租额。并且渐渐地,地权关系也发生变化,彼此买卖山林的行为屡有发生。那么,一些靠种菁积攒了一些钱财的畲民便可以在滨海山林卜地居家,乃至衍为村落。
福安也曾在此前两年的农历四月被攻破县城,倭寇进城烧杀抢掠整整四天,时人称“嘉靖己未福安井邑一烬于倭”①。半年后,新授知县卢仲佃赴任,见到的仍是“荆棘满城,灰烬遍市,二百载烟火辏集之区,一旦荒墟”②的景况。而福安正是后来闽东北畲民人口最多的县份。
缪品枚统计闽东北现存蓝、雷、钟三姓族谱,有明一代入迁者有30支之多(不含宁德设区市属各县间的互迁),其中洪武1,永乐2,景泰1,天顺4,成化1,嘉靖1,隆庆1,万历7,天启2,崇祯9,具体时间不详。③那么,大倭患后迁入闽东的畲民(20支)占到明代各朝总数(29支)的69%。缪文以为明代畲族大量迁入的历史契机在于当时纺织业发展对于蓝靛染料的需求,此说不为无见。只是在总体上明代福建人口压力已经很大的情况下,大量菁客要从临时搭寮租山赁种,改换为纷纷“卜筑”兴村,没有一个大的人地关系变动,恐怕不能成气候。嘉靖十七年(1538年)以来,倭寇频频侵扰闽东北滨海地区,本土原居民死伤逃离严重,加上前述官府地簿税册的破坏,与畲民买山定居之间应当是有内在联系的。至于这个问题所涉历史关节,尚有若干未明之处,容另文再考。
畲民入迁闽东北的更大的历史机缘,在于清初的迁界、复界政策。为了隔绝祖国大陆与台湾拥明政权的联系而实行的禁海和迁界,使人口繁盛的东南沿海三十里内外成为不见人烟的废墟,但客观上为畲族预备了一个广阔的去处,朝廷复界以后,畲民便和许多汉人一样络绎迁入。关于清初闽东的迁界、复界和畲族居住格局变化的基本情况,前引缪品枚文已经做过比较具体的描述,这里不必多说。
本文仅补充说明两点。
其一,复界后,福建畲族比较集中地迁居今日宁德市境内(包括邻境的罗源和连江),当与闽东北滨海区域的地表形态有密切关系。闽东北的地表形态与整个福建的情况,同中有异。例如,多山,溪河多独流入海,山岭纵横河道交错的结果,是把大地分划成许多“格子状”的小单位,“格子”与“格子”之间能够相互联系,但不便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整个福建大体如此,而闽东北的地形要更“细碎”些,除了古田溪与闽江可以相通,这里的河流都自成格局,交溪为福建第五大河,霍童溪为福建第七大河,全区24条较大河流的流域总面积可以占到全部土地面积的将近89%。而且陡峭的丘陵直接延伸到海中,形成全国曲折度最大的一长段海岸线。这与闽东南较多滨海小平原是很不相同的。闽东南的地理条件比较优越,人口繁衍快,人地关系更紧张,汉族势力也更大。畲族在这里更难插足和立足,插上足的,接受汉族文化影响的速度也更快。而闽东北滨海地带亦山亦海、山在海中的特点,可以使初迁的山地畲民更快适应环境,在海滨丘陵从事传统的生产活动。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是,我国东南地区这次族群居住格局大变动发生在清代,而在某种程度上,清代正是传统时代畲族接受汉族文化影响的总结期,也是畲族文化的定型期,一族群在与他族群的接触和交流中澄明自身是文化史上常见的事。我很赞同蓝炯熹的一个看法:我们今天所能看到所能讨论的畲族传统文化,只能是经过有清一代的发展而定型的畲族文化。当然,清代以前已经有畲民,已经有畲民文化,尤其是南宋以来关于畲民开始有越来越频繁的文献记载,可是这些记载大都很简单,印象式的勾勒多,实证性的记录少,有的陈陈相因,不能提供新的信息,我们对宋、元、明畲族文化的把握,除了个别特征(如畲军等),其余的与苗、瑶、疍、客的分别还不够清晰,这个族群的个性文化面目还比较模糊。这也使学界对畲族形成时间、源流衍化、迁徙路线、文化核心特质等的判断容易产生分歧,有些问题至今不能达成共识。若先以文献、实物、口述材料较丰富、现实生活中遗留的痕迹也较明显的清代畲族文化样态为基点,再作前溯或后察,也许会有一些新的收获。
我们把目光收拢在清代闽东北滨海地带这个正处畲族文化重要定型期的族群集中聚居区,不难发现这里这时的畲族在经济生活、文化面相、公共治理、族群认同等方面都在渐渐发生一些意义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基本趋势,是加速采借与他们混居、邻居的汉族社会的先进经验,从而不无受阻但终归是要缓慢地适应和融入与相对强势的汉族和平共处之中(族群间的交往,即使是明显有着先进、欠先进之分的族群间交往,其文化影响也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当然也不会是均衡施受的,这是我们在沿用“汉化”一类词语时应当心存儆醒的)。
三、我国东南族群分布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动
畲民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段里大量迁徙到当时人口还不太密集的闽东北并定居下来,造成了这一地带乃至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族群生态结构的重要变动。以下对此略加分说。
其一,从畲民的歌谣、族谱两大载体中所提供的历史记忆,结合现代畲族人口分布情况,我们大体可以认为,这个族群的核心集居地,经历了从潮州到汀、漳再到福宁府的变化过程。这个表述和学术界的主流看法,差异或许不大。但笔者借此想要进而指出,从严格一些的判断标准来看,在“潮州中心期”,畲民的文化特点尚未与东南地区诸多山夷峒蛮清晰地区分开来,尤其未与同有盘瓠崇拜、同有“皇赐券牒”、且有共同姓氏和相似语言的瑶族清晰地区分开来,而当时的文书、方志也往往以瑶、畲联称或以猺、徭代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汀、漳中心期”。在“汀、漳中心期”,畲民农业经济从游耕趋于定耕,与同在深山老林的客家人共处渐密,相互影响渐多,宗族观念日益强化,他们与瑶族的区分则随着地块上的愈行愈远而逐渐增大起来。这时候常见的则是畲、客混称或联称。到了中晚清的“福宁府中心期”,畲民确立了定耕、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建宗祠、修族谱,参加科考,在受汉族文化影响越来越深的同时,注意持守自身的特色文化元素,至此,一个与汉族文化相区别的少数族群——畲族的建构过程基本完成,成为现代我国东南地区唯一的相对聚居的少数族群。
其二,根据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在畲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两个地理空间值得关注:一是公元7世纪以来的闽粤赣交界地区,二是元明清的闽浙赣交界地区”①。需要强调的是,由于粤、浙的介入,前后两个时期的赣和闽,所指并非同一地块。前期的“赣”,主要是今天的赣南地区;后期的“赣”,主要是今天的上饶地区(本文不拟涉及赣省族群结构变化问题)。前期的“闽”,主要指闽西,后期的“闽”,主要指闽东北。这是闽省少数族群的两大“高地”。谢重光主张客家和畲族都形成于两宋时期。他认为,在闽西,客家是“民族融合的主导力量”,到宋元之际,畲、客融合进程大大加速,“这一进程的主导方面是畲族被同化为客家,少数未被同化的畲民要么退进更深的大山中,要么被迫向别处迁移”②。迁移的去向,从后来的史实考察,大抵是先到闽东南,再迁闽东北,其中一部分又由闽东北而入浙或入赣。
畲族大量迁入闽东北后,建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聚居村落,也成为当地有相当势力的族群。陈支平分析罗源雷姓畲族的九件契约文书内容,得出的结论之一是清代闽东畲民与朝廷、与汉族的关系都比较平和、比较正常,所谓“汉族地主阶级和封建政权的剥削和压迫,缺乏史实上的强有力印证”①。
那么,闽东北地区客家的情况如何呢?目前这方面的资料极为缺乏,也未见到相关研究成果。这里仅从方言分布角度作一点简单的说明。
闽东北(这里指今宁德市)的汉语方言,总体上属闽方言福州话,其中古田、屏南二县为南片区,其余七县为北片区。也存在少数几种方言岛,其中汀州话(客家话)主要通行于古田凤都镇的后溪、珠溪二村(约5000人),霞浦县州洋乡的福鼎楼自然村(300多人),柘荣县城郊乡的倒龙山村(100多人),还有福安市社口乡的首觅村和溪潭乡的濑尾村、福鼎市磻溪镇的赤溪村和点头镇的观洋村以及寿宁县西南角个别自然村(平溪乡三角洋、云务坑、白岩下、彭地)也讲客家话,以上总数不及6000人,②所占人口比例极低,已经远非闽东北客家分布的原貌。而且其主体部分,即后溪、珠洋二村也已成为双语区,兼说古田话了。这表明在闽省的两大少数族群聚居区存在“客”进“畲”退,“畲”进“客”退的情势。在闽西,客家势力强大,20世纪50年代以后,尤其是80年代以后,在国家“民族优惠政策”的影响下,一部分畲姓客家人自愿恢复了畲族身份,但仍有一定数量的畲姓人口不愿意改变客家的身份。而在闽东,畲族并非主导族群,这里的客家人一般不想也不能改属畲族,久而久之,逐渐与当地一般汉族趋同,客家文化特征逐渐淡化。
从以上所述,我们对闽东北的族群分布结构的变迁,形成这样一个总体印象:明清以前,由于历代特别是中唐五代和两宋之交大批中原汉人络绎南下,与当地土著逐渐融合;疍民虽然具有鲜明文化特色,但他们是水上人家,所以这里的族群结构比较简单。明代以后特别是在有清一代,畲民频繁入迁,很快适应环境,立下脚跟,发展壮大。而由于福建客家人早在闽西一带建立了大本营,少量迁入闽东的,难以持守和发扬其固有传统;疍民又无权上岸生活,畲民便成为闽东北除汉族以外最主要的族群。
四、闽东滨海畲村群的形成
闽东北山海环抱,远离喧嚣,百姓生活历来“不贾而足,虽荒岁不饥”①,很少受到兵革动乱的冲击。但如上所述,从明代中叶到清初的百余年间,却接连遭受“倭寇”之洗劫、南明清军之激战、“迁海开界”之反复,沿海遂常有荒残之地,畲人得以离开深山临时搭盖的草寮而入居,渐由游耕转为定耕,建房兴村。这些畲村,多数海拔不高。现有的234个畲族建制村,笔者查得212村海拔情况,兹将闽东沿海县份和山区县份各海拔高程(单位:米)的村数(单位:个)列示如下:
说明:(1)材料主要采自前揭《闽东畲族文化全书·乡村卷》(189村),其余采自蓝运全、缪品枚主编《闽东畲族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俞郁田编《霞浦畲族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蓝纯干主编《宁德市(今蕉城区)畲族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2)海拔高程数据,“100以下”含100,“100—200”指100 以畲族建制村作为统计标准,有它的局限性,不能全面反映包括自然村在内的海拔情况,而且村落规模存在古今差异,当年的“主村”未必都会成为今日的建制村,反之亦然。但就总体而言,上表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闽东北畲族聚居村的海拔分布格局:海拔较高的畲村,集中在山区县,但总数无多;沿海地区畲村多,且海拔不比同区的汉族山村高,也不比它们偏僻,典型者,如福安溪潭镇,共有11个畲族建制村,仅瓜溪海拔230米,张家山海拔160米,其余都在70米以下,其中6村在10—30米之间。它们只有一村为纯畲族村,而十个畲、汉杂居村,一半畲族人口多于汉族,一半汉族人口多于畲族。这是以建制村为单位而作的描述,深入到它们所辖的众多自然村,情况会更加复杂些。据《霞浦县畲族志》引述1989年的调查材料,全县畲族聚居的自然村有501个,其中186村畲族人口占90%以上,381村畲族人口占60%以上。①那么,畲族人口比例在60%以下甚至不如汉族人口多的自然村,尚有120个。郭志超指出,与其他地方不同,“闽东畲汉杂居的情形多一些”②。笔者认为,畲汉同村杂居,与这些村庄上述位置特点,当有一定的联系。
闽东畲村群的形成,必须以畲族人口较大数量的繁衍为基础,而相对贫困的畲族人口的繁衍,又必须以获得基本口粮为保障,这就牵涉到明代中晚期以来福建粮食作物结构的一个重大变革。何炳棣早在1956—1957年就为文、著书具体论证美洲粮食作物玉米、番薯、花生和马铃薯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人口增长的巨大作用。③这些农作物后来在畲村也都颇为流行。当然,影响人口数量变化的因素十分复杂,何炳棣还谈到其他经济、行政因素和天灾(旱、涝)、兵灾的影响,但未涉及明清气候变冷问题,周翔鹤、米红对此有所纠补④。仅就闽东北畲村的大片成长而言,那些从美洲传入的不仅平原、而且可以种在丘陵的旱地、瘠土的高产作物,特别是度荒所赖的番薯,使无数贫苦畲民免于死亡,确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件。我们的这个看法,可以在方志的记载中得到印证。
例如,何乔远《闽书》卷150《南产志》引其自撰《番薯赋》载:“其初入吾闽时,值吾闽饥,得是而人足一岁。”
李拔《福宁府志》卷12《食货志·物产》“番薯”条载:“郡本无此种,明万历甲午岁荒,巡抚金学曾从外番丐种归,教民种之以当谷食。”又按语:“迩来生齿日繁,米价渐高,沿海民食,半赖于此。”
卢建其等《宁德县志》卷1《舆地志·物产》载:“(蕃薯)今其用比于稻谷;切而为干,藏以待乏。”
张景祁等《福安县志》卷7《物产》载:“其山田硗确,畲者悉种薯蓣,以佐粮食,贫民尤利赖焉。”
大致说来,番薯对贫民的意义,远重于富民;对畲民的意义,远重于汉民;在灾年的意义,远重于平年。畲民开始大量集结闽东北的时候,机缘巧合,也正是番薯逐渐在这里推广开的时候。当地畲谣:“番薯米,吃到老。”这大大降低了畲民的死亡率。我们不能想象,没有番薯的传入和传播,畲村会像大把明珠般洒落在闽东北大地(仅霞浦县1989年调查,畲族人口占60%以上的自然村就有381个①);也不能想象,从这里会迁出大量畲民到浙南立村安家,使它成为全国第二大畲族分布区。②
五、滨海畲族文化之新质
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的改变,畲汉相邻乃至相杂而居村落格局的出现,促使畲族社会生活逐渐有所变化,产生了一些文化新质。
其一,生产生活方式中的海元素的渗入。闽东北有些畲村就在海边,如福安下白石镇的长坑、坑门、樟澳诸村,湾坞乡的半屿村;霞浦牙城镇的凤江村,溪南镇的后慕、小马、炉坑诸村,盐田乡的南塘、姚澳诸村,北壁乡的盘前村,松港街道的大沙村;福鼎佳阳乡的象阳、罗唇诸村;蕉城漳湾镇的雷东、又加塘诸村,八都镇的金垂村,等等。半屿所辖的鹳屿和小马所辖的竹江两个畲族自然村,还在海中的小岛屿上。这些村子往往都有大片的滩涂,可以于农业之外兼营小海渔业,现在还发展了多种海产品养殖业。③不过,海边畲村数量不多,而且闽东北的汉民的海洋利用方式,传统的也是以海为田,作为农业的一种空间延伸,畲民更是如此。它对族群文化品性的影响,不宜估计过高。
其二,原有信仰与本地神明间的互动。畲族多元崇拜,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接受当地民族村民所信奉的“神明”。闽东富有特色的民间信仰,以陈靖姑和林公大王最为通行。据传,林公大王实有其人,名祖亘(也单称亘),善于搏虎,祖殿在今周宁玛坑乡杉洋村,建于明中叶(成化年间),后遍及闽东北。畲民主要供作猎神和村庄保护神。陈靖姑信仰与畲民巫术文化则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契合,二者同属“闾山教”谱系,在畲族巫师科仪唱本中,恭请陈靖姑行罡作法都是一项核心内容。有畲族学者认为,陈靖姑等三奶夫人实际上“已经具备了作为畲族内部神灵的资质”,在明清陈靖姑信仰的造神运动中,“大量迁入闽东方言区的畲族也参与其事,其中畲族巫师扮演了重要而特殊的角色”①。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可以看作是汉、畲两种文化在交流碰撞中产生文化新质的一个例子。
其三,儒家思想的浸润与牵引。畲族文化以蛮、越为底色,与儒家观念位差过大,两者原本难以相合。但到了前文所指的汀、漳中心期,畲、客往往同在一山,这两大边缘族群接触较密切,文化上发生初步交流,彼此都受到对方的影响。②而闽东北为丘陵沿海地带,海岸线绵长却富含内陆品性,且区位僻远,与浙江当时比较落后的温、处地区紧紧相连,这里的汉族,社会发展水平不很高,但朱熹理学在民间有一定的传播。畲族入迁时,二者的文化位差已有所缩小,加上这里人口密度比闽西高,村间及至村内畲汉杂居势不可免,文化采借逐渐从器物、技术层面上升到价值取向。霞浦白露坑半月里是著名的畲族文化名村,但房屋、坟墓形制与当地汉族无异,门匾、墓碑都标榜先祖出自中原世家。村陈列室收藏了一双“三寸金莲”绣花鞋。①一座清代秀才大厝在大门内侧还专设女眷过道,不与大厅相通。这其中,有客家文化的印记,也有闽东北汉族文化的影响。闽东北畲族谱牒的谱序、谱论、谱式、谱例,都贯穿着儒家伦理准则。族谱大多是请汉族文士修撰,他们在尊重东家文化基质的同时,也必然带进自己的儒学认知(由畲族读书人自己修谱,情况并无二致)。请人修谱的过程以及自身参加祭谱、阅谱的过程,成为学习儒家学理知识的过程。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由江西萍乡人钟大琨主持,历时7年修成157乡(包括城区居民点和祠堂3处)钟姓连环谱,其中137乡属闽东北沿海三县,加上罗源县6乡,合占总数的95.3%,可见本文指称的“滨海畲族”对谱事的热情和重视,也多少可以反映出儒学家族伦理对他们的影响。在新环境中畲民原来的“善啸聚”、“喜仇杀”的风习也渐渐有所变化。
其四,尝试运营“民族—家族”企业的新经验。到了清代,闽东北成为福建的重要茶区,茶市兴盛。同治十三年(1874年),宁德县八都猴墩村畲民顺应华茶对外贸易形势,开始创办茶庄,收购周边二县数十个畲村的茶叶,形成畲族茶叶专业市场,年销干茶4000多担,并择地开铺,兼营煤油、布匹、海产、山货,雷氏商号闻名遐迩,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繁荣。其主要经验,是农商并举,依靠“畲家阵”之间的相互信任,民族意识与家族伦理融为一体,构建和维护“茶农——猴墩茶市——福州茶叶中心市场”的稳定经济网络②。畲民本不经商,以往他们迁徙所至,也都是偏僻山林之地,农耕气息浓厚。而闽东北在明代就有重商风气。③八都是霍童溪的出海口,水、陆交通条件不错。当咸丰、同治间(1851—1874年)太平军四次入闽,武夷山从陆道运往广州茶叶外贸受阻,福宁府从水道到福州的茶路便迅速代之而起,猴墩畲村遂有机会成为所在一带的茶叶集散地,这里的畲民遂有机会成长为优秀的茶叶商人。
其五,族群权益意识、维权实践的初步表现。不能说畲民在本文指称的潮州中心期和汀漳中心期就没有权益意识和维权实践,①但确实少有记载(这与他们尚处徙居游耕阶段有关),也缺少官府方面在法制框架内的互动。福宁府中心期的情况,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畲民入迁之初,渐渐从游耕过渡到定耕,各地乡保摊派差徭,有无、多少,缺乏统一则例,畲民乍受摊派,特别不服,向地方官府强烈要求“免差徭”。县堂大约考虑到他们偏远零散,人少村贫,尚未站稳脚跟,答应给予宽免,并立碑明示。碑已不存,但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重修的福安甘棠田螺园《冯翊雷氏宗谱》和福鼎华洋(双华)《汝南蓝氏宗谱》②中各保存2篇这种文告,时间跨度为康熙三十七年至嘉庆七年(1698—1802年)。
闽东北畲村编图隶籍以后,征赋摊差相对规范化,畲民维权重点逐渐转向社会治安问题,尤以恶丐强乞与盗贼抢偷最为突出。于是,吁请县衙“出示严禁”,经过批准,畲村在路边勒石立碑,有的还成立巡逻自卫队。③这些碑刻或碑文,现尚存十余通,时间集中在光绪年间(1875—1908年)。常见的评论,把丐、盗骚扰及前述的“免差徭”都归属为“阶级剥削”“民族压迫”,这当然有相当的理据。但总的说来,清代官府对闽东北畲族的政策还是相对比较宽和的。故笔者以为,冲突的发生和展开,与人口压力增大后的资源竞夺、不同族群的文化传统隔阂以及晚清畲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意识的觉醒,也有一定关系。
如果说差徭负担及丐、盗骚扰主要涉及畲民基本生存权的层面,那么,争取平等参加科考,则已上升至发展权、政治权的层面。嘉庆七年(1802年)福鼎童生钟良弼赴福宁府试,书生王万年串通生监诬蔑畲族五姓为“犬生”,将钟赶出考场。钟在乡亲捐助下,变卖家产,层层上告至省衙,经巡抚李殿图批复,才获得圆满解决。此事一方面被官府编入志书(道光《福建通志》),一方面被畲民编成“长连”(小说歌),在闽浙畲区广为传播,影响极大。新近在紧邻福鼎的浙江苍南县(1981年从平阳县析出)发现道光年间(1821—1850年)畲民雷云“反阻考”诉状手稿,他在省、府二级官衙“缠讼三载”,写过23次诉状,1847年温州知府终于颁布了、《禁阻考告示》①。钟良弼和雷云的事迹,从他们自身方面看,表明晚清“滨海畲族”(苍南一带地块实与闽东北连为一体)在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与汉族有了较多交往之后,重视教育,捍卫科考权利,培塑本土精英的迫切诉求。
以上所述诸例,都属单向目标维权。1899年在霞浦创办的福宁山民会馆(后改称三民会馆、三明会馆),则可以看作是一个综合型维权的公益组织。在该会馆活动鼎盛期的30余年中,它以提供膳宿服务,促进畲族各姓的联谊;以搜集、整理畲歌,传播畲族文化;以举办祭祖大典,增加畲族的联宗凝聚,等等,大大扩张和突破了畲民原有组织的最高级形式——联姓宗祠的功能。因此,有的学者强调它是“畲族主要聚居区畲族民众联合组建的国内唯一跨省、跨地区的畲族社会团体②;有的学者指出“山民会馆的创建标志着畲族人民民族意识的兴起”③,这都是很到位、很深刻的表述。笔者还特别关注到它对内化解本族纠纷,对外则为畲民做主,代写诉状,代理官司,保护畲民合法权益,解决了多起畲民入学、畲汉山林、海埕纠纷。山民会馆的创建表明进入民国时期,畲族的维权意识、维权实践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
本文首次提出“滨海畲族”的概念,并就其概貌作了初步勾勒,譬之绘画摄影,只是几张速写、快照,难免有笼统、肤浅之处。希望今后有能力就文中已述或未述的若干要点,再作比较深入的专题讨论。
一、“滨海畲族”概念的提出
清初以来,畲族分布格局发生一个显著变化,闽东北逐渐成为这个族群的最集中的栖息地。闽东北共有11个畲族乡,从南至北分属连江、罗源、宁德(今蕉城区)、霞浦、福安、福鼎等6个沿海县份。现在的宁德市9个县(市、区),其中4个在沿海。宁德市有9个畲族乡,全部分布在沿海县份。蕉城(原为宁德县)的金涵,福鼎的硖门和佳阳,霞浦的盐田和水门,就在海边。福安的坂中、康厝和穆云,离海边有点距离,但也在长溪中游的主支流(穆阳溪)上,与长溪在福安入海处的几个港口大镇水路相通,情况有些类似于福州疍民之沿闽江而一路迁徙到上游的南平、建瓯、邵武和将乐(参见“维基百科”网的“福州疍民分布图”),只是他们离海比闽北疍民近得多。崇儒畲族乡距海稍远,但它所在霞浦县正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县份。
宁德市现有234个畲族村委会,其中沿海4个县份共有215个,占总数的91.88%;即使扣除沿海县份中离海稍远的畲族建制村,包括蕉城赤溪镇(2村),福安潭头、上白石和社口三镇(12村),霞浦崇儒、柏洋二乡(10村),福鼎管阳、蟠溪二镇(5村),仍有186个建制村,占总数的79.49%。①
如果从最为散漫的人口自然分布角度看,缪品枚在《畲族与闽东传统文化》一文中指出,沿海畲族人口占闽东畲族人口总数的44.26%。②缪文未交代统计口径,这里不便复核。新近发表的赖艳华《闽东畲族居住格局初探》一文,把闽东畲族人口分布划分为三大聚居区:福安交溪(应称作长溪)流域,福鼎、霞浦、蕉城(原宁德县)沿海一带,古田溪水库周边及水口水库上游;指出鼎(福鼎)、霞(霞浦)、蕉(宁德蕉城)三县(市)沿海一带畲族人口为70533人(已扣除崇儒),占闽东畲族人口的44.48%。③但拙文只就“滨海畲族”一点来考察,应当将赖文中长溪下半段5个乡镇的畲族人口划入统计范围(包括赛岐镇1919人,溪柄镇3349人,甘棠镇6324人,下白石镇4944人,湾坞乡2852人),则为89921人,所占百分比为57.13%。而按笔者的视角,如前文所述,长溪中游的坂中(7400人)、韩阳(2106人)、城阳(2928人)三地和其主要支流穆阳溪中段的穆云(7286人)、康厝(5503人)、溪潭(4285人)三乡镇都距海口不远,旧时通航条件很好,海船的客、货换乘溪船,可以顺利运抵长溪中游两岸④,这里的畲族其实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滨海性”,如果把这29508人也作为“准滨海人”来理解,所占比例就更高了。
据此,笔者提出“滨海畲族”这一概念。
当然,仅仅止于这些“事实”,还不足以籀绎出科学概念。我们并不必要在“畲族”之外再杜撰诸如“山地畲族”、“游耕畲族”之类新名词。我们创设概念,是要标示事物的分异和新质。现在大家常说全国畲族一半以上在福建,福建畲族一半以上在宁德市。“滨海畲族”则意在凸显这个散居民族的最大聚居区的地理特征,如上文所述,不仅宁德市是一个滨海城市,而且从人口自然分布到畲村聚落分布再到畲族乡行政性分布,统计单位的层级越高,畲族滨海意味越强(57.13%→79.49%→100%)。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有关民政、民族领导部门便以福建沿海为汉族地区等理由而对原为少数民族的“疍民”作出已经“汉化”、不再是少数民族的认定。民族政策对民族发展有很强的规整导向作用,疍民渐渐地而又很快地真的不成其为少数民族了。在这种形势下,“滨海畲族”更可谓是我国东南地区族群生态结构的一个巨大异数。
应当说明的是,本文本节及下一节的阐述,受手头材料限制,侧重于分析现在宁德市的情形,特别是对于乡村、人口、河流的数据使用方面,尤其如此。实际上,闽东北“滨海畲族”的指称范围,应当包括宁德邻境的罗源、连江二县,它们在孙吴至初唐四百多年间本同属一县,现在的地表形态和族群生态仍具有很大的一致性。
二、造就“滨海畲族”的历史机缘
“滨海畲族”的形成,或者说相对弱势、落后的畲族人口竟然在相对强势、先进的汉族地区,在汉族本身人地关系已显紧张的福建沿海地区大规模集结,与其强调它的必然性,不如说这需要一种很特殊的历史机缘。这个特殊历史机缘,笔者以为主要是明嘉靖后半叶二十余年“倭寇”连续大肆侵掠和清顺治、康熙之交二三十年间从禁海迁界到复界招徕的巨大反复。
关于晚明倭患与畲民入迁闽东北滨海丘陵的关系,由于史料欠缺,此前学界不见涉及。本文也无力深究,只是提出一个初步的考察,希望能够引起注意。
检读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刊本《宁德县志》卷一《舆地志·物产·货属》,发现在“菁靛”目下引有一条“旧志”的按语:
本县山场,无论城郭乡村,除附近庐舍坟墓者始为民业,高山深谷俱官山也。嘉靖初年,外郡人来县境栽菁,俱告于官,官则随山按户,置簿收租。自辛酉(公元1561年)倭变之后,官簿无存,土豪年估其租。今考本县州籍,民山并无分抄,悉属官山,尚存官山三顷二十亩九分之税匀派于通县,而利独归于数家。种菁之户,若仿故事,召各乡菁牙、菁客,随其众寡;置簿收租,归之公家,未为不可。然
在当时,则属豪强私占。而此日,承平已久,彼此授受买山者多矣。检核旧志,至“利独归于数家”之前,文字大抵照抄万历十七年(1589年)旧志;之后,掺入新志编纂者的意思;末句则为乾隆年间(1736—1795年)的地权状况。闽东北的菁客中,有不少畲民。他们在官山垦植,必须向官府办理登记手续,按章交纳租税。根据这则记事,嘉靖四十年辛酉年(1561年)“倭寇”攻陷宁德县城,税收档案被毁无存,改由地方豪强粗估租额。并且渐渐地,地权关系也发生变化,彼此买卖山林的行为屡有发生。那么,一些靠种菁积攒了一些钱财的畲民便可以在滨海山林卜地居家,乃至衍为村落。
福安也曾在此前两年的农历四月被攻破县城,倭寇进城烧杀抢掠整整四天,时人称“嘉靖己未福安井邑一烬于倭”①。半年后,新授知县卢仲佃赴任,见到的仍是“荆棘满城,灰烬遍市,二百载烟火辏集之区,一旦荒墟”②的景况。而福安正是后来闽东北畲民人口最多的县份。
缪品枚统计闽东北现存蓝、雷、钟三姓族谱,有明一代入迁者有30支之多(不含宁德设区市属各县间的互迁),其中洪武1,永乐2,景泰1,天顺4,成化1,嘉靖1,隆庆1,万历7,天启2,崇祯9,具体时间不详。③那么,大倭患后迁入闽东的畲民(20支)占到明代各朝总数(29支)的69%。缪文以为明代畲族大量迁入的历史契机在于当时纺织业发展对于蓝靛染料的需求,此说不为无见。只是在总体上明代福建人口压力已经很大的情况下,大量菁客要从临时搭寮租山赁种,改换为纷纷“卜筑”兴村,没有一个大的人地关系变动,恐怕不能成气候。嘉靖十七年(1538年)以来,倭寇频频侵扰闽东北滨海地区,本土原居民死伤逃离严重,加上前述官府地簿税册的破坏,与畲民买山定居之间应当是有内在联系的。至于这个问题所涉历史关节,尚有若干未明之处,容另文再考。
畲民入迁闽东北的更大的历史机缘,在于清初的迁界、复界政策。为了隔绝祖国大陆与台湾拥明政权的联系而实行的禁海和迁界,使人口繁盛的东南沿海三十里内外成为不见人烟的废墟,但客观上为畲族预备了一个广阔的去处,朝廷复界以后,畲民便和许多汉人一样络绎迁入。关于清初闽东的迁界、复界和畲族居住格局变化的基本情况,前引缪品枚文已经做过比较具体的描述,这里不必多说。
本文仅补充说明两点。
其一,复界后,福建畲族比较集中地迁居今日宁德市境内(包括邻境的罗源和连江),当与闽东北滨海区域的地表形态有密切关系。闽东北的地表形态与整个福建的情况,同中有异。例如,多山,溪河多独流入海,山岭纵横河道交错的结果,是把大地分划成许多“格子状”的小单位,“格子”与“格子”之间能够相互联系,但不便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整个福建大体如此,而闽东北的地形要更“细碎”些,除了古田溪与闽江可以相通,这里的河流都自成格局,交溪为福建第五大河,霍童溪为福建第七大河,全区24条较大河流的流域总面积可以占到全部土地面积的将近89%。而且陡峭的丘陵直接延伸到海中,形成全国曲折度最大的一长段海岸线。这与闽东南较多滨海小平原是很不相同的。闽东南的地理条件比较优越,人口繁衍快,人地关系更紧张,汉族势力也更大。畲族在这里更难插足和立足,插上足的,接受汉族文化影响的速度也更快。而闽东北滨海地带亦山亦海、山在海中的特点,可以使初迁的山地畲民更快适应环境,在海滨丘陵从事传统的生产活动。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是,我国东南地区这次族群居住格局大变动发生在清代,而在某种程度上,清代正是传统时代畲族接受汉族文化影响的总结期,也是畲族文化的定型期,一族群在与他族群的接触和交流中澄明自身是文化史上常见的事。我很赞同蓝炯熹的一个看法:我们今天所能看到所能讨论的畲族传统文化,只能是经过有清一代的发展而定型的畲族文化。当然,清代以前已经有畲民,已经有畲民文化,尤其是南宋以来关于畲民开始有越来越频繁的文献记载,可是这些记载大都很简单,印象式的勾勒多,实证性的记录少,有的陈陈相因,不能提供新的信息,我们对宋、元、明畲族文化的把握,除了个别特征(如畲军等),其余的与苗、瑶、疍、客的分别还不够清晰,这个族群的个性文化面目还比较模糊。这也使学界对畲族形成时间、源流衍化、迁徙路线、文化核心特质等的判断容易产生分歧,有些问题至今不能达成共识。若先以文献、实物、口述材料较丰富、现实生活中遗留的痕迹也较明显的清代畲族文化样态为基点,再作前溯或后察,也许会有一些新的收获。
我们把目光收拢在清代闽东北滨海地带这个正处畲族文化重要定型期的族群集中聚居区,不难发现这里这时的畲族在经济生活、文化面相、公共治理、族群认同等方面都在渐渐发生一些意义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基本趋势,是加速采借与他们混居、邻居的汉族社会的先进经验,从而不无受阻但终归是要缓慢地适应和融入与相对强势的汉族和平共处之中(族群间的交往,即使是明显有着先进、欠先进之分的族群间交往,其文化影响也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当然也不会是均衡施受的,这是我们在沿用“汉化”一类词语时应当心存儆醒的)。
三、我国东南族群分布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动
畲民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段里大量迁徙到当时人口还不太密集的闽东北并定居下来,造成了这一地带乃至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族群生态结构的重要变动。以下对此略加分说。
其一,从畲民的歌谣、族谱两大载体中所提供的历史记忆,结合现代畲族人口分布情况,我们大体可以认为,这个族群的核心集居地,经历了从潮州到汀、漳再到福宁府的变化过程。这个表述和学术界的主流看法,差异或许不大。但笔者借此想要进而指出,从严格一些的判断标准来看,在“潮州中心期”,畲民的文化特点尚未与东南地区诸多山夷峒蛮清晰地区分开来,尤其未与同有盘瓠崇拜、同有“皇赐券牒”、且有共同姓氏和相似语言的瑶族清晰地区分开来,而当时的文书、方志也往往以瑶、畲联称或以猺、徭代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汀、漳中心期”。在“汀、漳中心期”,畲民农业经济从游耕趋于定耕,与同在深山老林的客家人共处渐密,相互影响渐多,宗族观念日益强化,他们与瑶族的区分则随着地块上的愈行愈远而逐渐增大起来。这时候常见的则是畲、客混称或联称。到了中晚清的“福宁府中心期”,畲民确立了定耕、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建宗祠、修族谱,参加科考,在受汉族文化影响越来越深的同时,注意持守自身的特色文化元素,至此,一个与汉族文化相区别的少数族群——畲族的建构过程基本完成,成为现代我国东南地区唯一的相对聚居的少数族群。
其二,根据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在畲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两个地理空间值得关注:一是公元7世纪以来的闽粤赣交界地区,二是元明清的闽浙赣交界地区”①。需要强调的是,由于粤、浙的介入,前后两个时期的赣和闽,所指并非同一地块。前期的“赣”,主要是今天的赣南地区;后期的“赣”,主要是今天的上饶地区(本文不拟涉及赣省族群结构变化问题)。前期的“闽”,主要指闽西,后期的“闽”,主要指闽东北。这是闽省少数族群的两大“高地”。谢重光主张客家和畲族都形成于两宋时期。他认为,在闽西,客家是“民族融合的主导力量”,到宋元之际,畲、客融合进程大大加速,“这一进程的主导方面是畲族被同化为客家,少数未被同化的畲民要么退进更深的大山中,要么被迫向别处迁移”②。迁移的去向,从后来的史实考察,大抵是先到闽东南,再迁闽东北,其中一部分又由闽东北而入浙或入赣。
畲族大量迁入闽东北后,建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聚居村落,也成为当地有相当势力的族群。陈支平分析罗源雷姓畲族的九件契约文书内容,得出的结论之一是清代闽东畲民与朝廷、与汉族的关系都比较平和、比较正常,所谓“汉族地主阶级和封建政权的剥削和压迫,缺乏史实上的强有力印证”①。
那么,闽东北地区客家的情况如何呢?目前这方面的资料极为缺乏,也未见到相关研究成果。这里仅从方言分布角度作一点简单的说明。
闽东北(这里指今宁德市)的汉语方言,总体上属闽方言福州话,其中古田、屏南二县为南片区,其余七县为北片区。也存在少数几种方言岛,其中汀州话(客家话)主要通行于古田凤都镇的后溪、珠溪二村(约5000人),霞浦县州洋乡的福鼎楼自然村(300多人),柘荣县城郊乡的倒龙山村(100多人),还有福安市社口乡的首觅村和溪潭乡的濑尾村、福鼎市磻溪镇的赤溪村和点头镇的观洋村以及寿宁县西南角个别自然村(平溪乡三角洋、云务坑、白岩下、彭地)也讲客家话,以上总数不及6000人,②所占人口比例极低,已经远非闽东北客家分布的原貌。而且其主体部分,即后溪、珠洋二村也已成为双语区,兼说古田话了。这表明在闽省的两大少数族群聚居区存在“客”进“畲”退,“畲”进“客”退的情势。在闽西,客家势力强大,20世纪50年代以后,尤其是80年代以后,在国家“民族优惠政策”的影响下,一部分畲姓客家人自愿恢复了畲族身份,但仍有一定数量的畲姓人口不愿意改变客家的身份。而在闽东,畲族并非主导族群,这里的客家人一般不想也不能改属畲族,久而久之,逐渐与当地一般汉族趋同,客家文化特征逐渐淡化。
从以上所述,我们对闽东北的族群分布结构的变迁,形成这样一个总体印象:明清以前,由于历代特别是中唐五代和两宋之交大批中原汉人络绎南下,与当地土著逐渐融合;疍民虽然具有鲜明文化特色,但他们是水上人家,所以这里的族群结构比较简单。明代以后特别是在有清一代,畲民频繁入迁,很快适应环境,立下脚跟,发展壮大。而由于福建客家人早在闽西一带建立了大本营,少量迁入闽东的,难以持守和发扬其固有传统;疍民又无权上岸生活,畲民便成为闽东北除汉族以外最主要的族群。
四、闽东滨海畲村群的形成
闽东北山海环抱,远离喧嚣,百姓生活历来“不贾而足,虽荒岁不饥”①,很少受到兵革动乱的冲击。但如上所述,从明代中叶到清初的百余年间,却接连遭受“倭寇”之洗劫、南明清军之激战、“迁海开界”之反复,沿海遂常有荒残之地,畲人得以离开深山临时搭盖的草寮而入居,渐由游耕转为定耕,建房兴村。这些畲村,多数海拔不高。现有的234个畲族建制村,笔者查得212村海拔情况,兹将闽东沿海县份和山区县份各海拔高程(单位:米)的村数(单位:个)列示如下:
说明:(1)材料主要采自前揭《闽东畲族文化全书·乡村卷》(189村),其余采自蓝运全、缪品枚主编《闽东畲族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俞郁田编《霞浦畲族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蓝纯干主编《宁德市(今蕉城区)畲族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2)海拔高程数据,“100以下”含100,“100—200”指100
闽东畲村群的形成,必须以畲族人口较大数量的繁衍为基础,而相对贫困的畲族人口的繁衍,又必须以获得基本口粮为保障,这就牵涉到明代中晚期以来福建粮食作物结构的一个重大变革。何炳棣早在1956—1957年就为文、著书具体论证美洲粮食作物玉米、番薯、花生和马铃薯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人口增长的巨大作用。③这些农作物后来在畲村也都颇为流行。当然,影响人口数量变化的因素十分复杂,何炳棣还谈到其他经济、行政因素和天灾(旱、涝)、兵灾的影响,但未涉及明清气候变冷问题,周翔鹤、米红对此有所纠补④。仅就闽东北畲村的大片成长而言,那些从美洲传入的不仅平原、而且可以种在丘陵的旱地、瘠土的高产作物,特别是度荒所赖的番薯,使无数贫苦畲民免于死亡,确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件。我们的这个看法,可以在方志的记载中得到印证。
例如,何乔远《闽书》卷150《南产志》引其自撰《番薯赋》载:“其初入吾闽时,值吾闽饥,得是而人足一岁。”
李拔《福宁府志》卷12《食货志·物产》“番薯”条载:“郡本无此种,明万历甲午岁荒,巡抚金学曾从外番丐种归,教民种之以当谷食。”又按语:“迩来生齿日繁,米价渐高,沿海民食,半赖于此。”
卢建其等《宁德县志》卷1《舆地志·物产》载:“(蕃薯)今其用比于稻谷;切而为干,藏以待乏。”
张景祁等《福安县志》卷7《物产》载:“其山田硗确,畲者悉种薯蓣,以佐粮食,贫民尤利赖焉。”
大致说来,番薯对贫民的意义,远重于富民;对畲民的意义,远重于汉民;在灾年的意义,远重于平年。畲民开始大量集结闽东北的时候,机缘巧合,也正是番薯逐渐在这里推广开的时候。当地畲谣:“番薯米,吃到老。”这大大降低了畲民的死亡率。我们不能想象,没有番薯的传入和传播,畲村会像大把明珠般洒落在闽东北大地(仅霞浦县1989年调查,畲族人口占60%以上的自然村就有381个①);也不能想象,从这里会迁出大量畲民到浙南立村安家,使它成为全国第二大畲族分布区。②
五、滨海畲族文化之新质
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的改变,畲汉相邻乃至相杂而居村落格局的出现,促使畲族社会生活逐渐有所变化,产生了一些文化新质。
其一,生产生活方式中的海元素的渗入。闽东北有些畲村就在海边,如福安下白石镇的长坑、坑门、樟澳诸村,湾坞乡的半屿村;霞浦牙城镇的凤江村,溪南镇的后慕、小马、炉坑诸村,盐田乡的南塘、姚澳诸村,北壁乡的盘前村,松港街道的大沙村;福鼎佳阳乡的象阳、罗唇诸村;蕉城漳湾镇的雷东、又加塘诸村,八都镇的金垂村,等等。半屿所辖的鹳屿和小马所辖的竹江两个畲族自然村,还在海中的小岛屿上。这些村子往往都有大片的滩涂,可以于农业之外兼营小海渔业,现在还发展了多种海产品养殖业。③不过,海边畲村数量不多,而且闽东北的汉民的海洋利用方式,传统的也是以海为田,作为农业的一种空间延伸,畲民更是如此。它对族群文化品性的影响,不宜估计过高。
其二,原有信仰与本地神明间的互动。畲族多元崇拜,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接受当地民族村民所信奉的“神明”。闽东富有特色的民间信仰,以陈靖姑和林公大王最为通行。据传,林公大王实有其人,名祖亘(也单称亘),善于搏虎,祖殿在今周宁玛坑乡杉洋村,建于明中叶(成化年间),后遍及闽东北。畲民主要供作猎神和村庄保护神。陈靖姑信仰与畲民巫术文化则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契合,二者同属“闾山教”谱系,在畲族巫师科仪唱本中,恭请陈靖姑行罡作法都是一项核心内容。有畲族学者认为,陈靖姑等三奶夫人实际上“已经具备了作为畲族内部神灵的资质”,在明清陈靖姑信仰的造神运动中,“大量迁入闽东方言区的畲族也参与其事,其中畲族巫师扮演了重要而特殊的角色”①。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可以看作是汉、畲两种文化在交流碰撞中产生文化新质的一个例子。
其三,儒家思想的浸润与牵引。畲族文化以蛮、越为底色,与儒家观念位差过大,两者原本难以相合。但到了前文所指的汀、漳中心期,畲、客往往同在一山,这两大边缘族群接触较密切,文化上发生初步交流,彼此都受到对方的影响。②而闽东北为丘陵沿海地带,海岸线绵长却富含内陆品性,且区位僻远,与浙江当时比较落后的温、处地区紧紧相连,这里的汉族,社会发展水平不很高,但朱熹理学在民间有一定的传播。畲族入迁时,二者的文化位差已有所缩小,加上这里人口密度比闽西高,村间及至村内畲汉杂居势不可免,文化采借逐渐从器物、技术层面上升到价值取向。霞浦白露坑半月里是著名的畲族文化名村,但房屋、坟墓形制与当地汉族无异,门匾、墓碑都标榜先祖出自中原世家。村陈列室收藏了一双“三寸金莲”绣花鞋。①一座清代秀才大厝在大门内侧还专设女眷过道,不与大厅相通。这其中,有客家文化的印记,也有闽东北汉族文化的影响。闽东北畲族谱牒的谱序、谱论、谱式、谱例,都贯穿着儒家伦理准则。族谱大多是请汉族文士修撰,他们在尊重东家文化基质的同时,也必然带进自己的儒学认知(由畲族读书人自己修谱,情况并无二致)。请人修谱的过程以及自身参加祭谱、阅谱的过程,成为学习儒家学理知识的过程。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由江西萍乡人钟大琨主持,历时7年修成157乡(包括城区居民点和祠堂3处)钟姓连环谱,其中137乡属闽东北沿海三县,加上罗源县6乡,合占总数的95.3%,可见本文指称的“滨海畲族”对谱事的热情和重视,也多少可以反映出儒学家族伦理对他们的影响。在新环境中畲民原来的“善啸聚”、“喜仇杀”的风习也渐渐有所变化。
其四,尝试运营“民族—家族”企业的新经验。到了清代,闽东北成为福建的重要茶区,茶市兴盛。同治十三年(1874年),宁德县八都猴墩村畲民顺应华茶对外贸易形势,开始创办茶庄,收购周边二县数十个畲村的茶叶,形成畲族茶叶专业市场,年销干茶4000多担,并择地开铺,兼营煤油、布匹、海产、山货,雷氏商号闻名遐迩,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繁荣。其主要经验,是农商并举,依靠“畲家阵”之间的相互信任,民族意识与家族伦理融为一体,构建和维护“茶农——猴墩茶市——福州茶叶中心市场”的稳定经济网络②。畲民本不经商,以往他们迁徙所至,也都是偏僻山林之地,农耕气息浓厚。而闽东北在明代就有重商风气。③八都是霍童溪的出海口,水、陆交通条件不错。当咸丰、同治间(1851—1874年)太平军四次入闽,武夷山从陆道运往广州茶叶外贸受阻,福宁府从水道到福州的茶路便迅速代之而起,猴墩畲村遂有机会成为所在一带的茶叶集散地,这里的畲民遂有机会成长为优秀的茶叶商人。
其五,族群权益意识、维权实践的初步表现。不能说畲民在本文指称的潮州中心期和汀漳中心期就没有权益意识和维权实践,①但确实少有记载(这与他们尚处徙居游耕阶段有关),也缺少官府方面在法制框架内的互动。福宁府中心期的情况,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畲民入迁之初,渐渐从游耕过渡到定耕,各地乡保摊派差徭,有无、多少,缺乏统一则例,畲民乍受摊派,特别不服,向地方官府强烈要求“免差徭”。县堂大约考虑到他们偏远零散,人少村贫,尚未站稳脚跟,答应给予宽免,并立碑明示。碑已不存,但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重修的福安甘棠田螺园《冯翊雷氏宗谱》和福鼎华洋(双华)《汝南蓝氏宗谱》②中各保存2篇这种文告,时间跨度为康熙三十七年至嘉庆七年(1698—1802年)。
闽东北畲村编图隶籍以后,征赋摊差相对规范化,畲民维权重点逐渐转向社会治安问题,尤以恶丐强乞与盗贼抢偷最为突出。于是,吁请县衙“出示严禁”,经过批准,畲村在路边勒石立碑,有的还成立巡逻自卫队。③这些碑刻或碑文,现尚存十余通,时间集中在光绪年间(1875—1908年)。常见的评论,把丐、盗骚扰及前述的“免差徭”都归属为“阶级剥削”“民族压迫”,这当然有相当的理据。但总的说来,清代官府对闽东北畲族的政策还是相对比较宽和的。故笔者以为,冲突的发生和展开,与人口压力增大后的资源竞夺、不同族群的文化传统隔阂以及晚清畲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意识的觉醒,也有一定关系。
如果说差徭负担及丐、盗骚扰主要涉及畲民基本生存权的层面,那么,争取平等参加科考,则已上升至发展权、政治权的层面。嘉庆七年(1802年)福鼎童生钟良弼赴福宁府试,书生王万年串通生监诬蔑畲族五姓为“犬生”,将钟赶出考场。钟在乡亲捐助下,变卖家产,层层上告至省衙,经巡抚李殿图批复,才获得圆满解决。此事一方面被官府编入志书(道光《福建通志》),一方面被畲民编成“长连”(小说歌),在闽浙畲区广为传播,影响极大。新近在紧邻福鼎的浙江苍南县(1981年从平阳县析出)发现道光年间(1821—1850年)畲民雷云“反阻考”诉状手稿,他在省、府二级官衙“缠讼三载”,写过23次诉状,1847年温州知府终于颁布了、《禁阻考告示》①。钟良弼和雷云的事迹,从他们自身方面看,表明晚清“滨海畲族”(苍南一带地块实与闽东北连为一体)在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与汉族有了较多交往之后,重视教育,捍卫科考权利,培塑本土精英的迫切诉求。
以上所述诸例,都属单向目标维权。1899年在霞浦创办的福宁山民会馆(后改称三民会馆、三明会馆),则可以看作是一个综合型维权的公益组织。在该会馆活动鼎盛期的30余年中,它以提供膳宿服务,促进畲族各姓的联谊;以搜集、整理畲歌,传播畲族文化;以举办祭祖大典,增加畲族的联宗凝聚,等等,大大扩张和突破了畲民原有组织的最高级形式——联姓宗祠的功能。因此,有的学者强调它是“畲族主要聚居区畲族民众联合组建的国内唯一跨省、跨地区的畲族社会团体②;有的学者指出“山民会馆的创建标志着畲族人民民族意识的兴起”③,这都是很到位、很深刻的表述。笔者还特别关注到它对内化解本族纠纷,对外则为畲民做主,代写诉状,代理官司,保护畲民合法权益,解决了多起畲民入学、畲汉山林、海埕纠纷。山民会馆的创建表明进入民国时期,畲族的维权意识、维权实践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
本文首次提出“滨海畲族”的概念,并就其概貌作了初步勾勒,譬之绘画摄影,只是几张速写、快照,难免有笼统、肤浅之处。希望今后有能力就文中已述或未述的若干要点,再作比较深入的专题讨论。
附注
①据蓝炯熹在“全国畲族文化研讨会(2009年)”上的发言。按,蓝图、蓝炯熹的长篇论文《闽浙赣交界地:地理枢纽与畲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建构》尚为未刊稿,此次会上仅提供该文的引言和第一部分。
②谢重光:《畲族与客家早期关系述略》,载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等编《畲族文化研究》上册,第116、128页。
①陈支平:《清代闽东畲族社会经济的一个个案分析》,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②宁德地区方志委编:《宁德地区志》卷34《方言》,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6—1699页;福安市方志委编:《福安市志》卷37《方言》,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3页。
①《闽书》卷38《风俗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校点本,第947页。
①俞郁田编纂:《霞浦畲族志》第2编第1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
②郭志超:《畲族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页。
③何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15—228页。
④周翔鹤、米红:《明清时期中国的气候和粮食生产》,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
①俞郁田编纂:《霞浦县畲族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
②按,文成后,重看前揭郭志超《畲族文化述论》,其第四章“经济生活”第一节“生产与交换”在“农业·种植种类·薯芋”条已经指出:“自明晚期番薯从东南亚传入福建后,很快在畲区广为种植。番薯耐瘠耐旱,易种于山地,这极大地增强了畲族对山地环境的适应性。清代畲族在东南山区的广泛分布,特别是在闽东、浙南建立起本民族新的大本营,与番薯引种和普遍种植有着密切的关系。”见原书第136页。郭书与本文在内容上稍有详略同异,特予标出,并以自儆。
③关于畲族渔业的情况,很少得到反映。目前介绍最多的,是蓝炯熹总纂的《福安畲族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见该书第11章。
①蓝焰:《畲族巫术文化中的陈靖姑信仰——以福州、宁德畲族乡村为例》,载《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4期。
②畲族文化对客家的影响,可参见吴永章、谢开容《客家文化与畲族文化关系研究》,收入罗勇主编《“赣州与客家世界”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客家文化对畲族的影响,可参见谢重光《明清以来畲族汉化的两种典型》,载《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1期。
①有村民说鞋是嫁过来的汉族女性所穿,不知是否确实,但纵使如此,这鞋和鞋主人作为异文化符号在该家庭中的深度嵌入,也会产生一系列晕染效应。
②蓝炯熹:《近代闽东一个畲族村落的茶叶商帮》,载《宁德师专学报》2008年第1期。
③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纪》载:“福州会城及建宁、福宁……民多仰机利而食,俗杂好事,多贾治生。”按,张为江南商业中心杭州人,官至吏部尚书,万历年间辞归故里,以平生见闻著为《松窗梦语》8卷。今有中华书局点校本。
①例如,万历《漳州府志》卷12“猺人”条即载畲民“其与土人交,有所不合,詈殴讼理,一人讼,则众人同之;一山讼,则众山同之,土人莫敢与敌”。
②这4篇“免差徭”文告,已收录缪品枚编《畲族文化全书·谱牒祠堂卷》,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229—231页。
③蓝炯熹:《晚清闽东畲族乡村的乞丐问题——以九通“禁丐碑”碑文为中心》,载《民族研究》2007年第5期。
①邱新福:《“反阻考”诉状重现清代科举制度歧视少数民族》,苍南新闻网,2008年9月。
②郁田:《畲族历史文化的一大地标亮点——中华畲族福宁山民会馆》,载《福建民族》2010年第2期。
③前揭郭志超:《畲族文化述论》,第6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相关地名
盐田区
相关地名
南平市
相关地名
建瓯市
相关地名
邵武市
相关地名
将乐县
相关地名
福州市
相关地名
霞浦县
相关地名
赤溪镇
相关地名
潭头镇
相关地名
崇儒畲族乡
相关地名
管阳镇
相关地名
赛岐镇
相关地名
溪柄镇
相关地名
甘棠镇
相关地名
下白石镇
相关地名
溪潭镇
相关地名
三乡镇
相关地名
海口市
相关地名
福建省
相关地名
孙吴县
相关地名
官山镇
相关地名
景泰县
相关地名
兴村镇
相关地名
台湾省
相关地名
南宋乡
相关地名
潮州市
相关地名
古田县
相关地名
屏南县
相关地名
汀州镇
相关地名
凤都镇
相关地名
后溪镇
相关地名
柘荣县
相关地名
城郊乡
相关地名
福安市
相关地名
福鼎市
相关地名
磻溪镇
相关地名
点头镇
相关地名
和平溪乡
相关地名
白岩镇
相关地名
中原区
相关地名
南明区
相关地名
天全县
相关地名
牙城镇
相关地名
南塘镇
相关地名
北壁乡
相关地名
周宁县
相关地名
玛坑乡
相关地名
浙江省
相关地名
江西省
相关地名
萍乡市
相关地名
罗源县
相关地名
武夷山市
相关地名
广州市
相关地名
平阳县
相关地名
温州市
相关地名
苍南县
相关地名
三明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