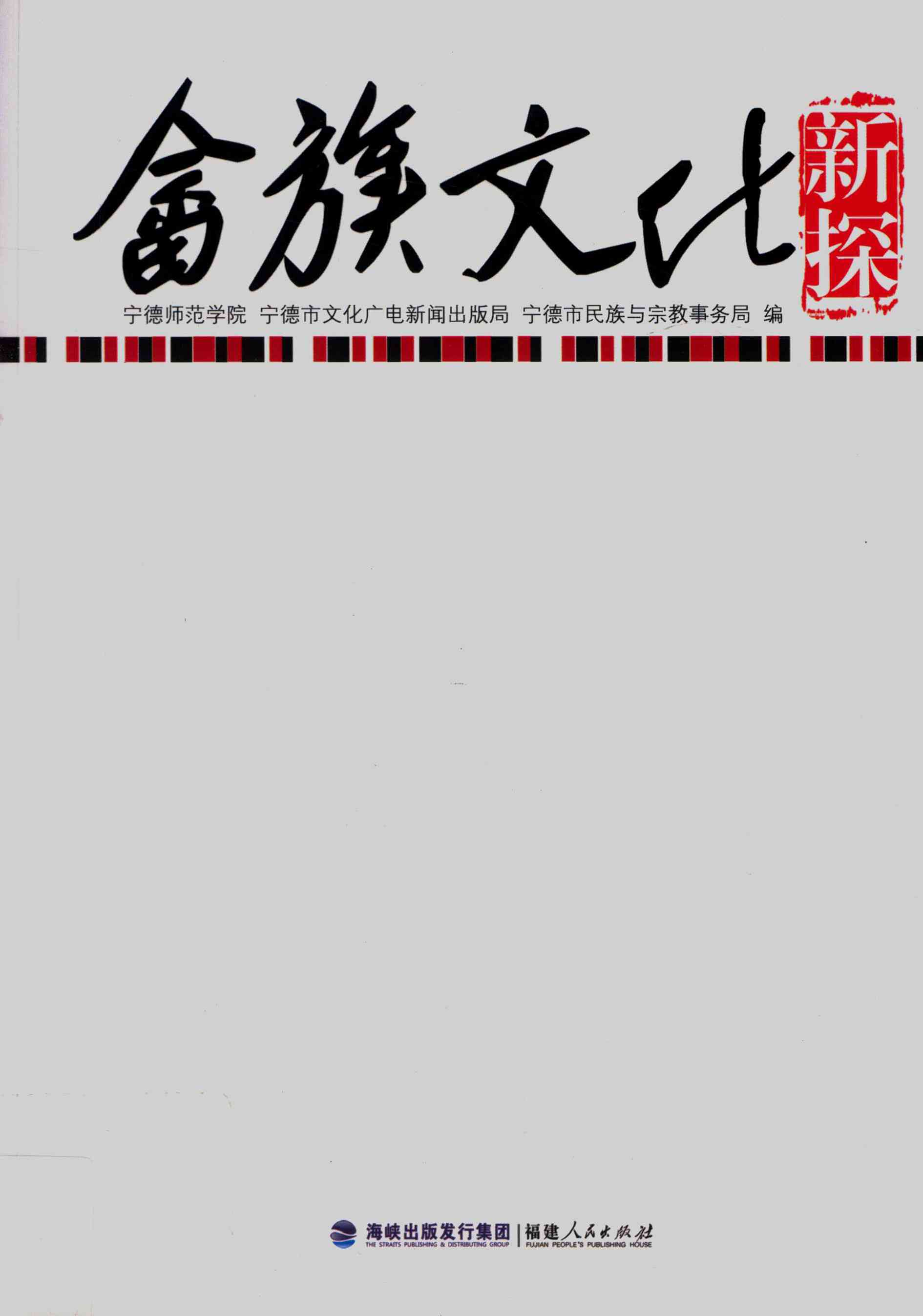内容
贵州畲族的民族身份是1996年6月才确定的。①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贵州畲族人口44926人,占全国畲族人口709592人的6.33%,位居全国第四。②贵州畲族主要分布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凯里市、麻江县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都匀市、福泉市。1996年确定民族身份时,都匀市有畲族2979人,福泉县4583人,凯里市1596人,麻江县32366人,共计41524人。其中,麻江县畲族不仅人口最多,占贵州畲族总人口的78.1%,而且其传统文化也被认为是保留得比较完整的。
在确定民族身份之前,贵州畲族被汉族称为东家人。东家人自称嘎孟,苗族称其为嘎斗。其中,“嘎”是表示语气的冠词,没有实际意义,“孟”和“斗”的意思则不明。③关于东家人的来源,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我们姑且分别称之为“土著说”和“外来说”。“土著说”认为,东家人就是历史上的东苗或鸭崽(子)苗,他们早在明代以前就生活在贵州境内。④“外来说”则认为,东家人曾居住在江西赣江流域及赣东、赣东北一带,元末和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因奉旨征讨、迁徙或避祸才迁入贵州,这也是他们定为畲族的一个重要依据。①这两种观点,哪一种更符合历史事实?或者,它们居然是可兼容的?这是笔者于2007年初秋赴黔东南进行实地调查后,一直在苦苦思索的问题。
一、史籍关于东苗的记载
据有人考证,东苗一词最早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东苗乱”而见载史册。②之后,明天顺二年(1458年),麻城人李添保“以逋贼逃入苗中,自诡为唐后”③,与“东苗干把猪④等僭伪号,攻都匀诸卫”⑤,远近震动。镇守湖广、贵州太监阮让等奏报:“东苗为贵州诸种蛮夷之首,负固据险,僭号称王,其他种类多被逼胁,东苗平则诸蛮夷莫不服从矣。”⑥英宗遂“命(方)瑛与巡抚白圭合川、湖、云、贵军讨之,克六百余寨”⑦,生擒干把猪。未久,李添保也被俘获。
从阮让等奏报给英宗的内容来看,既然东苗“为诸种蛮夷之首”,且“其他种类多被逼胁,东苗平则诸蛮夷莫不服从”,那么,东苗应该在明代之前,就已经在贵州生活了相当长时间,且人数甚众。否则,他们不可能拥有那么强大的势力。曾经在贵州担任布政使的罗绕典(1793—1854年)也认为,东苗来源于唐代的“东谢”。他说:
东晋时,命谢氏世为牂牁太守。及侯景乱梁,牂牁与中国不通,而谢氏保境如故。至唐时,牂牁又分裂,于是有东、西谢之称。其后遂以名其部族,曰“东苗”、“西苗”。⑧
《旧唐书》记“东谢”曰:
东谢蛮,其地在黔州之西数百里,南接守宫獠,西连夷子,北至白蛮。土宜五谷,不以牛耕,但为畲田,每岁易。俗无文字,刻木为契。散在山洞间,依树为层巢而居,汲流以饮。皆自营生业,无赋税之事。……其首领谢元深,既世为酋长,其部落皆尊畏之。①
因为东苗与西苗同源于东晋谢氏,所以相关史籍总是将两者并列在一起描述。更有学者据此认为,东苗、西苗“实为汉人的后裔,其族属应该为汉族”②。
关于东苗文化特征的记载,已知最早的为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的《贵州图经新志》。该书是贵州省现存最早的一部方志,书中记载了贵州宣慰司、龙里卫、新添卫、清平卫四地的东苗。贵州宣慰司东苗:
男髽髻,着短衣,色尚浅蓝,首以织花布条束发。妇着花裳,无袖,唯遮覆前后而已。裙亦浅蓝色,细褶,仅蔽其膝。其俗婚娶男女相聚歌舞,名为“跳月”。情意相悦者为婚,初不较其财,逮至一年方遣人责之,虽死亦不置。③
龙里卫东苗:
性憨而厉。男子科头赤脚,衣用青白花布,领缘以土锦。妇人盘髻,贯以长簪,衣用土锦,无襟。当幅中作孔,以首纳而服服之。别作两袖,作事则去之。杂缀海、铜铃、青白绿珠为饰。春月,以木刻马为神,召集男女祭以牛酒,曰“木马鬼”。老者坐饮马傍,未婚男女俱盛饰衣服,吹笙唱歌,旋马跳舞,类皆淫泆之词,谓之“跳月”,彼此情悦者遂同归。男家父母杀鸡占卜纳马女。父母论姿色索牛马,多至十五六。力不足者,累岁征之。④
新添卫所辖五长官司之东苗:
椎髻赤足,妇女以土锦为衣。婚不用媒,相悦则奔。既婚之后,始以牛马聘礼。①
清平卫东苗:
稍通汉语,服红花衣,头插白鸡毛,其俗同于犵狫。②
稍后的嘉靖《贵州通志》则记载了乖西司和龙里卫大平划司的东苗。乖西司苗:
其类有二:曰东苗,曰西苗。其俗相同,皆髽髻,着短衣,色尚浅蓝,以织花布条束发。妇女着花裳,无袖,唯遮覆前后而已。裙亦浅蓝细褶,仅蔽其膝。婚娶,集男女歌舞,名为“跳月”。《成婚图考》云:乖西苗性类犬羊,不通汉语。以十二支所肖为场,男妇持货交易,以供赋税。重财轻命,判服不常。死丧,杀牛祭鬼,击鼓作乐。③
对乖西司苗的记载和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对贵州宣慰司东苗的记载差不多。对龙里卫大平伐司东苗的记载则完全援引《贵州图经新志》对龙里卫东苗的记载。④
继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和嘉靖《贵州通志》之后,只有乾隆《贵州通志》对东苗的记载略有创新。其记曰:
有族无姓,衣尚浅蓝色,短不及膝,以花巾束发。妇人衣花衣,无袖,唯两幅遮前覆后,着细褶短裙。跳月与花苗同。以中秋祭先祖及亲族远近之亡故者。择牡牛以毛旋头角正者为佳,时其水草以饲,至禾熟牛肥,酿酒砍牛,召集亲属剧饮歌唱。延鬼师于头人之家,以木板置酒馔,循序而呼鬼之名,竟昼夜乃已。春猎于山,获禽,亦必以祭。畏见官长,事有不平,但听乡老决之。急公服役,比于良民,唯在平远、高堡等寨者多剽悍。近皆守法。⑤
他如万历《贵州通志》和明、清一些官员的著述,如郭子章(1543—1618年)的《黔记》、田雯(1635—1704年)的《黔书》等,对东苗文化特征的描述,均与上述三种大同小异。
关于东苗的地理分布,各种记载则不一。明代,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东苗在贵州宣慰司(贵阳周边一带,治所在今贵阳市)、龙里卫、新添卫(今贵定县)、清平卫(今凯里市炉山镇)等地;嘉靖《贵州通志》记东苗在乖西司(今开阳县)和龙里卫;万历《贵州通志》记东苗在龙里卫(今龙里县);①郭子章《黔记》记东苗在贵州宣慰司,特别是宣慰司所领九长官司之一龙里司。②
清代,田雯《黔书》记东苗在新贵(今贵阳市)、龙里。③他并称,龙里县的白苗“亦名东苗、西苗”④。乾隆《贵州通志》载东苗“在贵筑(今贵阳市)、龙里、清平”⑤。《大清一统志》载东苗在新添卫所辖五长官司及贵筑之谷池里。⑥爱必达(?—1771年)《黔南识略》载:“天柱县林深箐密,诸蛮杂处,为东苗羽翼。”⑦李宗昉(1779—1846年)《黔记》载“东苗在贵筑、修文、龙里、清镇及广顺(今长顺)各属”。⑧罗绕典在《黔南职方纪略》载东苗在平越(今福泉市)、麻哈(今麻江县)。⑨桂馥《黔南苗蛮图说》载东苗“唯贵筑、麻哈两属有”⑩。
民国时期,《贵州通志》载:“平越自清同治间地方收复后,向来所属诸苗较少,近则东南乡间有东苗、木老、仡兜数种,多与汉人杂处,男女衣服言语亦多仿汉人”。又“清平县东六个鸡、角冲、干坝等处,有东苗与西苗、鸭崽苗,杂居汉人村寨,或十家八家,三二十家不等”。①《麻江县志》载,该县有“夷族”近10种,其中也包括东苗。②
从这些记载来看,东苗在历史上的分布地主要为贵阳及其周边地区,包括开阳、修文、清镇、龙里、长顺、贵定、福泉、麻江、凯里、天柱等十余县。其中,贵阳及其东南的龙里是明清时期东苗聚集的主要区域。到清末民初,东苗的住居地已渐向黔东南转移,集中在福泉、麻江、凯里等地。东家人的“嘎须”仪式③也佐证了这一点,其“请先人的路线大体是从现居住地——烂坝——两板凳——土桥河——陆家桥——谷宾——景阳——谷硐——坝芒水头——昌明——平伐(今贵定县)”,这些地名均在麻江、贵定境内。这说明,“东家人入黔后散居贵定、平伐等地,后又迁徙至现所在地”。④
二、史籍关于鸭崽(子)苗的记载
东家人因为擅长养鸭而被人称为鸭崽苗或鸭子苗。⑤从笔者目前已掌握的资料来看,最早记载鸭崽(子)苗的是罗绕典。他在成书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的《黔南职方纪略》中详列黔地各“苗蛮”习俗时说:
鸭子苗,贵定有之,服食与青苗同。⑥
在介绍他们的居住地时,他又说:
贵定县有苗六种:一曰花苗,二曰白苗,三曰家苗,四日狇狫,五曰青苗,六曰鸭子苗,(鸭子苗)居西乡杨柳冲、龙塘湾、罗雍
诸寨。①
该书共列举了50种“苗蛮”类,其中既包括东苗,也包括鸭子苗。而且,他们的居住地也不相同,东苗在平越、麻哈,鸭子苗在贵定。换言之,在罗绕典看来,东苗与鸭子苗是两种不同的“苗蛮”种类。
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桂馥所撰《黔南苗蛮图说》,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共记载“苗蛮”86种,是“目前国内外所知同一种书中记载贵州民族种类最多、各种民族的信息量最大的文献”。作为一名地方官吏和文人画家,桂馥在贵州生活了30余年,经常深入民间,十分了解贵州各民族的生产生活状况,“由他绘制并撰写的《黔南苗蛮图说》具有很大的真实性”②。桂馥本人也声称:“余今所画,大都亲眼所及,非画工家所可同语。余自咸丰戊午,从事黔军营十有余年,历遍上下游,所至苗疆,察看山川形势,采访苗民风俗,以及性情之顺逆,好尚之美恶,服饰、饮食、屋宇,一一笔之于册。”③在该书中,桂馥也是把鸭崽苗和东苗作为两种不同的“苗蛮”来对待。关于东苗,他说:
东苗有族无姓,男子留顶发,以织花布条束之。短衣背甲,色尚浅蓝。妇人衣花衣,无两袖,以两幅遮前覆后,穿细褶短裙。中秋,合寨延鬼师祭祖、屠牛,以木板陈馔,循序而呼鬼之名。祭毕,集亲族畅饮尽夜。春猎于山,获禽兽必荐祖先而后食。唯贵筑、麻哈两属有。④
关于鸭崽苗,他说:
鸭崽苗,在都匀府属(辖今都匀、凯里、麻江、丹寨、独山、荔波等地)。男服饰效汉装,女则椎髻,短裙露胸,跣足。长簪大环,项圈锦襃。以种山、渔猎为务。风俗与水家、獞家等大略相同。①
而且,书中所绘之《苗蛮图》,东苗与鸭崽苗的男女服饰均有明显差异。②
甚至连民国《贵州通志》(1948年)也将东苗与鸭崽苗视作两个不同的群体。该志有两处援引《清平访册》云:
清平县东六个鸡、角冲、干坝等处,有东苗与西苗、鸭崽苗,杂居汉人村寨。③
佟(㹣)苗,清平县有之。《访册》云:佟(㹣)苗本名鸭崽苗,女衣黑,多著白花或蜡花。裙长仅五寸,近有长至尺二者。内着裤,中有一缝,外加密纽。裹腿直缠至肘腋,嗜养乳鸭。髻高尺许,继以花带,胸背著布一幅如背心。四时均若半截草履。与东、西苗杂居于县东之六角鸡、角冲、干坝等处。④
有意思的是,该志又新出现一个“佟(㹣)苗”,作为鸭崽苗的别称,并且说:
佟(㹣)苗,麻哈州(今麻江县)有之。《访册》云:佟苗类于夭(绕)家,住养鹅、杀寡等寨,善养鸭以是为营生,故人谓之鸭崽苗。⑤
该志原作“㹣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点校出版时改为“佟苗”。查汉语词典,“佟”的标准读音为tong,“㹣”的读音为zhong。但在民间,将“东苗”读作“冬苗”,再加上偏旁,成为“佟苗”或“㹣苗”,但读音仍为dong,是完全可能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该志也将“佟(㹣)苗”或鸭崽苗视作与“东苗”不同的群体。这说明,即使是到民国年间,在人们看来,东苗与鸭崽苗也还是有所区别的。
更早的民国《麻江县志》(1938年)在介绍麻江“夷俗”时说:
东苗妇以花布蒙首,项带银环,束青带,著青裤,好养鸭,又名“鸭崽苗”。①
这是到目前为止笔者所看到的唯一在东苗与鸭崽(子)苗之间划上等号的史料。这意味着,至少在麻江地域,东苗与鸭崽苗已趋同。
综合上述史料,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最晚在清代,在贵定县以东、以南的黔东南地区,出现了一个因善养鸭而被称作“鸭崽(子)苗”的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与东苗渐趋融合,以致又被人误称为“冬苗”,而写作“(佟)苗”。到民国后期,两个群体终于合而为一,成为当今人们所熟知的“东家人”。
三、民间关于东家人的历史记忆
笔者和研究生董波在麻江调查期间,曾经拍摄了赵、蓝、杨、王等数姓东家人的族谱。虽然这些族谱多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撰修,且形式和内容都非常简单,有的甚至只是抄录在笔记本上,笔迹粗糙,文句不通,但它们是东家人历史记忆的文字表达,对我们探寻东家人的来源、迁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六堡(也称陆堡)《赵氏族谱》之《本族简史》云:
据光绪年间,青岩我族举人赵以江册文简史记载,先祖原系江西省九江府守县东南乡南门街居住……清朝元年,下世祖,一祖公官封定国公,二祖公封文华殿大学士,江西省主考官,三祖公官至知府朝堂,四祖公为龙虎将军。祖公弟兄四人因任有官职,为于府门会上歧义,被奸臣谗言诬告我祖有起反之意,皇上欲斩四位祖公大人,因此弟兄商议,共同奔上贵州避难,大房公住安顺府提台街对面,二房公住遵义府桐梓县城,三房公和四房公住青岩城内,后分一支住古州,一支住八寨。我鼻祖赵公松近,系四房之后依(裔),迁居麻哈州北乡偿班,后移六堡大寨居住。②
虽然族谱如此记载,但六堡赵氏族人的口头传说可不是这样。他们认为,这个族谱是清末时,他们的族人赵枝秀、赵枝芳和赵枝才等,从甫中状元的贵阳青岩赵以炯(1857—1906年,与族谱所载之赵以江同族)家族抄来的,一起抄来的甚至还包括嗣后他们使用的字辈。而真实情况是,他们的始祖赵松近乃一孤儿,明末清初,因被偿班(碧波乡境内)赵王波收为养子而依赵姓,并起名为“进善”(音,意为进是汉族人)。顺治年间(约1653年),赵松近的三子赵乾苏又迁居六堡。①
如此看来,无论六堡赵姓是否与青岩赵姓同宗,他们原来的族属都应当是汉族,因为如上所述,他们的始祖赵松近本身就是汉族。据《赵氏族谱》载,赵松近的后裔分布在凯里、都匀、贵定等地,截至1997年修谱时,计有648户3564人。
隆昌坝寨《杨氏家谱》载:“杨氏祖,弘农郡,故籍江西,明朝初期入黔,定居于现在的麻哈碧波干溪高寨”②,后因猎熊羔而获此境,从此立足坝寨。其近祖为杨阿莽,开基远祖则不可考,只说“又不知过了多少代才到本祖杨阿莽”。1993年,有来自50多个地方总计528户杨姓后裔,集资为杨阿莽立碑。谱载,其江西字派为“再、正、通、光、昌、胜、秀”,入黔字派初为“文、国、枝、中、洪、大、有、德、步、光、辉、绍”,后来又增加“福、寿、天、子、朝、正、登”等数十个字。
马坡《蓝氏族谱》载:
我蓝氏原籍系江西绕(饶)州市景德镇猪市巷人,由因明朝洪武年间,遗乱地转调南征北(按:当为“调北征南”之误)而迁,由始祖蓝公发(宏)远带其儿女(奎越公、奎龙公、奎虎公)入黔,先后往拦河寨,后改平越,时因与官府不能协调,散居摆郎马口、毛粟树、雄通寨、周家庄、冷水营、黄平、重兴等地,后第起乃由祖居地平越府南乡摆郎迁移。始祖入黔至今已五百余年两千余人,迁偿班、马坡、新牌已有二百年。③
据该谱所载,从始祖蓝发(宏)远至今已繁衍23代,从第13世蓝登麟开始的字辈分别为“登、邦、正、玉、有、元、定、国、芳、宗、成、开”。虽然该谱前后矛盾,文字表达不清,但它透露出几个重要信息: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因“调北征南”,从景德镇猪市巷迁来;原居平越(今福泉市),后迁移至麻江的偿班、马坡、新牌等地。
翁把朗(隆昌旧称,东家语,意为水牯牛)《王氏族谱》载:
有祖吴龙,从(徙)居江西吉安府泰和县东门内珠市巷……吴普善有八子也,普生显,其先(抵)贵州,时草木渐荒,地看(瘠)寡利,苗蛮盘踞,原是鬼国,因洪武二年调北填南,是以世祖吴显伏上黔南,落业贵州麻哈县翁把朗。其时翁邑荒郊山岭,阔深纵横数十里。始祖开荒田亩,修整土园,千辛万苦,划地为邑,插草为标。俟至明清两时,改姓唤名曰王氏,子孙繁盛,永远遗嗣。①
吴姓改王姓的原因,据该谱所述,是因为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吴承元、吴承杰各将一子拜寄于王忠保其人,于是改从王姓。该谱还详述了其先祖在贵州各地分支、迁徙的时间、地点及路线。
除《赵氏族谱》外,其他族谱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述说他们的祖先是在“调北征南”或“调北填南”的历史背景下,于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从江西某地猪市巷(或珠市巷、珠子巷等)迁来。打开互联网网页搜索便不难发现,在贵州,说自己的祖籍在“江西猪市巷”的姓氏还有很多,甚至有人声称,贵州80%的人自称来自江西猪市巷。《凯里文史资料》在介绍东家人时也说:“东家在民国以前,迁徙亦甚频繁,据传祖籍源自江西省,经过长途跋涉,从江西经湖南,最后入境贵州。进入贵州后,散居在福泉、麻江、贵定、龙里等地。”②不过,它并没有明确说是源自江西猪市巷。
四、对东家人历史记忆的解读
江西肯定有名叫“猪市巷”或“珠市巷”等发音相近的地方,而且可能还不止一个,但那么多的姓氏都出自同一个地方,显然不太可能。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傅友德率30万大军入滇黔平乱,大获全胜。为了巩固边疆,扼守云南,明王朝留下部分军队,沿入滇通道次第布防,建立卫所,并将他们的家眷迁来,屯垦驻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调北征南”。洪武到永乐年间(1368—1424年),明王朝又以三年不纳粮租作为优抚条件,从中原、湖广、江南等省征调大批农民、工匠、役夫、商贾、犯官等迁居贵州,垦荒拓殖,并发给农具、耕牛、种子、田地等,这就是所谓的“调北填南”。那些江西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入黔地的。至今,东家人还流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从江西绑来的,途中还乘船渡江。他们现在走路时反手在背的习惯,就是因为当年被绑留下的,有的据说手臂上还遗有印迹。①当然,也不排除有少数江西人是在这之后,因为其他原因如逃债、避祸、躲瘟疫等入黔的。
由此推断,“猪市巷”很可能就是当年那些移民入黔前的一个集中地,而非他们真正的祖籍地。其中有的人甚至可能还是来自其他省份,而不是江西,所以在贵州的一些姓氏中,还有来源于南京猪市巷或江苏猪市巷等说法。正因为如此,所以,对那些宣称祖籍地在江西猪市巷的人来说,猪市巷也许并不具有寻根的意义,而只具有表征的意义,就像石壁村之于客家人,珠玑巷之于广府人,南京之于川滇诸多姓氏。这些地方或者是某个区域的先民流转迁徙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中转站,或者是他们情感归属的寄居地。
事实上,由于江西距离贵州相对较近,通过湖南进入贵州较为便利,所以入黔的人也特别多,这在史籍上也有记载。在进入贵州的江西人中,很多人恐怕都是单身,因为在那个交通隔阻、疾病横行的年代,携家带口长途跋涉,所付出的代价太大,风险亦极高。这些单身汉在黔地落脚之后,只能与当地土著人家的女子结婚,以解决配偶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子嗣被逐渐同化,而成为贵州“苗蛮”中的一员。清人李宗昉就曾形象地描述了这一过程,他说:“凡他省人客黔,娶妻生子,名‘转窝子’。转窝所生,名‘门斗子’。再传,则土人矣。‘转’读去声。江西人尤多。”①
在贵州的社会发展史上,这种民族间的融合曾长期存在。史料载,自春秋战国以来,就不断有汉人陆续进入黔地。民族融合的结果,是他们逐渐被同化,以致原有的社会文化特征丧失殆尽,而被人视作“苗蛮”种类。其中,最突出的例证当属宋家、蔡家。“宋家,春秋时宋人之裔。为楚所俘,放之南徼,遂流为夷”②,而“蔡家,本蔡国之裔。战国时楚将庄蹻灭牂牁,时蔡侯久为楚所灭,遂迁公族于牂牁,于是苗中有蔡家子矣”③。如前所述,即便东苗,也被认为是由唐代的“东谢”演变而来。对此,民国《贵州通志》评价说:
宋元以前,中国对于贵州仅取羁縻主义,故其戍卒居留、亡虏迁徙,久则习已俱化,而汉族与苗族遂有血统之混合。今之苗族,由历史上溯其遗迹,盖尚有多数为汉族同化者,如苗中有宋家,宋家之遗民为楚放逐者也;有蔡家,蔡之公族为楚迁徙者也;有龙家,汉武帝时蜀之大姓迁于牂牁者也。又平越、黄平间之夭苗多姬姓,相传为周后;平越、清平间之西苗有谢、马、何、卢、雷、罗等姓。黎平间之花苗有张、陆、姚、李、朱、潘、杨等姓,凡此非豪族大姓之子孙,亦流寓客民之遗裔也。④
由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一些在“调北征南”或“调北填南”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进入贵州的江西人,逐渐融入了此前已久居黔地的东苗中,而成为东家人的又一重要来源。好养鸭和善养鸭的生活习性,便是他们从江西带来的。明清时期,他们与东苗的融合尚不完全,而且又有擅长养鸭的明显特征,所以被称作鸭崽(子)苗,与东苗分属两个不同的苗蛮种类。清末至民国年间,随着文化融合的加快,鸭崽(子)苗与东苗日趋融为一体,而被人称为东家人。
但是,既然东家人是东苗与从江西迁来的鸭崽(子)苗融合的产物,那为什么现在的东家人都宣称自己的祖籍地在江西?这是否意味着,历史上的东苗都消失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其实,那些宣称祖籍地在江西的人,有许多就是历史上的东苗。而他们之所以宣称祖籍地在江西,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如赵华甫先生所认为的:明清政府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曾多次对起义的贵州土著民族进行大规模的血腥镇压。幸存者为了生存,被迫隐姓埋名,往外迁徙,并告诫其子孙后代,以后若遇官军盘问,就说自己是江西猪市巷迁来的,如此便可以避免官军的杀戮。①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则是,东苗原来实行子父联名制,没有像汉族那样固定的姓氏,②更没有文献记录的族谱,采汉姓之后,便像六堡村赵姓那样,直接抄录同姓汉人的族谱,于是便有了祖籍地在江西之说。
五、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民族身份确定为畲族的东家人是历史上的东苗与明代以后从江西迁入的汉人融合的产物。东苗与西苗均源于东晋的谢氏,早在明代之前很久,就已经在贵州生活了相当长时间,且人数甚众。明代,在“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的历史背景下,大批江西人进入贵州。他们在被当地土著民族同化的同时,又因为其中某个群体好养鸭和善养鸭,而被人称为鸭崽(子)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与东苗渐趋融合,以致又被人误称为“冬苗”,而写作“(佟)苗”。到民国后期,两个群体终于合而为一,成为人们所熟知的东家人。
在确定民族身份之前,贵州畲族被汉族称为东家人。东家人自称嘎孟,苗族称其为嘎斗。其中,“嘎”是表示语气的冠词,没有实际意义,“孟”和“斗”的意思则不明。③关于东家人的来源,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我们姑且分别称之为“土著说”和“外来说”。“土著说”认为,东家人就是历史上的东苗或鸭崽(子)苗,他们早在明代以前就生活在贵州境内。④“外来说”则认为,东家人曾居住在江西赣江流域及赣东、赣东北一带,元末和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因奉旨征讨、迁徙或避祸才迁入贵州,这也是他们定为畲族的一个重要依据。①这两种观点,哪一种更符合历史事实?或者,它们居然是可兼容的?这是笔者于2007年初秋赴黔东南进行实地调查后,一直在苦苦思索的问题。
一、史籍关于东苗的记载
据有人考证,东苗一词最早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东苗乱”而见载史册。②之后,明天顺二年(1458年),麻城人李添保“以逋贼逃入苗中,自诡为唐后”③,与“东苗干把猪④等僭伪号,攻都匀诸卫”⑤,远近震动。镇守湖广、贵州太监阮让等奏报:“东苗为贵州诸种蛮夷之首,负固据险,僭号称王,其他种类多被逼胁,东苗平则诸蛮夷莫不服从矣。”⑥英宗遂“命(方)瑛与巡抚白圭合川、湖、云、贵军讨之,克六百余寨”⑦,生擒干把猪。未久,李添保也被俘获。
从阮让等奏报给英宗的内容来看,既然东苗“为诸种蛮夷之首”,且“其他种类多被逼胁,东苗平则诸蛮夷莫不服从”,那么,东苗应该在明代之前,就已经在贵州生活了相当长时间,且人数甚众。否则,他们不可能拥有那么强大的势力。曾经在贵州担任布政使的罗绕典(1793—1854年)也认为,东苗来源于唐代的“东谢”。他说:
东晋时,命谢氏世为牂牁太守。及侯景乱梁,牂牁与中国不通,而谢氏保境如故。至唐时,牂牁又分裂,于是有东、西谢之称。其后遂以名其部族,曰“东苗”、“西苗”。⑧
《旧唐书》记“东谢”曰:
东谢蛮,其地在黔州之西数百里,南接守宫獠,西连夷子,北至白蛮。土宜五谷,不以牛耕,但为畲田,每岁易。俗无文字,刻木为契。散在山洞间,依树为层巢而居,汲流以饮。皆自营生业,无赋税之事。……其首领谢元深,既世为酋长,其部落皆尊畏之。①
因为东苗与西苗同源于东晋谢氏,所以相关史籍总是将两者并列在一起描述。更有学者据此认为,东苗、西苗“实为汉人的后裔,其族属应该为汉族”②。
关于东苗文化特征的记载,已知最早的为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的《贵州图经新志》。该书是贵州省现存最早的一部方志,书中记载了贵州宣慰司、龙里卫、新添卫、清平卫四地的东苗。贵州宣慰司东苗:
男髽髻,着短衣,色尚浅蓝,首以织花布条束发。妇着花裳,无袖,唯遮覆前后而已。裙亦浅蓝色,细褶,仅蔽其膝。其俗婚娶男女相聚歌舞,名为“跳月”。情意相悦者为婚,初不较其财,逮至一年方遣人责之,虽死亦不置。③
龙里卫东苗:
性憨而厉。男子科头赤脚,衣用青白花布,领缘以土锦。妇人盘髻,贯以长簪,衣用土锦,无襟。当幅中作孔,以首纳而服服之。别作两袖,作事则去之。杂缀海、铜铃、青白绿珠为饰。春月,以木刻马为神,召集男女祭以牛酒,曰“木马鬼”。老者坐饮马傍,未婚男女俱盛饰衣服,吹笙唱歌,旋马跳舞,类皆淫泆之词,谓之“跳月”,彼此情悦者遂同归。男家父母杀鸡占卜纳马女。父母论姿色索牛马,多至十五六。力不足者,累岁征之。④
新添卫所辖五长官司之东苗:
椎髻赤足,妇女以土锦为衣。婚不用媒,相悦则奔。既婚之后,始以牛马聘礼。①
清平卫东苗:
稍通汉语,服红花衣,头插白鸡毛,其俗同于犵狫。②
稍后的嘉靖《贵州通志》则记载了乖西司和龙里卫大平划司的东苗。乖西司苗:
其类有二:曰东苗,曰西苗。其俗相同,皆髽髻,着短衣,色尚浅蓝,以织花布条束发。妇女着花裳,无袖,唯遮覆前后而已。裙亦浅蓝细褶,仅蔽其膝。婚娶,集男女歌舞,名为“跳月”。《成婚图考》云:乖西苗性类犬羊,不通汉语。以十二支所肖为场,男妇持货交易,以供赋税。重财轻命,判服不常。死丧,杀牛祭鬼,击鼓作乐。③
对乖西司苗的记载和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对贵州宣慰司东苗的记载差不多。对龙里卫大平伐司东苗的记载则完全援引《贵州图经新志》对龙里卫东苗的记载。④
继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和嘉靖《贵州通志》之后,只有乾隆《贵州通志》对东苗的记载略有创新。其记曰:
有族无姓,衣尚浅蓝色,短不及膝,以花巾束发。妇人衣花衣,无袖,唯两幅遮前覆后,着细褶短裙。跳月与花苗同。以中秋祭先祖及亲族远近之亡故者。择牡牛以毛旋头角正者为佳,时其水草以饲,至禾熟牛肥,酿酒砍牛,召集亲属剧饮歌唱。延鬼师于头人之家,以木板置酒馔,循序而呼鬼之名,竟昼夜乃已。春猎于山,获禽,亦必以祭。畏见官长,事有不平,但听乡老决之。急公服役,比于良民,唯在平远、高堡等寨者多剽悍。近皆守法。⑤
他如万历《贵州通志》和明、清一些官员的著述,如郭子章(1543—1618年)的《黔记》、田雯(1635—1704年)的《黔书》等,对东苗文化特征的描述,均与上述三种大同小异。
关于东苗的地理分布,各种记载则不一。明代,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东苗在贵州宣慰司(贵阳周边一带,治所在今贵阳市)、龙里卫、新添卫(今贵定县)、清平卫(今凯里市炉山镇)等地;嘉靖《贵州通志》记东苗在乖西司(今开阳县)和龙里卫;万历《贵州通志》记东苗在龙里卫(今龙里县);①郭子章《黔记》记东苗在贵州宣慰司,特别是宣慰司所领九长官司之一龙里司。②
清代,田雯《黔书》记东苗在新贵(今贵阳市)、龙里。③他并称,龙里县的白苗“亦名东苗、西苗”④。乾隆《贵州通志》载东苗“在贵筑(今贵阳市)、龙里、清平”⑤。《大清一统志》载东苗在新添卫所辖五长官司及贵筑之谷池里。⑥爱必达(?—1771年)《黔南识略》载:“天柱县林深箐密,诸蛮杂处,为东苗羽翼。”⑦李宗昉(1779—1846年)《黔记》载“东苗在贵筑、修文、龙里、清镇及广顺(今长顺)各属”。⑧罗绕典在《黔南职方纪略》载东苗在平越(今福泉市)、麻哈(今麻江县)。⑨桂馥《黔南苗蛮图说》载东苗“唯贵筑、麻哈两属有”⑩。
民国时期,《贵州通志》载:“平越自清同治间地方收复后,向来所属诸苗较少,近则东南乡间有东苗、木老、仡兜数种,多与汉人杂处,男女衣服言语亦多仿汉人”。又“清平县东六个鸡、角冲、干坝等处,有东苗与西苗、鸭崽苗,杂居汉人村寨,或十家八家,三二十家不等”。①《麻江县志》载,该县有“夷族”近10种,其中也包括东苗。②
从这些记载来看,东苗在历史上的分布地主要为贵阳及其周边地区,包括开阳、修文、清镇、龙里、长顺、贵定、福泉、麻江、凯里、天柱等十余县。其中,贵阳及其东南的龙里是明清时期东苗聚集的主要区域。到清末民初,东苗的住居地已渐向黔东南转移,集中在福泉、麻江、凯里等地。东家人的“嘎须”仪式③也佐证了这一点,其“请先人的路线大体是从现居住地——烂坝——两板凳——土桥河——陆家桥——谷宾——景阳——谷硐——坝芒水头——昌明——平伐(今贵定县)”,这些地名均在麻江、贵定境内。这说明,“东家人入黔后散居贵定、平伐等地,后又迁徙至现所在地”。④
二、史籍关于鸭崽(子)苗的记载
东家人因为擅长养鸭而被人称为鸭崽苗或鸭子苗。⑤从笔者目前已掌握的资料来看,最早记载鸭崽(子)苗的是罗绕典。他在成书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的《黔南职方纪略》中详列黔地各“苗蛮”习俗时说:
鸭子苗,贵定有之,服食与青苗同。⑥
在介绍他们的居住地时,他又说:
贵定县有苗六种:一曰花苗,二曰白苗,三曰家苗,四日狇狫,五曰青苗,六曰鸭子苗,(鸭子苗)居西乡杨柳冲、龙塘湾、罗雍
诸寨。①
该书共列举了50种“苗蛮”类,其中既包括东苗,也包括鸭子苗。而且,他们的居住地也不相同,东苗在平越、麻哈,鸭子苗在贵定。换言之,在罗绕典看来,东苗与鸭子苗是两种不同的“苗蛮”种类。
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桂馥所撰《黔南苗蛮图说》,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共记载“苗蛮”86种,是“目前国内外所知同一种书中记载贵州民族种类最多、各种民族的信息量最大的文献”。作为一名地方官吏和文人画家,桂馥在贵州生活了30余年,经常深入民间,十分了解贵州各民族的生产生活状况,“由他绘制并撰写的《黔南苗蛮图说》具有很大的真实性”②。桂馥本人也声称:“余今所画,大都亲眼所及,非画工家所可同语。余自咸丰戊午,从事黔军营十有余年,历遍上下游,所至苗疆,察看山川形势,采访苗民风俗,以及性情之顺逆,好尚之美恶,服饰、饮食、屋宇,一一笔之于册。”③在该书中,桂馥也是把鸭崽苗和东苗作为两种不同的“苗蛮”来对待。关于东苗,他说:
东苗有族无姓,男子留顶发,以织花布条束之。短衣背甲,色尚浅蓝。妇人衣花衣,无两袖,以两幅遮前覆后,穿细褶短裙。中秋,合寨延鬼师祭祖、屠牛,以木板陈馔,循序而呼鬼之名。祭毕,集亲族畅饮尽夜。春猎于山,获禽兽必荐祖先而后食。唯贵筑、麻哈两属有。④
关于鸭崽苗,他说:
鸭崽苗,在都匀府属(辖今都匀、凯里、麻江、丹寨、独山、荔波等地)。男服饰效汉装,女则椎髻,短裙露胸,跣足。长簪大环,项圈锦襃。以种山、渔猎为务。风俗与水家、獞家等大略相同。①
而且,书中所绘之《苗蛮图》,东苗与鸭崽苗的男女服饰均有明显差异。②
甚至连民国《贵州通志》(1948年)也将东苗与鸭崽苗视作两个不同的群体。该志有两处援引《清平访册》云:
清平县东六个鸡、角冲、干坝等处,有东苗与西苗、鸭崽苗,杂居汉人村寨。③
佟(㹣)苗,清平县有之。《访册》云:佟(㹣)苗本名鸭崽苗,女衣黑,多著白花或蜡花。裙长仅五寸,近有长至尺二者。内着裤,中有一缝,外加密纽。裹腿直缠至肘腋,嗜养乳鸭。髻高尺许,继以花带,胸背著布一幅如背心。四时均若半截草履。与东、西苗杂居于县东之六角鸡、角冲、干坝等处。④
有意思的是,该志又新出现一个“佟(㹣)苗”,作为鸭崽苗的别称,并且说:
佟(㹣)苗,麻哈州(今麻江县)有之。《访册》云:佟苗类于夭(绕)家,住养鹅、杀寡等寨,善养鸭以是为营生,故人谓之鸭崽苗。⑤
该志原作“㹣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点校出版时改为“佟苗”。查汉语词典,“佟”的标准读音为tong,“㹣”的读音为zhong。但在民间,将“东苗”读作“冬苗”,再加上偏旁,成为“佟苗”或“㹣苗”,但读音仍为dong,是完全可能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该志也将“佟(㹣)苗”或鸭崽苗视作与“东苗”不同的群体。这说明,即使是到民国年间,在人们看来,东苗与鸭崽苗也还是有所区别的。
更早的民国《麻江县志》(1938年)在介绍麻江“夷俗”时说:
东苗妇以花布蒙首,项带银环,束青带,著青裤,好养鸭,又名“鸭崽苗”。①
这是到目前为止笔者所看到的唯一在东苗与鸭崽(子)苗之间划上等号的史料。这意味着,至少在麻江地域,东苗与鸭崽苗已趋同。
综合上述史料,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最晚在清代,在贵定县以东、以南的黔东南地区,出现了一个因善养鸭而被称作“鸭崽(子)苗”的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与东苗渐趋融合,以致又被人误称为“冬苗”,而写作“(佟)苗”。到民国后期,两个群体终于合而为一,成为当今人们所熟知的“东家人”。
三、民间关于东家人的历史记忆
笔者和研究生董波在麻江调查期间,曾经拍摄了赵、蓝、杨、王等数姓东家人的族谱。虽然这些族谱多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撰修,且形式和内容都非常简单,有的甚至只是抄录在笔记本上,笔迹粗糙,文句不通,但它们是东家人历史记忆的文字表达,对我们探寻东家人的来源、迁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六堡(也称陆堡)《赵氏族谱》之《本族简史》云:
据光绪年间,青岩我族举人赵以江册文简史记载,先祖原系江西省九江府守县东南乡南门街居住……清朝元年,下世祖,一祖公官封定国公,二祖公封文华殿大学士,江西省主考官,三祖公官至知府朝堂,四祖公为龙虎将军。祖公弟兄四人因任有官职,为于府门会上歧义,被奸臣谗言诬告我祖有起反之意,皇上欲斩四位祖公大人,因此弟兄商议,共同奔上贵州避难,大房公住安顺府提台街对面,二房公住遵义府桐梓县城,三房公和四房公住青岩城内,后分一支住古州,一支住八寨。我鼻祖赵公松近,系四房之后依(裔),迁居麻哈州北乡偿班,后移六堡大寨居住。②
虽然族谱如此记载,但六堡赵氏族人的口头传说可不是这样。他们认为,这个族谱是清末时,他们的族人赵枝秀、赵枝芳和赵枝才等,从甫中状元的贵阳青岩赵以炯(1857—1906年,与族谱所载之赵以江同族)家族抄来的,一起抄来的甚至还包括嗣后他们使用的字辈。而真实情况是,他们的始祖赵松近乃一孤儿,明末清初,因被偿班(碧波乡境内)赵王波收为养子而依赵姓,并起名为“进善”(音,意为进是汉族人)。顺治年间(约1653年),赵松近的三子赵乾苏又迁居六堡。①
如此看来,无论六堡赵姓是否与青岩赵姓同宗,他们原来的族属都应当是汉族,因为如上所述,他们的始祖赵松近本身就是汉族。据《赵氏族谱》载,赵松近的后裔分布在凯里、都匀、贵定等地,截至1997年修谱时,计有648户3564人。
隆昌坝寨《杨氏家谱》载:“杨氏祖,弘农郡,故籍江西,明朝初期入黔,定居于现在的麻哈碧波干溪高寨”②,后因猎熊羔而获此境,从此立足坝寨。其近祖为杨阿莽,开基远祖则不可考,只说“又不知过了多少代才到本祖杨阿莽”。1993年,有来自50多个地方总计528户杨姓后裔,集资为杨阿莽立碑。谱载,其江西字派为“再、正、通、光、昌、胜、秀”,入黔字派初为“文、国、枝、中、洪、大、有、德、步、光、辉、绍”,后来又增加“福、寿、天、子、朝、正、登”等数十个字。
马坡《蓝氏族谱》载:
我蓝氏原籍系江西绕(饶)州市景德镇猪市巷人,由因明朝洪武年间,遗乱地转调南征北(按:当为“调北征南”之误)而迁,由始祖蓝公发(宏)远带其儿女(奎越公、奎龙公、奎虎公)入黔,先后往拦河寨,后改平越,时因与官府不能协调,散居摆郎马口、毛粟树、雄通寨、周家庄、冷水营、黄平、重兴等地,后第起乃由祖居地平越府南乡摆郎迁移。始祖入黔至今已五百余年两千余人,迁偿班、马坡、新牌已有二百年。③
据该谱所载,从始祖蓝发(宏)远至今已繁衍23代,从第13世蓝登麟开始的字辈分别为“登、邦、正、玉、有、元、定、国、芳、宗、成、开”。虽然该谱前后矛盾,文字表达不清,但它透露出几个重要信息: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因“调北征南”,从景德镇猪市巷迁来;原居平越(今福泉市),后迁移至麻江的偿班、马坡、新牌等地。
翁把朗(隆昌旧称,东家语,意为水牯牛)《王氏族谱》载:
有祖吴龙,从(徙)居江西吉安府泰和县东门内珠市巷……吴普善有八子也,普生显,其先(抵)贵州,时草木渐荒,地看(瘠)寡利,苗蛮盘踞,原是鬼国,因洪武二年调北填南,是以世祖吴显伏上黔南,落业贵州麻哈县翁把朗。其时翁邑荒郊山岭,阔深纵横数十里。始祖开荒田亩,修整土园,千辛万苦,划地为邑,插草为标。俟至明清两时,改姓唤名曰王氏,子孙繁盛,永远遗嗣。①
吴姓改王姓的原因,据该谱所述,是因为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吴承元、吴承杰各将一子拜寄于王忠保其人,于是改从王姓。该谱还详述了其先祖在贵州各地分支、迁徙的时间、地点及路线。
除《赵氏族谱》外,其他族谱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述说他们的祖先是在“调北征南”或“调北填南”的历史背景下,于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从江西某地猪市巷(或珠市巷、珠子巷等)迁来。打开互联网网页搜索便不难发现,在贵州,说自己的祖籍在“江西猪市巷”的姓氏还有很多,甚至有人声称,贵州80%的人自称来自江西猪市巷。《凯里文史资料》在介绍东家人时也说:“东家在民国以前,迁徙亦甚频繁,据传祖籍源自江西省,经过长途跋涉,从江西经湖南,最后入境贵州。进入贵州后,散居在福泉、麻江、贵定、龙里等地。”②不过,它并没有明确说是源自江西猪市巷。
四、对东家人历史记忆的解读
江西肯定有名叫“猪市巷”或“珠市巷”等发音相近的地方,而且可能还不止一个,但那么多的姓氏都出自同一个地方,显然不太可能。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傅友德率30万大军入滇黔平乱,大获全胜。为了巩固边疆,扼守云南,明王朝留下部分军队,沿入滇通道次第布防,建立卫所,并将他们的家眷迁来,屯垦驻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调北征南”。洪武到永乐年间(1368—1424年),明王朝又以三年不纳粮租作为优抚条件,从中原、湖广、江南等省征调大批农民、工匠、役夫、商贾、犯官等迁居贵州,垦荒拓殖,并发给农具、耕牛、种子、田地等,这就是所谓的“调北填南”。那些江西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入黔地的。至今,东家人还流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从江西绑来的,途中还乘船渡江。他们现在走路时反手在背的习惯,就是因为当年被绑留下的,有的据说手臂上还遗有印迹。①当然,也不排除有少数江西人是在这之后,因为其他原因如逃债、避祸、躲瘟疫等入黔的。
由此推断,“猪市巷”很可能就是当年那些移民入黔前的一个集中地,而非他们真正的祖籍地。其中有的人甚至可能还是来自其他省份,而不是江西,所以在贵州的一些姓氏中,还有来源于南京猪市巷或江苏猪市巷等说法。正因为如此,所以,对那些宣称祖籍地在江西猪市巷的人来说,猪市巷也许并不具有寻根的意义,而只具有表征的意义,就像石壁村之于客家人,珠玑巷之于广府人,南京之于川滇诸多姓氏。这些地方或者是某个区域的先民流转迁徙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中转站,或者是他们情感归属的寄居地。
事实上,由于江西距离贵州相对较近,通过湖南进入贵州较为便利,所以入黔的人也特别多,这在史籍上也有记载。在进入贵州的江西人中,很多人恐怕都是单身,因为在那个交通隔阻、疾病横行的年代,携家带口长途跋涉,所付出的代价太大,风险亦极高。这些单身汉在黔地落脚之后,只能与当地土著人家的女子结婚,以解决配偶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子嗣被逐渐同化,而成为贵州“苗蛮”中的一员。清人李宗昉就曾形象地描述了这一过程,他说:“凡他省人客黔,娶妻生子,名‘转窝子’。转窝所生,名‘门斗子’。再传,则土人矣。‘转’读去声。江西人尤多。”①
在贵州的社会发展史上,这种民族间的融合曾长期存在。史料载,自春秋战国以来,就不断有汉人陆续进入黔地。民族融合的结果,是他们逐渐被同化,以致原有的社会文化特征丧失殆尽,而被人视作“苗蛮”种类。其中,最突出的例证当属宋家、蔡家。“宋家,春秋时宋人之裔。为楚所俘,放之南徼,遂流为夷”②,而“蔡家,本蔡国之裔。战国时楚将庄蹻灭牂牁,时蔡侯久为楚所灭,遂迁公族于牂牁,于是苗中有蔡家子矣”③。如前所述,即便东苗,也被认为是由唐代的“东谢”演变而来。对此,民国《贵州通志》评价说:
宋元以前,中国对于贵州仅取羁縻主义,故其戍卒居留、亡虏迁徙,久则习已俱化,而汉族与苗族遂有血统之混合。今之苗族,由历史上溯其遗迹,盖尚有多数为汉族同化者,如苗中有宋家,宋家之遗民为楚放逐者也;有蔡家,蔡之公族为楚迁徙者也;有龙家,汉武帝时蜀之大姓迁于牂牁者也。又平越、黄平间之夭苗多姬姓,相传为周后;平越、清平间之西苗有谢、马、何、卢、雷、罗等姓。黎平间之花苗有张、陆、姚、李、朱、潘、杨等姓,凡此非豪族大姓之子孙,亦流寓客民之遗裔也。④
由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一些在“调北征南”或“调北填南”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进入贵州的江西人,逐渐融入了此前已久居黔地的东苗中,而成为东家人的又一重要来源。好养鸭和善养鸭的生活习性,便是他们从江西带来的。明清时期,他们与东苗的融合尚不完全,而且又有擅长养鸭的明显特征,所以被称作鸭崽(子)苗,与东苗分属两个不同的苗蛮种类。清末至民国年间,随着文化融合的加快,鸭崽(子)苗与东苗日趋融为一体,而被人称为东家人。
但是,既然东家人是东苗与从江西迁来的鸭崽(子)苗融合的产物,那为什么现在的东家人都宣称自己的祖籍地在江西?这是否意味着,历史上的东苗都消失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其实,那些宣称祖籍地在江西的人,有许多就是历史上的东苗。而他们之所以宣称祖籍地在江西,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如赵华甫先生所认为的:明清政府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曾多次对起义的贵州土著民族进行大规模的血腥镇压。幸存者为了生存,被迫隐姓埋名,往外迁徙,并告诫其子孙后代,以后若遇官军盘问,就说自己是江西猪市巷迁来的,如此便可以避免官军的杀戮。①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则是,东苗原来实行子父联名制,没有像汉族那样固定的姓氏,②更没有文献记录的族谱,采汉姓之后,便像六堡村赵姓那样,直接抄录同姓汉人的族谱,于是便有了祖籍地在江西之说。
五、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民族身份确定为畲族的东家人是历史上的东苗与明代以后从江西迁入的汉人融合的产物。东苗与西苗均源于东晋的谢氏,早在明代之前很久,就已经在贵州生活了相当长时间,且人数甚众。明代,在“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的历史背景下,大批江西人进入贵州。他们在被当地土著民族同化的同时,又因为其中某个群体好养鸭和善养鸭,而被人称为鸭崽(子)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与东苗渐趋融合,以致又被人误称为“冬苗”,而写作“(佟)苗”。到民国后期,两个群体终于合而为一,成为人们所熟知的东家人。
附注
①1996年6月,贵州省人民政府分别以黔府函(1996)143号和144号两个文件,认定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之都匀市、福泉县(后改市)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之凯里市、麻江县共4个县(市)的东家人为畲族。
②其他省份分别为:福建375193人,浙江170993人,江西77650人,广东28053人,湖南2891人,湖北2523人,安徽1563人。
③麻江县六堡畲族小学校长赵华甫认为,“孟”(或“梦”)在东家人的语言里是指用来包粽子的小竹叶,俗称“粽粑叶”,“嘎梦”(或“阿孟”)意为住在粽粑叶林子里的人或山里人。贵州民族研究所的杨昌文先生则认为,“孟”是人的意思。
④杨昌文:《贵州的畲族》(未刊稿),参见http://www.shezu.net/666/dis-pbbs.asp?boardid=20&id=307.
①徐飞、陈乐基:《贵州畲族文化综述——兼谈保护畲族传统文化初步设想》,2007年潮州畲族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
②杨昌文:《贵州的畲族》(未刊稿)。笔者尚未找到其原始出处。
③乾隆《贵州通志》卷23《师旅考》,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版,第463页。
④乾隆《贵州通志》作“千把猪”。
⑤《明史》卷166《方瑛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488页。
⑥《明英宗实录》卷293,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6254—6255页。
⑦《明史》卷166《方瑛传》,第4488页。
⑧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卷9《苗蛮》,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336页。
①《旧唐书》卷197《西南蛮·东谢蛮》,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74页。
②李德龙:《黔南苗蛮图说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
③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1《贵州宣慰司上》,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9页。
④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11《龙里卫》,第118页。
①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11《新添卫》,第122页。
②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12《清平卫》,第132页。
③嘉靖《贵州通志》卷3《风俗》,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81页。
④包括今都匀、麻江、平塘、龙里等地。
⑤乾隆《贵州通志》卷7《苗蛮》,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版,第126页。
①参见万历《贵州通志》卷12《龙里卫》,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41页。
②郭子章:《黔记》卷59《诸夷》,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90页。
③田雯:《黔书》卷1《苗俗》,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页。
④对田雯的表述,学界有不同的解释。参见李汉林《百苗图校释》,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李德龙《黔南苗蛮图说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⑤乾隆《贵州通志》卷7《苗蛮》,第126页。
⑥乾隆《贵州通志》卷7《苗蛮》,第126页。
⑦参见民国《贵州通志·土司土民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页。
⑧李宗昉:《黔记》卷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页。
⑨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卷9《苗蛮》,第353页。
⑩桂馥:《黔南苗蛮图说》第34种《东苗》,载李德龙《黔南苗蛮图说研究·附录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页。
①民国《贵州通志·土司土民志》,第156页。
②民国《麻江县志》卷5《风俗》,1938年铅印本,厦门大学图书馆藏。
③据现年40岁的麻江县六堡畲族小学校长赵华甫介绍,“嘎须”是东家人请鬼师祭祀客死他乡的先人的一种仪式。祭祀时请众人相陪,席间禁讲汉语。祭毕,有人突然在屋外用汉语讲话,陪食者即用东家话大声说:“客家人来割鸡巴了,祖人请快走!”
④赵华甫:《东家人的迁徙路》,载赵华甫《赵华甫东家人研究》(未刊稿)。
⑤实地调查表明,东家人自身也认可这一说法。赵华甫介绍说,他小的时候,还看到奶奶养了很多鸭子。不过,现在养鸭的人已很少了。
⑥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卷9《苗蛮》,第360页。
①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卷9《苗蛮》,第364—365页。
②李德龙:《黔南苗蛮图说研究》,第24页。
③桂馥:《黔南苗蛮图说叙》,载李德龙《黔南苗蛮图说研究·附录一》,第151页。
④桂馥:《黔南苗蛮图说》第34种《东苗》,载李德龙《黔南苗蛮图说研究·附录一》,第172页。
①桂馥:《黔南苗蛮图说》第32种《鸭崽苗》,载李德龙《黔南苗蛮图说研究·附录一》,第171页。
②李德龙:《黔南苗蛮图说研究》附录二《八十六种苗蛮图》,第228、230页。
③民国《贵州通志·土司土民志》,第156页。
④民国《贵州通志·土司土民志》,第172页。
⑤民国《贵州通志·土司土民志》,第171页。
①民国《麻江县志》卷5《风俗》。
②六堡《赵氏族谱·本族简史》,1997年。
①赵华甫:《六堡赵氏来源考》,载赵华甫《六堡畲族史料研究》(第一卷),2006年未刊稿。
②隆昌《杨氏家谱》,1993年。
③马坡《蓝氏族谱》,2007年。
①翁把朗《王氏族谱》,1987年。
②李东相:《凯里市民族概况·东家》(1992年),《凯里文史资料》(少数民族专辑第5辑),第16—17页。
①赵华甫:《东家人入黔探析》,载赵华甫《东家人研究文集》(未刊稿)。
①李宗昉:《黔记》卷1,第5页。
②桂馥:《黔南苗蛮图说》第39种《宋家》,载李德龙《黔南苗蛮图说研究·附录一》,第175页。
③桂馥:《黔南苗蛮图说》第40种《蔡家》,载李德龙《黔南苗蛮图说研究·附录一》,第175页。
④民国《贵州通志·土司土民志》,第193页。
①赵华甫:《东家人入黔探析》,载赵华甫《东家人研究文集》(未刊稿);赵华甫:《六堡赵氏来源考》,载赵华甫《六堡畲族史料研究》(第一卷),2006年未刊稿。
②史料仅记载西苗有谢、马、何、罗、卢、雷等姓,而东苗的姓氏只字未提。
相关人物
董建辉
责任者
相关地名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相关地名
凯里市
相关地名
麻江县
相关地名
都匀市
相关地名
福泉市
相关地名
江西省
相关地名
赣江街道
相关地名
麻城市
相关地名
都匀市
相关地名
合川区
相关地名
牂牁镇
相关地名
龙里县
相关地名
卫东区
相关地名
平远县
相关地名
高堡乡
相关地名
贵阳市
相关地名
贵定县
相关地名
炉山镇
相关地名
开阳县
相关地名
龙里县
相关地名
清平镇
相关地名
天柱县
相关地名
修文县
相关地名
清镇市
相关地名
长顺县
相关地名
开阳县
相关地名
贵定县
相关地名
福泉市
相关地名
麻江县
相关地名
凯里市
相关地名
天柱县
相关地名
大余县
相关地名
西乡县
相关地名
丹寨县
相关地名
独山县
相关地名
荔波县
相关地名
青岩镇
相关地名
江西省
相关地名
桐梓县
相关地名
古州镇
相关地名
隆昌市
相关地名
景德镇市
相关地名
马坡镇
相关地名
湖南省
相关地名
云南省
相关地名
永乐镇
相关地名
中原区
相关地名
江南区
相关地名
江苏省
相关地名
南京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