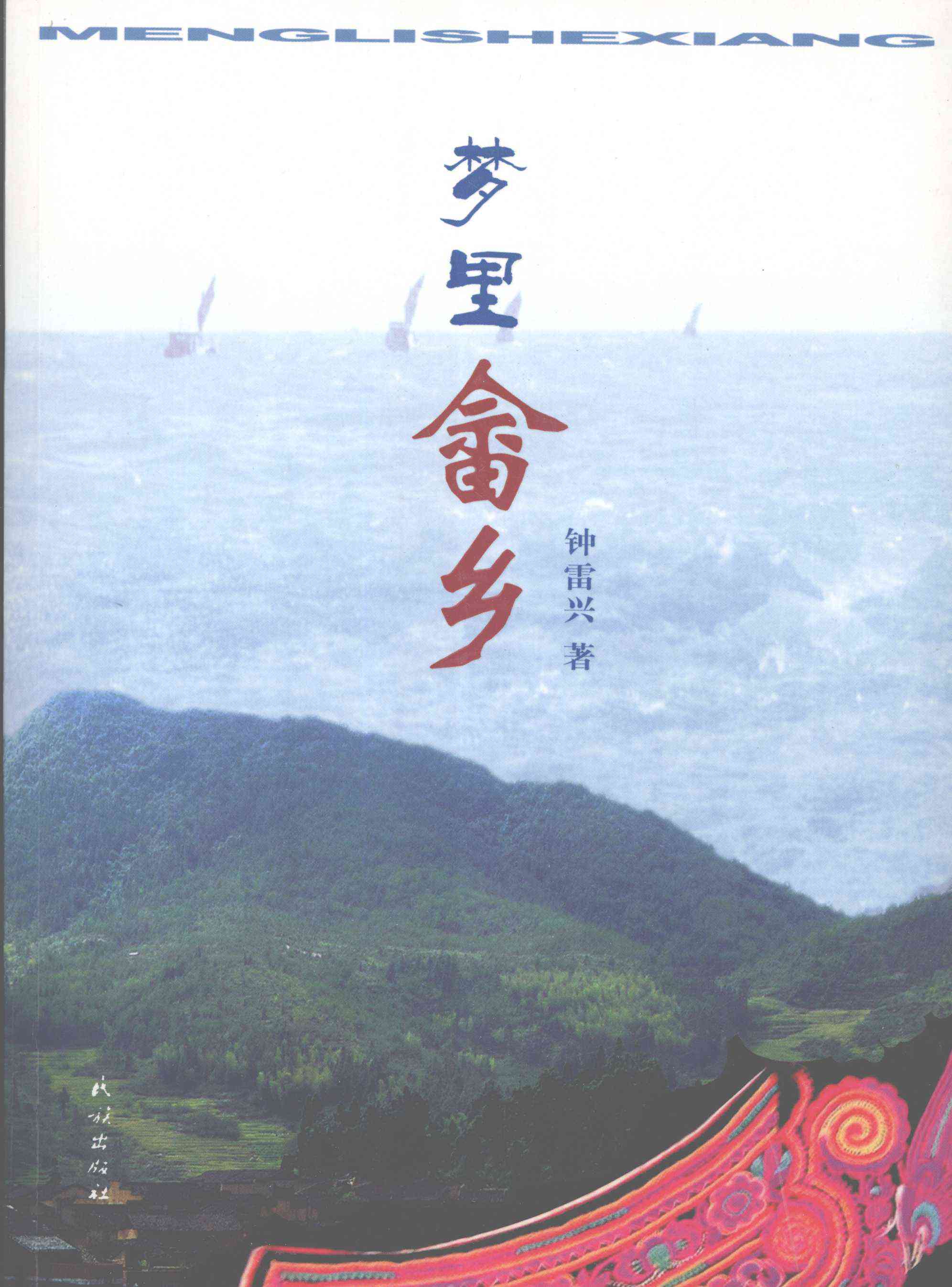内容
1
1945年正月初五,初春时节,我出生在宁德县(现在的蕉城区)八都镇南岗村的一个贫苦家庭。
南岗村,位于镇驻地东南4公里的山冈上,海拔366米,是一个典型的畲族少数民族自然村。新中国成立前,南岗村畲民和许多地方的畲民同胞一样,散处山区,搭寮而居,靠租种官山和地主山场过着“种树还山,种菁为活”、“受民田以耕”的粗放耕作生活。
新中国成立前,明朝至民国期间,宁德七都镇际头村,福安甘棠镇小岭村、北坑村、铜坑里村等畲族村,霞浦草岗村、青皎村等几个片区水稻的平均产量,亩产只有140多公斤。仅靠这样的亩产量,许多畲民连吃饭都成问题,更不用说大多数畲民的身份是佃农,既要与险恶的自然灾害和疾病作斗争,还得承受地主的盘剥、官府勒索。许多畲民始终挣扎在生存线上,如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南门岗畲族村发生瘟疫,全村83户在一个月内病死40多人,畲民生活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2
我的祖父叫钟日安,我出生时,祖父早已过世。祖父在我印象中的模样,完全来自于父亲的只言片语。父亲只告诉我,祖辈只留下一座简陋不堪的“土墙厝”。
虽然祖父的名字是那么陌生,但在他那个艰苦的年代能找到落脚地方,并且成家传承,已经值得骄傲了。
畲家的“土墙厝”,较为常见。“厝”在福建方言中,是屋子的意思,不同于用竹木和茅草搭起的“寮”。清代以前,畲民住房大多是以竹子为架搭成的“悬草寮”。这种茅寮称“千柱落脚”或者称为“千枝落地”,四面通风,呈“介”字形。架料多缚成框格型,寮面的茅草也是打成草匾之后盖上。这种茅寮不开窗户,没有烟囱,阳光不足,即便不是梅雨季节,泥土地面也十分潮湿。这样的住所,条件极为简陋,不能很好地抵御风侵雨淋,更不用说抵挡这里夏天常光临的台风暴雨了。因此,祖父建起的土墙厝,在我的家族中,实际上起到了一个“根”的作用。
我祖父留下的这座土房子,是清代以后畲家典型的“土墙厝”。土墙厝坐西朝东,土木结构,即四面以土筑墙,屋架直接安装在土墙上,中轴对称,屋顶呈“金”字形,整个空间分成四个部分,当地称为“四扇”。这种四扇的布局,便利于长子、次子等平均分得。父亲和我伯伯后来分家,各得一扇。房子周围,种有松、杉、毛竹等,浓荫蔽地。房子前有一个长长的石基,用大卵石砌成,长度约二十多米。因为大多数的畲民的房子盖在山坡上,这种石基起到了防止滑坡的作用。石基南端有一个长一米多的正方形蓄水池,用来蓄水,既可以供饮用,又可灌溉。直到现在,这个蓄水池还在发挥作用,但大多数仅用来灌溉农作物。现在的南岗村,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
常言道:“人生大事,起厝为先。”对选择宅地这样一大事,在畲族风俗里,也要请以阴阳八卦为职业的风水先生来看风水,以示慎重。其理论大致与汉族风水先生相同。畲族对家的重视或许是来自于先民的漂泊,毕竟有家才能挡风避雨。所以建房前,有一整套规矩:择吉日奠基,架木马,而后劈扇料,制作木构件;上梁之日,备好猪头、鸡、酒以及草鞋、木屐、雨伞,还有笔墨砚、镜子、头梳、红带子等物祭鲁班仙、请紫薇銮驾;到上梁时辰,鸣放鞭炮,木匠师傅将缠悬红布的正梁架好后,拿亲朋好友送来的稻米与红布压梁,并将事前备好的糍粑、粽子分馈众人,以示好彩头。同时,在当早设宴请工匠和亲戚朋友。
3
20世纪50年代,南岗还是一个乡。一听这地名,读者多少猜出这是位于山冈之上的村落。在畲民村落的命名中,有直接与风水有关的村名。如福安市有一个畲村的钟姓族人认为,所居处“高冈栖止频回顾,山头择地最为良”,故将村落命名为“山头庄”。我不清楚,历史上南岗的命名如何来的呢?估计是依山南而坐落,因此也叫“南门岗”村,顾名思义吧。
1957年,南门岗被设为乡。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畲族的专一管理。1957年7月8日,由宁德县人民委员会派出工作队到城关区后山乡进行建立民族乡的试点。其后,经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于9月8日正式设立后山、祭头、九仙、南山、南岗、北山、新楼、猴〓、雷东9个民族乡。民族事务由本民族人自管。1958年后,随着行政区域的撤区并乡,其后的少数民族事务又归并到新设的行政乡(村)兼管。直到1983年11月,县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后,经审定将畲族聚居的19个村庄划为畲族行政村。
南岗乡确切成立的时间为1957年10月10日。乡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11人,其中乡长、副乡长由畲族人担任;委员8人,畲族占6人。管辖水尾、金垂、云淡、韩丹4个村庄。韩丹村辖韩厝林、丹斗自然村,其中丹斗自然村和现在的南岗村一样,是纯畲族村。而云淡村则是一个海岛村,金垂村是沿海的一个大村,这两村以汉族为主,人口数量远远超过南岗村。到了1999年底,宁德市(现在的蕉城区)畲族人口相对聚居的行政村有33个,分布于城南、金涵、漳湾、七都、八都、九都、霍童和飞鸾、赤溪等乡镇。其中分布于八都镇和金涵乡最多,各有7个行政村。
4
南岗村,过去有近百户人家。近一二十年,多数人家往金垂村、红门里村以及城关等地搬迁。在1999年统计时,主村只有24户人家。近年来各级政府为改善山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实施“造福工程”,扶持边远山区的贫困群众往条件较好的地方搬迁集中,南岗村周围的外厝、水井两个自然村的几户人家也集中到主村来。
现在的南岗村,大部分的土墙厝都改成红砖墙的房子。有一两座房子主人的后代,大概是出于怀旧的心情,保留了原有的旧房,只是做了局部的修缮。
要说南岗村的特色,就是满山郁郁葱葱的树林,植被保护得很好。畲族,自古以来就有在村庄、住宅旁、路边、溪河边等处种树的习惯,大小的畲村均有面积不等的杂木林,畲民称之为“风水林”。自古,相当一部分的畲民开基乔迁伊始,对自身家居的营造方式是依山而建,住宅朴实无华,没有汉族的“泰山石敢当”字样的石碑等用来镇邪的添加物。但畲民谚语云:“造成风水画成龙”,畲家自有畲家的以树木培荫风水的传统。畲民认为,家居环境也许有先天不足,但人的身体和精神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家园,作为最有效的培荫风水的办法就是在房前房后植树,在村落周围造林,既可以阻挡山野之风,又可以添增家园之气。
有的畲民家族还将封山造林的规约写进家谱中,好让子子孙孙永远遵守。如清代光绪年间钟大《颍川钟氏族谱》记载,福安“仙岭洋乡长生公生道光丁末年(1847年),屋墙外有柳树一株,以为风水,子孙勿得斫伐”。植树补基,在汉族的堪舆家中也较推崇。只是畲家认为,房基植树的作用远不止一个补基功能,还有挡风聚气之功效,维护环境生态,使得村落在形态上更完美,景观上更显得丰富而有生机。
家乡的这些树木,有的历经数百年,默默见证着沧桑岁月。——是啊,这个以山为家,又谦称自己是“山里客人”的民族,和青山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缘,他们爱山,尊重大山,绝不去破坏山的尊严。试问,谁不爱自己的家乡!
山冈顶上最高处错落三座房子,其中朝北的那座就是我祖父留下的“土墙厝”,那是我出生的地方。我的两个儿子也出生在这里。
老房子面朝东,站在房前三十多米的一小块田地上,视野开阔,可遥望远在天边的东湖,于海天共一色。
这可是一个在我童年中留下奇特记忆的场景。东湖,就是现在宁德市的新城区,和我的家之间,隔着山冈、海湾、村庄和田野,直线距离大约有一二十公里之遥。20世纪在60年代以前,它是宁德县城边上的一片海湾,面积有两万来亩。潮来时,万顷波涛;潮退时,是一望无际的海滩。童年时的我,远望着东湖上的粼粼波光和山冈云霭,感觉是那么的遥远,遥远的似乎在天边云间。60年代中期,东湖经过围垦和开发,成为一片青葱的田畴和众多的湖泊湿地。现在又成了宁德市的新城区,有着繁华的街道、林立的高楼和彻夜不息、流光溢彩的灯火。而这一切,又是童年时站在高高山冈上的我,如何能够想象得出呢!
当年,每当清晨最早的一缕阳光透过云层,照在小田地的岩石上时,我常常和同龄的伙伴们,一道站在那里,遥望着晨曦中的东湖。冬天,山村无比的寒冷,而最早到来的阳光给了我温暖,也带给我无限的憧憬。
童年,我走地头、进树林,摘茶叶、做童工,目睹家乡的变迁,感受山民的善良。我热爱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许多年过去了,老房子终究不堪岁月侵蚀,墙残垣断。我的妻子和一个个体养猪专业户的堂孙钟坛金,他们决定在老房子的根基上重新修建。
是啊,人,不能忘根!
每逢春节,我都要带着妻子、孩子,回老家看看。一来,教育子女不要忘本;二来,忆苦思甜,感受家乡难得的发展变化,为父老乡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记得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我回老家看望他,父亲拉着我的手,走到那块小园地上,指着园埂上的一块岩石说:“伢,你小的时候,经常站在这里,看东湖那边的阳光照在山冈上。伢,我们山哈人,祖祖辈辈就是以山为家。”
以后,我每每回家乡,还能清晰地认得那个位置。望着天边的东湖之景,父亲的话语仿佛又在耳边。
5
我的父亲叫钟林助,父亲5个兄妹中属他最小。在他的兄妹中,大哥被抓壮丁,无回归也无音信;二哥抱给别人做儿子,其他的都因病先后早逝而去。
那时候,家里很穷,没有田,要靠租人家的田种。每一天忙碌的结果就是图个有地瓜米吃,每天一家人能“挣”到二两地瓜米就算很不错了。好在父亲靠自己的勤奋和聪明,学会一手精湛的木匠打笄本领。本村子甚至是邻村,只要谁家建房子、办喜事做家具,都会来邀请他去做事。父亲受到村里人的尊敬,大家尊称他为“先生”、“师傅”。父亲还是畲家的“法师”,能给人家“做会瞑”。总之,众事都有他在。
在畲家,法师有两种:一种以道教的形式,祈求吉利或者是为死去的灵魂驱鬼;一种就是文的形式,请神、念经安祖,做阴德,使死去的灵魂进入阴间后,不受折磨。畲族以农为本,在祭祀日和时令节日里,常举行祈求神灵庇护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仪式。其中,农历正月的清醮道场是最隆重的祈求丰收的祭祀仪式。畲族巫师在从事祈福等神事活动时,需要运用各种道具乐器组合伴奏,主要有龙角、三音板、铃刀、法鼓以及锣、钹与木鱼等,使得伴奏旋律清新,节奏明快,粗犷古朴,富有韵味。在道场上演奏的音乐,有专门的曲牌和乐器,比较有代表性的音乐片断有:《净坛》、《九夷清醮》、《踩罡》。记得10岁那年,父亲决定要我跟随他身边,在一旁打镲、打鼓,学做“法师”。只是后来,我不愿意干,他也就放弃了这一念头。我的大哥钟神兴、二哥钟细兴后来倒是学到父亲的一些本事,特别是大哥钟神兴,既会做木工,也会做“法师”,传承了父亲的手艺。
在我的眼里,父亲一生嗜酒。三天没酒,他人困力乏。无论劳作之中,还是空闲之余,他最爱的就是喝酒,而且每日辛劳,夜少眠,更是添增了他的酒瘾。为此,家中只要有粮,他就酿酒。父亲的酒量实在大,是个“酒仙”,酿来的酒不够自己喝。拮据的家境无法让他尽兴。
6
我特别要写一下我的母亲,追忆她那短暂的一生,以了却我对她无限的哀思,并传之于子孙后代。
我的母亲是天底下最好的母亲,贤惠、勤劳,不仅要生儿育女,还要劳动种田,尽心竭力去维持一个贫苦的家。父亲有时在外,一家的重担就压在她一个人身上。父亲所有的劳作报酬,抽烟喝酒竟占去大半,留给家里的钱寥寥无几。所有的家庭琐事都压在母亲的肩上,也没见母亲有什么怨言。母亲心里一定很苦,但她总是沉默寡言。是啊,她能说什么呢,我们那时都小,无法分担生活对她的重压。
在我印象中,母亲没有一天有过笑容,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我那时很小,不知道在她忧郁的背后,埋藏着多少沉重的悲痛。
畲族的妇女,农忙时要和壮年汉子一样,田间地头体力活样样都干。母亲身材中等、清瘦,可想而知,她要付出比常人多几倍的辛苦啊!
农闲时,母亲总是有忙不完的家庭琐碎的事情,但家里还是穷。大哥回忆说,在我两三岁时,好几次,为了一家能吃上饭,母亲只得向邻居赊借地瓜米,半斤地瓜米作为一家人的“饭”,沾着盐汤吃一天。
母亲常告诫我,要用敬仰的态度去对待粮食。她虽然无法用“民以食为天”这种高雅的语言,但作为一个普通的畲民,一个普通的妇女,一个艰辛持家的母亲,用她的言传身教告诉了我:农民天生与粮食有着特殊的感情。这种敬仰粮食、杜绝浪费的意识渗入了我的脑海里。小时候在家里吃饭,倘若米粒掉到桌面上,马上要捡起来吃,吃完饭的碗里不许遗有一粒米。家里人一起吃一盘菜,每个人只许吃自己面前的一部分,不许越过自己的区域去夹别人的菜。所以,我后来读到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时候,倍感亲切。
半斤地瓜米作“饭”,这样的饮食根本谈不上营养。据大哥回忆说,母亲生我妹妹坐月子时,家里穷得实在没有吃的了,好在邻居送来咸菜充饥。
按照我们畲家的风俗,大凡畲族兄弟姐妹都有给分娩的姐妹送鸡和蛋的风俗习惯,有的畲家连一般亲友也送。俗称“做门头”或“门头鸡”,这和汉族的风俗相似。因此,作为一般产妇都能吃到十几只鸡。畲族在送“门头鸡”到产妇家时,要将鸡放在大门外,人先进去通报,主人点火出来,将鸡身“烘”过之后,才把它拿进家里。这,其实就是预防家禽流行病的一种方式。还有畲族妇女分娩都在婆家。临产时都通常坐在木盆上,待婴儿产出后,婆婆或接生婆才近前帮忙。她们认为“分娩不洁”,以避免污天秽地,冲撞“神明”。因此,在大门口贴上“添丁大吉”四个大字。在孕妇分娩期间,丈夫不能近前。男人进过产房,一个月内忌讳上宫庙和做佛事。婴儿断脐沐浴之后,男婴用生父旧衣包裹,女婴以生母旧衣包裹,产妇和婴儿在一个月内洗脸、洗澡、洗足都要用“石菖蒲”汤。畲族虽也存在重男轻女思想,但对于第一胎,不论男女同样重视。女人生头胎,婆家必须备上瓮酒、线面和鸡蛋,以及大米掺薯米送上,畲族称为“送月子”。
在当时,这种风俗是难以实现的。我母亲当时能有地瓜米吃,已是求之不得了。所以,母亲多病,身体虚弱,一直很瘦。
我后来还有个妹妹,夭折了,这大都与当时农村生活贫苦有关。连吃都成问题,婴儿夭折,自然成了意料之中的事。新中国成立前,畲族的人口生产就普遍处在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状态。
母亲的死太突然了,那时我才6岁。在懵懵懂懂的幼小心灵中,竟然留下对母亲悲惨的记忆。
记得,那是1951年的夏季的一天。那天清晨时分,天刚刚亮,母亲与往日一样起来,开始操劳一天的家务活。早早儿挑柴到十来里外的山下的云淡村。云淡,是一个海岛渔村,所需的柴火,大都靠山区村民供应。而南岗村畲民,则将卖柴所得的钱,购买咸鱼、盐巴、虾油等。自明清以来,落籍闽东山区的畲族村民,由于受山区田地局限,除种植粮食作物外,又以“种树还山”的方式,以林木薪炭及其他林业副产品,换取生活必需的日用品。此外,种茶、种菁、种苎麻和放牧牛羊、狩猎也是补充家庭经济来源的重要途径。
那天,母亲从云淡村返回到家时,正是上午10时。从南门岗走到云淡,要走一个小时,何况还要挑着柴。就在正午时,母亲的肚子突然剧烈地疼痛起来,疼痛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许——疼痛竟然折磨了她5个多小时!她无法下床,只能躺在床上,经受着生命中最难以承受的巨大的痛苦,同时寄希望于时间慢慢地过去,奇迹能发生……
但母亲终于无法抗拒命运对她的不公,在剧痛中接受了死神对她的最后折磨。终于,母亲,我血肉相连的母亲,因延误抢救离我们而去,年仅49岁。
没有医生!我们兄妹们又不在她的身边!
5个多小时的疼痛,就带走了她没有快乐可言的一生。也许,是上苍的意愿吧,母亲,终于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不舍地离开了与她血肉相连的儿女。
父亲当时赶到家,也没有想到肚子痛会致她于死命。后来,大哥神兴告诉我,母亲是因为中暑成痧。换成是现在,一个小小的中暑,怎么可能会夺走她的生命……
母亲一生没有开心的笑容,操劳过度而显憔悴瘦弱。她在世时,曾经跟大哥叨念过:“什么时候不用辛苦,你们能吃上白米饭,我也能好好地睡上一觉,歇息脚步。”
死神啊,如果命中已经注定她一生贫穷和劳苦,为什么又不让她平平安安地度过苦难人生的最后的一刻啊!
——母亲,您不用再操劳了,终于可以长眠。如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而您却无法安享幸福!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这样幻想着:如果母亲还在世,我一定要接她在我身边,好好地照顾她,让她老人家享受幸福的晚年;即便上苍只满足我一天的愿望,让我的母亲在我的身边!哪怕只有一天,也能平复我终生的遗憾!写到这里,我的心潮难以平静,尽管我已算是历经沧桑的人了,仍然还是泪眼迷离……
俗话说,吃遍天下盐好,走遍天下娘好。儿时,尽管家里穷,母亲却从未骂过我,更没有打过我。可惜我那时年幼,能记下的片断少之又少。我现在回想起母亲,总仿佛看到她忙忙碌碌的身影,一个贤惠、操劳的典型的畲族妇女。
我永远深深地怀念着她——我的母亲雷清芳。
7
母亲生了我们9个兄弟姐妹。男孩子中数我最小,除去夭折的妹妹。两个姐姐早早地送给人家做童养媳,一个弟弟卖给人家做儿子。还有一个妹妹在母亲过世后,也给人家做童养媳。
我的大哥钟神兴,1956年是南门岗乡民兵队长。二哥钟细兴,70年代担任过村里的大队长。
大哥、二哥俩六七岁时就开始务农了,还要帮忙母亲照看弟弟、妹妹。现在,70高龄的大哥每当抽一口烟时,就会回忆起往事,总是说:“没吃的,真的没有吃的东西。在那个年代,就连过年,还没有地瓜米吃,还是母亲去别人家借了三四斤地瓜米来。”说时,眼眶倾盈泪水,老泪纵横。
1951年,母亲去世后,大哥和二哥分了家,各自独立生活。父亲跟二哥,我跟随大哥。我大哥至今还对我说:“我不是不让你念书啊,实在是没有能力。当时你到了念书的年龄时,家里还是很穷啊,当年,大嫂还带着你到福安,乞讨地瓜米吃。真的没有办法送你去读书啊。”
是啊,南岗村历经许多灾难。那种记忆,至今无法抹去。
8
我非常爱读书。1950年,村里一所私塾就设在我家的大厅。大厅外有个石磨,私塾老先生教书时,5岁的我个子矮,就站在石磨上,跟随学生朗读:“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私塾老先生和里面的孩子“之乎者也”,摇头晃脑地念着《三字经》。我被浓郁的读书氛围深深地吸引住。每天只要老先生给孩子们上课,石磨上便准时出现我,久而久之,石磨成了我的课桌。有一次,姨姨带我去山上采茶时,我居然一句句念了起来。她惊讶地问我:“你会念书?”
我渴望上学,但童年,我不仅因家境贫苦不能上学,而且疾病缠身。
7岁那年,我的左耳太阳穴边上长了一个脓肿瘤。有时,脓瘤肿大得像一个鸡蛋,有时虽自行缩小,但总无法消除。更可怕的是,我的嘴巴,竟然莫名其妙地一圈圈烂了起来,疼痛伴随着高烧。
根本没有钱买药。没有药水涂,我只能用口水涂抹,靠这样的方法治疗,苦不堪言,有时疼痛的使我在睡梦中惊醒。醒来,我就偷偷地祷告:祈求上天不要折磨我,第二天早上就能好起来。
但令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有一次上山放牛,一路上,常常和我一块儿去的两个最好的伙伴,开始侧着身,有意离我一段距离,并且一路上保持沉默状态。
他们开始注意到我嘴上难闻的气味!
雨天时,深山雾蒙蒙,四处只能看出几十米远。山林中,静寂得只能听见雨水从树叶上滴下的声音。在湿漉漉混沌的天和地之间,仿佛只有我们三个年幼的孩子和几头不会讲话的牛。等到我们把牛赶到坑底时,两个伙伴不见了,他们早就躲到树林子里。不堪寂寞的我,大声呼喊他们。可是,回应我的却是从树林子里传出一阵阵“老虎”的吼叫声。
他们受不了那种怪味,假装老虎的叫声弄我害怕,不让我靠近。这举动虽无意伤害我,却使我幼小的心灵感受到人生的寂寞和孤独。我记得,我一动不动地站在旷野中很久很久。我咬紧牙,始终不停地给自己打气,告诉自己:不要被吓倒!要有勇气!
人生不可思议,这么小的事,在我的脑海里依然清晰可见。许多年后,儿时的伙伴见面,他们说起这件事情,大家莞尔一笑置之。
嘴巴的溃烂和耳朵边上的脓肿瘤,一直折磨我近两年时间,一直到我9岁。
有一天,父亲的一个好朋友,他是八都新楼村畲族的“土医”,来我们家看到我的嘴巴烂成这样,惊讶地说:“怎么会这样,让我看看。”然后,他点燃两炷细香,叫我低下头,用点燃的细香靠近我的脖子,大概是点灼脖子上的穴位。他一边点灼,一边说:“你是个勇敢的孩子,不怕哦,不怕。过些天就会好起来了。”后来说了些什么话,我忘了,只记得他做完后,摸了摸我的头。
土医生只在我家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下山去了。至今,在我的印象中,还清晰记得那位土医生:1.6米多高,40多岁,穿着一身粗布衣裳,不爱说话,眼睛里透出慈祥。
果真不久,我的脓肿瘤和溃烂的嘴,开始慢慢痊愈。我至今还能记得那位土医的声音,如果现在他还在世的话,我要好好感谢他。这种神奇的治疗方式,多半是畲族医疗的单方。自古畲族多聚居高山峻岭,恶劣的环境因此造就了畲家神奇的医药学。在畲家特殊的医药学中,有着独特的疫病观、疾病命名和疾病分类、治疗方法。畲医大多系祖传,单线传艺,且传男不传女,不收外姓徒,绝大多数亦农亦医。新中国成立后,除少数被吸收到卫生院外,大多依旧散处民间,做赤脚医生。
童年生活虽艰苦,但也有快乐的记忆。那就是在我七八岁时与村里的伙伴一块儿到八都镇云淡村“讨小海”的那段记忆。
“讨小海”,就是趁大海退潮时,到滩涂上采集海蛎子、鲜贝等海货。从南门岗走到云淡村的海边,大约走40多分钟。那是一个夏日的中午,正值海水退潮。一到海滩边上,伙伴们就像活泼乱跳的鱼,个个活灵活现的。海泥亲吻着我的小脚丫,软软的,如果一直站着不动,细细的滩泥会慢慢地将小脚丫“包围”住。
我先学着捡香螺。照大人说的只要把海滩上的石头翻个底,就会拾到藏在石头下的香螺。还有学着大人捉螃蟹。螃蟹的螯常常会夹手,所以大人告诉我们,捉拿它时,要用一只手按住它的背壳,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从它的螯后面伸过去,轻轻地摁住,就可以把它捉了起来。我照例学着大人教的技巧,果然奏效。被“缴获”的小螃蟹,嘴里吐着白沫,两只螯不停地挥舞,样子很可爱。
一直到晚霞夕照,我们便又学着大人背着竹篓的样子,高高兴兴地带着一天的收获回家。那是我第一次赶海,这段经历,犹如一串珍珠,散落在我的回忆中。
9
我7岁时还穿着母亲的旧衣服,脚穿木鞋。再加上我的脚长,村子的人都管我叫“长厘”,即大船的意思。“长厘”外号,倒是形象地描绘出我当年个头矮、脚丫长,宽大的旧衣服裹着身子,犹如小舟在大海颠簸滑行的模样。
一个孩子,我的内心里多么盼望能穿上新衣服,即便不是崭新的,也希望能穿上合身的衣服。这种强烈的念头,随后就消逝到九霄云外。因为,困难时期最要紧的还是吃饭!生存!
大哥和二哥后来分了家,对此,幼小的我当时一直无法理解,一家人为什么要分开住。于是,我问父亲,父亲总是一个调子回答我:“人到了一定时候,要独立,自食其力,不能总依靠父母。”
我当初无法理解其中的缘由,但我后来发现这几乎是畲族家庭的模式。在畲族这个民族中,三代同堂的现象很少。我后来悟出一个道理:畲族,这个以山为家的民族,自古就要求畲民要学会独居生存。分,才会拼,才会赢。
人生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要靠自己的勇气改变贫穷。这样的意念由此根植于我的脑海中,并坚信不移。这就是畲族不怕艰辛、勤劳致富的精神。
自古以来,穷人的孩儿早当家。我7岁时就要帮家里做事,8岁给别人家放牛,9岁放羊。贫困的童年,给了我苦涩的回忆,但现在想起来,正是有了那份磨难,我才有了日后的坚强。也正是那种苦难,使我早早成熟,学会自食其力。这也许是我们“山哈人”的先祖留给我的一份最为宝贵的财富吧。
10
10岁那年,也就是1955年,父亲把我送到水尾村姑姑钟阿眉家里,让我在水尾村上小学。
水尾村,处在半山岭,是去南岗村的必经之地。从南岗村往回走只需半个多小时。村子里,大约住着十来户人家。许多年来,每当我回家乡,走到半山岭,看着这个村庄,仿佛看到过去的时光:一群孩子,背着书包,相互在田埂上追赶着,朝学校走去。
离开家那天,父亲送我和姑姑到村口,对我说了四个字——“认真读书”。话语中俨然有许多寄托,我懵懵懂懂地点着头。只是幼小的我当年无法细细品味,更不知其中的厚望。
姑姑牵着我的手向水尾村走去,我回头看了看,父亲站在原地,向我挥了挥手,突然停住,转头就走。等我走到村口的弯道时,我仍然感觉到背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
父亲还站在那里。我远远地看着他的背影,我慢慢地往前走,父亲的背影慢慢地、慢慢地消失在小路转弯处……
水尾村小学,说是一所学校,其实是村里的一座小庙。教室就设在庙的厅堂中间,面积只有十多平方米,十多个孩子围坐在一起,倒也温馨。我家里没钱,一年一担谷子作为学费,课本不用交钱。
我的老师叫林英赋,家住福安县八斗村,祖籍七都人。在当时那么艰苦条件下,林英赋老师仍然坚守岗位。他很敬业,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村子里,无论是上课还是放学时,每天清早或是傍晚,都能看到他微笑着站在学校的门口,眉目中带着慈祥。上课时,他拿着一条细细的竹鞭,我们不敢乱讲话。但却很少看他打孩子,多半是把竹鞭当成教鞭。
记得,上学的第一天,林英赋老师把我叫到他的身边,微笑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呀?哪个村的?”我一板一眼地回答:“我叫钟—雷—兴,南门岗村的。”
他仔细听了我的名字之后,说:“今天是你第一天上学,我给你取个学名吧。”他在我的本子姓名空格上端端正正地写上“钟铭钰”。然后对我说:“今后要勤奋学习,长大成才。”我点了头,“勤奋学习”这四个字深深刻在脑海里。
“钟铭钰”三个字,居然都是金字旁。林英赋老师没有说明为什么给我取这个名字。《礼记》中说:“男子二十冠而字。”这是古代一种礼仪,意思是说,男子到了20岁时要举行成人礼,开始戴“冠”。而且,除幼时命名之外,另外取个“字”。或许,林英赋老师认为我第一次入学,意味着人生开始迈向学识旅途。这,只是我的猜测。我后来也一直没问他其中的原因。
到水尾村上学,第一次离开父亲。
姑姑家的房子二楼是木板铺的,人走在上面,发出“噔噔”的响声。我很害怕,一到晚上就“尾随”在姑姑后面,夜里吵着要跟姑姑睡。一周、两周。到后来,姑姑看我丝毫没有决定要独自“勇敢”起来,便生气了,在阁楼上搭了个铺,算是我睡觉的地方。
在姑姑家,我还有一个表嫂,叫雷伏莲。倒是表嫂性格随和,我一天到晚就跟着表嫂。一到晚上,表嫂也总带上我到她的几个女伴那里聊天。我自然“乐得”陪她,好落个夜里有人一起睡觉。表嫂经常聊到夜里十点多钟回家,有时候点着蜡烛,还接着聊,总是有聊不完的话题。
表嫂对我很好,于是我便“死皮赖脸”地跟她睡觉。因为我的脚长,早上,总有一双大鞋子搁在表嫂的门前。
于是,表哥就拿我和她开玩笑,故意对着表嫂的面说:“啊,怎么每天晚上都有大男人在你的房间里?”“我就是疼爱他,怎么样?”说出这种话,羞得表嫂自己的脸通红通红。
从他们话语中,我听得出来,表哥和表嫂是幸福的一对。表嫂是童养媳,但却是幸运的。后来她生了3个男孩、3个女孩。现她已70多岁了。
“因为家里穷,只能让你回来做工。”在水尾村才念了一学期,大哥告诉了我这个消息。虽然在水尾村才读了短短的一个学期,但我至今时常回忆起林英赋老师、姑姑、表嫂。
有人说,人开始怀旧,就是老的时候。是啊,一叶而知秋!
水尾村至今还保持原来的模样,房子、田埂、姑姑家的花狗……仿佛所有的一切都定格在岁月中。而岁月仿佛是挂在眼前的瀑布,让人望后,顿生旧情。
现在回南岗的水泥路,正好修在水尾村村口旁。每每回南岗,经过水尾,我都要站在路边看一看,感到十分亲切。每看一回,都勾起我的回忆来。至今那座小庙还在,已经还原它的原本功能了。
11
“钟雷兴”这个名字,其实是隔壁村的一个老人给我取的。
6岁那年,父亲看我体弱多病,按照畲家风俗,把我的名字“寄”到隔壁村一个老人的家里,作为他名义上的寄子。老人家很穷,独自一人生活。
在畲家,这种“寄”名的风俗,大凡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是把孩子的名字“寄”到富贵人家,期望用富贵庇护孩子;第二种是把孩子“寄”给乞丐或者比自己家还穷的人家里,意思是让孩子的命“贱”些,寄希望于将来在成长过程中能顺顺当当。在汉族,也有寄名的风俗,甚至有将自己的婴儿寄名给少数民族做孩子,求得孩子平安、顺当。
我至今不知道他给我取这个名字有什么来由。后来,父亲又把我寄名给我的一个堂叔。堂叔叫钟仙乐,他是个单身汉。按畲家风俗,他过世时要找一个亲戚过嗣。
在我们村庄,过世的人,名下是不能没有儿子的。
从水尾村回到家后,虽然休学了一年,但我没有熄灭对知识追求的热情,坚持进村里的夜校班学习,这样断断续续地读完三年级。
少年时的我,好学上进,对新鲜事物敏感。村里来了工作队,我努力去接近他们。我认为,他们传递给南岗村的就是一种新的信息,我必须主动接受他们的教育和帮助,从他们的身上能学到与南岗村完全不同的知识。
敢于接受新信息、新知识的萌芽一直埋藏在我的心里,这种生命力不随岁月而流逝。后来,我还在村里担任过夜校辅导员。
12
1958年7月19日,地委作出《关于动员全党全民为今年实现粮食亩产二千斤力争全省第一的决定》,号召全社会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中。紧接着,地委根据上级的部署,把发展闽东地方工业倾向钢铁生产,并立下豪言:年内生产10万吨生铁,1万吨钢,争取探出蕴藏1000万~1500万吨的生铁矿藏,采矿35万吨。
到了入冬时节,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的浪潮席卷到南岗村。
尽管南岗村位于偏僻山区,交通不便,但炼钢的“钢炉”终于还是屹立在大队村部的操场上。大队干部一声令下,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把自己的铁锅砸了,并且只要是含铁的器具,就连门把上的铁门扣都撬下来,集中一起冶炼。
我也参加了这种生产运动。有一次,还跟随村里人到七都镇的马坂村一带洗铁沙。那里是七都溪上游的一个河滩,离南岗村二三十里路远,走路得半天时间。洗铁沙,就是用特制的筛子及其他器具,从河沙中淘出含铁的颗粒。淘过无数的河沙,却只能得到一些“铁沙”,并且这些“铁沙”,也只是一些含铁量并不高的矿物。我常帮大人拉风箱,不能停,从中午一直拉到傍晚,又累又困,有时就蹲在钢炉旁边睡觉。参加劳动的人可以吃大食堂。
童年时,还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参加生产队劳动的日子。那是冬天时节,每天,生产队队长的哨子一响,大伙都准时起来。走到田埂上,才发现厚厚的霜盖在田埂面上,即便是锄头都无法撬开。我那年14岁。一个这样的年龄的孩子,瞌睡。但一切都不是如自己所愿,常常和大炼钢铁的一样,劳动一结束就趴在自己的床上。那时候,所有的苦,都不算什么,只要让我在柔软的被窝里美美地睡上一觉就够了。
1960年10月,困难时期,大办食堂还没有撤销。
我那时才15岁,被安排当大食堂的总务。食堂只负责给每家每户做饭,各家各户领回去吃。当时粮荒严重,人均只有二三两的地瓜米,一家人炖一大缸地瓜米汤,算是一天的粮食。没有参加劳动的还要扣除口粮。如果公社没有救济粮发放,食堂就得停餐。
由于缺粮,村子的人开始陆续发生浮肿病,于是等待大公社发放糠饼。等到糠饼到了村里,就按照得浮肿病的程度进行分发。现在的孩子对那个年代不可思议,良田明明近在咫尺,怎么会没有饭吃?可在当时,大人们说,就是离家门几步路的田地,也没有时间去收割地里的粮食,因为修公路、修水利、炼钢铁需要劳动力太多了。
什么叫做真正的饥荒,我都经历和体验过。
1960年大饥荒时期,也是国家最为困难时期。这种困难有两层意思:
一是基础设施破坏严重,自然灾害严重,物质短缺,恢复极为缓慢。1960年10月上旬,宁德县委派工作组进驻七都公社六都大队,调查了解生产和群众口粮情况,并在该地召开县、社、队干部座谈会,强调当前农村工作的当务之急是解决社员群众吃饭问题。鉴于六都大队断粮严重,急电省委办公厅派工作队带猪种、马铃薯种进驻六都帮助当地农民发展生产。随即,还指示大队干部一定要向群众交清家底,要向群众讲明自救政策,要向群众许诺今秋明春政府不向群众征粮。
二是台海局势仍然处在紧张状况,福建处在前线战略地位。在当时,可以说为了充饥,我什么都吃。地瓜叶、苦菜、黄花菜叶,甚至是山上的野果、芭蕉根茎。也怪,那时肠胃特别好,什么东西填进去都能消化得了。但有一次,却让我后怕。
那天,生产队集中到金垂村收割早稻,我没有早饭吃,就徒步下田。可一到田里,肚子就开始咕咕叫。于是,一边收割稻谷一边抓稻穗生谷就吃,由于饥饿吃得很多,第二天肚子胀疼得要命,让人难以忍受。现在想起来,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13
1960年,入冬时节。那时,我仅15岁。
我的姐夫到福安建设顶头水库,做义务工。我当时去工地顶替姐夫,算“顶工”。我虽个头矮小,但挑土、抬石头,毫不落后。按当时建设水库所给的“待遇”,每个参加劳动的人都可以有二两地瓜米的饭吃。就这样,我连续干了近20天。算是今生第一次“正式”自食其力。
在顶头水库干了近20天后,我回家帮姐姐看孩子,等待下一个机会。
1961年,过完农历正月,同村的钟仙庆在福安顶头水库半岭村黄坑自然村当了上门女婿,村上的小学正好缺一名教师。经仙庆介绍,我到黄坑村教书,当上小学民办老师。当时教一至三年级复式班,十多个学生。
过年后,我便徒步到黄坑自然村,在钟仙庆家里搭了铺,算是我第一次当教师的宿舍。我那时16岁,为了带好学生,教好书,吃尽了苦头。晚上,自己拿课本,对照生词生句,揣摩出最精确的意思,字典或是可参照的资料根本没有。然后,自己读课文内容,力求自己读得流畅。每天这样坚持,才不至于白天上课误人子弟。
其实更难的,还是生活的料理。
早上要早起,然后将午饭、早饭一起煮,因为等到上午轮流给不同年级的学生上完课,大多已是正午时分。因此常常是洗一棵白菜全部下锅,然后分一小碟作为早菜。好在学生和当地的群众对我都很好。村里的学生家长给我送米,但总不够吃,我还要回家拿米。
我在黄坑村当小学老师,每每都想起自己5岁那年站在私塾课堂外的石磨上的情景,我深深知道,知识对一个畲家的孩子意味着什么。所以,我虽然很少对学生家长发过什么誓言,内心中一直都没有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我晚上几乎是放弃所有的空闲休息,加紧备课。
由于过去的小学生根本谈不上学习基础,而且又是复式班,差生较为普遍,工作压力大。但我始终坚持不歧视差生的观念,尽力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一个学生。所以,我后来正式走上工作岗位,都时时告诫自己:第一,千万不要歧视弱者或年幼者,只要不断地学习,落后者终会进步,幼稚的人终有成熟的一天;第二,不要做一个只会说而不会实干的人。
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但好学、上进,做什么事都很认真、细致。不知不觉,在黄坑村度过了一个学期。我要感谢岁月艰辛带给我人生的思考。
随后,在党、团组织的关怀帮助下,16岁的我正式加入了共青团。我现在回想起少年时代,老师曾经叫我们唱歌,我最爱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好》两首歌曲。每一个从那个时代中走出来的人,听到这两首歌曲,心潮一定都会澎湃涌动。
14
回想童年、少年时光,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滋润着我的心田。我感觉到,我的民族畲族特殊文化潜移默化地浸透到我的童年、少年成长岁月中。这种浸透不知不觉,一直到我后来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才意识到这种民族文化的璀璨。
畲族是一个特别能吃苦又富有创造精神的民族。畲族所处的环境和生活习俗,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哺育了我的吃苦耐劳的品质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以及日后的善于独立思考的良好习惯。畲族文化,在我的人生经历中,起到良好的作用!
我小时候,听得最多的就是山歌。畲族的山歌以口传为主,内容与畲民的生产密不可分。
畲族是喜爱歌唱的民族,“盘歌”是畲族民间最普遍流行的文娱活动项目。
通常正月初五、初六起,畲民陆续开始出门走亲戚。走访的范围大多在整个地区内,常常是五六个结成一伙。男男女女的畲民走亲戚,就是为了相互盘歌。
“盘歌”,以男女对唱为主,还有独唱、齐唱和二重唱等多种形式。“对唱”往往男女分组,通常是男唱女答,或者女唱男和。唱时由一方中的一人先唱,唱完一段或几段,然后再由另一人接着唱,一唱一和。如畲歌《七月不来八月来》:
男唱:阿妹落郎寨里来,阿郎看见笑颜开;前门开了摘橘子,后门开了扭茄菜。
女答:从小未落郎寨来,口吃甜果笑颜开;吃了相问一句话:问你甜果怎样栽?
男唱:甜果好吃树难栽,铜钱好使矿难开;阿妹爱吃甜果子,以后多落郎寨来。
女答:阿哥讲话中妹爱,心里思郎离不开;回头再留一句话:七月不来八月来。
畲歌大体上可分为叙事歌、传说歌、小说歌、杂歌4种类型。歌的内容十分广泛,甚至涵盖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一百多篇民间盛传的故事。由于对歌需要,平时有人拿着歌曲手抄本,这些手抄本大多是祖传的,用的是音标。不识字的“音乐爱好者”围坐在一起,听“高手”教,用音乐的感觉默识下来。
畲歌云:“肚里歌饱人相敬,肚里无歌出门难。”对歌通常要整夜进行,持续三天三夜。特别是畲族妇女,没有三天三夜的对歌本领,不敢出门“做表姐”。对唱双方都找自己熟悉的、对方生僻的大段歌演唱,唱时不乱套、不丢句、不能含混不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畲歌最有代表的是口传史诗《高皇歌》。《高皇歌》也称为《盘瓠歌》,是畲家祖传歌。
畲歌的内容,还有来自生活中的场景,叫杂歌。如《四季歌》,就是讲述畲民四季耕种农作物的内容。还有在对唱中临时编纂的新歌,现场根据对手的歌曲内容,即时对答,这大多是相互打趣,目的是为了考对方。有时是嬉笑俏骂的情歌,最为生动。
盘歌二重唱,是民歌中罕有的唱法。二重唱,又称“双音”或“双条落”。是由男女两人以上轮唱同一段歌词,唱时,由一位歌手先唱2个字或4个字,再由另一位歌手接唱。用假声、真声均可。这种唱法深受群众喜爱。八都猴一带畲村,还有男女室内对歌的习俗,上半夜先对唱,互考对方歌才;若旗鼓相当,下半夜就对“双音”。盘歌中,还有独唱,大多数是歌者独自抒情,解闷。
对唱终有结果,如果一方答不上来,则算输。输者,大多不能留此夜宿,以表“羞愧”。若是男方,则连夜溜出村子,而女方则蹲守村口,拦路留宿。
毕竟“得饶人处,且饶人”。我在7岁时,在自己的村子看到过这样的场景,记忆犹新。
畲族歌言是畲族文化的精华,畲民对歌就是学习,就是传承文化的主要方式。畲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无自己的文字。畲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有两种方言。本民族内用畲语,与外界交往使用汉语,通用汉字。所以盘歌,其实担当起畲民情感交流的“桥梁”。畲民就是靠平时的对歌进行交流,同时也培养了不少畲族艺术人才。
畲族走亲戚时,如何认得对方也是少数民族呢?这里面就有一个奥秘——畲族祖传秘语,即用来考验外来的陌生人,来者除讲畲族语言外,还必须对答秘语,能应对者,便认定为真正的畲民,则以亲人相待。否则,将不予理睬。
因此,畲民出行时,都将对既定的独特秘语做必要的预习,以备路上突如其来的提问。较为通俗的常用的应对秘语有:
问:一桁毛竹打几来?(即“一枝毛竹劈几片?”)
若来者姓“蓝”,即答:“六来。”若“雷”“钟”两姓者,则答:“五来。”
问:什么字头?(即指姓氏?)
若来者姓“蓝”,则答:“钉角。”姓“雷”,则答:“盖耳。”姓“钟”,则答:“千字头。”
问:成为成人?
来者已经传师学师者,则答:“成人。”未学师者,则答:“未成人。”
问:毛竹开桠没有?
来者已有子女者,则答:“已开桠。”没有子女的,则答:“未开桠。”
问:门前有几个踏步?
来者应按家中有几代人应答。
有研究学者认为,畲族的秘语与民间的隐语、行话、切口、杂话、方语等不属于一个范畴,作为畲族一种回避常人所知而设定的行为规范,反映了畲民的文化心理。
新中国成立后,畲族的传统文艺活动才有了根基和发展。1956年12月,原宁德县举办首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1959年,在当时的福安专区举办第二届文艺调演,上演节目就多达69个。到1988年1月,宁德地区畲族歌舞团创办,从2000年到2004年共举办了五届闽东畲族歌会,畲族文艺演出趋于经常化、专业化。
到农历的八月,这时恰好是收获季节。农历八月十五,畲民又迎来一年一度的对歌好时光,结伴出门对歌。持续到农历九月,进入冬季,正是回来收割稻谷的时间,然后将田野做彻底清理,聚族摆宴,男女劳力一起饮酒庆丰收,俗称“理园埕”。
1945年正月初五,初春时节,我出生在宁德县(现在的蕉城区)八都镇南岗村的一个贫苦家庭。
南岗村,位于镇驻地东南4公里的山冈上,海拔366米,是一个典型的畲族少数民族自然村。新中国成立前,南岗村畲民和许多地方的畲民同胞一样,散处山区,搭寮而居,靠租种官山和地主山场过着“种树还山,种菁为活”、“受民田以耕”的粗放耕作生活。
新中国成立前,明朝至民国期间,宁德七都镇际头村,福安甘棠镇小岭村、北坑村、铜坑里村等畲族村,霞浦草岗村、青皎村等几个片区水稻的平均产量,亩产只有140多公斤。仅靠这样的亩产量,许多畲民连吃饭都成问题,更不用说大多数畲民的身份是佃农,既要与险恶的自然灾害和疾病作斗争,还得承受地主的盘剥、官府勒索。许多畲民始终挣扎在生存线上,如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南门岗畲族村发生瘟疫,全村83户在一个月内病死40多人,畲民生活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2
我的祖父叫钟日安,我出生时,祖父早已过世。祖父在我印象中的模样,完全来自于父亲的只言片语。父亲只告诉我,祖辈只留下一座简陋不堪的“土墙厝”。
虽然祖父的名字是那么陌生,但在他那个艰苦的年代能找到落脚地方,并且成家传承,已经值得骄傲了。
畲家的“土墙厝”,较为常见。“厝”在福建方言中,是屋子的意思,不同于用竹木和茅草搭起的“寮”。清代以前,畲民住房大多是以竹子为架搭成的“悬草寮”。这种茅寮称“千柱落脚”或者称为“千枝落地”,四面通风,呈“介”字形。架料多缚成框格型,寮面的茅草也是打成草匾之后盖上。这种茅寮不开窗户,没有烟囱,阳光不足,即便不是梅雨季节,泥土地面也十分潮湿。这样的住所,条件极为简陋,不能很好地抵御风侵雨淋,更不用说抵挡这里夏天常光临的台风暴雨了。因此,祖父建起的土墙厝,在我的家族中,实际上起到了一个“根”的作用。
我祖父留下的这座土房子,是清代以后畲家典型的“土墙厝”。土墙厝坐西朝东,土木结构,即四面以土筑墙,屋架直接安装在土墙上,中轴对称,屋顶呈“金”字形,整个空间分成四个部分,当地称为“四扇”。这种四扇的布局,便利于长子、次子等平均分得。父亲和我伯伯后来分家,各得一扇。房子周围,种有松、杉、毛竹等,浓荫蔽地。房子前有一个长长的石基,用大卵石砌成,长度约二十多米。因为大多数的畲民的房子盖在山坡上,这种石基起到了防止滑坡的作用。石基南端有一个长一米多的正方形蓄水池,用来蓄水,既可以供饮用,又可灌溉。直到现在,这个蓄水池还在发挥作用,但大多数仅用来灌溉农作物。现在的南岗村,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
常言道:“人生大事,起厝为先。”对选择宅地这样一大事,在畲族风俗里,也要请以阴阳八卦为职业的风水先生来看风水,以示慎重。其理论大致与汉族风水先生相同。畲族对家的重视或许是来自于先民的漂泊,毕竟有家才能挡风避雨。所以建房前,有一整套规矩:择吉日奠基,架木马,而后劈扇料,制作木构件;上梁之日,备好猪头、鸡、酒以及草鞋、木屐、雨伞,还有笔墨砚、镜子、头梳、红带子等物祭鲁班仙、请紫薇銮驾;到上梁时辰,鸣放鞭炮,木匠师傅将缠悬红布的正梁架好后,拿亲朋好友送来的稻米与红布压梁,并将事前备好的糍粑、粽子分馈众人,以示好彩头。同时,在当早设宴请工匠和亲戚朋友。
3
20世纪50年代,南岗还是一个乡。一听这地名,读者多少猜出这是位于山冈之上的村落。在畲民村落的命名中,有直接与风水有关的村名。如福安市有一个畲村的钟姓族人认为,所居处“高冈栖止频回顾,山头择地最为良”,故将村落命名为“山头庄”。我不清楚,历史上南岗的命名如何来的呢?估计是依山南而坐落,因此也叫“南门岗”村,顾名思义吧。
1957年,南门岗被设为乡。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畲族的专一管理。1957年7月8日,由宁德县人民委员会派出工作队到城关区后山乡进行建立民族乡的试点。其后,经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于9月8日正式设立后山、祭头、九仙、南山、南岗、北山、新楼、猴〓、雷东9个民族乡。民族事务由本民族人自管。1958年后,随着行政区域的撤区并乡,其后的少数民族事务又归并到新设的行政乡(村)兼管。直到1983年11月,县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后,经审定将畲族聚居的19个村庄划为畲族行政村。
南岗乡确切成立的时间为1957年10月10日。乡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11人,其中乡长、副乡长由畲族人担任;委员8人,畲族占6人。管辖水尾、金垂、云淡、韩丹4个村庄。韩丹村辖韩厝林、丹斗自然村,其中丹斗自然村和现在的南岗村一样,是纯畲族村。而云淡村则是一个海岛村,金垂村是沿海的一个大村,这两村以汉族为主,人口数量远远超过南岗村。到了1999年底,宁德市(现在的蕉城区)畲族人口相对聚居的行政村有33个,分布于城南、金涵、漳湾、七都、八都、九都、霍童和飞鸾、赤溪等乡镇。其中分布于八都镇和金涵乡最多,各有7个行政村。
4
南岗村,过去有近百户人家。近一二十年,多数人家往金垂村、红门里村以及城关等地搬迁。在1999年统计时,主村只有24户人家。近年来各级政府为改善山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实施“造福工程”,扶持边远山区的贫困群众往条件较好的地方搬迁集中,南岗村周围的外厝、水井两个自然村的几户人家也集中到主村来。
现在的南岗村,大部分的土墙厝都改成红砖墙的房子。有一两座房子主人的后代,大概是出于怀旧的心情,保留了原有的旧房,只是做了局部的修缮。
要说南岗村的特色,就是满山郁郁葱葱的树林,植被保护得很好。畲族,自古以来就有在村庄、住宅旁、路边、溪河边等处种树的习惯,大小的畲村均有面积不等的杂木林,畲民称之为“风水林”。自古,相当一部分的畲民开基乔迁伊始,对自身家居的营造方式是依山而建,住宅朴实无华,没有汉族的“泰山石敢当”字样的石碑等用来镇邪的添加物。但畲民谚语云:“造成风水画成龙”,畲家自有畲家的以树木培荫风水的传统。畲民认为,家居环境也许有先天不足,但人的身体和精神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家园,作为最有效的培荫风水的办法就是在房前房后植树,在村落周围造林,既可以阻挡山野之风,又可以添增家园之气。
有的畲民家族还将封山造林的规约写进家谱中,好让子子孙孙永远遵守。如清代光绪年间钟大《颍川钟氏族谱》记载,福安“仙岭洋乡长生公生道光丁末年(1847年),屋墙外有柳树一株,以为风水,子孙勿得斫伐”。植树补基,在汉族的堪舆家中也较推崇。只是畲家认为,房基植树的作用远不止一个补基功能,还有挡风聚气之功效,维护环境生态,使得村落在形态上更完美,景观上更显得丰富而有生机。
家乡的这些树木,有的历经数百年,默默见证着沧桑岁月。——是啊,这个以山为家,又谦称自己是“山里客人”的民族,和青山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缘,他们爱山,尊重大山,绝不去破坏山的尊严。试问,谁不爱自己的家乡!
山冈顶上最高处错落三座房子,其中朝北的那座就是我祖父留下的“土墙厝”,那是我出生的地方。我的两个儿子也出生在这里。
老房子面朝东,站在房前三十多米的一小块田地上,视野开阔,可遥望远在天边的东湖,于海天共一色。
这可是一个在我童年中留下奇特记忆的场景。东湖,就是现在宁德市的新城区,和我的家之间,隔着山冈、海湾、村庄和田野,直线距离大约有一二十公里之遥。20世纪在60年代以前,它是宁德县城边上的一片海湾,面积有两万来亩。潮来时,万顷波涛;潮退时,是一望无际的海滩。童年时的我,远望着东湖上的粼粼波光和山冈云霭,感觉是那么的遥远,遥远的似乎在天边云间。60年代中期,东湖经过围垦和开发,成为一片青葱的田畴和众多的湖泊湿地。现在又成了宁德市的新城区,有着繁华的街道、林立的高楼和彻夜不息、流光溢彩的灯火。而这一切,又是童年时站在高高山冈上的我,如何能够想象得出呢!
当年,每当清晨最早的一缕阳光透过云层,照在小田地的岩石上时,我常常和同龄的伙伴们,一道站在那里,遥望着晨曦中的东湖。冬天,山村无比的寒冷,而最早到来的阳光给了我温暖,也带给我无限的憧憬。
童年,我走地头、进树林,摘茶叶、做童工,目睹家乡的变迁,感受山民的善良。我热爱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许多年过去了,老房子终究不堪岁月侵蚀,墙残垣断。我的妻子和一个个体养猪专业户的堂孙钟坛金,他们决定在老房子的根基上重新修建。
是啊,人,不能忘根!
每逢春节,我都要带着妻子、孩子,回老家看看。一来,教育子女不要忘本;二来,忆苦思甜,感受家乡难得的发展变化,为父老乡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记得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我回老家看望他,父亲拉着我的手,走到那块小园地上,指着园埂上的一块岩石说:“伢,你小的时候,经常站在这里,看东湖那边的阳光照在山冈上。伢,我们山哈人,祖祖辈辈就是以山为家。”
以后,我每每回家乡,还能清晰地认得那个位置。望着天边的东湖之景,父亲的话语仿佛又在耳边。
5
我的父亲叫钟林助,父亲5个兄妹中属他最小。在他的兄妹中,大哥被抓壮丁,无回归也无音信;二哥抱给别人做儿子,其他的都因病先后早逝而去。
那时候,家里很穷,没有田,要靠租人家的田种。每一天忙碌的结果就是图个有地瓜米吃,每天一家人能“挣”到二两地瓜米就算很不错了。好在父亲靠自己的勤奋和聪明,学会一手精湛的木匠打笄本领。本村子甚至是邻村,只要谁家建房子、办喜事做家具,都会来邀请他去做事。父亲受到村里人的尊敬,大家尊称他为“先生”、“师傅”。父亲还是畲家的“法师”,能给人家“做会瞑”。总之,众事都有他在。
在畲家,法师有两种:一种以道教的形式,祈求吉利或者是为死去的灵魂驱鬼;一种就是文的形式,请神、念经安祖,做阴德,使死去的灵魂进入阴间后,不受折磨。畲族以农为本,在祭祀日和时令节日里,常举行祈求神灵庇护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仪式。其中,农历正月的清醮道场是最隆重的祈求丰收的祭祀仪式。畲族巫师在从事祈福等神事活动时,需要运用各种道具乐器组合伴奏,主要有龙角、三音板、铃刀、法鼓以及锣、钹与木鱼等,使得伴奏旋律清新,节奏明快,粗犷古朴,富有韵味。在道场上演奏的音乐,有专门的曲牌和乐器,比较有代表性的音乐片断有:《净坛》、《九夷清醮》、《踩罡》。记得10岁那年,父亲决定要我跟随他身边,在一旁打镲、打鼓,学做“法师”。只是后来,我不愿意干,他也就放弃了这一念头。我的大哥钟神兴、二哥钟细兴后来倒是学到父亲的一些本事,特别是大哥钟神兴,既会做木工,也会做“法师”,传承了父亲的手艺。
在我的眼里,父亲一生嗜酒。三天没酒,他人困力乏。无论劳作之中,还是空闲之余,他最爱的就是喝酒,而且每日辛劳,夜少眠,更是添增了他的酒瘾。为此,家中只要有粮,他就酿酒。父亲的酒量实在大,是个“酒仙”,酿来的酒不够自己喝。拮据的家境无法让他尽兴。
6
我特别要写一下我的母亲,追忆她那短暂的一生,以了却我对她无限的哀思,并传之于子孙后代。
我的母亲是天底下最好的母亲,贤惠、勤劳,不仅要生儿育女,还要劳动种田,尽心竭力去维持一个贫苦的家。父亲有时在外,一家的重担就压在她一个人身上。父亲所有的劳作报酬,抽烟喝酒竟占去大半,留给家里的钱寥寥无几。所有的家庭琐事都压在母亲的肩上,也没见母亲有什么怨言。母亲心里一定很苦,但她总是沉默寡言。是啊,她能说什么呢,我们那时都小,无法分担生活对她的重压。
在我印象中,母亲没有一天有过笑容,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我那时很小,不知道在她忧郁的背后,埋藏着多少沉重的悲痛。
畲族的妇女,农忙时要和壮年汉子一样,田间地头体力活样样都干。母亲身材中等、清瘦,可想而知,她要付出比常人多几倍的辛苦啊!
农闲时,母亲总是有忙不完的家庭琐碎的事情,但家里还是穷。大哥回忆说,在我两三岁时,好几次,为了一家能吃上饭,母亲只得向邻居赊借地瓜米,半斤地瓜米作为一家人的“饭”,沾着盐汤吃一天。
母亲常告诫我,要用敬仰的态度去对待粮食。她虽然无法用“民以食为天”这种高雅的语言,但作为一个普通的畲民,一个普通的妇女,一个艰辛持家的母亲,用她的言传身教告诉了我:农民天生与粮食有着特殊的感情。这种敬仰粮食、杜绝浪费的意识渗入了我的脑海里。小时候在家里吃饭,倘若米粒掉到桌面上,马上要捡起来吃,吃完饭的碗里不许遗有一粒米。家里人一起吃一盘菜,每个人只许吃自己面前的一部分,不许越过自己的区域去夹别人的菜。所以,我后来读到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时候,倍感亲切。
半斤地瓜米作“饭”,这样的饮食根本谈不上营养。据大哥回忆说,母亲生我妹妹坐月子时,家里穷得实在没有吃的了,好在邻居送来咸菜充饥。
按照我们畲家的风俗,大凡畲族兄弟姐妹都有给分娩的姐妹送鸡和蛋的风俗习惯,有的畲家连一般亲友也送。俗称“做门头”或“门头鸡”,这和汉族的风俗相似。因此,作为一般产妇都能吃到十几只鸡。畲族在送“门头鸡”到产妇家时,要将鸡放在大门外,人先进去通报,主人点火出来,将鸡身“烘”过之后,才把它拿进家里。这,其实就是预防家禽流行病的一种方式。还有畲族妇女分娩都在婆家。临产时都通常坐在木盆上,待婴儿产出后,婆婆或接生婆才近前帮忙。她们认为“分娩不洁”,以避免污天秽地,冲撞“神明”。因此,在大门口贴上“添丁大吉”四个大字。在孕妇分娩期间,丈夫不能近前。男人进过产房,一个月内忌讳上宫庙和做佛事。婴儿断脐沐浴之后,男婴用生父旧衣包裹,女婴以生母旧衣包裹,产妇和婴儿在一个月内洗脸、洗澡、洗足都要用“石菖蒲”汤。畲族虽也存在重男轻女思想,但对于第一胎,不论男女同样重视。女人生头胎,婆家必须备上瓮酒、线面和鸡蛋,以及大米掺薯米送上,畲族称为“送月子”。
在当时,这种风俗是难以实现的。我母亲当时能有地瓜米吃,已是求之不得了。所以,母亲多病,身体虚弱,一直很瘦。
我后来还有个妹妹,夭折了,这大都与当时农村生活贫苦有关。连吃都成问题,婴儿夭折,自然成了意料之中的事。新中国成立前,畲族的人口生产就普遍处在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状态。
母亲的死太突然了,那时我才6岁。在懵懵懂懂的幼小心灵中,竟然留下对母亲悲惨的记忆。
记得,那是1951年的夏季的一天。那天清晨时分,天刚刚亮,母亲与往日一样起来,开始操劳一天的家务活。早早儿挑柴到十来里外的山下的云淡村。云淡,是一个海岛渔村,所需的柴火,大都靠山区村民供应。而南岗村畲民,则将卖柴所得的钱,购买咸鱼、盐巴、虾油等。自明清以来,落籍闽东山区的畲族村民,由于受山区田地局限,除种植粮食作物外,又以“种树还山”的方式,以林木薪炭及其他林业副产品,换取生活必需的日用品。此外,种茶、种菁、种苎麻和放牧牛羊、狩猎也是补充家庭经济来源的重要途径。
那天,母亲从云淡村返回到家时,正是上午10时。从南门岗走到云淡,要走一个小时,何况还要挑着柴。就在正午时,母亲的肚子突然剧烈地疼痛起来,疼痛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许——疼痛竟然折磨了她5个多小时!她无法下床,只能躺在床上,经受着生命中最难以承受的巨大的痛苦,同时寄希望于时间慢慢地过去,奇迹能发生……
但母亲终于无法抗拒命运对她的不公,在剧痛中接受了死神对她的最后折磨。终于,母亲,我血肉相连的母亲,因延误抢救离我们而去,年仅49岁。
没有医生!我们兄妹们又不在她的身边!
5个多小时的疼痛,就带走了她没有快乐可言的一生。也许,是上苍的意愿吧,母亲,终于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不舍地离开了与她血肉相连的儿女。
父亲当时赶到家,也没有想到肚子痛会致她于死命。后来,大哥神兴告诉我,母亲是因为中暑成痧。换成是现在,一个小小的中暑,怎么可能会夺走她的生命……
母亲一生没有开心的笑容,操劳过度而显憔悴瘦弱。她在世时,曾经跟大哥叨念过:“什么时候不用辛苦,你们能吃上白米饭,我也能好好地睡上一觉,歇息脚步。”
死神啊,如果命中已经注定她一生贫穷和劳苦,为什么又不让她平平安安地度过苦难人生的最后的一刻啊!
——母亲,您不用再操劳了,终于可以长眠。如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而您却无法安享幸福!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这样幻想着:如果母亲还在世,我一定要接她在我身边,好好地照顾她,让她老人家享受幸福的晚年;即便上苍只满足我一天的愿望,让我的母亲在我的身边!哪怕只有一天,也能平复我终生的遗憾!写到这里,我的心潮难以平静,尽管我已算是历经沧桑的人了,仍然还是泪眼迷离……
俗话说,吃遍天下盐好,走遍天下娘好。儿时,尽管家里穷,母亲却从未骂过我,更没有打过我。可惜我那时年幼,能记下的片断少之又少。我现在回想起母亲,总仿佛看到她忙忙碌碌的身影,一个贤惠、操劳的典型的畲族妇女。
我永远深深地怀念着她——我的母亲雷清芳。
7
母亲生了我们9个兄弟姐妹。男孩子中数我最小,除去夭折的妹妹。两个姐姐早早地送给人家做童养媳,一个弟弟卖给人家做儿子。还有一个妹妹在母亲过世后,也给人家做童养媳。
我的大哥钟神兴,1956年是南门岗乡民兵队长。二哥钟细兴,70年代担任过村里的大队长。
大哥、二哥俩六七岁时就开始务农了,还要帮忙母亲照看弟弟、妹妹。现在,70高龄的大哥每当抽一口烟时,就会回忆起往事,总是说:“没吃的,真的没有吃的东西。在那个年代,就连过年,还没有地瓜米吃,还是母亲去别人家借了三四斤地瓜米来。”说时,眼眶倾盈泪水,老泪纵横。
1951年,母亲去世后,大哥和二哥分了家,各自独立生活。父亲跟二哥,我跟随大哥。我大哥至今还对我说:“我不是不让你念书啊,实在是没有能力。当时你到了念书的年龄时,家里还是很穷啊,当年,大嫂还带着你到福安,乞讨地瓜米吃。真的没有办法送你去读书啊。”
是啊,南岗村历经许多灾难。那种记忆,至今无法抹去。
8
我非常爱读书。1950年,村里一所私塾就设在我家的大厅。大厅外有个石磨,私塾老先生教书时,5岁的我个子矮,就站在石磨上,跟随学生朗读:“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私塾老先生和里面的孩子“之乎者也”,摇头晃脑地念着《三字经》。我被浓郁的读书氛围深深地吸引住。每天只要老先生给孩子们上课,石磨上便准时出现我,久而久之,石磨成了我的课桌。有一次,姨姨带我去山上采茶时,我居然一句句念了起来。她惊讶地问我:“你会念书?”
我渴望上学,但童年,我不仅因家境贫苦不能上学,而且疾病缠身。
7岁那年,我的左耳太阳穴边上长了一个脓肿瘤。有时,脓瘤肿大得像一个鸡蛋,有时虽自行缩小,但总无法消除。更可怕的是,我的嘴巴,竟然莫名其妙地一圈圈烂了起来,疼痛伴随着高烧。
根本没有钱买药。没有药水涂,我只能用口水涂抹,靠这样的方法治疗,苦不堪言,有时疼痛的使我在睡梦中惊醒。醒来,我就偷偷地祷告:祈求上天不要折磨我,第二天早上就能好起来。
但令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有一次上山放牛,一路上,常常和我一块儿去的两个最好的伙伴,开始侧着身,有意离我一段距离,并且一路上保持沉默状态。
他们开始注意到我嘴上难闻的气味!
雨天时,深山雾蒙蒙,四处只能看出几十米远。山林中,静寂得只能听见雨水从树叶上滴下的声音。在湿漉漉混沌的天和地之间,仿佛只有我们三个年幼的孩子和几头不会讲话的牛。等到我们把牛赶到坑底时,两个伙伴不见了,他们早就躲到树林子里。不堪寂寞的我,大声呼喊他们。可是,回应我的却是从树林子里传出一阵阵“老虎”的吼叫声。
他们受不了那种怪味,假装老虎的叫声弄我害怕,不让我靠近。这举动虽无意伤害我,却使我幼小的心灵感受到人生的寂寞和孤独。我记得,我一动不动地站在旷野中很久很久。我咬紧牙,始终不停地给自己打气,告诉自己:不要被吓倒!要有勇气!
人生不可思议,这么小的事,在我的脑海里依然清晰可见。许多年后,儿时的伙伴见面,他们说起这件事情,大家莞尔一笑置之。
嘴巴的溃烂和耳朵边上的脓肿瘤,一直折磨我近两年时间,一直到我9岁。
有一天,父亲的一个好朋友,他是八都新楼村畲族的“土医”,来我们家看到我的嘴巴烂成这样,惊讶地说:“怎么会这样,让我看看。”然后,他点燃两炷细香,叫我低下头,用点燃的细香靠近我的脖子,大概是点灼脖子上的穴位。他一边点灼,一边说:“你是个勇敢的孩子,不怕哦,不怕。过些天就会好起来了。”后来说了些什么话,我忘了,只记得他做完后,摸了摸我的头。
土医生只在我家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下山去了。至今,在我的印象中,还清晰记得那位土医生:1.6米多高,40多岁,穿着一身粗布衣裳,不爱说话,眼睛里透出慈祥。
果真不久,我的脓肿瘤和溃烂的嘴,开始慢慢痊愈。我至今还能记得那位土医的声音,如果现在他还在世的话,我要好好感谢他。这种神奇的治疗方式,多半是畲族医疗的单方。自古畲族多聚居高山峻岭,恶劣的环境因此造就了畲家神奇的医药学。在畲家特殊的医药学中,有着独特的疫病观、疾病命名和疾病分类、治疗方法。畲医大多系祖传,单线传艺,且传男不传女,不收外姓徒,绝大多数亦农亦医。新中国成立后,除少数被吸收到卫生院外,大多依旧散处民间,做赤脚医生。
童年生活虽艰苦,但也有快乐的记忆。那就是在我七八岁时与村里的伙伴一块儿到八都镇云淡村“讨小海”的那段记忆。
“讨小海”,就是趁大海退潮时,到滩涂上采集海蛎子、鲜贝等海货。从南门岗走到云淡村的海边,大约走40多分钟。那是一个夏日的中午,正值海水退潮。一到海滩边上,伙伴们就像活泼乱跳的鱼,个个活灵活现的。海泥亲吻着我的小脚丫,软软的,如果一直站着不动,细细的滩泥会慢慢地将小脚丫“包围”住。
我先学着捡香螺。照大人说的只要把海滩上的石头翻个底,就会拾到藏在石头下的香螺。还有学着大人捉螃蟹。螃蟹的螯常常会夹手,所以大人告诉我们,捉拿它时,要用一只手按住它的背壳,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从它的螯后面伸过去,轻轻地摁住,就可以把它捉了起来。我照例学着大人教的技巧,果然奏效。被“缴获”的小螃蟹,嘴里吐着白沫,两只螯不停地挥舞,样子很可爱。
一直到晚霞夕照,我们便又学着大人背着竹篓的样子,高高兴兴地带着一天的收获回家。那是我第一次赶海,这段经历,犹如一串珍珠,散落在我的回忆中。
9
我7岁时还穿着母亲的旧衣服,脚穿木鞋。再加上我的脚长,村子的人都管我叫“长厘”,即大船的意思。“长厘”外号,倒是形象地描绘出我当年个头矮、脚丫长,宽大的旧衣服裹着身子,犹如小舟在大海颠簸滑行的模样。
一个孩子,我的内心里多么盼望能穿上新衣服,即便不是崭新的,也希望能穿上合身的衣服。这种强烈的念头,随后就消逝到九霄云外。因为,困难时期最要紧的还是吃饭!生存!
大哥和二哥后来分了家,对此,幼小的我当时一直无法理解,一家人为什么要分开住。于是,我问父亲,父亲总是一个调子回答我:“人到了一定时候,要独立,自食其力,不能总依靠父母。”
我当初无法理解其中的缘由,但我后来发现这几乎是畲族家庭的模式。在畲族这个民族中,三代同堂的现象很少。我后来悟出一个道理:畲族,这个以山为家的民族,自古就要求畲民要学会独居生存。分,才会拼,才会赢。
人生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要靠自己的勇气改变贫穷。这样的意念由此根植于我的脑海中,并坚信不移。这就是畲族不怕艰辛、勤劳致富的精神。
自古以来,穷人的孩儿早当家。我7岁时就要帮家里做事,8岁给别人家放牛,9岁放羊。贫困的童年,给了我苦涩的回忆,但现在想起来,正是有了那份磨难,我才有了日后的坚强。也正是那种苦难,使我早早成熟,学会自食其力。这也许是我们“山哈人”的先祖留给我的一份最为宝贵的财富吧。
10
10岁那年,也就是1955年,父亲把我送到水尾村姑姑钟阿眉家里,让我在水尾村上小学。
水尾村,处在半山岭,是去南岗村的必经之地。从南岗村往回走只需半个多小时。村子里,大约住着十来户人家。许多年来,每当我回家乡,走到半山岭,看着这个村庄,仿佛看到过去的时光:一群孩子,背着书包,相互在田埂上追赶着,朝学校走去。
离开家那天,父亲送我和姑姑到村口,对我说了四个字——“认真读书”。话语中俨然有许多寄托,我懵懵懂懂地点着头。只是幼小的我当年无法细细品味,更不知其中的厚望。
姑姑牵着我的手向水尾村走去,我回头看了看,父亲站在原地,向我挥了挥手,突然停住,转头就走。等我走到村口的弯道时,我仍然感觉到背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
父亲还站在那里。我远远地看着他的背影,我慢慢地往前走,父亲的背影慢慢地、慢慢地消失在小路转弯处……
水尾村小学,说是一所学校,其实是村里的一座小庙。教室就设在庙的厅堂中间,面积只有十多平方米,十多个孩子围坐在一起,倒也温馨。我家里没钱,一年一担谷子作为学费,课本不用交钱。
我的老师叫林英赋,家住福安县八斗村,祖籍七都人。在当时那么艰苦条件下,林英赋老师仍然坚守岗位。他很敬业,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村子里,无论是上课还是放学时,每天清早或是傍晚,都能看到他微笑着站在学校的门口,眉目中带着慈祥。上课时,他拿着一条细细的竹鞭,我们不敢乱讲话。但却很少看他打孩子,多半是把竹鞭当成教鞭。
记得,上学的第一天,林英赋老师把我叫到他的身边,微笑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呀?哪个村的?”我一板一眼地回答:“我叫钟—雷—兴,南门岗村的。”
他仔细听了我的名字之后,说:“今天是你第一天上学,我给你取个学名吧。”他在我的本子姓名空格上端端正正地写上“钟铭钰”。然后对我说:“今后要勤奋学习,长大成才。”我点了头,“勤奋学习”这四个字深深刻在脑海里。
“钟铭钰”三个字,居然都是金字旁。林英赋老师没有说明为什么给我取这个名字。《礼记》中说:“男子二十冠而字。”这是古代一种礼仪,意思是说,男子到了20岁时要举行成人礼,开始戴“冠”。而且,除幼时命名之外,另外取个“字”。或许,林英赋老师认为我第一次入学,意味着人生开始迈向学识旅途。这,只是我的猜测。我后来也一直没问他其中的原因。
到水尾村上学,第一次离开父亲。
姑姑家的房子二楼是木板铺的,人走在上面,发出“噔噔”的响声。我很害怕,一到晚上就“尾随”在姑姑后面,夜里吵着要跟姑姑睡。一周、两周。到后来,姑姑看我丝毫没有决定要独自“勇敢”起来,便生气了,在阁楼上搭了个铺,算是我睡觉的地方。
在姑姑家,我还有一个表嫂,叫雷伏莲。倒是表嫂性格随和,我一天到晚就跟着表嫂。一到晚上,表嫂也总带上我到她的几个女伴那里聊天。我自然“乐得”陪她,好落个夜里有人一起睡觉。表嫂经常聊到夜里十点多钟回家,有时候点着蜡烛,还接着聊,总是有聊不完的话题。
表嫂对我很好,于是我便“死皮赖脸”地跟她睡觉。因为我的脚长,早上,总有一双大鞋子搁在表嫂的门前。
于是,表哥就拿我和她开玩笑,故意对着表嫂的面说:“啊,怎么每天晚上都有大男人在你的房间里?”“我就是疼爱他,怎么样?”说出这种话,羞得表嫂自己的脸通红通红。
从他们话语中,我听得出来,表哥和表嫂是幸福的一对。表嫂是童养媳,但却是幸运的。后来她生了3个男孩、3个女孩。现她已70多岁了。
“因为家里穷,只能让你回来做工。”在水尾村才念了一学期,大哥告诉了我这个消息。虽然在水尾村才读了短短的一个学期,但我至今时常回忆起林英赋老师、姑姑、表嫂。
有人说,人开始怀旧,就是老的时候。是啊,一叶而知秋!
水尾村至今还保持原来的模样,房子、田埂、姑姑家的花狗……仿佛所有的一切都定格在岁月中。而岁月仿佛是挂在眼前的瀑布,让人望后,顿生旧情。
现在回南岗的水泥路,正好修在水尾村村口旁。每每回南岗,经过水尾,我都要站在路边看一看,感到十分亲切。每看一回,都勾起我的回忆来。至今那座小庙还在,已经还原它的原本功能了。
11
“钟雷兴”这个名字,其实是隔壁村的一个老人给我取的。
6岁那年,父亲看我体弱多病,按照畲家风俗,把我的名字“寄”到隔壁村一个老人的家里,作为他名义上的寄子。老人家很穷,独自一人生活。
在畲家,这种“寄”名的风俗,大凡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是把孩子的名字“寄”到富贵人家,期望用富贵庇护孩子;第二种是把孩子“寄”给乞丐或者比自己家还穷的人家里,意思是让孩子的命“贱”些,寄希望于将来在成长过程中能顺顺当当。在汉族,也有寄名的风俗,甚至有将自己的婴儿寄名给少数民族做孩子,求得孩子平安、顺当。
我至今不知道他给我取这个名字有什么来由。后来,父亲又把我寄名给我的一个堂叔。堂叔叫钟仙乐,他是个单身汉。按畲家风俗,他过世时要找一个亲戚过嗣。
在我们村庄,过世的人,名下是不能没有儿子的。
从水尾村回到家后,虽然休学了一年,但我没有熄灭对知识追求的热情,坚持进村里的夜校班学习,这样断断续续地读完三年级。
少年时的我,好学上进,对新鲜事物敏感。村里来了工作队,我努力去接近他们。我认为,他们传递给南岗村的就是一种新的信息,我必须主动接受他们的教育和帮助,从他们的身上能学到与南岗村完全不同的知识。
敢于接受新信息、新知识的萌芽一直埋藏在我的心里,这种生命力不随岁月而流逝。后来,我还在村里担任过夜校辅导员。
12
1958年7月19日,地委作出《关于动员全党全民为今年实现粮食亩产二千斤力争全省第一的决定》,号召全社会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中。紧接着,地委根据上级的部署,把发展闽东地方工业倾向钢铁生产,并立下豪言:年内生产10万吨生铁,1万吨钢,争取探出蕴藏1000万~1500万吨的生铁矿藏,采矿35万吨。
到了入冬时节,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的浪潮席卷到南岗村。
尽管南岗村位于偏僻山区,交通不便,但炼钢的“钢炉”终于还是屹立在大队村部的操场上。大队干部一声令下,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把自己的铁锅砸了,并且只要是含铁的器具,就连门把上的铁门扣都撬下来,集中一起冶炼。
我也参加了这种生产运动。有一次,还跟随村里人到七都镇的马坂村一带洗铁沙。那里是七都溪上游的一个河滩,离南岗村二三十里路远,走路得半天时间。洗铁沙,就是用特制的筛子及其他器具,从河沙中淘出含铁的颗粒。淘过无数的河沙,却只能得到一些“铁沙”,并且这些“铁沙”,也只是一些含铁量并不高的矿物。我常帮大人拉风箱,不能停,从中午一直拉到傍晚,又累又困,有时就蹲在钢炉旁边睡觉。参加劳动的人可以吃大食堂。
童年时,还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参加生产队劳动的日子。那是冬天时节,每天,生产队队长的哨子一响,大伙都准时起来。走到田埂上,才发现厚厚的霜盖在田埂面上,即便是锄头都无法撬开。我那年14岁。一个这样的年龄的孩子,瞌睡。但一切都不是如自己所愿,常常和大炼钢铁的一样,劳动一结束就趴在自己的床上。那时候,所有的苦,都不算什么,只要让我在柔软的被窝里美美地睡上一觉就够了。
1960年10月,困难时期,大办食堂还没有撤销。
我那时才15岁,被安排当大食堂的总务。食堂只负责给每家每户做饭,各家各户领回去吃。当时粮荒严重,人均只有二三两的地瓜米,一家人炖一大缸地瓜米汤,算是一天的粮食。没有参加劳动的还要扣除口粮。如果公社没有救济粮发放,食堂就得停餐。
由于缺粮,村子的人开始陆续发生浮肿病,于是等待大公社发放糠饼。等到糠饼到了村里,就按照得浮肿病的程度进行分发。现在的孩子对那个年代不可思议,良田明明近在咫尺,怎么会没有饭吃?可在当时,大人们说,就是离家门几步路的田地,也没有时间去收割地里的粮食,因为修公路、修水利、炼钢铁需要劳动力太多了。
什么叫做真正的饥荒,我都经历和体验过。
1960年大饥荒时期,也是国家最为困难时期。这种困难有两层意思:
一是基础设施破坏严重,自然灾害严重,物质短缺,恢复极为缓慢。1960年10月上旬,宁德县委派工作组进驻七都公社六都大队,调查了解生产和群众口粮情况,并在该地召开县、社、队干部座谈会,强调当前农村工作的当务之急是解决社员群众吃饭问题。鉴于六都大队断粮严重,急电省委办公厅派工作队带猪种、马铃薯种进驻六都帮助当地农民发展生产。随即,还指示大队干部一定要向群众交清家底,要向群众讲明自救政策,要向群众许诺今秋明春政府不向群众征粮。
二是台海局势仍然处在紧张状况,福建处在前线战略地位。在当时,可以说为了充饥,我什么都吃。地瓜叶、苦菜、黄花菜叶,甚至是山上的野果、芭蕉根茎。也怪,那时肠胃特别好,什么东西填进去都能消化得了。但有一次,却让我后怕。
那天,生产队集中到金垂村收割早稻,我没有早饭吃,就徒步下田。可一到田里,肚子就开始咕咕叫。于是,一边收割稻谷一边抓稻穗生谷就吃,由于饥饿吃得很多,第二天肚子胀疼得要命,让人难以忍受。现在想起来,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13
1960年,入冬时节。那时,我仅15岁。
我的姐夫到福安建设顶头水库,做义务工。我当时去工地顶替姐夫,算“顶工”。我虽个头矮小,但挑土、抬石头,毫不落后。按当时建设水库所给的“待遇”,每个参加劳动的人都可以有二两地瓜米的饭吃。就这样,我连续干了近20天。算是今生第一次“正式”自食其力。
在顶头水库干了近20天后,我回家帮姐姐看孩子,等待下一个机会。
1961年,过完农历正月,同村的钟仙庆在福安顶头水库半岭村黄坑自然村当了上门女婿,村上的小学正好缺一名教师。经仙庆介绍,我到黄坑村教书,当上小学民办老师。当时教一至三年级复式班,十多个学生。
过年后,我便徒步到黄坑自然村,在钟仙庆家里搭了铺,算是我第一次当教师的宿舍。我那时16岁,为了带好学生,教好书,吃尽了苦头。晚上,自己拿课本,对照生词生句,揣摩出最精确的意思,字典或是可参照的资料根本没有。然后,自己读课文内容,力求自己读得流畅。每天这样坚持,才不至于白天上课误人子弟。
其实更难的,还是生活的料理。
早上要早起,然后将午饭、早饭一起煮,因为等到上午轮流给不同年级的学生上完课,大多已是正午时分。因此常常是洗一棵白菜全部下锅,然后分一小碟作为早菜。好在学生和当地的群众对我都很好。村里的学生家长给我送米,但总不够吃,我还要回家拿米。
我在黄坑村当小学老师,每每都想起自己5岁那年站在私塾课堂外的石磨上的情景,我深深知道,知识对一个畲家的孩子意味着什么。所以,我虽然很少对学生家长发过什么誓言,内心中一直都没有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我晚上几乎是放弃所有的空闲休息,加紧备课。
由于过去的小学生根本谈不上学习基础,而且又是复式班,差生较为普遍,工作压力大。但我始终坚持不歧视差生的观念,尽力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一个学生。所以,我后来正式走上工作岗位,都时时告诫自己:第一,千万不要歧视弱者或年幼者,只要不断地学习,落后者终会进步,幼稚的人终有成熟的一天;第二,不要做一个只会说而不会实干的人。
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但好学、上进,做什么事都很认真、细致。不知不觉,在黄坑村度过了一个学期。我要感谢岁月艰辛带给我人生的思考。
随后,在党、团组织的关怀帮助下,16岁的我正式加入了共青团。我现在回想起少年时代,老师曾经叫我们唱歌,我最爱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好》两首歌曲。每一个从那个时代中走出来的人,听到这两首歌曲,心潮一定都会澎湃涌动。
14
回想童年、少年时光,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滋润着我的心田。我感觉到,我的民族畲族特殊文化潜移默化地浸透到我的童年、少年成长岁月中。这种浸透不知不觉,一直到我后来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才意识到这种民族文化的璀璨。
畲族是一个特别能吃苦又富有创造精神的民族。畲族所处的环境和生活习俗,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哺育了我的吃苦耐劳的品质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以及日后的善于独立思考的良好习惯。畲族文化,在我的人生经历中,起到良好的作用!
我小时候,听得最多的就是山歌。畲族的山歌以口传为主,内容与畲民的生产密不可分。
畲族是喜爱歌唱的民族,“盘歌”是畲族民间最普遍流行的文娱活动项目。
通常正月初五、初六起,畲民陆续开始出门走亲戚。走访的范围大多在整个地区内,常常是五六个结成一伙。男男女女的畲民走亲戚,就是为了相互盘歌。
“盘歌”,以男女对唱为主,还有独唱、齐唱和二重唱等多种形式。“对唱”往往男女分组,通常是男唱女答,或者女唱男和。唱时由一方中的一人先唱,唱完一段或几段,然后再由另一人接着唱,一唱一和。如畲歌《七月不来八月来》:
男唱:阿妹落郎寨里来,阿郎看见笑颜开;前门开了摘橘子,后门开了扭茄菜。
女答:从小未落郎寨来,口吃甜果笑颜开;吃了相问一句话:问你甜果怎样栽?
男唱:甜果好吃树难栽,铜钱好使矿难开;阿妹爱吃甜果子,以后多落郎寨来。
女答:阿哥讲话中妹爱,心里思郎离不开;回头再留一句话:七月不来八月来。
畲歌大体上可分为叙事歌、传说歌、小说歌、杂歌4种类型。歌的内容十分广泛,甚至涵盖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一百多篇民间盛传的故事。由于对歌需要,平时有人拿着歌曲手抄本,这些手抄本大多是祖传的,用的是音标。不识字的“音乐爱好者”围坐在一起,听“高手”教,用音乐的感觉默识下来。
畲歌云:“肚里歌饱人相敬,肚里无歌出门难。”对歌通常要整夜进行,持续三天三夜。特别是畲族妇女,没有三天三夜的对歌本领,不敢出门“做表姐”。对唱双方都找自己熟悉的、对方生僻的大段歌演唱,唱时不乱套、不丢句、不能含混不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畲歌最有代表的是口传史诗《高皇歌》。《高皇歌》也称为《盘瓠歌》,是畲家祖传歌。
畲歌的内容,还有来自生活中的场景,叫杂歌。如《四季歌》,就是讲述畲民四季耕种农作物的内容。还有在对唱中临时编纂的新歌,现场根据对手的歌曲内容,即时对答,这大多是相互打趣,目的是为了考对方。有时是嬉笑俏骂的情歌,最为生动。
盘歌二重唱,是民歌中罕有的唱法。二重唱,又称“双音”或“双条落”。是由男女两人以上轮唱同一段歌词,唱时,由一位歌手先唱2个字或4个字,再由另一位歌手接唱。用假声、真声均可。这种唱法深受群众喜爱。八都猴一带畲村,还有男女室内对歌的习俗,上半夜先对唱,互考对方歌才;若旗鼓相当,下半夜就对“双音”。盘歌中,还有独唱,大多数是歌者独自抒情,解闷。
对唱终有结果,如果一方答不上来,则算输。输者,大多不能留此夜宿,以表“羞愧”。若是男方,则连夜溜出村子,而女方则蹲守村口,拦路留宿。
毕竟“得饶人处,且饶人”。我在7岁时,在自己的村子看到过这样的场景,记忆犹新。
畲族歌言是畲族文化的精华,畲民对歌就是学习,就是传承文化的主要方式。畲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无自己的文字。畲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有两种方言。本民族内用畲语,与外界交往使用汉语,通用汉字。所以盘歌,其实担当起畲民情感交流的“桥梁”。畲民就是靠平时的对歌进行交流,同时也培养了不少畲族艺术人才。
畲族走亲戚时,如何认得对方也是少数民族呢?这里面就有一个奥秘——畲族祖传秘语,即用来考验外来的陌生人,来者除讲畲族语言外,还必须对答秘语,能应对者,便认定为真正的畲民,则以亲人相待。否则,将不予理睬。
因此,畲民出行时,都将对既定的独特秘语做必要的预习,以备路上突如其来的提问。较为通俗的常用的应对秘语有:
问:一桁毛竹打几来?(即“一枝毛竹劈几片?”)
若来者姓“蓝”,即答:“六来。”若“雷”“钟”两姓者,则答:“五来。”
问:什么字头?(即指姓氏?)
若来者姓“蓝”,则答:“钉角。”姓“雷”,则答:“盖耳。”姓“钟”,则答:“千字头。”
问:成为成人?
来者已经传师学师者,则答:“成人。”未学师者,则答:“未成人。”
问:毛竹开桠没有?
来者已有子女者,则答:“已开桠。”没有子女的,则答:“未开桠。”
问:门前有几个踏步?
来者应按家中有几代人应答。
有研究学者认为,畲族的秘语与民间的隐语、行话、切口、杂话、方语等不属于一个范畴,作为畲族一种回避常人所知而设定的行为规范,反映了畲民的文化心理。
新中国成立后,畲族的传统文艺活动才有了根基和发展。1956年12月,原宁德县举办首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1959年,在当时的福安专区举办第二届文艺调演,上演节目就多达69个。到1988年1月,宁德地区畲族歌舞团创办,从2000年到2004年共举办了五届闽东畲族歌会,畲族文艺演出趋于经常化、专业化。
到农历的八月,这时恰好是收获季节。农历八月十五,畲民又迎来一年一度的对歌好时光,结伴出门对歌。持续到农历九月,进入冬季,正是回来收割稻谷的时间,然后将田野做彻底清理,聚族摆宴,男女劳力一起饮酒庆丰收,俗称“理园埕”。
相关地名
南岗村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