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代畲族服饰文化变迁
| 内容出处: | 《畲族服饰文化变迁及传承》 图书 |
| 唯一号: | 130920020230001770 |
| 颗粒名称: | 第一章 古代畲族服饰文化变迁 |
| 分类号: | TS941.742.883 |
| 页数: | 9 |
| 页码: | 3-11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畲族服饰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地发展变化着,这些变化向人们无声地吐露着畲族人在历史进程中所经受的政治动荡、社会变革、经济发展、文化浸染、种族流变和宗教洗礼。 |
| 关键词: | 畲族服饰 文化变迁 |
内容
畲族服饰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地发展变化着,这些变化向人们无声地吐露着畲族人在历史进程中所经受的政治动荡、社会变革、经济发展、文化浸染、种族流变和宗教洗礼。
1.1 古代畲族服饰文化变迁历程
1.1.1 畲族服饰原始时期
畲族族源至今众说纷纭,有苗、瑶、畲同源于“武陵蛮”一说;有越人后裔一说;有源自古代广东土著居民一说等,尚无定论[1]。据畲民族谱记载,畲族起源于广东潮州凤凰山。在汉晋以后、隋唐之际,畲族先民就已劳作、生息、繁衍在粤、闽、赣三省交界地区。
据《后汉书·南蛮传》载,畲族先民盘瓠蛮“织绩木皮,染以果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衣裳斑斓”。直至唐初,畲族所处的地区山脉纵横,“莽莽万重山、苍然一色,人迹罕到”,使得早期畲族与世隔绝,受外界干扰少,因此上述独特的民族服饰特征得到了延续和保持。如《云霄县志》记载唐代居住在漳州地区畲族先民的发式和服饰为“椎髻卉服”。《赤雅》载:“刘禹锡诗,时节祀盘瓠是也其乐五合,其旗五方,其衣五彩,是谓五参:”唐朝陈元光《请建州县表》载.唐朝前期福建漳州一带畲族先民“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2]。《畲族历史与文化》一书也载:“唐宋时,畲族妇女流行‘椎髻卉服’,即头饰是高髻,衣服着花边”[2]。
可见汉至唐初畲族服饰较好地保持了原始风貌,其主要特征为:
(1)色彩:鲜艳的五色。
(2) 款式:衣摆或裙摆前短后长,部分衣服衣襟为“左衽”,呈现与中原相异的服饰特征。
(3) 发型:将头发编束成椎形的高髻。
1.1.2 畲族服饰多源融合时期
宋元之际,在反抗封建苛政特别是榷盐弊政的共同斗争中,畲族与周边其他各民族人民在合中通过交流,加强了融合,促进了畲族服饰文化的多源融合。
闽粤赣边区的上著居民属百越系统。直至汉初,这一地区仍主要居住着不同支系的越人即百越族群。正如《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断发”、“文身”当为百越服饰习俗代表,文献记载也颇多。《淮南子·齐俗训》:“越王勾践,剪发文身”。《战国策·越策》云:“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史记·赵世家》:“越之先世封于会稽,断发文身,披草莽而邑焉”。《逸周书·王会》曰:“越泯(瓯),剪发文身”。其他文献如《墨子·公孟》、《庄子·逍遥游》等也均有记载。而据《元史·完者都传》载:“黄华聚党三万人,扰建宁,号头陀军”。“头陀”即“断发文身”。“头陀军”也是“畲军”的代名词。南宋中叶宁化的畲军领袖晏彪也曾号“晏头陀”[3]。这说明宋元时期畲族起义军在与闽越土著的交流合作中,吸收了其服饰元素;或部分闽越土著直
接汇入畲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并随之引入了相应的服饰元素。
总结元时期畲族服饰的主要特征为:
(1)款式:吸收了文身这种百越民族服饰特征。
(2)头饰:吸收了断发这种百越民族头饰特征。
1.13 畲族服饰流徙从简时期
元朝统治者对抗元畲军进行了残酷镇压和分化瓦解,“至元十六年(1279年)五月辛亥,诏谕漳、泉、汀、邵武等处暨八十四畲官吏军民,若能举众来降,官吏例加迁赏,军民按堵者如故”[4]。这直接造成了畲族的大迁徙。从元后期至明万历年间,畲民开始大规模从闽西南沿闽南经闽东向浙南流徙明万历进士谢肇淛游福建太姥山过湖坪时,曾目睹“畲人纵火焚山,西风急甚,竹木迸爆如霹雳,……回望十里为灰矣”,并写下“畲人烧草过春分”的诗句。顾炎武亦云:畲民“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这些都是对明朝畲族游耕生活的真实记录。
据史料记载,明代畲民的风貌普遍为高髻赤足,较之先民显得颇为简朴,这与他们的流徙生活不无关系。如谢肇淛《五杂俎》载,福建畲族的服饰“吾闽山中有一种畲人……不巾不履。”明朝万历《永春县志》卷三《风俗》也载,畲族先民“通无鞋履”。《天下郡国利病书》载,广东博罗县畲族,“椎髻跣足。”《潮阳县志》载明代畲族“男女皆椎髻箕倨,跣足而行”《永乐大典·潮州府风俗》载,福建潮州畲族“妇女往来城市者,皆好高髻,与中州异,或以为椎髻之遗风”。
畲民自明代开始在山上搭棚种青靛,熊人霖著《南荣集》记载崇祯年间闽西南“汀之菁民,刀耕火耨,艺兰为生,编至各邑结寮而居”(编者按:“兰”同“蓝”);《兴化县志》也载闽中莆仙畲民“彼汀漳流徙,插菁为活”。历史上,有称畲族先民为“菁寮”、“菁客”,是因畲族先民所到之地,遍种菁草。据明代黄仲昭《人间通志》卷四一载,“菁客”所产菁靛品质极佳,其染色“为天下最”从这一时期起畲族服饰色彩即开始以青色为尊。
明代,赣闽粤交界区域已得到较为深入的开发,人稠地狭的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明中叶在政治腐败日益加深的背景下,赣南的土著客家矛盾与畲汉贫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交织在一起,造成连绵的暴动和起义。明政府剿抚并用,特别是王守仁巡抚南赣平乱时所推行的礼乐教化之心学主张,缓和了民族和阶级矛盾,促进了畲民的稳定向化[5]。部分畲民接受招抚加入官籍,他们的服饰也渐渐与汉族趋同。顾炎武即于《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提到“三坑招抚入籍,瑶僮亦习中国衣冠言语,久之当渐改其初服云”。
总结元末至明中后期这一时期畲族服饰的主要特征为:
(1)色彩:开始以蓝靛所染青色为主要服色。
(2)款式:与当地汉族趋同。
(3)头饰:高髻、不戴头巾。
(4)足饰:赤足。
1.1.4 畲族服饰涵化成型时期
清代,畲族逐渐结束了迁徙的生活,主要在福建东北部、浙江南部定居下来:在与汉族人民“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下,畲族服饰一方面形成了自身的民族特色,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汉族的影响。
畲族先民与以客家先民为代表的汉族人民在粤、闽、赣的交流渊源深厚早在晋代,永嘉之乱促使大批中原汉人举族南迁闽西、赣南、粤东[6]。自唐末至宋,客家人因黄巢起义战乱所迫,从河南西南部、江西中部和北部、安徽南部,迁至福建西部的汀州、宁化、上杭、永定,还有广东的循州、惠州和韶州、更近者迁至江西中部和南部。宋末到明初,因蒙元南侵,客家人自闽西、赣南迁至广东东部和北部。这几次迁徙的地点正好是闽、浙、赣的交界处[7]。他们与畲族先民产生接触、交往和斗争,并引起了畲族社会生活和文化状态的改变。
明清以来,各地畲族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汉化的道路,如:永春县畲族在服饰、饮食、礼俗等文化上“皆与齐民无别”,长汀县畲客“男子衣帽发辫如乡人”等[8]。
据《平和县志》的记载“瑶人瑶种椎髻跣足,以盘、蓝、雷为姓虞衡志云:‘本盘瓠之后,俗呼畲客。自结婚姻,不与外人通也。……明初设抚瑶土官使绥靖之,略赋山税,羁縻而已今则太平既久,声教日讫,和邑诸山,木拨道通,猺獞安在哉,盖传流渐远,言语相通,饮食、衣服、起居、往来多与人同,瑶獞化为齐民,亦相与忘其所自来矣”[9]。从上文的记载可知:明初对畲民采取了绥靖政策,后经过畲汉长期的交流共处,到清初康熙年间,畲民已被慢慢地同化,言语相通,饮食、衣服、起居、往来多与当弛汉人相同。
甚至部分畲民一改往日畲汉不能通婚的习俗,主动与汉人通婚,渐渐融入汉族据清道光十二年《建阳县志》记载:“嘉乐一带畲民,半染华风,欲与汉人为婚,则先为其幼女缠足,稍长,令学针黹坐闺中,不与习农事,奁资亦略如华人,居室仍在辟地,然规模亦稍轩敞矣妻或无子也娶妾,亦购华人田产,亦时作雀角争,亦读书识字,习举子业”[2]。
乾隆时期《皇清职贡图》中所绘罗源、古田两地畲族男女服装款式皆大襟右衽(图1-1、图1-2),同于当地淑民[10]。
可见、无论是在历史上畲族聚居区的赣、闽、粤边地,还是闽北、闽东、浙南等畲族大迁徙后的新居地,畲族都在不同程度上汉化了。
如表1-1所示[11],在这一时期除广东畲族服饰相对显得比较简朴外,福建、浙江、江西的畲族服饰基本类同。比较突出的服饰特征可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色尚青蓝:服饰色彩以青色、蓝色为主,浙江地区多“斑兰”花布。
(2)款式精短:畲服款式普遍为短衣、短裙,大部分裙长不及膝盖,清末也有改为着裤的情况。
(3)装饰颇盛:较之前朝的“不巾不履”,清代畲族男女在头饰、足饰、装饰品等各方面都更显丰富。
(4)男女有别:男子戴竹笠穿短衫,一般赤脚,耕作时穿草鞋:女子一般先梳高髻,以蓝花布包头,再戴竹制头冠,并装饰以彩色石珠。
(5)汉化加深:在畲汉交流日益深广的情况下,女子赤脚的习俗在清末逐渐转变,在正式场合开始穿与汉秀花鞋类似的布鞋,平时则穿草鞋或木屐。
纵观畲族服饰文化逾千年的变迁,能看到闽越土著百越族群的衣饰身影,也能发现以客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族:化对其的渗透影响。畲族服饰文化的发展演变一直是在与周边各民族的融合中进行的。可以说,通过畲族服饰的发展历史,可以窥见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居于闽、粤、赣的各个民族在文化上的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互相融会的历程,可以窥见中华民族文明发展演变历史之一斑。
1.2 文化变迁视野下的古代畲族服饰演变动因
文化变迁是指文化内容的增加或减少及其所引起的文化系统结构、模式、风格的变化[12]。文化的形成和变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气候、地理等诸多要素都能带来文化的差异。文化变迁研究是人类学、民族学关于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自19世纪下半叶起,文化如何变化及民族文化的未来走向成为人类学家会学家潜心研究的课题[13]。目前民族文化变迁研究在我国方兴正艾,它对于探讨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探讨儒家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分析民族文化融合的意义、途径、过程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1.2.1 占代畲族服饰演变因素
关于文化变迁的动因,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看法,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生物因素说、地理环境说、经济基础说、工业发展说、文化传播说和心理因素说[13]。这些学说所提及的因素也同样影响着畲族服饰文化的变迁。值得强调的是,虽然在畲族发展史乃至世界各民族发展史上,文化的传播、人的心理因素、生物性、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地理环境等都曾引起过颠覆性的民族服饰文化变迁,但是不能将以上的某个单一因素确定为民族服饰文化变迁的根本原因,也不能确定为历史上的某一次民族服饰演变的唯一原因。社会是发展变化的,各社会因素间也有着纷繁复杂的联系,文化的每一次进步都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之下,文化变迁可能由于以上任何因素的作用而发改变。因此,民族服饰文化的变迁往往是多种因素同时作用的结果。
1.21.1 生物因素——族源融合
文化变迁动因的生物因素说认为:包括文化在内的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其变迁、进化是一个生物有机过程[14]。其中的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化变迁理论将文化进化或变迁归结为生态环境中群落基因库的变异和基因为群的分布[14]。
闽、粤、赣边地历史上存在着重叠的三个基因群,最早为土著百越族群,然后为源于五溪地区的畲瑶族群,最后为来自中原代表汉族文化的客家族群。这三种族群文化相交,必然产生互动互融关系。随着畲族逐渐迁出与世隔绝的祖居地,他们与古越蛮族、以客家人为代表的汉族的交流日益深广,关系日益紧密。其中一部分通过通婚、集结起义等方式实现了身份的迭合与转化,在不断的种族融合进程中,畲族服饰文化也相应地产生了涵化。唐宋时,畲族妇女流行“椎髻卉服”,即头饰是高髻,衣服着花边[2]。显示出畲瑶先民盘瓠蛮的典型服饰风貌。元代,畲族起义军又号“头陀军”,“头陀”即“断发文身”,是百越民族的典服饰特色[15]。这说明宋元时期畲族起义军在与闽越土著的交流合作中,吸收了其服饰元素;或部分闽越土著直接汇入畲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并随之引入了相应的服饰元素。
清代《皇清职贡图》载:福建畲民“其习俗诚朴,与土著无异”,表明当时畲汉关系密切、表征趋同。据清道光《建阳县志》载,一部分畲民主动与汉人通婚,模仿汉族服饰文化习俗:“嘉乐一带畲民,半染华风,欲与汉人为婚,则先为其幼女缠足,稍长,令学针黹坐闺中,不与习农事,奁资亦略如华人。居室仍在僻地,然规模亦稍轩敞矣。妻或无子亦娶妾,亦购华人田产,亦时作雀角争,亦读书识字,习举子业”,畲汉界限十分模糊。时至今日,福建客家和畲民仍同梳高发髻,戴凉笠,着右衽花边衣,尚青、蓝色[16]。
事实上,很多学者认为畲族本来就是多族源民族共同体,族源“包括五溪地区迁移至此的武陵蛮、长沙蛮后裔、当地土生土长的百越种族和山都、木客等原始居民,也包括自中原、江淮迁来的汉族移民即客家先民和福佬先民”[3]。族源多元性这一文化变迁的生物因素正是畲族服饰文化变迁的初始动力。
1.2.1.2 地理因素——迁徙
自然环境不仅决定着文化的性质,也决定着文化的形式与内容地理环境改变了,社会文化也随之变迁。从元后期至明万历年间,畲族从祖居的赣、闽、粵边地向闽北、闽东、浙南、赣东等多处新居地大迁徙,导致了畲族服饰原料的地域性改变和分化,从而影响畲族服饰的演变。比如,浙江丽水景宁的畲族因为主要生活在山区,当地盛产芝麻,加之气候温暖,温差较小,故“皆衣麻”;而福建古田的畲族,主要聚居在平坝,以种植棉花为主,故其制作服装选用的衣料以棉布为主,“妇以蓝布裹发……短衣布带”[17]。
各个迁入地的不同地缘文化也对畲族服饰的演变造成影响如迁徙到温州地区的畲族服饰刺绣深受瓯绣的影响,而闽东畲族服饰刺绣题材很多取自于福建木偶戏及闽剧。
迁徙过程中要求服饰简便实用,而不强调其审美功能,这也是导致元末明初畲族大迁徙时期服饰装饰性削弱的原因之一。
1.2.1.3 经济因素——经济生活方式的转变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经济基础决定着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等诸多文化要素,经济因素在文化变迁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畲族主要散居于我国东南山区的山腰地带,从气候上看,紧靠北回归线北面,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在这样的自然环境里,畲族明清以前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是“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的游耕和狩猎并举的经济生活方式[18]。因生产活动场所主要是未开荒的深山密林,多荆棘枝挂,所以服饰品尽量精简可见当时畲族服饰“椎髻跣足”、“不巾不履”的特征是与游耕和狩猎并举的经济生活方式相适应的。
明清以后,畲民扩散到闽中、闽东、闽北、浙南、赣东等地,结束了辗转迁徙的生活,逐渐发展起以梯田耕作和定耕旱地杂粮为核心的生计模式[18]。由于生产活动的主要场所由林区转移到田地,故具遮阳功能的“巾”、“冠”、“笠”等头饰和具采集功能的“围裙”逐渐在畲族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位位置。同时,随着农耕生产的不断发展,农副产品日渐丰富,手工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畲族人民能够创作出“布斑斑”、“珠垒垒”的精美的头饰艺术品,必然得益于当时经济的发展和手工制造技艺的进步。
1.2.1.4 工艺发展因素——染织技术发展
自然科学知识的增长推动了人类社会文化史的发展与进化新技术一旦出现,它自身的生命和力量就构成了文化进化的源泉。纺织服装技术的发展引导了服饰文化的演进,对畲族服饰演变影响比较深远的是以制菁为代表的畲族染色技术的发展。
畲族有谚语说:“吃咸腌,穿青蓝”福建霞浦县新娘结婚“头蒙兰底白点的盖头,腰系黑色素面的结婚长裙,扎兰色腰带”[2]。足见畲民对黑色、蓝色的喜爱。青、黑色之所以为畲民所接受,是由畲族人民的染色技术决定的“青出于蓝”,青在古代指黑色,一般由天然染料青靛中提取。青靛也名蓝靛,古称“菁”。用于染色时,时久色重显黑,时微色淡显蓝:明万历年间,由于织机的改进,闽、浙纺织业发展很快,以致种芒和种菁的利润几倍于粮食在种菁热的带动下,畲族拓荒者所到之地,遍种菁草,故历史亦有称畲族为“菁客”到崇祯年间闽西南“汀之菁民,刀耕火耨,艺兰为生,编至各邑结寮而居”;闽中莆仙畲民“彼汀漳流徙,插菁为活”。“菁客”所产菁靛品质极佳,其染色曾被盛誉“为天下最”[19]。畲族制菁技术的发展直接导致了明清之际其服饰色彩由“五彩”、“卉服”向“皆服青色”的转变。
1.2.1.5 文化传播因素——主流文化侵染
威廉·里弗斯在《美拉尼西亚社会史》中曾说道:“各族的联系及其文化的融合,是发动各种导致人类进力量的主要推动力。”文化传播因素即是指外来文化传播对某文化变迁的影响和作用这一因素。反映在古代畲族服饰上,中原主流文化对畲族文化的入侵和浸染主要来自于历代统治者的政治压迫和招抚教化。
自唐代“平蛮开漳”以来,被称为“蛮”的畲族一直遭受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分化瓦解直至明末每个朝代都有朝廷派兵平畲的记载:宋代,朝廷镇压了“壬戌腊”漳州畲民起义;元代,镇压和分解抗元畲军;明代,镇压江西赣州府畲民起义,增设“营哨守把”[2]。这些残酷清剿和封建强化统治直接导致了畲族的大规模迁徙。可以想见,在长逾千年的避难历程中,畲民为了躲避杀戮,不得不隐藏自身的身份,将作为“妖氛之党”标志的“椎髻卉服”进行改易。直至明末,畲族普遍“椎髻跣足”、“不巾不履”,服饰越来越趋近简朴无华。
从宋代开始,封建统治者就对畲族采取剿抚并举的政策。其中,明代王守仁的教化心学主张收效尤其明显。如前文所引《平和县志》[9]记载,明初到清初的三百年间,平和县畲民已被当地汉人慢慢地同化,其至“化为齐民”、“忘其所自来矣”。包括服饰文化在内的“饮食、衣服、起居、往来”各方面社会生活也被汉化,服饰特征逐渐与当地汉人相同。而这一服饰文化的转变正是“抚瑶”、“绥靖”、“羁縻”之后畲族逐渐接受汉文化的结果。
清末,畲族曾主动顺应政府服饰改易的号召。福州《华美报》己亥(清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刊登了福建按察使司的盐法道曾发表的《示谕》:“有一种山民,纳粮考试,与百姓无异,惟装束不同,群呼为畲,山民不服,特起争端”,因此,“劝改装束与众一律,便可免此称谓”,而结果是畲民“无不踊跃乐从”[2]。这充分体现了当时位于主流的汉文化对于畲族文化强大的感召力量。
1.21.6 心理因素——模仿心理
19世纪末法国塔尔德(G.Tarde)曾提出,模仿是人类的主要心理,也是文化发展、变迁的主要动力。特别是当模仿受到阻碍、怀疑或反对等刺激的时候,人类会运用新的方法和手段进行模仿而达到目的,这是是一个循环往复、无止境的社会文化过程,也是其变迁的动因。[12]
畲族是一个杂散居的少数民族,与作为中国主体民族文化的汉族传统文化相对而言,畲族传统文化是一种弱势文化,文化上的弱势地位使畲族形成了既自尊又自卑,对汉文化既模仿又抵御的民族文化心理[18]。《建阳县志》载,“嘉庆间有岀应童子试者,畏蔥特甚,惧为汉人所击,遽冒何姓,不知彼固闽中旧土著也”。可见清代部分畲民由于“惧为汉人所击”,在自卑心理的诱导下,接受汉族习俗和文化,甚至改名换姓,“不知彼固闽中旧土著”。
1.2.2 古代畲族服饰的传承因素
畲族服饰虽然在政治动荡、社会变革、经济发展、文化浸染、种族流变和宗教洗礼等一系列历史进程中一直不断地发展变化着,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在从远古至今的漫长岁月中,畲族服饰中所体现出的文化内核却穿越千年,愈久弥新。
1.2.2.1 民族信仰因素——盘瓠崇拜
畲族传统文化以畲族的原始信仰——盘瓠图腾崇拜为核心,它也反映了畲族人民“尊宗敬祖”的人文精神。据畲族史诗《高皇歌》(也叫《盘瓠王歌》)记载,畲族始祖五色神犬盘瓠生于高辛帝皇后耳中,因平番有功金钟下变身为人后娶三公主为妻,而后定居广东转徙闽浙。畲民以“盘瓠(也作‘护’)”、“狗王”之后自居,将盘瓠图腾崇拜代代传承下来。南宋刘克庄著《漳州谕畲》载,“余读诸畲款状,有自称盘护孙者”。清代古田畲妇“以兰布裹发,或带冠,状如狗头”。学者们普遍认为,畲族确是笃信盘瓠的一个民族。“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椎髻卉服”的服饰特征都是图腾崇拜在畲族服饰中留下的遗迹,服色鲜艳源于盘瓠“毛色五彩”,而以衣摆(裙摆)前短后长为代表的“制裁有尾形”源于对盘瓠犬型的模拟[l9、20]。可见畲族人民的服装,其意义更多地在于表达着他们对祖先的缅怀与崇仰之情。盘瓠崇拜作为畲族人民内心的民族认知心理,跨越千年仍然深刻遗留于畲族民族文化中。直至今日我们仍可在畲族服饰中发现这一文化核心的表象:畲族新娘沿袭盘瓠之妻三公主的装束,着“凤凰装”,她们用红头绳扎的头髻,象征着凤髻;在衣裳围裙上刺绣出各种彩色花边,并镶绣着金丝银线,象征着凤凰的颈、腰部美丽的羽毛;那后腰随风飘动金黄色腰带,象征着凤凰的尾巴;周身悬挂着叮当作响的银器,象征着凤凰的鸣啭[20]。潮州饶平、潮安北部妇女戴“帕仔”的起源,也有一说是来源于凤凰山的畲族。“传说昔年石古坪村的始祖是狗头王,畲族妇女出门戴‘帕仔’是为祖先遮羞”,后来他们同汉族关系日趋密切,畲、汉通婚,故此习俗便传播开来[21]。
1.2.2.2 民族性格因素——反抗精神
一个民族不管怎样庞大、复杂,无论它的文化如何变迁,总有它的基本文化精神及其历史个性。正是这种文化精神和历史个性赋予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性格,才使他们保持了民族的独立和个性。畲族自古就是一个勇于反抗的民族。一部畲族的发展史,可以说是畲族人民反抗强权暴政的抗争史。唐代畲族英雄雷万兴、苗自成、蓝奉高为了反抗封建官府“靖边方”的政策,勇敢地与官军拼杀。元代畲族人民为了反抗元统治阶级的压迫,组成了“畲军”进行起义,其斗争的烽火几乎燃遍了所有的畲族地区,如闽南队吊眼起义,潮州畲妇许夫人起义,闽北黄华起义以及闽、粤、赣交界处的钟明亮起义[22]。长期残酷的封建压迫激发了畲族人民内心不屈的反抗意识和民族情结,并在作为文化符号的服饰上表现出来。福建霞浦县畲族新娘“内穿白色素衣,据说这是为了纪念被唐军杀害的父母亲人而流传下来”[2]。宋元时期畲族起义军,也曾以“红巾”等鲜明的传统民族服饰风貌示人,借以彰显其共通的民族意识和反抗封建统治者的决心。
服饰作为一种媒介,反映着人们的精神状态,传达着文明潜移默化的作用。畲族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其演变既反映出畲族人民的生活环境、生产方式等自然及技术状态的演变,也折射出畲族人民内心的民族意识、宗教情结、社会观念以及审美倾向等思想状态的转变,还体现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的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互相融会,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可以说,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文化互动互补的产物。
1.1 古代畲族服饰文化变迁历程
1.1.1 畲族服饰原始时期
畲族族源至今众说纷纭,有苗、瑶、畲同源于“武陵蛮”一说;有越人后裔一说;有源自古代广东土著居民一说等,尚无定论[1]。据畲民族谱记载,畲族起源于广东潮州凤凰山。在汉晋以后、隋唐之际,畲族先民就已劳作、生息、繁衍在粤、闽、赣三省交界地区。
据《后汉书·南蛮传》载,畲族先民盘瓠蛮“织绩木皮,染以果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衣裳斑斓”。直至唐初,畲族所处的地区山脉纵横,“莽莽万重山、苍然一色,人迹罕到”,使得早期畲族与世隔绝,受外界干扰少,因此上述独特的民族服饰特征得到了延续和保持。如《云霄县志》记载唐代居住在漳州地区畲族先民的发式和服饰为“椎髻卉服”。《赤雅》载:“刘禹锡诗,时节祀盘瓠是也其乐五合,其旗五方,其衣五彩,是谓五参:”唐朝陈元光《请建州县表》载.唐朝前期福建漳州一带畲族先民“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2]。《畲族历史与文化》一书也载:“唐宋时,畲族妇女流行‘椎髻卉服’,即头饰是高髻,衣服着花边”[2]。
可见汉至唐初畲族服饰较好地保持了原始风貌,其主要特征为:
(1)色彩:鲜艳的五色。
(2) 款式:衣摆或裙摆前短后长,部分衣服衣襟为“左衽”,呈现与中原相异的服饰特征。
(3) 发型:将头发编束成椎形的高髻。
1.1.2 畲族服饰多源融合时期
宋元之际,在反抗封建苛政特别是榷盐弊政的共同斗争中,畲族与周边其他各民族人民在合中通过交流,加强了融合,促进了畲族服饰文化的多源融合。
闽粤赣边区的上著居民属百越系统。直至汉初,这一地区仍主要居住着不同支系的越人即百越族群。正如《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断发”、“文身”当为百越服饰习俗代表,文献记载也颇多。《淮南子·齐俗训》:“越王勾践,剪发文身”。《战国策·越策》云:“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史记·赵世家》:“越之先世封于会稽,断发文身,披草莽而邑焉”。《逸周书·王会》曰:“越泯(瓯),剪发文身”。其他文献如《墨子·公孟》、《庄子·逍遥游》等也均有记载。而据《元史·完者都传》载:“黄华聚党三万人,扰建宁,号头陀军”。“头陀”即“断发文身”。“头陀军”也是“畲军”的代名词。南宋中叶宁化的畲军领袖晏彪也曾号“晏头陀”[3]。这说明宋元时期畲族起义军在与闽越土著的交流合作中,吸收了其服饰元素;或部分闽越土著直
接汇入畲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并随之引入了相应的服饰元素。
总结元时期畲族服饰的主要特征为:
(1)款式:吸收了文身这种百越民族服饰特征。
(2)头饰:吸收了断发这种百越民族头饰特征。
1.13 畲族服饰流徙从简时期
元朝统治者对抗元畲军进行了残酷镇压和分化瓦解,“至元十六年(1279年)五月辛亥,诏谕漳、泉、汀、邵武等处暨八十四畲官吏军民,若能举众来降,官吏例加迁赏,军民按堵者如故”[4]。这直接造成了畲族的大迁徙。从元后期至明万历年间,畲民开始大规模从闽西南沿闽南经闽东向浙南流徙明万历进士谢肇淛游福建太姥山过湖坪时,曾目睹“畲人纵火焚山,西风急甚,竹木迸爆如霹雳,……回望十里为灰矣”,并写下“畲人烧草过春分”的诗句。顾炎武亦云:畲民“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这些都是对明朝畲族游耕生活的真实记录。
据史料记载,明代畲民的风貌普遍为高髻赤足,较之先民显得颇为简朴,这与他们的流徙生活不无关系。如谢肇淛《五杂俎》载,福建畲族的服饰“吾闽山中有一种畲人……不巾不履。”明朝万历《永春县志》卷三《风俗》也载,畲族先民“通无鞋履”。《天下郡国利病书》载,广东博罗县畲族,“椎髻跣足。”《潮阳县志》载明代畲族“男女皆椎髻箕倨,跣足而行”《永乐大典·潮州府风俗》载,福建潮州畲族“妇女往来城市者,皆好高髻,与中州异,或以为椎髻之遗风”。
畲民自明代开始在山上搭棚种青靛,熊人霖著《南荣集》记载崇祯年间闽西南“汀之菁民,刀耕火耨,艺兰为生,编至各邑结寮而居”(编者按:“兰”同“蓝”);《兴化县志》也载闽中莆仙畲民“彼汀漳流徙,插菁为活”。历史上,有称畲族先民为“菁寮”、“菁客”,是因畲族先民所到之地,遍种菁草。据明代黄仲昭《人间通志》卷四一载,“菁客”所产菁靛品质极佳,其染色“为天下最”从这一时期起畲族服饰色彩即开始以青色为尊。
明代,赣闽粤交界区域已得到较为深入的开发,人稠地狭的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明中叶在政治腐败日益加深的背景下,赣南的土著客家矛盾与畲汉贫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交织在一起,造成连绵的暴动和起义。明政府剿抚并用,特别是王守仁巡抚南赣平乱时所推行的礼乐教化之心学主张,缓和了民族和阶级矛盾,促进了畲民的稳定向化[5]。部分畲民接受招抚加入官籍,他们的服饰也渐渐与汉族趋同。顾炎武即于《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提到“三坑招抚入籍,瑶僮亦习中国衣冠言语,久之当渐改其初服云”。
总结元末至明中后期这一时期畲族服饰的主要特征为:
(1)色彩:开始以蓝靛所染青色为主要服色。
(2)款式:与当地汉族趋同。
(3)头饰:高髻、不戴头巾。
(4)足饰:赤足。
1.1.4 畲族服饰涵化成型时期
清代,畲族逐渐结束了迁徙的生活,主要在福建东北部、浙江南部定居下来:在与汉族人民“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下,畲族服饰一方面形成了自身的民族特色,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汉族的影响。
畲族先民与以客家先民为代表的汉族人民在粤、闽、赣的交流渊源深厚早在晋代,永嘉之乱促使大批中原汉人举族南迁闽西、赣南、粤东[6]。自唐末至宋,客家人因黄巢起义战乱所迫,从河南西南部、江西中部和北部、安徽南部,迁至福建西部的汀州、宁化、上杭、永定,还有广东的循州、惠州和韶州、更近者迁至江西中部和南部。宋末到明初,因蒙元南侵,客家人自闽西、赣南迁至广东东部和北部。这几次迁徙的地点正好是闽、浙、赣的交界处[7]。他们与畲族先民产生接触、交往和斗争,并引起了畲族社会生活和文化状态的改变。
明清以来,各地畲族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汉化的道路,如:永春县畲族在服饰、饮食、礼俗等文化上“皆与齐民无别”,长汀县畲客“男子衣帽发辫如乡人”等[8]。
据《平和县志》的记载“瑶人瑶种椎髻跣足,以盘、蓝、雷为姓虞衡志云:‘本盘瓠之后,俗呼畲客。自结婚姻,不与外人通也。……明初设抚瑶土官使绥靖之,略赋山税,羁縻而已今则太平既久,声教日讫,和邑诸山,木拨道通,猺獞安在哉,盖传流渐远,言语相通,饮食、衣服、起居、往来多与人同,瑶獞化为齐民,亦相与忘其所自来矣”[9]。从上文的记载可知:明初对畲民采取了绥靖政策,后经过畲汉长期的交流共处,到清初康熙年间,畲民已被慢慢地同化,言语相通,饮食、衣服、起居、往来多与当弛汉人相同。
甚至部分畲民一改往日畲汉不能通婚的习俗,主动与汉人通婚,渐渐融入汉族据清道光十二年《建阳县志》记载:“嘉乐一带畲民,半染华风,欲与汉人为婚,则先为其幼女缠足,稍长,令学针黹坐闺中,不与习农事,奁资亦略如华人,居室仍在辟地,然规模亦稍轩敞矣妻或无子也娶妾,亦购华人田产,亦时作雀角争,亦读书识字,习举子业”[2]。
乾隆时期《皇清职贡图》中所绘罗源、古田两地畲族男女服装款式皆大襟右衽(图1-1、图1-2),同于当地淑民[10]。
可见、无论是在历史上畲族聚居区的赣、闽、粤边地,还是闽北、闽东、浙南等畲族大迁徙后的新居地,畲族都在不同程度上汉化了。
如表1-1所示[11],在这一时期除广东畲族服饰相对显得比较简朴外,福建、浙江、江西的畲族服饰基本类同。比较突出的服饰特征可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色尚青蓝:服饰色彩以青色、蓝色为主,浙江地区多“斑兰”花布。
(2)款式精短:畲服款式普遍为短衣、短裙,大部分裙长不及膝盖,清末也有改为着裤的情况。
(3)装饰颇盛:较之前朝的“不巾不履”,清代畲族男女在头饰、足饰、装饰品等各方面都更显丰富。
(4)男女有别:男子戴竹笠穿短衫,一般赤脚,耕作时穿草鞋:女子一般先梳高髻,以蓝花布包头,再戴竹制头冠,并装饰以彩色石珠。
(5)汉化加深:在畲汉交流日益深广的情况下,女子赤脚的习俗在清末逐渐转变,在正式场合开始穿与汉秀花鞋类似的布鞋,平时则穿草鞋或木屐。
纵观畲族服饰文化逾千年的变迁,能看到闽越土著百越族群的衣饰身影,也能发现以客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族:化对其的渗透影响。畲族服饰文化的发展演变一直是在与周边各民族的融合中进行的。可以说,通过畲族服饰的发展历史,可以窥见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居于闽、粤、赣的各个民族在文化上的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互相融会的历程,可以窥见中华民族文明发展演变历史之一斑。
1.2 文化变迁视野下的古代畲族服饰演变动因
文化变迁是指文化内容的增加或减少及其所引起的文化系统结构、模式、风格的变化[12]。文化的形成和变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气候、地理等诸多要素都能带来文化的差异。文化变迁研究是人类学、民族学关于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自19世纪下半叶起,文化如何变化及民族文化的未来走向成为人类学家会学家潜心研究的课题[13]。目前民族文化变迁研究在我国方兴正艾,它对于探讨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探讨儒家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分析民族文化融合的意义、途径、过程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1.2.1 占代畲族服饰演变因素
关于文化变迁的动因,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看法,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生物因素说、地理环境说、经济基础说、工业发展说、文化传播说和心理因素说[13]。这些学说所提及的因素也同样影响着畲族服饰文化的变迁。值得强调的是,虽然在畲族发展史乃至世界各民族发展史上,文化的传播、人的心理因素、生物性、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地理环境等都曾引起过颠覆性的民族服饰文化变迁,但是不能将以上的某个单一因素确定为民族服饰文化变迁的根本原因,也不能确定为历史上的某一次民族服饰演变的唯一原因。社会是发展变化的,各社会因素间也有着纷繁复杂的联系,文化的每一次进步都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之下,文化变迁可能由于以上任何因素的作用而发改变。因此,民族服饰文化的变迁往往是多种因素同时作用的结果。
1.21.1 生物因素——族源融合
文化变迁动因的生物因素说认为:包括文化在内的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其变迁、进化是一个生物有机过程[14]。其中的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化变迁理论将文化进化或变迁归结为生态环境中群落基因库的变异和基因为群的分布[14]。
闽、粤、赣边地历史上存在着重叠的三个基因群,最早为土著百越族群,然后为源于五溪地区的畲瑶族群,最后为来自中原代表汉族文化的客家族群。这三种族群文化相交,必然产生互动互融关系。随着畲族逐渐迁出与世隔绝的祖居地,他们与古越蛮族、以客家人为代表的汉族的交流日益深广,关系日益紧密。其中一部分通过通婚、集结起义等方式实现了身份的迭合与转化,在不断的种族融合进程中,畲族服饰文化也相应地产生了涵化。唐宋时,畲族妇女流行“椎髻卉服”,即头饰是高髻,衣服着花边[2]。显示出畲瑶先民盘瓠蛮的典型服饰风貌。元代,畲族起义军又号“头陀军”,“头陀”即“断发文身”,是百越民族的典服饰特色[15]。这说明宋元时期畲族起义军在与闽越土著的交流合作中,吸收了其服饰元素;或部分闽越土著直接汇入畲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并随之引入了相应的服饰元素。
清代《皇清职贡图》载:福建畲民“其习俗诚朴,与土著无异”,表明当时畲汉关系密切、表征趋同。据清道光《建阳县志》载,一部分畲民主动与汉人通婚,模仿汉族服饰文化习俗:“嘉乐一带畲民,半染华风,欲与汉人为婚,则先为其幼女缠足,稍长,令学针黹坐闺中,不与习农事,奁资亦略如华人。居室仍在僻地,然规模亦稍轩敞矣。妻或无子亦娶妾,亦购华人田产,亦时作雀角争,亦读书识字,习举子业”,畲汉界限十分模糊。时至今日,福建客家和畲民仍同梳高发髻,戴凉笠,着右衽花边衣,尚青、蓝色[16]。
事实上,很多学者认为畲族本来就是多族源民族共同体,族源“包括五溪地区迁移至此的武陵蛮、长沙蛮后裔、当地土生土长的百越种族和山都、木客等原始居民,也包括自中原、江淮迁来的汉族移民即客家先民和福佬先民”[3]。族源多元性这一文化变迁的生物因素正是畲族服饰文化变迁的初始动力。
1.2.1.2 地理因素——迁徙
自然环境不仅决定着文化的性质,也决定着文化的形式与内容地理环境改变了,社会文化也随之变迁。从元后期至明万历年间,畲族从祖居的赣、闽、粵边地向闽北、闽东、浙南、赣东等多处新居地大迁徙,导致了畲族服饰原料的地域性改变和分化,从而影响畲族服饰的演变。比如,浙江丽水景宁的畲族因为主要生活在山区,当地盛产芝麻,加之气候温暖,温差较小,故“皆衣麻”;而福建古田的畲族,主要聚居在平坝,以种植棉花为主,故其制作服装选用的衣料以棉布为主,“妇以蓝布裹发……短衣布带”[17]。
各个迁入地的不同地缘文化也对畲族服饰的演变造成影响如迁徙到温州地区的畲族服饰刺绣深受瓯绣的影响,而闽东畲族服饰刺绣题材很多取自于福建木偶戏及闽剧。
迁徙过程中要求服饰简便实用,而不强调其审美功能,这也是导致元末明初畲族大迁徙时期服饰装饰性削弱的原因之一。
1.2.1.3 经济因素——经济生活方式的转变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经济基础决定着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等诸多文化要素,经济因素在文化变迁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畲族主要散居于我国东南山区的山腰地带,从气候上看,紧靠北回归线北面,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在这样的自然环境里,畲族明清以前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是“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的游耕和狩猎并举的经济生活方式[18]。因生产活动场所主要是未开荒的深山密林,多荆棘枝挂,所以服饰品尽量精简可见当时畲族服饰“椎髻跣足”、“不巾不履”的特征是与游耕和狩猎并举的经济生活方式相适应的。
明清以后,畲民扩散到闽中、闽东、闽北、浙南、赣东等地,结束了辗转迁徙的生活,逐渐发展起以梯田耕作和定耕旱地杂粮为核心的生计模式[18]。由于生产活动的主要场所由林区转移到田地,故具遮阳功能的“巾”、“冠”、“笠”等头饰和具采集功能的“围裙”逐渐在畲族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位位置。同时,随着农耕生产的不断发展,农副产品日渐丰富,手工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畲族人民能够创作出“布斑斑”、“珠垒垒”的精美的头饰艺术品,必然得益于当时经济的发展和手工制造技艺的进步。
1.2.1.4 工艺发展因素——染织技术发展
自然科学知识的增长推动了人类社会文化史的发展与进化新技术一旦出现,它自身的生命和力量就构成了文化进化的源泉。纺织服装技术的发展引导了服饰文化的演进,对畲族服饰演变影响比较深远的是以制菁为代表的畲族染色技术的发展。
畲族有谚语说:“吃咸腌,穿青蓝”福建霞浦县新娘结婚“头蒙兰底白点的盖头,腰系黑色素面的结婚长裙,扎兰色腰带”[2]。足见畲民对黑色、蓝色的喜爱。青、黑色之所以为畲民所接受,是由畲族人民的染色技术决定的“青出于蓝”,青在古代指黑色,一般由天然染料青靛中提取。青靛也名蓝靛,古称“菁”。用于染色时,时久色重显黑,时微色淡显蓝:明万历年间,由于织机的改进,闽、浙纺织业发展很快,以致种芒和种菁的利润几倍于粮食在种菁热的带动下,畲族拓荒者所到之地,遍种菁草,故历史亦有称畲族为“菁客”到崇祯年间闽西南“汀之菁民,刀耕火耨,艺兰为生,编至各邑结寮而居”;闽中莆仙畲民“彼汀漳流徙,插菁为活”。“菁客”所产菁靛品质极佳,其染色曾被盛誉“为天下最”[19]。畲族制菁技术的发展直接导致了明清之际其服饰色彩由“五彩”、“卉服”向“皆服青色”的转变。
1.2.1.5 文化传播因素——主流文化侵染
威廉·里弗斯在《美拉尼西亚社会史》中曾说道:“各族的联系及其文化的融合,是发动各种导致人类进力量的主要推动力。”文化传播因素即是指外来文化传播对某文化变迁的影响和作用这一因素。反映在古代畲族服饰上,中原主流文化对畲族文化的入侵和浸染主要来自于历代统治者的政治压迫和招抚教化。
自唐代“平蛮开漳”以来,被称为“蛮”的畲族一直遭受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分化瓦解直至明末每个朝代都有朝廷派兵平畲的记载:宋代,朝廷镇压了“壬戌腊”漳州畲民起义;元代,镇压和分解抗元畲军;明代,镇压江西赣州府畲民起义,增设“营哨守把”[2]。这些残酷清剿和封建强化统治直接导致了畲族的大规模迁徙。可以想见,在长逾千年的避难历程中,畲民为了躲避杀戮,不得不隐藏自身的身份,将作为“妖氛之党”标志的“椎髻卉服”进行改易。直至明末,畲族普遍“椎髻跣足”、“不巾不履”,服饰越来越趋近简朴无华。
从宋代开始,封建统治者就对畲族采取剿抚并举的政策。其中,明代王守仁的教化心学主张收效尤其明显。如前文所引《平和县志》[9]记载,明初到清初的三百年间,平和县畲民已被当地汉人慢慢地同化,其至“化为齐民”、“忘其所自来矣”。包括服饰文化在内的“饮食、衣服、起居、往来”各方面社会生活也被汉化,服饰特征逐渐与当地汉人相同。而这一服饰文化的转变正是“抚瑶”、“绥靖”、“羁縻”之后畲族逐渐接受汉文化的结果。
清末,畲族曾主动顺应政府服饰改易的号召。福州《华美报》己亥(清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刊登了福建按察使司的盐法道曾发表的《示谕》:“有一种山民,纳粮考试,与百姓无异,惟装束不同,群呼为畲,山民不服,特起争端”,因此,“劝改装束与众一律,便可免此称谓”,而结果是畲民“无不踊跃乐从”[2]。这充分体现了当时位于主流的汉文化对于畲族文化强大的感召力量。
1.21.6 心理因素——模仿心理
19世纪末法国塔尔德(G.Tarde)曾提出,模仿是人类的主要心理,也是文化发展、变迁的主要动力。特别是当模仿受到阻碍、怀疑或反对等刺激的时候,人类会运用新的方法和手段进行模仿而达到目的,这是是一个循环往复、无止境的社会文化过程,也是其变迁的动因。[12]
畲族是一个杂散居的少数民族,与作为中国主体民族文化的汉族传统文化相对而言,畲族传统文化是一种弱势文化,文化上的弱势地位使畲族形成了既自尊又自卑,对汉文化既模仿又抵御的民族文化心理[18]。《建阳县志》载,“嘉庆间有岀应童子试者,畏蔥特甚,惧为汉人所击,遽冒何姓,不知彼固闽中旧土著也”。可见清代部分畲民由于“惧为汉人所击”,在自卑心理的诱导下,接受汉族习俗和文化,甚至改名换姓,“不知彼固闽中旧土著”。
1.2.2 古代畲族服饰的传承因素
畲族服饰虽然在政治动荡、社会变革、经济发展、文化浸染、种族流变和宗教洗礼等一系列历史进程中一直不断地发展变化着,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在从远古至今的漫长岁月中,畲族服饰中所体现出的文化内核却穿越千年,愈久弥新。
1.2.2.1 民族信仰因素——盘瓠崇拜
畲族传统文化以畲族的原始信仰——盘瓠图腾崇拜为核心,它也反映了畲族人民“尊宗敬祖”的人文精神。据畲族史诗《高皇歌》(也叫《盘瓠王歌》)记载,畲族始祖五色神犬盘瓠生于高辛帝皇后耳中,因平番有功金钟下变身为人后娶三公主为妻,而后定居广东转徙闽浙。畲民以“盘瓠(也作‘护’)”、“狗王”之后自居,将盘瓠图腾崇拜代代传承下来。南宋刘克庄著《漳州谕畲》载,“余读诸畲款状,有自称盘护孙者”。清代古田畲妇“以兰布裹发,或带冠,状如狗头”。学者们普遍认为,畲族确是笃信盘瓠的一个民族。“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椎髻卉服”的服饰特征都是图腾崇拜在畲族服饰中留下的遗迹,服色鲜艳源于盘瓠“毛色五彩”,而以衣摆(裙摆)前短后长为代表的“制裁有尾形”源于对盘瓠犬型的模拟[l9、20]。可见畲族人民的服装,其意义更多地在于表达着他们对祖先的缅怀与崇仰之情。盘瓠崇拜作为畲族人民内心的民族认知心理,跨越千年仍然深刻遗留于畲族民族文化中。直至今日我们仍可在畲族服饰中发现这一文化核心的表象:畲族新娘沿袭盘瓠之妻三公主的装束,着“凤凰装”,她们用红头绳扎的头髻,象征着凤髻;在衣裳围裙上刺绣出各种彩色花边,并镶绣着金丝银线,象征着凤凰的颈、腰部美丽的羽毛;那后腰随风飘动金黄色腰带,象征着凤凰的尾巴;周身悬挂着叮当作响的银器,象征着凤凰的鸣啭[20]。潮州饶平、潮安北部妇女戴“帕仔”的起源,也有一说是来源于凤凰山的畲族。“传说昔年石古坪村的始祖是狗头王,畲族妇女出门戴‘帕仔’是为祖先遮羞”,后来他们同汉族关系日趋密切,畲、汉通婚,故此习俗便传播开来[21]。
1.2.2.2 民族性格因素——反抗精神
一个民族不管怎样庞大、复杂,无论它的文化如何变迁,总有它的基本文化精神及其历史个性。正是这种文化精神和历史个性赋予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性格,才使他们保持了民族的独立和个性。畲族自古就是一个勇于反抗的民族。一部畲族的发展史,可以说是畲族人民反抗强权暴政的抗争史。唐代畲族英雄雷万兴、苗自成、蓝奉高为了反抗封建官府“靖边方”的政策,勇敢地与官军拼杀。元代畲族人民为了反抗元统治阶级的压迫,组成了“畲军”进行起义,其斗争的烽火几乎燃遍了所有的畲族地区,如闽南队吊眼起义,潮州畲妇许夫人起义,闽北黄华起义以及闽、粤、赣交界处的钟明亮起义[22]。长期残酷的封建压迫激发了畲族人民内心不屈的反抗意识和民族情结,并在作为文化符号的服饰上表现出来。福建霞浦县畲族新娘“内穿白色素衣,据说这是为了纪念被唐军杀害的父母亲人而流传下来”[2]。宋元时期畲族起义军,也曾以“红巾”等鲜明的传统民族服饰风貌示人,借以彰显其共通的民族意识和反抗封建统治者的决心。
服饰作为一种媒介,反映着人们的精神状态,传达着文明潜移默化的作用。畲族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其演变既反映出畲族人民的生活环境、生产方式等自然及技术状态的演变,也折射出畲族人民内心的民族意识、宗教情结、社会观念以及审美倾向等思想状态的转变,还体现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的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互相融会,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可以说,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文化互动互补的产物。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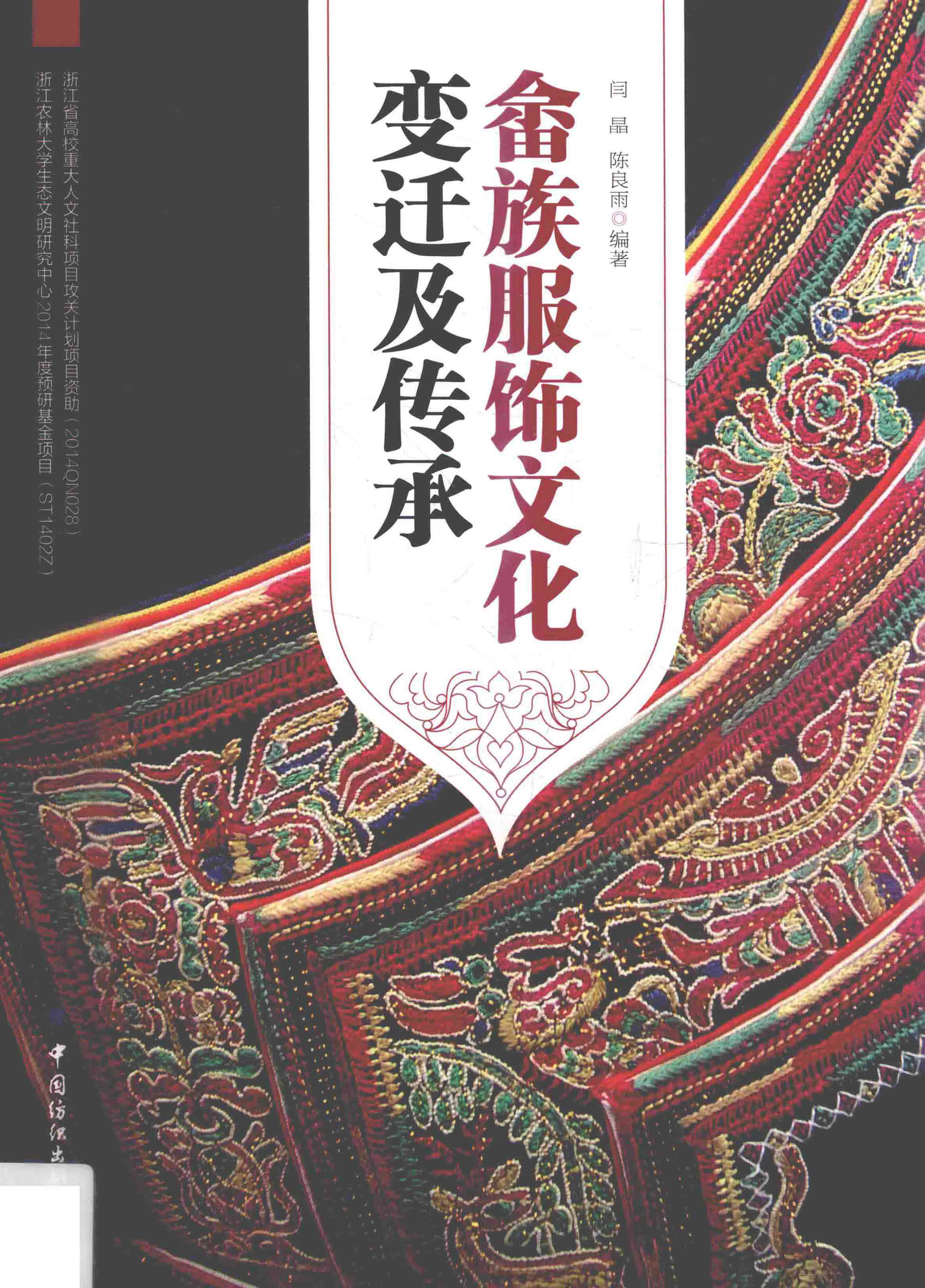
《畲族服饰文化变迁及传承》
出版者:中国纺织出版社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历史文献为依据,以畲族服饰发展和演变的历程为经、不同时期畲族的生活文化背景为纬,梳理了从汉唐、宋元、明、清时期直至20世纪的畲族服饰文化变迁轨迹。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畲族服饰在色彩、款式、装饰等方面所体现出的不同特色以及畲族文化生活背景对服饰发展变化的影响;本书第二部分从空间的维度对浙江、福建等地区的畲族服饰现状进行田野调査并做梳理.釆取田野调查和文献考据相结合以及个别研究、比较研究和整体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求对近现代畲族服饰、工艺及其文化背景有全面的、科学的、系统的认识。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