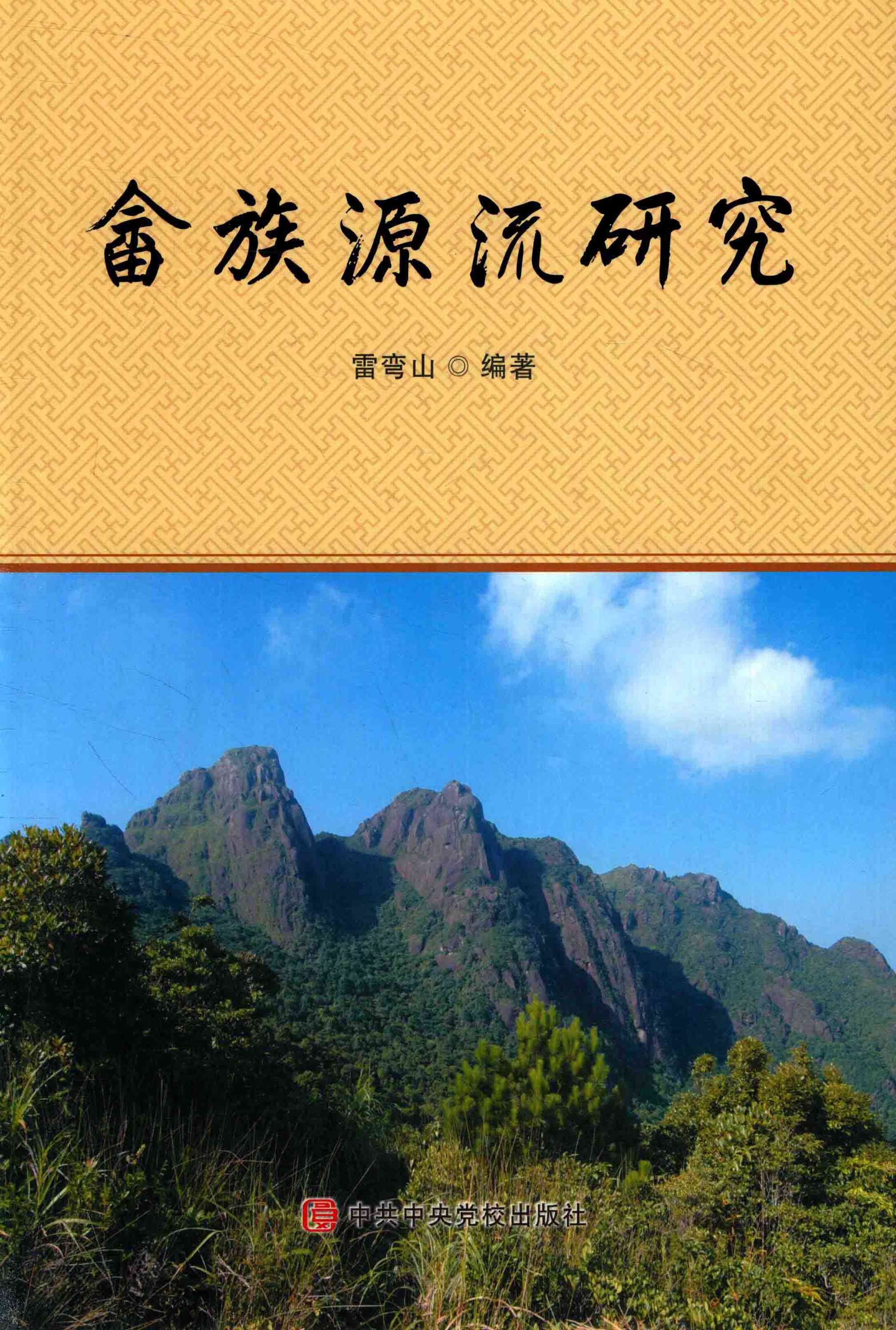内容
畲家为何要进行千年的民族大迁徙?“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①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畲家千年大迁徙的主要原因是封建统治者不但岐视畲家,且实行民族压迫,迫使畲家不断迁徙。
凤凰山区漳平山羊隔畲民的《苦历歌》,直接道出了畲家人被迫迁徙的原因:“到了元光入漳府,占去畲园个个诛:宋朝又说畲啸乱,文广派兵斩光光。五虎山下白磜坑,藏有畲族数百人;时到明朝又遭难,府兵屯杀廿几年。畲人逃身无立地,逃到龙江葫芦隔;掘蕨打猎兼种粟,身居草寮苦中苦。”
(一)不堪税赋
《漳州谕畲》中记载了“畲民不悦,畲田不税,由来已久”。也就是说,畲田、畲民原是不交税赋的。进入封建社会后,从畲民的记忆及相关文字资料看,唐之前统治者为了开发山区,往往以“不交赋税”为诱饵,引诱畲民到山中垦荒。“楚平王奉天承运出敕。大隋五年五月十五日,给会稽山七贤洞抚徭券碟……楚平王出敕钟太后上-十八族,放行广东路途,只望青山而去,遇山开产为业……唐代开始,封建统治阶级开始在凤凰山畲家聚居区推行封建化,畲家不但被称为“蛮僚”,且强迫畲民交纳贡赋,进行经济剥削。虽唐代统治者亦有“帝赐游行天下,砍伐山林,火耕石褥逍遥天地之间”的文告,而实际上是封建剥削不断加强,昭宗乾宁年间(894-898年)派官吏到凤凰山区“劝农桑,定租税”。①《临汀汇考》中写到,“唐武周年间,始郡县,其巢穴招集流亡,辟土殖谷,而纳贡赋。”②
畲家被迫进入山区后,是以棒、刀为劳动工具,从自然界获取现成的生活资料为主,生产力水平较低,辛勤劳动,不能糊口,还要上缴“徭赋”,没有粮食可剥夺,官府就向其征收蜜蜡、虎皮等土产,“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干诛货,稍笼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密腊、虎革、猿皮之类。畲人不堪。”③统治者在畲家聚居地侵占土地、大肆敛财,畲民不堪重负。畲民在无法承受的情况下,被迫向外迁移。但是所迁之处,土地山林一经开发又被地主所占有,而且封建剥削愈加严苛,刀耕火种,刀是唯一的劳动资料,对此封建统治者也不放过,实行"论刀为准”征收赋租的办法,规定畲民交纳山赋以“论刀若干”"出赋若干”。在统治阶级的不断压迫下,畲家开始分散迁徙。
明清时期,各地由于不堪官府压迫,而爆发多次武装反抗斗争,使得大量田地荒芜。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统治者开始招民垦荒。明正德中,广东畲民被子南池“世家”招募,“盗耕”香山县南三灶的政府禁地三百余顷。顺治初年,朝廷发布规定:“凡各处逃亡人民,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俾子安居乐业”。《汝南蓝氏宗谱》记载:“于是蓝雷钟等畲民入境,垦复田土。”但这些不是白给畲民垦植,实际上还是要交纳税赋,广东兴宁县有的畲民每年向山主交山粮七石;长乐县畲民有的每年要向山主交山粮五石五斗五升。④畲歌中记载了当时“开着地差难作食,开着地好官来争”,“种山又要交山租,交了山租毛得食,财主日日来逼租”、“外面官府欺侮人,三姓思量散来住”。歌词反映了当时统治阶层对畲家的欺压,开出好的田地被官府抢夺,差的田地难以饱腹。“每每彼所开垦之地,垦熟即被汉人地主所夺,不敢与较,乃他徙,故峭壁之巅,平常攀越维艰者,畲客皆开辟之,然每每刀耕火褥之所得,未成卒岁,则掘草药,种茯苓以自活”。①
开出的田地被子夺后,畲民落为“佃户”。浙南一带佃租的习俗是先付“垫底”,租又分“定租”与“分租”。“垫底”,就是畲民向地主、山主租种土地,首先要付“押金”,俗名叫“diandai”。“diandai”的多少,视土地的好坏和租额的多少而定,基本上是一年租额的代金。如有欠租事宜,即将“垫底”扣抵田租,撤佃改耕。贫穷的畲民要付一笔“垫底”是十分困难的,为了租得土地,拼凑“diandai”,东借西贷,忍受高利贷的盘剥,而地主剥削“diandai”的利息。借贷时,要有保人或实物抵押,还要先扣去第一年利息,借一元钱其实只拿到八角,以后仍要按一元钱计利。碧湖畲民蓝献文借了地主八元钱,利上加利,不到三年要还四十多元。就是这样,畲民还只能租到比较贫瘠的土地。并且逢年过节还要向地主送鸡、肉等,称“zhutanggai”。甚至有的地方还得服“tangzhugong”(汉语:田租工,即劳役)。“定租”又叫“硬租”。租土地时,先确定租额,租额是固定的。不论丰歉,租谷不变。另一种是“分租”称“做分”。即收成后按收获量分配,实行“四六分”(佃四主六)。不论何种形式,畲民辛勤一年所剩无几。地主用的秤和斗又比一般大,有的终年劳动尚不够交租。年景好,风调雨顺,地主加租;如遭灾,地主不肯减租,畲民辛劳一年,颗粒无收,地主还夺取畲民少量的产业,使其倾家荡产,地主收回佃田。对此德国学者史图博在《浙江景宁敕木山调查记》中评价道:“这样的佃租在欧洲的概念中当然还是高得难以置信”,“佃租高的吓人,税额也相当重”。
在浙江的遂昌、宣平、松阳,福建的浦城和江西的铅山、玉山等地的畲民,还要受到二地主——即“寮主”的剥削。明末熊人霖《南荣集》载:当时畲族地区有山主、寮主和青民三种人,“山主者土著有山之人,以其山卑寮主执之,而征其租者也。寮主者汀之久居各邑山中,颇有资本,披寮蓬以待菁民之至,给所委之种,俾为锄植,而征其租者也。菁民者一曰畲民,汀上杭之贫民也。每年数百为群,赤手至各邑依寮主为活,而受其佣值,或春来冬去,或留过冬为长雇者也”。清代,地主豪绅对畲民的剥削更是巧立名目,敲骨吸髓。如乾隆年间,福建宁德闽坑村的豪绅地主强迫畲民立承包约,以所谓对畲民的田园作物“看守”为词,榨取他们的血汗。该约规定,畲民每石稻田交谷子7.5公斤,每斗麦田交麦子1公斤,一千株番薯苗的地交钱五十文,菁靛一篓交钱一百文,姜种50公斤交谷子10公斤,一头牛交谷子15公斤。旧时畲民要交的租多如牛毛,田租、山租、牛租、房租、犁租、灰铺租、牛栏租、坟租、垃圾租等等。
交租,地主也规定了习俗,不能穿草鞋到地主家,不能坐。送租到地主家,先得把草鞋脱在门外,赤脚挑进去,不然非但田种不成,而且还要挨打。丽水碧湖镇鲤鱼头村钟有信,就曾因为送田租到松坑坪地主项章峰家,因地主不在,坐在厅堂前的石鼓上等候称租,被地主不问情由用鞭子打得遍体鳞伤,还把租田夺回,钟家被迫带着妻儿流落异乡,路上饿死了好几口。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景宁县志》中记载,“遇差役,县府票致之,贫不
能存,则亡徙以走”。
刀耕火种这种粗放的生产技术,没有广阔的空间、资源丰富的自然条件就不能进行,能满足这一条件的只能是没有开发的山区,因此畲民的迁徙只能是向山区扩散。闽东、浙南、赣东等地大多以丘陵山地为主,能为畲民的生产实践提供自然条件,畲家也就逐渐向这些地方进行迁徙。其实质是弱小民族,在强大封建制度的压迫下而产生的一种逃避封建化的行动;是落后的生产力,无法适应封建生产关系而产生的自发性的抗拒。
(二)反抗失败
面对封建统治者的岐视与剥削,畲民除了迁徙,就是反抗,一次次地开展反抗斗争。封建统治者对畲民的反抗首先采取武力镇压。
史藉记载,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泉潮间蛮僚啸乱”,唐高宗为了“靖边方”,派陈政父子率3600名唐军入闽,镇压畲民起义,屯驻于福建九龙江(旧时称“柳营江”)以东地区征伐“蛮僚”。凤凰山区的畲民组织起来与唐军进行斗争。在两军交战过程中,起义军屡胜唐军,陈政即上书朝廷:“群蛮来侵,自以众寡不敌,退保九龙山,奏请益兵。”唐统治者立即又派其兄陈敏、陈敷“领军校五十八姓来援”。其兄二人在途中死去,由其母魏氏携陈政之子陈元光“代领其众入闽”。陈氏家族倾家而出,但仍镇压不了“峒蛮”。仪凤二年(677年),陈政病死,陈元光受命“代领其众”与闽、广两地“峒蛮”作斗争。此时“蛮僚”首领苗自成、雷万兴率众抗击唐军,“守帅不能制”、“诛之难于屡诛,徙之难于屡徙”,①因此陈元光上书朝廷,要求增建“一州于泉、潮间,以控岭表”。唐王朝接受陈元光建议,于唐垂拱二年(686年),在福建增设漳州。
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爆发了更大的武装反抗斗争。“蛮寇雷万兴、苗自成之子纠党复起于潮”,两军斗争更为惨烈。睿宗景云二年(711年)11月,由蓝奉高率领的一支起义军直接与陈元光对垒,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于睿宗景云二年(711年)追至陈元光老巢绥安,把陈元光“刃伤而卒”。在近50年的斗争中,“蛮僚”屡屡打败了唐军的进犯。绥安是陈政“出镇”之地,也被起义军占领,但最终反抗斗争还是失败了。
漳州设府置郡后,针对漳州北部畲民的反抗,福州长吏唐循忠上书朝廷,“于潮州北、广州东、福州西光龙洞,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共三千户,奏置州,因汀溪为名。”唐王朝又听取唐循忠建议,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置郡汀州。然而,反抗斗争仍然不止,唐照宗乾宁元年(894年),出现宁化“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①唐统治者相继在漳州、汀州设置郡县强化封建统治,强迫畲民缴纳“贡赋”夕卜,还用两族通婚等手段对畲家进行强迫同化。
两宋时期,统治阶级对畲民的剥削和分化瓦解越加严重。因为在赋税方面畲民已没有多少可以剥削的。不能盘剥赋税,官府就从其它方面入手剥削畲民。畲族聚居地多在山地、丘陵,为了生存,畲民除了刀耕火种,还要进山狩猎,长此以往,畲民对射猎和用毒箭对敌都十分擅长。韩愈在《送郑尚书序》中曾写到:“机毒矢以待将吏”。②南宋刘克庄也曾提到“畲长技止于机毒矣”。由于畲民擅长狩猎,官府仍然不断地向其征求“蜜蜡、虎革、猿皮”等土产。畲民在不堪被剥削的情况下爆发反抗斗争。尤其是南宋偏安南渡,政治上极端腐败,经济上对百姓的剥削更加残酷,激起畲民的不断反抗。
高宗建炎中(1127-1130年)漳浦一带,绍兴十五年(1145年)江西虔州、广东梅州、闽南等地相继爆发了畲、汉人民的大起义。
宁宗嘉定二年(1209年)十一月,江西爆发以李元励为首的规模较大的反抗斗争,起义军“众数万,连破吉、郴诸县”,宋王室“诏遣荆、鄂、江、池四州军讨之”,结果,官兵被打败了。次年四月,李元励乘胜向广东南雄挺进,官军再度败退。接着多次击败江西官军,十一月间,进军赣州、南安。宋统治者“诏以重赏,募人讨之”。三年之久的起义斗争,直到李元励牺牲后,才被镇压下去。
南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年),漳州西畲最大的畲长李德,与西畲其他畲长并南畲三十余位畲长,一起带领畲民“怙众据险,剿掠省地”,漳州郡几乎要被攻陷,“距城仅二十里,郡芨芨甚矣”。统治者派遣卓侯到漳州进行军事镇压,卓侯一到漳州,见“一城红巾满野,久戍不解,智勇俱困”,感到愕然,只好到处张榜安抚,首先是千方百计招抚畲长。自李德被招抚、“纳款”后,“西九畲酋长相继受招”,“南畲三十余所酋长,各籍户口三十余家,愿为版籍民”。③统治者对人多势众的畲民采用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手段,削弱了畲民的反抗力量,使这次起义以失败告终。随后,因统治者忌惮人数众多的畲民,还许以利益,引诱畲长为其统治畲区。“以畲制畲”为统治者达到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剥削提供了保障。在起义失败和受到统治者、地主的双重压迫的情况下,畲民开始分散、迁徙。
宋末元初,朝代更迭。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年),元兵破汀州。南宋将领文天祥、张世杰分别在梅州、潮州领兵,随后在凤凰山区抗元。以陈吊眼、钟明亮、黄华为首的粤、闽两地畲民,跟随南宋将领文天祥、张世杰,展开声势浩大的抗元斗争。起义军由原先的一万余人逐渐发展到“聚众十万,连五十余寨”,成为“复宋反元”的主要武装力量之一。如今凤凰山陈吊眼抗元斗争遗迹确有50多处,如归湖镇砚田村对面的凤凰山南麓的陈吊王寨遗址,其海拔高304.6米,周围环绕着牛、狮、虎、龙、鹰、鸟笼、将军搭弓诸山,寨南面临凤凰溪,寨北峰峦叠嶂直连凤凰山,站在山寨上可望见韩江。寨址的开阔地虽然杂草丛生,但还能见东西两面各残存一条宽约二尺、长约百米的寨墙,墙外还挖有深约四尺的濠沟,在寨址还能见到不少宋代瓷器的碎片。
元代福建省共分八路,汀、漳、泉、邵4路是1043748人,专家粗略统计畲民有80万人,也就说,畲民占半个福建省人口的80%。广东比福建多。当时共有畲民210万人。①元朝统治者对畲军进行分化瓦解和残酷的军事镇压。《元史》载:“至元十六年(1279年)五月辛亥,诏谕漳、泉、汀、邵武等处暨八十四畲官吏军民,若能举众来降,官吏例加迁赏,军民安堵如故。”②元朝的招安政策使畲军军心动摇,力量削弱。元十九年(1282年),陈吊眼兵败,山寨被焚,“斩贼魁及其党首二万级”。③陈吊眼的父亲陈文桂、叔父陈桂龙、弟弟陈满安投降后,陈文桂及陈满安“纳款”被护送至京师,陈桂龙被流放于“答孙之地”。
元二十一年(1285年),黄华手下的畲军,“有恒产者为民,无恒产与妻子编为守城军。”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畲民钟明亮在福建汀州领导畲民起义,元统治者合四省兵镇压,“师之所经,寇之所及,男女老稚被执修,资财庐舍罹荡毁者甚多。”成宗元贞三年(1297年),元统治者下令将陈吊眼余部安插在漳州等地屯田。“命于南诏黎、畲各立屯田,调拨见戊军人,每屯置一千五百名,及将所招陈吊眼等余党人屯,与军人相参耕种为户。汀州屯一千五百二十五名,漳州屯一千五百一十三名。”①从元军南下闽、粤到元末年间,畲民一直进行着反元斗争。随着大范围的长时间战争和统治者的招安、屯田政策,畲民被迁徙到福建各地。
明代,封建统治者对畲民的统治全面加强,对畲族聚居区采取了三种统治管理方式。一是设置“輋官”对畲民进行间接管理。“永乐五年(1407年)冬十一月广东畲蛮雷纹用等来朝。……命各赐钞三十锭,彩币一……又明设土官以治之,衔曰輋官,所领又有輋,輋尝作畲,实录谓之畲蛮。”②二是在畲民聚居地增设军事或行政治所加强统治。军事治所以“寨”为名,并派武官管理及军队驻军。“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己丑正月十五日,逆贼曾延邦(兔洋人)、柯守岳(下溪人)、雷五(畲客)……倡惑乱民……里有典史刘茂者奏于朝,请建寨以镇之,诏以为可。”③压迫引发反抗,明正德年间,赣南山区爆发了畲民起义,明统治者派王守仁巡抚赣南。王守仁残酷镇压畲民起义后,在赣南采取联防的办法镇压人民的反抗,即“十家牌法”,一人犯上“十家均罪”,对畲民进行严密的控制与监视。增设县治也是明王朝对畲民所在地加强统治者的办法之一,“其初拳贼原系广东流来。光年奉巡抚都御使金泽行令安插于此……生长日蕃,羽翼渐多……始渐掳掠乡村……今幸奏闻征剿……但恐大兵撤后,未免复聚为患。合无三县适中去处,建立县治,实为久安长治之策等因。”④增设了五个县。三是通过寮主来约束畲民。“箐民者,一曰畲民,汀上杭之贫民也。每年数百为群,赤手至各邑,依寮主为活,而受其庸值,或春来冬去,或留过冬为长顾者也。”⑤畲民漂泊不定,统治者约束寮主,使其相互担保,相互监察来控制菁民。明统治阶级对畲族的重重监控与统治,让畲民难以生存,被迫迁徙,致使该地区的畲民基本上销声匿迹。
总之,封建统治者的残酷经济剥削和军事镇压,迫使畲民反抗;而面对封建统治者,畲家是弱小民族,一次次反抗斗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迫使畲族人民不断迁徙。
畲民离开凤凰山区后,没有生产资料,只能哪里能要到饭就往哪里迁。
畲民的迁徙以家庭、家族为单位,少则三、五人一伙,多则二、三十人一群,分散迁徙。他们跣足负担,一头挑着祖宗的牌位和骨灰,一头挑着幼儿,徐徐而行,傍树为家,依山而居。在畲家传统生计方式和以血缘关系为连接的居住方式的影响下,畲家在其进行民族大迁徙的过程中,发展出一种“不谋而居,不杂土著”的迁徙模式。这种模式使得畲家每迁到一地之后,当地人甚至“不知其始自何时”,有力的保存了民族的特性。如浙江遂昌县井头村《钟氏家谱》记载:“南宋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二月,钟谅、钟宜、蓝钟由原籍广东府朝阳县(即潮州),向外迁徙。迁迁往往,徐徐而行。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由钟石洪(即法桥)、钟法喜带领二十八口移浙江处州(丽水)景宁县二都田山源锦岱洋居住。”最终形成了如今“大分散、小聚居”于闽、粤、赣、浙、皖等省的分布形式。
凤凰山区漳平山羊隔畲民的《苦历歌》,直接道出了畲家人被迫迁徙的原因:“到了元光入漳府,占去畲园个个诛:宋朝又说畲啸乱,文广派兵斩光光。五虎山下白磜坑,藏有畲族数百人;时到明朝又遭难,府兵屯杀廿几年。畲人逃身无立地,逃到龙江葫芦隔;掘蕨打猎兼种粟,身居草寮苦中苦。”
(一)不堪税赋
《漳州谕畲》中记载了“畲民不悦,畲田不税,由来已久”。也就是说,畲田、畲民原是不交税赋的。进入封建社会后,从畲民的记忆及相关文字资料看,唐之前统治者为了开发山区,往往以“不交赋税”为诱饵,引诱畲民到山中垦荒。“楚平王奉天承运出敕。大隋五年五月十五日,给会稽山七贤洞抚徭券碟……楚平王出敕钟太后上-十八族,放行广东路途,只望青山而去,遇山开产为业……唐代开始,封建统治阶级开始在凤凰山畲家聚居区推行封建化,畲家不但被称为“蛮僚”,且强迫畲民交纳贡赋,进行经济剥削。虽唐代统治者亦有“帝赐游行天下,砍伐山林,火耕石褥逍遥天地之间”的文告,而实际上是封建剥削不断加强,昭宗乾宁年间(894-898年)派官吏到凤凰山区“劝农桑,定租税”。①《临汀汇考》中写到,“唐武周年间,始郡县,其巢穴招集流亡,辟土殖谷,而纳贡赋。”②
畲家被迫进入山区后,是以棒、刀为劳动工具,从自然界获取现成的生活资料为主,生产力水平较低,辛勤劳动,不能糊口,还要上缴“徭赋”,没有粮食可剥夺,官府就向其征收蜜蜡、虎皮等土产,“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干诛货,稍笼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密腊、虎革、猿皮之类。畲人不堪。”③统治者在畲家聚居地侵占土地、大肆敛财,畲民不堪重负。畲民在无法承受的情况下,被迫向外迁移。但是所迁之处,土地山林一经开发又被地主所占有,而且封建剥削愈加严苛,刀耕火种,刀是唯一的劳动资料,对此封建统治者也不放过,实行"论刀为准”征收赋租的办法,规定畲民交纳山赋以“论刀若干”"出赋若干”。在统治阶级的不断压迫下,畲家开始分散迁徙。
明清时期,各地由于不堪官府压迫,而爆发多次武装反抗斗争,使得大量田地荒芜。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统治者开始招民垦荒。明正德中,广东畲民被子南池“世家”招募,“盗耕”香山县南三灶的政府禁地三百余顷。顺治初年,朝廷发布规定:“凡各处逃亡人民,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俾子安居乐业”。《汝南蓝氏宗谱》记载:“于是蓝雷钟等畲民入境,垦复田土。”但这些不是白给畲民垦植,实际上还是要交纳税赋,广东兴宁县有的畲民每年向山主交山粮七石;长乐县畲民有的每年要向山主交山粮五石五斗五升。④畲歌中记载了当时“开着地差难作食,开着地好官来争”,“种山又要交山租,交了山租毛得食,财主日日来逼租”、“外面官府欺侮人,三姓思量散来住”。歌词反映了当时统治阶层对畲家的欺压,开出好的田地被官府抢夺,差的田地难以饱腹。“每每彼所开垦之地,垦熟即被汉人地主所夺,不敢与较,乃他徙,故峭壁之巅,平常攀越维艰者,畲客皆开辟之,然每每刀耕火褥之所得,未成卒岁,则掘草药,种茯苓以自活”。①
开出的田地被子夺后,畲民落为“佃户”。浙南一带佃租的习俗是先付“垫底”,租又分“定租”与“分租”。“垫底”,就是畲民向地主、山主租种土地,首先要付“押金”,俗名叫“diandai”。“diandai”的多少,视土地的好坏和租额的多少而定,基本上是一年租额的代金。如有欠租事宜,即将“垫底”扣抵田租,撤佃改耕。贫穷的畲民要付一笔“垫底”是十分困难的,为了租得土地,拼凑“diandai”,东借西贷,忍受高利贷的盘剥,而地主剥削“diandai”的利息。借贷时,要有保人或实物抵押,还要先扣去第一年利息,借一元钱其实只拿到八角,以后仍要按一元钱计利。碧湖畲民蓝献文借了地主八元钱,利上加利,不到三年要还四十多元。就是这样,畲民还只能租到比较贫瘠的土地。并且逢年过节还要向地主送鸡、肉等,称“zhutanggai”。甚至有的地方还得服“tangzhugong”(汉语:田租工,即劳役)。“定租”又叫“硬租”。租土地时,先确定租额,租额是固定的。不论丰歉,租谷不变。另一种是“分租”称“做分”。即收成后按收获量分配,实行“四六分”(佃四主六)。不论何种形式,畲民辛勤一年所剩无几。地主用的秤和斗又比一般大,有的终年劳动尚不够交租。年景好,风调雨顺,地主加租;如遭灾,地主不肯减租,畲民辛劳一年,颗粒无收,地主还夺取畲民少量的产业,使其倾家荡产,地主收回佃田。对此德国学者史图博在《浙江景宁敕木山调查记》中评价道:“这样的佃租在欧洲的概念中当然还是高得难以置信”,“佃租高的吓人,税额也相当重”。
在浙江的遂昌、宣平、松阳,福建的浦城和江西的铅山、玉山等地的畲民,还要受到二地主——即“寮主”的剥削。明末熊人霖《南荣集》载:当时畲族地区有山主、寮主和青民三种人,“山主者土著有山之人,以其山卑寮主执之,而征其租者也。寮主者汀之久居各邑山中,颇有资本,披寮蓬以待菁民之至,给所委之种,俾为锄植,而征其租者也。菁民者一曰畲民,汀上杭之贫民也。每年数百为群,赤手至各邑依寮主为活,而受其佣值,或春来冬去,或留过冬为长雇者也”。清代,地主豪绅对畲民的剥削更是巧立名目,敲骨吸髓。如乾隆年间,福建宁德闽坑村的豪绅地主强迫畲民立承包约,以所谓对畲民的田园作物“看守”为词,榨取他们的血汗。该约规定,畲民每石稻田交谷子7.5公斤,每斗麦田交麦子1公斤,一千株番薯苗的地交钱五十文,菁靛一篓交钱一百文,姜种50公斤交谷子10公斤,一头牛交谷子15公斤。旧时畲民要交的租多如牛毛,田租、山租、牛租、房租、犁租、灰铺租、牛栏租、坟租、垃圾租等等。
交租,地主也规定了习俗,不能穿草鞋到地主家,不能坐。送租到地主家,先得把草鞋脱在门外,赤脚挑进去,不然非但田种不成,而且还要挨打。丽水碧湖镇鲤鱼头村钟有信,就曾因为送田租到松坑坪地主项章峰家,因地主不在,坐在厅堂前的石鼓上等候称租,被地主不问情由用鞭子打得遍体鳞伤,还把租田夺回,钟家被迫带着妻儿流落异乡,路上饿死了好几口。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景宁县志》中记载,“遇差役,县府票致之,贫不
能存,则亡徙以走”。
刀耕火种这种粗放的生产技术,没有广阔的空间、资源丰富的自然条件就不能进行,能满足这一条件的只能是没有开发的山区,因此畲民的迁徙只能是向山区扩散。闽东、浙南、赣东等地大多以丘陵山地为主,能为畲民的生产实践提供自然条件,畲家也就逐渐向这些地方进行迁徙。其实质是弱小民族,在强大封建制度的压迫下而产生的一种逃避封建化的行动;是落后的生产力,无法适应封建生产关系而产生的自发性的抗拒。
(二)反抗失败
面对封建统治者的岐视与剥削,畲民除了迁徙,就是反抗,一次次地开展反抗斗争。封建统治者对畲民的反抗首先采取武力镇压。
史藉记载,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泉潮间蛮僚啸乱”,唐高宗为了“靖边方”,派陈政父子率3600名唐军入闽,镇压畲民起义,屯驻于福建九龙江(旧时称“柳营江”)以东地区征伐“蛮僚”。凤凰山区的畲民组织起来与唐军进行斗争。在两军交战过程中,起义军屡胜唐军,陈政即上书朝廷:“群蛮来侵,自以众寡不敌,退保九龙山,奏请益兵。”唐统治者立即又派其兄陈敏、陈敷“领军校五十八姓来援”。其兄二人在途中死去,由其母魏氏携陈政之子陈元光“代领其众入闽”。陈氏家族倾家而出,但仍镇压不了“峒蛮”。仪凤二年(677年),陈政病死,陈元光受命“代领其众”与闽、广两地“峒蛮”作斗争。此时“蛮僚”首领苗自成、雷万兴率众抗击唐军,“守帅不能制”、“诛之难于屡诛,徙之难于屡徙”,①因此陈元光上书朝廷,要求增建“一州于泉、潮间,以控岭表”。唐王朝接受陈元光建议,于唐垂拱二年(686年),在福建增设漳州。
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爆发了更大的武装反抗斗争。“蛮寇雷万兴、苗自成之子纠党复起于潮”,两军斗争更为惨烈。睿宗景云二年(711年)11月,由蓝奉高率领的一支起义军直接与陈元光对垒,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于睿宗景云二年(711年)追至陈元光老巢绥安,把陈元光“刃伤而卒”。在近50年的斗争中,“蛮僚”屡屡打败了唐军的进犯。绥安是陈政“出镇”之地,也被起义军占领,但最终反抗斗争还是失败了。
漳州设府置郡后,针对漳州北部畲民的反抗,福州长吏唐循忠上书朝廷,“于潮州北、广州东、福州西光龙洞,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共三千户,奏置州,因汀溪为名。”唐王朝又听取唐循忠建议,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置郡汀州。然而,反抗斗争仍然不止,唐照宗乾宁元年(894年),出现宁化“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①唐统治者相继在漳州、汀州设置郡县强化封建统治,强迫畲民缴纳“贡赋”夕卜,还用两族通婚等手段对畲家进行强迫同化。
两宋时期,统治阶级对畲民的剥削和分化瓦解越加严重。因为在赋税方面畲民已没有多少可以剥削的。不能盘剥赋税,官府就从其它方面入手剥削畲民。畲族聚居地多在山地、丘陵,为了生存,畲民除了刀耕火种,还要进山狩猎,长此以往,畲民对射猎和用毒箭对敌都十分擅长。韩愈在《送郑尚书序》中曾写到:“机毒矢以待将吏”。②南宋刘克庄也曾提到“畲长技止于机毒矣”。由于畲民擅长狩猎,官府仍然不断地向其征求“蜜蜡、虎革、猿皮”等土产。畲民在不堪被剥削的情况下爆发反抗斗争。尤其是南宋偏安南渡,政治上极端腐败,经济上对百姓的剥削更加残酷,激起畲民的不断反抗。
高宗建炎中(1127-1130年)漳浦一带,绍兴十五年(1145年)江西虔州、广东梅州、闽南等地相继爆发了畲、汉人民的大起义。
宁宗嘉定二年(1209年)十一月,江西爆发以李元励为首的规模较大的反抗斗争,起义军“众数万,连破吉、郴诸县”,宋王室“诏遣荆、鄂、江、池四州军讨之”,结果,官兵被打败了。次年四月,李元励乘胜向广东南雄挺进,官军再度败退。接着多次击败江西官军,十一月间,进军赣州、南安。宋统治者“诏以重赏,募人讨之”。三年之久的起义斗争,直到李元励牺牲后,才被镇压下去。
南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年),漳州西畲最大的畲长李德,与西畲其他畲长并南畲三十余位畲长,一起带领畲民“怙众据险,剿掠省地”,漳州郡几乎要被攻陷,“距城仅二十里,郡芨芨甚矣”。统治者派遣卓侯到漳州进行军事镇压,卓侯一到漳州,见“一城红巾满野,久戍不解,智勇俱困”,感到愕然,只好到处张榜安抚,首先是千方百计招抚畲长。自李德被招抚、“纳款”后,“西九畲酋长相继受招”,“南畲三十余所酋长,各籍户口三十余家,愿为版籍民”。③统治者对人多势众的畲民采用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手段,削弱了畲民的反抗力量,使这次起义以失败告终。随后,因统治者忌惮人数众多的畲民,还许以利益,引诱畲长为其统治畲区。“以畲制畲”为统治者达到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剥削提供了保障。在起义失败和受到统治者、地主的双重压迫的情况下,畲民开始分散、迁徙。
宋末元初,朝代更迭。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年),元兵破汀州。南宋将领文天祥、张世杰分别在梅州、潮州领兵,随后在凤凰山区抗元。以陈吊眼、钟明亮、黄华为首的粤、闽两地畲民,跟随南宋将领文天祥、张世杰,展开声势浩大的抗元斗争。起义军由原先的一万余人逐渐发展到“聚众十万,连五十余寨”,成为“复宋反元”的主要武装力量之一。如今凤凰山陈吊眼抗元斗争遗迹确有50多处,如归湖镇砚田村对面的凤凰山南麓的陈吊王寨遗址,其海拔高304.6米,周围环绕着牛、狮、虎、龙、鹰、鸟笼、将军搭弓诸山,寨南面临凤凰溪,寨北峰峦叠嶂直连凤凰山,站在山寨上可望见韩江。寨址的开阔地虽然杂草丛生,但还能见东西两面各残存一条宽约二尺、长约百米的寨墙,墙外还挖有深约四尺的濠沟,在寨址还能见到不少宋代瓷器的碎片。
元代福建省共分八路,汀、漳、泉、邵4路是1043748人,专家粗略统计畲民有80万人,也就说,畲民占半个福建省人口的80%。广东比福建多。当时共有畲民210万人。①元朝统治者对畲军进行分化瓦解和残酷的军事镇压。《元史》载:“至元十六年(1279年)五月辛亥,诏谕漳、泉、汀、邵武等处暨八十四畲官吏军民,若能举众来降,官吏例加迁赏,军民安堵如故。”②元朝的招安政策使畲军军心动摇,力量削弱。元十九年(1282年),陈吊眼兵败,山寨被焚,“斩贼魁及其党首二万级”。③陈吊眼的父亲陈文桂、叔父陈桂龙、弟弟陈满安投降后,陈文桂及陈满安“纳款”被护送至京师,陈桂龙被流放于“答孙之地”。
元二十一年(1285年),黄华手下的畲军,“有恒产者为民,无恒产与妻子编为守城军。”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畲民钟明亮在福建汀州领导畲民起义,元统治者合四省兵镇压,“师之所经,寇之所及,男女老稚被执修,资财庐舍罹荡毁者甚多。”成宗元贞三年(1297年),元统治者下令将陈吊眼余部安插在漳州等地屯田。“命于南诏黎、畲各立屯田,调拨见戊军人,每屯置一千五百名,及将所招陈吊眼等余党人屯,与军人相参耕种为户。汀州屯一千五百二十五名,漳州屯一千五百一十三名。”①从元军南下闽、粤到元末年间,畲民一直进行着反元斗争。随着大范围的长时间战争和统治者的招安、屯田政策,畲民被迁徙到福建各地。
明代,封建统治者对畲民的统治全面加强,对畲族聚居区采取了三种统治管理方式。一是设置“輋官”对畲民进行间接管理。“永乐五年(1407年)冬十一月广东畲蛮雷纹用等来朝。……命各赐钞三十锭,彩币一……又明设土官以治之,衔曰輋官,所领又有輋,輋尝作畲,实录谓之畲蛮。”②二是在畲民聚居地增设军事或行政治所加强统治。军事治所以“寨”为名,并派武官管理及军队驻军。“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己丑正月十五日,逆贼曾延邦(兔洋人)、柯守岳(下溪人)、雷五(畲客)……倡惑乱民……里有典史刘茂者奏于朝,请建寨以镇之,诏以为可。”③压迫引发反抗,明正德年间,赣南山区爆发了畲民起义,明统治者派王守仁巡抚赣南。王守仁残酷镇压畲民起义后,在赣南采取联防的办法镇压人民的反抗,即“十家牌法”,一人犯上“十家均罪”,对畲民进行严密的控制与监视。增设县治也是明王朝对畲民所在地加强统治者的办法之一,“其初拳贼原系广东流来。光年奉巡抚都御使金泽行令安插于此……生长日蕃,羽翼渐多……始渐掳掠乡村……今幸奏闻征剿……但恐大兵撤后,未免复聚为患。合无三县适中去处,建立县治,实为久安长治之策等因。”④增设了五个县。三是通过寮主来约束畲民。“箐民者,一曰畲民,汀上杭之贫民也。每年数百为群,赤手至各邑,依寮主为活,而受其庸值,或春来冬去,或留过冬为长顾者也。”⑤畲民漂泊不定,统治者约束寮主,使其相互担保,相互监察来控制菁民。明统治阶级对畲族的重重监控与统治,让畲民难以生存,被迫迁徙,致使该地区的畲民基本上销声匿迹。
总之,封建统治者的残酷经济剥削和军事镇压,迫使畲民反抗;而面对封建统治者,畲家是弱小民族,一次次反抗斗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迫使畲族人民不断迁徙。
畲民离开凤凰山区后,没有生产资料,只能哪里能要到饭就往哪里迁。
畲民的迁徙以家庭、家族为单位,少则三、五人一伙,多则二、三十人一群,分散迁徙。他们跣足负担,一头挑着祖宗的牌位和骨灰,一头挑着幼儿,徐徐而行,傍树为家,依山而居。在畲家传统生计方式和以血缘关系为连接的居住方式的影响下,畲家在其进行民族大迁徙的过程中,发展出一种“不谋而居,不杂土著”的迁徙模式。这种模式使得畲家每迁到一地之后,当地人甚至“不知其始自何时”,有力的保存了民族的特性。如浙江遂昌县井头村《钟氏家谱》记载:“南宋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二月,钟谅、钟宜、蓝钟由原籍广东府朝阳县(即潮州),向外迁徙。迁迁往往,徐徐而行。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由钟石洪(即法桥)、钟法喜带领二十八口移浙江处州(丽水)景宁县二都田山源锦岱洋居住。”最终形成了如今“大分散、小聚居”于闽、粤、赣、浙、皖等省的分布形式。
相关地名
漳平市
相关地名
龙江县
相关地名
广东省
相关地名
凤凰山乡
相关地名
始郡县
相关地名
三灶镇
相关地名
兴宁县
相关地名
长乐县
相关地名
浙江省
相关地名
景宁畲族自治县
相关地名
遂昌县
相关地名
宣平堡乡
相关地名
松阳县
相关地名
福建省
相关地名
浦城县
相关地名
江西省
相关地名
铅山县
相关地名
玉山县
相关地名
上杭县
相关地名
宁德市
相关地名
闽坑村
相关地名
丽水市
相关地名
碧湖镇
相关地名
鲤鱼头村
相关地名
靖边县
相关地名
九龙山乡
相关地名
漳州市
相关地名
福州市
相关地名
汀溪乡
相关地名
汀州镇
相关地名
宁化县
相关地名
南宋乡
相关地名
南渡镇
相关地名
漳浦县
相关地名
梅州市
相关地名
南雄市
相关地名
赣州市
相关地名
南安市
相关地名
潮州市
相关地名
归湖镇
相关地名
砚田村
相关地名
福建省
相关地名
邵武市
相关地名
南诏镇
相关地名
下溪镇
相关地名
金泽镇
相关地名
遂昌县
相关地名
井头村
相关地名
朝阳县
相关地名
景宁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