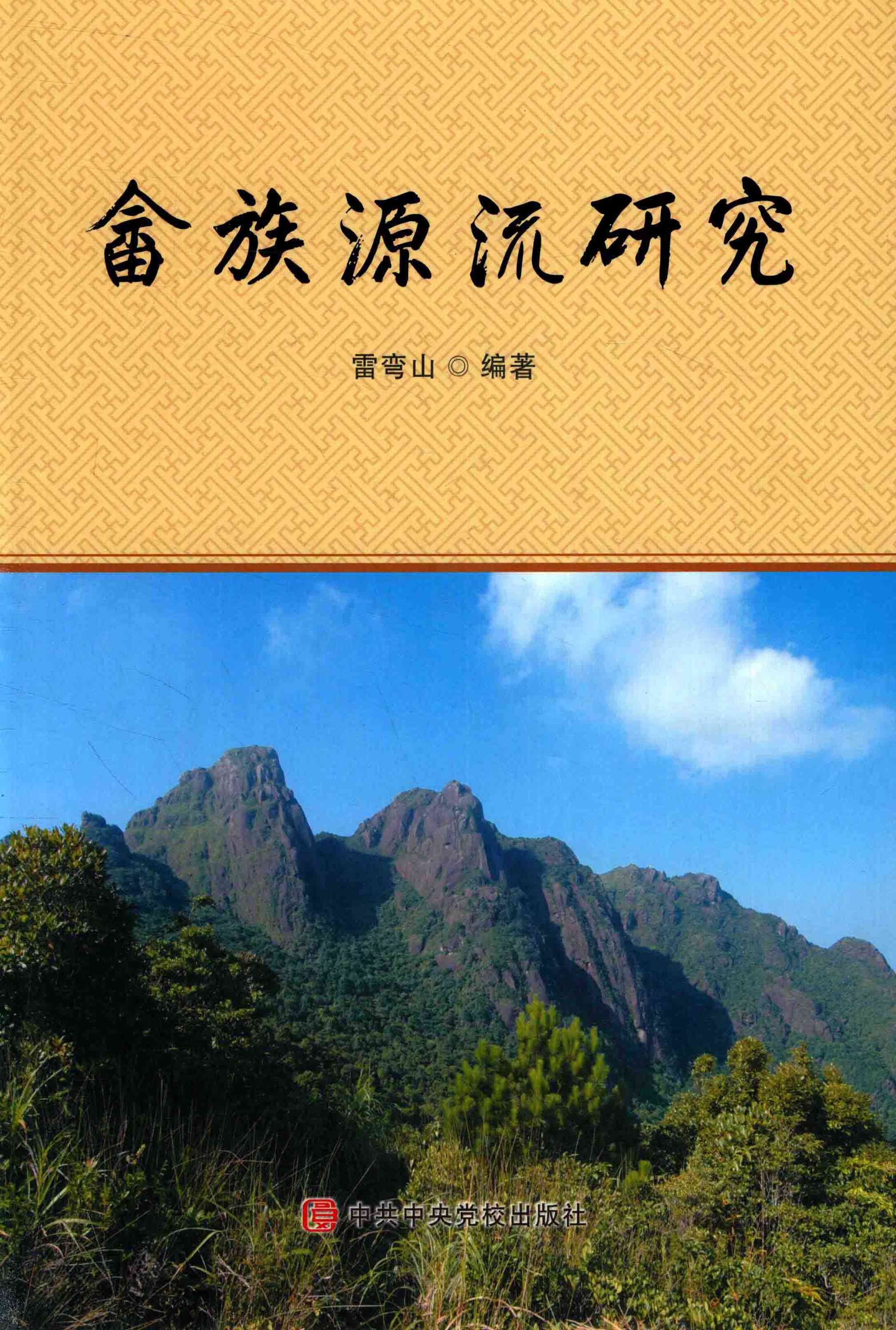内容
中原文化是以中原为基础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在中国文字历史记载上,中原自汉文字记载始至唐宋,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主流文化,因而对畲家等少数民族亚文化来说,其影响是极大。因本书主要是阐述畲族如今为何如此,特别是语言,所以只讨论中原语言对畲家语言的影响。
古代,商族的东夷语在中原与夏族语言和诸多原始方言融合后的华夏语是中原官话的雏形。以洛阳话为标准音的华夏语后来成为东周通用全国的雅言,进而发展成为扬雄《方言》提及的"通语、凡语①这种官方语言对畲语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说客家话”
20世纪50年代初,畲民识别调查中,调查组注重畲族作为单一的少数民族一般所必须具备共同语言,而不探求其本身具有的语言特征,对畲族语言没有进行全面深入地调查研究,认为“畲族有自己的语言”、“畲族基本上是以汉语客家方言为其共同语言”。继而语言学者在《国内各少数民族言系属概况简况表》中,把畲族与回族、满族列入“通用汉语文”,当时引起中央民族学院畲族学生的强烈不满。
1980年的《畲族简史》一书中写道:“畲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畲语和汉语的客家方言很接近,但在广东的海丰、增城、惠阳、博罗等县极少数畲族使用接近瑶族‘布努'语(属苗语支)。畲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通用汉文。在日常生活中,各地畲族皆通晓当地汉语方言。”①《畲族所说的客家话》一文云:“畲族使用两种语言:广东惠阳、海丰、增城、博罗一带的畲族使用的是畲语,属苗瑶语苗语支,约有一千人,占整个畲族人口的千分之四左右;其他地区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畲族,使用汉语客家方言”,“这种客家方言同现在使用的客家方言不完全相同,同汉语客家方言的分布也不一致,因此可以说畲族所说的这种话是一种超地区而又具有一定特点的客家话。我国少数民族由于同汉族长期共同生活和劳动,使用了汉语,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鲜见。随着民族的迁徙,脱离了原来的方言地区,在后来定居的地区又学会了当地汉语方言,并用它同当地的汉族交际,原来使用的汉语就成了本民族之间相互交际的工具。由于这种历史和使用的特点,常常使一种方言发生变化而具有明显的独特特点。畲族所说的客家话正是这种情况。”②进而有的加以引伸,运用逻辑推理得出“畲族没有自己的语言”、“一开始说的就是客家话”。引发了学术大讨论,进而引发其他问题。
这种观点产生的影响直到如今。③
许多学者、畲族干部群众反对上述观点:蓝周根在《畲族有自己的语言》一文中强调,畲族有自己的语言,不赞成“大多数畲族人所说的话是客家话”这一观点,并且认为即使是畲族同客家有共同的语言,也不能以语言接近就否定了一个民族的大多数人没有自己的语言。①雷先根在《畲语刍议》一文中认为,“我们应该把99%以上畲民使用的语言视为畲语,不因它接近广东汉语客家方言而不承认是畲语。这种语言之所以接近客家方言,那是两族文化互动、交融的结果。”②朱洪、姜永新在《广东畲族研究》一书中认为:“畲族有自己的语言,这从过去有限的史料记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大量实地调查中可以肯定回答。”并对畲族中只有广东的惠东、博罗等4县仍保留畲族的原生态语言的观点提出异议,指出:“居住于罗浮山、莲花山区的畲族,跟粤北南下的瑶族频仍交融,民族成份上互变共存,以至达到畲瑶不分地步”。“罗浮山、莲化山的畲语明显受到瑶语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延至凤凰山又消失殆尽。”“这是瑶族文化对罗浮山,莲花山畲族的渗透,以及两个民族在粤中的交融而致成。”③游文良一生对闽东、浙南畲语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在《论畲语》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罗浮、莲花山区的畲族从来源于湖南潭州,槃瓠王有六男六女的传说,使用属于苗瑶语族的语言等特点看,都跟凤凰山畲族不一样,而恰恰跟广东的瑶族一样;而且罗浮山、莲花山的畲族历来认为他们是‘瑶'而不是‘畲',这种自我意识也不同于凤凰山区的畲族,……据此,认为历史上罗浮、莲花山区的这支畲族可能就是瑶族的一支。”并提出罗浮山、莲花山区畲族使用的语言更接近瑶族语言而非古代畲语的遗存。在《浙江省少数民族志•浙江畲语》中进一步认为“浙江畲语含有古畲语底层、汉语客家话成分和现畲族居住地的汉语方言成分”。并指出“这种畲语是从古代畲语演变发展而来,它应是畲族的民族语言。”朱洪、姜永新、游文良都认为,现居住在广东凤凰山区以及福建、浙江等地绝大多数畲族使用的近似客家方言的语言才是畲族的民族语言,从而进一步阐明畲族只有一种语言。施联朱在《面向21世纪畲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中提出“有关畲族民族成份识别的几个余留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对广东罗浮山区增城、博罗,莲花山区惠东、海丰等县畲族民族成份质疑。其质疑主要从语言的角度提出的:广东增城、博罗、惠东、海丰4县有畲族一千多人,占全国畲族总人口千分之四,操“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语言,“跟苗语支的瑶族布努语炯奈话比较接近。”与占畲族总人口99%的、分布于闽、浙、赣、皖、粤东等地的畲族操接近于汉语客家话不同。“20世纪80年代,我与研究生雷玉虹(丽水畲族)调查了增城县的畲族,从文化特征看,增城的畲族与瑶族比较接近,语言相通,而与凤凰山区以及闽、浙、赣、皖等省的畲族不同。因而对增城等4县畲族的民族成份存疑,有必要作进一步鉴别。”
进入21世纪,语言学界则更注重对占畲族人口99%以上的畲族人所说的话进行调查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他们对畲族使用两种语言及其两者的关系、畲话的形成及其特性、畲语归属等问题,作了更广泛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并重视畲语本体的研究和探讨,并以此研究获得国家或省部级科研单位立项的课题多项,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及著作。张尚芳调查了景宁畲话后认为“我们不能说浙江畲话就是客家话,只能说它不完全是客家话。它吸收了五个层次的汉语方言,是汉语型的,音系上大体是客家话的,但并没有完全放弃本民族的东西,还有底层。”还指出“畲话音系中有些现象所反映汉语史时代比客家话要古老,因此把畲话说是畲族学的客家话,可能并不符合事实。”游文良在《畲族语言》一书中提出占全国畲族总人口99%以上畲族人所说的话就是本民族语言,并称之为“现代畲语”。指出现代畲语由三个部分组成:古代畲语的底层成分、汉语客家方言的中层成分和现代畲族居住地汉语方言或普通话的表层成分。并论证了现代畲语是从古畲语发展演变而来的。此论点较前又有了新的拓展,认为畲族语言自古以来就一直是一种独立的少数民族语言,从而否认畲族语言发展史上性质发生转换的事实以及过去大部分学者关于畲族有两种语言的观点。2001至2004年间,傅根清通过对景宁畲话比较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发表了《古全浊声母字今读情况》、《景宁畲话声母的超中古现象》、《景宁畲话语音系统中的粤语成分》、《景宁畲话尖团音分混现象研究》等有关景宁畲话的系列论文,认为畲话“是一种接近闽语而独具特色的汉语方言”。与徐瑞蓉、伍巍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俩在《长泰县磔头畲话的语音特点》一文中也指出,“磜头畲话与客家话的接近程度,远不如与闽方言密切。”而后傅根清又把景宁畲话与客家话代表点的声韵调作了系统比较,得出“客家话对畲话的影响是表层的、分散的,而不是深层的,更不是体系上”的结论。指出“畲话是一种古老的、非常复杂而又特殊的、以族群分布的、独具特色的混合型方言。”2000至2004年期间,赵则玲通过对浙江畲话5个方言点的调查和分析研究,首次对畲语、畲话、客家方言之间的关系作了比较明确的阐释。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以语音相似程度的高低作为判断两个方言亲属关系的重要标准,肯定了畲族语言发展史上性质发生转换的事实,否认占99%以上现代畲民使用的语言属于汉语客家话,主张把它作为汉语的一个特殊方言看待,是一种属于汉语系属的、与客家方言分立的少数民族人所说的汉语方言,可以称作“畲话”。并定性为比客家方言古老的、超地域分布的、与汉语方言关系密切的、历史层次复杂的语言。同时指出,这种畲话有进一步被“汉化”的趋势。2000—2003年间,台湾语言学专家张光宇及其弟子吴中杰,立项主持了关于畲族语言研究的两个课题:一是闽浙皖赣畲话及广东博罗畲语调查研究,二是广东潮安畲话调查研究,并且撰写了若干有关畲话的系列论文:《畲话的音节结构》、《广东潮安畲话调查研究》、《广东与浙江畲话之比较研究》、《畲话的介音问题探究》、《畲语和畲话的疑问词组》、《闽浙皖赣畲话和博罗畲语调查研究》、《畲话和客家话》、《畲语的正正重迭疑问句》等。提出:“畲语的语音系统和畲话相当不一样,词汇甚至词序也常见不同。纵使有零星的证据显示畲语和畲话彼此的关联性,我们仍必须强调:根据本文罗列的语言事实,畲话虽然和畲语及客家话都有关系,但畲话绝不等于是'客家话跟若干畲语残存成分的相加畲话的许多说法,既不同于客闽吴粤等汉语方言,又不同于畲语,可以说除了与畲语及客家话交迭的成分外,畲话各方言点间还分享着另一些共同性,这些是畲话所独有的特征吴中杰在《畲话和客家话》一文中认为:“尽管畲话和客家话有许多共通性,它们彼此之间仍存在着若干差异。但将畲话直接视为客家话的一种次方言,可能未尽恰当。”①上述半个世纪畲语研究的回顾表明,随着研究深入,90年代以来,结论越来越全面、正确:畲族有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有客家方言成份,但畲话并不等同于客家话,畲族说的并非是“客家方言”。当然,还可以从逻辑上分析“畲族没有自己的语言”、“畲族说的是客家话”观点存在逻辑错误。
首先,“畲族没有自己的语言”、“畲族说的是客家话”,是用不完全归纳推理得出的结论,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没有深入调查,有的甚至是根据他人的观点;或者是调查地点选在交通方便的公路边的畲汉杂居的畲村;为便于交流,被调查对象多数是从小就进汉族学校念书,后来一直从事教师职业、行政工作的干部;调查内容是调查者根据自己设计好的语言请畲民回答,不是问古代的词语,而问“人民公社好”一类现代词。于是就进行概括,得出结论。我们知道,语言这种社会现象,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它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早期人类从事简单的生产劳动,语言词汇也很简单,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语言词汇不断丰富、不断更新。畲语也不例外。现在畲民使用的语言多数是现代的共同语,或者是经过畲民改造过的共同语。这种共同语,不能代表原来的畲族语言。因此,这种田野调查,不但样本没有代表性,得到的不是原汁原味的畲族语言。况且,个别地方的调查,不能代表全部的畲语。
其次,语言分析过程中,只运用契合法和差异法,没有使用契合差异并用法。有的学者对畲族语言与客家方言的分析研究方法,是先从畲民所用的现代语言中,找出不同于汉语的词汇,再同客家方言比较,不同于客家方言的,才是畲语词汇,用了二次差异法。后用契合法,找出畲语与客家方言相同的词汇。再用剩余法,把相同的归到客家方言中,余下的才是畲语词汇。由于古代畲语词汇本来就不多,所以,余下的词汇就很少。于是有的学者就说,能找出几个畲语词汇,我们就承认畲族有自己的语言。其实,求因果关系要用契合差异并用法,也就是把畲语与客家方言相同的词汇,分别放到畲语和客家方言的各个语言区中契合。多数客家方言区中俱有的,少数畲族语言区中存在的词汇,那么就归到客家方言中;多数畲族语言区中俱有的,少数客家方言区存在的词汇,归到畲语中去。而不能把相同的,全部归到客家方言中去。如江西大余的“天亮”叫“天豁[tie33ho33]”,广东河源的“曾祖父”叫“公白[kon33pak3]”,“曾祖母”叫“阿白[a22pak2]”,“拔秧”的“拔”叫“瞒[man33]”,“看”叫“睇[tie33]”等跟福安畲语、浙江畲语义同音近。若说这些词是畲语吸收客家词,不如说是客语吸收畲族语词,因为,福安畲语所属各地畲话都有这些词,即99%畲民用这些词,且义同、音同,而客家话只有个别地方这些词的音、义与畲语相同或相近。
目前学界的研究基本上是用契合法、差异法在畲族语言中找客家方言,如果用契合法、差异法、契合差异并用法在客家方言中找畲语,那么,对畲族语言与客家方言的关系研究会更全面、更深入,更能揭示二者的关系。尤其是运用现代的概率演算等方法,不仅能定性而且能定量说明二者的关系。
再次,类比推理犯了“机械类比”的逻辑错误。逻辑上看,类比推理的结论是或然的、不具有必然性。如果不抓住事物的本质进行类比,往往导致“机械类比”的逻辑错误。在民族语言上,的确存在“我国少数民族由于同汉族长期共同生活和劳动,使用了汉语,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鲜见。随着民族的迁徙,脱离了原来的方言地区,在后来定居的地区又学会了当地汉语方言,并用它同当地的汉族交际,原来使用的汉语就成了本民族之间相互交际的工具。由于这种历史和使用的特点,常常使一种方言发生变化而具有明显的独特特点。”但畲族并不是这种情况,下面“相互交融”一小节中可说明之。
第四,畲族一开始说的就是客家话,这一论点是违反逻辑的;而“畲族有自己的语言”,却是逻辑推理得出的必然性结论。语言是种社会现象,语言与人的社会群体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随人的社会群体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消亡而消亡。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因语言是在劳动过程中,由社会的交际需要而产生的。人类的祖先在长期生存的劳动活动中锻炼了自己的大脑,改造了发音器官,具备了说话的能力,而且在共同劳动中又有了交流思想的需要,正如恩格斯所说:“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时,于是就产生了语言。语言离不开社会,社会也离不开语言,二者是相互依存的。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在互相交往中,都把语言作为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人们利用语言传送信息,交流思想,协调共同的活动,组织社会的生产,没有语言,社会便会停止,便会崩溃。社会的进步也离不开语言,生产斗争中经验的积累和传播都离不开语言。民族语言是在氏族语言和部落语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前面考古等资料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凤凰山区就有人类活动。在中原汉族没有进入闽、粤、赣交界北部之前,畲民已有相当数量的人数,社会发展水平许多方面不低于中原水平。
那么,在客家先民没有到闽、粤、赣交界北部山区,早在此生息数千年,人数如此之多,战斗力如此之强的畲民,如果没有语言,用什么来交流思想呢?不可能用汉族客家方言来交际,因为此时汉人没有进入此地,或者是很少汉人进入这个地区,更何况客家未形成,哪来的客家方言?!畲族人民肯定有自己的语言,斯大林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即令是最落后的,能够没有自己的语言,人种学不知道任何一个落后的部族,即令是比方说像十九世纪的澳洲人或火地人一样原始的或更原始的,能够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从目前畲族人民内部使用的畲语中找到其底层,根据“痕迹”来确定当时的面貌。始修于明弘治的《潮州府志》中,记载了当地畲族词汇:“火”叫“桃花溜溜”;“饭”是“拐火农”。李唐撰《丰顺县志》述:畲民“其土操土音,俗称为蛇罗语,极难异,今能操此语亦少。”可见,当时的畲语是存在的,也不同于如今的畲语,根据学术界的意见,称之为“古畲语”。
这里的推理是:任何部落一开始就有自己语言,畲族早在七世纪前就是一个强大的部落,所以,畲族在七世纪前就有自己的语言。如果畲族一开始说的是客家话,那么,客家话、客家应在畲民部落出现前产生;而客家话、客家晚于畲家二千年产生,所以,畲族一开始说的就不是客家话。
第五,畲族先民放弃了原有语言,用客家语言取代古畲语,也是违反逻辑的。畲家迁出凤凰山,已有1000多年历史,而且是迁进生产力更发达的福州、浙江、安徽等汉族地区,畲汉杂居,受到更为强大的汉语影响;封建统治阶级曾数次进行强行的语言同化,但直到如今,畲民仍然保留自己的语言。从广东的潮州到安徽的南部,畲民的语言都相通,保留共同的语言。难道畲族语言后来1000多年都不变,而在与客家相处的一段时间就完全丧失掉?这是不合乎逻辑的。而且部分畲民在唐初就迁到闽东、浙南等地繁衍后代,他们的子孙一直保留自己的语言。他们离开凤凰山区数百年后此地才出现客家方言。如果说,畲族说的是客家话,那么,他们必须回到凤凰山学会客家方言。实际上,回去学习客家方言,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两地相距数千里,不要说以前交通不便,难以实现,就是近年交通极其方便的条件下,浙南、皖南的畲民也没有几个人回过凤凰山,自然也谈不上学习客家方言了。
因此,雷阵鸣在《略论畲族与汉族客家在血统、语言及农耕等方面互动的“主客”定位》说:“汉语客家话最终是在畲语的影响下形成的,而不是畲族'放弃自己的语言①曹大明在《重塑“畲人”:赣南畲族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中也认为:众所周知,畲族人说的语言畲语,其实是客家话,所以部分畲族也自称客家人,据此有人认为客家人是畲族汉化,原本说畲语的畲族人接受汉文化后汉化了。
由于客家话和北方汉话的区大差异性,如果客家人是畲族汉化,那客家话一定就是古代畲语,不过,现实学术的研究中,一直存在将客家话(畲语)和赣语合二为一的讨论。因为客家话和赣语其实在所有的汉语族中差别是最小的,于至难于在学术上有个明确的分界线。
由此推论,现在江西自称汉人的赣语人,也有可能是畲族汉化,就算不是全部也至少占半数以上,否则很难解释现在所谓的江西汉人的语言不近官话反而极近客家话(畲族),以历史上畲族的地位低下,不可能隔空同化赣北汉人的。只能是占有绝大多数的畲语内混有少量的汉人,或者全部是畲族。
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已经形成标准汉语是汉语官话的正确论断下,赣语绝对不可能是南下汉人带来的语言,只能是畲语或者畲语受汉语影响下形成的新语言,江西汉人其实主体也是畲族。②
(二)相互交融
的确,畲族语言与客家方言声母、韵母有部分相同;畲语词汇中有不少和客家话相同;语法也有不少相同;初听,声调基本相同。这种相同,是“相互交融”的结果。
相互交融,是由于历史上在凤凰山区,畲家土著与中原来人友好相处,共同生活四百年,在这一时期,应该说,有矛盾、有斗争,但更多的是在同自然、同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中,共同合作,产生文化上互动、共生,这种文化上的互动、共生首先是语言上的互动、共生。这一时期,畲家操的母语是古畲语,客家先民操的语言应是中原古汉语及沿途吸取各地方言所形成的次古汉语。畲家与客先民共同生活、相互学习,古畲语吸收了客家人先民带来的次古汉语,客家先民带来的古汉语吸收了当地古畲语。
这种语言的互动,开始应是畲语影响汉语。
一是中原汉人是避难陆续进入这个地区的,开始迁入的汉人很少,他们的语言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对畲族发生重大影响。况且客家的起源也存在多种说法,主要的有“客家中原说”和“客家土著说”。客家中原说认为客家主体构成为来自中原的移民;而客家土著说则认为,客家共同体,是南迁汉人与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土著混化以后产生的共同体,其主体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土著,而不是少数流落于这一地区的中原人。嘉应大学的房学嘉先生通过考古学和田野调查等手段和方法,证明出“历史上并不存在客家人南迁史,客家主体是南方畲族。”房先生在其《客家源流探奥》一书中写道:客家是古越残存者与秦以来中原汉人互相混化而成的人们共同体……客家话的母语是闽粤赣三角地区古越族语。客家话中夹有相当多的中原古音,则是南迁的中原汉人带来的……历史上确曾有过一批批南迁客家地区的中原流人,但与当地人相比,其数量任何时候都属少数。台湾学者也认为,饶平客家人祖先是“性类徭僮”,即是经过汉化的“徭僮”。而事实上饶平客家人则有更多的古越人语言与文化留存,古越人后来在闽为“畲”,在粤为“俚”,两者在潮惠融合成“徭僮”。而且2005年古饶平县城(今三饶镇)发现一块古石碑,是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十一月初四日潮州府在饶平县城所立的《本府告示》碑刻,其中最明确的是提及饶平客家人祖先是「性类徭僮」。因此,有的专家说,这块石碑的发现,完完全全地粉碎了客家人是中原说的说法,它将客家人的先民是“徭僮”赤裸裸的完全现形。
历史上中原汉人来到闽、粤、赣交界的北部山区,多数学者认为是在两宋时期,在DNA中也得到证实。客家人父系DNA中,宋朝汉族血统占30%、秦汉汉族血统占10%、畲族03d血统占30%、越人血统及棕色人种血统各占10%;在母系DNA中,越人、汉族、畲族血统各占30%、棕色人种血统占10%。
斯大林分析语言的特征时指出,语言具有最明显的民族特点,即一个民族形成之后,由于历史传统、生活习俗、思维习惯、表达风格等特点,各民族语言具各自特征。它反映在民族生产、生活特点,保留和记录了本族人民的经验和智慧,也揭示了大量的本民族人民观察事物的方式方法,还有对他民族文化的见解。整个民族所有成员都时刻使用自己的语言。语言的社会性决定了语言的稳固性。这种稳固性,具有对强迫同化的巨大反抗力。少数中原来到此地的汉族人,只能是接受畲族的语言,他们学习了畲语。
因而,客家方言形成的时限,由最早的罗香林“五代宋初说”向后延。华东师范大学王东认为,“客家人之所以区别于非客家人,其中一个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语言。客家方言不仅是客家之成为客家的标志,而且也是客家民系自我认同的内聚纽带。也就是说,一个客家人之所以把另一个客家人认同为自己的属群,其最直接、也最简单的道理是因为他(她)也讲与自己的一样的客家话,而不是共同的地域、血缘或其他什么原因。正因为如此,以客家方言的形成与否,来作为客家民系形成与否的标志,应该说是没什么问题的。”“最早提到客家方言的应该是在明代”,其依据是,“明代嘉靖年间编修的《惠州府志》中有关方言方面的记载,可以被视作为关于客家方言的最早记录;还以同一时期编修的《兴宁县志》“方言”一目中所列举的方言特点加以证明。并根据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一书中关于汉语北方方言和南方方言声韵调的一系列演变现象的讨论,认为南方方言演变发生的时间基本上“不能晚于16世纪”,说明此时“客家方言已基本上割断了与北方方言的联系,而步入了独立发展的里程”。而因为“一旦客家先民的语言已完全与北方方言相分离,就表明客家方言已基本形成了”。因此,王东认为“客家方言的产生,当在15世纪至16世纪之间,即相当于明朝的中期”。
客家也在这一时期形成。客家研究院的李默《论客家的形成及民族融合》中认为:即说,明以前曾出现“客”的单称,也出现“畲”的联称。“客家”一词,作为汉族一支民系出现,应该是明正德间闽粤赣畲族大部分融化为客人之后,即入版籍,编里甲,纳租赋,输徭役,与齐民一体,正式称之客人。正德年间,“程乡盗起(畲民起义),众数万,钦至程乡,开谕祸福,其党伏,藉其丁壮老幼四千人,散遣之,使耕田筑,目其民曰新民”。《阳明集》载:“正德十二年十二月,剿横水(畲),广东程乡知县张哉统领部下新民、乡夫等搜剿”。明王朝在对畲族人民进行征剿的同时,对畲族地区加强封建统治,编里甲,促进山区生产,并兴文教设儒学。正德年间王阳明讨平广东的平远、长宁,平定湘头池仲容,乃立和平县(纯客语县);讨平江西横水,立崇义县(纯客语县);讨平福建汀州(纯客语地区)。以上地区的畲民起义,王阳明剿服始归化。此时,梅州及其邻汀州、虔州的畲族基本上归化为新民,融为客家。而星散的畲人,亦于其后融入客家。至此,以梅州为代表的客家民系亦告形成。①
二是闽、粤、赣交界的凤凰山区,自然环境、社会生态完全不同于中原,有许许多多的动物、植物、事物是中原没有的,而畲族此时对这些事物已有了自己的称呼;畲区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与中原也不同,中原汉族来到此地,随乡入俗,学习畲族人生产、生活方式。直到明代王守仁率兵镇压大帽山畲、汉农民联合起义时,还哀叹“处处山田尽入畲,可怜黎庶半无家”,“黎庶”当然是指刚到不久的客家,土著者是原来就有家的。林达泉《客说》即谓“凡膏腴之地先为土著,故客家所据地多硗瘠”。此时客家的农耕条件并无什么“优势”。自然在语言上,汉族人只有借用畲语语词。因此,对新的事物交流必需借助当地的名称。
三是语言的传承与母亲相关。南迁的汉人往往是男性,娶当地女子为妻。如今的福建人、客家人男性主要来自北方,而迁徙到福建等地的北方汉族中很少有女性移民,福建汉族多数是少数民族母亲生的。DNA检测也证明这一点。
复旦大学对南方各省(北方各省的Y染色体和线粒体的数据都接近1)血样的实际测定结果。
福建人Y染色体的相同率高达0.966,说明基本是北方汉族男性的后代。线粒体DNA的相同率很低(平均0.224),说明基本是南方少数民族女性的后代。综合两点,福建居民基本是北方汉族男性与南方少数民族女性婚配的后代。同时表明,迁徙到福建等地的北方汉族中很少有女性移民,福建汉族多数是畲族等少数民族母亲生的。①
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说“客家话在当地民间叫‘阿姆话',‘阿姆,与普通话的,母亲'同义,即客家话为母亲话……历史上散居于闽粤赣三角地带的少数原汉人跟当地古百越人等少数民族通婚,建立家庭,其语言、文化习俗自然跟随母亲的民族,此即客家话叫阿姆话之故”。这“母亲的民族”即畲族。陈晓红也说:“某些客家男人或频繁地外出经商,或攻读致仕当官等等,多长期在外,不过问家事,因此,家庭的农业生产劳动、生儿育女、养老扶幼以及一切家庭操持,多由妇女承担”。那么其子女当然是学说母亲民族的话。②
畲汉两个民族群体的语言互动、共生是从借词开始的。原来没有的事物的名称,各群体相互搬用;而一些各自有的词语,也因相互往来,逐渐先用畲、客先民同义词语。如,畲语称“什么”为“奚纳”,(i22n?5):称“摇摆晃动”为“湿啊湿”(it);称禽、鸟的翅膀为“劦刀”(iet5t?u33);称“天亮”为xau31(皞);称耘田除草即叫“薅草”(xau33ts'?u55)。客家话中的这些词,是从畲语中吸收去的,因这些词在唐宋时的“中原官话”中已经消失。畲、客读音相同的“知(道)”读t产、“蜘蛛,,读总%io33、“屐”读k3ia2、“盹”读k'in31”、“茄子”读k'io35、“嗅”和“鼻涕”都读p'i就、“要”和“爱”都读oi33、“被”和“分”都读pun33等词,来自畲语。
同时,中原汉语也影响畲语。这是由于中原的汉族人带来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带来了新的词语,这种新词,有的被畲族人接受下来,也有的进行着改造,变成畲语。如,汉语的“端午节”,各地的畲语都叫“五月节”,各客家方言点也叫“五月节”,根据畲语“五月节”的读音,是客家话“五月节”的借词;汉语的“剪刀”,各地的畲语都叫“zhandao”,各客家方言点也叫“剪刀”,根据畲语“剪刀”的读音,是客家话“剪刀”的借词;汉语的“苕帚”,各地的畲语都叫“guansao”,各客家方言点也叫“竿扫”,根据畲语“竿扫”的读音,是客家话“竿扫”的借词;汉语的“说”,各地的畲语都叫“讲”,各客家方言点也叫“讲”,根据畲语“讲”的读音,是客家话“讲”的借词;汉语的“跑”,各地的畲语都叫“zao”,多数客家方言点也叫“走”,根据畲语“走”的读音,是客家话“走”的借词;……特别是中原语言当时代表了官方语言,畲民对外交际需要用这一语言,中原语言影响了畲语。后来多数畲民迁居他地,余下的畲民,就慢慢地使用了客家方言。如今,闽西的畲族使用客家方言,就是如此。
学界也赞同“相互交融”的观点。1981年,詹伯慧在《现代汉语方言》一书中指出:“客家方言与畲族语曾经起过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作用1985年,陈宏文在《客家方言前途问题初探》一文中,认为“客家人多与当年的畲族同胞为邻,由于交往的需要,就吸收了一些畲族同胞的实用词汇。并凭自己带来的汉文化优势,把它融合过来。难怪有人把客家话误认为是‘蛮语①这“蛮”指的正是畲族。1992年,李默、张溥祥在广西桂林市举行的客家人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供的《论客家的形成及民族融合》一文,列举大量客家与畲族关系的事实,认为“客家的形成和发展也不例外,在特定条件下,中原汉文化在与当地百越土著文化的排斥和融合中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1994年6月,蒋炳钊在台湾举办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讨会上,宣谈《试论客家的形成及其与畲族的关系》一文,指出:“客家的形成过程,必须是入迁的汉人与当地畲族融合的过程”,“客家是入迁的汉人和当地畲族文化互动于闽粤赣交界处形成的一个新的文化共同体”。学者们的研究都表明,客家语言、客家的形成、发展是在与畲族的文化互动中形成发展的。
(三)丽水畲语
畲家在凤凰山区时,秦汉后语言受南下汉语影响,迁出凤凰山后,一直与汉族杂居,语言仍然受到当地汉方言的影响,因此,如今的畲族语言可以说没有所谓原生态的畲语。那么哪个地区的畲语有比较多的原生态成份呢?应是丽水畲语。
从语言的发展变化规律看,一种语言与不同语言接触时间越长、越多,那么受其影响就越大,保留的成份就越少;相反与不同语言接触时间越短、越少,那么其影响就越小,保留的成份就越多。丽水畲族入迁时间比福建、苍南、景宁较短,且人口数量多、居住集中,现有2个畲族镇(柳城、老竹)2个畲族乡(丽新、板桥)连成一片,其西北有三仁畲族乡,西南的碧湖、高溪、富岭等乡镇及城关畲族人口也较多。
闽东有的畲族干部、群众近年到此处交流畲语后,认为,此处比闽东原生态畲语保留得更多。
研究畲族语言的专家游文良认为,现代畲语分为9个区,其中浙南区是全国畲语方言的第二大区,里面还可分为苍南、景宁、丽水片区。丽水片区比苍南、景宁受闽东方言的影响小,比浙中、浙北区受汉语吴方言影响小。①
2015年10月出版的《潮汕方言历时研究》,是语言学家林伦伦先生化20年时间所写成,是对潮汕方言所作的纵向的历时性研究的总结。全书基本囊括了他迄今潮汕方言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而收录其中的“潮汕方言词法特点与历时研究”部分,是作者1994年获中国语言学界最高奖项——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吕叔湘奖)的系列论文。该书是潮汕方言研究的又一座学术高峰。第一至第四章的最主要内容,是对潮汕方言“是什么”、“哪里来”、“为何是这样”的学术解答。著作的开头说:潮汕方言,也叫作潮州话、汕头话、潮汕话,属于汉语闽方言的闽南次方言,所以,学术化的称谓应该叫作“粤东闽方言”。哪里来?早在原始社会,此地已有先民居住;春秋时期,这里居住的是百越支系。当时没有讲华夏语的居民,使用的是古台语。虽然当时楚语和吴越语已经形成,“但是,在当时,夏语和吴越语对远在天边的潮汕来说还是鞭长莫及的。汉人由闽入潮和由晋豫入潮,那都是之后的事。”“中原汉人入潮始于秦汉。”“当时楚语的影响是否延及潮汕地区呢?从历史事实和现代粤方言与潮汕话的系统看来,未发现有影响的迹象存在。因而,我们可以推定,春秋战国时期的潮汕先民所操的应该还是土著越语-----种属于壮侗语族支系的少数民族语言。”②潮汕方言文读系统的雏形在唐末才形成。
潮汕是凤凰文化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畲族的发源地、也是发祥地。一直至唐代中期,畲家还在此生息,秦汉之前的潮汕方言是畲家等土著的语言,如今畲族语言中与秦汉之前的潮汕方言相同的成份应是原生态的畲家语言。
1.语音
丽水畲语声母单纯,韵母发达,声调复杂,变调现象较普遍,音节多,在声、韵、调、音诸方面,与潮汕方言有许多共同之处。
(1)声母
丽水畲语声母有18个,比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少3个,而苗语有48个。
没有汉语普通话的翘舌音zh(ts)、ch(ts′)、sh(s)、r(β)四声母,因而没有翘舌音,凡汉语中的翘话音都读成舌面音或舌尖前音。如“主(Zhu)”读“t?y35”、“抽(Chou)”读“t?iu63”、“诗(Shi)”读“si22”、“热(rD”读“ni33”。另外,它仍保留古语中的鼻音声母n(疑母)。如“牛(niU)”读“nau22”、“咬(yao)”读“nai33”、“不(bu)”读“〓22”财(唔)。
今潮汕方言声母也是18个。
(2)韵母
丽水畲语韵母有60个,加上含有入声韵的如、〓、ia、io、i3、iai、iou、iau、iau、ioi,lau,iou及uo、y,计有76个,比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多37个。由A、i发展的韵母很发达,开合元音、齐齿元音多,入声韵也较多。韵母总数比《指掌图》多3个,入声韵与它相等。
如今“潮汕方言的韵母内部差异较大”。《潮汕方言历时研究》以汕头市话为代表,汕头市话韵母84个,比丽水畲语多8个。
潮汕方言六朝之前的古台语,无轻唇音[f-];无舌上音[ts-]、[tsh-];牙喉音相混。
(3)声调
潮汕方言与丽水畲语声调相同,都是8个。苗语是6调。苗语、汉语无入声。
潮汕方言8个声调
如今其他畲族地区的畲语基本上是4个声调,而丽水畲语8个声调。
(4)音节
丽水畲语音节有635个,比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多200个。635个音节中,与汉语普通话音节相同的只有200个,三分之二的音节是汉语所有的。它的声韵配合能度甚高,其中尤以p(35个)、p'(34个)、t(39个)、t'(32个)、n(38个)、1(46个)、k(53个)、k'(49个)为甚,只有f的能拼度最低(11个),而苗语音节结构与汉语相同。
2.词汇
丽水畲语词汇亦可分为实、虚词两类、十一种,实词尤为丰富。例如:蜘蛛——寮蛐,蜻蜓-------黄〔粘),蚯蚓--------蛇蜒,蟋蟀-------灶蛤
,跳蚤-------狗虱,苍蝇--------白蚊,青蛙---------〔蛙〕
,蜈蚣——蛐,海蛰——它,钉鳗——牛轭钉,鳗鱼---脯鱼鲐,鹅---------〔赤〕牛,鳅鸽-----------田〔担〕
,翠鸟---------刁鱼鹳,白眉鸟-----------寮公青,獾——猪豚,穿山甲——龙甲,松鼠——老鼠〔紧〕,刺猜---------(敏)。
丽水畲语与潮汕方言都保留着一些“土著越语”,如“寮”,是汉语的”简陋小屋”;“胡”,胡溜(,是汉语的“泥鳅”;“个”结构助词,略同于汉语普通话的“的”。
丽水畲语与潮汕方言都保留了一些先秦的词语。如,头发,两地话都叫“头毛”;驼背,都叫:忤逆,不肖,不听长辈劝示、劝告,都叫“忤逆”;酿酒剩下的渣滓,都叫;斟酒,两地都叫“酾”给予,都叫“分”;中午,都叫,“昼”;禽类的蛋或者圆的石头等,都叫“卵”;鸡的窝,都叫“埘”;看,都叫“睇”;用来祭祀的牲畜,都叫“三牲”等等。
丽水畲语词法的特点是单音节词多,有些词的变义用法,许多词由活用形式发展成为词义的转借和引伸、有些词变为畲语的专义,存在偏义址词,构词带有明显的“象形”、“指意”的色彩,一词多义、有些也是因为引申和比喻形成,把修饰、限制的偏词放在主词之后,词尾带有固定的腔调。也向汉语借词,尤其以通行的新名词为多,但大多数借词与汉语原读音有别,例如:“正经”读,“状元”读,“还原”读,“共产党”读,“结果”读,“社会”读,“北京”读,“电视”读。
丽水畲语名词常用词缀在前缀上,去掉潮汕方言的“阿”,保留了潮汕方言的“老、潮汕方言在亲属、排行、姓名之前都有前缀“阿”,而丽水畲语没有。共同的是都有“老”,如,曾祖父为“老公”;叔父为"老叔”;舅父为“老舅”等。名词常用词后缀都有“伙”、“鬼”、“田”、“头”、“公”、“母”、“客”等。
3.语法
丽水畲语与潮汕方言共同是以特定的语序、虚词和语感来表情达意的。常用反问句式表示肯定或否定、词序与现代汉语不同。如:谓语前置、宾语前置、定语状语后置、补语前置,及使动、意动和被动用法等等。
古代,商族的东夷语在中原与夏族语言和诸多原始方言融合后的华夏语是中原官话的雏形。以洛阳话为标准音的华夏语后来成为东周通用全国的雅言,进而发展成为扬雄《方言》提及的"通语、凡语①这种官方语言对畲语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说客家话”
20世纪50年代初,畲民识别调查中,调查组注重畲族作为单一的少数民族一般所必须具备共同语言,而不探求其本身具有的语言特征,对畲族语言没有进行全面深入地调查研究,认为“畲族有自己的语言”、“畲族基本上是以汉语客家方言为其共同语言”。继而语言学者在《国内各少数民族言系属概况简况表》中,把畲族与回族、满族列入“通用汉语文”,当时引起中央民族学院畲族学生的强烈不满。
1980年的《畲族简史》一书中写道:“畲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畲语和汉语的客家方言很接近,但在广东的海丰、增城、惠阳、博罗等县极少数畲族使用接近瑶族‘布努'语(属苗语支)。畲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通用汉文。在日常生活中,各地畲族皆通晓当地汉语方言。”①《畲族所说的客家话》一文云:“畲族使用两种语言:广东惠阳、海丰、增城、博罗一带的畲族使用的是畲语,属苗瑶语苗语支,约有一千人,占整个畲族人口的千分之四左右;其他地区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畲族,使用汉语客家方言”,“这种客家方言同现在使用的客家方言不完全相同,同汉语客家方言的分布也不一致,因此可以说畲族所说的这种话是一种超地区而又具有一定特点的客家话。我国少数民族由于同汉族长期共同生活和劳动,使用了汉语,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鲜见。随着民族的迁徙,脱离了原来的方言地区,在后来定居的地区又学会了当地汉语方言,并用它同当地的汉族交际,原来使用的汉语就成了本民族之间相互交际的工具。由于这种历史和使用的特点,常常使一种方言发生变化而具有明显的独特特点。畲族所说的客家话正是这种情况。”②进而有的加以引伸,运用逻辑推理得出“畲族没有自己的语言”、“一开始说的就是客家话”。引发了学术大讨论,进而引发其他问题。
这种观点产生的影响直到如今。③
许多学者、畲族干部群众反对上述观点:蓝周根在《畲族有自己的语言》一文中强调,畲族有自己的语言,不赞成“大多数畲族人所说的话是客家话”这一观点,并且认为即使是畲族同客家有共同的语言,也不能以语言接近就否定了一个民族的大多数人没有自己的语言。①雷先根在《畲语刍议》一文中认为,“我们应该把99%以上畲民使用的语言视为畲语,不因它接近广东汉语客家方言而不承认是畲语。这种语言之所以接近客家方言,那是两族文化互动、交融的结果。”②朱洪、姜永新在《广东畲族研究》一书中认为:“畲族有自己的语言,这从过去有限的史料记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大量实地调查中可以肯定回答。”并对畲族中只有广东的惠东、博罗等4县仍保留畲族的原生态语言的观点提出异议,指出:“居住于罗浮山、莲花山区的畲族,跟粤北南下的瑶族频仍交融,民族成份上互变共存,以至达到畲瑶不分地步”。“罗浮山、莲化山的畲语明显受到瑶语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延至凤凰山又消失殆尽。”“这是瑶族文化对罗浮山,莲花山畲族的渗透,以及两个民族在粤中的交融而致成。”③游文良一生对闽东、浙南畲语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在《论畲语》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罗浮、莲花山区的畲族从来源于湖南潭州,槃瓠王有六男六女的传说,使用属于苗瑶语族的语言等特点看,都跟凤凰山畲族不一样,而恰恰跟广东的瑶族一样;而且罗浮山、莲花山的畲族历来认为他们是‘瑶'而不是‘畲',这种自我意识也不同于凤凰山区的畲族,……据此,认为历史上罗浮、莲花山区的这支畲族可能就是瑶族的一支。”并提出罗浮山、莲花山区畲族使用的语言更接近瑶族语言而非古代畲语的遗存。在《浙江省少数民族志•浙江畲语》中进一步认为“浙江畲语含有古畲语底层、汉语客家话成分和现畲族居住地的汉语方言成分”。并指出“这种畲语是从古代畲语演变发展而来,它应是畲族的民族语言。”朱洪、姜永新、游文良都认为,现居住在广东凤凰山区以及福建、浙江等地绝大多数畲族使用的近似客家方言的语言才是畲族的民族语言,从而进一步阐明畲族只有一种语言。施联朱在《面向21世纪畲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中提出“有关畲族民族成份识别的几个余留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对广东罗浮山区增城、博罗,莲花山区惠东、海丰等县畲族民族成份质疑。其质疑主要从语言的角度提出的:广东增城、博罗、惠东、海丰4县有畲族一千多人,占全国畲族总人口千分之四,操“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语言,“跟苗语支的瑶族布努语炯奈话比较接近。”与占畲族总人口99%的、分布于闽、浙、赣、皖、粤东等地的畲族操接近于汉语客家话不同。“20世纪80年代,我与研究生雷玉虹(丽水畲族)调查了增城县的畲族,从文化特征看,增城的畲族与瑶族比较接近,语言相通,而与凤凰山区以及闽、浙、赣、皖等省的畲族不同。因而对增城等4县畲族的民族成份存疑,有必要作进一步鉴别。”
进入21世纪,语言学界则更注重对占畲族人口99%以上的畲族人所说的话进行调查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他们对畲族使用两种语言及其两者的关系、畲话的形成及其特性、畲语归属等问题,作了更广泛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并重视畲语本体的研究和探讨,并以此研究获得国家或省部级科研单位立项的课题多项,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及著作。张尚芳调查了景宁畲话后认为“我们不能说浙江畲话就是客家话,只能说它不完全是客家话。它吸收了五个层次的汉语方言,是汉语型的,音系上大体是客家话的,但并没有完全放弃本民族的东西,还有底层。”还指出“畲话音系中有些现象所反映汉语史时代比客家话要古老,因此把畲话说是畲族学的客家话,可能并不符合事实。”游文良在《畲族语言》一书中提出占全国畲族总人口99%以上畲族人所说的话就是本民族语言,并称之为“现代畲语”。指出现代畲语由三个部分组成:古代畲语的底层成分、汉语客家方言的中层成分和现代畲族居住地汉语方言或普通话的表层成分。并论证了现代畲语是从古畲语发展演变而来的。此论点较前又有了新的拓展,认为畲族语言自古以来就一直是一种独立的少数民族语言,从而否认畲族语言发展史上性质发生转换的事实以及过去大部分学者关于畲族有两种语言的观点。2001至2004年间,傅根清通过对景宁畲话比较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发表了《古全浊声母字今读情况》、《景宁畲话声母的超中古现象》、《景宁畲话语音系统中的粤语成分》、《景宁畲话尖团音分混现象研究》等有关景宁畲话的系列论文,认为畲话“是一种接近闽语而独具特色的汉语方言”。与徐瑞蓉、伍巍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俩在《长泰县磔头畲话的语音特点》一文中也指出,“磜头畲话与客家话的接近程度,远不如与闽方言密切。”而后傅根清又把景宁畲话与客家话代表点的声韵调作了系统比较,得出“客家话对畲话的影响是表层的、分散的,而不是深层的,更不是体系上”的结论。指出“畲话是一种古老的、非常复杂而又特殊的、以族群分布的、独具特色的混合型方言。”2000至2004年期间,赵则玲通过对浙江畲话5个方言点的调查和分析研究,首次对畲语、畲话、客家方言之间的关系作了比较明确的阐释。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以语音相似程度的高低作为判断两个方言亲属关系的重要标准,肯定了畲族语言发展史上性质发生转换的事实,否认占99%以上现代畲民使用的语言属于汉语客家话,主张把它作为汉语的一个特殊方言看待,是一种属于汉语系属的、与客家方言分立的少数民族人所说的汉语方言,可以称作“畲话”。并定性为比客家方言古老的、超地域分布的、与汉语方言关系密切的、历史层次复杂的语言。同时指出,这种畲话有进一步被“汉化”的趋势。2000—2003年间,台湾语言学专家张光宇及其弟子吴中杰,立项主持了关于畲族语言研究的两个课题:一是闽浙皖赣畲话及广东博罗畲语调查研究,二是广东潮安畲话调查研究,并且撰写了若干有关畲话的系列论文:《畲话的音节结构》、《广东潮安畲话调查研究》、《广东与浙江畲话之比较研究》、《畲话的介音问题探究》、《畲语和畲话的疑问词组》、《闽浙皖赣畲话和博罗畲语调查研究》、《畲话和客家话》、《畲语的正正重迭疑问句》等。提出:“畲语的语音系统和畲话相当不一样,词汇甚至词序也常见不同。纵使有零星的证据显示畲语和畲话彼此的关联性,我们仍必须强调:根据本文罗列的语言事实,畲话虽然和畲语及客家话都有关系,但畲话绝不等于是'客家话跟若干畲语残存成分的相加畲话的许多说法,既不同于客闽吴粤等汉语方言,又不同于畲语,可以说除了与畲语及客家话交迭的成分外,畲话各方言点间还分享着另一些共同性,这些是畲话所独有的特征吴中杰在《畲话和客家话》一文中认为:“尽管畲话和客家话有许多共通性,它们彼此之间仍存在着若干差异。但将畲话直接视为客家话的一种次方言,可能未尽恰当。”①上述半个世纪畲语研究的回顾表明,随着研究深入,90年代以来,结论越来越全面、正确:畲族有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有客家方言成份,但畲话并不等同于客家话,畲族说的并非是“客家方言”。当然,还可以从逻辑上分析“畲族没有自己的语言”、“畲族说的是客家话”观点存在逻辑错误。
首先,“畲族没有自己的语言”、“畲族说的是客家话”,是用不完全归纳推理得出的结论,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没有深入调查,有的甚至是根据他人的观点;或者是调查地点选在交通方便的公路边的畲汉杂居的畲村;为便于交流,被调查对象多数是从小就进汉族学校念书,后来一直从事教师职业、行政工作的干部;调查内容是调查者根据自己设计好的语言请畲民回答,不是问古代的词语,而问“人民公社好”一类现代词。于是就进行概括,得出结论。我们知道,语言这种社会现象,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它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早期人类从事简单的生产劳动,语言词汇也很简单,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语言词汇不断丰富、不断更新。畲语也不例外。现在畲民使用的语言多数是现代的共同语,或者是经过畲民改造过的共同语。这种共同语,不能代表原来的畲族语言。因此,这种田野调查,不但样本没有代表性,得到的不是原汁原味的畲族语言。况且,个别地方的调查,不能代表全部的畲语。
其次,语言分析过程中,只运用契合法和差异法,没有使用契合差异并用法。有的学者对畲族语言与客家方言的分析研究方法,是先从畲民所用的现代语言中,找出不同于汉语的词汇,再同客家方言比较,不同于客家方言的,才是畲语词汇,用了二次差异法。后用契合法,找出畲语与客家方言相同的词汇。再用剩余法,把相同的归到客家方言中,余下的才是畲语词汇。由于古代畲语词汇本来就不多,所以,余下的词汇就很少。于是有的学者就说,能找出几个畲语词汇,我们就承认畲族有自己的语言。其实,求因果关系要用契合差异并用法,也就是把畲语与客家方言相同的词汇,分别放到畲语和客家方言的各个语言区中契合。多数客家方言区中俱有的,少数畲族语言区中存在的词汇,那么就归到客家方言中;多数畲族语言区中俱有的,少数客家方言区存在的词汇,归到畲语中去。而不能把相同的,全部归到客家方言中去。如江西大余的“天亮”叫“天豁[tie33ho33]”,广东河源的“曾祖父”叫“公白[kon33pak3]”,“曾祖母”叫“阿白[a22pak2]”,“拔秧”的“拔”叫“瞒[man33]”,“看”叫“睇[tie33]”等跟福安畲语、浙江畲语义同音近。若说这些词是畲语吸收客家词,不如说是客语吸收畲族语词,因为,福安畲语所属各地畲话都有这些词,即99%畲民用这些词,且义同、音同,而客家话只有个别地方这些词的音、义与畲语相同或相近。
目前学界的研究基本上是用契合法、差异法在畲族语言中找客家方言,如果用契合法、差异法、契合差异并用法在客家方言中找畲语,那么,对畲族语言与客家方言的关系研究会更全面、更深入,更能揭示二者的关系。尤其是运用现代的概率演算等方法,不仅能定性而且能定量说明二者的关系。
再次,类比推理犯了“机械类比”的逻辑错误。逻辑上看,类比推理的结论是或然的、不具有必然性。如果不抓住事物的本质进行类比,往往导致“机械类比”的逻辑错误。在民族语言上,的确存在“我国少数民族由于同汉族长期共同生活和劳动,使用了汉语,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鲜见。随着民族的迁徙,脱离了原来的方言地区,在后来定居的地区又学会了当地汉语方言,并用它同当地的汉族交际,原来使用的汉语就成了本民族之间相互交际的工具。由于这种历史和使用的特点,常常使一种方言发生变化而具有明显的独特特点。”但畲族并不是这种情况,下面“相互交融”一小节中可说明之。
第四,畲族一开始说的就是客家话,这一论点是违反逻辑的;而“畲族有自己的语言”,却是逻辑推理得出的必然性结论。语言是种社会现象,语言与人的社会群体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随人的社会群体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消亡而消亡。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因语言是在劳动过程中,由社会的交际需要而产生的。人类的祖先在长期生存的劳动活动中锻炼了自己的大脑,改造了发音器官,具备了说话的能力,而且在共同劳动中又有了交流思想的需要,正如恩格斯所说:“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时,于是就产生了语言。语言离不开社会,社会也离不开语言,二者是相互依存的。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在互相交往中,都把语言作为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人们利用语言传送信息,交流思想,协调共同的活动,组织社会的生产,没有语言,社会便会停止,便会崩溃。社会的进步也离不开语言,生产斗争中经验的积累和传播都离不开语言。民族语言是在氏族语言和部落语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前面考古等资料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凤凰山区就有人类活动。在中原汉族没有进入闽、粤、赣交界北部之前,畲民已有相当数量的人数,社会发展水平许多方面不低于中原水平。
那么,在客家先民没有到闽、粤、赣交界北部山区,早在此生息数千年,人数如此之多,战斗力如此之强的畲民,如果没有语言,用什么来交流思想呢?不可能用汉族客家方言来交际,因为此时汉人没有进入此地,或者是很少汉人进入这个地区,更何况客家未形成,哪来的客家方言?!畲族人民肯定有自己的语言,斯大林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即令是最落后的,能够没有自己的语言,人种学不知道任何一个落后的部族,即令是比方说像十九世纪的澳洲人或火地人一样原始的或更原始的,能够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从目前畲族人民内部使用的畲语中找到其底层,根据“痕迹”来确定当时的面貌。始修于明弘治的《潮州府志》中,记载了当地畲族词汇:“火”叫“桃花溜溜”;“饭”是“拐火农”。李唐撰《丰顺县志》述:畲民“其土操土音,俗称为蛇罗语,极难异,今能操此语亦少。”可见,当时的畲语是存在的,也不同于如今的畲语,根据学术界的意见,称之为“古畲语”。
这里的推理是:任何部落一开始就有自己语言,畲族早在七世纪前就是一个强大的部落,所以,畲族在七世纪前就有自己的语言。如果畲族一开始说的是客家话,那么,客家话、客家应在畲民部落出现前产生;而客家话、客家晚于畲家二千年产生,所以,畲族一开始说的就不是客家话。
第五,畲族先民放弃了原有语言,用客家语言取代古畲语,也是违反逻辑的。畲家迁出凤凰山,已有1000多年历史,而且是迁进生产力更发达的福州、浙江、安徽等汉族地区,畲汉杂居,受到更为强大的汉语影响;封建统治阶级曾数次进行强行的语言同化,但直到如今,畲民仍然保留自己的语言。从广东的潮州到安徽的南部,畲民的语言都相通,保留共同的语言。难道畲族语言后来1000多年都不变,而在与客家相处的一段时间就完全丧失掉?这是不合乎逻辑的。而且部分畲民在唐初就迁到闽东、浙南等地繁衍后代,他们的子孙一直保留自己的语言。他们离开凤凰山区数百年后此地才出现客家方言。如果说,畲族说的是客家话,那么,他们必须回到凤凰山学会客家方言。实际上,回去学习客家方言,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两地相距数千里,不要说以前交通不便,难以实现,就是近年交通极其方便的条件下,浙南、皖南的畲民也没有几个人回过凤凰山,自然也谈不上学习客家方言了。
因此,雷阵鸣在《略论畲族与汉族客家在血统、语言及农耕等方面互动的“主客”定位》说:“汉语客家话最终是在畲语的影响下形成的,而不是畲族'放弃自己的语言①曹大明在《重塑“畲人”:赣南畲族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中也认为:众所周知,畲族人说的语言畲语,其实是客家话,所以部分畲族也自称客家人,据此有人认为客家人是畲族汉化,原本说畲语的畲族人接受汉文化后汉化了。
由于客家话和北方汉话的区大差异性,如果客家人是畲族汉化,那客家话一定就是古代畲语,不过,现实学术的研究中,一直存在将客家话(畲语)和赣语合二为一的讨论。因为客家话和赣语其实在所有的汉语族中差别是最小的,于至难于在学术上有个明确的分界线。
由此推论,现在江西自称汉人的赣语人,也有可能是畲族汉化,就算不是全部也至少占半数以上,否则很难解释现在所谓的江西汉人的语言不近官话反而极近客家话(畲族),以历史上畲族的地位低下,不可能隔空同化赣北汉人的。只能是占有绝大多数的畲语内混有少量的汉人,或者全部是畲族。
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已经形成标准汉语是汉语官话的正确论断下,赣语绝对不可能是南下汉人带来的语言,只能是畲语或者畲语受汉语影响下形成的新语言,江西汉人其实主体也是畲族。②
(二)相互交融
的确,畲族语言与客家方言声母、韵母有部分相同;畲语词汇中有不少和客家话相同;语法也有不少相同;初听,声调基本相同。这种相同,是“相互交融”的结果。
相互交融,是由于历史上在凤凰山区,畲家土著与中原来人友好相处,共同生活四百年,在这一时期,应该说,有矛盾、有斗争,但更多的是在同自然、同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中,共同合作,产生文化上互动、共生,这种文化上的互动、共生首先是语言上的互动、共生。这一时期,畲家操的母语是古畲语,客家先民操的语言应是中原古汉语及沿途吸取各地方言所形成的次古汉语。畲家与客先民共同生活、相互学习,古畲语吸收了客家人先民带来的次古汉语,客家先民带来的古汉语吸收了当地古畲语。
这种语言的互动,开始应是畲语影响汉语。
一是中原汉人是避难陆续进入这个地区的,开始迁入的汉人很少,他们的语言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对畲族发生重大影响。况且客家的起源也存在多种说法,主要的有“客家中原说”和“客家土著说”。客家中原说认为客家主体构成为来自中原的移民;而客家土著说则认为,客家共同体,是南迁汉人与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土著混化以后产生的共同体,其主体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土著,而不是少数流落于这一地区的中原人。嘉应大学的房学嘉先生通过考古学和田野调查等手段和方法,证明出“历史上并不存在客家人南迁史,客家主体是南方畲族。”房先生在其《客家源流探奥》一书中写道:客家是古越残存者与秦以来中原汉人互相混化而成的人们共同体……客家话的母语是闽粤赣三角地区古越族语。客家话中夹有相当多的中原古音,则是南迁的中原汉人带来的……历史上确曾有过一批批南迁客家地区的中原流人,但与当地人相比,其数量任何时候都属少数。台湾学者也认为,饶平客家人祖先是“性类徭僮”,即是经过汉化的“徭僮”。而事实上饶平客家人则有更多的古越人语言与文化留存,古越人后来在闽为“畲”,在粤为“俚”,两者在潮惠融合成“徭僮”。而且2005年古饶平县城(今三饶镇)发现一块古石碑,是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十一月初四日潮州府在饶平县城所立的《本府告示》碑刻,其中最明确的是提及饶平客家人祖先是「性类徭僮」。因此,有的专家说,这块石碑的发现,完完全全地粉碎了客家人是中原说的说法,它将客家人的先民是“徭僮”赤裸裸的完全现形。
历史上中原汉人来到闽、粤、赣交界的北部山区,多数学者认为是在两宋时期,在DNA中也得到证实。客家人父系DNA中,宋朝汉族血统占30%、秦汉汉族血统占10%、畲族03d血统占30%、越人血统及棕色人种血统各占10%;在母系DNA中,越人、汉族、畲族血统各占30%、棕色人种血统占10%。
斯大林分析语言的特征时指出,语言具有最明显的民族特点,即一个民族形成之后,由于历史传统、生活习俗、思维习惯、表达风格等特点,各民族语言具各自特征。它反映在民族生产、生活特点,保留和记录了本族人民的经验和智慧,也揭示了大量的本民族人民观察事物的方式方法,还有对他民族文化的见解。整个民族所有成员都时刻使用自己的语言。语言的社会性决定了语言的稳固性。这种稳固性,具有对强迫同化的巨大反抗力。少数中原来到此地的汉族人,只能是接受畲族的语言,他们学习了畲语。
因而,客家方言形成的时限,由最早的罗香林“五代宋初说”向后延。华东师范大学王东认为,“客家人之所以区别于非客家人,其中一个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语言。客家方言不仅是客家之成为客家的标志,而且也是客家民系自我认同的内聚纽带。也就是说,一个客家人之所以把另一个客家人认同为自己的属群,其最直接、也最简单的道理是因为他(她)也讲与自己的一样的客家话,而不是共同的地域、血缘或其他什么原因。正因为如此,以客家方言的形成与否,来作为客家民系形成与否的标志,应该说是没什么问题的。”“最早提到客家方言的应该是在明代”,其依据是,“明代嘉靖年间编修的《惠州府志》中有关方言方面的记载,可以被视作为关于客家方言的最早记录;还以同一时期编修的《兴宁县志》“方言”一目中所列举的方言特点加以证明。并根据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一书中关于汉语北方方言和南方方言声韵调的一系列演变现象的讨论,认为南方方言演变发生的时间基本上“不能晚于16世纪”,说明此时“客家方言已基本上割断了与北方方言的联系,而步入了独立发展的里程”。而因为“一旦客家先民的语言已完全与北方方言相分离,就表明客家方言已基本形成了”。因此,王东认为“客家方言的产生,当在15世纪至16世纪之间,即相当于明朝的中期”。
客家也在这一时期形成。客家研究院的李默《论客家的形成及民族融合》中认为:即说,明以前曾出现“客”的单称,也出现“畲”的联称。“客家”一词,作为汉族一支民系出现,应该是明正德间闽粤赣畲族大部分融化为客人之后,即入版籍,编里甲,纳租赋,输徭役,与齐民一体,正式称之客人。正德年间,“程乡盗起(畲民起义),众数万,钦至程乡,开谕祸福,其党伏,藉其丁壮老幼四千人,散遣之,使耕田筑,目其民曰新民”。《阳明集》载:“正德十二年十二月,剿横水(畲),广东程乡知县张哉统领部下新民、乡夫等搜剿”。明王朝在对畲族人民进行征剿的同时,对畲族地区加强封建统治,编里甲,促进山区生产,并兴文教设儒学。正德年间王阳明讨平广东的平远、长宁,平定湘头池仲容,乃立和平县(纯客语县);讨平江西横水,立崇义县(纯客语县);讨平福建汀州(纯客语地区)。以上地区的畲民起义,王阳明剿服始归化。此时,梅州及其邻汀州、虔州的畲族基本上归化为新民,融为客家。而星散的畲人,亦于其后融入客家。至此,以梅州为代表的客家民系亦告形成。①
二是闽、粤、赣交界的凤凰山区,自然环境、社会生态完全不同于中原,有许许多多的动物、植物、事物是中原没有的,而畲族此时对这些事物已有了自己的称呼;畲区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与中原也不同,中原汉族来到此地,随乡入俗,学习畲族人生产、生活方式。直到明代王守仁率兵镇压大帽山畲、汉农民联合起义时,还哀叹“处处山田尽入畲,可怜黎庶半无家”,“黎庶”当然是指刚到不久的客家,土著者是原来就有家的。林达泉《客说》即谓“凡膏腴之地先为土著,故客家所据地多硗瘠”。此时客家的农耕条件并无什么“优势”。自然在语言上,汉族人只有借用畲语语词。因此,对新的事物交流必需借助当地的名称。
三是语言的传承与母亲相关。南迁的汉人往往是男性,娶当地女子为妻。如今的福建人、客家人男性主要来自北方,而迁徙到福建等地的北方汉族中很少有女性移民,福建汉族多数是少数民族母亲生的。DNA检测也证明这一点。
复旦大学对南方各省(北方各省的Y染色体和线粒体的数据都接近1)血样的实际测定结果。
福建人Y染色体的相同率高达0.966,说明基本是北方汉族男性的后代。线粒体DNA的相同率很低(平均0.224),说明基本是南方少数民族女性的后代。综合两点,福建居民基本是北方汉族男性与南方少数民族女性婚配的后代。同时表明,迁徙到福建等地的北方汉族中很少有女性移民,福建汉族多数是畲族等少数民族母亲生的。①
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说“客家话在当地民间叫‘阿姆话',‘阿姆,与普通话的,母亲'同义,即客家话为母亲话……历史上散居于闽粤赣三角地带的少数原汉人跟当地古百越人等少数民族通婚,建立家庭,其语言、文化习俗自然跟随母亲的民族,此即客家话叫阿姆话之故”。这“母亲的民族”即畲族。陈晓红也说:“某些客家男人或频繁地外出经商,或攻读致仕当官等等,多长期在外,不过问家事,因此,家庭的农业生产劳动、生儿育女、养老扶幼以及一切家庭操持,多由妇女承担”。那么其子女当然是学说母亲民族的话。②
畲汉两个民族群体的语言互动、共生是从借词开始的。原来没有的事物的名称,各群体相互搬用;而一些各自有的词语,也因相互往来,逐渐先用畲、客先民同义词语。如,畲语称“什么”为“奚纳”,(i22n?5):称“摇摆晃动”为“湿啊湿”(it);称禽、鸟的翅膀为“劦刀”(iet5t?u33);称“天亮”为xau31(皞);称耘田除草即叫“薅草”(xau33ts'?u55)。客家话中的这些词,是从畲语中吸收去的,因这些词在唐宋时的“中原官话”中已经消失。畲、客读音相同的“知(道)”读t产、“蜘蛛,,读总%io33、“屐”读k3ia2、“盹”读k'in31”、“茄子”读k'io35、“嗅”和“鼻涕”都读p'i就、“要”和“爱”都读oi33、“被”和“分”都读pun33等词,来自畲语。
同时,中原汉语也影响畲语。这是由于中原的汉族人带来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带来了新的词语,这种新词,有的被畲族人接受下来,也有的进行着改造,变成畲语。如,汉语的“端午节”,各地的畲语都叫“五月节”,各客家方言点也叫“五月节”,根据畲语“五月节”的读音,是客家话“五月节”的借词;汉语的“剪刀”,各地的畲语都叫“zhandao”,各客家方言点也叫“剪刀”,根据畲语“剪刀”的读音,是客家话“剪刀”的借词;汉语的“苕帚”,各地的畲语都叫“guansao”,各客家方言点也叫“竿扫”,根据畲语“竿扫”的读音,是客家话“竿扫”的借词;汉语的“说”,各地的畲语都叫“讲”,各客家方言点也叫“讲”,根据畲语“讲”的读音,是客家话“讲”的借词;汉语的“跑”,各地的畲语都叫“zao”,多数客家方言点也叫“走”,根据畲语“走”的读音,是客家话“走”的借词;……特别是中原语言当时代表了官方语言,畲民对外交际需要用这一语言,中原语言影响了畲语。后来多数畲民迁居他地,余下的畲民,就慢慢地使用了客家方言。如今,闽西的畲族使用客家方言,就是如此。
学界也赞同“相互交融”的观点。1981年,詹伯慧在《现代汉语方言》一书中指出:“客家方言与畲族语曾经起过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作用1985年,陈宏文在《客家方言前途问题初探》一文中,认为“客家人多与当年的畲族同胞为邻,由于交往的需要,就吸收了一些畲族同胞的实用词汇。并凭自己带来的汉文化优势,把它融合过来。难怪有人把客家话误认为是‘蛮语①这“蛮”指的正是畲族。1992年,李默、张溥祥在广西桂林市举行的客家人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供的《论客家的形成及民族融合》一文,列举大量客家与畲族关系的事实,认为“客家的形成和发展也不例外,在特定条件下,中原汉文化在与当地百越土著文化的排斥和融合中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1994年6月,蒋炳钊在台湾举办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讨会上,宣谈《试论客家的形成及其与畲族的关系》一文,指出:“客家的形成过程,必须是入迁的汉人与当地畲族融合的过程”,“客家是入迁的汉人和当地畲族文化互动于闽粤赣交界处形成的一个新的文化共同体”。学者们的研究都表明,客家语言、客家的形成、发展是在与畲族的文化互动中形成发展的。
(三)丽水畲语
畲家在凤凰山区时,秦汉后语言受南下汉语影响,迁出凤凰山后,一直与汉族杂居,语言仍然受到当地汉方言的影响,因此,如今的畲族语言可以说没有所谓原生态的畲语。那么哪个地区的畲语有比较多的原生态成份呢?应是丽水畲语。
从语言的发展变化规律看,一种语言与不同语言接触时间越长、越多,那么受其影响就越大,保留的成份就越少;相反与不同语言接触时间越短、越少,那么其影响就越小,保留的成份就越多。丽水畲族入迁时间比福建、苍南、景宁较短,且人口数量多、居住集中,现有2个畲族镇(柳城、老竹)2个畲族乡(丽新、板桥)连成一片,其西北有三仁畲族乡,西南的碧湖、高溪、富岭等乡镇及城关畲族人口也较多。
闽东有的畲族干部、群众近年到此处交流畲语后,认为,此处比闽东原生态畲语保留得更多。
研究畲族语言的专家游文良认为,现代畲语分为9个区,其中浙南区是全国畲语方言的第二大区,里面还可分为苍南、景宁、丽水片区。丽水片区比苍南、景宁受闽东方言的影响小,比浙中、浙北区受汉语吴方言影响小。①
2015年10月出版的《潮汕方言历时研究》,是语言学家林伦伦先生化20年时间所写成,是对潮汕方言所作的纵向的历时性研究的总结。全书基本囊括了他迄今潮汕方言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而收录其中的“潮汕方言词法特点与历时研究”部分,是作者1994年获中国语言学界最高奖项——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吕叔湘奖)的系列论文。该书是潮汕方言研究的又一座学术高峰。第一至第四章的最主要内容,是对潮汕方言“是什么”、“哪里来”、“为何是这样”的学术解答。著作的开头说:潮汕方言,也叫作潮州话、汕头话、潮汕话,属于汉语闽方言的闽南次方言,所以,学术化的称谓应该叫作“粤东闽方言”。哪里来?早在原始社会,此地已有先民居住;春秋时期,这里居住的是百越支系。当时没有讲华夏语的居民,使用的是古台语。虽然当时楚语和吴越语已经形成,“但是,在当时,夏语和吴越语对远在天边的潮汕来说还是鞭长莫及的。汉人由闽入潮和由晋豫入潮,那都是之后的事。”“中原汉人入潮始于秦汉。”“当时楚语的影响是否延及潮汕地区呢?从历史事实和现代粤方言与潮汕话的系统看来,未发现有影响的迹象存在。因而,我们可以推定,春秋战国时期的潮汕先民所操的应该还是土著越语-----种属于壮侗语族支系的少数民族语言。”②潮汕方言文读系统的雏形在唐末才形成。
潮汕是凤凰文化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畲族的发源地、也是发祥地。一直至唐代中期,畲家还在此生息,秦汉之前的潮汕方言是畲家等土著的语言,如今畲族语言中与秦汉之前的潮汕方言相同的成份应是原生态的畲家语言。
1.语音
丽水畲语声母单纯,韵母发达,声调复杂,变调现象较普遍,音节多,在声、韵、调、音诸方面,与潮汕方言有许多共同之处。
(1)声母
丽水畲语声母有18个,比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少3个,而苗语有48个。
没有汉语普通话的翘舌音zh(ts)、ch(ts′)、sh(s)、r(β)四声母,因而没有翘舌音,凡汉语中的翘话音都读成舌面音或舌尖前音。如“主(Zhu)”读“t?y35”、“抽(Chou)”读“t?iu63”、“诗(Shi)”读“si22”、“热(rD”读“ni33”。另外,它仍保留古语中的鼻音声母n(疑母)。如“牛(niU)”读“nau22”、“咬(yao)”读“nai33”、“不(bu)”读“〓22”财(唔)。
今潮汕方言声母也是18个。
(2)韵母
丽水畲语韵母有60个,加上含有入声韵的如、〓、ia、io、i3、iai、iou、iau、iau、ioi,lau,iou及uo、y,计有76个,比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多37个。由A、i发展的韵母很发达,开合元音、齐齿元音多,入声韵也较多。韵母总数比《指掌图》多3个,入声韵与它相等。
如今“潮汕方言的韵母内部差异较大”。《潮汕方言历时研究》以汕头市话为代表,汕头市话韵母84个,比丽水畲语多8个。
潮汕方言六朝之前的古台语,无轻唇音[f-];无舌上音[ts-]、[tsh-];牙喉音相混。
(3)声调
潮汕方言与丽水畲语声调相同,都是8个。苗语是6调。苗语、汉语无入声。
潮汕方言8个声调
如今其他畲族地区的畲语基本上是4个声调,而丽水畲语8个声调。
(4)音节
丽水畲语音节有635个,比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多200个。635个音节中,与汉语普通话音节相同的只有200个,三分之二的音节是汉语所有的。它的声韵配合能度甚高,其中尤以p(35个)、p'(34个)、t(39个)、t'(32个)、n(38个)、1(46个)、k(53个)、k'(49个)为甚,只有f的能拼度最低(11个),而苗语音节结构与汉语相同。
2.词汇
丽水畲语词汇亦可分为实、虚词两类、十一种,实词尤为丰富。例如:蜘蛛——寮蛐,蜻蜓-------黄〔粘),蚯蚓--------蛇蜒,蟋蟀-------灶蛤
,跳蚤-------狗虱,苍蝇--------白蚊,青蛙---------〔蛙〕
,蜈蚣——蛐,海蛰——它,钉鳗——牛轭钉,鳗鱼---脯鱼鲐,鹅---------〔赤〕牛,鳅鸽-----------田〔担〕
,翠鸟---------刁鱼鹳,白眉鸟-----------寮公青,獾——猪豚,穿山甲——龙甲,松鼠——老鼠〔紧〕,刺猜---------(敏)。
丽水畲语与潮汕方言都保留着一些“土著越语”,如“寮”,是汉语的”简陋小屋”;“胡”,胡溜(,是汉语的“泥鳅”;“个”结构助词,略同于汉语普通话的“的”。
丽水畲语与潮汕方言都保留了一些先秦的词语。如,头发,两地话都叫“头毛”;驼背,都叫:忤逆,不肖,不听长辈劝示、劝告,都叫“忤逆”;酿酒剩下的渣滓,都叫;斟酒,两地都叫“酾”给予,都叫“分”;中午,都叫,“昼”;禽类的蛋或者圆的石头等,都叫“卵”;鸡的窝,都叫“埘”;看,都叫“睇”;用来祭祀的牲畜,都叫“三牲”等等。
丽水畲语词法的特点是单音节词多,有些词的变义用法,许多词由活用形式发展成为词义的转借和引伸、有些词变为畲语的专义,存在偏义址词,构词带有明显的“象形”、“指意”的色彩,一词多义、有些也是因为引申和比喻形成,把修饰、限制的偏词放在主词之后,词尾带有固定的腔调。也向汉语借词,尤其以通行的新名词为多,但大多数借词与汉语原读音有别,例如:“正经”读,“状元”读,“还原”读,“共产党”读,“结果”读,“社会”读,“北京”读,“电视”读。
丽水畲语名词常用词缀在前缀上,去掉潮汕方言的“阿”,保留了潮汕方言的“老、潮汕方言在亲属、排行、姓名之前都有前缀“阿”,而丽水畲语没有。共同的是都有“老”,如,曾祖父为“老公”;叔父为"老叔”;舅父为“老舅”等。名词常用词后缀都有“伙”、“鬼”、“田”、“头”、“公”、“母”、“客”等。
3.语法
丽水畲语与潮汕方言共同是以特定的语序、虚词和语感来表情达意的。常用反问句式表示肯定或否定、词序与现代汉语不同。如:谓语前置、宾语前置、定语状语后置、补语前置,及使动、意动和被动用法等等。
相关地名
洛阳市
相关地名
广东省
相关地名
海丰县
相关地名
博罗县
相关地名
惠东县
相关地名
凤凰山乡
相关地名
莲花山乡
相关地名
罗浮镇
相关地名
湖南省
相关地名
浙江省
相关地名
浙江省
相关地名
福建省
相关地名
丽水市
相关地名
增城县
相关地名
景宁畲族自治县
相关地名
长泰县
相关地名
台湾省
相关地名
潮安区
相关地名
江西省
相关地名
大余县
相关地名
河源市
相关地名
福安市
相关地名
福州市
相关地名
安徽省
相关地名
潮州市
相关地名
上饶市
相关地名
饶平县
相关地名
三饶镇
相关地名
张程乡
相关地名
横水镇
相关地名
兴文县
相关地名
平远县
相关地名
长宁区
相关地名
和平县
相关地名
崇义县
相关地名
汀州镇
相关地名
梅州市
相关地名
广西壮族自治区
相关地名
桂林市
相关地名
苍南县
相关地名
柳城县
相关地名
汕头市
相关地名
北京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