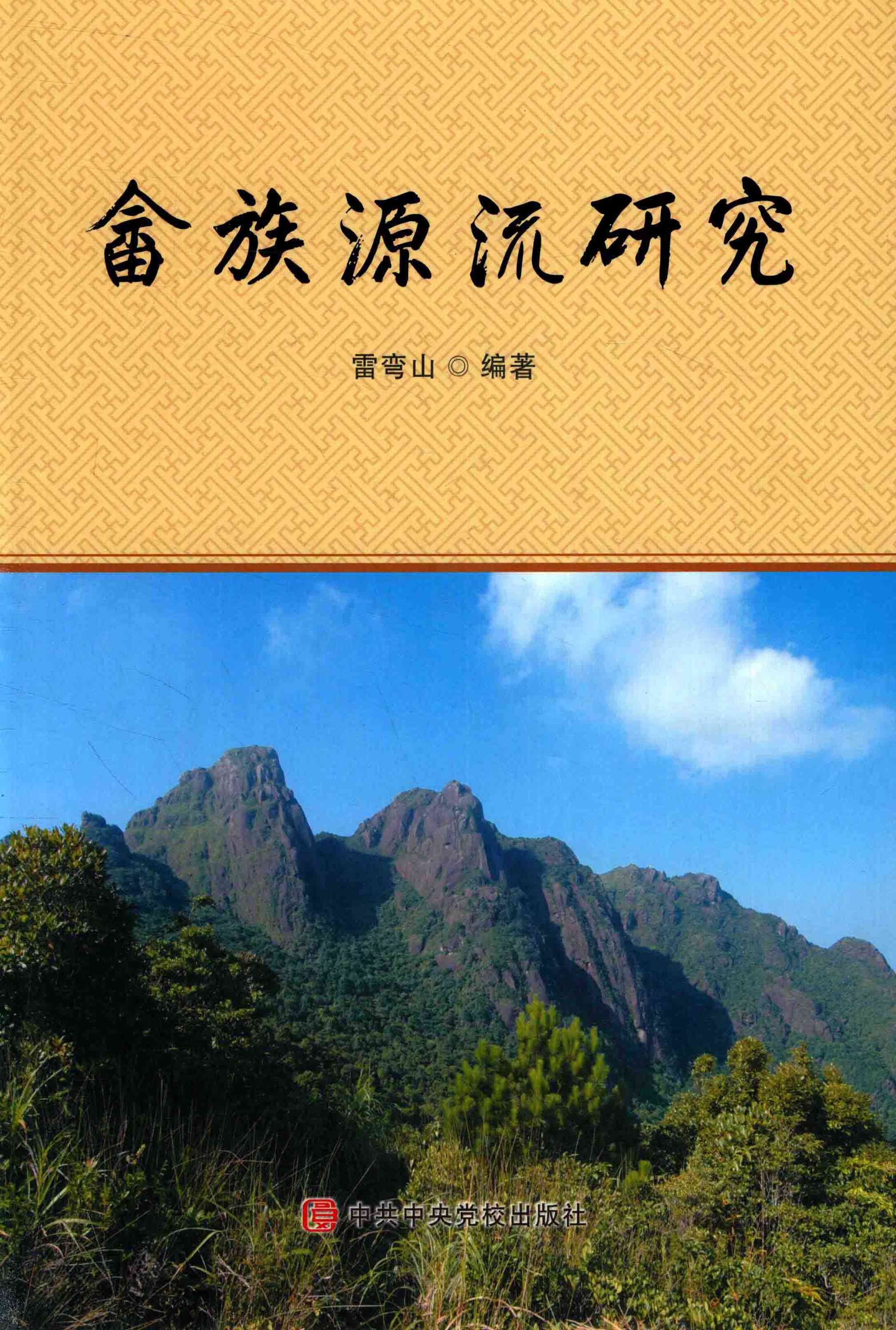内容
比较系统地用DNA技术分析畲族族源的著作,是2014年11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岭南民族源流史》一书。该书对“岭南”的鉴定是“指南岭山脉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和南海诸岛。”但书中专门写了畲族的族源,书中许多数据很有价值,许多观点给人启发。鉴于书的最后一篇即第四篇是“结语:史学与基因的交融刚刚开始”,因此,对认定畲族“分子人类学基因分析的裁判:畲苗族群”,①进行讨论,有着不同的解读。我们认为,此结论根据DNA工具得出,但对照DNA工具,及他们的观点,存在自相矛盾,需要重新比对、解读。
(一)自相矛盾
该项成果说,浙江景宁的畲族与广东连南的八排瑶的Y—SNP“距离比较近,而与大部分的瑶族距离远些,与布努群体则更远。看来起源上畲族与广东西北部的八排瑶有关系。
更明确的关系要通过STR的网络结构来判断,特别是苗瑶的特征单倍群M7的STR结构。”
在STR结构中,“畲族的主要类型也非常靠近中心位置,这说明畲族中的M7十分非常古老,应该是一种原生成分,而不是通过交流而获得自其他民族的。八排瑶与苗一布努类的关系很密切,与瑶族显然比较疏远。畲族有与八排瑶的联系,也有与苗和布努的联系。现在唯有广西贺州市鹅塘、沙田两个镇居住着土瑶,有6000多人,与广东连山的八排瑶相距比较近,在起源上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畲族应
该来源于苗一布努一八排瑶的类群。”①根据其这一论述,就不应该得出“畲族应该来源于
苗一布努一八排瑶的类群”,因在“在STR结构中,畲族的主要类型也非常靠近中心位置,这说明畲族中的M7十分非常古老,应该是一种原生成分,而不是通过交流而获得自其他民族的。”“对各个高频的单倍体做时间的估计,发现中国南方单倍群B,F,M7,R等大约5万年前就形成了,而发生族群分化的分支的年龄都有在2万年左右。”“八排瑶与苗一布努类的关系很密切,与瑶族显然比较疏远。”与瑶族大群体距离远,那么就有可能广东连山的八排瑶是畲族、或者与畲族有过融合,因连山靠近凤凰山。离布努群体则更远,就更不能归类于布努群体。
(二)方法错误
出现这一“自相矛盾”,导致结论的错误,重要的是方法错误。
1.与DNA方法背道而驰
以DNA这一遗传物质作为依据分析民族的起源,这是唯物主义的方法,是很好的科学方法,是此书的特色,也是科学。DNA方法是先比对、分析、解读数据,然后根据这些数据,结合历史文化,确定族属与关系。他们原先也是这么进行的。如在第一章《基因研究的悄然引入》中,列举了2002年李辉、侯井榕、杨宁宁的《广西六甲人来源的分子人类学分析》一成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县境内的古宜镇凤尾寨、周坪乡的马湾屯、下林江和溪脑屯的六甲人,人口约为三万多,操使六甲话,语言学界有不少学者认为六甲话归属于平话。六甲人有着不同于当地的侗、苗、瑶、壮及其他汉族群体的习俗。在民族识别过程中,三江六甲人于1952年曾经申报过“六甲族”;榕江的六甲人20世纪80年代以前也一直要求承认为少数民族,最后都被确认为汉族。很多的六甲人现在还认为他们不被承认为六甲族是因为人口太少了,而他们又“客不客,侗不侗”。于是研究者采用DNA工具进行分析。采集32个无可查亲缘关系的正常男子的血样。再经详细的调查排除掉其先祖中有侗族等其他民族的个体5个,研究的六甲人个体共27人。当中包括有侯、谢、荣、曹、吴、程和杨等姓氏,其中前四者是包括在六甲人的十二大姓中。结果,各姓氏内部的Y染色体单倍型并不一致。六甲人有的Hl、H5、H6、H8在各地汉族中是较普遍,而H11在南方汉族中也有。在单倍型种类上,云南、浙江、江苏、江西所含的种类都能涵盖六甲人所有种类。在各单倍型的频率上,六甲人与福建汉族最相近。把六甲人和各地汉族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9个所占信息大于0.1%的主成分,因此,六甲人的遗传组成与汉族没有区别。说明六甲人虽然文化上较奇特,但血统上还是汉族来源,是汉族的一个支系。然后结合历史文献、民族志等资料,他们可能源福建。DNA技术分析与历史资料一致。①
还有对汉族客家人的分析也是如此,是从父系遗传的Y染色体SNP的主要成分分析福建客家男子,发现客家人数据结构中汉族结构占80.2%,类畲族结构占13%,类侗族结构占6.8%:各族的M7个体Y-STR单倍体型的网络结构分析,发现客家人中类苗瑶结构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湖北,二是来自广东。客家人之类侗族结构可能来自江西土著干越。客家人母系遗传的线粒体RegionV区段9bp缺失频率为19.7%,mtD-NA与畲族很近,不同于中原汉族。单倍体暂缺。根据地这些结果,李辉认为,客家人的主要成分应是中原汉人,畲族是对客家人影响最大的外来因素。②
对畲族族源研究,本应也如前两者一样,是通过畲族的DNA与其他民族DNA进行比对,看其与哪个民族比较接近,然后确定其相互关系。然而该著作还是与原先那些传统研究范式一样,物质与意识关系的错位,不是用物质说明意识,而是用社会意识来说明社会存在。此著是先定其语言,把畲族语言归类于苗瑶语,然后与苗瑶比对DNA,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在逻辑上,其实结论已经隐含在前提中了,不用比对DNA,自然畲族源于苗瑶了。
这也违背了他们自己的初衷。该著作的第二章的开头云:“通常对于群体的分类主要是基于语言、文化和体质特征,再结合地理位置来进行的。这种群体分类方法简单、明了。然而,这种简单的群体归类方法多少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如果再加上一些人为因素或政治因素的介入,群体的定义就会越来越不精确,致使很多群体的生物起源、迁徙等到问题变得愈加模糊,这无疑给人类学、群体遗传学等学科的研究和发展带来一定的制约甚至误导,因为群体是遗传学研究的基本单位,只有定义或划分了群体,对许多问题的研究才能继续进行,但很难知道基于这些标准的分类在遗传学上是否合理。”①
2.样本数量过小
得出这个结论的主要样本来自浙江景宁的畲族。浙江景宁虽然是畲族自治县,但是景宁的畲族人口只有一万多,占全国畲族总人口的比例较低,不是畲族人口最集居之地,且该成果只用56个畲民样本进行分析。广东连山的八排瑶的人口占全国瑶族的比例更低。所以其结束语承认,“至于运用基因分子所得出的结论,因为样本选择的数量、广度及代表性因素的影响,也有待进一步科学验证。”②该成果第四篇《结语:史学与基因的交融刚刚开始》亦云:“但一方面分子人类学对岭南民族的研究还有空缺或样本不足等问题,如对瑶族分子人类学研究,还没有做到对瑶族五六十个支系进行全面的基因分析,对汉族平话人十几个支系亦然,这就影响对岭南民族源流的全面评价,从而造成对岭南各民族迁徙及演变历史进程的探究显得比较单薄。另一方面民族史对岭南各民族源流的研究在许多问题上又一直纷纭缠绕,在吸收分子人类学成果的过程中往往难以对号,难以取舍,难以贯穿。”③然而,书中还是取学界传统的一说,进行对号、贯穿,于是造成畲族等民族源流上的不科学。如果不是从语言出发,而是从地域出发,把畲族归类于“百越”、南岛语族,而不是归类于“苗蛮”,那么在DNA中比对遗传基因,共性会更多,自然结论更科学。
3.没有注意到各民族在历史上是不断流动的
用DNA遗传信息来确定个体、特别是父子之间的关系具有近100%的正确性。但是用来确定民族之间的遗传关系,不是个体间关系那么简单。正如该书开头引用费孝通先生1993年在《关于中国民族基因的研究——〈中国人类基因组〉评审研讨会上的发言》,所说:
3月初,我收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寄来的“中国不同民族基因组比较研究"的项目指南,我觉得研究目标中所提出的研究旨趣,诸如为人类进化和我国各民族源流、迁徙和划分提供生物学依据,无疑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这一项目所涉及的背景研究,自然也离不开人类学与民族学及其它社会科学的配合。
中国大地上历史的沉积、文化的积累、现代社会的投射,有过去历史形成、发展的很多复杂的过程及现实基础,作为中国社会的不同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其生物基础也有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基因研究可以对其复杂性有个基本的认识,其研究很有用处。
这种复杂性是极不平衡的,存在于区域之间,也存在于区域之内,有差别也有类同。中国历史上民族的分合过程及现代民族之间、民族内部的交流与整合,正是这一复杂性的典型体现。下面我提几点看法,仅供参考。
生存在中国土地的人最早的情况如何?这自然涉及到人类的起源。世界人类的起源并不是一个源,而是多源的。中国目前所发现的各进化阶段的人体化石,可以建立较完整的序列,说明中国这片大陆应是这很多源的一个。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人类化石为元谋人,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70万年左右,一般认为人类的分化即不同人种的出现是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目前,我们习惯用的人种分类是以1950年7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种宣言》所确定的蒙古利亚人种、尼格罗人种和高加索人种,分别称为“黄种”、“黑种”、“白种”。60年代以来,盛行地理分类法,仅以表征特征特别是肤色笼统的人种分类,常为区域性群体或区域性种族集团(EthnicGrouporEthnicstock)所取代。就是强调人类群体的区域性特征。
我在清华研究院结业时写了两篇论文,其中之一是《朝鲜半岛人种类型的分析》,这是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此后,也应当时驻北京的32军之约,调查该军体格,并对监狱犯人的体格特征进行分析。1935年与前妻王同惠女士去广西调查,我侧重于对当时称之为“特种民族”,即苗、瑶、侗、壮等少数民族的体质测量。我的这些研究,受到了我的俄籍导师史禄国教授的指导。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他把中原人的体质特征主要分为“a、β、r等若干种类型。华北、西北一带以a型为主,东南沿海到朝鲜半岛以β型为主,华南有较多的r类型。凭我的记忆说①,a型的人一般体高在1.60米以上,头型指数在70左右。面部特征表现为较细小的眼睛、宽额、扁平的鼻子、黄色的肌肤、宽阔的下巴、粗而长的头发;β型身高平均在1.60米以下,1.50米以上,类型指数在80左右,额部长而圆、鼻梁并不挺;r型,身高平均在1.50米到1.60米之间、长方型的脸,但双颊丰满、额长而宽、鼻梁不高、眼睛小、鼻端不尖稍圆。各类型的特征须查史禄国的原著。在此,我想把这三种类型的体质特征,和民族历史的迁徙联系起来谈几点看法。
中国各民族在历史上是不断流动的,而这些流动有它总的历史趋势。早在史前时代作为集团单位的人类群体就已存在,如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及甘肃青海的齐家文化之间的关联性。特别是陕西龙山文化经过宝鸡、天水,直接影响着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其它新石器时代文化区中各类型也反映了不同群体之间文化的传播、交流、汇集的过程。此种文化上的交流,在体质特征上也应当有所反映。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里,总的来说是北方民族的南下或东进,中原民族的向南移动,沿海民族的入海和南北分移,向南移的又向西越出现在国境。这一盘棋看清楚了,有助于我们的研究的展开。
在中国历史上,夏商周可谓东方β型与西方a型人种的第一次大汇合,发端于后称的羌戎之地的a型人,从夏开始向东进入关中西部,但其文化低于东方,实力强于西方。西方集团随后通过其军事力量,控制了东夷集团的齐鲁之地,作为β型的东夷集团子民,一部分β人开始了漫长的民族迁徙,其流向一部分进入朝鲜半岛,一部分分为两支,一支成为吴越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支为东夷中靠西南的一支,他们生活在淮河和黄河之间,这一批人,向长江流域流动,进入南岭山脉向东,在福建、江西、浙江的山区和汉族结合的那部分可能是畲,另外有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带,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的可能是苗。
在我前面提到的,《朝鲜半岛人种类型的分析》中,我看到β类型占的比重较大。1935年我所作的苗瑶等体质调查结果认为,苗瑶在体高和头型指数的系联表上所处的地位颇近于朝鲜半岛及华东人。在华南沿海地区的居民很可能有来自海上的r型,与吴越系统的β型相混合。上述民族集团的移动的路线,在人类学、民族学界并未定论,如果能结合不同民族基因的研究,把a、β、r等各种类型的特点找出来再进行比较研究,将有助于中国各民族人种问题的解决。
在对不同民族基因的研究中,我想在宏观上还应把握中国各少数民族历史和现状。我曾就此写过一篇“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对中国民族的变动及分合过程作了较为概括的研究,可供参考。在此,我想就操作层次提出一些意见,中国境内的民族集团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农牧接触的多民族走廊,然后为云贵高原和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其中不同区域内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似性及联系性要比不同区域之间不同民族的相似性与联系性多。此种特点在近年来的一些对少数民族的体质测量数据中也能反映出来。如彝族和藏族,男性头长的平均数最大为189.45和190.9,蒙古和维吾尔族分别为180.9和181.73。苗瑶侗族分别为1849、184.58、184.30;头型指数,彝族、藏族分别为78.52、79.94;蒙族和维吾尔族分别为84.25、84.68;苗瑶侗族分别为81.80、81.27、81.96②。其它体质测量数据也反映了这一特点。这与同一历史民族区内民族集团的频繁往来,关系甚大。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最好是以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区域进行研究。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中国境内的有待进一步识别的人类集团。
50年代,我们搞民族识别时,当时上报到中央的民族名称有400多个。由于历史原因有些也不是单一民族:经过二十多年的民族识别工作,我国多民族大家庭的构成基本上是搞清楚了,但还有些余留问题。现在已经提出要求识别的有:四川“平武藏人”,西藏东南部察隅县的僜人及南部定结县及定日县的夏尔巴人;云南省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的苦聪人以及还有一些不大为外边知道的本人、空格、三达、阿克、布夏、布果、贫满、等角、卡志、巴加、结多等人。这些问题大多是“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疑难问题。
最后,我们还应考虑不同民族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因为这种文化水平也影响到他们的孤立和流动较小的特点。
中国在解放前还有一部分少数民族保存着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他们主要分布在云南边疆地区的独龙、怒、佤、傈傈、布朗、景颇、崩龙等族,此外还有居住在内蒙古、黑龙江一带的鄂伦春、鄂温克和赫哲族,以及聚居在海南岛的部分黎族(五指山区内)。基本上属于这一类型的一共大约有60万人,现在这些民族都发生了剧烈的文化变迁,但其仍保留着一些传统的基调。目前,可以说在中国境内完全与外界隔离的民族单位是不存在的,但相对封闭的民族集团如具有“语言孤岛”之称的一些民族单位还是在一定地区内存在。
总之,我们在进行民族基因的研究中,要多考虑不同民族的自然、人文特点,同时还应考虑来自各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与健康、疾病医药的关系。我相信这一研究,除自然科学的意义之外,在学术上和实践应用上,也是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有力推动。
衷心希望这一研究能取得期望的成绩!
注释:①我在清华研究院的论文因战乱在搬迁中遗失。②可参考《中国人体质调查续集》,上海科技出版社,1990,第1—46页。
此文由当时跟随费老读博士生的麻国庆整理而成,为纪念费先生,麻国庆博士把这篇讲话发表于2005年《开放时代》的第4期上。
虽然该书开头全文引用费孝通先生的讲话,但是书中却没有根据其讲话进行分析。
“中国各民族在历史上是不断流动的”、“我们在进行民族基因的研究中,要多考虑不同民族的自然、人文特点,同时还应考虑来自各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与健康、疾病医药的关系。”用这一观点看,用DNA来分析畲族族源的《岭南民族源流史》,认定“分子人类学基因分析的裁判:畲苗族群”,①结论的不科学。正如该项成果鉴定专家的《意见与建议》所说:“在该项成果研究中,太过于倚重分子人类学。分子人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在人类学起源研究中还处在探索阶段;人类起源于非洲说也只是其中一说,况且上古人类与中古人类以至近代民族非是直线传承,其间的空间跨度相当漫长,因素也十分复杂,仅凭现代的人类基因分子来断定其与上、中古乃至近现代民族关系,有简单化之嫌,其观点必然会引起民族学界的争鸣。”①我们知道,历史文献上,南方少数民族部落长期被称谓为“蛮”,特别是苗瑶畲不分,书中也说“汉文史藉往往把畲族称为‘瑶人’或‘畲瑶’,有些地区的畲族也自称‘瑶人'或‘瑶家';分布在粤东的操苗瑶语族接近苗语支(即瑶族的‘布努'方言)的部分畲族,在海丰、惠阳两县被汉人称为‘畲人',但在增城、博罗两县却被称为‘山瑶'”。②从民族成份认定上看,20世纪50年代民族成份认定时,各村落主要根据自身认同,没有DNA技术,导致有的不一定科学。从地域上看,广东增城、博罗、连南等地是属于畲、瑶民族结合板块,不排除历史上民族融合。该成果的一项重大突破是“侗水人群约8000年前发源于福建厦门、广东汕头一带,后来可能由于政治压力向西北方向迁徙”。那么同样,瑶族有可能其中一部分是从凤凰山区迁徙过去的后再融合而成,因此,其DNA与其他瑶族不同,而与畲族有相同之处。
书中另一比对是线粒体DNA的多态性。“线粒体DNA的多态性也能体现出群体的特性。我们继续观察浙南这两个民族的线粒体DNA的单倍体情况。把线粒体单倍群大致分成了南北的两个类群。这两个类型都明显多于北方类型。这说明畲族是南方原住民族,而浙南汉族的母系成份中留有比父系更多的原住瓯越成分。”“非常特别的是畲族群体中有很高频率的Fla单倍体,这在其他民族群体中都是很少见的。Fla是一个古老的单倍体,在南亚语系的群体中就有已经存在,并且流传到了其他各个语系的人群。从网络结构中,笔者发现畲族的多态性并不低,其单倍体散布在网络结构的几个角落,这就说明畲族的Fla并不是瓶颈效应造成的。”③线粒体DNA的多态性,特别是畲族群体中有很高频率的Fla单倍体,这在其他民族群体中都是很少见的。Fla是一个古老的单倍体,在南亚语系的群体中就有已经存在,并且流传到了其他各个语系的人群。畲族更不能判断为“畲苗族群”,而应是南亚语系族群。
4.语言归类错位
把畲族语言归类于苗瑶语,仅仅采用学界的一种看法,而且是畲族人一直反对的看法,其实从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看,这个归类是错误的。
畲族语言也是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的认为是“畲族讲的客家话”,有的认为“客家讲的畲族话”,把只占畲族人口不到1%的1000人的增城、博罗的畲族,讲苗瑶语的作为畲族,而把占人口99%以上畲民作为“越化”、“汉化”者,多数学者、特别是畲民不认同这一种观点。占人口99%以上畲民归纳到1%讲苗瑶语中,逻辑上大前提不正确。因而,犯了“大前提虚假”的逻辑错误。
也没有考虑到民族认定的实际。广东增城、博罗的畲族,自称是瑶族。1955年《广东民族识别调查》中云:“增城、博罗两县自称‘贺爹',具有盘瓠传说和姓盘、蓝、雷、来的人却认为是‘瑶’,他们从未听老辈说过自己是‘畲’。1951年增城下水村来金德作为‘瑶族'代表去参加少数民族参观团,当时遇见海丰畲族代表,海丰畲族代表说:‘我们都是畲,你也是。’来金德就说:‘我不是,我们不来这里时,人家都是叫我们做瑶族的,你叫畲就叫畲,我们是认瑶族。’由此可见他们是很坚决的要称为‘瑶’。”“罗浮山区的群众说他们从祖公一直相传下来都说自己是‘瑶’讲的是‘瑶话’,族谱都是‘瑶人’,历代受瑶官统治,只向瑶官纳税,瑶官印上还写有‘增、龙、从、博抚瑶府’字样,解放前被被汉人称为‘山瑶佬'、‘山瑶仔'、‘瑶佬’、‘瑶仔’,他们使用汉语时亦自称为‘瑶人',所以他们认为历代相传是‘瑶',不是‘畲'。”“现乡干部及‘老大'蓝火桂、蓝石金提出意见说:畲族是政府说的……发土地证及普选时所填的‘畲族'也是别的同志写的,我们自己的祖公是'狗头王',又拜盘古王,是‘山瑶',不是‘畲',是‘瑶族',不是‘畲族’,要求政府将名称更正为‘瑶族'。”“对于连南瑶族他们认为虽然服饰讲话不同,也没有关系,姓同就是自己人,是同族。”①因此,畲民识别调查组主要成员、今中央民族大学施联珠教授认为,他们不是畲族,应认定为瑶族更合适。因而把这部分畲族作为畲族的样本也不恰当的。
5.与原有成果矛盾
李辉于2002年第4期《广西民族研究》发表的《百越遗传结构的一元二分迹象》中说,“最新的分子人类学材料——Y染色体DNA能对民族系统进行精细的分析。百越系统被发现与中国的其他系统差异很大,而与南岛语系民族(马来系统)特别是台湾语族群体相当接近。”“这些群体的Y染色体遗传结构体现出相当大的一致性,而与其他系统中研究过的群体完全不同。他们都有大量的M119、M110或M95、M88突变,而外族极少有这些遗传标记,与百越接触少的群体则没有。”“已经研究的百越群体显示出遗传发生关系和语言文化类型的差距,这与百越的整体认同和地域分化有关。”文章认为,“百越民族的起源问题。最初从非洲来到东南亚时,百越和南岛民族可能是同一个群体。而后百越民族北迁至广东,南岛民族南迁至马来。两者分开后分别发展成两个系统。”
(三)属南岛语族
从民族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与民族语言学的新证据、该书的DNA证据都表明,“南岛语族”与东南土著同属于一个人文系统,学术文献中的东南土著与“南岛语族”间并没有真正的文化内涵与族群系统的“差别”。该书表中(本书上页表)比对也指出,“畲族群体中有很高频率的Fla单倍体,这在其他民族群体中都是很少见的。Fla是一个古老的单倍体,在南亚语系的群体中就有已经存在,并且流传到了其他各个语系的人群。”因此,把畲族归类于南岛语族进行比对、分析,更科学。
“南岛语族(Austronesian)”即“马来一波利尼西亚语系”(Malayapolynesian),其中包括近千种语言,使用人口在100万以上的语言最多不超过20种,其余都是小种语言。
南岛语系地理范畴分布在南太平洋到印度洋上的百多个岛屿,这些岛屿多数人口稀少,东至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西跨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北到台湾岛北端,南到新西兰南端,主要居住地区包括中国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等地。南岛语族主要包括马来人(包括台湾高山族)、密克罗尼西亚、美拉尼西亚人、波里尼西亚人等几大族群,总人口达2.7亿,是一个十分庞杂的民族文化体系。
考古学方面看,南太平洋诸岛人来自中国东南沿海成为民族考古学者的共识。美国历史学派人类学家拜雅(H.0.Beyer),在东南亚与大洋洲土著民族文化的调查研究上享有盛誉,他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坚持菲律宾群岛地带做田野考古与史前文化的跨地域比较研究,是菲律宾考古的主要奠基人。其学生林惠祥教授运用拜雅及其同辈们的考古学研究,提出了马来民族起源于中国大陆百越系统的观点。厦门大学陈国强、蒋炳钊、吴绵吉、辛土成等,列举了考古与民族志材料中古代越族和东南亚民族共有的有段石锛、体质、语言、断发文身、缺齿、干栏、食人猎头、崖葬、洪水传说等为源流关系的主要证据,并从文献资料寻找越族三次向东南亚迁徙的事件,即楚灭越、秦统一岭南、汉武帝平两越等历史史实,延伸和发展了导师林惠祥教授观点,《百越民族史》一书认为,“早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百越民族的先民文化和东南亚各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关系就很密切,后来,越族曾数次南迁,特别是我国东南地区的越族,从大陆经台湾南迁进入菲律宾等地;在西南和南方的越族,也南迁进入印度支那等地。南迁的越族和当地土著一起,融合发展成为现在的东南亚民族。”徐松石先生出版的《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阐明了东南亚的“马来民族,缅甸民族,越南民族,泰民族和高棉民族等”,“他们的祖先都是由中国移民而来的。古代的中国南方住民,好像潮水一样,继续冲进这个区域。”
奥地利海因•戈尔登也根据中国和波里尼西亚都有段石锛的事实推断大洋洲的古文化有些是起源于中国的,主张东南亚史前文化和种族来源的北来说,认为新石器时代便有一种使用澳亚语(Austroasiaticspeech)而体质上属于蒙古利亚的民族迁移到了印度支那、华南大陆沿海、台湾、菲律宾、苏拉威西。日人鹿野忠雄也认为,波里尼西亚的有段石锛或者是由华南的民族及文化移动而传到,当时华南仍有土著民族,华南古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不但对东南亚、甚至对波里尼西亚都有关系。
2002年11月,凤凰山文化区的东山岛大帽山遗址开始首次发掘。这次发掘的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年代距今4300-5000年之间,位于东山县陈城镇大茂新村东北约1公里的大帽山东南坡。参加挖掘的工作人员有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和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的教授们,还有来自福建博物院和台湾中研院的研究员们。结果夭天都有发现:用来造船的原始工具——石镑、石箭镰、石球、凹石、各种纹饰的陶器、陶片、纺轮、骨制品和数不清的鱼骨、贝壳等等。夏威夷大学的罗莱教授说:“这里的石器无论是器形和制作手法,都与南岛语族的波利尼西亚石器十分相似。”而平潭岛的“壳丘头遗址”发现了目前最早的有段石锛,有距今6000年左右的历史,所以目前的国际考古学界和中国的考古学界就共同的把壳丘头当作是南岛语族最早离开原乡的起点。在对出土的石镑做了成分分析后,结果表明,绝大部分石镑的原材料竟来自澎湖列岛!原来生活在这里的原始居民,早在我们可以想象之前,就驾舟出海、渡过台湾海峡,频繁地来往于两地之间,进行双向交流。
来自哈佛大学的学者焦天龙也介绍说:“你看,这些陶器与澎湖列岛上锁港遗址的陶器有很多的相似性,而且我发现它们与台湾本岛某些遗址的陶器也惊人地相似。”尤其是在众多的出土文物中,有着大批红色的陶片,即便已经埋藏了五千年之久,今天看起来仍然是嫣红鲜艳。更是因为它看上去与在万里之外太平洋的小岛上出土的“红衣陶”如出一辙。而“红衣陶”是一种先抹一层红色化妆土再烧制而成的陶器,一直被认为是大洋洲新石器时代的“拉皮塔文化”居民群体的独特陶器。
南岛语族的许多岩画,如美拉尼西亚岩画中放射状图案和人体及足印,与东山的东门屿上发现的相类似。用放射线来表现太阳的光芒,是东山与美拉尼西亚岩画的共同特征,别无二致,同样反映了一种强烈的太阳崇拜意识。东山岛上还发现了不少的“祭祀穴坑”和“足印”岩画,南岛语族许多岛国上的岩画,都可以在漳州东山找到它们的联系。
民族学方面看,南太平洋诸岛上的居民都声称自己的祖先来自“北方的一个大岛屿”。有关权威专家研究表明,这些属于南岛语族的居民起源应该“位于中国台湾、澎湖列岛和东南沿海一带”。
体貌亦相似。从体质人类学上来说,南岛语族的个子比较矮小,比较黑,而福建沿海人一般都个子比较小,历史文献中记载凤凰山区早期有“小黑人”,有着相似的外形。2005年,遗传学家JonathanFriedlaender为了找出南岛语族在遗传学上的共性,对太平洋地区的41个族群中的952个个体进行研究,他分析了687类基因指标,既包括线粒体DNA,也包含Y染色体。分析结果显示,玻璃尼西亚人与台湾原住民的基因联系密切。这一结果表明,和台湾隔海相望的中国东南沿海是南岛语族的基因发源地。
福州大学闽商文化研究院院长苏文菁教授介绍说“从语言学上讲,有很多语言的基本词汇和语言结构是基本相似的”。厦门大学邓晓华教授在对闽方言和南岛语系的研究中表明,在当今的闽方言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南岛语系的词汇,而其中相关的闽方言特别是闽南语等。“比如说,闽南语中,脚就叫ka”,南岛语系的1000多种语言里,大部分有关腿或脚的词,都叫“ka”。在厦门等,都有叫“连坂”的地方,“坂”这个字的发音,在南岛语系中就是村子的意思。“肉”在闽南语中叫“ma”,而高山族叫“油”,“肉都是油的,所以两者在语言上有相关性。”通过寻找闽方言中同源词的数量、相似性分布,与上千种南岛语系的语言中的几种进行比较后,可以推断出南岛语是福建史前和上古时代先民的语言。①
东山方言为闽南语系,据考,标准闽南语是隋唐时中原正统汉语。但东山方言并非标准闽南语,它经常夹杂着许多无法用汉语拼音拼写出来的奇怪语音,但这种奇怪的语音却可以在南岛语系中找到归宿。
在夏威夷,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垂钓者事先都得在水边找来几块石头,码起来拜拜,否则鱼儿就不上钩,这与东山人“拜石公”的习俗相同。也与畲民一直保留的拜、谢猎神习俗相同。畲族自然村的村口,尤其是狩猎较多的村,直到20世纪中叶,基本上都有一个用三块石头搭起来的猎神庙,畲民狩猎前要在此处先祭拜,回来后要到此处致谢。
2010年5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等专家到泉州晋江深沪庵山遗址考察,亦发现庵山遗址出土的文物不少与台北十三行遗址出土文物十分相似,进一步证明南岛语族历史上的大迁徒中,台湾是一个重要迁徒地与中转地。
因此,5000多年前大帽山人或称东山岛人,或许就是今天南岛语族人的最早祖先,他们有能力借助原始的竹木筏穿越台湾海峡,并远航至辽阔的碧波万顷的太平洋吗?
结论当然是肯定的。由于气候原因,史前台湾海峡曾发生过3次比较大的海岸线变化。距今11万年前,台湾海峡的海平面比现在低130米〜140米,台湾岛和大陆是连为一体的;7万年前,台湾和大陆部分连接,虽然有浅海相隔,但是使用简单的舟楫还是可以通过的;在3万年前末次冰期,台湾和大陆仍有一定的连接,还可以方便通过。大陆和台湾岛的真正分离是从1万年前开始的,但是即使在距今5000年〜6000年前,两岸的交流依然十分方便、密切。
直到如今,仍然是可能的。2010年7月27月,法属波利尼西亚独木舟协会开始南岛语族“寻根之旅”活动,由6名南岛语族后人,使用船只总重量4吨,长15米、宽7米、桅杆高12〜15米,是一艘无人工动力的仿古独木舟,从南太平洋的大溪地起航,反向沿着先祖从中国东南沿海迁徙至太平洋诸岛屿的路线,开始他们近4个月的漂洋寻根之旅。一路上主要依靠风帆的力量顺风顺水航行,风小和没风的时候,船员们就必须划起船桨。为了真正体验祖先航海的生活,6个人都是在海里捕鱼生吃,或吃鱼干、喝椰子汁。沿途经过库克群岛、纽埃、汤加、斐济、瓦努阿图、圣克鲁斯群岛、所罗门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在历经1.6万海里航程后,登陆中国福建,在福州进行“寻根”文化活动。法属波利尼西亚独木舟协会长凯达布说,“我们的宗教信仰来自欧洲,但从人类学来讲我们的根在中国,这是一次回顾历史的历程。”易立亚等6名南岛语族后人参观平潭壳丘头遗址及相关博物馆时表示,石镑、石戈以及石叉等物品,在波利尼西亚仍常见。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东山人等漂洋过海呢?从中国历史看,居住在东山岛等地土著,是一个择水而居、擅长造船和航海的民族,他们是古书中记载的古越族的一支——实为畲家先民,后来中原地区的华夏文明越来越兴盛,畲家先民面临着被同化或被消灭的命运。他们一定不甘于就此消失,于是他们的目光投向了那一片浩瀚无际的蓝色大海。他们中勇敢的一群人,驾着竹筏、在星辰的指引下,乘着季风和洋流,驶人了茫茫的太平洋深处。但是一些古老的族群特质则隐秘地保留了下来,隐藏在信仰、风俗、语言和行为之中,向有心寻找的后人们透露出祖先的秘密。②而留下来的人们,由于汉代开始封建统治者的不断镇压,遁入山中的成为今天的畲族,他们无论老少,全认同来自凤凰山。
(一)自相矛盾
该项成果说,浙江景宁的畲族与广东连南的八排瑶的Y—SNP“距离比较近,而与大部分的瑶族距离远些,与布努群体则更远。看来起源上畲族与广东西北部的八排瑶有关系。
更明确的关系要通过STR的网络结构来判断,特别是苗瑶的特征单倍群M7的STR结构。”
在STR结构中,“畲族的主要类型也非常靠近中心位置,这说明畲族中的M7十分非常古老,应该是一种原生成分,而不是通过交流而获得自其他民族的。八排瑶与苗一布努类的关系很密切,与瑶族显然比较疏远。畲族有与八排瑶的联系,也有与苗和布努的联系。现在唯有广西贺州市鹅塘、沙田两个镇居住着土瑶,有6000多人,与广东连山的八排瑶相距比较近,在起源上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畲族应
该来源于苗一布努一八排瑶的类群。”①根据其这一论述,就不应该得出“畲族应该来源于
苗一布努一八排瑶的类群”,因在“在STR结构中,畲族的主要类型也非常靠近中心位置,这说明畲族中的M7十分非常古老,应该是一种原生成分,而不是通过交流而获得自其他民族的。”“对各个高频的单倍体做时间的估计,发现中国南方单倍群B,F,M7,R等大约5万年前就形成了,而发生族群分化的分支的年龄都有在2万年左右。”“八排瑶与苗一布努类的关系很密切,与瑶族显然比较疏远。”与瑶族大群体距离远,那么就有可能广东连山的八排瑶是畲族、或者与畲族有过融合,因连山靠近凤凰山。离布努群体则更远,就更不能归类于布努群体。
(二)方法错误
出现这一“自相矛盾”,导致结论的错误,重要的是方法错误。
1.与DNA方法背道而驰
以DNA这一遗传物质作为依据分析民族的起源,这是唯物主义的方法,是很好的科学方法,是此书的特色,也是科学。DNA方法是先比对、分析、解读数据,然后根据这些数据,结合历史文化,确定族属与关系。他们原先也是这么进行的。如在第一章《基因研究的悄然引入》中,列举了2002年李辉、侯井榕、杨宁宁的《广西六甲人来源的分子人类学分析》一成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县境内的古宜镇凤尾寨、周坪乡的马湾屯、下林江和溪脑屯的六甲人,人口约为三万多,操使六甲话,语言学界有不少学者认为六甲话归属于平话。六甲人有着不同于当地的侗、苗、瑶、壮及其他汉族群体的习俗。在民族识别过程中,三江六甲人于1952年曾经申报过“六甲族”;榕江的六甲人20世纪80年代以前也一直要求承认为少数民族,最后都被确认为汉族。很多的六甲人现在还认为他们不被承认为六甲族是因为人口太少了,而他们又“客不客,侗不侗”。于是研究者采用DNA工具进行分析。采集32个无可查亲缘关系的正常男子的血样。再经详细的调查排除掉其先祖中有侗族等其他民族的个体5个,研究的六甲人个体共27人。当中包括有侯、谢、荣、曹、吴、程和杨等姓氏,其中前四者是包括在六甲人的十二大姓中。结果,各姓氏内部的Y染色体单倍型并不一致。六甲人有的Hl、H5、H6、H8在各地汉族中是较普遍,而H11在南方汉族中也有。在单倍型种类上,云南、浙江、江苏、江西所含的种类都能涵盖六甲人所有种类。在各单倍型的频率上,六甲人与福建汉族最相近。把六甲人和各地汉族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9个所占信息大于0.1%的主成分,因此,六甲人的遗传组成与汉族没有区别。说明六甲人虽然文化上较奇特,但血统上还是汉族来源,是汉族的一个支系。然后结合历史文献、民族志等资料,他们可能源福建。DNA技术分析与历史资料一致。①
还有对汉族客家人的分析也是如此,是从父系遗传的Y染色体SNP的主要成分分析福建客家男子,发现客家人数据结构中汉族结构占80.2%,类畲族结构占13%,类侗族结构占6.8%:各族的M7个体Y-STR单倍体型的网络结构分析,发现客家人中类苗瑶结构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湖北,二是来自广东。客家人之类侗族结构可能来自江西土著干越。客家人母系遗传的线粒体RegionV区段9bp缺失频率为19.7%,mtD-NA与畲族很近,不同于中原汉族。单倍体暂缺。根据地这些结果,李辉认为,客家人的主要成分应是中原汉人,畲族是对客家人影响最大的外来因素。②
对畲族族源研究,本应也如前两者一样,是通过畲族的DNA与其他民族DNA进行比对,看其与哪个民族比较接近,然后确定其相互关系。然而该著作还是与原先那些传统研究范式一样,物质与意识关系的错位,不是用物质说明意识,而是用社会意识来说明社会存在。此著是先定其语言,把畲族语言归类于苗瑶语,然后与苗瑶比对DNA,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在逻辑上,其实结论已经隐含在前提中了,不用比对DNA,自然畲族源于苗瑶了。
这也违背了他们自己的初衷。该著作的第二章的开头云:“通常对于群体的分类主要是基于语言、文化和体质特征,再结合地理位置来进行的。这种群体分类方法简单、明了。然而,这种简单的群体归类方法多少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如果再加上一些人为因素或政治因素的介入,群体的定义就会越来越不精确,致使很多群体的生物起源、迁徙等到问题变得愈加模糊,这无疑给人类学、群体遗传学等学科的研究和发展带来一定的制约甚至误导,因为群体是遗传学研究的基本单位,只有定义或划分了群体,对许多问题的研究才能继续进行,但很难知道基于这些标准的分类在遗传学上是否合理。”①
2.样本数量过小
得出这个结论的主要样本来自浙江景宁的畲族。浙江景宁虽然是畲族自治县,但是景宁的畲族人口只有一万多,占全国畲族总人口的比例较低,不是畲族人口最集居之地,且该成果只用56个畲民样本进行分析。广东连山的八排瑶的人口占全国瑶族的比例更低。所以其结束语承认,“至于运用基因分子所得出的结论,因为样本选择的数量、广度及代表性因素的影响,也有待进一步科学验证。”②该成果第四篇《结语:史学与基因的交融刚刚开始》亦云:“但一方面分子人类学对岭南民族的研究还有空缺或样本不足等问题,如对瑶族分子人类学研究,还没有做到对瑶族五六十个支系进行全面的基因分析,对汉族平话人十几个支系亦然,这就影响对岭南民族源流的全面评价,从而造成对岭南各民族迁徙及演变历史进程的探究显得比较单薄。另一方面民族史对岭南各民族源流的研究在许多问题上又一直纷纭缠绕,在吸收分子人类学成果的过程中往往难以对号,难以取舍,难以贯穿。”③然而,书中还是取学界传统的一说,进行对号、贯穿,于是造成畲族等民族源流上的不科学。如果不是从语言出发,而是从地域出发,把畲族归类于“百越”、南岛语族,而不是归类于“苗蛮”,那么在DNA中比对遗传基因,共性会更多,自然结论更科学。
3.没有注意到各民族在历史上是不断流动的
用DNA遗传信息来确定个体、特别是父子之间的关系具有近100%的正确性。但是用来确定民族之间的遗传关系,不是个体间关系那么简单。正如该书开头引用费孝通先生1993年在《关于中国民族基因的研究——〈中国人类基因组〉评审研讨会上的发言》,所说:
3月初,我收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寄来的“中国不同民族基因组比较研究"的项目指南,我觉得研究目标中所提出的研究旨趣,诸如为人类进化和我国各民族源流、迁徙和划分提供生物学依据,无疑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这一项目所涉及的背景研究,自然也离不开人类学与民族学及其它社会科学的配合。
中国大地上历史的沉积、文化的积累、现代社会的投射,有过去历史形成、发展的很多复杂的过程及现实基础,作为中国社会的不同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其生物基础也有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基因研究可以对其复杂性有个基本的认识,其研究很有用处。
这种复杂性是极不平衡的,存在于区域之间,也存在于区域之内,有差别也有类同。中国历史上民族的分合过程及现代民族之间、民族内部的交流与整合,正是这一复杂性的典型体现。下面我提几点看法,仅供参考。
生存在中国土地的人最早的情况如何?这自然涉及到人类的起源。世界人类的起源并不是一个源,而是多源的。中国目前所发现的各进化阶段的人体化石,可以建立较完整的序列,说明中国这片大陆应是这很多源的一个。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人类化石为元谋人,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70万年左右,一般认为人类的分化即不同人种的出现是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目前,我们习惯用的人种分类是以1950年7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种宣言》所确定的蒙古利亚人种、尼格罗人种和高加索人种,分别称为“黄种”、“黑种”、“白种”。60年代以来,盛行地理分类法,仅以表征特征特别是肤色笼统的人种分类,常为区域性群体或区域性种族集团(EthnicGrouporEthnicstock)所取代。就是强调人类群体的区域性特征。
我在清华研究院结业时写了两篇论文,其中之一是《朝鲜半岛人种类型的分析》,这是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此后,也应当时驻北京的32军之约,调查该军体格,并对监狱犯人的体格特征进行分析。1935年与前妻王同惠女士去广西调查,我侧重于对当时称之为“特种民族”,即苗、瑶、侗、壮等少数民族的体质测量。我的这些研究,受到了我的俄籍导师史禄国教授的指导。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他把中原人的体质特征主要分为“a、β、r等若干种类型。华北、西北一带以a型为主,东南沿海到朝鲜半岛以β型为主,华南有较多的r类型。凭我的记忆说①,a型的人一般体高在1.60米以上,头型指数在70左右。面部特征表现为较细小的眼睛、宽额、扁平的鼻子、黄色的肌肤、宽阔的下巴、粗而长的头发;β型身高平均在1.60米以下,1.50米以上,类型指数在80左右,额部长而圆、鼻梁并不挺;r型,身高平均在1.50米到1.60米之间、长方型的脸,但双颊丰满、额长而宽、鼻梁不高、眼睛小、鼻端不尖稍圆。各类型的特征须查史禄国的原著。在此,我想把这三种类型的体质特征,和民族历史的迁徙联系起来谈几点看法。
中国各民族在历史上是不断流动的,而这些流动有它总的历史趋势。早在史前时代作为集团单位的人类群体就已存在,如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及甘肃青海的齐家文化之间的关联性。特别是陕西龙山文化经过宝鸡、天水,直接影响着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其它新石器时代文化区中各类型也反映了不同群体之间文化的传播、交流、汇集的过程。此种文化上的交流,在体质特征上也应当有所反映。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里,总的来说是北方民族的南下或东进,中原民族的向南移动,沿海民族的入海和南北分移,向南移的又向西越出现在国境。这一盘棋看清楚了,有助于我们的研究的展开。
在中国历史上,夏商周可谓东方β型与西方a型人种的第一次大汇合,发端于后称的羌戎之地的a型人,从夏开始向东进入关中西部,但其文化低于东方,实力强于西方。西方集团随后通过其军事力量,控制了东夷集团的齐鲁之地,作为β型的东夷集团子民,一部分β人开始了漫长的民族迁徙,其流向一部分进入朝鲜半岛,一部分分为两支,一支成为吴越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支为东夷中靠西南的一支,他们生活在淮河和黄河之间,这一批人,向长江流域流动,进入南岭山脉向东,在福建、江西、浙江的山区和汉族结合的那部分可能是畲,另外有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带,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的可能是苗。
在我前面提到的,《朝鲜半岛人种类型的分析》中,我看到β类型占的比重较大。1935年我所作的苗瑶等体质调查结果认为,苗瑶在体高和头型指数的系联表上所处的地位颇近于朝鲜半岛及华东人。在华南沿海地区的居民很可能有来自海上的r型,与吴越系统的β型相混合。上述民族集团的移动的路线,在人类学、民族学界并未定论,如果能结合不同民族基因的研究,把a、β、r等各种类型的特点找出来再进行比较研究,将有助于中国各民族人种问题的解决。
在对不同民族基因的研究中,我想在宏观上还应把握中国各少数民族历史和现状。我曾就此写过一篇“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对中国民族的变动及分合过程作了较为概括的研究,可供参考。在此,我想就操作层次提出一些意见,中国境内的民族集团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农牧接触的多民族走廊,然后为云贵高原和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其中不同区域内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似性及联系性要比不同区域之间不同民族的相似性与联系性多。此种特点在近年来的一些对少数民族的体质测量数据中也能反映出来。如彝族和藏族,男性头长的平均数最大为189.45和190.9,蒙古和维吾尔族分别为180.9和181.73。苗瑶侗族分别为1849、184.58、184.30;头型指数,彝族、藏族分别为78.52、79.94;蒙族和维吾尔族分别为84.25、84.68;苗瑶侗族分别为81.80、81.27、81.96②。其它体质测量数据也反映了这一特点。这与同一历史民族区内民族集团的频繁往来,关系甚大。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最好是以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区域进行研究。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中国境内的有待进一步识别的人类集团。
50年代,我们搞民族识别时,当时上报到中央的民族名称有400多个。由于历史原因有些也不是单一民族:经过二十多年的民族识别工作,我国多民族大家庭的构成基本上是搞清楚了,但还有些余留问题。现在已经提出要求识别的有:四川“平武藏人”,西藏东南部察隅县的僜人及南部定结县及定日县的夏尔巴人;云南省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的苦聪人以及还有一些不大为外边知道的本人、空格、三达、阿克、布夏、布果、贫满、等角、卡志、巴加、结多等人。这些问题大多是“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疑难问题。
最后,我们还应考虑不同民族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因为这种文化水平也影响到他们的孤立和流动较小的特点。
中国在解放前还有一部分少数民族保存着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他们主要分布在云南边疆地区的独龙、怒、佤、傈傈、布朗、景颇、崩龙等族,此外还有居住在内蒙古、黑龙江一带的鄂伦春、鄂温克和赫哲族,以及聚居在海南岛的部分黎族(五指山区内)。基本上属于这一类型的一共大约有60万人,现在这些民族都发生了剧烈的文化变迁,但其仍保留着一些传统的基调。目前,可以说在中国境内完全与外界隔离的民族单位是不存在的,但相对封闭的民族集团如具有“语言孤岛”之称的一些民族单位还是在一定地区内存在。
总之,我们在进行民族基因的研究中,要多考虑不同民族的自然、人文特点,同时还应考虑来自各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与健康、疾病医药的关系。我相信这一研究,除自然科学的意义之外,在学术上和实践应用上,也是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有力推动。
衷心希望这一研究能取得期望的成绩!
注释:①我在清华研究院的论文因战乱在搬迁中遗失。②可参考《中国人体质调查续集》,上海科技出版社,1990,第1—46页。
此文由当时跟随费老读博士生的麻国庆整理而成,为纪念费先生,麻国庆博士把这篇讲话发表于2005年《开放时代》的第4期上。
虽然该书开头全文引用费孝通先生的讲话,但是书中却没有根据其讲话进行分析。
“中国各民族在历史上是不断流动的”、“我们在进行民族基因的研究中,要多考虑不同民族的自然、人文特点,同时还应考虑来自各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与健康、疾病医药的关系。”用这一观点看,用DNA来分析畲族族源的《岭南民族源流史》,认定“分子人类学基因分析的裁判:畲苗族群”,①结论的不科学。正如该项成果鉴定专家的《意见与建议》所说:“在该项成果研究中,太过于倚重分子人类学。分子人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在人类学起源研究中还处在探索阶段;人类起源于非洲说也只是其中一说,况且上古人类与中古人类以至近代民族非是直线传承,其间的空间跨度相当漫长,因素也十分复杂,仅凭现代的人类基因分子来断定其与上、中古乃至近现代民族关系,有简单化之嫌,其观点必然会引起民族学界的争鸣。”①我们知道,历史文献上,南方少数民族部落长期被称谓为“蛮”,特别是苗瑶畲不分,书中也说“汉文史藉往往把畲族称为‘瑶人’或‘畲瑶’,有些地区的畲族也自称‘瑶人'或‘瑶家';分布在粤东的操苗瑶语族接近苗语支(即瑶族的‘布努'方言)的部分畲族,在海丰、惠阳两县被汉人称为‘畲人',但在增城、博罗两县却被称为‘山瑶'”。②从民族成份认定上看,20世纪50年代民族成份认定时,各村落主要根据自身认同,没有DNA技术,导致有的不一定科学。从地域上看,广东增城、博罗、连南等地是属于畲、瑶民族结合板块,不排除历史上民族融合。该成果的一项重大突破是“侗水人群约8000年前发源于福建厦门、广东汕头一带,后来可能由于政治压力向西北方向迁徙”。那么同样,瑶族有可能其中一部分是从凤凰山区迁徙过去的后再融合而成,因此,其DNA与其他瑶族不同,而与畲族有相同之处。
书中另一比对是线粒体DNA的多态性。“线粒体DNA的多态性也能体现出群体的特性。我们继续观察浙南这两个民族的线粒体DNA的单倍体情况。把线粒体单倍群大致分成了南北的两个类群。这两个类型都明显多于北方类型。这说明畲族是南方原住民族,而浙南汉族的母系成份中留有比父系更多的原住瓯越成分。”“非常特别的是畲族群体中有很高频率的Fla单倍体,这在其他民族群体中都是很少见的。Fla是一个古老的单倍体,在南亚语系的群体中就有已经存在,并且流传到了其他各个语系的人群。从网络结构中,笔者发现畲族的多态性并不低,其单倍体散布在网络结构的几个角落,这就说明畲族的Fla并不是瓶颈效应造成的。”③线粒体DNA的多态性,特别是畲族群体中有很高频率的Fla单倍体,这在其他民族群体中都是很少见的。Fla是一个古老的单倍体,在南亚语系的群体中就有已经存在,并且流传到了其他各个语系的人群。畲族更不能判断为“畲苗族群”,而应是南亚语系族群。
4.语言归类错位
把畲族语言归类于苗瑶语,仅仅采用学界的一种看法,而且是畲族人一直反对的看法,其实从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看,这个归类是错误的。
畲族语言也是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的认为是“畲族讲的客家话”,有的认为“客家讲的畲族话”,把只占畲族人口不到1%的1000人的增城、博罗的畲族,讲苗瑶语的作为畲族,而把占人口99%以上畲民作为“越化”、“汉化”者,多数学者、特别是畲民不认同这一种观点。占人口99%以上畲民归纳到1%讲苗瑶语中,逻辑上大前提不正确。因而,犯了“大前提虚假”的逻辑错误。
也没有考虑到民族认定的实际。广东增城、博罗的畲族,自称是瑶族。1955年《广东民族识别调查》中云:“增城、博罗两县自称‘贺爹',具有盘瓠传说和姓盘、蓝、雷、来的人却认为是‘瑶’,他们从未听老辈说过自己是‘畲’。1951年增城下水村来金德作为‘瑶族'代表去参加少数民族参观团,当时遇见海丰畲族代表,海丰畲族代表说:‘我们都是畲,你也是。’来金德就说:‘我不是,我们不来这里时,人家都是叫我们做瑶族的,你叫畲就叫畲,我们是认瑶族。’由此可见他们是很坚决的要称为‘瑶’。”“罗浮山区的群众说他们从祖公一直相传下来都说自己是‘瑶’讲的是‘瑶话’,族谱都是‘瑶人’,历代受瑶官统治,只向瑶官纳税,瑶官印上还写有‘增、龙、从、博抚瑶府’字样,解放前被被汉人称为‘山瑶佬'、‘山瑶仔'、‘瑶佬’、‘瑶仔’,他们使用汉语时亦自称为‘瑶人',所以他们认为历代相传是‘瑶',不是‘畲'。”“现乡干部及‘老大'蓝火桂、蓝石金提出意见说:畲族是政府说的……发土地证及普选时所填的‘畲族'也是别的同志写的,我们自己的祖公是'狗头王',又拜盘古王,是‘山瑶',不是‘畲',是‘瑶族',不是‘畲族’,要求政府将名称更正为‘瑶族'。”“对于连南瑶族他们认为虽然服饰讲话不同,也没有关系,姓同就是自己人,是同族。”①因此,畲民识别调查组主要成员、今中央民族大学施联珠教授认为,他们不是畲族,应认定为瑶族更合适。因而把这部分畲族作为畲族的样本也不恰当的。
5.与原有成果矛盾
李辉于2002年第4期《广西民族研究》发表的《百越遗传结构的一元二分迹象》中说,“最新的分子人类学材料——Y染色体DNA能对民族系统进行精细的分析。百越系统被发现与中国的其他系统差异很大,而与南岛语系民族(马来系统)特别是台湾语族群体相当接近。”“这些群体的Y染色体遗传结构体现出相当大的一致性,而与其他系统中研究过的群体完全不同。他们都有大量的M119、M110或M95、M88突变,而外族极少有这些遗传标记,与百越接触少的群体则没有。”“已经研究的百越群体显示出遗传发生关系和语言文化类型的差距,这与百越的整体认同和地域分化有关。”文章认为,“百越民族的起源问题。最初从非洲来到东南亚时,百越和南岛民族可能是同一个群体。而后百越民族北迁至广东,南岛民族南迁至马来。两者分开后分别发展成两个系统。”
(三)属南岛语族
从民族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与民族语言学的新证据、该书的DNA证据都表明,“南岛语族”与东南土著同属于一个人文系统,学术文献中的东南土著与“南岛语族”间并没有真正的文化内涵与族群系统的“差别”。该书表中(本书上页表)比对也指出,“畲族群体中有很高频率的Fla单倍体,这在其他民族群体中都是很少见的。Fla是一个古老的单倍体,在南亚语系的群体中就有已经存在,并且流传到了其他各个语系的人群。”因此,把畲族归类于南岛语族进行比对、分析,更科学。
“南岛语族(Austronesian)”即“马来一波利尼西亚语系”(Malayapolynesian),其中包括近千种语言,使用人口在100万以上的语言最多不超过20种,其余都是小种语言。
南岛语系地理范畴分布在南太平洋到印度洋上的百多个岛屿,这些岛屿多数人口稀少,东至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西跨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北到台湾岛北端,南到新西兰南端,主要居住地区包括中国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等地。南岛语族主要包括马来人(包括台湾高山族)、密克罗尼西亚、美拉尼西亚人、波里尼西亚人等几大族群,总人口达2.7亿,是一个十分庞杂的民族文化体系。
考古学方面看,南太平洋诸岛人来自中国东南沿海成为民族考古学者的共识。美国历史学派人类学家拜雅(H.0.Beyer),在东南亚与大洋洲土著民族文化的调查研究上享有盛誉,他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坚持菲律宾群岛地带做田野考古与史前文化的跨地域比较研究,是菲律宾考古的主要奠基人。其学生林惠祥教授运用拜雅及其同辈们的考古学研究,提出了马来民族起源于中国大陆百越系统的观点。厦门大学陈国强、蒋炳钊、吴绵吉、辛土成等,列举了考古与民族志材料中古代越族和东南亚民族共有的有段石锛、体质、语言、断发文身、缺齿、干栏、食人猎头、崖葬、洪水传说等为源流关系的主要证据,并从文献资料寻找越族三次向东南亚迁徙的事件,即楚灭越、秦统一岭南、汉武帝平两越等历史史实,延伸和发展了导师林惠祥教授观点,《百越民族史》一书认为,“早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百越民族的先民文化和东南亚各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关系就很密切,后来,越族曾数次南迁,特别是我国东南地区的越族,从大陆经台湾南迁进入菲律宾等地;在西南和南方的越族,也南迁进入印度支那等地。南迁的越族和当地土著一起,融合发展成为现在的东南亚民族。”徐松石先生出版的《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阐明了东南亚的“马来民族,缅甸民族,越南民族,泰民族和高棉民族等”,“他们的祖先都是由中国移民而来的。古代的中国南方住民,好像潮水一样,继续冲进这个区域。”
奥地利海因•戈尔登也根据中国和波里尼西亚都有段石锛的事实推断大洋洲的古文化有些是起源于中国的,主张东南亚史前文化和种族来源的北来说,认为新石器时代便有一种使用澳亚语(Austroasiaticspeech)而体质上属于蒙古利亚的民族迁移到了印度支那、华南大陆沿海、台湾、菲律宾、苏拉威西。日人鹿野忠雄也认为,波里尼西亚的有段石锛或者是由华南的民族及文化移动而传到,当时华南仍有土著民族,华南古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不但对东南亚、甚至对波里尼西亚都有关系。
2002年11月,凤凰山文化区的东山岛大帽山遗址开始首次发掘。这次发掘的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年代距今4300-5000年之间,位于东山县陈城镇大茂新村东北约1公里的大帽山东南坡。参加挖掘的工作人员有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和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的教授们,还有来自福建博物院和台湾中研院的研究员们。结果夭天都有发现:用来造船的原始工具——石镑、石箭镰、石球、凹石、各种纹饰的陶器、陶片、纺轮、骨制品和数不清的鱼骨、贝壳等等。夏威夷大学的罗莱教授说:“这里的石器无论是器形和制作手法,都与南岛语族的波利尼西亚石器十分相似。”而平潭岛的“壳丘头遗址”发现了目前最早的有段石锛,有距今6000年左右的历史,所以目前的国际考古学界和中国的考古学界就共同的把壳丘头当作是南岛语族最早离开原乡的起点。在对出土的石镑做了成分分析后,结果表明,绝大部分石镑的原材料竟来自澎湖列岛!原来生活在这里的原始居民,早在我们可以想象之前,就驾舟出海、渡过台湾海峡,频繁地来往于两地之间,进行双向交流。
来自哈佛大学的学者焦天龙也介绍说:“你看,这些陶器与澎湖列岛上锁港遗址的陶器有很多的相似性,而且我发现它们与台湾本岛某些遗址的陶器也惊人地相似。”尤其是在众多的出土文物中,有着大批红色的陶片,即便已经埋藏了五千年之久,今天看起来仍然是嫣红鲜艳。更是因为它看上去与在万里之外太平洋的小岛上出土的“红衣陶”如出一辙。而“红衣陶”是一种先抹一层红色化妆土再烧制而成的陶器,一直被认为是大洋洲新石器时代的“拉皮塔文化”居民群体的独特陶器。
南岛语族的许多岩画,如美拉尼西亚岩画中放射状图案和人体及足印,与东山的东门屿上发现的相类似。用放射线来表现太阳的光芒,是东山与美拉尼西亚岩画的共同特征,别无二致,同样反映了一种强烈的太阳崇拜意识。东山岛上还发现了不少的“祭祀穴坑”和“足印”岩画,南岛语族许多岛国上的岩画,都可以在漳州东山找到它们的联系。
民族学方面看,南太平洋诸岛上的居民都声称自己的祖先来自“北方的一个大岛屿”。有关权威专家研究表明,这些属于南岛语族的居民起源应该“位于中国台湾、澎湖列岛和东南沿海一带”。
体貌亦相似。从体质人类学上来说,南岛语族的个子比较矮小,比较黑,而福建沿海人一般都个子比较小,历史文献中记载凤凰山区早期有“小黑人”,有着相似的外形。2005年,遗传学家JonathanFriedlaender为了找出南岛语族在遗传学上的共性,对太平洋地区的41个族群中的952个个体进行研究,他分析了687类基因指标,既包括线粒体DNA,也包含Y染色体。分析结果显示,玻璃尼西亚人与台湾原住民的基因联系密切。这一结果表明,和台湾隔海相望的中国东南沿海是南岛语族的基因发源地。
福州大学闽商文化研究院院长苏文菁教授介绍说“从语言学上讲,有很多语言的基本词汇和语言结构是基本相似的”。厦门大学邓晓华教授在对闽方言和南岛语系的研究中表明,在当今的闽方言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南岛语系的词汇,而其中相关的闽方言特别是闽南语等。“比如说,闽南语中,脚就叫ka”,南岛语系的1000多种语言里,大部分有关腿或脚的词,都叫“ka”。在厦门等,都有叫“连坂”的地方,“坂”这个字的发音,在南岛语系中就是村子的意思。“肉”在闽南语中叫“ma”,而高山族叫“油”,“肉都是油的,所以两者在语言上有相关性。”通过寻找闽方言中同源词的数量、相似性分布,与上千种南岛语系的语言中的几种进行比较后,可以推断出南岛语是福建史前和上古时代先民的语言。①
东山方言为闽南语系,据考,标准闽南语是隋唐时中原正统汉语。但东山方言并非标准闽南语,它经常夹杂着许多无法用汉语拼音拼写出来的奇怪语音,但这种奇怪的语音却可以在南岛语系中找到归宿。
在夏威夷,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垂钓者事先都得在水边找来几块石头,码起来拜拜,否则鱼儿就不上钩,这与东山人“拜石公”的习俗相同。也与畲民一直保留的拜、谢猎神习俗相同。畲族自然村的村口,尤其是狩猎较多的村,直到20世纪中叶,基本上都有一个用三块石头搭起来的猎神庙,畲民狩猎前要在此处先祭拜,回来后要到此处致谢。
2010年5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等专家到泉州晋江深沪庵山遗址考察,亦发现庵山遗址出土的文物不少与台北十三行遗址出土文物十分相似,进一步证明南岛语族历史上的大迁徒中,台湾是一个重要迁徒地与中转地。
因此,5000多年前大帽山人或称东山岛人,或许就是今天南岛语族人的最早祖先,他们有能力借助原始的竹木筏穿越台湾海峡,并远航至辽阔的碧波万顷的太平洋吗?
结论当然是肯定的。由于气候原因,史前台湾海峡曾发生过3次比较大的海岸线变化。距今11万年前,台湾海峡的海平面比现在低130米〜140米,台湾岛和大陆是连为一体的;7万年前,台湾和大陆部分连接,虽然有浅海相隔,但是使用简单的舟楫还是可以通过的;在3万年前末次冰期,台湾和大陆仍有一定的连接,还可以方便通过。大陆和台湾岛的真正分离是从1万年前开始的,但是即使在距今5000年〜6000年前,两岸的交流依然十分方便、密切。
直到如今,仍然是可能的。2010年7月27月,法属波利尼西亚独木舟协会开始南岛语族“寻根之旅”活动,由6名南岛语族后人,使用船只总重量4吨,长15米、宽7米、桅杆高12〜15米,是一艘无人工动力的仿古独木舟,从南太平洋的大溪地起航,反向沿着先祖从中国东南沿海迁徙至太平洋诸岛屿的路线,开始他们近4个月的漂洋寻根之旅。一路上主要依靠风帆的力量顺风顺水航行,风小和没风的时候,船员们就必须划起船桨。为了真正体验祖先航海的生活,6个人都是在海里捕鱼生吃,或吃鱼干、喝椰子汁。沿途经过库克群岛、纽埃、汤加、斐济、瓦努阿图、圣克鲁斯群岛、所罗门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在历经1.6万海里航程后,登陆中国福建,在福州进行“寻根”文化活动。法属波利尼西亚独木舟协会长凯达布说,“我们的宗教信仰来自欧洲,但从人类学来讲我们的根在中国,这是一次回顾历史的历程。”易立亚等6名南岛语族后人参观平潭壳丘头遗址及相关博物馆时表示,石镑、石戈以及石叉等物品,在波利尼西亚仍常见。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东山人等漂洋过海呢?从中国历史看,居住在东山岛等地土著,是一个择水而居、擅长造船和航海的民族,他们是古书中记载的古越族的一支——实为畲家先民,后来中原地区的华夏文明越来越兴盛,畲家先民面临着被同化或被消灭的命运。他们一定不甘于就此消失,于是他们的目光投向了那一片浩瀚无际的蓝色大海。他们中勇敢的一群人,驾着竹筏、在星辰的指引下,乘着季风和洋流,驶人了茫茫的太平洋深处。但是一些古老的族群特质则隐秘地保留了下来,隐藏在信仰、风俗、语言和行为之中,向有心寻找的后人们透露出祖先的秘密。②而留下来的人们,由于汉代开始封建统治者的不断镇压,遁入山中的成为今天的畲族,他们无论老少,全认同来自凤凰山。
相关地名
广东省
相关地名
广西壮族自治区
相关地名
海南省
相关地名
浙江省
相关地名
景宁畲族自治县
相关地名
连南瑶族自治县
相关地名
鹅塘镇
相关地名
沙田镇
相关地名
连山区
相关地名
凤凰山乡
相关地名
广西壮族自治区
相关地名
三江县
相关地名
古宜镇
相关地名
周坪乡
相关地名
榕江县
相关地名
六甲区
相关地名
云南省
相关地名
江苏省
相关地名
江西省
相关地名
福建省
相关地名
湖北省
相关地名
中原区
相关地名
北京市
相关地名
甘肃省
相关地名
青海省
相关地名
宝鸡市
相关地名
天水市
相关地名
淮河镇
相关地名
贵州省
相关地名
南岭乡
相关地名
四川省
相关地名
平武县
相关地名
察隅县
相关地名
定结县
相关地名
定日县
相关地名
内蒙古自治区
相关地名
黑龙江省
相关地名
海丰县
相关地名
惠阳区
相关地名
增城区
相关地名
博罗县
相关地名
厦门市
相关地名
汕头市
相关地名
南北镇
相关地名
下水村
相关地名
台湾省
相关地名
东山县
相关地名
陈城镇
相关地名
大茂新村
相关地名
山东省
相关地名
南坡乡
相关地名
漳州市
相关地名
畲族自然村
相关地名
泉州市
相关地名
晋江市
相关地名
深沪镇
相关地名
福州市
相关地名
平潭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