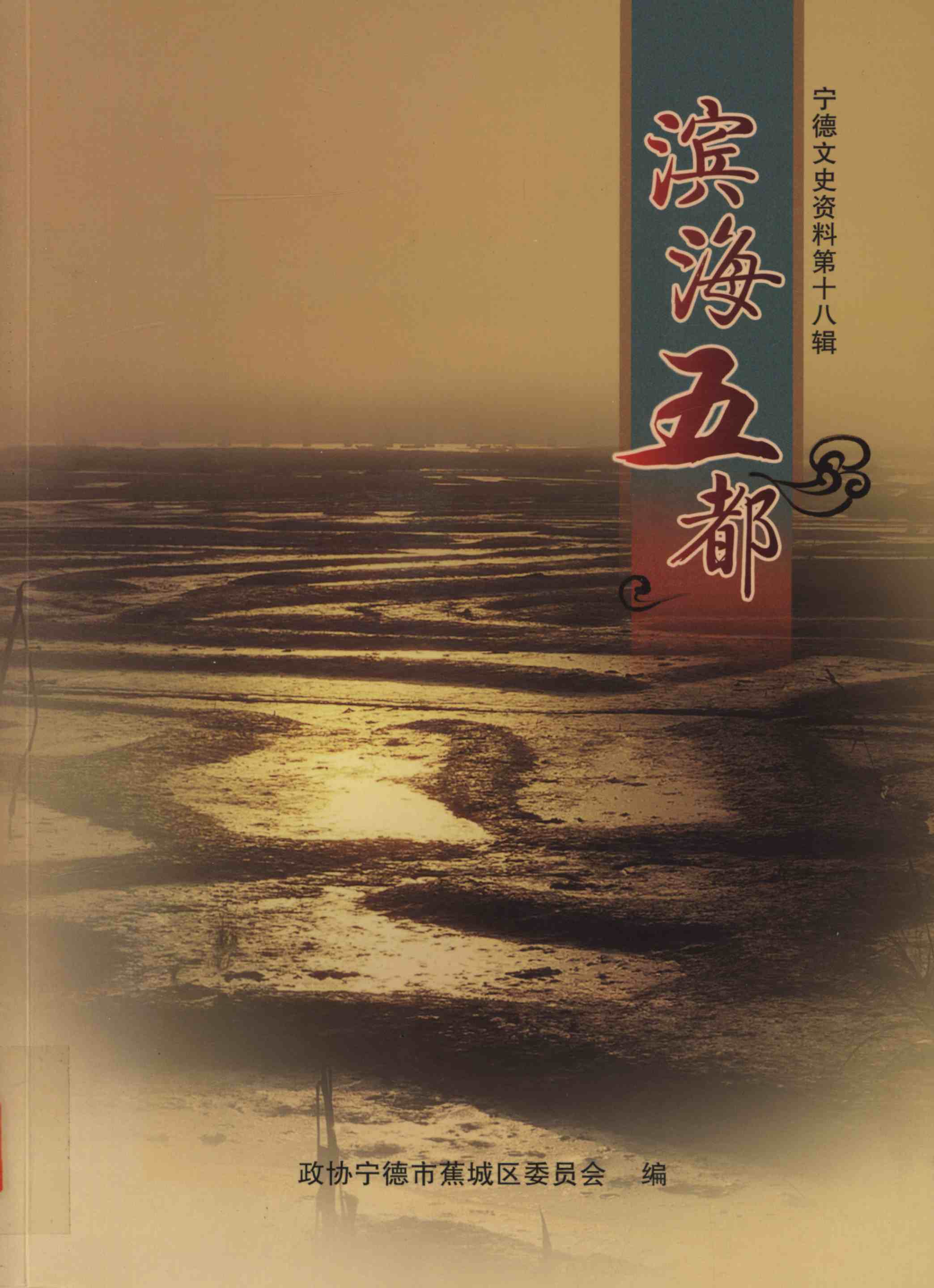七十年代金涵民生琐记
| 内容出处: | 《滨海五都》 图书 |
| 唯一号: | 130920020210001388 |
| 颗粒名称: | 七十年代金涵民生琐记 |
| 分类号: | K295.73 |
| 页数: | 15 |
| 页码: | 448-462 |
| 摘要: | 自七十年代在金涵插队以来,已近四十年。前后这点时间认识一个地方极有限。这一时期,城郊景观快速更叠,社会面相急遽转换,“文革”期间所见场景,早已消失。今不揣冒昧,记录点滴,以印证时代变化一二。口粮是七十年代农民最主要收入。七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水稻生产发生革命性变化。抢收早稻和抢种晚稻的“双抢”时节,生产队统一送饭下田,以抢农活,金溪平原一带称“食清昼(吃冷饭)”。要说六七十年代的生态环境好不好,较为复杂。除食粮之外可吃的东西,都叫“副食品”。蕉露是县酿造厂以“无米制作法”生产的酒,呈暗红色,很甜,有香气,度数要比米酒高,一斤五角六分钱。我在山区生产队时,恰好修村里的公路。大约1976年春耕开始后不久,公社派人在茶场边的山道上设卡拦木材。 |
| 关键词: | 宁德市 金涵乡 民生琐记 |
内容
自七十年代在金涵插队以来,已近四十年。前后这点时间认识一个地方极有限。这一时期,城郊景观快速更叠,社会面相急遽转换,“文革”期间所见场景,早已消失。今不揣冒昧,记录点滴,以印证时代变化一二。
口粮
口粮是七十年代农民最主要收入。生产队一般年中早稻收割后,按人口分配一次稻米。年终分配地瓜米(番薯丝)和晚稻,好一点的大队,分多一些晚稻。单身汉或劳动力多而人口少的家庭,粮食充裕些。我在茶场,每年可分到大约五百余斤口粮,内中约有三百斤左右是稻谷。口粮都放在仓库里,全体吃食堂,每顿自报吃几两地瓜米,由专人(两个人)监秤,置于饭甑(为一木桶)中蒸熟。开饭时,另由专人执一只桃型木柄,专职盛饭,当面称重。将一碗“泥”得尖尖的地瓜米,放在盘秤中,称出毛重,再刨去碗的重量。地瓜米蒸熟后,似乎要重上四倍多些。餐餐如此,虽然麻烦,但以程序正义保证实体正义,却没有口舌。吃白米,则自备饭盒,自已放米加水,放在蒸笼里。农民只在过年和早稻收割后的十来天吃大米,一般的人家,吃大米的时间(甚至包括大米掺地瓜米),全年不会超过一个月。稻谷一百斤,出米六十五到七十斤,吃是好吃,但数量少。因此,农民群众愿意用一比一比例,拿稻谷(不是大米)换地瓜米。这在当时是常见的事情。因此知青吃大米次数要比农民,特别是比有家口的农民多得多。据资料,1976年全县农民的平均口粮只有336斤,农业人口平均经济收入只有45.6元,远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蒸汽催芽(《杨家盛同志在全县公社脱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7月3日)
七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水稻生产发生革命性变化。1974年从夏到秋,我在一个山区生产队,参加过一季高杆单季稻的薅草及收割农事。此后,见都没有见到高杆水稻。到了1977年春,第一次见试种的杂交水稻,不料几年后就靠着杂交水稻吃上了无忧的饱饭。
其实从六十年代开始,宁德县水稻有个“三化”的过程,就是单季改双季,高杆改矮杆、间作改连作。加上开始大量使用化肥,产量增加不少。不过许多地方种双季稻,一般年景下,无霜期总不够长,晚季收割遇上“寒露风”,则出不齐穗多瘪粒歉收乃至绝收。于是只有将早稻播种提早。早年间平原沿海是清明播种,立夏插秧。后来提早到春分播种。稻种用温水浸,好出芽。山区无霜期短,就再提早到“雨水”节气播种。这时天气冷,出不了芽,就将稻种浸湿,置于密封房间内,用一口铁锅加水用稻壳焖烧,制造出一个类似桑拿的湿热小环境,叫作“蒸汽催芽。”
在山区生产队那年,我住二楼,楼下恰是蒸汽催芽的房间。农村土房子楼板就是一层,缝隙还不小,因此其实人也在被桑拿之列。次日晨起,见被子与草垫湿得出水。好在那时年青火气大,与同室之朱、丁等三人皆无事。但稻种出了芽不一定成得了秧,天冷就烂。秧一烂,为赶农时,即刻就要再下种催芽。如此甚至有再三再四的。1976年有倒春寒,近清明了,还有“西伯利亚寒流”。据说当时全县只因早稻烂秧,就损失了四百来担种子。
当时,硬是要在山区种双季稻,听说海拔近千米的天湖村也种了双季。这样就要做些出奇的事情,最终也不能证明“人定胜天”。
劳动送饭
抢收早稻和抢种晚稻的“双抢”时节,生产队统一送饭下田,以抢农活,金溪平原一带称“食清昼(吃冷饭)”。其实往往是一年中吃得最饱的一餐。我在山区生产队时,记得每个劳力按一斤半米的份额计算。称出稻谷,自己加工,先是砻(一种现在很难见着的磨一类的加工器具)米,再舂,筛,做出米来统一蒸煮。米是单季稻品种“白早”,这个品种米粒很大,如今可能连同“红早”一样已经绝种了。煮法用“捞炊”,就是先在大锅中煮得半熟,再置于蒸笼中炊熟。米饭呈颗粒状,极香。当然一斤半的米,大部分人一顿吃不下。不少人带了家小,分一碗米饭是没有人当面非议的。
在茶场里,也有几回送饭到田头。场里只一二个儿童,妇女也不下地,因此,尽管各人饭量有差别,但随吃随添,按每人一斤米的份量,能让每个人都吃得很饱。下饭菜只是油饼、油条、酸菜汤之类。有一回分猪肉,就不合在集体一起吃了,而是称出炊好的米饭,连同两斤猪肉,按人头分配。又有一回到金溪村前水田劳动,一位姓孙的少年——茶场里唯一多子女家庭的老二,吃量超过成年人,最后还喝木桶中盛的酸菜汤,鼓起的肚皮向左侧歪去,不得不让人担心出问题。画家黄永玉说,“小孩子的肚量,比圣人的肚量还宽阔”,这样惊人的饭量,是因为,许多人一年中,只有数回,甚至从来没有过吃饱大米饭的美好感觉。
这样的吃法算是正常的。不正常的生产队也有。一些地方群众对集体经营失去信心,吃光喝尽。据资料,当时,八都大队某生产队社员出工时,“点心”要吃米酒、扁肉、小炒肉,仅吃喝一项,就占去总收入的23.7%,几乎等于全年的农业生产成本。洋中凤田大队某生产队,1977年干部社员吃掉的“点心粮”就有90多担,分光吃尽,使得当年十分工分值只有2角2分(引自《继续揭批四人帮,深入开展两打斗争,落实党的政策,改变干部作风,为速度发展我县农业而努力奋斗——吴子金同志在县三级扩干会上的讲话》1978.10。)。
产生这种现象,有着更深一点的原因。一些农民认为,劳力少而人口多的家庭,在分配中多分了粮食和其他实物,即使超支欠款,也得到了实惠。甚至有单身汉认为,集体经营是在帮别人养家,有被剥削的感觉。这是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在当时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七十年代初,宁德县领导批判了农村分配时“搞按劳分配”的行为,但在七十年代中期后认为要坚持“按劳分配”(1968年底,宁德县革委会通过对年终收益分配工作的规范,恢复了部分农村“文革”武斗期间开始解体的集体经营体制。县革委会针对当时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鼓吹口粮按劳分配,分光吃光,不卖或少卖余粮,副业不归集体,搞投机倒把”的现象,特别指出,“如再搞‘按劳分配’者,要追查责任,要教育群众,认识这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见《宁革生财》(68)004号《关于分配1968年农业税征收任务的通知》。 1972年年底,宁德县革委会发文,指出,“搞好年终收益分配工作是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体现”,明确要求按照省委的“十六条”规定,以生产队为单位,逐条落实。“要弄清‘物质刺激’、‘工分挂帅’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界限”。见宁革生(72)第191号《关于1972年年终分配几个问题的通知》。 1975年7月6日,宁革(75)90号《关于夏季预分工作的意见》明确地提出,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对劳力外流,副业单干及弃农经商人员和其所负担的人口的口粮,“可留队里,待回队做出适当处理后,按月拨给”。),这种在根本问题上没有标准的现象,说明集体经营这种制度的确不适合于当时农村的生产力状况。农民讲实际道理,将劳动成果吃到肚里,心甘情愿,至于往后如何过日子不管不顾。这当然是一种相当阴暗而悲观的心理。
生态
要说六七十年代的生态环境好不好,较为复杂。那时几乎没有“三废”污染。空气、水、土地特别干净,大气能见度高,水质清澈,地里即便用了农药化肥,恐怕也比如今重金属、化学制品等污染要来得轻。但是,山上草、树都比现在少,特别是村庄田野附近的山上。植被稀疏,树少草少,这是因为每家燃料都用柴草。金涵山区农民一大收入,就是砍柴割草,有空时挑到城内卖了,得几只咸鱼当家。手头宽一些,有的还带几块光饼之类。“杆蒙”(芒箕草一类)一担在城中约值一、二元,而咸带鱼每斤三、四角钱,咸虾苗一斤仅一角多钱。
各家各户都在山上割蕨草,山上光溜溜的。大树在1958年时砍得差不多,到七十年代,也没有长茂盛。记得春耕时,要割些蒿(禾本科芒草)的嫩叶给牛当点心,还要走好几里路到“溪里”(今大金溪上游峡谷)深处才有。割蒿叶,工分既高,又有米一斤、现钱一元二角补贴,是很少的工种。但也很苦,无论本事多高,手终究要被割得血丝道道。
野生动物不好说。对比现在,有的少有的多。在金涵平原和山区,听过几次关于山上动物的事情。一是公社茶场后高海拔的中前大队八斗丘生产队,几个人打死一条大蛇。这蛇冬天不知为何跑了出来,钻到一家农户灶间的柴草堆中,被人惊动后,又自行爬出院子。正在翻过院墙时,在地里干活的一群人闻报赶到,用锄头打死在屋边。据说有一张半“篷”那样长,大约七米左右。这事情按推算,大约发生在六十年代中期或更早些。其二,一位后溪村人说,有一天在山垅中“拾水”(看水),一条大蛇在对面坡草丛中窜过。被此人惊动,跌到水田里,溅起的水花飞过一丘田,洒到这位吴姓农民的头上。问:“到底多大?”这位在茶场里的“学习班”的成员只笑不言。这事情发生在武斗那一年。其三,大约1974年秋,一只猛兽在金浿村头,半夜时咬走一只狗,留下一条长半米多的爪痕。村里有人说是“老虎”,但并没有人见到这只猛兽。差不多也在这一段时间,一队几个人在金邶寺前的水田里干活,巧遇一只半大的野猪窜进水田里。水田是烂泥田,因此跑不快,被十几个人追打,后成肉食。其四,听茶场里一位姓刘的中岗村农民讲挖裸狸(穿山甲)成功的经历。记得似乎说是七十年代初的事情,但不能肯定。不过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山上的确仍然有这东西。约在1976或1977年,我见过一只还是铜甲”(年纪大的)的,捕者自述在金涵水库上的公路边捕到,大约就是金涵乡院后村的地界里。总体上看,那时,野兔、野猪、麂子、山羊等食草类动物要比现少,尤其野猪比现在少很多。但是那时残留的一些动物,现在可能绝迹了。比如,原来住在溪里村的老农德志说,豪猪,合成氨厂未建时,大金溪边上的旱地中就有,现在显然没有这种野兽了。野兽减少,其中一大原因是因为人们的猎杀。文革期间,曾有文件要求捕猎,以供出国创外汇之用,甚至规定了收购虎、豹、水獭等动物毛皮的奖励办法(1971年底,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根据国务院(71)国发文88号的精神,下发了《关于发展狩猎生产的通知》(1971年12月25日,闽革产(71)484号)。宁德县革委会于1972年初也转发这份文件。文件中说,七十年代以前十几年,福建省每年平均提供四、五万张野生动物毛皮,最高年份达到7万张,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外汇。文件要求“进一步树立为革命狩猎”的思想,鼓励社员利用工余时间进行狩猎,决定“对虎豹类皮、水獭皮”等5种,每1元奖给布票3尺。还可凭大队证明,购买猎枪、子弹。“文革”中收缴的猎枪,经公社以上单位研究后,也可返还给个人。)。但是,一种物种的消失,更重要的可能是自然环境的变化。
当时,尽管金溪边上建成了工厂,但在七十年代中期,溪河里还有不少鱼。1975年12月那场大雪过后一天,公社茶场里羊群放牧到合成氨厂后的“溪里”峡谷。放羊的少年(场里有二、三个少年轮流与七、八个知青搭配牧羊,两人一班)在水中拾到一只尺把长,冻得半死不活的“溪滑”。牧羊归来,路过地区造纸厂,被人见着,用八元钱买走。“溪滑”就是大花鳗,在大海与山涧间回游。在溪里能拾到此物,说明当时河流是没有污染的,也说明这峡谷生态环境是很好的。但不知此鱼如何越过东湖塘的二十五孔闸。或许是在1969年东湖塘溃堤时,寻回祖先故里却无法返回海洋的冒失者,或是1964年海堤合垅前留在山涧的原住客。此前,还听说有一尾巨大的“溪滑”从北门电站(今军分区对面)压力水管中流落,缠住北门电站的水轮机,后被工人捕获。这事情发生在六十年代。这尾鱼当然也是从大金溪上游误入金溪渠道。
八元钱是一大笔钱,大约是六、七十斤地瓜米的价格,或可置一身新行头。对于农家少年来说,如同今人中万元大奖一样的感受,一同去放羊的陈姓知青有些遗憾。买此鱼者,听说是一位福州人,技术员。这人用一个月六、七分之一的钱买了稀世珍肴,算不得奢侈。
副食品
除食粮之外可吃的东西,都叫“副食品”。七十年代初期,用米面制作糕饼糍粑之类,自食不要紧,但用于出售,是不名誉的(1970年7月28日,县革委会生产指挥部《抓革命促生产简报第14期(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批评“粮食复制品大量上市”。南埕大队和漳湾大队有人,“拿着香烟、糕饼、薄荷糖到田间换粮食”,“每天蒸松糕四床,拿到粮食收购站去卖,每斤换大米两斤,每人一天就赚大米20多斤”。),办宴席也是不名誉的。
糍粑是金溪平原农民最喜欢的食品之一。据说,金涵一带结婚办酒席,头一碗是糍粑,次一碗是煮肉。酒席好不好,东家是不是慷慨,看糍粑分量足不足,煮肉够不够肥。煮肉切成四方形,边长二寸有余,甚至三寸,夸张的说法,是挑起肉块时,箸尖微微下沉。但是,插队四年,我没有见过一次这样的酒宴。倒是听过许多个打赌吃糍、肉或其他食品的故事,这样的拼命故事,能流传很长一段时间。
糍粑用粘性大一些的粳米(称为“大冬”)舂打。茶场里就有一方石臼和一只安了木柄的石杵。但只看过一次打糍粑,起因也忘了。一般来说,做糍粑有过节或办喜事的象征意味,公家活动很少或不做糍粑。畲族善做“糯米糍”,舂的力度就小得多。有一回,一位农民在冬至这一天请我吃糯米糍,一碗烙得烫嘴的糍和一碗盐煮碎五花肉汤,原汁原味,相当可口。但糍却白中带乌,与过去家里吃的白中带黄的不一样,不知何故,心中藏了些疑惑。许多许多年后,蓦然想起,这是因为农民家贫,铁锅平素无油,烙出的糯米糍当然乌突突,象是沾了尘土一般。
肉食很少。在茶场二三年,分配猪肉好像只一次,每人二斤五花肉。场里只有三口锅,一口煮猪食,一口蒸饭(以上两口锅有时洗净混用),一个小锅搞菜,因此排队煮肉,迟的轮到近半夜。羊肉每年吃一次,都在春季。将一个月龄的小公羊淘汰,凭场员意愿取多取少,说是吃了有力气“做春(开始春耕农忙)”。这些肉,算在此人当年支出中,叫“通伊(算他)借支”。公羊羔肉,最为高级,味极美,富有热量。但是场里没有那种先吃再讲管他洪水弥天的人物,因此每人取的都不多。牛肉只见场里农民吃过一次,是杀了一只将要死的母牛。两位刘姓青年合取(也是“通伊借支”)一只牛脚(从牛蹄到膝关节下的部位),拾掇细毛大骨半天,放在瓮中,点燃稻壳焖一夜。不料焖过了头,次日瓮中只余一堆散骨和一瓮的浓汤。因此两人情绪很不好,面沉似水。吃狗肉的回数倒多一些。场里两只母狗,生崽时有几个人抢着领养,却不喂狗,任其到处抢食脏东西。只待长成三四斤、四五斤,就杀狗吃肉。有些老农对此情况相当生气。
城里人那时肉食也少。每月每人半斤肉票,1976年新年时,市面上没有猪肉卖。
食物中鲜鱼很少,鲜海鱼更少。在山区、在茶场,几年时间,只见农民吃咸鱼,很少见他们吃鲜鱼。本来那几年宁德一县每年捕黄花鱼有三四百吨,但市场上很少见,可能收购之后统一运往他处,或加工成鲞。再或者,农民手上没有现金,赊销的传统又没有了,所以他们吃不到这一年一度立夏后的极品鲜味。农民家庭,淡水鱼也只在过年时享用。有个来自金涵水库后高乾村的农民,用鲢鱼煮成“冻”,装在陶盆子里,正月初六那天请大家吃,相当美味。后来才知道,这一道食品西乡一带农家过年是必备的。
黄花鱼鲞肉质筋道,味路纯正,呈红褐色,无需包装也可放很久,现在不会有这种食品了。在当时却是平常食物,我常从家中带着。农民吃得起黄鱼鲞,但更多的是廉价一些的咸魺、咸带鱼(宽五、六公分也是便宜货)、“虾苗”(小鱼小虾制成的咸酱,或许不能归于“鱼”类)等。装“虾苗”,是一种径有尺把的瓠瓜老壳制作的圆状容器,用竹篾扎紧,挑在扁担或枪担上。最次是一种咸过头的“油筒鱼”。
水产公司有时将库存的咸鱼经营坏了,就卖给农民当田里肥料用。品质在肥料与食物之间,价格就十分便宜。“咸油筒”就是这样的角色。油筒鱼,鳀类一种,多油脂,鲜鱼煎时,油越来越多。但这种油脂不是太适合人身体所需要,有刺鼻气味。腌制之后,味道好多了,但比起咸带鱼等,仍等而下之,不见得很多农民家庭买这种下饭菜。同房间一位单身汉常买“咸油筒”,只挑指甲盖般大小的一块鱼肉就能下一顿饭(地瓜米)。平素放在一个大木楻中,用簸箕覆盖。一旦翻开簸箕,硫化氢气味弥漫全屋,十分呛人。我也曾买过一回,味道极冲,远超腐乳、臭豆腐之类,故而下饭功用明显。但不久后开始烂脚,从大姆指开始,朝着膝盖的方向,隔十来公分的距离,一个脓肿接一个脓肿,此消彼长。可见真是不适合人类食用的东西。
酒
蕉露是县酿造厂以“无米制作法”生产的酒,呈暗红色,很甜,有香气,度数要比米酒高,一斤五角六分钱。我曾经在造纸厂的店铺买过六角钱,睡前一口气喝完。次日醒来,头痛欲裂,又见枕头几乎被鼻血洇满,病了二三天。后来知道这酒用山上的“狗七条”、“白拉刺头”做原料。前者可能是一种蕨科植物的块茎,油条般大,长满着金毛(据说可以止血),名叫金毛狗脊。也可能是另一种叫狗脊蕨的植物块茎。这些块茎中,的确有一些些淀粉,但是“白拉刺”(也叫“金刚刺”,学名不详)的根茎既硬且小,只有小号火腿肠的样子,为何可以酿酒,当时就费解。很多年之后,听酿造厂(城关人叫“酒厂”)老蔡说,成酒之后还有勾兑,加上一些香精之类。按今天标准,一些指标超标多少倍也不知道。
米酒也有,但在当时,恐怕算是奢侈品,没有见过一个农民平素吃米酒解乏。酿酒,特别是酿酒出售,几乎是一桩行走于“法律”边缘的事情。但在过年时,酒是足够的,偶然也有喝醉的。
“义务工”
我在山区生产队时,恰好修村里的公路。请来金涵水库测量队人员,测好路线,算出土方。不久开工。路有几公里长,基本都是土方,但路面挖得很宽,因而土方量很大。挖到离村一二公里外时,路程远,就要早出工。冬季夜长,极黑的清晨,村干部用锣声和高亢的声音,惊醒全村人,“做马路——下饭啊”。年青人好睡,有时惊出汗来。公路穿过一片树林,大部分是柯木,但也有不少其他树种,因此林中生态景观丰富。有一种发荧光的蘑菇,还见过七叶一枝花——很珍稀的蛇药,当时,都堆在土堆里了。从公路里侧将土方推到公路下,只几米的路,用土箕装、再倒,很花工,于是有人想出用耙拖土的办法。就是在耙齿上装木板,前面两人拖,后面一人扶,果然较率高了许多。有一回正拖着,公社里一行人来视察。见此发明,几个干部不吝美言,纷纷评论。但主要领导只点着头说,“细好、细好”,再不多一个字,如当时的最高指示,某某好,某某好一样。“细”,就是耙的方言。当时,连续劳动几个月,其实我已经“过力”(后来回家休息很长一段,力气也没有恢复),将人当牛来用,其实人比牛力气小得多。当时,拖耙极吃力,因此心中颇能理解炎炎赤日之下,农夫的辛劳感觉。
1974年底或1975年春,又在金涵水库一个来月,拖土,挖土,挑土。拖土用板车,运到大坝上。那时,好像大坝长到三分之二高了,因此要用“爬坡机”,就是用一种土制的缆车。钩子勾住板车(记得就勾在板车的把手上),从木制斜道上拖至坝面。坝面上土是松软的,此时拖车极吃力,边上打夯的人大声呵斥,指东指西,有时挺远的,甚至还要再拉上一、二十米,几乎将吃奶的力气都用尽。下坝时空车,需将轮子脱出板车架外,增大阻力,沿着之字形状的木栈道慢慢下来。我在此曾上下许多次,上下都十分吃力。
施工劳动的组织管理方式相当复杂,当时我只是成千上万民工中一员,年纪也不大,没有多少记忆。但以我个人经验,工地上的劳动收入,仍然由生产队支出,一是工分,二是现金。现金很少,似乎不足以支付每日伙食,工分则合入年底分配。当年,村里同时修几公里长的公路。大量无产出的工分(群众称“义务工”)加入年终分配,加之生产收益极低,这一年年底,我所在的第二生产队,工分值最低,十分只合七分钱,据说创了全省的记录。
拦柴
大约1976年春耕开始后不久,公社派人在茶场边的山道上设卡拦木材。一般情况下,由公社派个人来,可能是公社“市管组”的人,叫上“民兵”——就是场里几个青年人,设伏拦截从山上偷运而来的杉木以及桶、凳子、锅盖等木制品。公社茶场边的一条石阶道通往蔡洋几十村,远至洋中、古田和罗源的一些乡村。舍此之外,这些地方要到宁德县城或海边的一些村庄,没有其他路可走。那时,没有大白天扛木材的人,“拦柴”的时间段,一般是从午夜开始到清晨。
睡梦之中,常听得人声嘈杂,拦下的人、木材就放在茶场尾前的空坪上。没有见过农民与“执法者”吵架争执的,经常是哭求。有天清晨,见一位老者(按现在标准,也就五十挂零的中年人),面色苍黄,一脸油汗,衣衫褴褛,见人就作揖。我正早起煮猪食,问了他从哪里来,何时动身等闲话,居然要双膝跪下。后来知道,这人是虎洋(远在洋中方家山一带)人,半夜动身,扛一条百十来斤的杉木,走了三十来里的山路,将到平原地带,不想被抓。也不奢望讨回杉木,只想讨一碗饭。后来,做饭的给了他一碗捞地瓜米的汤(地瓜米在蒸之前,先要在沸水中捞半熟,内中有些地瓜米)。这人喝了之后,流着泪走了。
但不是完全没有争执的,毕竟是求生存的活计。有一回,我被抽来守夜,下半夜里,听得半山上有人声,于是与二三位民兵一同追上山道,快追到接近山项的蔡洋亭时,将三四个挑木桶的截住,意气风发带下山来。后来,其中一位黄姓老农悄声告诉我,这几人,也是虎洋人,有些武术,弄不好,会被他们“做”下山崖。头一次配合“拦柴”,公社一个干部就交待,切不可站在杉木一边。不然,扛杉木的可能一下子将杉木抛下肩膀,夜间看不清,就可能出事故,砸断了脚都不一定。
场里农民,尤其是有年纪的农民,不做半夜拦木头这类事情,我想是道德感使然。所谓意气风发之类,是建立在他人绝大痛苦基础之上。不论偷伐山林一类的事情该不该抓,在生存压力之下,如此艰难的日子,足以触动人的良心底线。
以民兵治民,是“上海经验”。1975年底有一次全省性民兵打击“投机倒把”的活动,我听说城关继光街的基干民兵甚至抓到单石碑来(单石碑当时属于北门三元大队的某个生产队,不属于金涵公社)。后来在资料中看到,当时,宁德县民兵在活动中搜得“金银15件、猪肉714斤、鱼类2957斤、活毛羊1只,私酒70斤……电工器材168件,钟表和的确良布料等(《福建省宁德县民兵指挥部简报第二期“11.30”统一行动情况》。)”。此类活动此后颇有几次。家里的金银都可能被“抓获”,况且是木头。
供销社
七十年代初,设于涵道村的公社供销社几乎是金溪平原上唯一的商业网点,也是周边山区村庄的购物中心。店里有一排长约二十米的柜台,柜台只有一小段是玻璃的,卖日用品,如肥皂、毛巾等,其余木头制成,漆着“清油”(桐油),呈嫩黄色。供销社的商品,从布匹、热水瓶、脸盆,到农药、铁耙、棕衣。生意似乎不太好,二、三个营业员寡言,表情也不丰富。其中有青年女营业员,是公众人物。可能因为从不晒太阳,因此白皙,异于常人。全公社的男人都有权就近观赏,甚至搭讪,但永远隔着柜台,正如流浪汉面对一份昂贵的菜单。
后溪村也有一处“供销社”。柜台与公社的几乎一个样子。油行村的供销社也有一个木制的柜台,同样宽,只是长度不一样。卖的货物基本相同。听说,二十多年前,路未通,后溪供销社卖化肥,要从三十里外涵道村挑来,后来池颂光市长跑到罗源协调,改成从十里外的中房调化肥。许多年后,农民依然念叨这事情。后溪村供销社,六七年前路过,看上去还与二、三十年前一个样子,只是卖的新东西多了些,柜台更旧。
电话
七十年代的电话用“摇把子”,电话机边都有个木匣子,装着两只长约一尺、茶缸子粗的大电池,手柄一摇,一条线上的几只电话都响。接听者先要听清找谁,无关者放下,有关者接话。倘若无关者不放下电话,那么这通电话就有两人以上在听。一般就近串连电话,如蔡洋岭一线,从最远的后溪开始,依次接上茶洋、菰洋、浮坪、中岗、公社茶场,直到涵道村边的公社里。
美景
1975年春节前几天,公社通知全社的下乡知青到灵坑村集中,县里领导来慰问。辛苦半年,可以放松,兴奋之情可以想象。于是走山路去灵坑村。天气晴朗,远山寂寥。峰回路转,突然见村子就在山下。时值涨潮,蔚蓝的海水紧傍着村子,村边泊着数十条船,支支桅杆错落。村子不小,乌瓦黄墙,密密排列,村边公路似金带飘向远方,公路上行着玩具般大小的车子。冬季白天短,下午三时许,阳光略西斜。明亮阳光照定海湾中央二、三条船,张着白色和褐色的帆,拖着影子,似乎一动不动。海湾的远端,青黄色夹杂的低山或岛屿,镶于蓝色的天际线上。
山很高,因此很静,听不到一点声响,同行的人,都静静地看了会儿村子和海。很多年后,有灵坑村的朋友对我说,西陂塘围垦前,灵坑村是鱼米之乡。因为我从半天空俯瞰过这个村子,所以,从内心赞同这种说法,同时还认为那个永远消失的画面,是一幅无与伦比的美景。
戴帽中学
七十年代中期,金涵公社有两所中学,都“挂”在小学校里。一所是金涵中心小学的初中班,两个年级,各一班。一位姓王的朋友当体育教师兼初二年级的班主任,学生篮球打得不错。学生是这一带工厂、机关单位的子弟,还有各村的小学毕业生。当时恐怕没有人特意将子女送到城里的宁德一中读初中。
另一个中学在金峰大队。金峰大队有十几个村,近两百户人家,七八百号人口,星散在水库后的“金字峰”山上,大的村庄,屋子也不会超过二十座。这些村子,原本连小学生都很少,但两个知青在此当民师,从小学教到毕业,接着就办初中班。1976年春,我到过金峰大队的院坪村(从水库后爬山一个多小时),见一幢大屋子的二楼,坐满了学生,印象中总有三十来人吧。“教室”只进一面光线,相当昏暗,似乎黑板的位置还是逆光,但学生神情十分专注。次年底,这个班的男教师考上学校,走出农门,女老师也招干进城,初中班就结束了,所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金字峰上各村早早地向平原迁徙,到本世纪初,山上已基本无人常住。七、八年前,这个村姓雷的会计告诉我,他就是这个初中班的学生,因为有初中,后来村里才有高中生。
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观,经常是个人在历史上作用微不足道,但“必须清楚地看到一个人、一个社会或是一个文化的可塑力有多么巨大”(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这两位年青人为千古不变的山区引进了新的文化,多少改变了这小小地方一代人的生活方式。男知青姓黄,女知青姓吴。后来,恢复高考后,一位是我的同学,一位是同机关大院的熟人。
农田基建
农业学大寨是七十年代宁德县农村最重要的活动。年年都要兴起高潮。这活动主要内容是农田基本建设。如平整水田,修水利,建田间道路,改造低产田等等。不仅平原,连山区也平整水田,农民称为“并丘”。这种活动十分艰辛,劳动量巨大,若无机械,必定要组织千军万马,这只有在七十年代才做得到。
我最早参加平整土地,在“石马洋”,大约在罐头厂、茶厂与金溪之间的水田中。水田中散布着牛马般大小的黑石头,这是洪积扇的特征。平整时,有人炸开并移走这些石头,而大多数人就是在田里将泥水搬来搬去。城里组织人员到石马洋帮忙,也包括了我们这些小学生。天气阴沉寒冷,一个姓辛的同学当时就喊关节痛。收工时,几十柄锄头胡乱堆在泥水中,我认不出自己的,又不晓得随意拿走一把,于是空手回家。因为丢了借来的锄头,一路垂头丧气。姓辛的同学后来得了白血病,他是班上最聪明的同学,山东莱阳人,其父亲在邮电局当领导,因为站“错队”,当时正在县里的学习班中被重点整治。
后来,特别是插队之后,参加过很多次平整水田的劳动。有的水田烂泥齐腰,也要并丘。当然并过之后,水田面积大了,改造了排水,田的等级肯定提高。1975年冬季那一场规模空前绝后的平整土地活动,我们茶场没有人参加。那天下大雪,冷得不行,清晨人人都在睡着,公社干部老林突然将大家喊起,说是千军万马都在平整土地,我们也要表态,于是大家拿着锄头,在造纸厂后的山路边挖了半天土,金溪平原上赤足浸在水田冰碴里干活的农民更加痛苦。这是金溪平原上所有够年纪的农民记忆深刻的一幕。
持续数年浩大的劳动场面,或许永不再来,但其进步的一面需要公允评价。
从七十年代初开始,全县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进行田园化的改造,平整了大量的梯田,改造了原来占全县水田总面积七成以上的低产田,这为八十年代之后农业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同时,完成了大量的防洪堤、水库、渠道以及围垦工程。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施工、完工的围垦工程共有19处,共扩大了耕地面积20800余亩,占当时全县水田总面积的13.8%(中共蕉城区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宁德县代表大会资料<总结经验,立场改革,为振兴宁德经济而努力奋斗——在中国共产党宁德县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杨家盛,1984年10月13日。)。这些家底,也为当下工业化、城市化奠定了重要的根基。
可谓苦一代人,利几代人。
口粮
口粮是七十年代农民最主要收入。生产队一般年中早稻收割后,按人口分配一次稻米。年终分配地瓜米(番薯丝)和晚稻,好一点的大队,分多一些晚稻。单身汉或劳动力多而人口少的家庭,粮食充裕些。我在茶场,每年可分到大约五百余斤口粮,内中约有三百斤左右是稻谷。口粮都放在仓库里,全体吃食堂,每顿自报吃几两地瓜米,由专人(两个人)监秤,置于饭甑(为一木桶)中蒸熟。开饭时,另由专人执一只桃型木柄,专职盛饭,当面称重。将一碗“泥”得尖尖的地瓜米,放在盘秤中,称出毛重,再刨去碗的重量。地瓜米蒸熟后,似乎要重上四倍多些。餐餐如此,虽然麻烦,但以程序正义保证实体正义,却没有口舌。吃白米,则自备饭盒,自已放米加水,放在蒸笼里。农民只在过年和早稻收割后的十来天吃大米,一般的人家,吃大米的时间(甚至包括大米掺地瓜米),全年不会超过一个月。稻谷一百斤,出米六十五到七十斤,吃是好吃,但数量少。因此,农民群众愿意用一比一比例,拿稻谷(不是大米)换地瓜米。这在当时是常见的事情。因此知青吃大米次数要比农民,特别是比有家口的农民多得多。据资料,1976年全县农民的平均口粮只有336斤,农业人口平均经济收入只有45.6元,远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蒸汽催芽(《杨家盛同志在全县公社脱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7月3日)
七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水稻生产发生革命性变化。1974年从夏到秋,我在一个山区生产队,参加过一季高杆单季稻的薅草及收割农事。此后,见都没有见到高杆水稻。到了1977年春,第一次见试种的杂交水稻,不料几年后就靠着杂交水稻吃上了无忧的饱饭。
其实从六十年代开始,宁德县水稻有个“三化”的过程,就是单季改双季,高杆改矮杆、间作改连作。加上开始大量使用化肥,产量增加不少。不过许多地方种双季稻,一般年景下,无霜期总不够长,晚季收割遇上“寒露风”,则出不齐穗多瘪粒歉收乃至绝收。于是只有将早稻播种提早。早年间平原沿海是清明播种,立夏插秧。后来提早到春分播种。稻种用温水浸,好出芽。山区无霜期短,就再提早到“雨水”节气播种。这时天气冷,出不了芽,就将稻种浸湿,置于密封房间内,用一口铁锅加水用稻壳焖烧,制造出一个类似桑拿的湿热小环境,叫作“蒸汽催芽。”
在山区生产队那年,我住二楼,楼下恰是蒸汽催芽的房间。农村土房子楼板就是一层,缝隙还不小,因此其实人也在被桑拿之列。次日晨起,见被子与草垫湿得出水。好在那时年青火气大,与同室之朱、丁等三人皆无事。但稻种出了芽不一定成得了秧,天冷就烂。秧一烂,为赶农时,即刻就要再下种催芽。如此甚至有再三再四的。1976年有倒春寒,近清明了,还有“西伯利亚寒流”。据说当时全县只因早稻烂秧,就损失了四百来担种子。
当时,硬是要在山区种双季稻,听说海拔近千米的天湖村也种了双季。这样就要做些出奇的事情,最终也不能证明“人定胜天”。
劳动送饭
抢收早稻和抢种晚稻的“双抢”时节,生产队统一送饭下田,以抢农活,金溪平原一带称“食清昼(吃冷饭)”。其实往往是一年中吃得最饱的一餐。我在山区生产队时,记得每个劳力按一斤半米的份额计算。称出稻谷,自己加工,先是砻(一种现在很难见着的磨一类的加工器具)米,再舂,筛,做出米来统一蒸煮。米是单季稻品种“白早”,这个品种米粒很大,如今可能连同“红早”一样已经绝种了。煮法用“捞炊”,就是先在大锅中煮得半熟,再置于蒸笼中炊熟。米饭呈颗粒状,极香。当然一斤半的米,大部分人一顿吃不下。不少人带了家小,分一碗米饭是没有人当面非议的。
在茶场里,也有几回送饭到田头。场里只一二个儿童,妇女也不下地,因此,尽管各人饭量有差别,但随吃随添,按每人一斤米的份量,能让每个人都吃得很饱。下饭菜只是油饼、油条、酸菜汤之类。有一回分猪肉,就不合在集体一起吃了,而是称出炊好的米饭,连同两斤猪肉,按人头分配。又有一回到金溪村前水田劳动,一位姓孙的少年——茶场里唯一多子女家庭的老二,吃量超过成年人,最后还喝木桶中盛的酸菜汤,鼓起的肚皮向左侧歪去,不得不让人担心出问题。画家黄永玉说,“小孩子的肚量,比圣人的肚量还宽阔”,这样惊人的饭量,是因为,许多人一年中,只有数回,甚至从来没有过吃饱大米饭的美好感觉。
这样的吃法算是正常的。不正常的生产队也有。一些地方群众对集体经营失去信心,吃光喝尽。据资料,当时,八都大队某生产队社员出工时,“点心”要吃米酒、扁肉、小炒肉,仅吃喝一项,就占去总收入的23.7%,几乎等于全年的农业生产成本。洋中凤田大队某生产队,1977年干部社员吃掉的“点心粮”就有90多担,分光吃尽,使得当年十分工分值只有2角2分(引自《继续揭批四人帮,深入开展两打斗争,落实党的政策,改变干部作风,为速度发展我县农业而努力奋斗——吴子金同志在县三级扩干会上的讲话》1978.10。)。
产生这种现象,有着更深一点的原因。一些农民认为,劳力少而人口多的家庭,在分配中多分了粮食和其他实物,即使超支欠款,也得到了实惠。甚至有单身汉认为,集体经营是在帮别人养家,有被剥削的感觉。这是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在当时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七十年代初,宁德县领导批判了农村分配时“搞按劳分配”的行为,但在七十年代中期后认为要坚持“按劳分配”(1968年底,宁德县革委会通过对年终收益分配工作的规范,恢复了部分农村“文革”武斗期间开始解体的集体经营体制。县革委会针对当时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鼓吹口粮按劳分配,分光吃光,不卖或少卖余粮,副业不归集体,搞投机倒把”的现象,特别指出,“如再搞‘按劳分配’者,要追查责任,要教育群众,认识这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见《宁革生财》(68)004号《关于分配1968年农业税征收任务的通知》。 1972年年底,宁德县革委会发文,指出,“搞好年终收益分配工作是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体现”,明确要求按照省委的“十六条”规定,以生产队为单位,逐条落实。“要弄清‘物质刺激’、‘工分挂帅’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界限”。见宁革生(72)第191号《关于1972年年终分配几个问题的通知》。 1975年7月6日,宁革(75)90号《关于夏季预分工作的意见》明确地提出,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对劳力外流,副业单干及弃农经商人员和其所负担的人口的口粮,“可留队里,待回队做出适当处理后,按月拨给”。),这种在根本问题上没有标准的现象,说明集体经营这种制度的确不适合于当时农村的生产力状况。农民讲实际道理,将劳动成果吃到肚里,心甘情愿,至于往后如何过日子不管不顾。这当然是一种相当阴暗而悲观的心理。
生态
要说六七十年代的生态环境好不好,较为复杂。那时几乎没有“三废”污染。空气、水、土地特别干净,大气能见度高,水质清澈,地里即便用了农药化肥,恐怕也比如今重金属、化学制品等污染要来得轻。但是,山上草、树都比现在少,特别是村庄田野附近的山上。植被稀疏,树少草少,这是因为每家燃料都用柴草。金涵山区农民一大收入,就是砍柴割草,有空时挑到城内卖了,得几只咸鱼当家。手头宽一些,有的还带几块光饼之类。“杆蒙”(芒箕草一类)一担在城中约值一、二元,而咸带鱼每斤三、四角钱,咸虾苗一斤仅一角多钱。
各家各户都在山上割蕨草,山上光溜溜的。大树在1958年时砍得差不多,到七十年代,也没有长茂盛。记得春耕时,要割些蒿(禾本科芒草)的嫩叶给牛当点心,还要走好几里路到“溪里”(今大金溪上游峡谷)深处才有。割蒿叶,工分既高,又有米一斤、现钱一元二角补贴,是很少的工种。但也很苦,无论本事多高,手终究要被割得血丝道道。
野生动物不好说。对比现在,有的少有的多。在金涵平原和山区,听过几次关于山上动物的事情。一是公社茶场后高海拔的中前大队八斗丘生产队,几个人打死一条大蛇。这蛇冬天不知为何跑了出来,钻到一家农户灶间的柴草堆中,被人惊动后,又自行爬出院子。正在翻过院墙时,在地里干活的一群人闻报赶到,用锄头打死在屋边。据说有一张半“篷”那样长,大约七米左右。这事情按推算,大约发生在六十年代中期或更早些。其二,一位后溪村人说,有一天在山垅中“拾水”(看水),一条大蛇在对面坡草丛中窜过。被此人惊动,跌到水田里,溅起的水花飞过一丘田,洒到这位吴姓农民的头上。问:“到底多大?”这位在茶场里的“学习班”的成员只笑不言。这事情发生在武斗那一年。其三,大约1974年秋,一只猛兽在金浿村头,半夜时咬走一只狗,留下一条长半米多的爪痕。村里有人说是“老虎”,但并没有人见到这只猛兽。差不多也在这一段时间,一队几个人在金邶寺前的水田里干活,巧遇一只半大的野猪窜进水田里。水田是烂泥田,因此跑不快,被十几个人追打,后成肉食。其四,听茶场里一位姓刘的中岗村农民讲挖裸狸(穿山甲)成功的经历。记得似乎说是七十年代初的事情,但不能肯定。不过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山上的确仍然有这东西。约在1976或1977年,我见过一只还是铜甲”(年纪大的)的,捕者自述在金涵水库上的公路边捕到,大约就是金涵乡院后村的地界里。总体上看,那时,野兔、野猪、麂子、山羊等食草类动物要比现少,尤其野猪比现在少很多。但是那时残留的一些动物,现在可能绝迹了。比如,原来住在溪里村的老农德志说,豪猪,合成氨厂未建时,大金溪边上的旱地中就有,现在显然没有这种野兽了。野兽减少,其中一大原因是因为人们的猎杀。文革期间,曾有文件要求捕猎,以供出国创外汇之用,甚至规定了收购虎、豹、水獭等动物毛皮的奖励办法(1971年底,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根据国务院(71)国发文88号的精神,下发了《关于发展狩猎生产的通知》(1971年12月25日,闽革产(71)484号)。宁德县革委会于1972年初也转发这份文件。文件中说,七十年代以前十几年,福建省每年平均提供四、五万张野生动物毛皮,最高年份达到7万张,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外汇。文件要求“进一步树立为革命狩猎”的思想,鼓励社员利用工余时间进行狩猎,决定“对虎豹类皮、水獭皮”等5种,每1元奖给布票3尺。还可凭大队证明,购买猎枪、子弹。“文革”中收缴的猎枪,经公社以上单位研究后,也可返还给个人。)。但是,一种物种的消失,更重要的可能是自然环境的变化。
当时,尽管金溪边上建成了工厂,但在七十年代中期,溪河里还有不少鱼。1975年12月那场大雪过后一天,公社茶场里羊群放牧到合成氨厂后的“溪里”峡谷。放羊的少年(场里有二、三个少年轮流与七、八个知青搭配牧羊,两人一班)在水中拾到一只尺把长,冻得半死不活的“溪滑”。牧羊归来,路过地区造纸厂,被人见着,用八元钱买走。“溪滑”就是大花鳗,在大海与山涧间回游。在溪里能拾到此物,说明当时河流是没有污染的,也说明这峡谷生态环境是很好的。但不知此鱼如何越过东湖塘的二十五孔闸。或许是在1969年东湖塘溃堤时,寻回祖先故里却无法返回海洋的冒失者,或是1964年海堤合垅前留在山涧的原住客。此前,还听说有一尾巨大的“溪滑”从北门电站(今军分区对面)压力水管中流落,缠住北门电站的水轮机,后被工人捕获。这事情发生在六十年代。这尾鱼当然也是从大金溪上游误入金溪渠道。
八元钱是一大笔钱,大约是六、七十斤地瓜米的价格,或可置一身新行头。对于农家少年来说,如同今人中万元大奖一样的感受,一同去放羊的陈姓知青有些遗憾。买此鱼者,听说是一位福州人,技术员。这人用一个月六、七分之一的钱买了稀世珍肴,算不得奢侈。
副食品
除食粮之外可吃的东西,都叫“副食品”。七十年代初期,用米面制作糕饼糍粑之类,自食不要紧,但用于出售,是不名誉的(1970年7月28日,县革委会生产指挥部《抓革命促生产简报第14期(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批评“粮食复制品大量上市”。南埕大队和漳湾大队有人,“拿着香烟、糕饼、薄荷糖到田间换粮食”,“每天蒸松糕四床,拿到粮食收购站去卖,每斤换大米两斤,每人一天就赚大米20多斤”。),办宴席也是不名誉的。
糍粑是金溪平原农民最喜欢的食品之一。据说,金涵一带结婚办酒席,头一碗是糍粑,次一碗是煮肉。酒席好不好,东家是不是慷慨,看糍粑分量足不足,煮肉够不够肥。煮肉切成四方形,边长二寸有余,甚至三寸,夸张的说法,是挑起肉块时,箸尖微微下沉。但是,插队四年,我没有见过一次这样的酒宴。倒是听过许多个打赌吃糍、肉或其他食品的故事,这样的拼命故事,能流传很长一段时间。
糍粑用粘性大一些的粳米(称为“大冬”)舂打。茶场里就有一方石臼和一只安了木柄的石杵。但只看过一次打糍粑,起因也忘了。一般来说,做糍粑有过节或办喜事的象征意味,公家活动很少或不做糍粑。畲族善做“糯米糍”,舂的力度就小得多。有一回,一位农民在冬至这一天请我吃糯米糍,一碗烙得烫嘴的糍和一碗盐煮碎五花肉汤,原汁原味,相当可口。但糍却白中带乌,与过去家里吃的白中带黄的不一样,不知何故,心中藏了些疑惑。许多许多年后,蓦然想起,这是因为农民家贫,铁锅平素无油,烙出的糯米糍当然乌突突,象是沾了尘土一般。
肉食很少。在茶场二三年,分配猪肉好像只一次,每人二斤五花肉。场里只有三口锅,一口煮猪食,一口蒸饭(以上两口锅有时洗净混用),一个小锅搞菜,因此排队煮肉,迟的轮到近半夜。羊肉每年吃一次,都在春季。将一个月龄的小公羊淘汰,凭场员意愿取多取少,说是吃了有力气“做春(开始春耕农忙)”。这些肉,算在此人当年支出中,叫“通伊(算他)借支”。公羊羔肉,最为高级,味极美,富有热量。但是场里没有那种先吃再讲管他洪水弥天的人物,因此每人取的都不多。牛肉只见场里农民吃过一次,是杀了一只将要死的母牛。两位刘姓青年合取(也是“通伊借支”)一只牛脚(从牛蹄到膝关节下的部位),拾掇细毛大骨半天,放在瓮中,点燃稻壳焖一夜。不料焖过了头,次日瓮中只余一堆散骨和一瓮的浓汤。因此两人情绪很不好,面沉似水。吃狗肉的回数倒多一些。场里两只母狗,生崽时有几个人抢着领养,却不喂狗,任其到处抢食脏东西。只待长成三四斤、四五斤,就杀狗吃肉。有些老农对此情况相当生气。
城里人那时肉食也少。每月每人半斤肉票,1976年新年时,市面上没有猪肉卖。
食物中鲜鱼很少,鲜海鱼更少。在山区、在茶场,几年时间,只见农民吃咸鱼,很少见他们吃鲜鱼。本来那几年宁德一县每年捕黄花鱼有三四百吨,但市场上很少见,可能收购之后统一运往他处,或加工成鲞。再或者,农民手上没有现金,赊销的传统又没有了,所以他们吃不到这一年一度立夏后的极品鲜味。农民家庭,淡水鱼也只在过年时享用。有个来自金涵水库后高乾村的农民,用鲢鱼煮成“冻”,装在陶盆子里,正月初六那天请大家吃,相当美味。后来才知道,这一道食品西乡一带农家过年是必备的。
黄花鱼鲞肉质筋道,味路纯正,呈红褐色,无需包装也可放很久,现在不会有这种食品了。在当时却是平常食物,我常从家中带着。农民吃得起黄鱼鲞,但更多的是廉价一些的咸魺、咸带鱼(宽五、六公分也是便宜货)、“虾苗”(小鱼小虾制成的咸酱,或许不能归于“鱼”类)等。装“虾苗”,是一种径有尺把的瓠瓜老壳制作的圆状容器,用竹篾扎紧,挑在扁担或枪担上。最次是一种咸过头的“油筒鱼”。
水产公司有时将库存的咸鱼经营坏了,就卖给农民当田里肥料用。品质在肥料与食物之间,价格就十分便宜。“咸油筒”就是这样的角色。油筒鱼,鳀类一种,多油脂,鲜鱼煎时,油越来越多。但这种油脂不是太适合人身体所需要,有刺鼻气味。腌制之后,味道好多了,但比起咸带鱼等,仍等而下之,不见得很多农民家庭买这种下饭菜。同房间一位单身汉常买“咸油筒”,只挑指甲盖般大小的一块鱼肉就能下一顿饭(地瓜米)。平素放在一个大木楻中,用簸箕覆盖。一旦翻开簸箕,硫化氢气味弥漫全屋,十分呛人。我也曾买过一回,味道极冲,远超腐乳、臭豆腐之类,故而下饭功用明显。但不久后开始烂脚,从大姆指开始,朝着膝盖的方向,隔十来公分的距离,一个脓肿接一个脓肿,此消彼长。可见真是不适合人类食用的东西。
酒
蕉露是县酿造厂以“无米制作法”生产的酒,呈暗红色,很甜,有香气,度数要比米酒高,一斤五角六分钱。我曾经在造纸厂的店铺买过六角钱,睡前一口气喝完。次日醒来,头痛欲裂,又见枕头几乎被鼻血洇满,病了二三天。后来知道这酒用山上的“狗七条”、“白拉刺头”做原料。前者可能是一种蕨科植物的块茎,油条般大,长满着金毛(据说可以止血),名叫金毛狗脊。也可能是另一种叫狗脊蕨的植物块茎。这些块茎中,的确有一些些淀粉,但是“白拉刺”(也叫“金刚刺”,学名不详)的根茎既硬且小,只有小号火腿肠的样子,为何可以酿酒,当时就费解。很多年之后,听酿造厂(城关人叫“酒厂”)老蔡说,成酒之后还有勾兑,加上一些香精之类。按今天标准,一些指标超标多少倍也不知道。
米酒也有,但在当时,恐怕算是奢侈品,没有见过一个农民平素吃米酒解乏。酿酒,特别是酿酒出售,几乎是一桩行走于“法律”边缘的事情。但在过年时,酒是足够的,偶然也有喝醉的。
“义务工”
我在山区生产队时,恰好修村里的公路。请来金涵水库测量队人员,测好路线,算出土方。不久开工。路有几公里长,基本都是土方,但路面挖得很宽,因而土方量很大。挖到离村一二公里外时,路程远,就要早出工。冬季夜长,极黑的清晨,村干部用锣声和高亢的声音,惊醒全村人,“做马路——下饭啊”。年青人好睡,有时惊出汗来。公路穿过一片树林,大部分是柯木,但也有不少其他树种,因此林中生态景观丰富。有一种发荧光的蘑菇,还见过七叶一枝花——很珍稀的蛇药,当时,都堆在土堆里了。从公路里侧将土方推到公路下,只几米的路,用土箕装、再倒,很花工,于是有人想出用耙拖土的办法。就是在耙齿上装木板,前面两人拖,后面一人扶,果然较率高了许多。有一回正拖着,公社里一行人来视察。见此发明,几个干部不吝美言,纷纷评论。但主要领导只点着头说,“细好、细好”,再不多一个字,如当时的最高指示,某某好,某某好一样。“细”,就是耙的方言。当时,连续劳动几个月,其实我已经“过力”(后来回家休息很长一段,力气也没有恢复),将人当牛来用,其实人比牛力气小得多。当时,拖耙极吃力,因此心中颇能理解炎炎赤日之下,农夫的辛劳感觉。
1974年底或1975年春,又在金涵水库一个来月,拖土,挖土,挑土。拖土用板车,运到大坝上。那时,好像大坝长到三分之二高了,因此要用“爬坡机”,就是用一种土制的缆车。钩子勾住板车(记得就勾在板车的把手上),从木制斜道上拖至坝面。坝面上土是松软的,此时拖车极吃力,边上打夯的人大声呵斥,指东指西,有时挺远的,甚至还要再拉上一、二十米,几乎将吃奶的力气都用尽。下坝时空车,需将轮子脱出板车架外,增大阻力,沿着之字形状的木栈道慢慢下来。我在此曾上下许多次,上下都十分吃力。
施工劳动的组织管理方式相当复杂,当时我只是成千上万民工中一员,年纪也不大,没有多少记忆。但以我个人经验,工地上的劳动收入,仍然由生产队支出,一是工分,二是现金。现金很少,似乎不足以支付每日伙食,工分则合入年底分配。当年,村里同时修几公里长的公路。大量无产出的工分(群众称“义务工”)加入年终分配,加之生产收益极低,这一年年底,我所在的第二生产队,工分值最低,十分只合七分钱,据说创了全省的记录。
拦柴
大约1976年春耕开始后不久,公社派人在茶场边的山道上设卡拦木材。一般情况下,由公社派个人来,可能是公社“市管组”的人,叫上“民兵”——就是场里几个青年人,设伏拦截从山上偷运而来的杉木以及桶、凳子、锅盖等木制品。公社茶场边的一条石阶道通往蔡洋几十村,远至洋中、古田和罗源的一些乡村。舍此之外,这些地方要到宁德县城或海边的一些村庄,没有其他路可走。那时,没有大白天扛木材的人,“拦柴”的时间段,一般是从午夜开始到清晨。
睡梦之中,常听得人声嘈杂,拦下的人、木材就放在茶场尾前的空坪上。没有见过农民与“执法者”吵架争执的,经常是哭求。有天清晨,见一位老者(按现在标准,也就五十挂零的中年人),面色苍黄,一脸油汗,衣衫褴褛,见人就作揖。我正早起煮猪食,问了他从哪里来,何时动身等闲话,居然要双膝跪下。后来知道,这人是虎洋(远在洋中方家山一带)人,半夜动身,扛一条百十来斤的杉木,走了三十来里的山路,将到平原地带,不想被抓。也不奢望讨回杉木,只想讨一碗饭。后来,做饭的给了他一碗捞地瓜米的汤(地瓜米在蒸之前,先要在沸水中捞半熟,内中有些地瓜米)。这人喝了之后,流着泪走了。
但不是完全没有争执的,毕竟是求生存的活计。有一回,我被抽来守夜,下半夜里,听得半山上有人声,于是与二三位民兵一同追上山道,快追到接近山项的蔡洋亭时,将三四个挑木桶的截住,意气风发带下山来。后来,其中一位黄姓老农悄声告诉我,这几人,也是虎洋人,有些武术,弄不好,会被他们“做”下山崖。头一次配合“拦柴”,公社一个干部就交待,切不可站在杉木一边。不然,扛杉木的可能一下子将杉木抛下肩膀,夜间看不清,就可能出事故,砸断了脚都不一定。
场里农民,尤其是有年纪的农民,不做半夜拦木头这类事情,我想是道德感使然。所谓意气风发之类,是建立在他人绝大痛苦基础之上。不论偷伐山林一类的事情该不该抓,在生存压力之下,如此艰难的日子,足以触动人的良心底线。
以民兵治民,是“上海经验”。1975年底有一次全省性民兵打击“投机倒把”的活动,我听说城关继光街的基干民兵甚至抓到单石碑来(单石碑当时属于北门三元大队的某个生产队,不属于金涵公社)。后来在资料中看到,当时,宁德县民兵在活动中搜得“金银15件、猪肉714斤、鱼类2957斤、活毛羊1只,私酒70斤……电工器材168件,钟表和的确良布料等(《福建省宁德县民兵指挥部简报第二期“11.30”统一行动情况》。)”。此类活动此后颇有几次。家里的金银都可能被“抓获”,况且是木头。
供销社
七十年代初,设于涵道村的公社供销社几乎是金溪平原上唯一的商业网点,也是周边山区村庄的购物中心。店里有一排长约二十米的柜台,柜台只有一小段是玻璃的,卖日用品,如肥皂、毛巾等,其余木头制成,漆着“清油”(桐油),呈嫩黄色。供销社的商品,从布匹、热水瓶、脸盆,到农药、铁耙、棕衣。生意似乎不太好,二、三个营业员寡言,表情也不丰富。其中有青年女营业员,是公众人物。可能因为从不晒太阳,因此白皙,异于常人。全公社的男人都有权就近观赏,甚至搭讪,但永远隔着柜台,正如流浪汉面对一份昂贵的菜单。
后溪村也有一处“供销社”。柜台与公社的几乎一个样子。油行村的供销社也有一个木制的柜台,同样宽,只是长度不一样。卖的货物基本相同。听说,二十多年前,路未通,后溪供销社卖化肥,要从三十里外涵道村挑来,后来池颂光市长跑到罗源协调,改成从十里外的中房调化肥。许多年后,农民依然念叨这事情。后溪村供销社,六七年前路过,看上去还与二、三十年前一个样子,只是卖的新东西多了些,柜台更旧。
电话
七十年代的电话用“摇把子”,电话机边都有个木匣子,装着两只长约一尺、茶缸子粗的大电池,手柄一摇,一条线上的几只电话都响。接听者先要听清找谁,无关者放下,有关者接话。倘若无关者不放下电话,那么这通电话就有两人以上在听。一般就近串连电话,如蔡洋岭一线,从最远的后溪开始,依次接上茶洋、菰洋、浮坪、中岗、公社茶场,直到涵道村边的公社里。
美景
1975年春节前几天,公社通知全社的下乡知青到灵坑村集中,县里领导来慰问。辛苦半年,可以放松,兴奋之情可以想象。于是走山路去灵坑村。天气晴朗,远山寂寥。峰回路转,突然见村子就在山下。时值涨潮,蔚蓝的海水紧傍着村子,村边泊着数十条船,支支桅杆错落。村子不小,乌瓦黄墙,密密排列,村边公路似金带飘向远方,公路上行着玩具般大小的车子。冬季白天短,下午三时许,阳光略西斜。明亮阳光照定海湾中央二、三条船,张着白色和褐色的帆,拖着影子,似乎一动不动。海湾的远端,青黄色夹杂的低山或岛屿,镶于蓝色的天际线上。
山很高,因此很静,听不到一点声响,同行的人,都静静地看了会儿村子和海。很多年后,有灵坑村的朋友对我说,西陂塘围垦前,灵坑村是鱼米之乡。因为我从半天空俯瞰过这个村子,所以,从内心赞同这种说法,同时还认为那个永远消失的画面,是一幅无与伦比的美景。
戴帽中学
七十年代中期,金涵公社有两所中学,都“挂”在小学校里。一所是金涵中心小学的初中班,两个年级,各一班。一位姓王的朋友当体育教师兼初二年级的班主任,学生篮球打得不错。学生是这一带工厂、机关单位的子弟,还有各村的小学毕业生。当时恐怕没有人特意将子女送到城里的宁德一中读初中。
另一个中学在金峰大队。金峰大队有十几个村,近两百户人家,七八百号人口,星散在水库后的“金字峰”山上,大的村庄,屋子也不会超过二十座。这些村子,原本连小学生都很少,但两个知青在此当民师,从小学教到毕业,接着就办初中班。1976年春,我到过金峰大队的院坪村(从水库后爬山一个多小时),见一幢大屋子的二楼,坐满了学生,印象中总有三十来人吧。“教室”只进一面光线,相当昏暗,似乎黑板的位置还是逆光,但学生神情十分专注。次年底,这个班的男教师考上学校,走出农门,女老师也招干进城,初中班就结束了,所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金字峰上各村早早地向平原迁徙,到本世纪初,山上已基本无人常住。七、八年前,这个村姓雷的会计告诉我,他就是这个初中班的学生,因为有初中,后来村里才有高中生。
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观,经常是个人在历史上作用微不足道,但“必须清楚地看到一个人、一个社会或是一个文化的可塑力有多么巨大”(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这两位年青人为千古不变的山区引进了新的文化,多少改变了这小小地方一代人的生活方式。男知青姓黄,女知青姓吴。后来,恢复高考后,一位是我的同学,一位是同机关大院的熟人。
农田基建
农业学大寨是七十年代宁德县农村最重要的活动。年年都要兴起高潮。这活动主要内容是农田基本建设。如平整水田,修水利,建田间道路,改造低产田等等。不仅平原,连山区也平整水田,农民称为“并丘”。这种活动十分艰辛,劳动量巨大,若无机械,必定要组织千军万马,这只有在七十年代才做得到。
我最早参加平整土地,在“石马洋”,大约在罐头厂、茶厂与金溪之间的水田中。水田中散布着牛马般大小的黑石头,这是洪积扇的特征。平整时,有人炸开并移走这些石头,而大多数人就是在田里将泥水搬来搬去。城里组织人员到石马洋帮忙,也包括了我们这些小学生。天气阴沉寒冷,一个姓辛的同学当时就喊关节痛。收工时,几十柄锄头胡乱堆在泥水中,我认不出自己的,又不晓得随意拿走一把,于是空手回家。因为丢了借来的锄头,一路垂头丧气。姓辛的同学后来得了白血病,他是班上最聪明的同学,山东莱阳人,其父亲在邮电局当领导,因为站“错队”,当时正在县里的学习班中被重点整治。
后来,特别是插队之后,参加过很多次平整水田的劳动。有的水田烂泥齐腰,也要并丘。当然并过之后,水田面积大了,改造了排水,田的等级肯定提高。1975年冬季那一场规模空前绝后的平整土地活动,我们茶场没有人参加。那天下大雪,冷得不行,清晨人人都在睡着,公社干部老林突然将大家喊起,说是千军万马都在平整土地,我们也要表态,于是大家拿着锄头,在造纸厂后的山路边挖了半天土,金溪平原上赤足浸在水田冰碴里干活的农民更加痛苦。这是金溪平原上所有够年纪的农民记忆深刻的一幕。
持续数年浩大的劳动场面,或许永不再来,但其进步的一面需要公允评价。
从七十年代初开始,全县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进行田园化的改造,平整了大量的梯田,改造了原来占全县水田总面积七成以上的低产田,这为八十年代之后农业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同时,完成了大量的防洪堤、水库、渠道以及围垦工程。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施工、完工的围垦工程共有19处,共扩大了耕地面积20800余亩,占当时全县水田总面积的13.8%(中共蕉城区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宁德县代表大会资料<总结经验,立场改革,为振兴宁德经济而努力奋斗——在中国共产党宁德县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杨家盛,1984年10月13日。)。这些家底,也为当下工业化、城市化奠定了重要的根基。
可谓苦一代人,利几代人。
相关人物
甘峰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