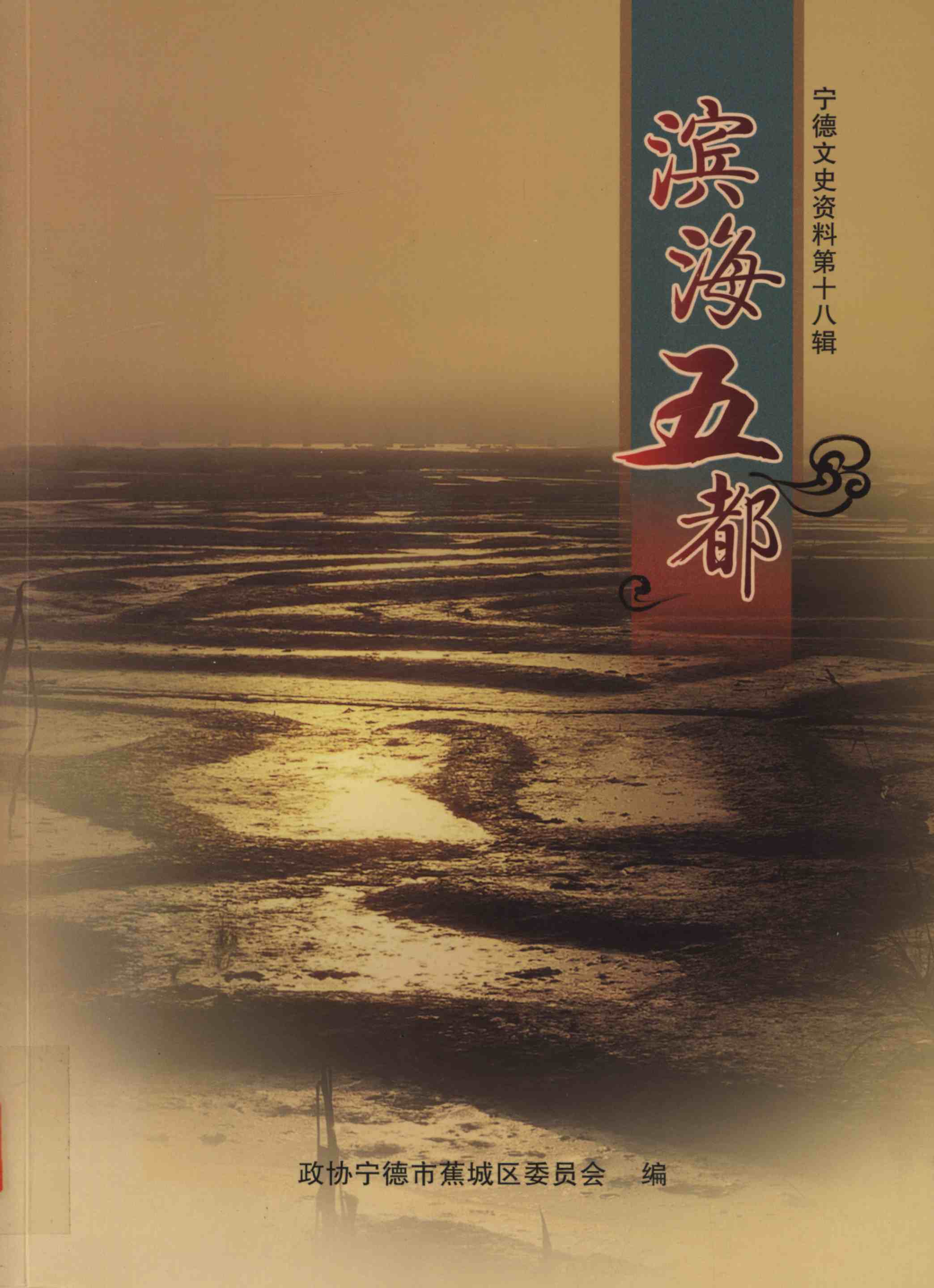内容
近几十年来,我区沿海的渔业生产也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过去传统的渔业生产方式,许多由祖宗遗留下来的陈旧作业,有的已被抛弃,有的也行将逝去,化成一桩桩的历史记忆。
—、告别大黄鱼汛期
宁德市蕉城区被国家授予“中国大黄鱼之乡”。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这里仍处于大黄鱼自然繁殖时期,每年从“立夏”至“夏至”四个节气的天文大潮,闽东沿海各县(含相邻的罗源、连江)居民均自发组织“瓜对”船前往三都澳中心—官井洋这一特定海域捕捞野生大黄鱼,收获甚丰。誉曰:“官井洋,半年粮。”意即官井洋一季捕获的大黄鱼,将占全年收入的一半。
[=此处为插图=]
1、天文渔汛。从理论上说,大黄鱼的汛期,每年从“立夏”至“夏至”有四个节气,即四次大潮水。其实,多数年份仅三次大潮水的捕捞期,原因是这中间要受到节气和潮水的两大制约。一是节气要到,再加大潮水的配合。农谚曰:“夏在洋没鱼尝,夏在厝没鱼厝。”意为“立夏”之日前把船开到官井洋是没有用的,因为鱼还没有上洋。如果节气虽到,但非大潮日,也捕不到鱼。因为水无流则鱼无路,像一盘散沙,既无明确目标,又无流送动力。以民国时期为例,1918年是农历3月26日“立夏”,5月14日“夏至”,勉强说,有4个潮水的捕鱼期,但尾潮太短,不到15日已“夏至”,汛期将满,故多选择放弃。但第二年1919年农历4月初7日“立夏”,5月22日“夏至”,只有3个潮水的捕鱼期。因此,全年只有3个潮水10天左右的上洋捕鱼时间。过了“夏至”,鱼群退出,“瓜对”散伙。当地人有个口头禅,说:“三水黄瓜鱼”,就是这个意思。
从前,每年到了大黄鱼汛期,宁德县境内最热闹的地方,起码有三个。一是官井洋的千船万桨闹海的壮观场景。按1956年官井洋渔汛指挥部统计数字,上洋“瓜对”船的顺序号码为1036,有母子船计2072艘,下船劳力超过一万人。加上闽东沿海各县的大黄鱼收购船和工作人员,这么多的人、船繁忙地交织穿梭于官井洋海面,其桨声、人声、鱼声和得鱼时吹螺的欢呼声,响成一片,构建这一“市井”的亮丽风景,是何等的热烈而壮观。二是官井洋几个岛屿的村庄,尤其是斗姆岛的斗姆村和青山岛的虾荡尾村,既要为“瓜对”船提供后勤的物资补给,又是大黄鱼的收购和储运的中转站。晚上,“瓜对”船进坞避风过夜,渔船成排,人声沸腾。原宁德县水产供销公司老职工老范告诉我说:“文革前,宁德没有冰库,“黄瓜季”,多的日子捕大黄鱼达一万担,其中约半数是在斗姆、青山水产站收购,负责转售、运输、腌制等任务。其库容爆满,关门拒收是常有的事。三是城关下尾埠的海滨路各个码头,和里、外二街,特别是面海的外街,彻夜通明,俗称“黄瓜瞑”。当日脯潮(白天的潮水)捞的鱼,从官井洋运至城关,民船约需4小时航程,这里又是水旱码头,涨潮才能靠岸,故大黄鱼收购船到达的时间,一般是在晚8点左右。再起鱼、过秤等,搞完交易过程,已时过子夜,如果鱼多交易量大,或是初二、三与十六、七的潮水,就要通宵达旦了。
2、“瓜对”分配。往昔,每年到了渔汛期,闽东沿海居民男劳动力多被选上“瓜对”船,本人也以能上官井洋讨鱼为荣。特别是头次上“瓜对”船,将鱼带回分赠诸亲友,亲友也应报以太平(鸡蛋)等,表示认同他的劳动价值。故有民谣曰:“好样男儿上官井,好吃女人去生产(生孩子坐月里)。”
所谓“瓜对”,就是由一大一小两艘母子船组成一队围捕黄瓜鱼作业单位的简称。“母船”是这一作业组的指挥船,指挥人称为“掌縺”。人员有“掌縺”(兼舵手),“罾头”(管鱼网兼握头桨)、“二桨”、“三桨”、“尾桨”(兼管网尾)、“主海”(“瓜对”老板或由老板指定的人)及“火头”(炊事员)等计6至7人。仔船是辅助者,应完全听从于“母船”“掌縺”的指挥,紧随其后,把“母船”上“罾头”放下的网子按指定方向拖走撒开,围往鱼群。得鱼后,收拢一起,将网里的鱼共同捞出装入船舱。人员有仔船老舵,副手(兼握仔船头桨)、二桨、三桨等计4人。故一“瓜对”,共需10至11个男全劳动力。因为划桨追桩和起网装鱼都是重活、急活(赶潮再撒下网),还须“主海”和“火头”来帮忙。
[=此处为插图(捕获114斤大黄鱼(资料图片))=]
“瓜对”所用的船只,是沿海村民生产、运输的普通木船。唯“母船”要大些,以载重3吨左右的漳湾艋艚(隔密舱福船)为好,但要卸下后舵,改用椿木做的尾橹,伸入水中,既能掌握航行方向,又便于“掌镰”借此收听水里的鱼群传来的声波。而“仔船”,随便小板船就可以了。
“瓜对”船,属于沿海居民自发组织的季节性生产团体,但需要相应的资金投入,也有一定的经济风险。故在1955年秋,“农业合作化大风暴”未能来到之前,他们属个体经营。尤其在建国前的私有制时代,“主海”多是村上较为富有的人来当。比如:民国十七年前,濂坑村未遭匪劫,为“两象十八牯牛”的大好发展时期,“象”户王应奎一人做12条“瓜对”船,他家拥有专门的织鱼网作坊,名网楼,常年雇用女工在里面搓线织网(据说每张渔网要用老秤90斤的苎麻作原料,编织成一种改良型的大围网,口围约45米,网索长60余米,中辅两条大筋绳。织成后用荔枝木染煮成棕褐色,网口每隔1米有一陶制约半斤重的网坠)。“牛”户王克芳也做9条“瓜对”船。当“主海”的要准备船只、渔网、橹浆等渔需物资,负责船上人员的伙食,腌鱼的食盐等。1956年之后,因农村实行集体化,先是全部生产资料折价加入“高级社”,后即过渡到人民公社为核算单位,“瓜对”船归入集体所有,也由集体经营,除雇用“掌縺”的报酬面议外其余人员是记工分参与年终分红。私有制时期的“瓜对”收益分配,是由经济性质来决定。原则上为劳、资兼顾,技术加奖励的方式。由于“掌縺”是“瓜对”船的主角,决定捕捞成败的关键人物,故其应与收益挂钩。首先,从总收中抽出15%给“掌縺”,余下85%,一半归“主海”,一半分给全体伙计。在伙计中,“罾头”因兼握头桨,和掘二桨的人最费力(桨离水近,吃水深),另由“主海”给予适当的鱼奖励。此外,还有几条不成文的规定。一是除大黄鱼外,捕到的其他鱼类,如马鲛、白蛎等应归主海,除非主海同意留给船上人员改善伙食或赏给某人外。二是带水尾(月头的初三四和月中的十七、八日)还有鱼讨时,可留较多的鱼给伙计带回家去。三是倘若水尾无鱼,“主海”也要将前一两天讨来的鱼,即使已被腌制成鱼鲞,分给他们,不能空手回家。
3、船上禁忌。凡是上“瓜对”船的伙计,每逢渔汛期头潮的傍晚,均集中,由“主海”出钱吃“水头瞑”(晚饭)。月半水为农历十三日,月初水为农历上月二十八日,这一餐在岸上吃得很好,饭菜、酒肉很丰盛,吃完就顺潮开船。从这时起,就得按船上的规矩行动和讲话。如睡眠不能俯卧(据说是溺水者死相,不吉利),吃鱼不能翻(不雅),吃饭的筷子不能搁在碗面上(太危险)等。在船上应少说话,必须讲时,也得轻声细语,一些日常用品的叫法也与在家时不同,如碗子叫“载”,这个字在本地话里,既有装载的意思,又有船舱储鱼之义。把饭多装一点,叫做多“载”一点。筷子叫揪扛,即得鱼时用以辅助起网的工具——竹杠。
如果进网的鱼多,约三四十担至一百多担时,依靠活鱼自身的托力,渔网就会浮出水面,这时人即站在网面上施行“开尾”,用刀子将渔网割开一个约60公分大的口子,拿鱼篮往网里捞鱼搬运到船上来,待到余下十担左右渔网的浮力下降后,人回到船上,就得“下栓”,即把“开尾”的口子用绳子扎起来,借用工具揪杠和人工的拉力,将鱼带网拖上船。把鱼从网里倒出后,取出备用的线子把渔网的口子缝好,又能继续使用。若是进网的鱼少,就用带柄的“兜仔”(抄网)直接从网里把鱼掏出来就可以了。
4、“掌縺”职业。“掌縺”是一种很特殊的职业。其特殊,特在它的专业性,风险性和季节性的“三性”上。干此行当,不仅有渔民,且更多是土生土长的沿海半农半渔村民。他们每年都上“瓜对”船当伙计,跟随在老“掌縺”身边,耳濡目染,身体力行,再在其口传身教之下,经过历练,方能入行。新中国成立前后,闽东沿海各县的“瓜对”船达到千余号,当“掌縺”的人也就有千余个。因为从业者多,其中良莠不齐。据说,当时宁德贵岐村的陈登勇、福安白溪村的连专顺等人,是这一行中的佼佼者。该二人都是讨“红流”时的“出门鱼”①。网无虚张,收益甚巨。他俩在“黄瓜季”的收入,已够一家人的全年生活。但也有些“掌縺”,在“黄瓜季”讨不到鱼或只讨到很少的鱼,不仅自己劳而无获,吞声忍气,而主海和伙计也要跟着他倒霉。
笔者原对“掌縺”这一职业很陌生,但在数年前,因从一位水产局退休干部手中得到一本编写于清乾隆八年(1743年)的捕捞大黄鱼秘籍——《官井书》后,由于该书的专业性强,内有许多生僻的名词和术语,难以读懂,为能理解它,曾走访过当年做过掌縺的人,获益匪浅。最大的体会是,凡事皆有规律可循。只要认真去体验。东海大黄鱼之所以选择到官井洋产卵,因为东冲水流湍急,刺激性大,加上这里食物丰富,水温适宜,又有礁腊为窝。鱼生水下,也要食宿。平潮水汐(落),潜伏于礁(腊);大涨大喷(退),寻食于路(流)。此即(书)中说的“水无流,鱼无路”。再者,大黄鱼有趋光性,却又有怕强光的特性,则黎明、傍晚喜浮于水面。特别是在生殖时会发出“咕咕”的叫声,密集的鱼群,声如水沸声或松涛声。这就是大黄鱼汛期为什么大多旺发于早潮或“脯(白天)汐”大涨大喷时的原因。故此,当“掌镰”的人,首先须知鱼性,随看鱼色,听懂鱼声,方能放网。其次是知道鱼群的行走路线和踏伏窝巢,做到有的放矢,网无虚张。再次是熟悉这一特定海域的地理、水文等情况,以利人身与船的安全。
附:掌縺苦吟
掌縺,掌縺,目睭红炎。
“瓜对”开船,就像做年。
番薯未插,草生岩前。
田也未播,无米做年。
十三开船,十四试縺。
十五无鱼,十六吃盐。
人放流中,你放流乾。
人得一千八百,你得无钱。
主海算数,烟盒储钱。
回家母亲又骂,老婆又嫌。
这潮无鱼,要看下潮。
今年失败,再等明年。
——流传于宁德沿海村庄民间
5、送鱼风俗。由于天然大黄鱼是季节性的很强的鱼类,除非汛期,平时极难捕到,一般人也吃不起。故当地居民都争取在“黄瓜季”的盛产期吃到黄瓜鱼,即使很穷的人也设法尝个鲜味,哪怕是一头小的。民间有谚曰:“黄瓜(鱼)不吃明年事,寒衣当掉能赎回。”此时,适逢天气转热,把脱掉的寒衣和卸下的棉被拿去当铺,当掉,拿钱来买鱼吃,到有钱时还可赎回,若是这一年的大黄鱼不吃,却补不回来。可见,人们对大黄鱼的渴望程度。
过去闽东人的婚俗,子女长大,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经媒人牵线,开生庚,如能合配,父母同意即可结成终年伴侣。女家一旦收到男家的订婚礼品,这女子就是男家的人了,有权择日迎娶。从此,男家必须给女家送三节(春节、端午、中秋)。端午时,正是黄瓜鱼季节,故给岳父家送黄瓜鱼是必不可少的。
且要送得早,个中且新鲜,一般以两尾共6斤以上为宜。因为女家早见鱼早高兴,则多数是在头一潮水,即端午节的前几天送鱼,况且男家也怕以后是否有鱼很难说,所以见鱼就买,买来就送。这送鱼的礼俗,已被闽东沿海人所看重,不仅是大黄鱼的品味高,而且名字也好听。在女家来说,嫁出黄花女,收你黄瓜鱼,理所当然。在男家来说,娶得黄花女,家门满堂春,脸上也有光。故此,相互图个吉利。再说前人很尊敬老人,每年头次的黄花鱼煮熟后端到桌上,必须让长辈人先尝鲜,他未下筷子,晚辈人不敢动。长幼有序,这是规矩。
二、告别定制网艋艚
渔网种类繁多。定制网是张网中的一种,叫“桩张网”。因为水下埋有木桩,通过绳索把渔网固定在港道流水处,网罗过路(逐流)的鱼儿,故名。它与这一捕捞作业的船只连在一起,称作“艋艚船”,捕获的海产品,叫作“艋艚货”,大潮日挂网生产,小潮日解网回家。全年作业,旺在春汛。好处是一人一船一网,就能生产,但因被固定在海中的风浪尖上,过去没有通讯工具,台风、雷暴袭击,时常发生人船安全问题。故家属在家无时不刻担心海上丈夫的安全,抱怨说:“未过重阳日,还不知道今年是否还能同丈夫一起过年?”所以有做艋的村庄,如原蕉城的中南、漳湾的岐后、八都的下汐等村,对每年农历九月初九的重阳节很重视,都要热烈庆祝一番,因为过了重阳节以后,闽东近海就无台风、雷暴了。
据1990年统计,宁德市(今蕉城区)有定置网614条,分布在境内的官井洋、三都、漳湾等作业海区(场),捕捞品种主要有:毛虾、对虾、鲳鱼、鲂鱼、鳓鱼、海蜇、石斑鱼、马鲛鱼、龙头鱼、梭子蟹、锯缘青蟹等。年产量在一千吨左右,约占海洋捕捞总量的三分之一(详见1995年出版《宁德市志》(蕉城区)卷七、渔业)。
迄今,时过二十余年,上述的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由于人为原因,近海的自然资源在逐年减少,新的现象是:一方面,旧的捕捞作业因捕不到鱼,在逐渐减少,甚至消亡;另一方面,新的人工网箱养鱼又在逐年增加,不断挤压艋艚作业的空间。笔者在撰写本文时,也曾了解过多个今在经营水产品生意的人,均说如今本区的艋艚已寥若晨辰,几乎是看不到了。
在旧社会的私有制时代,艋艚定制的“桁”位要用钱买卖或租赁,尤其是好的“桁”位,标价更高。主要在于选址难,打“桁”(桩)也要花本钱。建国后1951年6月,宁德县实行渔区“土改”,此时的蕉城镇中南街黄承志虽已死去多年,却因建国前经营城关德顺埠鱼货牙行,占有宁德海面多个艋艚“桁”位出租,并强行收购渔货,被评定为“海霸”。直至“文革”前的数十年间,均被当作以阶级斗争的“靶子”,进行批判。渔区“土改”中,根据1950年6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土地改革法》第四章的各条规定,原则上江、海、河、港、湖、沼等水面之所有权,应收归国有,但考虑到渔业生产的需要,可将其定给原经营者所在的乡镇民主管理之,并由该经营者继续经营的精神,宁德海面的艋艚“桁”位不再为私人所有,应收归原经营者所在的乡政府管理,个人经营。后来,农村实行集体化,即由集体管理,个人承包经营之。
这艋艚打“桁”埋桩是一件大事,既要定位准确,又得安全可靠。前人迷信思想很重。打“桁”(桩),除要选择好日子外,还要搞请“元帅神”仪式。建国后,政府提倡破除迷信,这请神的仪式没有了,但择日仍不可少。其事先应备好两大部件:一是打入海底的“桁”,叫“锹”,用松木做的,不够长可以接上去;二是接在“锹”的外端的绳索,叫“筋”,用竹篾加稻杆打成的绳子,要一而贯之,不能接。届时,同行的人会来帮忙。在退潮时,两条船只靠拢一起,将已备好的“桁”放入水中,竖起来,用一大木斗,把中空约一米多长的一头套在“桁”的上方,实心的一头向上,木头的两边穿着两条长长的竹制抬杠,两艘船上的十几个劳动力以步骤相一致的动作,将木头抬起放下,再抬起放下,直至把“桁”打入海底。留“筋”在水面上,再分支用于缆鱼网或船只。这种竹篾加稻杆制成的“筋”只能使用两年时间,到时就要更换。现在改用尼龙丝做“筋”,使用寿命长达五六年之久。艋艚“桁”打好后,将木斗收藏起来,主人还得宴请大家,欢聚一堂,以资庆祝。
三、告别放鹰叼杂鱼
驯鹰叼鱼,是沿海居民传统的捕鱼方法之一,过去很普遍,现在没有了。鱼鹰,也叫“鱼老鸦”,鸟纲,鸬鹚科,通称鸬鹚。体长可达0.8米,羽毛多为黑色而带有紫色金属光泽,喜栖在河川、湖沼和海滨,善潜水,捕食鱼类,常巢于草丛中或矮树、峭壁上。
沿海、沿江的村民有谣曰:“两只鸬鹚胜过一张渔网”。就是说,过去连家船的渔民,依靠一船一网养活一家子人,而岸上的村民只要能驯养两只鸬鹚出去叼鱼,也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了。笔者在五十多年前,曾两次见过鱼鹰叼鱼的事。首次是1955年夏,八都区金垂乡搞“改造落后乡”工作的检查验收时,该村有一林姓的老人驯养8只成年的鸬鹚,每天划着竹筏,上面放个加盖的装鱼大竹篓,竹筏两旁的栏杆上各站4只鸬鹚。他自个儿顺着水草丰美的江边,悠然自得地划呀!划呀!而筏上两旁站立的鸬鹚也眼睁睁地盯住水面,瞧着!瞧着!其中的一只鸬鹚发现目标,迅即跳入水中,潜游下去。不一会儿,鸬鹚口里就噙着一头活蹦活跳的鱼儿爬上竹筏,渔翁即从它口里掏出来,约有一斤多重。这只鸬鹚初战告捷后,抖动一下身子,去掉水分,松动羽毛,又站到杆上去。接着,另一只鸬鹚下水……上述的情景,撩动了当时我那年轻的好奇心,很想探询个究竟。有一天,村上分派工作组人员伙食,到了这渔翁家,餐桌上未免有几道海鲜,正是向他探询鸬鹚一事的极好机会,故在用餐中,宾主有一段颇具趣味性的对话,今日想起,记忆犹新。摘录如下,以供参考。
“你家8只鸬鹚一天出去能捕到多少鱼?”我在餐桌上恳切地问道。
“不一定,这个需要看季节和天气如何。平时一天出去一趟,捕个一、二十斤鱼是有的。”他回答后,又觉得不够完整,稍后思索,补充说:“严冬,鱼儿深藏水底;下雨,鱼花看不清楚,均难捕到鱼。特别是天寒,鸬鹚怕冷,不能出去,在家还要用小鱼小虾喂它。
“你家的鸬鹚是怎么来的?”同桌的驻乡工作组姚同志接过话题问道。
“是我父亲遗留下来的,起先只有4只。由于霍童溪的海水交汇处鱼多,捕获量比现在还多。”老渔翁回答。
“那你现在这多出的4只鸬鹚是怎么来的呢?”
“有的是用渔网诱捕来的,有的是鸬鹚巢里抓的幼鸟。”
“这些从野外抓来的鸬鹚,不管是成鸟或幼鸟,肯定野性十足,你又是如何去驯化?”
“这驯化鸬鹚,确实很费工夫。简单说来,有栓脚、箍颈、站杠、熬鹰等几个环节。也就是说,抓到鸬鹚后,先用绳子将它的脚栓起来,不让其飞走。再拿削细的竹篾将它的脖子箍好,不让它吞食半斤以上的鱼儿。然后用一条木杠让它站立在上面,喂食睡觉都不要让它下来。这一环节极为关键,要结合主人与它对视——目对目来做。时间一长,习惯成自然,就被你驯化了。”老渔翁解答问题的大意是这样,今随时间的推移,细节已被遗忘。
过后一年多,农业合作社大风暴来临时,我下乡路过八都的溪池村,又碰见一次竹筏在霍童溪放鹰叼鱼,经查问是福安人过来的。此后,我再也没有看见鸬鹚叼鱼的作业了。
今日的宁德,这鸬鹚叼鱼的作业虽已消亡,但历史上因此而产生的俚语却仍流传于民间。比如:“鸬鹚箍着(脖子)吃。”是指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又如:“今年冬天要做鸬鹚了。”是说没有寒衣、棉被过冬。再如:“鸬鹚拍来贼拍去。”是指到手的财物,又被他人搞走了。
四、告别夜黑投白船
我知道有“投白船”,是童蒙时期从一句民间成语中来。笔者幼年在家,时常结伴玩耍。有一次,正玩得高兴时,大人却告诉我们说:你看!投白船荡(划)过来了,他会骂人的,赶快走开。听了这话,孩子们一哄而散。我走出几步,就回过头来顺着大人手指的方向看去,哪里有什么船儿。分明是个瘸子,走路身子不平衡,直摇晃着,一拐一拐的往前行。这时的心里有些迷惑不解,却也朦朦胧胧的过去了。时隔数年,我已经是在校的高小生了,放暑假时跟随家里人去云淡村堂姐家做客。船到村口泊岸,见坡上有一简陋的民房,里面并排摆放着十几艘窄长的小木船,尖头方尾,长近二丈,宽约三尺,不像是龙舟。当日,在我堂姐家隔夜,第二天早晨起床,看见她家天井里放着一只大竹篓,里面装有约十多斤活蹦活跳的鱼儿,内最大的一尾身长背黑,眼睛红红的,大约有五六斤重。我就问我堂姐夫这是怎么回事,哪里搞来的这么多鱼?他回答说,昨夜天空很黑,村上的投白船出去捕的鱼。当我听到“投白船”这三个字时,就想起数年前大人把瘸子走路比喻成投白船的话并告诉他。他听了并未立即回答,只是带我去看村口坡上摆放的投白船和搁在船旁边两块用来在水中“刷白”的杉木板,那木板长约一丈,宽五六寸。看后才介绍说,这种船是专门为诱鱼上船而设计的,窄而长,只能容纳一个人,使用一橹一浆,涨潮时从本村起航,开往对面南浦村边,由下至上,将已刷白的两块木板连接起来,搁在船的右舷边,持一定的向外倾斜度,最好外侧要贴近水面。因船狭窄,浆子一划,船身就会晃动,船舷白板与荡漾的水花相映,会发出闪光,这里的鲻科鱼类,比如:青头、只鱼、红目缁、跳蚤缁等有趋光性,晚间涨潮出来到岸边寻食时,见了即往光处跳跃,多能落入船中。船再沿着金垂村边,开至八都村外,到回程时,将船上的白板搬到左舷,往下游开回去,来回约需两个多钟头。此一作业的好处是可以引诱鱼儿上船,十几二十斤重的都有。鸬鹚叼鱼,三四斤的就没办法了。大的鱼跳上船,就得脱下身上的棕衣把它盖住,船身也震动得厉害。不然,这鱼又会跳到水中。我俩边看边谈,回到我堂姐家。中午,在他家吃了饭,正好涨潮,就搭船回家了。此次到云淡村走亲戚,虽未亲眼看到“鱼跳上船”的情景,但投白船与捕获的鱼都已见到,特别是堂姐夫给我介绍的话,使我明白了把瘸子走路比喻成投白船,是一形象性的语言。
1959年秋,我以驻村工作组员的身份到了云淡村,很想前去体验一下这投白船捕鱼的作业过程,经查问村里干部,得知这一捕鱼作业早已没有了。
五、告别撑枷截鱼群
撑枷拦截退潮鱼,是夏秋季节浅海鱼类肥美时,沿海村民在潮水“前滨区”进行的一种围捕。据我回忆,从能记事起,故乡的西陂塘每年都搞好几次撑枷作业,各户均备有一副以上专门用来捕鱼的“罩”。它是用竹篾编就上小下大的喇叭状捕鱼工具,形似“鸡笼”,两只配对,高过膝盖,紧扎棕绳,整体牢固。上口为抓手,使用时一手抓一只,往水里罩,被罩入的鱼儿在里面挣扎,伸手抓住即可。这“罩”有雌雄,可以套起来用绳子串着背在身上,不用时又套在一起挂到墙上去。
撑枷作业规模大,用网多,受益广。领头者,过去多为村上有威望的人。因为西陂塘滩涂大多是养殖缢蛏,万一被踩踏有损失,也好出面解决赔偿问题。作业时,选个有鱼儿出没的港汊,以观鱼色(粪便)作判断,确定后,白天退潮时,按五米的距离扦插撑杆(竹子),牵拉鱼网(埋下)等。关键是在港汊的低洼处布螺旋“阵”、安储鱼“斗”。范围要覆盖这一特定水脉的全流程,包括港汊两旁高处。做好后,让潮水淹没进去。待到半夜潮水退落,形成一定流速,鱼儿将开始随潮退出时,守在港汊两旁高阜处两艘船只,即从高处潮水先退的地方着手,顺着撑杆将渔网持上水面,将两旁海面上的鱼儿赶往港汊去,驱入已布好的螺旋“阵”,再落到储鱼“斗”,集中网罗起来。但当海面的鱼儿被驱赶入港中,有些因触网而受惊动,就会掉头,逆流而上,这部分鱼,按照村规民约,是允许村民拾取的。这撑枷的作业多选择在像初一、十五的大潮日进行,天亮不久,潮水就回涨了。所以,去撑枷鱼的人不耽误白天干活。背着“罩”子去罩鱼的人很多,连十一、二岁在校的学生都跟着大人去,因人矮无法使用“罩”,只好跟在后面去手摸躲藏在足迹里的鱼。因为港汊两旁都是泥滩,人们走过后,踩出深陷的足迹,鱼被打“罩”后,会胡奔乱窜,藏入足迹。笔者幼年也曾跟随大家去摸鱼过,体验过这种生活,其感受是摸到一只鱼比吃下一只鱼的情趣更浓更有意思。很可惜,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于鱼类资源减少,此项作业已经没有了。
六、告别挖壑存鱼
从前,每到沿海的一个村庄,均能看到村前“潮间带”的海滩上,都挖有许多大小不一的储水坑,即便是退潮期间,滩涂已经干涸,这坑里仍储满着水。这到底是干什么的?陌生人不知道,原来为了储水存鱼蟹。在西陂塘未围垦前,沿岸各村都有,俗称鱼“壑”。小的为住户所独有;大的是合作共有。每年的“清明”节前,都要将“壑”清淤一遍,把挖出的泥用来增高培固外堤,然后再在低处安个涵洞,高处搞石砌预洪坝通水。涵洞一堵,就能储水,任其潮起潮落,直至农历五月“端午节”前开涵放水,“壑”内的鱼蟹任你抓取。“小壑”可收获几十斤,大“壑”几百斤不等。我幼年在家时,看见一天中放“壑”几十个。过节时,有挖“壑”的人家都排满着许多的鱼、虾、蟳等,特别是蟳,几天吃不完,将腿脚齐全、七八分饱满的都养起来,可以吃十几天。没有挖“壑”的人家,也多接受别人的馈送。同时,放“壑”是允许别人捡“壑”底的,所以,家有小孩半劳力的也不缺鱼蟹。这“壑”放后又堵上,下次放“壑”是农历七月十五“中元”祭祖节前和再下一次的八月十五“中秋”节前了。此后,小“壑”放弃,大“壑”九月初九“重阳”节前仍能再放一次。因为天气转冷,“壑”小水浅,不存鱼蟹了。
说到鱼“壑”,不觉使我想起童年在家亲眼看见的一件事,今虽时隔六十多年,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我家离海很近,小时候常在海边,或玩耍,或戏水,或讨些小海的东西。1949年,国民党107旅部队驻宁时,下属有一排的兵士驻在濂坑乡(时为乡建制)的炮台(它是1928年海军上将萨镇冰前来赈灾时建下的“守御堡”)。夏日,骄阳似火,酷热难熬。一天中午,几个兵士来到海边,因是小潮,海水已经退去。遗下的是一片干涸的滩涂,只有那一个个人工开挖的鱼“壑”仍充满着蓝色的海水。这些兵士可能是外地人,不知就里,即脱掉外面的衣衫,只穿一条短裤,走进“壑”中去洗澡。不料,却惹来大麻烦了。其中一人的脚被蟳螯钳住,痛的呼爷叫娘,他不知到蟳的特性,用手去抓,越抓越钳得越紧,在水中挣扎起来,“壑”水被搅动后,别的蟳也漂上来,螯住他身上的多个部位,还差点被淹死在水里。我当时才七、八岁,一帮小伙伴看见了,觉得很好笑。另外,还听长辈们讲过“豚困鱼壑”的故事。大概是从前有一年夏天,一只海豚进入西陂塘的“壑”里觅食,不知是因为贪食而迷路,或是别的原因,潮水退去,仍困在“壑”里,“壑”主痛恨它把储存的鱼全糟蹋了,故将水放干,抓拿回去,有二百余斤。此为往事,但笔者幼年在家,海豚进入西陂塘为常事,特别是夏暑季节,涨潮时多能见到它欢悦在水面上。至于鱼“壑”,自七十年代后,由于人为因素近海资源减少,已经没有了。
—、告别大黄鱼汛期
宁德市蕉城区被国家授予“中国大黄鱼之乡”。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这里仍处于大黄鱼自然繁殖时期,每年从“立夏”至“夏至”四个节气的天文大潮,闽东沿海各县(含相邻的罗源、连江)居民均自发组织“瓜对”船前往三都澳中心—官井洋这一特定海域捕捞野生大黄鱼,收获甚丰。誉曰:“官井洋,半年粮。”意即官井洋一季捕获的大黄鱼,将占全年收入的一半。
[=此处为插图=]
1、天文渔汛。从理论上说,大黄鱼的汛期,每年从“立夏”至“夏至”有四个节气,即四次大潮水。其实,多数年份仅三次大潮水的捕捞期,原因是这中间要受到节气和潮水的两大制约。一是节气要到,再加大潮水的配合。农谚曰:“夏在洋没鱼尝,夏在厝没鱼厝。”意为“立夏”之日前把船开到官井洋是没有用的,因为鱼还没有上洋。如果节气虽到,但非大潮日,也捕不到鱼。因为水无流则鱼无路,像一盘散沙,既无明确目标,又无流送动力。以民国时期为例,1918年是农历3月26日“立夏”,5月14日“夏至”,勉强说,有4个潮水的捕鱼期,但尾潮太短,不到15日已“夏至”,汛期将满,故多选择放弃。但第二年1919年农历4月初7日“立夏”,5月22日“夏至”,只有3个潮水的捕鱼期。因此,全年只有3个潮水10天左右的上洋捕鱼时间。过了“夏至”,鱼群退出,“瓜对”散伙。当地人有个口头禅,说:“三水黄瓜鱼”,就是这个意思。
从前,每年到了大黄鱼汛期,宁德县境内最热闹的地方,起码有三个。一是官井洋的千船万桨闹海的壮观场景。按1956年官井洋渔汛指挥部统计数字,上洋“瓜对”船的顺序号码为1036,有母子船计2072艘,下船劳力超过一万人。加上闽东沿海各县的大黄鱼收购船和工作人员,这么多的人、船繁忙地交织穿梭于官井洋海面,其桨声、人声、鱼声和得鱼时吹螺的欢呼声,响成一片,构建这一“市井”的亮丽风景,是何等的热烈而壮观。二是官井洋几个岛屿的村庄,尤其是斗姆岛的斗姆村和青山岛的虾荡尾村,既要为“瓜对”船提供后勤的物资补给,又是大黄鱼的收购和储运的中转站。晚上,“瓜对”船进坞避风过夜,渔船成排,人声沸腾。原宁德县水产供销公司老职工老范告诉我说:“文革前,宁德没有冰库,“黄瓜季”,多的日子捕大黄鱼达一万担,其中约半数是在斗姆、青山水产站收购,负责转售、运输、腌制等任务。其库容爆满,关门拒收是常有的事。三是城关下尾埠的海滨路各个码头,和里、外二街,特别是面海的外街,彻夜通明,俗称“黄瓜瞑”。当日脯潮(白天的潮水)捞的鱼,从官井洋运至城关,民船约需4小时航程,这里又是水旱码头,涨潮才能靠岸,故大黄鱼收购船到达的时间,一般是在晚8点左右。再起鱼、过秤等,搞完交易过程,已时过子夜,如果鱼多交易量大,或是初二、三与十六、七的潮水,就要通宵达旦了。
2、“瓜对”分配。往昔,每年到了渔汛期,闽东沿海居民男劳动力多被选上“瓜对”船,本人也以能上官井洋讨鱼为荣。特别是头次上“瓜对”船,将鱼带回分赠诸亲友,亲友也应报以太平(鸡蛋)等,表示认同他的劳动价值。故有民谣曰:“好样男儿上官井,好吃女人去生产(生孩子坐月里)。”
所谓“瓜对”,就是由一大一小两艘母子船组成一队围捕黄瓜鱼作业单位的简称。“母船”是这一作业组的指挥船,指挥人称为“掌縺”。人员有“掌縺”(兼舵手),“罾头”(管鱼网兼握头桨)、“二桨”、“三桨”、“尾桨”(兼管网尾)、“主海”(“瓜对”老板或由老板指定的人)及“火头”(炊事员)等计6至7人。仔船是辅助者,应完全听从于“母船”“掌縺”的指挥,紧随其后,把“母船”上“罾头”放下的网子按指定方向拖走撒开,围往鱼群。得鱼后,收拢一起,将网里的鱼共同捞出装入船舱。人员有仔船老舵,副手(兼握仔船头桨)、二桨、三桨等计4人。故一“瓜对”,共需10至11个男全劳动力。因为划桨追桩和起网装鱼都是重活、急活(赶潮再撒下网),还须“主海”和“火头”来帮忙。
[=此处为插图(捕获114斤大黄鱼(资料图片))=]
“瓜对”所用的船只,是沿海村民生产、运输的普通木船。唯“母船”要大些,以载重3吨左右的漳湾艋艚(隔密舱福船)为好,但要卸下后舵,改用椿木做的尾橹,伸入水中,既能掌握航行方向,又便于“掌镰”借此收听水里的鱼群传来的声波。而“仔船”,随便小板船就可以了。
“瓜对”船,属于沿海居民自发组织的季节性生产团体,但需要相应的资金投入,也有一定的经济风险。故在1955年秋,“农业合作化大风暴”未能来到之前,他们属个体经营。尤其在建国前的私有制时代,“主海”多是村上较为富有的人来当。比如:民国十七年前,濂坑村未遭匪劫,为“两象十八牯牛”的大好发展时期,“象”户王应奎一人做12条“瓜对”船,他家拥有专门的织鱼网作坊,名网楼,常年雇用女工在里面搓线织网(据说每张渔网要用老秤90斤的苎麻作原料,编织成一种改良型的大围网,口围约45米,网索长60余米,中辅两条大筋绳。织成后用荔枝木染煮成棕褐色,网口每隔1米有一陶制约半斤重的网坠)。“牛”户王克芳也做9条“瓜对”船。当“主海”的要准备船只、渔网、橹浆等渔需物资,负责船上人员的伙食,腌鱼的食盐等。1956年之后,因农村实行集体化,先是全部生产资料折价加入“高级社”,后即过渡到人民公社为核算单位,“瓜对”船归入集体所有,也由集体经营,除雇用“掌縺”的报酬面议外其余人员是记工分参与年终分红。私有制时期的“瓜对”收益分配,是由经济性质来决定。原则上为劳、资兼顾,技术加奖励的方式。由于“掌縺”是“瓜对”船的主角,决定捕捞成败的关键人物,故其应与收益挂钩。首先,从总收中抽出15%给“掌縺”,余下85%,一半归“主海”,一半分给全体伙计。在伙计中,“罾头”因兼握头桨,和掘二桨的人最费力(桨离水近,吃水深),另由“主海”给予适当的鱼奖励。此外,还有几条不成文的规定。一是除大黄鱼外,捕到的其他鱼类,如马鲛、白蛎等应归主海,除非主海同意留给船上人员改善伙食或赏给某人外。二是带水尾(月头的初三四和月中的十七、八日)还有鱼讨时,可留较多的鱼给伙计带回家去。三是倘若水尾无鱼,“主海”也要将前一两天讨来的鱼,即使已被腌制成鱼鲞,分给他们,不能空手回家。
3、船上禁忌。凡是上“瓜对”船的伙计,每逢渔汛期头潮的傍晚,均集中,由“主海”出钱吃“水头瞑”(晚饭)。月半水为农历十三日,月初水为农历上月二十八日,这一餐在岸上吃得很好,饭菜、酒肉很丰盛,吃完就顺潮开船。从这时起,就得按船上的规矩行动和讲话。如睡眠不能俯卧(据说是溺水者死相,不吉利),吃鱼不能翻(不雅),吃饭的筷子不能搁在碗面上(太危险)等。在船上应少说话,必须讲时,也得轻声细语,一些日常用品的叫法也与在家时不同,如碗子叫“载”,这个字在本地话里,既有装载的意思,又有船舱储鱼之义。把饭多装一点,叫做多“载”一点。筷子叫揪扛,即得鱼时用以辅助起网的工具——竹杠。
如果进网的鱼多,约三四十担至一百多担时,依靠活鱼自身的托力,渔网就会浮出水面,这时人即站在网面上施行“开尾”,用刀子将渔网割开一个约60公分大的口子,拿鱼篮往网里捞鱼搬运到船上来,待到余下十担左右渔网的浮力下降后,人回到船上,就得“下栓”,即把“开尾”的口子用绳子扎起来,借用工具揪杠和人工的拉力,将鱼带网拖上船。把鱼从网里倒出后,取出备用的线子把渔网的口子缝好,又能继续使用。若是进网的鱼少,就用带柄的“兜仔”(抄网)直接从网里把鱼掏出来就可以了。
4、“掌縺”职业。“掌縺”是一种很特殊的职业。其特殊,特在它的专业性,风险性和季节性的“三性”上。干此行当,不仅有渔民,且更多是土生土长的沿海半农半渔村民。他们每年都上“瓜对”船当伙计,跟随在老“掌縺”身边,耳濡目染,身体力行,再在其口传身教之下,经过历练,方能入行。新中国成立前后,闽东沿海各县的“瓜对”船达到千余号,当“掌縺”的人也就有千余个。因为从业者多,其中良莠不齐。据说,当时宁德贵岐村的陈登勇、福安白溪村的连专顺等人,是这一行中的佼佼者。该二人都是讨“红流”时的“出门鱼”①。网无虚张,收益甚巨。他俩在“黄瓜季”的收入,已够一家人的全年生活。但也有些“掌縺”,在“黄瓜季”讨不到鱼或只讨到很少的鱼,不仅自己劳而无获,吞声忍气,而主海和伙计也要跟着他倒霉。
笔者原对“掌縺”这一职业很陌生,但在数年前,因从一位水产局退休干部手中得到一本编写于清乾隆八年(1743年)的捕捞大黄鱼秘籍——《官井书》后,由于该书的专业性强,内有许多生僻的名词和术语,难以读懂,为能理解它,曾走访过当年做过掌縺的人,获益匪浅。最大的体会是,凡事皆有规律可循。只要认真去体验。东海大黄鱼之所以选择到官井洋产卵,因为东冲水流湍急,刺激性大,加上这里食物丰富,水温适宜,又有礁腊为窝。鱼生水下,也要食宿。平潮水汐(落),潜伏于礁(腊);大涨大喷(退),寻食于路(流)。此即(书)中说的“水无流,鱼无路”。再者,大黄鱼有趋光性,却又有怕强光的特性,则黎明、傍晚喜浮于水面。特别是在生殖时会发出“咕咕”的叫声,密集的鱼群,声如水沸声或松涛声。这就是大黄鱼汛期为什么大多旺发于早潮或“脯(白天)汐”大涨大喷时的原因。故此,当“掌镰”的人,首先须知鱼性,随看鱼色,听懂鱼声,方能放网。其次是知道鱼群的行走路线和踏伏窝巢,做到有的放矢,网无虚张。再次是熟悉这一特定海域的地理、水文等情况,以利人身与船的安全。
附:掌縺苦吟
掌縺,掌縺,目睭红炎。
“瓜对”开船,就像做年。
番薯未插,草生岩前。
田也未播,无米做年。
十三开船,十四试縺。
十五无鱼,十六吃盐。
人放流中,你放流乾。
人得一千八百,你得无钱。
主海算数,烟盒储钱。
回家母亲又骂,老婆又嫌。
这潮无鱼,要看下潮。
今年失败,再等明年。
——流传于宁德沿海村庄民间
5、送鱼风俗。由于天然大黄鱼是季节性的很强的鱼类,除非汛期,平时极难捕到,一般人也吃不起。故当地居民都争取在“黄瓜季”的盛产期吃到黄瓜鱼,即使很穷的人也设法尝个鲜味,哪怕是一头小的。民间有谚曰:“黄瓜(鱼)不吃明年事,寒衣当掉能赎回。”此时,适逢天气转热,把脱掉的寒衣和卸下的棉被拿去当铺,当掉,拿钱来买鱼吃,到有钱时还可赎回,若是这一年的大黄鱼不吃,却补不回来。可见,人们对大黄鱼的渴望程度。
过去闽东人的婚俗,子女长大,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经媒人牵线,开生庚,如能合配,父母同意即可结成终年伴侣。女家一旦收到男家的订婚礼品,这女子就是男家的人了,有权择日迎娶。从此,男家必须给女家送三节(春节、端午、中秋)。端午时,正是黄瓜鱼季节,故给岳父家送黄瓜鱼是必不可少的。
且要送得早,个中且新鲜,一般以两尾共6斤以上为宜。因为女家早见鱼早高兴,则多数是在头一潮水,即端午节的前几天送鱼,况且男家也怕以后是否有鱼很难说,所以见鱼就买,买来就送。这送鱼的礼俗,已被闽东沿海人所看重,不仅是大黄鱼的品味高,而且名字也好听。在女家来说,嫁出黄花女,收你黄瓜鱼,理所当然。在男家来说,娶得黄花女,家门满堂春,脸上也有光。故此,相互图个吉利。再说前人很尊敬老人,每年头次的黄花鱼煮熟后端到桌上,必须让长辈人先尝鲜,他未下筷子,晚辈人不敢动。长幼有序,这是规矩。
二、告别定制网艋艚
渔网种类繁多。定制网是张网中的一种,叫“桩张网”。因为水下埋有木桩,通过绳索把渔网固定在港道流水处,网罗过路(逐流)的鱼儿,故名。它与这一捕捞作业的船只连在一起,称作“艋艚船”,捕获的海产品,叫作“艋艚货”,大潮日挂网生产,小潮日解网回家。全年作业,旺在春汛。好处是一人一船一网,就能生产,但因被固定在海中的风浪尖上,过去没有通讯工具,台风、雷暴袭击,时常发生人船安全问题。故家属在家无时不刻担心海上丈夫的安全,抱怨说:“未过重阳日,还不知道今年是否还能同丈夫一起过年?”所以有做艋的村庄,如原蕉城的中南、漳湾的岐后、八都的下汐等村,对每年农历九月初九的重阳节很重视,都要热烈庆祝一番,因为过了重阳节以后,闽东近海就无台风、雷暴了。
据1990年统计,宁德市(今蕉城区)有定置网614条,分布在境内的官井洋、三都、漳湾等作业海区(场),捕捞品种主要有:毛虾、对虾、鲳鱼、鲂鱼、鳓鱼、海蜇、石斑鱼、马鲛鱼、龙头鱼、梭子蟹、锯缘青蟹等。年产量在一千吨左右,约占海洋捕捞总量的三分之一(详见1995年出版《宁德市志》(蕉城区)卷七、渔业)。
迄今,时过二十余年,上述的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由于人为原因,近海的自然资源在逐年减少,新的现象是:一方面,旧的捕捞作业因捕不到鱼,在逐渐减少,甚至消亡;另一方面,新的人工网箱养鱼又在逐年增加,不断挤压艋艚作业的空间。笔者在撰写本文时,也曾了解过多个今在经营水产品生意的人,均说如今本区的艋艚已寥若晨辰,几乎是看不到了。
在旧社会的私有制时代,艋艚定制的“桁”位要用钱买卖或租赁,尤其是好的“桁”位,标价更高。主要在于选址难,打“桁”(桩)也要花本钱。建国后1951年6月,宁德县实行渔区“土改”,此时的蕉城镇中南街黄承志虽已死去多年,却因建国前经营城关德顺埠鱼货牙行,占有宁德海面多个艋艚“桁”位出租,并强行收购渔货,被评定为“海霸”。直至“文革”前的数十年间,均被当作以阶级斗争的“靶子”,进行批判。渔区“土改”中,根据1950年6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土地改革法》第四章的各条规定,原则上江、海、河、港、湖、沼等水面之所有权,应收归国有,但考虑到渔业生产的需要,可将其定给原经营者所在的乡镇民主管理之,并由该经营者继续经营的精神,宁德海面的艋艚“桁”位不再为私人所有,应收归原经营者所在的乡政府管理,个人经营。后来,农村实行集体化,即由集体管理,个人承包经营之。
这艋艚打“桁”埋桩是一件大事,既要定位准确,又得安全可靠。前人迷信思想很重。打“桁”(桩),除要选择好日子外,还要搞请“元帅神”仪式。建国后,政府提倡破除迷信,这请神的仪式没有了,但择日仍不可少。其事先应备好两大部件:一是打入海底的“桁”,叫“锹”,用松木做的,不够长可以接上去;二是接在“锹”的外端的绳索,叫“筋”,用竹篾加稻杆打成的绳子,要一而贯之,不能接。届时,同行的人会来帮忙。在退潮时,两条船只靠拢一起,将已备好的“桁”放入水中,竖起来,用一大木斗,把中空约一米多长的一头套在“桁”的上方,实心的一头向上,木头的两边穿着两条长长的竹制抬杠,两艘船上的十几个劳动力以步骤相一致的动作,将木头抬起放下,再抬起放下,直至把“桁”打入海底。留“筋”在水面上,再分支用于缆鱼网或船只。这种竹篾加稻杆制成的“筋”只能使用两年时间,到时就要更换。现在改用尼龙丝做“筋”,使用寿命长达五六年之久。艋艚“桁”打好后,将木斗收藏起来,主人还得宴请大家,欢聚一堂,以资庆祝。
三、告别放鹰叼杂鱼
驯鹰叼鱼,是沿海居民传统的捕鱼方法之一,过去很普遍,现在没有了。鱼鹰,也叫“鱼老鸦”,鸟纲,鸬鹚科,通称鸬鹚。体长可达0.8米,羽毛多为黑色而带有紫色金属光泽,喜栖在河川、湖沼和海滨,善潜水,捕食鱼类,常巢于草丛中或矮树、峭壁上。
沿海、沿江的村民有谣曰:“两只鸬鹚胜过一张渔网”。就是说,过去连家船的渔民,依靠一船一网养活一家子人,而岸上的村民只要能驯养两只鸬鹚出去叼鱼,也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了。笔者在五十多年前,曾两次见过鱼鹰叼鱼的事。首次是1955年夏,八都区金垂乡搞“改造落后乡”工作的检查验收时,该村有一林姓的老人驯养8只成年的鸬鹚,每天划着竹筏,上面放个加盖的装鱼大竹篓,竹筏两旁的栏杆上各站4只鸬鹚。他自个儿顺着水草丰美的江边,悠然自得地划呀!划呀!而筏上两旁站立的鸬鹚也眼睁睁地盯住水面,瞧着!瞧着!其中的一只鸬鹚发现目标,迅即跳入水中,潜游下去。不一会儿,鸬鹚口里就噙着一头活蹦活跳的鱼儿爬上竹筏,渔翁即从它口里掏出来,约有一斤多重。这只鸬鹚初战告捷后,抖动一下身子,去掉水分,松动羽毛,又站到杆上去。接着,另一只鸬鹚下水……上述的情景,撩动了当时我那年轻的好奇心,很想探询个究竟。有一天,村上分派工作组人员伙食,到了这渔翁家,餐桌上未免有几道海鲜,正是向他探询鸬鹚一事的极好机会,故在用餐中,宾主有一段颇具趣味性的对话,今日想起,记忆犹新。摘录如下,以供参考。
“你家8只鸬鹚一天出去能捕到多少鱼?”我在餐桌上恳切地问道。
“不一定,这个需要看季节和天气如何。平时一天出去一趟,捕个一、二十斤鱼是有的。”他回答后,又觉得不够完整,稍后思索,补充说:“严冬,鱼儿深藏水底;下雨,鱼花看不清楚,均难捕到鱼。特别是天寒,鸬鹚怕冷,不能出去,在家还要用小鱼小虾喂它。
“你家的鸬鹚是怎么来的?”同桌的驻乡工作组姚同志接过话题问道。
“是我父亲遗留下来的,起先只有4只。由于霍童溪的海水交汇处鱼多,捕获量比现在还多。”老渔翁回答。
“那你现在这多出的4只鸬鹚是怎么来的呢?”
“有的是用渔网诱捕来的,有的是鸬鹚巢里抓的幼鸟。”
“这些从野外抓来的鸬鹚,不管是成鸟或幼鸟,肯定野性十足,你又是如何去驯化?”
“这驯化鸬鹚,确实很费工夫。简单说来,有栓脚、箍颈、站杠、熬鹰等几个环节。也就是说,抓到鸬鹚后,先用绳子将它的脚栓起来,不让其飞走。再拿削细的竹篾将它的脖子箍好,不让它吞食半斤以上的鱼儿。然后用一条木杠让它站立在上面,喂食睡觉都不要让它下来。这一环节极为关键,要结合主人与它对视——目对目来做。时间一长,习惯成自然,就被你驯化了。”老渔翁解答问题的大意是这样,今随时间的推移,细节已被遗忘。
过后一年多,农业合作社大风暴来临时,我下乡路过八都的溪池村,又碰见一次竹筏在霍童溪放鹰叼鱼,经查问是福安人过来的。此后,我再也没有看见鸬鹚叼鱼的作业了。
今日的宁德,这鸬鹚叼鱼的作业虽已消亡,但历史上因此而产生的俚语却仍流传于民间。比如:“鸬鹚箍着(脖子)吃。”是指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又如:“今年冬天要做鸬鹚了。”是说没有寒衣、棉被过冬。再如:“鸬鹚拍来贼拍去。”是指到手的财物,又被他人搞走了。
四、告别夜黑投白船
我知道有“投白船”,是童蒙时期从一句民间成语中来。笔者幼年在家,时常结伴玩耍。有一次,正玩得高兴时,大人却告诉我们说:你看!投白船荡(划)过来了,他会骂人的,赶快走开。听了这话,孩子们一哄而散。我走出几步,就回过头来顺着大人手指的方向看去,哪里有什么船儿。分明是个瘸子,走路身子不平衡,直摇晃着,一拐一拐的往前行。这时的心里有些迷惑不解,却也朦朦胧胧的过去了。时隔数年,我已经是在校的高小生了,放暑假时跟随家里人去云淡村堂姐家做客。船到村口泊岸,见坡上有一简陋的民房,里面并排摆放着十几艘窄长的小木船,尖头方尾,长近二丈,宽约三尺,不像是龙舟。当日,在我堂姐家隔夜,第二天早晨起床,看见她家天井里放着一只大竹篓,里面装有约十多斤活蹦活跳的鱼儿,内最大的一尾身长背黑,眼睛红红的,大约有五六斤重。我就问我堂姐夫这是怎么回事,哪里搞来的这么多鱼?他回答说,昨夜天空很黑,村上的投白船出去捕的鱼。当我听到“投白船”这三个字时,就想起数年前大人把瘸子走路比喻成投白船的话并告诉他。他听了并未立即回答,只是带我去看村口坡上摆放的投白船和搁在船旁边两块用来在水中“刷白”的杉木板,那木板长约一丈,宽五六寸。看后才介绍说,这种船是专门为诱鱼上船而设计的,窄而长,只能容纳一个人,使用一橹一浆,涨潮时从本村起航,开往对面南浦村边,由下至上,将已刷白的两块木板连接起来,搁在船的右舷边,持一定的向外倾斜度,最好外侧要贴近水面。因船狭窄,浆子一划,船身就会晃动,船舷白板与荡漾的水花相映,会发出闪光,这里的鲻科鱼类,比如:青头、只鱼、红目缁、跳蚤缁等有趋光性,晚间涨潮出来到岸边寻食时,见了即往光处跳跃,多能落入船中。船再沿着金垂村边,开至八都村外,到回程时,将船上的白板搬到左舷,往下游开回去,来回约需两个多钟头。此一作业的好处是可以引诱鱼儿上船,十几二十斤重的都有。鸬鹚叼鱼,三四斤的就没办法了。大的鱼跳上船,就得脱下身上的棕衣把它盖住,船身也震动得厉害。不然,这鱼又会跳到水中。我俩边看边谈,回到我堂姐家。中午,在他家吃了饭,正好涨潮,就搭船回家了。此次到云淡村走亲戚,虽未亲眼看到“鱼跳上船”的情景,但投白船与捕获的鱼都已见到,特别是堂姐夫给我介绍的话,使我明白了把瘸子走路比喻成投白船,是一形象性的语言。
1959年秋,我以驻村工作组员的身份到了云淡村,很想前去体验一下这投白船捕鱼的作业过程,经查问村里干部,得知这一捕鱼作业早已没有了。
五、告别撑枷截鱼群
撑枷拦截退潮鱼,是夏秋季节浅海鱼类肥美时,沿海村民在潮水“前滨区”进行的一种围捕。据我回忆,从能记事起,故乡的西陂塘每年都搞好几次撑枷作业,各户均备有一副以上专门用来捕鱼的“罩”。它是用竹篾编就上小下大的喇叭状捕鱼工具,形似“鸡笼”,两只配对,高过膝盖,紧扎棕绳,整体牢固。上口为抓手,使用时一手抓一只,往水里罩,被罩入的鱼儿在里面挣扎,伸手抓住即可。这“罩”有雌雄,可以套起来用绳子串着背在身上,不用时又套在一起挂到墙上去。
撑枷作业规模大,用网多,受益广。领头者,过去多为村上有威望的人。因为西陂塘滩涂大多是养殖缢蛏,万一被踩踏有损失,也好出面解决赔偿问题。作业时,选个有鱼儿出没的港汊,以观鱼色(粪便)作判断,确定后,白天退潮时,按五米的距离扦插撑杆(竹子),牵拉鱼网(埋下)等。关键是在港汊的低洼处布螺旋“阵”、安储鱼“斗”。范围要覆盖这一特定水脉的全流程,包括港汊两旁高处。做好后,让潮水淹没进去。待到半夜潮水退落,形成一定流速,鱼儿将开始随潮退出时,守在港汊两旁高阜处两艘船只,即从高处潮水先退的地方着手,顺着撑杆将渔网持上水面,将两旁海面上的鱼儿赶往港汊去,驱入已布好的螺旋“阵”,再落到储鱼“斗”,集中网罗起来。但当海面的鱼儿被驱赶入港中,有些因触网而受惊动,就会掉头,逆流而上,这部分鱼,按照村规民约,是允许村民拾取的。这撑枷的作业多选择在像初一、十五的大潮日进行,天亮不久,潮水就回涨了。所以,去撑枷鱼的人不耽误白天干活。背着“罩”子去罩鱼的人很多,连十一、二岁在校的学生都跟着大人去,因人矮无法使用“罩”,只好跟在后面去手摸躲藏在足迹里的鱼。因为港汊两旁都是泥滩,人们走过后,踩出深陷的足迹,鱼被打“罩”后,会胡奔乱窜,藏入足迹。笔者幼年也曾跟随大家去摸鱼过,体验过这种生活,其感受是摸到一只鱼比吃下一只鱼的情趣更浓更有意思。很可惜,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于鱼类资源减少,此项作业已经没有了。
六、告别挖壑存鱼
从前,每到沿海的一个村庄,均能看到村前“潮间带”的海滩上,都挖有许多大小不一的储水坑,即便是退潮期间,滩涂已经干涸,这坑里仍储满着水。这到底是干什么的?陌生人不知道,原来为了储水存鱼蟹。在西陂塘未围垦前,沿岸各村都有,俗称鱼“壑”。小的为住户所独有;大的是合作共有。每年的“清明”节前,都要将“壑”清淤一遍,把挖出的泥用来增高培固外堤,然后再在低处安个涵洞,高处搞石砌预洪坝通水。涵洞一堵,就能储水,任其潮起潮落,直至农历五月“端午节”前开涵放水,“壑”内的鱼蟹任你抓取。“小壑”可收获几十斤,大“壑”几百斤不等。我幼年在家时,看见一天中放“壑”几十个。过节时,有挖“壑”的人家都排满着许多的鱼、虾、蟳等,特别是蟳,几天吃不完,将腿脚齐全、七八分饱满的都养起来,可以吃十几天。没有挖“壑”的人家,也多接受别人的馈送。同时,放“壑”是允许别人捡“壑”底的,所以,家有小孩半劳力的也不缺鱼蟹。这“壑”放后又堵上,下次放“壑”是农历七月十五“中元”祭祖节前和再下一次的八月十五“中秋”节前了。此后,小“壑”放弃,大“壑”九月初九“重阳”节前仍能再放一次。因为天气转冷,“壑”小水浅,不存鱼蟹了。
说到鱼“壑”,不觉使我想起童年在家亲眼看见的一件事,今虽时隔六十多年,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我家离海很近,小时候常在海边,或玩耍,或戏水,或讨些小海的东西。1949年,国民党107旅部队驻宁时,下属有一排的兵士驻在濂坑乡(时为乡建制)的炮台(它是1928年海军上将萨镇冰前来赈灾时建下的“守御堡”)。夏日,骄阳似火,酷热难熬。一天中午,几个兵士来到海边,因是小潮,海水已经退去。遗下的是一片干涸的滩涂,只有那一个个人工开挖的鱼“壑”仍充满着蓝色的海水。这些兵士可能是外地人,不知就里,即脱掉外面的衣衫,只穿一条短裤,走进“壑”中去洗澡。不料,却惹来大麻烦了。其中一人的脚被蟳螯钳住,痛的呼爷叫娘,他不知到蟳的特性,用手去抓,越抓越钳得越紧,在水中挣扎起来,“壑”水被搅动后,别的蟳也漂上来,螯住他身上的多个部位,还差点被淹死在水里。我当时才七、八岁,一帮小伙伴看见了,觉得很好笑。另外,还听长辈们讲过“豚困鱼壑”的故事。大概是从前有一年夏天,一只海豚进入西陂塘的“壑”里觅食,不知是因为贪食而迷路,或是别的原因,潮水退去,仍困在“壑”里,“壑”主痛恨它把储存的鱼全糟蹋了,故将水放干,抓拿回去,有二百余斤。此为往事,但笔者幼年在家,海豚进入西陂塘为常事,特别是夏暑季节,涨潮时多能见到它欢悦在水面上。至于鱼“壑”,自七十年代后,由于人为因素近海资源减少,已经没有了。
附注
注释:(1)红流时出门鱼。红流,方言,指潮水涨落二分有流速时(假设将潮水的涨落分作十个等分来计算);出门鱼,指平潮止汐时,水无流鱼无路,潜入礁石中,到涨落二分有流速时,成群结队出门寻食。此刻,好的“掌縺”就能抓住机会,准确地撒下网子,截取鱼群,获得丰收。它在《官井书》中,叫作“过腊(腊,礁石)开津”。但有极大的危险性,如果“掌镰”技术不过硬,产生偏离,触到礁石,既有网破船翻之虞。
(2)特定海域。指在三都澳官井洋内。过去,因受到民船和技术等条件的限制,也由于人们有着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意识,不能越界捕捞。范围现在下自东冲口罗源属吉壁“铜盘”,上至三都本岛北“灶屿”为止。故民间有谣曰:“黄瓜不上灶,带鱼不上盘。”
作者简介:王致纯,1947年濂坑村中心小学毕业。1958年至1959年县业余大学进修现代汉语,1951年起先后在县委秘书室、监委会、审干办、统战部工作,1995年退休。现住蕉城。
相关人物
王致纯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