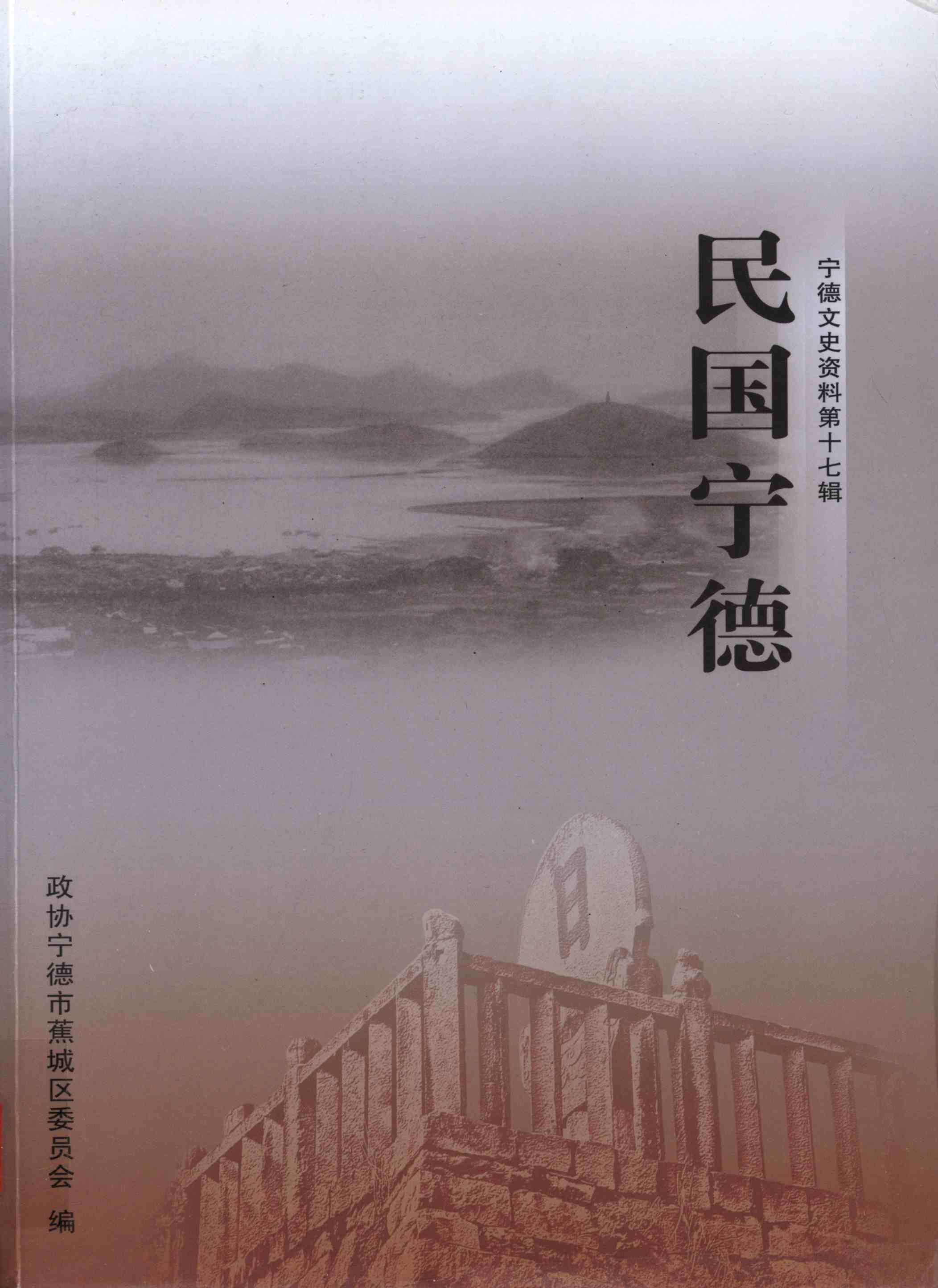古溪村的古风旧俗
| 内容出处: | 《民国宁德》 图书 |
| 唯一号: | 130920020210000457 |
| 颗粒名称: | 古溪村的古风旧俗 |
| 分类号: | K892.2 |
| 页数: | 7 |
| 页码: | 228-234 |
| 摘要: | 古溪村位于蕉城市区南郊,古称“汐头”。自古背山面海,居民富庶,民风淳朴,历史久远。早在唐代就有余、汤二姓泛海而至。南宋时期,林姓由莆田八角井迁入。元末明初,祖籍中原的陈、谢二姓相继入住。各个姓氏所带来的不同地域的风俗习惯,经过长期的融合演变,造就了这方水土诸多特殊的地方文化和民俗活动。诸如春节、端午、中元、中秋等传统节日,以及婚丧嫁娶,都存在着诸多与蕉城其他乡村迥然有别的风俗习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是我国汉族人民的传统节日。唯有赛龙舟这项最为盛大的活动,却与其他沿海乡镇有所不同。多数年份,都是古溪村的两支队伍夺得冠军。 |
| 关键词: | 风俗 民间 宁德县 |
内容
古溪村位于蕉城市区南郊,古称“汐头”。自古背山面海,居民富庶,民风淳朴,历史久远。早在唐代就有余、汤二姓泛海而至。南宋时期,林姓由莆田八角井迁入。元末明初,祖籍中原的陈、谢二姓相继入住。各个姓氏所带来的不同地域的风俗习惯,经过长期的融合演变,造就了这方水土诸多特殊的地方文化和民俗活动。诸如春节、端午、中元、中秋等传统节日,以及婚丧嫁娶,都存在着诸多与蕉城其他乡村迥然有别的风俗习惯。
端午“扒龙船”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是我国汉族人民的传统节日。闽东民间把端午节称为“五月节”,过端午称为“做节”。在闽东蕉城、福安、寿宁、古田、屏南等县(市)的大部份乡镇都是五月初四过节,而包括古溪在内的蕉城城区以及周边乡镇都是按照传统,在初五这天过节。古溪民间过端午节没有什么特殊的习俗,在端午节即将来临的几天里,不外乎就是给小孩子添置新衣,打扫房屋卫生,包裹粽子,女婿忙着给岳家“送节”之类。到了初五这天,每家每户准备丰盛的午餐,悬挂菖蒲,喝雄黄酒,给孩子佩戴长命缕。唯有赛龙舟这项最为盛大的活动,却与其他沿海乡镇有所不同。
古溪村民从事海洋捕捞和养殖的历史十分悠久,村子东南的大片滩涂位置优越,盛产泥蚶、螠蛏、牡蛎、花蛤等海产品,畅销福州、长乐、福清、古田等地。古溪村民把赛龙舟称作“扒龙船”,活动开展的地点也是在村前的“东湖塘”。在东湖塘东南方向有个“龙船塌”(位置大概在大门山与虎山交界处)的地名,据说有一年赛龙船,有一条船在这片海域无缘无故失踪。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是,古溪村民没有能力制造专门用作赛龙船的龙形船只,只是借用村里私人的运输船只。船只作为海上必备的交通、运输工具,古溪民间全盛时有大小船只三十余艘,到民国时期还有十余艘。船只按大小分为称为“三杆栋”(即有三张帆,可负重数百石,多作为外洋运输之用)、“两杆栋”(即有两张帆)、“铜舵”(多作为海上捕捞之用)、“扒舵”(运壳灰、粪便之用,可负重数十石)、“舢板”。由于三杆栋、两杆栋、铜舵体积大而笨重,舢板体积太小,都不理想。只有扒舵最为合适,所以村里的五六条扒舵就逐年轮流,不计报酬。
古溪村每年参加赛龙船的有两支队伍,分别由上厝保(又称古溪元境)、下厝保(又称古溪正境)组成。上厝、下厝龙船上各张挂着一面三角旗,上厝的为红底白边,色如鸡冠,称为“鸡角(公鸡)旗”;下厝为白底红边,形如蜈蚣,称为为“蜈蚣旗”。参加比赛的除了古溪的两支队伍,还有东湖沿岸的南门四村头(南门兜、桥头下、小场、下宅园)、塔山、金蛇头、蓝田等村,以及城内马厝坪、东门外下尾埠。参赛船只皆为“扒舵”,唯有南门兜因为商贩较多,实力雄厚,才拥有一条像模像样的龙船。比赛起止地点是由古溪的决兜至下尾码头,大致三四公里的距离。一路上设有众多标杆,标杆以竹竿制作,上悬鸭子、老酒、手帕、白扇等奖品,夺标最多即为优胜者。多数年份,都是古溪村的两支队伍夺得冠军。
参加龙船赛的每条船上都有二十位参赛者,其中划桨十六人,掌尾舵一人,一人放鞭炮,另外两人负责敲锣打鼓。民国时期,古溪村经常参加龙舟赛的村民知名的有陈关葛、陈细细妹、陈方下、谢红伢妹、阮嫩弟、谢清弟等人。其中以陈关葛、陈细细妹两位“大力水手”最为知名,二人虎背熊腰,臂力过人,划龙舟时短桨(俗称“扒靸”)都必须有两把重叠使用,否则会因为用力过猛而折断。
蕉城有一句俗语说的好“龙船没水干汐兴”。可见,赛龙船是一件“乐事”,是闲人才能参与的娱乐性活动。当时很多人家忙于生计,除了春节能休息几天,其余节日还是要下田干活的。所以,每年赛龙船时往往不能凑齐参赛的人数。一些爱搞恶作剧的人,就提上一桶海水,或沾上一身泥巴,将不愿参赛的村民身上搞脏,逼迫他们下海参赛。抗战时期,民国政府曾一度下令禁止娱乐活动。当时,下厝有一位绰号谢买卖的光棍,喝醉酒还想着能有龙船赛。他负着一支尾舵,沿街叫人去参加龙船比赛,一边走一边口里还嘀咕:“联保(相当于如今的乡长)我买卖做,龙船拔去扒。”反复念叨,走路摇摇晃晃,最后掉进了路边水沟,惹来路人的阵阵嘲笑。
还有一个姓陈的村民,家境贫穷,但又极爱面子。有一次过节吃了午饭,也去参加龙舟赛。同厝的一位叔伯兄弟也许是一片好意,对他说:“某某兄,大过节的,你中午就吃了一碗番薯米粉(番薯米最底层的碎末,含有泥土、虫粪等不洁之物),还有力气去扒龙船。”某某兄认为他是在侮辱自己,大动肝火,当即争吵起来,幸有旁人相劝,才得以平息。
中元“施食”
每年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古溪民间与山区乡镇不同,一般不做“普度”,只在中元之日,各行业商铺出资祭祀孤魂野鬼,称为“施食”。“施食”多安排在下午,遍插明香于店铺周围主要通道,尔后设千层糕、草鞋仔、“棉衣”、锡仔、米酒于店门口,祭祀完毕,将糕切成碎块,散发给路人。
农家也有“施食”,又叫“请地头公”,多在中禾收割完毕,晚稻刚刚播种的水田田埂上进行。祭祀时,除了在水田四周遍插明香外,其它仪式与店铺“施食”相同。
从祭祀含义来看,农家的“施食”有祀田神的遗意。因为蕉城民间视“地头公”为神灵,而不当作孤魂野鬼看待。所以,“地头公”是农家对“田祖”的民间称谓,既通俗又贴切。据乾隆版《宁德县志·风俗》:
“十一月,各乡赛祭,是时禾稼登场,杀牲为黍,以飱田祖,谓之冬福。”乾隆版《吴县志》:
“中元前后,农人耕耘甫毕,醵钱赛猛将之神”、“祀田神,各具粉团、鸡黍、果蔬之属,于田间十字路口再拜而祝,谓之‘斋田头’。按韩昌黎诗:莫向田头乐祀神。《周礼》疏曰:社者,五土之总神,又为田神所依。则是七月十五之祀,犹古之‘秋社’耳。”
现在,商铺“施食”、农家祭祀“地头公”已渐消失,倒是许多水果种植户、水产养殖户为了祈求事业平安有成,沿袭着了这一项古老而传统的祭祀活动。
中秋“牵磨连”
蕉城民间有一句俗话“年三天,节三顿,中秋立夏没一顿”。旧时民间提倡节俭,过中秋节时,各家各户无非吃些月饼,餐桌上的伙食并没有多大改善。虽然如此,蕉城中秋节的民间活动却是丰富多彩的,如相传起源于明代戚继光抗倭的曳石踩街,还有花灯、铁枝、肩头坪、踩高跷、线狮、纸扎,以及带有迷信色彩的“走阴间”等等。在古溪村,还有一个需要大人小孩共同参加、形式独特的“牵磨连”游戏。
在古溪下厝的头谢谢氏宗祠遗址(俗称“头谢坪”)门口,旧时用鹅卵石镶嵌有太极八卦图案,造型精美,十分显眼。在八卦石旁的草坪中,还有一块粉红色圆石,未经加工,却平滑如镜。这些就是“牵磨连”游戏的道具。每年的中秋节,孩子们就开始忙活着到处采摘芦荟(俗称“龙舌”),寻找苎麻皮(农村妇女轧纃的下脚料),这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芦荟、麻皮收集以后,将麻皮垫底、芦荟铺面,铺设于八卦石上。游戏需要四个大人、四个儿童同时参加。四个儿童站在磨盘石上,悬空做“一”字形平卧,双手上举,四个大人站于八卦石边沿,分别擒住一位儿童手腕,这样儿童的重心力量都由大人掌握着。准备妥当以后,脚踏实地的四个大人开时由慢转快渐渐旋转,由于芦荟起到润滑的作用,圆石随着脚步会越转越快,如腾云驾雾一般,十分刺激。这个游戏与今天的旋转木马、旋转飞车等游戏有些类似,在当时已算得上比较“新潮”的游戏了。
做“九月十四”
古溪是个完全信仰本土宗教的村庄。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天主教、基督教教徒都试图在村里传教,皆由于村民宗族意识强烈,未能实现。村中旧时有五大姓,即陈姓、谢姓、林姓、倪姓、池姓,按居住界限划分,又分为上厝、下厝、内厝。民国时期,这三个居民点皆设有保长,各自为政。古溪村民所尊奉的神灵十分复杂,有忠烈王、普济明王、临水夫人、师公、田元帅、齐天大圣等数十位,以忠烈王黄岳、普济明王林亘(即林公忠平王)、临水夫人陈靖姑为主神。村里供奉忠烈王黄岳的庙宇一忠烈行祠赫赫有名,在历代地方志中都有记载,它所建成的时期仅次于城关东门外的土主宫。供奉普济明王的庙宇在村东塘前头,隔着东湖,与塔山遥遥相望。这两位神灵,被村民尊称为“社头公”。临水夫人俗称“大侬奶”、“奶娘”,上、下、内三厝各有一尊(其中下厝有两尊,分别称为“旧奶娘”、“新奶娘”。除了下厝有单独的奶娘宫外,其他二尊皆供奉于祠堂)。除了春节,被古溪村民视为最大的节日应该就属每年农历“九月十四”的黄岳诞辰庆典了。忠烈王宫的公产不多,只有少量的土地和海埕出租。每年的收入勉强维持诞辰庆典之费用,如遇修缮庙宇的年头,就只能由村里殷实人家集资来完成。每一年负责庆典各项活动的人员皆为二十名,称作“社头头”,由村里成丁(蕉城民间习惯以十六岁成丁)男性轮流充当。据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回忆,每年到了农历九月十三这天早上,新当选的“社头头”就会开始准备供品,制作大量“寿桃”(即形如寿桃的糖包)。到了晚上,“社头头”就踏着月色,早早集中村西郊的忠烈王庙,备办“祭桌”(即祭祀物品),燃烛上香,届时还有“吹班”(闽剧清唱)助兴,庙内灯火通明,彻夜如昼。这一活动俗称“庆赞”。到了交子时时分,就有一名“社头头”手持铜锣,进入村中,边走边大声反复高喊:“新头新柱”(意思是说新的“社头头”已经产生),听到喊声的村民就会陆续醒来,到庙里上香,给忠烈王拜寿。旧时缺吃少穿,一年难得吃上几回好东西,这一晚能吃到香喷喷的白面糖包,所以也成为小孩子们最为高兴的节日。上香的成年人身后,总会跟随着一两个小孩,他们也可以兴高采烈地领回一合“寿桃”。
九月十四至九月十六这三天时间,按例都要演出闽剧。届时村里家家户户都要邀请亲友来观看演出,一日三餐还要备办茶饭,用度甚高,对多数人家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负担。但村民乐此不疲,相沿成俗。就是在民国时期,有一段时间为了搞好治安,禁止民间娱乐。为了保证整个活动不出事端,村民陈骰子宁愿自己入狱作担保,使庆典照常进行。
上面我们已经说过,由于忠烈王庙的公产很少,捉襟见肘,所以备办忠烈王“祭桌”就得由当年的“社头头”自己掏腰包。为了凑齐这一款项,就逐渐产生了“贴喜”的习俗。所谓“贴喜”,就是由“社头头”作若干个“糯米大寿桃”(将糯米蒸熟后,拌上红糖,做成寿桃模样,大者数十斤,小者十余斤),送到当年村里有喜事的人家。喜事无论大小,小至砌灶、砌猪圈,大至建房、娶媳、生子,都必须“贴喜”。“寿桃”大小也视喜事隆重程度而定,以娶媳(俗称“新妇喜)、第一胎生男(俗称“长男喜”)最为注重。“社头头”们在忠烈王圣诞的前几日,会把写有喜事内容的红字条“贴”到该村民住宅的大门之上。该村民就得视自家喜事大小交纳款项。由于一年中,村里的喜事有多有寡,碰上不好的年份,“社头头”们就只好自己凑足金额了。
顺便带一笔,每年农历正月十五的“奶娘诞”,村里的成丁男女不仅要举行“过关”仪式,还有所谓“送烛母”的习俗。“送烛母”的对象是村里刚刚成婚的人家,或者有结婚后长期不生育的人家。在每年的“奶娘”巡游完毕“圆宫”以后,这些人家男子的年轻好友都会邀上四五位,带着一双奶娘座前请来的红烛(点燃着的),一铁铲熊熊燃烧的木炭,送到家中。年轻的夫妻们就会高高兴兴地予以接受,将红烛供奉在祖先的龛位前,而炭火则倒入炉灶。尔后,准备酒菜招待这些热心的朋友,尽兴而散。
而今,随着时代的飞跃发展,各种旧的习俗已遭到舍弃。忠烈王庆典中除了“庆赞”、“演戏”等还保留以外,“分寿桃”、“贴喜”、“送烛母”等似乎意味着贫穷落后而不再流传。也许随着人们传统意识的淡薄,其他仪式也将一去不复返,只留下记忆供人们回味!
婚前“请仪校”
蕉城民间对男婚女嫁十分讲究,比外省外县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古至今,蕉城还流传着许多特殊的婚嫁习俗,如沿海乡镇的“打醮”、“新郎伴睏”,飞鸾二都的“扭星”(新媳妇过门时,亲友要掐其手臂肉)以及古溪村的“请仪校”。
请仪校在古溪至少已经流传了一两百年,它的来由,包括它的正式写法已无从查考。“请仪校”的时间都安排在结婚前一天,即新郎(女儿出嫁无此仪式)“打醮”(又称“请喜神”)的当天晚上,这项仪式多由村里年长的男性老人完成。当天晚饭过后,办喜事的家庭就要煮两碗线面,每碗面上放上两粒煮熟剥壳的鸡蛋(俗称“一碗面两粒蛋”),还要准备红烛一合,香六支,红酒一斤,锡酒壶一合,酒盅十只,锡帛一捆。装入“碗栳”,送到前去“请仪校”的老人家中。当晚夜深人静的时候,老人带上这些物品,到祠堂仪门(俗称“雨亭”上厝的居民多在陈氏上祠堂,下厝的居民多在尾谢祠堂)前,在廊前石板上就地祭祀。祭祀时间大约为半柱香功夫。老人在祭祀过程中,还要默默祷告,内容为新郎新娘双方姓名、年龄、住址,最后祈求神灵保佑夫妻白头偕老,生活美满。祭祀完毕,烧过锡帛,老人将蛋面带回家中,分给家人享用。装蛋面的“碗栳”必须在三日以后,等新郎(新娘)办完喜事后送还。也就是说,“请仪校”虽然是办喜事的人家分内之事,但至始至终,他们都没有直接参与。这样一个古怪风俗,它的祭祀对象是谁呢?有的说是祭祀临水夫人,但烧的却是鬼魂使用的锡帛?有的说是祭祀祖先,却为什么不在祠堂内祭祀呢?孰是孰非,就是操持“请仪校”的老人自己也难以说清。
端午“扒龙船”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是我国汉族人民的传统节日。闽东民间把端午节称为“五月节”,过端午称为“做节”。在闽东蕉城、福安、寿宁、古田、屏南等县(市)的大部份乡镇都是五月初四过节,而包括古溪在内的蕉城城区以及周边乡镇都是按照传统,在初五这天过节。古溪民间过端午节没有什么特殊的习俗,在端午节即将来临的几天里,不外乎就是给小孩子添置新衣,打扫房屋卫生,包裹粽子,女婿忙着给岳家“送节”之类。到了初五这天,每家每户准备丰盛的午餐,悬挂菖蒲,喝雄黄酒,给孩子佩戴长命缕。唯有赛龙舟这项最为盛大的活动,却与其他沿海乡镇有所不同。
古溪村民从事海洋捕捞和养殖的历史十分悠久,村子东南的大片滩涂位置优越,盛产泥蚶、螠蛏、牡蛎、花蛤等海产品,畅销福州、长乐、福清、古田等地。古溪村民把赛龙舟称作“扒龙船”,活动开展的地点也是在村前的“东湖塘”。在东湖塘东南方向有个“龙船塌”(位置大概在大门山与虎山交界处)的地名,据说有一年赛龙船,有一条船在这片海域无缘无故失踪。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是,古溪村民没有能力制造专门用作赛龙船的龙形船只,只是借用村里私人的运输船只。船只作为海上必备的交通、运输工具,古溪民间全盛时有大小船只三十余艘,到民国时期还有十余艘。船只按大小分为称为“三杆栋”(即有三张帆,可负重数百石,多作为外洋运输之用)、“两杆栋”(即有两张帆)、“铜舵”(多作为海上捕捞之用)、“扒舵”(运壳灰、粪便之用,可负重数十石)、“舢板”。由于三杆栋、两杆栋、铜舵体积大而笨重,舢板体积太小,都不理想。只有扒舵最为合适,所以村里的五六条扒舵就逐年轮流,不计报酬。
古溪村每年参加赛龙船的有两支队伍,分别由上厝保(又称古溪元境)、下厝保(又称古溪正境)组成。上厝、下厝龙船上各张挂着一面三角旗,上厝的为红底白边,色如鸡冠,称为“鸡角(公鸡)旗”;下厝为白底红边,形如蜈蚣,称为为“蜈蚣旗”。参加比赛的除了古溪的两支队伍,还有东湖沿岸的南门四村头(南门兜、桥头下、小场、下宅园)、塔山、金蛇头、蓝田等村,以及城内马厝坪、东门外下尾埠。参赛船只皆为“扒舵”,唯有南门兜因为商贩较多,实力雄厚,才拥有一条像模像样的龙船。比赛起止地点是由古溪的决兜至下尾码头,大致三四公里的距离。一路上设有众多标杆,标杆以竹竿制作,上悬鸭子、老酒、手帕、白扇等奖品,夺标最多即为优胜者。多数年份,都是古溪村的两支队伍夺得冠军。
参加龙船赛的每条船上都有二十位参赛者,其中划桨十六人,掌尾舵一人,一人放鞭炮,另外两人负责敲锣打鼓。民国时期,古溪村经常参加龙舟赛的村民知名的有陈关葛、陈细细妹、陈方下、谢红伢妹、阮嫩弟、谢清弟等人。其中以陈关葛、陈细细妹两位“大力水手”最为知名,二人虎背熊腰,臂力过人,划龙舟时短桨(俗称“扒靸”)都必须有两把重叠使用,否则会因为用力过猛而折断。
蕉城有一句俗语说的好“龙船没水干汐兴”。可见,赛龙船是一件“乐事”,是闲人才能参与的娱乐性活动。当时很多人家忙于生计,除了春节能休息几天,其余节日还是要下田干活的。所以,每年赛龙船时往往不能凑齐参赛的人数。一些爱搞恶作剧的人,就提上一桶海水,或沾上一身泥巴,将不愿参赛的村民身上搞脏,逼迫他们下海参赛。抗战时期,民国政府曾一度下令禁止娱乐活动。当时,下厝有一位绰号谢买卖的光棍,喝醉酒还想着能有龙船赛。他负着一支尾舵,沿街叫人去参加龙船比赛,一边走一边口里还嘀咕:“联保(相当于如今的乡长)我买卖做,龙船拔去扒。”反复念叨,走路摇摇晃晃,最后掉进了路边水沟,惹来路人的阵阵嘲笑。
还有一个姓陈的村民,家境贫穷,但又极爱面子。有一次过节吃了午饭,也去参加龙舟赛。同厝的一位叔伯兄弟也许是一片好意,对他说:“某某兄,大过节的,你中午就吃了一碗番薯米粉(番薯米最底层的碎末,含有泥土、虫粪等不洁之物),还有力气去扒龙船。”某某兄认为他是在侮辱自己,大动肝火,当即争吵起来,幸有旁人相劝,才得以平息。
中元“施食”
每年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古溪民间与山区乡镇不同,一般不做“普度”,只在中元之日,各行业商铺出资祭祀孤魂野鬼,称为“施食”。“施食”多安排在下午,遍插明香于店铺周围主要通道,尔后设千层糕、草鞋仔、“棉衣”、锡仔、米酒于店门口,祭祀完毕,将糕切成碎块,散发给路人。
农家也有“施食”,又叫“请地头公”,多在中禾收割完毕,晚稻刚刚播种的水田田埂上进行。祭祀时,除了在水田四周遍插明香外,其它仪式与店铺“施食”相同。
从祭祀含义来看,农家的“施食”有祀田神的遗意。因为蕉城民间视“地头公”为神灵,而不当作孤魂野鬼看待。所以,“地头公”是农家对“田祖”的民间称谓,既通俗又贴切。据乾隆版《宁德县志·风俗》:
“十一月,各乡赛祭,是时禾稼登场,杀牲为黍,以飱田祖,谓之冬福。”乾隆版《吴县志》:
“中元前后,农人耕耘甫毕,醵钱赛猛将之神”、“祀田神,各具粉团、鸡黍、果蔬之属,于田间十字路口再拜而祝,谓之‘斋田头’。按韩昌黎诗:莫向田头乐祀神。《周礼》疏曰:社者,五土之总神,又为田神所依。则是七月十五之祀,犹古之‘秋社’耳。”
现在,商铺“施食”、农家祭祀“地头公”已渐消失,倒是许多水果种植户、水产养殖户为了祈求事业平安有成,沿袭着了这一项古老而传统的祭祀活动。
中秋“牵磨连”
蕉城民间有一句俗话“年三天,节三顿,中秋立夏没一顿”。旧时民间提倡节俭,过中秋节时,各家各户无非吃些月饼,餐桌上的伙食并没有多大改善。虽然如此,蕉城中秋节的民间活动却是丰富多彩的,如相传起源于明代戚继光抗倭的曳石踩街,还有花灯、铁枝、肩头坪、踩高跷、线狮、纸扎,以及带有迷信色彩的“走阴间”等等。在古溪村,还有一个需要大人小孩共同参加、形式独特的“牵磨连”游戏。
在古溪下厝的头谢谢氏宗祠遗址(俗称“头谢坪”)门口,旧时用鹅卵石镶嵌有太极八卦图案,造型精美,十分显眼。在八卦石旁的草坪中,还有一块粉红色圆石,未经加工,却平滑如镜。这些就是“牵磨连”游戏的道具。每年的中秋节,孩子们就开始忙活着到处采摘芦荟(俗称“龙舌”),寻找苎麻皮(农村妇女轧纃的下脚料),这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芦荟、麻皮收集以后,将麻皮垫底、芦荟铺面,铺设于八卦石上。游戏需要四个大人、四个儿童同时参加。四个儿童站在磨盘石上,悬空做“一”字形平卧,双手上举,四个大人站于八卦石边沿,分别擒住一位儿童手腕,这样儿童的重心力量都由大人掌握着。准备妥当以后,脚踏实地的四个大人开时由慢转快渐渐旋转,由于芦荟起到润滑的作用,圆石随着脚步会越转越快,如腾云驾雾一般,十分刺激。这个游戏与今天的旋转木马、旋转飞车等游戏有些类似,在当时已算得上比较“新潮”的游戏了。
做“九月十四”
古溪是个完全信仰本土宗教的村庄。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天主教、基督教教徒都试图在村里传教,皆由于村民宗族意识强烈,未能实现。村中旧时有五大姓,即陈姓、谢姓、林姓、倪姓、池姓,按居住界限划分,又分为上厝、下厝、内厝。民国时期,这三个居民点皆设有保长,各自为政。古溪村民所尊奉的神灵十分复杂,有忠烈王、普济明王、临水夫人、师公、田元帅、齐天大圣等数十位,以忠烈王黄岳、普济明王林亘(即林公忠平王)、临水夫人陈靖姑为主神。村里供奉忠烈王黄岳的庙宇一忠烈行祠赫赫有名,在历代地方志中都有记载,它所建成的时期仅次于城关东门外的土主宫。供奉普济明王的庙宇在村东塘前头,隔着东湖,与塔山遥遥相望。这两位神灵,被村民尊称为“社头公”。临水夫人俗称“大侬奶”、“奶娘”,上、下、内三厝各有一尊(其中下厝有两尊,分别称为“旧奶娘”、“新奶娘”。除了下厝有单独的奶娘宫外,其他二尊皆供奉于祠堂)。除了春节,被古溪村民视为最大的节日应该就属每年农历“九月十四”的黄岳诞辰庆典了。忠烈王宫的公产不多,只有少量的土地和海埕出租。每年的收入勉强维持诞辰庆典之费用,如遇修缮庙宇的年头,就只能由村里殷实人家集资来完成。每一年负责庆典各项活动的人员皆为二十名,称作“社头头”,由村里成丁(蕉城民间习惯以十六岁成丁)男性轮流充当。据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回忆,每年到了农历九月十三这天早上,新当选的“社头头”就会开始准备供品,制作大量“寿桃”(即形如寿桃的糖包)。到了晚上,“社头头”就踏着月色,早早集中村西郊的忠烈王庙,备办“祭桌”(即祭祀物品),燃烛上香,届时还有“吹班”(闽剧清唱)助兴,庙内灯火通明,彻夜如昼。这一活动俗称“庆赞”。到了交子时时分,就有一名“社头头”手持铜锣,进入村中,边走边大声反复高喊:“新头新柱”(意思是说新的“社头头”已经产生),听到喊声的村民就会陆续醒来,到庙里上香,给忠烈王拜寿。旧时缺吃少穿,一年难得吃上几回好东西,这一晚能吃到香喷喷的白面糖包,所以也成为小孩子们最为高兴的节日。上香的成年人身后,总会跟随着一两个小孩,他们也可以兴高采烈地领回一合“寿桃”。
九月十四至九月十六这三天时间,按例都要演出闽剧。届时村里家家户户都要邀请亲友来观看演出,一日三餐还要备办茶饭,用度甚高,对多数人家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负担。但村民乐此不疲,相沿成俗。就是在民国时期,有一段时间为了搞好治安,禁止民间娱乐。为了保证整个活动不出事端,村民陈骰子宁愿自己入狱作担保,使庆典照常进行。
上面我们已经说过,由于忠烈王庙的公产很少,捉襟见肘,所以备办忠烈王“祭桌”就得由当年的“社头头”自己掏腰包。为了凑齐这一款项,就逐渐产生了“贴喜”的习俗。所谓“贴喜”,就是由“社头头”作若干个“糯米大寿桃”(将糯米蒸熟后,拌上红糖,做成寿桃模样,大者数十斤,小者十余斤),送到当年村里有喜事的人家。喜事无论大小,小至砌灶、砌猪圈,大至建房、娶媳、生子,都必须“贴喜”。“寿桃”大小也视喜事隆重程度而定,以娶媳(俗称“新妇喜)、第一胎生男(俗称“长男喜”)最为注重。“社头头”们在忠烈王圣诞的前几日,会把写有喜事内容的红字条“贴”到该村民住宅的大门之上。该村民就得视自家喜事大小交纳款项。由于一年中,村里的喜事有多有寡,碰上不好的年份,“社头头”们就只好自己凑足金额了。
顺便带一笔,每年农历正月十五的“奶娘诞”,村里的成丁男女不仅要举行“过关”仪式,还有所谓“送烛母”的习俗。“送烛母”的对象是村里刚刚成婚的人家,或者有结婚后长期不生育的人家。在每年的“奶娘”巡游完毕“圆宫”以后,这些人家男子的年轻好友都会邀上四五位,带着一双奶娘座前请来的红烛(点燃着的),一铁铲熊熊燃烧的木炭,送到家中。年轻的夫妻们就会高高兴兴地予以接受,将红烛供奉在祖先的龛位前,而炭火则倒入炉灶。尔后,准备酒菜招待这些热心的朋友,尽兴而散。
而今,随着时代的飞跃发展,各种旧的习俗已遭到舍弃。忠烈王庆典中除了“庆赞”、“演戏”等还保留以外,“分寿桃”、“贴喜”、“送烛母”等似乎意味着贫穷落后而不再流传。也许随着人们传统意识的淡薄,其他仪式也将一去不复返,只留下记忆供人们回味!
婚前“请仪校”
蕉城民间对男婚女嫁十分讲究,比外省外县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古至今,蕉城还流传着许多特殊的婚嫁习俗,如沿海乡镇的“打醮”、“新郎伴睏”,飞鸾二都的“扭星”(新媳妇过门时,亲友要掐其手臂肉)以及古溪村的“请仪校”。
请仪校在古溪至少已经流传了一两百年,它的来由,包括它的正式写法已无从查考。“请仪校”的时间都安排在结婚前一天,即新郎(女儿出嫁无此仪式)“打醮”(又称“请喜神”)的当天晚上,这项仪式多由村里年长的男性老人完成。当天晚饭过后,办喜事的家庭就要煮两碗线面,每碗面上放上两粒煮熟剥壳的鸡蛋(俗称“一碗面两粒蛋”),还要准备红烛一合,香六支,红酒一斤,锡酒壶一合,酒盅十只,锡帛一捆。装入“碗栳”,送到前去“请仪校”的老人家中。当晚夜深人静的时候,老人带上这些物品,到祠堂仪门(俗称“雨亭”上厝的居民多在陈氏上祠堂,下厝的居民多在尾谢祠堂)前,在廊前石板上就地祭祀。祭祀时间大约为半柱香功夫。老人在祭祀过程中,还要默默祷告,内容为新郎新娘双方姓名、年龄、住址,最后祈求神灵保佑夫妻白头偕老,生活美满。祭祀完毕,烧过锡帛,老人将蛋面带回家中,分给家人享用。装蛋面的“碗栳”必须在三日以后,等新郎(新娘)办完喜事后送还。也就是说,“请仪校”虽然是办喜事的人家分内之事,但至始至终,他们都没有直接参与。这样一个古怪风俗,它的祭祀对象是谁呢?有的说是祭祀临水夫人,但烧的却是鬼魂使用的锡帛?有的说是祭祀祖先,却为什么不在祠堂内祭祀呢?孰是孰非,就是操持“请仪校”的老人自己也难以说清。
相关人物
陈仕玲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