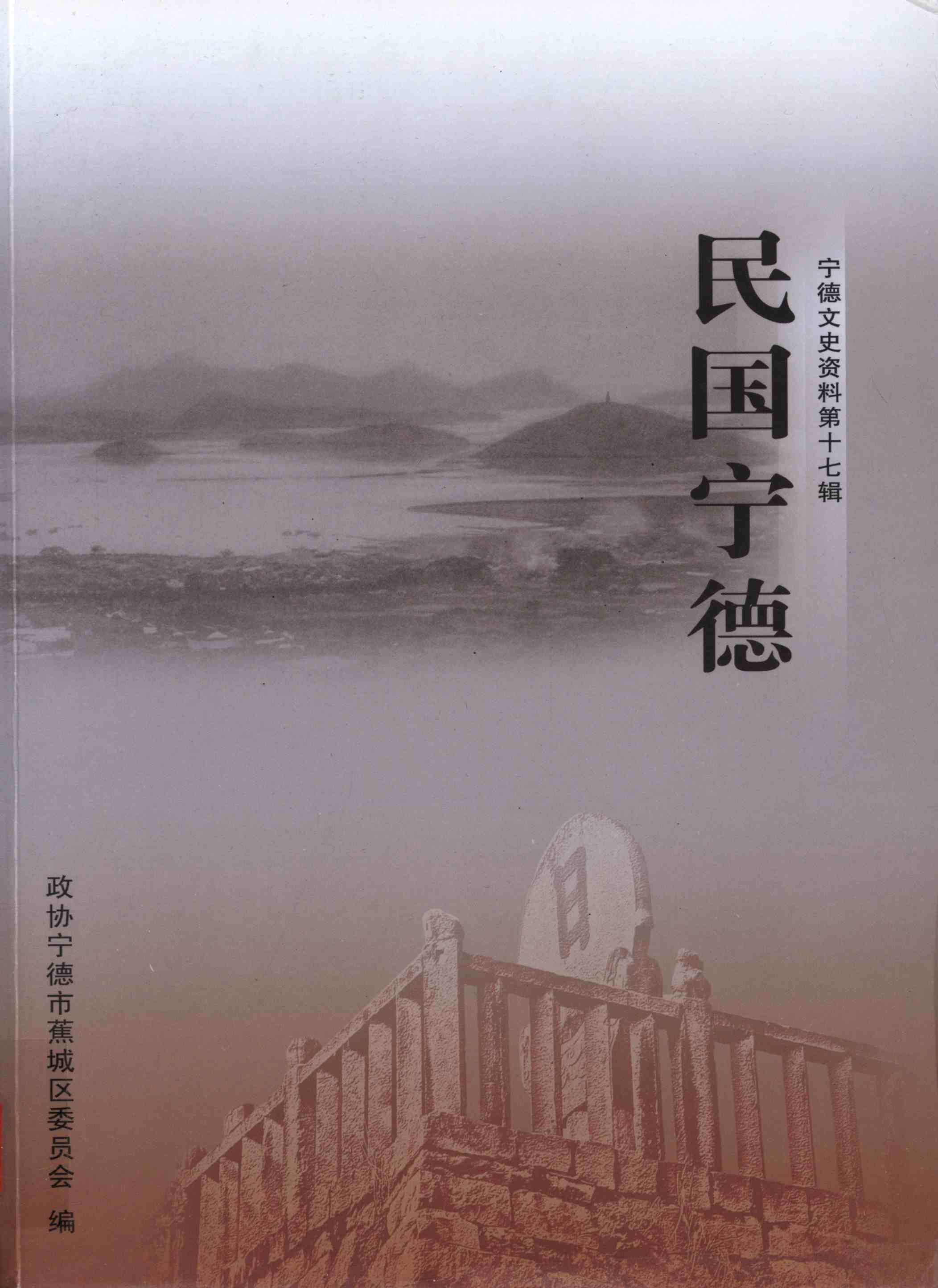内容
本文在翻阅若干民国时期档案以及采访的基础上写成。试图描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宁德县“公产”的概貌,提示隐藏于“公产”背后复杂的关系,再现民国时期(本文“民国时期”,专指1911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一些奇特而有趣的现象。
民国时期公产的类型——渊源与衍变
民国时期宁德县的“公产”,一部分是自清代以来“官产”的延续,一部分是国家(政府)出于公共的需要,使用和管理了原本归属于某些社会团体所有及管理的财产。这其中,包括了“前清”时期县政府、军队、官办机构遗留的一些建筑物与地产、渡口码头,以及一些宗族或宗教团体、群体(社区)所有或者管理的祠、宫、庙、观、会馆,最后,还包括部分庙产、学田(公田)。
建筑财产
宁德县城在1949年,有房屋建筑32万平方米。自晚清以来,除几幢教堂及洋楼外,无论公共建筑还是民房,绝大部分为木结构土夯墙或空斗砖围墙传统建筑。
这一类的公产主要有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官宅”。即清朝政府机构和官办机构遗留的建筑与地产。如县衙、游击署、官仓以及文庙、官办书院。在民国时期,这些旧建筑被国家(政府)使用管理,分别成为县政府、执法机关、公众体育场和国民党党部、官立学校。如县衙(旧县衙,位置大体在今区政府院内,内中建筑解放后陆续拆除。)。据资料表明,明代所建县衙,有正堂3间,堂后为内宅,堂左为幕厅,堂右为库藏。堂下又有14间卷房,前有仪门5间,另有吏舍20多间,规模相当大。除县衙之外,宁德县城中还有县丞署、教谕署、典吏署,以及军械库、监狱等多处。
第二部分,各种宫、庙、寺、观、会馆。宁德一地,宫庙寺观极多,这些宗教建筑原有的功能及管理使用情况十分复杂。在清代时,有的宫庙祠由官方祭祀,属于全县甚至数县范围民众信仰供奉;有的是一个、数个社区范围(境)内或某宗族一姓、数姓民众祭祀供奉;有的归于宗教团体或个别宗教人员供奉管理。会馆则由创建者——地域性团体或行业公会所使用。
集中于城区之内的各类宫观寺庙,清朝末期开始实施“新政”之后,大量被用于学校办学和政府机构的办公,特别是原先就归属于政府管理,官员祭祀的宫、庙、祠,建筑保存较好的,均被官办机构使用。各座原属于社区共有的宫庙及由外地客商兴建和管理的会馆,民国时期大部分时间里,也较多地被当地政府、社会团体所管理使用,或用于驻军。
第三部分,较为特别,就是分布很广的各姓祠堂。民国时期,各姓祠堂也被广泛地用于兴办学校和政府机构办公以及社会团体活动。
在乡村也多有这般情况。特别是宁德县乡村中的祠堂、祖厅,是民国之前乡村中分布最多、最为主要的公共建筑,因此民国时期的公共机构及学校也多设在其中。如漳湾的官办小学,设于阮氏祠堂中,古溪村陈氏上祠堂因较为宽敞,乡公所与小学皆设于其中。
尽管这些公用建筑物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使用者各有不同,但以“公产”名义存在,却是没有疑义的。“公产”,又可称为“行政公产”,其法律释义十分复杂。总的说,指公众直接使用的财产或公务使用的财产。目前在我国,行政公产是指行政主体(“行政主体是指享有国家行政权力,能以自己的名义从事行政管理活动并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的组织”。转引自“百度百科”。)为了提供公用而所有或管领的财产。民国时期,除“行政公产”之外,社区或团体所使用与管理的财产,也使用了“公产”的概念。民国时期,至少在上个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宁德县政府设立有“整理公款公产委员会”,其主任由县长兼任(见蕉城区档案馆档案《整理及调查官、公产卷》,编号2-3-736。)。从相关档案中也可看出,当时政府与民间所认定的“公产”范围十分宽泛,不仅包括“官产”——国家(政府)直接管理使用的财产,一部分原本属于社会团体(社区)使用管理的建筑,也使用了“公产”这一名词。例如,位于“西山路”的“龙首境”宫(位置在今市新华书店附近),在四十年代的地籍登记中,就直接标明“龙首境公产”(见蕉城区档案馆档案:12-3-1。)。在社会实践中,以用途的公共性和管理的有效性来看,上述这些建筑财产,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公产”。
田产、地产
关于“公产”,还有一种类型,就是自古以来存在的各类公田(祠堂田、公轮田、墓田)、学田和部分寺庙管理的田产,这部分田产,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土地改革之前,约占全县耕地的30%(见姚智卿《恢复发展改造——记建国初期宁德经济状况》一文,载于《宁德文史资料.十一辑》第70页。)。其中有一部分公田,主要是学田与若干庙产,为政府掌握,其收益用于教育经费开支。
自1901年清朝廷颁布办学的新政以来,不仅书院直接转变成为学校,一些地方的祠堂和寺庙以及财产,都以法令的方式,成为办学的主要资源,并在实践中得到有力的推广(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1901年9月14日),作为新政的举措之一,清政府下诏办学,谕令“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6:176)。苦于办学经费不足,清政府实施了“庙产兴学”的政策。1902年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和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都有将地方祠庙及其财产提拨为学堂之用的规定,如《钦定小学堂章程》第一章第八节规定,地方办理小学堂时,“均得借用地方公所祠庙以省经费”(见舒新城编,1981:400);又,所谓“庙产兴学”,狭义地说,就是指征用各寺庙财产来兴办教育,包括庙产补助学费,将庙址划拨为学校。如日本学者村田雄二郎所言:“清末民国时期实行的一系列没收寺观神庙财产(寺院领地、田产、庙宇等),充当振兴地方初中等教育费用的一系列政策、运动”(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2006:561)。这一理解主要根据当时人的言论和光绪皇帝的上谕。就实践层面来说,“庙产兴学”运动所涉及的地方公产除了寺庙财产外,还包括会馆与祠堂的产业,民间各类会产,以及斗捐、官秤、红庄等地方公费。——转引自《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一期,梁勇《清末庙产兴学与乡村权势的转移——以巴县为中心》之注解。)。在宁德县民国档案中,有一卷档案记载了1935到1936年间,县政府对“龟漈寺”的田产进行召租的过程(蕉城区档案馆档案(关于龟漈寺等田产召标的文书)2-3-708。),其名义就是“学租”。还有一份卷宗记载了1940年赤溪小学与当地某寺僧人因为学校基金会的“学田”问题产生纠纷,呈文请县政府调查的事情。还有一份档案,记载了1936年县政府对文庙的田产和滩涂租金收入使用的指示。从这些案例中可见,当时的公产,不仅包括一些实物(建筑),也包括了一部分田产的财产权,国家(政府)对这部分财产,具有收益、处分等权利(作者注:这种权利,法律上称为物权中的“用益物权”,指得是一定条件下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这种财产权利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上个世纪的前五十年,社会经历激烈的变革,由清末、民国初期、抗战期间,到了民国后期(本文专指抗战胜利的1945年到1949年间,下同),由于各种原因,这些田产的“公产”性质,有的也产生了不小的变化。一部分原属于寺庙的田产,成为政府或学校管理与收益的“公产”,而有些政府的财产权益,也流失于民间,无法得到体现。
“公产”的衍变
从历史渊源来说,民国时期的公产,相当部分是清代“官产”的遗物。而清代的官产,有的也是前朝(明朝)的遗物。在王朝更迭,社会动荡时期,产权时有变易,甚至在政局平稳时期,也有将官产出售而变为私产,或买入私产成为官产的事例。
1、官山成为私产。清代乾隆《宁德县志.卷一.舆地志》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旧志按云:本县山场无论城郭乡村,除附近庐舍坟墓者始为民业,高山深谷俱官山也。嘉靖初年,外郡人来县境栽菁,俱告于官,官则随山按户置簿收租。自辛酉倭变之后,官簿无存,土豪年估其租……今考本县册籍民山,悉属官山,……而此日承平已久,彼此授受买山者多矣。”这一段文字,说的是原来属于官产的山场,由于战乱、经济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属变动,由官产变为私产的原因与过程。
2、私产成为官产。这本旧志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游击署,在北门内,原系崔家房屋。自国朝顺治五年设立专营,买置为署。……十四年(乾隆),游击潘公从龙改建三堂,并修葺头门、大堂、二堂、三堂……规制一新。”(引自清《宁德县志.卷二.建置志》。)这里说的是私宅成为公署的过程。这座“游击署”,在今培英路旁,旧时民间称为“大纛衙门(以方言音,或为‘大道衙门’)”,在民国时期成为体育场,解放后,仍为公产,即是现在公安局的拘留所位置。
民国之前,产业由官而私,或私人宅地因为官府购买而成为官产的例子还有。如今大华路薛氏大宅,民国时期范围颇大,内有花园等。从清代县志上看,明代以前是“射圃”——县学学生或驻兵练习武艺的场所,后建布政分司署。址废,成为民宅。明嘉靖年,县令林时芳又“贸易民宅”,建按察分司。清乾隆年间,此处建“鹤峰书院”,不久,书院迁西门外今十中址,改名“莲峰书院”。石堂巡检司署(县政府的分署机构)几经搬迁,“寓县城”,驻于此处。到了清代中期后,此地售于薛氏。至今,此处还有“巡司弄”的旧地名。
辛亥革命之后,“前清”绝大部分官产的权属性质,并未因为社会动荡而产生变化,这与民国初年就确定清代有关物权的部分法律条文有效(“1914年,大理院在上字第三0四号判例中认为:民国民法典尚未颁布,前清之《现行律》除制裁部分及与国体有抵触外,当然继续有效。至前清《现行律》虽名为《现行刑律》,而除刑事部分外,关于民商事之规定,仍属不少,自不能以名称为刑律之故,即误会其为已废。同年,大理院在上字第九三八号判例再次确认:前清现行律关于民事各条,除与国体及嗣后颁行成文法相抵触之部分外,仍应认为继续有效。”——转引自2008年第六期《北方法学》,姜茂坤《论民国初期“物权契约理论”的发展》。),并且民国政府很早就开始登记和清查官产(“民国4年(1915),福建省财政厅向财政部上报本省官产价值为46万余元,当年8月,设立福建省清理官产处,重新清查各县区官产,造册上报。”——引自1994年版《福建省志.财税志》第八章第六节。)有关系。清末民初交替时期,宁德县城未经战火与动乱,民国时期的官产,“平稳”地由民国政府接收,在政府、社会团体与民众之间,没有太多的争议。
但是“公产”并不全部都是产权明确的“官产”。由于产权模糊,到了三四十年代,出现了涉及寺观田产、神庙田产、渡口等一些关于“公产”的纠纷。同时,还有一些公共建筑处于无人管理或管理不善的状态,或为流民所居,或由社会团体暂管,或由个人承租管理。
“公产”的分布——时代特征与过渡状况
民国时期哪些财产属于“公产”,只能以当时的概念来认定。要全面的弄清民国时期“公产”的情况十分困难,但现有档案大体透露出这方面的概况。
今藏于区档案馆中的编号为12-3-1的档案,是一份十分罕见的地籍图。这份档案,是用1:500的比例制作的城关、飞鸾、霍童、八都等城区镇区1943年的平面图,图中示明土地的类型与归属,人们从中可以得知当年城区及相关乡镇公产与私产的一些状况。
图中土地类型大部分为“宅”,即建筑物,也有“杂(空地)”、“荡(池塘)”、“田”、“园”等等。还标明了街、巷的名称与走向。“宅”的类型中,则写明其名称,标注出其权属。
据图,宁德城关中,政府机关、学校、银行、办公处、供销处、地证处、贸易公司、体育场、训练处,以及只标明“公产”的建筑有25处,官办机构“社会服务处”一处。宗教场所如基督教圣公会、天主公教、自立会等4处,祠、宫、庙、观等15处。各姓氏的宗祠则有12处。图籍不但标明了这些建筑的名称,还准确在标注出其位置与面积,相邻的建筑。
试分类例举:
学校
“三民国民学校”,在三民路,即今中南街;“北山国民学校”,在遵化路,即今北门街;“蕉城中心学校”,在三民路(今蕉城一小附近的学前路是这段路的一部分)。还有两处“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处”,均在三民路,也在今蕉城一小内。以上学校校址,原来建筑分别为蔡姓宗祠、城隍庙、文庙(作者注:此时“宁德初级中学”业已成立,校址在原莲峰书院,今宁德十中处,此图未载。毓秀小学此时已创办多年,址在今宁德医院内,此图亦未载。)。
政府机关
县政府,在“县府路”左(此图“县府路”,即今街中头西门路至大华路口的路段),今蕉城区政府大院在此范围之内。还有一些只标明“县政府”的建筑,分别位于“中山路”(今八一五大街处)、“文昌弄”(今鹤峰弄)、南门筱场边等地。在今东门兜旁,有五处房产直接标注“县政府”。这些只标明“县政府”的建筑,此时可能是一些县政府的办事机关或一些公共的场所(1994年版《宁德市志》载:1937年6月,县政府曾出垫资2000元建东门菜市场。此处所提“今东门兜旁五处标为县政府”的地产,或为此。此菜市场址,约于七十年代中期改建为百货商店,俗称“下百货”。)。
公共建筑
“宁德青年体育场”,在培英路;“公共体育场”,较场边。这其中,可以识别的,前者即是今公安局看守所,后者是数年前的体育场,今已成宁川路和部分民宅。还有一处“体育场办公处”,在较场边,其位置似乎即是今蕉城第三小学校址。
其他公共单位
“福建省银行”,在大华路;“供销处”,在遵化路,今北大路;贸易公司,在北大路。这些公共机关,有的今已成为民宅,有的现在的用途不祥,有的已被拆迁,成为所谓的“新城”商业建筑了。
以上例举诸机关办公所在建筑,是由国家掌控的公产。这些建筑或为“前清”政府“遗产”,或由民国政府购置,或为政府机关征用。在1943年时,这些建筑以国家机构的名义登记在册,已成为名符其实的“官产”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三十年代登记为“公产”的若干建筑,到此时,可能已成为私产。如西门的戚公祠,在图籍中已找不到,很可能在这一段时间内,由公变私。而这种转化的最大可能性就是公产的出售。但真实原因不详。
除以上所列之“官产”以外,还列出了不少基本属于社会团体所有和管理的“公产”建筑,主要是由民众祭祀与管理的神庙,以及各姓氏所有及管理的宗祠。
宫、庙、祠
“鹤成境”,在南大路较场边,即今蕉城三小附近;“文昌帝庙”,在中正路,今八一五中路一带;“鹏成(程)境”,在环城路,即南环路口,今兴业银行大厦处;“福山境”,在复兴路,即今福山街,今妈祖庙右侧,等等(此外,旧时蕉城周围还有陈太尉宫(今区防疫站内)以及灵溪寺、天王寺、南漈寺、地藏庵等数座宫、观、寺、庵、堂,或因当时处于城外,亦不见载于此图中。)。
此外,这份图中标明的宗祠及“众厝”十几处,均能明确地与私宅区分开来。如溪井乾处的王氏祠堂、北大路的韩氏祠堂、前林路的陈氏祠堂(今莱茵城,原宁德人民会场址)、环城路的陈氏祠堂(小东门街原县文化馆)、龚氏众厅(约在今八一五中路农业银行前)、“三民路”(竹兜街)的“马众祠堂”(其址或为原“红星街道”办事机构,附近另有一座马厝众厅。)、文庙西侧的林、郑祠堂,等等。
此外,这份地藉图还制作了飞鸾、八都、霍童的镇区的平面图,从中也能看出当时“公产”与“私产”之间的一些情况。
除了这分地籍图以外,馆藏档案保存不少有关政府招租、追租的文本,处理公产纠纷的文本,也能大体上体现“公产”的分布情况。从这些文本中可见,除宁德城关多处建筑财产为“公产”之外,政府还占有相当数量的田产。
民国时期,宁德县政府曾经对公田进行登记造册。1938年,宁德县政府通过统计,明确了全县儒学田计有933亩,公学田39亩。1942年,通过统计,宁德县中学基金田965亩多,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量。在1940年以前,政府还对寺庙的田产进行登记,据1948年的数字,各类“神产”计有田1826.49亩,园77.14亩(1995年版《宁德市志》,第535页。),这些“神产”中,有一部分就是政府掌控的。
关于田产,很可能还涉及一部分由政府投资围垦的部分。宁德县面海,历史上多有官府投资及牵头组织民众围垦海滩的事例。馆藏编号为2-3-736的档案中,有一份写于1942年的有趣文本。这份由南埕“济农塘”董事陈世泰等人写给县“整理公款公产委员会”的报告,陈述了“济农塘”的由来,以及他们与政府对塘中“公产”的不同理解。兹录于下:
“窃南埕海滨,绝少园山田地,居民专以晒盐为生,相沿日久。民国三年,政府以南埕盐质不佳,下令除坎,盐民三百余户骤告失业,彷徨无措。赖已故邑绅林理斋先生领导请愿,设法救济,呼吁迫切,而其长公子,前四川盐运使林振翰君,洞悉情形,居间斡旋,始蒙部准发帑,建筑济农塘,以资盐民生计。并由福建前盐务稽核所正经理主持其事,亲临履勘,延聘工程师测量。同时专指董(“董”,指“董事”,即陈世泰等三位具报告人的自称。)等为建塘董事。已故崔伯乾先生为经理,林理斋先生为名誉经理,八年始成。由县府派员照盐户坎数分配田亩,多寡不等。各盐户以塘堤规模初具,根基诸未坚固,若不预谋善后,难期久远。乃以应分田亩,酌量抽成,储为盐民公共田地,将来披修取资于此。惟是八年开始垦荒,直到十六年克成业,略有收获。”
这段描述,承认了政府投资围垦、分配及留有“公田”的事实。然而,政府的这一笔投资,直到1942年,仍然未能收回,并且这塘中的“公田”也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份报告中描述了自民国十六年以来济农塘所遇到种种困难,而后向县政府陈述:“伏念政府筑堤救济南埕盐户,其全部塘内田地即均属盐户,永远享有业权,而此项养塘公田又系盐户当分田之时,自愿公抽做为基本,似于公款公产显有分别。”最后,董事们还警告政府,“当此风雨飘摇,秋潮洪猛,……诚恐因循贻误,关系扉轻……”
从民国三年到民国三十一年,时局多有变化,后任的县长,想要主张二三十年前的财产权,恐怕是无法实现了,档案中惜未见此事后文。但是,民国时期宁德县政府向滩涂要田地的进取心仍然相当强烈。1947年,宁德县政府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围垦——西陂塘工程,在这个巨大的工程中,政府将可能实现多少“公产”,未尽其详。最终这个工程未能完成。
还有一类特殊的公产,就是渡口。馆藏档案中有一份编号为2-3-736的《整理及调查官公产卷》,内中有一份“蓝田渡船管理人陈细耳”向公款公产清查处主任陈情的文本。文本中称:
“窃民于去年十一月见钧处布告,招人承租公产,遵经依照法定手续,向钧处租出蓝田溪官渡,筹造新船,以渡行人。新造船一只,垫费二千五百元,口于废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新旧交替,归由民撑渡行人,业经有日。当由钧处发给公产租约为凭,年纳租谷六市担,租约有效期间为五年,由三十一年十一月起口口口六年十二月止。讵料蓝田土豪吴秉文等侵渔公产,食髓知味,意图永远霸占及饰词朦耸,钧处(作者注:从后文来看,可能是“钧处”的个别人)以溪河不算公产,有意阻挠清查公款公产工作,影响抗建(战)前途,至为重大。
……查蓝田溪官渡适合于《土地法》第八条第(一)、(二)、(六)等款及《官产条例》第二条第二款《公款公产整理纲要》第二条第九款之规定,确属公产无疑。若谓为私产,试问有无依法取得所有权?设非公产,当日钧处断无贴布告招人承租及给发租约准民租为造船撑渡行人之用。再查本省《处分官产暂行条例》第十七条之规定:“官产一经招租定案后,无论何人不得再行呈请变更”。是见政府立法之注重威信。今吴秉文等贪利无口,敢出于政府告争夺利,其胆大妄为可以概见。万一再被霸占,而蓝田溪鱼潭年可获鱼十余担,亦归乌有,公私两俱损失。近有贪利违背职务之一二不肖公务人员,尚且为吴秉文等奔走说项疏通,实属违法已极,合亟备由呈请鉴核:依法严惩,驳斥无理请求,以绝私饱,而维威信,实为公便。”
此份档案涉及“官渡”这一久已存在的事物。在清代乾隆时,曾设置六都、金垂、飞鸾等多处官渡,官府配备人员、确定薪酬。百年之后,大约因为陆路交通变化,或私人船只增多,其他“官渡”已无存在之必要,但兰田渡却仍然保留着“官渡”的传统管理运营方式,只是时代变迁,私权逐渐地取代公权了。该卷档案中,有关蓝田渡的文本,仅此一份,尽管为“一面之词”,但亦可见当时一般民众对“公产”的认识有相当的深度。
民国时期政府所认定的公产数量远不止于此。特别是属于“官产”的建筑财产,在此后的社会鼎革中,大部分保持了其公共性,甚至一直存留至今。
当然,以上所列财产或财产权,以今天的观点看,有的或许不能算做“公产”。但是,如果从民国时期这些财产的“公共性”,以及政府与公共团体对其有效管理的角度来观察,其“公产”的性质,是显而易见的。
宁德县政府对不同类型的公产,有着不同的管理方式,主要表现为:直接使用(办公、办学)、登记造册、收取租金。使用管理的有效性,是认定公产的主要指标,应当说,这个时期一些“公产”,所有权究竟属于何者,并无契约,但是国家(政府)机构、执政党(国民党、三青团)和一些公共团体有效的管理使用,却明确地体现了“行政主体”对财产占有和支配的权利。
政府、执政党团、官办机构直接使用的公产
清朝末期开始实行“新政”,政府机构开始增加,民国建立之后,司法、民政、税务等机关增加了不少,宁德城关内多处原来的官产,遂由这些机构进入办公。
原来的县衙、官仓(今县政府内),成为民国时期县政府和看守所(见1995年版,《宁德市公安志》,第20页。)。
建于南宋嘉泰四年(1204)的“土主宫”(址在原蕉城镇机关,后为“二月花商场”,今商业城“锦福城”旁),称为“忠烈王庙”,神主为唐代的太学生黄岳。清代末年,清朝筹建新型的警察机构,宁德县警察署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设于土主宫中。直到四十年代初,警察局移至前林坪蔡氏家庙,这里又成为具有官办色彩的“社会服务处”。
宁德县文庙,当时是全县乃至闽东最为恢宏的一处建筑群,在1904年清朝废除科举制度后,就成为民国时期多种官办机构办公的地点。从1927年开始,文庙所属的考院(今人民影院,当时俗称“考坪”)成为执政党国民党的党部。文庙的大成殿仍然保持着祭孔的功能,也做为学校的礼堂。小学最初办在明伦堂两侧的厢房,抗战初期,文庙中建新校舍,为宁德县官办的国民模范小学。1944年,县临时参议会会址曾经设于文庙之中。
城隍庙,建于南宋(绍兴元年,1131),历八百余年,经多次修葺,到民国初期,仍然保持着较为完整的建筑,很可能仍然保持着民间迎神祭祀的功能。民国十二年(1923),县公署(后改称县政府)奉命禁止迎神赛会,作为民间祭祀最主要场所的城隍庙,其功能很可能就此式微乃至终结。到了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时,城隍庙多被用于公共目的。庙曾被驻军征用,庙中城隍神像被迁于不远处的武圣庙(址在北门街与培英路交叉处附近,姑称为“北门武圣庙”)内。1935年,县卫生院曾设于庙中,1938年,三都中学暂时迁此(见1995年版《宁德市志》第20、24页。),到了四十年代初,这里又成为“新兵接待所”和“北门国民学校”。后来,简易师范、三青团也曾经将这里做为团址,旧时还有一家“报社”亦以此为社址,兼有印刷所。
位于城隍庙北边,与之一路(路原为城墙,1939年拆后城为环城路)之隔的朝天境神庙,规模颇大。自三十年代后,此处被用于县医院处,内设手术室,办公室及病房。一直沿用到解放初期。
南门校场边的武圣庙,原来为“前清绿营兵”驻扎,是一处名副其实的“官产”,但在民国初,“祭祀废,渐倾圯”,已是十分残破,被流民所居。民国二十四年(1935),由“乐善社”募修,管理(蕉城区档案馆档案,编号:2-3-663。)。抗战期间,委派而来的福州籍体育场长,扩修400米跑道,将该庙拆迁,遂成为体育场一部分。南门校场,原来是地方驻军的习武之处,民国时期,曾辟为体育场。校场周围有若干建筑,在1943年的民国档案中,还明确的标明为“县政府”的财产。后来权属流变,今已成为私产。
从当年的档案来看,有的祠堂,在民国时期,也成了一些政府机构的办事之处。较为典型的是前林坪蔡氏家庙(今已毁,存一仪门),四十年代时,县警察局在此办公。据今年九十岁的陈继佑先生介绍,解放前蕉城镇公所址多有变动,也一度设在这里。在前林坪的另一家蔡氏祠堂,也曾设为蕉城镇公所和县田赋管理处。
旧时县政府大门东侧县衙路(即今西门路)旁的彭氏祠堂,民国时期这座祠堂被政府机构使用或与彭氏家族共用。据彭氏族人回忆,解放前,这座祠堂曾经被用于办“文化馆(据今年九十岁的林承荣回忆,此处曾设过“民众教育馆”,“文化馆”一说,疑为指此。)”。后继为警察所,到了“张同英”任县长时,县政府围垦西陂塘,这里又成为围垦工程的办事机构和仓库(张桐膺,1945.7——1947.3在宁德县任县长。见《政协文史资料》第五辑151页。)。
龚氏祠堂(位置约在今八一五中路工商银行前的路段中),此祠堂原为图书馆,后于1933年设为“民众教育馆”后来“民众教育馆”转到这里(见1995年版《宁德市志》,798页。)。在60年代初大街开辟前,曾充任文化馆。
陈氏祠堂(位置在今东门兜附近“莱茵城”处,原成德境巷口),民国时期一度为“三青团”办公处,七十年代后为文化馆和电业局的办事地点。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直接使用”,并不意味着旧有功能完全丧失。有的神庙及祠堂,在此时,很可能仍然保存着一年一度祭祀的功能。只是平时被“公家”所用。如上述之彭氏祠堂,据说直到五十年代之后,祠中的牌位等才被搬出。
以上是政府或公共机构直接使用的“公产”,实际上,被政府机构直接使用的公产不止这些,乡镇各地情况也大抵如此。此处不一一例举。
兴办各类学校所使用管理的公产
清末开始兴办新式学校,光绪三十一年(1905),官办的莲峰书院改为“官立”莲峰高等小学堂。城区内还有4所“公立”小学堂,由县政府每年拨给50元补助。民国以后,宁德县学校数量增加了很多。民国四年(1915),宁德城内有国民学校(初等小学)5所,各乡有31所。进入三四十年代之后,宁德县还办起了初级中学(1940年,设于莲峰书院内),有中心国民学校、国民学校60多所(引自1995年版《宁德市志》728页。)。清末民初学校的兴起,使用了大量原本“公用”的建筑。这其中包括了庙、寺及大量的祠堂。
办学使用寺观和祠堂,在宁德有其传统。宁德县自古以来,不但有县学,还有社学、义学和许多书院及私塾。这些教育机构的校址,有的创建(如城关的莲峰书院、霍童的双峰书室),有的购买寺庙(如灵溪寺和广福寺在明代都曾经办学),有的通过官司将寺院变成书院(如清咸丰年间的洋中鞠多寺,官判为书院),但也有读书人自建读书处,后来成为寺观(如龙湫寺)。至于私塾数量更多,多半办于私宅内和祠堂中。清末、民初,就城区而言,有前林坪富豪蔡氏办学于自家中、前清文人林其荣办学于陈氏祠堂、前清罗源县教谕林理斋办学于林氏祠堂、前清文人牛兰金办学于崔氏祠堂(见黄建琛《祠堂、民宅塾馆》一文,载于黄建琛、黄澍、姜翔骅等编《蕉城古风貌建筑及其他》,2007年版。),等等。后来新式学校兴起,使用旧有的“公用”建筑,继承了这一传统。
民国初,政府有资助私塾部分经费的做法,一些原本只读旧书的塾斋开始引入新式教材,分科教学,但校址仍然办在家宅或祠堂中,新式小学兴起,仍用旧址。如漳湾创办的小学,就设戚公祠侧的阮氏祠堂中。西乡(“西乡”,习惯上指蕉城区西部山区乡镇石后、洋中、虎浿一带。)一带,这种现象十分普遍。据今年九十六岁的刘祖宽先生言:大约民国十年(1922),他由家乡灵下村的私塾转洋中第一所新式小学——青田小学读书,就是在东山村陈氏祠堂中读书。后来,青田小学移至洋中村,办学地点的“中厝厅”和“巷口厅”,此后直到解放后,学校一直使用祠堂(“众厅”)作为校址。石堂自古学风兴盛,民国时期“上西乡小学”设于梅鹤村的林氏祠堂之中,办学规模颇大,甚至洋中的学生也来此就学。据刘先生介绍,其童年读书时,曾见县里督学下乡视察办学情况。假如督学认可原来的私塾的确转成新式小学,则给予资助。当然这些资助微薄,无法创建新的校舍。
宁德城关也有祠堂成为学校的现象。据林承荣先生介绍,当时吴氏祠堂相邻的蔡氏祠堂(址在“三民路”(民国时期“三民路”,由蔡氏家庙附近的前林路至人民影院,即今中南路,解放后还称为“红星街”,俗称“竹兜街”。),今八一五中路南侧),四十年代时为某学校办学于此,其校长姓关,今年尚健在,已年逾九十。从前述之地籍图中,也可确知,这所学校名称为“三民国民学校”。
学校使用宫庙与寺观的现象相当常见。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寺庙管理条例》,进一步确定了寺庙办理“公益事业一种或数种”的法律根据(转引自付海晏《革命、法律与庙产》,载《历史研究》2009年第三期。)。由于城关内保存较好且较为宽敞的宫、庙、祠等建筑数量多,因此,进入民国之后,学校办在这些宗教建筑之内的情况更为普遍。
民国二十五年(1936),当时的广泽尊王庙(即“泉郡会馆”,俗称“圣公庙”,1953年毁于火,今饲料厂位置(见黄澍《泉郡会馆轶闻》一文,载于黄建琛、黄澍、姜翔骅等编《蕉城古风貌建筑及其他》,2007年版。))为“镇第二短期小学”(引自蕉城区档案馆档案,编号:2-3-663。);更为宽敞的城隍庙,其东北角(后大殿)曾也当做“北门国民学校”的驻地,与“新兵接待处”在庙的前后殿共处相安。前述之“北门”武圣庙,曾办过某“简易学校”。宁德北门外天主教堂,也腾出礼拜堂外一处平房,办了学校(名为“崇德小学”),其址约在环城北路边今实验幼儿园东侧。
租金收入
收取租金,是民国时期宁德县政府占有公产的另一种形式,并以教育经费支出为主要。“公产”办学,不仅仅只是使用建筑,还有一部分田产收益。
民国时期教育经费来源相当复杂。官办学校以国家支出(省拨款和县政府拨款)为主,公办的学校,除上述支出外,还有民间原来公田、学田以及社会上的捐助。
民国3年,全县财政经费总支出的8.65%,共1680元为教育经费开支。据刘祖宽先生回忆,20年代时,小学教师每月的工资,约为十二个银元。假设每年以十个月计,则在百元以上。民国4年时,城区内有国民学校5所,各乡村国民学校有31所,民国24年(1935年),县级义务教育经费开支预算达到12000元,其中省补助5164元,县自筹6818元。此时,全县“短期小学”已达50所。显然,上述之教育经费,显然不能满足开支(引自1995年版《宁德市志》第728、764页。)。
用于支付教育的经费开支的学田、公田租金,除文庙的学田收入外,也有一部分由政府支配的寺观田产收入。
从明代万历年间开始,县政府屡置学田,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原有的新旧学田共有76亩5分,加上乾隆十八年从凤山寺(址在今周宁咸村)移拨的寺田租5000斤,乾隆四十五年,学田岁收租谷15800斤。这些学田,分布于乡村和城内、城郊,包括了溪坂、滩涂、房基地、店铺及水田等等(见清乾隆《宁德县志》1983年版,第315页到320页。)。直到民国三十年(1941),当时县政府还以“催缴儒学兴贤租谷”的名义,动员公权力,派兵丁前往漳湾马山等地,催缴历年所欠租谷157担(蕉城区档案馆藏档案,编号:2-3-727。)。在今南门下宅园村附近,曾有围垦的“圣人塘”一处,相传这片田产的收入,就属于当时的官学所有,故此称为“圣人”的产业。
在古代社会,一些较大的宫庙寺观普遍拥有“香灯田”,祠堂则有“油灯田”和学田。如清代县志所载“城隍庙”一项中,有“香灯田:后溪村施洋了尾五斗,后溪村施洋北斗头四斗,共九斗”,周墩(今周宁县城)城隍庙“乡民周活七捐香灯田一石二斗”。还有“忠烈王庙”(即土主宫)“现存香灯田……以上共田一石零八升五合……”。类似的记载,还有“忠烈行祠”、东平王庙(民间称“新塘宫”,祀张巡、雷万春等,在今人民影院附近)、武庙(已废,址在今蕉城三小附近)、天后庙(即妈祖庙,今存,在东湖市场附近)、“报德祠”(原址在今城隍庙附近)(见清乾隆《宁德县志》1983年版,第133页到150页。)等等。这些载入县志的宫庙,多以官方名义给予祭祀,其田产,自然属于“官产”。如果考虑到学田规模的稳定性,这些官产,在民国时期,应当仍然归于县政府收入。
如前所述,部分寺庙所拥有的田产收入,在兴学的全国性浪潮之中用于办学,宁德县也不例外。但这其中的产权关系极为复杂,也不是所有的庙产收入都被运用于兴办学校。民国时期,庙产的多寡是十分悬殊的。大的寺庙,如支提寺、龟山寺、漈山寺等,有着大片的田产,而有的寺庙近于圯废,僧人毫无收入,生活甚至几近乞丐。进入四十年代后,一些管理有效的寺庙的田产,也得到了法律和宗教高层的保护。
登记造册
宁德县民国时期公产的确认,除了上述之使用、管理与出租之外,还对一些建筑进行登记造册,以此来明晰“公产”的产权。
1936年6月,福建省第一行政督察公署下达训令,要求宁德县长负责“先哲先烈祠庙财产”的保护与管理(馆藏档案,编号:2-3-663。)。这是一次全国性的登记造册行动,其法源在于民国政府内政部所颁布的《先哲先烈祠庙财产管理规定》。登记造册过程同时下发《概况登记报告表》。报告表包括应登记的祠庙的名称、地址、建立年代、公建或募建、先哲先烈事略,以及包括动产与不动产在内的财产评估、存款、事业基金等等。
从1936年6月开始,登记活动历时年余。在这份档案中,保留了三十年代末期宁德县一些祠庙的概况。
登记在册的祠庙,包括周宁城关的文昌阁、三都的吕祖庙、城关祭祀历史上的贤令林时芳、韩绍、汪大润的“遗爱祠”、北门关帝庙、周墩武圣庙等等。
如孔庙一项。其内容如下:
“先哲孔庙,南门内,道光二十年,蔡志谅捐资鼎建,大成宝殿一座,东西庑各一间,五代祠一座。占地五亩有奇,有牌位,现充模范小学使用。”在登记内容中,还写明文庙的部分公产,“东门外三叉港,蛏埕租,年小洋三百角,由民□□,前县长拨为修庙之用,近年已降价,仅收十余元”。
这一年年底,福建省政府重又发文对此次登记造册进行指导。说明“文昌阁”不算“先哲先烈”,天后宫改为“林孝女祠”,同时告知孔庙另外登记,并要求写清有关祠庙的“事迹”,等等。此次发文,还要求将各祠庙的年收益、年拨祭礼经费数、有无僧道管理及年拨生活费、已否举行办何种事业或改作其他用途及改变现状,保管或借用于祠庙处理改善意见(可否做学校校舍)等事项列入造册,相当慎重其事。嗣后,宁德县又将天后宫、南门武圣庙、遗爱祠、广泽尊王庙、灵杰候王庙等或重新列入,或充实其原先所登记的内容。
如城关南门武圣庙。这座庙在南门的校场边,其原址大体上在今蕉城三小东侧。这座庙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占地面积一亩半。三十年代时,仅余有正殿一座,其他的已倾圯。初次上报时,这座庙没有列入造册,后宁德县将此庙列入。
今天,南门武圣庙、西门戚公祠、东门外广泽尊王庙等已荡然无存。“戚少保祠,西门观音阁下,建于前清初年,公建,深二丈八尺,阔一丈一尺,”三十年代时,今继光街五显宫前,还有这样一座建筑,如今原址于何处,已令人费解了。而广泽尊王庙,在当时记载“现为东门外镇第二短期小学”,后来,因1953年一场大火,烧为平地。
三十年代时,还有一些尽管已列入登记造册,但这部分公共建筑并未使用于公共目的,或者至少政府并未对其行使有效的管理。如“北门”武圣庙,此时就是私人管理,由一马姓人员“向官产处投标,承买安置物件仍祀关帝”。
以上四种方式,或不能全面概括当时“公产”的管理与权属状况,但大体上反映了民国时期数量有限的公产使用与管理的一些现象。
“公产”的复杂背景——公权、法律、舆论与传统
民国时期的几份涉及“公产”使用或纠纷的馆藏档案,折射出这些公产背后十分复杂的社会关系,进而透露出不少相当有趣的时代气息与特定的历史氛围。
民国时期国家(政府)对公产的强势支配力
档案编号为12-3-1的地籍图产生的时候,已进入四十年代。从清末、民国初年、三十年代以来,随着新政的发展、现代国家机构的增加,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政府、执政党及一些公共团体大量地使用了原本属于宗教、宗族所占有及管理的宫、庙及宗祠。在这份地籍图中,有不少宫庙祠等建筑,已被直接标上了某单位或学校的名称,其原来的名字已经消失了。这表明,这部分建筑的宗教或宗族性功能已淡化或丧失,宗教或宗族性质的“公产”,已变易为“官产”。
如上文所述之溪流坑的“忠烈王庙”及“三民路”的蔡氏祠堂,此时直接注明“社会服务处”与“三民国民学校”。前述之三十年代尚登记在册的南门武圣庙,此时已不见踪影,成为“公共体育场(此图籍中另有一处公产为“公共体育场办公处”,位置约在今蕉城三小处,或为武圣庙址。)”的一部分了,说明这部分的“公产”,已经完全地变易为“官产”。
这份图籍上还有一些仍然标明着某姓宗祠的地点,但这时事实上已成为政府机构。蔡氏家庙、龚氏祠堂、陈氏祠堂等虽然仍以旧名,但实际上已经分别是县警察局、“民众教育馆”和三青团服务社了。但既注明原来的名称,很可能此时该宗族性公产仍未全部丧失其功能。也就是说,祠堂中的牌位等或许仍然保留着,呈现出使用和管理的过渡状况。
这涉及民国时期人们对“公产”的理解。
如前所述,如果仅就“公共的目的”以及“公用”这两个方面来看,无论是社会团体(宗教或宗族,或以“境”为代表的社区)使用与管理的财产,还是以国家与执政党(政府、国民党、三青团等)名义使用与管理的财产,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均可认定为“公产”。二者界限在民众的认识中,可能是相当模糊的。也就是说,所谓的“公产”,在当时,其实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今日之“行政公产”概念,自然不能概括“公产”之义,应当仅仅是“官产”。
从上述之宗祠、宫庙较多成为政府机关、公共设施、学校的现象看,当时,公权力对“公产”的占有与管理过程中,具有支配性的作用。尽管现在不清楚一些宫、庙或宗祠成为政府机关或官办机构,是否通过了赎买等程序,但在自清末新政,特别是“兴学”浪潮以来,在以法律的名义以及在倡导“进步文明”和“破除迷信”的社会舆论之下,社区性的公产,显然极易成为国家(政府)的财产。
国家公权力对公产的支配性质,还表现为以公权力收取公产收益,如派兵征学租。馆藏档案《催追儒学兴贤租谷卷》中有一份名册,列出欠了“学租”的佃户的名字及欠租数量、收据,税单若干份。在这份案卷中,还包括了县长“熊”(蕉城档案馆档案编号:2-3-723。“县长熊”的手令内容是:“…….前往马山等乡,清收三十年份兴贤祠租谷,以就近交由集兴米厂负责人收据报销,随带队兵二人……限于二十日前清收具报…….”)手札一封及后一任县长钟干丞(1942年2月至1942年12月任宁德县县长。见《宁德文史资料第五辑》150页。)继续追讨“学租”的批示。
卷中所列“欠租”的佃户,分布于六都乡、七都乡、郑歧乡、南埕乡、马山乡、“林家施”等地,计约20多人,数量分别在一二百斤到2666斤之间,总计为157担72斤半。
租种学田的佃户们,面对在承租学租的中介人(米厂负责人)追租时,或因实际困难而拖延,但在公权力面前,佃户们恐无拒交的决心与能力。这份档案,以今之观点来看,或可解释为反动政府欺压百姓的一个实例,但是,民众似乎对交纳这种属于公产的租金也尽力为之。马山乡欠租的佃户林文添,在交付一定的租谷之后,还向政府打报告,请求“俟明年早稻登场补还无法交清的谷子”。显然,这一户农民实际上已是将当年的收成尽囊而出。这一方面体现出国家(政府)维护“公产”的强制力,同时也透露出部分民众对官产应尽义务的一些认识。
民国时期法律对公产的规定与调整
在民国时期,对官产、公产法律涵义的界定,散见于各类法律文件之中。前文提到的《整理及调查官公产卷》中“蓝田渡船管理人陈细耳”的文本,即引用《土地法》、《处分官产暂行条例》、《公款公产整理纲要》三份法律的具体条文,来支持自己的主张:
……查《土地法》第八条规定“左列土地不得为私有:(一)可通运之水道;(二)天然形成之湖泽而为公共需用者;……(六)公共需用之水坞”。又第十二条规定:“凡未经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权之地,为公有土地。”又本省《处分官产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官产之种类如左:……(二)官有洲田、海滩、湖荡及水坞”。又本省各县区《公款公产整理纲要》第二条,第九款已指明,“其他公有之款产为公款公产”。
此外,较多的宫庙及寺产成为“官产”,也与民国时期出台的各类法律文件有关,并非宁德县一地的现象。而这些法律文件的出现,则与“破除迷信”的时代潮流有关,
清末“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兴学”,到了民国时期,特别是北伐前后,各地打倒宗教,没收庙产的事件十分普遍。当时,国民政府力图实践“三民主义”的蓝图,强调“改移不良之习俗,实行训导民众,趋于日新之生命”,要“破除中国人的种种迷信”(转引自付海晏《革命、法律与庙产》,2009年3期《历史研究》)。民国成立之后,政府在管理寺庙方面,有不少的法规和政策,如1913年曾颁布《管理寺庙暂行规则》、1921年颁布《修正管理寺庙条例》,1928年颁布《寺庙登记条例》、《神祠存废标准》、《废除卜筮星相巫觋堪舆办法》,1929年颁布《取缔经营迷信物品办法》。此后,还颁布了《寺庙管理办法》,《监督寺庙条例》等等。在一些学者看来,这些法规的出现,体现了国民政府巩固清代“庙产兴学”以来将地方寺庙财产监管权由地方庙首、会首手中,逐渐转移到近现代国家以及依附于国家之地方自治团体的努力,并且作为一种制度在整个民国时期长期延续下来(同上。)。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必然产生关于“公产”的复杂的法律关系。民国档案中,有一些涉及“公产”的司法文本,提供了一些有趣的历史氛围。
试举若干档案。
“龟漈寺”的田产招标档案。名称为《各商民申请承包龟漈寺租》,馆藏编号为:2-3-708。时间为民国三十年(1941)。
这份档案的主要内容,是一些“商民”,向当时的县政府申请承包来年的龟漈寺等寺观的田产收入。这些寺庙包括“龟漈寺”、“仓王爷”、“戚公祠”、“威灵公”等六家,合计产租480担,其中又以“龟漈寺”为最多,达150担。在1941年,申请承包者有13人。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原承包者李成坤承包额的基础上,进行兑标,向当时的县长“熊(熊方)”申请。申请人范围分布在宁德县的八都、城关等地。
二十九年承包者李成坤的承包额为500元(应为法币),但次年申请承包者大都增加承包金300元以上。并且,在申请书中提出了一些相当有趣的理由。
如“登仁保14甲”的林福民,申请理由是:“窃以抗战时期国家经济亟宜整理,吾邑教费支绌濒于极点,民属国民分子,应为国效劳,冀得稍尽天职……钧府有儒学一项,前由…….领办,年认缴500元,……愿在原额上增加200元。”
还有郑、王两位承包者,提出以450元承包,但其另有有利条件,即掌握着“公产”的原始契约。承包者指出,“钧府(县政府)”的“年租因为无底册,由人领办缴课,还是权宜之计,于法终究欠完善,”然后提出,他们所认识的王、陈两人,愿将底册交出,条件是“请求委办(承包)”。申请书中还提到:“固不论其真确与否,然往年之无所稽考,听人把持操纵之弊,则有所廓清,政府既有藉依,自能逐渐整顿,冀免日久埋漫之虞”。但是,县长“熊”(即熊方,1939年12月至1942年2月任宁德县县长。见《宁德文史资料》第五辑,150页。)不吃这一套,批复中指出,先将原始契约交到政府手中再议。民众与政府皆以法为工具进行博弈心态,可见一斑。
从以上的案例大体可知。一,这些公产权益的处置,主要通过法制的渠道来处理;这些田产属于“教费”所用;二,这些公产的产权并不十分清晰。表现为:政府并未完全掌握这些“公产”的原始凭证,民间认可公权力对这部分田产的所有权和管理权;三、国家(政府)对这部分“公产”的管理相当粗糙。表现为:对应得租金失于控制,很显然曾被原有承包者占了很长时间的便宜,并且,还是通过中介人来管理相关。四、政府所控制的“田产”份额并不大。当时,全县范围内有寺庙百多所,县政府直接掌握的田租收入,一年只有数百担(除文庙田产之外)而已。
至于“龟漈寺”为何有如此之多“公产”?庙产为何大规模地转移到国家(政府)手中?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有趣问题。龟山寺在民国二十五年(1934)曾遭遇战火,寺庙部分被毁(见1997年版《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第8页。),可能与此有关。
处理涉及“公产”纠纷的案件。在编号为2-3-742的《处理寺产案卷》有不少案例。
内中有一份学校与寺僧的田产纠纷案。1942年,赤溪乡中心小学的校长傅洪琼及校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杨忠帮,曾向县政府报告,民国二十四年(1935),广教寺住持僧曾向校基金“资助”租田四千觔(“觔”,同“斤”。),“历管无异”。到了三十一年(1942),新的住持提出学校侵占其田产,并且上告至佛教协会发函交涉,并诉至县司法局,引起一次法律的诉讼。这两位学校负责人称广教寺僧“向司法处起诉,蒙票传质讯,但过去情形恐未详细,务恳将本案全卷转司法处察核以资审讯。”
同一卷中,还有一份“侵占寺产”的人员名录,范围涉及城关、漳湾、霍童、七都、金涵、八都等地,数量多达几十人。卷宗中还包括这些“案”的处理意见,调查过程以及佛教协会的要求政府进行调查干预的函,等等(作者注:从其内容来看,这些庙产并不一定是“公产”,更可能是因时代变迁,庙产的产权产生模糊,因此产生了身为地主的僧人与佃户之间的争纷。)
在三十年代,宁德县政府曾经对“神产”进行大规模的登记,其目的显然是通过这样的途径掌握原先在政府控制之外的“公产”。这种登记,在法律的体系内进行,一旦产生纠纷,则进入司法渠道。
有一份档案,记载了西山保第二甲马懋添向县长陈情,认为民国三十六年(1947)登记神产时,误将其购于1937年位于“五都东楼”的一亩地,记为神产,因此产生了与一位吴姓人士的纠纷。另外还有一份关于张、许、郑、谢四人因“五都溪口”的一块田地被登记为神产,要求县长解决的呈文。
从已查的档案看,不清楚司法结果如何。但是蕉城区档案馆中民国时期司法类的档案十分丰富,研究者或可从中揭示更为详细与准确的历史信息。
政党、社会舆论及民间力量的作用
如上所述,民国时期“破除迷信”成为社会潮流,甚至中医、农历等传统中华文化的载体也被视为落后的事物,有的还以法令的形式加以限制、废除。
在这种社会舆论和时代气氛中,一些政党机关,社会团体以革命与文明的名义使用公产,对“落后”、“迷信”的民间旧势力,有着强烈的排他性。他们在使用一些宫庙、宗祠当做办公地点时,只要提出一些简单理由,直接向政府行文申请,无需与原来的管理者——社区性团体交涉。有的则干脆直接占用原有的公产。如文庙的考院(今人民影院址)成为党部、城隍庙成为三青团办公地点等等,都说明这一点。
现档案中保存着一份三青团写给县政府的“请拨城隍庙为本团永久团址”的呈文。在此之后,还有一份三青团向县政府具文要求占用“溪面”与“成德境”神庙为印刷社地址的报告(三青团原在城隍庙,后迁到陈氏祠堂(宁德城关内,民国时期有多座“陈氏祠堂”和一座“陈氏众厅”。据宁德县原文化馆工作过的陈继佑先生介绍,这座祠堂为宁德城区“埠头陈”之宗祠,其原址在东门兜北侧约四五十米的环城路边,其西侧有“成德境”神庙,门前为护城河。解放后曾充为文化馆、电业所,九十年代初,建城区内首家歌舞厅(酒店)“华福泉”,今已成为“莱茵城”之一部分。)),函称,“为发展业务起见,拟设立宁德青年服务印刷所中正室(图书室)报告各一所,除将现有之陈氏祠堂作为服务社址外,拟请口成德境庙舍及陈氏祠对面溪面口口归本处口修建应用,希转内政部备考….”
馆藏档案中,还见过一份某医院医师向县政府要求将妈祖庙的一部分充为诊所的文本。
从这些档案中,可体味到民国时期不但教育事业“理所当然”地使用公产,以“革命”与“进步”自居的执政党和以现代文明为标志的西式医学,对“公产”建筑的占有,也是相当强势的。
这种形势自然与清末民国初“庙产兴学”的全国性潮流以及国民政府所奉行的政策有关,但在国家(政府)、执政党组织及社会团体占用庙产以及其他宗教性的建筑、产业的过程中,民间及原有的宗族宗教团体,并非对政府机关与政党团体使用公产没有非议,有的以各种方式来干预,或借助上层宗教力量来影响舆论与司法。
前述“寺产纠纷”的官司,曾打到省里。中国佛教会福建分办事处负责人圆瑛曾致函给省政府,“近有地方一二土劣,违反法令,乘机驱僧夺产”,“请转饬各佃户归还寺产”,1942年,以省长刘建绪的名义,颁布78457号布告,称“查信教自由,载在政纲,保护寺产,法有专文”,要求地方政府对侵害寺产的情况,依法追究(蕉城区档案馆档案《处理寺产卷》,编号:2-3-742。)。
在庙产兴学及民国政府对庙产、神产的控制过程中,宗教团体、宗族团体及民众也采取了一些保护其原有利益的行动。
民国二十四年(1935),宁德乡绅蔡汝梅(四十年代末为商会会长,宁德县参议会议员)、陈有昌、左志儒三人向县政府呈文,要求政府出示公告,对南门关庙加以保护。呈文描述:“南门外较场边武圣庙,供奉壮缪关夫子,为汉族之英雄,作军人之模范,一心忠义,万姓钦荣……数年间,因乏人管理,被一般刁民将拉杂渔具任意堆塞,并引起流丐杂居其中,遂使栋折墙颓,荒秽不堪。”接着呈文称:“…..董事等为保存古迹,提倡尚武…..发起募修庙宇,再整金容,略告完成,藉资瞻仰……”,最后,呈文要求县长“出示禁止堆积及杂居流丐,以资保护”。次年,政府登记“先哲先烈祠庙”中,将这座关庙列入造册,并在现状中指出:此庙“前清由绿营管理,光绪间绿营撤,祭祀废,去年由乐善社募修,暂归其管理”。这种“暂归管理”也不长久,大约在四十年代,这座建筑被政府拆毁,成为“公共体育场”的一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传统旧例是确认产权的重要因素,民间因此也有了与国家、政党及强势的社会团体博弈的机会。从档案中披露的情况看,民国时期一些“公产”的原始契约或许是不完整的,如档案《承租龟漈寺等学租卷》中表明,有人就掌握着政府未曾掌握的田产契约。三十年代民国政府对祠庙等进行登记造册的活动,也包涵着建立原始档案的用意。至于这些神宫庙祠的法律文本凭据最终确立,已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情了。
掌握契约或原始凭证,是民众有力的工具。在个别案件中,有的因为原始契约残失,导致产权争议,最终政府部门引入了最为原始的证据。《处理寺产卷》中,有一份有趣的文本,《抄录清乾隆十七年圆明寺碑文》。抄录这份碑文的目的,在于理清漳湾乡数位村民与圆明寺僧之间的田产纠纷。原始碑文以宁德县令“本府正堂加三级”的名义,不厌其烦地从宋代大儒杨复(信斋)事迹说起,叙述后人捐田俸产,先为祭田,明代时寺田归公而致田产或为先儒祭田或为寺产“尚未分晰”的过程,后来又提到清代时杨家后人争产的情况等等,说明保护庙产的理由。时隔百余年,到了民国三十一年(1942),宁德县政府部门为解决这些田产纠纷,又郑重其事地抄录“前清”的原始凭据。从这件事情来看,民国时期,久存于民间的习惯、旧俗以及一些传统做法,应当对政府使用与管理“公产”的过程,对民国政府试图将寺庙财产纳入法制化监管体系的建设目标(引自付海晏《革命、法律与庙产》,2009年第三期《历史研究》),有着一定的约束与制约。
“公产”的法律内涵十分复杂,不同国别,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释义。民国时期,何处财产属于“公产”在当时就有不少争议(如蓝田渡口一案)。以今人的观点看那个时期的“公产”,在法理上更是难做清晰的界定。因此,本文所提供的史料,只是对宁德县民国时期一些现象、一种氛围、一些惯例的间接反映与简略介绍,供读者参考。本文所涉及的“公产”,其保存状况及其权属,亦多有变化。文中的陈述与观点,只是个人看法,不足引为法律凭据。兼受资料和水平的限制,文中或有观点含混、法律用语未能精当、引用材料及分析错误、疏漏之处,望有识者纠正。
本文在薛赞平、姜翔骅、黄澍等同志帮助下写成。在此一并致谢。
民国时期公产的类型——渊源与衍变
民国时期宁德县的“公产”,一部分是自清代以来“官产”的延续,一部分是国家(政府)出于公共的需要,使用和管理了原本归属于某些社会团体所有及管理的财产。这其中,包括了“前清”时期县政府、军队、官办机构遗留的一些建筑物与地产、渡口码头,以及一些宗族或宗教团体、群体(社区)所有或者管理的祠、宫、庙、观、会馆,最后,还包括部分庙产、学田(公田)。
建筑财产
宁德县城在1949年,有房屋建筑32万平方米。自晚清以来,除几幢教堂及洋楼外,无论公共建筑还是民房,绝大部分为木结构土夯墙或空斗砖围墙传统建筑。
这一类的公产主要有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官宅”。即清朝政府机构和官办机构遗留的建筑与地产。如县衙、游击署、官仓以及文庙、官办书院。在民国时期,这些旧建筑被国家(政府)使用管理,分别成为县政府、执法机关、公众体育场和国民党党部、官立学校。如县衙(旧县衙,位置大体在今区政府院内,内中建筑解放后陆续拆除。)。据资料表明,明代所建县衙,有正堂3间,堂后为内宅,堂左为幕厅,堂右为库藏。堂下又有14间卷房,前有仪门5间,另有吏舍20多间,规模相当大。除县衙之外,宁德县城中还有县丞署、教谕署、典吏署,以及军械库、监狱等多处。
第二部分,各种宫、庙、寺、观、会馆。宁德一地,宫庙寺观极多,这些宗教建筑原有的功能及管理使用情况十分复杂。在清代时,有的宫庙祠由官方祭祀,属于全县甚至数县范围民众信仰供奉;有的是一个、数个社区范围(境)内或某宗族一姓、数姓民众祭祀供奉;有的归于宗教团体或个别宗教人员供奉管理。会馆则由创建者——地域性团体或行业公会所使用。
集中于城区之内的各类宫观寺庙,清朝末期开始实施“新政”之后,大量被用于学校办学和政府机构的办公,特别是原先就归属于政府管理,官员祭祀的宫、庙、祠,建筑保存较好的,均被官办机构使用。各座原属于社区共有的宫庙及由外地客商兴建和管理的会馆,民国时期大部分时间里,也较多地被当地政府、社会团体所管理使用,或用于驻军。
第三部分,较为特别,就是分布很广的各姓祠堂。民国时期,各姓祠堂也被广泛地用于兴办学校和政府机构办公以及社会团体活动。
在乡村也多有这般情况。特别是宁德县乡村中的祠堂、祖厅,是民国之前乡村中分布最多、最为主要的公共建筑,因此民国时期的公共机构及学校也多设在其中。如漳湾的官办小学,设于阮氏祠堂中,古溪村陈氏上祠堂因较为宽敞,乡公所与小学皆设于其中。
尽管这些公用建筑物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使用者各有不同,但以“公产”名义存在,却是没有疑义的。“公产”,又可称为“行政公产”,其法律释义十分复杂。总的说,指公众直接使用的财产或公务使用的财产。目前在我国,行政公产是指行政主体(“行政主体是指享有国家行政权力,能以自己的名义从事行政管理活动并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的组织”。转引自“百度百科”。)为了提供公用而所有或管领的财产。民国时期,除“行政公产”之外,社区或团体所使用与管理的财产,也使用了“公产”的概念。民国时期,至少在上个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宁德县政府设立有“整理公款公产委员会”,其主任由县长兼任(见蕉城区档案馆档案《整理及调查官、公产卷》,编号2-3-736。)。从相关档案中也可看出,当时政府与民间所认定的“公产”范围十分宽泛,不仅包括“官产”——国家(政府)直接管理使用的财产,一部分原本属于社会团体(社区)使用管理的建筑,也使用了“公产”这一名词。例如,位于“西山路”的“龙首境”宫(位置在今市新华书店附近),在四十年代的地籍登记中,就直接标明“龙首境公产”(见蕉城区档案馆档案:12-3-1。)。在社会实践中,以用途的公共性和管理的有效性来看,上述这些建筑财产,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公产”。
田产、地产
关于“公产”,还有一种类型,就是自古以来存在的各类公田(祠堂田、公轮田、墓田)、学田和部分寺庙管理的田产,这部分田产,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土地改革之前,约占全县耕地的30%(见姚智卿《恢复发展改造——记建国初期宁德经济状况》一文,载于《宁德文史资料.十一辑》第70页。)。其中有一部分公田,主要是学田与若干庙产,为政府掌握,其收益用于教育经费开支。
自1901年清朝廷颁布办学的新政以来,不仅书院直接转变成为学校,一些地方的祠堂和寺庙以及财产,都以法令的方式,成为办学的主要资源,并在实践中得到有力的推广(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1901年9月14日),作为新政的举措之一,清政府下诏办学,谕令“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6:176)。苦于办学经费不足,清政府实施了“庙产兴学”的政策。1902年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和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都有将地方祠庙及其财产提拨为学堂之用的规定,如《钦定小学堂章程》第一章第八节规定,地方办理小学堂时,“均得借用地方公所祠庙以省经费”(见舒新城编,1981:400);又,所谓“庙产兴学”,狭义地说,就是指征用各寺庙财产来兴办教育,包括庙产补助学费,将庙址划拨为学校。如日本学者村田雄二郎所言:“清末民国时期实行的一系列没收寺观神庙财产(寺院领地、田产、庙宇等),充当振兴地方初中等教育费用的一系列政策、运动”(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2006:561)。这一理解主要根据当时人的言论和光绪皇帝的上谕。就实践层面来说,“庙产兴学”运动所涉及的地方公产除了寺庙财产外,还包括会馆与祠堂的产业,民间各类会产,以及斗捐、官秤、红庄等地方公费。——转引自《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一期,梁勇《清末庙产兴学与乡村权势的转移——以巴县为中心》之注解。)。在宁德县民国档案中,有一卷档案记载了1935到1936年间,县政府对“龟漈寺”的田产进行召租的过程(蕉城区档案馆档案(关于龟漈寺等田产召标的文书)2-3-708。),其名义就是“学租”。还有一份卷宗记载了1940年赤溪小学与当地某寺僧人因为学校基金会的“学田”问题产生纠纷,呈文请县政府调查的事情。还有一份档案,记载了1936年县政府对文庙的田产和滩涂租金收入使用的指示。从这些案例中可见,当时的公产,不仅包括一些实物(建筑),也包括了一部分田产的财产权,国家(政府)对这部分财产,具有收益、处分等权利(作者注:这种权利,法律上称为物权中的“用益物权”,指得是一定条件下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这种财产权利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上个世纪的前五十年,社会经历激烈的变革,由清末、民国初期、抗战期间,到了民国后期(本文专指抗战胜利的1945年到1949年间,下同),由于各种原因,这些田产的“公产”性质,有的也产生了不小的变化。一部分原属于寺庙的田产,成为政府或学校管理与收益的“公产”,而有些政府的财产权益,也流失于民间,无法得到体现。
“公产”的衍变
从历史渊源来说,民国时期的公产,相当部分是清代“官产”的遗物。而清代的官产,有的也是前朝(明朝)的遗物。在王朝更迭,社会动荡时期,产权时有变易,甚至在政局平稳时期,也有将官产出售而变为私产,或买入私产成为官产的事例。
1、官山成为私产。清代乾隆《宁德县志.卷一.舆地志》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旧志按云:本县山场无论城郭乡村,除附近庐舍坟墓者始为民业,高山深谷俱官山也。嘉靖初年,外郡人来县境栽菁,俱告于官,官则随山按户置簿收租。自辛酉倭变之后,官簿无存,土豪年估其租……今考本县册籍民山,悉属官山,……而此日承平已久,彼此授受买山者多矣。”这一段文字,说的是原来属于官产的山场,由于战乱、经济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属变动,由官产变为私产的原因与过程。
2、私产成为官产。这本旧志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游击署,在北门内,原系崔家房屋。自国朝顺治五年设立专营,买置为署。……十四年(乾隆),游击潘公从龙改建三堂,并修葺头门、大堂、二堂、三堂……规制一新。”(引自清《宁德县志.卷二.建置志》。)这里说的是私宅成为公署的过程。这座“游击署”,在今培英路旁,旧时民间称为“大纛衙门(以方言音,或为‘大道衙门’)”,在民国时期成为体育场,解放后,仍为公产,即是现在公安局的拘留所位置。
民国之前,产业由官而私,或私人宅地因为官府购买而成为官产的例子还有。如今大华路薛氏大宅,民国时期范围颇大,内有花园等。从清代县志上看,明代以前是“射圃”——县学学生或驻兵练习武艺的场所,后建布政分司署。址废,成为民宅。明嘉靖年,县令林时芳又“贸易民宅”,建按察分司。清乾隆年间,此处建“鹤峰书院”,不久,书院迁西门外今十中址,改名“莲峰书院”。石堂巡检司署(县政府的分署机构)几经搬迁,“寓县城”,驻于此处。到了清代中期后,此地售于薛氏。至今,此处还有“巡司弄”的旧地名。
辛亥革命之后,“前清”绝大部分官产的权属性质,并未因为社会动荡而产生变化,这与民国初年就确定清代有关物权的部分法律条文有效(“1914年,大理院在上字第三0四号判例中认为:民国民法典尚未颁布,前清之《现行律》除制裁部分及与国体有抵触外,当然继续有效。至前清《现行律》虽名为《现行刑律》,而除刑事部分外,关于民商事之规定,仍属不少,自不能以名称为刑律之故,即误会其为已废。同年,大理院在上字第九三八号判例再次确认:前清现行律关于民事各条,除与国体及嗣后颁行成文法相抵触之部分外,仍应认为继续有效。”——转引自2008年第六期《北方法学》,姜茂坤《论民国初期“物权契约理论”的发展》。),并且民国政府很早就开始登记和清查官产(“民国4年(1915),福建省财政厅向财政部上报本省官产价值为46万余元,当年8月,设立福建省清理官产处,重新清查各县区官产,造册上报。”——引自1994年版《福建省志.财税志》第八章第六节。)有关系。清末民初交替时期,宁德县城未经战火与动乱,民国时期的官产,“平稳”地由民国政府接收,在政府、社会团体与民众之间,没有太多的争议。
但是“公产”并不全部都是产权明确的“官产”。由于产权模糊,到了三四十年代,出现了涉及寺观田产、神庙田产、渡口等一些关于“公产”的纠纷。同时,还有一些公共建筑处于无人管理或管理不善的状态,或为流民所居,或由社会团体暂管,或由个人承租管理。
“公产”的分布——时代特征与过渡状况
民国时期哪些财产属于“公产”,只能以当时的概念来认定。要全面的弄清民国时期“公产”的情况十分困难,但现有档案大体透露出这方面的概况。
今藏于区档案馆中的编号为12-3-1的档案,是一份十分罕见的地籍图。这份档案,是用1:500的比例制作的城关、飞鸾、霍童、八都等城区镇区1943年的平面图,图中示明土地的类型与归属,人们从中可以得知当年城区及相关乡镇公产与私产的一些状况。
图中土地类型大部分为“宅”,即建筑物,也有“杂(空地)”、“荡(池塘)”、“田”、“园”等等。还标明了街、巷的名称与走向。“宅”的类型中,则写明其名称,标注出其权属。
据图,宁德城关中,政府机关、学校、银行、办公处、供销处、地证处、贸易公司、体育场、训练处,以及只标明“公产”的建筑有25处,官办机构“社会服务处”一处。宗教场所如基督教圣公会、天主公教、自立会等4处,祠、宫、庙、观等15处。各姓氏的宗祠则有12处。图籍不但标明了这些建筑的名称,还准确在标注出其位置与面积,相邻的建筑。
试分类例举:
学校
“三民国民学校”,在三民路,即今中南街;“北山国民学校”,在遵化路,即今北门街;“蕉城中心学校”,在三民路(今蕉城一小附近的学前路是这段路的一部分)。还有两处“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处”,均在三民路,也在今蕉城一小内。以上学校校址,原来建筑分别为蔡姓宗祠、城隍庙、文庙(作者注:此时“宁德初级中学”业已成立,校址在原莲峰书院,今宁德十中处,此图未载。毓秀小学此时已创办多年,址在今宁德医院内,此图亦未载。)。
政府机关
县政府,在“县府路”左(此图“县府路”,即今街中头西门路至大华路口的路段),今蕉城区政府大院在此范围之内。还有一些只标明“县政府”的建筑,分别位于“中山路”(今八一五大街处)、“文昌弄”(今鹤峰弄)、南门筱场边等地。在今东门兜旁,有五处房产直接标注“县政府”。这些只标明“县政府”的建筑,此时可能是一些县政府的办事机关或一些公共的场所(1994年版《宁德市志》载:1937年6月,县政府曾出垫资2000元建东门菜市场。此处所提“今东门兜旁五处标为县政府”的地产,或为此。此菜市场址,约于七十年代中期改建为百货商店,俗称“下百货”。)。
公共建筑
“宁德青年体育场”,在培英路;“公共体育场”,较场边。这其中,可以识别的,前者即是今公安局看守所,后者是数年前的体育场,今已成宁川路和部分民宅。还有一处“体育场办公处”,在较场边,其位置似乎即是今蕉城第三小学校址。
其他公共单位
“福建省银行”,在大华路;“供销处”,在遵化路,今北大路;贸易公司,在北大路。这些公共机关,有的今已成为民宅,有的现在的用途不祥,有的已被拆迁,成为所谓的“新城”商业建筑了。
以上例举诸机关办公所在建筑,是由国家掌控的公产。这些建筑或为“前清”政府“遗产”,或由民国政府购置,或为政府机关征用。在1943年时,这些建筑以国家机构的名义登记在册,已成为名符其实的“官产”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三十年代登记为“公产”的若干建筑,到此时,可能已成为私产。如西门的戚公祠,在图籍中已找不到,很可能在这一段时间内,由公变私。而这种转化的最大可能性就是公产的出售。但真实原因不详。
除以上所列之“官产”以外,还列出了不少基本属于社会团体所有和管理的“公产”建筑,主要是由民众祭祀与管理的神庙,以及各姓氏所有及管理的宗祠。
宫、庙、祠
“鹤成境”,在南大路较场边,即今蕉城三小附近;“文昌帝庙”,在中正路,今八一五中路一带;“鹏成(程)境”,在环城路,即南环路口,今兴业银行大厦处;“福山境”,在复兴路,即今福山街,今妈祖庙右侧,等等(此外,旧时蕉城周围还有陈太尉宫(今区防疫站内)以及灵溪寺、天王寺、南漈寺、地藏庵等数座宫、观、寺、庵、堂,或因当时处于城外,亦不见载于此图中。)。
此外,这份图中标明的宗祠及“众厝”十几处,均能明确地与私宅区分开来。如溪井乾处的王氏祠堂、北大路的韩氏祠堂、前林路的陈氏祠堂(今莱茵城,原宁德人民会场址)、环城路的陈氏祠堂(小东门街原县文化馆)、龚氏众厅(约在今八一五中路农业银行前)、“三民路”(竹兜街)的“马众祠堂”(其址或为原“红星街道”办事机构,附近另有一座马厝众厅。)、文庙西侧的林、郑祠堂,等等。
此外,这份地藉图还制作了飞鸾、八都、霍童的镇区的平面图,从中也能看出当时“公产”与“私产”之间的一些情况。
除了这分地籍图以外,馆藏档案保存不少有关政府招租、追租的文本,处理公产纠纷的文本,也能大体上体现“公产”的分布情况。从这些文本中可见,除宁德城关多处建筑财产为“公产”之外,政府还占有相当数量的田产。
民国时期,宁德县政府曾经对公田进行登记造册。1938年,宁德县政府通过统计,明确了全县儒学田计有933亩,公学田39亩。1942年,通过统计,宁德县中学基金田965亩多,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量。在1940年以前,政府还对寺庙的田产进行登记,据1948年的数字,各类“神产”计有田1826.49亩,园77.14亩(1995年版《宁德市志》,第535页。),这些“神产”中,有一部分就是政府掌控的。
关于田产,很可能还涉及一部分由政府投资围垦的部分。宁德县面海,历史上多有官府投资及牵头组织民众围垦海滩的事例。馆藏编号为2-3-736的档案中,有一份写于1942年的有趣文本。这份由南埕“济农塘”董事陈世泰等人写给县“整理公款公产委员会”的报告,陈述了“济农塘”的由来,以及他们与政府对塘中“公产”的不同理解。兹录于下:
“窃南埕海滨,绝少园山田地,居民专以晒盐为生,相沿日久。民国三年,政府以南埕盐质不佳,下令除坎,盐民三百余户骤告失业,彷徨无措。赖已故邑绅林理斋先生领导请愿,设法救济,呼吁迫切,而其长公子,前四川盐运使林振翰君,洞悉情形,居间斡旋,始蒙部准发帑,建筑济农塘,以资盐民生计。并由福建前盐务稽核所正经理主持其事,亲临履勘,延聘工程师测量。同时专指董(“董”,指“董事”,即陈世泰等三位具报告人的自称。)等为建塘董事。已故崔伯乾先生为经理,林理斋先生为名誉经理,八年始成。由县府派员照盐户坎数分配田亩,多寡不等。各盐户以塘堤规模初具,根基诸未坚固,若不预谋善后,难期久远。乃以应分田亩,酌量抽成,储为盐民公共田地,将来披修取资于此。惟是八年开始垦荒,直到十六年克成业,略有收获。”
这段描述,承认了政府投资围垦、分配及留有“公田”的事实。然而,政府的这一笔投资,直到1942年,仍然未能收回,并且这塘中的“公田”也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份报告中描述了自民国十六年以来济农塘所遇到种种困难,而后向县政府陈述:“伏念政府筑堤救济南埕盐户,其全部塘内田地即均属盐户,永远享有业权,而此项养塘公田又系盐户当分田之时,自愿公抽做为基本,似于公款公产显有分别。”最后,董事们还警告政府,“当此风雨飘摇,秋潮洪猛,……诚恐因循贻误,关系扉轻……”
从民国三年到民国三十一年,时局多有变化,后任的县长,想要主张二三十年前的财产权,恐怕是无法实现了,档案中惜未见此事后文。但是,民国时期宁德县政府向滩涂要田地的进取心仍然相当强烈。1947年,宁德县政府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围垦——西陂塘工程,在这个巨大的工程中,政府将可能实现多少“公产”,未尽其详。最终这个工程未能完成。
还有一类特殊的公产,就是渡口。馆藏档案中有一份编号为2-3-736的《整理及调查官公产卷》,内中有一份“蓝田渡船管理人陈细耳”向公款公产清查处主任陈情的文本。文本中称:
“窃民于去年十一月见钧处布告,招人承租公产,遵经依照法定手续,向钧处租出蓝田溪官渡,筹造新船,以渡行人。新造船一只,垫费二千五百元,口于废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新旧交替,归由民撑渡行人,业经有日。当由钧处发给公产租约为凭,年纳租谷六市担,租约有效期间为五年,由三十一年十一月起口口口六年十二月止。讵料蓝田土豪吴秉文等侵渔公产,食髓知味,意图永远霸占及饰词朦耸,钧处(作者注:从后文来看,可能是“钧处”的个别人)以溪河不算公产,有意阻挠清查公款公产工作,影响抗建(战)前途,至为重大。
……查蓝田溪官渡适合于《土地法》第八条第(一)、(二)、(六)等款及《官产条例》第二条第二款《公款公产整理纲要》第二条第九款之规定,确属公产无疑。若谓为私产,试问有无依法取得所有权?设非公产,当日钧处断无贴布告招人承租及给发租约准民租为造船撑渡行人之用。再查本省《处分官产暂行条例》第十七条之规定:“官产一经招租定案后,无论何人不得再行呈请变更”。是见政府立法之注重威信。今吴秉文等贪利无口,敢出于政府告争夺利,其胆大妄为可以概见。万一再被霸占,而蓝田溪鱼潭年可获鱼十余担,亦归乌有,公私两俱损失。近有贪利违背职务之一二不肖公务人员,尚且为吴秉文等奔走说项疏通,实属违法已极,合亟备由呈请鉴核:依法严惩,驳斥无理请求,以绝私饱,而维威信,实为公便。”
此份档案涉及“官渡”这一久已存在的事物。在清代乾隆时,曾设置六都、金垂、飞鸾等多处官渡,官府配备人员、确定薪酬。百年之后,大约因为陆路交通变化,或私人船只增多,其他“官渡”已无存在之必要,但兰田渡却仍然保留着“官渡”的传统管理运营方式,只是时代变迁,私权逐渐地取代公权了。该卷档案中,有关蓝田渡的文本,仅此一份,尽管为“一面之词”,但亦可见当时一般民众对“公产”的认识有相当的深度。
民国时期政府所认定的公产数量远不止于此。特别是属于“官产”的建筑财产,在此后的社会鼎革中,大部分保持了其公共性,甚至一直存留至今。
当然,以上所列财产或财产权,以今天的观点看,有的或许不能算做“公产”。但是,如果从民国时期这些财产的“公共性”,以及政府与公共团体对其有效管理的角度来观察,其“公产”的性质,是显而易见的。
宁德县政府对不同类型的公产,有着不同的管理方式,主要表现为:直接使用(办公、办学)、登记造册、收取租金。使用管理的有效性,是认定公产的主要指标,应当说,这个时期一些“公产”,所有权究竟属于何者,并无契约,但是国家(政府)机构、执政党(国民党、三青团)和一些公共团体有效的管理使用,却明确地体现了“行政主体”对财产占有和支配的权利。
政府、执政党团、官办机构直接使用的公产
清朝末期开始实行“新政”,政府机构开始增加,民国建立之后,司法、民政、税务等机关增加了不少,宁德城关内多处原来的官产,遂由这些机构进入办公。
原来的县衙、官仓(今县政府内),成为民国时期县政府和看守所(见1995年版,《宁德市公安志》,第20页。)。
建于南宋嘉泰四年(1204)的“土主宫”(址在原蕉城镇机关,后为“二月花商场”,今商业城“锦福城”旁),称为“忠烈王庙”,神主为唐代的太学生黄岳。清代末年,清朝筹建新型的警察机构,宁德县警察署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设于土主宫中。直到四十年代初,警察局移至前林坪蔡氏家庙,这里又成为具有官办色彩的“社会服务处”。
宁德县文庙,当时是全县乃至闽东最为恢宏的一处建筑群,在1904年清朝废除科举制度后,就成为民国时期多种官办机构办公的地点。从1927年开始,文庙所属的考院(今人民影院,当时俗称“考坪”)成为执政党国民党的党部。文庙的大成殿仍然保持着祭孔的功能,也做为学校的礼堂。小学最初办在明伦堂两侧的厢房,抗战初期,文庙中建新校舍,为宁德县官办的国民模范小学。1944年,县临时参议会会址曾经设于文庙之中。
城隍庙,建于南宋(绍兴元年,1131),历八百余年,经多次修葺,到民国初期,仍然保持着较为完整的建筑,很可能仍然保持着民间迎神祭祀的功能。民国十二年(1923),县公署(后改称县政府)奉命禁止迎神赛会,作为民间祭祀最主要场所的城隍庙,其功能很可能就此式微乃至终结。到了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时,城隍庙多被用于公共目的。庙曾被驻军征用,庙中城隍神像被迁于不远处的武圣庙(址在北门街与培英路交叉处附近,姑称为“北门武圣庙”)内。1935年,县卫生院曾设于庙中,1938年,三都中学暂时迁此(见1995年版《宁德市志》第20、24页。),到了四十年代初,这里又成为“新兵接待所”和“北门国民学校”。后来,简易师范、三青团也曾经将这里做为团址,旧时还有一家“报社”亦以此为社址,兼有印刷所。
位于城隍庙北边,与之一路(路原为城墙,1939年拆后城为环城路)之隔的朝天境神庙,规模颇大。自三十年代后,此处被用于县医院处,内设手术室,办公室及病房。一直沿用到解放初期。
南门校场边的武圣庙,原来为“前清绿营兵”驻扎,是一处名副其实的“官产”,但在民国初,“祭祀废,渐倾圯”,已是十分残破,被流民所居。民国二十四年(1935),由“乐善社”募修,管理(蕉城区档案馆档案,编号:2-3-663。)。抗战期间,委派而来的福州籍体育场长,扩修400米跑道,将该庙拆迁,遂成为体育场一部分。南门校场,原来是地方驻军的习武之处,民国时期,曾辟为体育场。校场周围有若干建筑,在1943年的民国档案中,还明确的标明为“县政府”的财产。后来权属流变,今已成为私产。
从当年的档案来看,有的祠堂,在民国时期,也成了一些政府机构的办事之处。较为典型的是前林坪蔡氏家庙(今已毁,存一仪门),四十年代时,县警察局在此办公。据今年九十岁的陈继佑先生介绍,解放前蕉城镇公所址多有变动,也一度设在这里。在前林坪的另一家蔡氏祠堂,也曾设为蕉城镇公所和县田赋管理处。
旧时县政府大门东侧县衙路(即今西门路)旁的彭氏祠堂,民国时期这座祠堂被政府机构使用或与彭氏家族共用。据彭氏族人回忆,解放前,这座祠堂曾经被用于办“文化馆(据今年九十岁的林承荣回忆,此处曾设过“民众教育馆”,“文化馆”一说,疑为指此。)”。后继为警察所,到了“张同英”任县长时,县政府围垦西陂塘,这里又成为围垦工程的办事机构和仓库(张桐膺,1945.7——1947.3在宁德县任县长。见《政协文史资料》第五辑151页。)。
龚氏祠堂(位置约在今八一五中路工商银行前的路段中),此祠堂原为图书馆,后于1933年设为“民众教育馆”后来“民众教育馆”转到这里(见1995年版《宁德市志》,798页。)。在60年代初大街开辟前,曾充任文化馆。
陈氏祠堂(位置在今东门兜附近“莱茵城”处,原成德境巷口),民国时期一度为“三青团”办公处,七十年代后为文化馆和电业局的办事地点。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直接使用”,并不意味着旧有功能完全丧失。有的神庙及祠堂,在此时,很可能仍然保存着一年一度祭祀的功能。只是平时被“公家”所用。如上述之彭氏祠堂,据说直到五十年代之后,祠中的牌位等才被搬出。
以上是政府或公共机构直接使用的“公产”,实际上,被政府机构直接使用的公产不止这些,乡镇各地情况也大抵如此。此处不一一例举。
兴办各类学校所使用管理的公产
清末开始兴办新式学校,光绪三十一年(1905),官办的莲峰书院改为“官立”莲峰高等小学堂。城区内还有4所“公立”小学堂,由县政府每年拨给50元补助。民国以后,宁德县学校数量增加了很多。民国四年(1915),宁德城内有国民学校(初等小学)5所,各乡有31所。进入三四十年代之后,宁德县还办起了初级中学(1940年,设于莲峰书院内),有中心国民学校、国民学校60多所(引自1995年版《宁德市志》728页。)。清末民初学校的兴起,使用了大量原本“公用”的建筑。这其中包括了庙、寺及大量的祠堂。
办学使用寺观和祠堂,在宁德有其传统。宁德县自古以来,不但有县学,还有社学、义学和许多书院及私塾。这些教育机构的校址,有的创建(如城关的莲峰书院、霍童的双峰书室),有的购买寺庙(如灵溪寺和广福寺在明代都曾经办学),有的通过官司将寺院变成书院(如清咸丰年间的洋中鞠多寺,官判为书院),但也有读书人自建读书处,后来成为寺观(如龙湫寺)。至于私塾数量更多,多半办于私宅内和祠堂中。清末、民初,就城区而言,有前林坪富豪蔡氏办学于自家中、前清文人林其荣办学于陈氏祠堂、前清罗源县教谕林理斋办学于林氏祠堂、前清文人牛兰金办学于崔氏祠堂(见黄建琛《祠堂、民宅塾馆》一文,载于黄建琛、黄澍、姜翔骅等编《蕉城古风貌建筑及其他》,2007年版。),等等。后来新式学校兴起,使用旧有的“公用”建筑,继承了这一传统。
民国初,政府有资助私塾部分经费的做法,一些原本只读旧书的塾斋开始引入新式教材,分科教学,但校址仍然办在家宅或祠堂中,新式小学兴起,仍用旧址。如漳湾创办的小学,就设戚公祠侧的阮氏祠堂中。西乡(“西乡”,习惯上指蕉城区西部山区乡镇石后、洋中、虎浿一带。)一带,这种现象十分普遍。据今年九十六岁的刘祖宽先生言:大约民国十年(1922),他由家乡灵下村的私塾转洋中第一所新式小学——青田小学读书,就是在东山村陈氏祠堂中读书。后来,青田小学移至洋中村,办学地点的“中厝厅”和“巷口厅”,此后直到解放后,学校一直使用祠堂(“众厅”)作为校址。石堂自古学风兴盛,民国时期“上西乡小学”设于梅鹤村的林氏祠堂之中,办学规模颇大,甚至洋中的学生也来此就学。据刘先生介绍,其童年读书时,曾见县里督学下乡视察办学情况。假如督学认可原来的私塾的确转成新式小学,则给予资助。当然这些资助微薄,无法创建新的校舍。
宁德城关也有祠堂成为学校的现象。据林承荣先生介绍,当时吴氏祠堂相邻的蔡氏祠堂(址在“三民路”(民国时期“三民路”,由蔡氏家庙附近的前林路至人民影院,即今中南路,解放后还称为“红星街”,俗称“竹兜街”。),今八一五中路南侧),四十年代时为某学校办学于此,其校长姓关,今年尚健在,已年逾九十。从前述之地籍图中,也可确知,这所学校名称为“三民国民学校”。
学校使用宫庙与寺观的现象相当常见。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寺庙管理条例》,进一步确定了寺庙办理“公益事业一种或数种”的法律根据(转引自付海晏《革命、法律与庙产》,载《历史研究》2009年第三期。)。由于城关内保存较好且较为宽敞的宫、庙、祠等建筑数量多,因此,进入民国之后,学校办在这些宗教建筑之内的情况更为普遍。
民国二十五年(1936),当时的广泽尊王庙(即“泉郡会馆”,俗称“圣公庙”,1953年毁于火,今饲料厂位置(见黄澍《泉郡会馆轶闻》一文,载于黄建琛、黄澍、姜翔骅等编《蕉城古风貌建筑及其他》,2007年版。))为“镇第二短期小学”(引自蕉城区档案馆档案,编号:2-3-663。);更为宽敞的城隍庙,其东北角(后大殿)曾也当做“北门国民学校”的驻地,与“新兵接待处”在庙的前后殿共处相安。前述之“北门”武圣庙,曾办过某“简易学校”。宁德北门外天主教堂,也腾出礼拜堂外一处平房,办了学校(名为“崇德小学”),其址约在环城北路边今实验幼儿园东侧。
租金收入
收取租金,是民国时期宁德县政府占有公产的另一种形式,并以教育经费支出为主要。“公产”办学,不仅仅只是使用建筑,还有一部分田产收益。
民国时期教育经费来源相当复杂。官办学校以国家支出(省拨款和县政府拨款)为主,公办的学校,除上述支出外,还有民间原来公田、学田以及社会上的捐助。
民国3年,全县财政经费总支出的8.65%,共1680元为教育经费开支。据刘祖宽先生回忆,20年代时,小学教师每月的工资,约为十二个银元。假设每年以十个月计,则在百元以上。民国4年时,城区内有国民学校5所,各乡村国民学校有31所,民国24年(1935年),县级义务教育经费开支预算达到12000元,其中省补助5164元,县自筹6818元。此时,全县“短期小学”已达50所。显然,上述之教育经费,显然不能满足开支(引自1995年版《宁德市志》第728、764页。)。
用于支付教育的经费开支的学田、公田租金,除文庙的学田收入外,也有一部分由政府支配的寺观田产收入。
从明代万历年间开始,县政府屡置学田,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原有的新旧学田共有76亩5分,加上乾隆十八年从凤山寺(址在今周宁咸村)移拨的寺田租5000斤,乾隆四十五年,学田岁收租谷15800斤。这些学田,分布于乡村和城内、城郊,包括了溪坂、滩涂、房基地、店铺及水田等等(见清乾隆《宁德县志》1983年版,第315页到320页。)。直到民国三十年(1941),当时县政府还以“催缴儒学兴贤租谷”的名义,动员公权力,派兵丁前往漳湾马山等地,催缴历年所欠租谷157担(蕉城区档案馆藏档案,编号:2-3-727。)。在今南门下宅园村附近,曾有围垦的“圣人塘”一处,相传这片田产的收入,就属于当时的官学所有,故此称为“圣人”的产业。
在古代社会,一些较大的宫庙寺观普遍拥有“香灯田”,祠堂则有“油灯田”和学田。如清代县志所载“城隍庙”一项中,有“香灯田:后溪村施洋了尾五斗,后溪村施洋北斗头四斗,共九斗”,周墩(今周宁县城)城隍庙“乡民周活七捐香灯田一石二斗”。还有“忠烈王庙”(即土主宫)“现存香灯田……以上共田一石零八升五合……”。类似的记载,还有“忠烈行祠”、东平王庙(民间称“新塘宫”,祀张巡、雷万春等,在今人民影院附近)、武庙(已废,址在今蕉城三小附近)、天后庙(即妈祖庙,今存,在东湖市场附近)、“报德祠”(原址在今城隍庙附近)(见清乾隆《宁德县志》1983年版,第133页到150页。)等等。这些载入县志的宫庙,多以官方名义给予祭祀,其田产,自然属于“官产”。如果考虑到学田规模的稳定性,这些官产,在民国时期,应当仍然归于县政府收入。
如前所述,部分寺庙所拥有的田产收入,在兴学的全国性浪潮之中用于办学,宁德县也不例外。但这其中的产权关系极为复杂,也不是所有的庙产收入都被运用于兴办学校。民国时期,庙产的多寡是十分悬殊的。大的寺庙,如支提寺、龟山寺、漈山寺等,有着大片的田产,而有的寺庙近于圯废,僧人毫无收入,生活甚至几近乞丐。进入四十年代后,一些管理有效的寺庙的田产,也得到了法律和宗教高层的保护。
登记造册
宁德县民国时期公产的确认,除了上述之使用、管理与出租之外,还对一些建筑进行登记造册,以此来明晰“公产”的产权。
1936年6月,福建省第一行政督察公署下达训令,要求宁德县长负责“先哲先烈祠庙财产”的保护与管理(馆藏档案,编号:2-3-663。)。这是一次全国性的登记造册行动,其法源在于民国政府内政部所颁布的《先哲先烈祠庙财产管理规定》。登记造册过程同时下发《概况登记报告表》。报告表包括应登记的祠庙的名称、地址、建立年代、公建或募建、先哲先烈事略,以及包括动产与不动产在内的财产评估、存款、事业基金等等。
从1936年6月开始,登记活动历时年余。在这份档案中,保留了三十年代末期宁德县一些祠庙的概况。
登记在册的祠庙,包括周宁城关的文昌阁、三都的吕祖庙、城关祭祀历史上的贤令林时芳、韩绍、汪大润的“遗爱祠”、北门关帝庙、周墩武圣庙等等。
如孔庙一项。其内容如下:
“先哲孔庙,南门内,道光二十年,蔡志谅捐资鼎建,大成宝殿一座,东西庑各一间,五代祠一座。占地五亩有奇,有牌位,现充模范小学使用。”在登记内容中,还写明文庙的部分公产,“东门外三叉港,蛏埕租,年小洋三百角,由民□□,前县长拨为修庙之用,近年已降价,仅收十余元”。
这一年年底,福建省政府重又发文对此次登记造册进行指导。说明“文昌阁”不算“先哲先烈”,天后宫改为“林孝女祠”,同时告知孔庙另外登记,并要求写清有关祠庙的“事迹”,等等。此次发文,还要求将各祠庙的年收益、年拨祭礼经费数、有无僧道管理及年拨生活费、已否举行办何种事业或改作其他用途及改变现状,保管或借用于祠庙处理改善意见(可否做学校校舍)等事项列入造册,相当慎重其事。嗣后,宁德县又将天后宫、南门武圣庙、遗爱祠、广泽尊王庙、灵杰候王庙等或重新列入,或充实其原先所登记的内容。
如城关南门武圣庙。这座庙在南门的校场边,其原址大体上在今蕉城三小东侧。这座庙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占地面积一亩半。三十年代时,仅余有正殿一座,其他的已倾圯。初次上报时,这座庙没有列入造册,后宁德县将此庙列入。
今天,南门武圣庙、西门戚公祠、东门外广泽尊王庙等已荡然无存。“戚少保祠,西门观音阁下,建于前清初年,公建,深二丈八尺,阔一丈一尺,”三十年代时,今继光街五显宫前,还有这样一座建筑,如今原址于何处,已令人费解了。而广泽尊王庙,在当时记载“现为东门外镇第二短期小学”,后来,因1953年一场大火,烧为平地。
三十年代时,还有一些尽管已列入登记造册,但这部分公共建筑并未使用于公共目的,或者至少政府并未对其行使有效的管理。如“北门”武圣庙,此时就是私人管理,由一马姓人员“向官产处投标,承买安置物件仍祀关帝”。
以上四种方式,或不能全面概括当时“公产”的管理与权属状况,但大体上反映了民国时期数量有限的公产使用与管理的一些现象。
“公产”的复杂背景——公权、法律、舆论与传统
民国时期的几份涉及“公产”使用或纠纷的馆藏档案,折射出这些公产背后十分复杂的社会关系,进而透露出不少相当有趣的时代气息与特定的历史氛围。
民国时期国家(政府)对公产的强势支配力
档案编号为12-3-1的地籍图产生的时候,已进入四十年代。从清末、民国初年、三十年代以来,随着新政的发展、现代国家机构的增加,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政府、执政党及一些公共团体大量地使用了原本属于宗教、宗族所占有及管理的宫、庙及宗祠。在这份地籍图中,有不少宫庙祠等建筑,已被直接标上了某单位或学校的名称,其原来的名字已经消失了。这表明,这部分建筑的宗教或宗族性功能已淡化或丧失,宗教或宗族性质的“公产”,已变易为“官产”。
如上文所述之溪流坑的“忠烈王庙”及“三民路”的蔡氏祠堂,此时直接注明“社会服务处”与“三民国民学校”。前述之三十年代尚登记在册的南门武圣庙,此时已不见踪影,成为“公共体育场(此图籍中另有一处公产为“公共体育场办公处”,位置约在今蕉城三小处,或为武圣庙址。)”的一部分了,说明这部分的“公产”,已经完全地变易为“官产”。
这份图籍上还有一些仍然标明着某姓宗祠的地点,但这时事实上已成为政府机构。蔡氏家庙、龚氏祠堂、陈氏祠堂等虽然仍以旧名,但实际上已经分别是县警察局、“民众教育馆”和三青团服务社了。但既注明原来的名称,很可能此时该宗族性公产仍未全部丧失其功能。也就是说,祠堂中的牌位等或许仍然保留着,呈现出使用和管理的过渡状况。
这涉及民国时期人们对“公产”的理解。
如前所述,如果仅就“公共的目的”以及“公用”这两个方面来看,无论是社会团体(宗教或宗族,或以“境”为代表的社区)使用与管理的财产,还是以国家与执政党(政府、国民党、三青团等)名义使用与管理的财产,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均可认定为“公产”。二者界限在民众的认识中,可能是相当模糊的。也就是说,所谓的“公产”,在当时,其实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今日之“行政公产”概念,自然不能概括“公产”之义,应当仅仅是“官产”。
从上述之宗祠、宫庙较多成为政府机关、公共设施、学校的现象看,当时,公权力对“公产”的占有与管理过程中,具有支配性的作用。尽管现在不清楚一些宫、庙或宗祠成为政府机关或官办机构,是否通过了赎买等程序,但在自清末新政,特别是“兴学”浪潮以来,在以法律的名义以及在倡导“进步文明”和“破除迷信”的社会舆论之下,社区性的公产,显然极易成为国家(政府)的财产。
国家公权力对公产的支配性质,还表现为以公权力收取公产收益,如派兵征学租。馆藏档案《催追儒学兴贤租谷卷》中有一份名册,列出欠了“学租”的佃户的名字及欠租数量、收据,税单若干份。在这份案卷中,还包括了县长“熊”(蕉城档案馆档案编号:2-3-723。“县长熊”的手令内容是:“…….前往马山等乡,清收三十年份兴贤祠租谷,以就近交由集兴米厂负责人收据报销,随带队兵二人……限于二十日前清收具报…….”)手札一封及后一任县长钟干丞(1942年2月至1942年12月任宁德县县长。见《宁德文史资料第五辑》150页。)继续追讨“学租”的批示。
卷中所列“欠租”的佃户,分布于六都乡、七都乡、郑歧乡、南埕乡、马山乡、“林家施”等地,计约20多人,数量分别在一二百斤到2666斤之间,总计为157担72斤半。
租种学田的佃户们,面对在承租学租的中介人(米厂负责人)追租时,或因实际困难而拖延,但在公权力面前,佃户们恐无拒交的决心与能力。这份档案,以今之观点来看,或可解释为反动政府欺压百姓的一个实例,但是,民众似乎对交纳这种属于公产的租金也尽力为之。马山乡欠租的佃户林文添,在交付一定的租谷之后,还向政府打报告,请求“俟明年早稻登场补还无法交清的谷子”。显然,这一户农民实际上已是将当年的收成尽囊而出。这一方面体现出国家(政府)维护“公产”的强制力,同时也透露出部分民众对官产应尽义务的一些认识。
民国时期法律对公产的规定与调整
在民国时期,对官产、公产法律涵义的界定,散见于各类法律文件之中。前文提到的《整理及调查官公产卷》中“蓝田渡船管理人陈细耳”的文本,即引用《土地法》、《处分官产暂行条例》、《公款公产整理纲要》三份法律的具体条文,来支持自己的主张:
……查《土地法》第八条规定“左列土地不得为私有:(一)可通运之水道;(二)天然形成之湖泽而为公共需用者;……(六)公共需用之水坞”。又第十二条规定:“凡未经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权之地,为公有土地。”又本省《处分官产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官产之种类如左:……(二)官有洲田、海滩、湖荡及水坞”。又本省各县区《公款公产整理纲要》第二条,第九款已指明,“其他公有之款产为公款公产”。
此外,较多的宫庙及寺产成为“官产”,也与民国时期出台的各类法律文件有关,并非宁德县一地的现象。而这些法律文件的出现,则与“破除迷信”的时代潮流有关,
清末“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兴学”,到了民国时期,特别是北伐前后,各地打倒宗教,没收庙产的事件十分普遍。当时,国民政府力图实践“三民主义”的蓝图,强调“改移不良之习俗,实行训导民众,趋于日新之生命”,要“破除中国人的种种迷信”(转引自付海晏《革命、法律与庙产》,2009年3期《历史研究》)。民国成立之后,政府在管理寺庙方面,有不少的法规和政策,如1913年曾颁布《管理寺庙暂行规则》、1921年颁布《修正管理寺庙条例》,1928年颁布《寺庙登记条例》、《神祠存废标准》、《废除卜筮星相巫觋堪舆办法》,1929年颁布《取缔经营迷信物品办法》。此后,还颁布了《寺庙管理办法》,《监督寺庙条例》等等。在一些学者看来,这些法规的出现,体现了国民政府巩固清代“庙产兴学”以来将地方寺庙财产监管权由地方庙首、会首手中,逐渐转移到近现代国家以及依附于国家之地方自治团体的努力,并且作为一种制度在整个民国时期长期延续下来(同上。)。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必然产生关于“公产”的复杂的法律关系。民国档案中,有一些涉及“公产”的司法文本,提供了一些有趣的历史氛围。
试举若干档案。
“龟漈寺”的田产招标档案。名称为《各商民申请承包龟漈寺租》,馆藏编号为:2-3-708。时间为民国三十年(1941)。
这份档案的主要内容,是一些“商民”,向当时的县政府申请承包来年的龟漈寺等寺观的田产收入。这些寺庙包括“龟漈寺”、“仓王爷”、“戚公祠”、“威灵公”等六家,合计产租480担,其中又以“龟漈寺”为最多,达150担。在1941年,申请承包者有13人。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原承包者李成坤承包额的基础上,进行兑标,向当时的县长“熊(熊方)”申请。申请人范围分布在宁德县的八都、城关等地。
二十九年承包者李成坤的承包额为500元(应为法币),但次年申请承包者大都增加承包金300元以上。并且,在申请书中提出了一些相当有趣的理由。
如“登仁保14甲”的林福民,申请理由是:“窃以抗战时期国家经济亟宜整理,吾邑教费支绌濒于极点,民属国民分子,应为国效劳,冀得稍尽天职……钧府有儒学一项,前由…….领办,年认缴500元,……愿在原额上增加200元。”
还有郑、王两位承包者,提出以450元承包,但其另有有利条件,即掌握着“公产”的原始契约。承包者指出,“钧府(县政府)”的“年租因为无底册,由人领办缴课,还是权宜之计,于法终究欠完善,”然后提出,他们所认识的王、陈两人,愿将底册交出,条件是“请求委办(承包)”。申请书中还提到:“固不论其真确与否,然往年之无所稽考,听人把持操纵之弊,则有所廓清,政府既有藉依,自能逐渐整顿,冀免日久埋漫之虞”。但是,县长“熊”(即熊方,1939年12月至1942年2月任宁德县县长。见《宁德文史资料》第五辑,150页。)不吃这一套,批复中指出,先将原始契约交到政府手中再议。民众与政府皆以法为工具进行博弈心态,可见一斑。
从以上的案例大体可知。一,这些公产权益的处置,主要通过法制的渠道来处理;这些田产属于“教费”所用;二,这些公产的产权并不十分清晰。表现为:政府并未完全掌握这些“公产”的原始凭证,民间认可公权力对这部分田产的所有权和管理权;三、国家(政府)对这部分“公产”的管理相当粗糙。表现为:对应得租金失于控制,很显然曾被原有承包者占了很长时间的便宜,并且,还是通过中介人来管理相关。四、政府所控制的“田产”份额并不大。当时,全县范围内有寺庙百多所,县政府直接掌握的田租收入,一年只有数百担(除文庙田产之外)而已。
至于“龟漈寺”为何有如此之多“公产”?庙产为何大规模地转移到国家(政府)手中?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有趣问题。龟山寺在民国二十五年(1934)曾遭遇战火,寺庙部分被毁(见1997年版《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第8页。),可能与此有关。
处理涉及“公产”纠纷的案件。在编号为2-3-742的《处理寺产案卷》有不少案例。
内中有一份学校与寺僧的田产纠纷案。1942年,赤溪乡中心小学的校长傅洪琼及校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杨忠帮,曾向县政府报告,民国二十四年(1935),广教寺住持僧曾向校基金“资助”租田四千觔(“觔”,同“斤”。),“历管无异”。到了三十一年(1942),新的住持提出学校侵占其田产,并且上告至佛教协会发函交涉,并诉至县司法局,引起一次法律的诉讼。这两位学校负责人称广教寺僧“向司法处起诉,蒙票传质讯,但过去情形恐未详细,务恳将本案全卷转司法处察核以资审讯。”
同一卷中,还有一份“侵占寺产”的人员名录,范围涉及城关、漳湾、霍童、七都、金涵、八都等地,数量多达几十人。卷宗中还包括这些“案”的处理意见,调查过程以及佛教协会的要求政府进行调查干预的函,等等(作者注:从其内容来看,这些庙产并不一定是“公产”,更可能是因时代变迁,庙产的产权产生模糊,因此产生了身为地主的僧人与佃户之间的争纷。)
在三十年代,宁德县政府曾经对“神产”进行大规模的登记,其目的显然是通过这样的途径掌握原先在政府控制之外的“公产”。这种登记,在法律的体系内进行,一旦产生纠纷,则进入司法渠道。
有一份档案,记载了西山保第二甲马懋添向县长陈情,认为民国三十六年(1947)登记神产时,误将其购于1937年位于“五都东楼”的一亩地,记为神产,因此产生了与一位吴姓人士的纠纷。另外还有一份关于张、许、郑、谢四人因“五都溪口”的一块田地被登记为神产,要求县长解决的呈文。
从已查的档案看,不清楚司法结果如何。但是蕉城区档案馆中民国时期司法类的档案十分丰富,研究者或可从中揭示更为详细与准确的历史信息。
政党、社会舆论及民间力量的作用
如上所述,民国时期“破除迷信”成为社会潮流,甚至中医、农历等传统中华文化的载体也被视为落后的事物,有的还以法令的形式加以限制、废除。
在这种社会舆论和时代气氛中,一些政党机关,社会团体以革命与文明的名义使用公产,对“落后”、“迷信”的民间旧势力,有着强烈的排他性。他们在使用一些宫庙、宗祠当做办公地点时,只要提出一些简单理由,直接向政府行文申请,无需与原来的管理者——社区性团体交涉。有的则干脆直接占用原有的公产。如文庙的考院(今人民影院址)成为党部、城隍庙成为三青团办公地点等等,都说明这一点。
现档案中保存着一份三青团写给县政府的“请拨城隍庙为本团永久团址”的呈文。在此之后,还有一份三青团向县政府具文要求占用“溪面”与“成德境”神庙为印刷社地址的报告(三青团原在城隍庙,后迁到陈氏祠堂(宁德城关内,民国时期有多座“陈氏祠堂”和一座“陈氏众厅”。据宁德县原文化馆工作过的陈继佑先生介绍,这座祠堂为宁德城区“埠头陈”之宗祠,其原址在东门兜北侧约四五十米的环城路边,其西侧有“成德境”神庙,门前为护城河。解放后曾充为文化馆、电业所,九十年代初,建城区内首家歌舞厅(酒店)“华福泉”,今已成为“莱茵城”之一部分。)),函称,“为发展业务起见,拟设立宁德青年服务印刷所中正室(图书室)报告各一所,除将现有之陈氏祠堂作为服务社址外,拟请口成德境庙舍及陈氏祠对面溪面口口归本处口修建应用,希转内政部备考….”
馆藏档案中,还见过一份某医院医师向县政府要求将妈祖庙的一部分充为诊所的文本。
从这些档案中,可体味到民国时期不但教育事业“理所当然”地使用公产,以“革命”与“进步”自居的执政党和以现代文明为标志的西式医学,对“公产”建筑的占有,也是相当强势的。
这种形势自然与清末民国初“庙产兴学”的全国性潮流以及国民政府所奉行的政策有关,但在国家(政府)、执政党组织及社会团体占用庙产以及其他宗教性的建筑、产业的过程中,民间及原有的宗族宗教团体,并非对政府机关与政党团体使用公产没有非议,有的以各种方式来干预,或借助上层宗教力量来影响舆论与司法。
前述“寺产纠纷”的官司,曾打到省里。中国佛教会福建分办事处负责人圆瑛曾致函给省政府,“近有地方一二土劣,违反法令,乘机驱僧夺产”,“请转饬各佃户归还寺产”,1942年,以省长刘建绪的名义,颁布78457号布告,称“查信教自由,载在政纲,保护寺产,法有专文”,要求地方政府对侵害寺产的情况,依法追究(蕉城区档案馆档案《处理寺产卷》,编号:2-3-742。)。
在庙产兴学及民国政府对庙产、神产的控制过程中,宗教团体、宗族团体及民众也采取了一些保护其原有利益的行动。
民国二十四年(1935),宁德乡绅蔡汝梅(四十年代末为商会会长,宁德县参议会议员)、陈有昌、左志儒三人向县政府呈文,要求政府出示公告,对南门关庙加以保护。呈文描述:“南门外较场边武圣庙,供奉壮缪关夫子,为汉族之英雄,作军人之模范,一心忠义,万姓钦荣……数年间,因乏人管理,被一般刁民将拉杂渔具任意堆塞,并引起流丐杂居其中,遂使栋折墙颓,荒秽不堪。”接着呈文称:“…..董事等为保存古迹,提倡尚武…..发起募修庙宇,再整金容,略告完成,藉资瞻仰……”,最后,呈文要求县长“出示禁止堆积及杂居流丐,以资保护”。次年,政府登记“先哲先烈祠庙”中,将这座关庙列入造册,并在现状中指出:此庙“前清由绿营管理,光绪间绿营撤,祭祀废,去年由乐善社募修,暂归其管理”。这种“暂归管理”也不长久,大约在四十年代,这座建筑被政府拆毁,成为“公共体育场”的一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传统旧例是确认产权的重要因素,民间因此也有了与国家、政党及强势的社会团体博弈的机会。从档案中披露的情况看,民国时期一些“公产”的原始契约或许是不完整的,如档案《承租龟漈寺等学租卷》中表明,有人就掌握着政府未曾掌握的田产契约。三十年代民国政府对祠庙等进行登记造册的活动,也包涵着建立原始档案的用意。至于这些神宫庙祠的法律文本凭据最终确立,已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情了。
掌握契约或原始凭证,是民众有力的工具。在个别案件中,有的因为原始契约残失,导致产权争议,最终政府部门引入了最为原始的证据。《处理寺产卷》中,有一份有趣的文本,《抄录清乾隆十七年圆明寺碑文》。抄录这份碑文的目的,在于理清漳湾乡数位村民与圆明寺僧之间的田产纠纷。原始碑文以宁德县令“本府正堂加三级”的名义,不厌其烦地从宋代大儒杨复(信斋)事迹说起,叙述后人捐田俸产,先为祭田,明代时寺田归公而致田产或为先儒祭田或为寺产“尚未分晰”的过程,后来又提到清代时杨家后人争产的情况等等,说明保护庙产的理由。时隔百余年,到了民国三十一年(1942),宁德县政府部门为解决这些田产纠纷,又郑重其事地抄录“前清”的原始凭据。从这件事情来看,民国时期,久存于民间的习惯、旧俗以及一些传统做法,应当对政府使用与管理“公产”的过程,对民国政府试图将寺庙财产纳入法制化监管体系的建设目标(引自付海晏《革命、法律与庙产》,2009年第三期《历史研究》),有着一定的约束与制约。
“公产”的法律内涵十分复杂,不同国别,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释义。民国时期,何处财产属于“公产”在当时就有不少争议(如蓝田渡口一案)。以今人的观点看那个时期的“公产”,在法理上更是难做清晰的界定。因此,本文所提供的史料,只是对宁德县民国时期一些现象、一种氛围、一些惯例的间接反映与简略介绍,供读者参考。本文所涉及的“公产”,其保存状况及其权属,亦多有变化。文中的陈述与观点,只是个人看法,不足引为法律凭据。兼受资料和水平的限制,文中或有观点含混、法律用语未能精当、引用材料及分析错误、疏漏之处,望有识者纠正。
本文在薛赞平、姜翔骅、黄澍等同志帮助下写成。在此一并致谢。
相关人物
甘峰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