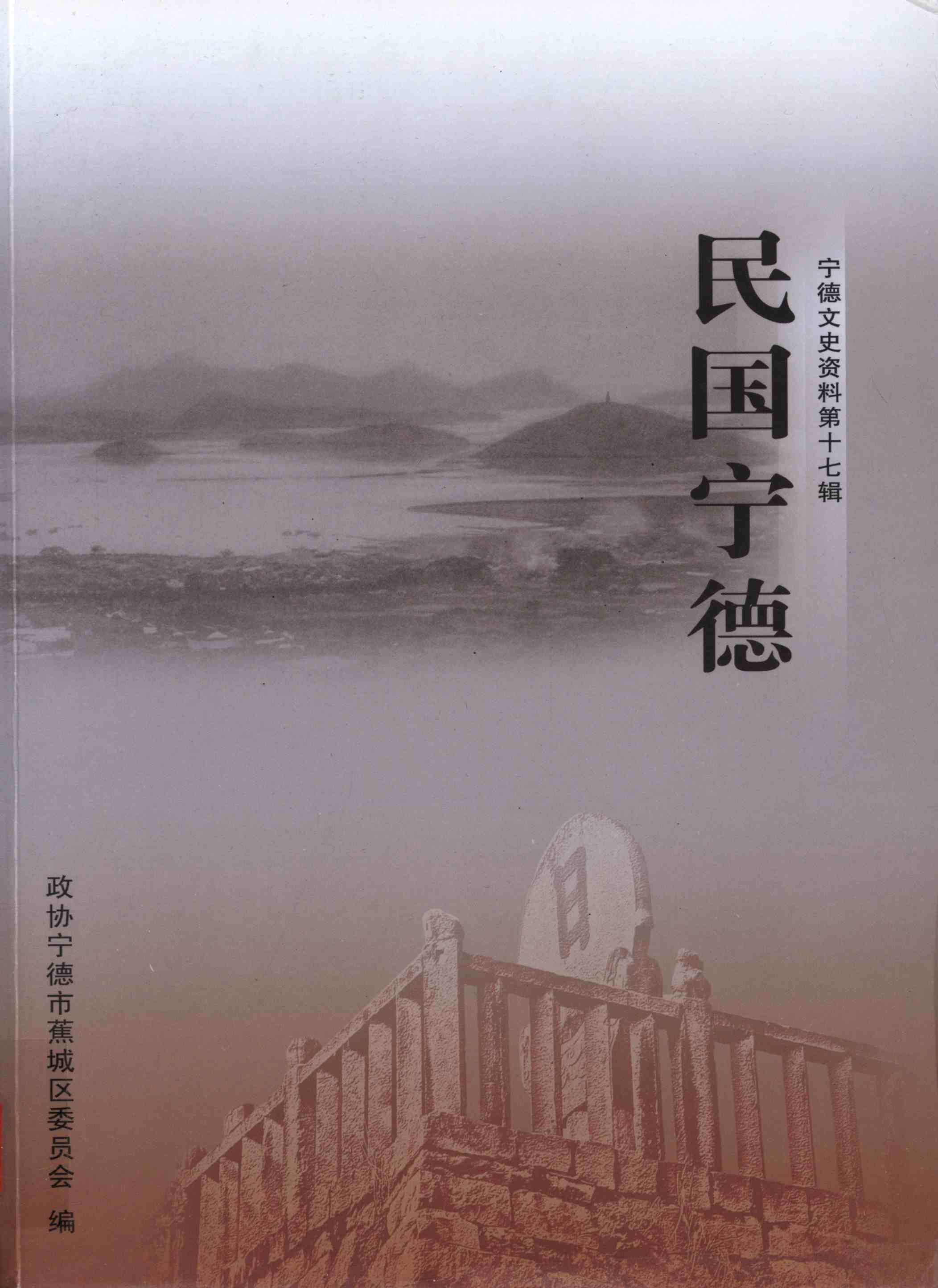内容
宁德县始设于公元933年,除了1000年析出关隶镇(今政和县)外,境域大体稳定,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民国二十四年(1935)5月,析出周墩区(今周宁县狮城、浦源、李墩、礼门、七步一带,面积约639.6平方公里)为特种区,直属省第一行政督察区(公署驻长乐),后曾划回宁德将近一年时间。三十七年9月,又析出咸杉乡(今周宁咸村镇和玛坑乡,面积约127.7平方公里)。根据民国十九年续修《宁德县志》抄本的记载,当时全县陆域,东西约142里,南北约169里,周长600里。粗略说来,民国时期宁德县的最大面积,要比今天的蕉城区大了760多平方公里。另一个显著的不同,县城东面濒海,与潮水相接,邻近虽也有一些围垦成田,但规模都小,大的也才二、三百亩,潮来碧波弥望,舟、岛点点,潮去滩涂辽阔,港汊纵横。那时候的“城关”面积还不及2平方公里,比起60年代建成金马海堤以后的城区陆地面积要小得多。另外,民国时期宁德县的自然环境,不论山海江河,都比今天要“自然”得多,野生动植物资源也丰富得多,例如,处在生物链高端的第三级食肉者华南虎、金钱豹、狼等凶兽,现在已经绝迹。
明清两朝分全县为三乡七里二十五都,民国初年沿用旧制,九年(1920)三乡(含周墩)合计近5万户,24万人,这是民国时期宁德人口之峰值。十七年改乡为区,区下设村,次年统计全县4.4万户,20万人,人口数下降,可能与社会比较动乱有一定关系。二十三年5月,设城关、霍童、洋中、三都和周墩五个区,并实行保甲制度,这本当有利于落实人口数据,但次年统计全县约3.3万户,23.9万人,如果说户数比6年前减少一万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周墩脱离县辖,那么,户数减少四分之一,人口数反增将近五分之一,则难以给出合理解释。三十二年撤销区署,只设14个乡(镇),三十七年咸杉乡划归周宁县,保留蕉城、漳南(漳湾)、八都、霍童等四镇和濂坑(金涵)、七都、赤溪、洋中、溪源(洋中石后的一部分)、上西乡(虎贝)、飞鸾、碗城(三都飞鸾的一部分)、三都等九乡。据宁德户籍档案,民国三十二至三十六年平均户数约为3.2万,人口数将近17.8万;三十七年随咸杉乡同时划出10125人。
宁德县的居民,部分人群中应当遗传有古代闽族、越族或闽越族的血缘基因,但难以详究,通常都标榜自己是中原名门之后,属于正宗汉族,主要姓氏有蔡、郑、林、黄、陈、张、薛、马、崔、龚、周、余、姚、彭、阮、刘、叶、吴、王、李、谢、孙、萧等等。民国时期这里的少数族群,主要是畲族和疍民。畲民大致从明中叶开始迁入,在偏僻山区落脚,清代逐渐向沿海发展,有的还到岛上定居。民国时的畲村布局,仍保持散居而相对集中在三大片:八都猴盾村连至九都九仙村,七都漈头村连至金涵乡,飞鸾马山村连至南山村。据民国档案,二十六年(1937)第一区(城关区)和第二区(霍童区)有蓝、雷、钟三姓畲族1600户4800人,当时的宁德共有三区,上述第一片属霍童区,第二、三片属城关区,都在沿海、沿江地带。所以这个人口数据并不完全,况且那个时代还没有进行系统的民族识别,实际上畲民当远不止此数。疍民的来源,目前尚无定论,一般以为是当地古越人的遗类。他们水性好,善行舟,以船为家,从事渔业和运输,似仍保留些许古闽越族的体质特征。疍民生活在沿海、溪河水域,长期受陆上汉人和官府的欺凌。中华民国政府立法禁止歧视疍民,渐有疍民上岸居住,大规模的“连家船改造”则要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东南各省的疍民曾一度被视为一个少数民族,1955年民族识别调查后,官方最后认定它是汉族的一部分。但一些学人关于畲疍同源的意见,至今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辛亥革命的发生和中华民国的成立,大大加快了全国包括宁德县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这个转型虽不彻底,却很多方面。表现在政治方面,例如,民国元年(1912),福建都督府委任王国瑞为宁德县知事,周墩、三都两个特种区各配县佐,并设立县、区两级议会;七年,奉令成立参、众两院初选事务所,官、民开始缓慢接触、学习和实践从西方刚刚舶来的选举制度。十七年开始实行《县组织法》,尝试以法条规范县政。三十二年
成立县临时参议会,次年由县府主持,以职业团体和乡镇为单位,选举产生40名参议员,组成正式参议会,县府部门公务员不得兼任。参议会制定有工作章程、会议制度,参议员按程序提出和讨论议案。与此同时,民主革命斗争也逐渐在民间铺开,郑长璋、蔡泽鏛就是早期斗争的杰出代表,后来叶飞、曾志等人也到宁德进行革命活动,农会、渔会、妇女会、盐工协会等组织风行一时,影响深入农村底层草根。他们已不单纯是传统时代的反对官府,而程度不等地包含了向往民主社会的新诉求。
民国时期宁德县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也表现在经济方面,例如,民国元年(1912)三都澳总局和宁德县二等邮局增办商务传单业务。次年,三都分防委员会发布《三都商埠外国人租地章程十八条》。华兴瑞记矿业公司注册成立。三年,中国银行三都澳分行成立。四年,省下发各县通行货币种类表(宁德银币、铜币和纸钞计11种)。1916年发生了三件今日看来颇为意味深长的事:1月,因税重挫伤制碗业,官府呈文省署申请减轻碗窑粗瓷税率;4月,万顺春等人贩茶遭劫,三都海军陆战队五旅受命驻兵宁德保护茶商;8月,闽海道官产处委员林宗远假借公务勒索扰民,被八都商民联名控告,解交省法庭查办。这说明当时带有若干现代经济色彩的工厂主和商人的力量已有一定成长,社会地位渐渐重要起来了。此后,工商业继续发展,渐渐形成略具影响的茶叶、棉布、京果(亦称南京店)和医药市场,“德顺鱼行”承包渔税,垄断一方,酿酒业、制碗业等也有所发展,各业在日寇轰炸、攻陷三都前夕最臻繁盛。但总的说来,速度不快,规模有限,直到1949年春,全县城乡登记小厂、作坊不满六十家,注册资金不过一千数百万元(国币);1950年城乡私营商业八百多家,从业者一千数百人,资金不到二十七万元(旧币)。
民国时期宁德县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还表现在文化方面。例如,在宣传媒介上,30—40年代国民党宁德县党部先后创办了《宁德民报》和《闽东日报》,抗战中县抗敌后援会创办了《宁德导报》;同一年代,县民众教育馆主持放映一些无声电影。
再如,在医疗设施上,民国十年(1921)洋中人阮琼珠接掌圣教妇幼医院,大力拓展西医项目,逐步把它改造成为综合性的医院(永生医院);二十四年,成立县卫生院,其后又陆续成立三都、霍童、洋中卫生所(二十九年改卫生分院);周墩区卫生院于二十七年成立,其时已不归县管。
卫生院、所初设,除永生医院稍具规模,余者都很简陋,但毕竟使西医西药渐得普及。
再如,在学校教育上,清末,县里随着外国传教士首先办起洋学堂,县立莲峰高等小学堂、霍童兴文小学堂和邑人林廷伸办的碧山小学堂等几所新式分科教学机构也渐次成立,旧学已受到不小的冲击。民国元年(1912),学堂改称学校,改莲峰小学堂为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三都小学堂为第二高等小学。至次年,全县共有小学27所,在校生近千人。四年,初等小学改称国民学校,县城5所,各乡31所(包括东洋里即后来的周墩区4所:周墩,浦源,端源,萌源)。八年,郑丹诚等在浦源、周墩创办县立第三高等小学。二十二年,省立霞浦初级中学(省立第三中学)迁三都,成为宁德县第一所现代普通中学。二十五年,政府推行“全民教育”。二十九年,成立县初级中学;政府提出一乡办一所中心小学,学制6年,一保办一所国民学校,学制4年。咸杉乡及当地4所学校划归周宁后,三十八年全县有公立小学49所,私立小学1所,在校生近四千人,中学2所,在校生近七百人。虽然入学率还很低,但现代学校体制已完全确立。
再如,在宗教活动上,道教源流久远,但明代以来日渐衰微,民国时期道观寥寥无几,且绝大多数被改作寺庵。佛教传入的历史同样很悠长,发展缓慢,民国时期留存寺院庵堂约70所,抗战中比较活跃,民国三十六年(1947),成立了县佛教协会,寺院之间的联络、协调有所加强。其实,民众对真正的佛教、道教相当隔膜。平常百姓信仰驳杂,崇拜对象五花八门,遇事热衷于算命、看相、求签、卜卦、扶乩、还愿等等,往往辗转出入于多种民间信仰服务者之门。十二年,县府颁令禁止迎神赛会,这是全国从上到下一致的政治导向,实际成效则很难持久。天主教从明末开始传入,民国时有本堂5处,分别在城关北门外、城南岐头村、漳湾瓜园村、飞鸾岚口村和三都松岐村;还有行教堂8处和一个行教公所,也都在滨海各村。基督教从晚清传入,宁德县主要有圣公会、安息日会和聚会处三个教派,十几个教堂,以分布在城关、金涵、飞鸾、三都、漳湾、七都、八都等沿海地带为主,并延伸到霍童、洋中(含石后)的山区,周墩除沿用光绪年旧教堂做礼拜,民国十二年又续建一幢土木结构的牧师房。当时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数量很少,但与传统文化冲突不少。这种冲突多会受到小地方“熟人社会”温馨人际关系的浸润而软化,但真正处理好所谓全球化漫长历程中的中西文化关系,自然还有待于更长历史时期的探索和实践。
与全国一样,民国时期宁德的社会转型,不可能是一个匀质性的变化过程,其中充满诸多种类的不平衡发展。从地理空间角度观察,东南滨海地带与西北山区差异巨大,三都澳通关后对工商业和农副产品贸易的直接拉动,西学包括宗教和科技的广泛影响,都明显呈现由沿海向内陆逐级辐射之态势。从社会空间角度观察,城关、郊区、乡镇、村寮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高下悬殊,县一级的代议机构、党部、商会、银行、图书馆、民众教育馆、诗社等等都在城关,医院、学校也相对集中分布在城区周遭。那里的社会风气比起偏远的山村无疑要合乎时尚得多。从社会分层的角度观察,精英人物和一般民众在社会转型中的表现也会有很大不同。民众虽是推动社会转型的基座性的力量,但通常是隐形的、深层次的,需要在长时段中才能真切感受到。精英阶层的活动比较外显,如,黄树荣在南北对峙中之所谓斡旋时局,郑长璋、蔡泽鏛、阮元皋等人之筹建国民党宁德县党部,林振翰之努力促进中国盐政现代化,石磊之筹办中央计政学院等等,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但在宁德这样的小县,恐怕有更多地方精英当年的具体行事,今日已难见多少痕迹了。
与全国一样,民国时期宁德的社会转型至少存在二大问题。一是没有解决阶级对立阶级剥削,二是在抗日战争以还遭受巨大挫折。这些前人述之已详,文中未再强调。关于早期现代化或早期全球化的发轫,诚如牛津大学的拉纳·米特(RanaMitter)博士所指出,民国时代的重要性可能被低估和误解了。放宽历史视界,自清末到民国再到今日,也可以看作是走向现代社会的一个连续过程。本文仅从这条线索勾粘旧物往事,自然远不能算作全面的评价。好在读者诸君手中早有辩证法的锐利武器,可以批判分析。民国时期宁德社会实际状况,具有十分复杂的面相,系统的研究,目前还没有起步,需要爬梳大量档案资料,访问众多耆宿乡贤,参考已有相关成果,才能有真正的初步收获。上述文字,充其量只是抛砖引玉而已。
明清两朝分全县为三乡七里二十五都,民国初年沿用旧制,九年(1920)三乡(含周墩)合计近5万户,24万人,这是民国时期宁德人口之峰值。十七年改乡为区,区下设村,次年统计全县4.4万户,20万人,人口数下降,可能与社会比较动乱有一定关系。二十三年5月,设城关、霍童、洋中、三都和周墩五个区,并实行保甲制度,这本当有利于落实人口数据,但次年统计全县约3.3万户,23.9万人,如果说户数比6年前减少一万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周墩脱离县辖,那么,户数减少四分之一,人口数反增将近五分之一,则难以给出合理解释。三十二年撤销区署,只设14个乡(镇),三十七年咸杉乡划归周宁县,保留蕉城、漳南(漳湾)、八都、霍童等四镇和濂坑(金涵)、七都、赤溪、洋中、溪源(洋中石后的一部分)、上西乡(虎贝)、飞鸾、碗城(三都飞鸾的一部分)、三都等九乡。据宁德户籍档案,民国三十二至三十六年平均户数约为3.2万,人口数将近17.8万;三十七年随咸杉乡同时划出10125人。
宁德县的居民,部分人群中应当遗传有古代闽族、越族或闽越族的血缘基因,但难以详究,通常都标榜自己是中原名门之后,属于正宗汉族,主要姓氏有蔡、郑、林、黄、陈、张、薛、马、崔、龚、周、余、姚、彭、阮、刘、叶、吴、王、李、谢、孙、萧等等。民国时期这里的少数族群,主要是畲族和疍民。畲民大致从明中叶开始迁入,在偏僻山区落脚,清代逐渐向沿海发展,有的还到岛上定居。民国时的畲村布局,仍保持散居而相对集中在三大片:八都猴盾村连至九都九仙村,七都漈头村连至金涵乡,飞鸾马山村连至南山村。据民国档案,二十六年(1937)第一区(城关区)和第二区(霍童区)有蓝、雷、钟三姓畲族1600户4800人,当时的宁德共有三区,上述第一片属霍童区,第二、三片属城关区,都在沿海、沿江地带。所以这个人口数据并不完全,况且那个时代还没有进行系统的民族识别,实际上畲民当远不止此数。疍民的来源,目前尚无定论,一般以为是当地古越人的遗类。他们水性好,善行舟,以船为家,从事渔业和运输,似仍保留些许古闽越族的体质特征。疍民生活在沿海、溪河水域,长期受陆上汉人和官府的欺凌。中华民国政府立法禁止歧视疍民,渐有疍民上岸居住,大规模的“连家船改造”则要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东南各省的疍民曾一度被视为一个少数民族,1955年民族识别调查后,官方最后认定它是汉族的一部分。但一些学人关于畲疍同源的意见,至今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辛亥革命的发生和中华民国的成立,大大加快了全国包括宁德县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这个转型虽不彻底,却很多方面。表现在政治方面,例如,民国元年(1912),福建都督府委任王国瑞为宁德县知事,周墩、三都两个特种区各配县佐,并设立县、区两级议会;七年,奉令成立参、众两院初选事务所,官、民开始缓慢接触、学习和实践从西方刚刚舶来的选举制度。十七年开始实行《县组织法》,尝试以法条规范县政。三十二年
成立县临时参议会,次年由县府主持,以职业团体和乡镇为单位,选举产生40名参议员,组成正式参议会,县府部门公务员不得兼任。参议会制定有工作章程、会议制度,参议员按程序提出和讨论议案。与此同时,民主革命斗争也逐渐在民间铺开,郑长璋、蔡泽鏛就是早期斗争的杰出代表,后来叶飞、曾志等人也到宁德进行革命活动,农会、渔会、妇女会、盐工协会等组织风行一时,影响深入农村底层草根。他们已不单纯是传统时代的反对官府,而程度不等地包含了向往民主社会的新诉求。
民国时期宁德县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也表现在经济方面,例如,民国元年(1912)三都澳总局和宁德县二等邮局增办商务传单业务。次年,三都分防委员会发布《三都商埠外国人租地章程十八条》。华兴瑞记矿业公司注册成立。三年,中国银行三都澳分行成立。四年,省下发各县通行货币种类表(宁德银币、铜币和纸钞计11种)。1916年发生了三件今日看来颇为意味深长的事:1月,因税重挫伤制碗业,官府呈文省署申请减轻碗窑粗瓷税率;4月,万顺春等人贩茶遭劫,三都海军陆战队五旅受命驻兵宁德保护茶商;8月,闽海道官产处委员林宗远假借公务勒索扰民,被八都商民联名控告,解交省法庭查办。这说明当时带有若干现代经济色彩的工厂主和商人的力量已有一定成长,社会地位渐渐重要起来了。此后,工商业继续发展,渐渐形成略具影响的茶叶、棉布、京果(亦称南京店)和医药市场,“德顺鱼行”承包渔税,垄断一方,酿酒业、制碗业等也有所发展,各业在日寇轰炸、攻陷三都前夕最臻繁盛。但总的说来,速度不快,规模有限,直到1949年春,全县城乡登记小厂、作坊不满六十家,注册资金不过一千数百万元(国币);1950年城乡私营商业八百多家,从业者一千数百人,资金不到二十七万元(旧币)。
民国时期宁德县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还表现在文化方面。例如,在宣传媒介上,30—40年代国民党宁德县党部先后创办了《宁德民报》和《闽东日报》,抗战中县抗敌后援会创办了《宁德导报》;同一年代,县民众教育馆主持放映一些无声电影。
再如,在医疗设施上,民国十年(1921)洋中人阮琼珠接掌圣教妇幼医院,大力拓展西医项目,逐步把它改造成为综合性的医院(永生医院);二十四年,成立县卫生院,其后又陆续成立三都、霍童、洋中卫生所(二十九年改卫生分院);周墩区卫生院于二十七年成立,其时已不归县管。
卫生院、所初设,除永生医院稍具规模,余者都很简陋,但毕竟使西医西药渐得普及。
再如,在学校教育上,清末,县里随着外国传教士首先办起洋学堂,县立莲峰高等小学堂、霍童兴文小学堂和邑人林廷伸办的碧山小学堂等几所新式分科教学机构也渐次成立,旧学已受到不小的冲击。民国元年(1912),学堂改称学校,改莲峰小学堂为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三都小学堂为第二高等小学。至次年,全县共有小学27所,在校生近千人。四年,初等小学改称国民学校,县城5所,各乡31所(包括东洋里即后来的周墩区4所:周墩,浦源,端源,萌源)。八年,郑丹诚等在浦源、周墩创办县立第三高等小学。二十二年,省立霞浦初级中学(省立第三中学)迁三都,成为宁德县第一所现代普通中学。二十五年,政府推行“全民教育”。二十九年,成立县初级中学;政府提出一乡办一所中心小学,学制6年,一保办一所国民学校,学制4年。咸杉乡及当地4所学校划归周宁后,三十八年全县有公立小学49所,私立小学1所,在校生近四千人,中学2所,在校生近七百人。虽然入学率还很低,但现代学校体制已完全确立。
再如,在宗教活动上,道教源流久远,但明代以来日渐衰微,民国时期道观寥寥无几,且绝大多数被改作寺庵。佛教传入的历史同样很悠长,发展缓慢,民国时期留存寺院庵堂约70所,抗战中比较活跃,民国三十六年(1947),成立了县佛教协会,寺院之间的联络、协调有所加强。其实,民众对真正的佛教、道教相当隔膜。平常百姓信仰驳杂,崇拜对象五花八门,遇事热衷于算命、看相、求签、卜卦、扶乩、还愿等等,往往辗转出入于多种民间信仰服务者之门。十二年,县府颁令禁止迎神赛会,这是全国从上到下一致的政治导向,实际成效则很难持久。天主教从明末开始传入,民国时有本堂5处,分别在城关北门外、城南岐头村、漳湾瓜园村、飞鸾岚口村和三都松岐村;还有行教堂8处和一个行教公所,也都在滨海各村。基督教从晚清传入,宁德县主要有圣公会、安息日会和聚会处三个教派,十几个教堂,以分布在城关、金涵、飞鸾、三都、漳湾、七都、八都等沿海地带为主,并延伸到霍童、洋中(含石后)的山区,周墩除沿用光绪年旧教堂做礼拜,民国十二年又续建一幢土木结构的牧师房。当时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数量很少,但与传统文化冲突不少。这种冲突多会受到小地方“熟人社会”温馨人际关系的浸润而软化,但真正处理好所谓全球化漫长历程中的中西文化关系,自然还有待于更长历史时期的探索和实践。
与全国一样,民国时期宁德的社会转型,不可能是一个匀质性的变化过程,其中充满诸多种类的不平衡发展。从地理空间角度观察,东南滨海地带与西北山区差异巨大,三都澳通关后对工商业和农副产品贸易的直接拉动,西学包括宗教和科技的广泛影响,都明显呈现由沿海向内陆逐级辐射之态势。从社会空间角度观察,城关、郊区、乡镇、村寮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高下悬殊,县一级的代议机构、党部、商会、银行、图书馆、民众教育馆、诗社等等都在城关,医院、学校也相对集中分布在城区周遭。那里的社会风气比起偏远的山村无疑要合乎时尚得多。从社会分层的角度观察,精英人物和一般民众在社会转型中的表现也会有很大不同。民众虽是推动社会转型的基座性的力量,但通常是隐形的、深层次的,需要在长时段中才能真切感受到。精英阶层的活动比较外显,如,黄树荣在南北对峙中之所谓斡旋时局,郑长璋、蔡泽鏛、阮元皋等人之筹建国民党宁德县党部,林振翰之努力促进中国盐政现代化,石磊之筹办中央计政学院等等,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但在宁德这样的小县,恐怕有更多地方精英当年的具体行事,今日已难见多少痕迹了。
与全国一样,民国时期宁德的社会转型至少存在二大问题。一是没有解决阶级对立阶级剥削,二是在抗日战争以还遭受巨大挫折。这些前人述之已详,文中未再强调。关于早期现代化或早期全球化的发轫,诚如牛津大学的拉纳·米特(RanaMitter)博士所指出,民国时代的重要性可能被低估和误解了。放宽历史视界,自清末到民国再到今日,也可以看作是走向现代社会的一个连续过程。本文仅从这条线索勾粘旧物往事,自然远不能算作全面的评价。好在读者诸君手中早有辩证法的锐利武器,可以批判分析。民国时期宁德社会实际状况,具有十分复杂的面相,系统的研究,目前还没有起步,需要爬梳大量档案资料,访问众多耆宿乡贤,参考已有相关成果,才能有真正的初步收获。上述文字,充其量只是抛砖引玉而已。
相关人物
林校生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