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永昌县当地出土的番禾瑞像
| 内容出处: | 《刘萨诃、番禾瑞像与圣容寺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292020020220001955 |
| 颗粒名称: | 二、永昌县当地出土的番禾瑞像 |
| 分类号: | K879.3 |
| 页数: | 8 |
| 页码: | 29-36 |
| 摘要: | 本文记述永昌县当地出土的番禾瑞像介绍了Ⅰ型番禾瑞像、Ⅱ型番禾瑞像、Ⅲ型番禾瑞像、番禾瑞像佛首、对永昌出土造像的一些认识。 |
| 关键词: | 永昌县 番禾瑞像 出土 |
内容
1.Ⅰ型番禾瑞像
Ⅰ型造像于上世纪80年代在金川西村出土现藏于永昌县博物馆(图四)。造像为砂岩质,残高,80厘米,宽53厘米。佛像赤足站立于仰覆莲台上,整个背屏雕成山崖状,背屏右上部已残,颈肩处横贯一道裂纹,头面部及五官残损不清,尚可辨出轮廓。佛像为高浮雕,着衣袒右肩;胸口双领袈裟下边阴刻有锯齿状纹饰;左手握住衣襟一角,左手下部悬出的衣襟层次分明,状若飘起;左边腰部以下至足部的裙襟阳刻有两层锯齿状纹饰;右手下垂,但肘部已不可辨识,应是作与愿印;两腿之间刻有U形纹饰,自上而下呈阶梯状排歹。佛像与背屏之间空白处仍残留有浅红色彩,可知原像应当是敷色填彩的。
此像没有任何题记及其它纪年信息,可能是未雕刻或已毁蚀,造成对佛像的时代认定产生了一些分歧。张宝玺先生认为应是北魏所造,文静、魏文斌二位先生认为其造于初唐。业师杜斗城先生在对此像经过实地考察后,指出其制作年代应当在北魏到西魏之间,最迟不会晚于西魏。笔者也认同业师杜斗城先生和张宝玺先生的观点。其残存的头部、身躯以及手臂都比较瘦长;肩部平削,头光和身光连为一体,背光呈上宽下窄的瘦莲瓣形;面部与北魏佛像那种方颐的面庞相类似,整体风格也略显清癯。另从这尊佛像的质地来看,与当地所产石质相同,应当是在本地出产并雕造完成。依此来看,此像应当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番禾瑞像的石雕像,这可能对于现存的一些其它造像的时代划分和相关文献的记载具有一定的意义。
2.Ⅱ型番禾瑞像
这尊造像原存于圣容寺大殿东十几米处的一个较大的石窟中,后运至永昌县博物馆保存(图五)。造像为砂岩质,造像通高114厘米,佛像高约94厘米,宽约40厘米。头部及膝部以下皆残缺,立姿,着衣袒右肩,左手握衣角,胸口双领袈裟下边亦阴刻锯齿状纹饰,右手下垂,肘部以下残损不能辨识;头光是分两层交错雕刻而成,呈莲瓣形;佛像两侧的背光中浮雕有化佛,腰部、肩部和头部两侧对称分布各三身,顶部一身,共七身跏趺坐小化佛。背光呈舟形,再向外则表现出嵯峨的山崖。该石窟现为当地僧俗所雕凿重修,原貌已不存,石窟的情况,典籍中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但孙修身先生曾做过比较详细的调查和记录。①原窟室高约2.7米,长宽约3到4米之间,敞口、略称方形;前有长约9米,宽约4.5米,高4米的前廊,与后边的窟室相连。
此像也未留下任何关于纪年的文字信息,孙修身和张宝玺二位先生对其做了简单记录。②张宝玺先生认为此像是北魏时期的造像,没有更进一步说明断代的缘由。③从残存造像所表现出的一些风格特征来看,Ⅱ型的时代要较之于Ⅰ型晚。与Ⅰ型相比,Ⅱ型佛像体型更趋丰满,胸口袈裟的锯齿状纹饰更为明显。头光出现了莲瓣造型,背屏则由瘦莲瓣形变为舟形,并在背屏上浮雕出七身小化佛。
3.Ⅲ型番禾瑞像
Ⅲ型造像被当地人称作“青龙佛”,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永昌县城西南的红山窑乡青龙山庙遗址中被发现,原供奉于青龙山庙之内而得名,后寺庙破毁,现藏于永昌县博物馆(图六)。造像为石灰岩质地,以高浮雕、圆雕手法凿刻而成,部分已残。通高170厘米,宽85厘米,跣足立于仰覆莲台上,体量巨大,与真人几近相等,正是所谓“等身佛”。佛首已断裂,后经修复安装合于一身。低圆发髻,着衣袒右肩,右手沿体下垂作与愿印,左手握衣角,下部悬出衣襟;胸口衣领处的锯齿纹及左侧裙边的两层锯齿形纹饰与前面出现的Ⅰ型、Ⅱ型雕刻如出一辙;两腿之间自上而下雕刻有整齐的浅U形纹,膝部以下的衣纹也呈密集的浅U形,衣纹更富韵律感;背屏呈舟形,肩部以上的背屏两侧雕有五身跏趺坐小化佛,顶部已残,顶部可能有一身小佛,两侧对称雕有六身小佛;背屏周边嵯峨的山崖则用浮雕手法表现出来。
佛籍和县志中均没有关于青龙山庙及此像的相关记载,造像本身未雕刻题记,但整尊佛像体量巨大,丰满圆润,线条流畅,衣褶纹饰栩栩如生,表现出娴熟高超的雕刻技法,应是盛唐的作品无疑。
4.番禾瑞像佛首
番禾瑞像佛首于上世纪70年代由原文化馆黄馆长在金川西村望御谷一农户家牛圈墙的垒石中起获,现存于永昌县博物馆(图七)。佛首为青砂岩质,高67厘米,发髻已残,眉间白毫残缺,鼻、耳朵、唇等处也被磨损。面形圆润,头顶结满低平小螺髻。关于此像的时代和是否为番禾瑞像“原像”的问题,笔者认为还有重新讨论的必要。孙修身、张宝玺二先生对其分别做了记录。孙氏未说明时代,只说其为早期造像,并有着“受印度造像影响”的痕迹;张氏则认为此像就是佛籍中之凉州瑞像,现存于永昌圣容寺的佛身成于正光元年(520年),而这颗佛首则雕造于北周闵帝元年(557年)。佛首的断代还需要进一步判别和认识,因为后世佛首跌落复又安装之次数较多,最初的佛首存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5.对永昌出土造像的一些认识
基于对相关典籍文献的了解以及对以上儿尊佛像的初步认识,可以通过其所透露出的时代信息而对永昌出土佛像的时代进行排序。特别是Ⅰ型佛像,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尊佛像,对于它的出现和进一步认识,可能存在一定的意义:不仅可以改变以往学界对那尊佛首的认定,而且可能会使以往对身首合璧的番禾瑞像的诞生时代会有新的结论。先来看佛首:孙氏认为佛首就是《续高僧传》中所记载的“凉州城东七里涧”发现的佛首,实际情况就是在凉州雕刻好佛首之后,又搬运至番禾县望御谷后安装于无头的佛身上;张氏则直接说其雕刻完成于北周元年(557年),是番禾瑞像原像首,根据则不外于道宣的著作。其次,从相关的典籍来看,最先出现的应当是身首合璧的那尊体量巨大的“丈八石像”(图八),也就是今天仍然能看到的那尊大的浮雕像。番禾瑞像也应当是在“具足”以后才会被各地“依图供养”其他的小的雕像、造像等等都是依样画葫芦照着原,来的丈八大佛像再行仿制的,这也符合常理。北魏于534年之后分裂为东魏、西魏,西魏于557年又为北周所替。但按照文字记载,佛首最早完成与像身的合璧也在北周元年,那么这尊北魏的Ⅰ型佛像怎么会早于北周的丈八石佛出现?如此一来,就会出现以下几种可能性:第一,杜斗城先生很早就指出北魏正光年间望御谷已经出现了造像活动。①在这一系列造像活动中,就可能已经有那种特定造型的佛像被雕造出来,那么这颗佛首就不应该是“原像”了,而是它依照已经成型的番禾瑞像而再行仿制的。如此一来,文献的记载就出现了讹误。第二,正光年间已有佛首刻出,但不知何故丢失,或者说佛首因为某种原因没有雕刻好,无法安装。北周出现的佛首指的是在凉州东七里涧或其他地方被雕刻出的另外的佛首第三,番禾瑞像是先有像身,后有佛首,其间有“仪容雕缺四十余年,身首异所二百余里”的分离期。番禾瑞像的特别之处在于手印、躯干、衣纹等部位有其自身特点,佛首的形象一般来讲与其他佛像相差不是很大,在近四十余年的空白期是否已经有人先雕出了全像则不得而知,尽管这种可能性比较小。但以上几种可能的情况和典籍中的记载就出现了矛盾,这就说明了刘萨诃及番禾瑞像等一系列神异的事件属于附会的可能性极大,信徒为宣扬佛教,扩大佛教的影响力而对原有的故事“添枝加叶”了。
从以上四尊佛像表现出的特点可以看出:番禾瑞像在当地是随着朝代的更替发展而不断变化的。造像的细节部分出现了新的装饰,比如增加了莲瓣、化佛以及背屏的变化等等,雕刻更加精美,体量也由小变大。与此同时,望御谷的造像活动自北魏开始就一直没有中断过,且不局限于望御谷一地,并在隋唐之际更加兴盛。番禾县当地的这种状况,清楚地表明了由刘萨诃的神异事迹而衍化出的传说故事具有很强大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番禾瑞像也为当地僧俗所崇信,使得瑞像信仰在番禾县世代相传。
Ⅰ型造像于上世纪80年代在金川西村出土现藏于永昌县博物馆(图四)。造像为砂岩质,残高,80厘米,宽53厘米。佛像赤足站立于仰覆莲台上,整个背屏雕成山崖状,背屏右上部已残,颈肩处横贯一道裂纹,头面部及五官残损不清,尚可辨出轮廓。佛像为高浮雕,着衣袒右肩;胸口双领袈裟下边阴刻有锯齿状纹饰;左手握住衣襟一角,左手下部悬出的衣襟层次分明,状若飘起;左边腰部以下至足部的裙襟阳刻有两层锯齿状纹饰;右手下垂,但肘部已不可辨识,应是作与愿印;两腿之间刻有U形纹饰,自上而下呈阶梯状排歹。佛像与背屏之间空白处仍残留有浅红色彩,可知原像应当是敷色填彩的。
此像没有任何题记及其它纪年信息,可能是未雕刻或已毁蚀,造成对佛像的时代认定产生了一些分歧。张宝玺先生认为应是北魏所造,文静、魏文斌二位先生认为其造于初唐。业师杜斗城先生在对此像经过实地考察后,指出其制作年代应当在北魏到西魏之间,最迟不会晚于西魏。笔者也认同业师杜斗城先生和张宝玺先生的观点。其残存的头部、身躯以及手臂都比较瘦长;肩部平削,头光和身光连为一体,背光呈上宽下窄的瘦莲瓣形;面部与北魏佛像那种方颐的面庞相类似,整体风格也略显清癯。另从这尊佛像的质地来看,与当地所产石质相同,应当是在本地出产并雕造完成。依此来看,此像应当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番禾瑞像的石雕像,这可能对于现存的一些其它造像的时代划分和相关文献的记载具有一定的意义。
2.Ⅱ型番禾瑞像
这尊造像原存于圣容寺大殿东十几米处的一个较大的石窟中,后运至永昌县博物馆保存(图五)。造像为砂岩质,造像通高114厘米,佛像高约94厘米,宽约40厘米。头部及膝部以下皆残缺,立姿,着衣袒右肩,左手握衣角,胸口双领袈裟下边亦阴刻锯齿状纹饰,右手下垂,肘部以下残损不能辨识;头光是分两层交错雕刻而成,呈莲瓣形;佛像两侧的背光中浮雕有化佛,腰部、肩部和头部两侧对称分布各三身,顶部一身,共七身跏趺坐小化佛。背光呈舟形,再向外则表现出嵯峨的山崖。该石窟现为当地僧俗所雕凿重修,原貌已不存,石窟的情况,典籍中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但孙修身先生曾做过比较详细的调查和记录。①原窟室高约2.7米,长宽约3到4米之间,敞口、略称方形;前有长约9米,宽约4.5米,高4米的前廊,与后边的窟室相连。
此像也未留下任何关于纪年的文字信息,孙修身和张宝玺二位先生对其做了简单记录。②张宝玺先生认为此像是北魏时期的造像,没有更进一步说明断代的缘由。③从残存造像所表现出的一些风格特征来看,Ⅱ型的时代要较之于Ⅰ型晚。与Ⅰ型相比,Ⅱ型佛像体型更趋丰满,胸口袈裟的锯齿状纹饰更为明显。头光出现了莲瓣造型,背屏则由瘦莲瓣形变为舟形,并在背屏上浮雕出七身小化佛。
3.Ⅲ型番禾瑞像
Ⅲ型造像被当地人称作“青龙佛”,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永昌县城西南的红山窑乡青龙山庙遗址中被发现,原供奉于青龙山庙之内而得名,后寺庙破毁,现藏于永昌县博物馆(图六)。造像为石灰岩质地,以高浮雕、圆雕手法凿刻而成,部分已残。通高170厘米,宽85厘米,跣足立于仰覆莲台上,体量巨大,与真人几近相等,正是所谓“等身佛”。佛首已断裂,后经修复安装合于一身。低圆发髻,着衣袒右肩,右手沿体下垂作与愿印,左手握衣角,下部悬出衣襟;胸口衣领处的锯齿纹及左侧裙边的两层锯齿形纹饰与前面出现的Ⅰ型、Ⅱ型雕刻如出一辙;两腿之间自上而下雕刻有整齐的浅U形纹,膝部以下的衣纹也呈密集的浅U形,衣纹更富韵律感;背屏呈舟形,肩部以上的背屏两侧雕有五身跏趺坐小化佛,顶部已残,顶部可能有一身小佛,两侧对称雕有六身小佛;背屏周边嵯峨的山崖则用浮雕手法表现出来。
佛籍和县志中均没有关于青龙山庙及此像的相关记载,造像本身未雕刻题记,但整尊佛像体量巨大,丰满圆润,线条流畅,衣褶纹饰栩栩如生,表现出娴熟高超的雕刻技法,应是盛唐的作品无疑。
4.番禾瑞像佛首
番禾瑞像佛首于上世纪70年代由原文化馆黄馆长在金川西村望御谷一农户家牛圈墙的垒石中起获,现存于永昌县博物馆(图七)。佛首为青砂岩质,高67厘米,发髻已残,眉间白毫残缺,鼻、耳朵、唇等处也被磨损。面形圆润,头顶结满低平小螺髻。关于此像的时代和是否为番禾瑞像“原像”的问题,笔者认为还有重新讨论的必要。孙修身、张宝玺二先生对其分别做了记录。孙氏未说明时代,只说其为早期造像,并有着“受印度造像影响”的痕迹;张氏则认为此像就是佛籍中之凉州瑞像,现存于永昌圣容寺的佛身成于正光元年(520年),而这颗佛首则雕造于北周闵帝元年(557年)。佛首的断代还需要进一步判别和认识,因为后世佛首跌落复又安装之次数较多,最初的佛首存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5.对永昌出土造像的一些认识
基于对相关典籍文献的了解以及对以上儿尊佛像的初步认识,可以通过其所透露出的时代信息而对永昌出土佛像的时代进行排序。特别是Ⅰ型佛像,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尊佛像,对于它的出现和进一步认识,可能存在一定的意义:不仅可以改变以往学界对那尊佛首的认定,而且可能会使以往对身首合璧的番禾瑞像的诞生时代会有新的结论。先来看佛首:孙氏认为佛首就是《续高僧传》中所记载的“凉州城东七里涧”发现的佛首,实际情况就是在凉州雕刻好佛首之后,又搬运至番禾县望御谷后安装于无头的佛身上;张氏则直接说其雕刻完成于北周元年(557年),是番禾瑞像原像首,根据则不外于道宣的著作。其次,从相关的典籍来看,最先出现的应当是身首合璧的那尊体量巨大的“丈八石像”(图八),也就是今天仍然能看到的那尊大的浮雕像。番禾瑞像也应当是在“具足”以后才会被各地“依图供养”其他的小的雕像、造像等等都是依样画葫芦照着原,来的丈八大佛像再行仿制的,这也符合常理。北魏于534年之后分裂为东魏、西魏,西魏于557年又为北周所替。但按照文字记载,佛首最早完成与像身的合璧也在北周元年,那么这尊北魏的Ⅰ型佛像怎么会早于北周的丈八石佛出现?如此一来,就会出现以下几种可能性:第一,杜斗城先生很早就指出北魏正光年间望御谷已经出现了造像活动。①在这一系列造像活动中,就可能已经有那种特定造型的佛像被雕造出来,那么这颗佛首就不应该是“原像”了,而是它依照已经成型的番禾瑞像而再行仿制的。如此一来,文献的记载就出现了讹误。第二,正光年间已有佛首刻出,但不知何故丢失,或者说佛首因为某种原因没有雕刻好,无法安装。北周出现的佛首指的是在凉州东七里涧或其他地方被雕刻出的另外的佛首第三,番禾瑞像是先有像身,后有佛首,其间有“仪容雕缺四十余年,身首异所二百余里”的分离期。番禾瑞像的特别之处在于手印、躯干、衣纹等部位有其自身特点,佛首的形象一般来讲与其他佛像相差不是很大,在近四十余年的空白期是否已经有人先雕出了全像则不得而知,尽管这种可能性比较小。但以上几种可能的情况和典籍中的记载就出现了矛盾,这就说明了刘萨诃及番禾瑞像等一系列神异的事件属于附会的可能性极大,信徒为宣扬佛教,扩大佛教的影响力而对原有的故事“添枝加叶”了。
从以上四尊佛像表现出的特点可以看出:番禾瑞像在当地是随着朝代的更替发展而不断变化的。造像的细节部分出现了新的装饰,比如增加了莲瓣、化佛以及背屏的变化等等,雕刻更加精美,体量也由小变大。与此同时,望御谷的造像活动自北魏开始就一直没有中断过,且不局限于望御谷一地,并在隋唐之际更加兴盛。番禾县当地的这种状况,清楚地表明了由刘萨诃的神异事迹而衍化出的传说故事具有很强大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番禾瑞像也为当地僧俗所崇信,使得瑞像信仰在番禾县世代相传。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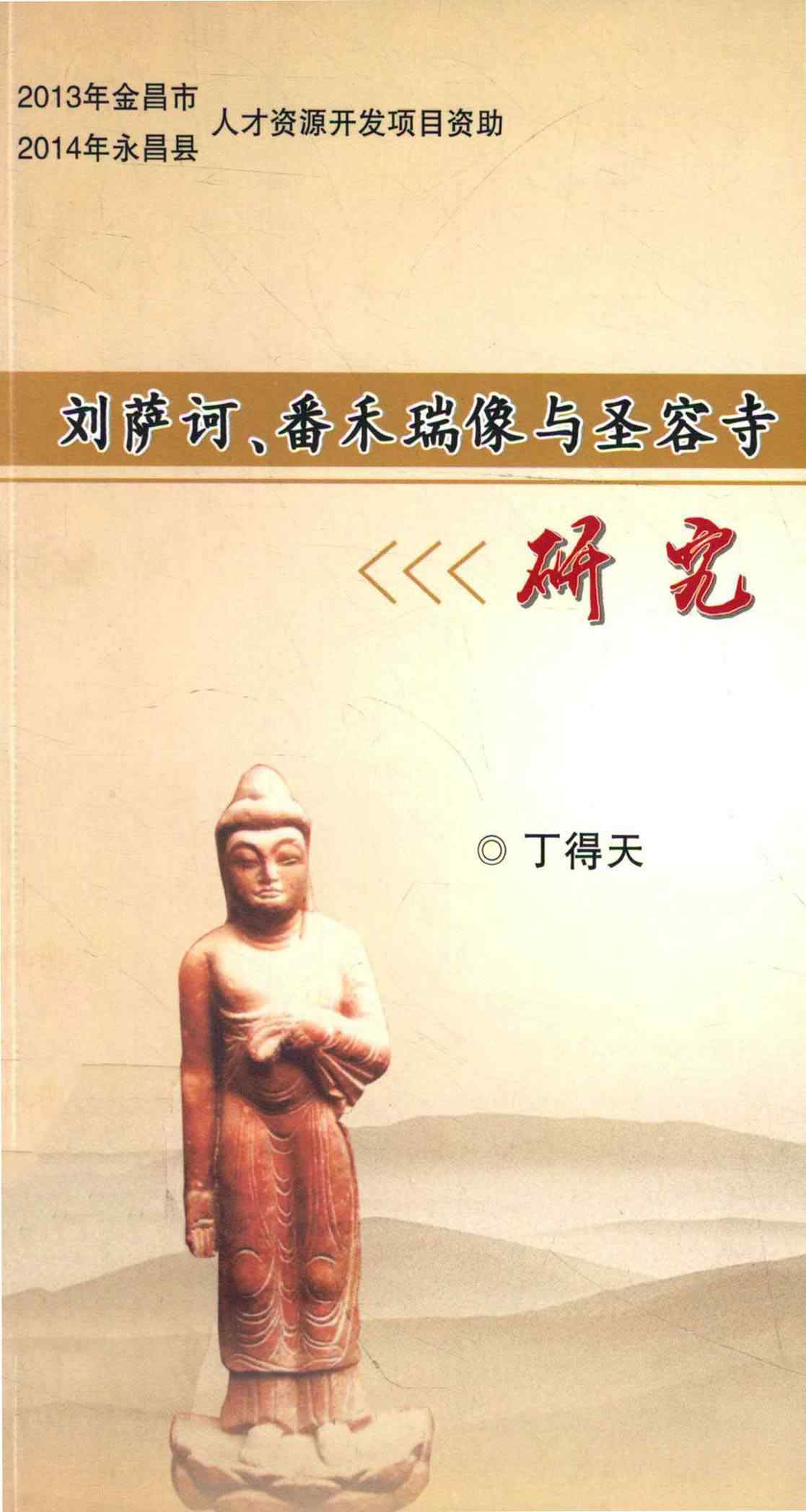
《刘萨诃、番禾瑞像与圣容寺研究》
本书分为三章分别介绍了刘萨诃的生平以及番禾瑞像和圣容寺的情况,对望御谷及周边的佛教遗迹做了全面的调查,著录了金昌市境内散见的佛教石窟寺遗迹以及清代《永昌县志》所记载的古寺。
阅读
相关地名
永昌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