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番禾瑞像
| 内容出处: | 《刘萨诃、番禾瑞像与圣容寺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292020020220001953 |
| 颗粒名称: | 第二节 番禾瑞像 |
| 分类号: | K879.3 |
| 页数: | 1 |
| 页码: | 9-26 |
| 摘要: | 本文记述永昌县番禾瑞像的介绍,番禾瑞像与望御谷、永昌县当地出土的番禾瑞像、其他代表性造像及文物资料。 |
| 关键词: | 永昌县 番禾瑞像 研究 |
内容
一、番禾瑞像与望御谷
番禾瑞像既诞生于番禾县望御谷,番禾县和望御谷的关系就需要做一简单的了解,尤其是望御谷的情况以前多被研究者所忽视,现在看来,望御谷的地理位置和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是番禾瑞像诞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番禾一作“番和”,初为汉置县,名番和,魏晋因之,其故治在今永昌县西。望御谷之名最初不知从何而来,亦不见于史册,最初或叫做“御山”。番禾县自西汉置郡以来,一直沿用到晚唐五代宋时期,凡历700多年,期间因为朝代的更替和战争的缘故,有几次暂废和改称,尽管时间都较为短暂,但是番禾郡的故治并未随之而发生变化。从一些史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①,番禾古城的规模之大在河西地区也是比较少见的。有说番禾县故址在今焦家庄乡南约一公里处,有说在今之南、北古城一带,皆因没有充足的史料、考古遗迹加以佐证而未有定论,尚待详考,因这一问题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此处不再展开。但可以确定的是,不论番禾古城的故址在焦家庄乡南或是南北古城一带,其地理方位均在永昌县西,这就与道宣所记载的刘萨诃向东北方向之望御谷“遥礼”是完全吻合的。事实上,道宣本人并没有亲自到过河西走廊一带。而位于今永昌县城北部的望御谷,也不过就是一个偏僻的峡谷而已,番禾县城就处在望御谷的西南方向,并且中间还隔着武当山,二者相距十几里地,道宣和之前大多数的作者都没有亲自考察过,其记载却丝毫不差。类似于此种夹杂着道听途说式的有关望御谷的记载,说明望御谷在当时就已经颇负声名,甚至早在番禾瑞像尚未出世的时候就已经为人所熟知了。
番禾瑞像,也称作凉州瑞像,凉州番禾县瑞像或御容山瑞像、永昌圣容瑞像等等不一而足,也有因刘萨诃预言诞生之故而称其为刘萨诃瑞像者,大同小异,皆指今永昌城北圣容寺后依山而立的浮雕瑞像。该像的称名之所以产生了一点小的分歧,主要是对此像的神格、信仰还不能进行准确的区分或界定,而绝大多数的佛教造像是以神格来命名的。番禾瑞像出世的时候,番禾县只是凉州下辖的一个县,凉州则为更高一级的行政机构,属于上下级行政隶属的关系,所以时人在记载此事的时候前面务须要加上“凉州”二字,也就是今之学界大多称其为凉州瑞像的原因。相对来说,在尚未弄清此像系哪一尊佛像的时候,用出世时所在的地名来为其命名是更为合适的,如凉州瑞像、御容山瑞像、永昌圣容瑞像等。肥田路美先生称其为凉州番禾县瑞像,将僧传的记载和诞生地都表述出来,无疑更为准确。尚丽新先生简称为番禾瑞像,更加简练,易于表达,笔者在文中也多从此说。另因为此像的出世实是源于刘萨诃之故,也有以刘萨诃之名冠之者,但从后来出土的一些文书、造像及其他相关文物来看,番禾瑞像信仰和刘萨诃信仰分属于两种不同的信仰,发展的脉络和传播的地域也互有差别,二者本身表征的意涵也不尽相同。实际上,番禾瑞像应当是释迦牟尼像。现存于山西省博物馆的李元封等造的番禾瑞像的题记中就有“释迦圣容立像”之名。若以其神格来为之命名的话,可以称其为“释迦圣容瑞像”,或“释迦圣容立像”,或者叫做“释迦圣容佛”。总之,只要能指明此像即可。
二、永昌县当地出土的番禾瑞像
1.Ⅰ型番禾瑞像
Ⅰ型造像于上世纪80年代在金川西村出土现藏于永昌县博物馆(图四)。造像为砂岩质,残高,80厘米,宽53厘米。佛像赤足站立于仰覆莲台上,整个背屏雕成山崖状,背屏右上部已残,颈肩处横贯一道裂纹,头面部及五官残损不清,尚可辨出轮廓。佛像为高浮雕,着衣袒右肩;胸口双领袈裟下边阴刻有锯齿状纹饰;左手握住衣襟一角,左手下部悬出的衣襟层次分明,状若飘起;左边腰部以下至足部的裙襟阳刻有两层锯齿状纹饰;右手下垂,但肘部已不可辨识,应是作与愿印;两腿之间刻有U形纹饰,自上而下呈阶梯状排歹。佛像与背屏之间空白处仍残留有浅红色彩,可知原像应当是敷色填彩的。
此像没有任何题记及其它纪年信息,可能是未雕刻或已毁蚀,造成对佛像的时代认定产生了一些分歧。张宝玺先生认为应是北魏所造,文静、魏文斌二位先生认为其造于初唐。业师杜斗城先生在对此像经过实地考察后,指出其制作年代应当在北魏到西魏之间,最迟不会晚于西魏。笔者也认同业师杜斗城先生和张宝玺先生的观点。其残存的头部、身躯以及手臂都比较瘦长;肩部平削,头光和身光连为一体,背光呈上宽下窄的瘦莲瓣形;面部与北魏佛像那种方颐的面庞相类似,整体风格也略显清癯。另从这尊佛像的质地来看,与当地所产石质相同,应当是在本地出产并雕造完成。依此来看,此像应当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番禾瑞像的石雕像,这可能对于现存的一些其它造像的时代划分和相关文献的记载具有一定的意义。
2.Ⅱ型番禾瑞像
这尊造像原存于圣容寺大殿东十几米处的一个较大的石窟中,后运至永昌县博物馆保存(图五)。造像为砂岩质,造像通高114厘米,佛像高约94厘米,宽约40厘米。头部及膝部以下皆残缺,立姿,着衣袒右肩,左手握衣角,胸口双领袈裟下边亦阴刻锯齿状纹饰,右手下垂,肘部以下残损不能辨识;头光是分两层交错雕刻而成,呈莲瓣形;佛像两侧的背光中浮雕有化佛,腰部、肩部和头部两侧对称分布各三身,顶部一身,共七身跏趺坐小化佛。背光呈舟形,再向外则表现出嵯峨的山崖。该石窟现为当地僧俗所雕凿重修,原貌已不存,石窟的情况,典籍中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但孙修身先生曾做过比较详细的调查和记录。①原窟室高约2.7米,长宽约3到4米之间,敞口、略称方形;前有长约9米,宽约4.5米,高4米的前廊,与后边的窟室相连。
此像也未留下任何关于纪年的文字信息,孙修身和张宝玺二位先生对其做了简单记录。②张宝玺先生认为此像是北魏时期的造像,没有更进一步说明断代的缘由。③从残存造像所表现出的一些风格特征来看,Ⅱ型的时代要较之于Ⅰ型晚。与Ⅰ型相比,Ⅱ型佛像体型更趋丰满,胸口袈裟的锯齿状纹饰更为明显。头光出现了莲瓣造型,背屏则由瘦莲瓣形变为舟形,并在背屏上浮雕出七身小化佛。
3.Ⅲ型番禾瑞像
Ⅲ型造像被当地人称作“青龙佛”,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永昌县城西南的红山窑乡青龙山庙遗址中被发现,原供奉于青龙山庙之内而得名,后寺庙破毁,现藏于永昌县博物馆(图六)。造像为石灰岩质地,以高浮雕、圆雕手法凿刻而成,部分已残。通高170厘米,宽85厘米,跣足立于仰覆莲台上,体量巨大,与真人几近相等,正是所谓“等身佛”。佛首已断裂,后经修复安装合于一身。低圆发髻,着衣袒右肩,右手沿体下垂作与愿印,左手握衣角,下部悬出衣襟;胸口衣领处的锯齿纹及左侧裙边的两层锯齿形纹饰与前面出现的Ⅰ型、Ⅱ型雕刻如出一辙;两腿之间自上而下雕刻有整齐的浅U形纹,膝部以下的衣纹也呈密集的浅U形,衣纹更富韵律感;背屏呈舟形,肩部以上的背屏两侧雕有五身跏趺坐小化佛,顶部已残,顶部可能有一身小佛,两侧对称雕有六身小佛;背屏周边嵯峨的山崖则用浮雕手法表现出来。
佛籍和县志中均没有关于青龙山庙及此像的相关记载,造像本身未雕刻题记,但整尊佛像体量巨大,丰满圆润,线条流畅,衣褶纹饰栩栩如生,表现出娴熟高超的雕刻技法,应是盛唐的作品无疑。
4.番禾瑞像佛首
番禾瑞像佛首于上世纪70年代由原文化馆黄馆长在金川西村望御谷一农户家牛圈墙的垒石中起获,现存于永昌县博物馆(图七)。佛首为青砂岩质,高67厘米,发髻已残,眉间白毫残缺,鼻、耳朵、唇等处也被磨损。面形圆润,头顶结满低平小螺髻。关于此像的时代和是否为番禾瑞像“原像”的问题,笔者认为还有重新讨论的必要。孙修身、张宝玺二先生对其分别做了记录。孙氏未说明时代,只说其为早期造像,并有着“受印度造像影响”的痕迹;张氏则认为此像就是佛籍中之凉州瑞像,现存于永昌圣容寺的佛身成于正光元年(520年),而这颗佛首则雕造于北周闵帝元年(557年)。佛首的断代还需要进一步判别和认识,因为后世佛首跌落复又安装之次数较多,最初的佛首存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5.对永昌出土造像的一些认识
基于对相关典籍文献的了解以及对以上儿尊佛像的初步认识,可以通过其所透露出的时代信息而对永昌出土佛像的时代进行排序。特别是Ⅰ型佛像,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尊佛像,对于它的出现和进一步认识,可能存在一定的意义:不仅可以改变以往学界对那尊佛首的认定,而且可能会使以往对身首合璧的番禾瑞像的诞生时代会有新的结论。先来看佛首:孙氏认为佛首就是《续高僧传》中所记载的“凉州城东七里涧”发现的佛首,实际情况就是在凉州雕刻好佛首之后,又搬运至番禾县望御谷后安装于无头的佛身上;张氏则直接说其雕刻完成于北周元年(557年),是番禾瑞像原像首,根据则不外于道宣的著作。其次,从相关的典籍来看,最先出现的应当是身首合璧的那尊体量巨大的“丈八石像”(图八),也就是今天仍然能看到的那尊大的浮雕像。番禾瑞像也应当是在“具足”以后才会被各地“依图供养”其他的小的雕像、造像等等都是依样画葫芦照着原,来的丈八大佛像再行仿制的,这也符合常理。北魏于534年之后分裂为东魏、西魏,西魏于557年又为北周所替。但按照文字记载,佛首最早完成与像身的合璧也在北周元年,那么这尊北魏的Ⅰ型佛像怎么会早于北周的丈八石佛出现?如此一来,就会出现以下几种可能性:第一,杜斗城先生很早就指出北魏正光年间望御谷已经出现了造像活动。①在这一系列造像活动中,就可能已经有那种特定造型的佛像被雕造出来,那么这颗佛首就不应该是“原像”了,而是它依照已经成型的番禾瑞像而再行仿制的。如此一来,文献的记载就出现了讹误。第二,正光年间已有佛首刻出,但不知何故丢失,或者说佛首因为某种原因没有雕刻好,无法安装。北周出现的佛首指的是在凉州东七里涧或其他地方被雕刻出的另外的佛首第三,番禾瑞像是先有像身,后有佛首,其间有“仪容雕缺四十余年,身首异所二百余里”的分离期。番禾瑞像的特别之处在于手印、躯干、衣纹等部位有其自身特点,佛首的形象一般来讲与其他佛像相差不是很大,在近四十余年的空白期是否已经有人先雕出了全像则不得而知,尽管这种可能性比较小。但以上几种可能的情况和典籍中的记载就出现了矛盾,这就说明了刘萨诃及番禾瑞像等一系列神异的事件属于附会的可能性极大,信徒为宣扬佛教,扩大佛教的影响力而对原有的故事“添枝加叶”了。
从以上四尊佛像表现出的特点可以看出:番禾瑞像在当地是随着朝代的更替发展而不断变化的。造像的细节部分出现了新的装饰,比如增加了莲瓣、化佛以及背屏的变化等等,雕刻更加精美,体量也由小变大。与此同时,望御谷的造像活动自北魏开始就一直没有中断过,且不局限于望御谷一地,并在隋唐之际更加兴盛。番禾县当地的这种状况,清楚地表明了由刘萨诃的神异事迹而衍化出的传说故事具有很强大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番禾瑞像也为当地僧俗所崇信,使得瑞像信仰在番禾县世代相传。
三、其他代表性造像及文物资料
番禾瑞像“出世”以后,不仅在番禾县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波及到河西走廊及附近地区,现存数量众多的石窟寺遗迹、壁画、雕塑等相关文物就是最好的例证。以下选取三个比较典型的出现在河西走廊附近的造像或文物来举例说明。
1.张掖马蹄寺千佛洞第6窟番禾瑞像
张掖马蹄寺石窟开凿于五世纪初,其后历代皆有营修,今仍存70余窟,千佛洞第6窟建于初唐(图九)。该窟坐西向东,高约6米,宽5.5米,进深4.6米,窟内正壁佛像高4米。现存于窟内的造像在1992年之前被当地僧俗重修过,与原像的细节特征有出入,特别是原来左手握衣角的造型被改造成了现在的左手托莲台,以致改变了主尊造像的神格,幸得1987年出版的《河西石窟》一书录其原貌。①张善庆先生很早就指出了这次重修活动所造成的影响,并对其进行了详实的考证。②沙武田先生指出此像“主尊处山形中,时代为唐前期”,③这就说明番禾瑞像背后山崖的表现不是只有将山崖雕饰在佛像背屏上的一种方式,特别是这种较大规模的开窟造像,在地况、材料等各种条件具备的时候,完全可以照搬番禾瑞像最初诞生时的那种方式。张掖东邻永昌,番禾瑞像的造型出现以后,随着瑞像信仰的影响不断扩大,向西传播的第一站就是张掖,更兼马蹄寺本就是河西之佛教圣地,番禾瑞像在这里的出现自然是顺理成章。
2.莫国高窟第72窟南壁番禾瑞像故事画及其他
酒泉、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现存有大量的刘萨诃和番禾瑞像相关的遗迹文物,大多是唐、五代及以后出现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莫高窟第72窟、237窟等。莫高窟72窟南壁的番禾瑞像故事画长约6.5米,高4.3米,下部大约三分之二的壁画因流沙磨蚀而不能清晰辨认,西侧下部和东侧也有小部分脱落,仅存上部约三分之一。霍熙亮先生复原了72窟的线描图,并推测其绘于晚唐初期,后经过五代、宋重修。统中国艺术中对宗教偶像最为深刻的思考的画”(图十),①同时也表现了番禾瑞像在身首复合时的情景(图一一),为今天人们了解古代修缮安装佛像的程序提供了确切的资料。其它如敦煌莫高窟第十六、二十六、四十九、五十五、八十四、一二二、三〇〇、三三二等窟,敦煌西千佛洞第十九窟,安西榆林窟第三十三窟,酒泉文殊山万佛洞等石窟均存有番禾瑞像的壁画或塑像,此处不一一详述。
敦煌、酒泉地区是经过河西走廊通向内地的门户,地接西域,又与凉州番禾县相距不远,回鹘、归义军及一些其它短暂出现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大都尊崇佛教,客观上也为瑞像信仰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数量如此之多的番禾瑞像题材出现于酒泉、敦煌等地,特别是出现于晚唐五代至北宋之际营建的石窟中,就是最好的例证,也足以说明瑞像信仰在这一地区兴盛的程度。
日本滨田德海旧藏的编号为ChinMs:C121的敦煌文书题记中,记录了宋初营修凉州感通寺的一些情况。敦煌研究院马德先生于日本抄录了此文书题记,其内容如下:
文书名:宋乾德六年修凉州感通寺记
正文:凉州御山感通寺圣容天卡来
大祖文皇帝膺千年之圣 百代之英运
属龙非时当凤举廓三籁于道销庇四民于
德寰维释氏之 纲缀儒〔〕之绝纳泽流遐
外九
被无穷 皇帝时乘驭寓幄历君临德
泉道光日月不住无为而孝慈兆庶不 有
为而丘拘万机洞九宅之非絙树三宝之圣福
于保定九年凉州奉之方知尊容神异靡
又空钟震响寔韵八音灯轮自转 符三点亲
崄者发奇悟于真源传听者荡烦嚣于 派
澡慕之流京野翘汪公惟大慈府降宜就表
受罄舍珍财敬营塔寺依峰树 栋丹彩于重
霄因材构宇晓朱青于凉〔〕尽人工之妙房
周通迎势放祗园禅室连扃形模鹫岭
左瞻崆峒想轩辕之所游
乾德六年六月廿二日僧道和纪之耳
此文本后的题款为“僧道和纪之耳”,故本文皆以“道和文本”称之。这里先简要交代一下“道和文本”所处的唐末五代时期凉州及永昌政治环境变迁的背景①:
唐末五代时期正是河西地区政治势力迭起,民族变迁频繁,战乱相寻的时代凉州先后为吐蕃、归义军、甘州回鹘、嗢末人和凉州吐蕃部等政治势力统治或控制。763年,吐蕃大军开始自东向西攻占唐朝所属的河西地区。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吐蕃重兵围攻凉州,唐河西节度使杨志烈未能抵挡吐蕃的猛烈攻势而西奔甘州,河西重镇凉州旋即陷落,766年,吐蕃相继攻下甘州、肃州,河西大部为吐蕃所据,永昌时为凉州所辖,766年之前也已陷于吐蕃。到大中二年(848年),沙州张议潮率部反抗吐蕃,驱逐吐蕃势力,光复了瓜、沙二州。大中三年(849年),张氏自西向东相继收复肃州、甘州。大中五年(851年),唐朝政府在沙州设立归义军,授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咸通二年(861年),张议潮攻克凉州。重镇凉州的攻克,意味着河西走廊基本上已被归义军政权所控制。在张议潮自西向东进兵的时候,嗢末和一些吐蕃部族也被驱赶到凉州一带,并在这里盘踞下来。中和四年(884年),西迁至河西的回鹘人势力日盛,与甘州原有的吐蕃、退浑等“十五家”部族经常发生战事,这些部族被迫撤出甘州,甘州遂成为回鹘人在河西的政治经济中心,甘州回鹘因此而得名,并在其后逐渐控制了河西地区的大部。十世纪初,以六谷部为首的吐蕃人又入据凉州,取代了原来控制凉州的嗢末等部,成为凉州新的统治者。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取代后周称帝,建立宋朝,是为宋太祖。以六谷部和折逋家族为首的凉州吐蕃诸部在宋初又臣服于宋。乾德四年(966年),吐蕃部首领折逋支护送欲往天竺取经的六十余名汉僧至甘州,上奏宋庭后,太祖赵匡胤“诏褒答之”①;五年(967年),凉州吐蕃首领闾逋哥、督廷、督南、割野、麻里等六人向宋朝进贡马匹,可见当时双方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②
“道和文本”可能是时间久远或是其他原因,有几处字词不全,从文中透露出的有关圣容寺的信息并不是很丰富,但仍然是一份极为重要的史料,以下对此文本做一简单的考释。第一,寺名的问题。文首“凉州御山感通寺圣容天卡来”中的“凉州御山感通寺”即今之永昌圣容寺。“天卡来”不明何意,或是讹误之故。孙修身先生认为圣容寺之名是在吐蕃统治凉州时期出现的。敦煌莫高窟第231窟为阴嘉政在吐蕃统治时期所营修,窟内壁画中番禾瑞像旁边的榜题为“盘和都督府御谷山番禾县北圣容瑞像”其中有“圣容”一词出现,圣容寺即从此来。实际上,,从目前已经发现的文物资料来看,“圣容”一词早在唐朝就已出现。甘肃省博物馆藏的唐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的造像,题记中就有“父母及法界,众生造圣容”等字样。①山西省博物馆藏原存于万荣县的唐朝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李元封等八人奉造的释迦立像,其台座上铭文刻有“敬造玉石圣容像一区”、“开元廿五年岁次丁丑五月甲戌朔十五日戊子建立”等题记①,其中也有圣容一词,说明“圣容”的出现时间是要早于吐蕃的。“道和文本”虽有“圣容”一词,寺名却仍然沿袭了隋唐时期感通寺之名,可见圣容寺之名最早应是出现在北宋乾德年之后了。西夏时期皇陵中供奉帝后神御的寺庙也称为圣容寺,是否和永昌圣容寺互有渊源,尚待进一步详考。②第二,时代和年号。乾德六年即开宝元年(968年),是年十一月癸酉,赵匡胤改元开宝,大赦天下,凉州吐蕃向宋称臣,故沿袭宋之年号。“大祖文皇帝”中“大祖”系“太祖”之误,指宋太祖赵匡胤。“于保定九年,凉州奉之,方知尊容神异”一句,指的是在凉州城东七里涧发现佛首之后又奉其至感通寺,佛首与像身“宛然符会”之事。“保定”为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年号,然此年号只有五年。566年,武帝改元天和,若仍依九年往下推之,则为569年,这就与道宣的记载出现了时间上的矛盾。道宣《续高僧传》中说:“至北周元年(557年),治凉州城东之七里涧,忽有光现,彻照幽显,观者异之,乃像首也。便奉至山岩安之,宛然符会。仪容雕缺四十余年,身首异所二百余里相好还备,太平斯在。保定元年(561年),置为瑞,像寺焉。”依道宣的说法,因瑞像之故,保定元年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瑞像寺。在修建瑞像寺之初,佛像应当是“灵相圆备”的,如果身首不合就专为其修建寺院,也不合常理,况且北周保定初期,天下太平,也与刘萨诃的预言相符合。那么“道和文本”中这个“保定九年”的记载就是有误的,其记录的内容较《续高僧传》晚出300余年,又不存于史,可见道和的记载也存有不少道听途说的成分,或者是源于当地流传下来的故事。不过“道和文本”也反映出,从凉州发现佛首义奉至圣容寺安装符会的故事,已经广为人们所熟知和认可了,否则不会将其专门记录下来。第三,捐资修寺者。“澡慕之流京野,翘汪公惟大慈,府降宜就表”“受罄舍珍财,敬营塔寺,依峰树??栋丹彩于重”两,句中,“汪公”是何许人,无从可考,但身份定然不低,家道亦非常殷实,而且能舍财修寺者必然是虔诚的信佛者,因为塔寺的营修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资财的,有了当权者的庇佑和支持,感通寺的香火才会愈加旺盛。第四,营修感通寺的情况。既有身份显贵之人带头舍财以“敬营塔寺”,修建的规模定然不小。文中“塔寺”一词,说明了乾德六年对圣容寺山后的舍利塔也进行了维修。今圣容寺山后的舍利塔始建于唐代,体量巨大,高约12米,其形制与小雁塔极为相似,然最初建塔的情况却于史无考,也未发现有营造碑记,“道和文本”的记录是第一次反映后世营修圣容寺舍利塔的情况。重新营修后的感通寺,“周通迎势,放祗园禅室,连扃形、模鹫岭”,佛寺的修建总体布局融合了周边的山形地势,修建了大殿、禅室、僧房等等。这次营修不仅修复了过去在兵燹、战乱中受损的塔寺,而且又新修了众多的佛教建筑,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一片规模宏大的佛教建筑群,几乎是“弥山亘谷,处处僧坊”。其规模之大,甚至可令人“左瞻崆峒,想轩辕之所游”。新修塔寺之壮丽,竟能左望崆峒山,虽不过是形容其盛况的一个借代而已,寺庙规模之盛可见一斑。最后,记录者僧道和。文末题款为“乾德六年六月廿二日,僧道和纪之耳”,可知此文是由一名叫道和的僧人所书。道和之名,于僧传、史书皆无可考,这份文书何以能流传至敦煌亦不得而知,然营修感通寺记由道和来笔受,则道和至少应是感通寺中的高僧,甚或就是感通寺的住持。总之,“道和文本”是一份记录北宋初营修感通寺的重要文献,对于考察圣容寺历代的营修和变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番禾瑞像既诞生于番禾县望御谷,番禾县和望御谷的关系就需要做一简单的了解,尤其是望御谷的情况以前多被研究者所忽视,现在看来,望御谷的地理位置和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是番禾瑞像诞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番禾一作“番和”,初为汉置县,名番和,魏晋因之,其故治在今永昌县西。望御谷之名最初不知从何而来,亦不见于史册,最初或叫做“御山”。番禾县自西汉置郡以来,一直沿用到晚唐五代宋时期,凡历700多年,期间因为朝代的更替和战争的缘故,有几次暂废和改称,尽管时间都较为短暂,但是番禾郡的故治并未随之而发生变化。从一些史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①,番禾古城的规模之大在河西地区也是比较少见的。有说番禾县故址在今焦家庄乡南约一公里处,有说在今之南、北古城一带,皆因没有充足的史料、考古遗迹加以佐证而未有定论,尚待详考,因这一问题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此处不再展开。但可以确定的是,不论番禾古城的故址在焦家庄乡南或是南北古城一带,其地理方位均在永昌县西,这就与道宣所记载的刘萨诃向东北方向之望御谷“遥礼”是完全吻合的。事实上,道宣本人并没有亲自到过河西走廊一带。而位于今永昌县城北部的望御谷,也不过就是一个偏僻的峡谷而已,番禾县城就处在望御谷的西南方向,并且中间还隔着武当山,二者相距十几里地,道宣和之前大多数的作者都没有亲自考察过,其记载却丝毫不差。类似于此种夹杂着道听途说式的有关望御谷的记载,说明望御谷在当时就已经颇负声名,甚至早在番禾瑞像尚未出世的时候就已经为人所熟知了。
番禾瑞像,也称作凉州瑞像,凉州番禾县瑞像或御容山瑞像、永昌圣容瑞像等等不一而足,也有因刘萨诃预言诞生之故而称其为刘萨诃瑞像者,大同小异,皆指今永昌城北圣容寺后依山而立的浮雕瑞像。该像的称名之所以产生了一点小的分歧,主要是对此像的神格、信仰还不能进行准确的区分或界定,而绝大多数的佛教造像是以神格来命名的。番禾瑞像出世的时候,番禾县只是凉州下辖的一个县,凉州则为更高一级的行政机构,属于上下级行政隶属的关系,所以时人在记载此事的时候前面务须要加上“凉州”二字,也就是今之学界大多称其为凉州瑞像的原因。相对来说,在尚未弄清此像系哪一尊佛像的时候,用出世时所在的地名来为其命名是更为合适的,如凉州瑞像、御容山瑞像、永昌圣容瑞像等。肥田路美先生称其为凉州番禾县瑞像,将僧传的记载和诞生地都表述出来,无疑更为准确。尚丽新先生简称为番禾瑞像,更加简练,易于表达,笔者在文中也多从此说。另因为此像的出世实是源于刘萨诃之故,也有以刘萨诃之名冠之者,但从后来出土的一些文书、造像及其他相关文物来看,番禾瑞像信仰和刘萨诃信仰分属于两种不同的信仰,发展的脉络和传播的地域也互有差别,二者本身表征的意涵也不尽相同。实际上,番禾瑞像应当是释迦牟尼像。现存于山西省博物馆的李元封等造的番禾瑞像的题记中就有“释迦圣容立像”之名。若以其神格来为之命名的话,可以称其为“释迦圣容瑞像”,或“释迦圣容立像”,或者叫做“释迦圣容佛”。总之,只要能指明此像即可。
二、永昌县当地出土的番禾瑞像
1.Ⅰ型番禾瑞像
Ⅰ型造像于上世纪80年代在金川西村出土现藏于永昌县博物馆(图四)。造像为砂岩质,残高,80厘米,宽53厘米。佛像赤足站立于仰覆莲台上,整个背屏雕成山崖状,背屏右上部已残,颈肩处横贯一道裂纹,头面部及五官残损不清,尚可辨出轮廓。佛像为高浮雕,着衣袒右肩;胸口双领袈裟下边阴刻有锯齿状纹饰;左手握住衣襟一角,左手下部悬出的衣襟层次分明,状若飘起;左边腰部以下至足部的裙襟阳刻有两层锯齿状纹饰;右手下垂,但肘部已不可辨识,应是作与愿印;两腿之间刻有U形纹饰,自上而下呈阶梯状排歹。佛像与背屏之间空白处仍残留有浅红色彩,可知原像应当是敷色填彩的。
此像没有任何题记及其它纪年信息,可能是未雕刻或已毁蚀,造成对佛像的时代认定产生了一些分歧。张宝玺先生认为应是北魏所造,文静、魏文斌二位先生认为其造于初唐。业师杜斗城先生在对此像经过实地考察后,指出其制作年代应当在北魏到西魏之间,最迟不会晚于西魏。笔者也认同业师杜斗城先生和张宝玺先生的观点。其残存的头部、身躯以及手臂都比较瘦长;肩部平削,头光和身光连为一体,背光呈上宽下窄的瘦莲瓣形;面部与北魏佛像那种方颐的面庞相类似,整体风格也略显清癯。另从这尊佛像的质地来看,与当地所产石质相同,应当是在本地出产并雕造完成。依此来看,此像应当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番禾瑞像的石雕像,这可能对于现存的一些其它造像的时代划分和相关文献的记载具有一定的意义。
2.Ⅱ型番禾瑞像
这尊造像原存于圣容寺大殿东十几米处的一个较大的石窟中,后运至永昌县博物馆保存(图五)。造像为砂岩质,造像通高114厘米,佛像高约94厘米,宽约40厘米。头部及膝部以下皆残缺,立姿,着衣袒右肩,左手握衣角,胸口双领袈裟下边亦阴刻锯齿状纹饰,右手下垂,肘部以下残损不能辨识;头光是分两层交错雕刻而成,呈莲瓣形;佛像两侧的背光中浮雕有化佛,腰部、肩部和头部两侧对称分布各三身,顶部一身,共七身跏趺坐小化佛。背光呈舟形,再向外则表现出嵯峨的山崖。该石窟现为当地僧俗所雕凿重修,原貌已不存,石窟的情况,典籍中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但孙修身先生曾做过比较详细的调查和记录。①原窟室高约2.7米,长宽约3到4米之间,敞口、略称方形;前有长约9米,宽约4.5米,高4米的前廊,与后边的窟室相连。
此像也未留下任何关于纪年的文字信息,孙修身和张宝玺二位先生对其做了简单记录。②张宝玺先生认为此像是北魏时期的造像,没有更进一步说明断代的缘由。③从残存造像所表现出的一些风格特征来看,Ⅱ型的时代要较之于Ⅰ型晚。与Ⅰ型相比,Ⅱ型佛像体型更趋丰满,胸口袈裟的锯齿状纹饰更为明显。头光出现了莲瓣造型,背屏则由瘦莲瓣形变为舟形,并在背屏上浮雕出七身小化佛。
3.Ⅲ型番禾瑞像
Ⅲ型造像被当地人称作“青龙佛”,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永昌县城西南的红山窑乡青龙山庙遗址中被发现,原供奉于青龙山庙之内而得名,后寺庙破毁,现藏于永昌县博物馆(图六)。造像为石灰岩质地,以高浮雕、圆雕手法凿刻而成,部分已残。通高170厘米,宽85厘米,跣足立于仰覆莲台上,体量巨大,与真人几近相等,正是所谓“等身佛”。佛首已断裂,后经修复安装合于一身。低圆发髻,着衣袒右肩,右手沿体下垂作与愿印,左手握衣角,下部悬出衣襟;胸口衣领处的锯齿纹及左侧裙边的两层锯齿形纹饰与前面出现的Ⅰ型、Ⅱ型雕刻如出一辙;两腿之间自上而下雕刻有整齐的浅U形纹,膝部以下的衣纹也呈密集的浅U形,衣纹更富韵律感;背屏呈舟形,肩部以上的背屏两侧雕有五身跏趺坐小化佛,顶部已残,顶部可能有一身小佛,两侧对称雕有六身小佛;背屏周边嵯峨的山崖则用浮雕手法表现出来。
佛籍和县志中均没有关于青龙山庙及此像的相关记载,造像本身未雕刻题记,但整尊佛像体量巨大,丰满圆润,线条流畅,衣褶纹饰栩栩如生,表现出娴熟高超的雕刻技法,应是盛唐的作品无疑。
4.番禾瑞像佛首
番禾瑞像佛首于上世纪70年代由原文化馆黄馆长在金川西村望御谷一农户家牛圈墙的垒石中起获,现存于永昌县博物馆(图七)。佛首为青砂岩质,高67厘米,发髻已残,眉间白毫残缺,鼻、耳朵、唇等处也被磨损。面形圆润,头顶结满低平小螺髻。关于此像的时代和是否为番禾瑞像“原像”的问题,笔者认为还有重新讨论的必要。孙修身、张宝玺二先生对其分别做了记录。孙氏未说明时代,只说其为早期造像,并有着“受印度造像影响”的痕迹;张氏则认为此像就是佛籍中之凉州瑞像,现存于永昌圣容寺的佛身成于正光元年(520年),而这颗佛首则雕造于北周闵帝元年(557年)。佛首的断代还需要进一步判别和认识,因为后世佛首跌落复又安装之次数较多,最初的佛首存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5.对永昌出土造像的一些认识
基于对相关典籍文献的了解以及对以上儿尊佛像的初步认识,可以通过其所透露出的时代信息而对永昌出土佛像的时代进行排序。特别是Ⅰ型佛像,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尊佛像,对于它的出现和进一步认识,可能存在一定的意义:不仅可以改变以往学界对那尊佛首的认定,而且可能会使以往对身首合璧的番禾瑞像的诞生时代会有新的结论。先来看佛首:孙氏认为佛首就是《续高僧传》中所记载的“凉州城东七里涧”发现的佛首,实际情况就是在凉州雕刻好佛首之后,又搬运至番禾县望御谷后安装于无头的佛身上;张氏则直接说其雕刻完成于北周元年(557年),是番禾瑞像原像首,根据则不外于道宣的著作。其次,从相关的典籍来看,最先出现的应当是身首合璧的那尊体量巨大的“丈八石像”(图八),也就是今天仍然能看到的那尊大的浮雕像。番禾瑞像也应当是在“具足”以后才会被各地“依图供养”其他的小的雕像、造像等等都是依样画葫芦照着原,来的丈八大佛像再行仿制的,这也符合常理。北魏于534年之后分裂为东魏、西魏,西魏于557年又为北周所替。但按照文字记载,佛首最早完成与像身的合璧也在北周元年,那么这尊北魏的Ⅰ型佛像怎么会早于北周的丈八石佛出现?如此一来,就会出现以下几种可能性:第一,杜斗城先生很早就指出北魏正光年间望御谷已经出现了造像活动。①在这一系列造像活动中,就可能已经有那种特定造型的佛像被雕造出来,那么这颗佛首就不应该是“原像”了,而是它依照已经成型的番禾瑞像而再行仿制的。如此一来,文献的记载就出现了讹误。第二,正光年间已有佛首刻出,但不知何故丢失,或者说佛首因为某种原因没有雕刻好,无法安装。北周出现的佛首指的是在凉州东七里涧或其他地方被雕刻出的另外的佛首第三,番禾瑞像是先有像身,后有佛首,其间有“仪容雕缺四十余年,身首异所二百余里”的分离期。番禾瑞像的特别之处在于手印、躯干、衣纹等部位有其自身特点,佛首的形象一般来讲与其他佛像相差不是很大,在近四十余年的空白期是否已经有人先雕出了全像则不得而知,尽管这种可能性比较小。但以上几种可能的情况和典籍中的记载就出现了矛盾,这就说明了刘萨诃及番禾瑞像等一系列神异的事件属于附会的可能性极大,信徒为宣扬佛教,扩大佛教的影响力而对原有的故事“添枝加叶”了。
从以上四尊佛像表现出的特点可以看出:番禾瑞像在当地是随着朝代的更替发展而不断变化的。造像的细节部分出现了新的装饰,比如增加了莲瓣、化佛以及背屏的变化等等,雕刻更加精美,体量也由小变大。与此同时,望御谷的造像活动自北魏开始就一直没有中断过,且不局限于望御谷一地,并在隋唐之际更加兴盛。番禾县当地的这种状况,清楚地表明了由刘萨诃的神异事迹而衍化出的传说故事具有很强大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番禾瑞像也为当地僧俗所崇信,使得瑞像信仰在番禾县世代相传。
三、其他代表性造像及文物资料
番禾瑞像“出世”以后,不仅在番禾县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波及到河西走廊及附近地区,现存数量众多的石窟寺遗迹、壁画、雕塑等相关文物就是最好的例证。以下选取三个比较典型的出现在河西走廊附近的造像或文物来举例说明。
1.张掖马蹄寺千佛洞第6窟番禾瑞像
张掖马蹄寺石窟开凿于五世纪初,其后历代皆有营修,今仍存70余窟,千佛洞第6窟建于初唐(图九)。该窟坐西向东,高约6米,宽5.5米,进深4.6米,窟内正壁佛像高4米。现存于窟内的造像在1992年之前被当地僧俗重修过,与原像的细节特征有出入,特别是原来左手握衣角的造型被改造成了现在的左手托莲台,以致改变了主尊造像的神格,幸得1987年出版的《河西石窟》一书录其原貌。①张善庆先生很早就指出了这次重修活动所造成的影响,并对其进行了详实的考证。②沙武田先生指出此像“主尊处山形中,时代为唐前期”,③这就说明番禾瑞像背后山崖的表现不是只有将山崖雕饰在佛像背屏上的一种方式,特别是这种较大规模的开窟造像,在地况、材料等各种条件具备的时候,完全可以照搬番禾瑞像最初诞生时的那种方式。张掖东邻永昌,番禾瑞像的造型出现以后,随着瑞像信仰的影响不断扩大,向西传播的第一站就是张掖,更兼马蹄寺本就是河西之佛教圣地,番禾瑞像在这里的出现自然是顺理成章。
2.莫国高窟第72窟南壁番禾瑞像故事画及其他
酒泉、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现存有大量的刘萨诃和番禾瑞像相关的遗迹文物,大多是唐、五代及以后出现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莫高窟第72窟、237窟等。莫高窟72窟南壁的番禾瑞像故事画长约6.5米,高4.3米,下部大约三分之二的壁画因流沙磨蚀而不能清晰辨认,西侧下部和东侧也有小部分脱落,仅存上部约三分之一。霍熙亮先生复原了72窟的线描图,并推测其绘于晚唐初期,后经过五代、宋重修。统中国艺术中对宗教偶像最为深刻的思考的画”(图十),①同时也表现了番禾瑞像在身首复合时的情景(图一一),为今天人们了解古代修缮安装佛像的程序提供了确切的资料。其它如敦煌莫高窟第十六、二十六、四十九、五十五、八十四、一二二、三〇〇、三三二等窟,敦煌西千佛洞第十九窟,安西榆林窟第三十三窟,酒泉文殊山万佛洞等石窟均存有番禾瑞像的壁画或塑像,此处不一一详述。
敦煌、酒泉地区是经过河西走廊通向内地的门户,地接西域,又与凉州番禾县相距不远,回鹘、归义军及一些其它短暂出现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大都尊崇佛教,客观上也为瑞像信仰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数量如此之多的番禾瑞像题材出现于酒泉、敦煌等地,特别是出现于晚唐五代至北宋之际营建的石窟中,就是最好的例证,也足以说明瑞像信仰在这一地区兴盛的程度。
日本滨田德海旧藏的编号为ChinMs:C121的敦煌文书题记中,记录了宋初营修凉州感通寺的一些情况。敦煌研究院马德先生于日本抄录了此文书题记,其内容如下:
文书名:宋乾德六年修凉州感通寺记
正文:凉州御山感通寺圣容天卡来
大祖文皇帝膺千年之圣 百代之英运
属龙非时当凤举廓三籁于道销庇四民于
德寰维释氏之 纲缀儒〔〕之绝纳泽流遐
外九
被无穷 皇帝时乘驭寓幄历君临德
泉道光日月不住无为而孝慈兆庶不 有
为而丘拘万机洞九宅之非絙树三宝之圣福
于保定九年凉州奉之方知尊容神异靡
又空钟震响寔韵八音灯轮自转 符三点亲
崄者发奇悟于真源传听者荡烦嚣于 派
澡慕之流京野翘汪公惟大慈府降宜就表
受罄舍珍财敬营塔寺依峰树 栋丹彩于重
霄因材构宇晓朱青于凉〔〕尽人工之妙房
周通迎势放祗园禅室连扃形模鹫岭
左瞻崆峒想轩辕之所游
乾德六年六月廿二日僧道和纪之耳
此文本后的题款为“僧道和纪之耳”,故本文皆以“道和文本”称之。这里先简要交代一下“道和文本”所处的唐末五代时期凉州及永昌政治环境变迁的背景①:
唐末五代时期正是河西地区政治势力迭起,民族变迁频繁,战乱相寻的时代凉州先后为吐蕃、归义军、甘州回鹘、嗢末人和凉州吐蕃部等政治势力统治或控制。763年,吐蕃大军开始自东向西攻占唐朝所属的河西地区。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吐蕃重兵围攻凉州,唐河西节度使杨志烈未能抵挡吐蕃的猛烈攻势而西奔甘州,河西重镇凉州旋即陷落,766年,吐蕃相继攻下甘州、肃州,河西大部为吐蕃所据,永昌时为凉州所辖,766年之前也已陷于吐蕃。到大中二年(848年),沙州张议潮率部反抗吐蕃,驱逐吐蕃势力,光复了瓜、沙二州。大中三年(849年),张氏自西向东相继收复肃州、甘州。大中五年(851年),唐朝政府在沙州设立归义军,授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咸通二年(861年),张议潮攻克凉州。重镇凉州的攻克,意味着河西走廊基本上已被归义军政权所控制。在张议潮自西向东进兵的时候,嗢末和一些吐蕃部族也被驱赶到凉州一带,并在这里盘踞下来。中和四年(884年),西迁至河西的回鹘人势力日盛,与甘州原有的吐蕃、退浑等“十五家”部族经常发生战事,这些部族被迫撤出甘州,甘州遂成为回鹘人在河西的政治经济中心,甘州回鹘因此而得名,并在其后逐渐控制了河西地区的大部。十世纪初,以六谷部为首的吐蕃人又入据凉州,取代了原来控制凉州的嗢末等部,成为凉州新的统治者。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取代后周称帝,建立宋朝,是为宋太祖。以六谷部和折逋家族为首的凉州吐蕃诸部在宋初又臣服于宋。乾德四年(966年),吐蕃部首领折逋支护送欲往天竺取经的六十余名汉僧至甘州,上奏宋庭后,太祖赵匡胤“诏褒答之”①;五年(967年),凉州吐蕃首领闾逋哥、督廷、督南、割野、麻里等六人向宋朝进贡马匹,可见当时双方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②
“道和文本”可能是时间久远或是其他原因,有几处字词不全,从文中透露出的有关圣容寺的信息并不是很丰富,但仍然是一份极为重要的史料,以下对此文本做一简单的考释。第一,寺名的问题。文首“凉州御山感通寺圣容天卡来”中的“凉州御山感通寺”即今之永昌圣容寺。“天卡来”不明何意,或是讹误之故。孙修身先生认为圣容寺之名是在吐蕃统治凉州时期出现的。敦煌莫高窟第231窟为阴嘉政在吐蕃统治时期所营修,窟内壁画中番禾瑞像旁边的榜题为“盘和都督府御谷山番禾县北圣容瑞像”其中有“圣容”一词出现,圣容寺即从此来。实际上,,从目前已经发现的文物资料来看,“圣容”一词早在唐朝就已出现。甘肃省博物馆藏的唐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的造像,题记中就有“父母及法界,众生造圣容”等字样。①山西省博物馆藏原存于万荣县的唐朝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李元封等八人奉造的释迦立像,其台座上铭文刻有“敬造玉石圣容像一区”、“开元廿五年岁次丁丑五月甲戌朔十五日戊子建立”等题记①,其中也有圣容一词,说明“圣容”的出现时间是要早于吐蕃的。“道和文本”虽有“圣容”一词,寺名却仍然沿袭了隋唐时期感通寺之名,可见圣容寺之名最早应是出现在北宋乾德年之后了。西夏时期皇陵中供奉帝后神御的寺庙也称为圣容寺,是否和永昌圣容寺互有渊源,尚待进一步详考。②第二,时代和年号。乾德六年即开宝元年(968年),是年十一月癸酉,赵匡胤改元开宝,大赦天下,凉州吐蕃向宋称臣,故沿袭宋之年号。“大祖文皇帝”中“大祖”系“太祖”之误,指宋太祖赵匡胤。“于保定九年,凉州奉之,方知尊容神异”一句,指的是在凉州城东七里涧发现佛首之后又奉其至感通寺,佛首与像身“宛然符会”之事。“保定”为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年号,然此年号只有五年。566年,武帝改元天和,若仍依九年往下推之,则为569年,这就与道宣的记载出现了时间上的矛盾。道宣《续高僧传》中说:“至北周元年(557年),治凉州城东之七里涧,忽有光现,彻照幽显,观者异之,乃像首也。便奉至山岩安之,宛然符会。仪容雕缺四十余年,身首异所二百余里相好还备,太平斯在。保定元年(561年),置为瑞,像寺焉。”依道宣的说法,因瑞像之故,保定元年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瑞像寺。在修建瑞像寺之初,佛像应当是“灵相圆备”的,如果身首不合就专为其修建寺院,也不合常理,况且北周保定初期,天下太平,也与刘萨诃的预言相符合。那么“道和文本”中这个“保定九年”的记载就是有误的,其记录的内容较《续高僧传》晚出300余年,又不存于史,可见道和的记载也存有不少道听途说的成分,或者是源于当地流传下来的故事。不过“道和文本”也反映出,从凉州发现佛首义奉至圣容寺安装符会的故事,已经广为人们所熟知和认可了,否则不会将其专门记录下来。第三,捐资修寺者。“澡慕之流京野,翘汪公惟大慈,府降宜就表”“受罄舍珍财,敬营塔寺,依峰树??栋丹彩于重”两,句中,“汪公”是何许人,无从可考,但身份定然不低,家道亦非常殷实,而且能舍财修寺者必然是虔诚的信佛者,因为塔寺的营修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资财的,有了当权者的庇佑和支持,感通寺的香火才会愈加旺盛。第四,营修感通寺的情况。既有身份显贵之人带头舍财以“敬营塔寺”,修建的规模定然不小。文中“塔寺”一词,说明了乾德六年对圣容寺山后的舍利塔也进行了维修。今圣容寺山后的舍利塔始建于唐代,体量巨大,高约12米,其形制与小雁塔极为相似,然最初建塔的情况却于史无考,也未发现有营造碑记,“道和文本”的记录是第一次反映后世营修圣容寺舍利塔的情况。重新营修后的感通寺,“周通迎势,放祗园禅室,连扃形、模鹫岭”,佛寺的修建总体布局融合了周边的山形地势,修建了大殿、禅室、僧房等等。这次营修不仅修复了过去在兵燹、战乱中受损的塔寺,而且又新修了众多的佛教建筑,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一片规模宏大的佛教建筑群,几乎是“弥山亘谷,处处僧坊”。其规模之大,甚至可令人“左瞻崆峒,想轩辕之所游”。新修塔寺之壮丽,竟能左望崆峒山,虽不过是形容其盛况的一个借代而已,寺庙规模之盛可见一斑。最后,记录者僧道和。文末题款为“乾德六年六月廿二日,僧道和纪之耳”,可知此文是由一名叫道和的僧人所书。道和之名,于僧传、史书皆无可考,这份文书何以能流传至敦煌亦不得而知,然营修感通寺记由道和来笔受,则道和至少应是感通寺中的高僧,甚或就是感通寺的住持。总之,“道和文本”是一份记录北宋初营修感通寺的重要文献,对于考察圣容寺历代的营修和变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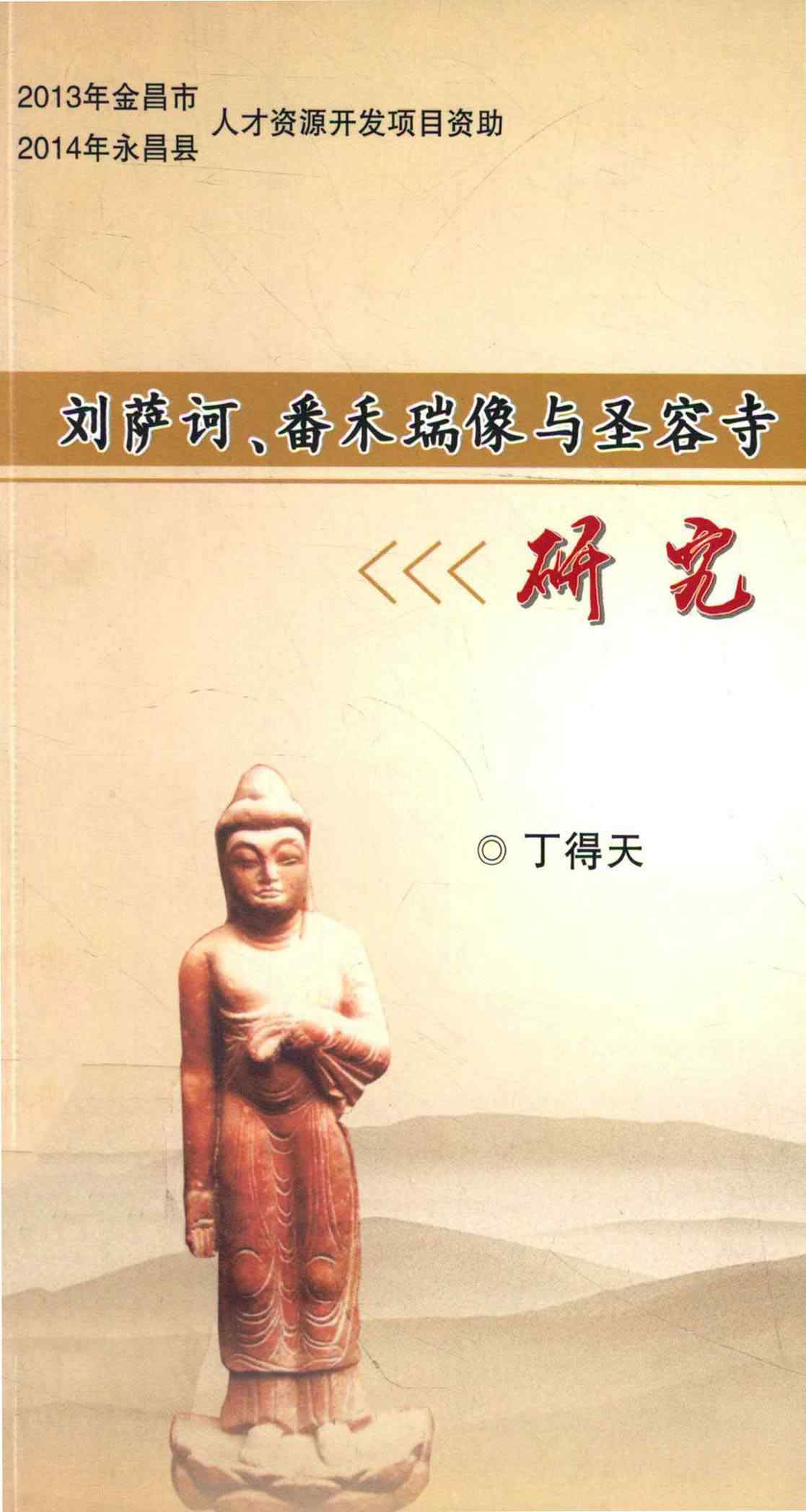
《刘萨诃、番禾瑞像与圣容寺研究》
本书分为三章分别介绍了刘萨诃的生平以及番禾瑞像和圣容寺的情况,对望御谷及周边的佛教遗迹做了全面的调查,著录了金昌市境内散见的佛教石窟寺遗迹以及清代《永昌县志》所记载的古寺。
阅读
相关地名
永昌县
相关地名